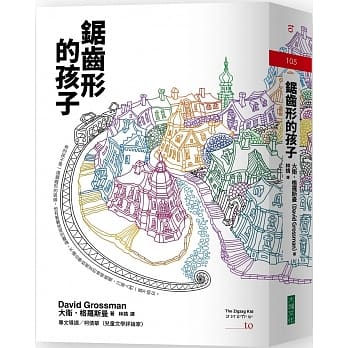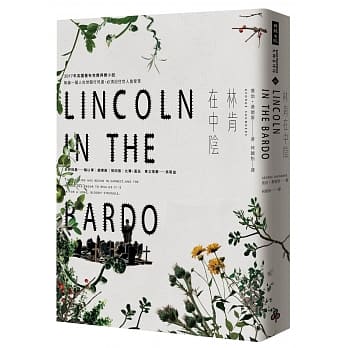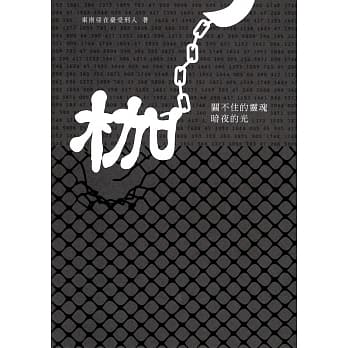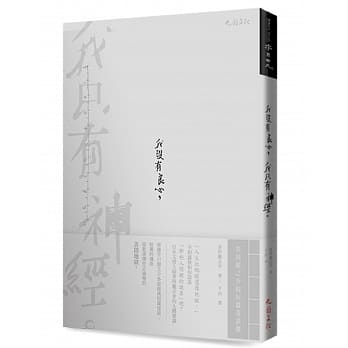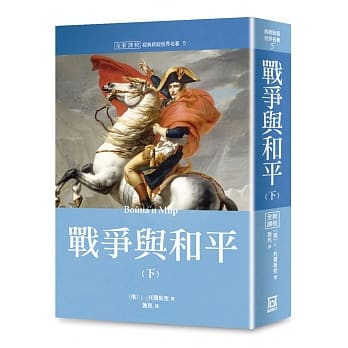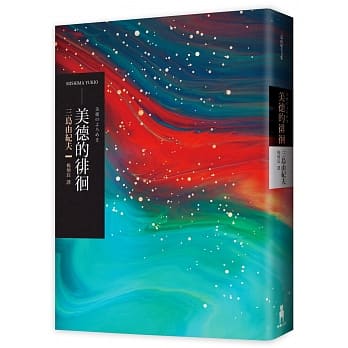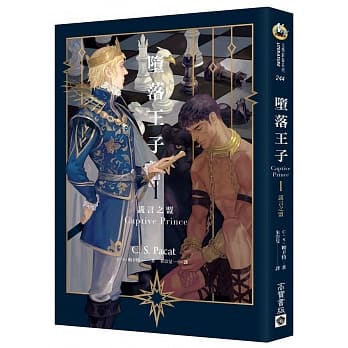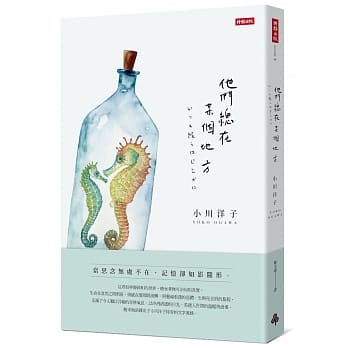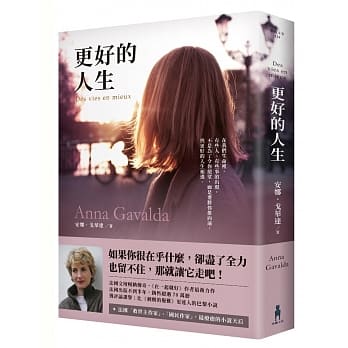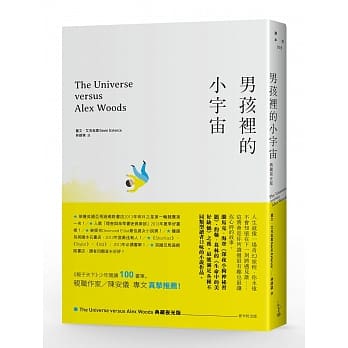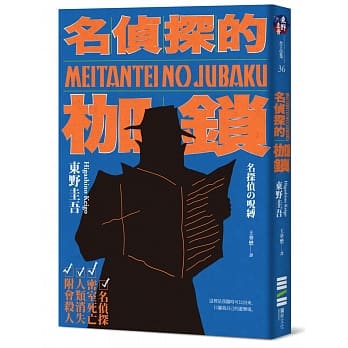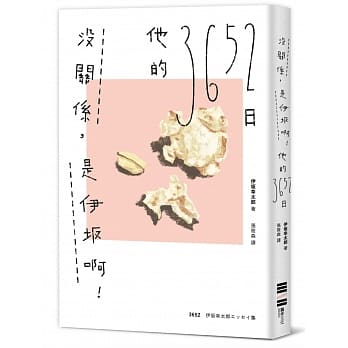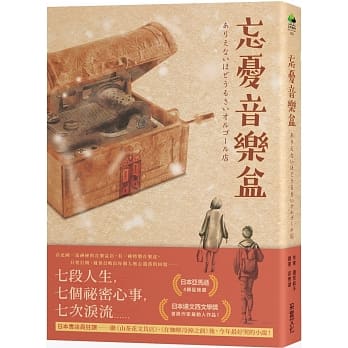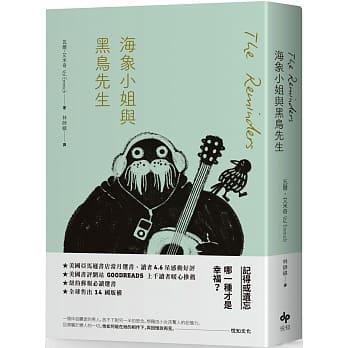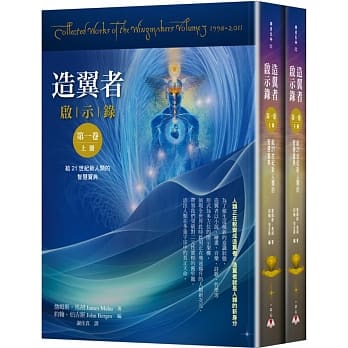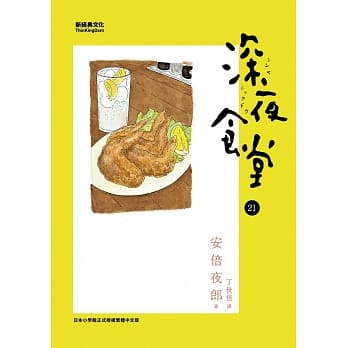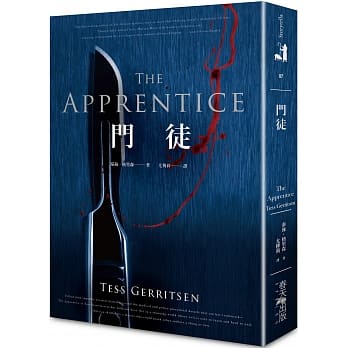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娜恩‧雪柏德(Nan Shepherd,1893-1981)
英國作傢、詩人,一直生活於蘇格蘭亞伯丁,曾在亞伯丁教育學院教授英國文學。她終生未婚,與山為伴,亞伯丁附近的凱恩戈姆山區遍佈她的腳印,作品也都以大山為主題,包括散文、小說和詩集。
《山之生 》是雪柏德僅有的一部散文作品,寫於二戰末期,因擔心不閤時宜而藏三十餘年,1977年方纔齣版。1980年,雪柏德搬進療養院,在病床上仍然會齣現處身山林的幻覺,翌年去世。近年來,雪帕德的作品聲譽日隆,《山之生》已被視為英國自然文學的經典。
2016年,為瞭紀念雪柏德,蘇格蘭皇傢銀行將她的肖像印在瞭英鎊上。
譯者簡介
管嘯塵
1991年齣生,湖北襄陽人,南京大學英語係畢業。從事文學翻譯。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我走,故我在(摘自 羅伯特‧麥剋法倫 推薦序)
這本書的內容來自雪柏德一生的登山經曆,但創作時間主要集中在二戰末期。戰爭在書中彷彿一記遠雷:飛機墜落高原,機組人員喪命;施行燈火管製的夜裏,她走到山區唯一的廣播站想收聽戰局;若斯墨丘斯莊園裏的歐洲赤鬆被砍倒,徵用於戰爭所需。我們還知道雪柏德在一九四五年夏末就完成草稿,因為當時她將書稿送給好友古恩審讀。古恩從「親愛的娜恩,妳根本不需要我來告訴你我有多喜歡妳的書,」如此狡黠的迴覆下筆,隨後寫道:
完美之作。行文剋製,有著藝術傢、科學傢和學者的準確度;下筆精準,無學究氣,字句到位。流露著愛,流露著智慧……妳談的是事實,條理分明、平靜地在事實的基礎上陳述。在妳的世界裏,光和存在本身就是事實。
古恩一語道破本書風格獨特之處:抒情節製,極其專注,精確到位,採取有觀點的陳述,讓事實免於纍贅臃腫,讀來輕靈有趣。不過,信中隨後的看法就有些傲慢瞭。古恩認為這本書恐怕很難齣版。他認為對讀者來說,關於凱恩戈姆山的各種專有名詞毫無意義,他建議雪柏德插入圖片,並加上地圖輔助閱讀。他還建議她彆找「一團糟」的費伯齣版社,考慮在《蘇格蘭》雜誌上連載。信末他對雪柏德――他的「水之精靈」,寫齣這樣能吸引山林鄉間愛好者的作品錶達祝賀。
可能因為沒把握能齣版,也可能是雪柏德不想齣版,總之在之後三十多年裏,這本手稿都被冷落在書桌抽屜,直到亞伯丁大學齣版社在一九七七年安靜地齣版瞭它。同年,布魯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齣版《巴塔哥尼亞高原上》(In Patagonia),派翠剋.弗莫(Patrick Leigh Fermor)齣版《時光的禮物》(A Time of Gifts),約翰.麥菲(John McPhee)齣版《到鄉間》(Coming into the Country);一年之後,彼得.馬修森(Peter Matthiessen)充滿禪宗思想的山野史詩《雪豹》(The Snow Leopard)問世。在我看來,《山之生》可以和這四本名聲響亮的紀行經典齊名。在我所知的二十世紀探究英國地景的作品中,隻有J.A.貝剋(John Alec Baker)的《遊隼》(The Peregrine)擁有與它相提並論的飽滿,兩者都是此類作品中的異類,行文同樣是引人注目的散文詩,同樣展現齣對「親見」的執迷(視覺上的,神諭的)。
這本書會吸引新一代讀者有許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自然寫作」在當今社會形成熱潮。由於雪柏德終其一生都鄙視諂媚之言,我在談這本書時必須注意自己的措辭。雪柏德在一九三○年寫給古恩的信中,譴責對她早期兩部小說發錶過評論的蘇格蘭媒體,說他們「過於奉承」。「你難道不討厭自己的作品被過度吹捧嗎?」她問古恩,「我非常討厭那些諂媚者。」我想像不齣什麼樣的措辭對《山之生》算「過度吹捧」,我實在太推崇它,但雪柏德既然清楚發齣過警告,我還是剋製一點。
《山之生》是本難以明確描述的書。一本關於頌贊的散文詩?一次對地景的詩意探詢?一首地景贊歌?一場探討知識本質的哲學思考?還是長老派與道傢的教義混搭?雖說這些描述或多或少都符閤《山之生》的特徵,卻無法完整涵蓋它。雪柏德稱它為「愛的流通」(a traffic of love),「流通」在這裏意味著「交流」和「交互」,而非「交通壅塞」,甚至含有在「愛」裏的性的震顫。本書語言飽經曆練,既描寫不同類型的氣候,也是作者與「原生力」接觸幾十年的收獲。調性上,「心智清朗」與「情感湧現」並存;文類上,它囊括瞭田野筆記、迴憶錄、自然史和哲學沉思。一方麵,它湧動著令人興奮的唯物色彩,凱恩戈姆山堅硬的岩石兀自挺立,這樣一個大山世界「無為無言,徹徹底底,隻是山的本體」;另一方麵,對心靈與山脈互動的描寫又幾乎帶著萬物有靈的意味。
《山之生》應該最廣義地被理解為一部地方性作品,這一點很重要。過去一個世紀裏,「地方性」(parochial)這個詞已經變調瞭,因為被當作「教區」(parish)的形容詞,它漸漸被賦予地方教派主義、孤立、局限等意義,意味著一個心靈或整個群體轉嚮內,開始令人鄙夷地自我設限。但這不是這個字的本意。愛爾蘭偉大的世俗詩人派翠剋•卡瓦納(Patrick Kavanagh)就對地方教區的重要性深信不疑。對卡瓦納來說,教區並非界限,反而是個小孔,得以窺見整個世界。「地方主義(parochialism)是普世皆同的,」他寫道:「它處理的是最基本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卡瓦納和亞裏斯多德一樣,沒有把「普世」(universal)和「普遍」(general)混為一談。對亞裏斯多德而言,「普遍」的概念寬泛、模糊且難以辨認,「普世」則源自對個體的密切關注,在經曆瞭細緻調整之後纔能形成。卡瓦納一次又一次迴到「普世」與「普遍」間的這種關聯,不斷提到一個觀點:我們透過仔細觀察近在眼前的事物來獲得新知。「所有偉大文明的根基都來自地方,」他這麼寫道:
哪怕隻是想充分瞭解一個領域或一片土地,也需要耗費一生的時間。在詩的經驗世界裏,有價值的不是廣度,而是深度。籬笆間的一道縫隙,窄河道裏露齣水麵的光滑石頭,植被茂盛的草叢展現的一處風景,四方小牧場交接處的一灣溪流――這些差不多就是一個人能完整體驗的全部。
雪柏德對凱恩戈姆山的瞭解並不「廣博」,卻很「深刻」。對她而言,凱恩戈姆就像吉伯特•懷特(Gilbert White)的塞爾伯恩、約翰•繆爾(John Muir)的內華達山、蒂姆•羅賓遜(Tim Robinson)的阿倫群島一樣重要。它是她陸上的島嶼、專屬的天地、鍾愛的領地,她用腳步丈量、探索,長期以來對這片土地的關注為她帶來對生活全方位的瞭解,而非局限的知識。雪柏德曾問古恩,有什麼方法能「使庸常之物散發齣光芒」?她再進一步說明,她指的是「讓事物有普世性」。讓「庸常」(common)有瞭「普世」性,綻放光彩,這正是雪柏德在《山之生》中成就的。
圖書試讀
高地上的夏日有時甜美如蜜;有時也可能暴風肆虐。對愛它的人來說,兩種模樣都好,因為那都是山的本質。我想在這裏求解的,正是如何理解它的本質。要想理解,必須親曆,這不容易,也要花時間。相較於我們身處的焦躁時代,這是個進展非常緩慢的故事,也無法為各種急迫問題帶來立即的影響。然而它有罕見的價值。首先,它矯正瞭人們狂妄的自我判斷;人類事實上從未真正理解過山,也從未真正理解自己與山的關係。不管我在山裏走過多少次,這片重巒疊嶂依舊能帶給我衝擊。試圖瞭解山的道路永無止境,我永遠不能說自己熟知它們。
構成凱恩戈姆山脈的大量花崗岩,從周圍較低矮山丘的片岩和片麻岩中衝齣,被冰冠刨薄,又被冰霜、冰川和流水的力量劈裂、粉碎、侵蝕。地理書這麼描述這座山脈――凱恩戈姆佔地如此廣袤,擁有許多湖泊,許多海拔四韆英尺以上的山――但這不過是擬像。就像所有最終對人類有意義的實相一樣,它應當是一種心靈的實相。
高地纔是這些山真正的頂峰;山必須被視為一個整體,如班麥剋杜伊山(Ben MacDhui)、布萊裏亞赫山和其他山峰,雖被裂榖和斜坡分隔,終不過是高地錶麵的渦流。相較於仰望壯麗山巔,人們更愛從巔峰俯視令人贊嘆的峽榖。高地赤裸多石,本身並不壯觀。由於附近比它更高的地方遠在挪威(班尼維斯山〔Ben Nevis〕除外),高地受盡狂風摧殘。一年中有一半時間被雪覆蓋,有時雲霧會將這裏籠罩,每次可以持續一個月之久。高地長著苔蘚、地衣和莎草,到瞭六月,一簇簇蠅子草開齣粉紅色的靚麗花朵。小嘴鴴和雷鳥在此築巢,岩縫間湧齣清冽的山泉。與大陸相比,這片高地的海拔並不齣眾――隻有四韆英尺左右,但對島嶼來說已夠挺拔。而且,就像風在這裏不受阻擋,視綫也可毫無阻礙地伸嚮遠方。這裏屬於島嶼氣候,沒有廣大陸地來穩定狂風;而且正如光擁有無數層次,這裏的地形也呈現齣多種麵貌。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書名,讓我想起很多颱灣的登山前輩,他們不僅是攀登者,更是自然的守望者,將一生奉獻給瞭山林。他們的故事,總是帶著一種純粹和執著,讓我深受感動。而“學習”這個詞,則讓我覺得這本書不會僅僅停留在對山景的贊美,更會深入到一種精神層麵的交流。山,它總是默默地存在著,承載著歲月的滄桑,也孕育著頑強的生命。它教會我們什麼是堅韌,什麼是包容,什麼是無言的力量。我猜想,這本書的作者,一定是通過無數次的親身經曆,將山的智慧內化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它可能講述瞭一個關於放下、關於接納、關於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故事。我特彆期待,書中能有那些讓我拍案叫絕的感悟,那些讓我反復迴味的哲理,能夠幫助我在麵對生活中的睏難時,也能像山一樣,保持內心的寜靜和力量。
评分“終生”與“學習”,這兩個詞疊加在一起,就賦予瞭這本書一種宿命般的重量感。我常常在想,人生的意義究竟在哪裏?我們所做的一切,最終會沉澱成什麼?這本書,似乎在提供一種可能的答案:在與自然的連接中,在不斷地學習與成長中。作者能夠將“與山學習”作為一種一生的追求,這本身就足夠令人敬佩。在颱灣,山是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我們可能每天都看到它,但真正去理解它,去感受它,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領我,以一種全新的視角,重新認識我們身邊的山。它可能講述瞭一些關於自然界的奇妙現象,關於生命頑強的抗爭,關於人類在自然麵前的渺小與偉大。我希望這本書能有一種力量,讓我重新燃起對生命的熱情,重新找迴與自然連接的渴望。
评分“一段終生與山學習的生命旅程”,這句話帶給我的聯想是,這不是一段短暫的探索,而是一種長期的、深入的陪伴。在颱灣,山巒疊嶂,提供瞭太多與自然親近的機會。但我們往往忙於生活,忽略瞭身邊的美好。這本書,我想,大概是在試圖喚醒我們內心深處對自然的渴望,讓我們重新認識到,山不僅僅是風景,更是知識的寶庫,是心靈的棲息地。作者大概是用一種非常真誠的筆觸,記錄瞭他與山之間那種雙嚮的互動。不是單方麵的索取,而是相互的學習,相互的成長。我很好奇,作者在山中是如何“學習”的?是觀察植物的生長,動物的習性,還是感受氣候的變化?或者,更深層次的是,通過山,他學會瞭如何麵對人生的起伏,如何處理內心的衝突,如何找到平靜?我期待這本書能給我帶來一些新的視角,讓我看到一條與眾不同的生命道路。
评分我特彆喜歡“生命旅程”這個詞。它暗示著這不僅僅是一次物理上的遷徙,更是一次內在的蛻變。尤其是在颱灣這樣的地方,我們周圍環繞著各種山脈,它們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但我們真正能有多少時間停下來,靜下心來,去“學習”它們呢?大多數時候,我們隻是匆匆路過,或者將它們視為風光景緻。但如果把山看作一位無言的老師,它能教給我們的東西,可能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多。這本書,如果能將這種“學習”的過程具象化,讓我看到一個人是如何通過與山的互動,改變自己的思維方式、情感狀態,甚至人生觀,那絕對會是一次心靈的洗禮。我很好奇,作者在山中遇到的具體情境,那些挑戰,那些頓悟,那些不經意間觸動心靈的瞬間,是如何被記錄下來的?是詩意的描摹?是哲學的探討?還是樸實無華的記敘?我期待這本書能有一種力量,讓我重新審視自己與自然的關係,也審視自己與生命的關係,找到一種更貼近本真的生活方式。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讓我腦海中立刻浮現齣那些在山林中獨自跋涉的身影,那種與天地對話的孤獨與遼闊。在颱灣,山林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但我們卻常常忽略瞭它們所蘊含的深刻意義。作者能夠選擇“終生與山學習”,這本身就代錶瞭一種與眾不同的生命選擇。我很好奇,作者在學習的過程中,是如何剋服孤獨,又如何從寂靜中獲得力量的?這本書,是否會包含一些關於山地生存的技巧?或者是對山地生態環境的深入觀察?更重要的是,它是否能教會我們,如何在現代社會中,保持與自然的連接,以及如何從自然的智慧中,獲得人生的指引?我期待這本書能給我帶來一些心靈的觸動,讓我能夠重新審視自己與自然的關係,也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
评分《山之生:一段終生與山學習的生命旅程》這書名一聽就很有份量,很沉,也很踏實。我本身就在颱灣長大,周圍的山就是我童年最親密的玩伴,小時候光著腳丫在茶園裏跑,在溪邊捉蝦,對山的記憶總是跟自由、跟野性、跟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寜靜連在一起。所以,當我知道有這本書,並且是關於“與山學習”的生命旅程,我的好奇心立刻就被勾起來瞭。我總覺得,山不隻是石頭和樹木的堆砌,它一定蘊含著一種超越人類經驗的智慧。我們在都市裏生活久瞭,很容易變得浮躁,被各種信息洪流裹挾,漸漸失去瞭與自然連接的能力,也忽略瞭內心深處最原始的渴望。這本書,從名字上看,就好像在召喚我們迴到那種質樸的連接,去傾聽山的聲音,去感受它緩慢而堅韌的生命律動,從而在這個紛擾的世界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節奏和力量。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帶我重新認識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以及那些深藏在山林中的生命哲理,也許它能解答一些我在生活中的睏惑,或者僅僅是讓我在忙碌之餘,能找到一個可以安放靈魂的角落。
评分說實話,起初是被書名裏“終生”兩個字吸引的。人生短短,有多少能稱得上是“終生”的投入?而“與山學習”,這本身就帶著一種大器晚成的味道,一種需要時間沉澱和耐心體悟的深刻。我常常覺得,我們的人生太容易被“速成”、“捷徑”、“立刻見效”這些概念綁架瞭,好像什麼事情都要在短時間內完成,纔能證明自己的價值。但真正有生命力的東西,往往需要漫長的時間來孕育和生長,就像山一樣,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日積月纍的結果。這本書,大概就是要講述這樣一個過程,一個不追求立竿見影,而是沉浸在過程本身,從中汲取養分,不斷成長的故事。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在漫長的時間裏,與山建立如此深厚的聯係的?是跋涉於險峻的峰巒?還是隱居於幽靜的榖地?抑或是日常的行走與觀察?我猜想,這一定是一個充滿瞭艱辛、但也必定充滿瞭收獲的旅程。它不像是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更像是一種長期的駐紮,一種全身心的投入,去理解山所代錶的那些亙古不變的道理。
评分我猜想,這本書的作者,一定是一位非常沉靜、非常有耐心的人。因為“與山學習”這件事,本身就需要極大的耐心和長期的投入。不像城市裏的生活,節奏快,變化多,山是緩慢的,是堅韌的,它的生命律動是另一種截然不同的韻律。在颱灣,我們常說“靠山吃山”,但這本書,聽起來更像是“靠山學做人”。它可能講述瞭一個人如何從山的身上,學會瞭什麼是堅守,什麼是靜默,什麼是順應自然。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將山的智慧,轉化為自己生活的實踐的?是體現在他的工作方式上?還是體現在他與人相處的方式上?亦或是體現在他處理情感的方式上?我期待這本書能給我帶來一些關於“慢生活”和“深度連接”的啓發,讓我能夠在喧囂的世界裏,找到屬於自己的那片寜靜之地。
评分“生命旅程”這個詞,讓我立刻聯想到人生的不同階段,不同的心境。這本書,聽起來就像是作者在人生的不同時期,都與山保持著一種連接,並且從中汲取著生命的力量。在颱灣,我們從小就接觸山,但往往隻是把它當做背景,或者是一種戶外活動的目的地。但如果能夠將山看作是一位老師,並且是“終生”的老師,那將是多麼富有啓發性的一件事!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展現齣,作者是如何在不同的生命階段,以不同的方式與山互動,又從中獲得瞭怎樣的成長和改變。是少年時期的勇敢探索,是青年時期的迷茫尋覓,還是中年時期的沉澱思考?我希望這本書能有一種溫度,一種真誠,讓我感受到作者與山之間那種深厚的情感,以及他對生命那種不懈的追求。
评分我總覺得,每一座山都有它自己的故事,而這本書,可能就是在講述一位旅者,如何傾聽這些故事,並將它們融入自己的生命。在颱灣,山是地理的標誌,也是文化的符號,承載瞭太多曆史的記憶和情感的寄托。作者能夠將“與山學習”作為一種“終生”的追求,這本身就說明瞭一種非凡的毅力與熱愛。我很好奇,作者在學習的過程中,是否遇到瞭什麼特彆的挑戰?是體能上的極限,還是思想上的睏惑?而這些挑戰,又是如何被他剋服的,又從中獲得瞭怎樣的啓示?我期待這本書能展現齣一種真正的“在地”視角,而不是那種隔靴搔癢的介紹。我想象,書中可能會有對颱灣本土山林獨特的生態環境的描繪,對原住民與山之間古老關係的探討,以及作者個人在融入這片土地過程中所産生的深刻體悟。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