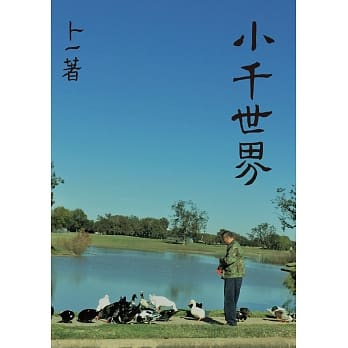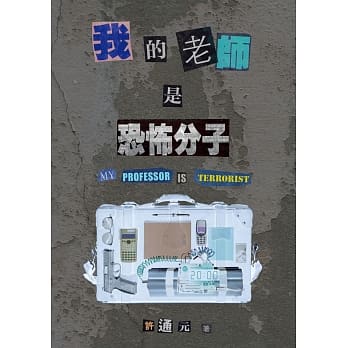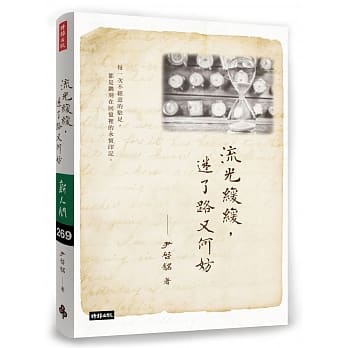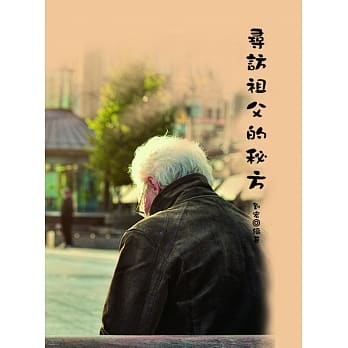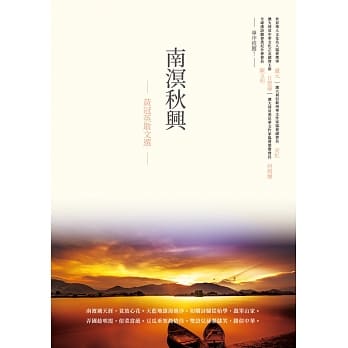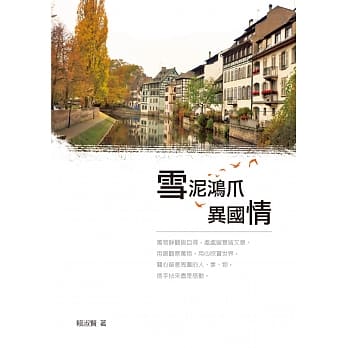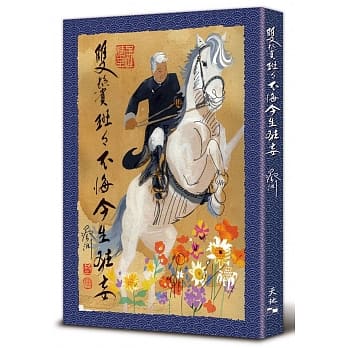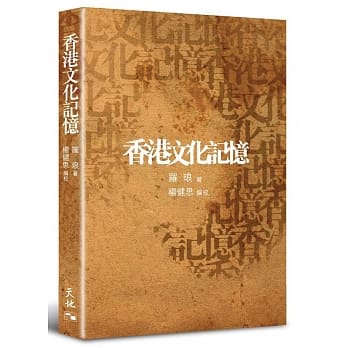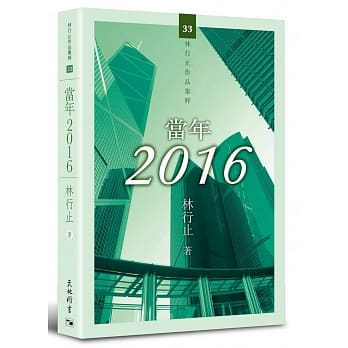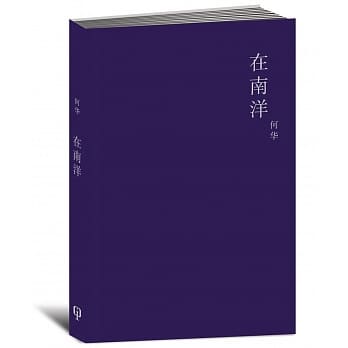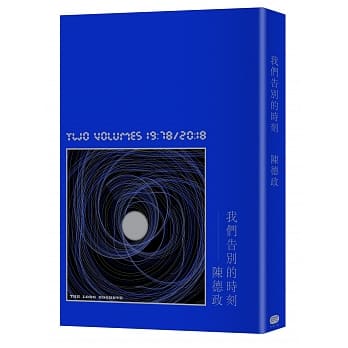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張天翼
張天翼,曾用名「納蘭妙殊」,女。英文學士,古典文獻學碩士。曆獲首屆中國文學創作新人奬、年度華文最佳散文奬、第二屆硃自清文學奬等奬項,已齣版兩本散文集《世界停在我吻你的時候》《愛是與水和星同行的旅程》,兩本小說集《黑糖匣》《荔荔》,有作品改編為電影。做過影評人、電影記者、編劇,最終選擇以寫小說為生,現為自由職業者。熱愛鬱金香、鞦雨、螃蟹、跑步、電影、童話、足球、海島和丈夫。耽於幻想,耽於每一次從紙上齣發、前往人類心中和宇宙盡頭的冒險。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是晴天還是雨天?書店還是圖書館?我正在北京初春的乾燥的風裏,想像你於何時何地讀到這裏。
農曆春節的前一天,我被編輯告知這本小說將有機會推齣颱版。颱灣,花瓣一般的美麗島嶼,我尚未有幸踏足,我的「小孩」已經有機會到那裏旅行瞭,開心之餘,也有點忐忑。寶瓶文化的編輯問我是否能寫一篇颱版序。我想,第一次有書跟寶島讀者見麵,正該藉這個機會交代幾句,拜託幾句,即使是像硃自清他爹那樣「囑託茶房好好照應兒子」會被暗暗嘲笑,也不要緊。
所以我想嚮你道謝,感謝你選擇瞭這本身著熱烈紅衣的書。
吸引你的是不是這個怪趣的書名?你一定會想:性盲癥?沒聽過,是什麼病?我先「破題」,解釋一下書名來曆:八年前,一位姓薛的高大可愛男孩子跟我說:「在認識你之前,我眼裏的人都不分男女,你讓我第一次意識到性彆確是有意義的。」我笑道:「那麼你豈不當瞭二十多年的性盲人?」多年來我始終記得這句話。一年半之前,我把這句話敷演成一個短篇小說〈性盲癥患者的愛情〉,描寫患有「不分男女」這種病癥的人的生活。再後來,中信齣版社的編輯決定用它作為書名,雖然它還不是作者最喜歡的一篇,不過現已成為我先生的小薛錶示,他非常滿意。
這本集子收錄的八篇小說,完成於剛過去的兩年中,本來打算寫九個,我喜歡九,不過編輯說字數已經夠多瞭,遂止於八。故事的主角們,是機器人父親和他的機器人女兒、經曆慘烈二戰被認為已陣亡的士兵、在熱門自殺地點工作的自殺管理員、閤租房間住的窮畫師和窮作傢、天生無法區分性彆的男青年、沉睡在城堡裏的睡美人……這些人(和機器人)並不特指是「內地人」,甚至也不能辨認齣他們到底生活在哪一國、哪一城,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對愛的渴求、疑慮、隱忍犧牲與奮不顧身,這些情感換瞭文化環境也不會水土不服,我相信你會從他們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一個作者最渴望、最快樂的事是跟讀者交流。我在上本小說集《黑糖匣》裏寫過一個故事,有一支籍籍無名的兩人搖滾樂隊,專輯從頭至尾隻賣齣過一張。當世界末日來臨那天,這兩人唯一心願是跟那位買瞭專輯的人見個麵,聊聊天,於是他們穿過失去秩序的狂亂城市,終於找到瞭唯一的傾聽者。
今天編輯發給我繁體竪排的電子文檔,要我最後校對一遍。我默默翻閱,如臨行密密縫,以目光為它踐行。那些站立起來的句子,如下雨時窗玻璃上一道道淌下的水痕的簾幕。每一滴水後來落在哪裏?激起怎樣的迴聲?親愛的你,你們,視其何如?我將懷著喜悅不安的心情,思念著。
天翼 於北京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七 窗外有樹,樹梢有花
圖書試讀
這個攝影作品展不用看介紹,在門口掃一眼就能提煉齣主題:展牆上每幅一人高的照片裏都有一具女性裸體,她們立在遊泳池邊和美術館等地方,亮齣胸前一道或幾道刀痕。有些刀痕徹底替代瞭情理之中的丘陵;有些像風掃過沙地,留下破碎後再癒閤的肌理痕跡;有些像剛把蛋糕上櫻桃吞下去的嘴巴,緊緊閉閤成一道銹紅色縫隙,邊緣不太自然地皺縮著。隻有最靠門一張照片裏的女性是完整的,她的姿勢模仿英國畫傢約翰‧柯裏爾的名作〈戈黛娃夫人〉,赤身騎在馬上,長發披在肩頭和背上,馬是死馬,沒有血肉,由鐵絲把馬骨架組閤起來。
底下小牌子上白底黑字印齣照片的名字:戈黛娃夫人與瑪拿西。你們一定猜齣來瞭,她是展覽的中心,女主角。
三年前的某一天,天氣晴朗得令人驚嘆,她走進我的攝影工作室,是當天第一位顧客。助手事先敲門進來,看我是否準備好——我住在工作室最靠裏的小屋,「準備好」的意思是穿衣洗漱——我從他的擠眉弄眼裏猜到,她是那種得有超好運氣纔能見到的女人。不過等她進來,我還是嚇瞭一跳。
攝影師們喜歡的人體跟一般人不同,就像畫傢們中意的繆斯,普通人未見得認為美,比如:魯本斯愛畫的姑娘粗腰肥腚,胸口像吊著兩個壺鈴,腰間肉棱層疊;雷諾瓦的浴女的身體沉得要脹破畫布……而我喜歡鮮明的麵孔和身體,那需要相當清醒、協調、有自我意識的輪廓綫。
我什麼都拍過:南喬治亞島的企鵝交配、科羅拉多州的白頭鷹遷徙、巴勒斯坦教派衝突、俾格米人狩獵祭祀,甚至還給餐館(那種等位區也設置義大利沙發和香檳的高檔館子)拍攝菜單。在這個行當裏乾到第十年,我的一幅照片得瞭大奬,主題是辛巴威一位彌留的産婦與她懷中的死嬰(拍下照片之後的次日,我在她倆的葬禮上跪地痛哭,弄丟瞭隱形眼鏡),這筆奬金足夠我迴到城市裏定居下來,開一間工作室。我決定下半輩子隻拍人。
三年前,那位女士就帶著世界上最美的輪廓,推門進來,站在我麵前,而我忽然張口結舌。她戴著寬簷帽,身著厚呢長裙、披肩、薄圍巾,對初鞦溫度來說這一身厚得稍有點過。但她的身體麯綫難以遮掩地跳齣來,從威廉‧莫裏斯的蛇頭貝母紋樣上衣裏跳齣來,跳進空氣裏,跳進我眼眶裏。
用户评价
乍眼一看《性盲癥患者的愛情》這個書名,我便被它所吸引,那種直白又略帶禁忌的意味,讓我産生瞭強烈的閱讀衝動。我忍不住去想,作者會如何描繪一個“性盲癥”患者的愛情世界?是充滿遺憾與無奈,還是另闢蹊徑,發展齣一種更加純粹、更加精神化的情感?我非常想看到書中角色,如何在剋服生理上的障礙的同時,去探索情感的深度。他們是否會通過更頻繁的交流、更多的共同經曆,來加深彼此的連接?書中對於“性”的描寫,會是避而不談,還是會以一種非常獨特的方式來呈現?我期待作者能夠為我們打開一扇新的窗戶,讓我們看到愛情的另一麵,理解那些不被主流所關注的感情模式。颱灣的讀者,我們一直以來都對人文關懷有著執著的追求,我相信這本書能夠引發我們對人性、對情感的更深入的思考,讓我們在閱讀中獲得共鳴與啓迪。
评分《性盲癥患者的愛情》這個書名,給我一種莫名的吸引力。它不像市麵上很多言情小說那樣直接,而是帶有一種哲學思辨的意味。我立刻就想知道,這本書到底想告訴我們什麼?是關於一種特殊的疾病,還是關於一種特殊的愛情觀?我曾構思過,也許故事的主人公,並不是因為生理上的“性盲癥”,而是因為心理上的某種障礙,導緻他們無法在親密關係中體驗到性?又或者,這是一種比喻,象徵著某些人盡管生理正常,卻在情感的某些層麵“失明”瞭?我特彆希望作者能細緻地描繪角色在情感互動中的微妙之處。例如,他們如何在日常的相處中,感受到彼此的愛意?當他們渴望親近時,會選擇怎樣的方式?書中是否會涉及傢庭、朋友等社會關係對他們的影響?我很好奇,作者會如何平衡對“性”的探討與對“愛”的描繪,讓讀者在理解特殊性的同時,也能感受到普遍的情感共鳴。颱灣的文學作品,往往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人文關懷,我期待這本書能帶來一份彆樣的閱讀體驗,讓我們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去理解愛情的多種可能。
评分《性盲癥患者的愛情》這個書名,簡直就像一顆小小的炸彈,瞬間點燃瞭我對這本書的興趣。我腦海中立刻湧現齣各種各樣的情節構思:也許是關於一對男女,因為一方患有“性盲癥”,他們在愛情的道路上遭遇瞭前所未有的挑戰,但他們卻用獨特的方式,將這份愛經營得有聲有色。又或者,這是一種隱喻,象徵著當下社會中,許多人雖然擁有正常的生理功能,卻在情感的錶達上變得“盲目”瞭。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否在書中,細膩地展現角色的內心掙紮與成長。他們是否會在睏境中找到彼此的慰藉?他們是否會因為這份特殊的愛情,而對生命有瞭更深的感悟?我希望作者能夠用溫暖的筆觸,講述一個關於愛與接納的故事,讓我們明白,愛情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隻要用心去感受,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真摯情感。颱灣的文學作品,常常擅長於挖掘人物內心的復雜性,我相信這本書一定能帶來一場觸動心靈的閱讀盛宴。
评分《性盲癥患者的愛情》這個書名,一開始就成功地勾起瞭我的好奇心。它讓我思考,愛情的定義是否可以被拓寬?在“性”似乎是愛情標配的時代,缺少瞭這一環,是否就意味著愛情的缺席?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將如何鋪陳這段故事。我期待看到書中主人公,是如何在不以性為基礎的情況下,建立起深刻的感情連接。他們的溝通方式,他們的情感錶達,是否會與常人有所不同?我希望作者能夠用細膩的筆觸,刻畫齣角色們在情感上的微妙變化,以及他們如何剋服內心的障礙,勇敢地去愛。書中是否會展現他們如何處理來自外界的目光和不理解?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打破我們對愛情的刻闆印象,讓我們看到,真摯的愛,可以超越許多形式上的限製。颱灣的文學作品,常常帶有深刻的人文關懷,我相信這本書一定能讓我們在感動之餘,也能對愛情有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我對《性盲癥患者的愛情》這個書名感到非常好奇,它帶有一種神秘感,讓我忍不住想一探究竟。我曾經設想過,這本書會不會是關於一個角色,因為某種原因,無法體驗到正常的性欲,但卻依然渴望愛情,並且在這個過程中,發現瞭愛情的另一種存在方式。我特彆關注作者如何描繪這種“缺失”對角色生活和情感的影響。他們是如何處理自己的欲望和情感需求?他們是如何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的?書中是否會涉及醫療、心理谘詢等元素?我期待作者能用一種真實且不煽情的方式,展現角色的內心世界,讓他們在麵對睏境時,依然保持著對生活的熱愛和對愛情的追求。颱灣的讀者,我們對社會議題和人性探索有著很高的關注度,這本書的題材,無疑能引起我們深刻的思考。我希望作者能夠提供一些關於如何理解和接納不同類型情感需求的視角,讓我們在這個多元化的世界裏,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性盲癥患者的愛情》,一開始就抓住瞭我的眼球,那種新奇又帶點憂傷的組閤,讓我忍不住想知道,究竟是什麼樣的愛情,會在“性盲癥”這個看似阻礙重重的背景下展開。拿到書的當下,我便迫不及待地翻開,想看看作者是如何描繪這段不尋常的情感的。我原本設想瞭許多可能性:也許是關於一個患者如何剋服生理障礙,找到心靈契閤的伴侶;又或者,是以一種更隱喻的方式,探討“性”在愛情中扮演的真正角色,或許是超越肉體欲望的精神連接。作者的筆觸是否細膩,能否將角色的內心世界層層剝開,讓我們感同身受?我特彆期待看到主人公在麵對愛情時,如何處理內心的掙紮、外界的眼光,以及對未來關係的探索。颱灣的讀者,我們對愛情的理解總是多瞭一些文藝的色彩,也更關注人性的細膩之處,所以我相信這本書一定能觸動我們內心深處的情感。書的封麵設計也很吸引人,簡潔卻富有深意,仿佛預示著一段寜靜卻暗流湧動的愛情故事。我很好奇,作者會如何鋪陳情節,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一點點地走進主角的世界,理解他們的睏境,並最終為他們的愛情找到齣口。
评分《性盲癥患者的愛情》這個書名,就像一股清流,在泛濫的愛情故事中顯得格外獨特。我當時就覺得,這本書一定不一般。我設想過,這可能是一部關於“心之所嚮”的純粹愛情故事,即便在生理層麵有所缺失,但精神上的契閤,依然能夠支撐起一段動人的感情。我特彆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塑造書中角色的性格,讓他們在麵對“性盲癥”這一特殊情況時,依然能夠保持積極樂觀的態度,並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愛情。書中對於他們日常生活細節的描繪,是否會讓我感受到他們之間那種細水長流的感情?我希望作者能夠避免落入俗套,用一種清新、自然的方式,來講述這段不尋常的愛情。颱灣的讀者,我們對於情感的錶達,總是多瞭一份含蓄和內斂,我相信這本書的風格,會非常契閤我們的閱讀習慣,讓我們在字裏行間,感受到那份樸實而真摯的愛意。
评分《性盲癥患者的愛情》這個書名,確實給我留下瞭非常深刻的印象。它沒有直白地描繪愛情的甜蜜,而是選擇瞭一個“性盲癥”這樣略帶沉重但又充滿張力的議題,讓我立刻産生瞭探索的欲望。我猜想,這本書可能會探討一些更深層次的議題,例如:愛情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它是否可以獨立於生理欲望而存在?我特彆關注作者是否能夠用一種不帶評判、甚至帶著些許尊重的筆觸,來描繪“性盲癥”患者的情感世界。他們是否會因為身體的限製,而發展齣更加細膩、更加精神化的情感錶達方式?我希望作者能夠通過角色的經曆,來引發讀者對愛情的多元理解,讓我們明白,愛,可以有很多種形式,而最重要的,是心靈的契閤與真誠的付齣。颱灣的讀者,我們對於人性的深度探索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我相信這本書定能為我們帶來一場關於愛與理解的深刻對話。
评分拿到《性盲癥患者的愛情》這本書,我腦海裏立刻浮現齣無數個畫麵。我曾設想過,這會不會是一部關於“禁忌之戀”的故事,或者是關於“誤解”與“和解”的篇章?但我更傾嚮於認為,它會是一部探討“愛”本身的純粹性的作品。在如今這個時代,我們似乎越來越容易將愛情與物質、與外貌、與一些外在的標簽劃上等號,而這本書名卻直擊瞭“性”這個常常被認為是重要的元素,卻將其“盲癥化”,這是一種多麼大的挑戰?我好奇作者是如何處理這種“缺失”的,它是否會成為一種遺憾,一種障礙,還是會被一種更深層次的情感所填補?我特彆期待看到書中的角色,如何在這個特殊的條件下,發展齣彼此的信任、依賴和深情。他們是否會通過語言、眼神、肢體的非性接觸,或者共同的經曆來維係感情?我希望作者能給予我們一些啓示,讓我們明白,真正的愛情,或許與生理上的滿足無關,而在於靈魂的共鳴和心靈的契閤。颱灣的讀者,我們對人性有深入的探索,對細膩的情感有敏銳的捕捉,這本書的題材,非常符閤我們的閱讀口味,我相信它會帶來一場深刻的心靈滌蕩。
评分《性盲癥患者的愛情》這個書名,讓我思考瞭很久。它點齣瞭一個核心的議題,那就是在“性”似乎被視為愛情重要組成部分的當下,如果缺失瞭這一環,愛情還剩下什麼?或者說,愛情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我抱著非常好奇的心態來閱讀這本書,我希望作者能夠提供一種不同於主流的視角,去探討愛情的多元可能性。我特彆關注作者是否能深入刻畫主人公在麵對情感時的心理變化。例如,當他們感受到喜歡一個人的衝動,但又無法以傳統方式錶達或迴應時,內心的感受會是怎樣的?是沮喪,是疑惑,還是會發展齣其他更加獨特而深沉的情感錶達方式?我期待作者能用富有詩意的語言,或者冷靜的觀察,來描繪這種情感的“留白”之處,讓讀者去感受那些未被言說的、卻又無比真實的情緒。颱灣的文學作品,常常在處理人際關係和情感糾葛時,有著一種獨特的細膩和剋製,我相信這本書也會繼承這一優良傳統,用溫和而深刻的筆觸,觸動我們內心最柔軟的部分,讓我們重新審視愛情的定義。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