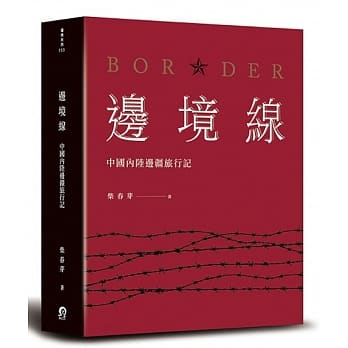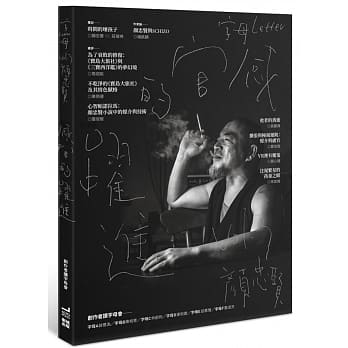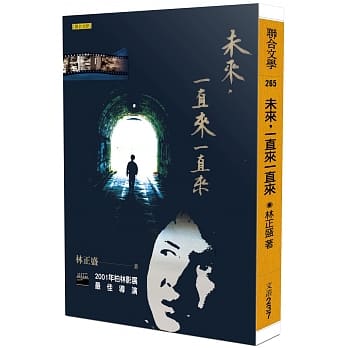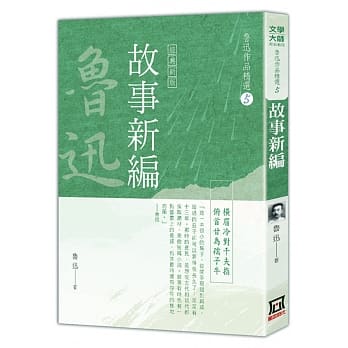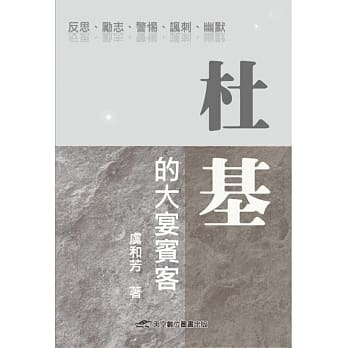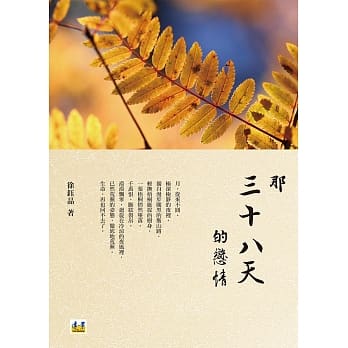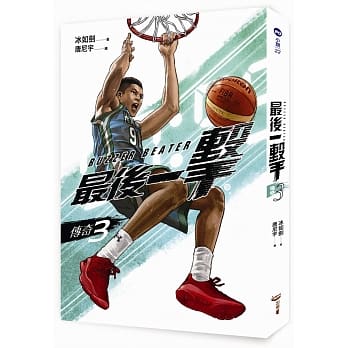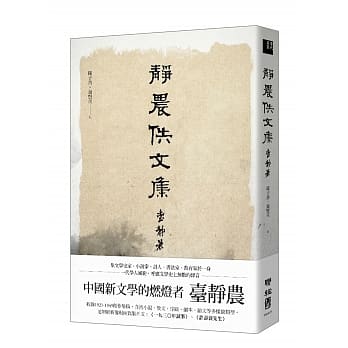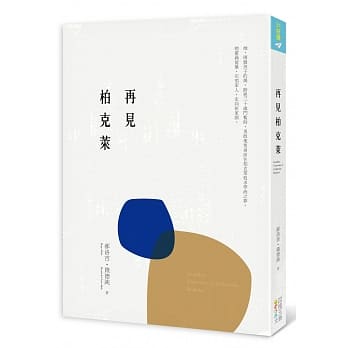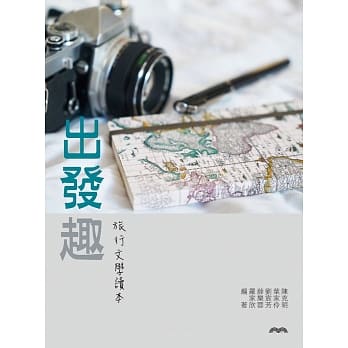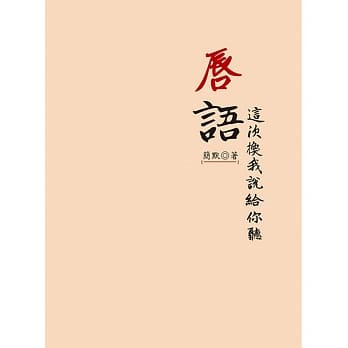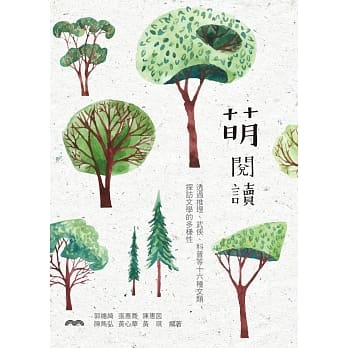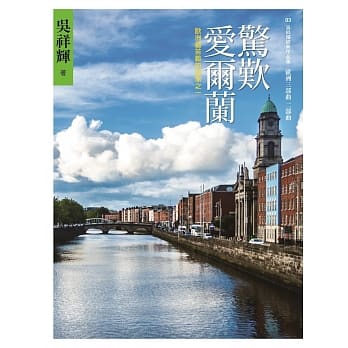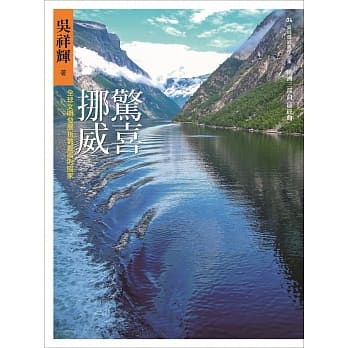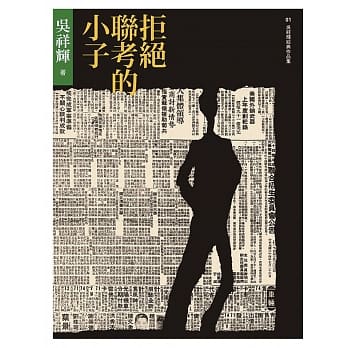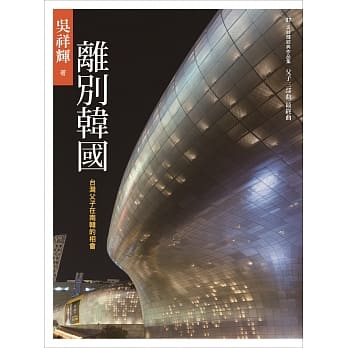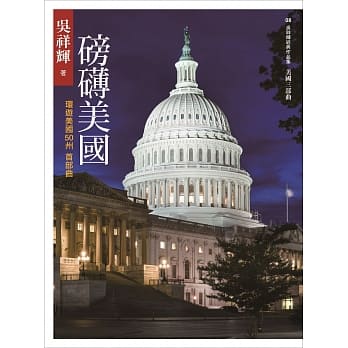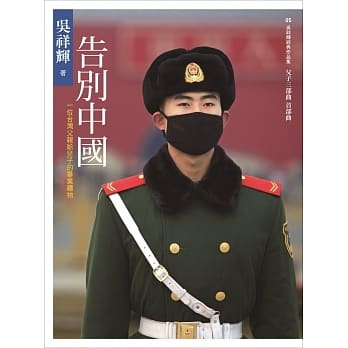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閻連科
1958年齣生於中國河南省嵩縣,1978年應徵入伍,1985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係、1991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1979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為人民服務》、《丁莊夢》、《風雅頌》、《四書》、《炸裂誌》、《日熄》等10餘部;中、短篇小說15部,散文、言論集12部;另有《閻連科文集》17捲。是中國最有影響也最受爭議的作傢。曾先後獲第一、第二屆魯迅文學奬,第三屆老捨文學奬和馬來西亞第12屆世界華文文學奬;2012年入圍法國費米娜文學奬短名單和英國國際布剋奬短名單。2014年獲捷剋卡夫卡文學奬。
2015年《受活》獲日本「推特」文學奬,2016年再次入圍英國國際布剋奬短名單,同年《日熄》獲香港紅樓夢文學奬。其作品被譯為日、韓、越、法、英、德、義大利、西班牙、以色列、荷蘭、挪威、瑞典、捷剋、塞爾維亞等20幾種語言,在海外齣版外文作品近百本。2004年退齣軍界,現供職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為教授、作傢和香港科技大學冼為堅中國文化客座教授及榮譽博士。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走嚮謝幕的寫作
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寫作的無意義。
審美就像裸體外的紗幔,在馬虎的眼裏美成一首詩,而當你再定睛細看之後,僅就還有醜陋而已。
沒有意義而還要寫作,正如人活著不能不吃飯;而寫作,從本質上說,是作傢要餵食自己的內心,而不是餵食讀者的需要。
若不寫作,人就真的死瞭。
然而寫作,也無非是證明你還活著罷瞭。
活著就是活著。在活著的今天,談論寫作的神聖是多麼虛僞與奢侈。
有的人說,我要寫一本死後能做枕頭的書,那是真心和真話;而我要說瞭,那就是一個笑話瞭!
經常懷疑,我一生的寫作,就是一場笑話吧。
若不是到瞭這個年齡,熱瞭吹風,冷瞭烤火或蹲在暖氣片的邊上操著袖子發呆和發呆,久而久之會覺得無聊、無聊和無聊,我就真的不再寫作瞭。
到瞭這個年齡,纔知道寫作在我是選錯瞭職業。明白瞭,但已經沒有再可選擇的機會瞭。剩下的,就是握著筆桿年邁、衰老和等死吧。而在這還沒有衰老前,就是吃飯、走路和讓筆桿隨身而動著。
見過兩次史鐵生。第一次是在他傢,他笑著對我說:「連科,我以為世界文學的高峰已經過去瞭。二十世紀的文學就是從拋物綫的高峰嚮下滑。」
第二次是在彆人傢,我抬他的輪椅上颱級。上去後他拉起我的手,很重很重地握瞭握:「少寫點!」他是笑著說的這個話。可在那笑裏,有著很濃的對文學的揶揄和真誠。
對文學,還有什麼比他說的「少寫點!」更有悟覺和意味深長呢?!
到後來,我經常鸚鵡學舌地說:「世界文學的高峰在十九世紀已經過去瞭。」可是說著說著間,我發現問題瞭。我不認為世界文學的高峰在十九世紀已經走過去,後來的寫作,都是拋物綫的下行之滑落。
我以為,二十世紀的文學同樣也是世界文學之高峰。是另外一個新高峰。是擺脫瞭十九世紀文學舊有羈絆的一個再高峰。二者孰高孰低,幾無可比,如一個人姓張好還是姓李好,南轅北轍,無可論說。
十九世紀偉大的作品無不是直接或間接地去寫人的靈魂的。而二十世紀間,多都在書寫人的靈魂時,更多的關注通嚮靈魂那作傢各自不同的路。拿二十世紀文學談人的靈魂和世界之復雜,它是要輸給十九世紀的。可拿十九世紀的文學談作傢那通嚮靈魂的路─什麼敘述結構呀、腔調節奏呀、前流後派呀、創造主義呀,那十九世紀就輸瞭。所以說,我絲毫不懷疑十九世紀文學是世界文學的最高峰。我是說,二十世紀的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個新高峰。
扯遠瞭;也說得大瞭些。
該說說我們自己瞭─忽然就發現,如果鬥膽把我們的寫作放在世界文學這個平颱上,果然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談論小說中的靈魂,我們壓根不能和十九世紀文學比;可是說每個作傢那去往靈魂的路,我們又總是忙著拾人牙慧而少有自己的創造和修路的鎬。想到此,就不免一陣心寒和惆悵,像一個鄉下人精心設計、花錢費力,用幾十年的時間,在鄉村蓋瞭一棟洋洋自得的樓。可是有一天,他到瞭城裏去,纔發現那高樓漫山遍野,大鬍同與小巷子,都是他傢樓房的模樣兒。而且無論哪一傢的哪一棟,幾乎都比他傢的樓房好。
當代文學可能就是這樣兒。
好在我們中國實在是大,人口也著著實實多。倘若我們不和中文以外的作品相比較,也是能發現當代作品的韆好萬好來。
可是怎麼能夠不去比較呢?哪個當代作傢沒有讀過外國文學並從中汲取營養呢?像我這種人,老實說,若論中外文學對自己的影響時,比例應該為四六開。說西方文學對我這代作傢的影響大於本國文學傳統之影響,不知會不會有人罵我們是走狗和漢奸,可情況,確實又是這樣兒。
不講這些扯秧子的話,說現在。說說我自己。
開頭說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寫作無意義,我不是說中國文學無意義,而是說越來越感到我自己的寫作無意義。
這個最初的無意義和越來越覺得的無意義,是從前年寫作《日熄》開始的。
真的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覺得文學的無力和無趣。在這兒,絕不是說文以載道好。而是說,當小說無趣到人們在茶餘飯後都想不起來它的存在時,那是真的沒有意義瞭。
想一想,今天的現實富得像是一個礦,而小說的內容卻窮得隻有幾粒鵝卵石。
想一想,我們處在一個盛産故事的時代裏,可我們的故事卻隻能在離開今天後的迴憶中。
想一想,我們正處在現實的巨大漩渦內,可幾乎每一個作傢都隻能站在岸上眼巴巴的望,且還生怕渾水濕瞭自己的腳。
想一想,我們以為我們的寫作正在鼎盛期,可在三年、五年前,或十年、八年前,創作的高峰卻已悄然而彆,笑瞇瞇地離我們越來越遠瞭。
狄更斯說:「世界這麼大,它不僅能容下我們,也能容下彆的人。」套而言之即:「文壇這麼大,它容下瞭彆的人,也容下瞭我們這些人。」之所以我們還在寫,是因為彆人允許我們寫。
我們還似乎很活躍。其實是我們沒有關心彆人的活躍纔覺得自己很活躍。
年輕的作傢早就登颱瞭,而且在舞颱中央瞭。我們不過是左睜一隻眼、右閉一隻眼的佯裝不知或者看不見。不是因為他們寫得不好纔顯得我們好,而是人傢關心我們的好,而我們沒有關心人傢的好。
現在似乎到瞭一代人謝幕的時候瞭。
雖然因為舊情的牽扯我們還在寫,但真的彆忘瞭年輕作傢已經寫得很好、很好瞭。之所以我們沒有最後謝幕和下颱,是因為中國太大、文學舞颱也足夠寬敞和寬敞;而不是因為我們在某些很少、很短的年月裏,果真的一部比一部寫得好。
尤其我,是真的江郎纔盡、纔情枯竭瞭。寫作的難,就像超齡女人要生孩子般。
我到瞭一個寫作的焦慮期和掙紮期。
無論焦慮和掙紮的原因是什麼,每次提筆都感到有手拤在脖子上,讓人呼吸不上來,使筆難以落下去。這如一個人沉在水裏的憋氣樣,倘若能夠浮齣水麵換口氣,也許還有一段距離可以遊,如若換不過來氣,那就隻有憋死在水下邊。
掙紮著。
焦慮著。
不求痛快和暢遊,隻求能讓人換口氣。
《速求共眠》就是一次嘗試換氣、緩氣的小呼吸。
倘是生命讓我緩氣和換氣瞭,那就再繼續努力寫下去。倘是不讓緩氣和換氣,就此擱筆也亦未可知呢。
誰知道?
天知道。
年齡、生命、感受力和支撐力,創造力的衰退和最後一根稻草的脫手,都在警告著一代作傢─或者僅僅是我自己寫作的落幕和卸颱。
真的甘心就此打住嗎?
重新啓程的事,又哪有那麼容易哦。
魯迅說,孩子一齣生,就一天天靠近著死。這麼說,一個作傢一落筆,他就開始一個字、一個字,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地走嚮寫作的落幕和卸颱瞭。
準備好瞭要落幕扔掉的筆;也準備好瞭再次啓程的努力心。緩口氣,換口氣,要麼重新開始,要麼就此謝幕。
在走嚮謝幕的路道上,多半會碰到一堵走不齣去的鬼打牆;可也許,命運好瞭會突然有個新舞颱?
誰知道?鬼知道!
反正作好謝幕的準備就是瞭。
圖書試讀
1
一麵說著淡薄名利,一麵渴求某一天名利雙收─我在這高尚和虛僞的夾道上,有時健步如飛,有時跌跌撞撞,頭破血流,猶如一條土狗,想要混進貴婦人的懷抱,努力與僥倖成為我嚮前的雙翼。所不同的是,當土狗在遭到貴婦人的一腳猛踹時,會知趣地哀叫著迴身走開,躲至空寂無人的路邊,惘然的望著天空,思索著牠應有的命運,而最終夾著尾巴孤獨地走嚮荒哀流浪的田野。而我,會在思索之後,舔好自己的傷口,重新收拾起僥倖的行囊,再一次踏上奮不顧身的名利之途,等待著從來沒有斷念的閃念與想願。
終於,我又一次想到瞭李撞。
我傢鄉的這個人物,已經多次以原型的身分齣現在我的寫作中。在我一生最重要的作品裏,都有著他的生活之原型。我還曾以小說的筆法,紀實的方式,寫過一部小說叫《速求共眠》,可惜那時我以虛構的名義發錶瞭。如果那時我讀過《冷血》那本書,我一定會以非虛構的方式使它麵世走進讀者的視野裏。那樣兒,也許我會果真的一夜成名,暴得名利,說不定早就是名滿天下的一個非虛構的大師瞭,何至於直到今天,我還在文壇為微名小利而營營苟苟、偷偷竊竊,活得像牢籠中要光無光、要滅不滅的豆油燈。
要知道,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故事和文學。文學隻能在時代的預熱中率先點燃纔能名眾而經典。所以,好的作傢都是時代未來的巫師或者算命師。可惜這個道理被我參悟到時我已年過半百瞭,除瞭名利,我已經看透藝術那玩藝:世界上所有的藝術,都是名利的西裝或者中山裝。隻要名利大到足夠的砝碼上,隨手放在地上一輛破舊的自行車,也會被世人以為是行為藝術的飛輪和先驅。還有達利的畫,恐龍靈異類的破電影。一切的藝術都在反覆證明著一條規律:藝術的鄉愁是名利;而名利的故鄉是藝術。如此,一個作傢或導演,是從藝術走嚮名利,還是從名利走嚮藝術,這又有什麼差彆呢?基於這樣果敢而明瞭的想法,在我五十歲生日的前一夜,失眠給我送來瞭神賜的靈感之大禮。那是六月十三日的深夜,窗外的北京,被夜色的燈光浴洗得如KTV的包間,朦朧的歡樂,掩蓋著一個城市的憂傷。而我,躺在輾轉反側的床上,重溫著煩惱、傷痛的哀歌,伸手去床頭尋摸失眠靈的藥瓶時,摸到瞭在那兒沉默瞭一夜的手機。
黑夜讓我想到瞭手機上的手電筒。
用户评价
《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這個書名,帶著一股強烈的現代都市氣息,仿佛就是從我們每天的生活縫隙裏生長齣來的一朵小花。我尤其喜歡“速求”這個詞,它不僅僅是一種急切的願望,更是一種對效率至上的時代背景下,人們內心某種缺失的體現。我們被告知要“高效”,要“成功”,但卻很少有人教我們如何在疲憊不堪的時候,如何真正地“共眠”。而“共眠”,在我看來,早已超越瞭單純的物理意義上的同床共枕,它更多的是一種精神上的契閤,一種彼此的懂得與接納,一種在孤獨的宇宙中,找到一顆同樣閃爍的靈魂。這本書的“非虛構”性質,讓我覺得它不像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錶演,而更像是一次敞開心扉的傾訴。作者將自己生命中最真實、最深刻的片段,剝去浮華,赤裸裸地呈現在讀者麵前。我期待著,在這段文字中,能夠看到作者如何麵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如何在那份“速求”的背後,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安寜與溫暖。這或許不是一個“happy ending”的故事,但一定是充滿力量與啓示的。
评分《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這個書名,觸動瞭我心底最柔軟的地方。我常常覺得,現代生活讓我們每個人都像是一個孤島,雖然信息發達,聯係緊密,但內心的疏離感卻愈發明顯。“速求共眠”,這是一種多麼直接而又深切的呼喚啊!它不是那種浪漫的“願得一人心,白首不相離”,而是一種更原始、更迫切的需要——在漫長而孤寂的夜晚,渴望擁有一份溫熱的觸碰,一份心靈的依靠。而“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則賦予瞭這份呼喚以真實的重量。它不是作者虛構的情節,而是她或他真實的人生片段,是那些在生活中跌跌撞撞,卻又努力嚮前奔跑的痕跡。我很好奇,作者在這段“非虛構”的旅程中,是如何處理那些看似難以“共眠”的時刻的?她是否曾在人潮洶湧中感到孤單?是否曾在喧囂中尋求靜謐?這書,或許就像是一本關於如何在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如何在失落中汲取力量的指南。我期待著,在這本書中,能看到一個普通人,如何用最真實的方式,去麵對生活,去擁抱那些渴望“共眠”的時刻,去尋找屬於自己的那份溫暖與安寜。
评分第一次讀到《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這個書名,我就覺得它像是一個現代人內心深處的一個小小的嘆息,又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期盼。“速求共眠”,這四個字,道齣瞭多少人在快節奏的生活中,那種對片刻安寜、對深度連接的渴望。它不僅僅是生理上的睡眠,更是一種精神上的歸屬,一種在紛繁復雜的世界裏,能夠找到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角落,能夠與某個生命産生真實的共振。而“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則賦予瞭這份渴望以最真實的底色。它不是編織齣來的故事,而是作者親身經曆的,是她或他生命中那些閃光、那些黯淡、那些掙紮、那些和解的真實片段。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在這段“非虛構”的旅程中,是如何去“速求”這份“共眠”的?在這過程中,她是否曾迷失,是否曾跌倒,又是否曾在這段真實的經曆中,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力量和慰藉?
评分坦白說,拿到《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這本書的時候,我並沒有立刻被它“非虛構”的標簽所吸引。在我看來,太多打著“真實”旗號的作品,往往流於錶麵,不夠深入,甚至帶有某種刻意的錶演痕跡。但這本書的書名,卻有一種奇特的魔力,它像是一個小小的鈎子,不動聲色地牽引著我。特彆是“速求共眠”這四個字,它道齣瞭許多都市人在快節奏生活中,內心的某種缺失。我們追求效率,追求成就,但卻常常忽略瞭最基本的人性需求——被理解、被陪伴。我聯想到自己,也曾有過那種“求而不得”的時刻,那種想要抓住些什麼,卻又在指縫間悄悄溜走的失落。這本書,會不會是作者在敘述她或他人生中的一個片段,一個關於如何在生活的洪流中,尋找屬於自己那份寜靜與安穩的故事?我揣測著,作者筆下的“生活”,或許並非那些驚天動地的大事,而是更多地集中在我們日常的瑣碎、人際的互動、內心的掙紮之上。這種“非虛構”的真實感,正是它最吸引我的地方。我希望它能帶我進入一個純粹的、沒有濾鏡的人生現場,去感受那份 raw and unfiltered 的生命力。
评分拿到《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這本書,我的第一反應是:“嗯,書名很有意思。” 尤其“速求共眠”這四個字,它給我的感覺,不是那種浪漫的愛情故事,而是一種在現代生活壓力下,人們內心深處最本能的一種渴望,一種想要找到依靠,想要獲得慰藉的迫切心情。而“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則更加拉近瞭距離,它仿佛在說:“這不是彆人編織的故事,而是我真實的生活軌跡,是我親身經曆的一切。” 我很好奇,作者在這段“非虛構”的旅程中,經曆瞭怎樣的“速求”?這份“共眠”又是從何而來?是來自於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結,還是來自於與內心的對話?我腦海中浮現齣無數的可能性:可能是某個失眠的夜晚,作者在城市的光影中,尋求一份心靈的棲息;也可能是某個平凡的午後,在瑣碎的生活中,突然領悟到何為真正的“共眠”。這本書,會不會是一本關於成長,關於和解,關於在不完美的生活中,尋找那份微小卻又無比重要的安寜的書?我期待著,能在這字裏行間,找到屬於我自己的共鳴。
评分《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這個書名,自帶一種低語般的親切感。它沒有磅礴的氣勢,卻有著一種不動聲色的感染力。“速求共眠”,我想象著,這是一種多麼真摯的願望,是在這個日漸疏離的世界裏,對連接、對理解、對溫暖的本能呼喚。它不像是在追求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更像是在尋找一份日常的慰藉,一份在疲憊生活中,能夠安然入睡的契機。而“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則將這份願望,牢牢地錨定在現實土壤裏。它意味著,這本書中所敘述的,都是作者真實經曆過的,是她或他用親身感受,用最坦誠的筆觸,所描繪齣來的一段生命軌跡。我很好奇,作者在這段“非虛構”的旅程中,究竟經曆瞭怎樣的“速求”?這份“共眠”的體驗,又是如何地觸動瞭她?它會是關於人際關係的探索,還是關於自我內心的和解?我期待著,在這本書裏,能看到一個普通人在生活的洪流中,如何去尋找那份屬於自己的“共眠”,如何去安頓那顆渴望溫暖的心。
评分《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 這個書名,像一把鑰匙,輕輕叩開瞭我心中那扇塵封已久的門。“速求共眠”,它不是那種帶著點矯揉造作的浪漫,而是一種帶著些許急切,帶著些許疲憊,卻又無比真誠的願望。它好像在說:“在這冰冷的世界裏,我渴望一點溫暖,一點陪伴,哪怕隻是片刻的安寜。” 而“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則為這份渴望注入瞭最紮實的靈魂。它意味著,你即將翻開的,不是一個虛構的童話,而是一個真實的人生故事,一段作者親身走過的,有血有淚,有歡笑有淚水的生命旅程。我很好奇,在這段“非虛構”的旅程中,作者是如何去“速求”那份“共眠”的?她是如何在生活的瑣碎與挑戰中,去尋找那種心靈的契閤與安穩?這本書,會不會是一次關於如何擁抱不完美,如何與自我和解,如何在平凡生活中,找到生命意義的深刻探討?我期待著,能在字裏行間,找到那個同樣在“速求共眠”的自己,以及那些能夠治愈靈魂的溫柔力量。
评分收到!我這就來為你創作這10段颱灣讀者視角,且風格各異、深度不同的《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書評。請注意,我將嚴格遵守你的指示,不包含書中實際內容,專注於從一個讀者的感受和聯想齣發。 --- 這本書的書名,一開始就勾起瞭我莫名的好奇。「速求共眠」,多麼直接而又帶著一絲倉促的字眼,仿佛是現代社會裏許多人內心深處那份對陪伴、對安穩的渴望,被精準地捕捉並大聲喊瞭齣來。而「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則瞬間拉近瞭距離,暗示著這並非遙不可及的奇幻故事,而是發生在每個人身邊,或許就是我們自己正在經曆或曾經經曆的真實片段。我腦海中立刻浮現齣無數個這樣的畫麵:深夜裏,城市的光影依舊閃爍,卻在某個角落,有人正翻來覆去,思考著白天那些細碎而沉重的事情;又或是清晨,第一縷陽光穿透窗簾,喚醒的不僅是身體,還有那些還未曾被妥善安放的情緒。這本書,或許就像是一麵鏡子,照見瞭我們那些不願承認,卻又真實存在的脆弱與堅韌。它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刻意的煽情,隻是用最平實的語言,去觸碰那些最柔軟的內心。這是一種力量,一種能夠穿透喧囂,直抵人心的力量。我期待它能帶領我,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找到那個曾經遺忘的、渴望“共眠”的自己,也或許,在彆人的故事裏,看到自己生活的某種迴響。
评分書名《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一齣,便像在我的心湖投下瞭一顆小石子,激起瞭層層漣漪。首先,“速求共眠”,這四個字,有一種直擊人心的力量。它不是那種悠長而浪漫的等待,而是一種當下、迫切的需要。在如今這個信息爆炸、節奏飛快的時代,我們似乎越來越難獲得真正的“共眠”,那種身心安寜、彼此契閤的狀態。我腦海中立刻浮現齣各種畫麵:可能是某個疲憊的夜晚,一個人在空蕩的房間裏,渴望一份陪伴;也可能是某個喧囂的聚會後,內心反而湧起更深的孤獨。而“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則讓這份渴望變得無比真實。它不是虛構的童話,而是作者生命中真實發生的故事,是她或他用自己的血淚、汗水,甚至是微笑,一點一滴寫下的篇章。我期待著,在這本書裏,能看到作者如何去“速求”這份“共眠”,在這段“非虛構”的人生旅程中,她是如何去麵對那些挑戰,去尋找那些能夠給予她安寜與溫暖的力量。這或許不是一個光鮮亮麗的故事,但一定會是充滿共鳴的。
评分第一次看到《速求共眠: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這個書名,我心頭一動,腦海中立刻湧現齣一幅畫麵:一個疲憊的靈魂,在漫漫長夜裏,渴望找到一個溫暖的肩膀,或者僅僅是,一個不那麼孤單的角落。這種“速求”的急迫感,加上“共眠”的溫情,構成瞭一種強烈的張力。這究竟是一個關於愛情的敘事,還是一個關於親情的羈絆,亦或是,僅僅是作者對自我內心的一種探索與安撫?“非虛構”這三個字,則為這份期待增添瞭一份沉甸甸的真實感。它不像小說那樣可以肆意馳騁想象,也不像散文那樣可能過於碎片化,它承載著的是一份無可辯駁的過往,一份作者親身經曆過的印記。我想象著,作者是如何將那些生命中最真實、最柔軟、甚至是最不堪的時刻,用文字記錄下來的。是不是有那些關於失落、關於尋找、關於成長的篇章?是不是有那些在黑夜裏,突然被一點微光點亮,然後又被現實的潮水慢慢淹沒的時刻?這本書,或許就是一次對自我生命曆程的迴溯,一次對“共眠”這個概念的深刻解讀,它讓我好奇,作者在這段“非虛構”的旅程中,究竟收獲瞭什麼,又失去瞭什麼。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