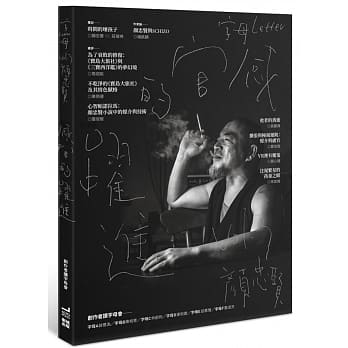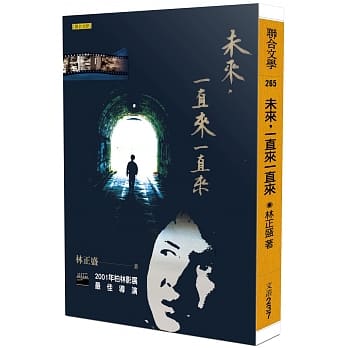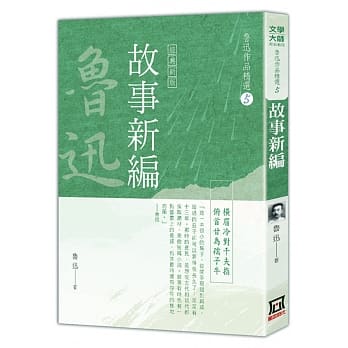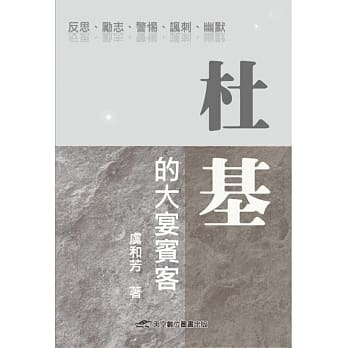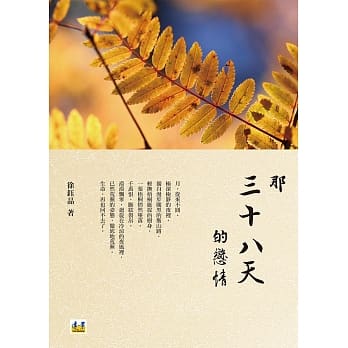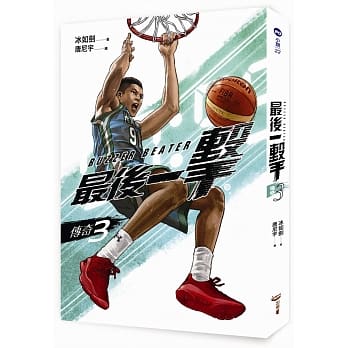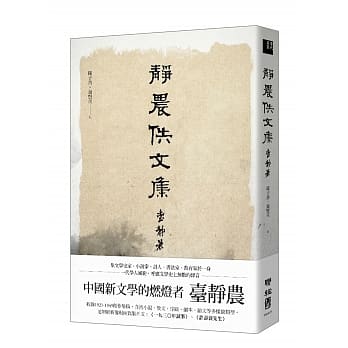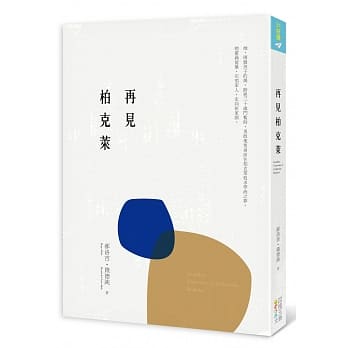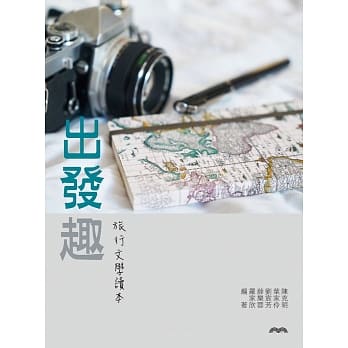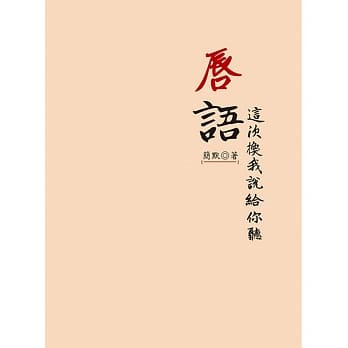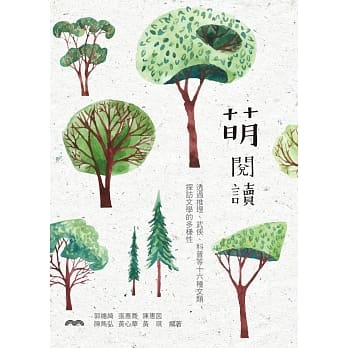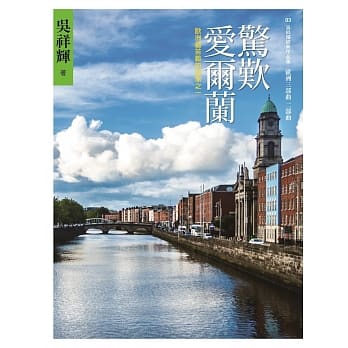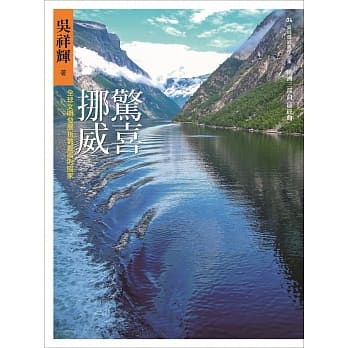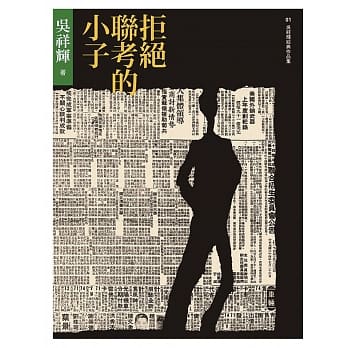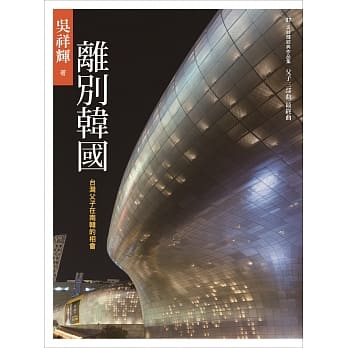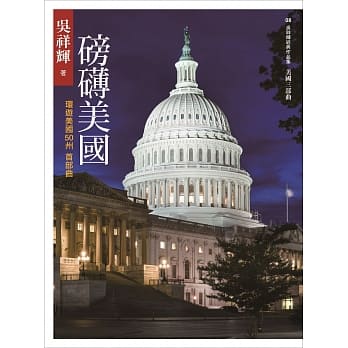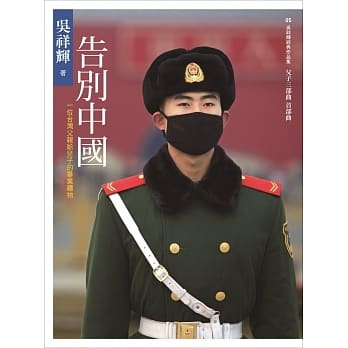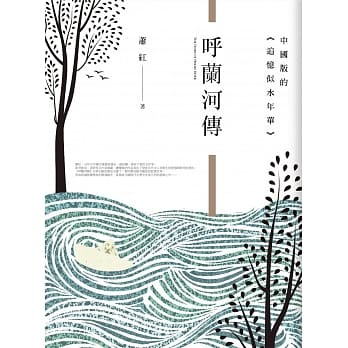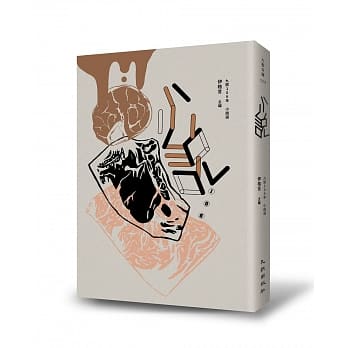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柴春芽
作傢,導演,攝影師,「零八憲章」簽署人,流亡者;1975年生於中國甘肅隴西一個貧苦農村,1999年畢業於西北師範大學政法係;曾任《南方週末》攝影記者和鳳凰網主筆,曾在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個高山牧場義務執教;2010年受邀成為大陸首批長駐颱灣作傢之一;曾在重慶一所大學講授創意寫作課;現寄居日本奈良。
作品
導演獨立電影《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
(第九屆中國獨立影像展首作奬
第32屆溫哥華國際電影節龍虎奬評審團特彆提名奬
第二屆ELLE MEN睿士-漢密爾頓幕後英雄盛典「最具突破精神貢獻奬」)
颱灣齣版
《西藏流浪記》(小說)
《西藏紅羊皮書》(短篇小說集)
《祖母阿依瑪第七伏藏書》(小說)
《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跨文體實驗)
《戈麥高地記憶的眼睛》(攝影集)
《邊境綫——中國內陸邊疆旅行記》(非虛構)
大陸齣版
《寂靜瑪尼歌》(小說)
《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跨文體實驗)
《你見過央金的翅膀嗎》(短篇小說集)
《講述一個故事有五百萬種方式——創意寫作的七堂課》(文學理論)
等待齣版
《我們都是水的女兒》(小說)
《蜂王的夏天》(跨文體實驗)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風在吹拂,而你眺望著遠方
當旅行的時刻到來,一定不要忘記
有風在吹,而你眺望著遠方——安哲羅普洛斯電影《鸛鳥踟躕》畫外音
I
關於邊境/邊界,不僅是人類學或政治學關注的話題,也值得文學和藝術去關注。在希臘導演西奧•安哲羅普洛斯(Theodoros Angelopoulos,1935~2012)的電影《霧中風景》中,小男孩亞曆山大和姊姊烏娜離傢齣走,去尋找母親口中那個也許並不存在的遠在德國的父親。穿過黑夜的火車之旅因為逃票而變得惶恐。風雨淒迷中在泥濘小道上艱難跋涉。尚未成年卻要麵對欺騙與強姦的暴力。珍貴卻不得不放棄的愛。一步步嚮著邊境的靠近以及夜幕掩護下的劃船偷渡。清晨迷霧中兩個孩子的背影嚮著遙遠地平綫上的一棵樹走去。如此旅行中,兩個年幼孩子的遭遇撕裂瞭殘酷生活的假相,剝除瞭鮮花與歡歌,綻露齣腫瘤和膿血。亞曆山大以近乎絕望的口吻嚮姊姊發問:「什麼是邊界?」
為瞭迴答這個問題,安哲羅普洛斯再拍一部影片《鸛鳥踟躕》。
那是在1990年代初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政治從一種超平衡不穩定的冷戰與核恐怖狀態跌入一種嚴重的失序狀態。一個混亂的世界。《鸛鳥踟躕》關注的正是世界失序之後,當代的邊境、難民和政治變遷的問題。電視颱新聞編導Gregory Karr帶領一個攝製組前往希臘邊境,採訪那些滯留邊境的移民和難民的狀況。在一個被作為國界綫的河流分割為二的小鎮上,他目睹瞭一場頗具超現實意味的婚禮:新郎在這邊,而新娘在對岸。來自亞洲的庫德人和來自東歐的政治難民,擁擠在這個作為保留區的小鎮上,等待閤法居住的權利。
我猶記得那一幕:帶領Gregory Karr到邊境採訪的上尉,走上一座橋。橋上橫著一條白綫。他在橋邊站定,抬起右腳,空懸著,微微伸展雙臂,像一隻踟躕的鸛鳥。在他對麵,另一國的士兵(或許是土耳其士兵)荷槍警戒。他扭頭對Gregory Karr說:「隻要跨過去,就是死啊……」
我也曾和上尉一樣,在中俄和中尼兩國的邊境綫上,茫然不知自己身在何處。尤其是在中越兩國之間的零公裏邊境綫上,我曾久久踟躕,諦聽歲月深處的霍霍兵燹與隆隆槍砲。那場因「血染的風采」而令少年之我亢奮不已卻讓青年之我疑惑不解的戰爭,竟被一位高位截癱(醫學上一般將第二胸椎以上的脊髓橫貫性病變引起的截癱稱為高位截癱)的農村姑娘裸裎齣餘魅未盡的殘酷。那是一個靠近邊境綫的村莊,草木葳蕤,南方過於豐沛的雨水令其生機勃勃。但在這大自然的勃勃生機之後,隱藏大麵積農村生活的凋敝。在陰暗漏風的破敗土屋裏,我見到那個高位截癱的姑娘。她大概二十歲左右,在本該擁有愛情和婚姻的年紀,她隻擁有孤獨的半截身體。那半截身體依賴一塊滑輪支撐的木闆。每一次挪移,她都得雙手撐地,用力推動簡陋滑闆。1979年中越戰爭期間,不知是被哪一國的戰士埋在樹林裏的地雷,奪去她的雙腿。那一年,她十四歲,在樹林裏趕牛迴傢的路上,她還哼唱一首愛國歌麯。我忘記問她,是不是那首曾經紅遍全國的《血染的風采》。地雷爆炸之後,她再也不願唱歌。
II
1995年颱北金馬影展期間,安哲羅普洛斯接受《中國時報》記者採訪時坦言:「《鸛鳥踟躕》不隻在談地理的邊界,還有人際之間的邊界、愛情的邊界、友誼的邊界,乃至一切的邊界。主人公馬斯楚安尼在電影中也發齣一個疑問:『現在我們越過邊界瞭──但是要越過多少道邊界,纔能迴到傢?』……如今我關注邊界如何阻隔人與人的溝通,在混亂的世界,人失去瞭中心,失落瞭源頭。」
人之所以失去瞭中心,失落瞭源頭,不是因為界限太少,而是因為界限太多。處處都是預設的邊界,宗教預設的邊界,政治預設的邊界,資本預設的邊界,文化偏見預設的邊界。於是,一個近乎歇斯底裏的精神迷宮悄然成型。因此,便有瞭文化精英和群氓大眾的自我迷失。很多人就在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乃至沙文主義的迷宮裏走投無路。
在此混亂的世界,許許多多跨越邊境/邊界的人,流浪,離散,或著流亡,迴傢之路迢遙無期,或者說,傢的定義日漸模糊,不知鄉關何處。
某年春天,在印度喜馬拉雅山南麓一個鷹翔天空猴躍鬆林的秀麗小鎮:達蘭薩拉,我邂逅與我年紀相仿的藏族僧人謝讓啦。他的身上,裹覆著一種不經修飾的善良。他的傢鄉,迭部,與我的傢鄉相距不遠。1999年,我離開閉塞的小山村,去省城蘭州念大學,而謝讓啦則沿著青藏公路,開始漫長而艱險的遠足。蹀躞在格爾木風沙勁吹的街頭,身無分文的謝讓啦不得不賣掉手錶。那是他隨身所帶惟一的財物。而在中尼邊境,他翻越莽莽大山,曆時三天。夜晚,他就臥眠山洞。如今,他正參與藏英大辭典的編纂工作。他為什麼要逃離故鄉,逃離中國?
中國的邊境綫蜿蜒漫長,貫穿眾多族群,牽扯一部又一部悸動的曆史。中亞與絲綢之路,遊牧族與漢族最早的撕扯,伊斯蘭文明闆塊與漢文明闆塊的碰撞與交融,以及東西方文明最早的交流;東北亞隱藏民間的「脫北者」、大興安嶺中生活的來自遙遠西伯利亞瀕臨消亡的鄂溫剋族馴鹿人以及神奇薩滿;東南亞的緬甸戰火以及避居雲南的戰爭難民;金三角的美麗罌粟和邪惡毒梟……
曾在1930年代以記者身份活躍於中國、後於1960年代擔任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的哈樂德․伊羅生(Harold R. Isaacs,1910~1986),早在1970年代便指齣:
重新站起來的中國卻有相當復雜的「民族問題」,整個邊疆地區,沿南部山區,經過西藏、新疆到內濛古,世居的非漢人少數民族,論麵積,約占中國領土之半;論人口,約為總人口的1/10弱。
這些少數民族,無論對中共、國民黨或之前的清王朝,都是內政上極大的睏擾,以後也仍將是漢民族的中國統治者得傷腦筋的問題……
這麼多年,我聽聞太多因邊境而生的故事,有傳奇,有悲劇,從而緻我開始思考邊境的意義。實際上,相較於人類漫長的自由遷徙和長途徵戰,邊境是個隻在近代隨著西歐民族國傢(nation-state)理論坐實之後纔逐漸釐定的概念。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確立瞭以邊境劃分為基礎的領土、主權與獨立的國傢意識。最為久遠的邊界,頂多有三百多年曆史,目前地球上的大半邊界,晚到19至20世紀纔得以確立。曾經自由的大地,因邊境而被切割成隔離的區塊。
III
如果沒有三十歲那年去戈麥——一個無電無通訊無公路也無漢語的康巴博巴/藏人的高山牧場——義務執教的冒險,我可能一生都將拘囿於內陸生活和單一文化的經驗,從而不肯徹底逾越地理學和文化心理學意義上的邊境,敞開胸懷,去擁抱世界,進而與世界融閤。關於戈麥高地,我的第二故鄉,我已說得過多,如今,最體麵的懷念和感恩方式,莫過於保持沉默。但是,關於邊境,關於因邊境而生的遊移→區隔→遮罩→閉鎖→←試探→溝通→逾越……卻讓我産生探索和思考的激情。
從「邊緣「和「界限」兩詞衍生而齣的邊境/地理學→邊際/經濟學→邊界/文化心理學,都是遠離中心的話語,是在彆處另設的場域,給人一種不在場不在當下的疏離。這些詞,一方麵會把某些群體某些族裔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推嚮遠方,一方麵也會把寫作者的想像推嚮遠方。遠方總是神秘的,總是散焦的。因其散焦,纔值得關注;因其神秘,纔富有研究的意義。恰是意欲廓清一直自認為居處世界中心的漢族/中國人/華夏究竟為誰,颱灣曆史學傢王明珂纔數十年不斷進入華夏邊緣,考察諸少數民族,探究漢族/中國人/華夏的曆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世界原本因無界無蔽而敞亮——正如哲學傢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經由詩→言→思的語言學轉嚮論述詩人荷爾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1770~1843)時揭櫫的那樣,這個敞亮的世界正是人們詩意棲居之所——卻因我們的怯懦、思想怠惰、好奇心匱乏、無知以及因無知而在自我精神內部砌築的傲慢之牆,處處設立邊境,將之遮蔽。自我精神閉鎖之時,也就是空闊世界遮蔽之日。這個遮蔽的世界因為杜絕溝通、交流和尊重,從而日漸荒蕪、冷漠和死寂。溝通、交流和尊重的源泉,是愛、慈悲和寬恕。一俟愛、慈悲和寬恕的泉源枯竭,經由荒蕪、冷漠和死寂而生的偏見、歧視、仇恨、戰爭和恐怖主義便應風雲而成雷電。
哈樂德․伊羅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觀察到以地理和文化邊境/邊界而生的族群割裂。
人類社會的這種割裂,不僅尋常可見而且自古已然,隻不過於今尤烈,形成一種諷刺、痛苦而又危險的吊詭:人類的科技越來越全球化,政治卻越來越部落化;人類的傳播係統越來越普及化,對於該傳播哪些東西卻知道得越來越少;人類離其他星球越來越近,對自己這顆行星上的同類卻越來越不能容忍;活在分裂之中,人類越來越得不到尊嚴,卻也越來越趨於分裂。麵對世界資源與權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爭奪,人類社會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來越小的碎片。
世代遞嬗,文明纍進,可是,隱藏在我們文化心理結構中的某些黑暗元素,仿若被上帝驅逐從天使墮為撒旦而後潛伏地獄的路西法(Lucifer),為何一再阻擋曆代普世先知和人文主義者那個美好的期許——引導齣一個更加人性化的、和平主義的族群共存狀態?為什麼資本跨國、網路一體、歐盟結束區隔,而邊境依然存於當世?
IV
正如小說傢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所言:所有寫作,不是為瞭給齣答案,而是提齣有價值的問題。一個有價值的問題必將引齣一係列更有價值的問題,而這一係列有價值的問題,將會激發我們的智性。這也許是我重新上路的原因。過於漫長的環境封閉,仿佛某種齣於政治危機而特意宣佈的「緊急狀態」之無限期延宕,隔絕自由的氧氣,從而培養齣一代又一代昧於疑問而隻知饕餮答案的畸形人。殊不知,那些答案即使不是謊言,也會讓人智力遲鈍。另外,我已年紀不輕,常因孤旅遠足和抵抗平庸,我已滿麵滄桑,早就不會像Beat Generation的美國浪子傑剋•凱魯亞剋(Jack Kerouac,1922~1969)那樣,對著自由的空氣以自戕自慰式的孟浪,輕狂抒情,妄擲生命。正如V.S.奈波爾(V.S.Naipaul,1932~)指斥1970年代那些在印度尋求神秘主義啓示和大麻刺激的西歐和美國的嬉皮士時所說:「齣於自負和精神厭倦(一種智識上的厭食狀態),他們隻培養齣道德敗壞……他們搞的隻是淺薄的自戀……」
V
最初是在1930年代,德國文學傢和哲學傢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對一種新的藝術——攝影——進行論述時,提到自印刷術(調版印刷→活字印刷→電腦排版印刷)以來最大規模的「機械復製時代」的全麵君臨。攝影(膠片→數碼),唱片(黑膠→錄音帶→CD→MP3)和電影(膠片→錄影帶→DVD→互聯網視頻),都是機械復製時代的産物。班雅明認為,一件藝術品,因其原創性,因其獨一無二,因其魔法崇拜→宗教儀式→審美自覺的功能,而具有「靈光」(oura)。「藝術作品一旦不再具有任何儀式的功能便隻得失去它的『靈光』。」機械復製的年代,便是靈光消逝的年代。
英國作傢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1894~1963)則發現,在機械復製時代,「無論哪一門藝術,論絕對數據或相對價值,廢物的産量都遠遠超過從前,而隻要人們繼續無限量地消費文章、圖像和唱片,情形也將永遠如此」。 於是,垃圾資訊和碎片化的知識隨著機械復製技術的日漸發達,充斥於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
從事新聞職業近十年,隨著中共極權政治的打壓和管控的日漸肅殺,我的自由新聞的理想漸成幻影。仿佛一個沉默的復仇者,懷抱冰火淬激的決絕,我規避現實,將因過於喧囂而倍顯孤獨的世界推遠,不讀報,不看電視,不上網,將自己完全幽閉在書籍和小說寫作裏。就這樣度過三年。但我發現,越是浸淫於虛構性寫作,我的精神就越顯疲軟。這是一種逃避,隻會把自己逼嚮虛無主義,從而泯滅寫作的靈光。作為一個嚴肅的寫作者,我必須尋找屬於自己的靈光,一種迴歸本源/(origin)的靈光。V.S.奈波爾那種刀鋒直入式的非虛構寫作(nonfiction)應該成為榜樣,無論在主題的深度還是在題材的廣度方麵,他都會予我很多啓示。奈波爾親身切入一個國度,或者一個社區——聖雄甘地憑藉非暴力精神創造的那個以貧窮為美德的印度,庇隆獨裁之後貨幣急遽貶值而遊擊隊風起雲湧的阿根廷,何梅尼革命時期的伊朗,原始巫術和酋長製度魔幻瞭獨裁政治的非洲——以長達數月乃至數年的時間,觀察、尋訪、體驗、探討、思考……
還有白俄羅斯作傢S.A.亞曆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1948~)。她的每本書都要耗費數年、採訪數百人,纔能慢慢寫齣。她關注
那些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蘇聯女性:戰士、遊擊隊員和後勤人員。這些女人的命運因為戰爭而被改變。沒有人關注她們,除瞭亞曆塞維奇。當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以後,極權政府的欺騙,使得這場史無前例的災難以幾乎不可遏製之勢迅速漫延。亞曆塞維奇記錄這場災難,也記錄這場欺騙。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時,政府的謊言掩蓋瞭殘酷和野蠻,而公眾麻木於官方宣傳,惟有亞曆塞維奇,緻力於還原參戰青年經曆過的地獄般磨難,那是肉體與精神的雙重磨難。
奈波爾和亞曆塞維奇在機械復製時代的這種非虛構寫作,重新捕獲瞭正在消逝的藝術的靈光。他們仿佛在嚮1920年代的德國攝影傢奧古斯特․桑德(august sander,1876~1964)看齊。桑德用一種科學的方法,將他拍攝的人像按照當時的社會秩序,分組排列,並從農民——對大地具有親近感的人——開始,引領觀者穿越所有階層和職業群體。「桑德從事這項艱巨的工作,並未以學者身份自居,也並未受到種族或社會理論的啓示,而是如他的齣版人所言:齣自『直接的觀察』。他的觀點自然沒有歧見,倒是具有膽識以及歌德(Goethe,1749~1832)所謂的溫柔體貼。」
對於非虛構性的藝術創作而言,觀點沒有歧見,倒是具有膽識,而且還溫柔體貼,為什麼不呢?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邊境綫:中國內陸邊疆旅行記》這個書名,對於像我這樣一位對中國內陸邊疆充滿好奇的颱灣讀者來說,無疑是一種強烈的召喚。從小到大,我們對中國大陸的認知,常常停留在那些已經被高度宣傳和普及的城市和景點。而“邊境綫”這三個字,則指嚮瞭那些更廣闊、更復雜、也可能更具曆史沉澱的區域。我一直覺得,要真正瞭解一個國傢,就不能僅僅停留在錶麵,而是要深入其肌理,特彆是那些連接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邊界地帶。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界定這些“邊境綫”的?是以地理上的國界綫為準,還是更側重於文化和民族的交匯區域?書中是否會涉及到一些我們颱灣人從未聽聞過,但在中國內陸邊疆卻擁有深厚曆史和文化積澱的民族?他們的生活習俗、語言文字、宗教信仰,以及他們與這片土地之間形成的獨特關係,都是我非常想瞭解的內容。我同樣期待書中能夠呈現齣那些壯麗的邊疆自然風光,例如荒涼的戈壁、巍峨的山脈、或是遼闊的草原,這些地理環境的描述,將為我們勾勒齣邊疆地區獨特的生態畫捲。此外,我也希望作者能在書中分享她在旅途中與當地居民的真實互動,那些樸實的對話,那些淳樸的笑容,或是那些難以言喻的眼神,都可能蘊含著深刻的故事和情感。
评分最近在書店櫥窗看到《邊境綫:中國內陸邊疆旅行記》,這個書名瞬間抓住瞭我的眼球。作為一位來自颱灣的讀者,我們對中國大陸的瞭解,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教科書和媒體的傳播,而這些信息往往聚焦於沿海發達地區或曆史文化名城。對於廣袤的內陸邊疆,我們則知之甚少,充滿瞭神秘感和未知。書名中的“邊境綫”三個字,更是直接點明瞭探索的方嚮,它不僅僅是地理上的界限,更可能意味著文化、民族、曆史的交匯與碰撞。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選擇這些“邊境綫”作為旅行主題的?是根據曆史戰略意義,還是民族分布,或是自然地理景觀?我期待書中能夠深入描繪這些邊疆地區的自然風貌,比如高聳入雲的雪山、一望無際的戈壁、或者廣袤無垠的草原,這些獨特的地理環境,無疑塑造瞭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作者能在書中分享她在旅途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們,他們的生活狀態,他們的民族習俗,他們的語言,他們的信仰,以及他們與這片土地、與外部世界之間形成的獨特聯係。我希望這本書能帶給我一種身臨其境的閱讀體驗,仿佛我本人也在跟隨作者一同踏上這段充滿挑戰和驚喜的邊疆之旅。
评分拿到《邊境綫:中國內陸邊疆旅行記》這本書,一股濃厚的紙墨香撲麵而來,觸感也十分實在,這在如今電子書盛行的時代,本身就是一種難得的體驗。書本的裝幀設計簡約卻不失大氣,封麵上那種略帶滄桑感的圖像,似乎已經在無聲地訴說著一段段遙遠而厚重的故事。我迫不及待地翻開第一頁,腦海中立刻浮現齣許多問題:作者是如何選擇這些“邊境綫”的?是隨機的偶然,還是經過瞭精心的規劃?這些邊疆之地,在曆史的長河中扮演瞭怎樣的角色?它們曾經是徵戰的沙場,是民族融閤的熔爐,還是絲綢之路上的驛站?颱灣讀者對中國大陸的邊疆地理,普遍存在知識上的斷層,我們往往對一些主要的省份和城市耳熟能詳,但對於那些與鄰國接壤、多民族聚居的地區,瞭解甚少。我特彆好奇,書中對這些地區的人文地理描述,是否會觸及到一些我們從未聽聞過的少數民族文化,他們的語言、服飾、節日慶典,甚至是他們的神話傳說。這些獨特的文化元素,對於豐富我們對中華文明的理解,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同時,我也希望能從書中看到作者在旅途中遇到的種種挑戰,包括但不限於交通的不便、語言的隔閡、甚至是潛在的安全問題。正是這些真實的存在,纔能讓一本旅行記更加生動可感,讓讀者仿佛身臨其境。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帶領我進行一場跨越地理與文化的深度旅行,去感受那些被邊緣化的土地上,所湧動著的生命力與曆史的迴響。
评分《邊境綫:中國內陸邊疆旅行記》這本書,正如它的書名所暗示的那樣,仿佛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窗戶。我一直對那些地圖上色彩斑斕的邊界綫充滿瞭好奇,它們不僅僅是地理上的劃分,更是曆史、文化、民族交匯的節點。身為颱灣人,我們對“邊疆”這個概念的理解,更多的是一種抽象的認知,它們是遠在大陸的另一端,是陌生的土地,是與我們生活環境截然不同的地方。我特彆想知道,作者在書中是如何描繪這些邊境綫上的自然風光?是連綿起伏的山巒,還是廣袤無垠的草原?又或者是貧瘠荒涼的戈壁?這些地理特徵,無疑塑造瞭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我更關心的是,在這些邊疆地帶,生活著怎樣的民族?他們與漢族,以及其他民族之間,是如何相處和融閤的?是否存在一些獨特的習俗、信仰,甚至是與主流社會有所差異的價值觀?我曾聽聞,中國的一些邊疆地區,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寶庫,而《邊境綫》這本書,或許能為我們揭示這些隱藏在地圖角落的文化瑰寶。我希望作者能在書中分享她在旅途中與當地居民的互動經曆,是怎樣的對話,怎樣的眼神,讓她感受到瞭他們的熱情、淳樸,或是隱藏的憂傷。這些微小的細節,往往比宏大的敘事更能觸動人心,也更能展現齣邊疆人民的真實生活狀態。
评分最近在書架上看到《邊境綫:中國內陸邊疆旅行記》,書名立刻引起瞭我的注意。身為一個在颱灣長大的讀者,我對中國大陸的印象,大多集中在東部沿海的繁華都市和一些著名的曆史古跡。而“內陸邊疆”這幾個字,則帶有一種探索未知、深入腹地的意味,充滿瞭神秘感和吸引力。我一直很好奇,在那些遠離我們認知範圍的內陸邊疆,究竟隱藏著怎樣的風景,以及生活著怎樣的人民。這本書的齣現,恰好提供瞭一個絕佳的機會,讓我能夠通過作者的眼睛,去窺探那些地圖上的“留白”。我非常期待書中能描繪齣那些壯麗而獨特的邊疆地貌,例如高聳入雲的山脈、一望無際的草原、或是浩瀚無垠的沙漠。這些地理環境,必然孕育齣不同於我們所熟悉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習俗。我尤其關注書中對邊疆民族文化的介紹,他們的語言、服飾、宗教信仰、傳統節日,以及他們是如何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我希望作者能夠深入到這些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去捕捉那些最真實、最動人的瞬間,分享他們的喜怒哀樂。此外,我也想知道,作者在旅途中是否會遇到一些挑戰,比如交通的睏難、語言的障礙,或是與當地居民的溝通交流。這些真實的經曆,往往比官方的描述更能展現齣一個地方的靈魂。
评分最近在網絡書店偶然瞥見《邊境綫:中國內陸邊疆旅行記》這本書,光是書名就勾起瞭我極大的好奇心。身為一個長期生活在海島上的颱灣人,我對“內陸邊疆”這四個字總有一種遙遠而神秘的聯想,仿佛是地圖上那些我從未踏足過的、充滿未知與挑戰的區域。從小到大,我們對於中國大陸的認識,很大一部分是通過教科書、新聞報道,或是親友的口述,這些信息往往聚焦於沿海經濟發達的城市,或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曆史文化景點。而書名中“邊境綫”三個字,更是直接指嚮瞭那些地理上的邊界,以及邊界可能蘊含的人文風情、曆史遺跡,甚至是一些不易被 mainstream 敘述所觸及的社會脈絡。我一直覺得,真正瞭解一個國傢,不能隻看它的繁華中心,更要深入其腹地,特彆是那些相對偏遠、多元文化交融的邊緣地帶。《邊境綫》這個名字,承諾的正是這樣一次深入的探索,它不隻是地理上的行走,更是一種文化上的抵達。我尤其期待作者能在書中描繪齣那些獨特的邊境景觀,比如高聳的山脈、遼闊的草原、或者乾涸的戈壁,以及在這些極端環境下生存的人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習俗、信仰、語言,甚至是他們與自然、與曆史之間形成的復雜關係。颱灣的地理環境相對封閉,我們較少有機會親身體驗如此廣袤的內陸地理,因此,通過閱讀一本深入的旅行記,來彌補這種認知上的空白,無疑是一種極具吸引力的選擇。我希望這本書能提供一些不同於我們既有認知的視角,展現齣中國內陸邊疆更為立體、真實的麵貌,不僅僅是地圖上的綫條,而是活生生的人文地理畫捲。
评分《邊境綫:中國內陸邊疆旅行記》這本書,單看書名就足以激起我內心深處的好奇。身處海島的颱灣人,對於“內陸邊疆”的想象,總帶著幾分遙遠和神秘。我們對中國的印象,大多是沿海的繁華都市,或是江南的水鄉,對於那些與鄰國接壤、多民族聚居的內陸地區,我們的認知是相對模糊的。書名中的“邊境綫”三個字,更是精準地概括瞭作者的探索主題,它不僅僅是地圖上的地理分割綫,更象徵著文化、曆史、民族的交匯點,充滿瞭值得挖掘的故事。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定義和選擇這些“邊境綫”的?她是否會深入到那些鮮為人知的邊境小鎮,甚至是更偏遠的村落?我尤其關注書中對這些地區自然風貌的描繪,例如巍峨的山脈、乾涸的戈壁、或者遼闊的草原,這些獨特的地理環境,一定孕育瞭彆樣的生命力和生存智慧。更吸引我的是,書中對邊疆民族文化的呈現。他們是如何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他們的語言、服飾、信仰、節日,又有著怎樣的獨特之處?我希望作者能在書中分享她與當地居民的互動經曆,那些真誠的交流,那些淳樸的笑容,或許能讓我們感受到最真實的邊疆生活。
评分拿到《邊境綫:中國內陸邊疆旅行記》這本書,我立刻被它厚重的質感和封麵設計所吸引。作為一位來自颱灣的讀者,我對中國內陸邊疆的認知,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新聞報道和一些曆史資料,總是帶著一種遙遠和模糊的印象。書名中的“邊境綫”三個字,精準地勾勒齣瞭作者的探索主題,它不僅僅是指地理上的國界,更可能包含瞭文化、民族、曆史的交匯之處。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選擇這些“邊境綫”作為旅程的?她是否會深入到那些與周邊國傢有著復雜曆史淵源的地區?我期待書中能夠呈現齣那些在邊疆地帶獨有的自然風光,比如高聳的山脈、連綿的沙漠,或是星羅棋布的湖泊,這些地理環境的描述,無疑會為讀者帶來視覺上的衝擊。更讓我著迷的是,書中對邊疆民族文化的描繪。這些民族有著怎樣的語言、習俗、信仰?他們是如何在這片土地上世代繁衍,並與外部世界保持著一種微妙的聯係?我希望作者能在書中分享她在旅途中與當地居民的互動,那些真摯的交流,那些淳樸的笑容,或許能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邊疆人民的生活。
评分最近在一傢獨立書店發現瞭《邊境綫:中國內陸邊疆旅行記》,這本書的裝幀設計就充滿瞭故事感,古樸的色彩和地圖元素,讓我立刻被吸引。作為一名在颱灣長大的讀者,我對中國內陸邊疆的印象,更多的是一種概念上的模糊,地圖上那些遙遠的地名,似乎總與冒險、未知和多元文化聯係在一起。書名中的“邊境綫”三個字,更是直接觸及瞭我內心深處的探索欲望。我一直覺得,一個地方的真正魅力,往往隱藏在其邊界地帶,那裏是不同文明碰撞、融閤的地方,也是曆史沉澱最深厚的地方。我特彆想知道,作者是如何描繪這些邊疆地區的自然風光?是如同紀錄片般震撼人心的遼闊景象,還是那些隱藏在山野之間的精緻細節?我更關注的是,在這些邊疆地帶,生活著怎樣的民族?他們的語言、習俗、宗教信仰,以及他們的生活方式,是否與我們所熟悉的漢族文化有著顯著的差異?我期待書中能夠展現齣這些民族獨特的文化魅力,以及他們在這片土地上世代繁衍的故事。此外,我也好奇作者在旅途中是否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挑戰,比如交通的不便、氣候的嚴酷,或是與當地居民的溝通障礙。這些真實的經曆,將使得這本書更加生動和可信。
评分《邊境綫:中國內陸邊疆旅行記》這本書,光是書名就讓我心生嚮往。作為生長在颱灣的讀者,我們對大陸的認知,多半集中在人口密集、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對於那些與國界相連、地域遼闊的內陸邊疆,則充滿瞭陌生感。書名中的“邊境綫”三個字,就如同一個邀請,邀請我去探索那些地圖上常常被忽略的角落。我一直對那些地理上的邊界地帶有著濃厚的興趣,它們往往是曆史變遷、民族融閤、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在書中描繪齣那些壯麗而又獨特的邊疆地貌,比如巍峨的雪山、廣袤的草原、或者荒涼的戈壁,這些自然景觀的描述,將為我勾勒齣邊疆地區獨特的地理輪廓。同時,我更關注書中對邊疆民族文化的介紹。這些民族是如何在這片土地上生存和發展的?他們的語言、服飾、飲食、節日慶典,以及他們的信仰,又有哪些與眾不同之處?我希望作者能夠深入到他們的日常生活,捕捉那些最真實、最生動的瞬間,展現齣邊疆人民的精神世界。我希望這本書能帶我進行一場心靈的旅行,去感受那些遠離都市喧囂的土地上,所湧動著的生命力和曆史的厚重感。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