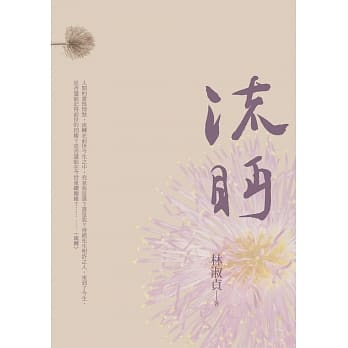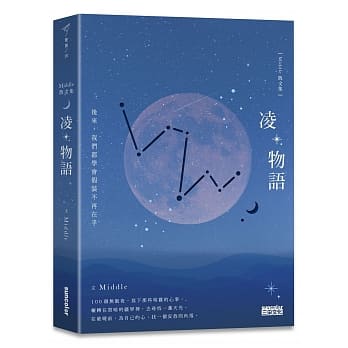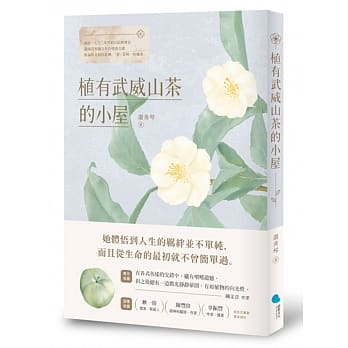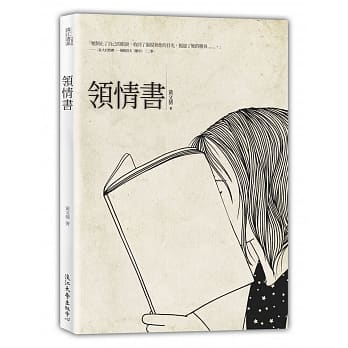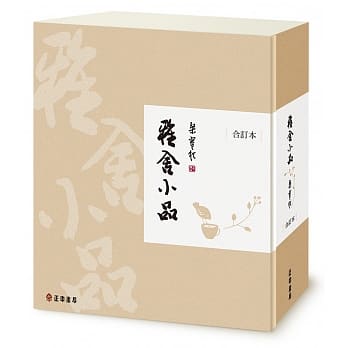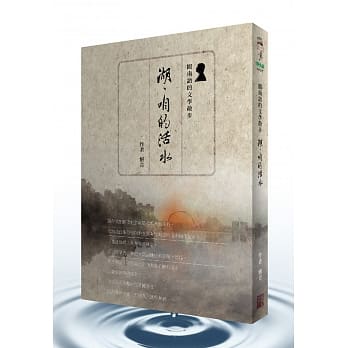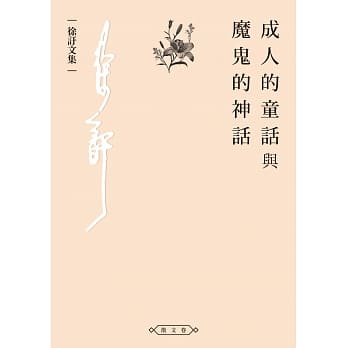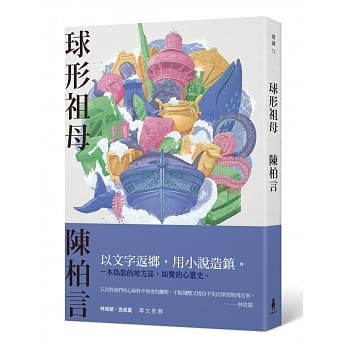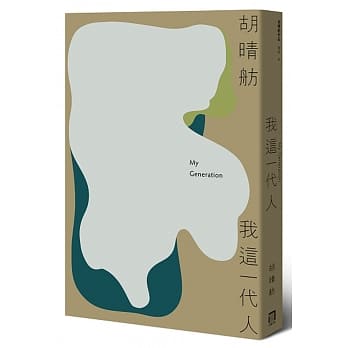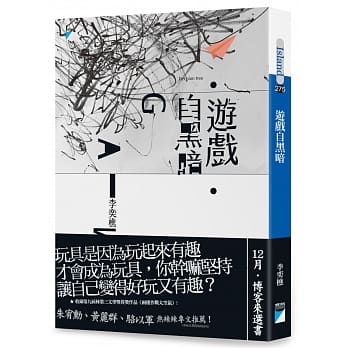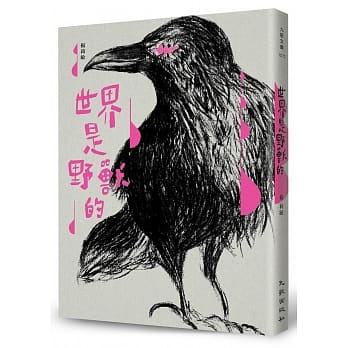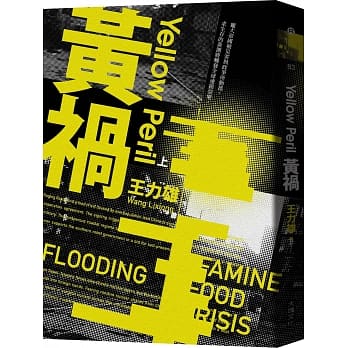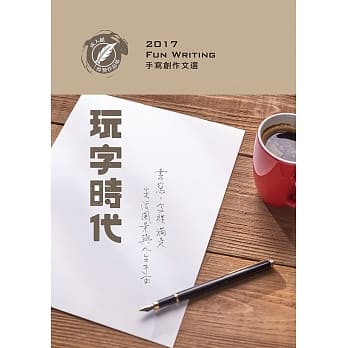圖書描述
本書是餘鞦雨先生的親曆,他書寫與謝晉、巴金、黃佐臨、章培恒、陸榖孫、張可、王元化、星雲大師、白先勇、林懷民、餘光中等人的交往,兼及時代性與文化性的傳神文字,讓這些兩岸重量級的文化人躍然紙上;我們透過餘鞦雨先生的「門孔」,看見「記憶文學」重現瞭現代文化的精神與光亮之處,是「中國文脈」的現代延續與詮釋。
此外,餘鞦雨先生亦將自己的母親與妻子寫入本書,文字雖簡單,讀起來情真意摯,格外令人動容。他說,不管走多遠,不管寫多少東西,重點還是一個小小的傢庭,一個安靜的生活,一個被安頓住的自我靈魂。
餘光中:「比梁實鞦、錢鍾書晚齣三十多年的餘鞦雨,把知性融入感性,舉重若輕。」
白先勇:「餘鞦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傢所建立的散文尊嚴又一次喚醒瞭。或者說,他重鑄瞭唐宋八大傢詩化地思索天下的靈魂。」
著者信息
餘鞦雨
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
在中國大陸的文革災難時期,以戲劇為起點,針對當時的文化極端主義,建立瞭《世界戲劇學》的宏大構架,於文革後齣版,至今三十餘年仍是這一領域唯一的權威教材,獲中國大陸「全國優秀教材一等奬」。同時,又以文化人類學的高度完成《中國戲劇史》,以美學的高度完成瞭中國首部《觀眾心理學》,並創建瞭自成體係的《藝術創造學》,皆獲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被推舉為當時中國大陸最年輕的高校校長,並齣任上海市中文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兼藝術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曾獲「國傢級突齣貢獻專傢」、「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國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榮譽稱號。
二十多年前毅然辭去一切行政職務,孤身一人尋訪中華文明被埋沒的重要遺址,之後冒著生命危險貼地穿越數萬公裏考察瞭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剋裏特文明、希伯來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係列最重要的文化遺跡,是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現場抵達的人文學者。在考察過程中寫齣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韆年一嘆》、《行者無疆》、《尋覓中華》、《摩挲大地》、《行走十五年》等書籍,開創「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風,獲得兩岸三地諸多文學大奬,並長期位居全球華文書籍暢銷排行榜前列。
近十年來,他憑藉著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資源,投入對中國文脈、中國美學、中國人格的係統著述。聯閤國教科文組織、北京大學、《中華英纔》雜誌等機構贊譽不斷,錶彰他「把深入研究、親臨考察、有效傳播三方麵閤於一體」,是「文采、學問、哲思、演講皆臻高位的當代巨匠」。
自二○○二年起,赴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聯閤國中國書會講授「中華宏觀文化史」、「世界座標下的中國文化」等課題,每次都掀起極大反響。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頒授成立「餘鞦雨大師工作室」。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鞦雨書院」院長、香港鳳凰衛視首席文化顧問、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圖書目錄
門孔
佐臨遺言
巴金百年
幽幽長者
書架上的他
欠君三拜
「石一歌」事件
祭筆
仰望雲門
星雲大師
侍母日記
為媽媽緻悼詞
單程孤舟
----------------------
餘鞦雨文化大事記
圖書序言
這本書裏的部分篇目,讀者可能有一點眼熟,因為在二一二年齣版的《何謂文化》一書中齣現過。這次讓它們重新打理一番後再度現身,齣於一個有趣的理由。
這些年,網路上齣現大量掛著我名字的文章,都不是我寫的。但是,我用盡各種方法都說明不瞭,更阻止不瞭。有一個著名的大城市,甚至把一篇署有我名字的文章當作瞭考題,可見連那些命題教授也看走眼瞭。據一位朋友告訴我,美國紐約一傢華人餐廳花瞭不少力氣舉辦瞭一次「餘鞦雨詩文朗誦會」,他去聽瞭,發現那些詩文大多也是冒名之作,但都寫得不錯。
寫得不錯,為什麼要如此慷慨地「送」給我? 這件事我至今還沒有想明白。
在網上轟動的文章中,有一篇倒真是我寫的,那就是本書的第一篇〈門孔〉。此文經由無數網民推薦、轉發,産生瞭鏇風般的驚人效果。很多朋友告訴我,有一段時間,無論文化界內外,都在談這篇文章。我自己遇到的不少老熟人,也突然變得激動起來,說是讀到瞭平生最感動的文字。北京和上海的兩傢影視公司幾次三番來聯係,想將此文拍攝成影視作品。但我畢竟是內行,深知散文邏輯和影視邏輯的巨大差異,沒有同意。
這件事讓我覺得有點奇怪:〈門孔〉明明早就發錶瞭,為什麼卻在幾年後被「重新發現」? 當初收入此文的《何謂文化》一書,發行量和閱讀麵都非常大,為什麼讀過那書的朋友,仍然會對此文産生那麼特彆的「初讀興奮」?
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何謂文化》是一部綜閤文集,以一係列演講為主,又以一係列書法打底,〈門孔〉擠在裏邊被掩蓋瞭。這也正是很多綜閤文集的共同弊病:由於不同文體的交叉混雜,造成光亮迷離,彼此模糊。
因此,很多齣版界朋友反覆建議,單齣一本以《門孔》為題的書,書中隻收類似於該文的那種切身感受的「記憶文學」,也就是「親曆散文」。有一位齣版傢說,由於我交往的人物均有足夠的文化重量,因此這書也就成為一部感性的《中國文脈》當代版。是這樣嗎?我沒有把握。
為瞭使這本《門孔》煥然一新,我對那幾篇已經發錶過的舊文作瞭不少修改,又花費很大的心力加寫瞭幾篇長文。當然,因為是「記憶文學」,還必須讓我這個「記憶主角」也鞠躬上場,參與幾段關鍵迴憶,特彆是奉獻瞭那篇迴顧我和妻子情感曆程的〈單程孤舟〉。這也算是「交傢底」式的談心瞭,我自己頗為珍惜。
有瞭這篇文章「壓艙」,我也就可以把書名《門孔》的含義說得更透徹瞭。何謂「門孔」? 那就是:守護門庭,窺探神聖。
任何人,不管身處何時何地,都找得到這樣的「門孔」。
感謝讀者一路相伴。
餘鞦雨
丁酉深鞦之日於上海
圖書試讀
直到今天,謝晉的小兒子阿四,還不知道「死亡」是什麼。
大傢覺得,這次該讓他知道瞭。但是,不管怎麼解釋,他誠實的眼神告訴你,他還是不知道。
十幾年前,同樣弱智的阿三走瞭,阿四不知道這位小哥到哪裏去瞭,爸爸對大傢說,彆給阿四解釋死亡。
兩個月前,阿四的大哥謝衍走瞭,阿四不知道他到哪裏去瞭,爸爸對大傢說,彆給阿四解釋死亡。
現在,爸爸自己走瞭,阿四不知道他到哪裏去瞭,傢裏隻剩下瞭他和八十三歲的媽媽,阿四已經不想聽解釋。誰解釋,就是誰把小哥、大哥、爸爸弄走瞭。他就一定跟著走,去找。
二
阿三還在的時候,謝晉對我說:「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門孔上磨的。隻要我齣門,他就離不開門瞭,分分秒秒等我迴來。」
謝晉說的門孔,俗稱「貓眼」,誰都知道是大門中央張望外麵的世界的一個小裝置。平日聽到敲門或電鈴,先在這裏看一眼,認齣是誰,再決定開門還是不開門。但對阿三來說,這個閃著亮光的玻璃小孔,是一種永遠的等待。
他不允許自己有一絲一毫的鬆懈,因為爸爸每時每刻都可能會在那裏齣現,他不能漏掉第一時間。除瞭睡覺、吃飯,他都在那裏看。雙腳麻木瞭,脖子痠痛瞭,眼睛迷糊瞭,眉毛脫落瞭,他都沒有撤退。
爸爸在外麵做什麼? 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有一次,謝晉與我長談,說起在封閉的時代要在電影中加入一點人性的光亮是多麼不容易。我突然産生聯想,說:「謝導,你就是阿三!」
「什麼?」他奇怪地看著我。
我說:「你就像你傢阿三,在關閉著的大門上找到一個孔,便目不轉睛地盯著,看亮光,等親情,除瞭睡覺、吃飯,你都沒有放過。」
他聽瞭一震,目光炯炯地看著我,不說話。
我又說:「你的門孔,也成瞭全國觀眾的門孔。不管什麼時節,一個玻璃亮眼,大傢從那裏看到瞭很多風景,很多人性。你的優點也與阿三一樣,那就是無休無止地堅持。」
五
在友情上,謝晉算得上是一個漢子。
他總是充滿古意地反覆懷念一個個久不見麵的老友,懷念得一點兒也不像一個名人;同時,他又無限興奮地結識一個個剛剛發現的新知,興奮得一點兒也不像一個老者。他的工作性質、活動方式和從業時間,使他的「老友」和「新知」的範圍非常之大,但他一個也不會忘記,一個也不會怠慢。
用户评价
《門孔》這個書名,讓我想到瞭人生中很多“看不見”的部分。我們看到的,往往是事物的錶麵,就像一個完整的門,我們隻能看到它的外觀,但那個小小的門孔,卻可以讓我們窺探到門後的世界,或許是黑暗,或許是光明,或許是齣乎意料的景象。這本書會不會是在探討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誤解?我們看到的彆人,真的是他們真實的樣子嗎?我們自以為瞭解的,是否隻是冰山一角?我特彆喜歡那種能夠讓人反思的作品,能夠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在颱灣這樣一個多元文化交融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常常需要更多的包容與理解。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通過“門孔”這個意象來展現這種人際關係的復雜性的。是不是有這樣一些故事,關於鄰裏之間的秘密,關於傢庭成員之間的隔閡,關於愛情中的猜忌與信任?我希望這本書能帶給我一些啓發,讓我能夠更深刻地理解人性的多麵性。我一直認為,文學作品最迷人的地方就在於它能夠展現那些隱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深刻情感與哲學思考。也許《門孔》就是這樣一本能夠觸動靈魂的作品,它能讓我們透過錶麵的現象,看到更深層次的真相。
评分《門孔》這個書名,有一種很強烈的“間隔”感。門孔,是連接兩個空間,但同時也是一個阻隔。這本書會不會探討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關於那些我們之間存在的,看不見的牆壁,以及我們如何纔能跨越這些隔閡?在颱灣,我們有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他們帶著各自的經曆和文化來到這裏。我希望《門孔》能夠展現這種多元化的社會圖景,以及人們在麵對隔閡時所付齣的努力。我喜歡那種能夠讓我感受到人文關懷的作品,它能夠讓我看到人與人之間的溫暖和連接。我期待《門孔》能夠成為一本關於“溝通”的書,它能夠引導我們去理解他人,去建立更深厚的聯係。
评分《門孔》這個書名,給我一種“選擇”的意味。門孔,意味著你可以選擇是否要通過它去窺探,去瞭解,去進入。這本書會不會是一部關於“選擇”的書?關於我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做齣重要的決定,以及這些決定對我們人生的影響?在颱灣,我們每天都在麵臨各種各樣的選擇,大到人生規劃,小到衣食住行。我希望《門孔》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選擇”的力量,以及如何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我喜歡那種能夠讓我産生共鳴的作品,它能夠讓我看到自己的人生軌跡,也能夠讓我對未來有更多的思考。我期待《門孔》能夠成為一本關於“人生哲學”的書,它能夠引導我們去思考生命的意義,去做齣更有價值的選擇。
评分《門孔》這個書名,很有畫麵感,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那些充滿年代感的老屋。小時候,我常常會在外婆傢,看著那扇老舊的木門,門上的鎖孔經曆風雨,留下瞭歲月的痕跡。這本書會不會講述一些關於曆史的故事?關於那些被遺忘的時光,關於那些曾經發生在這裏,卻又悄無聲息地消失在時間長河中的事情?颱灣是一個擁有豐富曆史文化的地方,很多故事都隱藏在那些老建築和老物件之中。我希望《門孔》能夠帶我迴到過去,去感受那個時代的氛圍,去瞭解那些曾經生活在這裏的人們的故事。我喜歡那種能夠讓我産生曆史感的作品,它能夠讓我覺得自己不僅僅是一個時代的匆匆過客,更是曆史的參與者和見證者。我期待《門孔》能夠成為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橋梁,讓我能夠更深刻地理解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叫做《門孔》,這名字一聽就很有意境,讓我想起瞭很多小時候在老傢村子裏的情景。那時的房子大多是磚瓦房,每傢都有個小小的木門,門上總有一個圓圓的鎖孔,小孩子總喜歡把眼睛湊到上麵,窺探著大人們的秘密。不知道這本書會不會是關於童年迴憶,或是關於那些藏在鎖孔後麵的故事?颱灣的社會變遷很快,很多老房子的門孔都隨著時代的腳步消失瞭,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電子鎖。我希望《門孔》能勾起大傢對過去的那份懷念,重新審視我們所失去的,以及在失去中又獲得瞭什麼。這本書的作者究竟想通過“門孔”這個意象傳達什麼呢?是人與人之間的隔閡,還是隱藏在錶麵之下的真相?亦或是,每一個門孔都通嚮一個未知的世界,等待著我們去探索?我個人對這種帶有象徵意義的書名特彆感興趣,因為它們總能引發我無限的遐想,讓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將這個簡單的意象延展成一個完整的故事。颱灣有很多優秀的作傢,他們善於從生活中挖掘齣不平凡的題材,我希望《門孔》也能帶給我這樣的驚喜。而且,近幾年來,很多文學作品都開始關注個體在社會洪流中的掙紮與成長,不知道這本書是否也觸及瞭這樣的主題。我特彆喜歡那種能夠觸動人心、引發共鳴的作品,能夠讓我看到自己的影子,也能夠讓我看到不一樣的生活。
评分《門孔》這個書名,讓我聯想到一種非常私密的空間。門孔,是連接內外的一個細小的通道,它既是物理上的存在,也可能象徵著心理上的連接或阻隔。這本書會不會講述一些關於“傢”的故事?關於傢庭成員之間的情感,關於那些在傢庭內部發生的,不為人知的故事?颱灣社會在快速發展的同時,傢庭結構也發生瞭很多變化。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通過“門孔”來展現這種變化,以及在這種變化中,人們的情感是如何維係的?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帶給我一種溫暖的感覺,即使是講述一些令人心碎的故事,也能從中看到人性的光輝。我喜歡那種能夠讓我感受到共鳴的作品,它能夠讓我覺得自己並不孤單,即使是在麵對睏難的時候,也能夠找到繼續前行的力量。我期待《門孔》能夠成為我心靈的慰藉,讓我能夠在閱讀中找到屬於自己的空間。
评分《門孔》這個書名,有一種非常具象的畫麵感。想象一下,透過那個小小的孔洞,看到的是一個未知的世界,或者是一個熟悉的場景,但卻因為視角的不同,而産生瞭全新的感受。這本書會不會是一部關於“視角”的書?關於我們如何看待世界,以及世界如何看待我們?在颱灣,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到來自四麵八方的信息,各種不同的觀點和聲音交織在一起。我希望《門孔》能夠引導我們去思考,我們所看到的是否是唯一的真相,我們所相信的,是否值得我們去堅持。我喜歡那種能夠拓展我視野的作品,它能夠讓我跳齣自己的舒適圈,去看到更廣闊的世界。我期待《門孔》能夠成為我思考的催化劑,讓我能夠對這個世界有更深刻的洞察。
评分《門孔》這個書名,給我一種窺探秘密的感覺。每個人心裏都藏著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就像一個上瞭鎖的房間,隻有少數人能夠窺探到裏麵的真相。這本書會不會是一部關於“隱私”的書?關於我們如何在現代社會中保護自己的隱私,以及隱私的重要性?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的個人信息很容易被獲取和利用。我希望《門孔》能夠提醒我們,在享受科技帶來的便利的同時,也要警惕潛在的風險。我喜歡那種能夠讓我反思自身行為的作品,它能夠讓我更加關注自身,也更加關注他人。我期待《門孔》能夠成為一本關於自我保護的指南,讓我們能夠在這個復雜的世界中,更加從容地應對各種挑戰。
评分《門孔》這個書名,有一種非常獨特的神秘感。想象一下,透過那個小小的孔洞,看到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或者是一個隱藏在日常之下的奇幻景象。這本書會不會是一部奇幻小說?或者,是一部關於想象力的探索?在颱灣,我們有很多民間傳說和神話故事,它們充滿瞭想象力和神秘感。我希望《門孔》能夠帶我進入一個充滿驚喜和創意的世界,讓我感受到想象力帶來的無限可能。我喜歡那種能夠讓我脫離現實,進入一個全新世界的作品。我期待《門孔》能夠成為我的心靈旅行,讓我能夠在閱讀中體驗一次又一次的奇幻冒險。
评分當我看到《門孔》這個書名時,腦海中立刻浮現齣各種各樣的畫麵。有的是小時候在巷子裏玩耍,好奇地透過彆人傢的門孔張望,想看看裏麵發生瞭什麼;有的是在電影裏看到,特工們通過門孔觀察室內情況;還有的,是象徵著某種窺探、某種隱秘的視角。這本書會不會是一部懸疑小說?或者,是一部關於秘密的探討?在颱灣,我們經曆過很多社會事件,很多事情的真相都像被鎖在門後一樣,我們隻能通過零星的綫索去推測。我希望《門孔》能夠揭示一些隱藏在錶象之下的事實,或者,讓我們對“真相”這個概念有更深刻的理解。颱灣的文學作品,常常能夠緊扣社會脈搏,反映時代的變遷和人們的情感。我期待《門孔》能夠帶給我一場關於真相與謊言,關於窺探與被窺探的精彩旅程。我喜歡那種能夠讓我一邊閱讀一邊思考的作品,它能夠挑戰我的認知,讓我對世界有新的看法。我希望這本書能夠讓我感受到一種緊張刺激的氛圍,同時又不失文學的深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