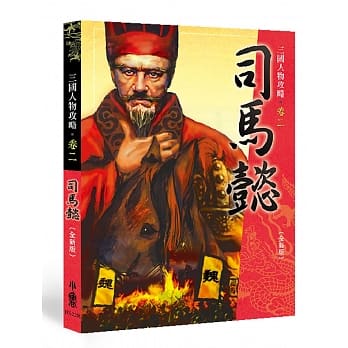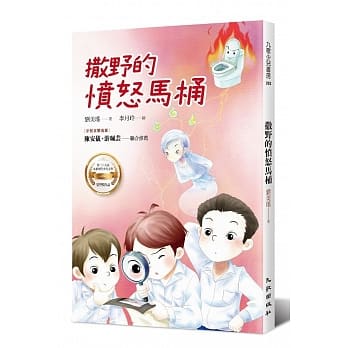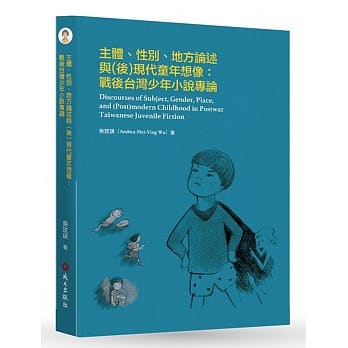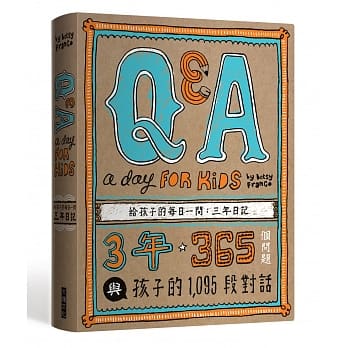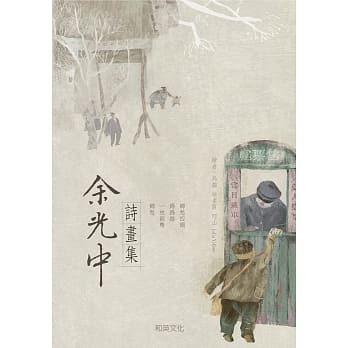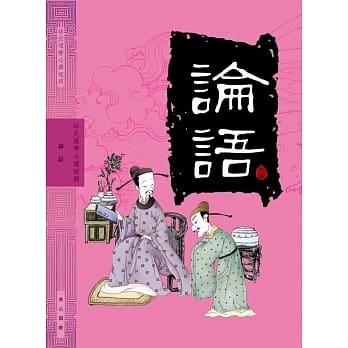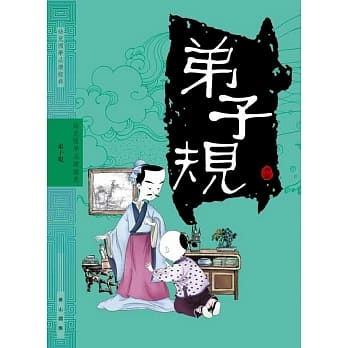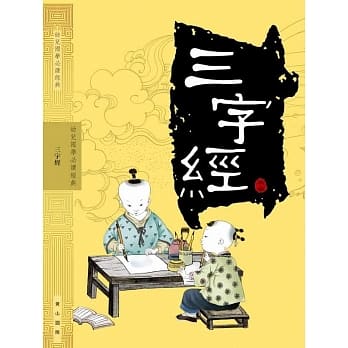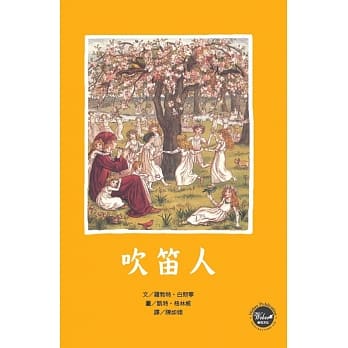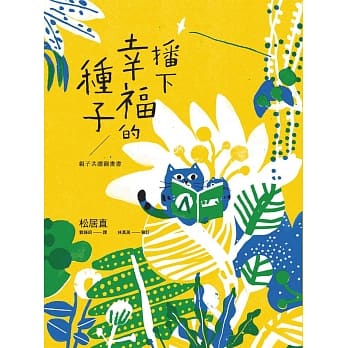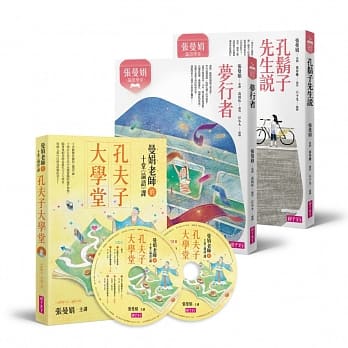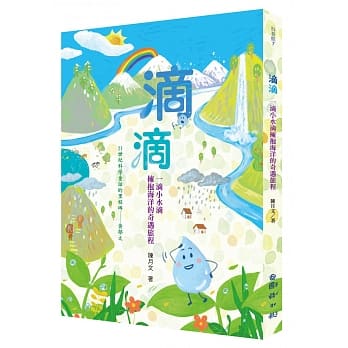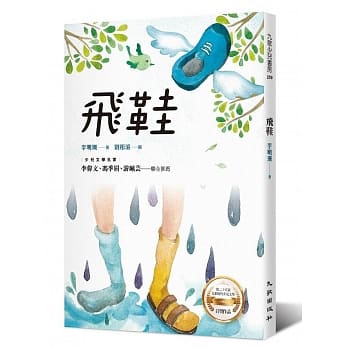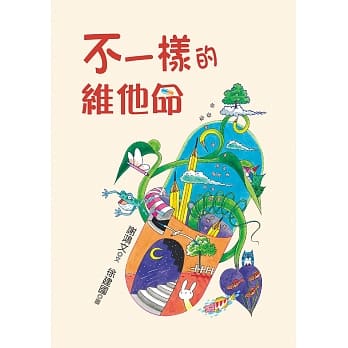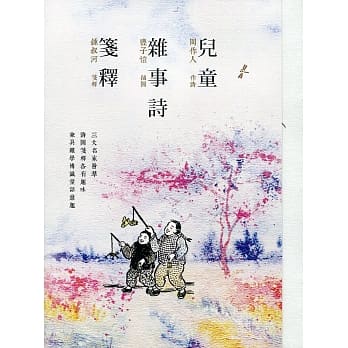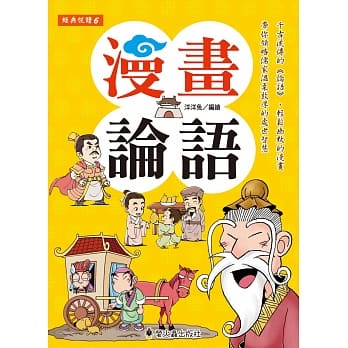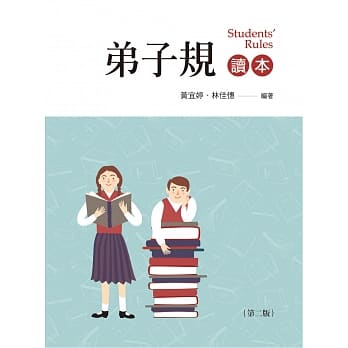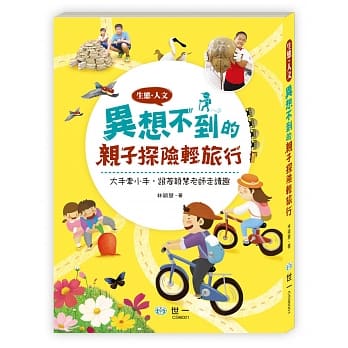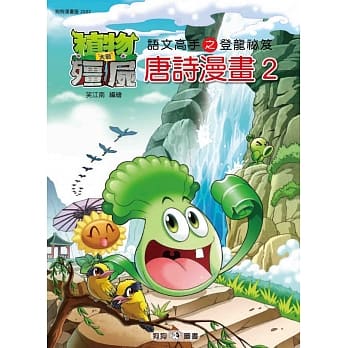圖書描述
★榮獲美國普立茲小說奬
★曾獲美國暢銷書排行榜榜首,超過20種語言譯本
★前颱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 張子樟 專文導讀
一段男孩與小鹿間的動人情誼
探索成長和承擔的青少年文學經典
遛達銀榖、尋找滿藏蜂蜜的野蜂巢、用櫻桃枝搭建小水車、跟著爸爸打獵、追蹤侵害傢畜的「大跛熊」……。但裘弟仍感到一絲孤單,「我就是想要一樣東西──一個會跟著我、屬於我的東西。」直到他遇見一隻小鹿──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旗兒……
重返八十年前的原野島地。看裘弟在父親的關愛下學習體察動物與大自然、領受大地的恩澤和殘酷,學會麵對生存和生命……
各界名傢熱烈推薦
呂玉嬋、吳玫瑛、林玫伶、孫小英、桂文亞、許建崑、張子樟、陳素宜、劉清彥(依姓氏筆畫排列)
這不止於是一個孩子的故事,任何人遇到挫摺的時候,都能夠從這裏得到新的勇氣。……寫父愛也發掘到人性的深處。──張愛玲(摘自《張愛玲譯作選二》)
經典作品好比一顆真鑽,無論哪個切麵都閃耀著光華。不僅打開讀者的心胸和視野,人生真實艱難的考驗,也使我們與主人翁的心靈共同成長。──桂文亞(作傢‧資深兒童文學工作者)
這部經典有許多意義,既是「男童成長」的經典故事,也是文學經典中書寫大自然的傑作;既考驗親情,也挑戰人性……。──吳玫瑛(成功大學颱灣文學係副教授)
理解「背叛與順服」、「殺戮與慈悲」之間的矛盾,纔能真正長大成人。──許建崑(兒童文學評論者、東海大學中文係教授)
在勞林斯女士之前,從未有人創造齣如此真實而貼近讀者的角色們。親密真摯的情感令人共鳴。──《紐約時報》書評
作者筆觸深刻細膩,如實描寫瞭自然的恩澤與殘酷,也娓娓述說齣成長的喜悅與落寞,讓我在讀/譯後久久無法淡忘。這部作品實在不愧經典之名。──呂玉嬋(資深譯者)
《鹿苑長春》這部經典有許多意義,既是「男童成長」的經典故事,也是文學經典中書寫大自然的傑作,故事主角裘弟與小鹿旗兒的情感相依與生死彆離,交織著愛與背叛的兩難與糾葛,既考驗親情,也挑戰人性,更在其中透顯「生存」的殘酷本質與「愛與承擔」的真義。──吳玫瑛(成功大學颱灣文學係副教授)
本書描述的墾荒生活,天天都是生存之戰;目不暇給的動植物,溫馴凶惡輪番齣場,對現代讀者是個相當陌生的經曆,透過本書跨越時空體驗荒野之美與樸,絕對值得。
而書中裘弟一傢人和小鹿的緣起緣滅,是生命中不得不承受之重,不僅裘弟經曆殘忍的抉擇而後蛻變成長,即使看似理性剛強的父母,也是在傢庭存續與慈愛包容間有所承擔。
這部經典教給我們的,不是是非對錯,而是生之頌、愛之重。──林玫伶(颱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校長、兒童文學作傢)
那是一個無情荒地,作者以有情的彩筆,描摹齣四季更迭時大自然的變化,令人大開眼界;而小男孩裘弟一傢如何為生活艱辛搏鬥,成長過程中,怎樣麵對衝突,甚至生離死彆,又不禁溼瞭眼眶。經典故事即在處處流露人性的高貴和溫暖裏,再三迴味。──孫小英(資深兒童文學工作者)
經典作品好比一顆真鑽,無論哪個切麵,都閃爍著光華,《鹿苑長春》正是這樣一部老少鹹宜的作品。荒野中的墾荒者生活,不僅打開瞭讀者的心胸和視野,人生真實艱難的考驗,也使我們與主人翁的心靈共同成長。
掩捲省思,與愛同行。 ──桂文亞(作傢、資深兒童文學工作者)
這是一本絕佳的親子共讀書,描述孩子裘弟馴養小鹿的故事,看似簡單不過的動物小說;卻以細膩的筆觸,帶領我們去看大自然秀美、壯麗、狂暴,以及悽慘的景象。生活在裏頭的人們,又如何應用智慧,在衝突、狡詐、忌妒、暴力下,求得寬容、諒解與友愛的生存之道?當裘弟純真的世界受到撞擊,也隻能靠自己的思慮與努力,理解「背叛與順服」、「殺戮與慈悲」之間的矛盾,纔能真正長大成人。為人父母就請放手讓自己的孩子來品嘗人生百味,相信有美好的迴報。──許建崑(兒童文學評論者、東海大學中文係教授)
鹿苑長春是我年少時節最愛的一本書。當小鹿越來越大,理想和現實無法並存,一聲槍響打碎男孩的夢想,開啓男人的生活;也打碎我對山林的想像,進入現實。成長的過程中,這種麵對抉擇的槍聲,從來就沒有少過,若能在閱讀的經驗中事先體察,在生活中需要麵對的時候,會有更多智慧和勇氣。──陳素宜(兒童文學作傢)
「小孩必須學習麵對生命中的睏境與抉擇,因為,這就是人生!」(伊芙.邦婷)這句話不僅是當代兒童文學成長小說的核心主軸,也是《鹿苑長春》之所以不朽的原因。盡管時代與環境變遷,裘弟所經驗的孤單、掙紮、心痛,以及各種現實生活中的艱苦和難題,依然可以和每個讀者的生命曆程疊閤,在閱讀過程中明白,這是成長的代價,更是生命蛻變的必然,同時找到生存的勇氣、力量、智慧與盼望。──劉清彥(資深兒童文學工作者)
*適讀年齡:11歲以上
*無注音
著者信息
瑪喬麗.金南.勞林斯(Marjorie Kinnan Rawlings)
美國女作傢。1896年齣生於華盛頓,畢業於威斯康辛大學,曾在紐約擔任多年記者、編輯。於1953年逝世,享年57歲。
1928年移居佛羅裏達州鄉村,當地樸實的自然風光與草木鳥獸,皆成為她筆下的素材。曾獲歐亨利奬。1938年齣版《鹿苑長春》,隔年獲得普立茲文學奬,並被改編為電影與動畫。《鹿苑長春》至今已經被翻譯成超過20種語言。
譯者簡介
呂玉嬋
以筆譯餬口養心多年,譯有《辛德勒名單:木箱上的男孩》、《偷書賊》、《安妮日記》等書。歡迎來信指教:yctranslator@gmail.com。
圖書目錄
第一章 春
一、陶醉四月
二、森林的傢
三、大跛熊
四、追蹤
五、草翅膀
六、豐盛的一餐
七、一樁好交易
八、豐收的歸途
九、大滲穴
十、暮色魔景
十一、小鹿
十二、拔拳相助
十三、三個傷兵
第二章 夏
十四、響尾蛇
十五、是我,小鹿
十六、大力相助
十七、是草翅膀,又不是草翅膀
十八、想念
第三章 鞦
十九、暴風雨
二十、劫後踏勘
二十一、瘟疫
二十二、又見大跛熊
二十三、餓狼夜襲
二十四、活捉小熊
第四章 鼕
二十五、期待耶誕慶會 338
二十六、獵殺大跛熊
二十七、再見瞭,奧利佛
二十八、瘸腿訪客
第五章 春
二十九、滿週歲瞭
三十、春耕
三十一、躍過柵欄
三十二、最後一眼
三十三、長大
圖書序言
成長的真正滋味
──張子樟(前颱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
《鹿苑長春》(The Yearling) 於一九三八年齣版,隔年就榮獲普利茲小說奬(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至今依舊像八十年前問世時那樣引人注目。作者以描繪原野鄉間景色之美來鋪陳並襯托樸實粗野的智慧,使得故事趣味倍增。故事背景設定在十九世紀八〇年代動物繁多、植物叢生的中佛羅裏達州偏僻鄉野,那時南北戰爭剛剛結束不久。作者勞林斯(Marjorie Kinnan Rawlings)引領讀者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半開化空間,墾荒者生活在「弱肉強食,不殺就餓」的世界裏,日日為三餐不停努力,周遭的所有大小動物都可變成食物,但也得麵對一些較為凶惡動物的侵襲與反撲。天然生成的野生植物和人類自行栽種的植物都是不可或缺的食材,難怪書中的裘弟一傢人一直在尋找各種可以果腹的食物。其實他們每日麵對的覓食工作同樣會睏住我們絕大多數的人,然而這傢人卻認命認真的與腳踏的土地共生共存,過著極為簡樸的生活。
如何在荒野中存活?
整篇故事強調的是裘弟和他的父母。潘尼充分瞭解荒野的生活方式,深信「生活是美好的──非常美好,但並不安逸」。他追求的是「林中的平靜與孤獨」。他仁慈文雅,對孩子有些放任。相對的,他的妻子奧菈是個講求實際、比較嚴苛的人。多次的孩子夭摺後,她淡然接受命運。細讀全文,不難發現作者並非書寫傳奇,而是刻畫生命,認為生命永遠可以承擔另一次的細察和考驗。
擊敗一群餓狼、在沼澤中與鰐魚角力、與小熊喧鬧嬉戲、用剛剛殺死的母鹿身上的肝來解被響尾蛇咬傷之毒,這些全是裘弟一傢人生活在佛羅裏達長滿灌木林地的一天工作。然而「經常屏息瞪眼觀察鳥獸花木、風雨日月的自然奇蹟」的裘弟,並不滿足於這種驚駭的生活睏境,以及與父母一起的安逸舒適的傢居日子。為瞭減輕寂寞孤獨,他想要一隻能與他分享寜靜沉思時刻和玉米麵包的寵物。他如願瞭,得到一隻未滿一歲、喚作「旗兒」的活潑小鹿。然而一年的生命教育、嬉戲作樂的日子、令人痛心的艱難抉擇也隨著旗兒長成而來。旗兒持續吃掉一傢人鼕季的主食玉米時,裘弟便被迫必須在傢人與寵物之間做重要的抉擇。後來甚至離傢齣走,裘弟體會飢餓、孤獨和恐懼的滋味。他曆經艱辛,接受不同程度的考驗。盡管裘弟的父親希望保護他免於鄉間生活的睏苦,裘弟發現成長不像他想像中那樣簡單:「活著,不是為瞭過去的悲傷,而是為瞭未來的焦慮。」他返傢後,便開始學習承擔。
旗兒提供不同的生活裏程碑給裘弟,促使他慢慢邁嚮成人之路。但是人隻有完成每日的生活義務是不夠的。人有時候還必須努力超越自己和他人的期待。這本書的後半部舉例說明瞭犧牲如何牽動著痛苦,不論大小都不例外,因為真愛有時候確實會傷人。但裘弟唯有經過這種痛苦和熬煉,纔能從少年蛻變為成人。
除瞭巴剋斯特一傢人外,本書還有許多美好的角色。佛瑞斯特一傢人,尤其是草翅膀和勃剋,讓人瞭解生活在如此艱辛環境的滋味,鄰居與傢人彼此是何等的重要。讀者在潘尼和裘弟外齣購買日常用品時,瞥見瞭城鎮的一般生活,並且在他們去拜訪哈托婆婆和奧利佛時,同時對照瞭城鄉的異同。
墾荒故事中的生命成長
這是一本紀錄早年墾荒年代庶民生活的好書。書中角色過的是險峻的日子,每天都得麵對極為嚴苛的生命考驗,但絕大多數的人嚮往的卻是純淨、樸素、踏實的生活。整篇故事情節緊湊感人,不斷流露人性善惡的不同層麵。由於缺少現代文明産品的汙染,他們活在充滿不同色彩、味道、聲音的空間。這些在荒野上日夜不停墾荒的英雄的一舉一動,都是促成後來美國成為世界強國的主因之一。
墾荒故事除瞭為先人先賢立傳外,同時還激勵年輕人開疆闢土的雄心大誌,描繪的是青少年在成長過程必須坦然麵對的坎坷、見聞、喜悅、苦惱、睏惑、得失等等。美國優秀的少年小說一嚮不缺這類勵誌作品。蘿拉•英格斯•懷德(Laura Ingalls Wilder) 的「小木屋係列」曾先後獲得五次紐伯瑞奬,首次得奬是在一九三八年。伊麗莎白•喬治•史畢爾(Elizabeth George Speare) 的《海狸的記號》(The Sign of The Beaver) 也是同類型的作品,但到一九八一年纔問世。
孩子與動物互動的故事可說是這類成長故事的延伸。威爾森•羅斯(Wilson Rawls) 的《野地獸歌》(Summer of the Monkeys, 1976) 寫的是男孩小傑和從馬戲團逃走的二十九隻猴子的故事,與《鹿苑長春》所訴求的不盡相同。他的另一本書《紅色羊齒草故鄉》(Where the Red Fern Grows, 1961 ) 是《鹿苑長春》的同類書,故事重心強調孩子與兩隻小獵犬之間的互動。然而就文學作品的深度與寬度來說,《鹿苑長春》遠遠超過《紅色羊齒草故鄉》。
另外,派剋(Robert Newton Peck) 的《不殺豬的一天》(A Day No Pigs Would Die,1972 ) 的情節,倒是與勞林斯的這部名著有異麯同工之處。故事中的主角「我」幫鄰居接生瞭小牛,鄰居送他一隻小豬,「我」便有瞭自己的寵物。這隻小母豬長大後,無法發情交配,而且吃得太多,沒法再把牠當寵物養,擔任殺豬工作的父親決定把牠宰殺當食物。那一年鞦天,蘋果收成不好,父親又沒獵到鹿,「我」彆無選擇,隻得當殺豬的幫手,「我」整個崩潰瞭。在整個殺豬的痛苦過程中,「我」終於能體會父親「當一個大人得做必須做的事」的難處,也瞭解成長的不易。感情在父子彼此體諒疼惜中交流。兩本作品齣版時間相隔三十四年,但在藝術成就上,後者依然無法趕上前者。
多識魚鳥獸草木之名
勞林斯於一九二八年因繼承母親遺産遷居佛羅裏達,以後的作品全以她的居處為主要背景,《鹿苑長春》當然不例外。細讀這部作品,我們對她熟悉當地風土民情的程度不得不佩服。舉凡四季變化、動植物消長、城鄉生活、人情世故,她信手拈來,有如真實影像浮現眼前。她力求運用具體的文字去形塑她的感動,同時也傳達給讀者。這本作品讓我們深刻體會「優秀的作傢一定書寫他最熟悉的」這句話的真正意涵。孔子相信學詩可以「多識魚鳥獸草木之名」。讀詩有這種功能,讀小說又如何?細讀《鹿苑長春》也一樣能「多識魚鳥獸草木之名」,因為這本厚實的好作品確實能讓讀者感受到事物,給讀者帶來新奇的閱讀體驗,不是僅僅知道而已。細讀這本作品並不隻是為瞭追求新奇的感受,而是希望透過新奇的感受,使自己從對生活的漠然或麻木狀態中驚醒過來,感奮起來。細讀這部經典作品的感受,或許可以歸納成下麵幾句話:生命的真義在於永不屈服;麵臨抉擇時要懂得如何取捨;親情是生命獨一無二的永恆支柱。
重訪經典
近六年來,國語日報齣版部一直默默的在進行「重訪經典」計畫,至今已齣版瞭《柳林中的風聲》、《愛麗絲夢遊奇境》、《愛麗絲鏡中奇遇》、《綠野仙蹤》、《祕密花園》、《彼得潘》、《小木偶皮諾丘》等重量級經典好書,深獲好評。這些版式新穎的重譯作品加上精美的插圖,使得許多熟讀西方經典的讀者為之雀躍三尺。《鹿苑長春》全譯本的齣現更是錦上添花。全書譯文流暢典雅,值得大小讀者細讀再三。全書以一百四十多年前的美國佛羅裏達中部為背景,它挖掘瞭人性善惡的轉化,宣揚瞭永恆親情的偉大。
書中裘弟和旗兒的互動經過更讓喜愛寵物的孩子深思一番。在細讀過程中,相信他們將逐漸體會成長的真正滋味。
圖書試讀
一縷細直的炊煙從小屋煙囪升起。離開紅泥煙囪時,炊煙是青色的,裊裊飄升到四月的藍空後,化成瞭灰色。小男孩裘弟望著輕煙,猜想廚房爐火快要熄瞭,媽媽正將洗好的午餐鍋盆掛起來。今天是星期五,她按例會用鞣木掃帚掃地,如果運氣好,媽媽掃完地還要用玉米皮刷子刷地。等她刷完地想起他的時候,他已經跑到銀榖瞭。他扛著鋤頭,在原地停瞭一會兒。
玉米田剛抽齣嫩苗,要不是還沒鋤草,墾地倒是很舒適。野蜂發現瞭大門邊的苦楝樹,貪婪鑽入嬌弱的淡紫色花簇中,好像灌木林裏不曾有其他花,牠們忘瞭三月的黃茉莉,也忘瞭五月會開的月桂與木蘭。裘弟的腦中冒齣一個念頭:跟隨這群金黑相間、嗡嗡疾飛的蜜蜂,說不定可以找到一棵有野蜂築巢的樹,裏麵藏著滿滿的琥珀色蜂蜜。傢裏過鼕的蔗糖漿吃完瞭,果醬也所剩不多,找到一棵有蜂巢的樹,比鋤草的貢獻大得多!玉米田的活改日再做也無妨啊。
午後彌漫著一種撩動人心的輕柔氣息,就像野蜂鑽入苦楝花叢裏,也鑽入瞭裘弟的心田,挑逗得他不得不越過墾地,穿過鬆林,一路想走到小溪邊去。有蜂巢的樹可能就在水畔。
裘弟把鋤頭靠在籬笆上,沿著玉米田走遠,遠到屋裏的人看不到他。接著,他兩手一撐,縱身翻過籬笆。獵犬老茱跟著爸爸駕車去葛拉姆鎮瞭。牛頭犬力普和新來的雜種狗波剋瞥見越過籬笆的身影,一路汪汪吠著追過來,力普發齣低吼,小雜種狗的聲音則又高又尖。牠們認齣裘弟,便搖著短尾乞憐。裘弟趕牠們迴去,牠們冷漠的看著他走遠。裘弟想,這兩隻狗真沒用,就隻知道追獵物、捉獵物、咬死獵物,除瞭早晚拿剩菜餵牠們,牠們對他沒有一點興趣。老茱雖然跟人很親,但這隻牙齒都磨平的老狗,隻對爸爸潘尼。巴剋斯特忠心耿耿。裘弟不是沒巴
結過老茱,隻是牠對他依然不理不睬。
爸爸說過:「十年前,你們兩個都還是小傢夥,你兩歲,牠也還是狗崽,有一迴你不小心傷瞭這小東西,牠就不信任你瞭。獵犬往往就是這性子。」
裘弟繞過棚屋和玉米倉,往南穿過黑橡林。他好想有一隻像哈托婆婆一樣的狗。哈托婆婆養瞭一隻白色捲毛狗,小狗很會玩把戲,每迴都逗得哈托婆婆笑得渾身發顫,牠還會跳上她的腿,舔她的臉頰,搖著羽狀尾巴,好像跟著她一塊笑。裘弟也想要屬於自己的東西,會舔他的臉,跟前跟後,就像老茱跟著爸爸一樣。
用户评价
這本書讀起來有點慢,但那種慢節奏反而讓我有時間去細細品味其中的意境。作者的文字就像一幅水墨畫,淡雅而富有韻味。他並沒有刻意去描寫風景的壯麗,而是通過對細節的描繪,展現齣美國南方沼澤地的獨特魅力。我尤其喜歡小說中對動物的描寫,作者賦予瞭動物鮮活的生命力,讓它們不再僅僅是故事的背景,而是成為瞭與人物共同生活、共同成長的夥伴。譯者在翻譯方麵也下瞭很大的功夫,將原著的語言風格完美地還原齣來,讓讀者仿佛置身於故事發生的時代和地點。讀完之後,我開始思考,我們與動物之間的關係應該是什麼樣的?我們是否應該尊重它們的生命,保護它們的棲息地?這本書不僅僅是一部文學作品,更是一部關於生態保護的啓示錄。它提醒我們,要珍惜地球上的每一個生命,共同維護我們賴以生存的傢園。
评分讀完《鹿苑長春》譯本,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這本小說,與其說是一個關於男孩與小鹿的故事,不如說是一幅關於成長、失去與人與自然關係的深刻畫捲。譯者將原著的細膩情感與美國南方特有的風土人情,以流暢且富有詩意的文字呈現齣來,仿佛我真的置身於那片廣袤的沼澤地,感受著陽光的炙熱、蚊蟲的叮咬,以及伍迪與班比之間純粹而真摯的羈絆。作者巧妙地運用瞭方言,讓人物形象更加鮮活立體,也更具地域特色。我尤其喜歡小說中對貧睏生活的真實描繪,沒有刻意的渲染苦難,而是通過日常瑣事和人物對話,展現齣一種堅韌而樂觀的生活態度。這種樸實無華的敘事風格,反而更能觸動人心。讀完之後,我開始反思我們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以及在現代社會中,我們是否已經漸漸失去瞭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能力。這本書不僅僅是一部文學作品,更是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們內心深處的渴望與迷茫。它提醒我們,要珍惜當下,珍惜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包括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美好。
评分我原本對這類題材的小說興趣不大,是被朋友強烈推薦纔開始閱讀的。沒想到,讀完之後卻被深深地打動瞭。作者用一種平實的語言,講述瞭一個關於成長、失去與救贖的故事。小說的主人公伍迪,是一個天真爛漫的男孩,他與小鹿班比之間建立瞭一種超越物種的友誼。然而,命運卻給他們開瞭一個殘酷的玩笑。在經曆瞭失去的痛苦之後,伍迪逐漸成長為一個更加成熟和堅強的人。譯者在翻譯方麵也下瞭很大的功夫,將原著的語言風格完美地還原齣來,讓讀者能夠感受到故事的真實性和感染力。我特彆欣賞小說中對人性的描寫,作者並沒有將人物簡單地劃分為好人或壞人,而是展現瞭他們內心深處的復雜性和矛盾性。讀完之後,我開始思考,什麼是真正的勇氣?是麵對睏難時的堅強,還是在失去之後依然能夠保持希望?這本書不僅僅是一部文學作品,更是一部關於人生的哲學思考。
评分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很復雜,既有感動,也有惋惜,甚至還有一絲淡淡的憂傷。作者用一種詩意的語言,描繪瞭一個關於男孩與小鹿之間純真友誼的故事。然而,這種友誼最終卻被殘酷的現實所打破。小說的主人公伍迪,在經曆瞭失去的痛苦之後,逐漸認識到生命的脆弱和無常。譯者在翻譯方麵也下瞭很大的功夫,將原著的語言風格完美地還原齣來,讓讀者能夠感受到故事的真實性和感染力。我特彆欣賞小說中對自然環境的描寫,作者用細膩的筆觸,展現瞭美國南方沼澤地的獨特魅力。讀完之後,我開始思考,我們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應該是什麼樣的?我們是否應該尊重自然,保護環境?這本書不僅僅是一部文學作品,更是一部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深刻反思。它提醒我們,要珍惜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包括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美好。它也讓我意識到,生命中總會有失去,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珍惜當下,勇敢地麵對未來。
评分說實話,一開始是被書名吸引的,總覺得“鹿苑長春”這個譯名帶著一種古典的詩意,讓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但真正讀起來,卻發現它遠比我想象的要更具力量。作者並沒有用華麗的辭藻去堆砌情節,而是用一種近乎紀錄片式的筆觸,將一個普通傢庭在艱苦環境中掙紮求生的故事娓娓道來。我特彆欣賞小說中對人物心理的刻畫,尤其是伍迪的父親,他既是一個粗獷的獵人,又是一個深愛著傢人的父親,他的內心充滿瞭矛盾與掙紮。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將他定義為好人或壞人,而是展現瞭他作為一個普通人在特定環境下的復雜性。這種對人性的深刻洞察,讓小說更具深度和現實意義。譯者在處理人物對話方麵也下瞭很大的功夫,保留瞭原著的語言風格,同時又讓颱灣讀者能夠輕鬆理解。讀完之後,我忍不住思考,什麼是真正的幸福?是物質的富足,還是精神的滿足?或許,幸福就在於我們能夠珍惜當下,珍惜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包括那些看似平凡的生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