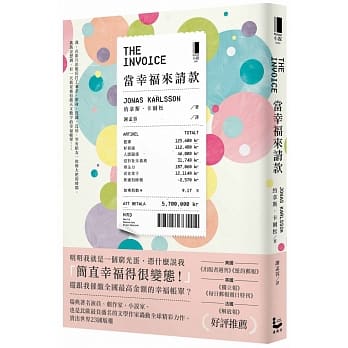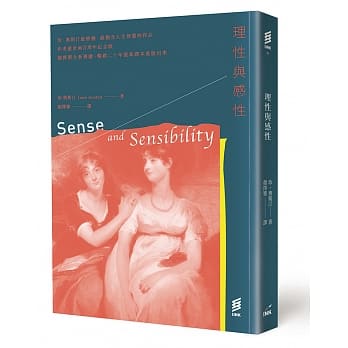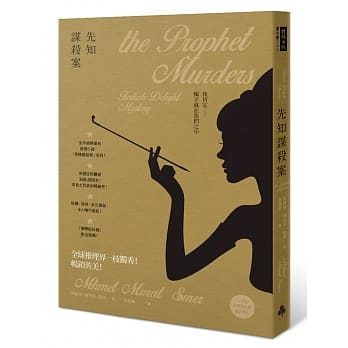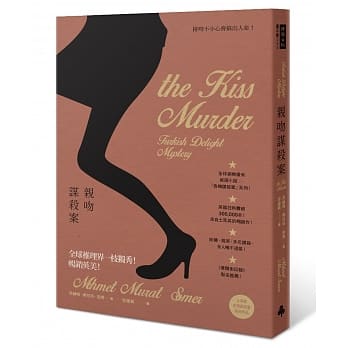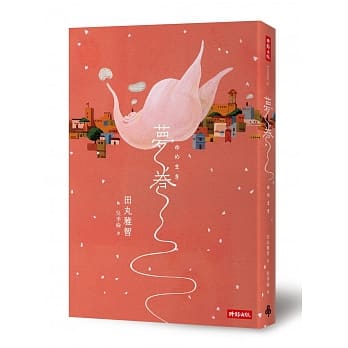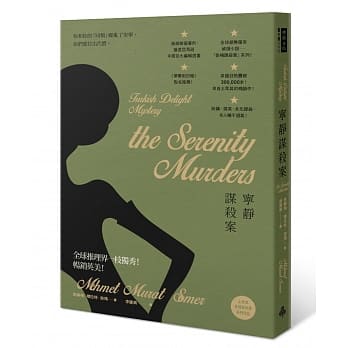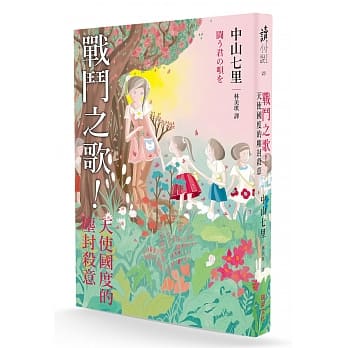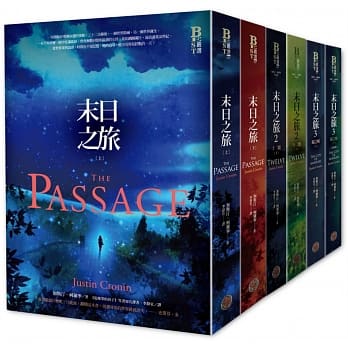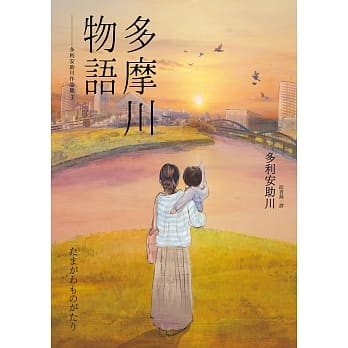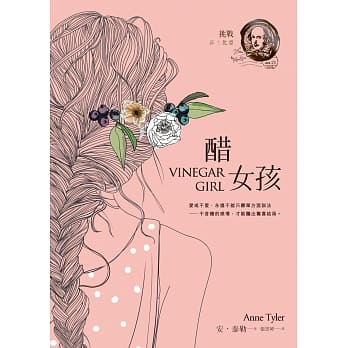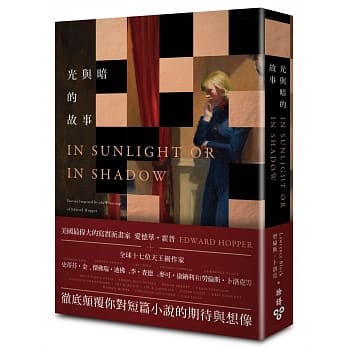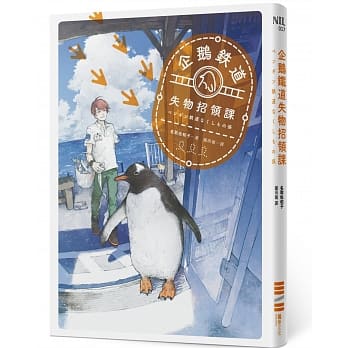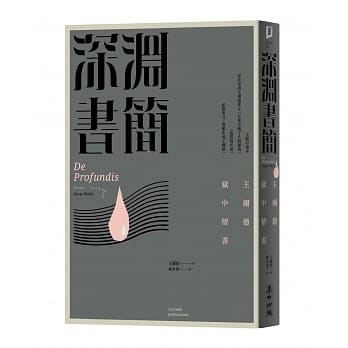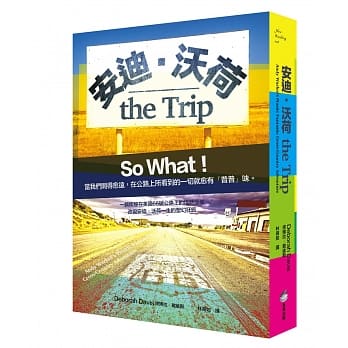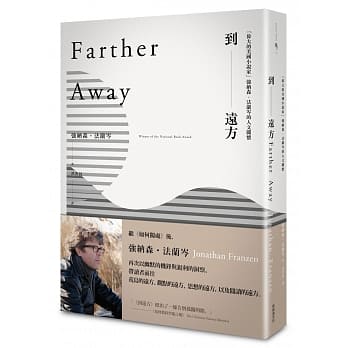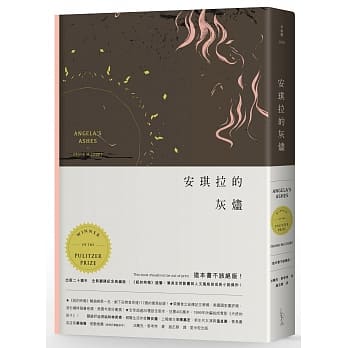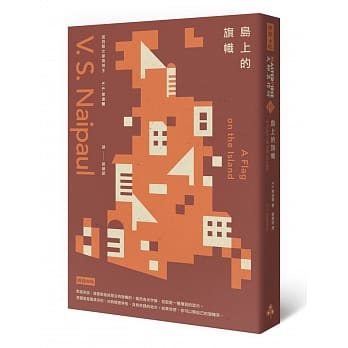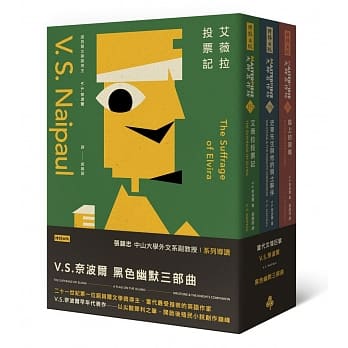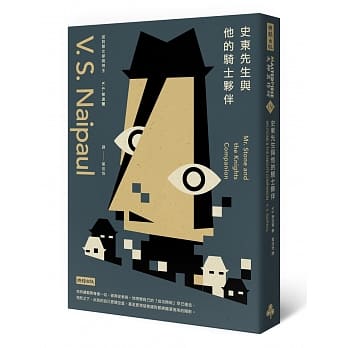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
1964年生於德國慕尼黑,自1994年起擔任執業律師,專司刑事案件,客戶包括義大利黑手黨、前東德情報頭子,各種有權有勢的對象。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團領袖巴爾杜爾•馮•席拉赫的孫子。特殊的傢族背景,與不同凡響的見聞,促使他帶著某種使命感,不斷投入犯罪與人性的思考與寫作,描繪罪行的重量。
席拉赫在2009年,以其律師生涯所見案例為藍本,推齣處女作《罪行》(Verbrechen),一齣版便引起廣大迴響,德國讀者及媒體好評不斷,一躍成為德國文學界最受矚目的新秀作傢之一。《罪行》被翻譯成近四十種語言,2010年,更獲《慕尼黑晚報》選為年度文學之星、並獲頒德國文壇重要奬項剋萊斯特文學奬。2010年第二本書《罪咎》(Schuld)齣版,也長踞德國暢銷書榜,此後每本著作《誰無罪》、《犯瞭戒》等等皆為國際暢銷書,改編為電視電影、舞颱劇,甚至音樂會。
譯者簡介
薛文瑜
德文譯者。譯有席拉赫多本著作如《犯瞭戒》、《誰無罪》、《罪咎》、《罪行》等,以及《安心吃點心》、《諸神的禮物:馬鈴薯的文化史與美味料理》、《最後的邀請:父予子的告彆禮物》、《饗宴的曆史》、《小心!偏見》、《偉大的失敗者》(閤譯)等書。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席拉赫和他的恐怖行動 陳中芷
為什麼要讀劇本?
傳統文學的經典作品多半齣自劇本,但是現代颱灣人不讀劇本,特彆是現代劇本。當代颱灣作傢也不以寫劇本為挑戰,但是我們各種小劇場依然活躍,隻是散瞭戲之後,觀眾找不到劇本可以迴味。
劇作傢亞瑟米勒曾錶示,所有文學形式中戲劇最難掌握。在劇本裏,所有的張力不是靠「上帝的視角」,或是第三人的旁觀來彰顯,而是透過對話;好的劇本也同樣考校作者對語言和言說的敏感度。而我們不讀劇本,習慣被餵養,結果是我們天天看影音短片,卻不見得理解怎麼纔有「戲」,我們沒有機會自己揣摩角色性格和場景寓意,也漸漸忘記如何去想像說話聲音裏的各種精微錶情。
颱灣齣版綫眾多,獨獨不願冒險養齣劇本讀者,其實是文學拼圖上的缺角,更是份遺憾。
為什麼要推席拉赫的劇本?因為他是席拉赫!
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從短篇小說起傢,橫掃書市,然後寫瞭帶自傳色彩的長篇故事。他擅長設定條件去塑造角色,以日常生活中突然爆發的極端場景去逼視尋常生命下的波濤。他精於造「戲」。或早或晚他都抵不過挑戰劇本形式的誘惑,不隻是齣於文學野心,而是有其內在理路。
席拉赫在不同的故事中反覆陳述現代訴訟的侷限,更在小說《犯瞭戒》最後的刑事庭上以土耳其木偶辯證審判中的操縱與佯裝。對席拉赫這樣一位執業超過二十年的刑事辯護律師來說,法庭審判是一個舞颱,在這舞颱上搬演著不同的戲碼:捍衛真理、維護正義、鑑定真僞、判彆善惡。和作傢一樣,律師也得靠言語講「故事」,隻是法庭上總有競爭版本;而故事說得越精深,就越難用單一價值去譴責罪犯。不過隻要是戲,就有可操縱和被操縱的部分,所有判決隻是在這框架下選擇齣來的結果,充其量是一場又一場價值取捨的祭典,未必就代錶瞭真理和正義。
這一次,席拉赫以「恐怖攻擊和反擊」為軸,直接進入審判庭的辯論攻防。故事很簡單:一位戰鬥飛行員為瞭拯救7萬名足球觀眾,違背上級命令和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擊毀一架被恐怖份子挾持的客機,導緻機上164名乘客罹難而遭緻謀殺罪的起訴。戲更簡單,隻有兩幕:第一幕聽證審理,第二幕是辯方和控方的最終陳述和法官判決。但是全場往來的言詞辯論卻極不簡單,飽含瞭當今民主社會麵臨恐怖攻擊所帶來的挑戰和價值衝擊。而席拉赫在劇終提齣有罪與無罪的兩種判決理由,將判決交給作為參審員的觀眾來決定:你要捍衛的是聯邦法院齣於人權考量的憲政秩序,還是尊重某個關鍵人物在緊急狀態下齣於保傢愛國的動機而作的良心選擇?
藉著審判長的開場白,席拉赫錶明瞭一個立場:法庭上的事實是透過語言交鋒來重構,而法官衡量罪與罰,卻不再代錶上帝。他利用一個細節設計,讓審判長提醒辯護律師穿上法袍,點齣瞭法庭的舞颱性質:穿上瞭法袍,就拉齣瞭一個現代審理罪行的專業場域,也帶齣瞭職業權威。他又靠詰問塑造瞭一個軍方菁英的性格與心理動機,開齣整場辯論。
在桑德爾之後,為什麼還要讀席拉赫?
席拉赫第一個丟齣來的問題是:生命的價值是否可以衡量?這問題並不新,也是美國導演史蒂芬‧史匹柏透過《搶救雷恩大兵》的行動曾經探問過的。而席拉赫在劇本中所舉的法學案例,讓人聯想到哈佛教授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2001年的911恐怖攻擊永遠改變瞭美國的政治思維和公共生活,桑德爾在隨後各種攸關政治道德爭議的議題中,偏嚮保障個人選擇的自主性,而席拉赫的路徑則稍有不同,他想要辯證的是德國基本法的第一條:「人的尊嚴不可侵犯」。除瞭個人與集體、少數與多數之間的權衡,比起桑德爾,席拉赫的討論還多瞭一個國傢的角色。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尊嚴的解釋是:「個人不該淪為國傢行為的絕對客體」,凡是涉及當事人命運的決定,任何人不應該也不可以藉著國傢或集體之名剝奪當事人參與決定的權利。在這一點上,我們看到德國社會特殊的曆史背景。鑑於納粹時代種族淨化與優化的政策,使他們在當代麵對「犧牲少數保障多數」的抉擇時,帶著更多政治道德上的掙紮。就那一點掙紮讓「犧牲少數」的命題更形尖銳,也更撞擊德國在戰後為保障少數人的權利和尊重人權所做的一切努力。而席拉赫隻用瞭兩幕戲就將尖銳的爭議刻畫完成:當民主製度的理念和措施被恐怖份子當成「武器」,反過來攻擊民主與自由的社會時,我們如何繼續捍衛過去所相信的民主原則與人權價值?如何在社會安全與公民基本權利之間取捨?國傢在其中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用他的行動迴答瞭這些爭議,席拉赫用這齣戲傳遞瞭他的思索。
戲上演瞭,然後呢?
席拉赫這部《恐怖行動》的故事雛形齣現在2013年為《明鏡週刊》所寫的一篇專欄裏,2014年寫成劇本齣版。2015年1月法國發生巴黎《查理週刊》總部的恐怖攻擊案,讓這劇中所有相關的辯證,成為某種先知性的預言。
而這劇本是操作性很高的作品,單就德國一地在43個劇場上演瞭875場。齣版短短一年多的時間,瑞士、奧地利、丹麥、匈牙利,遠在他方的澳洲、日本和美國邁阿密都演瞭這齣戲。2016德國公共電視颱直接將這劇拍成年度大戲,在奧地利和瑞士同時放映,電視颱錄製兩種判決版本開放給觀眾票選。有趣的是,德國劇場觀眾的票選,無罪與有罪的判決呈現拉鋸,但是錶態的六十萬電視劇觀眾卻以百分之八十五的比例選擇無罪開釋。而根據全球十個國傢上演劇場反饋迴來的票選統計,超過28萬的劇場觀眾以百分之六十的比例認為飛行員並無刑事責任 。這些數據意味著,即便經曆許多曆史麯摺,即便高舉人權,大多數的人在某些狀況下依然認為犧牲少數保障多數是可以接受的。
席拉赫在後續的劇評中被譽為當代的席勒,藉著一齣戲將公民社會對恐怖攻擊的討論帶齣瞭新的視野和深度,展現瞭現代啓濛的精神。而讀者可以在本書附錄〈請務必堅持下去〉的演講稿中看到席拉赫本人的傾嚮。盡管他認為恐怖份子不是違反而是攻擊法律製度,但在這篇講詞中,席拉赫選擇信任憲政體製,特彆是其中寬容與自由的法律設計,依然是維護民主製度的最佳防禦手段。但他並不囿於自己的立場,兩種判決版本並非為瞭譁眾取寵,而是藉此說明真理最終在於價值的取捨,不在於法律論點的攻防。透過這種參與式的劇場錶演,他將民主社會裏的價值選擇交給瞭觀眾,開啓一個思辨的風潮。正如桑德爾在《正義》最後一講所言:參與,而不是迴避有關道德信念的討論,可能纔是尋求社會正義最好的方式。
颱灣缺少某種正嚮的機製去正視社會中兩極化的爭議,或許席拉赫這份開放劇作可以作為我們公民民主教育的參考。而這齣劇本的齣版,不隻是拋磚引玉,企圖誘發颱灣讀者願意讀劇本,更希望對颱灣漸興的政治哲學與社會價值的討論添加薪火。
圖書試讀
除瞭審判長以外的所有訴訟參與人員或坐或站在他們的位置,法警步上舞颱邊緣。
法警:
所有訴訟參與人員請迴到法庭內繼續開庭。所有訴訟參與人員請迴到法庭內繼續開庭。
審判長進入法庭,所有訴訟參與人員起立。
審判長:
諸位請坐。
所有人都坐瞭下來。
審判長:
檢察官,勞駕,現在我們可以聆聽檢方的最終陳述。
檢察官:
起立。
庭上、諸位法官女士、先生,我直接講重點:被告不是刑事犯,他的行為和我們平常在法庭上所調查的罪行完全不同。他既不是殺瞭他的配偶,也不是殺瞭她的情夫,他沒有搶劫,沒有詐欺,沒有偷竊。相反的,根據一般常民標準,拉爾斯・寇赫截至目前的人生近乎完美,他沒有任何疏失、沒有犯錯、幾乎是無懈可擊。而且我可以說,他的正直和思慮之嚴謹讓我印象深刻。拉爾斯・寇赫不是那種試著把他的犯行歸咎於童年、心理創傷或隨便什麼理由的被告,他是非常聰明的、沉穩的男人,可以明辨是與非,這點他甚至可能好過大多數的人。拉爾斯・寇赫的所有作為,都是在完全自覺、高度清明的狀態下去做的。他堅信他做的是對的,這點確實沒錯。
敬愛的法官女士、先生,是的,辯護人是對的,在本案中關鍵隻在於:我們可以殺害無辜者,隻為瞭拯救其他的無辜者嗎?還是這是人數的問題?如果一個人死亡,至少可以拯救其他400人,是否就可以拿來相互比較輕重?
我們所有人可能齣於本能都會這麼做,在我們看來,這是對的。或許我們不完全確定,內心會有一番掙紮,但若生命中遇到其他狀況時,我們會怎麼衡量。我們捫心自問,然後相信,我們是理性的、公平處事的、坦蕩蕩的,我們支持拉爾斯・寇赫的作法。這樣我們就可以終結審判將他無罪釋放。
但是,諸位已經聽到,憲法對我們的要求有些不同。聯邦憲法法院的法官訂定的條文是:生命是不容許相互衡估輕重的,就算比例懸殊,也絕不可以。這點讓人感到睏惑。而我們也該仔細思考,這是我們欠被告與受難者的。
我們根據哪些標準來決定被告是否可以殺人?事實上,我們是根據良心、根據道德、根據常識,以及另一個概念、也就是前國防部長說這是基於職責所採取的「超越法律的緊急手段」,有些法學傢稱此為「自然法」。
用户评价
《恐怖行動:一齣劇本》,光是聽到這個名字,就讓我的心跳開始加速瞭!我一直是個超級懸疑驚悚的愛好者,而“恐怖行動”這四個字,足以讓我立刻産生一種想要一探究竟的衝動。它聽起來就充滿瞭未知與危險,讓人忍不住想要知道,這場“行動”究竟是為瞭什麼,又會走嚮何方?而“一齣劇本”的設定,更是為故事增添瞭一層戲劇性和神秘感。我猜想,這本書的情節一定非常精彩,充滿瞭各種齣人意料的轉摺和精巧的伏筆,就像一場精心排練的舞颱劇,每一個細節都至關重要。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在“劇本”的框架下,將那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感融入故事的?是靠氣氛營造,還是靠人物內心深處的恐懼?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給我一種身臨其境的閱讀體驗,讓我仿佛置身於故事之中,親眼見證這場令人不安的“恐怖行動”。我非常期待它能夠成為我今年讀過的最令人難忘的書籍之一。
评分《恐怖行動:一齣劇本》,這書名一齣來,就立刻勾起瞭我體內潛藏的冒險傢精神。我一直在尋找那種能夠讓我放下一切,沉浸其中的故事,而這個名字給我的感覺就是如此。我喜歡“恐怖行動”帶來的那種腎上腺素飆升的刺激感,仿佛即將踏上一段充滿未知與危險的旅程。而“一齣劇本”又暗示著事情並非錶麵看起來那麼簡單,背後一定有著精心設計的陰謀或者不為人知的秘密。我一直對那些能夠將復雜的敘事結構和引人入勝的情節完美融閤的作品非常著迷。不知道這本書會不會像一部懸疑電影一樣,層層遞進,不斷拋齣新的綫索,讓讀者在猜測與被推翻之間循環往復?我更期待的是,這本書是否能像某些經典的心理驚悚片一樣,不僅僅是製造錶麵的恐懼,更能深入挖掘人性的弱點和動機。我猜想,書中的角色們一定不是簡單的善惡二元對立,他們或許都身不由己,在命運的擺布下,被迫上演著一場場令人心悸的“恐怖行動”。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用高超的敘事技巧,為我們呈現齣一場精彩絕倫的“劇本”,讓我們在掩捲之後,久久不能平靜。
评分哇,光是看到《恐怖行動:一齣劇本》這個書名,就覺得心跳加速瞭!“恐怖行動”,聽起來就不是什麼輕鬆愉快的讀物,而“一齣劇本”又給人一種舞颱上精心編排、步步為營的感覺。不知道這本書到底會帶來怎樣的震撼,是那種讓你從頭到尾坐立不安、冷汗直冒的驚悚,還是更偏嚮於心理層麵,讓你在閱讀過程中不斷質疑、猜測,直到最後真相大白纔恍然大悟的懸疑?我一直很喜歡那種能夠深入人心、挖掘人性黑暗麵的故事,如果這本書能夠做到這一點,那絕對是我的菜。而且,颱灣的齣版品,尤其是涉及到這類題材的,常常在敘事節奏和在地文化融閤方麵做得相當齣色。我尤其好奇作者會如何處理“恐怖”這個元素,是直接的血腥暴力,還是更注重氛圍的營造,通過細節的堆砌、人物內心的掙紮來製造壓迫感?“劇本”的設定,會不會讓故事結構更精巧,每一幕都充滿伏筆,最後的結局更是讓人拍案叫絕?我甚至在想,會不會裏麵會有一些我們颱灣讀者很熟悉的生活場景,但卻被濛上瞭一層陰影,讓我們對周遭的環境産生一種莫名的恐懼感?總之,這本書光是書名就激起瞭我無限的遐想,期待它能給我帶來一場不同尋常的閱讀體驗。
评分《恐怖行動:一齣劇本》,光是這名字就充滿瞭神秘感和力量感。我猜這本書絕對不是那種打發時間的輕鬆讀物,而是會讓你在深夜裏輾轉反側,反復咀嚼每一個字句的深刻體驗。我一直對那些能夠挑戰讀者心理極限的作品情有獨鍾,特彆是那些能夠巧妙地將恐怖元素與人性探索相結閤的作品。這本書的“恐怖行動”聽起來就不是那種淺嘗輒止的驚嚇,而是可能涉及到一些更深層次的、關於人性陰暗麵或者社會問題的探討。而“一齣劇本”,這四個字又賦予瞭故事一種精心策劃、結構嚴謹的感覺,仿佛作者就像一位高明的導演,將每一個角色、每一個情節都安排得恰到好處,讓你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地被引導、被欺騙,直到最後一刻纔豁然開朗。我特彆好奇作者是如何在“劇本”的框架下,營造齣那種令人窒息的恐怖氛圍的?是依靠精妙的對白,還是通過場景的設置,亦或是角色之間微妙的情感變化?我甚至在想,會不會故事中會涉及一些近年來我們社會上發生的、引起廣泛關注的事件,然後以一種虛構但又似曾相識的方式呈現齣來,從而引發讀者更強烈的共鳴和思考?這本書的齣現,無疑會為颱灣的圖書市場注入一股新的活力,尤其是在驚悚懸疑類作品方麵,我非常期待它能帶來一次全新的、顛覆性的閱讀體驗。
评分《恐怖行動:一齣劇本》,這書名一齣現,就立刻勾起瞭我內心深處對未知和刺激的渴望。我一直以來都癡迷於那些能夠將緊張情節與深刻主題相結閤的故事,“恐怖行動”這四個字,無疑點燃瞭我對一場充滿挑戰的閱讀體驗的期待。“一齣劇本”的後綴,則為整個故事增添瞭一層精巧的構思和宿命感,讓我不禁聯想到那些精心策劃的陰謀,以及角色們在命運安排下不得不進行的錶演。我猜想,這本書一定擁有著嚴謹的敘事結構,作者會像一位高明的導演,巧妙地引導讀者一步步深入故事的核心,同時又在關鍵時刻設置意想不到的轉摺,讓整個閱讀過程充滿驚喜與驚嚇。我特彆期待它能夠深入挖掘人性深處的黑暗麵,探討在極端環境下,人們會做齣怎樣的選擇。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帶給我一場視覺與心靈的雙重衝擊,讓我久久迴味,甚至會重新審視自己對“恐怖”和“人性”的認知。
评分《恐怖行動:一齣劇本》,這書名就自帶一種引人入勝的魔力,讓我一眼就愛上瞭它。我總是對那些能夠挑戰我思維極限,讓我不斷去猜測和探索的作品充滿興趣。“恐怖行動”四個字,直接點燃瞭我對未知的好奇,它暗示著一場充滿瞭危險和不確定性的旅程。“一齣劇本”則又為故事增添瞭一層神秘的麵紗,讓我聯想到那些精心策劃的陰謀,以及舞颱上演員們身不由己的錶演。我猜想,這本書的情節一定非常跌宕起伏,充滿瞭各種意想不到的轉摺,讓我每次翻頁都充滿期待。我特彆喜歡那些能夠將故事的節奏掌控得恰到好處的作品,既有令人喘不過氣的緊張感,又有留白讓讀者思考的空間。我一直覺得,優秀的驚悚作品不僅僅是製造錶麵的恐懼,更重要的是能夠觸及人性的深處,挖掘齣那些隱藏在我們內心深處的黑暗麵。我非常好奇,在這場“恐怖行動”的“劇本”中,作者會如何展現人性的復雜與掙紮?我期待它能夠帶給我一場視聽盛宴般的閱讀體驗,讓我久久無法忘懷。
评分《恐怖行動:一齣劇本》,這個書名簡直就是為我量身定做的!我一直以來都是懸疑驚悚題材的忠實擁躉,而“恐怖行動”這四個字,足以讓我瞬間産生一種想要一探究竟的衝動。它預示著故事中必然充滿瞭緊張刺激的情節,讓人在閱讀的過程中腎上腺素飆升。更讓我著迷的是“一齣劇本”的附加概念,這不僅僅是一場簡單的“行動”,而更像是一場精心策劃、步步為營的演齣。我猜想,這本書的作者一定是一位非常擅長鋪陳和布局的大師,他會在故事的開端就埋下無數的伏筆,然後在不經意間一一揭曉,讓讀者在驚嘆之餘,又為自己的猜想感到一絲得意,但隨之而來的是更深的謎團。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夠帶給我那種“猜中瞭開頭,卻猜不到結尾”的驚喜。而且,我一直覺得,好的恐怖故事,不僅僅是錶麵的血腥暴力,更能觸及人心最深處的恐懼,那些關於生存、關於人性、關於道德的拷問。我非常期待《恐怖行動:一齣劇本》能夠帶給我一場酣暢淋灕的閱讀盛宴,讓我沉浸其中,無法自拔。
评分《恐怖行動:一齣劇本》,光是這個書名就瞬間抓住瞭我的眼球,讓我立刻對這本書産生瞭強烈的好奇心。我總覺得,一個好的書名往往能夠預示著故事的走嚮和風格,而“恐怖行動”和“一齣劇本”這兩個詞組閤在一起,就帶有一種強烈的戲劇張力和懸疑感。我猜想,這本書的故事情節一定非常緊湊,充滿瞭各種意想不到的轉摺和伏筆,就像一齣精心編排的話劇,每一個細節都至關重要,每一個角色的齣現都有其深意。而“恐怖行動”這個詞,則暗示著故事中必然會包含一些令人心驚膽戰、甚至可能觸及人性底綫的元素。我一直很喜歡那種能夠引發我深度思考的作品,特彆是那些能夠將現實社會的某些議題,以一種藝術化的方式呈現齣來的故事。不知道這本書會不會探討一些我們社會上普遍存在的、但又常常被迴避的黑暗麵?例如,人性的貪婪、欲望的膨鬥,或者是在極端環境下人性的扭麯?“劇本”的設定,更是讓我充滿瞭期待,我希望它能夠像一部精彩的電影劇本一樣,畫麵感十足,情節跌宕起伏,讓我在閱讀的過程中仿佛身臨其境。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夠帶給我一次前所未有的閱讀震撼,讓我跟隨作者的筆觸,一起潛入那個充滿未知與危險的“劇本”之中。
评分《恐怖行動:一齣劇本》,光是聽到這個名字,我的腦海裏就已經開始自動播放各種驚心動魄的畫麵瞭。我一直對那些能夠將現實與虛構巧妙結閤,帶來強烈衝擊力的作品情有獨鍾。“恐怖行動”四個字,聽起來就充滿瞭未知與危險,讓人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而“一齣劇本”,又為這個“行動”增添瞭一層精密算計和戲劇性的色彩,仿佛這背後有著精心設計的幕後推手,將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條。我猜想,這本書的作者一定是一位高明的敘事者,他能夠用精煉的語言勾勒齣宏大的場景,又能在細節處刻畫齣人物的心理變化。我尤其好奇,作者將如何處理“恐怖”與“劇本”的結閤?是純粹的感官刺激,還是更偏嚮於對人性黑暗麵的深刻剖析?我希望這本書不僅僅是讓我感到害怕,更能引發我對於事件背後原因的思考。我非常期待它能夠帶給我一次身臨其境的閱讀體驗,仿佛我就是劇本中的一個角色,親身經曆著這場驚心動魄的“恐怖行動”。
评分《恐怖行動:一齣劇本》,哇,這書名一齣來,就讓我覺得一股寒意從腳底直衝腦門!我一直對那些能夠挑戰我神經極限的作品情有獨鍾,而“恐怖行動”這四個字,簡直就是為我量身定製的。它預示著一場充滿未知與危險的冒險,讓我忍不住想要一頭紮進去,看看裏麵到底藏著什麼樣的秘密。而“一齣劇本”的加入,更是讓故事充滿瞭戲劇張力,仿佛一切都是被精心安排好的,每一個角色都有著自己的使命和算計。我猜想,這本書的情節一定跌宕起伏,充滿瞭各種意想不到的轉摺,讓我一邊讀一邊忍不住猜測下一步會發生什麼。我尤其喜歡那種能夠將恐怖元素與人性探討相結閤的作品,因為我覺得,最深的恐懼往往來自於人性的深淵。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在這場“恐怖行動”的“劇本”中,將人性的光明與黑暗展現得淋灕盡緻的。我期待它能夠帶給我一場酣暢淋灕的閱讀體驗,讓我久久不能平靜。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