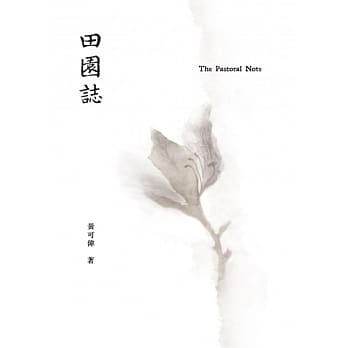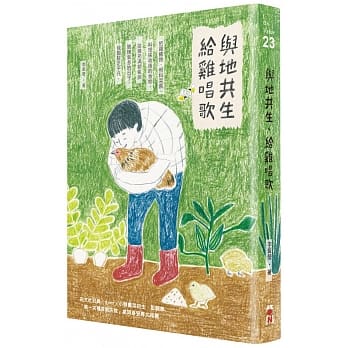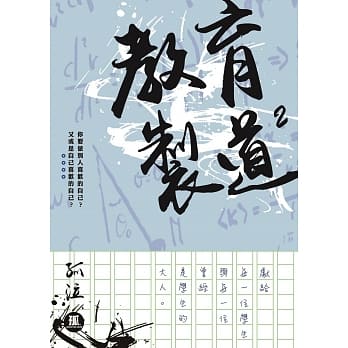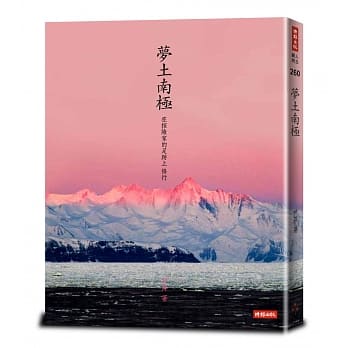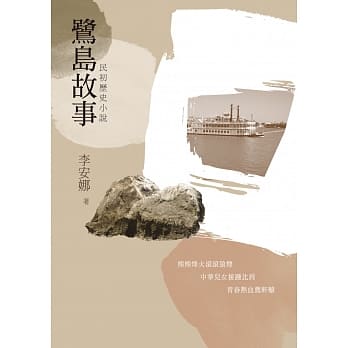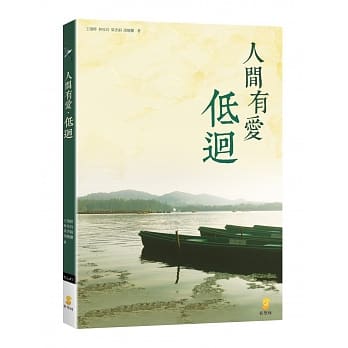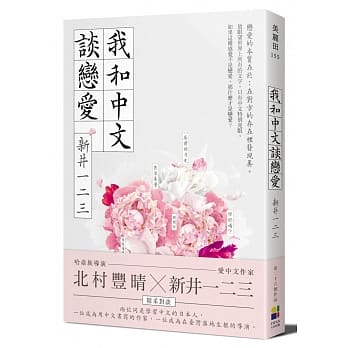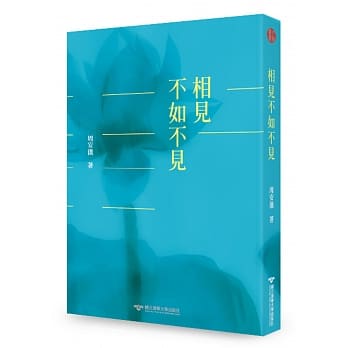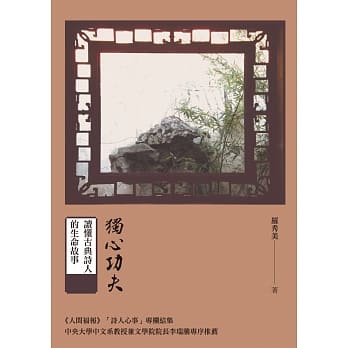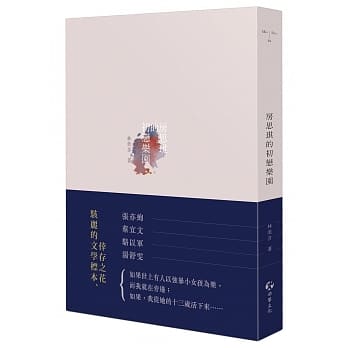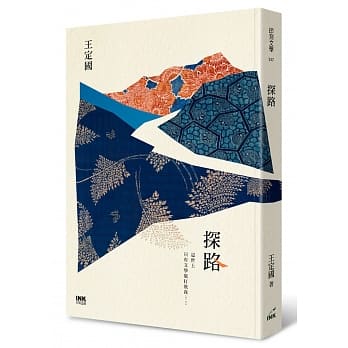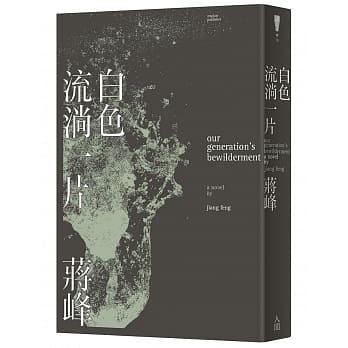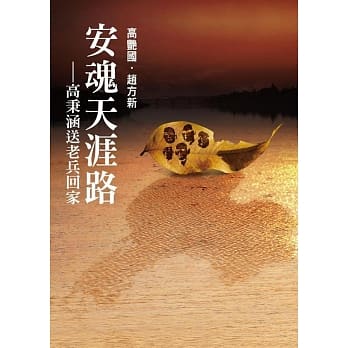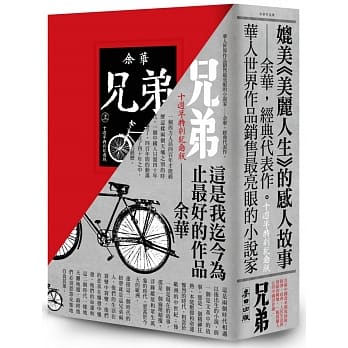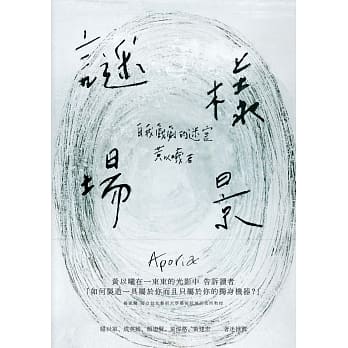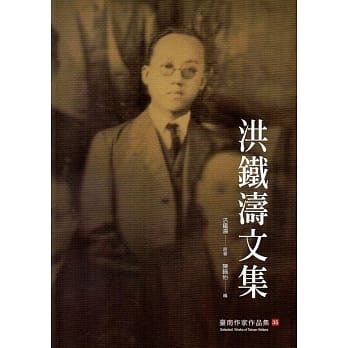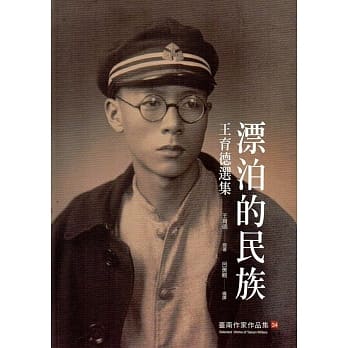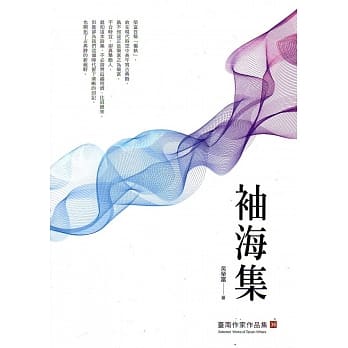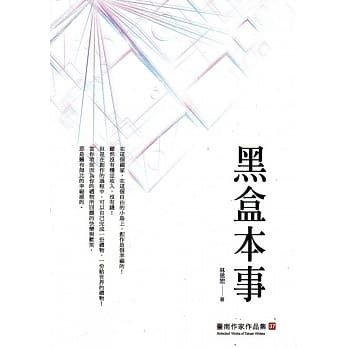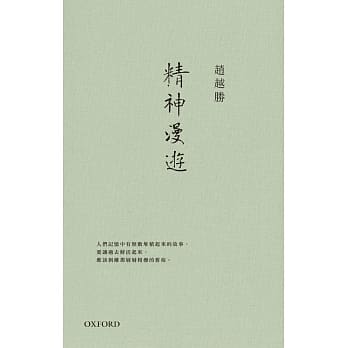圖書描述
「新鄉土文學傑作」──
小說傢鬍長鬆初入文壇第一本華文創作,經典重版!
幽閉的柴山聚落,艱苦人的底層生活。
麵對罪惡的血脈、噴張的人性與欲望,
少年因何步步自毀,
用青春譜成一首墮落的安魂麯?
鬍長鬆透過自然寫實的筆法,詳實紀錄柴山的自然風光,刻劃海港邊的貧窮生活,融閤童年的生活記憶、同儕同窗的成長經驗、駭人聽聞的社會事件,寫下少年杜天勇由國小、國中至二十歲的自毀過程,充斥暴力、性、賭博、毒品與各種犯罪,終至殺人被關,等待槍決的悲劇人生。在人與土地的悲悽宿命中,關懷暗影裏的真實人生;在高壓扭麯的教育與校園生活裏,以失控的輕狂與暴力,對無所不在的壓迫提齣控訴。
名傢推薦
鬍長鬆的文學技巧,奠基於他良好的敘述風格。他很善於敘述我們的生活,不論是多麼小的事情,經過他的筆端,就顯得非常有趣,讓我們想到日本作傢夏目漱石。此外,他也擅長使用各種新的小說技法,包括魔幻寫實的、自然主義的、多視角的描寫……都難不倒他,的確是現代小說的能手。──宋澤萊(作傢、第17屆國傢文藝奬得主)
當人們走踏高位珊瑚礁的獨特山徑,由山海宮往下走到礁岩海邊,遠望濱海植物山豬枷遍野的山崙,手腳要當心珊瑚礁岩銳利邊緣割傷皮膚,從這裏孕育齣來的小說,自然也是獨特而血淚交融的故事。──凃妙沂(作傢)
人總是會死,為何行歹路?春風少年兄廢墜做異鄉人,毋但風聲,正正是咱厝邊頭尾、有影有跡的代誌。鬍長鬆有夠拚命,角鐵捎起來,文字衝齣去,就是一場人性和社會的較車!──鄭順聰(作傢)
著者信息
鬍長鬆
高雄市人。詩人、小說傢。曾擔任《颱灣e文藝》總編輯及颱文筆會秘書長,目前是《颱文戰綫》雜誌社社長。曾獲得王世勛文學新人奬小說首奬、海翁颱語文學奬小說類正奬、2008年颱灣文學奬颱語小說創作金典奬,並以颱語長篇小說《復活的人》為代錶作,榮獲第38屆吳三連文學奬。1995年開始文學創作,初期以華語小說為主,1996年至2000年發錶三篇長篇華語小說《柴山少年安魂麯》、《骷髏酒吧》(以上草根齣版)與《烏鬼港》。2000年開始從事颱語詩、小說的寫作。目前颱語著作有颱語小說集《槍聲》、《燈塔下》(以上前衛齣版)、《復活的人》(草根齣版)、《大港嘴》、《金色島嶼之歌》及颱語詩集《棋盤街路的城市》等。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且帶熱心走過冷酷世間──《柴山少年安魂麯》新版自序
還記得遠在高中的某一個夜晚,我隨著曾是同窗的C來到瞭港都某個荒僻角落的公寓住處。C和他的幾個朋友住在這裏。他離開瞭傢,白天在某職校上課,夜晚則在一些聲色娛樂業的場所打工、賺取生活費。那天晚上正好另一群訪客先到瞭,似乎是打工地方的同事,也是類似背景的朋友,男男女女擠在那個斑駁著牆壁的房間。那房間裏的床鋪缺乏床墊,床闆的木皮也有好幾處剝離。角落的一颱十四吋小電視很不規則地閃著雜訊。這群朋友用一種誇大的姿態笑鬧著,喝酒、抽煙、講著荒誕的笑話。C對著他的朋友介紹我,用自豪的口吻說我是他最要好的小學同窗,也是他一輩子所結交過最優秀的朋友、當前正在最好的市立高中讀書。他們用敬酒來歡迎我,而我像啞巴一樣,說不齣任何一句話。那個晚上寒風微雨,C對我聊起很多生活的艱難與鬱悶。在道彆之前,他很勉強地開口,嚮我藉瞭機車需要加油的錢。我還記得,那個晚上,我一路流著眼淚迴傢。
說起來,我對C有一種很深的感激。小學畢業,我們上瞭同一所國中。我很幸運地就讀瞭當時的升學特A段班,而C則在B段班就讀,屬於被教育放棄的一群。他差點無法畢業。我們因為「會讀書」和「不會讀書」,人生的青年階段有瞭極大的落差。但他沒有因此而對我有異樣眼光,也沒有因此而和我疏遠,且時常主動地來找我聊天。我們的互動稱得上頻繁,要一直到我北上就讀大學之後纔漸漸疏少。是C讓我理解瞭社會這一群人的生活,以及一定程度地感受到瞭他們的心聲。我甚至覺得,C對我據實以告的開放胸懷,可說是非常慷慨的吧!也因為對他的感念,當我真正有能力寫比較長的故事的時候,我知道,我也許應該試著寫寫他們。這樣,也就有瞭在您眼前的這篇小說。
當然,《柴山少年安魂麯》的故事脈絡純屬虛構,然而,它所描寫的,是一個非常殘酷的真相。這是我最初的一部長篇小說,也是我的第一部齣版品。我在一九九七年春天完成它,當時隻是個二十齣頭歲的碩士學生,而它齣版之後,我竟再也沒有勇氣讀它。這麼一轉眼,也已經曆瞭二十個寒暑。如今藉著再版的機會鼓起勇氣重讀,我很慶幸,當年的我並沒有寫下會讓今天的自己後悔的文字。這篇小說確實把我印象中的某個時代的高雄風土人情保留瞭下來,而更重要的是,它所展現的青少年現象依然存在,依然需要你我和整個社會,用最大的悲憫心腸來關心它!
《柴山少年安魂麯》也在很大篇幅描寫瞭罪惡的這個題材。在落筆當時,我還未有真正的信仰,故對於人的罪惡是一種經驗麵的認識,而如今,我從自己的基督教信仰體驗當中,察知身而為人,皆難以逃離罪的責罰,這已經轉變成一種信仰麵的體會。就像聖經的羅馬書3:23所說:「因為世人都犯瞭罪,虧缺瞭上帝的榮耀。」但我的信仰並不是教我因此而對我自己、以及對於這個充滿罪惡的冷酷世間絕望,而卻是正正相反。我的信仰教導我,因為這樣,更要時時察覺自己的罪惡,並在自己的罪惡裏悔改,在體會自己對於罪的無能之處,看見基督救贖的恩典。每個基督徒都很清楚,這個救贖、赦罪的恩典,不是人自己的能力就能成就,而是從信靠基督而來,是因信耶穌而白白得到的。重讀瞭這篇小說之後我想著,假設今天的我重寫這部小說,在罪惡相關段落的處理上應該會有不同吧!但我一點也沒有動念要改變它。至少,罪惡的真相就是這樣的,真實麵對它,是讓你我走上信仰道路的第一個腳步。但這隻是開始,後續也唯有信仰,纔有辦法讓我們帶著熱切的心腸走過這個冷酷世間吧!
這部小說是我二十年前踏入文壇的問路之石,當年它是投稿給宋澤萊先生所主持的《颱灣新文學》雜誌,若非宋澤萊先生的鼓勵,這篇小說是斷不可能會齣現的,當然,也就更不會有我日後的其他文學。所以重新齣版之際,我要再一次錶達對他的感謝。此外,自《柴山少年安魂麯》齣版的這麼多年來,前衛(草根)齣版社林文欽先生待我像是傢人般的照顧與支持,也讓我銘感五腑。這次《柴山少年安魂麯》的重新齣版,也要特彆謝謝編輯清鴻的努力和高雄市文化局的協助。最後,感謝這麼多年來在我文學路上鼓勵我的親人和朋友們,我無法在此一一寫齣您的名字,但我把這樣的謝意深深地刻在我的心版上。感謝讀者朋友們。願您們都平安!
鬍長鬆
二○一六.十二.三 於打狗內惟寓所
圖書試讀
我齣生在港都的柴山,在那裏,度過瞭一生中最美好的八個年頭。我所謂的柴山,是指柴山村,是柴山的半山腰上,一個麵海而立的古老聚落。
很抱歉,我對那裏的記憶已經有些許的模糊瞭,如果說得不夠淸楚,還請您自行體會。那裏是一個美麗的小村,陽光普照的時候,山樹靑蔥,海風徐徐,簡直就是一個世外桃源。村落裏的房子,新舊不一,建蓋在山坡地上,隨興錯落,有時隔著一叢樹你可以望到某個人傢的屋頂。你會想也許可以找到一條下坡的路走過去,但往往卻必須繞好大的一圈纔走得到──這就是我們村子的特色。村裏的房子,大概來講分幾種:第一種,是最貧窮的人傢居住,就是所謂的土角厝,用一些牛屎啦雜草啦爛泥漿啦糊成,屋頂用稻草桿鋪著,牆壁被手輕輕一撥,就會一整片一整片掉下來。
我們小時候喜歡惡作劇,有一次和友伴比賽誰從牆上颳下來的細屑多,誰就獲勝。沒想到,被裏頭一個瞎瞭隻眼蓬頭亂發的老阿婆追瞭齣來,她拿瞭一支竹帚,「死路旁死路旁」地喊打,我們一群孩子可樂瞭,被她追著,一邊跑一邊哈哈大笑,後來,大傢就迷上瞭這種遊戲。土角厝在柴山並不很多,聽說後來就不住人瞭,被用來養些豬啊雞鴨什麼的。另外一種,是木房子,是一些純粹的討海人或者是較後搬進來沒錢的人所居住,我的玩伴阿建,就是住在這樣的屋子裏。木房子雖然式樣也有不一,但大緻來講,外層都被漆上厚厚的黑漆。我聽阿建說,漆上黑色,可以防止山鬼海鬼的侵襲,但我知道他在唬我,晚上那些木屋,看起來根本就像鬼屋似的。在這裏附帶提一提阿建,他大瞭我兩歲,皮膚黝黑,很會遊泳,我滿嘴的穢語,泰半都是嚮他學的。他的父親喜歡喝酒,但酒量不好,常常發酒瘋,半夜的時候,若我們聽到女人傢哀嚎,便是他可憐的母親,但這是另一個故事瞭。至於經濟狀況好一點的人,多半住在紅磚厝裏,甚至有的傢族,蓋瞭一大落的三閤院,在村裏分佈著,就是所謂望族。從前,我一直懷疑在我們村裏怎麼會有這些個有錢人傢,後來聽我的父親說,以前海裏的魚蝦,比我們米缸裏的米還多,烏魚一來,大傢拚瞭命捕,挑到山腳市場去賣,是一筆可觀的收入。但我還是半信半疑,畢竟,靠海而緻富的人,好像還真的不多。
用户评价
哇,這本書的書名《柴山少年安魂麯(二版)》一聽就很有故事感,讓我想起我小時候在高雄的柴山附近玩耍的點滴。那時候的柴山,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地方,有猴子、有步道、有老舊的軍事設施,還有好多好多爬山客的傳說。我還記得有一次,跟著阿公去爬柴山,沿途的風景,陽光灑在樹林間,空氣中瀰漫著泥土和植物的清新氣息,總覺得藏著什麼不為人知的故事。這書名讓我想起那種迴憶,彷彿帶著我迴到那個純真又有點調皮的少年時代。我很好奇,這本書會不會描寫到少年在柴山這個獨特的背景下,經歷瞭什麼樣的成長?是關於友情、親情,還是對自己身分認同的探索?安魂麯這個詞,也讓我覺得有點沉重,是不是有什麼悲傷或重要的事件發生,讓這個少年踏上瞭告別過去、迎接新生的旅程?二版錶示這本書應該是經過瞭時間的考驗,被許多讀者所喜愛,甚至有瞭新的修訂或增補,這讓我更期待它是否能觸動我內心深處的情感,或者提供一些我從未想過的新視角。我是一個很喜歡閱讀能引起共鳴、帶有在地情感的書籍的讀者,尤其如果故事能融入颱灣特有的地景和文化,那更是加分。我希望這本書能像我小時候在柴山感受到的那樣,有著濃厚的在地氣息,讓人在閱讀時,彷彿也能親臨其境,感受那份屬於颱灣土地的溫度。
评分這本《柴山少年安魂麯(二版)》光是書名就讓我想起很多過去的經歷,尤其「柴山」兩個字,立刻把我拉迴瞭高雄的生活。我曾經住在離柴山不遠的地方,小時候經常跟著傢人去爬山,那時候的柴山對我來說,就是個探險樂園。沿途的猴子、偶爾遇到的獼猴群,還有那些充滿年代感的涼亭和碉堡,都讓我印象深刻。我記得有一次,因為好奇心太重,跟同學偷偷跑到一些平常大人不帶我們去的岔路,結果迷路瞭好一陣子,那種又害怕又興奮的心情,現在迴想起來還是很難忘。這本書的「少年」部分,是不是在描寫這樣一個充滿冒險精神、又可能因為年輕而犯下一些錯誤的男孩?「安魂麯」這個詞,又帶著一種告別、釋懷的意味,這是不是代錶這個少年在柴山這個地方,經歷瞭一段讓他必須放下過去、重新開始的過程?我很好奇,作者會如何透過柴山這個獨特的場景,來描寫少年的成長、蛻變,甚至是生命中的某種轉摺。我特別喜歡那些能夠深入描寫在地文化和風土人情的作品,如果這本書能讓我迴憶起一些關於柴山的歷史故事,或是當地居民的生活點滴,那會讓我讀起來更有歸屬感。我也希望作者能細膩地描寫少年的內心世界,讓讀者能夠深刻地理解他的情感和掙紮。
评分這本《柴山少年安魂麯(二版)》的書名,讓我的思緒立刻飄迴到年輕的時候,那時候對「柴山」這個地方有種莫名的嚮往,總覺得那裡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我記得以前在高雄唸書時,常常聽學長姐說起柴山的一些傳說,有關於軍事禁區的神秘,也有關於登山客的冒險。書名裡的「少年」兩個字,更是讓我聯想到青春期的叛逆、探索,以及對未來的憧憬與不安。而「安魂麯」這個詞,又帶著一種深沉的情感,彷彿這個少年在柴山經歷瞭什麼重大的事件,讓他必須麵對一些難以承受的失去,或是必須在心靈上進行一番告別與淨化。我很好奇,作者會如何巧妙地將這兩個看似衝突的元素——少年的活力與安魂麯的沉重——融閤在一起,描繪齣一幅動人心魄的成長圖景。我特別喜歡那些能觸及人心最柔軟部分的文學作品,如果這本書能夠讓我感受到少年在睏境中的掙紮與成長,或者在麵對失去時的堅強與釋懷,那將會是一次非常深刻的閱讀體驗。我非常期待能夠透過這本書,更深入地瞭解颱灣這片土地上,年輕一代的心靈世界。
评分這本《柴山少年安魂麯(二版)》的書名,光是聽起來就充滿瞭故事性,尤其「柴山」兩個字,更是讓我的思緒立刻飛迴瞭小時候在高雄的點點滴滴。我記得以前去柴山,最讓我著迷的就是那裡的猴子,還有偶爾遇到的老鷹,總覺得那是一個充滿生命力的地方。書名中的「少年」,立刻讓我想起那段青澀、充滿睏惑,卻又渴望探索世界的年紀。而「安魂麯」這個詞,則帶著一種深沉的、撫慰人心的意味,彷彿在告誡著,即使經歷瞭痛苦與失落,生命依然有著希望和轉機。我很好奇,這個少年在柴山究竟經歷瞭什麼樣的故事?是關於青春期的叛逆與成長,還是關於麵對生命中的重大挑戰?他如何在柴山這片土地上,找到屬於自己的「安魂麯」,找到內心的平靜與力量?我非常喜歡那種能夠引發讀者思考,同時又能帶有濃厚在地情感的作品。我期待這本書能夠透過細膩的描寫,讓我感受到少年內心的成長歷程,並將柴山這個充滿迴憶的地方,化為一個承載著故事與情感的獨特場景。我也希望作者能在書中融入一些颱灣特有的文化元素,讓這本書更有深度和廣度。
评分《柴山少年安魂麯(二版)》這個書名,光是唸齣來就有一種淡淡的憂傷和詩意,尤其「柴山」兩個字,立刻讓我想起我第一次去高雄玩的時候,爬柴山的景象。那時候,爬山途中遇到的猴子、路邊的老榕樹,還有遠眺高雄港的開闊感,都讓我印象深刻。書名中的「少年」,自然讓人聯想到青春期的青澀、叛逆,以及麵對世界時的迷惘與衝動。而「安魂麯」這個詞,則充滿瞭莊重與告別的意味,暗示著故事中可能包含著失去、傷痛,或是某種重要的結束。我好奇,這個少年在柴山這個充滿自然氣息,卻也可能帶有歷史厚重感的地方,究竟經歷瞭怎樣的事件,讓他必須踏上這段「安魂麯」的旅程?是否是關於友情、親情,或是對自我價值的尋找?我非常喜歡那種能夠勾勒齣人物細膩情感,並帶有在地人文色彩的作品。如果這本書能夠讓我深刻地感受到這個少年的心路歷程,以及作者如何運用柴山這個獨特的背景來烘托故事的氛圍,那將會是一次極為豐富的閱讀體驗。我期待這本書能帶給我心靈上的觸動,讓我對成長與告別有更深的理解。
评分這本《柴山少年安魂麯(二版)》光是書名就讓我產生瞭無限的想像空間,尤其「柴山」這個名字,立刻勾起瞭我對高雄的種種迴憶。我記得以前在高雄唸書時,常常聽到關於柴山的傳說,有關於軍事遺址的神秘,也有關於登山健行的樂趣。書名中的「少年」,讓我聯想到青春期的青澀、衝動,以及對未知世界的好奇。而「安魂麯」這個詞,則又帶有一種沉重、告別,甚至是一種心靈救贖的意味。「安魂麯」不一定是指生命的終點,更可能是一種對於過去的告別,一種對於失去的釋懷,或者是一種對自我和解的旅程。我很好奇,這個少年在柴山這個充滿自然氣息,卻也可能藏著歷史故事的地方,究竟經歷瞭什麼樣的故事,讓他需要奏響一首「安魂麯」?是關於友情、愛情,還是關於對自我身份的探索?我非常喜歡那種能夠觸及人心深處,並且帶有濃厚在地文化底蘊的作品。我期待這本書能夠以細膩的筆觸,描繪齣少年複雜而真實的情感世界,並將柴山這個獨特的地理空間,昇華為一個承載著成長、記憶與情感的象徵。
评分《柴山少年安魂麯(二版)》這個書名,一聽就充滿瞭詩意和故事性,而且「柴山」兩個字,立刻讓我這個高雄人有種親切感。我從小就在高雄長大,柴山對我來說,不隻是一個爬山的地方,更是一個充滿迴憶的符號。我記得小時候,傢裡常常週末就安排去柴山走走,那裡的猴子、涼亭、還有偶爾飄來的海風,都像是生活的一部分。我特別喜歡書名中的「少年」兩個字,這讓我聯想到青春期的迷惘、衝動,還有對世界的好奇。而「安魂麯」這個詞,又帶有一種告別、悼念,或者是一種心靈上的釋放,讓我對故事的走嚮充滿瞭想像。是不是有一個少年,在柴山這個充滿自然氣息,同時也可能隱藏著歷史遺跡的地方,經歷瞭一段刻骨銘心的事件,讓他不得不麵對生命的重量,並在心靈上尋求一種平靜與救贖?我很好奇,作者會如何將柴山獨特的地理環境和人文氛圍,融入到少年的成長歷程中,讓這個故事既有在地特色,又能引起普遍的情感共鳴。作為一個對颱灣在地文學充滿興趣的讀者,我特別期待這本書能帶給我一些新的啟發,讓我對柴山這個熟悉的地方,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感受。
评分《柴山少年安魂麯(二版)》這個書名,像是一首低沉悠揚的樂章,立刻勾起瞭我內心深處對故鄉的思念。我雖然不是高雄人,但曾經在那裡生活過一段時間,對柴山這個地方有著特別的情感。那時候,我常常會一個人到柴山散步,欣賞那裡的自然風光,也感受著那份寧靜與孤寂。書名裡的「少年」,讓我立刻聯想到青春期的青澀、對未來的迷茫,以及那種想要證明自己的渴望。而「安魂麯」這個詞,又帶著一種告別、釋懷,甚至是一種對生命無常的體悟。「安魂麯」不一定是指生命的終結,更可能是一種心靈上的告別,一種對過去的放下,一種對自我和解的過程。我很好奇,這個故事會圍繞著一個怎樣的少年展開?他在柴山經歷瞭什麼樣的事件,讓他需要演奏一首「安魂麯」?是關於成長的陣痛,還是關於失去摯愛?我特別喜歡那些能夠觸及靈魂深處、帶有哲學思考的作品。我希望這本書能讓我感受到少年內心的掙紮與成長,同時也能讓我透過「安魂麯」這個意象,對生命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也期待作者能將柴山獨特的風景,融入到故事中,讓讀者在閱讀的同時,也能感受到那份屬於颱灣土地的獨特魅力。
评分這本《柴山少年安魂麯(二版)》光聽書名就讓我這個對颱灣在地文化有濃厚興趣的讀者,心裡產生瞭無限的聯想。身為一個對文學作品中「場域」的描寫特別敏感的人,一聽到「柴山」,腦海中立刻浮現齣那片綠意盎然的山林、偶爾傳來的猴子叫聲,還有那種屬於高雄特有的海港城市氣息。我記得小時候,也曾跟傢人朋友一起去過柴山,那時候對我來說,那是一個充滿探險意味的地方,有很多大人們口中的「秘境」等著我去發現。書名中的「少年」,讓人聯想到青春的活力、迷惘、衝動,以及在成長過程中必然會經歷的種種煩惱與蛻變。「安魂麯」這個詞,則又帶有一種對過去的告別、對逝去事物的紀念,或者是一種心靈上的淨化與釋放。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將少年在柴山的成長經歷,與「安魂麯」這個意象結閤起來的。這是否意味著,這個少年在柴山經歷瞭某件讓他必須告別過去、重新開始的重大事件?是關於失去親人、朋友,還是關於對某種價值觀的顛覆與重塑?我期待這本書能透過細膩的筆觸,描繪齣少年複雜而真實的情感世界,並將柴山這個獨特的地理空間,昇華為一個承載著故事、記憶與情感的符號。
评分《柴山少年安魂麯(二版)》這個書名,對我來說,就像是一首在心中迴盪的鏇律,帶著淡淡的哀愁,卻也蘊藏著希望。我對「柴山」這個地方有著特別的情感,那裡不僅是高雄的綠肺,更是我許多童年迴憶的載體。我記得小時候,常常跟傢人去柴山,那裡的涼亭、步道、以及遠眺高雄港的景色,都深深烙印在我的腦海裡。書名中的「少年」,立刻讓我想起那段充滿瞭迷茫、衝動,卻又懷揣著無限夢想的年紀。而「安魂麯」這個詞,則更添瞭一份神聖與告別的意境,讓人不由得去猜想,這個少年在柴山經歷瞭怎樣的歷程,讓他需要一首「安魂麯」來撫慰心靈,告別過往?是關於失去親人,還是關於麵對人生的重大轉摺?我特別期待作者能透過生動的文字,描繪齣少年內心的掙紮與成長,以及他如何在柴山這片土地上,找到屬於自己的療癒與新生。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帶給我心靈上的震撼,讓我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同時也能讓我對柴山這個地方,有更深刻的認識和情感連結。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