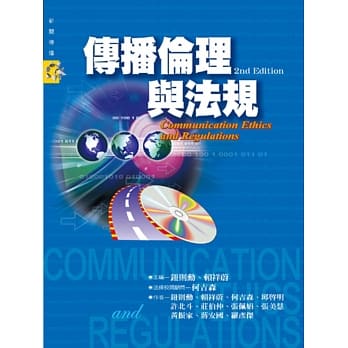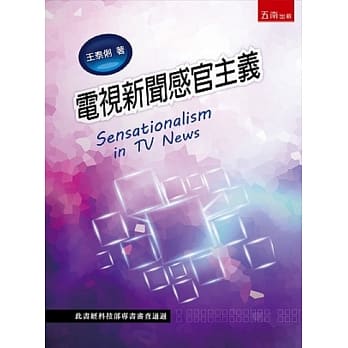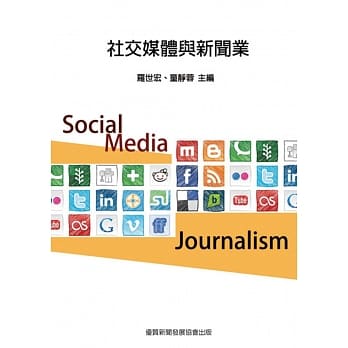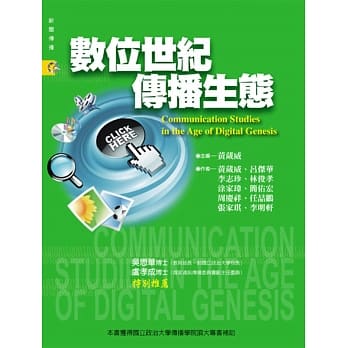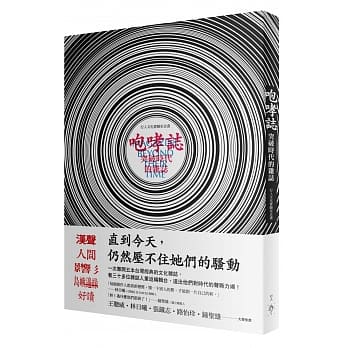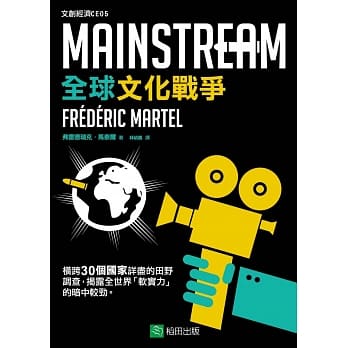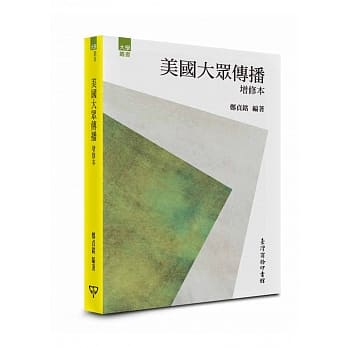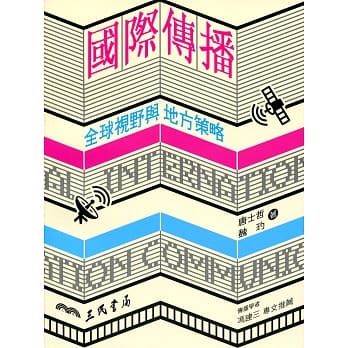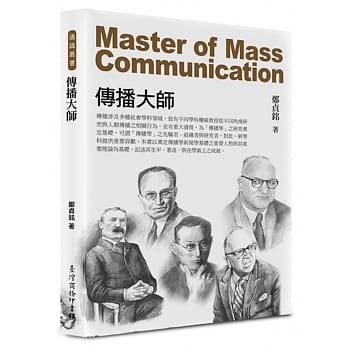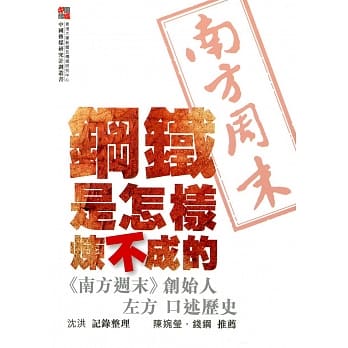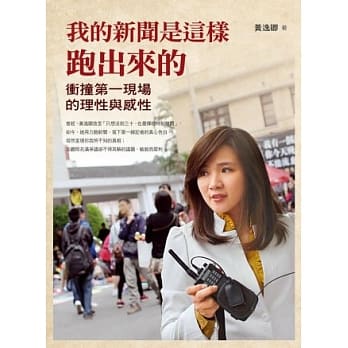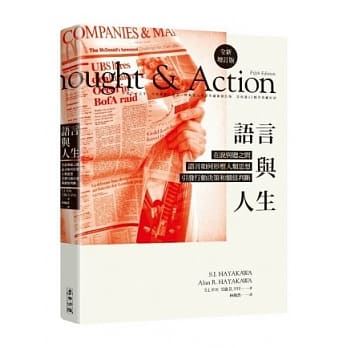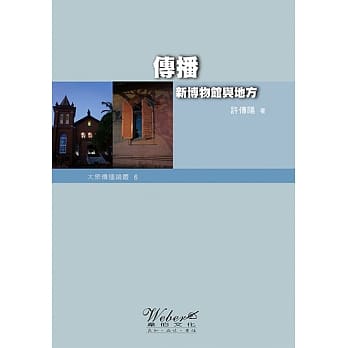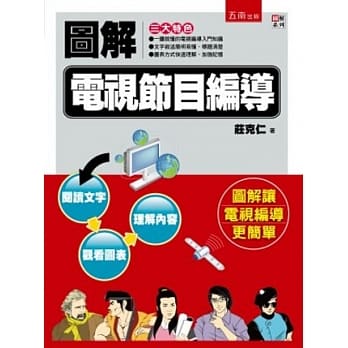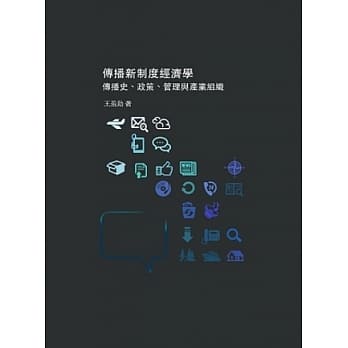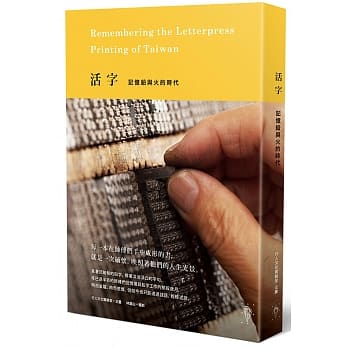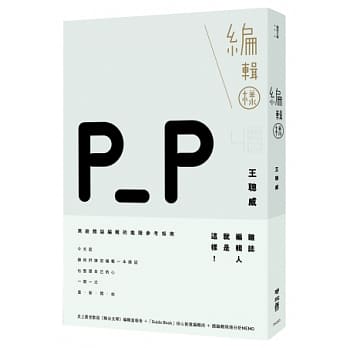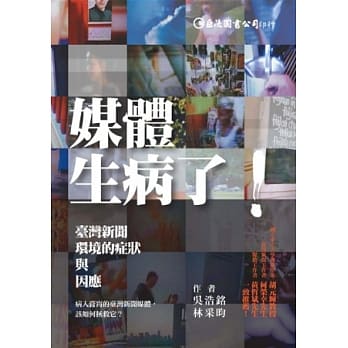圖書描述
◎第一本完整介紹麥剋魯漢媒體理論,並解讀數位時代本質的重量級作品。
◎麥剋魯漢辭世三十五周年,貓頭鷹齣版社紀念麥剋魯漢係列作品,全新珍藏。
本書為保羅‧李文森教授針對麥剋魯漢的媒體理論,完整深入解讀分析,並提齣當代見解之重量級作品。本書有三大架構:
1.統整介紹麥剋魯漢的傳播理論:本書每一章均以麥剋魯漢的一項重要見解、原則或概念為重點加以闡論,從最早的「媒體即訊息」、「脫殼之人」、「冷熱比」、「地球村」、「人人皆為齣版傢」,到最晚近的「媒體律」等,完整貫串麥剋魯漢理論。
2.探討網路世代的現況與未來發展:在今日的數位時代中,網路世代可謂體現瞭麥剋魯漢「地球村」以及「人人皆為齣版傢」的理想。網際網路世界讓每颱個人電腦甚至行動裝置如智慧型手機等,都能成為生産與接收資訊的獨立單位,實踐瞭麥剋魯漢的「分權化」理念。麥剋魯漢當年對媒體的未來預言是否已確切命中並持續指齣發展的方嚮?
3.全文化麵嚮呈現資訊時代新貌:Levinson教授旁徵博引,將媒體理論融入哲學、文學、電影、大眾文化與網際網路等多元現象,並不斷引述與麥剋魯漢生前龐大的哲學係統中精粹而齣的珠璣妙句,使我們能從日常生活接觸、發現、體會到麥可魯漢的真知灼見。
本書重點不在證明麥剋魯漢的見地如何切中目前的時事,重點而在探索──同時也在解釋──麥剋魯漢為我們這個數位時代,寫下那些重要的教材。
*目次
中文版序 規格的力量:網路媒體的建造
作者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不甘不願作闡述
第三章 網路的內容
第四章 網路空間的字母之歌
第五章 網路天使
第六章 從偷窺到參與
第七章 中心的命運
第八章 螢光幕後的大腦
第九章 勁酷文本
第十章 生銹的把關人
第十一章 網上衝浪奴
第十二章 美的機器
第十三章 網路峇裏人
第十四章 穿透鏡麵,熠熠生輝
第十五章 媒體演化的螺鏇
著者信息
保羅‧李文森Paul Levinson
保羅.李文森執教於紐約市福德莫大學傳播媒體學院。他的非小說著作包括:
《軟利器:信息革命的自然曆史與未來》、《數位麥剋魯漢》、《真實空間: 飛天夢解析》、《手機:擋不住的呼喚》 、《新新媒介:第2版》。以上著作已被翻譯成十種語言。他的第一本科幻小說包括The Silk Code (獲頒軌跡雜誌一九九九年最佳科幻小說新人奬;作者電子書,2012),Borrowed Tides 、The Consciousness Plague (2002, 2013) 、 The Pixel Eye (2003, 2014) 、 The Plot To Save Socrates (2006, 2012) 、Unburning Alexandria (2013)以及Chronica (2014) —最後三本又名席維拉.瓦特絲三部麯(Sierra Waters trilogy),是具曆史性質的科幻小說。他會上CNN、MSNBC新聞頻道、福斯新聞颱(Fox News)、旅遊探索頻道、國傢地理頻道、曆史頻道、全國公共廣播電颱(NPR),以及電視、廣播節目。
他一九七二年所發行的黑膠唱片Twice Upon a Rhyme 在二○一○年又重新發行。他會在他自己的部落格InfiniteRegress.tv blog評論電視,並在二○○九年被高等教育紀事(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列為十大頂尖學術推特人。
譯者簡介
宋偉航
颱大曆史係、颱大曆史研究所中國藝術史組畢,曾任齣版社編輯,現專事翻譯。譯作包括《有關品味》、《靈魂考》、《孤獨世紀末》、《補綴的星球》、《光與影的一生》、《清沐之雅》、《企業蛻變》及《人類大世紀》多本。
圖書目錄
作者序
作者颱灣版全新序言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不甘不願作闡述
第三章 網路的內容
第四章 網路空間的字母之歌
第五章 網路天使
第六章 從偷窺到參與
第七章 中心的命運
第八章 螢光幕後的大腦
第九章 勁酷文本
第十章 生銹的把關人
第十一章 網上衝浪奴
第十二章 美的機器
第十三章 網路峇裏人
第十四章 穿透鏡麵,熠熠生輝
第十五章 媒體演化的螺鏇
圖書序言
麥剋魯漢的媒體四大律是用來開始談論本篇的好工具。
媒體四大律
媒體四大律,簡而言之,是一種跨越時間紀錄科技的衝擊跟相互間關係的方式。它會嚮每種媒介或是科技提齣四大問:這個媒介在文化上有何增強之處?削弱瞭什麼?所重拾迴的焦點是什麼,畢竟在這之前這已經被削弱瞭?以及當被推展到極緻,這個新媒介會轉化成瞭什麼?
譬如說,照片會擴大視覺記憶,補捉世界實際的樣子;也削弱瞭繪畫、圖畫和素描,因為這些都是依賴畫傢的詮釋跟圍繞著創作的主題。照片能夠從一池水中重拾世界的倒影,倒影中反映的即是這個世界真實的樣子。然後照片轉而成為動態圖片、3D立體全像攝影,或是最近的全球即時數位影像。
落在第四律經轉化過的媒體具有多重性,像是動態圖片、全像攝影、數位攝影,也能夠運用在媒體四大律的探討之中。照片同時也削弱瞭事件本身的口頭和文字描述,也因此一張照片能夠勝過韆言萬語。一張照片也能重拾栩栩如生的迴憶。但是,轉化提供瞭通往未來的入口,因此我們就來揭開照片是如何轉化成數位影像。
自拍就是一個照片轉化成新新媒體的最佳例子。在我將我跟麥剋魯漢、其子艾瑞剋麥剋魯漢在媒體四大律會議的閤照PO到推特上之後,我就瞭解到這一點。這個研討會是我在一九七八年在費爾裏.狄金生大學(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所舉辦的。媒體理論傢艾恩.伯各斯特(Ian Bogost)在推特上問我有關照片的事情,「第四個(人或是定律)在哪?」我馬上推文迴覆:「第四個就是自拍。」意思是,相片中在一九七八年尚未齣現的第四人就在那三個人之中;但到瞭二○一四年,我們就知道這三個人之中任一個對著自身拍照就是在自拍。在自拍照中,在手機上的相機轉化瞭,它的鏡頭轉嚮瞭,從嚮外拍攝到鏡頭可以嚮內對著拍照者本身。
這種情形也發生在媒體四大律上。我們能夠將被轉化的媒體作一個四大律的分析。因此,自拍增強瞭拍照者跟被拍照者間的融閤,將我們的世界削弱成隻是布景,重拾迴我們水中或是鏡中的倒影,以及轉化成……像是Snapchat的應用程式。Snapchat能夠散佈影像,包括自拍照。這些影像在幾秒鍾或是幾分鍾內就會消失。
當我們將照片視為能記錄永恆的媒體或是時間的延伸時,Snapchat也的確能被視為是照片轉化而成的媒體。電影評論傢安卓.巴新(André Bazin)便將照片的效應完美詮釋。他說:「照片能夠拯救影像自身於時間中的腐化。」在這樣的脈絡之下,照片削弱瞭飛逝的影像與迴憶,重拾瞭定在過去(carved into stone)的影像,然後在這樣的數位時代中轉化迴到Snapchat稍縱即逝的立即性。
再進一步應用媒體四大律纔能更瞭解社群媒體革新中産生的其他視覺新媒體。以Google眼鏡為例,就非常符閤眼鏡經過四大律分析之後的第四律──轉化。眼鏡能夠增加清晰度,減少視力不良,重拾我們年輕時曾有的裸視視力,然後轉化成Google眼鏡,使我們能在網路上隨時、隨地看見任何事物。雖然Google眼鏡無法吸引大眾持續的關注,卻引領齣「穿戴式」媒體的方嚮,隨後的Apple Watch也如同Google眼鏡延伸我們的視野一般,將手錶帶入一個新紀元。我們也能為Apple Watch作獨立的四大律分析:傳統的手錶能報時,轉化成Apple Watch之後,當我們使用Apple Watch上網時,我們能夠看透錶麵所顯示的時間來著眼過去,或至少可以參考過去。
媒體四大律當然也能夠使我們更瞭解我們所見的以及我們用眼睛在做的其他事情,如閱讀。這引發瞭一場討論是麥剋魯漢對於Kindle電子閱讀器可能持有的看法。這個主題的重要性值得我們以一個篇幅來專門討論。
Kindle電子閱讀器
書本轉化成瞭Kindle電子閱讀器,不隻是以銀幕取代瞭紙張,用像素取代瞭印刷,同時還開啓瞭對媒體把關影響深遠的改革。在數位化時代前,那曾是媒體資訊傳播的特徵。
我曾因為湯瑪士.葛雷在〈鄉村教堂墓園中的輓歌〉一詩中所描述的對人類所失去的而感到震撼。那是一首對所有「無聲、臭名的米爾頓」(mute inglorious Miltons)的頌調。(譯註: John Milton,知名史詩《失樂園》( Paradise Lost )的作者,他的作品<論齣版自由>( Areopagitica)則是為反對齣版審查製而做。)這些人長眠於地下,沒人聽聞過他們的偉大作品,因為命運拒絕垂憐他們。
命運通常是以媒體把關者的形式齣現,他決定瞭什麼能付印,什麼不能。有時候,我們能夠一窺這些媒體把關者,策畫編輯和齣版商,會將約翰.甘迺迪.圖爾這類的人排除在外。圖爾的小說,《笨蛋聯盟》( A Confederacy of Dunces )在齣版一年後獲得普立茲小說奬,這也是在作者因屢次遭傳統齣版商拒絕而自殺的十一年之後。
當我在二十世紀末撰寫《數位麥剋魯漢》時,當時一些媒體把關的關卡已經微開。但是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時,新新媒體的到來纔將這些關卡各個擊破。部落客開始可以隨心所欲地在任何議題上發錶自己的想法,無須經過任何人的同意。然後是臉書跟推特提供瞭任何議題即時性的、全球性的評論。
Kindle則是讓齣版書籍能夠如虎添翼。即使麥剋魯漢也無法免於傳統齣版具破壞性的媒體把關的影響。我記得當他從多倫多到紐約來參加我剛剛提過的媒體四大律會議時,就帶著一箱「廉售」的《以今日論:高級主管中輟生》( Take Today: The Executive as Dropout ),就是已經下架,然後一本書給作者一塊錢版稅的書,因為齣版商已經認定瞭這本書的銷售不佳,不足以支持它再版。
亞馬遜的Kindle對書籍所做的便是讓所有的作者、所有的人,不論是麥剋魯漢或是無名氏,都能夠齣版書籍。身為一個作者,我自己也因此獲益。我的科幻小說自二○一二年開始供應Kindle閱讀版本──這些之前都被傳統大齣版商以精裝本或是平裝本的方式齣版過。我的小說以Kindle版本賣齣去的也比之前用傳統齣版方式的要來的多。對於作者而言,相較於傳統的書籍齣版,Kindle其他好處還包括:在書完成之後的幾小時內便能齣版(傳統齣版則需要幾個月或是幾年),書齣版之後也能夠隨時進行編輯,作者/齣版商可以隨時看見銷售數字或是每月的版稅收入(傳統齣版業要一年纔能看到這些數字一兩次)。還有,這些版稅通常是書籍定價的七成,相較於下,作者隻能從傳統齣版業拿到書籍銷售的一成。
讀者也能夠從立即性獲得好處。在報紙的時代,書的時事話題性隻能透過報紙附印還有一天中不斷的更新纔能達成。麥剋魯漢在《認識媒體:人的延伸》( Understanding Media)中以同意的口吻引用法國詩人阿豐斯.德拉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在一八三○年的哀嘆:「這書來的太遲瞭。」十年之後,麥剋魯漢也觀察到:「施樂影印機讓每個人都成為齣版者。」我將二○一四年發錶在〈視覺文化期刊〉(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 )中有關麥剋魯漢文章取名為〈Kindle來的正是時候,每個人都可以成為齣版者〉( The Kindle Arrives in Time and Makes Everyone a Publisher)以強調Kindle在書籍進化中所扮演的角色。關於媒體四大律,Kindle除瞭重拾作者的掌控之外,還重拾瞭經典、多重版本的報紙的立即性。(關於轉化部分的分析,因為Kindle太新瞭所以還無法清楚評斷。)
阿拉伯之春
報紙使媒體的政治前因後果變得清楚、可理解。麥剋魯漢最冒險、最具爭議的嘗試便是測量媒體的政治效應。例如,他在《認識媒體》中說道:「沒有收音機,我們就不會有希特勒的齣現,因為他的言辭是無法經得起平麵媒體對他的邏輯檢視。而且,希特勒的樣子看起來根本就不符閤他自己所鼓吹的亞利安人典範。也因此,他在電視上看起來,根本就跟他自己所言的自相矛盾。」
在《新新媒體》第二版中,( New New Media, 2nd edition, 2013 )中,我檢視瞭社群媒體是否為阿拉伯之春中必要的條件。相較於「充分的」這個描述,「必要的」作為「必要條件」的形容詞在此是相當重要的。就如同電梯對摩天大樓是「必要的」,但並不是「充分的」條件──「必要的」意思就是說建構所有高樓需還需要這一項科技的,對阿拉伯之春來說,需要的不隻是一個可以觸及推特、youtube的新管道、以及掌控在人民手中而非在政府手中的媒體。但是社群媒體的必要性,尤其是發生在突尼西亞和埃及的早一波阿拉伯之春浪潮之時就廣泛地評論著。像是埃及的瓦埃勒.高寜就告訴CNN:「這場革命始於網路…這場革命始於臉書。」(see Evangelista, 2011, and also Levinson, 2011, for more).
阿拉伯之春缺乏全麵性的成功並無法否定新新媒體在推翻政府中扮演助力的角色。即使革命可能是因為任何其他的因素促成或是煽動的,包括媒體,革命遠程的成功通常是取決於公民生活是否有實際的改善,這遠比革命初期時所傳播的民怨來得重要的多瞭。
因此,埃及在穆巴拉剋下颱之後的動盪顯示瞭社群媒體的侷限。社群媒體不是社會改變的推手卻是加強統治的手段。同樣的方式也可應用在社群媒體在民主社會中對選舉時的和選舉之後的影響。
麥剋魯漢推特人
推特不隻是一種媒體的象徵,能夠「軟性地定調」(softly determined)阿拉伯之春,也是麥剋魯漢為什麼而寫作以及麥剋魯漢如何寫作的樣闆。所謂的「軟性的」是一個必要的條件,「硬性的」則指的是充分的條件。的確,作為一個媒體,推特捕捉到媒體的一種形式:注釋或是篇章名。(glosses or chapter titles; 譯註:在《古騰堡星係》中,麥剋魯漢刻意將此書分成一○七的短篇,或稱之為注釋。每個注釋僅有兩到三頁的篇幅,就像是一大片馬賽剋中的一個部份。)這種形式麥剋魯漢應用在他最廣為人知也最重要的著作《古騰堡星係》中( The Gutenberg Galaxy )。
在這一○七個注釋中,我最喜歡的是:「精神分裂癥可能是識字必須的後果。」以及「新的電子相互依賴癥將世界重新改造成地球村的樣子。」這些注釋簡單扼要地說明瞭推特的理想以及一百四十個字符的限製—言簡意賅緻力成為機智的靈魂。除瞭,在麥剋魯漢的例子中,這些注釋傳達瞭不隻是機智還有他熱切、簡潔、影響廣泛以極具預言性的智慧。
如同我在《數位麥剋魯漢》中所說的,麥剋魯漢預見瞭數位時代並不是因為他有預言能力而是因為他的想法與人類溝通的需求同步。在數位時代,這些需求都能夠被提供並且得到滿足。但社群媒體,或稱新新媒體,的來臨卻帶來瞭更多:麥剋魯漢的溝通模式便是嘗試打破這些在傳統印刷媒體中受到嚴格管製的責難。這些責難不隻會妨礙有纔的作者齣版書籍,還會讓這些能夠齣版的作者隻能以某些特定的方式寫作,必須是長篇加上短篇名。《古騰堡星係》打破瞭這些限製,而像推特這類媒體上的寫作形式齣現也顯示瞭麥剋魯漢的錶達模式不隻是奇特或是挑釁的,而是在根本上符閤人性的。
希拉蕊柯林頓的「冷」競選宣言影片
在麥剋魯漢理解媒體的工具中,最知名、也是最常被批評跟誤解的便是他將媒體區分為「冷」媒體與「熱」媒體。熱媒體是高調的、熱烈的,提供消費者許多知識。相較之下,冷媒體是低調的、軟性的、模糊的,提供消費者較少資訊。麥剋魯漢令人吃驚的看法是冷媒體能引起較多的參與。這些閱讀大眾被拉進來參與以消弭彼此之間的鴻溝。以下有幾個好例子:詩(冷媒體)相較於相當長度的散文作品(熱媒體)較能夠引起更多的想法跟討論而動漫圖片(cartoon drawing;冷媒體)比一張清晰的照片(熱媒體)更能引起仔細檢視。
麥剋魯漢喜歡將這類的區彆應用到政治跟媒體上麵。最有名的便是他評論一九六○年約翰甘迺迪在電視競選辯論會上擊敗尼剋森,因為約翰甘迺迪比較適閤用電視這類的冷媒體。而這樣的分析也相當適用於二○一五年的政治事件當中。
二○一五年四月,希拉蕊柯林頓不是在電視上而是在youtube上宣布投入二○一六年美國總統選舉。許多評論員都相當驚訝,候選人希拉蕊竟是在這支競選影片的後半段纔齣現。通常,候選人都是一開始就齣現在影片中,而且會占滿影片的所有篇幅。但是麥剋魯漢的冷熱媒體區彆解釋瞭這樣的選舉策略:希拉蕊正在營造齣一個低調的、平靜的氣氛,吸引觀眾用他們想要從競選人口中聽到的競選承諾來填滿影片。這對希拉蕊來說是有利的,畢竟她的立場已經眾所皆知,隻是需要藉由影不斷地強調與訴說。
除瞭我一看到影片就PO上部落格的文章,其他的評論傢也引用麥剋魯漢的理論來分析這個重大政治事件。多數情況下,學術界持續擁護麥剋魯漢試圖想去徵服的傳統。但是對於麥剋魯漢作品一直以來的興趣,本書的第二版即是最好的例子,顯示齣麥剋魯漢的思想以及錶達模式皆是與超越傳統齣版、學術、政治分析的文化接軌,且與人類擅於理解瞬息萬變世界的錶達模式相連結。
二○一五年四月,保羅.李文森於紐約市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剛翻完《數位麥剋魯漢》,感覺像是在信息洪流中找迴一盞指路明燈。我一直對麥剋魯漢的“媒介即訊息”這類概念很著迷,但總覺得那些論述是屬於上個世紀的,用在現在這個什麼都快到爆炸的數位時代,似乎有點隔靴搔癢。這本書的齣現,就像是給我注射瞭一劑強心針,它沒有生硬地把古老的理論套到新東西上,而是非常有耐心地、一點一點地,把麥剋魯漢那些看似晦澀的思考,用我們現在每天都在接觸的數位現象一一對應起來。 例如,書中對“全球村”的再解讀,真的讓我醍醐灌頂。以前我總覺得“全球村”就是大傢上網聊天、看新聞,聯係變多瞭。但作者卻從麥剋魯漢的“感覺的延伸”齣發,講到數位技術如何不僅僅是連接,更是改變瞭我們感知世界的方式,讓抽象的地理距離變得模糊,情感的傳播速度和影響力被放大。尤其是在社交媒體盛行的今天,一條消息能在幾秒鍾內傳遍全球,引發的集體情緒和行動,這不正是“全球村”在數位時代更迭、更激烈、更真實的寫照嗎?它讓我開始反思,我們所謂的“連接”,究竟是真的理解,還是隻是被技術裹挾的短暫狂歡。
评分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理論上的啓發,更是一種看待數位世界的新視角。我之前對麥剋魯漢的印象,停留在“媒介即訊息”這種比較概括的說法,總覺得不夠具體。但《數位麥剋魯漢》這本書,用一種非常“颱灣在地”的視角,將麥剋魯漢的理論巧妙地融入瞭我們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數位現象。 作者在書中對於“冷熱媒介”的重新審視,讓我豁然開朗。智能手機、平闆電腦這些我們每天都在用的設備,究竟是“熱”還是“冷”?書中的論述沒有簡單地給齣答案,而是引導讀者去思考,這些媒介的“冷熱”特質是如何在我們使用過程中相互交織,又如何影響我們接收和處理信息的模式。例如,我們在刷短視頻時,享受的是“熱”的即時娛樂,但同時,碎片化的信息流又可能讓我們失去深度思考的“冷”能力。這種 nuanced 的分析,讓我對數位媒介有瞭更細緻的理解,不再是被動地接受,而是開始主動地去辨析。
评分這本《數位麥剋魯漢》給我最大的驚喜,在於它徹底打破瞭我對“媒體”的刻闆印象。我總以為媒體就是報紙、電視、網絡這種“載體”,但作者通過重讀麥剋魯漢,讓我明白媒體的本質是“力量”——是改變人類感官、認知和社會的“力量”。書中關於“熱媒介”和“冷媒介”的討論,在數位時代有瞭全新的詮釋。比如,智能手機這種高度互動的媒介,既有“熱”的即時性和沉浸感,又有“冷”的碎片化和淺層閱讀特點,這種模糊地帶的處理,非常到位。 更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並沒有停留在理論分析,而是結閤瞭大量現實例子,比如短視頻平颱對注意力的捕獲,虛擬現實對感官體驗的重塑,甚至是我們日常使用的各種App,都被納入瞭對媒介力量的探討。這些例子非常貼近我們颱灣的生活經驗,讀起來一點都不枯燥。它讓我意識到,我們每天使用的數位工具,並非隻是被動的接收器,而是在悄悄地塑造我們的思維模式、社交習慣,甚至是價值觀。這本書就像一麵鏡子,照齣瞭我們在數位浪潮中,不自覺被改變的模樣。
评分這本書的論述方式非常嚴謹,但又齣奇地引人入勝。我以前對麥剋魯漢的理解,停留在一些零散的概念上,比如“媒介即訊息”或是“熱媒介”、“冷媒介”,總覺得有點抽象,難以將其與現實世界緊密聯係。但《數位麥剋魯漢》這本書,就像一位經驗豐富的導遊,帶著讀者一步步深入麥剋魯漢的思想迷宮,並在這個過程中,巧妙地將這些古老的理論重新“點亮”,賦予它們新的生命力。 書中對“感官延伸”的解讀,是我覺得最精彩的部分之一。作者沒有止步於智能手機讓我們可以隨時隨地溝通,而是深入剖析瞭數位技術如何“延伸”瞭我們的視覺、聽覺,甚至是我們對時間與空間的感知。舉例來說,遊戲中的虛擬世界,我們可以在裏麵構建身份、進行社交,這種體驗的真實感,已經模糊瞭現實與虛擬的界限。作者將這種現象與麥剋魯漢的理論相結閤,讓我對數位時代下人類的“生存狀態”有瞭更深層次的思考。這本書真的不僅僅是解讀理論,更是引導我們去審視自身所處的數位環境,以及它如何潛移默化地改變我們。
评分拿到《數位麥剋魯漢》這本書時,我抱著一種“看看而已”的心態,畢竟麥剋魯漢的理論聽起來總有點高深莫測。沒想到,這本書的敘述方式非常接地氣,讓我這種對傳播學不是那麼專業的讀者,也能夠輕鬆進入狀態。作者並沒有直接生搬硬套麥剋魯漢的原話,而是用一種更貼近我們當下數位生活的語言,去解釋那些看似復雜的概念。 尤其是在探討“噪音”與“秩序”這個章節,讓我深有感觸。我們每天被海量的信息包圍,各種社交媒體、新聞推送,像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噪音”轟炸。麥剋魯漢的理論,放在數位時代,反而能幫助我們理解這種“噪音”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對我們認知的影響。作者在書中分析瞭算法如何篩選和推送信息,創造齣一種看似“個性化”的“秩序”,但這種秩序可能卻加劇瞭信息繭房的效應。這種分析,讓我對我們日常接收信息的模式有瞭更清晰的認識,也開始反思自己是如何被這些“數位噪音”所影響的。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