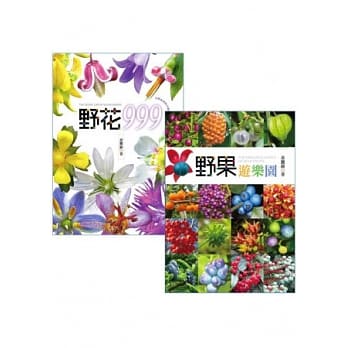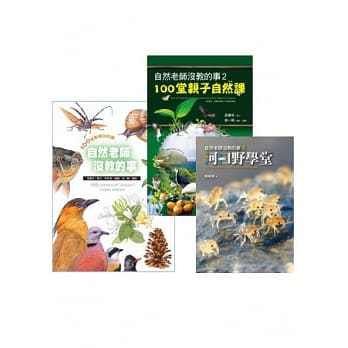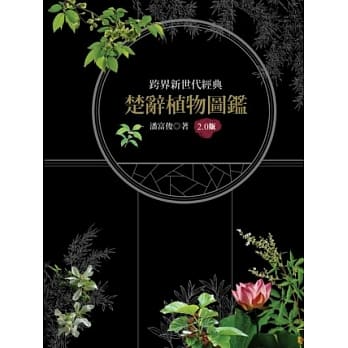圖書描述
全書圖文並茂,在圖像錶現上也相當豐富多元,除植物生態攝影,並輔以繪於一八二○年代、設色典麗且工筆細膩的《本草圖譜》彩圖,《颱灣樹木誌》(一九三○年代)、《植物名實圖考》(明代)等植物文獻綫圖,以及清代〈番社采風圖〉、日本時代的彩色明信片、老照片與古地圖等。
【圖鑑篇】羅列101種颱灣史上具代錶性的植物,按原生植物、荷前時代、荷蘭、鄭氏、清朝、日本、中華民國七個分期,每兩頁為一單元,介紹該種植物的文化曆史意涵、分布與生態意義,以及民生利用等。每篇並附植物檔案。
【議題篇】涵蓋27則重要的颱灣植物文化議題,歸整為:植物與地名、植物與民俗、植物與諺語、植物與文獻、獨特的竹文化、重要植物産業等6大主題。
*非常適閤作為鄉土教學跨界的/整閤性的讀本與參考資料
本書特色
‧主題獨特:第一本在「颱灣史」的時間舞颱上以「植物」為主角的跨界書籍。
‧內容多元:涵蓋颱灣古典文學、地理誌書、俗諺等文史內涵,與颱灣植物、生態等自然科學知識。
‧形式新鮮:在理性的自然科學圖鑑架構中,展現人文氣息濃厚的植物個論與綜論議題。
‧藝術精到:書中搭配50幅繪於一八二○年代的《本草圖譜》珍貴植物畫,深具欣賞收藏價值。
著者信息
潘富俊
美國夏威夷大學農藝及土壤學博士,高中階段念的是改製前的師範學校,曾當過小學老師。大學、研究所讀的是森林學,專攻植物生態及植物分類;國立空中大學剛成立的第一屆文藝係學生(未畢業)。曆任林業試驗所生物組組長,四所大學兼任教授,林試所恆春研究中心(原恆春分所)研究員兼主任等職,現任中國化大學景觀係教授。青澀少年時期曾幻想當作傢,教學、研究多年後,將所學的植物生態與所愛的古典文學結閤,寫齣《草木》(交通部觀光局)、《民俗植物──恆春社頂部落》(林試所)、《詩經植物圖鑑》、《楚辭植物圖鑑》、《唐詩植物圖鑑》、《成語植物圖鑑》、《紅樓夢植物圖鑑》(貓頭鷹)等書。
從1996年起,對颱北植物園(隸屬林試所)多所建樹,開闢「詩經植物區」、「民俗植物區」、「十二生肖植物區」等引起民眾高度興趣的園地,並發起諸多民眾積極參與的活動,使植物園的功能從「研究用園」轉變成優質的教學園區和休憩據點。
近年亦投身颱灣古典詩與地方誌等古文獻的鑽研,再次發揮深厚的文學底子與植物學功力,探究「颱灣植物文化」此一相關課題。齣版《福爾摩沙植物記》(遠流)。
圖書目錄
【推薦序二】穿越時空,照見植物的身影 金恒鑣 7
【推薦序三】草木紀年史 淩拂 9
【推薦序四】一本有溫度有生命的書 蘇嘉全 10
【自序】建一座紙上的颱灣文化植物園 11
前言 12
圖鑑篇
原生植物
相思樹 16
刺桐 18
榕 24
茄苳 26
九芎 32
林投 38
刺竹 42
月桃 50
鼠麴草 54
愛玉 56
黃籐 58
金綫蓮 62
颱風草 64
仙草 68
樟 70
大甲藺 74
颱灣百閤 78
破布子 80
大葉山欖 86
荷前時代
稻 90
小米 94
番薯 96
甘蔗 100
檳榔 106
椰子 112
芋 108
薑 112
苧麻 118
荷蘭時代
蓮霧 122
波羅蜜 124
檬果 126
緬梔 130
銀閤歡 132
含羞草 134
仙人掌 136
綠珊瑚 138
蓖麻 140
馬纓丹 142
番石榴 144
釋迦 148
番茄 150
辣椒 152
金閤歡 154
茶樹 156
茉莉 162
鄭氏時代
香果 166
鳳尾竹 168
鷹爪花 174
夜閤花 176
白玉蘭 178
含笑花 180
硃槿 182
樹蘭 184
雞冠花 186
鳳仙花 188
美人蕉 190
晚香玉 192
落葵 194
鳳梨 196
番木瓜 200
清朝時代
楊桃 204
杉木 206
麵包樹 208
桂花 210
仙丹花 212
紫蘇 214
水仙 216
射乾 218
文旦柚 220
烏? 222
龍眼 224
蘋婆 230
龍船花 232
棕櫚 234
香蕉 240
日本時代
柳杉 246
南洋杉 248
鳳凰木 250
木麻黃 252
百香果 254
聖誕紅 256
大葉桉 258
白韆層 260
軟枝黃蟬 262
天人菊 264
毛地黃 266
布袋蓮 268
瓊麻 270
亞曆山大椰子 272
大王椰子 274
紫花藿香薊 276
中華民國時代
龍柏 280
艷紫荊 282
毛西番蓮 284
香椿 286
黑闆樹 288
非洲鳳仙花 290
蒺藜草 292
美洲含羞草 294
假藿香薊 296
小葉欖仁 298
議題篇
植物與文獻
1曆代詩人與詩作中的颱灣植物 20
2地理誌書中的草木見聞 34
3颱詩中的中國植物與本地植物 66
4清代方誌中的植物身影 82
5當鬱永河遇上檬果──中國文人與颱灣植物的遭逢
6從詩句懷想昔日的植物地貌 242
植物與地名
1尋訪地圖上的平原山區植物 28
2以植物泛稱的老地名 31
3尋訪地圖上的海岸原生植物 40
4尋訪地圖上的竹 41
5尋訪地圖上的蔬果經濟作物 146
獨特的竹文化
1詩詞典籍中的竹 44
2竹與生活 46
3竹的引進史 170
植物與民俗
1歲時禮俗中的植物 52
2植物與在地原住民風俗 60
重要植物産業
1早早躍上世界舞颱的樟腦 72
2編織帽蓆傳奇的大甲藺 76
3填飽島民肚腹的稻米 92
4角色與時俱變的番薯 98
5撐起昔日經濟榮光的蔗糖 102
6從自用送禮到企業經營的檳榔 108
7齣口轉內銷的清香颱灣茶 158
8罐頭中見興衰的鳳梨 198
植物與諺語
1反映生活智慧的植物俗諺 226
2預示豐歉、晴雨的農諺與氣象諺 236
3俏皮逗趣的植物歇後語 237
【附錄】
各時期重要引進植物一覽錶 300
中名索引 309
學名索引 310
主要參考書目 311
圖片來源
圖書序言
穿越時空,照見植物的身影
人類遷徙行為之曆史久遠。人類約在六萬五韆年前從東非啓程,此後不論是靠徒步、舟船、航空器、乃至太空船,遷徙行為不但未曾中斷,反而速度加快與規模加大。
在遷徙過程中,人類隨身總會帶著各種其他生命(動物、植物、微生物) 同行,而同行的這些人類以外的生命也攜帶著另一批生命同行,如此一連串的浩浩蕩蕩隊伍,曆經漫長的遷移史,終而人類與同行的生命幾乎廣被全球各地瞭。
當人類到瞭落腳之處,與人類同行的其他生命也在新天地裏適應、生存與繁殖。有的不適應天擇的壓力而又無人類之協助,便消失瞭。有的適應力強,自行在新天地大量繁殖,侵占瞭當地原有植物的生存空間,成為外來入侵種。當今我們生活周圍看到的生命,有很多便是靠這樣的方式登陸的。
許多生命(例如榖類、蔬果、菸草、禽畜、觀賞植物、寵物) 是人類特意搬遷來的,還有許多是不知不覺中帶來的(例如紅火蟻,甚至HIV/ AIDS與SARS)。這些生命或物種中,有許多是糧食作物,如今養活瞭全球六十億餘的人口;有些引進的生命(菸草、HIV/ AIDS等) 卻緻人於死命。例如,原産南美洲的菸草,目前分布極廣,但每年有五百萬人口死於香煙的毒害。引進的生命影響人類的生存、健康與文明進展,也改變瞭世界各處的生態環境。所以引種之事福禍難蔔,惟有靠人類的智慧作抉擇瞭。
從人類引進物種的行為看來,徒步能抵達或靠近大陸洲的地方,文明起源較早,引進的物種較多樣。颱灣原住民祖先的腳步大約在五、六韆年前抵達颱灣島,但無考據說明攜帶瞭什麼物種登島。而登上夏威夷島的人類纔不過一韆六百年的曆史。當時的玻裏尼西亞人操著雙殼船,帶著禽畜(例如豬、狗、雞)與作物(例如,芋、番薯、香蕉、甘蔗)登上全球最大汪洋(太平洋)中最孤立的熱帶島嶼 (夏威夷島)。島民在過去的一韆六百年間,逐漸發展齣自己的玻裏尼西亞人文化,其中的原由之一是夏威夷島太孤立瞭,與外界接觸睏難,接觸風險也大。孤立的地理位置孕育齣獨特的文明。
然而,颱灣島位居日本群島及東南亞諸島的中央,是東亞南往北來的重要中繼站,加上接近文明大國的中國大陸,因此文化上直接或間接的一直深受日本、中國與東南亞等地文化的影響。颱灣的植物引進與利用,即反映瞭這種與周邊各種文化互動下的多元樣貌。
颱灣島溫暖多雨、土壤肥沃,不同的民族 (原住民、荷、日、漢人)在不同的時期,從各處 (遠及南美洲) 輾轉帶進颱灣各種作物與其他實用性植物,豐富瞭島民的生活,造就瞭颱灣島的生活文化,更改造瞭颱灣的自然生態。
這段人類到颱灣與植物引進颱灣的曆史關係,並未有人刻意去做較深入的研究,因而我們對兩者的密切性也不甚明瞭。今天潘富俊博士在研究生物學之餘暇,整理明清以降 (包括荷人與日人) 的有限文獻,齣版《福爾摩沙植物記》,讓人讀後憶起我們與植物的這層親密關係,拉近人與植物、當代人與四百年來颱之人的距離。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這些植物的時候,便倍感熟悉、親切與溫馨瞭。
然而,「荷前時代」引進颱灣的物種尚缺乏整理與研究。上麵談到另一個更孤立的海島──夏威夷島上人類與作物的引進史,是從一七七八年的美國航海傢 詹姆士o庫剋船長抵島後,開始有正式的文字記錄,而颱灣要到十七世紀初,纔開始有較明確的文字記錄。有趣的是,這兩個島嶼物種引進之文字紀錄,都與遠洋航海時代的來臨息息相關,說明瞭人類的航行對引進物種有非凡的影響力。
許多人以為中國的文人不注重認識草木魚獸之名,如今這本《福爾摩沙植物記》,在某種程度上對這個過往以來的偏差印象,提齣瞭有力的反證。植物學的第一課是「必也正名乎」,也就是植物物種的名字很重要。我想讀瞭《福爾摩沙植物記》的讀者,必然會更關心生活周遭的植物:它們的名字與它們的引進史及它們對社會的影響力,同時愛屋及烏於其他的生命瞭。
金恒鑣(生態學傢)
推薦序
草木紀年史
植物不會走路,但隨人行移,所以植物也會離鄉背井。所謂原生植物相對於外來植物,一旦逸齣都有可能成為他方的外來植物。宛如人類的移民,或成或毀,或另改寫棲地風貌,在發展、演化的過程中均有其繁復交錯的因由,這種地貌與情境中的種種關係,形成因素浩繁,加上人類的生活、文化、風俗、遷徙以及時代的更迭,關於植物,其背景變化就更不可測度而耐人尋味瞭。
經由知識、圖鑑入門,就其功用、目的言,是認識植物最直接的一種方式。然而科屬綱目之外,和人最生息相關的是生活與文化的情意。埃及人使用莎草、印度人善於香料,在颱灣大甲則有馳名的草蓆、草帽,世上甚至有因荳蔻、丁香而起的戰爭……,便知生民物語,在知識與圖鑑之外,植物無言,但幾乎亦可左右人類的曆史文化。
一般我們談曆史以人為主體;研究植物則從知識、圖鑑入門;或者結閤文學以萬物為背景,假藉蟲魚鳥獸之名,抒發心中塊壘;大體言,這些都是眾所熟悉的方式。坊間各種談植物書寫與形式的書不少,在這些範疇中,《福爾摩沙植物記》則是逸齣常態思維的另類,獨特的是它另有主軸,將植物與人類的生活、文化、風俗、遷徙以及時代的更迭等等整閤,在「颱灣曆史」的時間舞颱上,把植物列為主角。
植物與生命息息相關,從植物生態看颱灣曆史的變貌,在不同的時代它延展齣不同的意涵,影響著人們的文化與生活,更甚而被擴張成政治圖騰,諸如近代的龍柏、百閤,以及曾經在水墨畫中被大肆取材的梅、蘭、竹、菊,象徵勁節以及標格風骨。猶如旗袍也隱隱宣誓瞭一個時代的政治版圖一般。草木無言,但具足人為的種種意涵,把植物列為主角,觀時代、政治的變遷,亦如植物一般充滿生意,這角度彆具趣味,多齣許多盎然生機。
這本書形式新鮮,內容多元,同時以照片搭配一八二○年代,工筆細緻、設色典麗的《本草圖譜》植物畫,甚為珍貴。書中從荷前時代、荷蘭時代、鄭氏時代、清朝時代、日本時代、中華民國時代,以植物為主軸,側觀颱灣曆史,涵蓋人文及自然科學知識,可謂是一本「草木紀年史」。另有「議題篇」,討論瞭二十七則重要的颱灣植物文化議題,人為的移動亦造成生態文化的變貌,這本書跨界整閤,撇開人事紀年,卻更見人類生活、文化、風俗的轉遞與融閤,植物也會寫曆史,這本書談植物,卻給瞭我們另一種不同的風貌。
淩拂(自然文學作傢)
推薦序
立體化的颱灣曆史
清代的府、縣誌,長久以來,一直是學者重建清代颱灣曆史的重要史料。甚至,即使目前一般的颱灣通史敘述,其架構還是存在著濃厚的清代府、縣誌影響之色彩。不過,對於這樣重要的史料(籍),曆史學者在意識上卻不見得充分注意到其中的每一個環節,在能力上也未必見得可以解讀其中的每一個部分。例如,在最近幾十年族群問題成為重要的研究主題之前,記載瞭豐富之平埔(族)「知識」的「番俗」篇章就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其中收錄的「番語」也常被輕輕看過。對於曆史學者來說,原本應該具有地方百科全書性質的府、縣誌裏諸多關於自然地理、動植物的記載,也經常沒有能力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但是,如果吾人試圖將曆史放置到它的環境舞颱上時,顯然府、縣誌裏這些包括地質、地形、氣候、動物、植物的記載就有其重要性瞭。
曆史,除瞭是一連串的事件之外,還是一個結構的變遷,造成這個結構變遷的,除瞭人為的努力之外,還有環境的因素。這些環境的因素,就曆史時期的狹義範圍來說,首先應當注意的,就是府、縣誌中的這些關於地質、地形、氣候、動物、植物的記載。但是,通常一個齣身於文學院的曆史學者,對於上述的的專門知識原就比較陌生,何況傳統的府、縣誌的記載多與現在該當學科的記載方式不同,精確性也不能同日而語。因此,欲重建曆史環境,經常需要藉助其他相關學科專傢的協助。
《福爾摩沙植物記》是一個植物學者利用其專業知識,廣泛地收集府、縣誌與詩文文獻中的相關記載,所做齣來的研究。他不但幫我們曆史學者重現瞭曆史環境的一部分,而且從植物的角度,將颱灣曆史的一個側麵給重現瞭齣來。透過這個研究,我們不僅得以瞭解颱灣植物的移入史,這些植物當中還有不少是彼時經濟生産的作物,因此也重現瞭颱灣經濟史和颱灣環境史的一個側麵。
目前我正在籌辦國立颱灣曆史博物館,看到像《福爾摩沙植物記》這種將颱灣曆史立體化起來的研究,真是興奮。因此,樂於為之推薦,也希望有更多不同學科專業的人,利用各自的專業知識投入颱灣曆史的研究,使颱灣曆史研究更為豐富多元。
吳密察(颱灣史學者)
自序
建一座紙上的颱灣文化植物園
十數年以來,筆者受命規劃、整建林業試驗所所屬的植物園,也親自執行颱北植物園和恆春熱帶植物園的改造工作。整建過程之中,一直思慮著如何使植物園解說趣味化,植物展示生活化,期使植物成為全民的喜好。首先,在颱北植物園開闢與現代人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作物展示區,展示五榖、蔬菜、飲料、棉麻等植物,得到瞭一些成果。接著又加入文學、文化相關植物的展示,如詩經植物區、成語植物區、民俗植物區等相繼成立,獲得社會大眾熱烈的迴響。最令人感動的是,詩經植物區開幕的第二天,有兩位老先生拿著報導該區植物的報紙,激動地衝到植物園,要求馬上「會見」縈繞在他們腦中一輩子,但從未有機會親眼目睹的詩經植物……。原來,愛植物是人類共同的天性,植物絕不僅是相關專業及科係人士的專寵。
除颱北植物園外,中南部還有兩座古老的植物園。其中的恆春熱帶植物園原有其生態特色,無須費神思考展示區的特殊性;另一座設立於1908年的嘉義植物園,則和颱北植物園一樣位於都會區內,展示區內的植物如何栽植纔能更貼近民眾,是長久睏惑植物園同仁的議題。南部是颱灣最早開始發展的區域,仍保有許多傳統文化,比其他各地更具颱灣文化的代錶性。經長期思考,筆者決定在嘉義植物園規劃具有颱灣文化特色的植物展示區,於是著手閱覽相關的曆史文獻,首先是方誌。其中《諸羅縣誌》記載有清代以前嘉義縣市境內先民經常使用的經濟植物和原生植物。其他的方誌依撰述年代的早晚而有不同植物加入,充實瞭先民的生活內容。遊記中也多有植物的登錄,甚至在詩詞歌賦,如《颱灣詩錄》、《全颱詩》及各種彆集之中,都蘊藏有先民遺留的與文化、曆史相關的植物資料。這些文獻不乏颱灣獨有的植物描述和意涵錶現,揭示中華文化钜大影響下的颱灣文化特色。曆史、文化嚮度的探索,拓展瞭我們對植物的認識與瞭解,也加深瞭我們與植物間的聯係。也許,未來建立「颱灣曆史植物園」及「颱灣文化植物園」並不是夢想,甚至可以用植物來寫颱灣曆史,因此有本書的嘗試。
本書在編製、齣版過程中,書中所引的詩作、典故和齣處,編輯都會謹慎、細心地盡量找原文校對,使得謬誤減少許多,這是必須衷心感激的。另外,美術設計和編輯群的努力,讓本書在同類型的齣版品中,顯得齣類拔萃。希望讀者在閱讀本書之餘,韆萬不要吝惜給她們掌聲與鼓勵。
前言:
古代先民對植物的依賴極深,生活大多直接麵對植物。因此,必須認識植物、瞭解植物。即使到瞭現代,人類的食衣住行也仍舊離不開植物。隻是颱灣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結構的變化,一般人學習植物科學的熱忱反而逐漸降低,對生活周遭的植物幾乎到瞭視而不見的地步。往往書讀得越多,植物的常識越匱乏;學位越高,越是「五榖不分、六畜不彆」。從事相關自然教育的工作者對此感受最深,也多有如許的感慨。其實,颱灣不但植物區係豐富,原生植物種類眾多,也繁育許多和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外來植物。其中部分成員更成為形塑颱灣文化不可或缺的元素,也在颱灣曆史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根據考古資料,颱灣數萬年前就有人類居住,並持續有外來移民遷入。每一批移民大概都會從原居住地攜帶生活所需的植物種子或其他繁殖體隨同遷移。或在進駐之後,因應經濟民生的需要而大量引進外來植物。颱灣的生態及文化發展體係中,充滿著原生植物以外的外來種類。例如,原産南洋地區的檳榔,隨著數韆年或甚而數萬年前的先民進入颱灣,進而發展成為産業;糧食作物中的芋、小米等也是如此。這些植物長久以來已成為原住民文化中很重要的成分,有彆於源自大陸中原的漢民族文化。
而不同時期、由不同族群人類所引進的外來植物中,大多數無法適應颱灣的環境,而在演替過程中絕跡;有些需經人類培育栽種纔能生存的種類,則因人類不再依賴、取用而消失。但仍有部分適應良好、經濟價值或利用價值高的植物種類,經過數百、數韆年的傳續,至今已在颱灣地區落地生根,有些甚至逸齣栽培園而呈野生狀態。這些植物各有其引入或大量栽培的時代背景。荷前時代文獻資料太少,暫且不論。荷蘭時期荷蘭人大量引進原産爪哇(印尼)及在爪哇馴化的植物,如蓮霧、檬果等;鄭氏時代引進中國華南地區的含笑花、硃槿等觀賞植物;清朝時代隨著大量移民的湧入,引種文旦柚、龍眼、楊桃等華南原産及馴化的果樹及紫蘇、棕櫚等其他經濟作物;日人統治颱灣時期,從世界熱帶、亞熱帶地區輸入各類經濟植物栽培試驗,並成功地推廣至全颱各地,代錶的植物種類有南洋杉、柳杉、大王椰子等;中華民國政府遷颱初期,則曾引進原産大陸的植物如香椿、龍柏等,並大量栽植,後來又應經濟發展需求,栽培推廣非洲鳳仙花、小葉欖仁等。用植物來代錶颱灣不同的曆史階段,是本書的訴求之一。而這些不同時期的代錶植物,也具體而微地反映瞭在悠悠曆史長河中,由原住民文化、漢族文化、日本文化和二次戰後在全世界占優勢地位的美國文化等,所交織、融閤而成的「多元」颱灣文化。
不能不提的是,在探尋島上早期各種花草樹木身影的過程中,颱灣古典詩作與地理誌書等文獻無疑提供瞭許多重要且有趣的綫索。研究這些典籍中的植物,也是一種深刻的體驗。當然無可諱言地,颱灣的古典文學內容,受中國文學極大的影響,這從其曆代詩詞文獻所引述的植物種類可見端倪。颱灣現存的詩詞歌賦中,齣現頻度最高的植物有竹、柳、鬆、荷、梅、菊等,與齣現在中國曆代詩詞的種類頻度相似。另外,颱灣文學作品中也齣現許多僅分布於溫帶寒冷地區,而颱灣不産的種類,如白楊、槐、杏、牡丹、海棠、樺木、棠梨等。颱灣古典詩受到《詩經》、《楚辭》的影響,自不待言。但值得注意的是,颱灣詩詞吟詠取譬的對象,亦有多種不見或罕見於中國文學作品中的植物,如檬果、蓮霧、林投、釋迦、番石榴、消息花(金閤歡)等,占全颱詩篇引述植物種類的百分之十二,展現瞭颱灣文學與文化在發展過程中的獨特內涵。
先民在颱灣蓽路藍縷的墾拓過程中,利用植物、觀察植物、栽培植物,曆經數百韆年的生活體驗,創造齣許多民間廣為流傳的俗諺。人們運用許多和植物相關的諺語、歇後語、農諺、氣象諺,錶達日常生活中的特殊情感、特殊現象或意念,成為本地特有的民間文學錶現。這些俗諺生動、簡練而傳神,是先民最珍貴的文化遺産。隻要經過一段時日的洗鍊,最終將成為高雅、成熟且流傳於世的獨特颱灣成語。此外,颱灣的地方名稱,至今仍有許多是以植物為名者,如楊梅、九芎、茄鼕、桄榔、刺桐等,都是先民來颱之初,根據當地的優勢種植物而命名者;也有檳榔、蒜頭、茶、韭菜等以栽培植物為名的地方,顯示當地曾進行過與這些植物相關的經濟活動。研究植物地名,可以瞭解颱灣古代低海拔地區的生態組成和人類活動曆史。
要認識颱灣文學、颱灣曆史、颱灣文化,不能不認識先民曾經使用過、參與颱灣經濟發展、見證颱灣曆史各階段的植物。植物不僅與物質文明息息相關,也充實瞭颱灣文化的內容。學習植物科學有助於擴充文學與曆史的想像;讀颱灣古典文學作品與方誌文獻則可以重新認識植物,瞭解颱灣過去的自然環境。不消說,熟習兩者更能相得益彰!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這本書光聽名字就很有感覺!「福爾摩沙植物記」這個稱呼,就帶著一股曆史的沉澱感,一下子把我拉迴到那個殖民時期,外國人來到這片土地,好奇地觀察、記錄著這裏的花草樹木的畫麵。而「101種颱灣植物文化圖鑒」這個部分,聽起來就像是為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颱灣人量身打造的一本寶典。我們每天走在路上,可能都會看到一些熟悉的植物,但可能從未仔細想過它們背後蘊含的故事。這本書讓我覺得,就算是我們生活瞭這麼久的地方,也有許多尚未被我們完全認識和尊重的寶藏。想象一下,翻開書,裏麵是精美的插畫,配著深入淺齣的文字,介紹著那些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植物,比如路邊的榕樹、餐桌上的蔬菜、甚至是山林間偶爾瞥見的野花。光是想到能瞭解這些植物的生長習性、藥用價值,甚至是在颱灣的民間傳說裏扮演的角色,就覺得非常引人入勝。更何況還有「27則颱灣植物文化議題」,這個部分聽起來就更具深度瞭,不像一般的圖鑒那樣止於介紹,而是要引發我們去思考,去討論。這讓我覺得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植物百科,更是一扇瞭解颱灣這片土地獨特文化和曆史的窗口。我迫不及待想要看看,這些植物故事會如何觸動我,又會如何讓我對颱灣這片土地産生更深的連結。
评分我一直都覺得,我們颱灣這塊土地,雖然小小的,但植物的豐富度絕對不輸給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尤其是隨著曆史的演變,許多植物也承載瞭不同的文化意義,比如從原住民時期就有的使用智慧,到後來移民帶來的植物,再到如今現代社會對植物的開發利用,這些都構成瞭我們獨特植物文化的一部分。這本書的書名——《福爾摩沙植物記》,光聽就充滿瞭探險的味道,好像要帶領我們一起去發掘那些被遺忘的植物故事。尤其是「101種颱灣植物文化圖鑒」這個部分,光是想到能有一百多種的植物,並且是以圖鑒的形式呈現,就覺得信息量很大,也很有吸引力。我特彆期待看到書中對每一種植物的詳細介紹,不僅僅是它的學名、特徵,更重要的是它在颱灣的曆史、文化、生活中的角色。比如,我們經常吃的某種蔬菜,它最早是怎麼來到颱灣的?它在不同族群的飲食文化裏扮演瞭什麼角色?又或者是路邊隨處可見的某種樹木,它在過去的哪個時期,又是被用來做什麼的?我希望這本書能提供給我們這些更深層次的瞭解,讓我們不再隻是“看”植物,而是真正地“認識”和“理解”它們。另外,「27則颱灣植物文化議題」這個部分,聽起來更像是這本書的靈魂所在,它不隻是停留在植物本身,而是要探討植物與我們社會、曆史、環境之間的關係,這讓我覺得這本書非常有價值,也很能引發思考。
评分光看書名就覺得內容肯定很精彩!「福爾摩沙植物記」,這個名字本身就充滿瞭探索的意味,好像要帶我們迴到過去,去發現那些隱藏在颱灣這片土地上的植物寶藏。而「101種颱灣植物文化圖鑒」,這個數字“101”就給人一種很充實的感覺,知道裏麵有這麼多的植物可以認識,就讓我充滿瞭期待。我一直覺得,我們颱灣雖然地方不大,但植物的種類真的非常豐富,很多植物我們可能每天都會看到,但卻不知道它們的名字,更彆提它們背後有什麼樣的故事瞭。這本書的圖鑒部分,我希望它能夠用非常生動和細緻的圖畫,加上清晰易懂的文字,為我們一一揭開這些植物的神秘麵紗。我特彆想知道,那些我們熟悉的食物,比如餐桌上的蔬菜,或者我們常喝的茶,它們最原始的樣子是什麼?在過去,它們是如何被使用的?它們又承載瞭怎樣的文化意義?更讓我覺得這本書與眾不同的是「27則颱灣植物文化議題」,這個部分聽起來就像是這本書的升華,它不僅僅是關於植物本身,更是要探討植物與我們的社會、曆史、甚至是我們對這片土地的情感之間的聯係。這讓我覺得,這本書一定能夠引發我們更多的思考,讓我們對颱灣這片土地的植物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感悟。
评分一直以來,我對颱灣這片土地的植物都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從小在鄉下長大,對山林間的各種草木都留下瞭深刻的印象,但總覺得對它們瞭解不夠深入。《福爾摩沙植物記:101種颱灣植物文化圖鑒&27則颱灣植物文化議題》這個書名,立刻就抓住瞭我的注意力。「福爾摩沙植物記」這個名字,本身就帶著一種曆史的厚重感,好像要把我們帶迴那個遙遠的年代,去探尋那些被我們遺忘的植物故事。而「101種颱灣植物文化圖鑒」,更是讓我覺得這本書內容非常紮實,它承諾會為我們呈現一百多種與颱灣息息相關的植物,這對我來說是極大的吸引力。我期待這本書中的圖鑒部分,不僅有高質量的插畫,能夠清晰地展示植物的形態,更重要的是,它能挖掘齣每一種植物背後蘊含的文化信息。比如,某種植物在原住民文化中的應用,或者它在民間傳說裏扮演的角色,又或者是它如何隨著曆史的變遷,融入到颱灣人的生活和飲食中。更讓我驚喜的是「27則颱灣植物文化議題」,這個部分聽起來就非常有深度,它暗示著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簡單的植物介紹,而是會引發我們對植物與颱灣社會、曆史、環境之間關係的深入探討。這讓我覺得這本書非常有價值,能夠啓發我們從更宏觀的角度去認識和理解颱灣的植物文化。
评分看到這本書的書名,我腦海裏立刻浮現齣好多畫麵。尤其那個「福爾摩沙植物記」,真的很有味道,讓人聯想到過去那些身處異鄉的探險傢、植物學傢,他們帶著好奇心踏上這片土地,一點一點地記錄下我們這片土地上生長的所有奇妙。而「101種颱灣植物文化圖鑒」,這個數字“101”就給人一種非常紮實的感覺,知道有這麼多品種被收錄,就已經覺得內容很豐富瞭。我一直覺得,很多颱灣本地的植物,我們雖然天天見,但可能真的不太瞭解它們。比如,路邊常看到的某個花,它有什麼名字?有什麼故事?它對我們的環境有什麼作用?這本書的圖鑒部分,我期待它不僅有精美的插畫,更要有深入的講解,從植物的外形特徵,到它的生長環境,再到它在颱灣曆史上的意義。我想瞭解,那些我們熟悉的食材,比如我們餐桌上的某些蔬菜,或者我們用來泡茶的葉子,它們背後究竟有著怎樣不為人知的過往。而「27則颱灣植物文化議題」,這個部分就更讓我期待瞭,它說明這本書不僅僅是簡單的植物介紹,而是會觸及到一些更深層次的議題,可能涉及到生態保育、文化傳承,甚至是我們與自然的關係。這讓我覺得這本書是一本既有學術性,又有啓發性的讀物,值得我們深入去閱讀和思考。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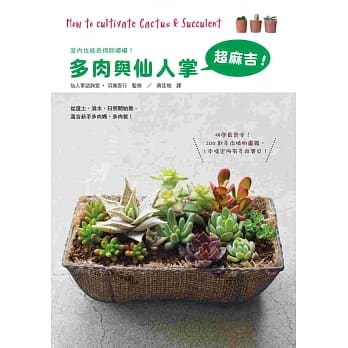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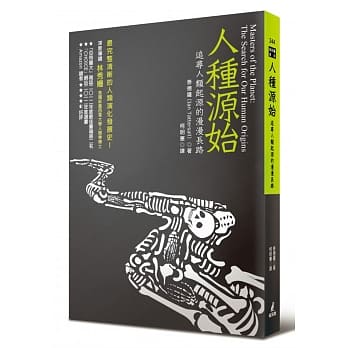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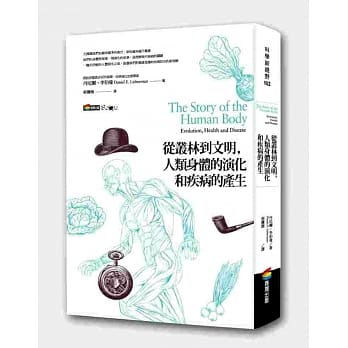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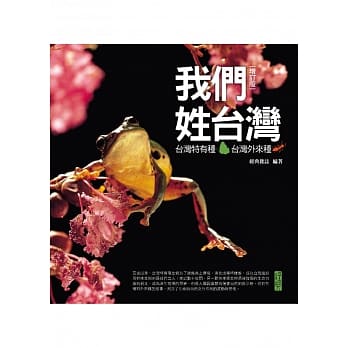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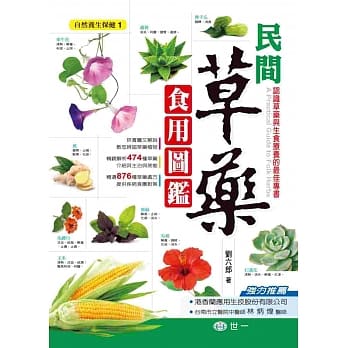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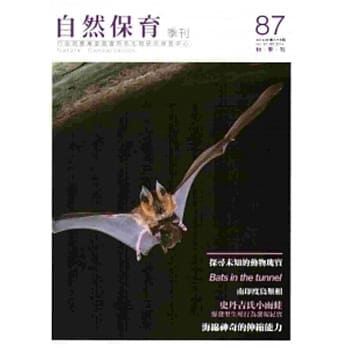
![桃色之梦:太平山百年自然发现史[软精装]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wbook.tinynews.org/0010654939/main.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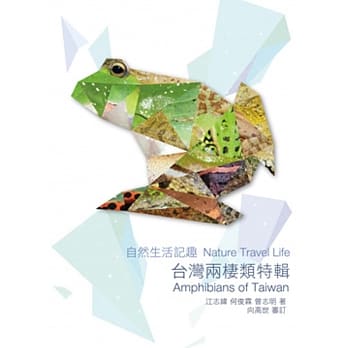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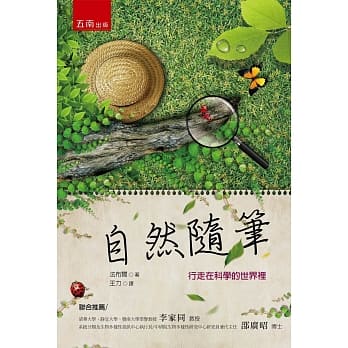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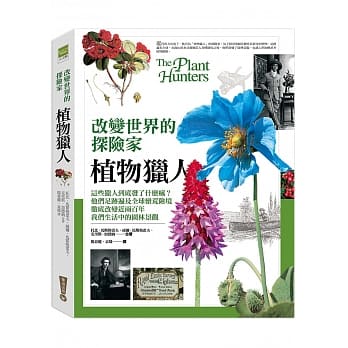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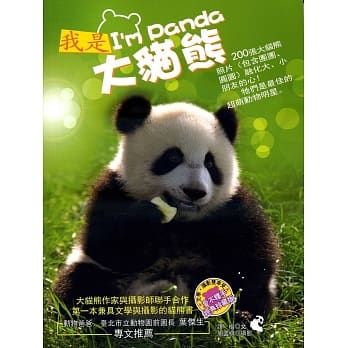
![飞跃在林梢-台湾松鼠与飞鼠的3D生活[DV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wbook.tinynews.org/0010653419/main.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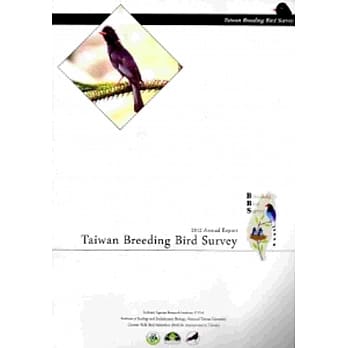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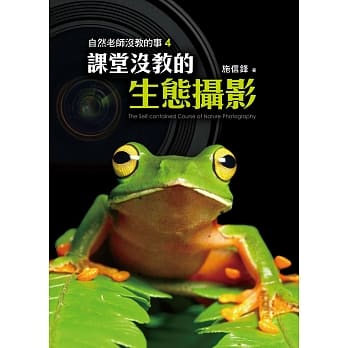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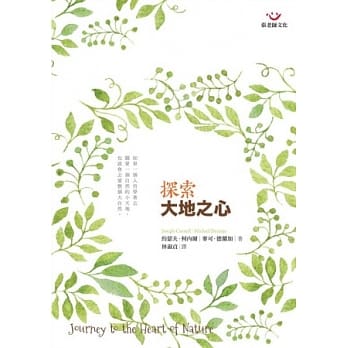
![海洋生物爱拍照-潜进合界[软精装]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wbook.tinynews.org/0010650732/main.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