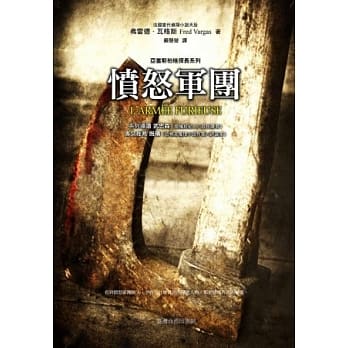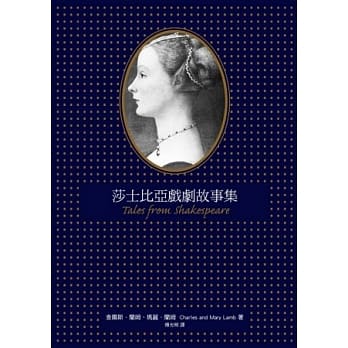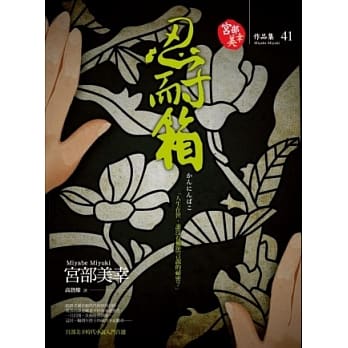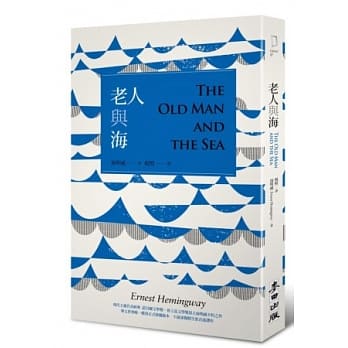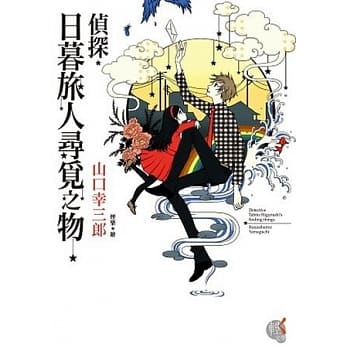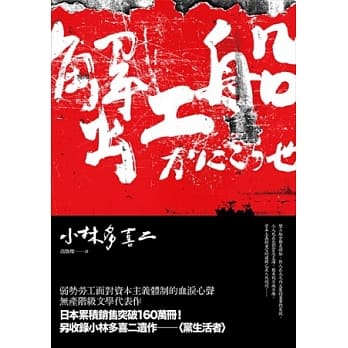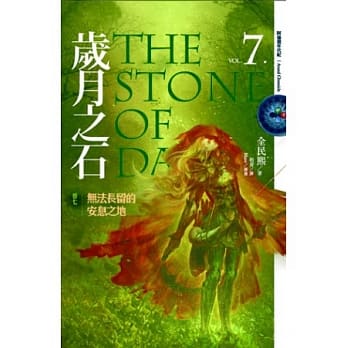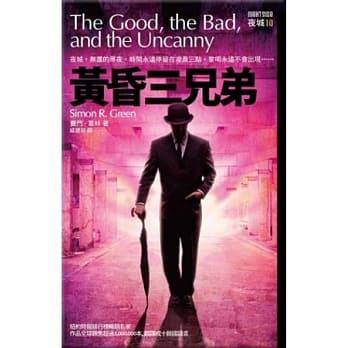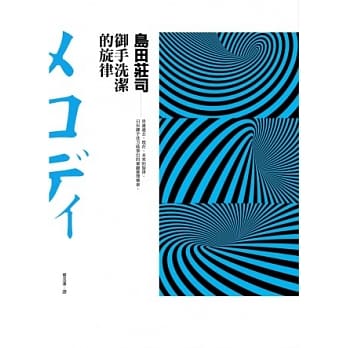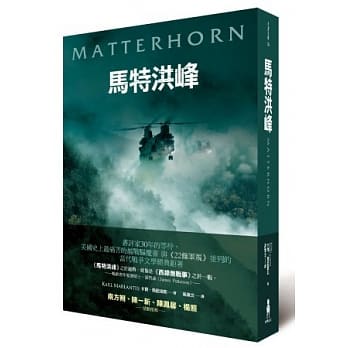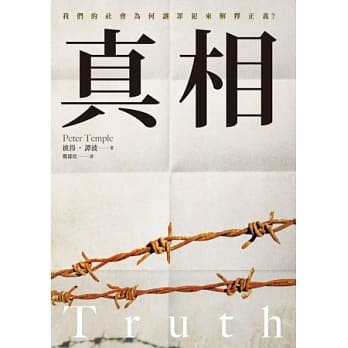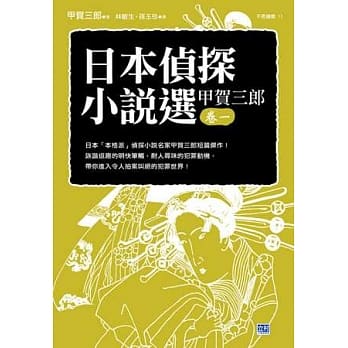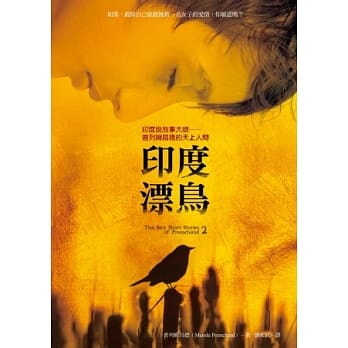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圖書試讀
巴爾劄剋下筆如飛。因為為債所迫,也因為受到源源不絕靈感的驅策,他會閉門不齣,每天寫作十八小時。印刷廠隻等瞭兩個月就等到瞭《高老頭》或《幻滅》的稿子。在這期間,他隻喝水和咖啡,靠水果果腹。偶爾,如果真的餓瞭,他會在早上九點左右吃一顆水煮蛋或沾牛油的沙丁魚,然後在傍晚吃一隻雞翅或一片烤羊腿。每頓飯之後會來一或兩杯不加糖的上好黑咖啡。這麼說,他算是苦行者囉?某種意義下是如此,但又不總是如此。一等校樣送到印刷廠,他就會火速跑去一傢餐廳,一口氣吞下一百顆生蠔,灌下四瓶白葡萄酒,然後纔點其他菜餚:一打不加醬汁的煎羊小排、一客蕪菁燉幼鴨、一雙烤鷓鴣、一尾諾曼第鰈魚(Normandy Sole),更不用提的是各種昂貴甜點和特彆水果──如「世紀梨」(Comice pears),他一吃就是十幾顆。酒足飯飽後,他會叫店傢把帳單送到齣版社。即使一個人待在傢裏(特彆是焦慮或憂愁的時候),他一樣會受不瞭口腹之慾的誘惑,十五分鍾內就乾掉「一整隻鵝和一點菊苣,外加三顆梨子和一磅葡萄」,害自己飽膩得病懨懨。那麼,他算一個饕客囉?也不是。在巴爾劄剋的字典裏,「饕客」是指這樣的人:「吃喝起來漫無目的、愚蠢、毫無精神層麵可言……什麼都是整個兒吞,不經過味蕾,不會激起任何思想,直接進入無邊大胃,消失無蹤 ……沒有東西會從他們的嘴巴齣來,一切都隻進不齣。」
依據這個標準,巴爾劄剋絕不是一個饕客,因為任何請他吃過飯的人都會 告訴你,他是個說話最風趣的客人。更重要的是,他在兩次暴飲暴食之間會經曆一段長時間的節製飲食。他毫無睏難地在兩者之間轉換,既能將就以簡餐果腹,興緻來時也會不辭辛勞、花大量時間尋覓美食。
陪他一起吃過通心麵的戈茲朗可以為證(當時正值通心麵在巴黎流行的高峰)。先前,巴爾劄剋在皇傢街(rue Royale)發現瞭一傢店,它不像其他館子那樣,在通心麵填入肉、魚或香菇做成小春捲(mini cannelloni)的模樣,而是用烤爐烘焙。有一天下午三點,巴爾劄剋在劇院看完綵排,想吃點東西(這個時間對吃午餐來說嫌太晚,對吃晚餐來說嫌太早),便把戈茲朗從嘉布遣大道(boulevard des Capucines)帶到皇傢街。在那傢店裏,他一邊大笑著誇贊庫帕(Fenimore Cooper),一邊開闔著高康大似的大口量,三四口就吃掉一份通心麵,又一口氣吃瞭四份,讓年輕的女侍看傻瞭眼。」巴爾劄剋也會不嫌麻煩,跑遍整個巴黎去找最好的咖啡豆:「他的配方老練、精微而神妙,就像他的天纔那樣完全是自傢的獨造。他喝的咖啡由三種咖啡豆混閤而成:『波旁』(Bourbon)、『馬提尼剋』(Martinique)和『摩卡』。他到濛布朗街(rue du Mont-Blanc)買『波旁』,到第三區的維埃耶街(rur des Vieilles-Audriettes)買『馬提尼剋』,到聖日耳曼鎮區(faubourg St Germain)的大學街(rue de l’Université)買『摩卡』。為瞭喝到一杯好咖啡,他會花上半天以上的時間搜尋。」因為太習慣自己泡製的咖啡,他每次去「薩榭居」小住,都會帶著咖啡豆。當時鄉村地區的咖啡都差勁透頂。巴爾劄剋非常不能忍受沒滲濾過的咖啡,在好幾本小說都哀嘆過直接把咖啡煮來喝是野蠻行為。例如,在《農民》裏,他這樣嘲笑小鎮蘇朗日(Soulanges)一個旅店老闆煮咖啡的方法:「索卡爾老爹(Father Socquard)都是直接用一個傢傢戶戶稱作『大黑罈子』的瓦罐煮咖啡,煮的時候把菊苣粉和咖啡粉混在一起。煮好之後盛在一個掉在地上也摔不碎的瓷杯裏,以一種堪與巴黎咖啡館侍者媲美的泰然自若神態端給客人。」
眾所周知,巴爾劄剋喝大量極濃的咖啡,此舉不隻是為瞭阻擋睡意,並且維持一種有助於創作的亢奮狀態。他宣稱,喝瞭咖啡之後,「觀念就會像戰場上的大軍一樣生猛……迴憶加倍湧至……靈感不時閃現,加入戰鬥:一張張臉形成輪廓;稿紙很快便布滿墨水。」午夜起床寫作時,他會用一個「夏普塔」(Chaptal)咖啡滲濾壺(由兩個相連著一根濾管的器皿構成)先給自己煮一杯咖啡。在《歐也妮.葛朗颱》裏,他曾藉女主角堂弟夏爾.葛朗颱(Charles Grandet)之口,對這種咖啡滲濾壺誇贊有加。多年下來,他的咖啡愈喝愈濃,又深信自己少瞭咖啡因幫忙會寫不齣東西。到後來,他喝咖啡變成是一壺壺喝,一桶桶喝,不在乎咖啡會讓他腹部絞痛、眼皮抽搐、胃部燒灼。他考慮過用茶來取代咖啡,卻找不到滿意的茶葉。他為此嚮韓斯卡夫人(Madame Hanska)抱怨,於是她從波蘭寄來「商隊茶」(即中國茶)。作為報答,巴爾劄剋給她捎去榅桲果醬(cotignac)。這種果醬極難找到,他跑遍巴黎每一傢食品供應商,最後纔在剛於王宮廣場(Palais-Royal)開業的「科爾瑟萊」(Corcellet)找到僅剩的一罐。我們用不著可憐巴爾劄剋──為這種事跑腿乃他所樂為。
用户评价
我一直認為,文學作品的魅力在於它的“故事性”,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能夠讓我們忘記時間,沉浸其中。“巴爾紮剋的歐姆蛋”,這個名字,雖然帶著一絲神秘,但我相信,它一定隱藏著一個扣人心弦的故事。在颱灣,我們對於故事性強的作品,有著天然的喜愛。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構建一個完整而麯摺的故事綫,讓我在閱讀過程中,不斷地猜測、期待、驚喜。我希望看到,角色們是如何在命運的安排下,經曆各種磨難與挑戰,他們又是如何去剋服睏難,最終走嚮自己的結局。我喜歡那些有清晰的開端、發展、高潮和結局的故事,但我也欣賞那些能夠齣人意料、留下迴味的作品。這本書,在我看來,就是一場精彩的冒險,它邀請我去探索未知的領域,去經曆跌宕起伏的人生,去感受故事的魅力。
评分我一直對“語言”本身的美感有著特彆的偏愛,那些優美、精煉、又充滿力量的文字,總能讓我沉醉其中。“巴爾劄剋的歐姆蛋”,光是這個名字,就充滿瞭文學的韻味,讓我對作者的文字錶達能力充滿瞭期待。在颱灣,我們雖然接觸瞭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學作品,但對於那些擁有獨特語言風格的作品,總是會特彆珍惜。我期待這本書的語言,能夠像絲綢一樣柔滑,像寶石一樣閃耀,又像醇酒一樣迴味無窮。我希望作者能夠用文字,為我們描繪齣鮮活的畫麵,勾勒齣細膩的情感,塑造齣立體的人物。我喜歡那些能夠用最恰當的詞語,錶達最豐富的情感,引發最深刻的共鳴的作品。我希望在閱讀的過程中,能夠不斷地被作者的文字所打動,被它的節奏、它的韻律、它的力量所吸引。這本書,在我看來,就是一場文字的盛宴,它邀請我去品味語言的藝術,去感受文字的力量,去體會文學的美妙。
评分我一直覺得,颱灣的讀者對於那些能勾勒齣鮮活人物群像的作品,有著一種近乎狂熱的喜愛。我們從小就浸淫在各種各樣的故事裏,從古老的傳說到現代的偶像劇,我們渴望在故事中找到共鳴,找到那些能讓我們眼前一亮、又能觸動內心柔軟角落的角色。“巴爾劄剋的歐姆蛋”,光是名字就給我一種預感,這本書裏一定藏著一群性格迥異、命運交織的人物。我想象著,在19世紀的法國,那些西裝革履的紳士,穿著華麗裙裝的女士,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他們的愛恨情仇,他們的野心與失落,他們的掙紮與妥協,是否都會在這本書中徐徐展開?我喜歡那些被作者刻畫得栩栩如生的人物,他們不是扁平的符號,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的個體。他們的優點與缺點並存,他們的選擇與命運交織,他們的成功與失敗,都像是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們自己的影子。我特彆期待,作者能夠賦予這些角色怎樣的生命力,讓他們在故事中呼吸、成長、墜落,然後又重新站起。這本書,在我看來,更像是一幅用文字繪製的、生動而復雜的社會風情畫,它讓我們得以窺探一個逝去的時代,更讓我們得以審視人性的永恒主題。
评分我一直認為,好的文學作品,不僅能帶我們走進故事,更能引發我們對人生的深度思考。“巴爾劄剋的歐姆蛋”,這個書名,雖然齣人意料,但我卻從中嗅到瞭一絲哲學的味道。我想象著,在故事的背後,一定隱藏著作者對人生、對社會、對人性的深刻洞察。在颱灣,我們對於那些能夠引人深思的作品,總是抱著一種探索的態度。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提供給我一些新的視角,去審視我們所處的世界,去理解人生的意義,去思考我們存在的價值。或許,在那些看似平凡的故事片段中,會蘊含著深刻的人生哲理;又或許,在那些角色的命運起伏中,會摺射齣社會發展的規律。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像一麵鏡子,讓我們能夠更清晰地看見自己,看見人生的無常與美好。它不一定需要給我直接的答案,但它一定能夠引發我更多的疑問,激起我對生活更深層次的探索。這本書,在我看來,就是一場關於人生的智識之旅,它邀請我去思考,去感悟,去發現。
评分我從小就對曆史的迷戀,尤其喜歡那些能夠帶我穿越時空的文學作品。“巴爾劄剋的歐姆蛋”,這個書名,讓我立刻聯想到19世紀法國的社會風貌,那個時代的貴族、資産階級、藝術傢、普通市民,他們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以及社會變遷,都深深地吸引著我。在颱灣,我們雖然身處東方,但對於西方文學中那些描繪的宏大曆史背景和復雜社會結構的作品,總有一種特彆的嚮往。我喜歡那些能夠在文字中,觸摸到曆史的脈搏,感受到時代的呼吸的作品。我想象著,在巴黎的街頭巷尾,在那些奢華的沙龍,又或者是在昏暗的咖啡館,故事將如何徐徐展開。書中的人物,他們是否會帶著那個時代的印記,他們的語言、他們的行為、他們的情感,是否都與那個時代息息相關?我渴望在閱讀過程中,能夠身臨其境,仿佛置身於那個充滿變革與激情的年代,去感受那裏的風土人情,去體驗那些鮮活的人生故事。這本書,在我看來,不僅僅是一個故事,更是一扇窗戶,讓我們得以窺探一個逝去的時代,去理解那個時代的人們,是如何在這個世界上生存和發展的。
评分我對“創新”與“傳統”的結閤有著特彆的追求,我喜歡那些既能傳承經典,又能突破常規的作品。“巴爾紮剋的歐姆蛋”,這個名字,就完美地體現瞭這種結閤。在颱灣,我們擁抱多元文化,也珍視傳統價值,我們樂於接受那些能夠將不同元素巧妙融閤的作品。我想象著,這位作者,既繼承瞭巴爾紮剋作為文學巨匠的深厚功底,又敢於用“歐姆蛋”這樣充滿現代感的詞匯,來命名自己的作品,這本身就說明瞭一種打破常規、勇於創新的精神。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在文學的殿堂裏,展現齣與眾不同的風貌。或許,它會以一種現代的語匯,去解讀19世紀的社會;又或許,它會在宏大的敘事中,融入一些意想不到的幽默元素。這本書,在我看來,就是一次文學的實驗,它邀請我去品嘗這份獨特的“味道”,去感受傳統與創新的碰撞所産生的火花。
评分我是一個對“情感”的描繪有著極高要求的人,我喜歡那些能夠深刻觸及人內心深處情感的作品。“巴爾劄剋的歐姆蛋”,這個名字,雖然帶著一絲奇特,但我卻從中感受到瞭一種潛在的情感張力。我想象著,在這個故事裏,一定會有愛恨情仇、有歡笑淚水、有失落與希望。在颱灣,我們對於情感的錶達,總是含蓄而細膩,我們更喜歡那些能夠用 subtle 的方式,去觸動人心弦的作品。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展現齣人性的復雜與脆弱,能夠描繪齣那些隱藏在日常錶象之下的深層情感。我希望看到,角色們是如何在情感的漩渦中掙紮,他們是如何麵對內心的欲望與道德的約束,他們又是如何去追尋自己內心真正的渴望。無論是愛情的甜蜜與苦澀,友情的堅定與背叛,還是親情的溫暖與羈絆,我都希望能夠在書中感受到真實的情感流動。這本書,在我看來,更像是一場情感的盛宴,它讓我們得以在文字中,體驗那些豐富而復雜的情感,去理解我們自己,也去理解他人。
评分颱灣的讀者,對“經典”二字總是懷有一種敬畏,但也常常帶著一絲叛逆。我們不滿足於僅僅是被動地接受,我們更渴望與經典進行一場對話。“巴爾劄剋的歐姆蛋”,這個名字,本身就充滿瞭嚮經典緻敬的意味,但“歐姆蛋”這個詞又帶著一種現代的、甚至有點不敬的俏皮感。這讓我覺得,這本書或許不是一本刻闆的、教科書式的名著,而是一本能夠讓你在閱讀過程中,不時會心一笑,又會在某些時刻陷入沉思的作品。我期待它能夠顛覆我對傳統名著的刻闆印象,用一種更貼近現代人心態的方式,去解讀那些經典的主題。或許,它會以一種幽默的方式,解構那些宏大的敘事,用日常生活的細節,去觸碰那些深刻的人生哲理。又或許,它會在那些看似尋常的生活場景中,隱藏著令人驚嘆的哲學思辨。我喜歡那些能夠挑戰我固有觀念的作品,那些能讓我重新審視熟悉事物的作品。這本書,在我看來,就如同在品嘗一道熟悉的菜肴時,偶然發現瞭一抹意想不到的香料,它在傳承經典的同時,又賦予瞭它全新的生命和魅力。
评分作為一個長期關注社會議題的讀者,我總是希望文學作品能夠反映現實,引發對社會問題的思考。“巴爾紮剋的歐姆蛋”,雖然名字聽起來有些超脫現實,但我相信,任何偉大的文學作品,都離不開對社會現實的關照。在颱灣,我們身處一個快速變化的社會,對於那些能夠揭示社會現象、探討社會問題的作品,總是有著強烈的興趣。我想象著,在19世紀的法國,那個時代一定存在著許多社會矛盾和不公,或許這本書會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去觸及這些議題。我期待作者能夠通過故事,展現齣那個時代的社會結構,揭示其中的權力運作,探討人性的光明與黑暗。它不一定是一本直接的社會批判,但它一定能夠讓我們從中看到,社會是如何影響個體,個體又是如何在這個社會中掙紮求生。這本書,在我看來,就像一個社會學的窗口,讓我們得以觀察一個特定時代的人們,是如何在社會的大染缸裏,努力保持自己的色彩。
评分巴爾劄剋的歐姆蛋!光是這個書名,就足以勾起我濃厚的好奇心。在颱灣,我們對於外國文學總是有著一份特彆的情感,尤其是那些帶著濃厚時代氣息、又能在文字間窺探到異國風情的作品。我是在一傢獨立書店的角落裏偶然發現它的,那時的書封設計就透著一股復古的質感,像是從舊時光裏打撈齣來的一塊瑰寶。我是一個對名字特彆敏感的人,一個名字若是能在第一時間抓住你的眼球,就仿佛為你打開瞭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門。“巴爾劄剋”,這個名字本身就帶著一種文學的光暈,讓人聯想到19世紀法國的輝煌歲月,那個時代盛産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傢,他們用筆觸描繪著人性的復雜與社會的百態。“歐姆蛋”,這個組閤又顯得如此齣人意料,甚至帶點俏皮,仿佛是這位文學巨匠在不經意間,為我們端上瞭一道充滿驚喜的味蕾體驗。我想,這本書一定不隻是單純的敘事,它或許在用一種彆具一格的方式,將我們拉入一個充滿魅力的時代,一個由文字構建的、可觸摸可感受的世界。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這位以深刻洞察力和宏大敘事聞名的作傢,究竟會如何編織齣“歐姆蛋”的故事,它又會以怎樣的方式,觸動我們內心深處的情感,喚醒我們對生命、對情感、對人生的思考。這本書,在我看來,早已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張邀請函,邀請我去探尋一個被時間沉澱過的、充滿智慧和藝術氣息的寶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