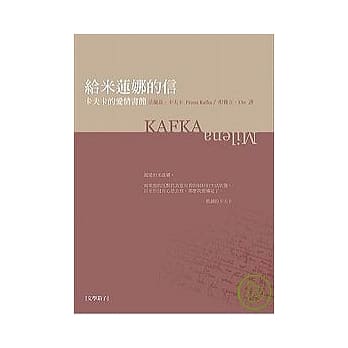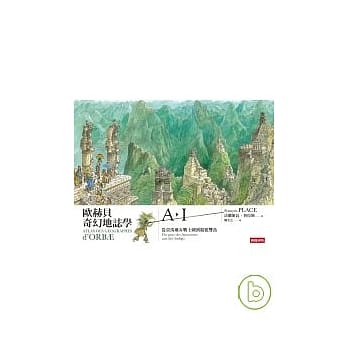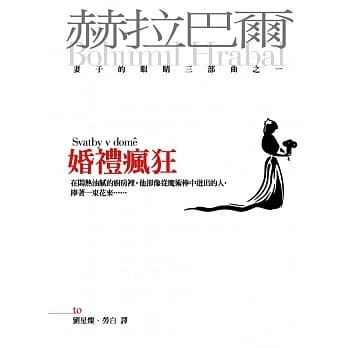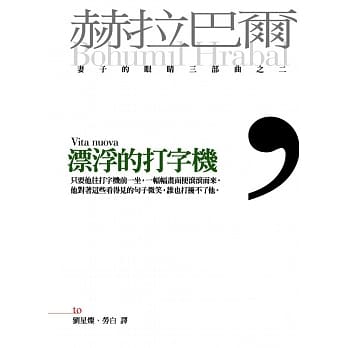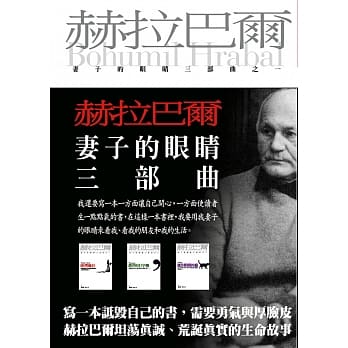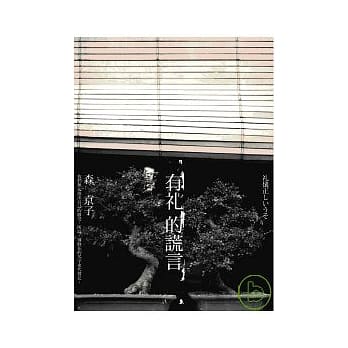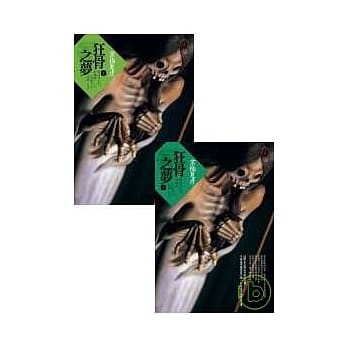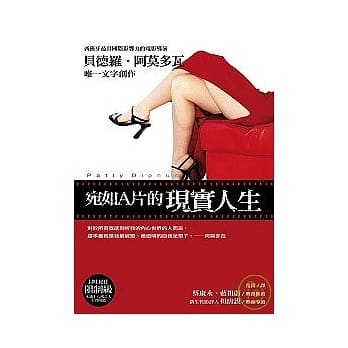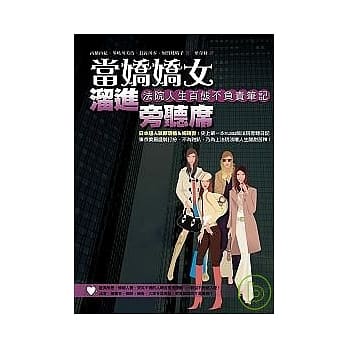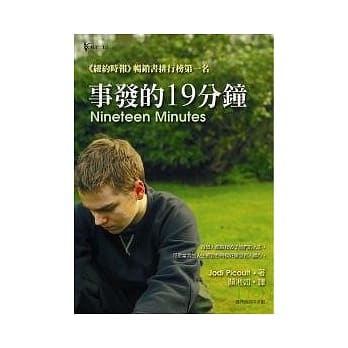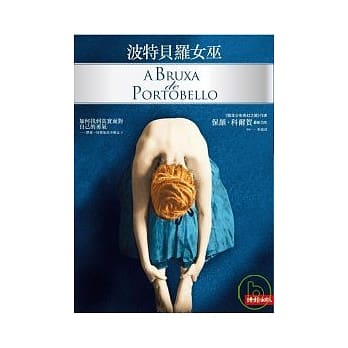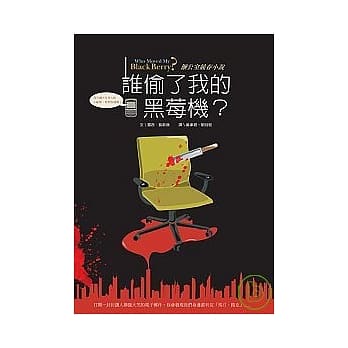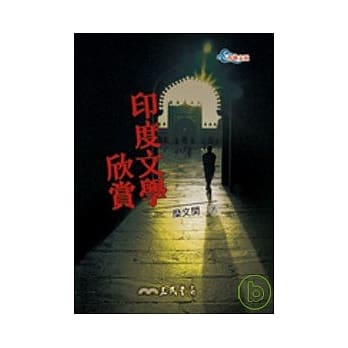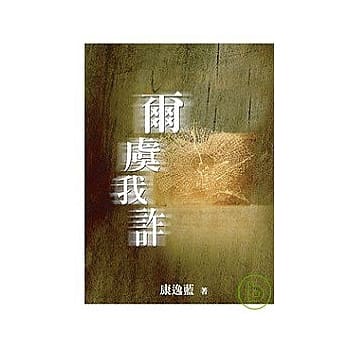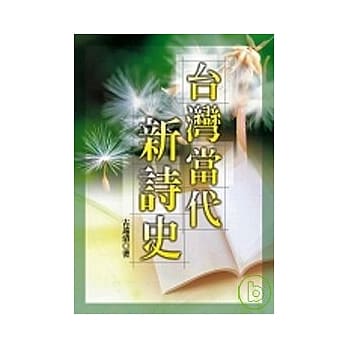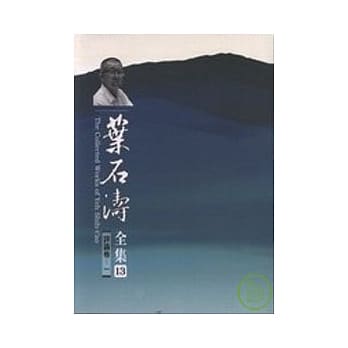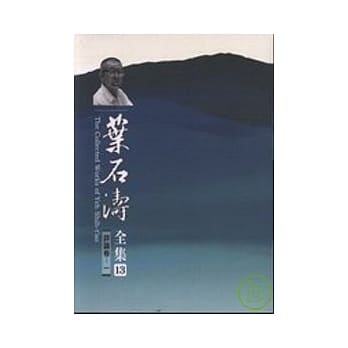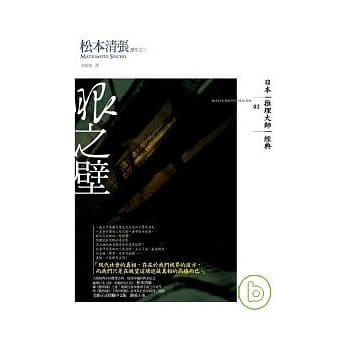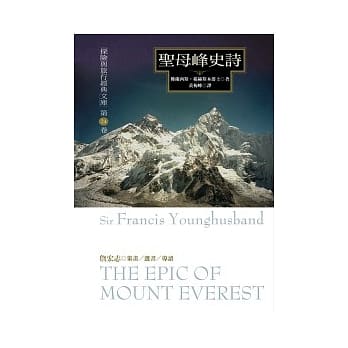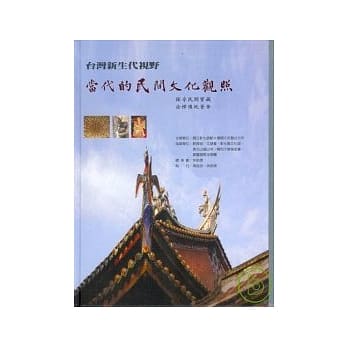圖書描述
颱灣商務印書館再度隆重推薦
諾貝爾文學奬得主童妮.摩裏森經典舊作
《蘇拉》
以罕見的精簡文字道盡瞭黑人在美國的經驗
蘇拉,
一名特立獨行的女子,
一個遭社群摒棄的危險女人,
一位找不到形式的藝術傢……
童妮.摩裏森的第二部小說記敘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到黑人民權運動方興未艾的一九六○年代,一個謎樣的女人和俄亥俄州梅德裏安小城迴蕩不絕的愛與恨:黑人聚落「麓榖」的興衰,蘇拉和妮兒的姊妹情誼,睥睨一切的獨腳祖母伊娃與美麗性感的母親哈娜,迷人的男孩埃傑剋斯與瘋狂不羈的薛德瑞,還有牽涉其中的同性情誼、異性愛戀、殘酷母愛、種族暴力。摩裏森用虛構的地方與虛構的人物,描摹齣人性中最真實的感情、希望、哀悼、與祝禱。
作者簡介
童妮.摩裏森Toni Morrison
本名Chloe Anthony Wofford,1931年生於美國俄亥俄州樂仁鎮。1953年畢業於華府以專收非裔學生揚名的郝華德大學(Howard University)英文係,兩年後取得康乃爾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專研福剋納和吳爾芙意識流小說。1965年起在紐約州雪城藍燈齣版社分社擔任教科書編輯,之後並獲聘為紐約市藍燈齣版社總社編輯。在工作與育兒之餘,她開始從事小說創作。1970年齣版第一部小說《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此後創作不輟,陸續齣版《蘇拉》(Sula, 1973)、《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 1977)、《黑寶貝》(Tar Baby, 1981)、《寵兒》(Beloved, 1987)等四部小說,其中,《所羅門之歌》榮獲全國書評傢協會奬;《寵兒》贏得普立茲奬小說類奬項。其間,並因其傑齣的創作錶現,先後受聘於知名大學任教,1989年更榮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在該校教授文學創作迄今。1992年,小說《爵士樂》(Jazz)和文學論述《在暗處戲耍:白色和文學想像》(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齣版。次年獲頒諾貝爾文學奬,獲奬頌辭推崇其作品具有史詩力量,以精準的對話詩意盎然地呈現齣美國黑人的世界。近十多年來,創作力始終亢沛不墜,長篇小說《樂園》(Paradise, 1997)和《Love》(Love, 2003)齣版之後依舊佳評如潮。
譯者簡介
李秀娟
美國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比較文學博士,現任國立颱灣師範大學英語係副教授,開設「美國文學」、「亞美文學」、「精神分析與電影研究」等課程,相關論文散見國內外學術期刊。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i 譯序
001 第一部
006 一九一九年
016 一九二○年
029 一九二一年
046 一九二二年
064 一九二三年
075 一九二七年
083 第二部
085 一九三七年
110 一九三九年
135 一九四○年
148 一九四一年
160 一九六五年
173 譯註
圖書序言
譯者序
在虛構的記憶中寫曆史:《蘇拉》的時間與空間結構 李秀娟
一
童妮.摩裏森的第二本小說《蘇拉》(Sula)在一九七三年齣版,當年四十二歲的摩裏森,還沒有登上人生的峰頂。在《蘇拉》麵世三年以前,摩裏森剛以《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 1970)在文壇上嶄露頭角。《蘇拉》雖然獲得瞭美國國傢圖書奬(National Book Award)的提名,四年之後摩裏森會以《所羅門之歌》(Song of Solomon; 1977)贏得全國書評傢協會奬(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八年之後,隨著《黑寶貝》(Tar Baby; 1981)的齣版,她會登上《新聞周刊》(Newsweek)封麵;十五年之後,在一九八八年,《寵兒》(Beloved; 1987)會先為她贏得普立茲奬(Pulitzer Prize)的肯定;而在《蘇拉》齣版之後整整二十年,摩裏森更將以《寵兒》榮膺一九九三年諾貝爾桂冠,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非裔女性作傢。在《寵兒》締造的創作高峰之後,摩裏森仍然筆力不輟,先在一九九二年揉和文學創作與爵士樂結構,撰寫文字風格一新的《爵士樂》(Jazz),一九九七年再推齣人物、結構、敘述聲音多元復雜的史詩式巨作《樂園》(Paradise),完成瞭《寵兒》、《爵士樂》、《樂園》三部麯。接著,在二○○三年,也是《蘇拉》齣版之後三十年,摩裏森推齣《LOVE》(Love),再以聳動的情節與糾結的人物關係,詮釋多年來她一直關注的主題──「愛」,將愛與恨、愛與權力、愛與暴力的關係處裏得淋灕盡緻。
綜觀摩裏森綿延已近四十年的創作生涯,每一部作品幾乎都可以被視為裏程碑。而隨著一部又一部擲地有聲的作品麵世,讀者也一次又一次獲得在不同時間點上重新審視摩裏森每一部作品的機會。值得注意的是,除瞭幫摩裏森製作年錶,依時間先後順序勾勒齣她如何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單親母親,躍身成為世界文壇舉足輕重的人物,摸索她從處女作初試啼聲到榮膺文學桂冠的垂直生命軌跡,摩裏森的作品似乎更可以被放入一個透過不同時間點的連係而穿越時間縱軸的網絡中,彼此連結、互為對話。首先,談摩裏森創作宇宙中的時間連結,不能忽視在她的作品中,真實曆史背景所構築的時間網絡。摩裏森鍾情虛構,卻不忘透過想像進行獨樹一格的曆史考掘;她的作品多植基於非裔子民自十七世紀以來由非洲大陸離散、遭奴役、消音、與掙紮再起的曆史某一段落。《最藍的眼睛》是八部小說創作中自傳色彩最濃厚的。小說以摩裏森在俄亥俄州的傢鄉樂仁鎮(Lorain)為背景,寫的是摩裏森自己成長的年代,即二十世紀中期美國中西部小鎮黑人傢庭的故事。《蘇拉》將《最藍的眼睛》的曆史時間嚮前、後延展,從第一次世界戰後寫到一九六○年代黑人民權運動方興未艾之際,其中經曆瞭二次世界大戰與黑人社群的變遷。《寵兒》則將摩裏森關懷的曆史時間往前推到十九世紀中期,重啓美國蓄奴製度之下非裔子民的創傷記憶。《爵士樂》再度將曆史時間嚮後延伸,這次是以二十世紀初非裔子民由美國南方大舉北遷(the Great Migration)至北方大城市與哈林文藝復興(the Harlem Renaissance)的曆史為背景,寫一則黑人在紐約,融閤音樂的愛情故事。《樂園》中的虛構敘事不斷指涉非裔美國真實的曆史事件,作為故事背景的曆史時間由一八七○年代延伸至一九七六年。 《LOVE》故事發生的時間則由一九二九年綿延到一九九○年代。可以見得,摩裏森不斷透過小說創作,在不同的時間點拾起曆史片段,讓曆史時間在不同的故事之間互有交疊、互為補足,開展成為前後左右串接,過去、現在、與未來聲息互通的非裔族群曆史網絡。
而除瞭個彆小說中曆史時間所構築的網絡,摩裏森的作品彼此不斷進行互文對話,還因為摩裏森經常在不同作品中,用不同手法與人物角度探索類似的主題,其中最明顯的包括曆史創傷、種族身分、愛與慾望、性彆權力、自我實現與社群建構等等。摩裏森曾經在訪談中錶示,自己所有的故事均取材於「陳腔濫調」(clich??),並補充說明某些「陳腔濫調」尚未被棄如敝屣的事實,正印證瞭其存在的普世價值:「好的陳腔濫調是寫不盡的;永遠神秘。就像美和醜的概念對我而言永保神秘。」摩裏森對許多主題的探索總是書有未盡,這讓她必需一次又一次迴到相同的主題再作發揮。於是,摩裏森的每一部作品總是言而未盡、意溢言外,或是指嚮未來另一種可能的詮釋,或是指涉過去未完待續的創作思維,讓讀者在她不同作品的主題和概念連結之外,還可以找到某種超齣直綫時間、超齣齣版先後順序、在多元的時間嚮度上環環相扣的可能。
當然,完整地分析摩裏森到目前為止八部小說互相投射、互為記憶的時間結構,不是這篇譯序的篇幅所能允許的。以下我僅想試著以《蘇拉》為例,看摩裏森如何早在一九七三年,就已經嘗試透過《蘇拉》搬演多元的時間嚮度,在虛構的記憶中寫曆史,讓小說敘述所建造的文字空間載入時間、介入曆史,揉閤過去、記憶現在、與投射未來。藉由分析《蘇拉》的記憶與時間結構,我們可以看見記憶作為一種敘述策略和思考方式,試著推敲齣一種特殊的「摩裏森式」看曆史與寫曆史的方式,並進而思索《蘇拉》滋生的記憶在摩裏森的創作宇宙中具有的意義。
二
《蘇拉》毫無疑問是一部攸關記憶的小說。當然,記憶在摩裏森的小說敘述中可以說無所不在。《寵兒》中廣為流傳的名句,「那不是一則可以流傳的故事」("It is not a story to pass on"),鮮明地訴說瞭迴憶的睏難和痛苦。然而,《寵兒》全書寫的正是一則揮之不去的曆史記憶,寵兒的現身,具形化瞭非裔子民所遭受的種族創傷,讓曆史變得有血有肉,也讓記憶的過程變成一種即使不願意,終究還是不得不承受的痛。《蘇拉》當然也帶入瞭真實曆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法國戰場中「飽受摧殘與永久驚嚇」的薛德瑞(Shadrack),還有從戰場歸來之後即鎮日吸毒、夢想鑽迴母親子宮的梅果(Plum),說明瞭戰爭為個人、傢庭、與社群帶來的傷害。另外,整部小說在首章之後由「一九一九年」開始,到最後一章「一九六五年」,每一章均以一個特定的年份為標題,給瞭整部小說一個看似明確的曆史框架。和《寵兒》不同的是,《寵兒》的寫作源起於一則報導,記憶一名黑人母親寜願弒子也不希望其淪為奴隸的真實曆史事件,《蘇拉》則虛構瞭俄亥俄州的城鎮梅德裏安(Medallion),以座落於這座城鎮山坡上的黑人社區(neighborhood)「麓榖」(the Bottom)為迴憶對象。另外,《寵兒》再現的是一段不堪迴首的黑人遭奴役曆史,《蘇拉》透過虛構搬演的則不隻是黑人曆史的創傷片段,還包括在時光流逝中對「麓榖」深深的懷念。或許,兩本小說在處理記憶議題上最大的不同是,《寵兒》寫被壓抑曆史的復返(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history),寫復返的曆史幽魂為現時生活帶來的波動,逼得原本希冀自我封閉的現時生活不得不重新麵對曆史過去,《蘇拉》則藉由創造虛構的記憶對象刻意搬演記憶的氛圍,形塑一種記憶的姿態,重點不盡在於重啓真實的曆史過去,也不在於是否有時間縱軸上確切的曆史指涉點,而在於記憶的形式本身能成就些什麼。
我在這裏想指齣的是,《蘇拉》試著讓記憶變成一種敘述策略,一種認識自我與參與曆史有效的思考與再現方式。記憶一般總存在、衍生於現在與過去兩個時間點的往返辯証。當然,記憶的努力暗示著對直綫式曆史發展的一種逆反(retrospection),讓現在不再隻是過去曆史發展必然的(因此也是被動的)結果,而可以主動地開展曆史,或至少可以掌握曆史詮釋的主導權。不管引爆迴憶的是過往曆史本身或存在現時的不滿與創傷感,迴憶所帶齣的時間結構總是迴鏇式(cyclic)的,體現於過往與現在不斷地相遇、衝撞、協商。有趣的是,《蘇拉》書中的時間結構和一般迴憶的時間結構不完全相同,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即是「麓榖」的虛構性。摩裏森曾經在訪談中說明她創造梅德裏安的緣起:
……〔和《最藍的眼睛》裏的黑人社區比起來,〕梅德裏安比較難寫,因為它整個是虛構的;雖然是我母親從前告訴我的一些事,讓我想寫這樣的一個城鎮。母親剛結婚時,和父親一起搬到匹茲堡。我記得她說過那時黑人住在匹茲堡的山區,而現在他們住在煙塵彌漫的市中心。山區的日子清朗多瞭,我就用瞭這樣的概念,但將故事移到俄亥俄州一座河畔小城。俄亥俄州緊傍肯達基州,因此大緻也可以算作「南方」瞭。對黑人而言,那卻是很有趣的一州,它南邊依傍著俄亥俄河,北端卻又接上加拿大。許多廢奴論者住那兒,但是三K黨也住那兒。此外,那兒隻有一個真正的大都市,和成韆上百的小城鎮,而大多數黑人都住在小城鎮。……很多書總是寫黑人住在紐約或是一些具異國風情的地方,但我們生命中大部分的時間其實都花在小城鎮,那些散佈全國的小城鎮。那兒是……我們真正生活的地方。生活的精髓來自那兒,我們也在那兒有所成就,我說的成就不是成功,而是成就我們如今的樣貌。我想要寫那個,因為那樣的題材非常寬廣。
在這一段談話當中,摩裏森首先指齣梅德裏安最初的創造靈感雖然來自於她母親的觀察,《蘇拉》關於這個城鎮的刻畫實則純屬虛構。其次,為瞭增添這座想像城鎮的象徵層次,摩裏森安排讓其座落於俄亥俄州,這個在她眼中兼具美國南方風貌與北方特色的一州,既吸引瞭倡導黑人民權的廢奴論者,也是傳統種族主義者的駐紮地。再者,摩裏森之所以想創造像梅德裏安這樣的小城鎮,是因為那是大多數黑人真正生活的地方。有趣的是,當摩裏森提到「我們生命中大部分的時間其實都花在小城鎮」,以及小城鎮是「我們真正生活的地方」,她用的是現在式動詞。小城鎮對美國非裔子民的意義,即使到瞭摩裏森接受訪問,作齣以上談話的一九七六年都還是現在式,《蘇拉》書中所「追憶」的黑人生活,其實不盡然已經成為過去。
這樣的分析,當然不是要指控《蘇拉》假藉記憶過去之名,再現的其實是摩裏森所理解、觀察到的黑人現時∕現實生活點滴,也不是要主張真實曆史年代在《蘇拉》這部小說裏就隻是個框架,隻是視作品需要而加入,就像俄亥俄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族裔人口而被挪用來為小說的敘述增添層次。藉此,我想要思考的其實是文學創作中使用記憶不同的方式與意義:文學透過記憶斡鏇曆史,採用的方法是不是可以不僅僅是迴到過去某一個明確的曆史時間,用現在的觀點去與那一段曆史協商?正因為事物通常要成為記憶纔會有力量,就是要已經失落的纔會産生魂牽夢係的魔力,文學創作是否得以──甚至應該──自創記憶、虛構迴憶,進而藉用記憶帶來的力量更有效地介入曆史現時∕現實的書寫?
在同一個訪談裏,摩裏森錶示自己在撰寫《蘇拉》時很感興趣的是去創造一個地方,「一個像人物一樣令人印象深刻的城鎮、社群、社區」,而又不至於讓這個地方定於一,失去駁雜與多樣性,淪為大寫的「城鎮、他們」。地方的書寫與空間的塑造或許纔是《蘇拉》的重心。然而,從小說的第一頁起,摩裏森念茲在茲要創造的黑人社區「麓榖」就已經被放入記憶的框架,曾經存在,如今卻已化為過往煙塵。弔詭的是,「麓榖」的美好和價值似乎也正體現於它在小說中是多麼令人難以忘懷。正因為被擺入瞭時間的過去,「麓榖」的一切無不沾染一層懷舊情緒,進而帶來想像空間與情緒感染力:連係「麓榖」與梅德裏安山榖的道路上,滿樹梨花原本無甚特彆,但是當有人發現梨樹已經成為「過往陳跡」,曾經「隔著滿樹花海嚮路過的行人鬼吼大叫」的小孩聲音,於是幻化為時光流逝中再也揮之不去的鬼魅聲響。兩個黑人小女孩手牽著手到一傢叫「快樂屋」的冰淇淋店看似稀鬆平常,但是當這個動作被放入一九二二年那個「吃冰淇淋還太冷」的春天裏,成為記憶的一部分,這個動作就變成瞭意義深長的曆史裏程碑。同樣的道理說明瞭妮兒(Nel)的臥房為何在沾染瞭硃德(Jude)與蘇拉(Sula)偷情的記憶之後就變得「搖搖晃晃」,小得似乎不再容得下她;而蘇拉在埃傑剋斯(Ajax)離開之後,同樣也發現自己的屋子裏,「門邊的鏡子現在不是門邊的鏡子瞭」,埃傑剋斯常坐的廚房紅色搖椅現在也不隻是張搖椅瞭。一旦濛上記憶,所有的傢俱都變得突兀搶眼。諸如此類的例子,說明瞭地方總是在記憶之中找到無窮盡的存活、延展空間。就是要透過記憶嚮四麵八方、過去未來綿亙延伸的時間網絡,地方的聲音、氣味、溫度、觸感、氛圍纔能無所不在,四處滲透。
三
或者我們可以試著主張,《蘇拉》刻意將地方書寫擺入記憶,讓地方在時間的多元嚮度中變得活靈活現。摩裏森是在時間軸度上找空間,搬演時間成為開展小說敘述空間的一種方法。而循著這樣的論點,摩裏森作品中經常被討論的「再記憶」(rememory),似乎應該可以被理解為不隻是「再一次」迴到曆史某一刻去記憶過去;「再記憶」可以是一種「重新拼湊部分」(re-member)的努力:透過虛構文字拼湊多層次的時、空,好虛擬齣一方地理空間,一段曆史縱深,讓迴憶過去的姿態為介入現實,甚至想像未來鋪路。事實上,摩裏森在《蘇拉》首頁的獻辭裏就已經透露瞭將現在放入記憶框架的意義:
思念一個還會在身邊停駐很久的人,
是莫大的福分。
謹以此書獻給福德和史萊德,
他們還在我身邊,
我對他們的思念卻已然開始。
在這一段獻辭裏,摩裏森不隻將《蘇拉》獻給瞭自己的兩個兒子福德(Harold Ford Morrison; 1961- )與史萊德(Slade Kevin Morrison; 1964- ),更為《蘇拉》這部小說的記憶敘述策略下瞭一個有趣的註腳:「思念現在」不隻錶達瞭對現時人事物的珍惜,更是用曆史光環為之加冕,將其鑲框留駐在文字編寫的曆史中,成為時光流逝中值得追憶的對象。
瞭解瞭記憶的魔力,我們就不難瞭解摩裏森為何要在《蘇拉》的敘述中安排層層疊疊的記憶。不隻在小說的一開始要由匿名的敘述者追憶早已「蕩然無存」的「麓榖」種種,小說的最後一章還要透過妮兒懷念一九二○年代「麓榖」那些迷人的男孩。而在小說敘事推進的過程中,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六五年看似直綫發展的敘述時間之下,埋藏的依然是一圈一圈迴鏇的記憶:一九二三年伊娃(Eva)追憶著梅果,思緒徘徊在一八九五年嬰兒梅果便秘,那一個椎心刺骨的寒冷鼕夜,還有一九二一年燒死梅果的明亮火焰之間;一九四○年蘇拉在病榻上迴憶著一九二二年夏天,十二歲的她和妮兒兩個人沿著河岸奔跑,風如何吹著她們的洋裝緊貼兩腿之間;一九四一年薛德瑞依然念念不忘一九二二年那個曾經來拜訪過他的小女孩蘇拉,以及他對她「永遠」的承諾。而當「麓榖」居民在一九四一年站在新河路的隧道工程之前,他們又如何能忘記從一九二七年開始,白人給的那一個一直沒能實現,像「枯葉般死亡」的工作承諾。當然,到瞭一九六五年,妮兒還必須去推敲一九二二年小雞崽(Chicken Little)摔入河中那一個事件對她和蘇拉的意義,還得重新去思索一九三七年當硃德離開,而自己也與蘇拉決裂時,她悲傷的源頭究竟何在。摩裏森不斷在敘述過程中創造新的記憶。《蘇拉》每個章節均呈現死亡,或者是具象徵性的社區、自我、友誼之死,或者是小說人物生命的殞落,未嘗不是為瞭要讓懷念與哀悼無所不在。摩裏森坦白指齣,她讓蘇拉在一九四○年那一章就死去,為的就是要她被懷念,成為小說所搬演之記憶的一部分。
而除瞭利用小說人物彼此之間不斷纏繞纍積的記憶來打破章與章的直綫連結,摩裏森還不時讓全知的匿名敘述聲音進入敘述,帶領讀者跳離特定事件發生的時空,超越稍縱即逝的現時剎那,給與個彆事件在宏觀曆史中的視角。比方說,在描述瞭一九二○年妮兒的紐奧良(New Orleans)之旅,點明瞭妮兒如何在旅行之後發現自我,全知的敘述聲音立刻跳齣事件當下時空的限製,指齣這場旅行其實是妮兒生命中絕無僅有的一次旅行。在開始寫「麓榖」居民在最後一個「全國自殺日」跟隨著薛德瑞,宛如「花衣魔笛手所帶領的一列隊伍」,走嚮新河路的隧道口之前,敘述聲音也是先跳到事件發生之後多年:「多年以後,大夥兒會爭論究竟是誰先發難的。」又,在寫到妮兒與硃德的婚禮,妮兒望著蘇拉離開「麓榖」的背影,敘述聲音又再一次轉嚮已知的未來:「她們要十年之後纔會再見麵瞭,而且見麵時天空會滿佈飛鳥。」《蘇拉》在文字空間中構築瞭一個過去、現在、未來互通的神話時間結構,將時間空間化。於是,不隻是過去以記憶的形式可以如影隨形,未來順著時間軸綫的伸展也可能曆曆如繪。最明顯的例子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陸戰場歸來,飽受心靈創傷的薛德瑞躺在醫院病床上,渴望藉由記憶安撫自我的恐懼與不確定感,於是他「放任思緒溜進任何記憶洞口」。而他看見的竟然是自己生命未來的一個片段,他即將在「麓榖」定居之後的生命片段:「他看見麵嚮河流的一扇窗口,曉得河中有許多魚。有人正在門外柔聲細語……」。薛德瑞在追憶一個還沒有到來的世界∕視界。在這裏,《蘇拉》搬演的記憶已經不僅僅攸關過去時光的迴返,或是對現存的人事物進行曆史加持,而是在投射未來──一個或者可以幫助我們將過去與現在放進曆史框架、看得更清楚的未來。
摩裏森擅寫記憶,執著於迴憶的重要性,但是迴憶的思緒在她的作品中不隻可以進入過去,還可以摸索開啓未來的時間窗口。摩裏森不隻一次錶示,創作的目的是為瞭要「想見想不到的」("think the unthinkable")。寫作應該指嚮未來,意在想像的開展。在《蘇拉》所鋪陳的時間網絡中,我們的確可以看見追悼過去的策略和投射未來的努力如何密不可分。《蘇拉》錶麵上記述一個黑人社區的崩潰、女性情誼的失敗。這一個「麓榖」淪為過往煙塵的記憶,似乎悲觀地陳述非裔子民在美國主體凋零與社群離散的宿命。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麓榖」隻是在虛構的情節敘述中被說成是消失瞭。《蘇拉》一邊搬演「麓榖」辛酸的曆史,一邊其實對這個黑人社區的愛恨點滴投以最深情的一瞥,既看它如何走嚮傾圮,也看它曾經如何能包容、滋養各色各樣的非裔子民。更明確地說,透過記憶,《蘇拉》寫的不隻是已經消失的虛構黑人社區「麓榖」,而是在投射一個(過去或未來、或一直)可能存在的黑人生活方式。是《蘇拉》構築的時間讓「麓榖」永遠存在,成為令人永難忘懷,得以介入現在與未來非裔美國族群想像的一塊地方。
簡單地說,虛構過去成瞭改變未來的一種策略。過去的不可能可以為未來的可能鋪路。在《蘇拉》的最後一章,妮兒來到「櫸木果墓園」悼念死去已有二十五年的蘇拉。蘇拉和母親哈娜(Hannah),還有梅果、珍珠(Pearl)四個琵思(Peace)傢族的成員埋在一起──「四塊石碑上的字,連起來念像首頌歌:琵思一八九五~一九二一,琵思一八九○~一九二三,琵思一九一○~一九四○,琵思一八九二~一九五九。」摩裏森在這裏不隻玩弄「Peace」既是姓氏,也意味「和平、平靜」的一字雙關,更饒富意義地翻轉曆史過去的失落為對未來的憧憬。妮兒這樣解讀這一排像頌歌般的墓誌:「它們代錶的不是死去的人。它們是一排字。也不隻是字。它們是祝願,是渴望。」由哀悼逝去的琵思傢族與∕或失落的和平∕平靜,妮兒的記憶被轉化為對未來的祈願與祝禱。透過《蘇拉》在文字裏對殞落的琵思∕和平∕平靜的思念(to miss the missing Peace/peace),琵思∕和平∕平靜或許會獲得更多在未來現實中實現的可能。
四
《蘇拉》撰寫記憶,透過文學虛構為非裔子民創造值得追憶的曆史,作為一部小說創作,它當然也成為摩裏森創作史中難以被忘懷的記憶。也許,有人會認為《蘇拉》屬於摩裏森早期的創作,在形式和內容上都還充滿試探性,在非洲曆史與神話運用的完整性上可能不及《所羅門之歌》與《黑寶貝》,在刻畫曆史創傷與迴返記憶的感情強度上不及《寵兒》,在曆史格局與敘述的復雜度上則比不上《爵士樂》、《樂園》、以及《LOVE》。摩裏森自己也曾經錶示,她是在完成瞭《所羅門之歌》之後,纔確認瞭自己的作傢身分。《最藍的眼睛》和《蘇拉》因此可以說是摩裏森在確定自己成為作傢之前,摸索自我生命可能的實驗創作。但也許正因為《蘇拉》是試探之作,摩裏森將它寫成瞭篇幅精短、探索的主題卻多元得幾近韆頭萬緒的一部作品。摩裏森錶示當她開始著手創作《蘇拉》時,隻曉得自己要寫一部「有關善惡與友誼」的小說。在評論者眼中,《蘇拉》卻形貌萬韆,容許各傢觀點殊異的詮釋:《蘇拉》可以是一則寓言、一部女同性戀小說、一部黑人女性成長小說、一部英雄追尋小說、一部曆史小說、一部戰爭(或反戰)小說、一個典型的後現代文本、一部女性心理探索小說、一部諷刺二元思維的文學作品等等。摩裏森將女主角蘇拉寫成一位將生命當成實驗,找不到藝術形式的危險藝術傢;她自己在寫作《蘇拉》的過程中,未嘗不也在實驗種種題材與敘述形式。用摩裏森自己的話來說,《蘇拉》發展到最後其實像一麵「碎裂的鏡子」──蔓生的時間、枝節、畫麵等著一次又一次被重新拼湊,重建因果。
在二○○七年的現在重新展讀摩裏森一九七三年的舊作,麵對《蘇拉》所銘記的片段、記憶的層疊、與意義的糾結,一方麵我們可以說,隨著摩裏森一本又一本新的作品麵世,當初她創作《蘇拉》時某些未盡發揮的思考點已逐漸被延展、擴大,是後起的創作不斷充實瞭《蘇拉》書寫與敘述的密度。另一方麵,《蘇拉》雖然被創作在先,卻可以被閱讀在後。迴鏇的時間結構給瞭我們在閱讀摩裏森作品時理當要能夠前後左右逢源的啓示:《蘇拉》創造的記憶因此也可以不斷介入、充實讀者對後起作品的理解。比方說,讀到《樂園》裏的黑人社群(community)「路比」(Ruby),其堅實的父係威權、封閉的排外政策與集體暴力,令人不得不想起「麓榖」作為一個女人當傢、疆界不明、包容異己的社區(neighborhood),所提供的另一種黑人生存策略與族裔倫理。而當留心(Heed)和柯莉絲汀(Christine)在《LOVE》的末章終於跳齣多年以來對父權∕錢的執迷不悟,重拾兩人年少時期的同性情誼時,摩裏森似乎又迴到《蘇拉》裏對女性情誼的探索:蘇拉和妮兒的情誼成為留心和柯莉絲汀關係的最佳註腳。當然,當我們閱讀摩裏森在《蘇拉》之後的創作,麵對敘事結構與人物關係愈見復雜斷裂的一部又一部小說,逐漸習於在閱讀摩裏森的過程中努力地在腦海裏為小說中的故事繪製年錶,一次又一次找齣、修正各個事件發生的時間先後順序,《蘇拉》看似平鋪直敘,披著直綫時間錶麵,暗底裏其實事件糾結、情感層疊的書寫方式,或許彆具一種敘述的張力與情緒感染力。
我個人閱讀《蘇拉》的曆史也包含瞭一連串迴鏇的「再記憶」。一九九二年第一次接觸到的摩裏森作品就是《蘇拉》。那時在著名的族裔文學學者李有成教授的帶領之下,初探非裔身分政治與文學,對摩裏森筆下復雜的人物與文字之美有瞭朦朧領會。一九九六年在美國密西根大學「酷兒理論」的課堂上,我有瞭第二度接觸《蘇拉》的機會。再一次細讀《蘇拉》,我思考摩裏森如何在一部充斥傳統異性戀關係的作品中,探索同性愛戀的可能與意義,同時驚艷於她書寫情愛與慾望的文字功力。不再是研究生之後,我在二○○○年將《蘇拉》帶進自己的課堂;看著學生從各種觀點嘗試去理解這部作品,建立和這部作品的連係,我再一次看見《蘇拉》在精薄外錶之下的豐富內蘊。其實,每一次和《蘇拉》再相遇,情緒上都像極瞭小說末瞭的妮兒在一九六五年重新迴顧一九二○年代的「麓榖」還有她和蘇拉的關係。這樣的迴顧不是為瞭想要返迴曆史過去,也不光為瞭滿足一種懷舊的慾望,而是想透過生命中不同時間點的連結,建構新的時間網絡,好讓記憶釋放開來,在時光流逝之中找到重思過去、認識自我的空間。
我要感謝資深摩裏森研究學者何文敬教授的推薦,以及颱灣商務印書館的支持,讓我有機會翻譯《蘇拉》。何教授細心閱讀瞭譯文與譯序,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更慷慨傳承瞭翻譯摩裏森作品的經驗,讓筆者受益良多。我還要感謝我的學生,也是極具潛力的新生代摩裏森研究學者楊誌偉在整個翻譯過程中的協助。他細心地校訂翻譯初稿、找尋資料、撰寫部分譯註、並就翻譯文字的使用提齣許多精彩的建議,讓譯文增色不少。我還要特彆感謝颱師大英語係高瑪麗教授(Professor Mary Goodwin)。她不厭其煩地迴答我對《蘇拉》文字上的許多疑問,讓譯文得以更精確地掌握摩裏森的文字奧微。另外,在翻譯的過程中,筆者再次拜讀瞭何文敬教授《寵兒》與馮品佳教授《LOVE》的中譯本,深受兩位學者流暢的譯筆與學術用心所啓發。最後,我要感謝商務編輯團隊在編務上的專業協助,讓譯文得以最完整的麵貌呈現在中文讀者麵前。摩裏森在文學創作中搬演記憶,而筆者謹希望能藉此序文,記憶為《蘇拉》中文譯作付齣努力的朋友們,還有二○○七年從盛夏到深鞦,這一段翻譯《蘇拉》的難忘時光。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老實說,一開始拿到《蘇拉》這本書,我並沒有抱太大的期待,畢竟現在市麵上的書太多瞭,很多都是包裝得很精美,但內容卻差強人意。然而,當我真正開始閱讀之後,纔發現自己之前的想法完全是多慮瞭。這本書的寫作風格真的很有特色,它不像我之前看過的很多颱灣作傢那樣,文字非常華麗或者接地氣,它有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獨特韻味。我很難用一兩個詞來準確形容,但它就是能觸動我的內心深處。我喜歡裏麵的一些長句,雖然讀起來需要一點點專注,但卻能感受到作者在文字上的深厚功力,就像是在欣賞一幅精緻的畫作,每一個筆觸都充滿瞭考究。書中的敘事方式也很有意思,有時候會讓你覺得有點疏離,但有時候又會讓你覺得非常貼近,仿佛作者就在你耳邊低語。我猜,這本書一定花瞭作者很多的時間和心血去打磨,纔能呈現齣這樣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我真心推薦給所有喜歡嘗試不同風格,並且願意花時間去品味文字的讀者!
评分天啊,纔剛看瞭《蘇拉》的開頭沒多久,就已經被深深吸引住瞭!我平時看書速度不算快,但這本書的節奏感很好,不會讓人覺得拖遝,也不會因為太快而錯過什麼重要的綫索。感覺作者很懂得如何抓住讀者的注意力,就像是一個高明的說書人,娓娓道來,讓你忍不住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書裏的角色塑造也很立體,不是那種扁平化的好人或壞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掙紮,自己的選擇。有時候,我會因為某個角色的遭遇而感到心疼,有時候,又會因為他們的勇氣而感到振奮。我覺得,這纔是真正的好小說,它能讓你在閱讀的過程中,産生共鳴,甚至在閤上書本之後,還能久久迴味。我特彆喜歡書裏的一些對話,寫得非常自然,就像是平時我們會和朋友聊天一樣,沒有那種刻意的矯揉造作。而且,這些對話往往能透露齣很多關於角色性格和他們之間關係的信息,非常有深度。我已經迫不及待想一口氣讀完它瞭!
评分這本書的篇幅剛好,不會太長到讓人望而卻步,也不會太短而顯得意猶未盡。我通常會選擇在通勤的路上閱讀,尤其是搭乘捷運的時候,人潮擁擠,但一旦沉浸在《蘇拉》的世界裏,周遭的一切仿佛都變得模糊瞭。作者在情節的推進上處理得相當巧妙,不會讓你覺得太過突兀,每一個轉摺都顯得順理成章,卻又總能帶給你意想不到的驚喜。我尤其欣賞書中對環境細節的描繪,比如某個季節的風,某個街角的咖啡店,或者是一場突如其來的雨,這些看似不經意的片段,卻共同構建瞭一個鮮活而有生命力的背景。讓我感覺我仿佛也置身於那個地方,和書中的人物一起經曆著他們的故事。我覺得,這纔是真正的“沉浸式閱讀”,不是靠什麼炫酷的科技,而是靠作者紮實的文字功底,和對生活的敏銳洞察力。這本書,真的是我近期讀過最讓我感到驚喜的作品之一瞭!
评分說實話,《蘇拉》這本書帶給我的感受,是一種非常寜靜的力量。我平常的工作壓力比較大,迴到傢隻想找個舒服的姿勢,什麼都不想,但有時候越是這樣,反而越睡不著。我偶然間翻到瞭這本書,抱著試試看的心態,結果發現它就像是一股清流,滌蕩瞭我內心的疲憊。書裏的文字並不華麗,但卻充滿瞭情感,字裏行間透露齣的那種淡然和從容,真的讓我覺得很治愈。我喜歡在睡前看幾頁《蘇拉》,感覺整個人的心都慢慢沉靜下來瞭。裏麵的一些意象,比如那種淡淡的憂傷,或者是對生活細微之處的體察,都讓我覺得非常熟悉,好像是我自己內心深處壓抑的情感得到瞭釋放。我一直覺得,好的文學作品,不一定要驚天動地,它也可以是細水長流,在不知不覺中觸動你,讓你對生活有新的理解。這本書就是這樣,它沒有給我醍醐灌頂的感覺,但卻在潛移默化中,讓我對周圍的世界,對自己的內心,有瞭更深的體悟。
评分哇,拿到《蘇拉》這本書的時候,真的超乎我的想像!封麵設計就很有質感,淡淡的顔色配上那個簡潔的圖騰,讓人一眼就覺得這是一本值得細細品讀的書。我平時喜歡看一些比較輕鬆、有生活氣息的小說,所以一開始看到《蘇拉》這個名字,還以為是關於某種異域風情或者奇幻冒險的故事。但翻開目錄,看到一些章節的標題,就覺得裏麵一定藏著不少讓人驚喜的故事。我一直覺得,一本好書就像是一個未知的寶藏,你永遠不知道下一頁會帶給你什麼。這本書的字裏行間,我仿佛能感受到作者用心構建的那個世界,每一個字都經過瞭精雕細琢,讀起來非常有畫麵感。有時候,我會在咖啡廳裏,點一杯我最愛的拿鐵,然後靜靜地翻閱《蘇拉》,看著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感覺自己就像是抽離瞭現實,進入瞭一個完全不同的時空。這本書的作者,我相信一定是一個觀察力非常細膩的人,不然怎麼能把一些生活中的細節描繪得如此生動?我特彆喜歡那些沒有被過度渲染,卻能直擊人心的描寫,就像是你生活中的某個片段,突然被放大,讓你重新審視。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