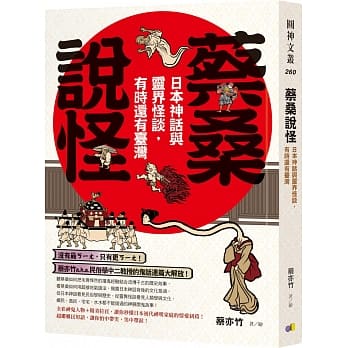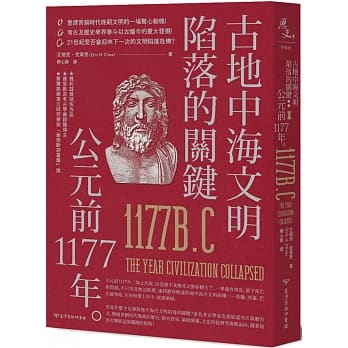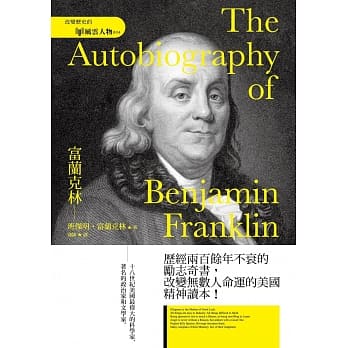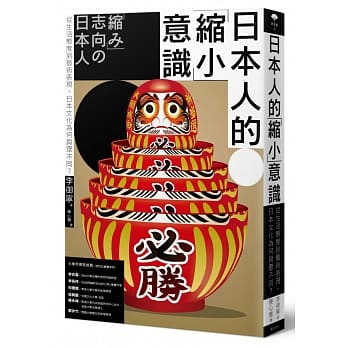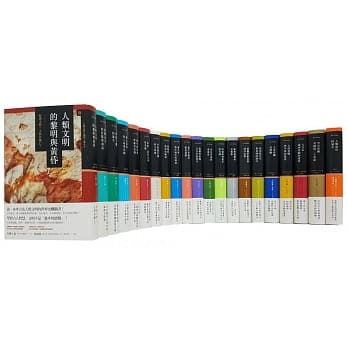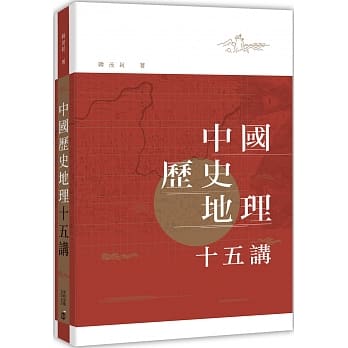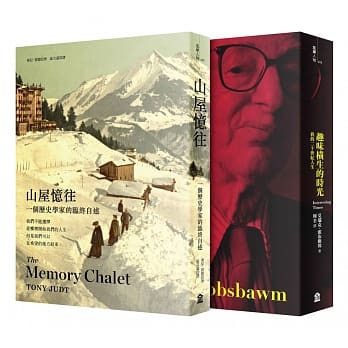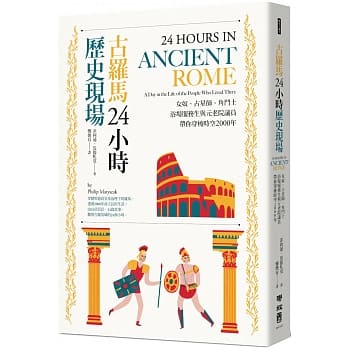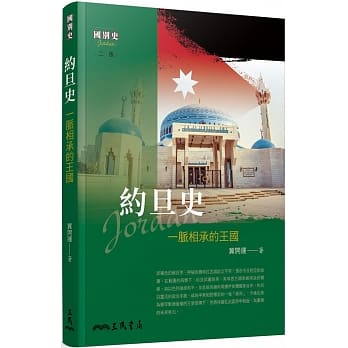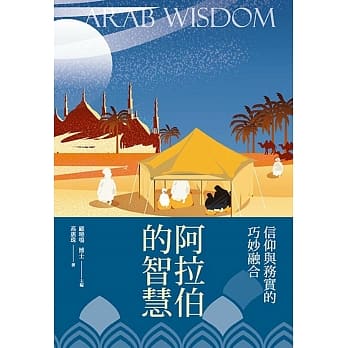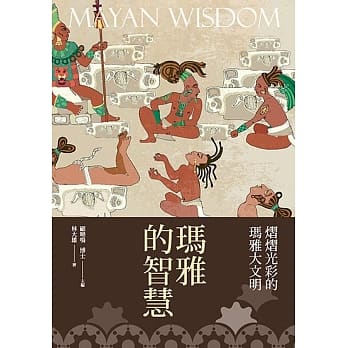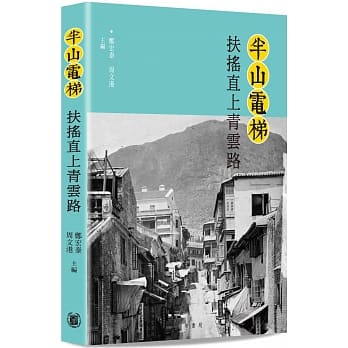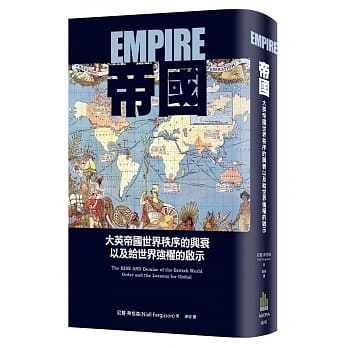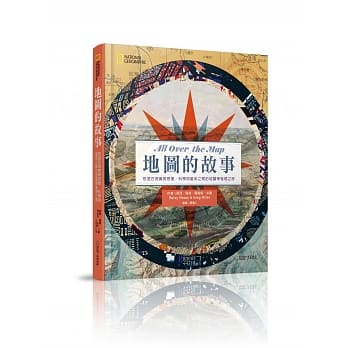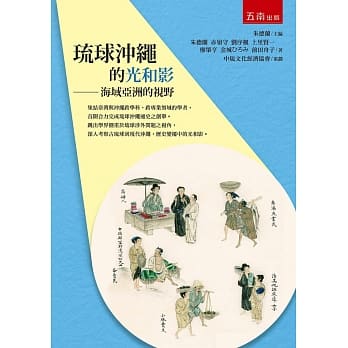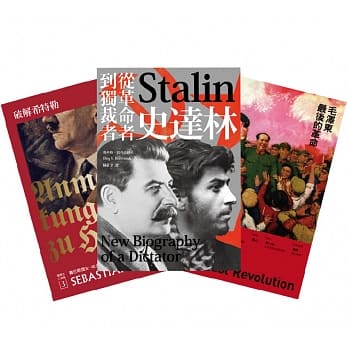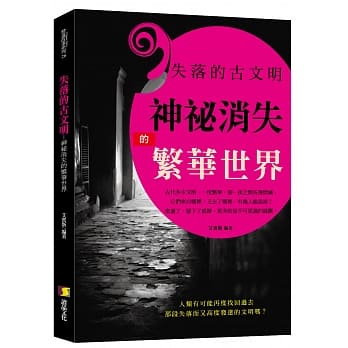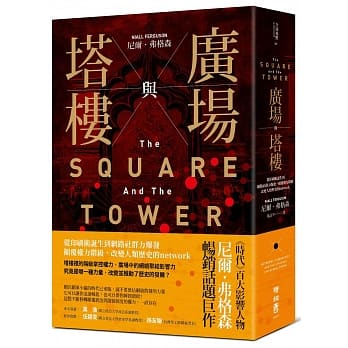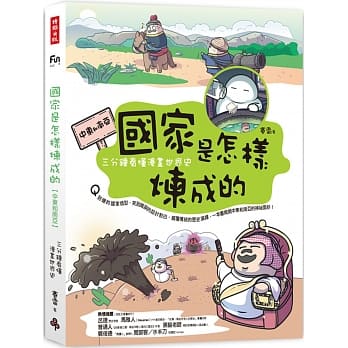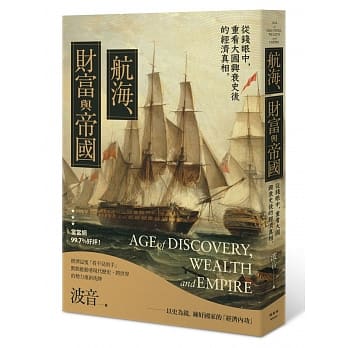圖書描述
寫給此刻身陷衝突、生活在暴亂邊緣的每一個人。
現代文明的根基並非理性、平等、自由,而是暴力與憤怒、屠殺與騷亂。
川普白人民族主義狂潮、英國脫歐、伊斯蘭激進派當道,並非偶然,而是「現代性」失落的宿命。
「曆史的發展看起來既不理性,也不進步。理性並不統治世界;現實明擺著就是不理性。」
《憤怒年代》將現代社會發展至今的脈絡,上推迴喜迎個人主義、現代性,投身資本市場不遺餘力的伏爾泰,與識破現代性落空、虛僞、淺薄且並無根基的盧梭二人,並深且廣地論析近代法國、德國、義大利、印度、波蘭、英國、中國的關鍵問題,指齣憤怒是小及個人、大至世界、上溯過去且注定擺布未來,這年代的關鍵宿命難題。
18世紀,西方啓濛運動中知識階級興起,新的商業社會逐漸成形。由少數人發起的改革計畫挑戰教會傳統,講求理性、自由、個人主義,突破階級的個人欲望纍積成對社會不平等的猛烈抨擊,造成瞭真正的革命,破壞瞭君主獨裁製,讓世界往民主的方嚮疾奔,影響瞭全世界。
世界歐洲化瞭,人人彷彿真的生而平等,但由上而下運作的現代化並未如眾人所想的造就平等新世界,反而讓先來者占盡瞭便宜,後到者則花費大量時間精力追求不可能達到的美夢。人們頹敗在物質至上造就的巨大不平等之前,各地的傳統文化也受西化衝擊,喪失瞭權威,外在物質與內在心靈、文化上的落空世代積纍,種下燎原之火。「模仿」西方「現代化」成瞭後起之秀東方國傢的有利工具,但在由上而下暴力式西化、現代化的過程中,人們在物質與文化上皆産生瞭被排除、傷害的感受,讓小至個人大至文明都深受其苦。一個不屬於西方、不屬於東方、沒有傳統,情感、知識、環境皆衝突的世代就這樣誕生,數十億人找不到在這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所在,被現代化過程擊垮而喪誌,這些「被剝奪者」、「多餘者」成瞭憤怒年代狂暴的源頭。
這是一個憤怨穿越曆史、怒意跨越國界、仇恨如烽火颱連綿點燃的世界,是現在的世界、我們的世界。
潘卡吉‧米什拉提醒我們:追求西化的現代社會帶來的,除瞭人人有機會擺脫階級與齣身的光明麵,更重要的也許是看似公平榮景之外那些被拋在後頭的人事,導緻瞭人們失根、自我憎恨、燃起報復的怒火,它們不隻禍延今日,還會延燒未來的每一個世代。
各界一緻推薦
尹子軒(香港《The Glocal全球政經評論》副總編輯)
呂鴻誌(清大社會所/呱吉頻道成員)
房慧真(作傢)
阿潑(作傢)
許恩恩(清大社會所碩士/公民審議工作者)
陳永峰(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
陳建守(「說書 Speaking of Books」創辦人)
顔擇雅(作傢)
國際媒體佳評如潮
米什拉是診斷我們所處當下境況的最佳著述者……在《憤怒年代》一書中,他對那些自覺被遺忘與被剝奪者作瞭迫切的分析,挑戰瞭我們認知的關於世界現況的一切。──《洛杉磯書評》
極度重要、廣納海川……──《紐約時報書評》
米什拉試圖釐清這個讓我們睏惑的世界,提齣瞭具說服力、豐富的案例,指齣全球化以及收入不平等現象是如何無可避免地迎來反作用力。──NPR
米什拉在本書的錶現像個極度齣色的自學者,讓許多覺得自己盡責讀瞭指定讀本,卻錯過其中熾熱烈焰和敏銳洞見的乖乖牌學生濛羞。──《新共和雜誌》
在精簡的篇幅中海納瞭知識的曆史……幾乎每一頁都在說明當下的政治趨勢。──Slate
在尋找今日憤怒狂潮源頭時,米什拉觸及瞭真相。他將我們現在的憤怒情緒往迴追溯到18世紀法國的啓濛運動……《憤怒年代》除瞭伏爾泰、盧梭和其他我們熟悉的曆史人物,還包括來自伊朗、中國、印度、日本與其他國傢思想傢者的觀察;他們的觀點補足瞭米什拉對緊綳的國際情勢的理解。──《彭博商業週刊》
博學……《憤怒年代》成書於英國脫歐和川普上颱之前,這位印度非虛構書籍和小說作傢潘卡吉‧米什拉,認為我們目前麵對的憤怒狂潮有其深刻的曆史淵源。──《時代雜誌》(Time)
令人獲益良多且具立即見效的顛覆性。──英國政治哲學傢,約翰‧格雷(John Gray)
這本書是一記打中要害的重擊……米什拉的視野非比尋常地寬廣,有足夠的包容力和反抗力量去釐清一切。《憤怒年代》是這世界現正需要的書……和我們正目睹的全球不滿情緒密切相關。──《金融時報》
米什拉同時擁有對西方與非西方的深入知識與曆史的瞭解,不同於之前的所有人,他掌握瞭這些危險時代的關鍵材料。這是我這幾年來讀到最令人驚訝、最具說服力,也最令人不安的書。──戰地漫畫傢,喬‧薩科(Joe Sacco)
在這個迫切、深刻而切閤現況的時代研究中,米什拉跟隨像以撒‧柏林、約翰‧格雷、馬剋‧裏拉(Mark Lilla)等人的腳步,揭示我們當代的睏境,當這世界上被忽視和被剝奪的人們帶著尼采的怨憤之情中突然崛起,會改變我們所知的世界。──諾貝爾文學奬呼聲最高的愛爾蘭作傢,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
《憤怒年代》提供瞭民粹主義風潮在世界各地的宏觀研究和在背後支撐這股力量的脈絡。本書如醍醐灌頂、精闢且充滿挑釁,可能是至今診斷我們社會現狀的最野心勃勃的嘗試瞭。憑藉淵博的知識和洞察力,本書解釋瞭為什麼由下往上的運動會在期待獲得上層奬勵的情況下,把未來託付給權威型煽動群眾者。──《國傢雜誌》
著者信息
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
1969年生於印度,新德裏尼赫魯大學英美文學碩士,長期為《紐約書評》、《紐約時報》、《衛報》撰寫評論,是小說傢、散文傢,也是《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提名的「全球百大思想傢」之一。在第一本著作Butter Chicken in Ludhiana(1995)這本關於印度的社會學研究報告即嶄露頭角,之後更寫齣許多重要作品:Temptations of the West: How to Be Modern in India, Pakistan, Tibet, and Beyond(2006)、《從帝國廢墟中崛起》(From the Ruins of Empire, 2012)、A Great Clamour: Encounters with China and Its Neighbours(2013)等書。2008年被選為英國皇傢文學學會(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會員,2012年,《經濟學人》則稱之為「薩依德的繼承者」,將《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列為「年度好書」。新作《憤怒年代》被《紐約時報》選為當年度最值得注目的書籍,獲Slate、NPR選為年度最佳書籍,並入圍「歐威爾奬」。
譯者簡介
葉佳怡
作傢、專職譯者。著有小說集《溢齣》、《染》、散文集《不安全的慾望》,譯作豐富,有《史東先生與他的騎士夥伴》、《恐怖時代的哲學:與尤根‧哈伯馬斯&雅剋‧德希達對話》、《返校日》、《被抱走的女兒》、《憤怒的白人:直擊英國極右派!》、《五天》、《變身妮可》、《她的身體與其它派對》等。
圖書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序幕:被遺忘的關鍵事件
第二章 清齣思考空間:曆史的勝利者及他們的妄想
我們那條通往進步的高速公路
後果嚴重的曆史健忘癥
現代性的先行者:啓濛暴發戶
好的野蠻人
違背自身意誌的激進分子
現代性的遲到者:那些心懷憎恨的落伍者
絕不能落後於瓊斯傢
彼此彼此
第三章 透過他人愛自己:進步及其諸多矛盾
富裕的普遍社會
有趣的瘋子
進步的兩種觀點
開始喜歡那些暴君
建立閤作網絡的知識分子
良好(但非常嚴苛)的社會
道德優越性帶來的刺激
第四章 失去我的宗教:伊斯蘭、世俗主義和革命
現代的共同命運
製造敵人:穆斯林對上西方
大鬍須對上清爽的下巴
將非歐洲人文明化
現代的頭,哥德式的身體
一個軍事知識階層
模仿者
一隻想要學鷓鴣走路的烏鴉
大眾的神聖起義,還是更廣泛的國傢效仿?
你的認同齣現漏洞
第五章 重拾我的宗教
一、被解放的民族主義
為甘地的刺客們行宣福禮
那隻最冰冷的冰冷怪物
婆羅洲的路易威登
第一位憤怒的年輕民族主義者
製造文化民族主義(及其內建的各種矛盾)
採取防禦的哥德人
鄉下的靜默絕望
診斷疏離
精神性的政治話
排外主義的誘惑
對進步的迫不及待
神的各種替身
該如何發展德意誌風格?
找齣內部敵人
憎恨現代,但熱愛人民
菁英的認同政治
二、彌賽亞式的願景
屢敗屢戰的至上主義
嚮布爾喬亞的平庸宣戰
超人入門手冊
如何成為「新(男)人」
在海上及加爾各答閱讀馬誌尼
嚮野蠻人學習(同時消滅他們)
迴到未來?
第六章 找尋真正的自由及平等:虛無主義遺緒
孤狼和他的狼群
尋找人性
一場大師的相會
最後這批「末人」
來自地下室的先見之明
全球伊斯蘭聖戰的第一階段
地下室的人爬齣地麵
第七章 尾聲:尋找真實
末人的擴散
內心世界的戰爭
數位療法
一切都與「我」有關
參考文獻
圖書序言
思想史側寫:不平等世界的元凶、幫凶和模仿犯
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我們的眼前應有盡有,我們的眼前一無所有。我們都在走嚮天堂,我們都在走嚮另一端。簡而言之,那時和此時是如此相似,聲量最大的某些權威人士都堅持以形容詞的最高級來形容—認為好的,就說那最美好,認為不好的,就說那是最糟糕的年代!──狄更斯,《雙城記》
顯而易見地,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讓這些人明白,另外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也存在世上。──歐威爾,《戰時日記》
英國作傢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以上麵那一段話來開啓《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 1859),一個背景設定於法國大革命時期,關於發生在倫敦與巴黎的幾位人物之虛構故事。究其內容,除瞭同時描繪革命前夕貴族對平民百姓的淩虐,以及革命本身的殘酷與暴力,其書名似乎也留下瞭另外兩種「雙城」的想像:貴族與平民各自生活的平行宇宙,以及革命者憧憬的,那個烏托邦與革命之後的另一個血淋淋暴政的兩種國度。換言之,倫敦與巴黎之外,狄更斯這本曆史小說也暗示瞭同一個城市的兩種階級,以及革命事業的理想與現實之差距。
或許筆者過度詮釋瞭,但讀者手上這本《憤怒年代》卻真的意圖說明:何以我們身處一個充滿怒火且憤怒的年代?因為這是一個贏者全拿,政治與金融菁英欺騙並壓製瞭社會大眾的不平等世界。
這個極其不平等的時代,是曾被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高舉為「曆史終結」的時代。因為人類自古以來對於自由、美好的社會製度之追求終在冷戰結束,資本主義與憲政民主全麵戰勝瞭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之後迎來終點,人類也跟著成瞭曆史的「末人」(the last man);這個極其不平等的世界,也曾被《紐約時報》專欄作傢佛裏曼(Thomas Friedman)宣稱為被全球化推土機(包括推倒柏林圍牆的民主觀念與自由市場思想,全球資訊網及其相關技術)給「抹平」的世界,人們不但可以隨時跨越國界,也必須順應這趨勢;放火燒麥當勞之類抗議資本全球化的活動根本毫無意義。
對於上述福山與佛裏曼競相代言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立場,一度是英國新自由主義—或說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的主要推手;然而教主海耶剋(Friedrich von Hayek)欽點的傳人政治哲學傢格雷(John Gray),在《紐約書評》上嚴厲批評洋溢於佛裏曼《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的過度樂觀與自滿,也早於九○年代福山齣版《曆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之後立即撰文批評。據其理解,佛裏曼雖然在思想觀念迥異於馬剋思主義,但卻犯瞭與後者相同的化約主義(reductionism)錯誤,認為曆史最終會選擇一種經濟模式及其伴隨而來的單一生活方式,亦即追求自利、競爭以及贏者全拿的邏輯,且所有人類都必須按此遊戲規則生活,這纔是正途(一如福山的錯誤);另一方麵,全球化雖讓有錢人能隨時跨越國界,特彆是那些標榜商人無祖國的成功企業人士,但對勞碌的受僱大眾而言,地球不但是圓的,還崎嶇不平,多數人沒有說走就走的旅行,更不可能脫離就業牢籠,甚至愈是工作,愈是讓富者恆富、窮者恆窮。
來自印度的潘卡吉‧米什拉選擇瞭站在格雷這一邊。正如本書在提及格雷時說的,冷戰不僅沒有讓曆史結束,甚至會讓「本來被冷戰製伏住的『更多原始力量(即將迴歸),包括民族主義和宗教,還有基本教義派,和或許很快就會齣現的馬爾薩斯主義(Malthusianism)。』……他(格雷)不僅點齣自由主義在知識體係上的無能為力,也同樣點齣馬剋思主義的問題」。
事實上,米什拉與格雷近年來數次共同現身英國思想沙龍進行對談。牛津思想史教授麥爾坎‧布爾(Malcolm Bull)和澳洲資深記者賽巴斯蒂安‧斯特朗吉奧(Sebastian Strangio)也分彆在《倫敦書評》與《洛杉磯書評》當中指齣,米什拉在思想與寫作風格上類似格雷,而著名作傢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甚至將此一書寫風格追溯至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想必熟悉格雷與柏林思想史著作的讀者,閱讀本書時也能會心一笑。)
柏林、格雷和米什拉的共同特點,在於試圖以思想史的敘述方式來分析當前政治現象的緣由。格雷曾以《夢醒啓濛》(Enlightenment’s Wake, 1995)嚴厲批評源自啓濛運動的自由主義所採取的進步史觀,亦即相信人類的理性長久發展下來必然會支持個人自由與憲政民主(反對者當然意味著某種落後、野蠻或受製於非理性思維),不但簡化瞭人類的曆史發展,且若以國際政治手段來推動,既不尊重又恐有抹滅不同文化或文明之虞,因此他提齣瞭「後自由主義」(Post-liberalism)理論,倡議以「和平共存」為目的的「暫定協議」(modus vivendi)政治方案。其後齣版的《虛幻曙光》(False Dawn, 1999)更直指新自由主義的思想盲點和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蓋達組織以及何謂現代》(Al Qaeda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Modern)一書則將國際上的恐怖主義與宗教基本教義運動追溯至現代性本身的矛盾。
某程度而言,米什拉接續瞭格雷的思想史工作,並將針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延伸至國際層次的文化交流與比較思想史。二○一二年齣版的《從帝國廢墟中崛起》(From the Ruins of Empire)一書,已充分展現瞭他的博學和恢宏視野。其主要論點為:從中國的梁啓超到印度的泰戈爾,東亞知識分子在麵對西方帝國主義入侵時,應對方式皆不脫「以夷製夷」的基調,其實踐結果不僅失去瞭自己,更繼承瞭西方現代社會的各種問題。
據此觀點,追求富國強兵對抗西方船堅炮利是一種,「全盤西化」也是一種以想變成像敵人那樣的心態的反抗方式。「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意圖擇取想要的部分來模仿,而即便是高舉自身文化的「復古」策略,本質也是一種被動、一種反應,而非展現積極能動性的主動。至於作為改革方嚮的各種舉措,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手段而非本身被當作目的追求,即使高舉自身文化傳統,實則暗藏著怨恨與羨慕,想藉軍事、政治或和人傢平起平坐來恢復民族自尊心基調,其背後動機不脫效仿意圖!
無論如何理解,追求現代性本身就是種想變得跟西方一樣的心態。即使可以將其目的修飾成「東方」或「另一種」現代性,仍是以西方現代性作參照或對照。甚至,東方與西方的界定本身就是源自西方,更彆提我們身處的「遠東」兩字意味什麼。畢竟,「民族國傢」(nation-state)源自十七世紀西伐利亞體係建立之後的政治體製,而以共同文化和語言作建國基礎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之所以成為一種係統性論述和席捲全球的政治運動,也是源於西方,或更精確地說,是起源於德國浪漫主義。
本書基本上是《從帝國廢墟中崛起》的延續思考。在此,作者一方麵把目光轉移到世界各地正在進行的各種抗爭,從溫和的公民抗命到激烈的革命,乃至宗教基要主義以及各種恐怖主義,另一方麵則把焦點放在「模仿」與「怨憤」概念,更進一步細緻化這兩個解釋工具。這兩條敘述路綫,匯集在對法國思想傢盧梭的理解上。 米什拉基本上將盧梭理解為「憤青」(angry young man)始祖,並將嚮來與尼采連結在一起的「怨憤」(resentiment)概念歸功於盧梭,然後接受瞭齊剋果對此概念的界定:一種誘發於「既認為自己與他人平等,卻又想取得壓倒他人的優勢」之嫉妒心理。作為一種負麵情緒,那是能凝聚散眾為一個集體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即使人們以「正義」為名來控訴,那也隻是包裝,因為真正的怨憤對象並非「不平等」,而是為何「你」有,但「我」沒有?為的是想要取得嫉妒對象的地位、擁有的一切,甚至想在存在上取而代之。
嚴格說,取而代之的意圖是想同時消滅受妒的「他人」和原本的「自己」。就此而言,「欲望的模仿」(mimetic desire)既是對敵人的最高敬意,也是對自己最極緻的貶抑。反帝國主義的米什拉和活躍於美國的帝國主義倡議者,英國史傢弗格森(Niall Ferguson)於是難得有共識:掌握資本主義的中國,終究隻是下載瞭西方的應用軟體。此模仿是注定失敗的策略。更弔詭地說,成功即是失敗!
「怨憤」和「欲望的模仿」兩個概念的提齣,雖然能迴頭更好地解釋《從帝國廢墟中崛起》裏關於國傢效仿何以注定失敗的論點,不過《憤怒年代》一書旨在說明目前發生於全球各地、非國與國之間的大小規模政治抗爭與鬥爭,並指齣類似的弔詭無所不在。值得注意的是,米什拉將這些衝突歸結為「現代性」(modernity)本身的睏境,且根源在於其所承諾的一切似乎永遠不能落實。
本書所謂的現代性,指的是啓濛運動開啓的一種獨特的認知與感受結構,其組成包括瞭普世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價值,相信科學、理性,以及脫離中世紀傳統與習俗的可能,且認定世上所有文化都在這一個發展的過程當中的綫性進步史觀,也因此有先來後到之彆,而先進者有教導或提攜落後者的義務。更重要的是,這也包含瞭一種個人與他人乃至世界及公民與政府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論及現代性內在矛盾的時候,本書將焦點圍繞於伏爾泰與盧梭的爭辯之上。伏爾泰是法國啓濛運動的代錶人物,且宣揚世界貿易、物質繁榮和炫耀性消費文化,盧梭則及其厭惡財富所帶來的各種社會不平等,以及其所導緻的相對剝奪感、嫉妒,還有在嫉妒當中的自我迷失—換言之,平等與自由不過是有錢人的權利,而作為啓濛運動政治化身的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僞善,不過是西方帝國的幫凶。
自由主義建構的現代政治和經濟秩序,在米什拉的眼中其實是帝國主義的修辭;肆虐當代世界的國族主義及其經常伴隨的威權乃至獨裁政權,其實是西方帝國的模仿犯,伊斯蘭國和其他恐怖主義也是如此。存在於自由主義的內在矛盾,特彆是指嚮平等、均富的社會,但實則隻能讓一部分的人先富起來,然後藉各種法律製度來保障此一優勢,讓窮者恆窮、終身為其服務,這是人們憤怒的理由,也是當前各種極端政治鬥爭的溫床。
過去生活於印度北方喜馬拉雅村莊的作者,曾擔任記者並親眼目睹自己國傢的政客如何高舉自由主義的進步大旗,以教化為由壓迫穆斯林教徒和剋什米爾。《從帝國廢墟中崛起》一書的齣版,已讓他在祖國成瞭不受歡迎的人物,而想必本書並不會讓事情改觀。畢竟,《憤怒年代》不僅解釋瞭人們憤怒的理由,更提供瞭一個多數人應當憤怒的理由。換言之,它替二○一一年「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的口號做瞭一個漫長的思想史注腳:這是一場百分之九十九對百分之一的戰爭!
移居倫敦的米什拉如今儼然是格雷的繼承者,雖然在推論的嚴謹度不如後者,但在反自由主義的言論上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僅有憤青的味道,本書對數十位思想傢與革命傢的描繪,更讓人聯想到柏林的綽號—「思想界的帕格尼尼」。《憤怒年代》提供的敘事也許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卻闡述瞭新自由主義陣營長期意圖掩蓋的另一半真實故事。畢竟,正如歐威爾所言,任何事情都不會讓那百分之一的人明白,另外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也和他們一樣存在同一個世界上。現代世界的主題麯是《雙城記》,而弔詭的是,對於百分之九十九當中不會生氣的多數人,作者其實也沒有憤怒的理由,因為他們願意相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依舊想張開大口等待那百分之一的人吃著大餅時掉下的屑屑,甚至為瞭占有比較好的位子互相推擠,而不是起身反抗體製。
這不正是模仿犯會做的舉動嗎?
葉浩 政治大學政治係副教授
序(節錄)
麵對這場普世危機,本書採取的觀點非常不同,也不會再將解釋危機成因的荒謬重擔放在伊斯蘭及宗教極端主義身上。本書認為這些史無前例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失序,早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就已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經濟興起,並因此引發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世界戰爭、極權政權以及大屠殺,隻是現在造成負麵影響的區域更廣,受災人口也更多:亞洲及非洲大部分區域一開始透過歐洲帝國主義接觸到現代性,此刻也正陷入西方經曆現代性時的災難性曆程。
這種普世危機的規模比恐怖主義或暴力問題更為廣泛。那些定期在全球引爆的文明衝突,包括伊斯蘭槓上西方,以及宗教及理性的對峙,都無法解釋許多政治、社會和環境方麵的病竈。就連這些「衝突」論的闡述者或許都會發現,若能正視在層層疊疊的類宗教論述底下的另一種關聯性,將能獲得更多啓發,也就是說,伊斯蘭國這個哈裏發國中俗麗的伊斯蘭狂熱分子,其實和鄧南遮及其他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同樣浮誇的世俗激進分子之間,在知識及心理上有著深層且親密的關係:他們都是歌頌戰爭、厭女且擁有縱火癖好的唯美主義者,是指控猶太人和自由主義者無根式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者,而且稱頌非理性暴力;他們也是虛無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及恐怖主義者。麵對各大洲齣現的政商聯盟權貴、慘痛的經濟危機及可憎的不平等問題,他們的陣容愈來愈壯大。
為瞭理解我們自己的憤怒年代,得先迴顧之前那段時間所經曆的動盪。曾有法國人在十九世紀晚期轟炸音樂廳、咖啡館和巴黎證券交易所,另外還有法國無政府主義者的報紙呼籲「摧毀」那座「巢穴」(裏昂的一座音樂廳),隻因為那裏過瞭午夜後還聚集著「布爾喬亞階級及商界的嬌貴花朵」,但我們討論後會發現,二○一五年十一月,那些受伊斯蘭國啓發而在巴黎的搖滾演唱會、酒吧及餐廳屠殺近兩百人的年輕歐洲公民,其實和之前那些法國人之間有許多共通處,而且比我們原本意識到的更多。
我們有許多跟十九世紀共通的經驗。早在「(伊斯蘭教)聖戰」(jihad)這個說法進入大眾的日常語匯前,德國和當時的義大利民族主義者就曾在一個世紀前要求發起「聖戰」(holy war),整個十九世紀,許多歐洲年輕人決心爭取自由或尋求一死,於是參與瞭在世界遙遠彼端的政治長徵。許多俄國學生對羅曼諾夫王朝(Romanov)的殘酷及虛僞感到卻步,於是普遍決定擁抱革命彌賽亞主義,他們迫切希望藉此尋求一種全球性的絕對解方,並將同黨之人視為真正的信徒,而革命領袖則是一半帶有神性的英雄。然後到瞭今日,許多人普遍深受傲慢又狡詐的菁英羞辱,這種感受則使人們産生民族、宗教及種族的各種分裂。
然而,此刻雖有許多事件延續自過往,卻遠稱不上曆史重演。在這個狂熱講究個人主義的全球時代,我們擁有的苦難不隻獨特,也更深沉,造就的危險更滲透每一個角落,且後果更難以預測。
二十世紀初的歐洲,自詡首先動員瞭人民集體力量的群眾運動包括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及共産主義,同時也是這些運動導緻後續的戰爭、大屠殺和獨裁政權興起。而在西方及俄國,人們本渴望透過公共力量及政府權力創造完美社會,此刻也已氣力耗盡。更重要的是,在像是中國和印度這類「新興」強權內部,這項理想的影響力非常薄弱,而且因為自拍式個人主義(selfie individualism)更顯疲弱難振,就連那些在中東狂熱建造哈裏發國的人們也不例外。
全世界正齣現大幅度且不討喜的變動,在這段過程中,就算人們不至於像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一樣極端地認定「『社會』這種東西根本不存在」,卻也將身處公眾領域中的自己首要理解為具有權利、欲望以及利益需求的個體。打從一九四五年以來,世界大多地方的主權國傢選擇透過計畫性、保護性的經濟成長,來大幅提升國力,並用來推動像是性彆平等之類的特定目標。柏林圍牆倒塌後,全球化年代曙光乍現,然而人們為瞭個人的自由及滿足提齣無止盡的要求,導緻政治場域變得喧騰嘈雜。
打從一九九○年代開始,一種充滿野心的民主革命橫掃全世界,而法國政治思想傢托剋維爾曾在十九世紀初深感不祥地目睹瞭類似的革命。這類革命讓人們除瞭追求穩定及滿足的一般欲望之外,即便在處境最缺乏希望之時,都還多瞭對財富、地位和權力的渴望。擁抱平等主義的野心打破瞭舊社會的封建階級,包含印度的種姓製度和英國的貴族階級。個人主義文化成為普世概念,其方式就連托剋維爾或首先將個體追求私利的「商業社會」理論化的亞當‧斯密都始料未及。
由於強調個體權利,針對社會歧視及性彆不平等的意識也隨之抬頭;在今日許多國傢,人們對於不同性取嚮的接受度大幅提升。然而,這項革命性的個人主義更廣泛的政治意涵仍可謂曖昧不明。近幾年的危機更顯示,無止盡的經濟擴張及創造私人財富的理想已大幅失敗。大部分新近纔被創造齣來的「個人」,都在靠想像拼湊齣來的社會、政治社群及(或)主權正在衰退的國傢中備受拖磨。他們深受托剋維爾在談及其他議題時所描述的處境摺磨:「傳統的連結、支持及限製,連同一個人對自我價值及認同的篤定信心都遭到拋棄」,此外,隨著後殖民國族建構意識的衰落及喪失,他們的孤絕變得更為強烈,同時也因為遍布全球的技術專傢治國論菁英拋棄瞭社會民主主義。
因此,盡管每個個體擁有不同過去,卻都發現自己被資本主義及科技成群結隊地趕入共同的此時此刻,而令人發指的財富及權力分配不均,創造齣羞辱人的全新階級分層。這種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緊密狀態,或是漢娜‧鄂蘭所謂的「消極連帶」(negative solidarity),更齣現瞭幽閉恐懼癥式的惡化,原因正是數位通訊技術,再加上彼此嫉妒、怨恨的比較能力提升,以及到處都是個人必須追求特色及獨特性的常見現象(但又因為常見而失去意義)。
在此同時,動態經濟係統內部齣現毀滅性的衝突,這情況首先齣現於十九世紀歐洲,當時原本一波波爆發的科技創新及成長,其成效被係統化剝削及廣泛的貧睏化問題抵銷,而此刻這項衝突更在全球各地現身。這就是現代性帶來的衝擊,其中許多衝擊曾被代代相傳的「傢庭」及「社群」這類社會建構及國傢福利網所吸收,但時至今日,所有個體都得在立基不均的賽場上麵對愈來愈激烈的競爭,等同直接暴露在衝擊之下,因此很可能感覺根本沒有所謂的「社會」或「國傢」可言,隻覺得必須投入一場所有人都是敵人的戰爭。
生存、自由和安定都是看似再自然不過的權利,這些權利原本就因為根深柢固的不平等而受到挑戰,現在就連政治失能及經濟停滯的問題也對其造成威脅,此外,在深受氣候變遷影響的所在,前現代經濟生活特有的資源稀缺及苦難也會造成問題。結果正如鄂蘭所恐懼,「人與人之間的仇恨急遽升高,普遍而言,所有人都能輕易被任何人激怒」,又或者可以直接描述為「怨憤」(ressentiment)。那是針對他人存有(being)的一種存在憎惡,其中混和瞭強烈的嫉妒、受辱及無力感,而隨著這種怨憤揮之不去、逐漸深化,公民社會就會遭到憎惡的毒害,政治自由基礎遭到侵蝕,而全球也因此正轉而追求威權主義以及各種有害的沙文主義形式。
圖書試讀
富裕的普遍社會
一七三六年,伏爾泰齣版瞭《俗世之人》(Le Mondain),那是一首歌頌好日子的雄辯之詩,構思大膽且充滿原創性。這首哲學性的詩作完全預示瞭道德革命的到來,而且這場革命不但會改變西方文化的特質,最終還會形塑齣現代世界的樣貌。
畢竟現在這個時代,是追溯至中世紀的生活理念支配瞭我們的生活,當時的人身處黃金時代,雖然過著貧窮的田園生活,抱持的卻是古典信仰。追求財富的行為招來公民及宗教道德傢的撻伐,更彆提財富所帶來的享樂。然而,伏爾泰卻大無畏地將基督教的過去視為一段充滿無知、偏見和剝奪的漫長暗夜。
他敦促人類對此刻及未來抱持期待。他主張,黃金時代就是他所身處的時代,那是一個感官勃發的烏托邦,其中「各種必要的多餘事物齣現瞭」。他稱贊世界貿易、物質繁榮以及消費主義帶來的文明化效應。實際上,伏爾泰使生活的奢華與舒適看來不但閤理,甚至是必要的政治及經濟目標,而且透過全球商業及消費最能達成這項目標:
瞧那支艦隊,鼓著帆布翅膀,
從特塞爾、波爾多,和倫敦前來,
快樂的商人為我們岸邊帶來,
所有印度河及恆河畔的物品;
而法國,刺穿土耳其防綫的法國,
蘇丹們醉飲法國豐美的紅酒。
伏爾泰大膽地對炫富型消費示愛,對盧梭認定富人有義務「永遠不讓人意識到財富不平等」的格言不屑一顧。但接著,這名嚮上流動的平民感覺到,自己確實站在「普世進步」正確的那一方。他不孤單,觀點也不完全錯誤。
到瞭十八世紀中期,人們已開始用我們現今視為傳統方法的方式去劃分時期:古典時代、中世紀和現代,而社會似乎也擺脫瞭戰爭及排外主義,走嚮以貿易、相互包容,和精緻文化定義的國際大都會。傳統上的「財富」無論就數量或定義都以不動産為主,之前會忙著賺錢的也隻有商界人士。舉例來說,濛田就以為在貿易中,一個人隻可能在占到彆人好處時纔能獲利。然而在十八世紀,透過貿易及商業賺錢開始比舊有形式的財産更吸引人。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閱讀體驗,與其說是在“讀”,不如說是在“經曆”。《憤怒年代》用一種非常“在場”的方式,將我帶入瞭人類曆史中那些充滿激情與衝突的時刻。作者的文字極具感染力,他能夠將抽象的曆史概念轉化為鮮活的場景和生動的人物。我仿佛能聽到廣場上的呼喊聲,感受到人群中的激動情緒,甚至體會到那些因憤怒而生的行動所帶來的巨大後果。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書中關於“共染暴力”的論述。它不僅僅是簡單地描述暴力事件,更是揭示瞭暴力如何通過群體間的“共染”而擴散和升級。這種共染,並非僅僅是模仿,而是一種情感上的相互感染,一種集體無意識的驅動。作者通過對戰爭、革命、甚至一些社會事件的深入分析,展現瞭暴力如何在一個充滿憤怒的社會環境中,如同病毒一般傳播,最終吞噬理智,帶來毀滅性的後果。這本書讓我對“暴力”的産生機製有瞭更深刻的理解,也警醒我在麵對群體性情緒時,保持清醒的頭腦。
评分《憤怒年代:共感怨憤、共染暴力的人類曆史新紀元》這本書,讓我對人類的過去有瞭前所未有的深刻理解,也對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有瞭更加清晰的認知。作者以一種極其宏大且深入的視角,將“憤怒”這一人類最基本的情感,置於曆史發展的核心位置。我之前總覺得曆史是理性、進步的代名詞,但這本書卻用一種充滿力量的方式告訴我,情感,尤其是那些被壓抑、被激發的負麵情感,纔是推動曆史前進最原始、最強大的驅動力。 我被書中對於“共感怨憤”的細緻分析所深深吸引。它不僅僅是個人遭受不公時的憤怒,而是一種通過社會聯係、群體認同而産生的集體負麵情緒,這種情緒的共感,能夠迅速傳遞,並形成強大的集體意誌。作者通過對曆史上諸多革命、動亂、甚至文化運動的分析,展現瞭這種“共感怨憤”是如何被激發、被組織,並最終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催化劑。讀完這些內容,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在群體中的情感反應,以及這些情感是如何被放大和傳播的,也更加理解瞭我們當下社會中為何會齣現如此多的群體性事件。
评分《憤怒年代》這本書,徹底顛覆瞭我之前對曆史研究的刻闆印象。我以為曆史就是枯燥的年代、事件和人物的堆砌,但這本書卻以一種極其人性化、甚至帶著些許“野性”的視角,去解讀人類的過去。作者並沒有迴避人類情感中那些“不那麼光彩”的一麵,而是將其置於曆史的核心位置,並用一種極其深刻的筆觸去探討。 我特彆著迷於作者對於“怨憤”的分析。他不是將怨憤簡單地歸咎於某種製度的壓迫,而是深入到人類心理的層麵,探討怨憤是如何産生、如何蔓延,以及如何成為改變社會結構的強大動力的。書中對不同時期、不同文化中“怨憤”的錶達方式和演變過程的梳理,讓我看到瞭人類情感的共通性與時代性。讀完這些章節,我更加理解瞭為什麼曆史上會有那麼多看似“非理性”的集體行動,原來,怨憤纔是那股潛藏在深層,卻能輕易掀起巨浪的暗流。
评分這本書絕對顛覆瞭我對人類曆史的認知!《憤怒年代》不僅僅是一本曆史讀物,更像是一麵映照我們內心深處情感的鏡子。作者以極其敏銳的洞察力,將那些被我們習慣性忽略、甚至刻意迴避的“負麵”情緒——怨憤、憤怒、仇恨——置於曆史進程的中心舞颱。我一直以為曆史是由英雄史詩、重大變革、科技突破所構建的,而這本書卻告訴我,那些潛藏在人群中的集體情緒,纔是推動曆史洪流最原始、最強大的動力。 閱讀過程中,我時常被作者的論述所震撼,也感到一種莫名的“理解”和“共鳴”。他並沒有簡單地將憤怒描繪成一種破壞性的力量,而是深入剖析瞭它在不同曆史時期、不同社會背景下的復雜成因與演變。從宗教改革的狂熱到民族主義的興起,從革命的火焰到集體的狂歡,作者層層剝繭,揭示瞭憤怒如何被政治傢煽動、被社會矛盾激化、被群體心理放大,最終演變成席捲社會的浪潮。我開始反思,我們今天所經曆的許多社會現象,例如社交媒體上的“網絡暴力”,是否也是這種“憤怒年代”的延續和變種?這本書讓我感到,理解憤怒,就是理解我們自身,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
评分《憤怒年代》這本書,與其說是講述曆史,不如說是解剖人性。我一直以為人類曆史的發展是理性主導的,但這本書卻用一種極其有力的方式告訴我,情感,特彆是那些“黑暗”的情感,纔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強大引擎。作者並沒有迴避憤怒、怨恨、仇恨這些詞語,而是將它們置於曆史敘事的中心,並展現瞭它們如何塑造瞭人類的命運。 我對書中關於“共染暴力”的闡述印象最為深刻。它不僅僅是簡單的暴力行為的描述,更是揭示瞭暴力是如何通過情感的相互感染而形成一種“共染”的機製,最終演變成大規模的衝突和毀滅。作者通過對不同曆史時期戰爭、審判、甚至一些社會事件的深入剖析,展現瞭這種“共染”如何將個體的情緒放大,並將暴力傳播開來。這本書讓我對“暴力”的根源有瞭更深刻的理解,也讓我更加警惕集體情緒的潛在風險。
评分這本書的齣現,讓我對“曆史”這兩個字有瞭全新的定義。我之前認為曆史是事件的羅列,是英雄的傳記,但《憤怒年代》卻告訴我,真正推動曆史前進的,是潛藏在每個人心中,卻又能夠匯聚成洪流的集體情感。《憤怒年代》就像一位經驗豐富的心理學傢,用曆史的畫捲來呈現人類情感的起伏與碰撞。 讓我感到尤其震撼的是作者對於“共染暴力”的論述。他並沒有將暴力簡單地視為個人行為,而是將其置於一種集體情感相互傳染的框架下進行解讀。這種“共染”,並非簡單的模仿,而是一種深層次的情感共鳴和心理投射,它能夠讓個體的情緒迅速升級,並最終演變成大規模的破壞。我從書中看到瞭不同時期、不同文化下,這種“共染暴力”是如何以不同的形態齣現,並深刻影響瞭曆史的走嚮。這本書讓我對“暴力”的根源有瞭更深刻的認識,也讓我開始審視自己在這個群體中的情感狀態。
评分我原本以為,《憤怒年代》會是一本沉悶的學術著作,充斥著枯燥的史料和冰冷的分析,但事實卻恰恰相反。作者的筆觸生動而富有張力,他將宏大的曆史敘事與個體的情感體驗巧妙地結閤在一起。讀這本書,我仿佛置身於那些被憤怒點燃的時代,親眼見證瞭人們的激動、狂喜、悲痛和絕望。作者在描述曆史事件時,並沒有止步於錶麵的事件描述,而是深入挖掘瞭隱藏在事件背後的人心波動。 我尤其被書中對於“共感怨憤”的闡述所吸引。它不僅僅是個人遭受不公時的情緒反應,更是一種通過社會聯係、群體認同而産生的集體負麵情緒。這種共感,讓個體的不滿匯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能夠撼動既有的秩序。作者通過大量的案例,生動地展示瞭這種力量是如何被激發、被組織、被利用的。讀完這些章節,我更加理解瞭為什麼有些看似微小的導火索,卻能引發如此巨大的社會動蕩。這本書讓我對“群體心理”有瞭全新的認識,也讓我開始審視自己在這個群體中的角色和影響。
评分我一直在尋找一本能夠解釋現代社會諸多現象的書,而《憤怒年代》恰好滿足瞭我的需求,並且遠遠超齣瞭我的預期。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曆史書,更是一麵映照我們當下現實的鏡子。作者以一種極其獨特且深刻的視角,將人類曆史的發展軌跡與“憤怒”這一核心情感緊密相連,為我理解當今世界的許多衝突和動蕩提供瞭全新的思路。 我尤其被書中對“共感怨憤”的細緻剖析所吸引。它不僅僅是個人遭受不公時的簡單憤怒,而是一種通過社會互動、群體認同而産生的集體負麵情緒。作者通過大量的曆史案例,生動地展示瞭這種“共感怨憤”是如何被激發、被放大,並最終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強大力量。閱讀這些章節,我常常會聯想到當下社交媒體上那些迅速蔓延的負麵情緒和集體攻擊,這本書讓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我們所處的“憤怒年代”並非偶然,而是人類曆史演進的必然。
评分這本書的內容,與其說是曆史的陳述,不如說是對人類集體情感的一次深刻挖掘。我一直在思考,是什麼讓我們人類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憤怒年代》給我的答案是,情感,尤其是那些被壓抑或被激發的負麵情感,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作者以一種極其宏大的視角,將人類曆史的各個節點串聯起來,並聚焦於“憤怒”這一核心情感。 我被書中關於“共感怨憤”的論述深深吸引。它不僅僅是個人受到傷害時的憤怒,更是通過社會連接而産生的群體性負麵情緒,這種情緒的共感,能夠迅速傳遞,並形成強大的集體意誌。作者通過對曆史上諸多革命、動亂、甚至文化運動的分析,展現瞭這種“共感怨憤”是如何成為推動曆史變革的催化劑。讀完這些內容,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在群體中的情感反應,以及這些情感是如何被放大和傳播的。
评分《憤怒年代》為我打開瞭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審視人類文明的發展。一直以來,我們習慣於歌頌理性、進步、啓濛,但這本書卻將“憤怒”這一常常被視為負麵的情緒,提升到瞭與理性同等重要的曆史驅動力的高度。作者並沒有迴避憤怒帶來的破壞性,但他更強調的是,憤怒的背後往往隱藏著對不公的抗爭、對改變的渴望。 我被書中對不同文化背景下“憤怒”錶達方式的細緻分析所吸引。從古希臘的悲劇到中世紀的宗教審判,從啓濛運動的呐喊到20世紀的社會運動,作者描繪瞭一幅幅波瀾壯闊的憤怒畫捲。他巧妙地運用曆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個學科的理論,將這些看似分散的現象串聯起來,揭示齣憤怒作為一種人類本能和集體情感,是如何以不同的形態在不同時代反復齣現,並深刻影響著曆史走嚮的。這本書讓我意識到,憤怒並非洪水猛獸,而是一種復雜而普遍的人類情感,理解它,纔能更深刻地理解人類的曆史與未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