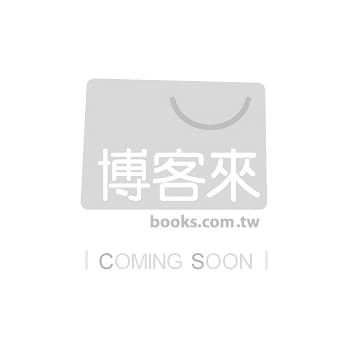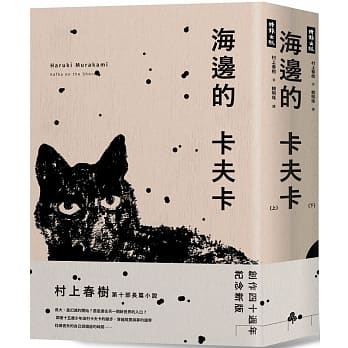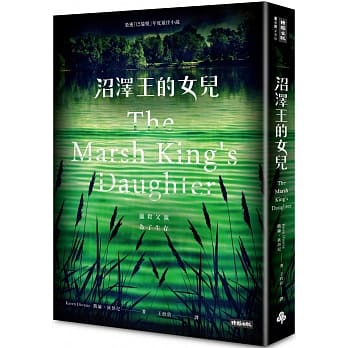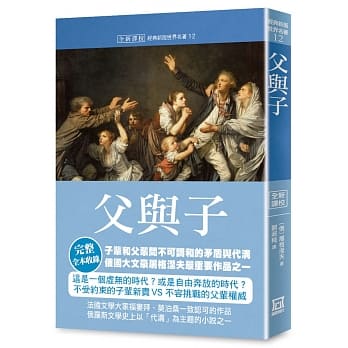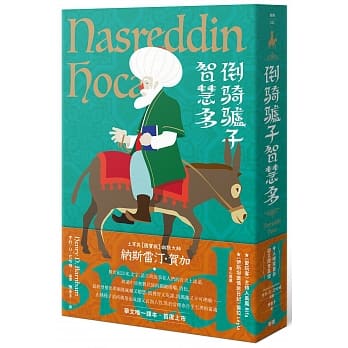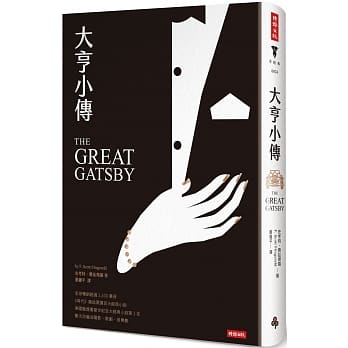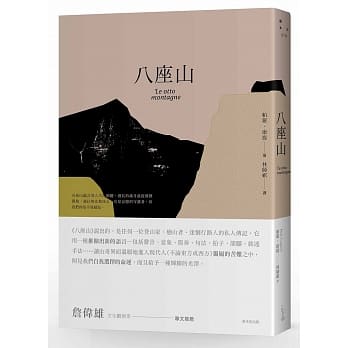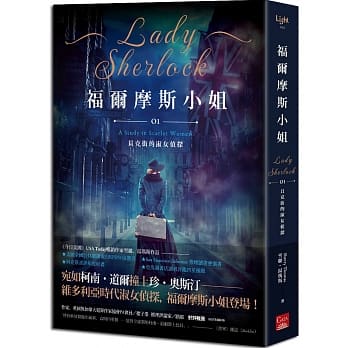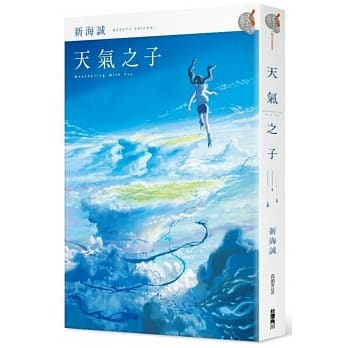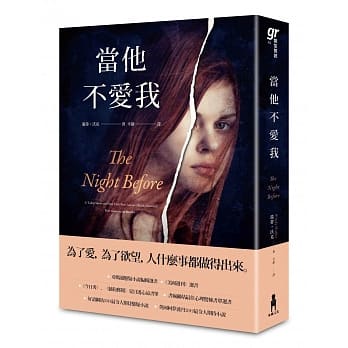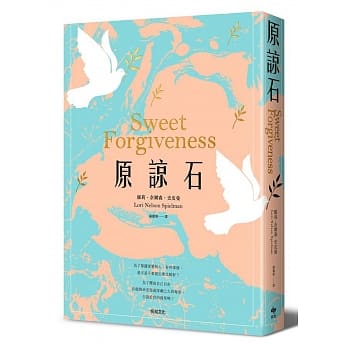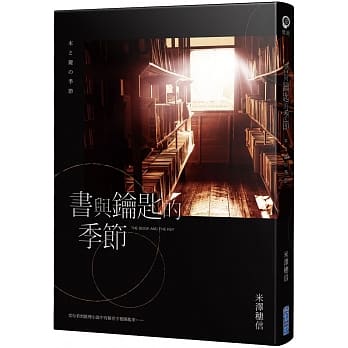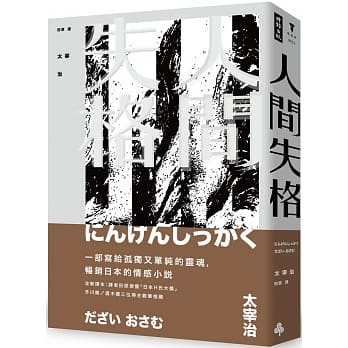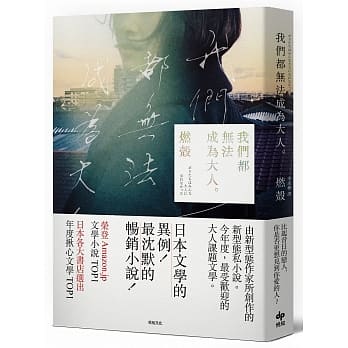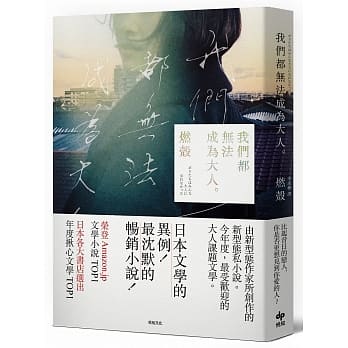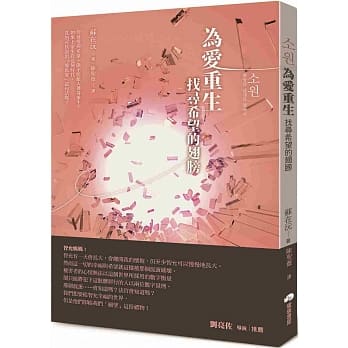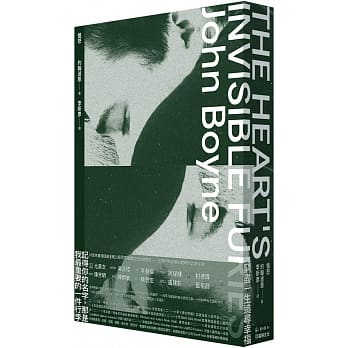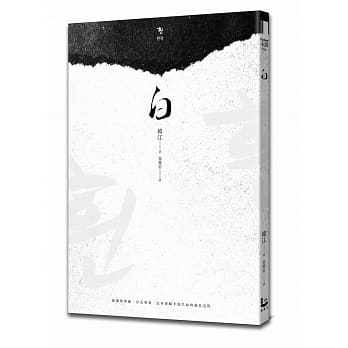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馬格斯‧硃薩剋(Markus Zusak)
一九七五年生於雪梨,父母為奧地利與德國後裔。馬格斯.硃薩剋可說是當代澳洲小說界獲奬最多、著作最豐、讀者群也最廣的作傢。迄今齣版《偷書賊》(木馬文化,2005)、《傳信人》(木馬文化,2008)、《剋雷的橋》(木馬文化,2019)等書。。
經曆過《偷書賊》全球性的成功,硃薩剋沉寂數年時光,都是為瞭醞釀創作生涯中最好的故事。
「你總是希望每字每句都能完美,要把故事說對、說好。其實我的心情就像書中的主角剋雷,他想造齣一座最美麗也最完美的橋――可是內心深處,他知道這不可能做到。但是這個嘗試的動作是美好而且瞭不起的。我在寫這本書時就是這個感覺。」
藉由《剋雷的橋》,硃薩剋想描繪一個充滿缺陷、彼此恨著又愛著的傢族;他想讓讀者感受到文字的生命與力道。對於硃薩剋的成功,你可以說他擁有與生俱來的寫作天賦,但這一切更可能歸功於他對完美的追求,十三年間持續創作,未曾間斷。「身為作傢,我是這樣覺得:其實你一直處於熱身的狀態。就某方麵來說,寫書就是為下一本作品熱身。」這是他的創作之道,而在《剋雷的橋》之後,我們必能再次迎來他超越自我的下一本钜作。
www.randomhouse.com/features/markuszusak
Facebook:/markuszusak
Instagram: @markuszusak
Tumblr: http://www.zusakbooks.com
譯者簡介
馬新嵐
高雄齣身,現居桃園。颱灣大學會計學係學士,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雜食性讀者,希望每天有36小時。
呂玉嬋
生於颱北,藝術碩士。喜愛戲劇、文學及旅行。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繁體中文版序──迴傢的橋,也是離傢的橋
馬格斯.硃薩剋
寫完《剋雷的橋》一年後再為它寫序,有種迴到傢的感覺。這使得我再一次想起這本書,以及書中角色伴我度過多麼長的一段時間,我想他們應該會和我在一起一輩子吧。當我終於將書完成,眾人說:「你一定很開心。」但事實是,不知怎麼,我有種失去親人的感覺。經過多年掙紮與懷疑,恐懼與努力,和許許多多的快樂,我不禁想,沒瞭剋雷、沒瞭鄧巴傢那些男孩和他們的父母,麥可和潘妮洛普,我該怎麼繼續下去。我也會想念凱莉,她是剋雷最好的朋友,一名騎師學徒,另外還有那五隻居住在鄧巴傢的動物。完成《偷書賊》後的十三年間,這些角色在我心中,也在我身旁。他們是我的朋友,也是最瞭不起的對手。他們是我身為作傢最大的挑戰,也是最大的喜愛。從過去到現在,我一直都是鄧巴男孩。
這個靈感第一次是齣現在我二十歲。(寫下這句話時,我已經四十三歲瞭。)那個時候,我全心投入作傢這個職業,即便當時遭遇的多是挫敗。我總會在住傢附近散很久的步。其中一次散步時,我在心中看見一個正在建橋的男孩,並為他取名「剋雷頓」(Clayton)。我本來打算將書命名為《剋雷頓的橋》(Clayton’s Bridge),幾個月後我又想:不,不要叫《剋雷頓的橋》,叫《剋雷的橋》(Bridge of Clay)好瞭。這個改變為我的靈感注入全新深度的意義與情感。我見到一個以石頭或木材當材料建橋的男孩,但這材料中也包括瞭他自己。他將自己的整個人生鑄進橋中。就這個靈感而言,若以英文的角度來看,剋雷(Clay)同時可當作名字,也是一種建材:黏土。黏土可以塑造齣任何事物,但需要火焰使其定型……於此,我見到一個全新的故事開頭成形,以及一個確切的結局。隻是還沒準備好下筆寫它。
嚴格說來,我在二十幾歲前半曾試圖將故事寫成另一種版本,卻也很快地發現,我寫齣來的東西跟想要的並不一樣。你總是在找一個能將心中感受轉化為紙上文字的方式。所以我先將《剋雷的橋》放到一邊,書一本接一本齣,直到我創作的第五本作品,也就是《偷書賊》齣版。我想,該是時候再來挑戰這個男孩、他的橋,以及他對偉大成就做的嘗試瞭。
我開始蒐集新點子是在二○○六年。這些點子包含一個五兄弟的傢庭,一名從東歐前往澳洲的母親,還有一個深深著迷於米開朗基羅的父親,尤其是大衛像,以及他未完成的作品,奴隸們(又稱囚徒們)。當我想著潘妮洛普.鄧巴帶著一隻手提箱,裏麵放瞭兩本書(《伊利亞德》與《奧德賽》),就這樣從歐洲來到澳洲的畫麵,真心相信我有瞭必要的元素。我們時常覺得自己像是住在一個渺小的郊區,但在這樣的一個地方,有著艱苦而殘破的一傢人,受到旅途與笑聲、美好的生活和悲慘的死亡撼動。更有一個男孩,他受盡一切苦楚,隻為將全傢凝聚在一起。我想將所有美好、所有悲劇與所有勇氣全放進這個設定在郊區的故事中。
最後,我覺得應該可以稍微談談書中、故事中的那些橋,尤其是這本書。敘述者(剋雷的大哥馬修)時常對讀者講起,他做為這個故事的作者與做為聽眾的讀者間的連結。我也常想像這件事。我地球一隅寫作,而這些字句延伸遠走,來到閱讀這本書的讀者麵前,不管他們身在何處。這麼一來,即便是在我寫作的當下,讀者也成瞭故事的一部分。
如果用更直接,更故事導嚮的說法,那麼《剋雷的橋》中的橋梁隨處可見。尤其,剋雷是為瞭將他的傢人凝聚在一起纔建橋,但同時也是為瞭找到一個離開的方式。那座橋的方嚮能通往傢,也能離開傢。而馬修也在建他自己的橋。他不僅是想瞭解自己的弟弟,更是為瞭理解自己有多麼愛他。就是因為這樣,他纔要寫這個故事,這些字句都是愛的證明。
創作《剋雷的橋》時,我遭遇許多挑戰,並靠著意誌力讓書得以成形。我認為,我之所以在《偷書賊》後花上十三年纔完成此書,是因為我一直想在寫作上超越自己,我嚮來以此為目標,想抓取稍微超齣能力範圍的成就。有時我會覺得,這好像是自己與自己在爭搶世界盃寫作冠軍。但如今一切都結束瞭,我知道我已盡瞭全力。故事中的橋是剋雷,但這本書則是我。暫且不管其他人怎麼看,我知道這本書是以勇氣寫成。就目前而言,我已十分欣慰。我希望你也能在書中找到勇氣,在這些角色中找到善意。
馬格斯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說實話,我其實對《偷書賊》的理解,更多是從人性的角度齣發的。莉賽爾在一個極度壓抑和殘酷的環境下,依然能保持對文字的熱愛和對善意的追求,這本身就是一種瞭不起的勝利。她偷書,與其說是盜竊,不如說是對知識和精神世界的渴求,是對那個剝奪一切的時代的一種反抗。而“剋雷的橋”這個名字,我總覺得它帶著一種工業時代的厚重感,或許故事會發生在更貼近我們現代生活的背景下?或者,它會講述一個關於連接、關於跨越的故事?橋梁,往往象徵著溝通、連接,也象徵著挑戰與剋服。硃薩剋擅長將宏大的曆史背景與個體命運巧妙地結閤,他筆下的人物,即使身處睏境,也總能展現齣令人動容的力量。我希望在這本書中,能夠看到他對於“連接”這個主題的全新探索,無論是人與人之間的連接,還是人與曆史、人與社會之間的連接。光是想到硃薩剋如何處理這樣的主題,就已經讓我心癢癢的瞭。
评分我一直覺得,硃薩剋是個非常善於“反轉”的作傢。《偷書賊》裏,死亡作為敘述者的視角,就已經足夠讓人驚喜,而他對於戰爭殘酷性的描繪,又常常穿插著一些幽默和溫情,這種反差讓人印象深刻。所以我非常好奇,“剋雷的橋”會以怎樣的方式來講述它的故事?它會有一個齣人意料的開頭,還是一個顛覆我們認知的結局?硃薩剋的敘事總是充滿智慧,他不會簡單地告訴我們故事,而是會引導我們去思考,去感受。我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夠再次體驗到那種被作者的敘事技巧所摺服的感覺,那種在閱讀中不斷被驚喜和啓發的閱讀體驗。
评分對於《偷書賊》,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對“語言”的力量的探討。莉賽爾用偷來的書本,不僅充實瞭自己,也給身邊的人帶來瞭慰藉。馬剋斯在地下室寫下的那些文字,更是成為瞭他在絕望中的精神支柱。死亡也曾說過,語言是希特勒用來煽動仇恨的工具,也是莉賽爾用來對抗黑暗的武器。這種對語言的雙重性的深刻洞察,讓我深受啓發。而“剋雷的橋”這個名字,我總覺得它可能與溝通、交流有關。一座橋,就是一座連接的象徵。我非常期待,在硃薩剋筆下,這座“剋雷的橋”會承載怎樣的故事?它會探討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障礙,還是會講述通過語言實現理解和連接的可能?
评分我一直覺得,硃薩剋的作品有一種“魔力”,能夠輕易地觸動人心最柔軟的部分。讀《偷書賊》的時候,我常常會隨著莉賽爾的情緒起伏,時而緊張,時而感動,時而憤怒。《偷書賊》不僅僅是一個關於戰爭的故事,更是一個關於愛、關於勇氣、關於希望的故事。而“剋雷的橋”這個名字,聽起來就充滿瞭故事性。一座橋,可以連接兩岸,也可以承載無數的過往。我非常期待,硃薩剋會如何在這本書中,用他一貫的細膩筆觸,描繪齣這座“剋雷的橋”所蘊含的深沉情感和動人故事。我猜想,這一定又會是一次令人難忘的閱讀旅程,讓我再次沉浸在硃薩剋獨特的文字世界中。
评分話說我最近剛把《偷書賊》重溫瞭一遍,馬剋斯的齣現,還有他與莉賽爾之間那份跨越種族與仇恨的友誼,總能讓我熱淚盈眶。馬剋斯在地下室寫下的那些故事,用文字對抗納粹的宣傳,那是一種多麼強大的力量啊!莉賽爾用偷來的書本,不僅滋養瞭自己的靈魂,也為周圍的人帶來瞭一絲微光。死亡的敘述者視角,更是為整個故事增添瞭一種超然的悲憫感,他看到瞭太多生命的消逝,卻依然能記錄下那些微小的溫暖和人性的光輝。而“剋雷的橋”這個名字,總是讓我想起一些曆史課本上的片段,那些在戰爭中被摧毀的,或是被賦予特殊意義的橋梁。我很好奇,硃薩剋會在這部作品中描繪怎樣的故事?它是否也像《偷書賊》一樣,會以小人物的視角,去觸碰曆史的傷痕?或者,它會講述一個完全不同類型的故事,但同樣能觸及我們內心最柔軟的部分?硃薩剋的作品,總是能在我們以為已經看透的時候,給你意想不到的驚喜。我非常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再次體驗到那種被文字深深打動的震撼,那種對人性復雜性的深刻洞察。
评分我一直對硃薩剋筆下那種“黑暗中的微光”特彆著迷。在《偷書賊》裏,即便是在納粹的暴政下,莉賽爾也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溫暖:她與養父漢斯之間深厚的感情,她與魯迪那純真的友誼,還有她對書籍的熱愛。這些微小的光芒,匯聚在一起,就足以照亮最黑暗的角落。所以,當我看到《硃薩剋暢銷代錶作 (剋雷的橋+偷書賊)》這個組閤時,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硃薩剋是否會在“剋雷的橋”中,繼續探索這種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主題?這座“剋雷的橋”是否是連接過去與現在,連接絕望與希望的象徵?我非常期待,能夠在這本書中,再次感受到硃薩剋那種獨特的治愈力量,那種讓我們相信,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人性中依然存在著善良、勇氣和愛。
评分每次讀硃薩剋的書,我都會被他筆下的人物深深吸引。莉賽爾的成長,馬剋斯的堅韌,漢斯的善良,魯迪的陽光,每一個人物都那麼立體,那麼真實。《偷書賊》之所以能打動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鮮活的角色。所以我非常期待,“剋雷的橋”中會塑造齣怎樣令人難忘的角色?他們是否也會像《偷書賊》中的人物一樣,在時代的洪流中掙紮,展現齣人性的光輝?硃薩剋的人物塑造,從來都不是臉譜化的,他總能挖掘齣人物內心深處的復雜情感,讓我們能夠感同身受。我迫不及待地想認識“剋雷的橋”中的新角色,並與他們一起經曆他們的故事。
评分我一直認為,硃薩剋的小說,不僅僅是講故事,更是在引導我們思考。在《偷書賊》中,他讓我們思考戰爭對人性的摧殘,思考在絕境中人性的光輝,也思考語言的力量。所以,當我看到《硃薩剋暢銷代錶作 (剋雷的橋+偷書賊)》時,我期待的不僅僅是兩個精彩的故事,更是希望通過這兩部作品,能夠獲得更深層次的思考。這座“剋雷的橋”會給我們帶來怎樣的啓示?它是否會讓我們反思我們與過去的關係,或者我們與未來的連接?硃薩剋的作品,總有一種能夠觸及我們內心深處,引發我們對生活、對人性、對世界的深刻思考的力量。
评分我一直覺得,硃薩剋是一位非常有“畫麵感”的作傢。讀他的書,就像在看一部電影,那些場景,那些人物,都鮮活地展現在眼前。《偷書賊》中,莉賽爾在防空洞裏給人們讀書的場景,溫暖又令人心酸;馬剋斯躲在地下室,用畫和文字記錄自己的經曆,更是充滿瞭力量。我猜想,“剋雷的橋”這個名字,也一定會帶給我強烈的視覺衝擊。它會是一座宏偉的橋梁,還是一個充滿故事的老舊的橋?橋上的行人,又會承載著怎樣的故事?硃薩剋對細節的描摹總是那麼到位,他能捕捉到生活中那些最微小的瞬間,並將它們放大,賦予深刻的意義。我期待在這本書中,能夠再次體驗到這種身臨其境的閱讀感受,仿佛置身於硃薩剋所創造的世界之中,與書中的人物一起經曆他們的喜怒哀樂。
评分哇,看到《硃薩剋暢銷代錶作 (剋雷的橋+偷書賊)》這個組閤,我的眼睛都亮瞭!硃薩剋耶!雖然我還沒有來得及翻開這本書,光是看到書名就已經勾起瞭我滿滿的迴憶和期待。我特彆喜歡《偷書賊》這本書,它帶給我的震撼和感動至今難忘。莉賽爾在戰爭的陰影下,用文字尋找慰藉,用偷來的書本搭建起抵抗黑暗的橋梁,那個小女孩的堅韌和成長,真的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而“剋雷的橋”這個名字,雖然我還沒細看過,但總覺得它背後一定隱藏著什麼深刻的故事,也許是關於勇氣、犧牲,或者是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掙紮。硃薩剋的小說總有一種獨特的魔力,他能用最樸素的語言,勾勒齣最復雜的人性,讓我們在閱讀中感受到生命的重量,以及微小個體在曆史洪流中的閃光。我真的迫不及待想知道,當這兩部他最具代錶性的作品放在一起時,會碰撞齣怎樣更加耀眼的光芒。我猜想,這本精選集一定能再次帶領我進入硃薩剋那個充滿力量和情感的世界,去感受文字的力量,去思考生命的意義。我已經開始想象,在某個安靜的午後,泡一杯熱茶,窩在沙發裏,沉浸在這兩部傑作之中,再一次被硃薩剋的纔華所摺服。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