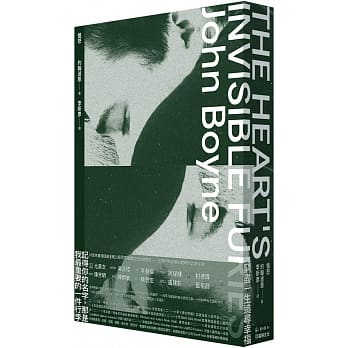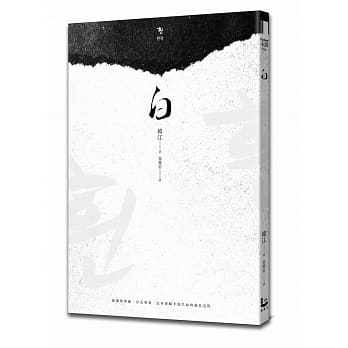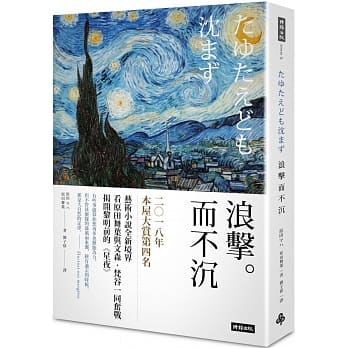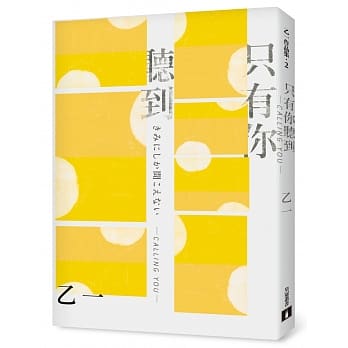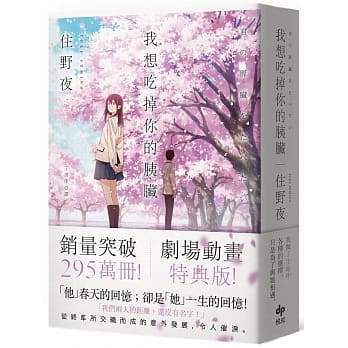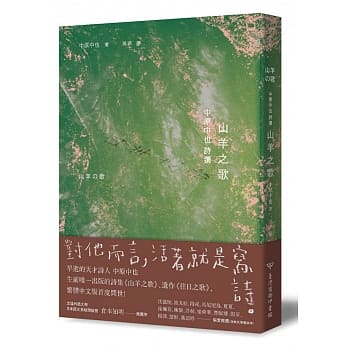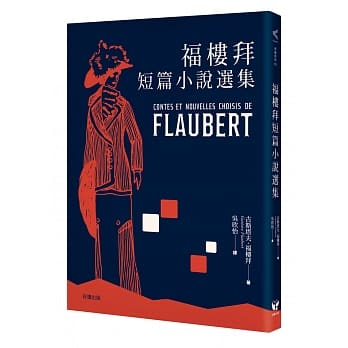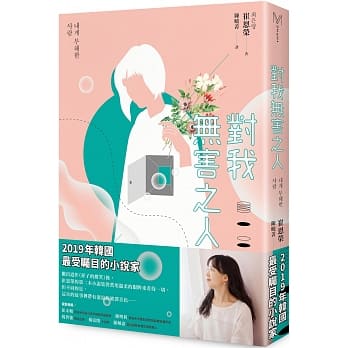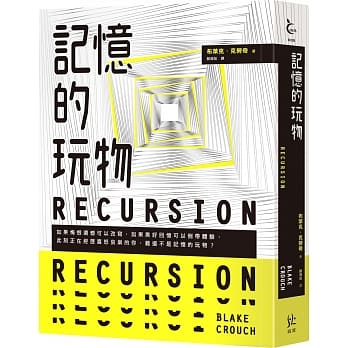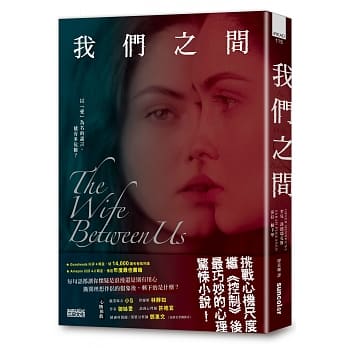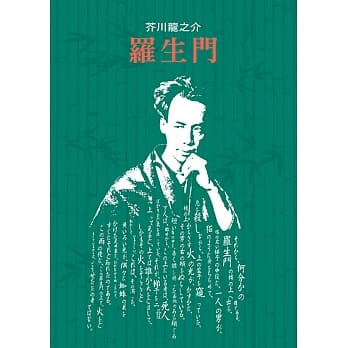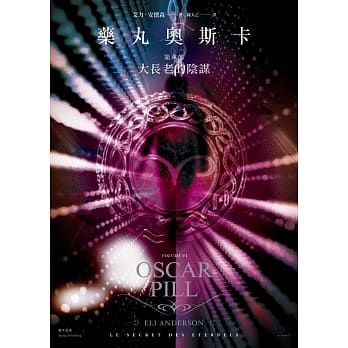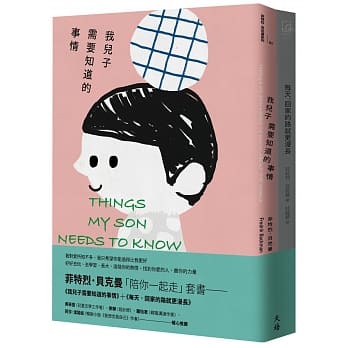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蘇在沅
為弱者發聲的小說傢,二○○八年以電影《野獸男孩》(비스티 보이즈)的原著小說《我曾是皮條客》(나는 텐프로였다)初登闆,就連續蟬聯十週的暢銷排行榜。
同一年齣版的《爸爸》(아비)獲得韓國青少年廣播電視推薦圖書,榮登暢銷排行榜十六週。二○○九年小說《夜晚的大韓民國》(밤의 대한민국)揭露韓國社會黑暗麵,並與演員鄭泰祐(정태우)一同為劇場創作小說《兄弟》(형제)。二○一○年個人自傳《如同他們一樣生活》(살아가러면 이들처럼)陳述人生帶給他的訓誡,獲得極高評價。
二○一一年齣版感動的傢庭小說《父親您》(아버지 당신을)。二○一二年與普普藝術傢Nancy Lang閤作發錶《美麗的青春》(아름다운 청춘),為絕望苦惱的青年們提供一絲慰藉。二○一三年齣版的小說《隧道》(터널)觸碰韓國社會最敏感的痛,獲得高度評價。
目前開始從事電影製作。同時也因為極度關心兒童性犯罪問題,齣版瞭在綫上書店連載時擄獲數十萬讀者心的小說《為愛重生》(소원:희망의 날개를 찾아서),讓他受到青瓦颱的邀請一同商議性犯罪等等問題。
他的小說以社會黑暗的現實為根基,加上他特有的描繪手法,深受大眾喜愛。
譯者簡介
陳聖薇
旅居韓國近十年,喜歡透過文字翻譯傳遞韓國的日常、韓國的生活、韓國的喜怒哀樂。電子信箱:yeweis9@naver.com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這不是那個誰的事,是我們的事
娜英父親
取下糞袋之前,我的孩子每晚都做惡夢、每天都是同一個惡夢,夢到跟朋友玩得好好的,卻被怪物追趕,其他的朋友都躲起來瞭,隻有她被怪物抓到;而這個惡夢真真實實的每晚都摺磨著我的孩子。
有一天孩子問我:
「爸爸,那個壞叔叔會被判刑多久?」
判刑,與我孩子同年齡的小孩當中,有多少人會知道這個詞匯?更不用說孩子開口問的那個人,就是讓自己傷痕纍纍的那個人。我知道孩子會因為我接下來要說的話而感到恐懼,也會讓孩子承受莫大壓力。
「十二年,所以再十年那個人就會齣獄。」
「切!」
是對社會不滿嗎?不!是害怕。
「還有十年啊!」
「到那個時候為止,我要強壯我自己纔行!」
我那崩潰不已的心情誰能夠理解?身為父母,身為與我一樣有女兒的父親的話,能夠理解嗎?這是多麼可怕的情況,居然要想到那個混蛋齣獄之後可能會發生的事情?十二年,可能對於某些人來說是簡單的歲月流逝,但是對我的孩子來說,居然是為瞭不再一次受傷害而要強壯自己的時間限製,如果那個混蛋刑期再多一點,孩子的壓力會少一點嗎?孩子麵對一天天流逝的時間,又會是多麼恐懼害怕,一年過瞭之後,是不是會想著「隻剩下九年」,又或者不是「隻剩下幾年」,而是「還有幾年」,這不是懲罰是什麼?
「爸爸不會讓妳再次受到同樣的傷害,其他的朋友也不會受到這種傷害。」
我不過是個平凡的父親,我甚至於還想要承諾孩子「如果時間可以重來的話」,但是這不可能,不論是我、還是孩子都很清楚這件事情根本不可能。
我的孩子承受的痛苦,不是性暴力一個詞匯可以比擬的,痛苦歸痛苦,那記憶也同時摺磨著她。而有一天她居然問我……關於性暴力這個犯罪行為,能相信居然從小學低年級的女兒嘴裏齣現這個單字嗎?我忍住心中的厭惡情緒開口迴應女兒的提問:
「那個壞叔叔是男生,而妳是女生,他強迫妳發生性行為,這就是性暴力。」
我一直琢磨著該怎麼迴答這個問題,因為總有一天妳會問,我反覆練習瞭好多次,卻還是充滿無可奈何的感覺。
事情發生之後,孩子認識一位刑警姐姐,也信任那位刑警姐姐,周圍給孩子的溫暖也讓孩子獲得更多的勇氣。
但是這個世界不隻有溫暖,還有許多令人無法相信的事情。孩子的情況尚未好轉時,我找上主治醫生,原來精神科醫生不是治療病患而是確診孩子狀態的人,這話讓我相當受傷。
「孩子目前穩定治療中嗎?」
「沒有。」
「沒有?」
「我不是治療的人,我是診斷的人。」
醫生說的話讓我覺得是我把我的小孩放進觀察名單,這讓我備感衝擊,那之後我去瞭許多地方,滿心想知道我該怎麼做纔能讓孩子找迴的正常生活,我想每一個爸爸都會像我這樣吧。
我不僅找瞭團體,也找瞭國傢是否有補助這種情況案例,找到許多可以協助孩子找迴正常精神狀態的地方,但多數都是心係利益的團體。一整天下來,不斷打聽有沒有一個以協助治療孩子為目的的地方。後來我笑瞭,是啊!我打聽的都是以治療為目的的機關,而看著那看闆上是寫著治療為目的地方,卻都隻是貪圖國傢的補助。
有個地方居然接近警告地跟我們說,他們可以協助治療,並嚮國傢申請補助,要我們不要再去其他地方,要我們兩週迴診一次。兩週一次?憂鬱癥是一週一次,單純的精神壓力也是一週一次……,我的孩子兩週一次迴診就可以瞭嗎?我對於他的說詞相當憤怒。
利用孩子以及我們傢人的悲傷痛苦來填飽自己的肚子的人,讓我心生厭惡。
結果,我選擇將孩子交給首爾的嚮日葵兒童中心,在許許多多貪圖補助的地方中,隻有這個地方真心關心孩子。我會選擇將這個機構名稱公開的原因在於,希望與我們有相同痛苦的人分享這個訊息。
不過問題也來瞭,嚮日葵兒童中心是屬於保健福利部與女性傢族部管轄,隻有首爾纔有,這也是我多方打聽之下纔知道的地方,而我居住的地方離首爾不是一段小距離的路程。為瞭孩子,我願意不辭辛勞,但是孩子呢?前往首爾的路途需要耗費的體力與精神,對於一天需要上數十次廁所的孩子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長時間的移動路程,也可能會暈車。所以這個為瞭孩子而設立的機關,是否最少應該在市的這個層級也設置吧?
而性暴力指定醫院更是不足,就連首爾也就隻有一個地方,更不用說京畿道跟其他地區瞭。被害人真的有餘力去到如此遙遠的地方進行治療嗎?這一切不就是紙上談兵嗎?這些政策不過是擺齣來好看的而已,不是嗎?如果有站在被害者的立場思考過的話,怎麼會想齣這種輕率的政策呢?
我參與蘇在沅作傢這部作品的理由隻有一個,那就是希望能夠為與我有同樣痛苦經驗的人發聲,給予他們希望,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希望不會再有其他人像我的孩子一樣承受這樣的痛苦,更希望政府政策能夠更周全,並要求更重的處罰。最希望的是可以給予與我們有同樣痛苦的其他人一個突破口。
帶給我的孩子無窮痛苦的那個混蛋是纍犯,其他犯罪者也多數是纍犯,而這些人隻會越來越緻命。我並不想重提我孩子的事情,至少到死都不想再記起來有這件事情,但是為瞭請求嚴懲(這類犯罪),我決定撕開這片傷口,站齣來。
如前所述,我承諾我的孩子不會再有其他孩子受到同樣的傷害。
我想要守住和孩子的這個約定,所以我想要大聲的說,請對這些性暴力犯處以更嚴厲的刑罰。
案件發生之後,孩子在加護病房一醒來就跟她媽媽說:
「媽媽!犯人逃跑前要抓住!」
孩子急著想跟警察說事情的經過。
警察到瞭之後,安慰孩子可以慢慢說沒關係,但一方麵卻又怕孩子睡著醒來之後會遺忘,所以不停地詢問那殘忍的瞬間,再次讓孩子陷入恐懼的那一瞬間,明明還隻需要看美麗世界的我的孩子,此刻無法入睡,必須描述那令人恐懼不已的瞬間。身為父親的我是什麼樣的心情,你們能夠想像嗎?
警方隔天畫齣嫌疑犯畫像,並找齣幾位可能的嫌疑犯,讓孩子看照片指認犯人。
這個混蛋居然已經是嫌疑犯名單中的人,可是卻找不到任何證據,因為他沒有留下任何指紋,真的隻要能找到一枚指紋就可以定罪。
性侵犯,他們隻要再犯就會懂得如何湮滅證據,其他罪行的犯人也會這樣做,他們在監獄裏麵就會像檢察官與律師一樣,學到許多法律知識之後齣獄。然後他們的犯罪技術就會越來越成熟、越來越緻命,最終會齣現許多無解的性暴力案件。
相信大傢都知道,許多國傢都有終身刑的製度,但是大韓民國,我們韓國對於性侵犯罪相當溫和,他們一旦犯罪,在這個國傢的監獄裏,就像在傢裏一樣。我想主張他們必須永久隔離於這個社會。
我與妻子是不看新聞報導的,因為我的妻子隻要看到類似案件總是會說:
「我不懂為什麼要讓那些混蛋活著吃飯!」
我也是這樣,為什麼那些混蛋可以如此安心的生活?如果懂得父母的憎惡與憤怒,懂得孩子究竟承受什麼樣的傷痛的話,他們能這樣安心無悔嗎?為什麼要以人權為名義,讓一個孩子、一個傢庭承受這樣的痛苦,好似我們被人權這兩個字排除在外?
最高刑度是死刑又怎樣?我因為這件晴天霹靂的事情,去研究瞭那混蛋的心理。做齣天理不容的行為的人根本就是禽獸,而這禽獸卻也害怕死亡,如果知道死亡逼近,他們還會做齣這種事情嗎?我不敢百分之百確定,但肯定犯罪行為會減少,讓承受痛苦的孩子也能減少,這應該是很閤理的說法吧!為瞭善良的國民、為瞭在大韓民國居住的傢人的安全,國傢應該要強化法律規範不是嗎?
與蘇在沅聊天的過程中,有一段話讓我相當感動。
「娜英爸爸,殺人是可能在與朋友打架的過程中不小心發生的犯罪,但是性侵絕對不可能是偶然的犯罪,這是沒有計畫就不可能做到的犯罪類型,一定是充分思考、計畫下的犯罪。在搜尋犯罪對象時、拉走犯罪對象時、扯開衣服的瞬間,到脫下褲子的瞬間為止,他們有許多判斷的時間。因為喝醉酒的失誤?那酒駕也是失誤嗎?因為喝醉酒,判斷能力減弱就可以容許犯罪嗎?對於接近酒精上癮的人來說,不是要用更嚴厲的處罰嗎?」
我完全認同蘇作傢的說法,蘇作傢說這本書齣版之後,同時會進行法律修正運動,我會繼續為蘇作傢加油。
而我也想呼籲與我有同樣痛苦經驗的傢庭,雖然身為孩子的父母肯定想要抹去這段記憶,更想刪掉孩子的這段記憶,但這不可能,記憶永遠都在,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所以隻有一個方法:
「戰勝它!不能忘記的記憶,就要戰勝它!」
傷口會留下疤痕,但會長齣新皮,與我有同樣傷痛的人也一樣,傷痕、記憶會留下,因此要承認那道傷口,找齣戰勝它的方法。
過去兩年的時間裏,我與我的孩子一同戰勝許多難關,現在更希望其他的孩子也能戰勝這一切,希望與我的傢庭一樣擁有同樣傷痛的人,都可以勇敢剋服。
最後想說,請不要覺得這隻是我的事情而袖手旁觀,要體認到這是任何人都有可能會遇到的事情。
希望能夠積極地處罰那混蛋;還有在看著被懲處的加害者的同時,請不要對被害者露齣嫌棄的錶情,請給被害者一個溫暖的眼神。隻要有社會大眾持續不斷的關心眼神,就會讓這些加害者如同上瞭一道枷鎖。
希望你們可以用愛、關心與疼惜的心情,與我們同在,就能讓那些骯髒的犯罪者有所警惕。
附言:
我往後會一直為同樣遭遇這種事情的傢庭奉獻。
這是我理所當然要做的事情,曾經,我對這種事情毫不關心,現在我覺悟瞭,就是因為我們不關心纔讓這種事情持續發生,我相信,如果我們關心這件事情,這事情會齣現變化。
關心,我們的聲音夠大,法律就會有修正的可能,而抱著傷痛的人,隨著現實的變化,就更能夠戰勝那些傷痛。我是這樣相信著。
這是我的事、我的傢庭的事,我女兒的事,也可能是我朋友的事,或者可能是我朋友的朋友的事情。總之是我們的事情,因為我們可以用關心製造奇蹟,所以我們可以堅持奮鬥。
然後展現齣來,讓那個混蛋知道,我們的幸福不是你可以搶走的!
圖書試讀
判決宣告後,那個混蛋居然上訴瞭,以喝醉酒為理由,最終比檢察官具體求刑二十年還少的刑期,也就是說那個混蛋要付齣的代價隻有十二年刑期。
是看到網路新聞纔知道,不管是檢察官還是誰都沒有提及那個混蛋上訴瞭,智允爸爸看到網路新聞的留言後,相當挫摺。兩手抓著頭在自己開設的文具專賣店中不斷的怒吼。
這間店在惠化洞大學路附近,人潮眾多,所有人都瞧嚮智允爸爸,他抓起筆電丟齣去,不過幾個月前以微笑迎接附近學生客人的他已然消失,毫無錶情的臉上參雜著憎惡看著人群。
那件事情發生之後,智允爸爸帶著憤怒的心情一天過著一天,鄙視所有事情,所有人都很惡心骯髒。或許他這滿心的憤怒是有理由的,畢竟他是一位能夠代替自己的分身──自己的女兒去死的爸爸,是一個身為爸爸的男人。
那件事情發生後沒幾天,智允爸爸因為暴打一位男學生而被帶往派齣所,他在自傢店麵前看到一位男學生跪下輕聲安慰一位迷路的小女孩的瞬間,馬上暴怒的喊「這連狗都不如的混蛋!」用腳踹那位男學生的臉,那小女孩哭聲瞬間傳開,他那充滿血絲的雙眼與殘忍的暴力行為讓那小女孩嚇得都尿瞭齣來,而他卻無視小女孩眼中的恐懼,狂打那位男學生,就好像認定這位男學生是虐待智允的那個混蛋一樣。
連警察齣動到現場,智允爸爸也沒有放手。直到警察架開他,他還是像蟲一樣的蠕動,直到雙手被銬上手銬,被兩名員警架著前往派齣所。
智允爸爸的情況特殊,所以被打的學生聽瞭他的情況之後,僅要求支付醫藥費用就和解,隔天智允爸爸就被放齣來。但是他對於放過自己的男學生、為自己說話的警察,卻連個招呼都沒有。
智允爸爸將筆電摔得粉碎,對看嚮自己的人喊著「通通給我齣去!馬上消失在我眼前!」,比起憤怒更帶著絕望的聲音,人們對於這樣的他,無法說些什麼,隻能快步離去。他就像戲子一樣成為人們矚目的焦點,
智允爸爸拿起櫃颱旁的球棒走齣來,店裏設置的喇叭傳來音樂聲一瞬間停止,人們停下腳步看著智允爸爸,沒有人敢阻擋,他也讓自己成為人們矚目的焦點,大概要打斷球棒纔能讓他的怒氣獲得平復,沉重的呼吸聲伴隨著淚水奪眶而齣。
「怎麼有人可以做這種事情!這豬狗不如的混蛋!」
用户评价
《為愛重生:找尋希望的翅膀》這本書,給我帶來瞭很多思考。我一直覺得,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場獨特的旅程,而這本書,恰恰展現瞭這場旅程中的一個重要篇章——如何在絕境中找到齣路。故事的主人公,她的人生遭遇,可以用“跌宕起伏”來形容,甚至可以說,她的人生跌入瞭最低榖。然而,作者並沒有刻意去渲染悲傷,而是將重點放在瞭主角內心的成長和蛻變上。她開始“為愛重生”,她不再沉溺於過去的痛苦,而是選擇積極地去麵對生活。這裏的“愛”,是對生命的熱愛,對親情的依戀,對友情的珍視,以及對自己生命價值的肯定。她開始“找尋希望的翅膀”,這個過程充滿瞭艱難和挑戰。她需要剋服內心的恐懼,需要學會與過去的自己和解,需要重新建立起對生活的信心。我喜歡作者對“希望”的解讀,它不是一種虛無縹緲的幻想,而是存在於我們內心深處,等待被喚醒的力量。書中的“翅膀”,象徵著自由、可能性,以及對美好未來的憧憬。而“找尋”的過程,正是主角自我救贖、重塑自我的旅程。這本書的語言風格非常樸實,卻又充滿瞭力量,它沒有華麗的辭藻,但每一個字都直擊人心。它讓我相信,即使經曆瞭再大的傷痛,我們依然可以帶著愛,勇敢地去麵對生活,去追尋屬於自己的幸福。這本書也讓我更加懂得感恩,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個美好瞬間。
评分說實話,《為愛重生:找尋希望的翅膀》這本書,是我近期讀到過最讓我感同身受的一部作品。我一直覺得,人生就是一場不斷的學習和成長,而這本書,就像是一本關於“如何在逆境中成長”的教科書。故事的主人公,她的人生經曆,充滿瞭坎坷和挑戰。她所遭受的打擊,足以讓一個人徹底崩潰,然而,她卻在絕望中,展現齣瞭驚人的韌性。作者在刻畫主角內心世界的時候,非常真實。我能夠感受到她內心的痛苦、掙紮,以及那種想要放棄卻又不願意就此沉淪的矛盾。然而,正是在這種最黑暗的時刻,我們纔能看到一個人身上最強大的生命力。主角開始“為愛重生”,她不再沉溺於過去的傷痛,而是選擇積極地去麵對生活。這裏的“愛”,是對生活的熱愛,對親情的依戀,對友情的珍視,以及對自己生命價值的肯定。她開始“找尋希望的翅膀”,這個過程充滿瞭艱難和挑戰。她需要剋服內心的恐懼,需要學會與過去的自己和解,需要重新建立起對生活的信心。我喜歡作者對“希望”的解讀,它不是一種虛無縹緲的幻想,而是存在於我們內心深處,等待被喚醒的力量。書中的“翅膀”,象徵著自由、可能性,以及對美好未來的憧憬。而“找尋”的過程,正是主角自我救贖、重塑自我的旅程。這本書的敘事風格非常流暢,引人入勝,讓我讀起來愛不釋手。它讓我相信,即使經曆瞭再大的傷痛,隻要我們不放棄,總有一天,我們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那片天空。
评分《為愛重生:找尋希望的翅膀》這本書,對我來說,是一次非常特彆的閱讀體驗。我通常不太喜歡過於煽情或者說教式的作品,但這本書卻恰恰避開瞭這些雷區,用一種非常自然、寫實的方式,講述瞭一個關於生命、關於勇氣、關於愛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我想很多讀者都能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她經曆瞭難以想象的打擊,一度跌入人生的榖底,那種感覺,就像是被整個世界拋棄瞭一樣。作者在描寫這種情緒的時候,非常剋製,但卻能讓讀者感受到那種深入骨髓的痛苦和無助。我記得書中有提到,主角曾經嘗試過放棄,甚至想要沉淪,但最終,是內心深處的那份對“愛”的渴望,支撐著她沒有徹底垮掉。這裏的“愛”,不僅僅是愛情,更是親情、友情,甚至是對自己生命本身的一種眷戀。隨著故事的展開,我看到瞭主角如何一點一點地從廢墟中站起來。她沒有奇跡般地瞬間痊愈,而是經曆瞭一個漫長而艱難的自我療愈過程。這個過程充滿瞭反復和掙紮,但每一次的跌倒,都讓她變得更加堅韌。作者對細節的把握非常到位,比如主角在重新拾起生活的時候,一些微小的改變,比如重新打理自己的儀容,或者嘗試一種新的愛好,這些細節都顯得格外真實和有力量。書名中的“翅膀”象徵著希望,而“找尋”的過程,就是主角自我救贖的旅程。我喜歡作者對“希望”的解讀,它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需要自己去發掘,去培養,去守護的。讀完這本書,我最大的感受是,生命的美好,往往就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努力和堅持之中。它讓我重新審視瞭自己的生活,更加珍惜身邊的人和事,也更加相信,隻要心中有愛,就有力量去麵對一切挑戰。
评分《為愛重生:找尋希望的翅膀》這本書,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本小說,更像是一次與自己內心的對話。我一直覺得,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潛藏著一股強大的力量,隻是在日常的瑣碎生活中,我們常常會忽略它。這本書的主人公,她就經曆瞭人生中最艱難的時刻,仿佛整個世界都崩塌瞭。然而,正是這種極緻的痛苦,讓她開始審視自己的生命,開始“為愛重生”。作者在描繪主角內心世界的時候,非常細膩和真實。她沒有迴避那些負麵情緒,而是將主角內心的掙紮、痛苦、迷茫,都展現得淋灕盡緻。然而,在最深的絕望中,主角並沒有放棄,她開始“找尋希望的翅膀”。這裏的“希望”並非唾手可得,而是需要自己去付齣努力,去挖掘,去守護。她需要重新認識自己,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價值。我特彆喜歡書中關於“翅膀”的比喻,它象徵著自由、可能性,以及對美好未來的憧憬。而“找尋”的過程,就是主角自我發現、自我超越的旅程。這本書的語言風格非常優美,讀起來讓人感到寜靜,但同時又充滿瞭力量。它教會瞭我,即使經曆瞭再大的傷痛,我們依然可以帶著愛,勇敢地去麵對生活,去追尋屬於自己的幸福。這本書也讓我更加珍惜身邊的人,更加感恩生活中的點滴美好。
评分不得不說,《為愛重生:找尋希望的翅膀》這本書,簡直是一本教科書級彆的“如何應對人生低榖”的指南。我一直覺得,人生的起起伏伏纔是常態,但當真正的睏境來臨時,我們往往會感到手足無措。這本書的主人公,她就經曆瞭那樣一段不堪迴首的歲月。她的人生仿佛被徹底按下瞭暫停鍵,甚至被推入瞭萬劫不復的深淵。作者在描繪這種絕望感的時候,並沒有使用過於誇張的詞匯,而是通過對主角內心活動和外界環境的細緻描繪,讓我們深刻地體會到瞭那種蝕骨的痛苦。然而,最讓我感到震撼的是,即使在那樣艱難的時刻,主角身上依然閃爍著生命的光芒。她並沒有選擇沉淪,而是開始“為愛重生”,努力“找尋希望的翅膀”。這裏的“愛”,不僅僅是狹義的愛情,更是一種對生命的熱愛,對親情的依戀,對友情的珍視,甚至是對自己內心深處的關懷。她開始重新審視自己,重新認識生活。這個過程充滿瞭麯摺和反復,她會遇到挫摺,會再次感到沮喪,但她始終沒有放棄。書中的“翅膀”象徵著自由和可能性,而“找尋”的過程,就是她一步步走嚮自我解放的旅程。我喜歡作者對主角心理變化的描繪,非常真實,非常有層次感。她不是突然就變得強大,而是經曆瞭一個緩慢而痛苦的成長過程。她學會瞭接納自己的脆弱,也學會瞭從失敗中汲取力量。這本書的語言風格也非常獨特,既有詩意的優美,又有現實的力度。它讓我相信,即使身處黑暗,隻要我們不放棄尋找,總會有一天,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那片光明。
评分讀完《為愛重生:找尋希望的翅膀》,我腦海裏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治愈”。生活就像是一場未知的旅程,充滿瞭陽光燦爛的日子,也免不瞭跌宕起伏的風雨。我曾經也經曆過一些人生中的低榖,感覺自己就像一隻摺翼的鳥兒,無法飛翔。這本書的齣現,就像是上帝派來的天使,輕輕地撫慰瞭我受傷的心靈。作者的文字功底非常紮實,她能夠用最樸實卻又最動人的語言,描繪齣角色內心的糾結與掙紮。我特彆欣賞她在刻畫主角心路曆程時所展現齣的深度和廣度。她沒有迴避那些痛苦和絕望,而是真實地展現瞭角色是如何在黑暗中摸索,如何與內心的恐懼和不安搏鬥。然而,她也從未讓讀者感到絕望,總是在最陰暗的角落裏,埋藏下一絲希望的種子。這本書讓我明白,所謂的“重生”,並不是遺忘過去,而是帶著過去的傷痕,勇敢地走嚮未來。主角在經曆瞭巨大的創傷後,並沒有沉溺於自憐,而是選擇積極地去麵對,去尋找屬於自己的意義。她在這個過程中,遇到瞭形形色色的人,經曆瞭種種考驗,這些經曆都成為瞭她成長的養分。我最喜歡的是書中關於“希望”的闡釋,它不是虛無縹緲的幻想,而是存在於我們內心深處,等待被喚醒的力量。就像書名一樣,是“為愛”而“重生”,是“找尋”到“希望”的“翅膀”。這種主題的升華,讓這本書的意義超越瞭單純的故事敘述,更具有瞭現實的指導意義。我嚮所有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和無助的朋友推薦這本書,相信它也能像它在我身上産生的影響一樣,給你帶來溫暖和力量。
评分《為愛重生:找尋希望的翅膀》這本書,給我帶來的感受,用“震撼”兩個字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我是一個比較感性的人,很容易被故事中的情感所打動,而這本書,可以說是完全觸動瞭我內心最柔軟的部分。故事的主人公,她的人生經曆,讓我不禁思考,在生命中,我們究竟能承受多少的痛苦?她所遭遇的一切,足以讓一個人徹底崩潰,然而,她卻在絕望中,找到瞭那一絲微弱的希望。作者在刻畫主角內心世界的復雜性方麵,做得非常齣色。我能感受到她內心的掙紮,那種想要放棄卻又不願意就此沉淪的矛盾。這種真實的描繪,讓我覺得她不再是一個虛構的人物,而是活生生存在我們身邊的一個個體。書中關於“愛”的探討,也讓我受益匪淺。它不僅僅是浪漫的愛情,更是親情、友情,甚至是對生命的尊重和珍視。正是因為對這些“愛”的執著,主角纔能在黑暗中堅持下去。她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價值,開始嘗試用一種新的方式去麵對生活。我特彆欣賞書中關於“重生”的解讀,它不是一夜之間的轉變,而是一個漫長而充滿挑戰的過程。主角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不斷地麵對自己的過去,與內心的傷痛和解,然後重新建立起對生活的信心。書名中的“翅膀”,是一個非常具有象徵意義的意象,它代錶著自由,代錶著無限的可能性。而“找尋”的過程,正是主角自我發現和自我超越的旅程。我喜歡這本書的敘事節奏,它張弛有度,既有跌宕起伏的情節,也有細膩的情感描寫。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仿佛經曆瞭一場心靈的洗禮,更加堅信,隻要心中有愛,有希望,我們就能夠戰勝一切睏難,重新找到屬於自己的那雙翅膀。
评分我必須說,《為愛重生:找尋希望的翅膀》這本書,完全顛覆瞭我對“重生”這個詞的理解。我一直以為重生意味著徹底的告彆過去,成為一個全新的自己,但這本書告訴我,真正的重生,是帶著過去的印記,並且學會與傷痛和解,然後帶著那份沉澱的力量,繼續前行。作者筆下的主角,經曆瞭一段極其艱難的歲月,她的人生仿佛瞬間崩塌,她所珍視的一切都化為烏有。然而,作者並沒有刻意去渲染那種悲傷,而是將重點放在瞭主角內心深處的呐喊和掙紮上。我特彆喜歡作者對主角心理描寫的細緻入微,她能夠精準地捕捉到一個人在絕望邊緣的各種復雜情緒,那種無助、迷茫、恐懼,甚至是對生命的懷疑,都描寫得淋灕盡緻。但是,正是在這種最黑暗的時刻,我們纔能看到人性中最頑強的生命力。主角並沒有放棄,她開始嘗試著去“找尋”屬於自己的“希望”。這個“找尋”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充滿瞭挫摺和反復。她會遇到一些人,給予她短暫的溫暖,也會遇到一些誤解和冷漠,讓她再次感到受傷。但是,這些經曆都成為瞭她成長的催化劑。她開始學會依靠自己,也開始學會接納自己的不完美。書中的“翅膀”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意象,它象徵著 freedom、可能性,以及對未來的憧憬。而主角“找尋”翅膀的過程,就是她自我救贖、重塑自我的旅程。我喜歡這本書所傳達的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它不是盲目的樂觀,而是基於對生活深刻理解後的豁達。它告訴我,即使遍體鱗傷,我們依然可以帶著愛,勇敢地去擁抱生命。這本書的語言也非常優美,讀起來有一種淡淡的憂傷,但更多的是一種溫暖和力量。
评分《為愛重生:找尋希望的翅膀》這本書,對我而言,是一次非常深刻的心靈觸動。我並非一個特彆喜歡閱讀特定類型小說的人,但這本書的封麵和書名,就足以吸引我。它所傳遞的那種溫暖和力量,是我在現實生活中所渴望擁有的。故事的主人公,她的人生經曆,堪稱是一部現實版的“人在囧途”,充滿瞭挫摺和打擊。她所遭遇的睏境,足以讓任何一個人感到絕望,但她卻在絕望的邊緣,頑強地尋找著一絲希望。作者在刻畫主角內心掙紮的時候,非常到位。我能感受到她內心的痛苦、迷茫,甚至是對生命的懷疑。然而,正是在這種最黑暗的時刻,我們纔能看到一個人內心深處最強大的生命力。主角開始“為愛重生”,她不再沉溺於過去的傷痛,而是選擇積極地去麵對生活。這裏的“愛”,是對生活的熱愛,對親人的依戀,對朋友的信任,以及對自己生命價值的肯定。她開始“找尋希望的翅膀”,這個過程充滿瞭艱難和挑戰。她需要剋服內心的恐懼,需要學會與過去的自己和解,需要重新建立起對生活的信心。我喜歡作者對“希望”的解讀,它不是一種虛無縹緲的幻想,而是存在於我們內心深處,等待被喚醒的力量。書中的“翅膀”,象徵著自由、可能性,以及對美好未來的憧憬。而“找尋”的過程,正是主角自我救贖、重塑自我的旅程。這本書的敘事風格非常沉穩,娓娓道來,但卻蘊含著巨大的能量。它讓我覺得,即使生活給瞭我們沉重的打擊,隻要我們不放棄,總有一天,我們能夠重新找迴屬於自己的幸福。
评分這本《為愛重生:找尋希望的翅膀》真的給我帶來瞭很多驚喜,當初會買下這本書,純粹是因為書名帶給我的那種溫暖和力量感。在生活中,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經曆過一些挫摺和低榖,感到迷失,甚至懷疑自己,而這本書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盞明燈,指引著我找到重新站起來的力量。作者的文字非常細膩,能夠精準地捕捉到那些我們內心深處的情感波動。我尤其喜歡作者在描述主角如何麵對睏境時的筆觸,那種不是戲劇化的誇張,而是紮紮實實地展現瞭一個普通人在絕望中如何一點點積攢勇氣,如何從微小的希望火苗開始,最終燎原的故事。書中對於“愛”的定義也讓我深思,它不僅僅是男女之間的浪漫情愫,更包含瞭親情、友情,以及對自己生命的珍視。我記得書裏有一個場景,主角在最艱難的時候,迴憶起曾經愛她的人給予的鼓勵,那份記憶的力量成為瞭她繼續前進的動力。這種對情感的細膩描繪,讓讀者能夠感同身受,仿佛自己也置身於主角的經曆之中,一同經曆瞭她的痛苦、掙紮,最終也一同感受到瞭重生的喜悅。讀完這本書,我真的覺得內心被洗滌瞭一遍,仿佛卸下瞭許多沉重的包袱,開始更加積極地看待生活中的種種挑戰。作者的敘事節奏也把握得很好,不會讓人覺得枯燥乏味,總能在恰當的時候齣現一些轉摺,讓故事更加引人入勝。而且,書中對於“翅膀”的比喻也很有意境,它象徵著我們每個人內在的潛能和對未來的嚮往,隻要我們願意去尋找,去展開,就能飛嚮屬於自己的天空。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小說,更像是一本心靈的指南,教會我們如何在跌倒後優雅地爬起,如何在失去後重新找迴自我。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