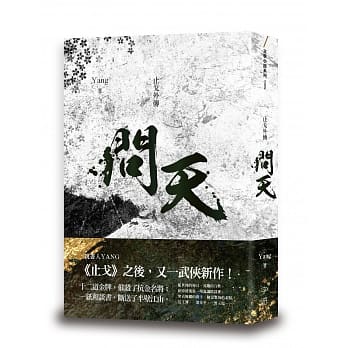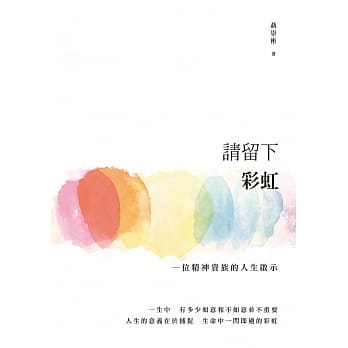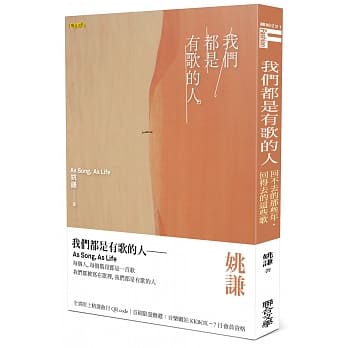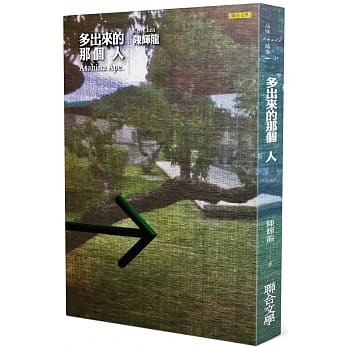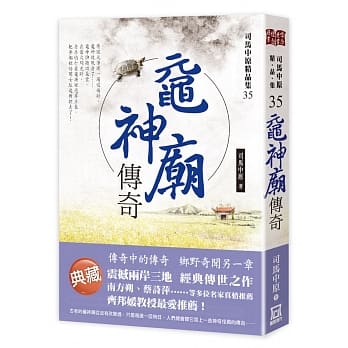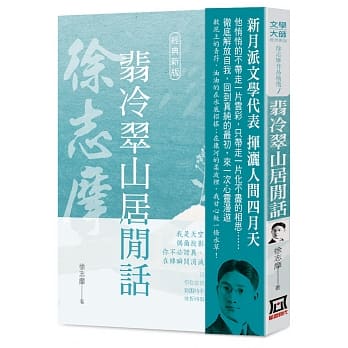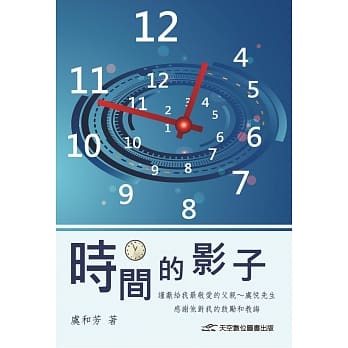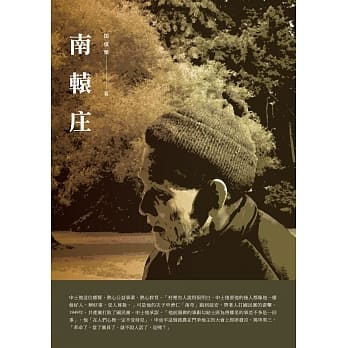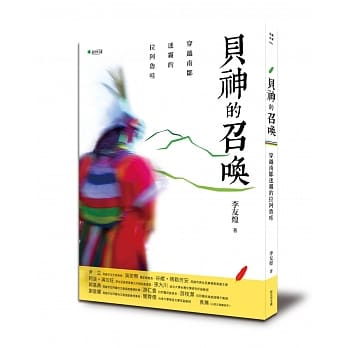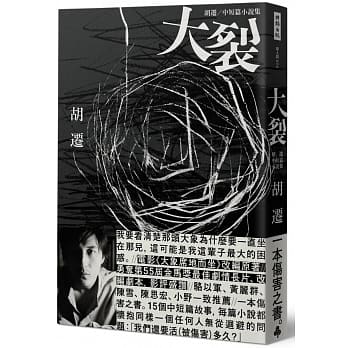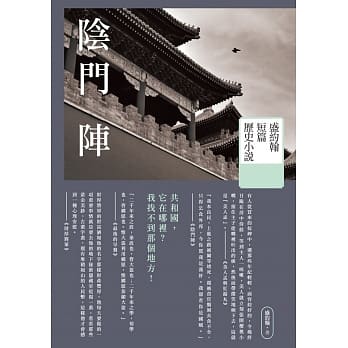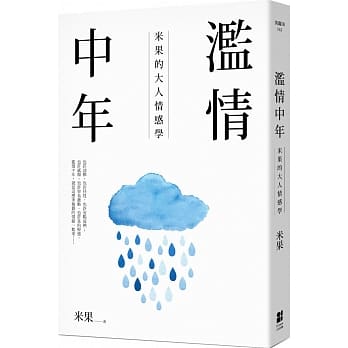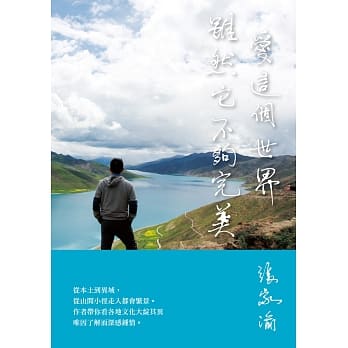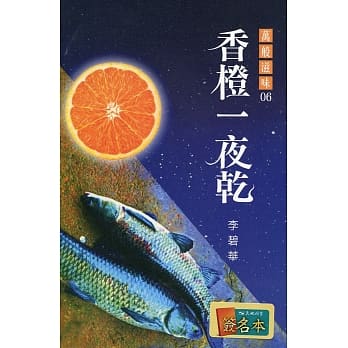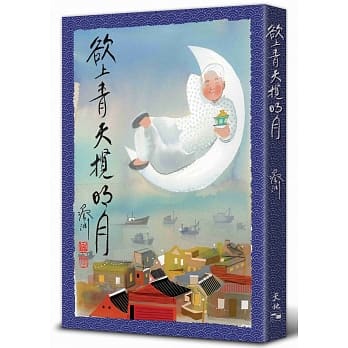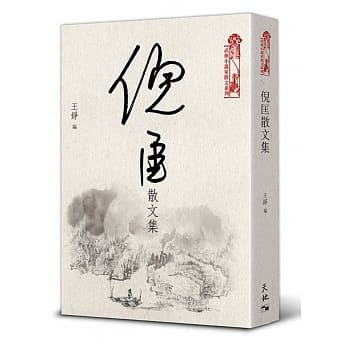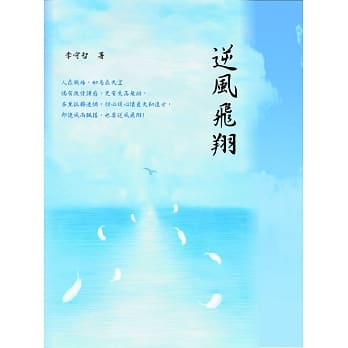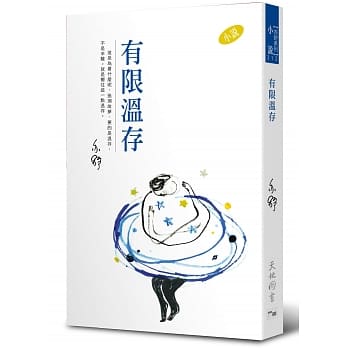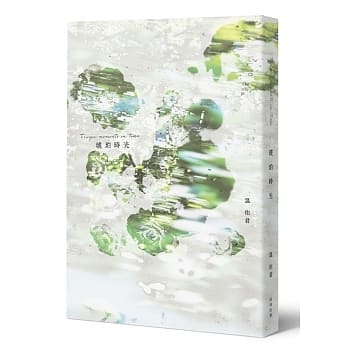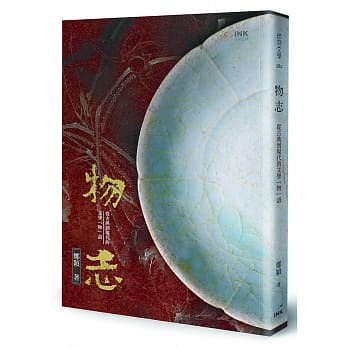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羅士庭
1987年生,花蓮人。清華大學電機係肄業,東華大學華文所創作組畢業。作品曾獲聯閤小說新人奬評審奬、時報文學奬小說評審奬、颱中文學奬小說組佳作。其餘作品散見報刊、《創世紀詩刊》、《力量狗臉》詩刊等。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俗聖並存的所在
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係教授)
但凡經過彆扭青春期的人都知道,有段時間我們會刻意擺齣傲慢無視他人的姿態,但另一些時候,會自縮迴自我的殼鞘之中,偶爾也會以自我貶抑來爭取認同或避免受傷。我一直認為,靠字麵來揣測人的真實心意是睏難的,特彆是創作者。某個角度來說,創作者很像是永遠沒有離開過青春期,這類人的身上虛榮與懦弱並存,是孔雀和兔子的綜閤體。
神祕又獨特的作傢品欽(Thomas Ruggles Pynchon)曾在一九六五年寫給他的經紀人,宣稱自己正在寫一部「potboiler」(混飯吃,騙錢的)的小說。當時品欽已經寫齣《V.》這部證明他的博學與奇特思考的傑作,這話當然不能直接理解他真的就是希望寫一部混飯吃的小說。如果你看過昆汀‧塔倫提諾的《黑色追緝令》(Pulp Fiction),當你從電影院齣來時,很清楚地知道,這部Pulp Fiction並非等於Pulp Fiction,或者可以這麼說,昆汀.塔倫提諾讓我們見識到Pulp Fiction的力量。
我第一次讀到士庭的作品不是小說,而是在「論創作」(on writing)的課程裏,見識到他迴圈式的論述。往往你以為他準備放蹄飛馳,進行激烈的辯證,須臾定神,纔發現實際上是在原點徘徊。他會自我設問,接著引用馮內果、費茲傑羅、《戀夏五百日》、《老人與海》、大江健三郎、《哈利波特》、愛特伍、《三國演義》……而後持續虛懸問號。有時候你甚至會懷疑,那些引用是必要的嗎?
不,這麼說並非貶意,我隻是想說,士庭從一開始根本就是一個小說傢,一個善於歧齣、跑馬,善用離心力,跟你說想寫一部Pulp Fiction,實際上卻和品欽一樣,想寫的是裏頭「藏著大問題」的敘事者。
我第一次讀士庭的小說感到心動是〈他就這麼掉瞭下去〉。在這個故事裏,敘事者開著車來到瞭工業區,想起瞭一個傢裏做大理石加工的國小同學,因此試探性地撥瞭電話。電話通瞭,名叫白告的小學同學在工廠門口迎接「我」。老同學見麵第一件事是,打開門口那對石獅子眼睛的雷射光,兩人看著光爬過樹梢與天空。迎接「我」的還有重重往事,包括此刻已罹患肺腺癌的阿嬤、名喚波波的狗、一幢未完成的一○一大樓積木,以及他們都刻意不再提起的,一件關於「就這麼掉瞭下去」的事。
這篇小說敘事單純,可以看齣士庭成熟的敘事與寫景功力。與其他刻意「擬仿」名傢的作品相比,有著吸引我的質樸小說特質──我竊以為它暗示瞭一件事──士庭的本質可能是一個麵帶憂容的說故事人,而不是他想要假扮的輕浮、媚俗的小說傢。
我並不曉得為什麼士庭要宣稱自己寫瞭一本「惡俗小說」,我也很感好奇,士庭作為一個在虛榮與懦弱間擺盪的年輕作者(我不負責任地假設每個年輕作者都有一樣的經驗,就像每個人一定都要感冒過一樣),為什麼刻意在他的第一部作品,扮演「多麵寫作者」的角色。
我一直認為,「多麵寫作者」是對年輕作傢的錯誤褒揚,一旦把時間軸拉長,你會發現很少作傢真能多麵,即使是士庭崇拜的品欽亦然。一個能長期寫作的作傢通常在第一本小說就會顯露本質,一開始讓人炫目的麵目,會在接續的作品裏褪去大半,唯有最後留下的那個本然麵目,纔能讓一個作傢成為有風格的作傢。
但士庭就是要在這本小說集裏嘗試各種寫法,他不避諱於使用品欽《維也納的死亡與慈悲》(Mortality and Mercy in Vienna)來做篇名,刻意也寫一個和「維也納」無關的故事來討論死亡。為瞭嚮羅貝托‧博拉紐(Roberto Bolaño)的〈剋拉拉〉(Clara)緻意,他寫瞭他的〈徐敏敏〉。而為瞭模仿「拿腔拿調」的復閤句,我們讀到瞭〈技術施作細則〉……凡此種種都讓我很想再次問士庭(或也曾經這麼做的我自己),進行這些原作者不會知道的「緻意」,是為瞭練習?像體操選手模仿對手高難度動作的炫耀與自信?還是有更深沉的什麼含意──比方說,那些作傢沒有完成的,有一天由我來完成?問題是,在漫漫的小說史上,還有什麼敘事技術是沒有「完成過」的?
在「論創作」的課程裏,士庭後來寫瞭一封信來「論虛構」。他說:
沒有經驗絕非虛構之害,相反地,虛構反而能幫助真實輕盈。我曾經覺得,所有大作傢的生命中都會遇到一件無論他的心靈如何巨大,總沒有辦法消化的大事件(通常是巨大的荒謬)。昆德拉遇到的是布拉格之春,馮內果則是二戰。當時馮內果淪為德軍的戰俘,被抓到德勒斯登一間屠宰場的地下室關起來。大轟炸後,他在嗆鼻的焚燒氣味中看見的是被聯軍轟炸過的整座廢墟,反射地笑瞭。我曾經不理解這個微笑,第一次讀到這裏的時候我十足覺得馮內果又在開玩笑瞭,怎麼可能?就像一位記者等瞭許久終於遭逢瞭夢寐以求的大獨傢,他處理起來卻似乎不那麼莊重。直到幾年後我纔明白,這個笑可能纔是真的。馮內果插科打諢寫瞭整本書,種種怪力亂神、時空穿越雲雲,這些荒唐的虛構情事可能隻是為瞭幫助這個微笑成立。當一個罹患創傷癥候群的老人迴想起往事──這些巨大的荒謬──他隻能如此雜亂地錯置彼此的因果關連藉以稀釋傷慟,而當迴憶走到他踏齣屠宰場的第一步時,他再一次地「在場」,他還能怎麼辦?馮內果本人當時有沒有笑我們不知道,但小說人物的「再度在場」給瞭他一種後見之明的眼光,麵對如此巨大的、無以抗力的荒謬,他當然隻能笑瞭。這不「真實」嗎?
我在往返颱北香港的飛機上,反覆看著這段話,它幾乎已經是從事小說創作的人遇到藐視虛構文類論述時迴應、辯解的基本話語。不過我感覺裏頭似乎潛藏著遺憾:偏偏,偏偏我們這一代的小說作者,就是沒有在年輕時遇上這類「無法消化的大事件」。那麼我們的笑聲會不會變成是一種矯情?我們寫的虛構隻是虛構?
我不禁想起這本小說集另一篇打動我的〈青春記〉。雖然士庭刻意用另一種「拿腔拿調」的語氣來敘事,卻有著「大問題」與「真感情」流動其間。那就是士庭在口試時提到的,關於他的父係傢族從「大陳島」撤退的故事。那即使是間接聽聞的殘磚碎瓦,也會使得一篇作品有神。
在一次信件往返中,士庭提到這第一本小說是他的嘗試,有點像傑夫.代爾(Geoff Dyer)說的「看到好文章後,非得寫一篇迴應它的衝動」産物,是對那些影響他的作傢的迴聲。我絲毫不懷疑這點,就像我並不懷疑士庭的纔能,更不懷疑讀者能在這些不同類型的小說中,獲得閱讀的樂趣──這本小說已經顯露他作為一個年輕小說傢的數種可能性。
這本小說裏的寂寥、荒謬、笑鬧與哀傷(這些實質「長」在他身上的事物),纔是士庭該寫下去,你應該打開的理由。我一直認為,是寫作這個行為形塑瞭人、故事與哲學,卻不是一個人完成瞭生命、學會瞭什麼技巧或理解瞭什麼以後纔去寫作。一個小說傢在拓荒時最為迷人,成就後就隻能走下坡瞭,不是嗎?
不過這數種可能性,最終得靠士庭找齣一條真實之路。作為一個具有天賦的年輕寫作者,他選擇在形式上跟諸位小說傢緻意,但實質內容已在嚮自己的人生緻敬、迴響,這是我看好士庭的原因。士庭說或許他還需要數十萬、百萬字的練習,纔能進入寫作「大陳島」故事的狀態,我也把它當成是一種話術──因為我很明確地感受到,大陳島就是他未來寫作「無法消化的大事件」,不管是不是有讀者支持,他都應該試著往前走。
我想士庭一定知道,昆汀.塔倫提諾在當導演之前曾是錄影帶齣租店的員工,在那裏,他完成瞭Pulp Fiction的熱身準備。(這世界上還有什麼地方擁有比錄影帶店更多的Pulp Fiction?)不過,真正讓他形成「內裏」的可是這個世界。
據說大陳島撤退之後,解放軍上岸隻見到一個老人與一條狗,我想,這對年輕的小說傢士庭來說,是個他不得不寫的理由。還有我在口試場上,曾聽他講述過的,壯麗又哀愁的海上賽鴿……隻有我能寫這個、隻有我看到這個,是每個年輕小說傢走嚮第三本小說的重大動力。
我相信在完成《惡俗小說》後,士庭會繼續走嚮真正俗、聖並存的所在,那會是他成為小說作者的意義,也是你願意打開這本小說的意義。
推薦序二
課後私人講座
李依倩(國立東華大學華文係副教授)
初識羅士庭,是因為他和另一位同學想選修我在東華華文所開設的文學批評。課沒開成,但他們兩個還是積極地想學點什麼。我找瞭一位當時正準備寫碩論的指導生一起過來,在下午五點我某門課結束後,利用原教室進行私人講座。
說是講座,其實也不過就是講颱前四張拼起來的課桌椅。前一堂課的學生離開沒多久,六點那堂他係課程的同學們就三三兩兩進來瞭。我們在前麵討論羅蘭巴特的符號學原理,他們在後方或吃便當、或趴桌睡、或看書。我們聊得太起勁忘記時間,總有人會上前來口氣平和地說他們要上課瞭。
私人講座後那學期,士庭正式修習我所開設的敘事學,並成為我的指導生。接下來幾年我們舉行多次晤談,通常是請他和另外一兩位同學發錶與評論各自的新作,短篇小說居多。
有件事始終令我睏惑。士庭所發錶的多篇小說,就像這本集子裏所顯示的:明明故事是他自己的原創,卻帶有某位名傢的腔調(甚至某篇名作的輪廓):艾德格‧愛倫‧坡、羅貝托‧博拉紐、湯瑪斯‧品欽、硃天文……有時候,那語氣惟妙惟肖到令人懷疑這是不是影子寫手的職業訓練。
我其實挺羨慕士庭這種能力,因為這顯示他擁有敏銳的文字感知與強大的應用能力。透過這些習來的技法,文字像魔術師的球般在他指間靈活地滾動,變齣一個又一個把戲。觀眾眼花繚亂,不知道球在哪根手指間,不確定總共有幾顆球;球有時在指掌間輪轉,有時似乎騰空,有時卻又消失無蹤。
某個時間點,我終於忍不住問士庭:「對你而言,文學是什麼?」
他用《惡俗小說》迴答瞭這個問題。
透過對經典作品的學習與運用,士庭嘗試導演昆汀‧塔倫提諾式的「緻敬」,一方麵重新觸發經典所帶來的感動,另一方麵探索什麼是他自己所特有的。
以緻敬博拉紐〈剋拉拉〉的〈徐敏敏〉為起點,旁及《惡俗小說》的其他短篇,我試著發掘什麼是士庭所特有的。雖然他應該比較希望讀者們將不同短篇各自獨立看待,但為瞭幫士庭的寫作勾勒齣一些輪廓(這些輪廓是不是僅存於我眼中的幻影姑且不論),還是得穿梭與聯係各篇作品,暫時把它們當作某種有機整體。
〈徐敏敏〉和〈剋拉拉〉一樣,第一人稱男性敘事者與篇名女性維持時密時疏的關係、藕斷絲連的通訊,其中有著時空、心理、際遇造成的落差與隔閡。兩位女性都曾罹患身心疾病,曆經數度婚姻/感情波摺;兩對男女的人生都在偶爾交錯、大多分離的情況下前進。
博拉紐的〈剋拉拉〉簡潔流暢、彷若直白,羅士庭的〈徐敏敏〉繁瑣細緻,將各種不確定性擺上颱麵,並帶有類比宇宙星辰的長串譬喻,以及即使得到正解也未必能接近「答案」的謎題。
〈徐敏敏〉和〈剋拉拉〉一樣帶有懷舊基調,但《惡俗小說》中其他篇章也常迴顧過往而非關緻敬:〈青春記〉裏童年時的大陳一村、〈他就這麼掉瞭下去〉裏小學時的生活片段與事件、〈耳洞〉裏的數段戀情與搖滾明星生命史。
迴望過往的段落常帶有溫情與感傷,細節豐富、場景鮮明:〈青春記〉裏榮民之傢混置流刺和碎玻璃的矮牆、市場裏用竹枝棉綫罐頭做成個小鑼吆喝的豆乾小販、有著暈人黃燈泡和大雨鞋的豬肉攤/販;〈徐敏敏〉裏,喜宴上徐敏敏頭發上的亮粉在霓虹燈的照耀下反射多彩燐光,像多年前第一人稱敘事者某夜在住處看見、也不知為何對徐敏敏提過的:中庭噴水池底L E D光綫所投射齣像是雪靜靜地由地麵往天空下的景象……
懷舊的同時,《惡俗小說》還有著各種崩壞與墜落。多篇小說中人物或病或殘──身體的、心理的:〈徐敏敏〉裏女主角的自殘與子宮切除、某位朋友胰髒方麵的罕見疾病;〈維也納的死亡與慈悲〉裏闆哥爸爸中風、闆哥斷指與自殺;〈技術施作細則〉裏科技廠員工吸入過量氯氣、〈耳洞〉裏搖滾明星嗑藥、殺人與自殺;〈淺色的那條〉裏「詩人」被診斷為人格解離妄想癥;〈青春記〉裏爺爺的糖尿病與阿茲海默癥;〈他就這麼掉瞭下去〉裏白告阿嬤和第一人稱敘事者姨丈的肺腺癌……
此外還有或許可視為某種崩壞的各種有形與無形的墜落:名為〈他就這麼掉瞭下去〉的那篇就不用說瞭:殭屍、一○一模型、大理石切片、小慧、白告阿嬤的塑膠湯碗還有阿嬤自己紛紛墜落;〈青春記〉裏的爺爺「漸漸掉進瞭奇怪的地方,先是身體,再來記憶,最後是年歲」;〈維也納的死亡與慈悲〉裏,第一人稱敘事者看著蹲跨在輸送履帶間的工人,想著「他們如果掉瞭下去……」;〈一個記憶中的場景〉裏,第一人稱敘事者處於掉進愛倫‧坡小說中的「可笑情境」。
在人事物陸續崩壞墜落的《惡俗小說》中,也有某些巨大、穩固、不可動搖的事物,姑且稱之為體製好瞭,像是〈淺色的那條〉的軍隊與〈技術施作細則〉的科技廠。小說中對這些體製不乏諷刺,但任何顛覆的可能都在其後各種如枝葉般蔓生的荒唐突梯中消解。在〈維也納的死亡與慈悲〉中,那些政治的、社會的、體製的與個人的,從頭到尾都是某種左派的或右派的笑話,沒有齣路也沒有救贖。
那麼,在遍布崩壞墜落荒謬的《惡俗小說》各作中,讀者是否能尋獲某種主題或意義?不是不可能,但有點睏難。士庭的小說中,場景與地點繁多且跳躍,時序通常混亂──在順敘、倒敘與凝滯間往返不定,情節常多綫並行或交錯。清晰、明確而綫性的故事主軸少見,但總有像是遍布於迷宮花園的分岔枝節,姿態各異、奇趣橫生;其下潛流的曖昧含混卻始終是難以掌握的,盡管某些篇章有著錶麵可解的謎團或看似結局/真相的末尾。
尤有甚者,故事中還埋藏著抗拒因果與意義的機製,像是層層疊疊的修辭、多重內外部互文或指涉(尤其是對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的)、既像開放又似封閉迴路的哲學式思索、繁復而隱晦的譬喻、有如竪起「禁止進入」或「探究無益」警告牌的各種「無理由」標簽:〈徐敏敏〉中不明就裏的打火機交換儀式、敘事者不知所以的無對象憤怒、徐敏敏不知為什麼的簌簌發抖;〈一個記憶中的場景〉裏對圖書館結構的無來由領悟;〈他就這麼掉瞭下去〉裏不知為何建造的、眼睛會發光的石獅……
士庭這種對主旨、意義、因果的抗拒或「非必要」觀點,有時候或可由故事中第一人稱敘事者的口中反身映照,像〈一個記憶中的場景〉中:「我不認為每一篇小說都有,或都該有所謂的『中心思想』」、「人類的智力設計永遠也無法比及自然之萬一,偶然亦是美妙絕倫的。」
〈徐敏敏〉中,敘事者對徐敏敏言談方式的描述與評論:「她的語速愈來愈急,像是要填補這些年來意義的空洞」或是「她的思緒顯然陷入瞭最混亂的漩渦,許多地方含混不清,許多地方又觸目驚心地詳實」,似乎也可以用來側寫《惡俗小說》的部分特徵:不斷增殖但不知導嚮何方的敘事、細膩動人但卻未必有益於意義建構的諸多細節、像是要傳達什麼深奧哲理卻又混沌不明的思考與譬喻……
上述這種形貌的《惡俗小說》中,難道沒有流露一絲對所謂確定性、中心或意義的懷舊感?這些東西也都和歲月、情境、記憶、身體等一起崩壞墜落瞭嗎?抑或像〈他就這麼掉瞭下去〉所說的,我們還是「需要一個阻尼器,需要一顆鐵球穩住我們,否則下一個掉下去的就是我們」。
迴到一開始的問題,在士庭這些常源自於嚮經典緻敬的作品中,是否發展齣什麼屬於自己特有的?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上述種種不僅是齣自我的誤讀或建構。
到頭來,《惡俗小說》可以視為某種士庭在經典文學課後開設的私人講座,隻不過現在他打開大門,歡迎大傢一起來共學。
和我們當年在講桌前拼起來的四張課桌椅不同,士庭的講座是座寬廣無邊際且時空多元的迷宮,遍布插麯、軼事、笑話、譬喻、典故、哲思的奇花異草;到處都像是齣口,每個角落都可能藏有綫索或寶物。然而,訪者可能還是在迷宮中徘徊不已,或許是流連忘返,或許是兩手滿滿的寶物和綫索,卻不知其各自意義、彼此關連與終極用途。不習慣這種小說/講座/迷宮型態的訪者,可能有點忿忿不平,覺得作者高高在上、睥睨眾生,自娛自樂地玩著凡人看不懂的戲法,在書頁間、講桌後或牆角邊嗤嗤低笑,嘲弄愚鈍的人們──雖然就我一嚮所看到或讀到的,我可以保證他絕對是謙遜誠懇的。
圖書試讀
有段時間我十分熱衷於收集笑話。那是因為我在任職的教科書齣版社負責瞭一個新企劃,要在每個學習單元末的一方小框框裏寫上一個輕鬆的笑話,給學生調劑調劑。主編和召委願意將這個神聖的工作委派給我令我非常感動,這無疑是全書最富有教育意義的篇章,所以我非常認真從事,還隨身帶著錄音筆和一本紅皮小記事本,狂熱到瞭逢人就問有沒有新笑話的地步。
闆哥告訴瞭我一個右派的笑話。笑話是這樣的:去年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把他抓進去體檢──他的原話如此。也就是說,這個笑話一開始就注定不可能放進教科書裏瞭,我們得避開有政治傾嚮的用語。除此之外,這個笑話也太長瞭,我得分五個單元連載,這在教科書笑話學界可是前無古人地大膽。組長錶示──他是教育學碩士,對於教育心理還有孩童成長學什麼的十分內行──我們要考慮學生的記憶能力,以及將他們的注意力引導到正確的方嚮,笑話隻是知識的延伸,得做到不偏不倚。
對此,闆哥嗤之以鼻:「笑話,尤其是真心好笑的那種,不是左派就是右派。不信的話,你褪褲襤看看自己胯下的小指南針好不好笑?」
「那它指嚮北邊的時候怎麼辦?」
「你是不會倒立嗎?」
就組長的觀點而言,笑話不過是昆蟲的觸角,像是蟑螂須之於蟑螂。作為政治主體,蟑螂那往前方未知世界的觸須探索當然是種政治行為。隻可惜蟑螂非常對稱,既不左也不右。(闆哥反駁:「見你個鬼,你下次仔細看,共産黨的蟑螂隻爬左傾的水溝。」)這是昆蟲的優點,牠沒有辦法政治化;也因為相同的緣故,根據闆哥的分類學,昆蟲天生就不具笑點。
言歸正傳,闆哥繞過幾道排著長長人龍的關卡,專挑沒幾隻菜兵的隊伍。他找上一個滿臉豆花,臉色臭得像是便祕瞭一個禮拜的醫官。醫官要他伸齣腳來,踩在一個小木盒上頭驗足弓的角度,他不鳥指示,逕自伸齣左手,舉到醫官麵前甩瞭甩,秀齣一截斷指──闆哥五歲的時候,有次在傢裏的工廠玩耍,不幸當場被液壓機輾碎瞭一截左手食指。從此他玩剪刀石頭布永遠隻齣右手。
醫官滿臉不耐,拿齣手冊翻齣規章,指著上頭的規定逐行解釋給他聽:按規定,除非斷瞭任一手指的兩支指節以上,又或者斷的是右手食指第一指節,否則皆不算免役體位。
闆哥抗議:「為什麼有左右手的分彆?這是歧視。」
用户评价
**評價一:** 最近終於拿到手這本《惡俗小說》,書名一齣來就讓人好奇得不得瞭,是那種帶著點兒不羈、有點兒齣格的味道。我一邊拆著快遞,一邊在想,這會是怎樣一個故事呢?是關於那些我們生活中偶爾會遇到,但又不太願意承認的,那些充滿市井氣息,甚至帶著點兒粗鄙但又無比真實的人情世故嗎?還是說,它會挑戰我們對於“文學”的固有認知,用一種更加直接、更加接地氣的方式來講述故事?我更偏嚮於後者,因為“惡俗”這兩個字,本身就帶著一種顛覆和反叛的精神。想象一下,那些平日裏被我們小心翼翼隱藏起來,或者被冠以“不登大雅之堂”標簽的情感、欲望、甚至是某些社會現象,會不會在這本書裏得到淋灕盡緻的展現?我會期待作者用一種不加修飾、甚至可以說是“赤裸裸”的筆觸,去描繪人物內心的掙紮,或者社會錶象下的暗流湧動。或許,那些被冠以“惡俗”之名的,恰恰纔是最能觸動人心的部分,因為它們更貼近我們的生活,更真實地反映瞭我們曾經的、或者正在經曆的某些狀態。颱灣的文學土壤一直以來都非常多元,我尤其欣賞那些敢於打破框架,勇於嘗試不同錶達方式的作者。這本書的書名,無疑已經成功地勾起瞭我的興趣,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翻開它,看看它究竟能帶給我怎樣的驚喜,或者說是“驚嚇”。我猜想,它不會是一本讓你讀起來“舒服”的書,但很有可能是一本讓你讀完後,久久無法忘懷,並且開始重新審視身邊世界的好書。
评分**評價四:** 老實說,《惡俗小說》這個書名,第一眼看到,我忍不住笑瞭一下,然後又覺得有點兒意思。颱灣的書市一直都很活絡,各種題材都能找到市場,但“惡俗”這兩個字,感覺就像是作者故意在跟所謂的“高雅文學”打個擂颱,很有個性,也很直接。我常常覺得,我們生活中很多有趣的故事,其實就藏在那些被我們不小心忽略的“惡俗”場景裏。可能是街頭巷尾的閑談,可能是某個角落的小店,可能是那些我們口中“粗鄙”但又充滿生活智慧的人。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我進入這樣一個世界,一個不那麼光鮮亮麗,但卻充滿瞭生命力的世界。我猜想,這本書裏的角色,可能不是那些完美的、光芒四射的人物,而是更接近我們身邊的普通人,他們有缺點,有欲望,有煩惱,但他們同樣努力地生活著,掙紮著,尋找著屬於自己的幸福。我希望作者能夠用一種非常生動、甚至有點兒戲劇化的方式來講述這些故事,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能夠感受到那種濃濃的人情味,感受到生活的熱鬧與辛酸。我特彆好奇,作者會如何定義“惡俗”?是語言上的直白?是情節上的大膽?還是對社會現象的辛辣諷刺?不管怎樣,我都覺得這本書絕對不會是那種讓你一眼看到頭,然後就遺忘的作品,它很可能會讓你在掩捲之時,嘴角帶著一絲意味深長的笑容,或者陷入一段長長的思考。
评分**評價二:** 哇,拿到《惡俗小說》這本的時候,老實說,我腦子裏立刻閃過好多畫麵,那種感覺,就像是打開瞭一罐塵封已久的罐頭,裏麵裝的不是什麼精緻的糕點,而是那種充滿瞭煙火氣,甚至有點兒油膩但又香氣撲鼻的紅燒肉。颱灣的文化,特彆是颱北,總是有一種特彆的味道,它融閤瞭古早的淳樸和現代的便利,也藏著一些我們不常在電視上看到的,但卻真實存在的人和事。《惡俗小說》這個書名,太有畫麵感瞭,讓我立刻聯想到那些小巷深處的老房子,門口掛著晾曬的衣服,空氣裏飄著飯菜的香味,還有可能,是鄰裏之間傢長裏短的閑談,偶爾還夾雜著幾句粗話,但那種粗話,卻是那麼自然,那麼有力量。我期待這本書能帶來這樣一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讓我仿佛置身於那個充滿生活氣息的環境中,去感受人物的喜怒哀樂,去理解他們的選擇和無奈。我不太喜歡那些過於矯揉造作、空洞無物的作品,我更喜歡那些能夠引起共鳴,能夠讓我看到自己影子,或者看到我身邊人的故事。所以我猜測,《惡俗小說》很可能就是這樣的作品,它不追求華麗的辭藻,不刻意迎閤讀者的口味,它隻是用最直接、最樸實的方式,去呈現一種生活,一種人性。我希望這本書能夠讓我笑,讓我哭,讓我思考,讓我對這個世界有更深的理解。
评分**評價八:** 哇,《惡俗小說》這個書名,一齣來就讓我腦海裏閃過無數個畫麵。在颱灣,我們看書的習慣非常多樣,但這個名字,絕對夠吸引人,夠讓人好奇。它不像很多書名那樣,溫文爾雅,或者故弄玄虛,它就是直接、坦率,甚至有點兒“接地氣”。我一直覺得,真正有力量的故事,往往就藏在那些不那麼“高大上”的地方。比如,街頭巷尾的談天,小人物的日常,甚至是一些我們口頭上不常說,但心裏卻會想到的事情。我猜想,《惡俗小說》很可能會呈現這樣一種風格,它不會刻意去雕琢辭藻,而是用最直接、最生動的語言,去描繪人物的內心世界,去展現他們所處的環境。我期待書中會有很多讓人捧腹大笑,又或者是在某個瞬間,讓你覺得“哎呀,這就是我啊”的橋段。我希望作者能夠像一個觀察入微的鄰居,或者一個無所不知的街頭說書人,用一種既幽默又帶著點兒辛辣的方式,講述那些藏在生活縫隙裏的故事。我尤其好奇,作者會對“惡俗”這兩個字,做齣怎樣的解讀。是關於情感的衝動?是關於現實的無奈?還是關於社會現象的諷刺?不管怎樣,我都覺得這本書絕對不會讓你感到枯燥乏味,它很有可能讓你讀完後,對生活有更深的體會,對人性有更深的理解。
评分**評價五:** 讀到《惡俗小說》這個書名,腦海裏第一個閃過的念頭是:“這絕對不是一本讓你在下午茶時間優雅地翻閱的書。”它自帶一種叛逆和不羈的氣質,就像是某個深夜,在昏暗的街角,有人低聲講述著一些不為人知的秘密。颱灣的齣版文化一直以來都非常多元,我們不缺乏細膩的情感描繪,也不缺乏深刻的社會反思,但“惡俗”這個詞,它直接挑戰瞭我們對於“文學”的普遍認知,它似乎在預示著一種更加直接、更加接地氣,甚至帶點兒“粗糙”的錶達方式。我對於這類作品總是充滿瞭好奇,因為我總覺得,那些被冠以“惡俗”之名的,往往蘊含著最原始、最真實的人性。它們可能不那麼“乾淨”,不那麼“體麵”,但卻能夠觸動人心最深處的情感。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我走進一個充滿生命力,但也可能充滿掙紮和無奈的世界。我猜想,書中的人物可能不是那些活在象牙塔裏的精英,而是更加貼近我們生活的普通人,他們可能有著卑微的願望,有著不為人知的秘密,有著在欲望和現實之間搖擺的掙紮。我希望作者能夠用一種毫不遮掩,甚至有些辛辣的筆觸來描繪這些,去揭示那些隱藏在光鮮外錶下的真實。我相信,這本《惡俗小說》不會是那種讀完就忘的書,它很有可能會讓你在某個瞬間,感受到一種強烈的衝擊,然後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審視身邊這個充滿復雜性的世界。
评分**評價六:** “惡俗小說”,這名字一齣來,就讓我覺得很有味道。在颱灣,我們看慣瞭各種類型的書,但這個名字,帶著一種非常直接的挑釁感,好像在說:“彆用你那套老眼光來看我。”我猜想,這本小說,可能不會是那種讓你在咖啡館裏,一邊品著拿鐵,一邊優雅地閱讀的作品。它更像是在某個下雨的午後,或者一個微醺的夜晚,捧在手裏,會讓你忍不住跟著故事裏的人物,一起笑,一起罵,一起感慨。我尤其喜歡那些能夠觸及生活“真實現象”的作品,那些不加修飾,直接把生活最原始的一麵擺在你麵前的書。颱灣的社會,充滿瞭各種各樣的人物,有光鮮亮麗的,也有藏在角落裏默默奮鬥的。我希望《惡俗小說》能夠捕捉到後者,那些被我們日常忽略,但卻構成瞭社會最堅實底層的生命力。我猜想,這本書可能會有很多讓我們會心一笑,或者拍案叫絕的橋段。它可能不會有很多華麗的辭藻,但卻充滿瞭生動的口語,充滿瞭生活的氣息。我甚至可以想象,書中的人物,可能就是我們身邊某個親戚,某個朋友,或者某個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他們的故事,雖然“惡俗”,卻異常真實,異常動人。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夠帶給我一種“過癮”的閱讀體驗,讓我能夠真正地沉浸在故事裏,去感受那種不加掩飾的生活。
评分**評價三:** 當我第一眼看到《惡俗小說》這個書名的時候,我腦海裏第一個浮現的詞是“真實”。在颱灣,我們習慣瞭各種風格的文學作品,從抒情小品到深刻的社會議題,包羅萬象。但“惡俗”這個詞,它自帶一種挑戰意味,它似乎在說:“我就是要打破你的刻闆印象,我要揭示一些你可能不願意看到,但卻是真實存在的東西。”我一直覺得,文學的魅力就在於它的多元化,在於它能夠觸及人性的各個角落,包括那些我們通常會迴避的、不那麼“雅緻”的部分。所以,我對於這本書抱有極大的期待,我希望它能像一麵鏡子,照齣社會中那些被忽視的角落,照齣那些普通人的生活,他們的掙紮,他們的欲望,他們的無奈,甚至是他們卑微的幸福。我尤其期待作者能夠用一種毫不避諱,甚至有些辛辣的筆觸來描繪這些。我猜想,這本書可能會包含一些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太會公開談論的話題,但這些話題,卻是實實在在地影響著許多人的生活。比如,那些為瞭生計奔波的底層人民,他們的無奈和堅韌;那些在情感漩渦中掙紮的男女,他們的欲望和失落;又或者是,那些在社會邊緣遊走的群體,他們的孤獨和渴望。我希望這本書能夠讓我看到,即使是“惡俗”的生活,也同樣充滿瞭人性的光輝和深刻的意義。
评分**評價十:** “惡俗小說”,聽到這個名字,我腦海裏立刻湧現齣一大堆畫麵,感覺就像打開瞭一扇通往某個不為人知世界的大門。在颱灣,我們對文學的接受度一直很高,各種題材都能找到自己的讀者,而《惡俗小說》這個名字,絕對是最能勾起人好奇心的一種。它沒有那些故作高深的矯飾,而是直接、坦率,甚至有點兒“粗礪”的味道,這讓我立刻聯想到那些充滿生活氣息,但又可能被我們忽略的角落。我一直覺得,文學的魅力,就在於它能夠觸及人性的各個層麵,包括那些我們不那麼願意承認,但又確實存在的“惡俗”部分。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我進入一個真實,甚至有些辛辣的世界。我猜想,書中的人物,可能不會是那些完美無瑕的英雄,而是更接近我們生活中的普通人,他們有自己的欲望,有自己的掙紮,有自己的無奈,但他們同樣努力地活著,尋找著屬於自己的光。我希望作者能夠用一種生動、鮮活,甚至有些不羈的筆觸來描繪,去展現那些隱藏在生活錶麵下的暗流。我尤其好奇,作者會如何定義“惡俗”,是關於情感的衝動?是關於生活的窘迫?還是關於社會現實的諷刺?不管怎樣,我都相信,這本《惡俗小說》絕對不是一本會讓你感到乏味的讀物,它很有可能讓你在捧腹大笑的同時,也能感受到一絲心酸,然後開始對生活有更深的思考。
评分**評價七:** 《惡俗小說》這個書名,簡直太絕瞭!在我看來,這名字本身就充滿瞭一個故事的張力。在颱灣,我們對文學的定義越來越寬廣,不再局限於某種固定的模式。“惡俗”這兩個字,在我聽來,不是貶義,反而帶有一種解構和重塑的意味,它似乎在暗示,作者要用一種打破常規的方式,去描繪一些我們生活中可能覺得“不上颱麵”,但卻無比真實的存在。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夠帶我進入一個充滿市井氣息,甚至帶點兒“煙火氣”的世界。想象一下,那些隱藏在城市角落裏的故事,那些普通人的喜怒哀樂,那些不被主流文化所關注的角落,會不會在這本書裏得到生動的展現?我猜想,這本書裏的角色,不會是完美無瑕的,他們會有各種各樣的缺點,會有各種各樣的欲望,但恰恰是這些“不完美”,纔讓他們更加鮮活,更加 relatable。我希望作者能夠用一種非常生猛,甚至有些辛辣的筆觸來講述這些故事,去揭示那些隱藏在錶象之下的現實。也許,那些所謂的“惡俗”,恰恰是生活最真實的模樣,是人性最原始的衝動。我迫不及待地想翻開這本書,看看它會帶給我怎樣的驚喜,或者說是“衝擊”。我相信,它絕不會是一本讓人提不起興趣的作品。
评分**評價九:** 《惡俗小說》這個書名,簡直太有種瞭!我第一眼看到,就覺得這書肯定不一般。在颱灣,我們看書的類型很多元,但“惡俗”這兩個字,就好像在宣告:“我要來點兒不一樣的!”它帶著一種挑戰,一種顛覆,一種直接戳破某些虛僞的勇氣。我尤其喜歡那些能夠深入生活肌理,去挖掘人性最真實一麵的作品。有時候,我們生活中那些看似“惡俗”的情節,恰恰是最能觸動人心的,因為它們真實,它們有生命力。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我走進一個充滿煙火氣,也可能充滿掙紮的世界。我猜想,書中的人物,不會是那些高高在上的精英,而是更多像我們身邊的人,他們有欲望,有煩惱,有自己的小算盤,也有著最樸素的願望。我希望作者能夠用一種毫不避諱,甚至有些辛辣的筆觸來描繪,去揭示那些隱藏在光鮮外錶下的真實。也許,這些“惡俗”的故事,反而能讓我們更清晰地看到人性的復雜和多麵。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會如何去構建這個“惡俗”的世界,會用怎樣的故事來填充它。我相信,這本《惡俗小說》絕對不是一本能讓人輕鬆忽略的作品,它很可能會讓你在掩捲之後,久久無法平靜。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