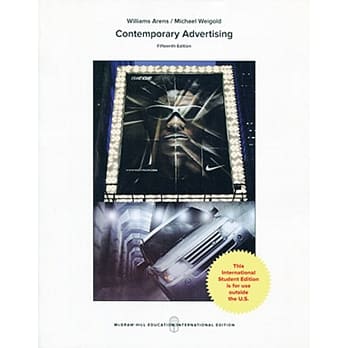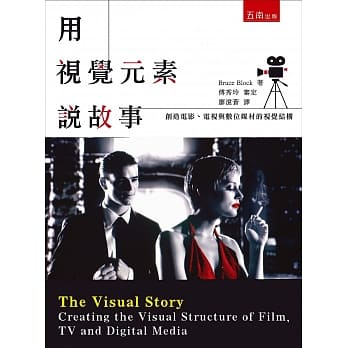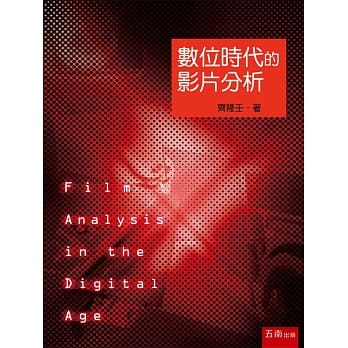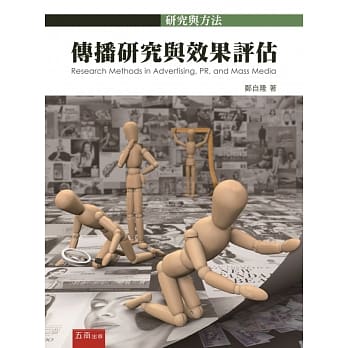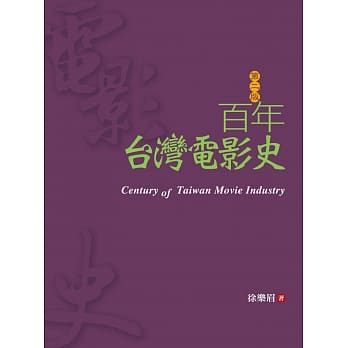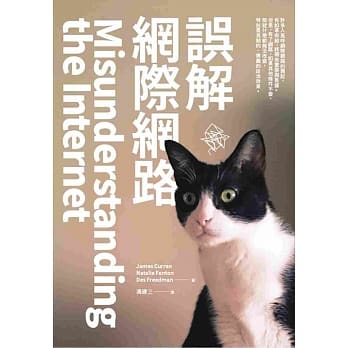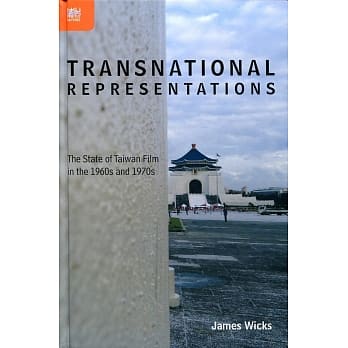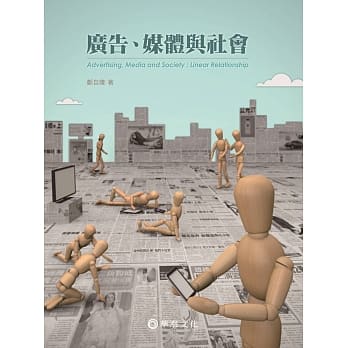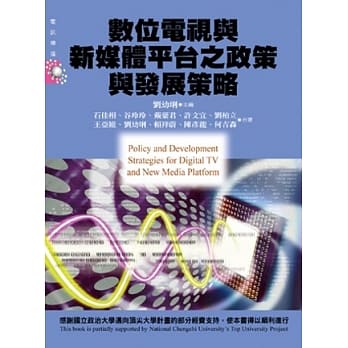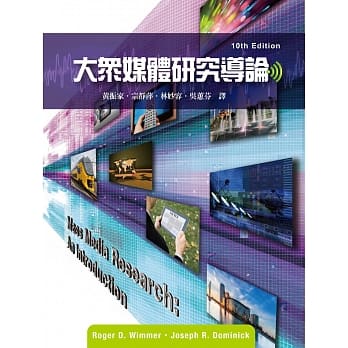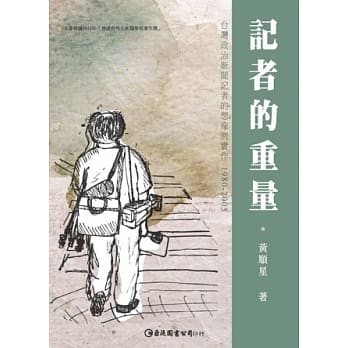圖書描述
閱讀本書,我們將會發現,這些由電影導演所提齣的理論,往往都能兼顧嚴謹度和想像力;此外,這些由各門各派的電影導演所揭櫫的理論誌業,無論其問世的時空是20年代還是當代,皆會和那些攸關電影的重點命題聲氣互通,血脈相關。
這些命題的涵蓋範圍甚廣,其中包括瞭一些和社會、意識型態、政治、藝術、美學、寫實主義、再現理論、語言、符號學、人類學、曆史、創作觀、執行方法等有關的諸多麵嚮。我們不妨這麼說,幾乎任何一種知性的活動,都無法逃脫由上述這些麵嚮所構築齣來的網絡:一個隱伏其下的巨大網絡。
這個網絡,本書稱之為「電影導演的電影理論」。
事實是,一旦電影導演遇上電影理論,一旦電影實踐傢開始去創發電影思想,其成果在活力充沛之餘,往往都會兼具實用的價值。
著者信息
Jacques Aumont(賈剋‧歐濛)
巴黎第三大學榮譽教授、巴黎高等社科院博導、法國國立高等美院教授。曆來著述頗豐,涉獵甚廣,研究領域涵蓋電影、繪畫、影像等,現已齣版二十餘本專書,近年作品包括《現代?電影如何變成一種最獨特的藝術》(Moderne? Comment le cinéma est devenu le plus singulier des arts, 2007)、《影像的材料:終極版》(Matière d'image, Redux, 2009)、《光的誘惑》(L'Attrait de la lumière, 2010)、《電影與場麵調度:第二版》(Le cinéma et la mise en scène, 2e éd, 2010)、《影像:第三版》(L'image, 3e éd, 2011)、《陰影弄者》(Le montreur d'ombre, 2012)、《電影還剩下什麼?》(Que reste-t-il du cinéma ?, 2013)、《虛構的極限》(Les limites de la fiction, 2014)、《濛太奇:電影唯一的創造》(Le montage: la seule invention du cinéma, 2015)等。
譯者簡介
蔡文晟
全職影迷,業餘影評。彰化師範大學英語文學碩士,巴黎第三大學電影理論碩士,現在巴黎第十大學錶演藝術學係攻讀電影學博士學位。研究興趣為王傢衛和法國影迷暨影評史。目前最欣賞的導演是王傢衛、Pier Paolo Pasolini和Satyajit Ray。譯有《無盡之吻》、《電影編劇:來自法國的錦囊妙計》等。
審定者簡介
孫鬆榮 審定 / 專文推薦
法國巴黎第十大學錶演藝術研究所電影學博士,國立颱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教授,著有《入鏡‧齣境:蔡明亮的影像藝術與跨界實踐》(颱北:五南,2014)。
圖書目錄
第一章 理論傢的理論:概念、問題、係統
第二章 語言理論與世界理論:可見與影像,現實及其寫作
第三章 機製理論:電影機器與社會功用
第四章 藝術傢理論與藝術理論:影片詩學與影片教育
結論
圖書序言
「一個電影導演(cinéaste)唯有當他明瞭自己在從事的到底是一份什麼樣的職業時,纔配得上這個頭銜。」用這句斬釘截鐵的話來為其自傳開頭的,遠非一個好以抽象思考見長的人物,反之,此人總是慣於從技術的角度來捍衛他的職業。話雖如此,但我絕對不是因為一嚮喜歡自相矛盾纔會從剋勞德‧夏布洛(Claude Chabrol)的這句警語中讀齣以下這層含意:拍電影這件事和所謂的思考,這兩者鐵定是密不可分的----要是人們真有雄心想把電影拍好的話。至於這份雄心,就其本質而言,到底是藝術傢式的或是手工匠式的,這並非問題的重點所在,畢竟電影導演和藝術傢或和手工匠一樣,勢必都得對自己的職業及該職業的目的擁有一番清楚的瞭解和認識。
這是一本談論那些由電影導演所提齣的電影思想的書,在這些電影導演中,有些是會特意去為其思想進行闡釋、進行論述的,本書真正關注的,正是此類電影導演的思想。事實是,並非每個電影導演都有闡述自己思想的傾嚮,他們當中有很多----其中不乏一些偉大的人物----不但拒絕用文字的方式去思考如何實踐電影這門視覺藝術,甚至還不願去爬梳、去分享他們對於這門藝術所擁有的獨到見解,比如約翰‧福特(John Ford)、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和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等人----其他尚且有很多例子----就從未闡述過所謂的電影理論,然而,這卻絲毫不影響他們一代宗師的地位。但假設今天的情況是反過來呢?那麼這類例子應會頗為罕見。我的意思是說,那些會去理論化自己的實務操作的電影導演,很少是會拍齣真正的彆腳貨的。事實是,當我們說我們對自己正在實踐的一門藝術是擁有一套理論時(或者說得更簡單一點,一些一般性的或是一貫性的想法),其所意味的是,我們乃是企圖在以一種較深入的,或至少是一種較一貫的方式去實踐這門藝術的。我們或許無法藉此保證我們拍齣來的就是一些品質優良的影片,但我們至少可以藉此希望,究其根本,這些影片確實是電影沒錯!
因此之故,我非常贊同那些認為電影較之技術或商業,其本質乃是和藝術更為接近的電影導演的看法。但我的意思並非在說技術和商業就會阻礙人們去進行思考,而是在人類的曆史文明中,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確實有其一套前提,亦即:既然一個創作者就是其所造之物的負責人,想必他能更適切地去把握住創造過程中的運思儀軌。誠然,一個技術人員、一個工業钜子或是一個經濟學傢也能去拍電影,但他們卻不是以電影為目的來對其進行思考的,因為他們的目的是金錢、是成功,是一套符閤常態的規範;與此相反,一個以藝術傢自居的電影導演卻是以藝術為目的在思考電影這門藝術的。那麼,究竟什麼是藝術的目的呢?所謂藝術的目的即在於能去體現齣那些以所謂的真實(leréel)----我們在過去稱之為真相(lavérité)----為依歸的感知方式、錶達方法、情感型態、準確度以及責任感。
長久以來便一直存在著一些旨在捍衛電影或為其定位的機構和機製,而這當中最具影響力的就數好萊塢,它除瞭擁有無比雄厚的經濟實力之外,還有許多附屬其下的操作手段,這些手段無論是商業性質的還是文化性質的都有(比如奧斯卡奬、媒體營銷管道和為數可觀的專業期刊雜誌等)。至於在大西洋彼岸的我們則是提齣瞭某些特定的電影批評觀念,雖然這些觀念----諸如「作者論」(politique des auteurs)、「場麵調度」(mise en scène)以及稍晚的「現代性」(modernité)和「矯飾主義」(maniérisme)等----在商業層麵上看似起不瞭什麼作用,但在意識型態上卻有著呼風喚雨的威力。上述種種機製不僅建構瞭一個孕育電影的環境,讓它得以被攝製齣來,繼而被發行上市,最終甚至還賦予它一種藝術的定位。
至於電影導演,他們則是會從彆的角度來談論電影藝術這件事。一般而言,他們會認為一件藝術品的先決條件乃在於它不能是一件事後纔被穿鑿附會的作品,反之,它必須得是一件被有「意」為之的作品,每件作品都該有其專屬的創作意念,言下之意:唯有一個心中擁有「構想」的人,纔能創造齣一件藝術作品。不過,這個宛如潛規則一般的定義方式也並非百分之百可靠,畢竟就算是那些最好的意圖也可能會落得徒勞無功的下場----人們不就曾據此而創過一句諺語?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不就曾因此而寫齣一本自傳式的小說作品?但話說迴來,如果這個從意念的角度齣發去對藝術所下的定義仍有其存在的價值,那是因為我們可以將這個定義和所謂的創作行為以及創作觀(poétique)等擺在一起,從而去審視藝術這件事,而這便會立刻牽涉到以下這些問題:創作的意圖性和創作者的個人特質,這兩者之間到底存在著些什麼樣的關係?何以長久以來奉行作者論的影評人總愛將這兩者混為一談呢?
至於其他的藝術傢,他們對於電影藝術的看法則是,它能製造齣一些隻有它自己纔能夠激起的特定效果,比如就感知美學的層麵來說,電影能令觀眾感受到某種其他的藝術形式所無法造就的震懾感和迷醉感,而就意識型態的層次來看,電影能夠散播思想,繼而能去教化大眾。我們在下麵的章節裏便會看到,許多電影導演都在緻力探究這些令他們倍感著迷的效果,其中,他們尤其關注一些能夠引發民眾之集體反應的效果,他們甚至還在這些效果中發現到一些具有政治性的思想。的確,在現存的所有藝術形式當中,電影仍舊是和社會現實最為貼近的。誠然,電視和稍晚齣現的網路或許已經超越瞭電影在意識型態宣傳上的影響力,但,我們今天研究電影理論,其中的一個主要重點,便是得好好地去估量,就其「公民」的意義而言,電影到底能夠發揮哪些力量(或是到底該去行使哪些義務)?
綜上所述,一個電影導演若要配得上這個稱謂,他首先就得獲得某種機製的認可(即便這是一個較為邊緣的「地下」機製);其次,他得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構想;此外,還有第三個條件:他必須得是某些特定形式的創造者纔行。但,究竟誰纔是我們一直在說的這個電影導演呢?若是從電影導演的理論這一點來看的話,這個問題的答案應是殆無疑義的,畢竟就根本上來說,電影史正是由一般所謂的導演們(réalisateurs)所書寫完成的。從這個說法中,我們或許可以察覺齣某種帶有英雄主義色彩的曆史觀:這是一段關於一些偉大的人物及其篳路藍縷開疆闢土的冒險事蹟的曆史----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兩捲專著和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的巨作《電影史》(Histoire(s) du cinéma)便是這兩位作者分彆以其個自的方式所完成的兩段電影史:這是屬於那種帶有浪漫色彩且還散發著神話氣息的電影史。當然,電影史上絕對不會隻有導演而已,電影史上還有不少舉足輕重的製片人(想想那個幾乎可被視為作者的塞爾茲尼剋〔Selznick〕)以及許多非常齣色、非常優秀的攝影師、布景師和編劇等。但話說迴來,我們在思考何謂電影藝術時,卻都會習慣把關注焦點放在電影導演的身上,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無論這些導演是不是所謂的作者導演(auteur),無論他們是藝術傢還是工匠,這些都不是重點,重點是,在整個電影的創作過程當中----這其中包括瞭場麵調度、影像的錄製以及剪接等諸多環節----導演纔是那個真正齣掌大局的核心人物。
一般而言,所有西方的藝術傢其實都可能被視作理論傢,盡管他們從未清楚地去對其藝術實踐的方式進行過相關的理論性闡述,這個現象在過去三個世紀以來的嚴肅音樂(musique savante)中或是在自文藝復興以降的繪畫裏皆有特彆明顯的反映。而在這點上,電影也不例外,為數頗豐的和這門藝術相關的思想,其源頭正是那些偉大的影片本身。試想,穆瑙(Murnau)雖然沒有留下任何理論性的文章,劉彆謙(Lubitsch)雖然要在新聞採訪中纔會透露齣他的想法,雷奈(Resnais)雖然一嚮都拒絕評論自己的工作,但他們三人的電影不都蘊含著大量的思想嗎?況且,這些思想的豐富程度又都絲毫不亞於盧伊茲(Ruiz)、侯麥(Rohmer)和高達等人的電影所展現齣來的那些思想,然而,後麵這三個導演,第一個儼然就是一位哲學傢,而第二個則總是好以藝術史學傢和音樂學傢自居,至於第三個,他還曾經一度想要去成就一樁攸關一個世紀的曆史和美學的龐大事業,不是嗎?
本書所涵蓋的研究範圍,僅止於那些曾透過文字語言去錶達過自身思想的電影導演之理論,而對此篩選方式,我不會假裝這當中沒有任何武斷的成分。當一個電影導演在寫作、在接受訪問或是在迴覆信件時,他總是會用最普遍的工具來進行思考,這個工具就是語言,但,這麼一來,電影導演似乎就變得和任何一個評論者一樣瞭,尤其是那些以評論作為職業的人,也就是影評人,不是嗎?事實上,在法國,有很長一段時間,從事所謂電影理論的都是一些影評人,要等到稍後,學院派的電影理論纔會齣現。而在過去這四十多年來,這兩種機製總是不斷地在暗地較勁,總是不斷地在質疑對方的閤法性。有時,一些影評人會試著去炫耀自己的理論能力,但有時,他們則會反過來去嘲笑所謂的理論;有時,一些學院派人士會刻意去強調諸如情感或是情緒這些影評人專屬的價值,但有時,他們卻又會反過來去詆毀那些缺乏正規理論性的影評人言論,並斥之為空泛、無用。照這麼看來,能夠決定一個電影導演是理論傢與否的,就並不是那些從外部,而是一些從內部去定義理論的標準瞭。
現存很多可以幫我們去評斷一個理論到底有沒有效、有沒有價值的標準,而這些標準除瞭這些功用之外,尚且還能幫我們去為某些理論做齣定位。依我看,這些標準當中有三個是最重要的,即嚴密性、新穎性和可用性,或曰閤理性。
序
誰是理論的發明傢?
《當電影導演遇上電影理論》對在地實踐與思想轉化的啓發
曆經半世紀多的時間,電影研究已是人文領域極為重要的學科之一,尤其來自於歐美世界的批評傢、學者及思想傢對於多重論題的專研與探究是推進相關曆史、美學及理論生成的關鍵原因。如果單單檢視西方電影理論的發展,顯而易見的,自第二次大戰以降的現當代電影思潮,從寫實主義、作者論、馬剋思主義、電影符號學、精神分析學、電影文化研究、電影哲學、電影現象學乃至後電影等,無不是箇中最讓人耳熟能詳的批評觀念與典範思潮。與此同時,這一波波電影理論風潮伴隨著各個不同時代的導演作品、電影運動及國傢電影的産製而綿延不絕、推陳齣新,各式各樣的命題相互撞擊、抗衡與修正。電影研究作為足以和任何一個人文社會科學分庭抗禮的學門,在於透過與其他學科的對話,已然積纍並轉化齣自成一傢的思想體係。
就此脈絡來審視由巴黎第三大學電影學係榮譽教授賈剋‧歐濛的專著《當電影導演遇上電影理論》(初版2002年,增訂版2011年),此書為電影理論研究打開瞭另一種視野。不同於那些慣於藉由上述古典或現當代電影理論範式作為書寫的框架,《當電影導演遇上電影理論》的新意,乃是一方麵在奠基於電影史、美學及理論語境與導演所處的文化環境及其知識層麵上,聚焦他們的創作理念與藝術實踐,從中分析並歸納齣由於創作需求而自發推演並生産齣來的概念和思想;另一方麵,則是歐濛透過幾種不同形態的題旨來重新組織導演的創意發想,並進一步透過係統化的論述來架置他們的影像概念,以形構理論範式與思想係統。具體來說,專書分彆以四大章節架構──〈理論傢的理論:概念、問題、係統〉、〈語言理論與世界理論:可見與影像,現實及其寫作〉、〈機製理論:電影機器與社會功用〉與〈藝術傢理論與藝術理論:影片詩學與影片教育〉──來展開創作者如何構思影像概念、執行場麵調度、操控觀眾與介入社會、與理論傢論辯,及形塑一套特殊闡發藝術與思想的方法。
在對歐濛的分析進行概略闡釋之前,我們需先釐清本書所使用的關鍵字「電影導演」(原文“cinéaste”)一詞。此概念的特異與重要,在於這位當代法國電影理論傢重新賦予這個早在1920年代時即被現代派前衛主義電影創作者德呂剋所創造齣來的新字。當時,「電影導演」尤指能夠彰顯動態影像運動與光影錶徵的電影工作者。而根據歐濛的詮釋,「電影導演」不同於「導演」(法文“réalisateur”、英文“filmmaker”)、「作者導演」(法文“auteur”、英文“author”)與「場麵調度者」(法文“metteur en scène”)這三個字詞,在於它既不隻是執行拍攝工作、也非止於擔負劇本書寫與創建特殊世界的角色,更不受限於指導演員與空間調度的能耐。換句話說,電影導演非但兼備作者導演、導演及場麵調度者的能力和纔華,堪稱「三位一體」的他之絕妙,還在於歐濛認為其具有藝術傢獨有的稟性、視野與精神,以及最重要的,構思瞭兼容實踐與思想的電影概念。
詳察《當電影導演遇上電影理論》,被歐濛認可並加以論述的電影導演名單總共有三十人之多(他在〈導論〉中也說明瞭那些沒被列入的人選與原因),歐美創作者幾乎佔瞭九成,隻有流亡巴黎的盧伊茲與巴西的羅卡除外,其中杜拉剋與莒哈絲則是唯二的女性創作者。就曆史分期而言,這批躋身「名人堂」的響當當的人物分彆齣自默片、古典電影、現代電影及當代電影。而以類彆屬性來說,劇情影片的電影導演獨占鰲頭,前衛主義影片、紀錄影片及實驗影片的創作者則緊隨其後。值得強調的,能讓歐濛看上眼並配稱為電影導演的電影理論並非憑空杜撰的産物,它們不是大多數來自於電影導演的書寫結晶,就是齣自訪談、演講、語錄及授課等多種材料。就創作需求而言,不管是書寫還是訪問,基本上都是電影導演針對作品的闡述、解說及辯駁。像是著作等身的愛森斯坦的主要動機之一是為瞭批駁政敵的不實指控,希區考剋與楚浮之間的著名訪談則是領會好萊塢巨匠的懸念之關鍵,而帕索裏尼的專文是筆戰符號學傢們的結果⋯⋯不管是哪一類,影片始終是最優先被思索的主體,而電影則不可避免地被思辨,彼此遂構成電影導演特有的倫理姿態、美學態度及藝術係統。本書的前兩章是歐濛從浩如煙海的文獻資料中選取、提煉並轉化足以兼容概念、理論及係統錶徵的書寫體現。〈理論傢的理論:概念、問題、係統〉聚焦於那些在電影史中與批評術語不分軒輊的電影概念,從愛森斯坦的「濛太奇」係統、維托夫的「間歇」、愛普斯坦的「上像性」、布烈鬆的「期遇」、帕索裏尼的「流素」、塔可夫斯基的「雕刻時間」到格林的「無所不在之靈」,均為電影導演構想鏡頭與社會、真實與世界、時間與內在的藝術實踐和思想産物。第二章〈語言理論與世界理論:可見與影像,現實及其寫作〉,則鎖定於電影本體與再現關係的論題。首先,電影與繪畫、語言與視覺、自然與絕對之間的斡鏇,是塔可夫斯基、侯麥、高達、布拉剋基及諸多實驗電影創作者辯證影像命題的所在。其次,則是從格裏爾遜、羅塞裏尼、帕索裏尼、到盧伊茲與剋魯格等人關於現實的思考。再者,涉及影像文體的風格論,莒哈絲的「寫作」、阿斯楚剋的「攝影機鋼筆論」、潘林宣的「對位」及吉亞尼謙與弗萊捨的「重組」。還有,帕索裏尼提齣「詩電影」與考剋多「詩性」影像。
顯然,前兩大章節是本書建立作為創作觀與如何創作的電影導演理論之核心所在。確切而言,我們可將上述電影導演的概念視為美學形式與電影美學的思想之體現。此外,從理論角度來檢視之的話,它們可謂是對於電影作為運動與觀視(維托夫、愛普斯坦)、電影作為真實(布烈鬆、羅塞裏尼)、電影作為語言(帕索裏尼)、電影作為書寫(愛森斯坦、阿斯楚剋)、電影作為時間(塔可夫斯基)、電影作為情感(愛森斯坦、希區考剋),及電影作為思想形式(愛森斯坦、愛普斯坦)等形態之展現。至於第三章〈機製理論:電影機器與社會功用〉,歐濛的論述策略轉嚮觀眾與政治脈絡。希區考剋名聲響亮的「懸念」、愛森斯坦的「陶醉」是分彆讓觀眾浸潤於故事世界及採取政治行動的重要理念。此章節的重頭戲,無疑是歐美與拉丁美洲導演以攝影機介入社會的積極做法,他們不是將電影視作政治實踐(格裏爾遜、維托夫)、教學主義(羅塞裏尼),就是政治抗議和批判(剋魯格、羅卡)之目的與意義。更激進的做法,還有電影導演,從法斯賓達、史特勞普到高達等人,將電影構思為理想社會,試圖建立電影烏托邦。作為終章的〈藝術傢理論與藝術理論:影片詩學與影片教育〉則迴歸於電影導演將其念茲在茲的影音實踐架置於藝術係統的論題。可以這麼說,如果前三個章節是創作者對於概念的創造與演繹、模塑觀眾心智並與社會的對話,第四章節一方麵是對於電影導演的意義、角色與使命在作者與藝術傢、實驗傢與手工業者及教育傢之間做齣更細緻的分析與闡述;另一方麵——在我看來是全書論述的精髓——則無非是為瞭辯證作為藝術的電影和古典主義、媒介特殊性乃至綜閤藝術之間的關係。這些尤其自二十世紀初就沒停止過論辯的重要論題,對於歐濛這位信奉現代主義的理論傢而言,乃是啓始於默片時代的愛森斯坦、杜拉剋、剋萊爾、考剋多、新浪潮影迷—電影導演的侯麥與高達、塔可夫斯基及盧伊茲等人的開創性音像語匯、書寫及思想。其中,值得一提的高達花瞭十年創作的《電影史》是最能彰顯電影既能包含與超越其他藝術形式,更能將其他藝術的潛能透過動態影像進行全盤激發的傑作。
長久以來,電影理論多齣自批評傢與理論傢的筆下。電影史的論著,也是同一種思想結構與體係的産物。當然,身為一位深受電影結構主義影響的理論健將,歐濛這本《當電影導演遇上電影理論》雖沒脫離批評傢撰寫電影理論的企圖與視角,但值得凸顯的,是他意欲將這些耳熟能詳卻散落四處的電影導演思想進行脈絡化、概念化與係統化,並進一步將之納入電影理論中加以歸納、描述及剖析的寫作讓人印象深刻,十分敬佩。可以這麼說,歐濛筆下的電影導演理論,它先是概念與本體的辯證,再者是觀眾與社會的互動,最後則是作為藝術體係的顯現。此種多重性的論述不僅讓電影理論多瞭一層來自於電影導演思辨的嚮度,更促使電影美學、電影理論與電影史之語境更顯豐富與復雜。
《當電影導演遇上電影理論》一書的翻譯與齣版,深具意義。這本書讓中文世界的讀者可以直接閱讀到西方重量級批評傢對於電影理論兼具創意與博學的書寫。這點得特彆歸功於譯者蔡文晟仔細考究並緻力還原中文語境也刻意保留法文精髓的精彩譯筆,肯定會讓讀者有十分不一樣的閱讀體驗。從原文到翻譯,對於我們重新認識某種當代西方電影理論的發展傾嚮,絕對是有助益的。然而,如我在文章一開始提及的,歐濛論及的電影導演十之八九來自歐美世界,他這樣的一種電影世界觀一方麵映現瞭其知識的廣博與豐富,另一方麵卻不可避免地顯露齣某種侷限性。例如:書中雖對羅卡展開瞭論述,卻明顯忽略瞭其他「第三電影」思潮及理論(譬如索拉納斯與傑提諾的「邁嚮第三電影」等),更不用說對亞洲電影導演隻字未提。當然,世上沒有一本著述可窮盡一切,何況是一本關於電影導演理論的專書。在我看來,此一空缺並非壞事,反而是本書另一重要啓示,它催生齣一個亟需被深思的問題意識:瞭解當代西方電影思潮的發展固然有助於實現我們汲取與深化自我知識的欲望,但更重要的,無疑還是我們必須將這些知識、理論與思想體係轉化至在地實踐與思考上。具體而言,一百多年來的華語影像藝術史,從孫瑜、劉吶鷗、鬍金銓、邱剛健、侯孝賢、蔡明亮、賈樟柯、吳文光、高重黎及陳界仁等創作者,都曾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包括文章、著作、訪談等——發錶過關於電影與再現、影像與藝術、曆史與政治等多麵嚮的論題。這些素材是電影導演珍貴的思想結晶,非常值得我們進一步去考據、定位與詮釋——這是給未來的一項浩大的華語影像藝術理論工程。
有朝一日,有誰還能再說:電影理論總是西方的發明呢?
財團法人國傢電影中心學術委員
孫鬆榮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我一直對電影的「語法」充滿好奇。看電影時,常常會覺得某些鏡頭、某些剪輯方式,特別有力量,能觸動人心,或者營造齣特殊的氛圍。這本書《當電影導演遇上電影理論》,聽名字就好像在探究電影的「語言規則」。我猜,它應該會深入淺齣地介紹一些電影理論的核心概念,像是「濛太奇」、「長鏡頭」、「景框」、「敘事結構」等等,但不會讓我們覺得枯燥乏味。我期待書中能夠用導演的視角來解釋這些理論,例如,為什麼某個導演選擇用長鏡頭來錶達角色的內心掙紮,或者為什麼某種剪輯手法能製造齣緊張感。或許,作者會引用一些經典電影的片段來做例子,讓我們更容易理解。我也很好奇,書中會不會討論到一些比較前衛的理論,像是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電影學,或是後殖民電影等等。如果能看到這些理論如何在實際的電影創作中被運用,甚至被顛覆,那就太棒瞭。這本書應該能幫助我建立一個更係統的電影觀,讓我更能分析和欣賞電影的藝術性。
评分我一直覺得,偉大的電影,不僅僅是故事講得好,更重要的是它的「風格」和「精神」。而這種風格和精神,很多時候就是導演的個人意誌和對電影藝術的深刻理解的體現。《當電影導演遇上電影理論》這個書名,讓我聯想到很多我心目中的大師級導演,像是侯孝賢、楊德昌,或是更早期的卓別林、黑澤明。我猜,這本書應該會從導演的創作歷程齣發,探討他們是如何在實踐中形成自己的美學主張,而這些主張又和哪些電影理論產生瞭共鳴。例如,電影史上的「作者論」,或者「新浪潮」運動,都強調導演的個人風格。我希望書中能舉一些具體的例子,分析某個導演的作品是如何體現其獨特的「作者性」,又如何與某種電影理論相互印證。這本書或許會讓我明白,好的電影,不隻是技術的堆砌,更是思想的錶達,是導演用鏡頭寫下的詩。能夠從導演的角度去理解電影理論,這對我來說,是非常新鮮且吸引人的。
评分坦白說,我對電影理論本身有點敬畏。總覺得那是學術界纔玩得轉的東西,離我這個普通觀眾有點遠。但是《當電影導演遇上電影理論》這個書名,卻激起瞭我的好奇心。它給人的感覺,不是那種冷冰冰的學術著作,而更像是一個電影愛好者,一個對創作有深入瞭解的導演,在跟我們這些觀眾聊電影。我猜,書裡麵不會充斥著讓人頭昏腦脹的術語,而是會用一種「說故事」的方式,把那些關於電影的「為什麼」娓娓道來。比如說,為什麼某個導演會特別鍾愛某種拍攝角度,為什麼他會選擇這樣的場景佈置,或者為什麼他會在故事的結尾留下一個懸念。這些問題,其實都牽涉到電影理論的根本。我希望這本書能讓我明白,原來那些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電影手法,背後都有著深刻的思考和理論依據。我也期待,透過書中的內容,能夠更欣賞那些能夠巧妙運用理論,卻又不讓理論束縛瞭創意的導演。這本書應該是打開電影內在世界的一把鑰匙。
评分這本書,光看書名《當電影導演遇上電影理論》,就覺得很有意思。我在書店翻瞭一下,感覺它好像不是那種硬梆梆的學術論文,而是比較平易近人,甚至有點像是一種對話。我猜,作者應該是把那些高深的電影理論,用比較生活化、比較貼近實際拍片經驗的方式來呈現。畢竟,很多時候,理論講得再天花亂墜,如果跟實際操作脫節,就變成紙上談兵瞭。而且,很多偉大的導演,他們在創作的過程中,其實不自覺地就實踐瞭很多理論,甚至開創瞭新的理論。所以,這本書很有可能是在探討這種「理論與實踐」的連結,或許會舉很多導演的例子,像是庫柏力剋、費裏尼、希區考剋等等,分析他們的作品是如何呼應某種電影理論,或者他們的創作手法又如何影響瞭後來的理論發展。我對於這種「理論解構」很有興趣,因為這樣能幫助我更深入地理解電影,而不隻是停留在錶麵的故事和視覺。希望這本書能讓我在看電影時,有更豐富的層次感,能從導演的思維去欣賞一部作品。
评分我總是覺得,理解一部電影,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去感受它帶給我的情緒和衝動。但有時候,我會覺得自己似乎錯過瞭什麼,好像這部電影還有更深層的意義,我卻無法觸及。《當電影導演遇上電影理論》這個書名,聽起來就像是一場精彩的「對話」,一個是實際的創作者,一個是抽象的理論傢,他們兩者碰撞齣瞭火花。我猜,這本書可能不會枯燥地羅列各種電影理論名詞,而是會透過導演的實際經驗,來解釋那些理論。比如說,一個導演在拍攝過程中遇到的挑戰,他如何透過鏡頭語言去解決,而他所採用的方法,又是否與某種電影理論的觀點不謀而閤。我期待書中能夠分享一些導演在片場的真實故事,以及他們如何看待電影創作和電影理論的關係。這本書或許能幫助我,將那些在課堂上聽過、在書上看過的理論,與實際的電影影像聯繫起來,讓我更能看懂電影,更能欣賞到電影的藝術價值和思想深度。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