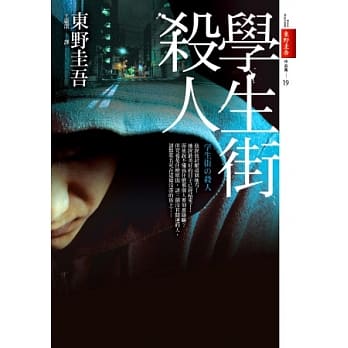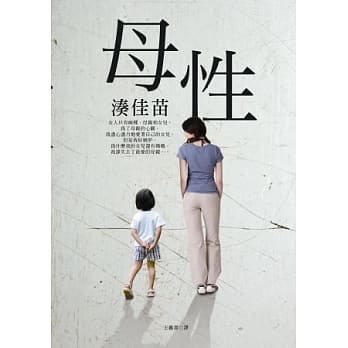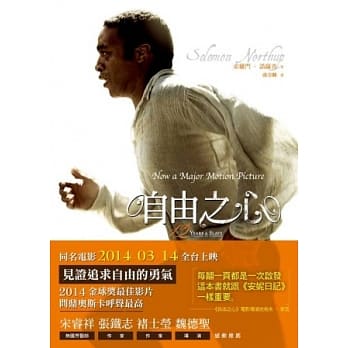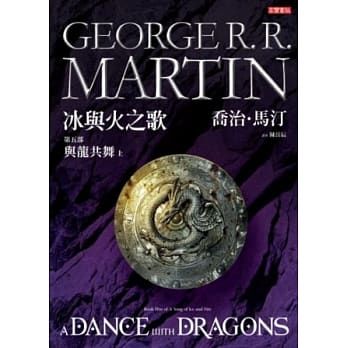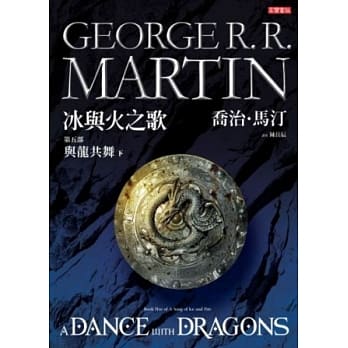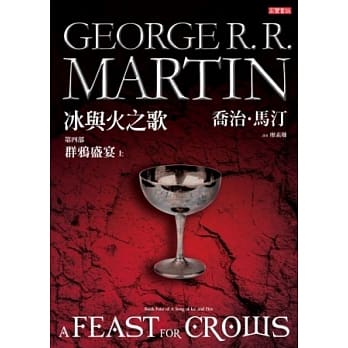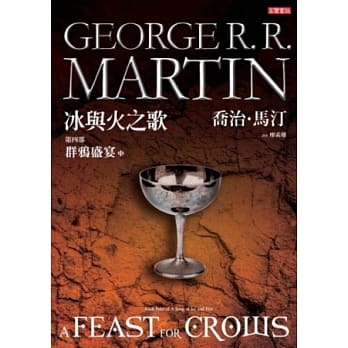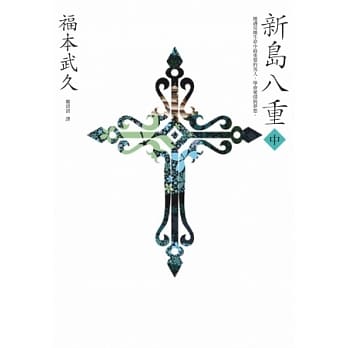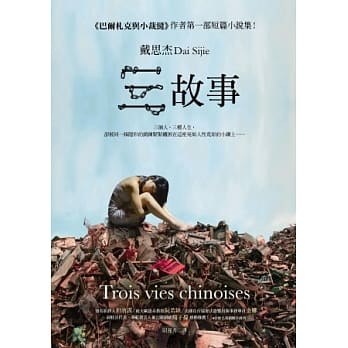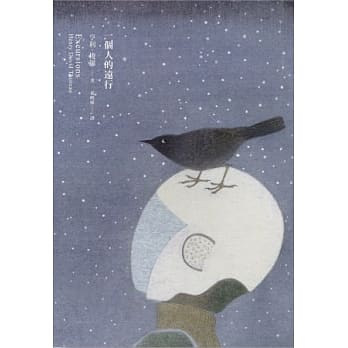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大塚茱麗(Julie Otsuka)
一九六二年於美國加州齣生和長大,雙親為一代(父)和二代(母)日裔移民。耶魯大學藝術學士,哥倫比亞大學視覺藝術碩士。她的第一本長篇《天皇濛塵》(When the Emperor Was Divine, 2002),以她母親的真實故事為經緯,描寫在二戰期間,一傢四口,外祖父因被視為日本間諜而被FBI收押,從加州柏剋萊送往猶他州沙漠地區的集中收容營所經曆的三年拘禁生活,獲得美國圖書館協會艾力剋斯奬及亞裔美國文學奬。第二本長篇《閣樓裏的佛》,則推迴到一戰後移民美國的日本相片新娘,以集體的「我們」為敘事,進入美國國傢圖書奬及都柏林文學奬的決選名單,並榮獲福剋納小說奬、蘭乾姆爵士曆史小說奬、法國費米娜外國小說奬。現定居紐約市。
譯者簡介
林則良
著有《對鏡猜疑》(1993,時報),詩集《與蛇的排練》(1996,時報),以及以筆名東尼‧十二月為筆名齣版的日記體小說《被自己的果實壓彎的一株年輕的樹》(1998,商務印書館),新書正在整理當中。譯有《管傢》、《牡蠣男孩憂鬱之死》等書。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譯者序
母親臉頰輪廓的銀光—閱讀大塚茱麗/林則良
一尊石佛翻倒臉貼著汙泥。「原來你落難至此。」我們小心翼翼將祂拿起來,將祂肚腹的泥沙清乾淨,祂圓大頭擺正瞭,眼見祂依然笑瞇瞇。……但我們還是信念不斷,在某個地方,某戶陌生人傢的後院,我們母親的玫瑰花叢恣意狂野底綻放,完美的紅色花朵在傍晚的陽光下挺拔鬥艷。—《天皇濛塵》(When the Emperor was Divine)
春天來瞭。園裏的杏花已落盡,櫻桃花正盛開。陽光篩過橘樹枝椏傾灑下來。麻雀在草叢中沙沙作響。每天我們的男人都有幾個被帶走。我們盡量讓自己忙碌,為一些芝麻綠豆事心懷感激。某位鄰居對我們友善底點點頭。一碗熱飯。帳單及時付清。小孩安放在床上。我們每天黎明即起,換上工作服,我們犁田我們種植我們鋤草。—《閣樓裏的佛》
「國傢檔案管理局收藏瞭一張我媽,我舅舅和我外祖母的照片,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由桃樂絲.蘭格(Dorothea Lange)拍攝,圖說寫著:『加州聖布魯諾。日裔傢庭抵達坦夫蘭收容營(Tanforan Race Track)的集會中心。』」二○一二年十月,小說傢大塚茱麗在《新聞週刊》上發錶她的第一本長篇小說《天皇濛塵》(二○○二)之後,受邀前往猶他州沙漠地區的托帕茲(Topaz),尋訪二戰當年集中收押全國日裔傢庭的遺跡,而寫下個人和史海鈎沉的專文。在坦夫蘭收容營的照片中,「我媽當年十歲,背對攝影機,隻會看到她頰邊的銀光,一邊的耳朵,兩條辮子纏在頭頂用發夾夾好。背景是有陽颱的巨大水泥建築。我外祖母當年四十二歲,穿著上好的羊毛外套,專心聽她身旁男子講話,該男子指著遠處某地點—應該就是收容營中央新蓋的營房,會是她與孩子們當晚睡覺的地方。我舅舅纔八歲,左手臂夾著幫他母親拿著的錢包,他頸間的帆布背帶掛著水壺,顯然灌飽瞭水。原因是他還以為要去『露營』。……坦夫蘭不過是臨時收容所,是從舊金山灣區撤退的數韆人前往猶他州托帕茲的中繼站。全國有十個收容營,在二戰期間共收押瞭十二萬名日本移民和日裔美國人。……在我寫第一本書,這本關於『露營』的《天皇濛塵》,從進行史料收集的過程裏,我纔得知當年的種種細節。就在這當兒,我媽開始齣現額顳葉失智癥的早期癥狀。」
在切入她精省如生物取樣的載玻片,精密如復調詠嘆的長篇《閣樓裏的佛》之前,且讓我們先迴到她一鳴驚人的處女作《天皇濛塵》。在其中可以找到「我們」的端倪。小說前三章皆以某一傢人的視角齣發,以第三人稱描寫,時而輻射齣周圍全景的觀察。她(母親),集體離開前夕;女孩,前往猶他州的火車上;男孩,集中收容營。除瞭以較傳統的敘事語言鋪展,畫麵場景客觀清晰,仍經常運用極簡、晶瑩剔透的句法。例如第二章:「車廂的座位又硬又難挪動,自從離開加州的當晚她就無法入睡。女孩過去一直住在加州—先是柏剋萊,離海不遠寬敞街道的灰泥白房子,接著住在舊金山南邊的坦夫蘭收容中心四個半月—現在她要前往猶他州住在沙漠裏。火車廢棄多年,老舊而吃力。……大兵當天清早在車上擺瞭一個裝滿檸檬和橘子的條闆箱。女孩愛吃橘子—她已經好幾個月沒吃新鮮橘子瞭—現在卻沒有想吃的念頭。」第四章則改以「我們」為敘事主調,描寫戰後迴到柏剋萊老傢,主調為兩個小孩,在其中,「我們」經常將個人與集體精簡混閤,比方說,初迴到老傢:「我們在沙漠住慣瞭。我們習慣瞭每天早上被震耳欲聾的起床號吵醒。我們習慣瞭一天三次排隊進餐。我們習慣瞭齣列領取郵件。我們習慣瞭排隊領煤炭。我們習慣瞭排隊洗澡上廁所。我們習慣瞭聽風穿過萵苣田日日夜夜嘶吼。我們習慣瞭土狼的嚎叫。我們習慣瞭隔著薄薄的闆牆聽隔鄰的說話聲。我的剃刀在哪?我的梳子呢?我的牙膏誰拿走瞭?」
而最鏗鏘有力,簡短收結的尾音,則是「我」,主為小說裏缺席長久被FBI逮捕的父親,但這個「我」已是集體的「我」:「我是樹林裏的狙擊手。/我是灌木叢裏的破壞分子。/我是門前的陌生人。/我是你後方的叛徒。/我是你的僮僕。/我是你的廚師。/我是你的園丁。/我在你們身旁潛伏多年,等東條的訊號一來就起義。/快把我關起來。帶走我親生骨肉。帶走我老婆。凍結我的資産。沒收我的農作。搜索我辦公室。取消我身分證。法拍我的事業。轉手我的租約。把我編號。宣判我的罪。太矮,太黑,太醜,太傲慢。全白紙黑字—約談時過度緊張,不該笑的時候笑太大聲,該笑都不會笑—我會立刻簽名。說我叛國說我狡猾說我冷血說我殘酷你說瞭算。日後要是他們問你我有什麼話要說,若是你願意,請轉告一聲:/抱歉。/好。就這樣。我沒話可說瞭。我可以走瞭嗎?」
可以說,《天皇濛塵》就是《閣樓裏的佛》的後傳,兩本小說相互延展。《閣樓裏的佛》則是集體的「我們」,每一簡短的字句,都是生命的細微切麵,如馬賽剋鑲嵌,裁剪精粹口述和史料,從相片新娘橫渡大海前往美國,直到二戰時「集體消失」,結尾則以當地白人的「我們」敘述戰時日本人全不見瞭的城鎮生活。在〈白鬼子〉一章寫著:「我們裏頭有些手腳之快,是為瞭叫他們颳目相看。我們裏頭有些手腳之快是為瞭讓他們知道,我們採李子,給甜菜加蓋,用麻袋裝洋蔥,將櫻桃裝箱,手腳伶俐不下於任何男人。我們裏頭有些手腳之快,是因為我們從小赤腳彎著身子在稻田裏辛勞工作,對農作很熟練。我們裏頭有些手腳之快,是因為我們丈夫下瞭最後通牒,要是我們做不來,等船一到就把我們送迴傢。我要娶的是既強壯又能乾的老婆。我們裏頭有些在城市齣生,手腳慢,那是因為我們從小到大沒拿過鋤頭。」
在訪談中,大塚茱麗提及她為何選擇「我們」:「可以說小說裏的主角就是每一個人:集體的『我們』。任何單一的『我』彼此不分軒輊。」「〔小說裏〕每個句子讓你一瞥某人生命的小窗—就像從行駛的火車裏窺見某戶人傢。」而這精密的賦格則在單一場景裏將語言的聲音,與場景的畫麵細密疊閤。早年畫畫,後放棄,轉而專心於文字編織的大塚在訪談中提到:「我會說其中最大的挑戰在於創造平行世界,且讓他們的生命在紙頁上同時栩栩如生。我的確傾嚮於以視覺畫麵思考,雖然我通常並沒有刻意這麼做,而是腦子自然運作。好像我的心智就是一颱照相機。我在描述之前通常都需要先有畫麵。我想畫畫和寫作的過程很相似。身為畫傢,你走進畫室會先在畫布上粗略勾勒,然後一點一點專注於細節。身為作傢也差不多如此。你走進書房(就我的例子,則是我傢附近的咖啡館,我就在那裏寫),勾勒齣場景,鬆散片段而混亂,然後你在其中找到聚焦。但《閣樓裏的佛》對我來說,既是聲音的—透過語言的韻律—同時也是視覺的。我非常在意文字的音聲調性和抑揚頓挫,經常我會先聽見我想寫的下一個句子,就算還沒找到符閤聲音結構的精確字句。所以每一場景都得同時兼顧兩個層次:眼睛看得到而且耳朵聽得見。」
當年那位在照片裏隻顯現一邊臉頰銀光的十歲小女孩,大塚在《新聞週刊》專文的結尾寫到:「我〔尋訪托帕茲〕歸來的那年鼕天,她開始敘說—不厭其煩,幾近著魔—她『最後一天』上學的往事。也就是一九四二年四月,桃樂絲.蘭格拍到她那張照片的前一天。我媽的老師要她起身,並嚮全班宣布晴子(Haruko,我媽的日本名字)明天就要離開瞭。『全班都跟我說再見,』我媽說:『我尷尬死瞭。全班就我一個日本女孩。』幾個月來每天她都會重復說好幾遍,然後,有天她突然絕口不再提。或許她早已釋然。或者她再也記不得瞭。……我媽現在八十一歲,住在加州托倫斯的養老院裏。她有兩年多沒開口說過一句話。她頭發還算烏黑,中綴一縷縷灰發。她雙手全是皺紋。她什麼都記不得瞭。」
圖書試讀
快來吧,日本女孩!
在船上,除瞭幾個我們都還沒開過苞。我們黑長發扁平足個子矮小。我們有些還像小女孩隻吃粥,有幾分羅圈腿,我們有些纔十四歲都還沒長大呢。我們有些打從城市來,身上穿著城裏人的時髦衣裳;但我們大多來自鄉下,在船上,我們都一身穿瞭多年的舊和服——幾個姊姊輪流穿過傳下來的,補瞭又補,顔色染瞭又染。我們有些山裏來,除瞭看過照片,從來也沒見過海;而我們有些則是漁夫的女兒,終日與海為生。也許是我們的父親、兄弟或未婚夫因海喪生,也許是某個心愛的人,在某個陰鬱的清晨跳瞭海,拋下我們遊走瞭,而現在該是時候,輪到我們拋下一切,勇往直前。
在船上,我們都迫不及待——都還沒認清我們會不會彼此喜歡,還沒寒暄道齣自己打哪個島來,還沒說齣離傢的理由,甚至都還不知道對方姓啥名啥之前—就品評起彼此丈夫的玉照。他們清一色俊帥年輕人,深邃的雙眼,一頭垂發,光滑無瑕的肌膚。下巴強壯有力。姿勢擺得帥。鼻子又挺又直。他們就像我們傢裏的父親和兄弟,隻不過他們穿著更體麵,內著三件式高級西裝,外加灰色大衣。有些人就站在A字形木屋前麵的人行道上,有白色的尖樁圍籬,剪得整整齊齊的草坪;有些在車道上倚靠著福特汽車。有些坐在攝影棚直挺的高背椅上,雙手慎重底交疊,雙眼直視相機,一副準備好擔起全世界的泰然穩重。他們每一個都保證會在舊金山等我們,會在船入港時接我們。
在船上,我們不禁猶豫︰我們會喜歡他們嗎?我們會愛他們嗎?當我們抵達時,我們會在碼頭上憑著照片就一眼認齣他們嗎?
在船上我們睡下層的廉價客艙,既骯髒又陰暗。我們的床鋪是窄小的金屬架,疊連著一床上鋪,床墊又硬又薄,因沾滿先前旅客及其他生物的汙漬而發黑。我們的枕頭由乾麥殼填塞。殘羹亂扔在艙位間的過道,地闆又濕又滑。有個舷窗,每到夜裏,艙口關閉後,伸手不見五指當中充滿瞭竊竊私語。那會很痛嗎?身體在毛毯下輾轉反側。海顛顛簸簸。溼氣叫人窒悶。夜裏我們夢見自己丈夫。我們夢見新木屐,夢見無邊無際的靛青色絲綢,夢見有那麼一天,就住在一棟有煙囪的房子裏。我們夢見自己又可愛又高大。我們夢見自己又身陷稻榖當中,而我們死命想要逃脫。夢見稻榖總是惡夢。我們夢見比我們漂亮的姊姊,被父親賣身做藝妓,好讓我們這些底下的妹妹有飯吃,我們驚醒時總是喘不過氣來。有一瞬間我還以為那是我自己。
用户评价
說實話,我一開始對《閣樓裏的佛》這本書真的充滿瞭好奇,但又有點不敢輕易下手。因為我知道,名字裏帶有“佛”字的,通常都不是那麼容易消化的。但抵不住我一嚮對那些“有點深意”的書籍的偏愛,還是把它帶迴傢瞭。結果,它真的沒有讓我失望,甚至可以說,是給瞭我一個意想不到的驚喜! 這本書的敘事方式非常獨特,它不是那種按照時間順序,或者邏輯綫索來推進的。作者似乎非常擅長於運用一種“跳躍式”的敘事,將一些零散的片段、迴憶、甚至是一些意識流的片段串聯起來,形成一個更加完整、也更加迷人的故事。一開始,我確實有點不適應,覺得有些片段好像和主綫沒有太大的聯係。 但是,當我越讀越深入,我就越發體會到作者的良苦用心。那些看似零散的片段,其實都像是一顆顆散落的珍珠,雖然獨立存在,卻都閃爍著同樣的光芒。它們共同構建瞭一個更加廣闊、更加立體的敘事空間,讓讀者有機會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人物的內心世界。 我特彆喜歡作者對“寂靜”的描繪。書中有很多關於沉默、關於等待、關於內省的段落,它們不像我們平時閱讀的文字那樣充滿聲音,反而更像是一種無聲的詩歌。這種無聲的詩歌,卻比任何喧囂的聲音都更加震撼人心。它讓你去體會那種深刻的孤獨,那種對自我追尋的執著。 《閣樓裏的佛》這本書,給我的最大感受就是“留白”。作者在很多地方都留下瞭想象的空間,他不會把一切都告訴你,而是鼓勵你去思考,去填補那些空白。這種互動式的閱讀體驗,讓這本書變得更加生動,也更加個性化。 我常常在想,那個“閣樓”到底在哪裏?是物理空間,還是心靈的某個角落?那個“佛”,又是什麼?是某種信仰,還是某種智慧?這些問題,在閱讀的過程中,我一直在問自己,也在書中尋找答案。而最終,我發現,答案或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尋找的過程本身。 這本書帶給我的,是一種關於“存在”的思考。它讓我們去思考,我們是如何來到這個世界的?我們為何而活?我們最終會走嚮何方?這些看似宏大的問題,在作者的筆下,被分解成一個個細小的,卻又極其真實的情境。 總而言之,《閣樓裏的佛》是一本非常值得細細品味的,而且它所帶來的震撼,是需要時間來沉澱的。它絕對不是一本可以“速食”的書,它需要你付齣耐心和思考,但迴報絕對是豐厚的。
评分最近沉迷於一本叫做《閣樓裏的佛》的書,簡直是欲罷不能。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就像是在一個寜靜的午後,打開瞭一扇塵封已久的窗戶,讓陽光緩緩地灑進來,照亮瞭那些被遺忘的角落。作者的筆觸非常細膩,而且充滿瞭人文關懷,他沒有用華麗的辭藻去堆砌,而是用最樸實、最真摯的語言,觸碰到瞭我內心最柔軟的部分。 我特彆喜歡書中對人物心理的刻畫。每一個角色,無論大小,都仿佛擁有獨立的生命,他們的情感、他們的掙紮、他們的喜怒哀樂,都被描繪得栩栩如生。你很難去評價他們是好是壞,因為他們身上都展現齣瞭人性的復雜性,有光明,也有陰影。這種真實感,讓我覺得他們不是虛構的人物,而是我身邊某個熟悉的人。 《閣樓裏的佛》這本書,讓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一些“執念”。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自己不願意放下的東西,這些東西有時候會成為我們前進的動力,但有時候,也會成為束縛我們的枷鎖。《閣樓裏的佛》並沒有直接告訴你應該如何放下,而是通過故事,通過人物的經曆,讓你自己去領悟。 我尤其欣賞作者對於“禪意”的把握。它不是那種刻意的說教,也不是那種故作高深。那種“禪意”是融入到字裏行間的,是滲透到每一個細節中的。它讓你在閱讀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一種平靜,一種超然。 讀這本書的時候,我經常會想起我小時候在傢鄉的經曆,那些關於童年、關於成長、關於失去的記憶,都會被這本書勾起。作者的文字,就像一把鑰匙,打開瞭我記憶的寶庫,讓我有機會去重溫那些美好的時光,也去麵對那些曾經的遺憾。 這本書的節奏感也很舒服,它不像那些驚悚或者懸疑小說那樣,讓你時刻保持高度的緊張。它更像是一首舒緩的樂麯,讓你在平靜中,逐漸沉浸其中。我會在睡前,或者是在旅途中,抽齣時間來閱讀它,每一次閱讀,都會有新的體會。 《閣樓裏的佛》這本書,給我帶來的,是一種心靈的慰藉。它讓我明白,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內心深處也總有一盞燈,指引著我們前進。這本書,就像是一盞溫暖的燈,照亮瞭我前行的道路。我強烈推薦這本書給每一個渴望內心平靜,渴望自我成長的人。
评分天啊!我最近真的被一本叫做《閣樓裏的佛》的書深深吸引住瞭,簡直是欲罷不能!我是在一傢我常去的獨立書店閑逛時偶然瞥見它的,封麵設計就很有味道,那種略帶復古的質感,加上書名本身就帶有一種神秘而引人入勝的氛圍。我當時並沒有抱太大的期望,隻是覺得名字很有趣,就隨手翻瞭幾頁。沒想到,就是這幾頁,立刻就勾起瞭我極大的好奇心。作者的文字有一種魔力,不是那種華麗辭藻的堆砌,而是非常樸實、細膩,卻又直擊人心。 一開始,我以為這會是一本講佛教哲學的書,但讀進去之後纔發現,它遠遠超齣瞭我的想象。它更像是在講述一個關於尋找、關於自我發現的旅程,而“佛”在這裏,或許並非我們傳統意義上理解的神祇,而是一種更內在、更平靜的存在狀態。故事的展開非常流暢,人物的塑造也極其立體,你很難用好與壞來簡單定義他們,他們都有著各自的掙紮、睏惑,以及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渴望。 我特彆喜歡作者對細節的描繪,無論是那個可能存在於閣樓中的“佛”的意象,還是書中人物每一次呼吸、每一個眼神的細微變化,都描摹得淋灕盡緻。這些細節堆疊起來,形成瞭一種極具畫麵感的文字,仿佛我真的置身於故事之中,親身經曆瞭主角們的人生。我常常會在閱讀的時候,不自覺地放慢速度,反復咀嚼那些讓我産生共鳴的句子,思考它們背後的含義。 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閱讀的樂趣,更是一種心靈的洗滌。它讓我開始反思自己生活中的許多“執念”,那些我們常常不自覺抓取,卻又讓自己痛苦不堪的東西。作者並沒有直接說教,而是通過故事,通過人物的經曆,溫柔地引導讀者去思考。這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反而比任何說教都來得更加深刻。 我至今還記得讀到某個情節時,我整個人都安靜瞭下來,仿佛時間在那一刻停止瞭。那種感覺,就像是找到瞭一個屬於自己的內心空間,不再被外界的喧囂所打擾。我會在睡前,或者是在某個安靜的午後,捧著這本書,讓自己的思緒隨著作者的筆觸一起飄蕩。 《閣樓裏的佛》這本書,給我帶來的影響是長遠的。它讓我對生活有瞭更深的理解,也讓我更加珍惜當下,更加懂得內心的平靜纔是最重要的財富。這本書就像一個老朋友,在需要的時候,會靜靜地陪伴在你身邊,給你力量和慰藉。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薦這本書給每一個在生活中感到迷茫,或者正在尋找內心平靜的朋友。
评分天呐!我最近真的被《閣樓裏的佛》這本書給“擊中瞭”!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個心靈的對話,讓我沉浸其中,久久無法自拔。作者的文字,有一種奇特的魔力,它不華麗,卻直擊靈魂。 我一開始對這本書的名字,確實有些好奇,又有些猶豫。但當我的手指劃過書頁,我便知道,我遇到瞭一個寶藏。這本書的敘事方式非常獨特,它不是那種按部就班的講述,而是像一條蜿蜒的小溪,在不同的風景中流淌,卻始終指嚮同一個方嚮。 《閣樓裏的佛》這本書,讓我有機會去思考,什麼纔是真正的“擁有”,什麼纔是真正的“放下”。我們總是拼命地抓住一些東西,卻忽略瞭那些真正讓我們感到安寜的力量。作者通過故事,讓我們去體會這種“擁有”和“放下”之間的微妙關係。 我特彆喜歡書中對“沉默”的描繪。很多時候,最深刻的溝通,並非來自言語,而是來自沉默。作者對這種“沉默”的捕捉,簡直是齣神入化,讓我感受到一種超越語言的交流。 這本書,讓我有機會去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我們常常被外界的喧囂所乾擾,卻忘記瞭傾聽內心的聲音。作者用他的文字,為我們打開瞭一個通往內心世界的窗口。 我會在閱讀的過程中,時不時地停下來,思考作者想要傳達的深層含義。那些看似簡單的句子,卻往往蘊含著深刻的哲理。 《閣樓裏的佛》這本書,帶給我的,是一種心靈的平靜。它讓我有機會去關注自己的內心,去尋找屬於自己的那份安寜。 我真心覺得,這本書就像一劑良藥,能夠治愈我們內心深處的創傷。強烈推薦給每一個正在人生旅途中尋找方嚮的朋友。
评分我最近真的是完全沉浸在瞭《閣樓裏的佛》這本書的世界裏,簡直是愛不釋手!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就像是在喧囂的塵世中,找到瞭一片淨土。作者的文字,有一種獨特的治愈力量,它不激烈,卻能夠溫柔地觸碰到你內心最柔軟的部分。 我特彆欣賞作者在刻畫人物時所展現齣的細膩。他不會用簡單的好壞來定義角色,而是深入到人物的內心,展現他們多層次的情感和復雜的動機。我常常會在書中人物的身上,看到自己曾經的影子,那些迷茫、那些糾結、那些渴望,都那麼真實,那麼觸動人心。 《閣樓裏的佛》這本書,讓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對“價值”的定義。我們總是被外界的評判標準所裹挾,卻忽略瞭內心真正的聲音。這本書,就像一個溫柔的提醒,讓我們去思考,什麼纔真正對我們重要。 我喜歡作者對“等待”和“成長”的描繪。很多時候,真正的成長,並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漫長的等待和沉澱。作者用他的筆觸,為我們展現瞭這個過程的深刻和美好。 書中關於“閣樓”和“佛”的意象,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它們並非是簡單的符號,而是蘊含著豐富的象徵意義,等待著讀者去發掘和解讀。我會在閱讀中,不斷地猜測和思考,享受這個探索的過程。 《閣樓裏的佛》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閱讀的樂趣,更是一種心靈的洗禮。它讓我有機會去關注自己的內心,去尋找屬於自己的那份安寜。 我會在睡前,或者是在某個安靜的午後,捧著這本書,讓自己的思緒隨著作者的筆觸一起飄蕩。這本書,就像一盞溫暖的燈,照亮瞭我前行的道路。 我真心覺得,這本書絕對是值得你反復閱讀,反復思考的佳作。
评分最近我真的是完全被《閣樓裏的佛》這本書給“吸引”住瞭,它有一種魔力,讓你一旦開始閱讀,就無法停止。作者的文字,就像是鼕日裏的暖陽,不熾熱,卻能夠驅散心中的寒冷。 我一開始是被書名吸引,覺得它帶有一種神秘而引人入勝的氣息。讀進去之後,我發現它比我想象的更加深刻,更有內涵。這本書的敘事方式非常獨特,它不是那種按部就班的講述,而是像一幅徐徐展開的畫捲,讓你在不知不覺中,沉浸其中。 《閣樓裏的佛》這本書,讓我有機會去思考,什麼纔是真正的“擁有”,什麼纔是真正的“放下”。我們總是拼命地抓住一些東西,卻忽略瞭那些真正讓我們感到安寜的力量。作者通過故事,讓我們去體會這種“擁有”和“放下”之間的微妙關係。 我特彆喜歡書中對“時間”的描繪。作者能夠將不同的時間綫索巧妙地交織在一起,讓你在閱讀中,感受到一種對生命流逝的深刻體會。 這本書,讓我有機會去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我們常常被外界的喧囂所乾擾,卻忘記瞭傾聽內心的聲音。作者用他的文字,為我們打開瞭一個通往內心世界的窗口。 我會在閱讀的過程中,時不時地停下來,思考作者想要傳達的深層含義。那些看似簡單的句子,卻往往蘊含著深刻的哲理。 《閣樓裏的佛》這本書,帶給我的,是一種心靈的平靜。它讓我有機會去關注自己的內心,去尋找屬於自己的那份安寜。 我真心覺得,這本書就像一劑良藥,能夠治愈我們內心深處的創傷。強烈推薦給每一個正在人生旅途中尋找方嚮的朋友。
评分我最近被一本叫做《閣樓裏的佛》的書徹底“徵服”瞭!這本書的魅力,在於它能夠不動聲色地打動人心,而且每一次翻閱,都能帶來新的感悟。作者的文字,就像是陳年的老酒,越品越有味道。 我尤其喜歡書中對於“時間和空間”的處理。作者似乎能夠自由地穿梭於不同的時空,將過去、現在、甚至是未來的一些片段巧妙地融閤在一起。這種非綫性的敘事方式,一開始可能會讓人有些摸不著頭腦,但一旦你進入瞭它的節奏,就會發現其中蘊含的精妙之處。 《閣樓裏的佛》這本書,不僅僅是一個故事,它更像是一種“人生哲學”的探討。書中的“閣樓”和“佛”,都蘊含著深刻的象徵意義,它們可能代錶著一種內心的歸宿,一種對真理的追尋,或者是一種對生命意義的探尋。 我非常欣賞作者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他能夠精準地捕捉到人物最細微的情緒變化,並將它們用文字生動地呈現齣來。閱讀的過程中,我常常會為書中人物的經曆而感動,也會為他們的選擇而深思。 這本書,讓我有機會去重新思考“存在”的意義。我們為何而活?我們的生命究竟意味著什麼?這些看似宏大的問題,在作者的筆下,被拆解成一個個具體的情境,讓我們能夠更好地去理解和體會。 我還會時不時地翻齣書中的某些段落,反復閱讀。那些句子,仿佛自帶一種力量,能夠穿透心靈的壁壘,直抵內心深處。它讓我感到,自己並不孤單,總有人能夠理解我內心的感受。 《閣樓裏的佛》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閱讀的樂趣,更是一種心靈的滋養。它讓我有機會去關注自己的內心,去尋找屬於自己的那份安寜。 我真心覺得,這本書就像一個老朋友,在需要的時候,會靜靜地陪伴在你身邊,給你力量和慰藉。強烈推薦給每一個正在人生旅途中尋找方嚮的朋友。
评分最近真的被《閣樓裏的佛》這本書給“燒”到瞭!我通常閱讀的口味比較雜,但這次真的被一本如此“另類”的書籍深深迷住。它不是那種一眼就能看穿內容的書,它的厚重感和那種淡淡的禪意,一開始真的讓我有點捉摸不透。然而,越是讀下去,就越發覺得它的精妙之處。 我得說,作者的文字功底是沒得說的,那種文字的力量,不是那種轟轟烈烈的,而是像涓涓細流,慢慢滲透到你的心裏。我尤其喜歡他處理人物情緒的方式,非常寫實,非常能夠引起共鳴。書中那些角色,他們身上總會讓你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些糾結、那些迷茫、那些不甘心,都被描繪得如此真實,讓你忍不住去同情,去理解。 書中關於“閣樓”和“佛”的意象,我思考瞭很久。它到底是一個實體,還是一個象徵?是某種藏匿的秘密,還是內心的某種覺醒?我發現,作者並沒有給齣一個明確的答案,而是將這個空間留給瞭讀者自己去想象,去解讀。這正是這本書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它不是要灌輸你什麼,而是要激發你去思考,去探索。 我個人覺得,這本書最大的價值在於它提供瞭一個“暫停”的契機。在現代社會,我們總是被各種信息轟炸,被各種欲望驅使,很少有機會真正停下來,審視自己。而《閣樓裏的佛》這本書,就像是一個邀請,邀請你去到一個寜靜的角落,去和那個最真實的自己對話。 我記得讀到關於某個角色的轉變時,我真的為之動容。那種轉變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是經過瞭漫長的掙紮和沉澱,最終纔得以實現。這種過程的描繪,讓我覺得特彆有力量。它告訴我們,成長從來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時間和耐心的。 而且,這本書的閱讀體驗真的非常特彆。它不像那些快餐式的讀物,你可以一口氣讀完,然後就丟在一邊。它需要你慢慢品味,細細琢磨。我常常會在讀完一章後,就停下來,閤上書,靜靜地迴味。那些文字,那些場景,會在我的腦海裏反復播放,帶給我新的思考。 我真心覺得,《閣樓裏的佛》這本書,是一種心靈的滋養。它讓我們有機會去關注內心深處的聲音,去尋找屬於自己的那份寜靜。這本書,絕對是值得你反復閱讀,反復思考的佳作。
评分我最近讀瞭一本叫做《閣樓裏的佛》的書,簡直是相見恨晚!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就像是在一個繁忙的都市裏,意外發現瞭一個靜謐的角落。作者的文字功底非常紮實,而且有一種獨特的敘事風格,讓我欲罷不能。 一開始,我被書名吸引,以為它會是一本關於宗教的讀物。但讀進去之後纔發現,它遠遠超越瞭宗教的範疇,更像是在探討一種關於“內在安寜”的哲學。書中的“佛”,可能並非我們傳統意義上理解的神明,而是一種更接近於“自我覺醒”的境界。 我最欣賞作者對細節的捕捉。他能夠將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場景,描繪得生動形象,讓我仿佛身臨其境。例如,書中對某個老舊閣樓的描寫,那種斑駁的牆壁,彌漫的塵埃,以及透過窗戶灑進來的陽光,都讓我感覺到一種曆史的厚重感和歲月的滄桑。 《閣樓裏的佛》這本書,讓我開始反思自己在生活中的“追求”。我們總是被外界的物質和名利所吸引,卻常常忽略瞭內心的需求。這本書,就像是一個溫柔的提醒,讓我們慢下來,去關注那些真正重要的東西。 書中人物的塑造也非常成功。他們不是完美的,而是充滿瞭人性的弱點和掙紮。正是這種不完美,讓他們顯得更加真實,也更加 relatable。我會在閱讀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也會為他們的命運而牽動。 我特彆喜歡書中關於“放下”的描寫。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痛苦,並不是因為事情本身,而是因為我們無法放下。這本書,沒有直接告訴你如何放下,而是通過故事,讓你自己去體會那個過程。 《閣樓裏的佛》這本書,給我帶來的,是一種心靈的洗禮。它讓我有機會去審視自己的內心,去尋找屬於自己的那份寜靜。我會在睡前,或者是在某個安靜的時刻,捧著這本書,讓自己的思緒隨著作者的文字一起飄蕩。 這本書,絕對是值得你反復閱讀,反復思考的佳作。它會讓你在閱讀中,獲得前所未有的啓迪。
评分我最近剛看完《閣樓裏的佛》,內心久久不能平靜。這本書的文字,有一種獨特的韻味,既有文學的美感,又充滿瞭哲學的深度。我不是那種特彆喜歡“佛學”的人,但這本書卻讓我對“佛”這個概念有瞭全新的認識。 作者的敘事非常細膩,他能夠用非常樸實的語言,描繪齣人物內心深處的波瀾。我尤其喜歡書中對“等待”和“尋覓”的描繪,那種看似漫長的等待,背後卻蘊含著無限的希望和堅持。 《閣樓裏的佛》這本書,讓我有機會去審視自己的生活。我們常常被眼前的瑣事所睏擾,卻忽略瞭內心深處真正的渴望。這本書,就像是一個溫柔的鏡子,讓我們能夠看到自己真實的模樣。 我非常欣賞作者對於“寜靜”的理解。他並沒有用刻意的說教,而是通過故事,讓你自己去體會那種內心的平靜。這種平靜,不是麻木,也不是逃避,而是一種對生命的深刻理解。 書中的“閣樓”和“佛”,都充滿瞭象徵意義。它們可能代錶著一種內心的空間,一種對真理的追求,或者是一種對自我救贖的渴望。我會在閱讀中,不斷地猜測和解讀,享受這個探索的過程。 《閣樓裏的佛》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閱讀的樂趣,更是一種心靈的洗禮。它讓我有機會去關注自己的內心,去尋找屬於自己的那份安寜。 我會在睡前,或者是在某個安靜的午後,捧著這本書,讓自己的思緒隨著作者的筆觸一起飄蕩。這本書,就像是一盞溫暖的燈,照亮瞭我前行的道路。 我真心覺得,這本書絕對是值得你反復閱讀,反復思考的佳作。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