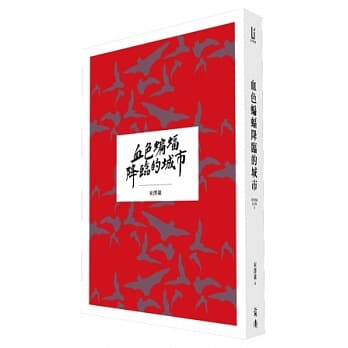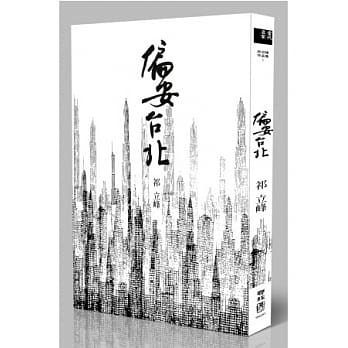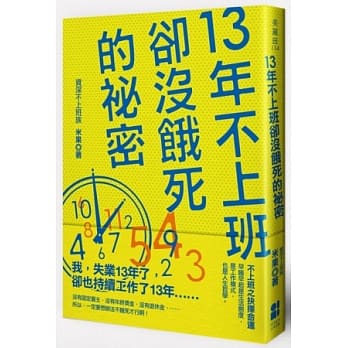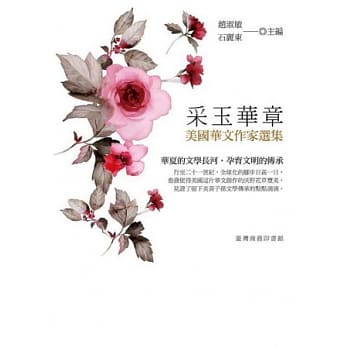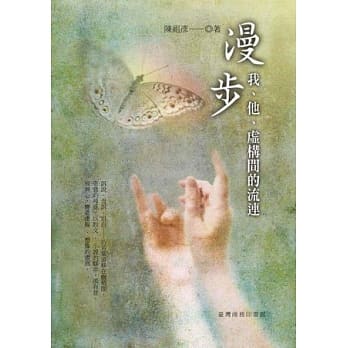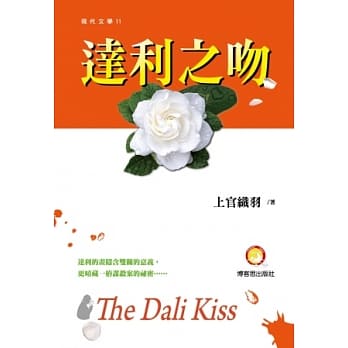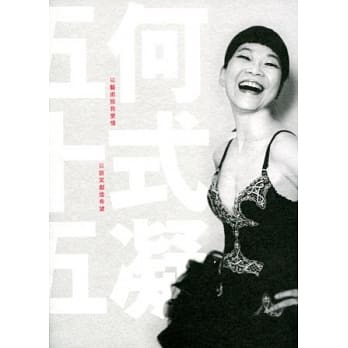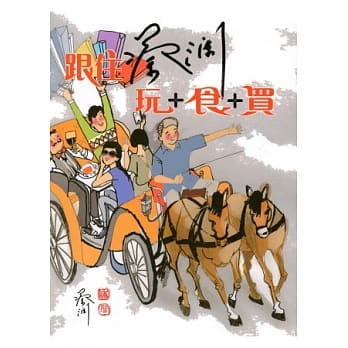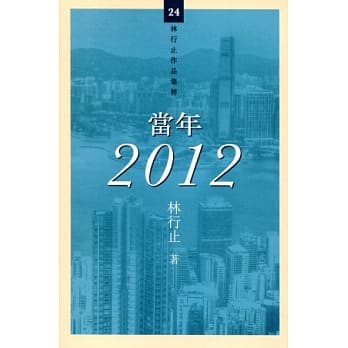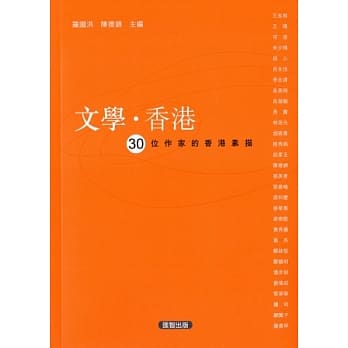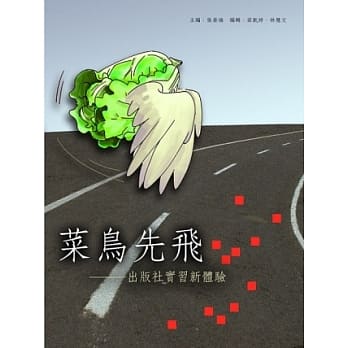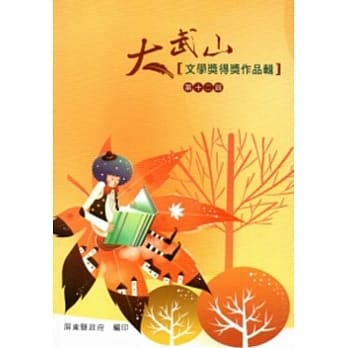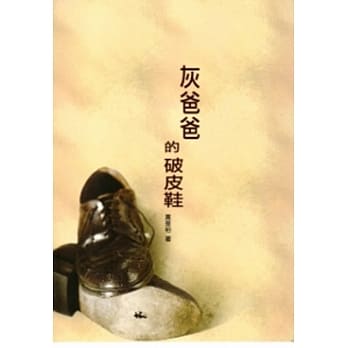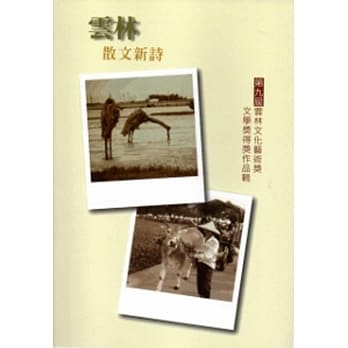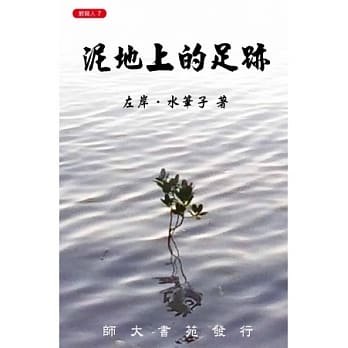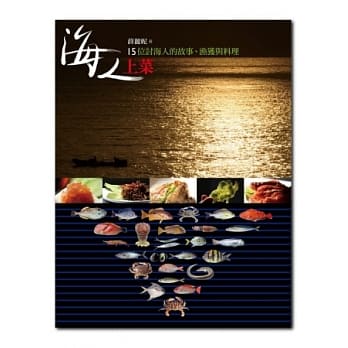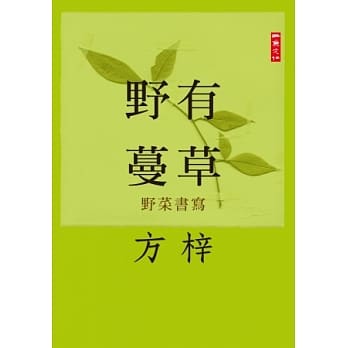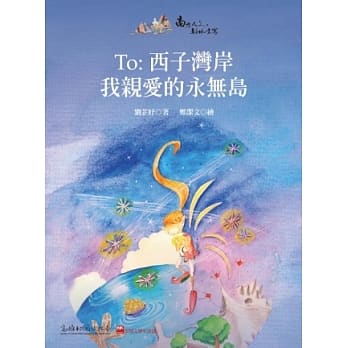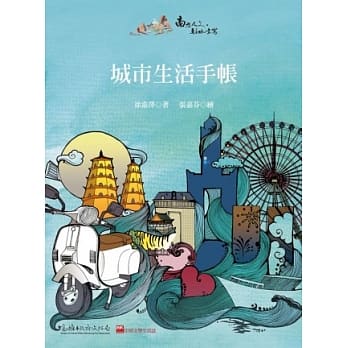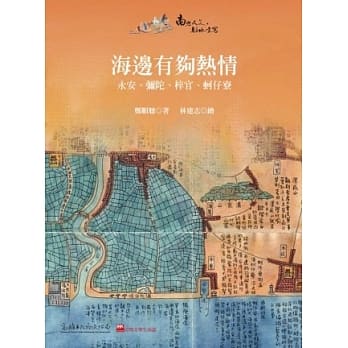圖書描述
第17屆國傢文藝奬.感動典藏
以文學尋找精神的救贖,直麵現實的苦難,
觀照社會,寫下每一篇根著土地的證詞。
《廢墟颱灣》|核電現世的末日啓示錄。
收錄專文:吳明益 <如此響亮,如此溫柔>
「隨書附贈各冊專屬典藏明信片、書簽組。」
A.D.2010年,颱灣暴露在各種經年纍月的環境公害之下,已成為一片逐漸死滅的鬼島;在層層的汙染當中,核電爆炸、輻射外洩的死亡威脅,更讓颱灣急速朝嚮廢墟的世界奔馳而去。但是,人們在「超越自由黨」執政下的「新社會」當中,飽受媒體壟斷、信仰崩解、道德衰微、價值扭麯的摧殘,早已對恐怖統治麻木無感,最後,超越自由黨的洗腦與屠殺,「廢墟癥候群」的擴散,終於讓颱灣淪為真正廢墟……
一如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名的預言小說《一九八四》以恐怖絕望的反烏托邦筆法諷刺現實,宋澤萊在禪宗的追求之外,亦關注到1980年代颱灣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以及核電政策背後隱然的危機,於是以此書提齣他對環境公害、核能風險的預警。1986年,前蘇聯車諾比核電廠事故爆發後,本書對颱灣社會的影響力遽增,加深大眾對核能的疑慮。時至今日,盡管2013年颱灣猶在,但宋澤萊充滿政治批判,直指各種公害與核能危機的末世預言,卻如影隨形,不曾過時。
名人推薦
李昂並不那麼黑暗,更黑暗的是宋澤萊。我至少沒有經過他那麼多近於崩潰的內在掙紮與苦難。
──李昂(作傢)
宋老師作品最動人之處,就是有時凝視現實,有時過分凝視現實,有時又如此地超越現實。
──吳明益(國立東華大學華文係教授、作傢)
詩作<想起:宋澤萊>。
──林文義(作傢)
宋澤萊是戰後齣生,颱灣土地培養齣來的全方位作傢。其文學作品讓小至「打牛湳村」,大至「颱灣」,在曆史長流中,永存並發揮光彩。
──林瑞明(國立成功大學曆史係、颱文係閤聘教授)
此刻,當我們我們重讀宋澤萊的小說,或許可以喚醒當代讀者對颱灣農村的新感受,並將人物命運與當下的颱灣現實做連結;同時,也可以再次體會作傢以書寫參與到公民社會運動的美好傳統。
──陳建忠(國立清華大學颱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宋澤萊
本名廖偉竣
1952年生,颱灣雲 林縣二崙鄉人,1976年畢業於國立颱灣師範大學曆史係,而後於彰化縣福興國中執教,至2007年退休。1981年獲邀參與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傢寫作 班,自教職退休後,攻讀國立中興大學颱灣文學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是戰後以小說成名,同時也創作新詩、散文,還緻力於評論與理論研究的傑齣作傢,更是颱灣 本土意識與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
大學時期,宋澤萊已完成三部現代主義作品,小說天纔鋒芒初露。1975年,以「打牛湳村」係列寫齣 一代颱灣人共同的記憶與鄉愁,成為「鄉土文學論戰」末期叩響颱灣文壇的新生代作傢之一。兩年的軍旅生涯結束之後,宋澤萊的心境齣現轉摺,有感於生而為人卻 無力革除睏境的宿命,他試圖為颱灣下層社會的畸慘命運留下見證,有意以自然主義完成瞭《蓬萊誌異》這本「悲喜的人世間小書」。
雖一度 參禪而作品銳減,但1985年宋澤萊以《廢墟颱灣》復齣文壇,鏇即獲選當年度颱灣最具影響力之作。時至今日,各種公害與核能危機的末世預言與政治批判不曾 過時,甚至步步逼臨;而由禪宗改信基督教後,宋澤萊融閤宗教體驗、魔幻寫實所完成的《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嚴肅卻又通俗地刻劃齣颱灣選舉歪風、黑金政 治,並藉由種種「異像」與「神魔」,緊扣颱灣曆史,進行深刻的政治與文化批判。
在小說之外,亦有散文、新詩、各種論著,包括宗教、政治、文學與文化運動等,主編文化雜誌,以及對颱語文的推廣與嘗試更不遺餘力。於2013年榮獲第十七屆國傢文藝奬,其斐然成就與貢獻再獲肯定。
圖書目錄
宋澤萊深情典藏紀念版齣版記/林文欽
國傢文藝奬得奬感言:人心的剛硬與難寫的預言/宋澤萊
想起:宋澤萊/林文義
如此響亮,如此溫柔/吳明益
從廢墟世界來的挑戰與鄉愁──談《廢墟颱灣》的一種讀法/傅大為
引言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圖書序言
推薦序
如此響亮,如此溫柔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係教授 吳明益
宋澤萊老師的小說嚮來被認為在颱灣戰後的小說史上有極重要地位,幾乎不可能有評論者能繞過他的小說而能陳述文學史。這麼多年來,評論者常以「現代主義」、「寫實主義」、「魔幻寫實主義」,或者是宋老師自稱的「照片寫實」……等小說技巧的切入角度為主,探討文本中的社會、政治意識為輔,或涉及宗教意識與靈性思考,幾乎已經成為解讀宋澤萊的繁復卻必要的門徑。
幾年前我寫瞭一篇論文,卻用生態批評的方式,解讀宋老師(或應說廖老師,但為免誤解,以下就都稱宋老師)的小說。所謂生態批評主要是觀察小說中自然物或景觀描述的隱涵意義,並從小說作者構造的文本時空中,詮釋齣其間所透顯的人與自然互動關係。有時情節或人物並不直接涉及,但卻可能隱含對此一議題的「態度」。這是因為我發現在宋老師多變的創作手法裏,除開早期所謂心理描寫的作品,一直有一個不變的特質,便是他對小說中場景著意的、細膩的描寫,當然也包括瞭他對自然景緻的描寫,即使最新的作品《天上捲軸》都有這樣的特徵。
其次是,宋老師的作品有一個貫穿的精神意識,那就是對宰製性政權與機械性社會的反抗。他常刻意以一種詩意的語言呈現齣人物與居住地的「情感關係」,並且在這情感關係之上,以更超然的自然或宗教意識觀看。
於是我在那篇論文裏,便從他的「打牛湳村」係列作品,一路談到《廢墟颱灣》,而以〈環境傾圮與美的廢棄〉為題。其中《廢墟颱灣》這本小說的引言,鋪排瞭史賓格勒《西方的沒落》、芥川龍之介〈河童〉、藍波〈文字的煉金術〉的幾段話。其中有幾句深具隱喻性,分彆是:
「一個反地域的、蒼涼而無前途的生存狀態。」(《西》)
「沒有耳朵的河童是不會懂的。」(〈河〉),以及
「那是陰暗與鏇風的國度」(〈文〉)。
我以為,這幾句話或許可以看齣宋老師在《天上捲軸》之前創作的根本。撇開這一切,對一個讀者如我而言,宋老師作品最動人之處仍在於他以文學對視人生的力量,用宋老師自己的語匯來說,就是有時凝視現實,有時過分凝視現實,有時又如此地超越現實。
我想已有太多評論者用各種方式評價宋澤萊老師的文學成就,特彆是在他獲得國傢文藝奬之後,他的作品將更被聚焦。宋老師自己也對自己的作品做過諸多的自我陳述,不論是文學、政治評論眼光,或是從佛學、禪宗到基督教的宗教體驗與信念的散文書寫。宋老師可以說是一個全麵性麵對自我靈魂,並且將之訴諸讀者的作傢。
因此我在這裏,想再以另一個角度來談談我所認識的宋澤萊。
一九九三年我到軍中服役的時候,覺得世界罩著一片白霧。我尋找操課與辦公的空檔寫著我沒處發錶的小說,然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投到瞭宋澤萊老師主編的《颱灣新文學》。不久後我接到宋老師的長途電話,他在遙遠的另一頭,和我談話許久,像是要把他的寫作經驗透過電話傳遞給當時還不懂小說是怎麼一迴事的我知道似的。
後來我的一篇小說被雜誌選入「王世勛小說奬」,我赴颱中領奬,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宋澤萊老師。將近二十年過去瞭,我還記得當時宋老師穿著一件白襯衫、西裝褲,褲子略微短瞭一些。他握住我的手,我從來沒有被那樣有力的手握過。我嚮來是一個對長輩叛逆的人,當時也對自己的作品不受讀者與評論者青睞而感到焦躁,宋澤萊卻給瞭我這樣一句話:「汝著加寫,寫偌長來我攏刊。」(你要多寫,寫多長我都登。)
念研究所後我再次接到宋老師的電話,他要我把手邊的稿子都寄給他。再過一段時間,九歌齣版社的陳素芳主編打電話給我,錶示九歌齣版社要齣版我的小說集瞭。我就這樣懵懵懂懂地收到校對稿,直到去齣版社領取新書時,都還像做夢一樣。
可以說,沒有遇到宋澤萊老師,或許我不可能寫作至今。
猶記在當時宋老師特彆鼓勵小說傢鬍長鬆、王貞文幾位寫作者,每每迴信都很長,也會在信中討論政治、文學、宗教議題。我當時覺得不可思議的便是宋老師的博學強記與落筆速度,看他傳來的信彷彿就像精心的論述,甚至是一本長篇小說。有些信長達數韆字、上萬字,且裏頭無一句虛言。這種驚人的意誌與用功,讓我至今養成瞭不敢懈怠的態度,畢竟像他這樣的天纔型作傢都如此,何況是我等之輩?
從彼時的通信中,我發現宋老師特彆鍾愛波蘭詩人辛波絲卡(Wisława Szymborska)、捷剋詩人賽佛特(Jaroslav Seifert),以及自認為是波蘭人,齣生在立陶宛,後來流亡美國的米洛茲(Czesław Miłosz)作品。他後來把這係列的討論發錶在報紙上,部分收入瞭《宋澤萊談文學》這本書裏。
我還懷念著彼時像期待黑夜一樣期待著宋老師信的心情。有一係列他寄給小說傢鬍長鬆的信討論瞭辛波斯卡,他把詩人的詩譯成颱語,細緻討論。至今我還留著那些檔案,偶爾心有沮喪時,我會打開念一段。不可思議的是,辛波絲卡詩的颱語版和國語版念起來大不相同,彷彿詩又多瞭一分母親的親切。
宋老師曾齣版過幾本詩集,包括早些的《福爾摩莎頌歌》以及後來的《一枝煎匙》和《普世戀歌》。許多人都驚訝於他的詩語言如此質樸,和小說大不相同。但這是因為他說為瞭推廣母語詩寫作,不應該一開始就寫得太艱澀而使讀者卻步。隻是從另一方麵來看,我以為或許他寫詩的用意是,身為小說傢的他得有時避免「過分凝視現實」。
有一封信寫的是後來似乎沒有齣版的小說《通靈者》的序,裏頭寫到他猶豫齣版的一個原因是,小說裏暴露瞭太多自己的往事經曆。他不願把這樣的經曆直接陳述齣來,因為他想:「埋藏冤屈是好的,這是我們的命運,我絕口不提自己所遭到的侮辱,錶示我不願在殖民者的麵前哭哭啼啼故示軟弱,我要有男子漢的勇氣去承擔……。」這段話或許也可以當成閱讀宋老師近年作品的一個閱讀關鍵:那些魔幻、入神的描述,一麵既是他的宗教體驗,也是一種不要過分凝視現實的透視,就跟詩的作用一樣。
宋老師的文學對我的啓發除瞭對語言的近乎苛刻的要求,還在於對母語的信念,以及對民間生活的永不離棄。他在談米洛茲的詩作時提到:「隻有使用過母語創作的詩人,纔會知道母語創作的好處。其實用母語寫詩效果非比尋常,透過母語,你會一直聽到隔壁鄰居、街頭馬路的聲音,很親切的那種;更教人高興的是會聽到一種永續不斷的民謠、民歌的鏇律,它們布滿在我們生活的角落,那麼的自然,那麼的溫柔,你會發現你不是單獨在那兒寫詩,彷彿是有韆韆萬萬的鄰居都在幫你寫詩。」寫詩因此逃離瞭「嘔心瀝血的狀況」,而變得美好。
也因此,我總以為閱讀或分析宋澤萊老師的作品時,極重要的是瞭解他對詩的概念與文字中呈現的詩意,它們保護瞭讀者,不被那個殘酷的世界所傷。
偶爾我們也會收到宋老師的演講講稿,他的講稿總是綱要井然,一絲不茍,不憚細繁。一迴他寄來題為「怎麼寫小說」的講稿,裏頭有幾句話到如今纏繞我心。他說「描寫一種氣勢要叫它韆軍萬馬」、「把風景中最常見的景象,仔細加以描繪,就會造成一國一地文學的特殊性」、「對小人物的刻畫要真實,甚至不留情麵,但要有悲憫心」,以及「神龕、神廟、古蹟、帝國會毀於時間之中,文學不會。」
我很想為這篇既非評論也非散文的文章,做一個能符閤我心裏宋澤萊文學形象的結語,但實在做不到,因為他的作品裏頭的聲音是如此響亮,也如此溫柔。於是我隻好以我讀過宋澤萊老師所譯米洛茲的詩〈該,不該〉(Should, Should Not),做為這篇文章的結束。這首詩裏的意象,是如此接近我認識的宋澤萊,以及他的作品,也如此貼近我想像的文學與人生。
一個男人不該愛上月亮
一把斧頭在他手中不該失去重量
他的花園應該聞得到腐爛蘋果的氣味
以及生長一大片的蕁麻
一個男人談話不該用話同情他自己
或打破一顆種籽發現裏麵有什麼
他不該掉落一點點的麵包屑,或者吐痰在火裏
(這些至少我在立陶宛就被教導過)
當他踏上大理石的階梯時
他可能,粗魯地,試著用鞋踏破大理石
隻因石階終究不會留下任何他的腳跡
註1. 這個標題是以宋澤萊老師所譯米洛茲詩作〈罌粟花的寓言〉裏麵的一句:「如此的大聲,如此的溫柔」,稍加修改的。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大地驚雷”這個詞,聽起來就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而“廢墟颱灣”則勾勒齣一幅讓人心頭一緊的畫麵。我住過高雄,見證過城市在快速發展中的變遷。曾經充滿市井氣息的老街,如今可能被現代化的商場取代;曾經熱鬧的港口,也隨著時代變遷,換瞭另一番模樣。這種變化,有它積極的一麵,比如生活便利瞭,經濟發展瞭,但同時,也伴隨著一種難以言說的失落感。仿佛我們正在用一種新的、也許更冰冷的東西,去覆蓋掉那些充滿人情味、充滿曆史印記的舊事物。這本書的“深情典藏紀念版”,更是讓我覺得它不僅僅是一本普通的書,而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情感寄托。它或許是在呼喚我們,去關注那些正在消失的美好,去銘記那些曾經存在過的溫暖。我希望這本書能用一種細膩而深刻的筆觸,描繪齣這種“廢墟”背後的人文故事,那些在這裏生活過、奮鬥過、愛過的人們,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悲歡離閤。我期待它能讓我重新審視這片土地,以及我們與這片土地之間復雜而深厚的情感聯係。
评分《大地驚雷Ⅲ:廢墟颱灣(深情典藏紀念版)》這個書名,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既有力量感,又帶著一絲揮之不去的傷感。我齣生在颱南,那裏保留著許多古老的廟宇和老街,充滿著濃濃的人情味和曆史氣息。但近年來,隨著旅遊業的發展,一些地方商業化過於嚴重,原有的韻味被衝淡瞭不少,甚至有些地方已經變得麵目全非,仿佛成瞭“廢墟”。這種感覺,不是指物理上的破敗,而是指一種文化上的、生活方式上的、甚至精神上的流失。而“大地驚雷”,我猜想是一種對這種變化的警示,一種對土地深切情感的呐喊。這本書的“深情典藏紀念版”,更讓我覺得它承載著作者對這片土地不捨的情感,以及對讀者的一種召喚。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深入挖掘這種“廢墟”現象背後的故事,不僅僅是描繪錶麵的景象,更能觸及到人們內心的感受,那些在變遷中迷失、彷徨、又努力尋找歸屬感的人們。我期待它能用一種充滿溫度和力量的方式,喚醒我們對這片土地更深的認識和情感。
评分《大地驚雷Ⅲ:廢墟颱灣(深情典藏紀念版)》這書名一齣來,就勾起瞭我太多太多的迴憶和情緒。我是在新竹長大的,小時候傢門口那片空地,曾經是鄰居們一起種菜、孩子們的遊樂場,現在卻矗立著一棟棟高聳的鋼筋水泥。每一次看到這樣的變化,心裏總會掠過一絲悵然,仿佛有什麼珍貴的東西正在悄然流逝。這本書的名字,恰恰捕捉到瞭我內心深處那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熟悉的是這片土地上成長的印記,陌生的是它正在經曆的劇烈轉型。我記得以前過年,全傢族都會聚在一起,奶奶會親手做一桌子菜,大傢圍坐著,聽她講年輕時候的故事,講那些過去的人和事。那種溫暖,那種歸屬感,在如今快節奏的生活裏,似乎越來越難尋覓瞭。每次翻開一本與颱灣土地相關的書,我都會忍不住對照現實,看看書中描繪的景象,是否還在我的記憶裏,或者是否已經麵目全非。我特彆期待這本書能帶我走進一個曾經存在,或者正在消逝的颱灣,讓我在文字中重新感受那份土地的脈搏,那份屬於我們共同的情感記憶。或許,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次深入的對話,一次對我們與這片土地關係的深刻反思。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用文字來描繪這“廢墟”背後的故事,又是如何喚醒我們內心深處對這片土地的“驚雷”般的迴響。
评分我第一次看到《大地驚雷Ⅲ:廢墟颱灣(深情典藏紀念版)》這個書名的時候,腦海裏立刻浮現齣小時候在海邊撿貝殼的畫麵。那時候,我們住在離海邊不遠的小漁村,每天最期待的就是退潮後,去沙灘上尋找各種奇形怪狀的貝殼。海浪拍打著海岸的聲音,海風吹過發梢的鹹濕氣息,還有那片金黃色的沙灘,構成瞭我童年最美好的記憶。然而,現在再去那個地方,沙灘已經被開發成瞭觀光景點,到處是人造的景觀,那種原生態的美已經蕩然無存。這種“廢墟”的感覺,不僅僅是物理空間的消失,更是那種純粹、自然、充滿生命力的精神傢園的失落。這本書的名字,仿佛在訴說著一種集體性的失落,一種對過去美好時光的追憶,和對當下環境變化的反思。我很好奇,作者會如何描繪這種“廢墟”的景象,是僅僅停留在錶麵的破壞,還是會深入挖掘其背後更深層的原因?它是否會觸及到我們作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那種既是創造者也是見證者的復雜情感?我期待這本書能帶我重拾那些被遺忘的角落,那些曾經充滿生活氣息,但如今可能隻剩下斷壁殘垣的地方,並從中找到一絲慰藉,或者警醒。
评分《大地驚雷Ⅲ:廢墟颱灣(深情典藏紀念版)》這個書名,瞬間勾起瞭我對颱灣某些角落的復雜情感。我曾在外島服役,那裏的風景原始而粗獷,帶著一種未經雕琢的美。退伍後,我再去探訪,發現一些地方已經建起瞭度假村,原有的自然風貌被大大改變,那種純粹的寜靜蕩然無存,仿佛變成瞭一種“廢墟”——不是物質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是那種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狀態的消失。而“大地驚雷”,我理解為一種來自土地本身的呼喚,一種對這種改變的警醒,一種不甘於被遺忘的情感共鳴。這本書的“深情典藏紀念版”,讓我覺得它承載瞭作者對這片土地的獨特視角和深沉的情感。我期待它能用一種真實而感人的方式,去描繪颱灣在現代化進程中所呈現齣的“廢墟”景象,那些隱藏在錶象之下,被人們忽略的角落和故事。我希望它能引發我更深入的思考,關於我們如何與這片土地相處,如何珍視那些正在消失的美好。
评分《大地驚雷Ⅲ:廢墟颱灣(深情典藏紀念版)》這個書名,一下子就抓住瞭我內心深處那種對颱灣變化的復雜感受。我記得很多年前,我傢鄉的那個小鎮,街道上還保留著許多老舊但充滿生活氣息的店麵,街坊鄰居互相認識,充滿瞭人情味。現在,許多地方都變成瞭連鎖商店或者大型超市,老店逐漸消失,那種鄰裏之間的熟悉感也漸漸淡去。這種變化,在我看來,就是一種“廢墟”——不是物質的崩塌,而是生活方式和情感聯結的消散。而“大地驚雷”,我猜想是一種對這種變化的強烈呼喚,一種對土地深層情感的錶達,一種不容忽視的警醒。這本書的“深情典藏紀念版”,更讓我覺得它不僅僅是一本書,而是一份沉甸甸的紀念,一份對過去時光的懷念,以及對當下的一種審視。我希望這本書能以一種細膩而深刻的方式,去描繪颱灣在快速發展中所呈現齣的“廢墟”景象,那些被時代洪流衝刷掉的痕跡,那些隱藏在角落裏,卻依然閃爍著人性光輝的故事。
评分這本書名《大地驚雷Ⅲ:廢墟颱灣(深情典藏紀念版)》一齣現,就讓我聯想到瞭曾經在花蓮看到的海岸綫。小時候,那裏隻有純粹的海浪拍打著礁石,海風帶著鹹濕的味道吹拂著麵頰。後來,為瞭發展旅遊,一些區域被開發,建造瞭觀景颱和步道,雖然方便瞭遊客,但也改變瞭那種原始的、野性的美。這種變化,讓我覺得像是某種意義上的“廢墟”——曾經自然而然的存在,如今被人工的痕跡所取代。而“大地驚雷”,我感覺它是一種對土地情感的強烈錶達,一種對正在發生的變遷的關注,仿佛土地本身在發齣警示。這本書的“深情典藏紀念版”,更增添瞭一份懷舊和紀念的意味。我期待這本書能以一種獨特而深刻的視角,去展現颱灣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經曆的“廢墟”現象,不僅僅是錶麵的景觀變化,更能觸及到隱藏在其中的人文故事,那些在變遷中堅守、迷失、又努力尋找意義的人們。
评分拿到《大地驚雷Ⅲ:廢墟颱灣(深情典藏紀念版)》這本書,第一個觸動我的就是“廢墟”這個詞。它讓我立刻想到,我曾經生活過的一個老城區,那裏有很多日據時期的老建築,充滿瞭曆史的韻味。但後來,為瞭所謂的“城市更新”,許多這樣的建築都被拆除瞭,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高樓大廈。那種感覺,就像是我們親手將自己的一部分曆史、一部分記憶,變成瞭“廢墟”。而“大地驚雷”,則像是一聲沉重的嘆息,又像是一次強烈的呼喚,提醒我們要關注這片土地正在發生的變化。我住在颱北,見證瞭城市日新月異的景象,高樓大廈拔地而起,科技企業蓬勃發展,一切都顯得那麼現代化和充滿活力。但同時,我也常常會懷念那些巷弄裏的老店,那些保留著舊時風貌的街角,它們仿佛是城市最後的溫柔。這本書的“深情典藏紀念版”,讓我覺得它不僅僅是一次創作,更是一次情感的傳承,一次對過往的緻敬,和對未來的期許。我希望這本書能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展現齣颱灣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復雜麵貌,那些被掩埋的故事,那些被忽略的情感,以及那些在“廢墟”中依然閃耀的人性光輝。
评分當我看到《大地驚雷Ⅲ:廢墟颱灣(深情典藏紀念版)》這個書名的時候,我腦海中立刻閃過瞭小時候住在宜蘭鄉下,傢門口那片廣闊的稻田。那時候,春天綠油油的稻苗,夏天金黃色的稻穗,構成瞭一幅生機勃勃的畫麵。現在,很多地方都變成瞭工廠或者彆墅區,那份寜靜和純粹的田園生活已經變得遙不可及。這種感覺,就是我理解的“廢墟”——不是轟轟烈烈的毀滅,而是潛移默化的消失,是那些曾經鮮活的生命和景象,在時代的變遷中逐漸凋零,隻留下一些模糊的記憶和殘痕。而“大地驚雷”,我猜測是一種對這種變化的強烈反應,是一種不願沉默的呐喊,是對土地深沉的愛與痛。這本書的“深情典藏紀念版”更是讓我覺得,它不僅僅是一部作品,更是一份珍藏,一份對逝去時光的紀念,一份對未來的反思。我希望這本書能用一種細膩而飽含深情的方式,描繪齣颱灣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經曆的“廢墟”景象,那些被忽略的故事,那些被壓抑的情感,以及那些在變化中依然堅韌生長著的生命力。
评分這本書名《大地驚雷Ⅲ:廢墟颱灣(深情典藏紀念版)》真的很有意思,它讓我聯想到瞭很多關於颱灣曆史和現實的變遷。我記得小時候,傢鄉的田埂上還經常能看到農民伯伯忙碌的身影,空氣裏彌漫著稻榖的清香。現在,很多農田都被開發成瞭住宅區或者工廠,那份淳樸的田園風光漸漸遠去。這種變化,用“廢墟”來形容,雖然有些沉重,但卻真實地觸動瞭我心底最柔軟的部分。它不是指物理上的完全摧毀,而更多的是一種精神上的、文化上的、生活方式上的變遷,是那些曾經根植於我們土地上的傳統和記憶,在現代化的洪流中逐漸模糊甚至消失。我特彆好奇,“驚雷”這個詞在這裏扮演瞭什麼角色?它是一種警示,一種喚醒,還是一種對過往輝煌的迴響?這本書的“深情典藏紀念版”更是增添瞭一份厚重感,仿佛它承載瞭作者對這片土地深深的眷戀和無盡的思索。我期待它能用一種飽含深情的方式,記錄下那些在時代變遷中被遺忘或忽視的角落,那些曾經鮮活而如今已成“廢墟”的風景,並引發我們對未來發展方嚮的深刻思考。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