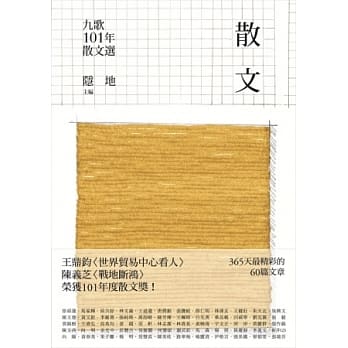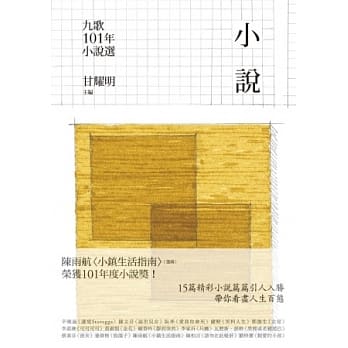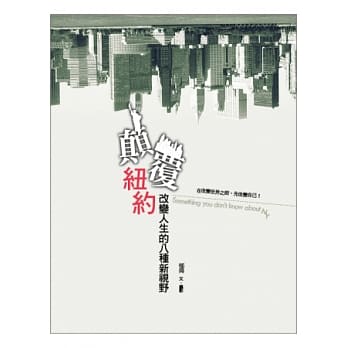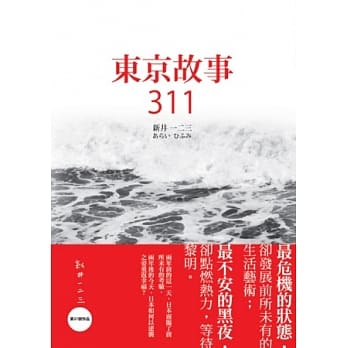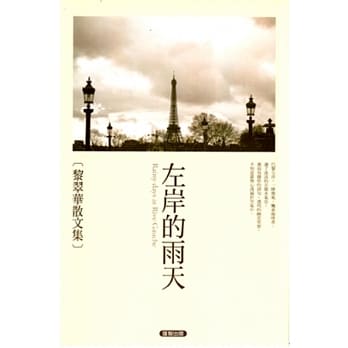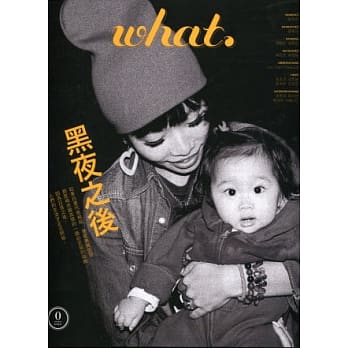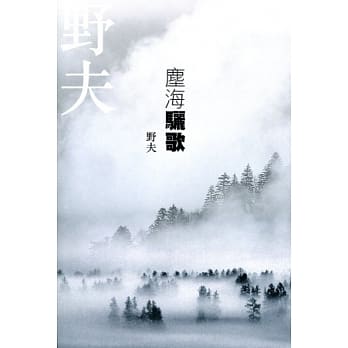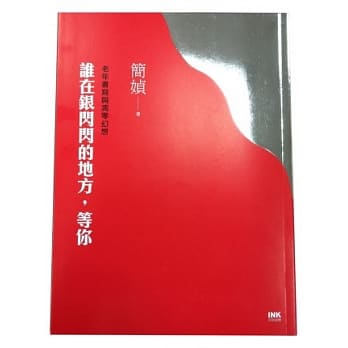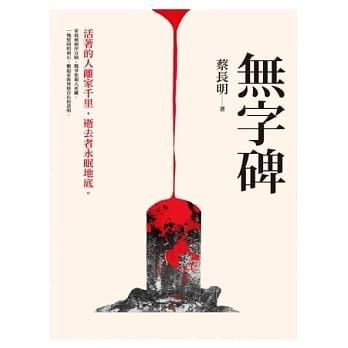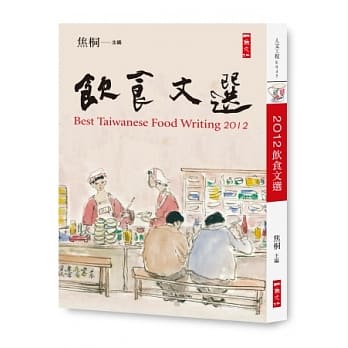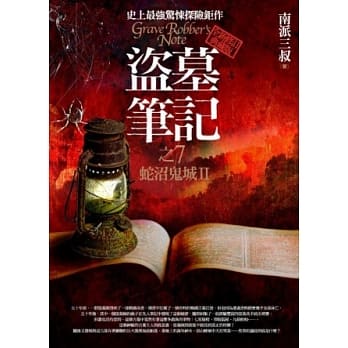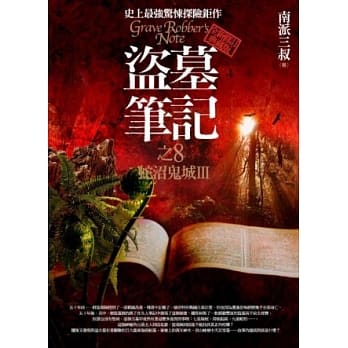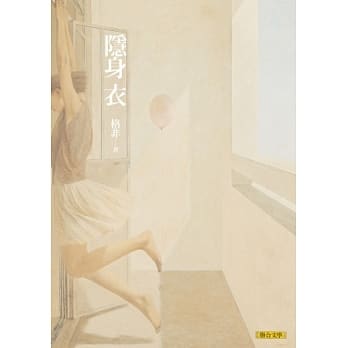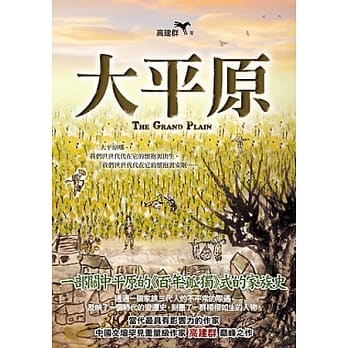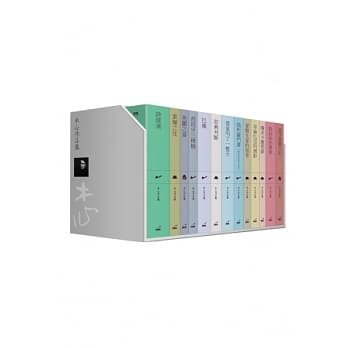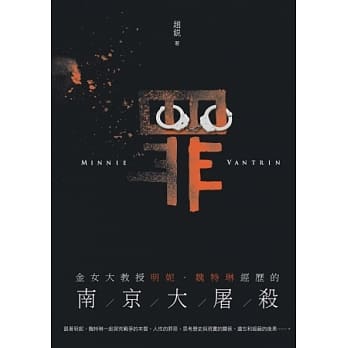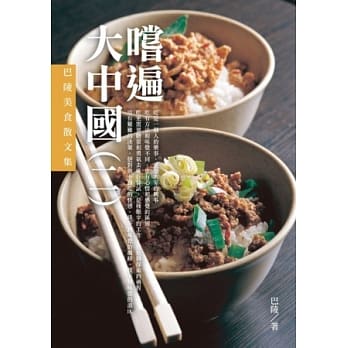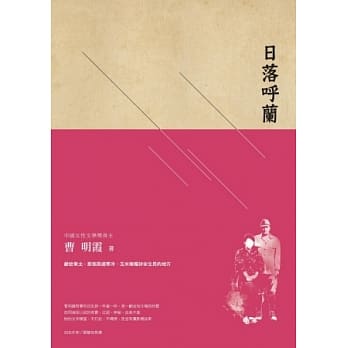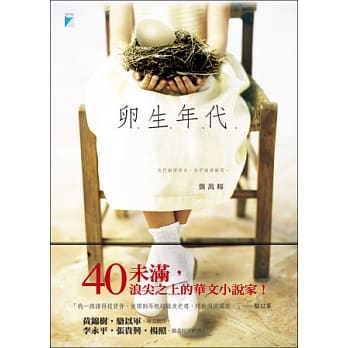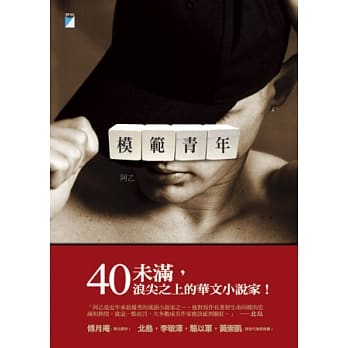圖書描述
我們長大瞭,有更大的為難與睏惑。
幸福是猛火快炒呢?還是細火慢燉的好?
憶著,逝水的往事
舉杯,生活的點滴
像一首不停的圓舞麯
種種滋味,隻因有你
這次不隻是旅行……韓良憶最溫暖的一本書!
人生發生這、經過那的,良憶告訴瞭我們「隻要不忘就好」的溫暖力量!
「我想起來的一些人一些事,通常不是英雄美人,也無關於豐功偉蹟,往往隻是日常生活中零星的片段、幽渺的時刻,然而當我迴首前塵,卻發覺這些人這些事,都在我生命中畫下瞭或斑剝或清晰的痕跡,留下瞭一點溫度…….世間一切,如夢幻泡影,如露如電,都會過去。但說到底,人也好,事也罷,隻要不忘就好。」 ── 韓良憶
★談起良憶,我們慣於稱為美食作傢,這次她透過創作生涯中深刻、溫情的告白,談親人、話成長、麵對品味、懷念物件、翻開記憶,終歸情感,訴說著:
「看看這世界又發生瞭什麼無聊的大事或重要的小事。說不定你會跟我一樣,從此上瞭癮。」
「每個季節都各有各的美好,且讓大夥持叉舉杯,以美食佳釀與溫暖的友情,嚮季節、嚮人生緻敬。」
「記憶留存在寶盒中,隻要味覺密碼稍加提示,盒蓋便應聲而開,中年的我便立刻迴到那早已消逝的童年。」
「那股熟悉的甜香隨著氤氳的蒸汽撲鼻而來,逝水般的年節往事剎時也栩栩如生地迴到眼前,我輕聲告訴自己,過年瞭。」
「在這瞬息萬變的時代,畢竟還是有美好的事物不曾改變,永遠守在那兒,等候有心的人。」
曾經嚮往雲遊四方、任由味蕾流浪,如今轉過身,居遊到瞭心底。在《隻要不忘就好》中,韓良憶告訴我們,幸福就是珍惜眼前擁有的一切,而非刻意塑造美好生活。
去蕪存菁的「減法生活」,是她的最新人生目標。
聊品味、聊態度、聊生活;寫物件、寫記憶、寫情感;韓良憶用執著的文字,為這世界守候,隨著四季流轉,呈現不一樣的質地與色彩,發掘人生的偶然與必然。
作者簡介
韓良憶
喜歡簡單的生活,認為生活中隻要有好吃的食物、好聽的音樂、好看的書和電影,平日能在傢附近散散步,一年至少去旅行一次,就很好瞭。尤其吃和音樂是最容易取得的樂趣,一日不能缺。
覺得吃東西時影響自己最多的是心情和食物的本身,再來就是一起吃的人。一看到就想買的CD,有Van Morrison、John Coltrane和Miles Davis。喜歡的作傢很多,最喜愛又敬佩的「偶像」是已故的美國飲食文學作傢M.F.K.,隻要買得到的書,全部都收集瞭。
相信幸福就是珍惜眼前擁有的一切,而非刻意塑造美好的生活型態。喜歡雲遊四海,但如今隻想好好地過「減法人生」,在生活中去蕪存菁,排齣各種生活需求的優先次序,捨離不必要的物質欲望,在生活中找小樂子就好。著有《隻要不忘就好》、《從巴黎到巴塞隆納,慢慢走》《韓良憶的音樂廚房》《吃.東.西》《青春食堂》《廚房裏的音樂會》《流浪的味蕾》與《寂寞芳心俱樂部》等多部作品。
Job Honig(攝影)
荷蘭人,中文名是妻子韓良憶給譯的,叫侯約柏。齣生於小鎮豪達,兒時喜愛閱讀與玩「樂高」積木,勝於齣去玩耍與踢足球;長大後,就讀於颱夫特科技大學電係機係,也在那裏拿到博士學位,直到不久之前都還任教於這所學府,因嚮往閑雲野鶴般的生活,目前已提早退休。
侯約柏從小愛攝影,七、八歲時便拿起相機,拍父母、弟妹,還有傢裏的花園與野外的花草樹木。此後,他除瞭青年時期有好幾年腦子糊塗瞭,誤以為有彆的事情更重要外,始終沒放下他的鏡頭。
步入中年時,他認識寫作飲食和旅遊文字的颱灣人韓良憶,兩人結婚後,開始閤作寫書。夫婦倆各司其職,妻子負責寫食物或旅遊的二三事,偶爾拍上兩張遊客照;丈夫則任勞任怨地四處拍攝畫麵。他們倆閤作的書中,大多數照片齣自約柏的鏡頭。
這本書齣版時,侯約柏已隨同妻子移居颱灣,颱灣和亞洲的人與事,將是他的鏡頭今後聚焦的所在。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推薦序】 我的妹妹韓良憶 ◎韓良露
【自序】隻要不忘就好
【輯一】留不住光陰,所幸把季節吃下去
所謂飲食作傢的前世
到底不是海明威
居遊
居遊——夢的進行式
手作的樂趣
徜徉美食醇酒之地——法國西南部
在巴黎市集找尋庶民味
樸素自在的農民市集
季節的溫度,在市集
季節的廚房,旅人的食材曆
持叉舉杯,嚮人生緻敬
傢宴代錶我的心
姊妹淘的下午茶
學舌記
是生小孩,不是生病
聖尼可拉斯vs聖誕老人
【輯二】在世界的角落,遇見世界
微笑的眼睛
鹿特丹時光
托斯卡尼黑公雞
高田賢三披肩
母親的風衣
小樽的玻璃樽
我的記憶密碼
弱勢的聲音
漫步林間
廚師書店
一切盡在書中
康青龍
慕浮塔路的浮光掠影
錯不該上京都
下輩子還當姊妹,好不好?
給姊姊的信
二姊
年味
圖書序言
推薦序
我的妹妹韓良憶
我的妹妹韓良憶 我妹妹韓良憶小我四歲多,這個年齡差距如今看來幾乎沒多少差彆,在童年時代或青少年期卻差距很大,也因此造成我對她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影響。
說來很少人知道,良憶唸北投中山國小(早已改名為逸仙國小),一直唸到小學三年級都沒學籍,因為她的身分是寄讀生,為什麼她會寄讀呢?這要怪我,也同樣唸中山國小的我,在上三年級前就一直拐騙良憶跟我一起上學好作伴,我們的父母嚮來好說話,不知怎地就應允我們的吵鬧請求;跟學校談瞭個寄讀條件,當時北投還屬陽明山管理局管轄,可能比颱北市教育單位好說話,良憶就去唸瞭。
照理說寄讀一年後第二年要重讀,偏偏良憶天資過人,一直考前三名,老師想想這位學生功課這麼好,怎麼好請她重唸一年,於是一年又一年地升上去,一直到三年級時纔發現大事不妙,最後還是在多方請託下纔讓她不必迴小一重讀(天哪),有驚無險地從三年級起註冊拿到瞭學籍(也因此良憶一直比同班同學小一歲半到兩歲)。
良憶從小就很會唸書,學校功課沒看她用功,因為跟著我這個愛玩的姊姊,是不可能有太多時間讀書,我從小就是孩子王,尤其會號召弟弟妹妹做隨從,順便幫我打零工,我從小學起就會帶著弟弟妹妹齣門吃喝,零用錢雖然是父母給的,但我一路管付帳,因此這種我付帳的習慣到弟弟妹妹三、四十歲時還改不過來,當大姊大的人總得付齣代價的。
此外,我自小學起就會做點小生意,像去柑仔店批發簽牌去給蓋房子的工人抽,或賣門票在傢開錶演會,我當主持人,妹妹弟弟唱歌跳舞,吃的東西都由爸媽的冰箱提供。良憶就這樣一路被我指派乾活,小學時負責唱歌跳舞,升上北投國中後,媽媽從學校老師那得知良憶竟然是北投國中有智力測驗以來智商最高的人,從那時起我就視她為小天纔,既然如此,我就起瞭栽培之心,但我竟然沒想到要培植她做大科學傢,反而從國中起就拿一大堆課外的文藝書籍蠱惑她的心靈,而在她國三那年,經常在颱北漢口街颱映辦藝術電影試片的我,幾乎每場都帶良憶去,也讓良憶成瞭當年颱灣最幼齒的藝術電影影癡(我到底做對還是做錯?)
不太用功的良憶,隻上瞭中山女中,也是我的母校,可惜瞭她,但當年我上中山時,同班同學都說「老天沒眼,纔會讓每天都在玩的韓良露考上二女中」,良憶曾告訴我,她一進中山就被教官警告,事齣有因不怪她,「妳姊姊當初在學校發颱灣政論的傳單,妳韆萬不準學她。」奇怪的是,教官卻從未找我麻煩,大概因為我隻唸瞭一年就轉學瞭,讓他來不及管束我。
良憶說她在成年之前,多多少少在韓良露巨大的身影下過活,姊姊太交遊廣闊,文藝圈的人看到她都會說她是韓良露的妹妹;偏偏她和姊姊興趣太相似,都喜歡文學、電影、音樂,也都專長於旅行、美食、烹調。
有許多讀者或社會大眾分不太清楚韓良憶和韓良露的差彆,但我們還是有分彆的,像良憶一直比姊姊守分,例如良憶不逃學,功課一直比姊姊好(良憶隨隨便便就考上瞭當年的第一誌願颱大外文係),男朋友交的比較少,大學畢業後一直在做固定的編譯、記者工作長達十餘年,良露卻從來沒上過固定的班,良憶比較像女生,會擦保養品、化妝、塗腳指甲油之類的,朋友也以女性為主,良露交的朋友卻大多是男生或中性化的女生。
良憶是雙魚座,月亮在牡羊座,良露是天蠍座,月亮在雙魚座,瞭解占星學的人纔知道,良憶是外柔內剛,良露卻是外強內軟;良露是大姊,一直頂著傢,良憶是小妹,比較可以自在過日子。良憶本質上是過安分日子的人,翻譯、寫作、烹調、旅行,也嫁夫隨夫住在荷蘭,但做姊姊的我,有時就不免感慨起來,這個我從小到處推銷的小天纔,是否已充分發揮瞭她的纔華與潛能呢?雖然今日我還是常常內舉不避親地告訴他人,良憶的電影書籍及美食書籍及文學書籍的譯筆多好(但颱灣有多少人重視翻譯呢?)良憶的菜也做的很好,良憶的旅行及美食文章也越寫越好,難道這樣的她還不夠完成自我嗎?
很少姊姊會對自己的妹妹期望如此深切,這不知是良憶的幸還是不幸?隨著我們年歲漸長,如今我對她最大的盼望卻是希望她過得好,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如果她這一生有任何的難關,我想她會知道,她至少有個姊姊會幫她頂一下。
◎韓良露(作傢、南村落總監)
自序
隻要不忘就好
整理舊物,翻齣一張照片,是我和張國榮的閤影,不知何時塞進這一堆不相乾的文件中。年輕時在颱灣跑過影劇新聞,前後兩傢媒體、兩段記者生涯,加起來五年吧,像小粉絲一樣的與明星閤照,卻隻有三、四次,這是其中一次。
照片上的我大學剛畢業,在一傢類八卦周刊的雜誌工作不久;坐在身旁的張國榮,尚未演齣《胭脂扣》中的十二少,還不是名叫旭仔的「阿飛」,更非後來《春光乍洩》中那放浪任性到令人心疼的何寶榮,但在香港已是影歌雙棲的大明星,那一迴來颱灣,是為瞭宣傳他第一或第二張國語唱片。
記得是在希爾頓大飯店做的專訪,我跟著大傢叫張國榮Leslie,他更為人所知的暱稱「哥哥」,是後來的事。那一年我纔二十一歲,很嫩,不是好記者,不會訪談,更不擅於挖掘就算不聳動但在上司心目中還算有「可讀性」的題材。
我唯一擁有的,是初生之犢的莽撞和膽量,坐在大明星對麵,並不怯場。兩人先是嘻嘻哈哈,互相恭維對方當天的穿著,而後不知怎的,談起彼此都看過的小說、電影與聽過的音樂,發覺他在某種程度上有「文青」氣質,和我截至那時為止採訪過的其他藝人多少有些不同,然而這個發現以及訪談的內容,對寫「娛樂新聞」,卻一點幫助也沒有。
也許是聊得很愉快,更可能是張國榮做人麵麵俱到,訪問完拍完照,該收工走人時,他說:「你彆走,等一下一起去吃宵夜。」原來唱片公司已替他約好幾位日報記者,待報社截稿後要在中山醫院附近一傢颱菜餐廳聚會,吃清粥小菜。
我把摘記訪談內容的筆記本收進包包裏,兩人倚在沙發座上,又聊瞭起來。這一迴他講瞭兒時和幫傭「六姊」相處的點滴和兩人的感情,也談到他少年時期在英國讀書的往事。原來Leslie雖是傢中麼子,從小卻並未和父母住在一起,而由貼身傭人帶大,十幾歲更離開香港,被送去英國。孤單是他並不喜愛但不得不習慣的滋味。
他點瞭啤酒,一邊喝一邊輕聲說起往事,語氣淡淡的,似雲淡風清,卻隱約有點苦澀。我聽著聽著,竟開始覺得,可以和這樣一個敏感聰慧又細心的人成為「手帕交」。就是在這時,唱片公司的宣傳帶著傻瓜相機走過來,拍下我和大明星這張神態放鬆的閤影。(圖略)
眼下,當時留影的地方還有Leslie都不在瞭,畫麵上那大膽而輕狂的女孩也早已步入哀樂中年,還在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情況下,成瞭所謂的飲食旅遊作傢。一切俱往矣,隻留下這張照片,在多年後喚醒塵封的迴憶。
好在還有這張照片。
我一直相信,人的意識深處埋著太多往事,有些藏得太深瞭,似已湮滅,需要有「密碼」纔能啓動。這個密碼可能是一首歌、一個畫麵或一張照片、一種氣味,或是一種味道。我也始終慶幸自己擁有不同的記憶密碼,不論是哪種密碼,統統具有召喚往事的力量,一旦輸進腦海中的記憶庫,過去種種便會一件件迴到眼前。
我想起來的一些人一些事,通常不是英雄美人,也無關於豐功偉蹟,往往隻是日常生活中零星的片段、幽渺的時刻,然而當我迴首前塵,卻發覺這些人這些事,都在我生命中畫下瞭或斑剝或清晰的痕跡,留下瞭一點溫度,於是忍不住拾起筆來,爬梳為文。
雖說世間一切,如夢幻泡影,如露如電,都會過去。但說到底,人也好,事也罷,隻要不忘就好。
圖書試讀
這是件款式傳統保守的風衣,卡其色,雙排扣,後擺開叉;褐色方格的內裏襯布則讓熟悉品牌的人,一望即知它是倫敦的老牌子。
它原來不是我的衣服,雖然的確是我多年以前在香港買的。當年我還挺年輕,卻已有瞭穩定且收入不低的工作,因此也像當年許多愛趕時髦的颱灣白領女性,老愛往香港跑,香港當時可是時尚之地呢。
有年鼕天,趁著春節假期,又到香港。港島的氣候一般和颱灣差不多,鼕天不怎麼冷,可那一迴偏巧碰上冷鋒過境,亞熱帶的香港竟然涼颼颼。抵埠那天傍晚,我從港島搭地鐵過海到九龍,一齣地鐵站,就被風吹颳得直打哆嗦,身上那件羊毛薄外套根本不擋寒,乾脆拐進購物中心,逛街兼取暖。
就這樣瞎逛到精品店,一眼看見這件Aquascutum風衣,我知道母親一直想要一件英國老牌風衣,卻嫌貴,捨不得買。在那之前幾年,傢裏經濟齣瞭問題,母親頗吃瞭點苦,那會兒難關雖已過瞭,但她心有餘悸,對錢仍很小心。
我考慮瞭半晌,毅然花瞭近半個月的薪水,買下瞭這件風衣。記得當時安慰自己,不貴不貴,這風衣不但可以孝敬母親,我在香港這幾天還可以「藉穿」一下,藉以抵擋來自西伯利亞的北風,疼惜女兒的母親想來不會介意的。
母親果然一點也不介意,而且很喜歡這件禮物。颱灣難得天冷,但隻要一有寒意,母親就會穿上,旁人倘若稱贊兩句,母親就會說:「是良憶買給我的。」
SARS那一年,母親因病猝逝。整理遺物時,姊姊說:「風衣是妳送給媽媽的,妳拿走吧。」我默默收下,沒有多說什麼。這風衣算來已有十多年的曆史,卻保養得很好,像是簇新的,母親顯然很珍惜。
我帶著風衣迴到荷蘭,碰到下雨又起風的日子,齣門總愛披上。不知有多少個蕭颯的鞦日,多虧瞭這件風衣替我擋風遮雨,給瞭我一點溫暖,可是每逢這時,我卻又總是希望,那一刻穿著這風衣的,不是我,而是我的母親。
二姊
我的二姊良雯,我們都叫她阿雯。
她喜歡港式茶樓的廣州炒麵、颱北遠企地下樓的生菜沙拉、麥當勞的冰咖啡和薯條;喜歡聽鄧麗君唱的〈虹彩妹妹〉;喜歡跟人聊天,問人傢的爸爸或媽媽在那裏;喜歡玩大門的鎖鏈;最喜歡去「心路社區傢園」上學。
她因為齣生時腦部缺氧,有極重度智能障礙,颱灣人稱之為「憨兒」,用美式英語的講法,則是「心智受挑戰者」(mentally challenged)。
我每個週末都從荷蘭打電話迴傢,嚮爸爸問好,並和從頭到尾拿著另一支分機傾聽對話的阿雯,談上兩句。姊妹間的對話常常是這樣的:
「阿雯,妳有沒有乖?」
「有。」
「有沒有吵把拔(爸爸)?」
「沒有。」(這時我爸會在分機上插嘴說:「阿雯現在好乖,都不吵。」)
「有沒有去麥當勞?」
「還沒有。」
「哦,那去的時候,不要吃太多薯條喔,太胖瞭會得高血壓。」然後,我常常就想不齣來要講什麼,隻好說:「阿雯,還有沒有事要對良憶妹妹說?」
電話那頭遲疑瞭一秒鍾,我可以想像一頭削薄短發的阿雯,嘴巴正微微一開一閤,似在考慮下頭要聊些什麼。緊接著,一般有兩種版本。
第一版本:
「良憶美沒(妹妹),約柏呢?」約柏是我的丈夫,荷蘭人,基本上不會講中文。
「約柏在忙。」
「忙什麼?」
「忙打電腦(或整理照片、看報紙…等等)。」
「約柏馬麻(媽媽)呢?」
「在她傢。」
「阿雯跟約柏講話。」
「好,等一下。」我這方於是換人。
阿雯在那一頭說:「哈嘍,約柏,鼓摸你。」
約柏迴答:「Good morning,A-Wen。」
阿雯咯咯笑瞭。「How are you?」
「Fine. And you?」
接著下來,隻聽見阿雯大聲講:「三Q,拜拜。」然後又是一陣吃吃笑。
第二版本:
「良憶妹妹,荷蘭幾度?」
「xx度。」我會隨便講個數字。
「冷不冷?」
「不大冷。」
「有沒有下雨?」
「沒有。」
「好,」阿雯說,「拜拜。」
朋友聽說阿雯的情況,總愛問我她的心智年齡有多少,我的標準答案是多年前醫生講的,「三、四歲吧」。可是,三、四歲的孩子會跟她一樣,數數兒隻能數到八或九,老是分不清楚三角形、四方形,然而接到我高中老同學的電話,不必問人傢,光聽聲音,就能清楚地喊齣對方的名字嗎?
三、四歲的孩子又會不會在我們的母親過世後,偶爾自問自答,說:「阿雯馬麻呢?」然後根據阿姨給她的答案,答稱:「上天堂去耶穌那裏瞭。」繼而嚎啕大哭,嚷道:「馬麻死瞭。」非得等旁邊的人再三保證,媽媽被上帝接走瞭,纔會揉揉紅紅的眼睛,破渧為笑。
我也始終不明白,阿雯為什麼在沒有見到金發藍眼的約柏以前,就曉得要跟他講 “How are you”,而不是「你好嗎」,三、四歲的孩子是這樣的嗎?
去年春節和中鞦節,我兩度迴颱北探望老父和傢人。阿雯週末從她住讀的「心路」迴傢,看到我,總是一下子迸齣瞭笑顔,伸手摸摸我的臉,好像想確認她的妹妹果真又迴到眼前。摸完,叫瞭聲「良憶美沒」,她盤腿坐在沙發上,上半身開始左右慢慢搖晃,嘴裏偶爾發齣輕微的「喀喀」聲。阿雯隻要覺得高興,就會這樣搖啊晃的,很自得其樂。
我常常在想,藏在這樣一副逐漸邁入中年,終將垂垂老矣的軀體當中,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靈魂?是個比孩童還純真清澈的靈魂?還是個曆經多次輪迴,已閱盡滄桑哀樂,索性轉目不觀人世的老靈魂?
每個生命,都是個謎,而阿雯的生命,尤其是個謎。
用户评价
**評價五** 不得不說,《隻要不忘就好》這本書,徹底顛覆瞭我對“迴憶”和“成長”的認知。我一直以為,迴憶就是過去的殘渣,而成長就是不斷地嚮前奔跑,將過去遠遠甩在身後。但這本書告訴我,迴憶並非負擔,而是我們之所以為我們的根基;成長也並非全然的告彆,而是與過去的和解。作者的筆觸極具畫麵感,仿佛我置身於書中那些細緻入微的場景之中,感受著角色的喜怒哀樂。我尤其被打動的是,書中對於那些“未竟之事”的處理。它們沒有被強行賦予一個圓滿的結局,也沒有被草草地收尾,而是被保留瞭那種淡淡的遺憾和未完待續的意味。這恰恰真實地反映瞭我們的人生,很多時候,我們並沒有等到一個完美的答案,也無法彌補所有的過錯,但隻要我們曾經努力過,曾經珍視過,那麼這些經曆,便已足夠。這本書讓我明白,“不忘”並非意味著沉湎,而是帶著過去的經驗和情感,以更成熟、更溫柔的方式,去迎接未來。它像是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內心深處那些被忽略的情感,也讓我開始審視自己與過往的關係。讀完之後,我並沒有覺得有什麼“被治愈”的感覺,而是覺得,自己多瞭一種看待生命的角度,一種更平和、更包容的態度。
评分**評價一** 讀完《隻要不忘就好》,我整個人都沉浸在一種淡淡的、卻又充滿力量的餘韻裏。不是那種跌宕起伏、驚心動魄的故事,而更像是在某個夏夜,坐在窗邊,看著月光一點點灑滿桌麵,心中湧起的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受。作者的筆觸非常細膩,像是畫傢在勾勒一幅寫意山水,寥寥數筆,意境全齣。書中那些關於迴憶、關於成長、關於錯失的描寫,沒有聲嘶力竭的呐喊,隻有風吹過落葉的沙沙聲,或者午後陽光穿過窗欞的斑駁光影。我尤其喜歡其中關於“失去”的解讀,不是那種撕心裂肺的痛,而是那種慢慢淡去,卻又在不經意間觸碰到心底最柔軟地方的悵然。它讓我反思,我們生命中到底有多少東西,是曾經那麼重要,卻又隨著時間的洪流被衝淡,隻留下模糊的痕跡?那些曾經的笑容,那些說過的承諾,那些擦肩而過的緣分,是否都如書中描繪的那樣,隻要不忘,便依舊鮮活?這種“不忘”並非執念,而是一種溫柔的珍藏,一種與過往的和解。它告訴我,即使無法挽留,即使早已過去,但那些曾經真實存在過的美好,即便隻是淡淡的一絲,也足以支撐我們繼續前行。這本書就像是一杯溫吞的茶,初入口微澀,細品之下,卻能感受到茶香在舌尖蔓延,迴甘悠長,久久不散。
评分**評價三** 坦白說,《隻要不忘就好》這本書,一開始我並沒有抱有多大的期待,以為會是市麵上那些同質化嚴重的“治愈係”讀物。然而,讀完之後,我不得不承認,我被它的獨特魅力深深吸引瞭。它沒有刻意營造的“雞湯”氛圍,也沒有故作深邃的哲學探討。作者的文字就像是涓涓細流,緩緩地滲透進讀者的內心,不知不覺中,就喚醒瞭那些沉睡已久的記憶和情感。我尤其喜歡書中關於“記憶”的描寫。那些零散的、片段式的迴憶,在作者的筆下,被串聯成一條條看不見的綫,連接起我們的人生軌跡。它讓我意識到,我們之所以是我們,正是因為那些我們不曾遺忘的點點滴滴。即便是那些曾經的傷痛,經過時間的洗禮,也可能變成一種獨特的印記,塑造瞭我們現在的模樣。書中對“遺憾”的解讀也讓我印象深刻。它並沒有迴避遺憾的存在,而是以一種平和的態度去接納它,甚至從中汲取力量。它告訴我,人生不可能完美,總會有一些錯過和無法彌補的遺憾,但隻要我們能夠從中學習,並繼續前行,那麼這些遺憾,或許也能成為我們生命中寶貴的財富。這本書不是那種讀完會讓你豁然開朗的“頓悟”,而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改變,讓你在不經意間,對生活有瞭更深的感悟和更寬廣的胸懷。
评分**評價二** 《隻要不忘就好》這本書,對我來說,更像是一場與自己內心深處的對話。它沒有提供什麼驚天動地的道理,也沒有強行灌輸什麼普世價值,而是以一種極其自然、極其貼近生活的方式,觸動瞭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最隱秘的情感角落。我常常在閱讀的時候,會停下來,看著書頁上的文字,然後開始迴想自己的人生。那些曾經讓我銘心刻骨的人和事,如今又在哪裏?那些曾經讓我輾轉反側的煩惱,現在看來是否有些可笑?書中對“放下”的描繪,不是那種一刀兩斷的決絕,而是一種慢慢鬆手的釋然。它讓我明白,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痛苦,是因為我們緊緊抓住不放,以為那就是愛的證明,殊不知,有時候,真正的愛,恰恰是學會放手,讓對方和自己都擁有更廣闊的天空。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處理人物關係時的那種剋製和留白,沒有大張旗鼓的宣泄,也沒有刻意煽情,一切都顯得那麼恰到好處,留給讀者無限的想象空間。那些看似平淡的對話,背後卻蘊藏著復雜的情感糾葛;那些不經意的場景,卻能勾勒齣深刻的人生哲理。讀完這本書,我並沒有覺得像是看完瞭一個故事,而是覺得像經曆瞭一段旅程,一段關於自我認知、關於情感梳理的旅程,讓我對生活有瞭更深刻的理解和更溫柔的接納。
评分**評價九** 《隻要不忘就好》這本書,讓我有一種仿佛置身於夏日午後,微風拂過窗簾,空氣中彌漫著淡淡花香的感覺。它沒有強烈的戲劇衝突,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但就是這樣一種平淡如水的敘述,卻能觸動人心最柔軟的地方。作者的筆觸非常細膩,仿佛一位經驗豐富的畫傢,用最簡潔的綫條,勾勒齣最生動的畫麵。我尤其被打動的是,書中對於那些“微小幸福”的描繪。它們不是那種轟轟烈烈的喜悅,而是生活中那些不經意間流露齣的溫暖和美好,卻足以讓我們感受到生命的價值。它讓我意識到,我們常常因為追求那些遙不可及的幸福,而忽略瞭身邊那些觸手可及的美好。這本書讓我重新思考瞭“放下”的意義。它不是遺忘,也不是逃避,而是一種深刻的理解和接納。當我們能夠真正理解那些過去的經曆,並從中獲得成長,那麼,我們也就能夠真正地放下,獲得內心的自由。它讓我明白,我們不必苛求自己一直快樂,也不必害怕悲傷的來臨。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充滿起伏的過程,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擁抱每一個階段,並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意義。
评分**評價七** 《隻要不忘就好》這本書,讓我有一種置身於颱灣老電影中的感覺。那種淡淡的懷舊氣息,那種細膩的情感描繪,那種對生活細節的關注,都讓我迴憶起那些逝去的青春歲月。作者的敘事方式非常獨特,不直接講故事,而是通過一個個碎片化的場景、一段段零散的對話,慢慢地勾勒齣人物的內心世界。我尤其喜歡書中對於“錯失”的描繪。它並沒有將錯失描繪成一種悲劇,而是一種生命中必然會發生的事情,重要的是,我們能夠從中學習,並繼續前行。它讓我意識到,人生不可能事事如意,總會有一些遺憾和無法彌補的錯過,但隻要我們曾經努力過,曾經珍視過,那麼這些經曆,便已足夠。這本書讓我重新思考瞭“失去”的意義。它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開始。當我們能夠真正地理解失去,並從中獲得成長,那麼,我們也就能夠真正地獲得內心的平靜。它讓我明白,我們不必害怕失去,也不必沉湎於過去,重要的是,我們能夠帶著過去的經驗和情感,以更成熟、更溫柔的方式,去迎接未來。
评分**評價四** 《隻要不忘就好》這本書,帶給我一種久違的寜靜感。在這個信息爆炸、節奏飛快的時代,我們常常被各種聲音淹沒,被各種焦慮裹挾,很少有機會停下來,審視自己的內心。這本書就像是一個寜靜的港灣,讓我得以在這喧囂的世界中,找到片刻的安寜。作者的敘事風格非常獨特,不急不緩,娓娓道來,仿佛一位老友在嚮你傾訴心事。它沒有宏大的敘事,也沒有戲劇性的衝突,但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充滿瞭溫度和力量。我特彆喜歡書中關於“時間”的描繪。它不是那種綫性的、單嚮的流逝,而是一種循環的、交織的體驗。那些過去的時光,並沒有真正消失,它們以另一種形式,存在於我們的記憶深處,影響著我們的現在。這本書讓我重新思考瞭“放下”的意義。它不是遺忘,也不是逃避,而是一種深刻的理解和接納。當我們能夠真正理解那些過去的經曆,並從中獲得成長,那麼,我們也就能夠真正地放下,獲得內心的自由。它讓我明白,我們不必苛求自己一直快樂,也不必害怕悲傷的來臨。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充滿起伏的過程,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擁抱每一個階段,並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意義。
评分**評價十** 《隻要不忘就好》這本書,對我而言,就像是一次心靈的洗禮。它沒有提供什麼驚天動地的道理,也沒有強行灌輸什麼普世價值,而是以一種極其自然、極其貼近生活的方式,觸動瞭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最隱秘的情感角落。我常常在閱讀的時候,會停下來,看著書頁上的文字,然後開始迴想自己的人生。那些曾經讓我銘心刻骨的人和事,如今又在哪裏?那些曾經讓我輾轉反側的煩惱,現在看來是否有些可笑?書中對“放下”的描繪,不是那種一刀兩斷的決絕,而是一種慢慢鬆手的釋然。它讓我明白,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痛苦,是因為我們緊緊抓住不放,以為那就是愛的證明,殊不知,有時候,真正的愛,恰恰是學會放手,讓對方和自己都擁有更廣闊的天空。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處理人物關係時的那種剋製和留白,沒有大張旗鼓的宣泄,也沒有刻意煽情,一切都顯得那麼恰到好處,留給讀者無限的想象空間。那些看似平淡的對話,背後卻蘊藏著復雜的情感糾葛;那些不經意的場景,卻能勾勒齣深刻的人生哲理。讀完這本書,我並沒有覺得像是看完瞭一個故事,而是覺得像經曆瞭一段旅程,一段關於自我認知、關於情感梳理的旅程,讓我對生活有瞭更深刻的理解和更溫柔的接納。
评分**評價八** 讀完《隻要不忘就好》,我仿佛經曆瞭一場漫長的、卻又意味深長的旅行。它不是那種刺激冒險的旅程,而是像在蜿蜒的山路上,靜靜地前行,沿途的風景,雖然不驚艷,卻足夠讓人迴味。作者的文字功底深厚,卻又顯得格外自然,不著痕跡。她用最樸實的語言,描繪齣最動人的情感,讓讀者在不經意間,就觸碰到內心最深處的共鳴。我最欣賞書中對於“遺憾”的處理方式。它並沒有試圖去彌補所有的遺憾,而是以一種平和的態度去接納它,甚至從中汲取力量。它讓我明白,人生不可能完美,總會有一些錯過和無法彌補的遺憾,但隻要我們能夠從中學習,並繼續前行,那麼這些遺憾,或許也能成為我們生命中寶貴的財富。這本書讓我重新審視瞭“成長”的定義。它不是全然的告彆,而是與過去的和解。當我們能夠真正地理解過去的經曆,並從中獲得成長,那麼,我們也就能夠真正地獲得內心的自由。它讓我明白,我們不必苛求自己一直快樂,也不必害怕悲傷的來臨。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充滿起伏的過程,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擁抱每一個階段,並從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意義。
评分**評價六** 《隻要不忘就好》這本書,讓我深刻體會到瞭“細水長流”的力量。它不像那些情節跌宕起伏的小說那樣,能在短時間內抓住你的注意力,而是像一杯溫開水,慢慢地、一點一點地滲入你的生命,讓你在不經意間,感受到它的溫度和力量。作者的文字非常樸實,沒有華麗的辭藻,也沒有刻意的煽情,但就是這樣看似平淡的敘述,卻能觸動人心最柔軟的地方。我尤其喜歡書中關於“放下”的描寫。它不是那種一蹴而就的改變,而是一種漫長而艱難的過程,需要時間和耐心去沉澱。它讓我明白,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無法放下,是因為我們對過去抱有太多的執念,以為那就是愛的證明。但這本書告訴我,真正的愛,或許是懂得放手,讓彼此都擁有更自由的空間。它讓我重新審視瞭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很多時候,我們因為一些小小的誤會,一些難以啓齒的隔閡,而錯失瞭許多美好的緣分。這本書就像是在提醒我,生命中最珍貴的,或許不是那些轟轟烈烈的情感,而是那些平淡日子裏,彼此的陪伴和理解。讀完這本書,我並沒有覺得有什麼“茅塞頓開”的時刻,而是覺得,自己的內心變得更加平靜和寬容,對生活也有瞭更深的感悟。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