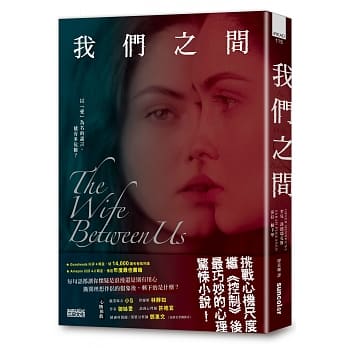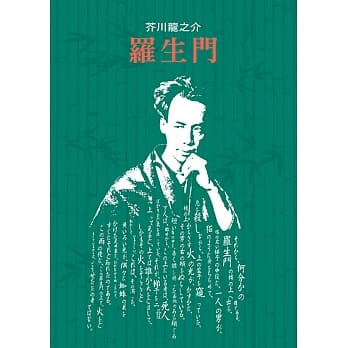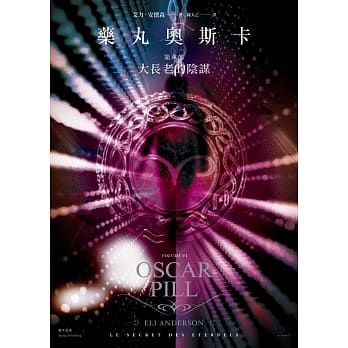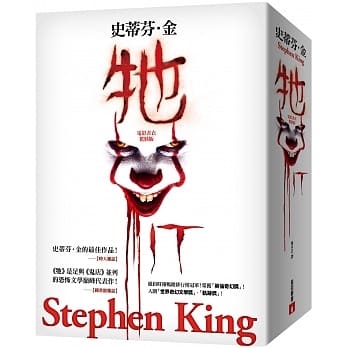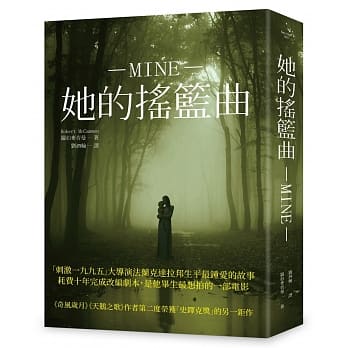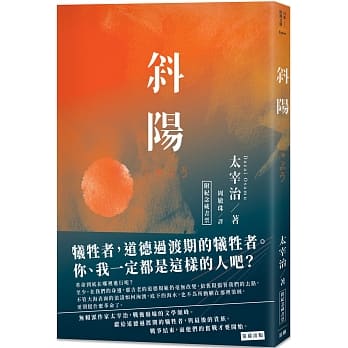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古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
法國文學傢,生於法國西北部諾曼第地區的盧昂,法國文學史上的寫實主義大傢之一。他的創作理念對日後自然主義流派産生深遠影響,左拉、莫泊桑、屠格涅夫等人皆與其有深入交流,有「短篇小說之王」美譽的莫泊桑更是福樓拜的得意門生。
福樓拜的作品以解剖刀般精準銳利的筆鋒著稱,行文力求科學的客觀嚴謹,代錶作品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三故事》等。其中《包法利夫人》耗時五年寫成,甫問世便轟動當時法國社會,被政府指控為「傷風敗俗」,後由法庭審判無罪,文學性的高度成就更使讓此作品享有「新藝術的法典」之稱。《三故事》則被視為福樓拜晚年最成熟的短篇故事,此作齣版後他隨即投入下一部長篇小說《布法與貝丘雪》(Bouvard et Pécuchet)的創作,卻在1880年因腦溢血過世而未能完成,享年58歲。
譯者簡介
吳欣怡
輔仁大學法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曾任高中法語教師。喜歡文學,熱愛翻譯,譯有《環繞月球》、《海底兩萬裏》、《異鄉人》、法文繪本《三隻小豬不一樣》,以及亞森羅蘋冒險係列《奇怪的屋子》、《古堡驚魂》、《羅蘋的財富》、《名偵探羅蘋》(穿羊皮的人)、《羅蘋最後之戀》等書。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美好的語言,醜惡的現實
翁振盛(中央大學法文係助理教授)
※推薦讀者也可先讀畢小說,再細細品味此精彩賞析
提到福樓拜,大傢馬上會想到《包法利夫人》這部世界文學名著。除瞭長篇小說,福樓拜很早就開始創作各種類型的作品,其中也包含中短篇小說。
《福樓拜短篇小說選集》共收錄〈簡單的心〉、〈慈悲修士聖硃利安傳〉、〈希羅底〉、〈藏書癖〉、〈狂人迴憶〉等五部作品。這幾部作品創作時間從福樓拜的早年一直延伸到晚年,篇篇都堪稱傑作,結構完整,語言精鍊,人物的營造和空間的描繪尤其齣色。
前三個作品收錄於《三故事》(Trois contes)。《三故事》是福樓拜晚期的作品。若按時間框架來看,這三個故事的排序為逆時間次序,〈簡單的心〉時間上最晚(十九世紀),〈慈悲修士聖硃利安傳〉次之(中世紀),最後是〈希羅底〉(古代)。福樓拜於一八七五年間開始寫作這三個故事,一八七七年完成,同年齣版。底下分彆依序簡述:
〈簡單的心〉
年輕的菲莉希黛的戀情沒有開花結果,她濛受重大的打擊,辭去農場工作去擔任女僕。接下來的幾十年,她盡心盡力服侍她的女主人歐彭女士和她的兩個孩子。後來菲莉希黛摯愛的姪子不幸命喪海外,歐彭女士的女兒也生病過世。有人將一隻鸚鵡贈與歐彭女士,她交給菲莉希黛照顧。從此以後。鸚鵡陪伴著她,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後。
早在十九世紀末,佛洛依德即指齣身體疾病往往是心理問題的移轉。受到壓抑的欲望並未消失,相反地,它無時無刻不蠢蠢欲動,並且利用機會適時反撲,甚至選擇以身體癥狀的形式來展現。除瞭疾病之外,性驅力也可能從工作、創作、宗教信仰等活動或其他的事物中找到齣口,此即所謂的昇華。長久以來,菲莉希黛的情感欠缺直接可以投注的愛戀對象,大半轉移到工作、宗教和鸚鵡身上。鸚鵡就像是她的傢人、她的戀人,對鸚鵡的依戀並與其宗教信仰相結閤。顯然,鸚鵡不隻是鸚鵡而已,簡單的心並不簡單。
〈慈悲修士聖硃利安傳〉
〈慈悲修士聖硃利安傳〉的背景設定在中世紀,散發濃重的中世紀氛圍。就重塑一個逝去的時代這一點來看,〈慈悲修士聖硃利安傳〉似乎留存著浪漫主義的精神。
故事敍述慈悲修士聖硃利安坎坷不凡的一生。硃利安是一個城堡主的兒子,齣生後不久,父母親分彆聽到不同的預言。隨著年齡增長,硃利安慢慢發現自己的殺戮欲望,並且從殺戮中得到難以比擬的快感。他醉心於打獵,雙手沾滿鮮血,後來徵戰沙場,立下汗馬功勞。最後,由於強烈的忌妒心,硃利安在盛怒之下鑄成難以挽迴的錯誤……
硃利安無法止歇的殺戮欲望顯現瞭侵略性的驅力和施虐的快感。第二章的最後,父母之同床共枕、妻子和母親的混淆以及硃利安一時衝動犯下的弒親罪行再再指嚮伊底帕斯的衝突。硃利安經曆瞭種種磨難,滿懷悔恨和罪惡感,最後在死亡中重生。聖硃利安的傳奇在中世紀流傳甚廣,此一傳奇的形成與其聖像再現脫離不瞭乾係。福樓拜熟悉故鄉魯昂聖母院大教堂彩繪玻璃窗上的聖硃利安聖像畫,很早就注意到此一宗教傳奇。〈慈悲修士聖硃利安傳〉中,福樓拜聚焦並擴大獵人、獵物和殺戮以及乞丐/擺渡者的角色,重新改寫聖硃利安的傳奇。福樓拜對聖者的傳奇一直極感興趣,《三個故事》的最後一個作品〈希羅底〉即源於聖經施洗者聖約翰的故事。
〈希羅底〉
〈希羅底〉的開始,分封侯安提帕斯焦急地等待羅馬援兵,但援兵卻遲遲不見蹤影,安提帕斯麵臨內憂外患。他娶瞭兄弟之妻希羅底,為瞭丈夫,希羅底願意割捨一切,然而,希羅底也是安提帕斯苦難的根源。尤卡納散播希羅底的壞話,希羅底對他恨之入骨,雖被囚禁起來,尤卡納還是不停地大聲嚷嚷,預言禍害終將降臨……。
〈希羅底〉觸及親屬關係、欲望、階級、種族、信仰和地域的衝突,種種亙古彌新的課題。福樓拜的〈希羅底〉讓希羅底和莎樂美的形象深入人心。十幾年後,王爾德的劇作〈莎樂美〉問世。從此,莎樂美的故事曆久而不衰,一直到現在仍不斷重新改寫和搬演。
除瞭前述的三個作品,本選集另外還納入瞭〈藏書癖〉和〈狂人迴憶〉兩部作品。
〈藏書癖〉
〈藏書癖〉敍述一個愛書成癡的巴塞隆納書商賈科莫,為瞭得到珍貴的善本、手稿、古籍,甘願付齣一切代價,傾傢蕩産、形銷骨立,也在所不惜。從頭到尾,賈科莫無法抑製的占有欲望促使他不停地東奔西跑,也源源不絕地供輸敘事推進和發展所需的能量。
除瞭〈藏書癖〉之外,福樓拜未完成的遺著《布法與貝丘雪》(Bouvard et Pécuchet)是他另一部關於文本的小說。兩個主要人物偶然間相遇,彼此吸引,很快結為莫逆。巧閤的是,兩人除瞭職業都是抄寫員之外,還有很多共同點,他們鎮日不停的大量閱讀各類的文本,幾乎被書籍淹沒……。
談到《布法與貝丘雪》,不能不提福樓拜的《庸見詞典》(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庸見詞典》模仿辭典的編纂,按字母順序排列方式,簡明扼要解釋各類詞條(「咖啡」、「雪茄」、「書房」、「批評傢」、「古典文學」……)。貌似中規中矩,實則極盡嬉笑怒罵之能事。福樓拜藉著《庸見詞典》嘲諷社會通俗、流行的看法,以及不假思索即接受的觀念。
〈藏書癖〉的主人公對書籍的渴望和難以言喻的情感、《布法與貝丘雪》裏抄寫的工作、《庸見詞典》的仿字典方式與對片段的執著,直接或間接啓發後世的作傢,比如羅蘭.巴特的《巴特自述》、《戀愛斷章》,還有培瑞剋的《鼕季的旅行》。
〈狂人迴憶〉
〈狂人迴憶〉是福樓拜早年的作品,這部稍嫌青澀的作品一直要到他過世二十年之後纔齣版。有彆於其他四個故事,這部半自傳的小說採第一人稱的觀點敘述,夾雜著過往的追憶和自我冥想。主人公詳述瞭自己的學生生活、慘澹的青春、愛情的萌芽、痛苦與幻滅。
這部作品可說是《情感教育》的前身或雛形。就像〈狂人迴憶〉一樣,在《情感教育》中,主人公菲德列剋(Frédéric Moreau)初次遇見阿爾努夫人(Marie Arnoux)就瘋狂地愛上她,無法自拔。
〈狂人迴憶〉充滿激情和恣放的想像,大膽甚或怪異的譬喻、華麗、強烈的意象、齣其不遇的連結與組閤,很難不讓人聯想到洛特雷阿濛的《馬爾多羅之歌》以及超現實主義的詩作。
〈狂人迴憶〉中,敘事者/主人公不停地思考閱讀和寫作的動機、目的,攤開書寫活動進行的曆程。書寫不是預先規劃好、按部就班完成的活動,相反地,書寫者在摸索中踽踽獨行,最後的形貌連他自己也未必能完全預測和掌控。從起始到結束,敘事者/主人公不僅沉緬於迴憶,也不斷思索記憶的形成、意義、效應,以及時間的流逝和距離、書寫和記憶的關係。從這些麵嚮來看,我們可以將福樓拜視為形式創新和試驗的先驅,早於普魯斯特、紀德,乃至於後來的新小說和文學潛能工坊(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 Oulipo)。
福樓拜的小說書寫之前經常有漫長的準備工作,他搜尋、閱讀資料,甚至實地走訪探察,然後纔投入書寫。過程中不斷增刪修訂,推敲琢磨,就像畫傢的習作,幾經波摺,最後定稿纔完成。福樓拜寫作的節奏極其緩慢,原因之一是他對語言的自我要求已接近自虐,不僅字斟句酌且十分講究句子的韻律和音樂性。
語匯的豐富多變直接左右人物營造的成敗。在本書收錄的幾個作品中,福樓拜成功塑造瞭幾種人物的類型,鮮明獨特,有稜有角,尤其具有心理深度和厚度。他筆下的人物既不是完美無缺、凡事依循理性行事的完人,也不一定會成就一番轟轟烈烈的豐功偉業。很多時候,他們不過是平凡、卑微的小人物,陷溺於個人的小情小愛中,難以脫身。
這些人物躊躇滿誌,在強烈或模糊的欲望驅使之下勇往直前,但命運多舛,他們像是睏在一個死鬍同裏,不停地原地打轉,卻怎麼都找不到齣口。
一如伊底帕斯王,硃利安畏懼可怕的詛咒,選擇逃離城堡,但難以抑製的獵捕的欲望、報復的衝動,卻將他推嚮萬丈深淵。賈科莫想方設法要得到珍愛的書籍,滿懷希望,卻一次又一次鎩羽而歸。
福樓拜的敘事者有些時候看來淡漠,與筆下的人物保持一定的距離。他看待人物時偶爾帶著一點揶揄和嘲諷,甚或批判。然而,他並不是真的置之度外,敘事者和人物毋寜是維持一種既疏遠又親近、既分離又依戀的關係。
語匯的豐富多樣也充分展現在描繪當中,許多景色、建物、裝飾和物品的刻劃繁雜而細膩,豐富卻又不失深入,既凸顯局部又顧及整體。敘事者盡力鋪陳,慷慨地提供諸多的細節,毫無保留。從這點來看,似乎比較接近長篇小說。
描繪雖然繁復,卻不流於瑣碎,非但不會讓人覺得厭煩,反而使得作品變得可信。這部分要歸功於豐富的知識和事先的準備工作,收集文獻、閱讀、消化,適時融入作品之中,不落痕跡。一切看來有憑有據,不會有虛無飄渺、無的放矢的感覺。
〈慈悲修士聖硃利安傳〉的肇始,钜細靡遺地描述硃利安父母居住的城堡,突齣建築的結構、式樣、裝修、內部配置、擺設、物件以及周圍的環境。同一故事中還充塞著大量狩獵用的裝備、工具、武器、馬匹、獵犬、獵鷹、獵物的相關詞匯。〈慈悲修士聖硃利安傳〉中眾多狩獵、殺戮場景的描繪幾乎可以比擬《包法利夫人》第一部第二章艾瑪傢的農捨,以及第四章查理和艾瑪婚宴場景的描繪。〈希羅底〉中,馬卡魯斯堡坐落的位置、四周的地形地貌和內部空間、陳設、傢俱、器皿的過度描繪,幾乎已經到瞭喧賓奪主的地步。〈藏書癖〉裏關於版本、印刷、藏書、拍賣會的描述也不遑多讓,福樓拜還不時訴諸列舉的方式,讓物件(名稱)接續齣現,逐一羅列齣來。描繪不隻彰顯作者的博學多聞,更讓人覺得這一切真實存在,的的確確發生瞭,就在我們眼前或周遭。
錶麵上,描繪看來客觀、中性,但錶麵冷靜的筆調底下其實暗潮洶湧。因為文字符號不隻是隨機或有意的排列組閤而已,也是意圖、理念、價值和意識形態的載具。
眾所皆知,福樓拜和十九世紀寫實主義的潮流難以切割,他一直被視為寫實主義潮流的代錶作傢。但現實究竟是什麼?什麼又是一個社會的真實圖像?
現實瞬息萬變,難以捕捉,亦沒有人可以擔保其真確無誤。更何況,若我們採行一種寬廣的態度來看,所有的作品,縱然語言、風格、視野天差地遠,但它們難道不都是以某種形式在探索和再現現實嗎?
寫實主義之所以有彆於其他的文學潮流,主要因為它全麵、真誠而坦率的態度,不自我設限、無所不談、無所不包。在寫實主義的大纛之下,好壞並立、善惡共存,可以傳達情感之純淨,亦可以展現欲望之奔流;歌頌生命的幸福與愉悅的同時,也披露現實的陰暗和醜陋。將日常生活的一切忠實呈顯齣來,沒有造假,沒有遮掩,也沒有扭麯,毫無保留地揭發人之自私、貪婪、僞善、虛榮、唯利是圖。
如果說福樓拜長久以來一直被視為寫實主義的中流砥柱(盡管他自己抱持保留的態度),或許正是因為他麵對生命,正視生命,尤其是生命中的不完滿與莫可奈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淬鍊造就瞭他精準、幽微、豐富的語言,讓他知道應該如何去看待和梳理龐雜、捉摸不定、變化萬韆的現實。以一種美好的語言去刻劃醜惡的現實,鞭闢入裏,直指核心,沒有多少人可以做得比他更好。
圖書試讀
第一章
主教橋市的太太們對歐彭女士羨慕有半個世紀之久,人人都想同她一般,有個像菲莉希黛這樣的女僕。
菲莉希黛的年薪有一百法郎,包辦煮飯、灑掃、縫衣、洗衣、燙衣。她懂得如何套馬繮繩、飼養傢禽、攪打奶油,且對女主人忠心耿耿,盡管對方並非隨和之人。
歐彭女士嫁給一位英俊窮小子,一八○九年初丈夫過世,留下兩名幼子及龐大債務。於是她變賣名下不動産,隻保留杜剋農場與傑佛斯農場,因兩處地租最多可達五韆法郎。她接著搬離聖梅萊納的居所,另外住進花費較少、位於市場後方的祖宅。
這棟鋪石房子在兩條巷子中間,其中一條通往河流。屋內地麵高低不一,容易絆倒摔跤,狹窄的玄關隔開廚房與起居室,歐彭女士經常坐在起居室靠窗的草編扶手椅,就這樣待上一整天。漆白的牆邊排放八張桃花心木椅,晴雨計下方有架舊鋼琴,上頭盒子紙箱成堆,疊得像座金字塔。路易十五風格的黃色大理石壁爐旁,擺瞭兩張絨綉扶手椅,中間放置象徵竈神廟的擺鍾。因地闆比花園還低,屋裏總有點黴味。
來到二樓,首先看到「太太」的臥室,極為寬敞,壁紙是淺色花紋,牆上掛著身穿保皇派服飾的「老爺」肖像,臥室又通往一處較小的房間,裏頭可見兩張沒有床墊的小孩床。再過去是客廳,廳門長年緊閉,裏麵堆滿傢具,全以布巾覆蓋。接著是通往書房的走廊,進入書房後,裏頭有張黑色原木書桌,書桌雙側及後方皆為書架,上頭塞滿書籍、文件,兩側牆麵掛滿鋼筆素描、水粉風景畫及歐德洪的版畫,紀念消逝的奢華年代及美好時光。光綫透過三樓天窗照亮菲莉希黛的房間,從天窗可以俯瞰整片草原。
為瞭避免錯過彌撒,菲莉希黛每日天剛亮就起床,不停工作到晚上,晚餐後清理碗盤、關妥大門、往爐灰裏添柴火,最後纔躺在壁爐前,拿著玫瑰經念珠入睡。沒人比她更會討價還價,清潔程度也是無人能及,她的鍋子亮到能令其他女傭自卑。因為節儉,她刻意放慢吃飯速度,掉落桌麵的麵包屑也撥成堆撚來吃,麵包是她自己準備的,一個十二磅,可吃二十天。
她一年四季都披著一條印度披巾,以彆針固定,頭發藏進軟帽,著灰色長襪、紅色襯裙,上衣外頭罩著如醫院護士穿的翻領圍裙。
用户评价
在眾多的文學作品中,福樓拜的短篇小說對我來說,始終占據著一個特殊的位置。他的文字,不張揚,不浮誇,卻帶著一種不動聲色的深刻,能夠輕易地觸動人心。我曾在一個午後,陽光正好,我捧著《福樓拜短篇小說選集》,細細品味《傷心旅店》。主人公在陌生的城市裏,遇見形形色色的人,經曆著瑣碎而真實的日常,但在這看似平淡無奇的經曆中,他卻在不斷地審視自己,反思自己的生活。福樓拜對細節的把控,簡直令人嘆為觀止,每一個場景,每一個對話,都充滿瞭生活的氣息,讓我們仿佛身臨其境。他的人物,也並非完美無瑕,他們有缺點,有欲望,但正是這種不完美,纔讓他們顯得如此真實,如此 relatable。這種真實,讓我們在閱讀中,能夠找到自己的影子,也能夠看到他人內心的風景。
评分對於一個習慣瞭快節奏生活的現代人來說,閱讀福樓拜,需要一份沉靜的心,一份願意慢下來去品味的耐心。他的小說,沒有驚心動魄的情節,沒有跌宕起伏的衝突,但卻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張力,一種源自對生活本質的深刻洞察。我曾在一場突如其來的感冒中,窩在沙發裏,翻開瞭《三故事》。那裏麵的每一個故事,都像是經過精心打磨的短篇小說,雖然篇幅不長,但蘊含的意味卻十分深遠。《聖硃利安的傳說》,那種對精神世界的追尋,那種對人性的拷問,以及最終獲得的救贖,都讓我陷入瞭沉思。福樓拜並沒有直接給齣答案,他隻是呈現瞭一個過程,讓我們在閱讀中自己去尋找答案。這種留白,正是他高明之處。它激發瞭讀者的思考,讓作品在閱讀之後,依然能在心中迴響。他筆下的人物,或許都有著各自的缺陷和局限,但他們對某種意義的追尋,對生命價值的探索,卻能引起我們內心的共鳴。
评分對於一個閱讀者來說,能夠遇見一本真正觸動心靈的書,是一種幸運。而福樓拜的短篇小說,對我而言,就是這樣一本值得反復品味的寶藏。他沒有誇張的劇情,沒有刻意的煽情,但他的文字卻能直擊人心,引發深刻的思考。我曾在一個微雨的周末,靜靜地坐在窗前,讀著《包法利夫人》。愛瑪那種對平庸生活的不甘,對浪漫愛情的渴望,那種在現實與幻想之間掙紮的痛苦,都讓我感到心酸。福樓拜並沒有將她塑造成一個純粹的悲劇人物,他展現瞭她內心的復雜,她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以及她最終的沉淪。這種對人性的深刻洞察,是福樓拜作品中最吸引我的地方。他筆下的人物,都帶著一種人性的光輝與陰影,讓他們顯得更加立體,更加真實。
评分我一直認為,好的文學作品,就應該像一麵鏡子,能夠照見我們內心深處的自己。而福樓拜的短篇小說,恰恰擁有這樣的力量。他的文字,帶著一種不動聲色的力量,能夠輕易地穿透人心的壁壘,觸及那些最柔軟的情感。我曾在一個安靜的夜晚,翻開《一個簡單的心》。費莉西泰的生命,或許在很多人眼中是平凡的,但她身上所散發齣的那種對生活的熱愛,對生命的尊重,那種純粹而質樸的情感,卻深深地打動瞭我。她與她的鸚鵡,與她的貓,都建立瞭深刻的情感聯係,這種聯係,超越瞭功利,超越瞭世俗的眼光。福樓拜並沒有美化她的生活,他隻是真實地呈現瞭她的存在,但正是這種真實,讓她散發齣迷人的光輝。她的身上,體現瞭一種最本真的生命力,一種即使在最睏頓的環境中,也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的韌性。
评分讀福樓拜,總覺得像是在進行一場緩慢而深刻的自我對話。他的故事,不像現代小說那樣追求情節的跌宕起伏,而是更側重於人物內心的細膩描摹和對生活本質的探尋。我曾在一個失眠的夜晚,翻開《包法利夫人》,即便我早就知道這個故事,但每一次閱讀,都有新的體會。愛瑪那種對生活的熱情與對現實的失望,她的虛榮與對浪漫的嚮往,那種在平庸生活中試圖尋找齣口的努力,都讓我覺得既熟悉又悲哀。福樓拜的文字,有一種不動聲色的批判,他並不直接指責愛瑪的虛榮,而是通過細緻的描寫,讓我們看到這種虛榮是如何滋生,又是如何一步步將她推嚮深淵。他筆下的人物,似乎都背負著某種無法擺脫的宿命,他們掙紮,他們渴望,但最終,往往是被現實的洪流所吞噬。這種宿命感,或許正是福樓拜作品中最吸引我的地方。它讓我們思考,在人生的洪流中,我們有多少自主選擇的權利?我們的渴望,是否注定隻能成為泡影?這是一種帶著些許冷峻的哲學思考,但卻是在最真實的生活場景中展開,因此更具震撼力。
评分閱讀福樓拜,需要一點點耐心,需要一點點沉浸,因為他筆下的世界,總有一種淡淡的憂傷,一種不張揚的深刻。他並不需要華麗的辭藻來包裝,他的文字本身就帶著一種獨特的魅力,一種不動聲色的力量。我曾在一個忙碌的工作日結束後,感到身心俱疲,於是我翻開瞭《一顆簡單的心》,試圖從中尋找一絲慰藉。故事中的費莉西泰,她的一生,在世人眼中或許是平凡的,但她對生活的熱愛,對所有生命的尊重,那種純粹而質樸的情感,卻深深打動瞭我。她與她的鸚鵡,與她的貓,都建立瞭一種深刻的情感聯係,這種聯係,超越瞭功利,超越瞭世俗的眼光。福樓拜並沒有美化她的生活,他隻是真實地呈現瞭她的存在,但正是這種真實,讓她散發齣迷人的光輝。她的身上,體現瞭一種最本真的生命力,一種即使在最睏頓的環境中,也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的韌性。
评分每次翻開福樓拜的短篇小說,我都會有一種“迴到”的感覺,迴到那個更加純粹、更加真實的年代,去感受那些被時間沉澱下來的情感。他的文字,不像流水賬,也不像戲劇錶演,而是一種溫潤的流淌,將讀者緩緩地帶入故事之中。我特彆喜歡他在描繪人物心理時,那種不動聲色的洞察力。比如《三個故事》中的《聖硃利安的傳說》,那個不斷贖罪的人,他的內心掙紮,他的痛苦與堅持,都錶現得淋灕盡緻。福樓拜並沒有給齣明確的道德評判,他隻是呈現瞭人物的內心世界,讓我們去體會,去理解。這種客觀而冷靜的敘述方式,反而更能引起讀者的思考。他筆下的人物,或許都有著各自的睏境,但他們對生命意義的探索,對精神世界的追尋,卻能引起我們內心的共鳴。
评分我一直認為,真正的文學作品,不應該僅僅是講一個故事,更應該讓我們在閱讀之後,對這個世界、對人性産生新的認識。而福樓拜,無疑做到瞭這一點。他的短篇小說,篇篇都是精品,像是經過精心雕琢的玉石,雖然不張揚,卻散發著溫潤的光澤。我尤其欣賞他對女性心理的刻畫,那種細膩入微,仿佛能窺探到女性內心最深處的隱秘。在《一個簡單的心》裏,那個叫做費莉西泰的老女僕,她的一生,看似平淡無奇,卻充滿瞭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生命的虔誠。她對鸚鵡的愛,對一切生靈的憐憫,那種純粹的善良,在那個充斥著虛僞和算計的世界裏,顯得尤為珍貴。福樓拜並沒有試圖去美化她的生活,他的描寫是真實而樸素的,但正是這種真實,纔讓她的形象如此動人。她身上所體現齣的,是一種最原始的生命力,一種不被外界乾擾的內在平靜。閱讀她的故事,我仿佛能感受到一種來自土地的芬芳,一種最純粹的生命之美。
评分初次接觸福樓拜,是在一個飄著細雨的午後,咖啡館裏昏黃的燈光,伴隨著那本厚實的《福樓拜短篇小說選集》。我不是那種會輕易被華麗辭藻打動的讀者,但福樓拜的文字,像是一種沉靜的力量,不動聲色地將你捲入一個又一個真實到近乎殘酷的世界。他筆下的人物,不論是初入社會的年輕姑娘,還是經曆世事的中年婦女,抑或是懷揣夢想卻又步履維艱的藝術傢,都散發著一種揮之不去的寂寥和對現實的掙紮。我尤其喜歡他對於細節的捕捉,那種不動聲色的觀察,仿佛一位敏銳的解剖師,一層層地剝開人物的內心,展現齣人性中最幽微、最復雜的部分。比如,在《一個聖心》裏,那個渴望得到救贖的女人,她的每一次祈禱,每一次內心的獨白,都充滿瞭令人心酸的真實感。福樓拜並沒有給予她一個圓滿的結局,但正是這種不圓滿,纔讓她的形象更加立體,更加令人難忘。他似乎總能洞察到我們生活中那些被忽視的角落,那些被壓抑的情感,然後用最精準的語言將它們呈現齣來,讓我們在閱讀中,不自覺地看到瞭自己的影子,看到瞭自己內心深處的渴望與失落。這種共鳴,是他在我心中留下深刻印記的關鍵。
评分在我看來,福樓拜的短篇小說,是對“真實”二字最好的詮釋。他不像某些作傢那樣,為瞭製造戲劇衝突而刻意誇大或扭麯生活,他隻是用最冷靜、最客觀的筆觸,去描繪那些真實存在的情感和境遇。比如《傷心旅店》,我讀到的不是一個簡單的旅行故事,而是一個關於自我發現、關於內心孤獨的旅程。主人公在陌生的城市裏,遇見形形色色的人,經曆著瑣碎而真實的日常,但在這看似平淡無奇的經曆中,他卻在不斷地審視自己,反思自己的生活。福樓拜對細節的把控,簡直令人嘆為觀止,每一個場景,每一個對話,都充滿瞭生活的氣息,讓我們仿佛身臨其境。他的人物,也並非完美無瑕,他們有缺點,有欲望,但正是這種不完美,纔讓他們顯得如此真實,如此 relatable。這種真實,讓我們在閱讀中,能夠找到自己的影子,也能夠看到他人內心的風景。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