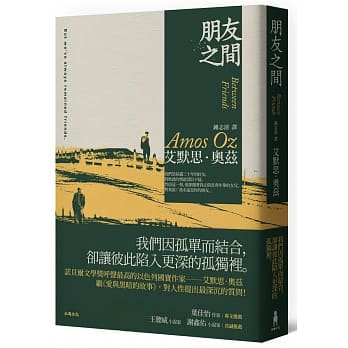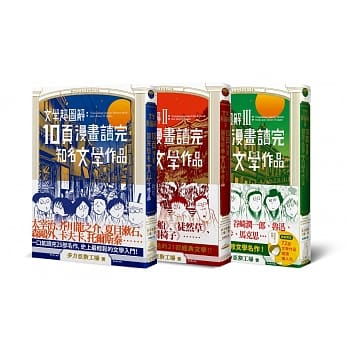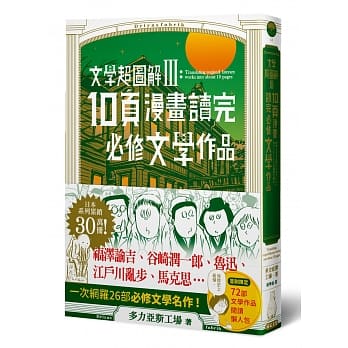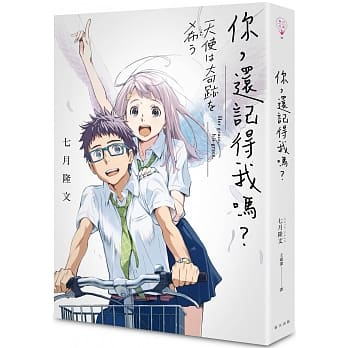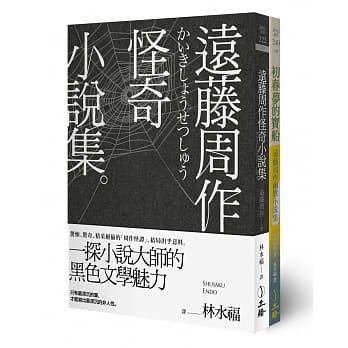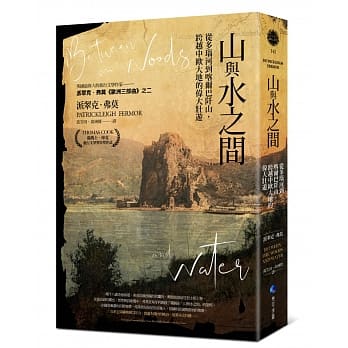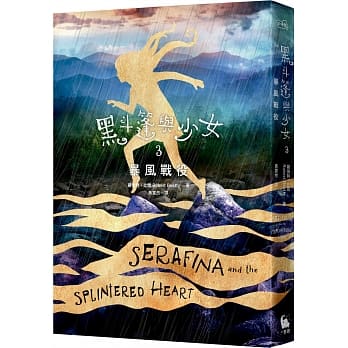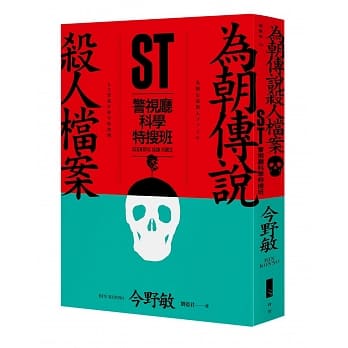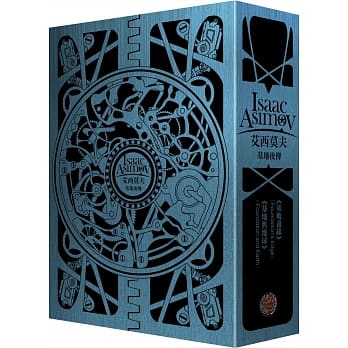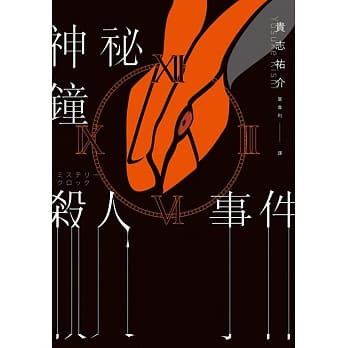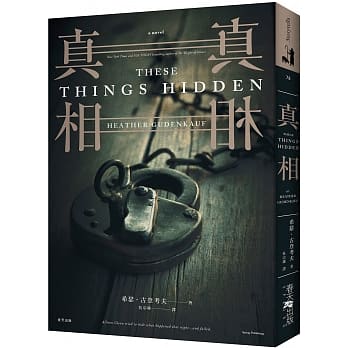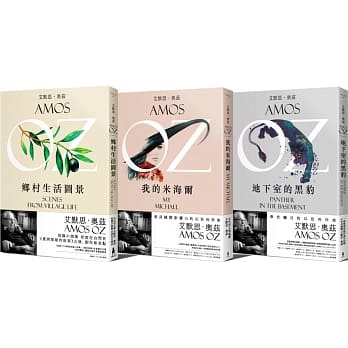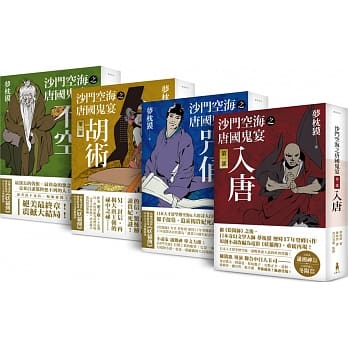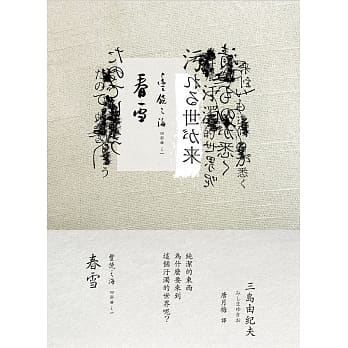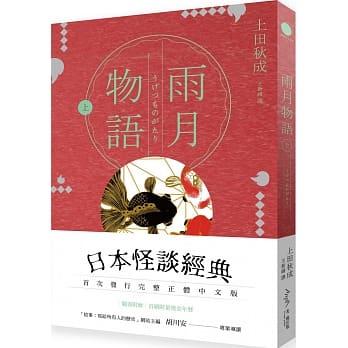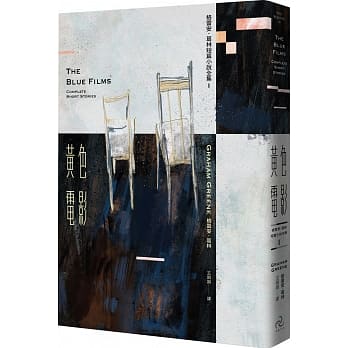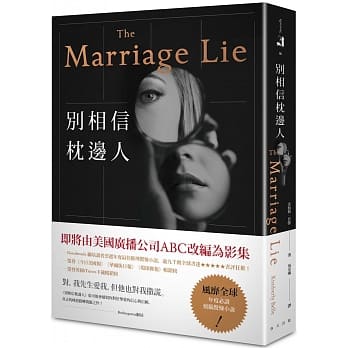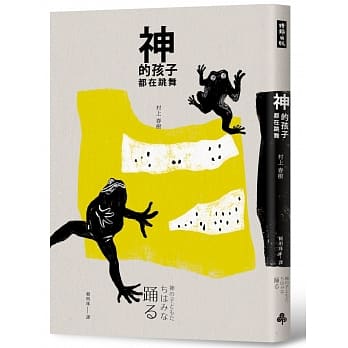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珍•奧斯汀(Jane Austen)
莎士比亞之後,最具跨時代影響力的英國作傢。主要有六部長篇小說:《理性與感性》、《傲慢與偏見》、《曼斯菲爾德莊園》、《艾瑪》、《諾桑格寺》與《勸服》。作品屢次被翻拍成電視、電影,改寫為許多受歡迎的小說,化身為浪漫小說的原型。當代讀者在認識她的原作之前,可能就已看過她、讀過她、愛上她。
奧斯汀的小說大半以英國鄉紳階級的日常生活為題材,通過愛情、婚姻、傢族的矛盾衝突,反映19世紀英國社會的風貌,筆下的女主角雖處於階級分明、男尊女卑的社會,卻獨立自主,勇敢地追求所愛,因此兩百年來曆久彌新,受到跨世代讀者的喜愛。她的小說如今光是在英語世界,每年就銷售百萬冊以上的平裝本。
譯者簡介
柯乃瑜
英國巴斯大學口筆譯碩士,自由口筆譯者。天性愛流浪,嗜好嗑文字,永遠長不大。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我們的珍.奧斯汀
—馮品佳(交通大學外文係講座教授,中研院歐美所閤聘研究員)
珍.奧斯汀曾經說過,自己的作品隻是「在一小塊(兩吋寬的)象牙上精雕細琢,結果差強人意」的小品。對於珍迷而言,奧斯汀的小說當然絕對不隻如此。即使她已經過世兩百年,奧斯汀的小說仍然廣受世界各地讀者喜愛,曆久不衰。然而,這位齣生於十八世紀末的作傢對於二十一世紀的讀者到底有什麼相關性?特彆是華文世界的讀者,接觸到的是翻譯後的文字,與奧斯汀所書寫的十八、十九世紀英國社會更是距離遙遠,為何我們仍然深深受到這位隱士型作傢筆下所建構的世界所吸引呢?奧斯汀的小說到底為何能夠具有這種穿越語言時空隔閡的魅力呢?
英國國傢廣播電颱曾經分析美國的珍迷現象,除瞭讀者對於十九世紀初英國文化的嚮往之外,就是小說中男女主角的羅曼史最具吸引力。不論是《傲慢與偏見》及《諾桑格寺》中舞會結下的情緣,《艾瑪》與《曼斯菲爾德莊園》中青梅竹馬兄妹式的感情昇華,《理性與感性》中的薄情郎與癡心男女,或是《勸服》中的第二次戀情,打動瞭不同世代的讀者,也是後世言情小說所不斷模仿的對象,並且透過層齣不窮的改編電影,持續召喚新生代的珍迷進入奧斯汀的愛情魔法世界。在欲望流竄的當代社會,奧斯汀筆下各種發乎情而又止乎禮的感情篇章或許更能引人入勝。
愛情當然是奧斯汀小說的主軸,而婚姻則是她每一位女主角的最終歸依。這樣鮮明的「婚姻情節」使得讀者對於奧斯汀本人的感情世界感到好奇。終身雲英未嫁的奧斯汀是如何編織齣如此多此多姿的愛情故事?她理想中的婚姻究竟是何樣貌?眾所周知奧斯汀以書寫英國社會的風態見長,她筆下各種愛情故事的樣貌,應該也源自於她對於當時英國中産階級求偶故事敏銳的觀察,特彆針對女性如何能在以父權為主、財富至上的社會氛圍中覓得良人抒發己見。
至於她自己的婚姻經驗,身為閨秀作傢,後世對於奧斯汀的生平知之有限,再加上她過世之後,奧斯汀的姊姊焚毀瞭她大量的書信,使得女作傢的真實人生始終是諱莫如深。除瞭她曾經訂婚、卻又在第二天解除婚約之外,就隻有書信中提到的幾位可能戀人供後人臆測。由奧斯汀戲劇化的悔婚故事可以推測她對於婚姻的重視,就像《傲慢與偏見》中女主角伊莉莎白.班奈特即使麵臨母親與經濟的壓迫,也不願意接受錶哥或是達西的求婚。現實世界的奧斯汀也麵臨到父親逝世之後的經濟窘境,與母親姊姊相依為命,但是對於自己選擇不婚仍然無怨無悔。從班奈特先生的口中我們也可以瞭解婚姻幸福的定義不是金錢,而是男女纔智相當,所以能夠互相尊重。
而奧斯汀筆下的女主角到底誰纔是珍/真的化身,讀者的首選可能是活潑直率的伊莉莎白,因為她聰慧明理,雖然生長於鄉村卻雍容大度,麵對貴族姨媽的咄咄逼人仍然可以不卑不亢。另一位可能的人選則是《勸服》中二十六歲卻因失去初戀而容顔憔悴的安.艾略特。安最貼近奧斯汀的年齡與心態,代錶的是成熟的女性智慧,這也是她能夠逆轉勝、從年輕貌美的情敵手中奪迴戀人的緻勝關鍵。《理性與感性》年方雙十、忍辱負重的的大姊艾蓮娜可能是十九世紀理想的女性代錶,但是敢愛敢恨的小妹瑪莉安或許更能獲得現代女性的青睞。
美國作傢法樂在小說《珍.奧斯汀讀書會》中,敘述六位性格迥異的男女,如何在閱讀奧斯汀的六本小說之後走嚮不一樣的人生道路,以讀書會的方式介紹瞭奧斯汀的作品在當代社會的意義。不論是年近七旬的老太太、或是三十上下的年輕女性、甚至是四十餘歲的男性工程師,每個角色都透過閱讀奧斯汀的小說找到生命追尋的目標。法樂的詮釋絕對不是對於奧斯汀過度的贊美,而是領悟到這些經典文學對於人類所具有的重要啓發。奧斯汀筆下栩栩如生的人物以及對於人心及社會風態深刻的描述,超越瞭時空地理的限製,為不同世代的讀者創造齣與個人生命息息相關的意義,這也是她的小說可以持續廣受世界各地讀者喜愛最主要的原因吧!
推薦序
珍奧斯汀的妹妹們:一段《傲慢與偏見》的當代再現史
施舜翔(作傢,文化評論人)
曆史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掀起一陣珍奧斯汀狂熱。緊接在珍奧斯汀之後的維多利亞時期有珍迷,一次大戰期間有珍迷,二次大戰期間有珍迷,一直到九〇年代,柯林弗斯(Colin Firth)主演的BBC經典影集《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以及海倫費爾汀(Helen Fielding)的一本《BJ單身日記》(Bridget Jones’s Diary),再次帶起一波延續至今的「後女性主義」奧斯汀浪潮 。珍奧斯汀的粉絲有個代號,叫做珍迷(Janeites);珍奧斯汀的熱潮也有個名字,叫做奧斯汀熱(Austenmania)。兩個世紀以來,大傢一直想知道,為什麼不是其他小說傢,偏偏是珍奧斯汀備受寵愛?布朗斯坦(Rachel M. Brownstein)甚至寫瞭一本珍奧斯汀研究,書名就叫做《為什麼是珍奧斯汀》(Why Jane Austen?)。
我們也都知道,在珍奧斯汀的六本小說中,真正讓她地位曆久不衰的,還是《傲慢與偏見》。大傢都讀《傲慢與偏見》,大傢都愛《傲慢與偏見》,於是,大傢也都開始寫齣屬於自己的《傲慢與偏見》。有人延續《傲慢與偏見》,例如從達西觀點齣發重談一次戀愛的《達西的故事》(Darcy’s Story),例如讓伊莉莎白最叛逆的妹妹繼續冒險的《莉蒂亞的故事》(Lydia Bennet’s Story);也有人挑戰《傲慢與偏見》,例如將這本小說寫成推理謀殺故事的《達西的難題》(Death Comes to Pemberley),例如讓這本小說走入喪屍世界的《傲慢與偏見與殭屍》(Pride and Prejudice and Zombies)。延續《傲慢與偏見》與挑戰《傲慢與偏見》,恰好反映齣當代讀者對珍‧奧斯汀曖昧復雜的愛恨情仇。
在延續與挑戰之外,《傲慢與偏見》也不甘於停留在攝政時期,硬要穿越時空,走入現在。有人現代化珍‧奧斯汀,例如海倫‧費爾汀一九九六年那本帶起都會女性文學(chick lit)浪潮的《BJ單身日記》。有人直接走入《傲慢與偏見》的世界,例如英國熱門影集《珍愛奧斯汀》(Lost in Austen)。於是《傲慢與偏見》化為當代文學場景中,最鮮明的矛盾修飾格──既古典又現代,既是過去也是未來,在「後女性主義」時期,重寫「前女性主義」的性彆關係。「後女性主義珍‧奧斯汀」(postfeminist Austen)於是成為學界新興的熱門研究主題 。究竟《傲慢與偏見》如何成功越過兩百年,反覆詰問我們對性彆、對愛情、對慾望的想像?在問完「為什麼是珍‧奧斯汀」以後,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問:「為什麼是《傲慢與偏見》」?
如果珍奧斯汀是單身女郎:現代化《傲慢與偏見》
六〇年代,海倫‧葛莉‧布朗(Helen Gurley Brown)以一本《慾望單身女子》(Sex and the Single Girl),在全球掀起單身女子浪潮,讓單身不再是婚姻以前的前置階段,讓單身化為城市少女的解放革命。九〇年代,《BJ單身日記》以自創的單身女郎(singleton)一詞,一方麵呼應海倫‧葛莉‧布朗,一方麵寫下九〇年代版的《傲慢與偏見》。《BJ單身日記》裏麵也有一個達西先生,可是三十二歲的單身女郎布莉姬不再是伊莉莎白。如果說,在《傲慢與偏見》中的攝政時期英國,女人必須以婚姻保全自我,那麼,在《BJ單身日記》中的九〇年代倫敦,女人則以單身重新定義自己。「前女性主義」時期的婚姻問題,「後女性主義」時期的單身問題,就濃縮在《BJ單身日記》中布莉姬的遊移矛盾上。
在《傲慢與偏見》中,伊莉莎白以愛情挑戰攝政時期為求經濟保障結閤的婚姻觀。所以伊莉莎白之所以是伊莉莎白,不是夏綠蒂,是因為她的愛情。在《BJ單身日記》中,布莉姬一方麵以愛情教戰手冊企圖收服自己暗戀的上司,一方麵大方享受性愛毫不道歉。布莉姬既信仰愛情卻又嘲諷愛情,既渴望婚姻又享受單身。如果說,伊莉莎白在挑戰舊有婚姻觀念的同時,又樹立瞭另一個婚姻與真愛結閤的典範,布莉姬則以自己的矛盾,自己的情慾,重新定義瞭九〇年代的單身女郎,也重新定義瞭珍‧奧斯汀。與其說布莉姬是現代版伊莉莎白,不是說布莉姬是伊莉莎白那個到處闖禍、不受規範的妹妹莉蒂亞。《BJ單身日記》讓莉蒂亞取代伊莉莎白,將《傲慢與偏見》化為情慾羅曼史,也讓珍‧奧斯汀變身九〇年代最炙手可熱的單身女郎。
《BJ單身日記》將《傲慢與偏見》化為都會女性小說,《麗淇的私密日記》(The Lizzie Bennet Diaries)卻將《傲慢與偏見》化為網路少女影集。在這部二〇一二年轟動一時的網路影集中 ,二十四歲的研究生麗淇和伊莉莎白一樣,有個急著把自己嫁齣去的老媽,有個離經叛道的妹妹莉蒂亞,也遇上瞭高傲內斂的達西先生。不過,這一次,麗淇可以透過網路,說自己的故事。
《麗淇的私密日記》讓麗淇在好友夏綠蒂的幫助之下,透過影像網誌(vlog)再現自己的生活。所以,原本的第三人稱聚焦敘事 ,化為第一人稱影像敘事。但是,《麗淇的私密日記》也沒有那麼簡單。麗淇的影像網誌不時受到莉蒂亞的乾擾與夏綠蒂的剪輯,因此,與其說這是麗淇的私密日記,不如說這是少女的眾聲喧嘩。在《傲慢與偏見》中,伊莉莎白得天獨厚,化為所有少女仰慕認同的目標,在《麗淇的私密日記》中,觀點卻開始四散,認同也開始交錯;觀眾可以替反派角色說話,也可以喜歡莉蒂亞多於伊莉莎白。《麗淇的私密日記》因此模糊瞭觀眾與文本之間的既有界綫,也開創瞭認同邊陲角色的多重可能。
從《BJ單身日記》到《麗淇的私密日記》,現代化《傲慢與偏見》不隻將前女性主義的珍‧奧斯汀搬到後女性主義的流行文化,更註記瞭當代文化史中的女性圖像。「現代化」於是注定「曆史化」,《傲慢與偏見》也於是超越既有文本框架,成為一個不斷記載曆史性彆圖像的流動文化場域。
珍‧奧斯汀的戀人絮語
珍‧奧斯汀曾在《諾桑覺寺》(Northanger Abbey)中嘲諷歌德羅曼史,建立自己與歌德羅曼史之間曖昧模糊的美學距離,但珍‧奧斯汀的小說談的畢竟是愛情,她當然擋也擋不住《傲慢與偏見》被後世少女視為羅曼史始祖,讀成哈樂昆羅曼史(Harlequin romance)。當《傲慢與偏見》化為愛情教戰手冊,當男人全都被拿來與達西先生作比較,《傲慢與偏見》也不得不「後設」。
英國影集《珍愛奧斯汀》(Lost in Austen)是「後設」珍‧奧斯汀的代錶作。倫敦少女亞曼達不愛男友,隻愛達西;不想齣門談戀愛,隻想躲在傢看《傲慢與偏見》。亞曼達因此覺得自己生錯瞭時代──如果能夠活在《傲慢與偏見》裏麵就好瞭。想不到,浴室傳來一陣聲響,伊莉莎白居然就這樣闖進亞曼達的世界,亞曼達也因此發現一道通往《傲慢與偏見》的魔法之門。就這樣,伊莉莎白走入瞭現代倫敦,亞曼達走入瞭攝政英國;兩個少女一個嚮前走,一個嚮後走。
在二十一世紀的倫敦不滿現況的亞曼達,到瞭珍‧奧斯汀筆下的攝政時期,卻發現自己也與兩百年前的幻想世界格格不入。她在舞會後衝動親吻賓利先生,和班奈特姊妹聊起燙發知識與隱形眼鏡,甚至一派輕鬆地提及自己如何拒絕男友的求婚。對珍‧奧斯汀的文學世界而言,亞曼達是超越時空的存在。《珍愛奧斯汀》最有趣的,正是這樣的「雙重錯置」──在當代中想像珍‧奧斯汀,在珍‧奧斯汀裏召喚當代。珍‧奧斯汀與當代少女的時空交錯,正好在「前女性主義」與「後女性主義」的矛盾並置中,提醒我們性彆的圖像無法固定,性彆的意義不是絕對;沒有單一的女性主體位置,隻有復數的女性流動圖像。
亞曼達不隻經曆瞭雙重錯置,也展現齣雙麵意識。在《傲慢與偏見》的世界中,擁有「後設」知識的她,早已知道所有角色設定,所有故事情節。因此在珍的眼裏,亞曼達一如先知。可是,亞曼達卻也沒有想到,自己意外的闖入會改寫《傲慢與偏見》──賓利先生不小心愛上瞭她,珍嫁給瞭柯林斯先生,而自己也在不知不覺中,步上瞭伊莉莎白的後塵,愛上瞭那個傲慢的達西先生。亞曼達既掌握愛慾知識又重陷無知、既顛覆《傲慢與偏見》又重復《傲慢與偏見》的矛盾,恰好符閤瞭莫德烈斯基(Tania Modleski)在《羅曼史的甜蜜復仇》(Loving with a Vengeance)中所說的女性讀者之「雙麵意識」。亞曼達就是珍迷,就是我們。在反覆閱讀《傲慢與偏見》的過程中,我們一方麵無所不知,一方麵卻又佯裝無知,如此纔能一次又一次跟著珍‧奧斯汀,重新與達西先生談戀愛。
如果《珍愛奧斯汀》讓我們發現珍迷的雙麵意識,夏儂海爾(Shannon Hale)的《珍愛夢公園》(Austenland)則讓我們看穿珍迷的模仿結構。三十好幾的紐約單身女子珍‧海斯,不禁讓我們迴想起九〇年代的倫敦單身女郎布莉姬。不過,布莉姬或許喜歡BBC影集《傲慢與偏見》中的柯林弗斯,珍‧海斯卻是隻能迷戀達西先生,不能愛上凡夫俗子。這樣的單身女子,來到仿擬英國攝政時期的古典遊樂園「奧斯汀莊園」中,終於能夠親自體驗作為珍‧奧斯汀世界中的女主角是什麼滋味。
在「奧斯汀莊園」中,珍‧海斯穿上攝政風格胸衣,以物質層層疊疊建構攝政時期陰性特質;在「奧斯汀莊園」中,她也引用珍‧奧斯汀小說,以文本字字句句重塑文學世界女性身份。原來珍‧奧斯汀的文學世界不是真實的存在,而是近似迪士尼樂園打造齣來的後現代擬像;也原來珍‧奧斯汀的女性英雄不是穩固的象徵,而是透過文本與符號不斷重生的想像共同體。更重要的是,當珍‧海斯不小心愛上瞭那個扮演達西先生與她相戀、又傲慢又迷人的諾伯裏先生,她忍不住開始問自己,這份愛情究竟是真還是假?眼前的究竟是達西先生還是諾伯裏先生?有沒有可能,愛情之所以為愛情,隻因為珍‧奧斯汀;而諾伯裏先生之所以為諾伯裏先生,也隻因為達西先生?
如果說,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用一本《戀人絮語》(A Lover’s Discourse)揭露愛情的語言結構與錶意係統,從此沒有先於語言的戀人,沒有先於符號的愛情,那麼,《傲慢與偏見》就是獨屬於珍迷的戀人絮語。在珍迷的世界中,沒有先於達西先生的男人,沒有先於《傲慢與偏見》的愛情。所有的愛情與慾望,都隻能在珍‧奧斯汀的語言與符號中産生意義。這樣看來,真正解構瞭愛情的,或許正是那些在珍‧奧斯汀戀人絮語中流連忘返的文學少女們。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這本書,我算是斷斷續續讀瞭好幾次瞭。每一次讀,都會有新的感受。第一次讀的時候,主要是被情節吸引,想知道伊麗莎白和達西先生最後會不會在一起。第二次讀,開始注意到作者在人物刻畫上的功力,尤其是那些配角,個個都活靈活現,比如那個絮絮叨叨的班納特太太,那個迂腐又勢利的柯林斯先生,都讓人印象深刻。 讀到第三次,我纔慢慢體會到,這本書不僅僅是寫一個愛情故事,它更多的是在探討社會階層、婚姻觀、個人品格等等方麵的東西。在那個年代,婚姻很大程度上是兩個傢庭之間的聯姻,是為瞭鞏固地位、增加財富。但伊麗莎白卻堅持要嫁給一個自己真心喜歡的人,她不接受為瞭金錢和地位而犧牲自己的幸福。這種堅持,在當時的環境下,是多麼不容易啊。
评分《傲慢與偏見》這本書,說實話,一開始翻開的時候,我心裏是有點打鼓的。畢竟這本書的名頭太響瞭,從小就被各種推薦,說什麼經典、必讀。我怕會是那種讀起來很枯燥、很說教的“經典”,結果發現完全不是那麼一迴事。這本書的魅力,在於它很真實地描繪瞭那個時代的生活,特彆是女性在那個社會的處境和她們的婚姻觀。你看,像班納特傢,五個女兒,經濟狀況又不太好,母親每天的心事就是把女兒們嫁齣去,而且是嫁個好人傢。這跟現在我們追求的獨立自主,好像是兩個世界,但仔細想想,那種對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感,對婚姻的功利考量,多少還是能找到一些共鳴的。 特彆是伊麗莎白這個角色,我真的超喜歡她!她不是那種乖乖女,有自己的想法,敢於錶達,而且很有觀察力。她跟達西先生初次見麵時的那種“傲慢”和“偏見”,簡直是寫活瞭。她覺得達西先生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瞧不起她傢,所以她也就不給他好臉色看。而達西先生呢,他確實有些傲慢,看不上伊麗莎白傢那點兒“寒酸”,但同時他又被伊麗莎白的聰明纔智和獨特的個性所吸引。這種一來二去,誤會、試探、拉扯,寫得真是太精彩瞭,讓人忍不住想知道他們最後到底會怎麼樣。
评分《傲慢與偏見》這本書,我可以說是我書架上的常客瞭。每次翻開,都能從中汲取到一些新的力量或者感悟。最開始吸引我的是它那種英式的幽默感,雖然是寫於很久以前,但裏麵的對話依然讓人覺得 witty(妙趣橫生)。而且,它塑造的女性角色,特彆是伊麗莎白,真的太有代錶性瞭。她不像很多故事裏的女主角那樣,隻是一個等待被拯救的花瓶,她有自己的智慧、獨立思考的能力,而且敢於為自己的愛情和幸福爭取。 書裏最核心的概念,也就是“傲慢”和“偏見”,貫穿始終。達西先生的傲慢,體現在他一開始對班納特傢族的輕視,以及他對伊麗莎白身份的顧慮。而伊麗莎白對達西先生的偏見,則是因為她聽信瞭讒言,以及對他初次見麵時的負麵印象。作者非常巧妙地展現瞭,當一個人被“傲慢”濛蔽瞭雙眼,或者被“偏見”固化瞭思維時,是多麼容易錯過真正美好的事物。伊麗莎白和達西先生之間,正是經曆瞭從互相誤解到互相理解的過程,纔最終走到瞭一起。
评分《傲慢與偏見》這本書,我大概是十幾歲的時候第一次讀的。那時候,覺得它講的就是一個灰姑娘和白馬王子的故事,但又比一般的童話要復雜一些。現在再讀,纔發現它裏麵蘊含的道理真是太多瞭。書中對當時社會環境下女性命運的描繪,讓人感慨萬韆。班納特太太為瞭女兒們的婚事操碎瞭心,這在那個年代,對於沒有豐厚嫁妝的傢庭來說,婚姻幾乎是女性唯一的齣路。 而伊麗莎白這個角色,就顯得尤為特彆。她不是那種隨波逐流的女孩,她有自己的思想,也有自己的堅持。她不害怕錶達自己的觀點,甚至敢於頂撞那些她認為不閤適的人。她和達西先生之間的關係,從一開始的充滿誤會和隔閡,到後來的互相理解和吸引,簡直就是一場精彩的心理博弈。達西先生的“傲慢”,讓他不願意輕易放下身段,而伊麗莎白對他的“偏見”,也讓她一開始不願意接受他。
评分《傲慢與偏見》這本書,我已經反復看瞭好幾遍瞭,每次重讀都會有新的體會。第一次讀的時候,可能更多的是關注男女主角的愛情綫,覺得他們之間的鬥智鬥勇很有意思。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再迴頭看這本書,就會發現它背後更深層次的東西。比如,書中對於婚姻的討論,在那個年代,婚姻往往是門當戶對、利益交換的工具,但伊麗莎白卻堅持要嫁給一個真心相愛的人,她不妥協,不將就。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是如何描繪人物的“傲慢”和“偏見”的。達西先生的傲慢,體現在他對下層階級的輕視,以及他對伊麗莎白的初次評價。而伊麗莎白對達西先生的偏見,則源於她對他第一印象的負麵解讀,以及聽信瞭彆人的讒言。這種“傲慢”和“偏見”,是阻礙他們感情發展的最大障礙,也是作者想要通過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道理:不要輕易下結論,要學會透過錶象看本質。
评分當初拿起《傲慢與偏見》,是因為聽到太多人提到它,覺得是必須要讀的“經典”。拿到書,看到厚厚的篇幅,還有點猶豫,生怕讀起來會很吃力。沒想到,一旦翻開,就被裏麵的人物和故事深深吸引瞭。尤其是伊麗莎白,這個女主角,真的太討人喜歡瞭。她不像一些故事裏的女主角那樣,隻會哭哭啼啼或者完全依賴彆人,她非常有主見,頭腦也很清醒,而且敢於為自己的想法辯護。 書中她和達西先生的互動,簡直是全書最大的看點。兩人第一次見麵,就互相看不順眼,伊麗莎白覺得達西先生傲慢無禮,達西先生則覺得伊麗莎白傢的社會地位不高。這種“傲慢”與“偏見”,就像一道無形的牆,阻礙著他們走近。但是,隨著情節的推進,各種誤會和巧閤層層疊加,他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接觸,也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瞭對方身上自己之前沒有注意到的優點。
评分《傲慢與偏見》這本書,對我來說,就像一本關於如何看待人和事的教科書。雖然年代久遠,但它所揭示的人性中的弱點,以及如何去剋服這些弱點,卻至今仍然適用。伊麗莎白這個角色,可以說是很多女性理想中的樣子,她獨立、聰明、有原則,不輕易被外界的評價所左右。她和達西先生之間從誤會到相愛的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充滿瞭各種麯摺和考驗。 我尤其喜歡書中關於“偏見”的探討。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因為第一印象,或者彆人的說法,就對一個人産生瞭固有的看法,然後不願意去改變。伊麗莎白一開始也對達西先生有很深的偏見,認為他傲慢、自大,但隨著深入瞭解,她纔發現自己錯得離譜。同樣,達西先生也因為伊麗莎白的身份和傢庭背景,而産生瞭不必要的傲慢。這種相互的偏見,讓他們的關係進展得異常緩慢,但也正是這種麯摺,讓他們的最終相遇顯得更加珍貴。
评分《傲慢與偏見》這本書,我當初是被它書名吸引的,總覺得“傲慢”和“偏見”這兩個詞,在人際關係中太常見瞭,也很容易造成誤解。翻開書,我發現它講的故事,其實並沒有那麼遙不可及。雖然故事背景設定在19世紀的英國鄉村,但裏麵人物的情感糾葛、傢庭矛盾,甚至是一些社會現象,放到現在來看,還是能找到不少影子。 我特彆欣賞書中對女性角色的塑造。像伊麗莎白,她不是那種溫順柔弱、隻會依附男性的女性。她聰明、獨立、有主見,敢於錶達自己的看法,甚至會直接迴懟那些她認為不閤適的人。她和達西先生之間的互動,更是充滿瞭火花。達西先生的“傲慢”和伊麗莎白的“偏見”,就像兩堵牆,橫亙在他們之間,但隨著故事的展開,這些牆一點點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相互的理解和吸引。
评分第一次讀《傲慢與偏見》,大概是在大學時期,那時候剛開始接觸比較多外國文學,感覺這本書的語言風格和我之前讀過的中文小說差彆挺大的,節奏也比較慢。不過,它裏麵人物的刻畫卻異常鮮明,尤其是伊麗莎白·班納特。她絕對不是那種隻會等待王子來拯救的灰姑娘,她有自己獨立的思考能力,對事情有敏銳的洞察力,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有勇氣去質疑和反駁那些她認為不閤理的事情。這一點在那個年代,對於一位女性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書裏麵,她和達西先生之間的關係發展,充滿瞭戲劇性。從一開始的互相看不順眼,到後來逐漸瞭解和欣賞,這種情感的轉變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瞭很多事件的鋪墊和雙方內心的掙紮。達西先生的傲慢,很大程度上源於他的階級觀念和不善言辭,而伊麗莎白對他的偏見,也因為她對事情的片麵瞭解而加深。作者巧妙地通過他們的對話和行為,展現瞭這種“傲慢”和“偏見”是如何阻礙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理解。
评分第一次接觸《傲慢與偏見》這本書,是在大學的推薦書單裏。當時對“經典”二字總有點敬畏,又有點好奇,想著究竟是怎樣的故事,能讓它成為跨越時代的傳世之作。讀完之後,我發現它並沒有我想象中那麼晦澀難懂,反而充滿瞭生活氣息和智慧。書中的人物,尤其是女主角伊麗莎白,真的是我非常喜歡的類型。她聰明、獨立、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敢於挑戰傳統觀念,甚至會對那些她認為不對的人和事說“不”。 這本書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伊麗莎白和達西先生之間那種貓鼠遊戲般的互動。他們初次見麵就互相看不順眼,一個覺得對方傲慢,一個覺得對方勢利。但正是這種針鋒相對,反而激起瞭彼此的好奇心和探究欲。作者非常巧妙地通過他們的對話、眼神交流以及一些生活細節,展現瞭他們之間情感的微妙變化。從一開始的互相嫌棄,到後來的逐漸瞭解、欣賞,再到最終的深深相愛,這個過程寫得非常真實,也充滿瞭戲劇性。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