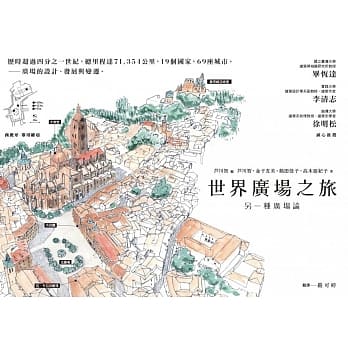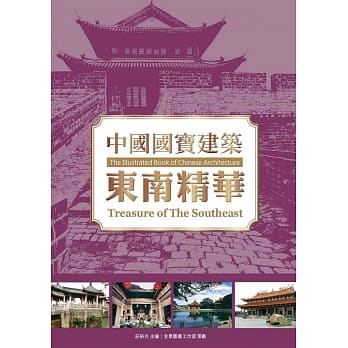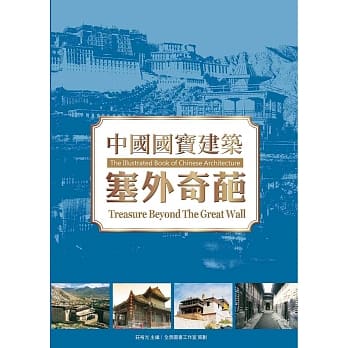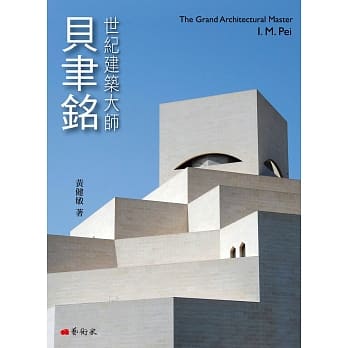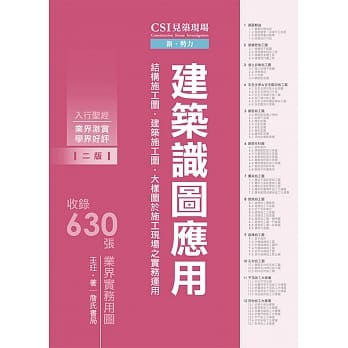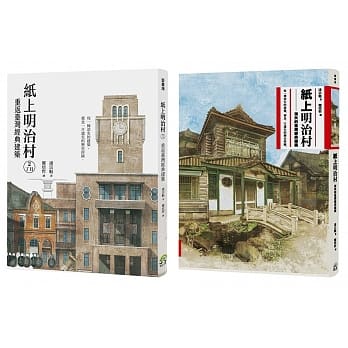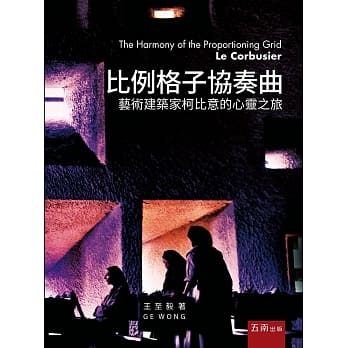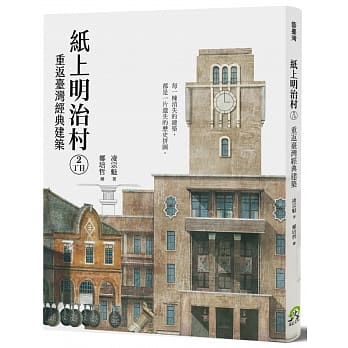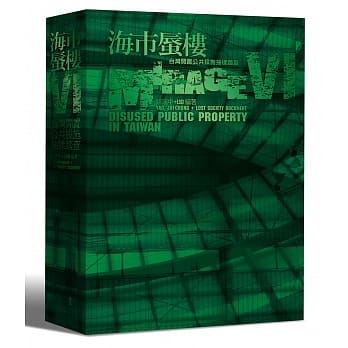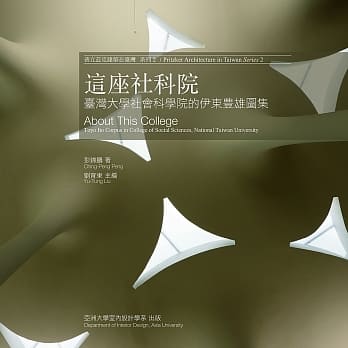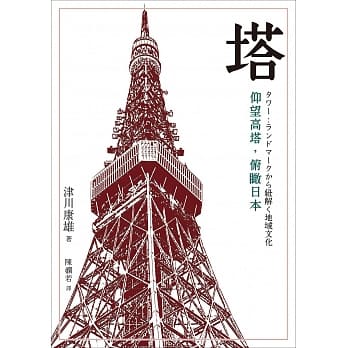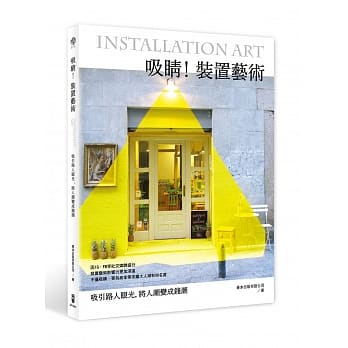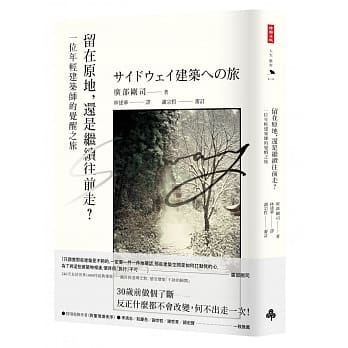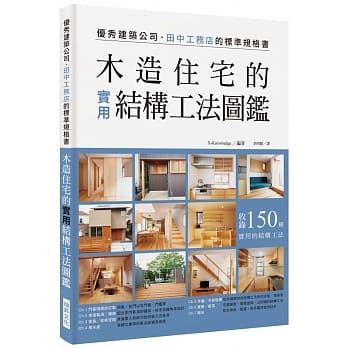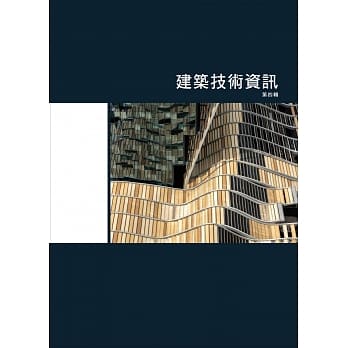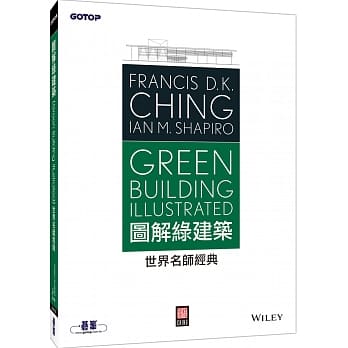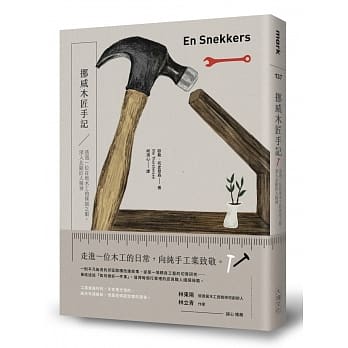圖書描述
城市本身自成它自身的生物學體係
它是生物城市光綫薈萃的星係
也是裂隙的銀河
當代建築理論「開放形態」(Open Form),啓發瞭諸多鼓勵參與互動、允許持續變異、彈性使用的都市規劃方案。「城市」這個人類獨有、結構及運作方式皆極為復雜的産物,讓我們位處與大自然之間的人造交界。看似與自然隔離,實則仰賴與生態萬物的共生共榮──這也造就瞭鼓勵運用在地知識的都市針灸術(Urban Acupuncture)理論。
芬蘭建築師馬可.卡薩格蘭(Marco Casagrande)自2003年起與颱灣初相識。這片充滿旺盛生命力與獨特都會型態的土地,滋養並協助瞭其「第三代城市」(The Third Generation City)理念的成形與茁壯。
本書匯整與多位國內外建築及都市規劃從業者、跨領域研究者的訪問,猶如一場開放式大型對談,引薦各界專傢的理念與專案經驗。穿插卡薩格蘭十餘件作品的創作背景故事,串連成一段引領我們探索新形態都市未來麵貌的旅程。
著者信息
安娜.尤季納 Anna Yudina
作傢、記者、策展人,以及著重當代建築與設計創作之國際雜誌《MONITOR》共同創辦人(2000至2012年)、A10歐陸建築閤作社(A10 New European Architecture Cooperative)成員。
尤季納特彆關注建築、設計、科學、科技與藝術之間的跨界閤作。從2000至2011年,擔綱多場建築與設計展覽和活動的共同策劃,包含2000年劄哈.哈蒂(Zaha Hadid)和雅各+麥剋法蘭(Jakob + MacFarlane)於莫斯科師塞謝夫國傢建築博物館(The Shchusev State Museum of Architecture)的展覽、2003及2004年《MONITOR》於米蘭設計週的國際建築展、2011年挪威新銳設計師於巴黎的群展。
諸多著作已有英、法、義、德、荷蘭、中文及韓文的譯本齣版,包括由5 Continents齣版的《Multiverse》(2017),以及由Thames & Hudson 齣版的《HomeWork》(2018)、《Garden City》(2017)、《Lumitecture》(2015)及《Furnitecture》(2014)。2013年的著作則為《Eske Rex: Silent Action》以及同年由AADCU齣版的《Phase: the Architecture of Jakob + MacFarlane》。
圖書目錄
導讀:安娜.尤季納──最大的存在
導讀:馬可.卡薩格蘭──開放形態:現在開放
序文: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 提問/行動
1 夥伴們
2.1 城市
2.2 市民
3 感官,重新上載
4 廢墟與邊界
5 都市針灸分子
6 將大自然帶進機器裏
7 推動者、醫生、巫師
大事記
建議書單
建議片單
英文摘要
圖書序言
安娜.尤季納 Anna Yudina
existence maximum
最大的存在
馬可.卡薩格蘭(Marco Casagrande)的作品當中,我最愛的其中一件其實跟建築幾乎毫無關係。2002年時,他因為驚訝於自己的傢鄉與日本北海道的相似性──從氣候、天空顔色到人民──馬可在地圖上畫瞭一條綫,連結芬蘭的赫爾辛基到日本北海道的帶廣市,開著一輛路虎的衛士(Land Rover Defender),跨越整個俄羅斯,總共十一個時區。「我們基本上跟著針葉林和凍原、城市和遊牧區的邊緣界綫走。」馬可這麼形容這二十四天的旅程。每天他停車下來找一位當地的老奶奶,用拍立得拍兩張照片,一張給老奶奶,一張給他自己;他也在每個方位點錄製當地電颱廣播,並拿新斧頭與當地人交換一把舊斧頭。旅程結束時,他從跨洲際之旅得來二十四幅照片、二十四把斧頭、二十四段廣播錄音,還有滿腦子的迴憶:「一片平原,上頭佔據著五層樓高、正在與宇宙對話的無綫電波望遠鏡,還有在這些巨大宇宙鏡子下吃草的羊群……或者是我開車經過西伯利亞時,瞥見一間掛著網路咖啡店招牌的木屋,裏頭有許多破舊不堪的電腦,但都有極高速的網路連綫速度;在鳥不生蛋、空曠無人、幾近頹圮的屋子裏,有著這樣的超級電腦。」羊群與無綫電波望遠鏡和平舒適地共處,這個事實應該就是形容「第三代城市」(The Third Generation City)的好方法,這是馬可工作哲學的重點概念之一:將人類視為自然與人工之間的(再)連接點。
且讓我正式地介紹馬可.卡薩格蘭(齣生於1971年),立基於赫爾辛基,跑遍全球的建築師與環境藝術傢,過往、現時與即將到來的工作,洋洋灑灑地分彆散布在芬蘭、義大利、日本、颱灣與美洲,這裏隻先列齣這幾個地點。然而,「你做什麼?」這個問題,是最應該被認真以對的──也就是為什麼這本書,不是一本「正常」的專題論文,而是種開放形式的對談;馬可、他的閤作夥伴、其他建築師、研究者、實論思考者,每個人的作品皆為──引述剋裏斯托佛.亞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 《大自然秩序的實證發現》(Empirical Findings from the Nature of Order)所說的──「探索我們知覺的方式、感覺生物與我們周遭環境的互動方式,如此的互動帶領我們去認識瞭解我們自己與生活的本質,最終,甚至希望能瞭解,至少在部分上,自我靈魂的本質。」令人驚異的是,分開獨立的訪談,最終彷如一場所有參與者相互對話的大對談。在這一係列的對談裏,我們檢視瞭第三代城市的不同麵嚮,來完成這城市的終極目標─將人類與所有可能的創造力互動極大化──同時基進地重新思考城市與自然(包含人類本質)的關係。
在〈建築師在生化圈的角色〉(The Architects’ Role in the Biosphere)一文中,生物學傢暨哲學傢伊霍.海拉(Yrjö Haila)將建設(construction)與栽培(cultivation),這兩個人類在地球上「取得我們的空間」的邏輯並列在一起。建設與綫型擴張和成果有關;而栽培與循環有關,並且立足在人類與大自然的互相依存之上纔得以完成。與其他任何生物相比,我們人類對地球生態造成的改變最大,但直到現在,我們纔開始發覺到,我們的生活「對於整個生物圈所維持的全球新陳代謝有多大程度的依賴」。挑戰在於,我們如何在建設與栽培這兩種態度之間取得平衡。而這項艱钜任務的深廣程度,讓我們無法立刻在大範圍裏看到它的結果──這也許是正常的;因為當你必須處理的不是形塑與控製生命,而是在讓它發生之際,同時間也找到你自己在其中的獨特位置。
這些篇章中呈現的思考與作品,突顯齣瞭不少第三代城市的成功實例,使其不隻是紙上談兵的概念或夢想而已。這是事實:是已經在發生的事實。更多的是,它已經一直在那裏瞭,即將從瀝青柏油路麵的裂隙中萌芽迸發而生。
本書最後一章,我們將反思建築師在變動的現實裏必須扮演的多重角色。能迴答這個問題的人,是那些擔任「推動者」的角色──能夠感知到可能性與潛力,更重要的是能連結這些流嚮,進而啓發不斷地創造,同時包容生命的發展,並提供讓更多生命得以發跡與生長的環境。
在馬可為《生物城市主義期刊》(Jorunal of Biourbanism)寫的一篇文章中,他說,「生物城市(biourban cities)不是某個文化、種族、經濟教條、時間軸或其他生活或存在方式的同質性平颱」,而是「工業發展環境中的裂縫裏,有機的知識流入的都市堆肥處」,而且在這裏,「工業都市主義」(industrial urbanism)已經被「吃進那個城市與大自然提供生命的係統達到和諧一緻的地方」。他自己的作品便呈現齣很隱微卻很強大的創造力,並且與針灸十分相似:感測到一個即將迸開的新裂縫,並且使其發生。他鼓勵嚮城市裏「官方」與「非官方」的共生區域學習;例如貧民窟、移工營、自力營建的居處、社區花園與都市農場,這些是「城市發展與大自然之間,試圖拯救城市的緩衝區」。
「工業主義與其他任何人類的控製會帶來僵硬;而且,如同大自然中的任何東西一樣,僵硬代錶死亡。彈性、流動性、柔軟與脆弱則帶有生命,所以問題本身可能含有比完全控製的企圖更好的解決之道。」喜愛俄羅斯科幻作傢斯特魯加茨基兄弟(Arkady and Boris Strugatsky)的馬可這麼錶示。斯特魯加茨基兄弟的社會科幻小說主題,處理的問題都無法在物質層麵提供令人滿意的解決之道。他們提問的答案,都隻有一種,且極度個人化,並且隻有在人們往自己內心深處探索時纔能取得。即興發揮與解決問題不一樣,而馬可傾嚮於選擇機會與即興發揮。
「時間不是金錢。」馬可說。我要加上:路徑不是公路。它沒有先被誰走過以確保我們的成功──每個時刻,隻在我們踩下步伐的時候發生,而且正是因為我們創造齣瞭這些時刻。
導讀
馬可.卡薩格蘭 Marco Casagrande
open form: now open
開放形態:現在開放
我們在玩「華沙遊戲」(the Warsaw Game),一種奠基於即興發揮與隨著更迭狀況作齣調整、策略性的「開放形態」(Open Form)遊戲,主導者是卑爾根建築學院(Bergen School of Architecture)創辦人史萬恩.哈特略(Svein Hatløy,1940-2015)、「微觀都市方略」(Micro-Urbanism)觀念的作者,以及「都市閃光工作坊」(Urban Flashes workshops)的創始人季鐵男。2002年在倫敦的都市閃光工作坊裏,史萬恩要求我們去找迴收的建築材料,放到一颱購物車裏,然後使用這些材料,讓它們能「主導」與「溝通」。季鐵男深受這背後的哲學觀吸引──這是他的道傢史觀第一次遇上開放形態。倫敦行之後,季鐵男開始在卑爾根教學,而史萬恩則去瞭中國。
開放形態論壇的概念一開始是在1959年由具前瞻性的建築師、理論傢暨藝術傢奧斯卡.漢森(Oskar Hansen)提齣,並進一步由史萬恩.哈特略發展而成。開放形態的觀念是立基於無作者的個人與集體行動,進而産齣接續反應的可能性。運用這個方式,建築師的角色轉變為指導齣具建設性的溝通。開放形態不是某個特定之人的不朽功業,而其曆經的程序也相對地更加生物性且自然。
史萬恩給瞭我一個在卑爾根建築學院的教職,我在那裏追求對開放形態更進一步的瞭解。慢慢地,我發展齣「都市針灸術」(Urban Acupuncture)的概念,這要感謝史萬恩以及季鐵男的「微觀都市方略」。現在迴頭來看,我們與薩米.林塔拉(Sami Rintala)在不同城市製作的建築裝置,我可以在那些裝置作品裏看到都市針灸術已然生成。如同針灸的針,那些裝置作品接閤在地社群的集體意識,並試圖與每個當地特有的知識溝通。我們的建築錶現法是開放形態,亦即我們並不倚賴任何特定的領域理念──甚至無關乎任何建築學派─而是自由地在藝術與科學的各種領域之間翱翔。
「首先你得先有東西想說,然後找到怎麼說齣來的方法。」1982至1994年的芬蘭總統毛諾.柯伊維斯托(Mauno Koivisto)說道。「所有藝術的關鍵就是你要在場。」芬蘭傳奇性舞者暨編舞傢賴霍.凱拉(Reijo Kela)這麼說道,他在1999年燒毀我們的〈大地的逃脫〉(Land(e)scape)。「真實的真實(Real Reality)是完全的,而且是不能夠被揣測的東西,」愛丁堡和赫爾辛基大學的阿拉伯文與伊斯蘭研究學係教授雅科.哈密-安提拉(Jaakko Hämeen-Anttila)這麼說,他繼續說道:「現今社會上毫無價值的虛空將被道德填補;如同角落裏必有空隙讓風灌入,使窒息的屋內空氣得以流通。」我們渴望感受這道風,並且打進更多的角落裏。設計,通常代錶著某種封閉的形式;它仰賴控製方法論,而控製方法論會扼殺「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設計不該取代真實(reality);真實是正常的。我們選擇相信超常態(supernormal),以及相信那些會嘲笑它們的「設計者」的作品。
我因意外而留在颱灣,雖然史萬恩老愛宣稱:「是我們派馬可去亞洲的。」真正的原因是在2000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時,發生瞭兩件看似不相乾的事情:季鐵男來參訪我們的〈60分鍾人〉(60 Minute Man)船隻,我則從地上撿到他的颱灣館宣傳單。於是我們碰麵,他邀請我到颱北參加我第一次的都市閃光。來到颱北之前,薩米與我在日本做瞭幾件作品,但颱灣纔是開放形態真正抓住瞭我的地方。我在寶藏巖,與寶藏巖一起,以及為瞭寶藏巖所做的一切,是開放形態帶給我的最重要的撞擊。在那裏,史萬恩教導的一切都化為真實,因為寶藏巖就是對抗官方城市的開放形態。如果沒有開放形態,我根本不可能處理那一切;沒有開放形態,我就不會想齣都市針灸術,也不會在淡江大學任教。那裏的學生在我成為他們的「意外老師」後,沒多久就開始玩起瞭華沙遊戲,所以就某種程度來說,史萬恩說對瞭:派我到颱灣的是他。
在淡江任教的時候,我獲得瞭全麵的支持來發展我的都市針灸術,研究廢墟的真髓,最後並發想齣瞭「第三代城市」(The Third Generation City)。之後,芬蘭阿爾托大學(Aalto University)的全球永續科技研究中心(Sustainable Global Technologies research centre, SGT)放手讓我從事跨領域設計,這再一次使我更接近開放形態,並且有更多的領域加入:河川工程學、未來學、文化研究、景觀建築、土木工程、社會學、園藝學與人類學等。2010年,我們得以在颱北成立瞭我們自己獨立的研究室〈廢墟建築學院〉。完全地跨領域並且奠基於開放形態,這個學術佔屋平颱的閤作單位包括瞭忠泰建築文化藝術基金會、阿爾托大學的全球永續科技研究中心、淡江大學,以及颱灣大學(尤其是社會學係)。同時,在義大利的阿爾泰納(Artena),一群跨領域的大學教授們成立瞭「國際生物城市主義協會」(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Biourbanism),並且也與〈廢墟建築學院〉建立瞭強烈的連結關係。經由這串連結關係,開放形態開始獲得更多的科學根基。這群生物城市主義者既是生物學傢,同時也是數學傢。
開放形態不屬於任何設計師;建築師不是作者,而是溝通者,或是一位人事情報員(human intelligence officer)。大部分的既存建築物都是「封閉形態」(closed form),也就是人類控製與權威的結構展現;大自然則是「開放形態」,因此建築的重責大任應該是在人類天性與大自然的聲音之間取得協調。都市針灸術試圖穿透瀝青與水泥的工業薄層,與原始的土壤連結。穿透城市肌理形成的裂縫,則提供瞭在地知識和開放形態(本質上是相同的東西)的孕育空間。「第三代城市」就是佈滿裂縫的城市。
建築是一種環境藝術。它不屬於建築師,而是屬於自然;它屬於我們的感官,而非依我們的控製而得來。缺乏敏感,就如同行屍走肉──它是死亡的同伴。
當我還是赫爾辛基科技大學(現已改為阿爾托大學,Aalto University)的學生時,1992至1997年時任建築係係主任的尤哈尼.帕拉斯瑪(Juhani Pallasmaa)教授要我們看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電影──《潛行者》(Stalker)。由塔可夫斯基執導、改編自斯特魯加茨基兄弟的小說《路邊野餐》(Roadside Picnic),其所描述的和生命有關,也正是一種開放形態──你在那個「異境」(Zone)之中要不是活命,不然就是死。森林永遠都是同一座,但路徑卻從不相同。路徑屬於意外的領域,但開放形態不是個謎題。重點在於建構與解構哪些元素,能夠增大生命茁壯成長的機會。這些能提供生命的元素──不論是房子、場域、社區,或是城市──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它們遵循生物性的法則。
「盡己所能活下去」(Existence Maximum)是大自然的既定法則。要能在特定狀況下取得最好的生存條件,就必須要放鬆人類的操控,讓大自然得以進入。大自然生態以及人類是一體且相同的,但人類的控製則是另一迴事;人類的控製是汙染與嫖娼的根源。建築師沒有義務成為設計的娼妓,建築也沒有必要為人類控製所錶彰。如果辦不到,那麼建築物應當被毀棄(be ruined)。
當人造物成為大自然的一部分時,一座廢墟即生成。開放形態試圖製造廢墟──因人類的錯誤而敝破的房屋、社區與城市,再將之轉化成裂縫的平颱。這些裂縫不是貧民窟、不是城市裏臭味外溢的區域,而是光綫得以進入的孔隙。在裂縫的宇宙裏,現代人是反生命的存在型態。房子並非盒子,人們不應該待在裏麵。建築提供必要的屏蔽、一個讓人休息與沉思的開放形態。建築物提供我們舒適的居所,但它不僅止於此。房子是光綫進入的所在,城市本身自成它自身的生物學體係,它是生物城市光綫薈萃的星係,也是裂隙的銀河。
拉動還能發齣聲音的搖鈴
忘瞭你所謂的完美提議
萬事萬物皆有裂縫
光綫纔得以進入
──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頌歌》(Anthem)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馬可.卡薩格蘭:邁嚮第三代城市”——這個書名瞬間勾起瞭我作為一個颱灣讀者對城市未來發展的強烈求知欲。我一直對城市的變化充滿瞭濃厚的興趣,從我童年記憶中的景象,到如今充滿高科技元素的都市,城市的麵貌在不斷地更新迭代。卡薩格蘭這位在國際城市規劃領域有著重要影響力的學者,他提齣的“第三代城市”概念,在我看來,絕非泛泛而談,而是蘊含著對未來城市形態的深刻洞察。我非常想知道,他所描繪的“第三代城市”究竟具有哪些與眾不同的標誌?它是否意味著更加強調綠色生態,例如在城市設計中融入更多的自然元素,實現能源的自給自足?又或者,它更側重於社會的包容性和社區的凝聚力,讓不同背景的人們都能在城市中找到歸屬感?我特彆關注的是,在追求效率和便利的同時,如何纔能夠保留城市的獨特魅力和曆史文脈。這本書,對我來說,就像是打開瞭一扇通往未來城市生活的美好想象之窗,我渴望從中找到關於如何構建一個既充滿活力又溫情脈脈的城市的新思路。
评分讀到“馬可.卡薩格蘭:邁嚮第三代城市”這個書名,我第一個浮現的畫麵是城市如同一棵正在成長的樹,有紮根於過去的根係,有承載現在的枝乾,而“第三代城市”便是它蓬勃嚮上、伸展至未來天空的新生枝葉。我一直覺得,颱灣的城市發展,尤其是在過去幾十年中,經曆瞭一段高速的、有時甚至有些粗糙的增長期。我們見證瞭高樓林立、交通網絡日益發達,但也伴隨著環境壓力、資源消耗以及人際關係的疏離。所以,當我看到“第三代城市”這個概念時,我本能地會聯想到,這是否意味著一種更可持續、更人性化、更有韌性的城市發展模式?卡薩格蘭這位國際知名城市規劃大師,他的觀點一定不隻是停留在錶麵上的摩天大樓或智能交通。我猜測,他提齣的“第三代城市”很可能涉及到更深層次的社會結構、生活方式甚至價值觀念的轉變。或許,他會探討如何通過城市設計來促進社區的凝聚力,如何利用科技來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同時又不犧牲掉我們與自然之間的聯係。這本書,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本關於建築和規劃的書,它更像是對我們未來生活方式的一次深刻的叩問,一次對人類與城市關係的重新審視。我想看看,卡薩格蘭是如何看待一個“活著的”城市,一個能夠適應變化、自我更新,並且真正為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服務的城市。
评分“馬可.卡薩格蘭:邁嚮第三代城市”——這個書名勾起瞭我內心深處對城市未來演進的好奇心。作為一名長期生活在颱灣的讀者,我親身經曆瞭城市從相對樸實的樣貌,蛻變為如今高樓林立、交通復雜的現代都市。每一次的改變,都伴隨著科技的進步和人口的增長,但我也常常會思考,我們這樣的城市模式是否真的是最終的形態?卡薩格蘭這位國際知名的城市規劃專傢,他的“第三代城市”概念,在我看來,一定不是簡單的“量變”,而是可能意味著“質變”。我非常想知道,他所描繪的“第三代城市”究竟擁有哪些與眾不同的特質?是更加注重生態平衡,還是更強調社會公平?亦或是,它是一種能夠真正實現人與技術、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全新城市形態?我尤其關注的是,在未來的城市發展中,如何纔能夠避免城市空間的單一化,如何保留城市的獨特韻味和曆史文脈。這本書,對我而言,就如同開啓瞭一扇通往未來城市生活的大門,我渴望從中汲取養分,理解我們應該如何為下一代構建一個更具吸引力、更可持續的城市。
评分“馬可.卡薩格蘭:邁嚮第三代城市”這個書名,讓我立刻聯想到一種關於城市演進的宏大敘事。作為一個從小在颱灣城市環境中長大的人,我親眼見證瞭城市從相對樸實的麵貌,逐步蛻變成高樓林立、交通繁忙的現代都市。然而,隨著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和人口的快速增長,我也常常會思考,我們目前的城市模式是否真的能夠長久持續?“第三代城市”這個概念,在我看來,並非簡單的“升級版”,而可能是一種全新的範式。我想知道,卡薩格蘭會如何解讀這個“第三代”的含義?它是否意味著更強的環境可持續性,例如在能源利用、廢物處理、綠色空間規劃等方麵有革命性的突破?抑或是,它更側重於社會層麵的創新,如何構建更包容、更公平、更具活力的社區?我尤其好奇,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他會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在塑造未來城市中的角色,以及它們將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這本書,對我而言,可能是一扇通往未來城市生活圖景的窗口,我渴望從中獲得啓發,理解我們應該如何為下一代構建更美好的城市傢園。
评分“馬可.卡薩格蘭:邁嚮第三代城市”——僅僅是這個書名,就足以讓我這個對城市規劃與未來發展充滿好奇心的颱灣讀者,燃起強烈的閱讀衝動。我一直在思考,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城市正經曆著前所未有的變革。從過去以工業為驅動的城市形態,到如今以信息和知識為核心的都市,我們似乎正在邁嚮一個新的階段。卡薩格蘭這位在城市領域享有盛譽的專傢,他所提齣的“第三代城市”概念,在我看來,絕非簡單的技術堆砌或空間擴張。我猜測,它更多地是一種對城市本質的重新思考,是對人類在城市中生存狀態的深刻洞察。我個人非常關心,在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中,如何能夠避免韆城一麵的尷尬,如何保持城市的獨特性和地方特色。我希望,“第三代城市”能夠是一種更加人性化、更具韌性、更能適應未來挑戰的城市形態。它是否會更加強調社區的活力,更加關注居民的幸福感,以及更加注重城市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這本書,對我而言,就像是一次與未來對話的邀請,我期待著能夠跟隨卡薩格蘭的腳步,一同探索城市進化的下一個可能性。
评分“馬可.卡薩格蘭:邁嚮第三代城市”——單單是這個書名,就讓我感覺到一種強烈的探索欲。我對“第三代城市”的想象,更多的是一種超越瞭“鋼筋水泥叢林”和“電子信息節點”的融閤體。我猜想,它會是一種更具生命力的存在,就像一個有機體一樣,能夠感知、能夠呼吸、能夠進化。卡薩格蘭作為一個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城市規劃師,他的視角必然是宏觀且前瞻的。我非常好奇,他會如何定義“第三代”的特質,它與我們現在所熟知的“第一代”(可能是早期城市聚落)和“第二代”(即現代城市)有何根本性的區彆?我個人比較關注的是,在強調科技發展和效率提升的同時,如何能夠保留甚至強化城市的文化底蘊和人情味。颱灣的城市,尤其是在一些老城區,仍然保留著許多寶貴的曆史印記和濃厚的生活氣息,我希望未來的城市發展,不至於讓這些美好的元素消失。這本書,或許能為我提供一些關於如何平衡發展與傳承、科技與人文的思考方嚮。我想深入瞭解,卡薩格蘭的“第三代城市”是否能夠實現科技的便捷與社區的溫暖共存,能否創造齣既高效運作又充滿生活情趣的城市空間。
评分“馬可.卡薩格蘭:邁嚮第三代城市”,這個書名本身就充滿瞭引人入勝的想象空間。作為一名長期關注城市發展和城市生活變遷的颱灣讀者,我一直在思考,城市到底應該如何發展纔能夠更好地服務於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我們經曆瞭從早期簡樸的聚落,到工業時代的擴張,再到信息時代的加速,每一步都帶來瞭巨大的變化。卡薩格蘭提齣的“第三代城市”概念,在我看來,絕不僅僅是技術上的迭代升級,而更可能是一種關於城市本質的深刻反思。我非常好奇,他會如何定義“第三代”的核心特徵?它是否意味著更加注重可持續性,例如在能源的利用、環境的保護、資源的循環等方麵有著全新的解決方案?又或者,它會更加強調人文關懷,如何在城市的設計中融入更多的社區互動,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歸屬感?我特彆希望,這本書能夠為我們提供一些關於如何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保持城市特色和文化傳承的思路。我想知道,卡薩格蘭的“第三代城市”是否能夠實現科技的便利與人情的溫暖並行,讓城市既充滿活力,又溫情脈脈。
评分“馬可.卡薩格蘭:邁嚮第三代城市”——這個書名瞬間點燃瞭我對城市未來發展的好奇心。我一直在思考,我們現在居住的城市,是否已經是發展的終點?或者說,我們是否正在朝嚮一個全新的方嚮邁進?卡薩格蘭作為一位在城市規劃領域享有盛譽的專傢,他所提齣的“第三代城市”概念,在我看來,絕非簡單的對現有城市模式的修修補補,而更可能是一種顛覆性的創新。我非常想知道,他所定義的“第三代城市”的核心理念是什麼?它是否意味著更加強調城市的韌性,以應對未來可能齣現的各種挑戰?抑或是,它更注重社區的活力和居民的參與感,讓城市真正成為一個充滿人情味的地方?我尤其關注的是,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他會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技術在城市建設中的作用,以及它們將如何重塑我們的生活方式。這本書,對我來說,就像是一次對未來城市生活的深度探索,我期待著能夠通過它,窺見一個更加美好、更加宜居的城市景象。
评分“馬可.卡薩格蘭:邁嚮第三代城市”,這個書名一齣現,就立刻觸動瞭我內心深處對於城市未來發展的種種思考。作為一名在颱灣生活多年的普通市民,我深切地感受到城市在我們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它所麵臨的各種挑戰。從我成長的年代,城市還是相對樸實的麵貌,到現在的高樓林立、車水馬龍,城市的麵貌變化實在是太快瞭。我一直很好奇,未來的城市會是什麼樣子?卡薩格蘭這位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城市規劃專傢,他提齣的“第三代城市”概念,在我看來,必然蘊含著他對城市發展深刻的洞察和前瞻性的思考。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他所說的“第三代”究竟是什麼意思?是比現在的城市更智能、更高效?還是更注重人與人之間的連接,更強調社區的活力?或許,它是一種能夠更好地應對氣候變化、資源短缺等全球性挑戰的城市模式?我特彆關注的是,在追求技術進步的同時,如何能夠保留城市的溫度和人情味,讓城市真正成為我們心靈的棲息地。這本書,對我而言,就像是一份關於未來城市生活的“預言書”,我渴望從中找到答案,理解我們應該如何共同努力,創造一個更美好的城市未來。
评分馬可.卡薩格蘭:邁嚮第三代城市,這個書名本身就勾起我無限的遐想。作為一名長期關注城市發展和未來趨勢的颱灣讀者,我一直以來都對“城市”這個概念抱持著高度的好奇心。從過去的聚落到現代化的都市,再到未來可能齣現的全新形態,每一步的演進都蘊含著人類社會的力量與智慧。卡薩格蘭這個名字,對我來說並不陌生,他是一位在城市規劃和發展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思想傢。我期待這本書能帶領我深入理解他對於“第三代城市”的獨到見解,究竟是什麼樣的概念?它將如何顛覆我們對現有城市的認知?是更強調科技的賦能,還是更注重人性的迴歸?抑或是兩者兼備,形成一種全新的城市生態?我腦海中浮現齣許多畫麵,或許是垂直農業與城市共生的綠色空間,或許是智能化交通係統徹底改變通勤模式,又或許是社區形態的重塑,讓居住者在城市中找到更深層次的歸屬感。書名中的“邁嚮”二字,更是充滿瞭動感,它暗示著我們正處於一個轉型期,未來的城市並非遙不可及的幻象,而是正在發生、逐步實現的現實。我迫不及待地想從書中的篇章中,一窺卡薩格蘭大師如何描繪這幅宏偉的未來城市藍圖,以及他為我們指引的路徑。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