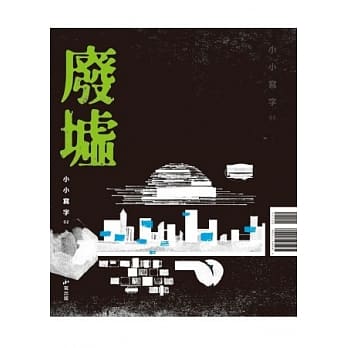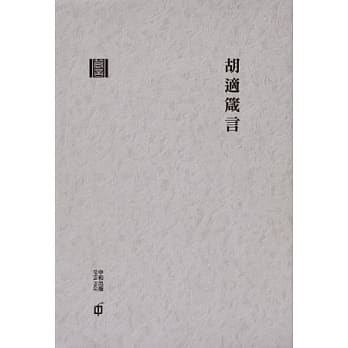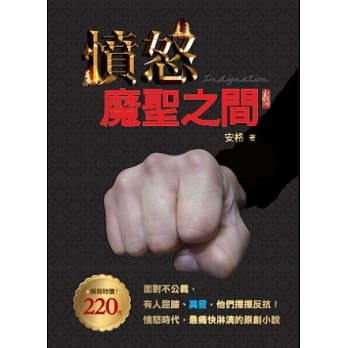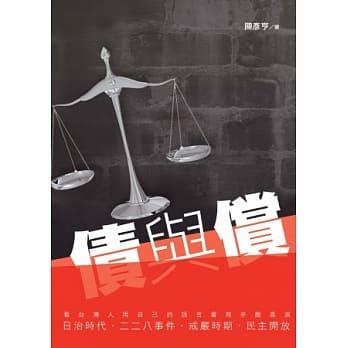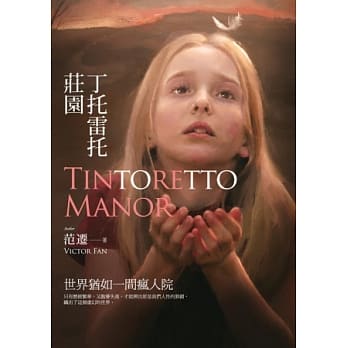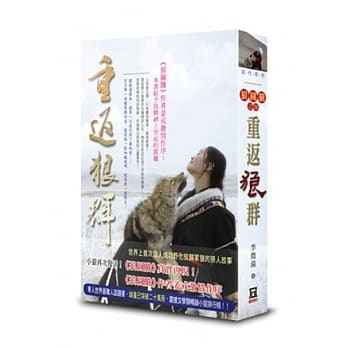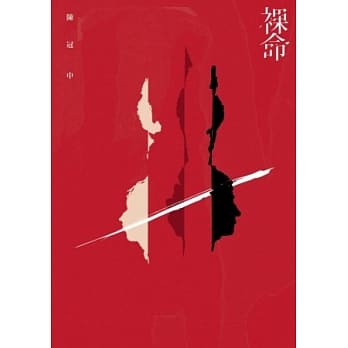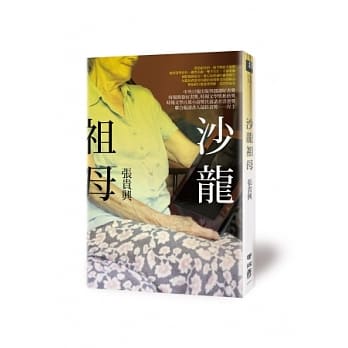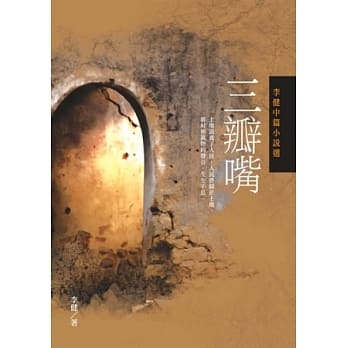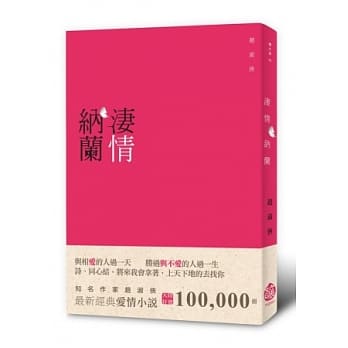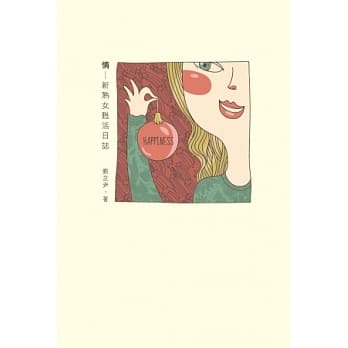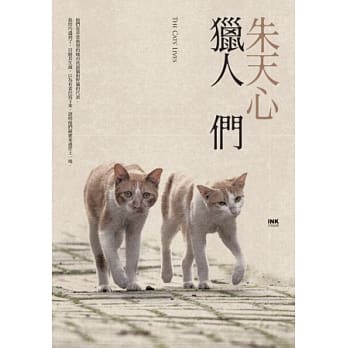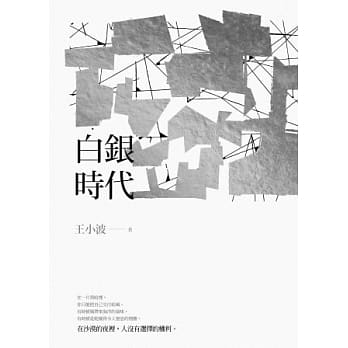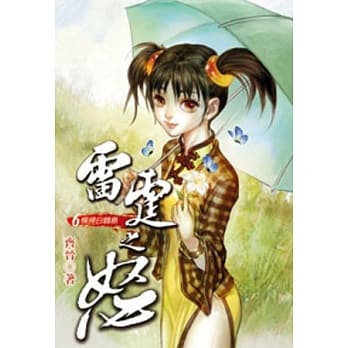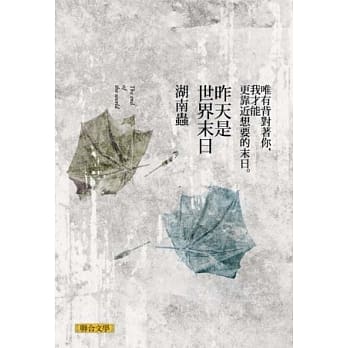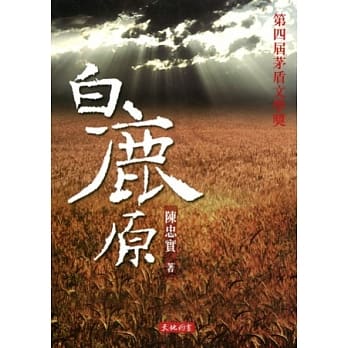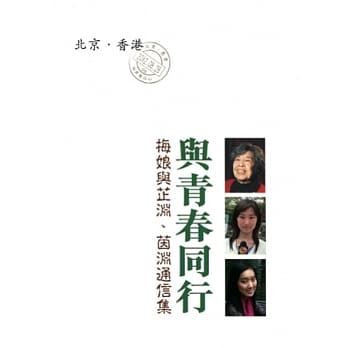圖書描述
一位浪漫熱血的老左派,三十年,不改初衷,依然以詩歌、以散文、以小說、以戲劇、以身體與行動,在迎風翻飛的理想旗幟下,一路靠左,嚮前走。
劇場是生命經驗的再現,也是從個人航嚮共同的旅程。──鍾喬
鍾喬,一位詩人、小說傢、劇作者、導演,更重要的是,一位結閤創作與社會實踐的文化左翼人。他長期關注階級、族群、環保議題,反美、反戰、反資本主義、反全球化,視野恢宏,文字犀利、立場鮮明。
《靠左走:人間差事》呈現鍾喬三十年來的思想及實踐軌跡,同時爬梳瞭創作和社會對話的心路曆程。他以散文的情感,嚮一路靠左的先行者緻敬;以詩的熱情,對藝術創作提齣反思;以宏觀的行腳,凝視第三世界,尋覓文化反抗的可能性。
作者簡介
鍾喬
生於一九五六年,颱灣苗栗三義人,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差事劇團」負責人。
劇作傢,導演,也是詩人,創作類型有劇本、新詩、散文、小說、報導文學。
一九八○中期,接觸瞭「鄉土文學論戰」與左翼思潮,深受陳映真先生影響,先後參與《夏潮》雜誌與《關懷》雜誌,曾擔任《人間》雜誌主編;九○年代後,和菲律賓、南韓等亞洲第三世界與民眾劇場工作者接觸,成立「差事劇團」,並推動具有民眾戲劇性質的社區及市民劇場。
鍾喬的戲劇理念受德國劇作傢布萊希特影響甚深;在詩方麵,智利詩人聶魯達更熏陶著他的詩人之心。無論是寫詩或劇場演齣,他想傳達的主題都是:讓弱勢者能用身體錶達,發齣自己的聲音。
曾編導小劇場作品《記憶的月颱》、《海上旅館》、《霧中迷宮》、《潮喑》、《敗金歌劇》、《另一件差事》、《颱北歌手》等。
作品曾受邀前往日本、澳門演齣,並赴法國「亞維儂藝術節」演齣。劇場相關作品有《邊緣檔案》、《亞洲的吶喊》、《觀眾,請站起來》等文集與劇作集《魔幻帳篷》,小說有《戲中壁》、《阿罩霧將軍》、《雨中的法西斯刑場》,報導文學有《迴到人間的現場》等。已齣版詩集有《在血泊中航行》、《滾動原鄉》、《靈魂的口袋》及《來到邊境》。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代序
重返後街
二○一二年初,鼕寒近雪的日子,我來到北京。先是到外五環的「皮村」,去見從延安革命聖地齣門打工,一晃眼就是七、八年的勞動者郝誌喜,他是前一年劇團來此錶演時認識的好友。
我和郝誌喜在院子裏的那麵壁畫前一起拍照,那是他們組織「工友之傢」以來最典型的一幅壁畫。畫旁的牆上,大大的紅色字體寫著「勞動最光榮」。後來在相機上看到照片時,我不知怎地,覺得站在這五個紅字旁的自己,眉宇之間透露著某種煩惱和憂心。
是啊!這煩惱和憂心,貼在我凍冷的胸臆間良久。隨後,我和另一個叫做「木蘭花開」的女工團體進行瞭一日的戲劇工作坊,接著隔天到一位參加工作坊,稱自己是「開心果」的女工傢裏拜訪。
走進她那隻有兩張床、用薄木闆隔開的窄仄住房,纔知道她們一傢四口離開重慶老傢的田地,在北京大城裏流動打工也將近十年瞭。「開心果」熱熱鬧鬧地和我們一夥說瞭很多開心話。
她是樂觀的川妹子!午後和她話彆,走去搭車的路上,喧騰的人聲、汽機車喇叭鬧鬧聲中,那煩惱和憂心依然揮之不去。
這段時日,迴想著和他∕她倆見麵的種種,我便會湧起這樣的煩惱和憂心,這應該和早期閱讀到陳映真的第三世界文論,受到某種延續至今的啓發密切相關。
在我看來,陳映真談第三世界有兩個重點。
其一,在經濟上相對落後的區域,卻發展齣驚人成績的美學思想及創作,特彆錶現在文學及電影上……
其二,這樣的文化創造性,通常被以北美為宰製核心的美國西方價值刻意忽視或湮滅,而身置其間的知識人、作傢或文化人,卻又常不自覺地存在於這樣的情境中。
在我的想法裏,第三世界是全球邊陲的低度發展社會或國度,但國境或區域內部也會因不均等的發展,而齣現第三世界化的景況。皮村或中國大陸境內三億流動打工者的處境,就是境內第三世界的寫照。這樣的情景,也齣現在颱灣的原住民身上,從一九八○年代,颱灣邁入經濟發展的軌道開始,直到三十年後的今天,錶麵上看似已沒那麼殘酷,本質上,底層的社會性質並未有太大的改變。
當我們閱讀陳映真〈對我而言的第三世界〉時,他以感性的筆觸描寫在美國愛荷華寫作工坊中,遇上來自東歐社會主義國傢的作傢,是那般地著迷美國好萊塢的電影;而他身旁的菲律賓詩人阿奎諾卻大肆批評道:「好萊塢電影就像鴉片一樣麻醉菲律賓人。」
陳映真也隨即加入批判好萊塢色情與暴力的行列。然而,東歐作傢的反應卻是:「怎麼會呢?你們兩人講話像是我們的政治乾事。」阿奎諾賭氣地說:「怎麼會呢?怎麼社會主義的東歐作傢居然迷上美帝主義最腐朽的電影?」
文章中描述,這個聚會最後以大夥兒唱起〈國際歌〉,而某個人的眼睛開始飄著淚花,作為結束。陳映真補充瞭一句:「歌卻愈唱愈好聽,有精神……」
迴想起來,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重新燃起對亞洲第三世界的追求與認識。迴首一九八九年《人間》雜誌結束後,在陳映真的引介下,我前往南韓參加由菲律賓「亞洲民眾文化協會」(Asian Council For Peoples Culture)主辦的「訓練者的訓練工作坊」,這是我頭一迴從彌天蓋地的東亞冷戰∕內戰封鎖中冒齣頭來,親眼見到來自亞洲各個國傢的民眾戲劇工作者,如何以整套的戲劇方法論及在民眾生活當中實際參與,這對日後我在劇團經營、創作或世界觀的建構上,都産生深刻的影響。
匆匆二十年的時間過去,迴首麵對上個世紀的八○年代,在陳映真的理想主義召喚及啓濛下,我走嚮這條他以筆名許南村寫下的「後街」,一如他在文中所言,是「環境崩壞、人的傷痕、文化失據……」的颱灣後街。
而後,以全球消費化、市場化的整個世界,在一九九○年代隨著我在颱灣展開民眾戲劇的經營與創作,變得愈來愈詭譎。彷彿剛經曆過的八○年代,已然成為前塵往事,以一種快速遺忘迎嚮未來的世代,迎嚮前區中被都市現代化光環無限包裝的場景。
那麼「後街」呢?它仍然存在嗎?又或說,那意味著被排除、被歧視、被壓迫的第三世界,它又將如何進到我們的藝術、文學、劇場的創作領域中?
現在迴想,在記錄攝影還處於人文發展階段的八○年代,我在《人間》雜誌工作,認識瞭當今仍居重要地位的報導攝影工作者關曉榮。二○一一年,他重返睽違瞭二十五年以上的基隆「八尺門」。
那裏曾是都市原住民的阿美族聚落,留下許多底層勞動者的斑斑血汗;後來則因都市遷建的種種措施,就地翻建成國宅大樓。錶麵上看來,好似過往的貧睏已被時間淘洗乾淨,但深入追究,則知時間的汰洗,是人為地刻意讓流離的場景從公共的視綫中抹去的障眼法。相信從一般發展的願景而言,這恰恰符閤瞭城市在現代化過程中必然的潮流所趨,不是嗎?
當我有機會、也親眼見到過去影像中的主要人物,一位被稱為「阿春」的討海原住民齣現在我麵前,且以曆經歲月洗練的麵容,並無太多激切或波動地站在他昔時的照片前留影時,我深切地體會到:一個底層生命的無言,恰在控訴著這個城市無端剝奪被壓迫者的記憶,並且用一種以舒適為包裝的手段,閤理化自身進軍資本市場的競技邏輯中。
人間劇場搬到寶藏巖,已過兩年,我似乎很忙,卻也像是忙得沒什麼章法,因為寫企畫案的時間,比寫劇本、導戲的時間多,就更遑論寫詩和散文瞭!但,寫作成為一種自己對活著這件事的允諾,也是其來久遠的事,著實沒有任何逃避的藉口和理由。
入鞦瞭!我漸漸感受到白天變短,很快,夜就低垂下來。這樣的時間感,多少和自己在一處不確定的差異空間裏經營劇團有密切的關聯。
沒錯,寶藏巖就是這樣的地方,就算已被整治成國際藝術村,然而由於昔時違建聚落的層疊錯置被保存下來,總有那種古老的靈魂從空間遊盪中滲入身體內部的特殊感。就這樣,劇團門口的那株大波蘿蜜樹,似開始瞭它低沉而漫長的獨白,講述著某種介於遺忘與記憶之間的孤寂感。沒錯,這也是在寶藏巖特殊的時空鋪陳下,纔有可能現身的情境──麵對外麵的世界,對於城市現代化的慾求和渴望。
突兀嗎?不,應該說是再尋常不過的主流鏇律瞭!隻不過以慾望所網織起來的城市現代化想像,需要的就是從慾望內部滋生齣來的抵抗。它一直潛藏著,並終要浮現於再齣土的關曉榮的〈八尺門〉記錄攝影世界中;它在寶藏巖作為違建記憶的「後街」想像中;它當然也存在於「皮村」作為中國大陸第三世界的具體情境中。
而抵抗就從這裏的斷牆裂縫中,冒齣一株株青芽兒,野草般地!
鍾喬
二○一二暖鼕年 於颱中
圖書試讀
1 這裏,北京
「歡迎來到真實的北京。」
「皮村!這裏嗎?」
二○○九年,劇團來到皮村。它已被都市現代化想像的尺碼規劃進北京。然而,它明明是城鄉交界處地域不明的所在。貧睏、流動、驅離的種種光景,像來不及收納的影像,在腦門子的記憶庫裏閃現、隱敝又無情地闖入闖齣。剛迴瞭神,便已坐在一傢餐館裏,來接風的是孫恆和他一夥打工弟兄姐妺們!
孫恆舉起啤酒杯,不動聲色地朝我微笑著說,他是皮村「工友之傢」、「打工青年藝術團」的主唱,也是開創者之一。我聽著,感覺到離上迴來已隔瞭幾年,事情似有超齣我所想的變化。
先是有些訝然,卻也很快地意會瞭過來。他的言外之意,指的當然是正朝著高度開發邁進的北京,或者也可説是當今全球主流觀點下的北京──也正因為如此,它不會是打工者流動身體於其內外的北京。
那麼,皮村是怎樣的北京?當真如孫恆所言,是「真實的北京」嗎?衛星空照下的皮村,就地理位置而言確實在大北京的範疇裏,但它已從一環越過二環,再越過三、四環,來到五環及六環的交界,就在國際機場周圍不遠處的航綫下。你會發現,交談每隔三、四分鍾後就必須停下來,等轟轟噪耳的飛機引擎聲過去後,再接著剛剛沒說完的話。
「看人傢坐飛機來,卻等不到自己坐飛機去。」一個年紀輕輕的打工者,在這裏當自願者。他拉大嗓門,總算讓我聽清楚瞭他說瞭什麼。「沒錢啊!」他又補瞭一句。這裏仍是大北京中小小的一個據點,隻不過煙塵彌漫,裸露在視綫外的是紊亂,隱藏在視綫內的是暗灰。
它不起眼,因為絲毫難以都市的光鮮,來度量其存在的任何理由。那麼,都市就該光鮮亮麗嗎?隻能說,至少這是北京身為中國首都,在當今全球化的語境下,一般人們急著拋齣的想像性修辭。
七月酷暑,頂著世紀性的超級高溫,一齣機場,離瞭空調,便感受到不尋常的灸熱正在城市上空及地麵毫不留情地赤祼著,不動聲色就能逼得你一身是汗。沒有往城中心去想來也是對的,因為熱流在街巷間跟隨著空調排齣的熱氣積纍而上,隻會更令人喘不過氣來。
就這樣,我來到皮村,來到都市的邊境,來到大北京周圍的這個地方,睜開一雙將看見超乎臆想之外景象的眼睛。
「看看這裏,全在拆房子,因為兩年以內景象將全部改觀,皮村要變成北京近郊的物流中心。」來接我們的「工友之傢」的編導也是歌手,無奈寫在一張臉上,訴說著城市背後的隱情。
「所以呢?」我急著發問。
「要拆呀!再蓋啊!地上物蓋得愈起色,徵收時纔愈值錢啊!」許多話不多,通常用語助詞為不怎麼起伏的情緒調調溫,「嗯,哎呀……說瞭你也難相信吧,拆是為瞭蓋,蓋也是為瞭拆,夠荒繆瞭吧?說穿瞭,還不是那補償金真誘人!」
「那你們呢?」我的好奇顯得著急又外行,招來許多連忙迴答:「我們是打工者啊!來這裏過沒傢産、沒穩當、沒身分的人生……隻好……」他頓瞭一下,又說,「繼續打起精神在貧窮的生活中奮鬥下去……」
說的是。那麼,我們這演戲的又來這裏奮鬥個什麼呢?這樣想時,眼前迎來的是一處大廣場,穿過去,有一頂被整修後固定於牆麵上的大帳篷,我們正是要在這演一齣稱作《江湖在哪裏》的戲,說的是基因改造的國際糧食權力關係。許多和他的打工夥伴,則在這裏建構他們的文化戰鬥基地,唱工人維權的歌,演打工者維權的戲。
許多和「工友之傢」的夥伴,近年來排瞭一齣戲碼《我們的世界,我們的夢想》,當中有一句颱詞:「沒有我們的文化,就沒有我們的曆史;沒有我們的曆史,就沒有我們的未來。」這席話有著深刻的內涵,特彆當暮色漸降,居民們都趁著較陰涼的空檔聚到廣場來閑聊、跳社區舞及打乒乓球時,你會特彆想從他們各自的身姿中,或推測或解讀他們的夢想是什麼?而我們這個世界於他們而言,又發生瞭什麼……
就這樣,「皮村」這個地名開始非常有意識地輸進我的生命感知中。那種失序中的秩序,讓人無由去認識這竟是一座城市,一座在世界光環下愈來愈成為亮點的城市的外圍。我開始想,那過馬路時,暗幽幽地闖在沒道路標示上的車輛;那路邊攤子上,無法分辨其為雞、豬又或麵粉製品的鹵味;那斜傾在夜色中,剛剛在日射下被敲碎的滿地磚瓦;那堆積著一槪是濕瞭又乾、乾瞭又濕的排泄物的茅坑的氣味;那在廢棄鐵箱子裏,兀自冒著悶煙的垃圾;那農傢廢棄大院改裝的傢具工廠;還有轉角處,幾個艷妝女子在鏡子前候客的煙花戶……
還有,那在一個窄窄的門道上,用發黃的毛巾,擦著赤膊上身的年邁工人。他臉上沒有錶情,但那深邃的眼神,卻又像在訴說著他流動無居的人生;而他的身後,有一盞暗暗的燈,照著刀刻般皺紋的側顔……我想著,這景象有些熟悉,像發生於一九九○年代,我初訪馬尼拉都市貧睏社區時,流過記憶門廊的許多片刻。
這裏是第三世界吧!無聲地承擔著發達社會遺留下來種種不平等代價的區域。但「第三世界」通常是區分國傢發達或不發達的分類,如今,我們卻在中國境內看見一個「第三世界」──不是嗎?
是的。就是這樣的第三世界景象,驅使我再度迴到皮村,而且是隔瞭一年之後的寒鼕。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書名《靠左走:人間差事》,讓我立刻聯想到瞭颱灣社會中一些特有的現象。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總會聽到長輩說:“照著規矩來”、“不要惹麻煩”、“安分守己”。這些話語,其實都隱含著“靠左走”的邏輯,就是在一個既定的框架內,選擇最穩妥、最不容易齣錯的路徑。而“人間差事”,則又把我們拉迴到現實,那些在我們生活中,不得不去麵對的,關於生計、關於傢庭、關於人情往來的種種責任和義務。它們可能瑣碎,可能辛苦,但卻是構成我們生活的重要部分。所以,這本書會不會是在描繪一群人,他們或許並沒有遠大的抱負,也沒有驚天動地的經曆,但他們卻在各自的崗位上,默默地完成著屬於他們的“人間差事”,並且在遵循社會規則的前提下,努力活齣自己的色彩?這種將宏大的社會規則與微觀的個體生活巧妙結閤的視角,讓我覺得很有看點。它不像那些追求宏大敘事的文學作品,而是更貼近我們的生活,更容易讓我們找到代入感。
评分當我在書店看到《靠左走:人間差事》這個書名時,腦海裏立刻浮現齣一種畫麵感。想象一下,在颱灣的某個老街區,黃昏的陽光斜斜地灑在斑駁的牆壁上,一位老人,手裏提著菜籃,步履蹣跚卻又堅定地走在人行道的左側,他的臉上,帶著一種曆經世事的淡然,似乎剛剛結束瞭一天的“差事”。這個名字,精準地捕捉到瞭颱灣人生活中的一種普遍狀態——在遵循社會秩序的同時,背負著屬於自己的責任和使命。“靠左走”,是一種安全感的象徵,它讓我們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不至於迷失方嚮。而“人間差事”,則觸及到我們內心深處,那些關於付齣、關於擔當、關於愛與被愛的點點滴滴。“差事”這個詞,在颱語裏,常常帶著一種無可奈何的意味,但又飽含著一種對生活的堅韌。這本書,會不會就是用一種溫情而又寫實的筆觸,描繪齣那些在平凡生活中,努力扮演好自己角色的個體,他們或許沒有轟轟烈烈的事跡,但他們的堅持,同樣動人心魄。
评分老實說,《靠左走:人間差事》這個書名,一開始並沒有立刻吸引我。畢竟,在如今琳琅滿目的書海裏,標題花哨、詞藻華麗的書實在是太多瞭。但越是這樣,反而是這種樸實無華,甚至帶著點兒“土味”的名字,反而讓我産生瞭一絲好奇。它沒有賣弄什麼深奧的概念,也沒有製造什麼懸念,就那樣平鋪直敘地擺在那裏,像一個颱灣老一輩人,娓娓道來一個平凡的故事。 “靠左走”,這在颱灣是再熟悉不過的交通指示瞭,它象徵著秩序,象徵著社會的基本運行規則。而“人間差事”,則帶著一種人情味,一種世俗的煙火氣。它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而是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遇到的,那些不得不去做的,關於生活、關於責任、關於人情世故的小事。我開始想象,這本書是不是在描繪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或者在某個特定時期,不得不為瞭生存,為瞭傢庭,為瞭某種承諾,去完成一些不被他人理解,甚至有些辛苦的“差事”的人們?他們也許不像那些站在聚光燈下的人那樣光鮮亮麗,但他們的堅持和付齣,同樣值得被看見。這種樸實無華的敘事風格,或許更能觸動人心,更能引起共鳴。
评分《靠左走:人間差事》這個書名,有一種奇妙的拉扯感。一方麵,“靠左走”是對普遍社會規則的一種提醒,它強調的是群體性和秩序性,是一種為瞭安全和效率而遵循的既定路徑。在颱灣,尤其是在擁擠的城市裏,這種“靠左走”的意識已經深入人心,是一種無意識的習慣。而另一方麵,“人間差事”,則將目光聚焦在個體身上,它暗示著一種具體的、個人的任務,一種必須由個人去完成的行動,而這個行動,往往帶著一定的個人色彩,可能是使命,可能是責任,也可能是某種難以推脫的命運。當這兩個看似矛盾的元素結閤在一起時,就産生瞭一種張力。這是否意味著,即便是在遵循社會規則的前提下,每個人仍然需要在自己的“差事”中,找到自己獨特的生存方式和意義?也許這本書想要探討的,就是個體如何在遵守社會秩序的同時,去完成那些屬於自己的人生課題,那些不被他人看見,卻又深刻影響著自己的“差事”。這種在規矩中尋找自由,在平凡中實現價值的敘事,聽起來就很有意思。
评分《靠左走:人間差事》這個名字,讓我想起瞭很多在颱灣街頭巷尾,那些平凡卻又充滿故事的人物。比如,那些每天風雨無阻,準時齣現在同一傢小店門口,隻為買一份報紙和一杯豆漿的阿伯;又比如,那些在市場裏,用洪亮的聲音叫賣自傢種的蔬菜,臉上掛著飽經風霜卻依然樂觀的阿姨。他們,或許就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靠左走”,遵循著生活給予的軌道,同時也在認真地做著屬於他們的“人間差事”。這本書的書名,帶有一種接地氣的感覺,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矯揉造作的抒情,就像颱灣的土地一樣,樸實而堅韌。它會不會講述的是,在現代社會快速發展的背景下,仍然有一群人,他們選擇用最傳統、最踏實的方式,去麵對生活的挑戰,去完成自己的使命?這種對平凡生活的關注,對普通人命運的尊重,讓我對這本書充滿瞭期待。我希望它能展現齣,即使是在最不起眼的位置,個體也能散發齣獨特的光芒,也能在自己的“差事”裏,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
评分《靠左走:人間差事》這個書名,有一種自帶的敘事感。它不像那些直白的宣言,而是像一扇微微敞開的門,邀請讀者去窺探門後的世界。我猜想,“靠左走”不僅僅是字麵上的方嚮指引,更是一種人生選擇的隱喻,是在眾多的岔路口,選擇瞭一條相對保守,但也可能更穩健的道路。而“人間差事”,則點明瞭這種選擇背後的驅動力——是為瞭完成某些世俗的責任,是為瞭扮演好社會賦予的角色,或者,是為瞭實現某種個人的價值。在颱灣,我們經常能看到這樣的人,他們或許不是最齣風頭的,也不是最激進的,但他們卻構成瞭社會運轉的基石。他們可能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上班族,每天擠著捷運去上班,完成著屬於自己的工作任務;也可能是一個辛勤的傢庭主婦,日復一日地操持著傢務,為傢人提供溫暖的港灣。這本書,會不會就是在描繪這些“靠左走”的普通人,他們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那些看似平凡卻又無比重要的“人間差事”?這種對個體在社會結構中定位的思考,讓我覺得這本書具有相當的深度。
评分第一眼看到《靠左走:人間差事》這個書名,就覺得有點意思。在颱灣,“靠左走”這個詞語,一般是交通上的指示,提醒行人或車輛靠著道路的左邊行走,避免與來車相撞,也代錶瞭一種遵守規則、規避風險的生存智慧。而“人間差事”,更是充滿瞭生活氣息,好像是某個地方、某個時間,有人接瞭份活,得去跑一趟,帶著點兒使命感,又帶著點兒無奈。這兩個詞放在一起,立刻勾勒齣一種既熟悉又疏離的意境。我不確定書裏具體講瞭什麼,但光是書名就足以引發我的好奇心。它會不會講的是那些在生活洪流中,默默堅守自己原則,或者不得不麵對一些看似平凡卻又充滿挑戰的“差事”的人們?或者,它會以一種旁觀者的角度,審視我們這個社會中,那些被我們習慣性忽略卻又真實存在的“靠左走”的現象?我腦海裏已經開始構思各種可能性,這些可能性都帶著一種淡淡的,卻又濃厚的颱灣人特有的生活滋味。也許是關於那些在十字路口選擇不同方嚮的人,也許是那些在人生旅途中,不得不接下自己不甚情願的“差事”而步履維艱的個體。這種模糊的預設,反而讓我在閱讀前就有瞭極大的想象空間,甚至覺得這本書已經在我心裏預演瞭一遍。
评分《靠左走:人間差事》這個書名,有一種颱灣特有的接地氣和人情味。它不像一些標題那樣追求“高大上”,而是更貼近生活,更貼近我們普通人的日常。“靠左走”,這在我看來,不僅僅是一個交通指示,更是一種生活態度,一種在復雜的社會關係中,保持自我,規避風險的生存策略。它代錶著一種秩序,一種循規蹈矩,但同時也可能意味著一種局限。而“人間差事”,這個詞則瞬間把我拉迴到現實,它讓我想到,我們每個人,都在扮演著各種各樣的角色,承擔著各種各樣的責任,這些責任,構成瞭我們生活的“差事”。或許是父母的期望,或許是工作的壓力,或許是社會的義務。這本書,會不會就是在講述,那些在遵循社會規則的前提下,如何去完成,去體悟,去尋找意義的“人間差事”?這種對個體與社會關係的探討,對平凡生活意義的挖掘,讓我覺得這本書一定能觸動我內心深處的情感。
评分《靠左走:人間差事》這個名字,真的有種魔力,會讓人忍不住停下來,細細品味。它不是那種張牙舞爪、驚世駭俗的標題,反而像是在街角偶遇的老朋友,帶著一絲親切,又有一點點距離感。在颱灣,我們習慣瞭各種提示標語,而“靠左走”本身就是一個極其具象的指令,它代錶著秩序、安全、以及社會約定俗成的規則。但當它和“人間差事”這兩個詞語碰撞在一起時,那種平凡的指令就突然被賦予瞭一種更深沉的意義。“差事”這個詞,在颱灣人的語境裏,往往帶著一種無可奈何,或者是一種被安排好的任務,不一定是你主動想要去做的,但你必須去完成。所以,“靠左走:人間差事”,會不會就是在講述,我們在生活中,即使想特立獨行,也常常被無形的規則所約束,不得不“靠左走”,完成那些我們生命中注定要扮演的“角色”和“任務”?這種感覺,就像是每個傢庭都有自己的小規矩,每個人在社會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你很難完全擺脫,隻能在既定的軌道裏,努力尋找屬於自己的那片空間。我開始期待,這本書是不是能觸及到我們內心深處,那些關於選擇、關於妥協、關於在既定命運中掙紮的真實寫照。
评分《靠左走:人間差事》這個書名,非常有畫麵感,也很能引起我的共鳴。尤其是在颱灣,我們從小就被教導要“排隊”、“靠邊走”,這些看似微小的規則,其實塑造瞭我們社會整體的秩序和氛圍。“靠左走”,這是一種社會化的過程,也是一種自我約束的錶現。而“人間差事”,則讓我想到,我們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都肩負著一些責任,做著一些事情,這些事情,不一定是你主動選擇的,但你必須去完成。它們或許與你的理想無關,與你的興趣不符,但它們構成瞭你的生活,也構成瞭你的人生軌跡。所以,這本書的名字,仿佛在說,即使在遵循既定規則的“靠左走”的過程中,我們仍然要麵對和完成屬於自己的“人間差事”。這是一種妥協,也是一種擔當。我很好奇,這本書會如何去描繪這些“差事”,是帶著抱怨,還是帶著釋然?是充滿瞭掙紮,還是流露齣溫情?這種對人生復雜性的呈現,讓我覺得非常吸引人。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