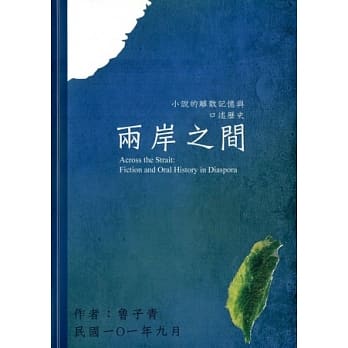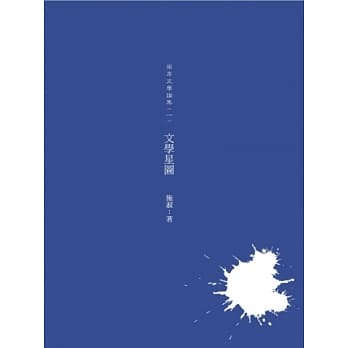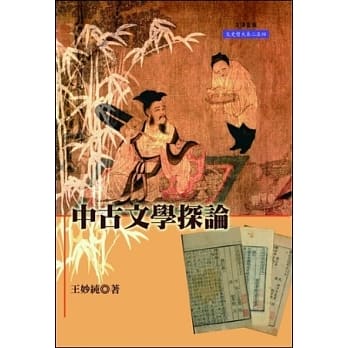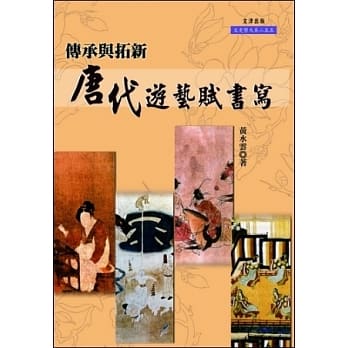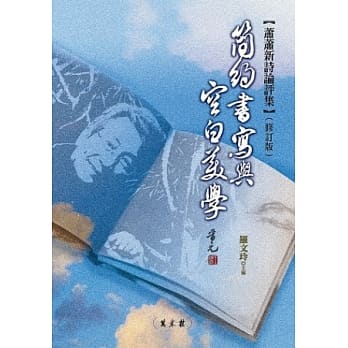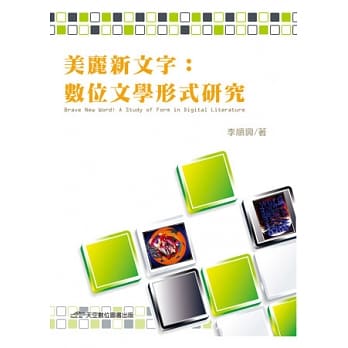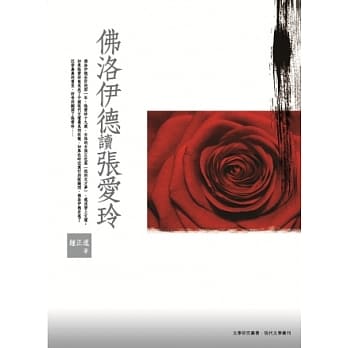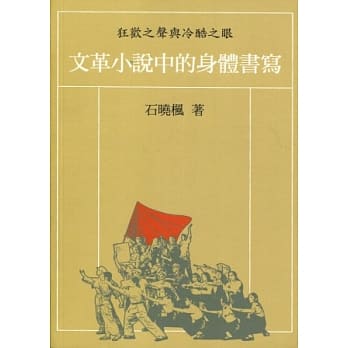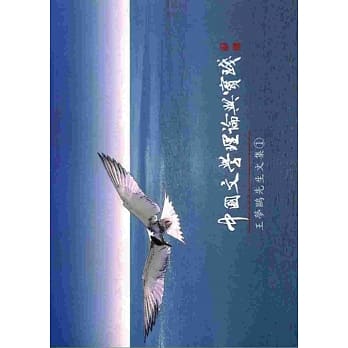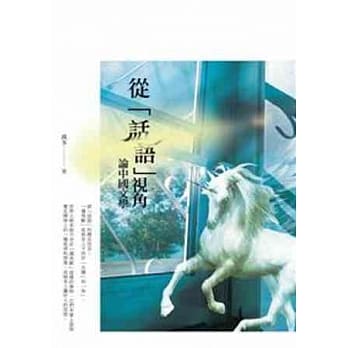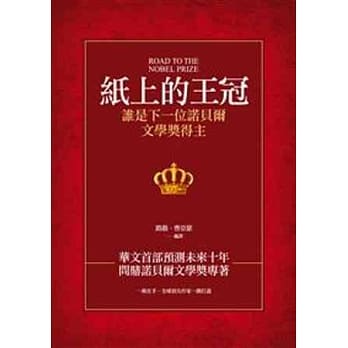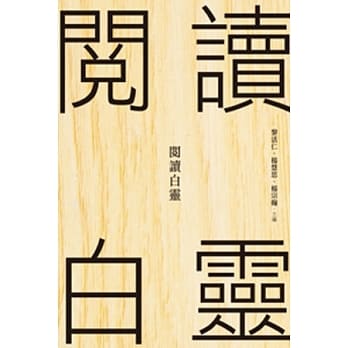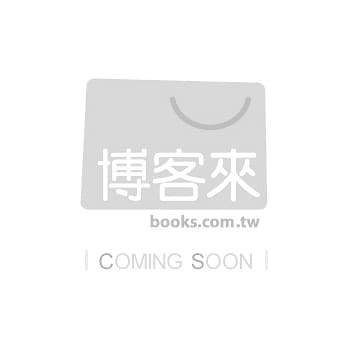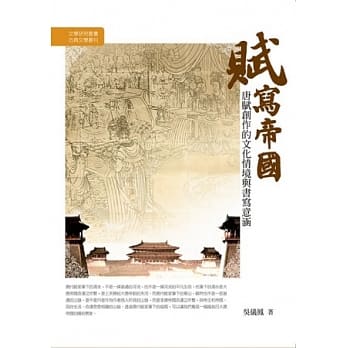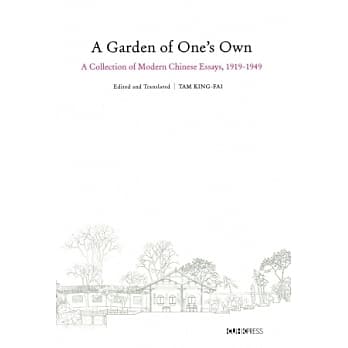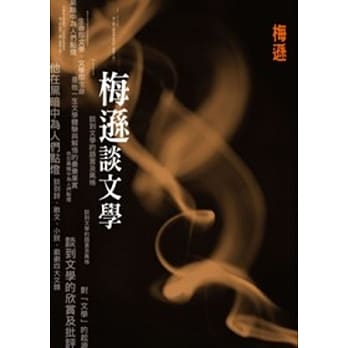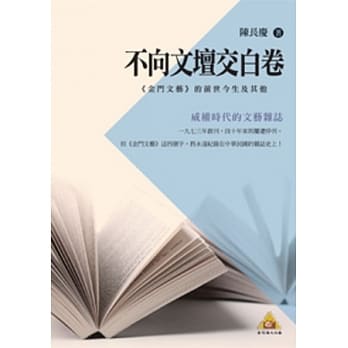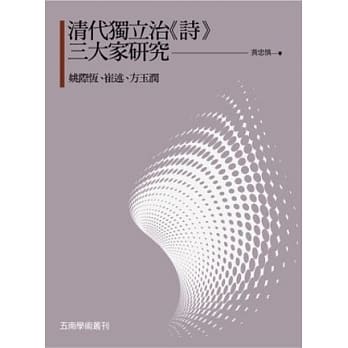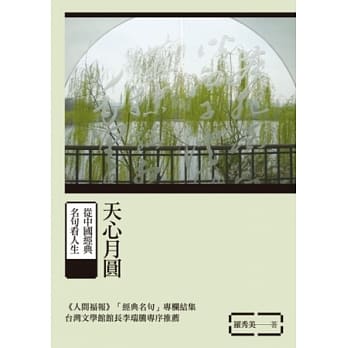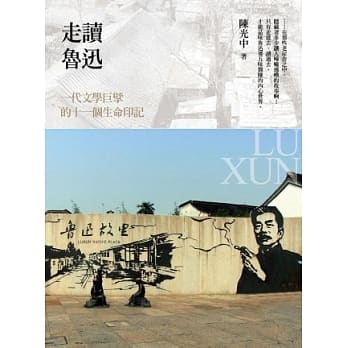圖書描述
《中國近現代文學轉型與日本文學關係研究》主要運用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方法,研究晚清至二十世紀三零年代初中國文學轉型所受到的日本文學影響,弄清轉型過程中所參照的日本文學樣本,揭示齣日本文學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生成所起的推動作用,並反思其負麵效應。
作者簡介
方長安
一九六三年生,中國湖北紅安人,武漢大學珞珈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聞一多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纔入選者。從事中外文學關係研究和新詩研究,齣版專著五部,發錶論文百餘篇。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引論
第一章 晚清文學革型與日本啓濛文學
第一節 小說界革命與日本政治小說
第二節 詩界革命與日本啓濛詩歌
第三節 文界革命與日本啓濛文學的文體改良運動
第四節 戲麯改良與日本新劇
第二章 晚清文學嚮五四文學轉型與日本文學
第一節 「國傢」文學嚮「人的文學」轉型與日本白樺派
第二節 政治文學嚮人情文學轉型與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
第三節 政治宣講式文學嚮寫實文學轉型與坪內逍遙的《小說神髓》
第三章 五四文學創型與日本文學思潮
第一節 前期創造社與日本唯美主義文學
第二節 前期創造社與日本自然主義文學
第四章 五四文學創型與日本文論
第一節 五四文學創型與夏目漱石的《文學論》
第二節 五四文學創型與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
第五章 五四文學型成中的魯迅與日本文學
第一節 魯迅立人思想與日本文化之關係
第二節 為人生的啓濛主義文學觀與日本文學
第六章 五四文學型成中的周作人與日本文學
第一節 「人的文學」觀的形成與日本文學關係
第二節 「人的文學」觀的裂變、轉換與日本文學
第三節 平和、沖淡、閑適的散文創作風格與日本文學
第七章 五四文學嚮無産階級革命文學轉型與日本無産階級文學
第一節 對日本無産階級文學的翻譯與交往
第二節 五四文學嚮無産階級革命文學轉型與日本無産階級文學運動
第三節 中國無産階級革命文學理論界說與日本無産階級文學
第八章 1930年代新型現代派小說與日本新感覺派
第一節 對日本新感覺派的譯介
第二節 對日本新感覺派形式觀念的認同及其意義
第三節 對「新感覺」的認同、化用及背離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圖書序言
引論
中日古典文學關係,基本上是中國輸齣日本接受的單嚮式影響關係,日本文學的生成、發展深受中國文學甘霖的滋潤,其肌體內流淌著中國文學的精血。如《古事記》對某些中國神話傳說的再書寫,《萬葉集》對《詩經》形式的吸納,《源氏物語》中的〈長恨歌〉神韻,等等。然而,近現代中日文學關係發生瞭逆轉,中國文學開始從昔日學生日本文學那獲取靈感與激情,正如實藤惠秀所言:「從1894-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到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開始以前這一段時期,無論從哪一方麵說,是日本文學影響中國文學的時代。」實氏此論雖然太絕對,有失偏頗,但他對中日文學交流基本態勢的言說,卻是準確的。
一
那麼,中日文學關係何以發生逆轉呢?怎樣逆轉的呢? 或者說,中國晚清至30年代初文學何以會迴過頭來關注日本文學、深受日本文學影響呢?
這些看似簡單實卻極為復雜的問題,與兩國近現代化語境、曆史進程、相互關係等相關聯。中日的近現代化,實際上是被近現代化,是在西方威脅、侵略下民族自救的痛苦迴應。近現代化一定意義上說,就是西化,而中國在曆史上與西方的關係,較日本與西方的關係,遠為密切一些,日本在更多的時期是通過中國瞭解西方的。中國人模仿歐式近現代化的條件「比日本人方便得多。」然而,由於種種原因,日本人在近現代化事業上卻捷足先登,通過明治維新乘勢躋身於世界強國之林,並於1894-1895年甲午之戰一舉擊敗清朝帝國。
1895年,對於中國人來說,是極為痛苦的一年,被嚮來視為蕞爾小邦的日本打敗,其震動、羞辱與尷尬體驗遠較半個世紀以前的鴉片戰爭敗於英國強烈得多。這一年徹底地改寫瞭中日關係史,改變瞭中國人的日本觀。老大帝國「始知國力遠遜於日本,但日本在數十年前固無赫赫之名於世界,而竟一戰勝我,則明治維新有以緻之」,羞辱之中一改過去對日本不屑一顧的態度,開始關注、研究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近現代化經驗,希望以之為師。
1896年,康有為編成《日本變政記》,次年齣版《日本書目誌》。後又作《日本明治變政考》,並於1898年2月,進呈光緒皇帝,諫其效法日本,進行變法。在他看來,「歐美新法和日本良規能迅速光照我神州大陸。」同月,竭力於維新變法的皇帝便「索尋」黃遵憲的《日本國誌》,「命樞臣進日本國誌,繼再索一部。」光緒此舉,旨在經由《日本國誌》熟悉瞭解日本國情,特彆是其變革曆史,以期獲取維新變法的資源。朝野上下對日本態度的這種變化,構成瞭中日文學關係逆轉的政治、文化背景。
當時,師法日本的主要舉措有二。一是翻譯日本新學書籍。日本新學大都來自西方,中國為何不徑取西書,而迂道日本?這一常識性問題,並非沒有引起世紀之交危機感強烈、心態焦急的維新派的思考。梁啓超曾認為:「泰西諸學之書,其精者日人已略譯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為牛,日人為農夫,而吾坐而食之。」1897年,他在上海建立大同譯書局,特彆強調瞭翻譯日文著作的重要性。在《大同譯書局敘例》中,他宣稱:「聯閤同誌,創為此局。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張之洞雖然在政治意見上與梁啓超往往相左,但對於譯介日本書籍的認識卻極為一緻。1898年,他在《勸學篇》中力言翻譯日文書籍之必要:「大率商賈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牘條約,法文之用多;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譯西書不如譯東書。」同年,康有為亦指齣:「(日本)其變法至今30年,凡歐美政治、文學、武備新識之佳書,鹹譯(成日文)矣……譯日本之書,為我文字者十之八,(因而譯成中文時)其費事至少,其費日無多也。」倡導變革的楊深秀在1898年的奏摺中,同樣指齣瞭日文翻譯之便:「臣曾細研日本變法,如彼邦已譯就西方佳著。日文書寫與我相同,僅若乾文法與我相反,苟經數月研習,即可大緻明瞭,故利於我譯(西方著作)也。」由此可見,倡導翻譯日文書籍,旨在「力省速效」,以解燃眉之急,這實乃民族危亡之際生存智慧的體現。
理論上的倡導導緻瞭日文譯著高潮的齣現。梁啓超曾說過:「壬寅、癸卯(1902-1903)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齣版之雜誌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齣,譯者動輒數傢,新思之輸入如火如荼矣。」有統計顯示,從1600年至1825年的225年間,由日文翻譯的中文書籍僅有12冊,且其間隻有2冊由中國人翻譯;而1902至1904年間譯自日語著作就達321本,占全部譯著533本的60.2%。又香港中文大學的譚汝謙與日本實藤惠秀等閤作統計齣,1896至1921年間譯自日文的共958本(不包括教科書及期刊連載的譯著),每年平均63.86本。
這些日文譯著大都為教育、法律、史誌、地理等類書,文學類極少,然而它們對於中國文學轉而接受日本文學影響的作用,卻不容忽視。它們使國人熟悉瞭日本的曆史,尤其是明治維新以後的變革史,意識到日本已非昔日的「蕞爾小邦」,而是一個近現代化程度頗高的新國傢,一個值得中國效法的國傢。這種新的日本觀,構成瞭中國人關注日本文學的前提條件。而其中的文學作品(雖為數不多),特彆是大量的文學性極強的政論文,其新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則使中國文學界對日本文學有瞭耳目一新的感覺,不再鄙視日本文學,從而使中日文學關係的逆轉成為可能。
舉措之二是派遣學生到日本留學。關於遊學日本之故,張之洞在《勸學篇.遊學》中陳析得更為具體、清晰:「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夏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齣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他不僅從經濟角度,而且從「情勢凡俗」上論述瞭去日之便。經濟上的節省對於國力衰微的晚清無疑是重要的;然而,張之洞所洞悉的,主要還是中日作為東亞國傢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相似的命運,特彆是近現代化的相似性、可比性。日本作為東亞近現代化的典範,成功地將自己的傳統文化同現代西方的製度和思想結閤起來瞭。具體言之,就是將專製性的國傢主義與民主性的啓濛主義結閤起來瞭。其經驗教訓對於因洋務運動失敗而睏惑不解的中國統治者,有著重要的藉鑑意義,使他們找到瞭如何在不動搖封建專製的國傢利益的前提下,學習西方以振興民族的方式與途徑。張的言述有理有據,不久即為治維新以後的變革史,意識到日本已非昔日的「蕞爾小邦」,而是一個近現代化程度頗高的新國傢,一個值得中國效法的國傢。這種新的日本觀,構成瞭中國人關注日本文學的前提條件。而其中的文學作品(雖為數不多),特彆是大量的文學性極強的政論文,其新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則使中國文學界對日本文學有瞭耳目一新的感覺,不再鄙視日本文學,從而使中日文學關係的逆轉成為可能。
舉措之二是派遣學生到日本留學。關於遊學日本之故,張之洞在《勸學篇.遊學》中陳析得更為具體、清晰:「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山縣、夏本、陸奧諸人,皆二十年前齣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凡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17他不僅從經濟角度,而且從「情勢凡俗」上論述瞭去日之便。經濟上的節省對於國力衰微的晚清無疑是重要的;然而,張之洞所洞悉的,主要還是中日作為東亞國傢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相似的命運,特彆是近現代化的相似性、可比性。日本作為東亞近現代化的典範,成功地將自己的傳統文化同現代西方的製度和思想結閤起來瞭。具體言之,就是將專製性的國傢主義與民主性的啓濛主義結閤起來瞭。其經驗教訓對於因洋務運動失敗而睏惑不解的中國統治者,有著重要的藉鑑意義,使他們找到瞭如何在不動搖封建專製的國傢利益的前提下,學習西方以振興民族的方式與途徑。張的言述有理有據,不久即為超、穆木天、田漢等極少數人,梁容若曾說過:「田漢、徐祖正等,雖自始學文學,但他們的專業是英文學,而不是日本文學。」這錶明,留學日本宗旨在於科學救國,並未想到在文學上取法日本。留美學生鬍適初去美國時以為:「文章真小技,救國不中用」,以至於「帶來韆捲書,一一盡分送。種菜與種樹,往往來入夢」,「種菜」、「種樹」在這裏代指現代農業科學,他當時想做農業科學傢,以農報國,這種在唯科學語境中視文章為小技的意識,實乃當時朝野上下及留學生(包括留日學生)的普遍心態。
然而,當局乃至留日學生們自己也未曾料到,許多留學生在日本自覺不自覺地轉嚮瞭文學,並由文學進而關注、藉鑑日本文學近現代化經驗,緻使中日文學關係發生瞭逆轉。上述四類人中,一、二類誌在當官發財,難以親近文學;而三、四類則不同,第三類人中的有誌者,由禁錮的中國來到異邦,擺脫瞭封建文化的壓迫,感受到瞭從未有過的輕鬆,個性得以自由生長,對於「仕途經濟」,興趣淡薄,不甘受枯燥乏味的政治、法律、自然科學等專業束縛,興趣自然由實學而轉嚮發抒精神自由的文學,如魯迅、鬱達夫、郭沫若、成仿吾等,他們在日本閱讀瞭大量的外國文學書籍,其中不少是日本文學書籍。而當時的日本文學,據美國學者恩斯特.沃爾夫所言,其「現代性的基本成分實際上仍然是現實主義和人道主義。」他這裏所謂的現實主義,並非狹隘的創作方法,而是指「反對語言和情節的種種傳統程序,作品運用白話,『像普通人說話一般』;寫的是現代的場景、現代的問題;這是一種描寫事物、描寫人的心理動機」的現實主義。而他所謂的人道主義,「就是承認人的價值,尊重人的願望,它是一種比較籠統的對小人物的苦難發齣的憐憫和同情,它企求人類的各種問題能得到公正閤理的解決。」日本文學中這種新的現實主義、人道主義精神,與轉嚮文學的留日學生的心靈相契閤,吸引瞭他們渴慕新知的視綫。在如飢似渴的閱讀中,他們深味齣,日本文學中的這種現實主義、人道主義,正是中國文學所缺乏而應加以藉鑑、學習的。它們不僅在留日學生心目中留下瞭深刻印象,一定程度地規約瞭他們對文學現代性的想像與理解,影響瞭他們的現代文學觀的形成,而且經由他們,最終創化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血肉。第四類,流亡到日本的許多革命者,遠離實際革命的鏇渦,又不可能真正忘卻革命,他們所能做的隻能是反思革命陷入低榖的原因,尋求更有效的革命武器。於是將革命與宣傳,宣傳與文學聯係起來瞭,這種聯係使他們開始認真研究日本明治維新與文學的關係。如梁啓超,他雖非留日學生,但維新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在反思戊戌變法何以失敗時,洞悉齣瞭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一大秘訣:「於日本維新之運有大功者,小說亦其一端也。」在《清議報全編》捲首的〈本編之十大特色〉中,他寫道:「本編附有政治小說兩大部,以稗官之體,寫愛國之思。二書皆為日本文界中獨步之作,吾中國嚮所未有也,令人一讀,不忍釋手,而希賢愛國之念自油然而生。為他書所莫能及者三。」他由此深信,政治小說能浸潤國民腦質,與變法、新民呈互動關係,要新民就必須利用文學這一啓濛利器。
由實學或革命而轉嚮文學,由文學而關注日本文學的啓濛、革命經驗,如魯迅、周作人譯介《現代日本小說集》,便是希望從日本現代小說那裏,獲取傳統小說現代化的經驗。而這種關注又必然改變他們嚮來鄙視日本文學的態度,如周作人在《現代日本小說集.序》中稱道:「日本的小說在20世紀成就瞭可驚異的發達,不僅是國民的文學的精華,許多有名的著作還兼有世界的價值,可以與歐洲現代的文藝相比。」太郎在《一夕話-談日本文學》中深信「日本明治末葉直到現在,最發達的要算文藝。」這種態度的轉變,是中日文學關係真正逆轉的心理前提與基礎。正是有瞭這一前提,梁啓超纔大力倡導國人創作日本式政治小說;周作人纔會在〈日本近30年小說之發達〉中倡言中國小說傢應以日本為榜樣,「擺脫曆史的因襲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彆人」,並呼籲「中國要新小說發達,須得從頭做起,目下所缺第一切要的書,就是一部講小說是什麼東西的《小說神髓》。」這種由實學或革命而走嚮日本文學,是第三、四類留學日本人員中轉嚮文學者共同的經曆,至此中日文學關係纔真正開始瞭因中國近現代化滯後而激起的逆轉。
二
中日文學關係發生逆轉的上述背景、原因與途徑,決定瞭中國文學取捨、接受日本文學的具體情形,即主要看取明治維新以後的新文學,以期獲取文學新舊轉型、現代性追尋的經驗。
而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文學,是在學習西方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正如謝六逸所概述的:「歐美各國的文學思潮,給日本的文藝界以很強烈的印象。在明治時代初期的文學裏,有寢饋英國的坪內逍遙博士,有對於德意誌文學造詣很深的森鷗外博士諸人。又有崇拜法蘭西思想的中江兆民,傾倒於俄國文學的長榖川二葉亭、內田魯庵等,因為有這些人物,日本文學遂有迅速的進步。此後自私淑左拉(Zola)的小杉天外的寫實主義、與歐洲大陸文學接近的田山花袋、島崎藤村的自然主義始,以至目前的文壇的新運動,大抵皆以從歐洲文學得到的新印象為原動力。不單是小說,即如戲麯、新體詩等,也是受瞭歐洲文學的影響與刺激而始發達的。現代文學的後半期,雖有大半是獨創的發展,而前半期卻大都在歐美文學的影響下。」由此可見,日本明治以後各流派文學的代錶作傢,都是師法歐美文學的,許多流派的發生發展是以歐美文學為原動力的,如果沒有歐美文學的移植、浸潤,就不可能有日本現代文學。正因如此,長期以來,一些論者認為,日本文學僅是中國文學接受歐美文學影響的橋樑、仲介,忽略或盲視日本現代文學的獨創性及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對此,我們又應作何種理解呢?
從文學傳播、接受途徑看,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文學,確實在中西文學交往中起瞭重要的橋樑作用,因為許多中譯西方文學名著,是通過日譯本轉譯的,例如魯迅、周作人翻譯的《域外小說集》;許多西方作傢、理論傢乃至文學思潮是經日本而走嚮中國的。然而,這些隻是中日文學關係的一個方麵,是錶層現象。如果眼光僅停留於此,認識就無法深入到中日文學關係的實質處,即真正的被影響與影響關係。
西方文學孕育於西方特定的曆史語境,當它被移植到日本時,隨著載體的變更,其內在關係、審美意蘊必然發生某種變異。因為移植的過程,是一個雙嚮同化的過程:一方麵西方文學同化著引進主體的心理圖式,另一方麵引進主體固有的心理圖式也同化著西方文學。這就是說,日本文學固有的傳統和當下的慾望製約著日本文學擇取西方文學的過程,決定著西方何種文學進入日本以及如何進入;盡管西方文學作為異質文學衝擊、改變瞭日本既有的文學係統,但日本文學的「前結構」也不斷地同化著西方文學,使之日本化。在這種雙嚮交流、同化過程中,日本文學得以改造、新生,換言之,完成瞭創造性轉換,一種新質的日本文學得以誕生。如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是在法國自然主義刺激下發展起來的,雖與法國自然主義在技巧上有相通的一麵,但在精神深處卻是日本化的,對「自然」的態度是日本傳統式的「瞑目對自然」,追求自然本性。其特殊形式「私小說」,以自我主義為中心,張揚個性,主觀性極強,深受日本古代日記文學傳統影響。所以,日本自然主義不是西方自然主義的翻版,而是日本化的自然主義。不單是自然主義,日本近現代文學思潮流派大都是在西方文學思潮衝擊下齣現的,與西方文學有著直接的聯係,然而其根基卻是日本文學傳統-寫實的真實、浪漫的物哀、象徵的空寂、幽玄和閑寂風雅,等等。
由於流注著傳統的血液,日本近現代文學成功地實現瞭日本化。對此,中國新文學先驅們有著深切的認識。1918年周作人在〈日本近30年小說之發達〉中,開篇就駁斥瞭那種認為日本文化隻是對「他者」的單純「模仿」之說,指齣日本的文化源自「創造的模擬」。他在稱引英國人 Laurence Binyon 的名言「世界上民族,須得有極精微的創造力和感受性,纔能有日本這樣的造就」之後,寫道:「所以從前雖受瞭中國的影響,但他們的純文學,卻仍有一種特彆的精神」,未失其民族性;而「明治四十五年中,差不多將歐洲文藝復興以來的思想,逐層通過;一直到瞭現在,就已趕上瞭現代世界的思潮。」雖錶麵上看是「模仿」西洋,但實質上是「創造的模擬」,所以「能生齣許多獨創的著作,造成20世紀的新文學。」也就是日本化的文學。鬍適也極為推崇日本人的模仿能力,認為日本文學「有很大的創造」,而這創造來自創造性模仿。化名T.F.C生的作者在緻鬍適信中指齣,「日本人善取歐美之長,以補己之短。」日本文學專傢謝六逸則從世界文學角度,審視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文學,認為其「許多優秀的作品,都有獨創的內容為形式,決不劣於歐美的作傢。」他們深知,自古以來,日本文學便是在異域文學的滋養中發展的,這是日本文學史的獨特性,所以日本文學往往是由模仿走嚮創造的,日本文學特性的形成過程,常常是異域文學日本化的過程。
而那些認為日本文學僅僅是中西文學仲介的人,所犯錯誤便是無視日本文學的獨創性、主體性,認為現代日本文學隻是西方文學的翻版。1921年陳望道先生緻友人的一段話,在今天仍不失其意義。他說「你說日本隻是間接的西學,我從這句話竟懷疑你底學問瞭!你已經瞭解日本文明?你還是連日本話都不曾懂,如那般無聊的日本留學生呢?據我所知,日本自有特長,不在摹仿西歐。中國如需摹仿外國,日本當然也有可以摹仿的地方,不會下於西歐。這以日本留學生而自餒的心情,似乎太不自愛瞭!你難道已經中瞭那不懂日本情形而說大話的人底毒瞭麼?願你三思,勿自捨棄!」陳望道希望日本留學生,應認識到日本現代文化不是間接的西方文化,日本「自有特長」,有值得中國學習之處。那麼,我們進而推之,作為日本文化分支的現代日本文學,亦不是間接的西方文學,盡管它深受西方文學浸潤,但仍是民族性文學。它不僅僅是中西文學之仲介,而且以自己的獨特性深刻地影響瞭晚清至30年代的中國文學。
馬爾羅(Malraux)在談到視覺藝術與敘事文學時說過:「每一個年輕人的心都是一塊墓地,上邊銘刻著一韆位已故藝術傢的姓名。但其中有正式戶口的僅僅是少數強有力的而且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鬼魂。」清以降的中國文學是在多種文學影響中發展起來的,而日本文學則是其中少數有「正式戶口」者,它在中國新文學發展史上銘刻著自己的名字,正因如此,我纔以它對晚清至30年代初中國新文學的影響作為研究課題,探討它是如何刻下自己的姓名以及對中國新文學發展的意義。
三
事實上,這一課題自20世紀20年代末期起就曾引起人們的注意。1928年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中指齣:「中國的新文藝是深受瞭日本的洗禮的」,一語道齣瞭中國新文藝與日本之關係特徵;同年尹若在《現代中國文學的新方嚮》中亦稱:「直接影響中國文壇的(中國也有文壇麼?不是西洋),卻還是日本。」與郭沫若相呼應。到1934年,周作人在閑話日本文學時更是作如此概括:「中國的新文學所遵循的途徑,全是和日本相同的,日本明治初期的小說如,『經國美談』與『佳人奇遇』等,中國翻譯過來,或為中國近代文學的源流,這是應該留心到的事情。」這些感興式的隻言片語,是本課題的最初緣起。它們雖為肯定式的判斷,但客觀上卻起到瞭命題的效果,觸動人們去作進一步地思考。
自那時起,中國新文學與日本文學之關係便成為一些論者感興趣的話題。不過真正深入地研究還是解放後的事情,尤其是新時期以來,湧現齣瞭一批富於獨創性的成果。如劉柏青的《魯迅與日本文學》、王曉平的《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程麻的《魯迅留學日本史》、秦弓的《覺醒與掙紮》、何德功的《中日啓濛文學論》、王嚮遠的《中日現代文學比較論》、(日)伊藤虎丸的《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等專著,以及孫席珍的《魯迅與日本文學》、陳漱渝的《日本近代文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等大批論文。它們或立足於辨析某一作傢的文學思想和創作中所化用的日本文學因子,或重點論析某一社團、流派所受日本文學影響,或綜論某一階段文學現象與日本文學之聯係,或平行比較中日同一文學思潮之異同,等等,均從各自角度開拓或推進瞭中日文學關係之研究。
然而,已有研究中尚存在著一些問題,如一些論者或滿足於資料羅列、事實比附;或多作寬泛的平行比較,深層聯係開掘不夠;或孤立地論述問題,視野受阻,對接受規律揭示不夠;而且論題過於集中,如魯迅與日本關係之研究成為多數論者興趣所在,而許多重要的問題卻無人問津,或僅被浮光掠影式地概說,整個研究既不夠深入,亦不夠全麵。基於對這一研究現狀的考察、瞭解,我纔將自己的論題確定為:「中國近現代文學轉型與日本文學關係研究」。
論述以事實為根據,但切忌簡單的資料羅列、事實比附,主要採取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影響研究方法,努力將局部透視與宏觀分析、考訂與思辨統一起來。
思考研究的重點有三。一、盡可能地深入考察、揭示中國近現代文學轉型與日本文學的深層聯係,即日本文學的哪些因素被中國作傢所擇取,如何擇取、變異,化為自己的血肉的,它們在中國新文學轉型過程中起瞭怎樣特殊的作用,意義何在。二、在動態發展中分析研究近現代中日文學交流史上的某些孤立現象、單個文本在中國新文學史上的意義。三、從接受日本文學影響角度,弄清20世紀中國文學某些特徵是在怎樣的情勢下,以什麼為參照與樣闆而形成的,即辨析20世紀中國文學某些新傳統之原型,及其最初的積極意義和負麵效應。這三點是我為自己預設的努力方嚮與目的,它意味著我在充分理解現有研究成果的前提下,正在作一種新的研究嘗試與努力,意味著我的研究有可能突破既有成果的某些局限性,在重新解讀中國近現代文學轉型關節點時對其內在動力結構做齣富有新意的闡釋。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一看到《中國近現代文學轉型與日本文學關係研究》這個書名,我的腦海中便立刻浮現齣無數值得探討的問題。近現代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極其關鍵的時期,它如同一個巨大的熔爐,吸收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文明成果。而日本文學,憑藉其獨特的東方美學底蘊和近代的西方化進程,無疑在中國作傢群體中留下瞭深刻的印記。我希望這本書能夠超越淺顯的“影響”論斷,而是深入剖析這種關係的復雜性與動態性。書中是否會涉及一些具體的文學批評傢的觀點,他們是如何評價日本文學的?這些評價又如何影響瞭當時中國文學界對日本文學的認知?我更期待看到書中能夠詳細對比分析一些中國近現代文學的代錶性作品,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日本文學作品,從敘事結構、人物塑造、情感錶達等多個維度,揭示兩者之間的內在聯係與差異。比如,對於那些受到日本“私小說”影響的中國作傢,書中是否會深入剖析他們是如何將這種個人化、內心化的敘事方式,融入到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語境中去的?如果這本書能夠呈現齣一種辯證的視角,既承認日本文學的影響,又不忽略中國文學自身的創新與發展,那我將感到非常滿意。
评分這本書的題目《中國近現代文學轉型與日本文學關係研究》立刻引起瞭我的關注。近現代是中國文學一個極其動蕩而又充滿活力的時期,各種思想、思潮、藝術形式都在經曆著前所未有的變革。而日本作為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在近代的文化發展上也走瞭一條獨特而又影響深遠的道路。因此,探究中國近現代文學的轉型與日本文學之間的關係,無疑是一個極具價值的研究方嚮。我迫切地想知道,這本書是否會詳細闡述這種關係的具體錶現形式。例如,在翻譯文學方麵,哪些日本文學作品被引入中國?這些作品的翻譯質量如何?對當時的中國讀者和作傢産生瞭怎樣的影響?又或者,在創作手法上,日本文學的某些技巧,比如濛太奇、內心獨白等,是否在中國小說中得到體現?我尤其希望書中能夠提供一些具體的文本分析,通過對比分析中國和日本的文學作品,來具體證明這種關係的“實錘”。如果書中能深入到對中國作傢群體,甚至是具體某位作傢的思想和創作,分析其日本文學閱讀經曆,以及這種經曆對其創作産生的潛移默化作用,那將是極具啓發性的。
评分這本《中國近現代文學轉型與日本文學關係研究》的標題本身就極具吸引力。我一直對中國近現代文學的勃興與演變充滿好奇,尤其是它在吸收外來文化滋養的過程中,如何孕育齣獨特而又具有世界影響力的作品。而提及日本文學,更是讓我眼前一亮。眾所周知,近代以來,日本文學在東西方文化交融的背景下,發展齣瞭極其豐富的麵貌,並對亞洲乃至世界文學産生瞭深遠影響。那麼,中國近現代文學在轉型過程中,究竟與日本文學發生瞭怎樣的碰撞與互動?是簡單的模仿,還是有更深層次的藉鑒與融閤?書中是否會深入剖析具體的作傢、作品,比如魯迅筆下的“娜拉”形象,是否能看到日本女權思潮的影子?又比如早期白話小說的敘事方式,是否受到日本小說技巧的啓迪?我對書中對這些具體例證的探討充滿瞭期待,希望能從中窺見中國文學界在那個充滿變革的時代,如何以開放的心態,汲取不同文化的養分,最終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同時,我也希望作者能夠深入分析這種關係背後的曆史語境,比如當時的政治、社會思潮,以及文化交流的渠道,這些都將是理解文學轉型不可或缺的要素。
评分閱讀一本探討文學史深度關係的著作,最令人期待的莫過於那些“撥雲見日”的洞見。尤其是《中國近現代文學轉型與日本文學關係研究》這樣的主題,往往隱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交流細節與學術爭論。《中國近現代文學轉型與日本文學關係研究》這本書,我預感其價值將體現在對中國文學在吸收與創新過程中的精微之處的揭示。它是否會梳理齣一條清晰的脈絡,展示日本文學的哪些元素,例如其細膩的心理描寫、對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思,或者某些特定的文學流派,是如何被中國作傢所感知、接受並加以改造的?我特彆好奇,書中是否會對比分析一些同時期中國和日本的代錶性作品,找齣它們之間在主題、結構、人物塑造上的異同,從而印證兩者之間的關聯性。另一方麵,我也希望這本書能夠超越簡單的“影響”說,深入探討中國文學在接受日本文學的過程中,是如何保持主體性,甚至發展齣超越原初藉鑒的獨特創造力的。例如,日本文學中的一些“舶來”元素,在與中國本土的文化傳統和民族心理結閤後,是否會發生意想不到的“變異”與升華,最終催生齣更具中國特色的文學作品。
评分《中國近現代文學轉型與日本文學關係研究》這個書名,在我看來,點齣瞭一個極富探討空間的研究領域。近現代文學的轉型,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場深刻的變革,而日本文學在這個過程中扮演瞭怎樣的角色,一直是許多學者關注的焦點。我特彆期待這本書能夠提供一種不同於以往的視角,或者說是更深入、更細緻的分析。它是否會關注到一些較為邊緣的文學現象,比如當時的報刊雜誌上發錶的文學評論,其中對於日本文學的討論?亦或是,書中是否會考察中國作傢在留學日本期間,與日本文壇的直接接觸,以及這種接觸如何影響瞭他們的創作理念和文學實踐?我設想,這本書可能會詳細梳理一些重要的文學事件或文學團體,分析其中是否存在與日本文學相關的淵源。同時,我也希望作者能夠對“轉型”這個概念進行更深入的解構,它不僅僅是文學形式上的改變,更是思想觀念、審美情趣的革新。這本書是否能夠清晰地展示,日本文學中的哪些元素,是如何契閤甚至催化瞭中國近現代文學的這種深層轉型的?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