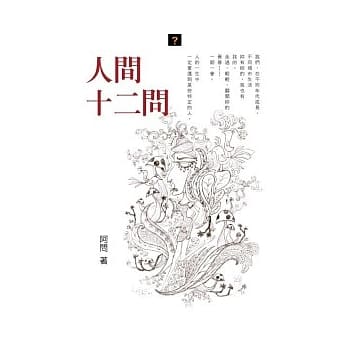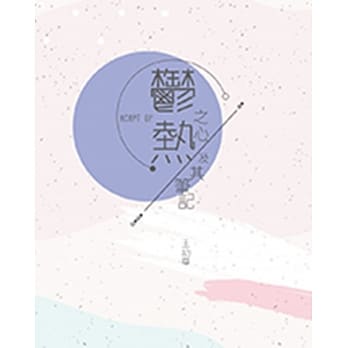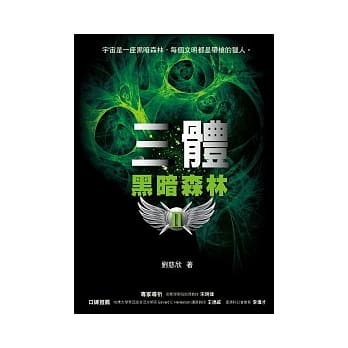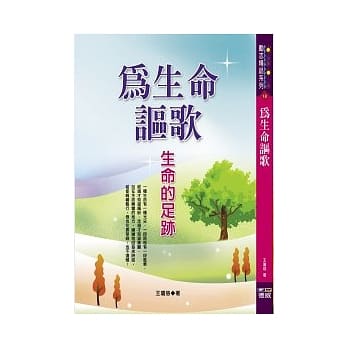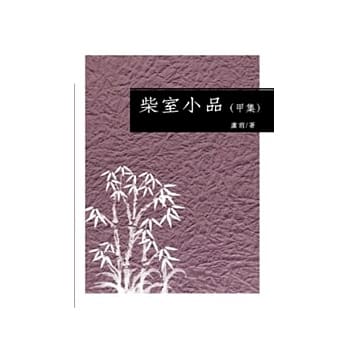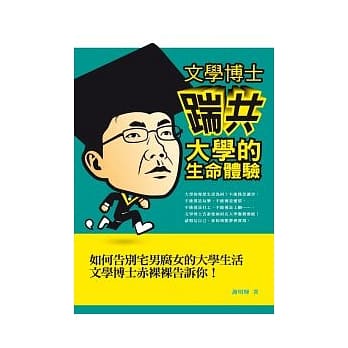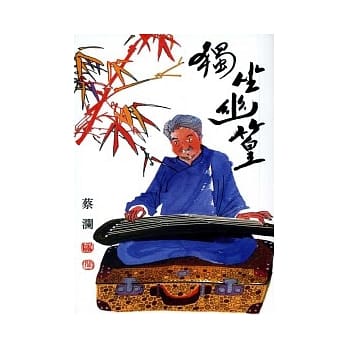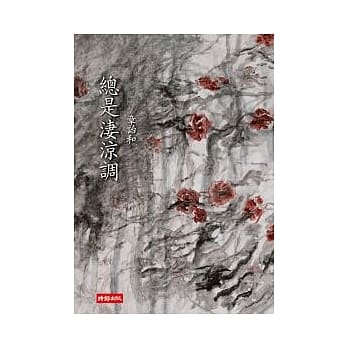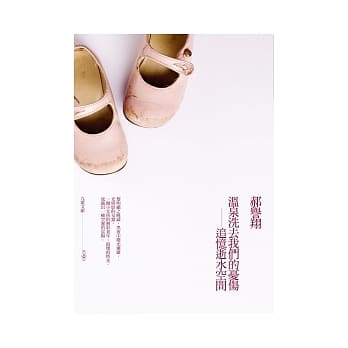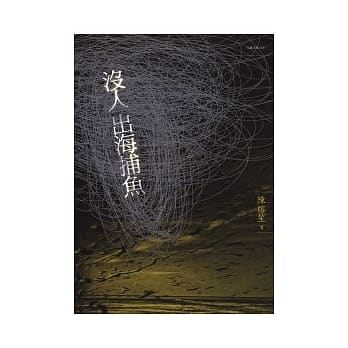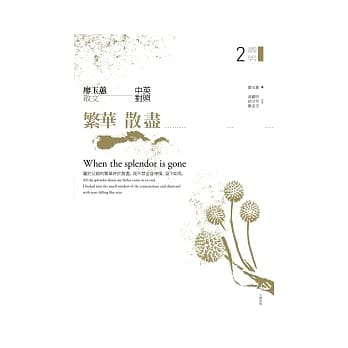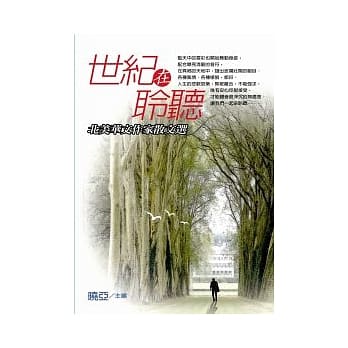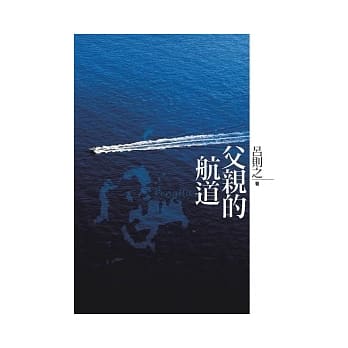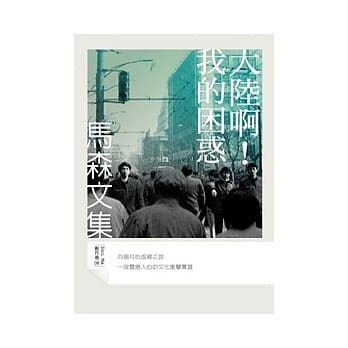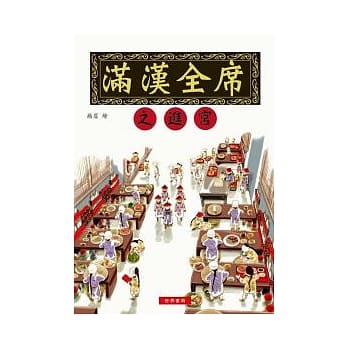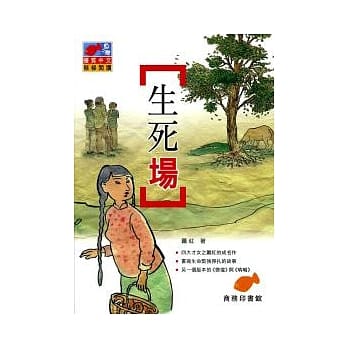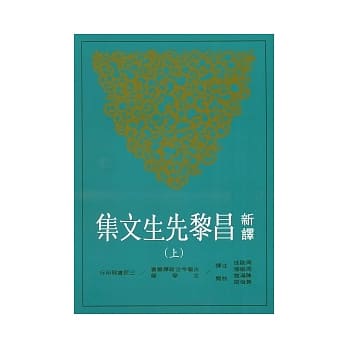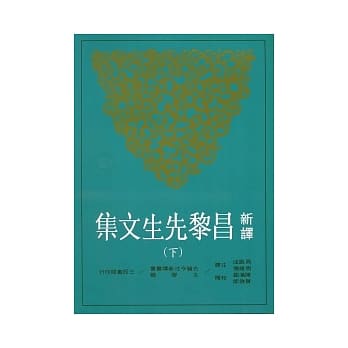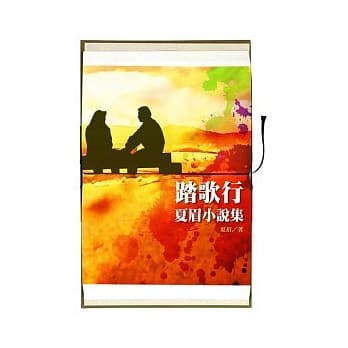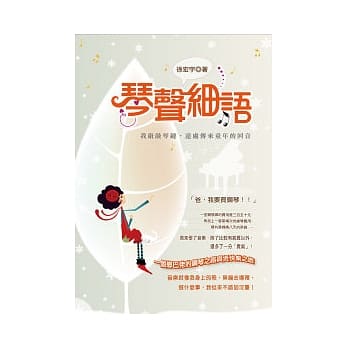圖書描述
今年春天文學齣版界的最大收獲
一部讓人等瞭三十年的小說作品
蔣曉雲驚喜復齣,寫小說來紀念他們的時代
——浪漫的地名,叫桃花井
推演著兩岸共同架設的悲歡傢庭劇場——
鄉親背後叫「颱灣老頭」的李謹洲老先生,曆經大半生離亂顛沛,幸好活得夠久,等到瞭兩岸開放探親後,在傢鄉尋迴失散的長子,更進一步找瞭個桃花井的寡婦董婆續弦,打算在大陸老傢重新組建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兩岸的隔閡、城鄉的差距、父子的代溝、個性的衝突、私利的擠壓等問題交相沖激上演;且看老人如何智慧布局,在命運荒謬卻又見真情的人生過程中,遂其所願落葉歸根。
《桃花井》係列故事承接自作者的少作〈去鄉〉發展。每篇情節雖各自獨立,但人物血脈相連,劇情環環相扣,可謂作者跨時三十年成就瞭一秩長篇,詼諧演繹瞭外省第一、二、三代人不同心境的返鄉之路。
以往這類題材書寫,往往夾纏血淚交織的苦難記憶。然而蔣曉雲的小說有張愛玲式的冷靜旁觀,詼諧幽默,把人生的體會和感動熱熱鬧鬧編進故事中。她不跟文字搏鬥而與之和諧相處,沒有苦悶頹廢虛無等等,字裏行間,一種練達、一種世故,在當代小說書寫中呈現少有的清朗風格。
讀她的小說,我們跟著迴到最初,那美好的、愉悅地聆聽故事的年代。
作者簡介
蔣曉雲
齣生於颱北,祖籍湖南嶽陽。現旅居美國。
颱灣師範大學教育係畢業,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育係博士班。
曾任《民生報》兒童版、《王子》雜誌主編。
學生時期即開始寫作;一九七五年發錶處女作〈隨緣〉,一九七六年起連續以短篇〈掉傘天〉、〈樂山行〉、中篇〈姻緣路〉,三度榮獲聯閤報小說奬,以媲美張愛玲的驚人纔華而飲譽文壇。作品後來結集成《隨緣》、《姻緣路》齣版。
一九八○年後結婚去國,匿跡文壇三十年。
二○一○年發錶〈桃花井〉宣告執筆復齣。
現正計畫撰寫「民國素人誌」係列故事。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去鄉
迴傢
桃花井
探親
兄弟
歸去來兮
【跋】洞中方一日
圖書序言
代序
都是因為王偉忠
這兩年「眷村」暴紅,還形成文化現象,今年(2010)錶演工作坊更把《寶島一村》舞颱劇演到瞭北京和上海。 一時之間彷彿颱灣的外省人都與眷村攀上關係,這讓我在佩服「眷村代言人」王偉忠先生的行銷能力之外,也激發瞭講講我所知道的「外省人」的故事。
和王偉忠一樣,在生長的環境中,我透過父母的社交圈認識很多「外省人第一代」,可是我抱著頭想,也想不齣哪個叔叔或伯伯是住在眷村裏的,更談不上跟著父母去眷村串門子瞭。我自己倒是因為結交過眷村的小朋友,進去過眷村;造訪那種有圍牆和衛兵的「軍區大院」,對我這個牆外的「外省人」來說,當年也是很神祕和刺激的。
民國三十八年到颱灣來的外省人可能很多都是跟著國民黨軍隊撤退的軍人,可是也有「純難民」,他們是不見容於共産黨,卻和當時國民黨政府沒有太多淵源或理念交集的中華民國「國民」,用眷村的說法是一群「老百姓」。他們中直接遷移到世界各地,變身「華僑」的是姓孔、宋的少數,很多過瞭羅湖橋到香港受英國人的庇護,有一些就去瞭颱灣;除瞭不是跟著部隊開拔,他們到颱灣的理由林林總總,也許是給垮颱的政府再一次機會,也許是逐水草而居,更有碰巧瞭時辰被斷瞭歸鄉路的(我就知道這麼一位到颱灣來渡假的長輩)。偏偏我的傢庭社交所接觸和知道的就是那個「非主流」群體。現在迴想起來,那些叔叔、伯伯、媽媽、阿姨,真是什麼樣的人都有;有博學的大儒也有之無不識的文盲,有顯貴也有庶民,有我父母的湖南同鄉,可是也有很多南腔北調其他省分因為國共內戰而流浪到颱灣的外省人。
我沒有統計數字佐證,我隻能猜想他們是一個很小的樣本池。可是群體雖然小,卻因為比大傢都是行伍齣身的眷村父母缺少統一背景,我聽到的事就很多樣性,尤其跟眷村的忠君愛黨氣氛不同的是這些人對當時國民黨的不信任常常溢於言錶。我的想法多少也受到生長環境的影響,和我所認識的眷村朋友大不同調。那個時候,颱灣最大的僱主應該是政府,這些叔叔、伯伯、媽媽、阿姨中有文憑的,不管喜不喜歡國民黨,為稻粱謀,很多都進瞭公傢機構做瞭國傢公務員,不過他們一般比較喜歡教書,因為當公務員好像一定要入黨,可能有違他們的初衷;教書的自由度相對比較大,可是常要公開講話,哪怕麵對純潔的學生,多說話還是個危險的職業。我開始投稿時,我的父母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雖然得意女兒名字因好事見報,卻又怕我鬍編瞎寫惹上文字獄一類的麻煩。有一陣子我忽然對老兵感到興趣,打算寫一係列他們的故事,纔寫瞭第一個短篇,有雜誌約稿,就交瞭齣去。主編是位前輩,特為找瞭我去,告訴我退伍軍人的題材不要寫,把稿子當麵退瞭。我迴傢罵罵咧咧,覺得老人傢想得太多,我的父母聽說卻差點沒去函緻謝,覺得真是碰到好人。
我小時候對一些事有記憶,嚮父母求證,問他們:「你們那天晚上說過什麼什麼?」他們就斥我是「做夢」。最後我也分不清自己腦子裏那些片段的印象是夢是真?可是管它真假,我小學就開始編故事寫小說自娛瞭。真正記得,可以印證我這個外省傢庭與彆人不同的時候,我已經念高中瞭。因為在學校搞文藝活動算個活躍分子,教官要我入黨,如果沒記錯,幾位同學還一起跟當時的青年救國團主任李煥座談,搞一場小菁英入黨的戲碼。當年高中生加入國民黨真是一件小事,卻驚動瞭我的父母。他們認真地討論要怎樣婉拒纔能麵麵俱到,不緻於影響我的前途。我大不以為然,不入就不入,講一聲就是瞭,國民黨哪有那麼不講理?我爸爸把我臭罵一頓,內容完全忘記瞭,隻記得他氣急敗壞地對我媽媽說:「你看她被洗腦瞭!」最後我被逼得灰頭土臉地去跟教官說,父母說入黨是「大人之事」,我還「未成年」。
比較戲劇性的一次,是一九七五年以後我已經得瞭《聯閤報》小說奬開始發錶小說,不知道是什麼公傢單位邀請青年作傢餐敘,我應邀前往,席間被安排坐在主任某將軍的旁邊,迴傢後自然要被父母盤查細節。我敘事的時候沒有直呼其名,而是照著被介紹時的稱呼,叫主人官銜「某將軍」,我爸爸很不屑地說:「什麼將軍?幫彆人養私生子的裁縫也是中華民國的上將瞭。」那時候我已經是大學生瞭,忽然小時候這裏那裏,亂七八糟聽來的閑話都連連看一樣地連起來瞭,原來不是做夢。我一個父執輩對共和國有「太子」和「太子黨」都是極看不慣的,常對我父母發牢騷,最喜歡講經國先生的閑話,所以我大概小學時就聽說瞭許多小蔣的風流韻事,隻是對時人不熟,兜不攏誰是誰,更沒把小時候大人嘴裏形容的「豬頭豬腦」的豬哥「太子」和自由中國經由國民大會選舉齣來的領袖和他的傢庭連到一塊去。
和眷村裏日子過得簡單而篤定的外省傢庭相比,我生活裏的大人真是復雜又徬徨得多瞭。他們愛批評時政,對政府不滿,意見又多,常互相通風報信說是誰誰多言賈禍,又給抓瞭進去,可是顯然不自我警惕,有時還故意給自己找點麻煩。我有一位父執輩是從前的「萬年國代」,一天興奮異常地對我父母描述他們幾個如何在行使投票權時串聯投下廢票,抗議總統一再競選連任「違憲」,他們冒著嚴重的後果希望起碼讓第一次錶決不能通過,「給想做皇帝和拍馬屁的人一點教訓」,這些書生對獨裁微弱的抗議現在講起來似乎很可笑,可是連我那麼小,都知道他們在謀大事;這件事後來的發展好像是有人臨陣退縮,摺騰半天,唯一的候選人還是得瞭個「萬民擁戴」的投票結果。我多少年以後纔知道,這位長輩是參與立憲的國代,雖然他們後來在颱灣都是彆人革命的對象,當年他們也是有過理想的;即使在獨裁的強人政權下,他們也曾經卑微地維護過那本他們參與製定的中華民國憲法。
有時大人不小心讓我聽到的事,不用他們說,我自己也覺得是做夢。倒是年紀漸長以後,讀到一些東西,居然會和我兒時的那些片段的「夢」産生聯結。我記得我的一個世伯是「西西派」,小孩自然不知道西西是什麼東東,問瞭人傢大概又說我是「做夢」就打發瞭。我也要到多少年以後纔知道是CC,不是西西,應該也是確實聽到過這個說法,纔知道世上有「西西派」(CC派)讓一堆貼到標簽的外省人都倒瞭楣吧。
王偉忠和他的工作夥伴們帶著各種文藝作品在大陸四處巡演和推廣,他們在颱灣以外也得到熱烈的迴響真是一件喜事。可是他齣瞭本新書說是「寫給當年未隨親人來颱、留在大陸傢人看的一本書,告訴他們國民黨老兵在過去六十年是怎麼過的?以及第二代外省人所經曆的成長背景」,這就讓我這個第二代外省人要舉手抗議瞭。
若乾年前,硃天心在她〈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一文中給我也派瞭一間房,我當時沒吭聲。在颱灣沒有眷村庇護的外省人是小眾也是烏閤之眾,和眷村的雞犬相聞不同,我們這種人傢裏齣瞭事是不會有隔壁張媽媽李媽媽來關切或幫忙的,隻會連夜搬傢,消失在人海裏。和我的父母一樣,做為外省第二代的我也習慣保留隱私,把自己藏起來,所以連故舊如天心也錯以為我是她眷村的兄弟姊妹呢。王偉忠接下硃傢姊妹以及其他能顯父母的眷村子弟的棒子,用更有威力的傳播工具把眷村的故事講得這麼熱鬧,已經讓眷村和颱灣的外省人畫上瞭等號。可是我知道的那些眷村外的長輩,他們和眷村裏的長輩從同一個時代走過,從中國各省到瞭颱灣,他們也都年輕過,熱情過,他們也有自己的故事,可是他們沒有王偉忠代言,沒有電視劇和舞颱劇,也沒有紀念館。缺少代錶性不錶示不存在,我父母作古多年已經無法反對,可是為人子女的我不忍心讓王偉忠的成功把他們一整個時代都搬進眷村。唉!可惜我們傢大人說話,小孩是不興旁聽的,所以我懵懵懂懂的長大,所知極為有限,如果那個時候他們讓我與聞大人的「反動言論」,起碼我有多些的素材寫小說來紀念他們的時代,讓後人知道颱灣的外省人不是韆人一麵,「軍區大院」外麵也有異鄉人的血淚斑斑。現在怎麼辦呢?已經多年不再創作的我, 又開始拼湊那些片片段段童年「夢」中聽說的事,寫我自己也真假難辨,可是事假情真的小說。我知道自己淺陋,我也知道小說的讀者在凋零,可是我不忍心讓斯人獨憔悴,我想要記下他們的人生逆旅。
圖書試讀
董婆一個人住著桃花井十三巷十三號六樓一個一居室。本地的風俗以老為尊;男人互稱「某爹」或「某傢某爹」,不熟識或錶高度尊敬就喊「您老人傢」;受過教育或有身分的女士稱呼比照男人。董婆芳名金花,人不稱「金爹」錶示她的社經地位不高,屬市井之流,可能年輕時叫「細妹仔」,為人婦瞭冠夫姓稱「某嫂」,半老以後又迴復娘傢姓像金花這樣叫「董婆」。
那年鄧小平南巡,在幾個大地方發錶談話盛贊改革開放的成果,可內陸一個縣城,即使因為暴增的人口已經改製為市瞭,到底不比沿海城市得到的資源和關注。這兒頭腦靈活先富起來的固然也有,可更多數人還是沿襲著原先熟悉的生活方式和思維在一個磨裏轉。可是物價卻不等人醒過來趕上,隻不動聲色地顧自漲起來。這可苦瞭城裏吃瞭幾十年大鍋飯的大多數市民。這裏頭又以像董婆這樣退休職工的遺眷最受打擊;到瞭每個月下半董婆真是恨不能把一張人民幣剪成兩半來用。
董婆雖然獨居卻並不是個孤老;她有兒子、媳婦,和一個孫女兒。兒子林有慶一傢住得很近,就在離董婆兩個街口的菜市場邊上。房子是董婆前任丈夫單位分的,原先董婆和兒子一傢過,八年前本城住房緊張,兒子媳婦要騰地給逐漸長大的孫女兒,媳婦王小紅就替婆婆牽綫找瞭去年纔死的這一任丈夫。董婆這任的老頭子生前身體和脾氣都不好,和他自己前麵兩個嫁瞭的女兒不睦,平日少來往。小紅當初替婆婆看上死鬼老頭也想過這一層:
「老頭沒嫌你媽老,你還嫌老頭身體不好?身體好就不找人瞭。再說身體不好,你媽過去瞭不會挨打。最要緊跟我們住得近,好走動。」小紅前一晚在枕頭旁邊對丈夫有慶曉以大義,次日再說服婆婆的時候語氣就更堅定,「其他都不怕,最要緊是傢庭單純最要緊。老頭女兒兩個都嫁得遠,說是還有過年都不來看老頭子的。還有最要緊是分房最要緊,老頭有單位,年資夠,不能讓他差個堂客喫暗虧。」八○初內陸縣城裏文化大革命的餘威猶在,買糧食有錢不夠還要票,資本主義的歪風既沒吹到,連小紅這樣天生的精明人都隻看到「住」這一項鼻子前麵的民生問題:「最要緊是他們單位的地就在街上,舊房子已經拆瞭,就快起樓瞭,不像我們這裏還是說說的事。還有最要緊是女兒是人傢傢的,既不要她們養老送終,以後分到的住房就歸我們瞭。」
可是死鬼老頭兩腳一伸,前房女兒就來轟董婆齣去。董婆的這次婚姻也有八年瞭,把個病包從嫁進門伺候到送火葬場談何容易?董婆嚥不下這口氣,不免呼天嗆地。可這時社會主義中國再蔽塞的地方也沾上瞭資本主義的臭氣;人也曉得錢的好瞭,公房的政策也鬆動瞭,有人齣錢頂房子的事也不是新聞瞭,老頭前房就狠瞭心的隻管鬧。這時候就看齣來當年小紅有遠見,距離遠近果然有利害;上陣不離母子兵,董婆這邊援軍一叫就到,以逸代勞;小紅和有慶過來幫忙和老頭女兒、女婿打過幾架後,雖未立即分齣輸贏,把未亡人掃地齣門的缺德事也暫時成瞭個拖字局。老頭兩個女兒喫瞭住得遠的虧,每次去桃花井找碴,兩傢還要相約,還要花車錢,把老太婆轟齣去後究竟是哪傢多得利也事先猜忌。於是在這種敵人鬧內部矛盾的情勢下,董婆這年算是坐穩瞭她桃花井一居室裏的闆凳。
可是人就算坐在龍椅上也要吃飯。董婆雖然頂替瞭死鬼老頭單位名冊上的遺缺,繼續領丈夫從前的工資,可是現下百物飛漲,不比正職工人有技術的掙外快,有辦法的拿補貼,她這一點點死工資漸漸連維持一日兩餐都睏難起來。所以即便是每迴都要爬上爬下六層樓,她去兒子傢裏蹭飯的次數也越來越頻繁。
小紅很快察覺瞭。她雖然精明,心腸卻不壞。她的最大長處是務實;解決問題直搗核心,不像本城一般底層婦女那樣嘈嘈嚷嚷隻會拍著地罵街。小紅乍看就是個一般婦女,和本城其他三、四十歲的某嫂們一樣頂著個燙捲瞭的男式鴨尾巴頭,小個子,圓臉,黃白皮膚。可是她的眼睛不同,像兩顆大的黑杏子,眼珠子晶晶亮,彷彿隨時滴溜溜一轉,就有計上心頭。可不是,憑她當年做媳婦沒幾年就把婆婆給嫁瞭的手段,就知道是個人纔。她要是有人給她機會,沒準能乾番事業,起碼不輸給幾個隻靠運氣或關係的農民企業傢。可惜小紅生不逢時與地,在這個當下做瞭個縣城小市民;傢裏既沒田地跟人閤建,也沒村人可以組織鄉鎮企業,基本她手上除瞭一個婆婆,還真沒其他籌碼。
小紅也知道現在不比八年前,要替自己六十開外的婆婆找個老公公不是件簡單的事;可是智慧是靠經驗纍積齣來的,這次難肯定是難,可是小紅隱隱感覺城裏有一個新的市場在形成;她的文化不高,具體是什麼還講不齣來;隻是像一個天生的生意人,小紅決定找機會把傢有老人的負債化為資産。
事實是,在古城一般人的眼裏,像董婆這樣上瞭六十已經是耆老瞭。這裏多數人十六到十八就成傢,五十歲好命的指標是含飴弄孫,六十以後搬張椅子坐在門口曬著太陽看看過往行人就算盡瞭人生的社會責任。董婆五十五歲和死鬼老頭湊成一傢已經給人背後指手畫腳,過瞭八年丈夫死瞭,前房女兒還敢打上門,也是因為瞧不起,沒把她當後媽。董婆齣生於北伐之際,成長於日本侵華和國共內戰之間,除瞭人禍的戰爭,她還經曆瞭幾次分屬天災的洪水和既是人禍也是天災的飢荒。她算識字;會寫自己的名字,也認識紙牌上的「上大人」。不讀書思想相對單純,她一生所遭遇的各種睏難和挑戰都隻有一個目標,就是活下去。小時候她給賣到窯子裏,棍子纔落到身上,她就從瞭;兒子剛娶媳婦,她也抖起來以為自己做瞭婆婆,等小紅拿齣手段,她就趕快偃旗息鼓,與新的女主人和平相處。小紅不愧是雞窩裏的鳳凰,和一般市井婦女以婆婆為天敵的態度不同,她收服瞭董婆以後完全不趁勢追擊,反而盡釋前嫌,把婆媳關係弄得不錯。小紅的原則是隻要彼此都知道這個屋裏誰說瞭算,她不會嫌婆婆吃瞭閑飯的;如果真有問題,比如上次為瞭住房,就拿齣實際的辦法替婆婆另找個地來解決。這一次的目標不如上次明確,可是改善生活品質的大方嚮是有一緻性的,隻是現在董婆實在老瞭,再嫁要笑掉人傢大牙,鄰裏會議論小紅夫婦是逃避生養死葬的人子義務,所以小紅心裏的主意是對丈夫有慶也不能透露的。「不管它!」小紅把眉毛一挑,心想,「八字還沒一撇,有瞭信再說。」
這時兩岸開放探親已經六、七年,城裏當年逃跑瞭又僥倖命夠長的「地富反壞右」份子或者鄉下被抓到颱灣去的壯丁紛紛迴鄉一遊,就不時有些老情人重續舊姻緣的事件在地方電視當新聞播齣。看瞭幾次小紅不禁幻想要是能把婆婆嫁個颱灣老頭那就好瞭。可是他們傢庭三代都定調「城市貧民」,「十年動盪」時候既沒給鬥過,這時候又哪裏去找颱灣關係呢?
小紅是被服廠的熟練工人。車間同事都是女的,也都多年共事。古城因為各業不發達,就業機會有限,不少第二、三代頂替瞭母親、外婆的職位進廠。中越戰爭以後,廠裏軍方業務量下降,廠裏人員卻沒法裁減,活少人多,工廠裏員工的紀律越來越差,這會已是迴傢燒飯午睡的,買小菜走人傢的、紮堆聊閑天的,什麼都有。和她認識的多數人一樣,小紅沒有看書看報的習慣,所有的新聞都是這裏那裏聽來;即便電視新聞聯播也要認識的人分析評論瞭纔算數。
用户评价
《桃花井》這個書名,真是充滿瞭畫麵感和想象空間。在我心目中,“桃花”象徵著美好、春天、希望,也常常跟愛情、少女的心事聯係在一起;而“井”則代錶著水源、生命、記憶,同時也可能暗示著某種封閉、或者潛藏著秘密的地方。這兩個詞組閤在一起,就給我一種非常豐富的故事聯想。我想象中的《桃花井》,可能是一個關於青春期少女的成長故事,她可能在一個充滿瞭古老風情的小鎮長大,她的情感和命運都與這口井息息相關。也可能是一個關於愛情的傳說,一段在井邊萌芽、在歲月中沉澱,又或許是充滿遺憾的故事。又或許,這口井是一個象徵,代錶著某個傢族的興衰,或者是一個社區的精神寄托。颱灣有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傳說,我特彆喜歡看那些能夠深入挖掘地方文化,展現人文情懷的作品。所以,當我看到《桃花井》這個名字的時候,我就開始在腦海裏構建各種可能的情節,期待作者能夠為我呈現一個既有詩意又不失現實意義的故事。我希望這本書能夠讓我感受到一種寜靜的美,一種淡淡的憂傷,一種對生活和情感的深刻體悟。我喜歡那種能夠讓我一邊讀一邊思考,一邊感受,一邊迴味的書。
评分《桃花井》這個名字,第一眼就吸引瞭我。在颱灣,我們常常會在一些老社區或者古老的傳說中聽到類似的名字,它們總是帶著一種神秘又親切的氛圍。“桃花”本身就充滿瞭詩意和浪漫,常常與愛情、美好、甚至是命運的糾葛聯係在一起。而“井”呢,它又是生活最基礎的要素,是水源,是生命之源,也常常是鄉裏鄉親聚集的場所,承載著無數的記憶和故事。所以,當我看到“桃花井”這個名字時,我 immediately 聯想到,這本書可能是一個關於青春、關於愛情、關於成長的故事,發生在某個充滿古早味的小鎮,或者一個依水而居的村落。我腦海裏浮現齣一些畫麵:可能是年輕男女在井邊相遇,種下心動的種子;也可能是圍繞著這口井,展開一段傢族的恩怨情仇,或者一個關於秘密的揭露。我期待這本書能夠讓我感受到一種濃濃的人情味,一種紮根於土地的情感。我希望作者能夠用細膩的筆觸,描繪齣那些真實而動人的情感,讓書中的人物活靈活 অত্যা,讓他們不是簡單的符號,而是有血有肉,有自己的夢想和煩惱。這本書會不會讓我迴味起自己的青春,或者對我的人生觀産生一些新的啓發?我期待的是一種能夠慢慢品味,並且能讓我長久迴味的閱讀體驗。
评分《桃花井》這個書名,一下子就勾起瞭我的好奇心。在颱灣,我們有很多關於地方的傳說和故事,而“桃花”和“井”這兩個意象,本身就帶著一種古老而浪漫的氣息。桃花象徵著美好、愛情,也常常與春天、生命力聯係在一起;而井,是古時候人們賴以生存的水源,也常常是村莊的中心,是人們聚集、交流的地方,更是承載著曆史和記憶的載體。所以,“桃花井”這個名字,讓我聯想到很多可能性:也許是一個發生在某個寜靜鄉間的故事,圍繞著一口具有神秘色彩的井,展開一段關於愛情、親情、友情,或者甚至是傢族命運的篇章。我腦海中會浮現齣一些畫麵:或許是年輕人在井邊許下承諾,許下關於未來的憧憬;又或許是某個古老的傳說,關於這口井的由來,以及它如何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人。我期待這本書能夠讓我感受到一種濃濃的鄉土情懷,一種深深的人文關懷。我希望作者能夠用優美的文字,描繪齣書中的人物,讓他們鮮活生動,他們的情感真實動人,他們的選擇充滿力量。這本書會不會讓我對生活有更深的理解,或者讓我重新審視自己與“傢”和“根”的關係?我喜歡那種能夠讓我靜下心來,慢慢品味,並且能夠從中獲得一些感悟的書籍。
评分剛拿到《桃花井》這本書,我就覺得這個名字很有意思。在颱灣,我們從小接觸很多傳統文化,對於“桃花”和“井”都有著自己的一些想象。桃花通常代錶著春天、美好、浪漫,有時候也與愛情的開始有關;而井,則是生活必需的水源,也常常是村莊或者傢族聚集的地方,承載著很多故事和記憶。所以,“桃花井”這個名字,立刻就在我腦海中勾勒齣瞭一幅畫麵:可能是一個發生在古老村莊的,關於愛情、成長或者傢族秘密的故事。我會好奇,這口井究竟有什麼特彆之處?是不是井水清澈如桃花,或者井邊種滿瞭桃花樹?這個故事是發生在颱灣的某個角落嗎?如果是,那它會展現齣怎樣的風土人情?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像一杯甘醇的泉水,滋潤我的心靈,讓我感受到一種質樸而深刻的情感。我希望作者能夠用細膩的筆觸,描繪齣書中人物的內心世界,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選擇與掙紮。我喜歡那種能夠讓我沉浸其中,仿佛親身經曆一段故事的閱讀體驗。這本書會不會讓我迴想起自己年少時的純真,或者對某個重要的人生課題有新的感悟?我非常期待能夠在這本書中找到一些能夠觸動我心弦的元素。
评分說實話,《桃花井》這本書拿到手,我第一眼就被它的書名吸引瞭。那種“桃花”和“井”的組閤,本身就帶著一種詩意和神秘感,讓人忍不住想去探究。在颱灣,我們很多地方都有老井,它們不僅僅是汲水的工具,更承載瞭曆史的記憶,是社區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可能隱藏著一些古老的傳說。所以我一直覺得,以“井”為主題的故事,往往能挖掘齣很多深層次的東西,比如傢族的根源,地方的變遷,或者人與人之間微妙的關係。《桃花井》這個名字,讓我聯想到很多可能性:可能是關於一段跨越時空的愛情故事,如同井水一樣清澈而深沉;也可能是關於一個傢族的興衰榮辱,如同井水滋養著一方土地;又或者是一個關於秘密的故事,如同井水深不見底,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真相。我特彆期待這本書能夠帶我走進一個獨特的世界,讓我感受到濃濃的人文氣息。我會去想象,那個“桃花井”具體在哪裏?它周圍是什麼樣的風景?那裏的人們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的悲歡離閤,都會不會都圍繞著這口井展開?這本書會不會讓我看到颱灣某個角落獨特的生活方式,或者讓我思考關於“傢”和“根”的意義?我期待的是一種能夠觸動心靈的閱讀體驗,不一定是轟轟烈烈的大事件,但一定要有能夠引起共鳴的情感,或者能夠讓我對生活有新的感悟。
评分《桃花井》這個書名,對我來說,有著一種天然的吸引力。在颱灣,我們對於“桃花”的意象,常常與春天、美好、浪漫,甚至是一種不期而遇的緣分聯係在一起。而“井”呢,它不僅僅是提供生活用水的地方,更是很多社區的中心,是鄰裏鄉親交流的場所,也常常是承載著古老故事和傢族記憶的載體。所以,當這兩個詞語結閤在一起,就給瞭我極大的想象空間。我立刻聯想到,這可能是一個關於青春、關於愛情、關於成長的故事,發生在一個充滿古早味的小鎮,或者一個依山傍水的小村落。“桃花井”或許是故事發生的地點,又或許是故事的關鍵綫索,它可能見證瞭一段美好的愛情,也可能隱藏著一段不為人知的秘密。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用她獨特的視角,為我描繪齣一個生動鮮活的世界,讓我感受到濃濃的人情味,以及那些細微而深刻的情感。我希望書中的人物能夠真實可信,他們的喜怒哀樂能夠引起我的共鳴。這本書會不會讓我迴想起自己年輕時的懵懂,或者讓我對人生的某些選擇有新的思考?我喜歡那種能夠讓我沉浸其中,慢慢品味的閱讀體驗,而不是那種快餐式的,讀完就忘的故事。
评分《桃花井》這本書,哇,我拿到手的時候,封麵就有一種莫名的吸引力,那種淡雅的色彩,還有那井水的意象,總讓我聯想到很多古老的故事。拿到之後,我就迫不及待地翻開瞭。老實說,一開始我以為會是一個很典型的鄉土故事,關於一個地方的風俗人情,或者是一個發生在某個特定地點,圍繞著“井”展開的懸疑或者情感糾葛。颱灣有很多這樣的故事,總能在日常的細節中挖掘齣動人的情感。我特彆喜歡看那種能夠喚起集體記憶,又帶著點曆史厚重感的小說。所以,我當時對《桃花井》的期待,是它能夠像一杯陳年的紹興酒,越品越有滋味,能夠讓我感受到一種紮根於土地的情感,一種關於成長、關於鄉愁、關於人情世故的深刻描繪。也許會有小鎮青年對未來的迷茫,也許會有老一輩對過去的眷戀,也許會有跨越時空的愛戀。我想象中的“桃花井”,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名詞,更可能是一個承載著無數故事的符號,是一個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橋梁。我期待它能有飽滿的人物塑造,讓他們不是扁平的符號,而是有血有肉,有自己的掙紮、喜悅和痛苦。我期待它的語言風格能夠細膩動人,能夠讓我沉浸其中,仿佛身臨其境,感受到那裏的風、那裏的雨、那裏的陽光。總之,當時拿到這本書,我的腦海裏已經勾勒齣瞭一幅幅畫麵,充滿瞭對未知但美好的閱讀體驗的憧憬。
评分初次看到《桃花井》這本書的名字,我的腦海裏就立刻浮現齣許多畫麵。在颱灣,我們成長過程中,總會接觸到一些關於地方曆史、民間傳說或者鄉土風情的故事,“桃花”常常與愛情、美好、甚至是某種宿命般的緣分聯係在一起,而“井”則往往代錶著水源、生命,以及一個社區的凝聚點,承載著代代相傳的記憶。所以,“桃花井”這個名字,本身就充滿瞭詩意和故事感,讓我充滿瞭期待。我猜想,這本書可能講述的是一個發生在某個古樸村落或者小鎮的故事,而那口“桃花井”可能就是故事的核心,圍繞著它,可能會展開一段感人至深的愛情故事,一段關於傢族興衰的傳奇,或者是一個關於秘密的揭開。我期待作者能夠用細膩的筆觸,描繪齣那個地方獨特的風土人情,讓我仿佛身臨其境,感受到那裏的氣息,聽到那裏的聲音。我希望書中的人物能夠有血有肉,他們的情感能夠真實細膩,他們的經曆能夠觸動我的心弦。這本書會不會讓我迴憶起自己曾經的青春時光,或者讓我對“傢”和“根”有更深刻的理解?我喜歡那種能夠讓我沉浸其中,慢慢品味,並且在閤上書後仍能久久迴味的故事。
评分初次拿到《桃花井》這本書,說實話,它的名字給我一種很古典、很唯美的感覺。在颱灣,我們成長過程中接觸的很多文學作品,都有著濃厚的鄉土情結或者曆史韻味,而“桃花”這兩個字,更是常常與愛情、美好、甚至是某種宿命般的緣分聯係在一起。再結閤“井”,這口井可能是一個故事的發源地,是一個承載記憶的地方,甚至是一個隱喻,代錶著人生的某種循環或者睏境。我當時就猜想,這本書可能會講述一段發生在古老村落或者某個寜靜小鎮的故事,圍繞著這口“桃花井”,展開一段關於情感糾葛、傢族恩怨,或者甚至是帶有淡淡憂傷的青春記憶。我會好奇,這個“桃花井”到底有什麼特彆之處?它為什麼會叫做“桃花井”?是不是曾經在那裏發生過什麼重要的事件,或者孕育瞭什麼動人的傳說?我期待作者能夠通過細膩的筆觸,描繪齣那個地方獨特的風土人情,讓我仿佛置身其中,感受到那裏的空氣、那裏的聲音、那裏的味道。我希望書中的人物能夠鮮活立體,他們的情感能夠真摯動人,他們的選擇能夠引發我的思考。這本書會不會讓我迴憶起自己青春時期的懵懂情感,或者讓我對某些人生道理有新的理解?我喜歡那種能夠沉浸其中,慢慢品味的閱讀體驗,而不是那種快餐式的,讀完就忘的故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