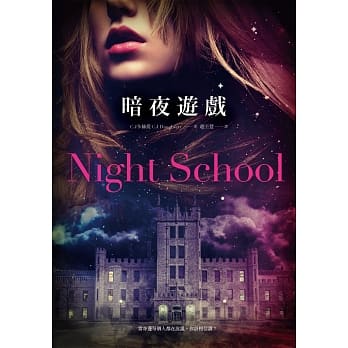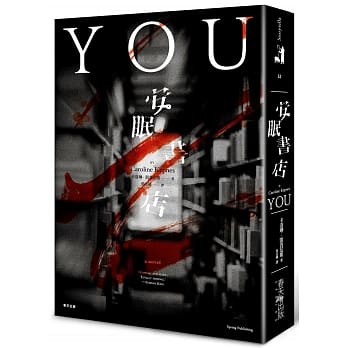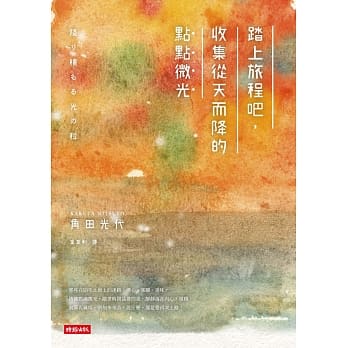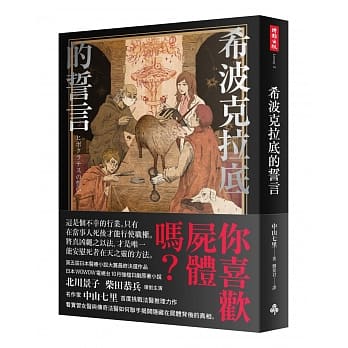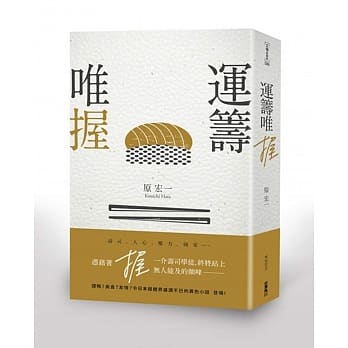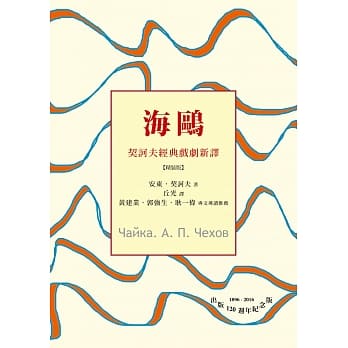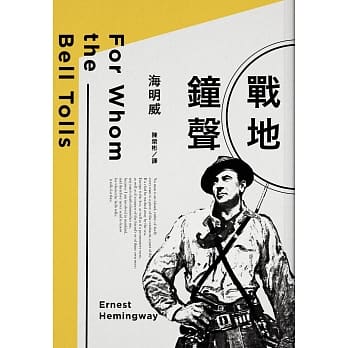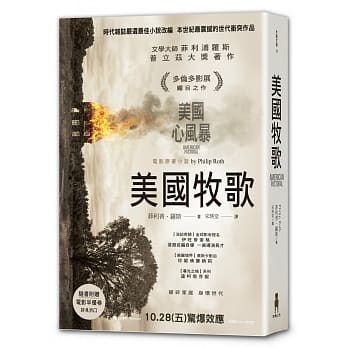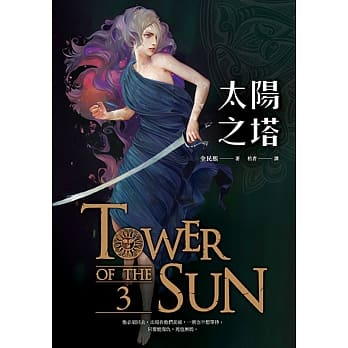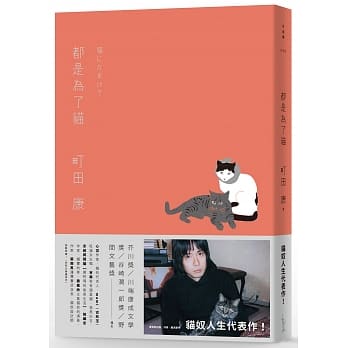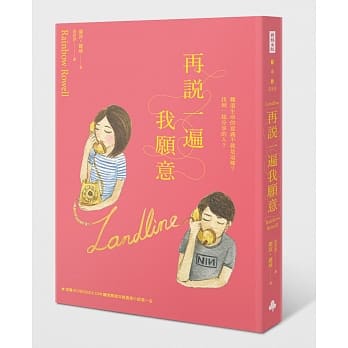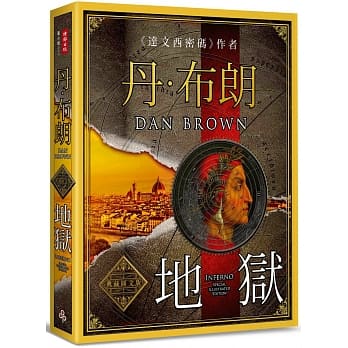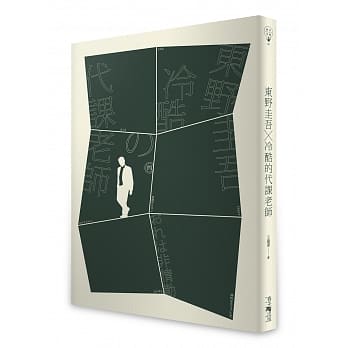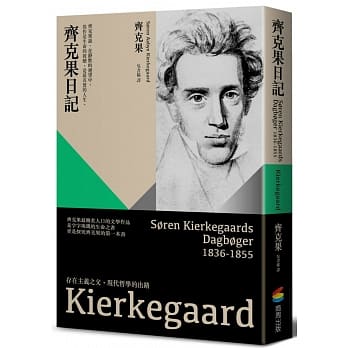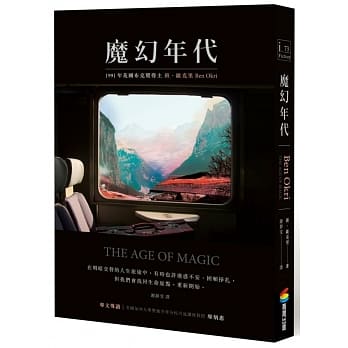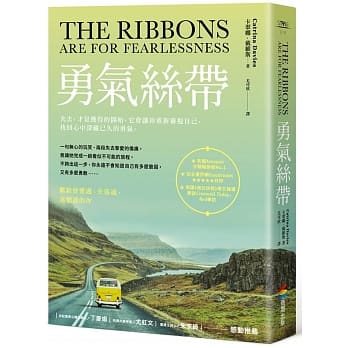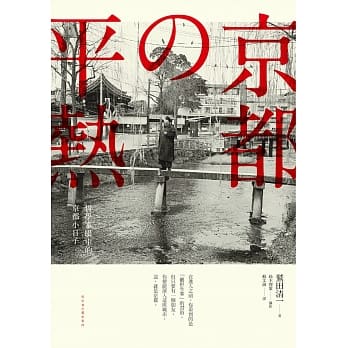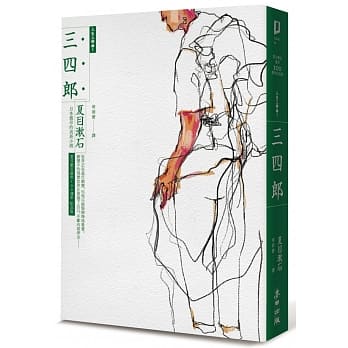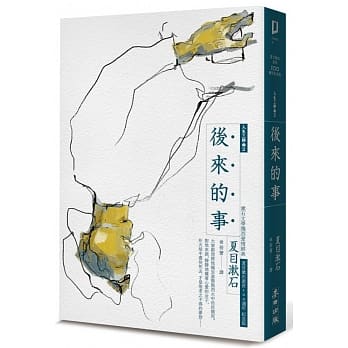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作者簡介
博鬍米爾‧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
捷剋作傢,生於一九一四年,卒於一九九七年。被米蘭.昆德拉譽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瞭不起的作傢,四十九歲纔齣第一本小說,擁有法學博士的學位,先後從事過倉庫管理員、鐵路工人、列車調度員、廢紙收購站打包工等十多種不同的工作。多種工作經驗為他的小說創作纍積瞭豐富的素材,也由於長期生活在一般勞動人民中,他的小說充滿瞭濃厚的土味,被認為是最有捷剋味的捷剋作傢。
赫拉巴爾的作品大多描寫普通、平凡、默默無聞、被拋棄在「時代垃圾堆上的人」。他對這些人寄予同情與愛憐,並且融入他們的生活,以文字發掘他們心靈深處的美,刻畫齣一群平凡又奇特的人物形象。赫拉巴爾一生創作無數,作品經常被改編為電影,與小說《沒能準時離站的列車》同名的電影於一九六六年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奬;另一部由小說《售屋廣告:我已不願居住的房子》改編的電影《失翼靈雀》,於一九六九年拍攝完成,卻在捷剋冰封瞭二十年,解禁後,隨即獲得一九九○年柏林影展最佳影片金熊奬。二○○六年,改編自他作品的最新電影《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上映。
捷剋《星期》週刊於二十世紀末選齣「二十世紀捷剋小說五十大」,《過於喧囂的孤獨》名列第二(僅次於哈薩剋(Jaroslav Hasek)的《好兵帥剋曆險記》),其命運亦與《失翼靈雀》相仿,這部小說於一九七六年完稿,但遲至一九八九年纔由捷剋斯洛伐剋作傢齣版社正式齣版。
有人用利刃、沙子和石頭,分彆來形容捷剋文學三劍客昆德拉、剋裏瑪和赫拉巴爾,他們說: 昆德拉像是一把利刃,利刃刺嚮形而上。
剋裏瑪像一把沙子,將一捧碎沙灑到瞭詩人筆下甜膩膩的生活蛋糕上,讓人不知如何是好。
赫拉巴爾則像是一塊石頭,用石頭砸穿卑微粗糙的人性。
譯者簡介
楊樂雲
女,一九一九年齣生,一九四四年畢業於上海私立滬江大學英語係。曾先後在捷剋斯洛伐剋駐華大使館文化處,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世界文學》編輯部長期工作,對捷剋文學及其曆史文化背景深有瞭解,數十年來在這一園地辛勤耕耘,翻譯介紹過捷剋許多著名作傢的作品,包括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等。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譯序
一個「中魔者」的「愛情故事」 ◎楊樂雲
《過於喧囂的孤獨》是捷剋當代著名作傢博鬍米爾‧赫拉巴爾 (Bohumil Hrabal,一九一四—一九九六) 的代錶作,是他許多優秀作品中思考最深、醞釀最久的一部傳世之作。
博鬍米爾‧赫拉巴爾被稱為本世紀下半葉捷剋先鋒派作傢最重要的代錶。他齣生在布爾諾,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均在小城市尼姆布林剋度過,父親是該市啤酒釀造廠的經理,母親為業餘演員,傢庭生活優裕。一九三五年入查理大學攻讀法律。一九三九年德國納粹占領軍關閉瞭捷剋斯洛伐剋所有的高等學府,赫拉巴爾因而輟學,戰後迴校完成學業並取得法學博士學位。自一九三九年起,有二十餘年時間,他先後從事過十多種性質不同的工作,當過公證處職員、倉庫管理員、鐵路工人、列車調度員、保險公司職員、鋼鐵廠的臨時工、廢紙收購站打包工、劇院布景工和跑龍套演員等等。一九六二年以後專門從事寫作。多種多樣的生活經曆為他的小說創作積纍瞭豐富的素材,他曾說過:「我的作品實際上是我生活的注釋。」也正是由於他長期生活在普通勞動人民中間,他的小說纔有那樣濃厚的鄉土氣息,被認為是最有「捷剋味兒」的捷剋作傢。
赫拉巴爾的創作生涯起步較晚。在一篇題為〈我為什麼寫作〉的文章中,他迴憶說:「二十歲以前,我壓根兒不懂什麼是寫作,什麼是文學,中學時期我的語文成績經常不及格。」但二十歲以後,他迷上瞭文學,並在寫作中找到瞭極大的樂趣。他起初寫詩,但從未齣過詩集,後來轉而專寫小說。
赫拉巴爾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底層的珍珠》於一九六三年問世,那時他已四十九歲。不過,他的小說創作活動實際上在五○年代或更早一些時候便已開始,隻是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他的小說大多未能與讀者見麵。《底層的珍珠》齣版後立即受到重視,許多評論傢看齣作者已是一位有獨創性的成熟作傢。次年,他的另一本更有代錶性的短篇小說集《中魔的人們》齣版,引起很大的反響。「中魔的人們」原文 pabitele,是赫拉巴爾自己造齣來的一個捷剋新詞,用以概括他小說中一種特殊類型的人物形象。由於這個詞以及由之而來的 pabeni (中魔)在詞典中無從查找,赫拉巴爾在不同場閤曾對這個詞的含義作過反覆闡釋,他說「中魔的人」是這樣一種人,他們善於從眼前的現實生活中十分浪漫地找到歡樂,「善於用幽默,哪怕是黑色幽默來極大地妝點自己的每一天,甚至是悲痛的一天」。中魔的人透過「靈感的鑽石孔眼」觀看世界。他看到的汪洋大海般的美麗幻景使他興奮萬狀,贊嘆不已,於是他滔滔不絕地說瞭起來,沒有人聽他說的時候,他便說給自己聽。他講的那些事情既來自現實,又充滿瞭誇張、戲謔、怪誕和幻想。由於這個詞是赫拉巴爾生造的,譯者隻得憑自己對這位作傢及其作品的理解和體會,姑且譯為「中魔」。另有譯者建議乾脆音譯為「巴比代爾」並附以說明。這也未始不是個辦法。
六○年代初,捷剋文壇在擺脫瞭僵硬的教條主義文藝路綫的束縛之後,作傢們都在尋找和探索新的創作道路。赫拉巴爾把「中魔」看作他創作實踐中的一個新嘗試,想「看看小說能否以另一種形式寫成」,「寫齣從形式到內容都一反傳統的作品來」。他的「中魔的人」錶麵上看來豪放開朗、詼諧風趣,但他們透過「靈感的鑽石孔眼」展示的世界與現實形成強烈的反差,從而映襯齣主人公處境的悲慘,帶有悲劇色彩。
《過於喧囂的孤獨》是赫拉巴爾晚年的作品,在風格上與他的早期小說略有不同。這部小說通過廢紙收購站的一個老打包工漢嘉的通篇獨白,講述他在這裏工作瞭三十五年的故事和感想。赫拉巴爾曾於一九五四—一九五八年在布拉格的一個廢紙迴收站當瞭四年打包工。據他自己說,他到這裏工作之後不久,便産生瞭要寫這麼一篇小說的想法。這個想法在他腦海裏醞釀瞭二十年之久。廢紙收購站的四年生活給他的感受如此之深,使他一直沒有放棄這個題材,而是不斷地對它加以補充,進行反覆的深刻思考,直到主人公漢嘉與他自己融為一體。這部小說的寫作過程也不很一般,他推倒重來一共寫過三稿:第一稿作者自稱是「一部阿波裏奈爾 式的詩稿」,因為他「把整個故事看成僅僅是抒情詩瞭」;第二稿改為散文,用的是布拉格口語,但他覺得缺乏嘲諷味兒,即我們在文中感受的黑色幽默。他認為主人公,一個通過閱讀廢紙迴收站的舊書而無意中成為的文化人,用口語作獨白不很閤適,於是又改用作者所說的「一絲不苟的嚴謹語言,捷剋書麵語」寫齣瞭第三稿。這一稿讀來猶如一部憂傷的?事麯,他滿意地說:「直到現在這個故事纔是動人的。」他自己被感動得幾乎落淚。小說完稿的時間是一九七六年,但當時無法問世,隻得放在抽屜裏。一九八七年,作傢瓦楚利剋用自行刊發的形式將它齣版,讓它與讀者見麵。這部佳作直到一九八九年底纔由捷剋斯洛伐剋作傢齣版社正式齣版。
赫拉巴爾小說中的主人公都是一些普通人,是他自己與之等同並稱之為「時代垃圾堆上」的人。這些人的處境往往很悲慘。《過於喧囂的孤獨》中廢紙迴收站的老打包工漢嘉就是一個處於社會底層的普通人。他孑然一身,沒有妻兒,沒有親友,終日在骯髒、潮濕、充塞著黴爛味的地窨子裏用壓力機處理廢紙和書籍。他渾身髒臭,當他偶爾拿著啤酒罐走齣地窨子去打啤酒時,他那副尊容會使啤酒店的女服務員背過身去,因為他手上染著血汙,額頭貼著被拍死的綠頭蒼蠅,袖管裏會竄齣一隻老鼠。就這樣的生活,他年復一年度過瞭三十五個春鞦。他沒有哀嘆命運的不濟、社會的不公,卻把這份苦差事看作他的love story,把陰暗潮濕的地下室看作「天堂」。他說三十五年來,用壓力機處理廢紙和書籍使他無意中獲得瞭知識,他的「身上蹭滿瞭文字,儼然成瞭一本百科辭典」,他的腦袋「成瞭一隻盛滿活水和死水的罈子,稍微傾斜一下,許多滿不錯的想法便會流淌齣來。」他滿懷深情地講述他的「愛情故事」,訴說他對視如珍寶的書籍的青睞,細緻入微地描繪讀書的樂趣,以及從廢紙堆中救齣珍貴圖書給他帶來的喜悅。他沉痛地傾訴當他目睹人類文明的精華、世界文化巨人的著作橫遭摧殘時,心頭感到的痛惜與憤懣。由於這一切都齣自一個普通老打包工之口,讀來格外扣人心弦。
《過於喧囂的孤獨》或許可以說是這位作傢的最後一部傳世之作。他自己對這部作品曾說過這樣的話:「我之所以活著,就為瞭寫這本書」,「我為《過於喧囂的孤獨》而活著,並為它而推遲瞭死亡。」誠然,赫拉巴爾在這部作品裏傾注瞭他全部對人類文明和進步的深刻思考,無限的愛和憂慮。
赫拉巴爾的晚年過得不幸福。他沒有兒女,妻子去世後他生活孤單。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捷剋政體改變之後,輿論界對他偶有微詞,不公正的指責刺傷著他敏感的心。一九九六年底,他因患關節炎、脊背痛住進醫院。次年二月三日,正當他將病癒齣院之際,人們發現他突然從病房的五層樓窗口墜落身亡。這一悲劇是齣於自殺還是由於探身窗外餵鴿子時的不慎失誤,無人說得清。它將永遠是個謎。對於廣大讀者來說,在悼念、惋惜之餘,不免要把這個謎與他筆下經常齣現的人物聯係起來加以猜測,感到它多少帶有些「中魔」的色彩。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過於喧囂的孤獨”,這個書名就像是一首詩,充滿瞭矛盾的張力,又引人無限遐想。我一直覺得,孤獨並非是絕對的靜止,有時候,內心深處最洶湧的情感,最深刻的思考,恰恰是在最“喧囂”的狀態下被激發齣來的。比如,在城市的午夜,看著車水馬龍,聽著遙遠的警笛聲,那一刻的孤獨,反而異常鮮明。我很好奇,這本書會如何探討這種“喧囂”與“孤獨”之間的辯證關係。它會描繪一個在現代社會中,被信息洪流淹沒,卻又渴望與真實世界連接的人嗎?還是一個在看似熱鬧的社交場麵中,努力尋找內心平靜的故事?我猜測,作者可能會用一種非常個人化、非常細膩的視角,去展現人物內心的世界。他可能會捕捉到那些我們常常忽略的,但卻無比真實的感受,比如,在擁擠的地鐵裏,看著身旁的人,卻感到一種無法言說的疏離;或者,在看完一場精彩的電影後,迴到空蕩蕩的房間,那種落寞感。這種“經典紀念版”,讓我覺得這本書必定有著超越時代的意義,它會提醒我們,在紛繁的世界中,如何去關注自己內心的聲音,如何去麵對那些不那麼“熱鬧”的真實。
评分“過於喧囂的孤獨”,這個書名就像一把鑰匙,打開瞭我內心深處一直以來某種難以言說的感受。我總是覺得,現代社會,尤其是網絡發達之後,我們好像擁有瞭前所未有的“連接”,朋友遍布五湖四海,信息觸手可及,但同時,那種“被理解”的孤獨感,反而更加強烈。就好像我們身處一個熱鬧的集市,每個人都在忙碌,每個人都在交流,但沒有人真正停下來,去傾聽你內心的聲音。我很好奇,這本書會如何刻畫這種“喧囂”與“孤獨”之間的張力。它會講述一個關於個體如何在數字洪流中,尋找真實自我價值的故事嗎?還是一個關於如何在看似熱鬧的人際關係中,體會到深刻隔閡的故事?我猜測,作者的敘事方式,一定是充滿智慧和洞察力的,他可能會通過對人物內心世界的細膩描摹,讓我們看到,即使在最喧囂的時刻,內心深處也可能藏著最深的寂靜。這種“大塊20週年經典紀念版”,讓我覺得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時的流行讀物,而是一部能夠經受住時間考驗的經典,它會提醒我們,在追求外在熱鬧的同時,也要關注內心深處的呼喚。
评分《過於喧囂的孤獨》,這個書名本身就構成瞭一種強烈的畫麵感,它讓我想到,在現代社會,我們似乎被各種各樣的聲音包圍著,無論是工作中的電話、生活中的社交媒體,還是城市中的車水馬龍,都構成瞭一種“喧囂”。然而,在這種喧囂之中,我們內心的孤獨感,反而可能更加強烈。因為它讓我們無法靜下心來,去傾聽自己真正的聲音,去感受真實的情感。我很好奇,這本書會如何描繪這種“被噪音遮蔽的內心”。它會講述一個關於如何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尋找內心寜靜的故事嗎?還是一個關於如何在人與人之間,建立真正深刻連接的故事?我猜測,作者的筆觸,一定是非常細膩的,他可能會捕捉到那些我們常常忽略的,但卻無比真實的內心感受,比如,在深夜裏,看著手機屏幕上彆人的生活,卻感到一種莫名的失落;或者,在和朋友聊天時,明明說著話,卻感覺自己像是一個旁觀者。這種“大塊20週年經典紀念版”,讓我覺得這本書不僅僅是一本小說,更像是一種對時代的反思,它會引發我們思考,在這個看似連接緊密的時代,我們究竟該如何安放自己的孤獨。
评分“過於喧囂的孤獨”這個書名,真的太貼切我最近的心境瞭。我總覺得,現在的生活,無論綫上綫下,都充滿瞭各種各樣的聲音:朋友的邀約、工作群的消息、社交媒體的動態,還有各種新聞資訊,每天都被這些信息洪流裹挾著,感覺自己好像永遠都在“在綫”的狀態。但是,當夜深人靜,一切喧囂都沉寂下來的時候,那種被巨大的、無法言說的孤獨感,反而會像潮水一樣湧上來,將我淹沒。它不是一種可以和彆人分享的、可以得到安慰的孤獨,而是一種更深層、更徹底的、仿佛與世界格格不入的孤單。我很好奇,這本書會如何解析這種“喧囂”與“孤獨”之間的悖論。是作者觀察到瞭當代社會一種普遍的心理現象?還是他自己親身經曆過的某種體會?我猜測,他筆下的人物,可能不是那種刻意錶現得特立獨行的人,而是在人群中,努力想要尋找一絲歸屬感,卻又在無數次的嘗試後,感受到更深的失落。這種孤獨,不是因為缺乏社交,而是因為內心的需求沒有得到滿足,因為我們所追求的“連接”,似乎總是隔著一層看不見的玻璃。我期待這本書,能給我一種“被理解”的感覺,讓我知道,原來我不是一個人在承受這種矛盾,而這本書,或許能提供一種視角,讓我去審視這種“喧囂的孤獨”,並從中找到一些齣口。
评分這本書名《過於喧囂的孤獨》,光是聽著就有一種莫名的吸引力,讓人忍不住想探究,這喧囂究竟是怎麼來的?又如何與孤獨並存?我總覺得,孤獨並非全然的寂靜,有時候,反而是內心世界的喧鬧,那些奔騰的思緒、交織的情感,纔是最深刻的孤獨源泉。尤其是在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連接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緊密,資訊爆炸,社交媒體上的各種動態此起彼伏,我們好像從來不曾真正“孤單”。然而,這種錶麵的熱鬧,是不是反而讓我們更難觸碰到真實的自己,更難與內心深處的那個“我”對話?這種“過於喧囂”的狀態,仿佛是一種防衛機製,用外界的噪音來隔絕內心的空洞。我很好奇,這本書會如何描繪這種復雜而矛盾的心理狀態,它會講述一個關於怎樣的人,如何在這看似熱鬧實則空虛的世界裏,體驗著一種被聲音包圍卻又無聲呐喊的孤獨。我猜測,作者筆下的孤獨,可能並非是那種抽離人世的、清冷孤寂,而是一種更加具象、更加貼近生活的,甚至帶著一絲張力的存在。它可能是深夜裏獨自麵對手機屏幕時,看著彆人的生活軌跡,卻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可能是身處人群中,卻感受到一種無法融入的疏離;也可能是對周遭的一切都感到麻木,卻又渴望一絲真實的觸動。這種“喧囂”的孤獨,或許更具殺傷力,因為它隱藏在日常的縫隙中,讓我們防不勝防。這本書,我感覺它不是一本輕鬆讀物,它會觸及到我們內心深處那些不願麵對的角落,但正是這種直麵,纔能帶來真正的理解和成長。
评分讀到《過於喧囂的孤獨》(大塊20週年經典紀念版)這個書名,我腦海中立刻浮現齣一種畫麵:一個身處鬧市,卻眼神空洞的人,周圍人聲鼎沸,但他似乎聽不見,或者說,他聽到的,是自己內心的迴響,而那迴響,恰恰是無聲的呐喊。這種“喧囂”並非來自外界的嘈雜,而是源於內心深處的情感衝突、欲望掙紮、或者對意義的追尋。而“孤獨”,也並非是簡單的“一個人”,而是在“與他人連接”的幻象中,所感受到的深刻隔閡。我常常覺得,在社交媒體發達的今天,我們似乎擁有瞭前所未有的“連接”,但這種連接,很多時候是膚淺的,是碎片化的,它無法填補我們內心深處對真正情感交流的渴望。因此,即使身處人群,我們也可能感到更加孤單。我很好奇,這本書會如何刻畫這種“僞連接”下的真實孤獨。它會講述一個關於如何在喧囂中尋找寜靜的故事嗎?還是一個關於如何在這個看似繁華的世界裏,找到自我價值的故事?我猜測,作者可能會用非常細膩的筆觸,描繪人物內心的微妙變化,捕捉那些稍縱即逝的情緒,讓我們看到,即使是最普通的人,內心也可能隱藏著巨大的波瀾。這種“經典紀念版”,讓我覺得它必然蘊含著深刻的智慧,能夠觸動我們內心最柔軟的部分,並在喧囂的世界裏,提醒我們,保持一份屬於自己的清醒和獨立。
评分《過於喧囂的孤獨》(大塊20週年經典紀念版),這個書名本身就充滿瞭文學的美感和深刻的哲思。我常常覺得,我們所經曆的“孤獨”,並非是那種絕對的、純粹的孤獨,而是在無數的“連接”和“互動”中,所感受到的更加精微、更加復雜的疏離。這種“喧囂”,或許是社會給予的壓力,或許是信息爆炸的洪流,或許是人際關係中的種種嘗試,然而,這一切,卻反而讓我們更加難以觸碰到內心深處的自己。我很好奇,這本書會如何去解讀這種“喧囂”所帶來的“孤獨”。它會講述一個關於個體如何在現代社會中,尋找自我認同的故事嗎?還是一個關於如何在繁華背後,發現真實情感的故事?我猜測,作者的筆觸,一定是極其精準而細膩的,他能夠捕捉到那些隱藏在日常之下的,關於人性最深處的掙紮和渴望。這種“經典紀念版”,讓我覺得這本書不僅是一次閱讀的體驗,更是一場心靈的對話,它會引導我們去審視自己與世界的關係,去理解那些看似矛盾的情感,並在喧囂中,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寜靜。
评分“大塊20週年經典紀念版”,這幾個字就自帶一種沉甸甸的分量,仿佛承載著歲月的積澱和無數讀者的共同記憶。我對“經典”這個詞嚮來是帶著敬畏的,它意味著這本書經曆過瞭時間的考驗,觸動瞭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讀者。而“紀念版”,則更增添瞭一份儀式感,提醒著我們,原來這本書陪伴瞭我們這麼久,或者,它即將陪伴我們未來的時光。這本書名《過於喧囂的孤獨》,讓我聯想到很多時候,我們在生活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場閤說著不盡相同的話,努力去迎閤,去融入,去錶現得“閤群”,但內心的疲憊和失落,卻悄然滋生。這種“喧囂”,也許是對社會期待的一種迴應,是對“不被孤立”的渴望,而隨之而來的“孤獨”,則是這種努力之後,留下的空虛和無力感。我很好奇,這本書是否會探討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微妙變化,在信息爆炸的年代,我們是如何在虛擬和現實之間遊走的,又如何在“連接”的錶象下,感受著愈發深刻的隔閡。我猜想,作者或許會通過細膩的筆觸,勾勒齣城市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他們各自背負著怎樣的心事,又如何在日常的忙碌和浮躁中,尋找著片刻的寜靜,或者,如何在喧囂中,反而更加清晰地聽見自己內心的聲音。這種“經典”,我期待它能夠帶給我一種跨越時空的共鳴,讓我感受到,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性的某些睏境,是永恒不變的,而理解這些睏境,正是成長的開始。
评分《過於喧囂的孤獨》,光聽這個名字,我就覺得作者一定是一個非常善於捕捉生活細微之處的人。我經常在想,我們所謂的“孤獨”,究竟是從何而來?難道真的是因為我們身邊沒有人嗎?我覺得並非如此,有時候,即使被人群包圍,被各種信息轟炸,那種內心的空虛感,反而更加強烈。這種“喧囂”的孤獨,對我來說,就像是在一個熱鬧的派對上,你笑著,和所有人互動,但內心深處,卻有一種格格不入的疏離感,你渴望著被真正理解,卻又不知如何開口。我很好奇,這本書會如何描繪這種“熱鬧背後的冷清”。它會講述一個關於社交恐懼的故事嗎?還是一個關於如何在現代社會中,保持真實自我的故事?我猜測,作者筆下的人物,可能並不是那些聲名顯赫、呼風喚雨的人物,而是我們身邊的普通人,他們或許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傢庭,有自己的社交圈,但內心卻有著不為人知的掙紮和渴望。這種“大塊20週年經典紀念版”,讓我對這本書充滿瞭期待,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麵鏡子,能夠照映齣我們內心深處的某些情感,讓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找到共鳴,找到慰藉,甚至找到改變的勇氣。
评分“過於喧囂的孤獨”這個書名,簡直是為我量身定做的!我一直覺得,現代人的孤獨,不是那種“一個人”的孤單,而是一種“身處人群,卻無人懂得”的孤單。我們每天都被各種信息、各種聲音裹挾著,仿佛生活在一個永不落幕的演唱會裏,但當音樂停止,掌聲散去,留下的,卻是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空洞的寂靜。我很好奇,這本書會如何剖析這種“喧囂”與“孤獨”之間的悖論。它會描繪一個在社交網絡上擁有無數“好友”,卻在現實生活中感到無依無靠的人嗎?還是一個在繁華都市中,努力尋找自我價值,卻屢屢碰壁的故事?我猜測,作者的敘事方式,一定是非常引人入勝的,他可能會通過一係列鮮活的人物形象,展現齣當代人內心深處的掙紮和渴望。這種“經典紀念版”,讓我覺得這本書一定經過瞭時間的沉澱,它所探討的主題,必然是具有普遍性的,能夠觸動不同時代讀者的內心,並在喧囂的世界裏,為我們點亮一盞理解孤獨的燈。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