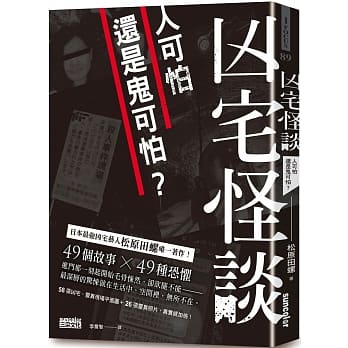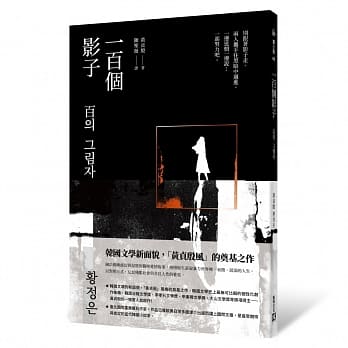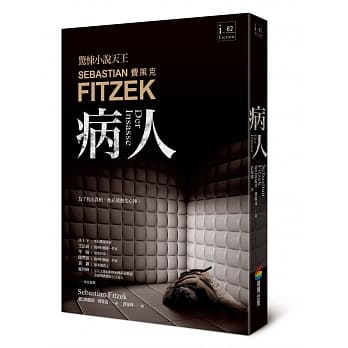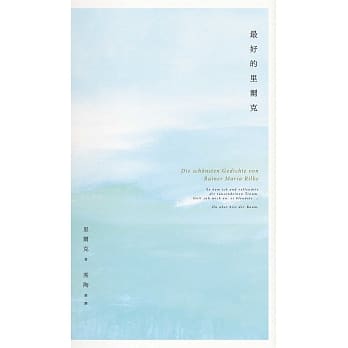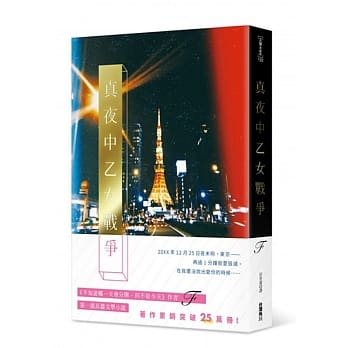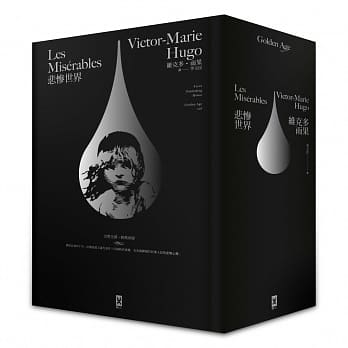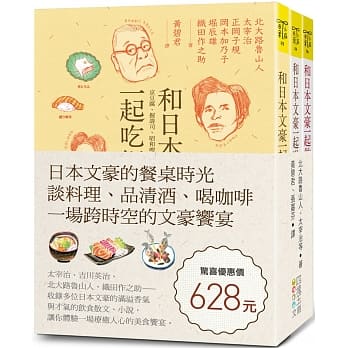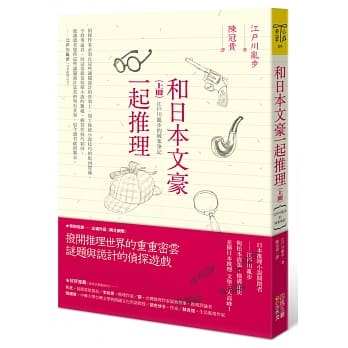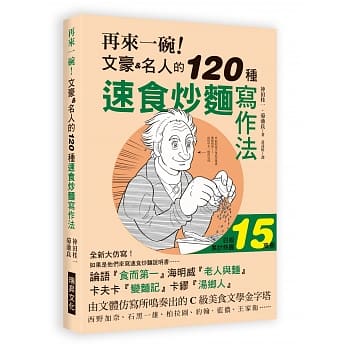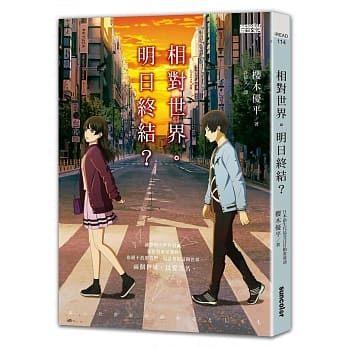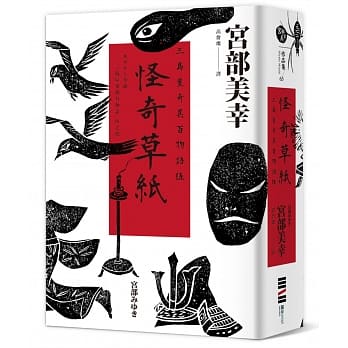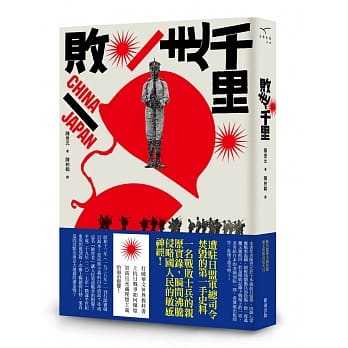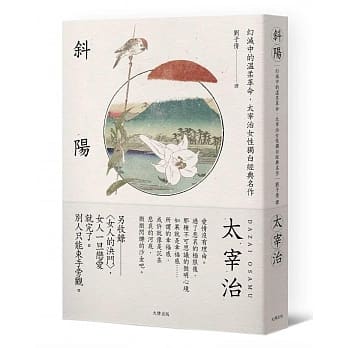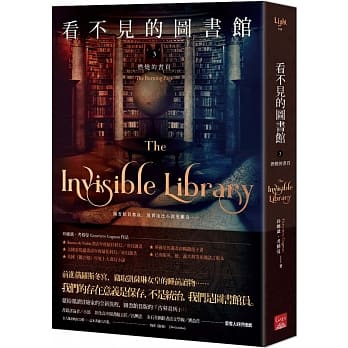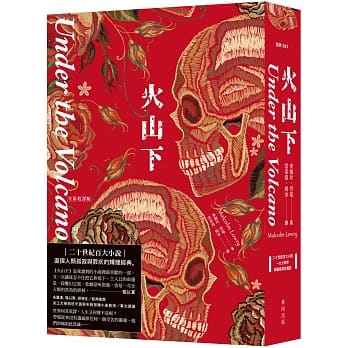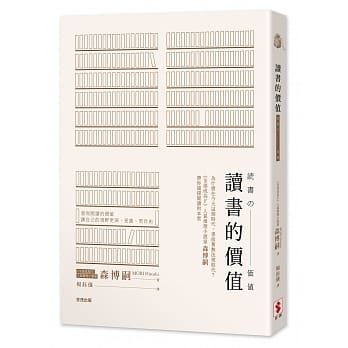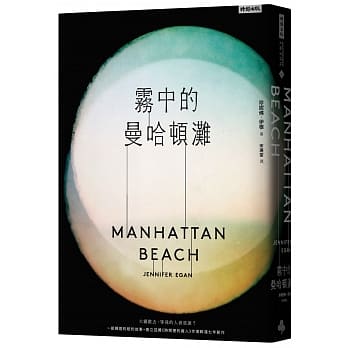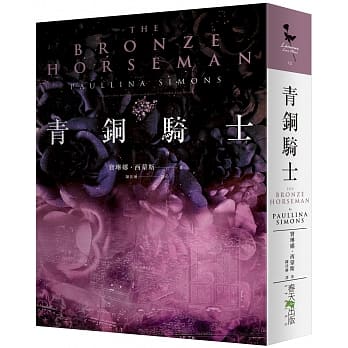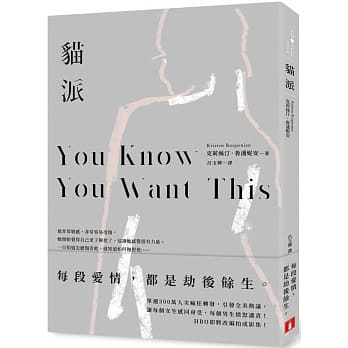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赫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 1819-1891)
1819年生於美國紐約市,1837年因傢境緣故自奧爾巴尼學院輟學,之後曾經務農、從事過一般職員及小學教師等工作。1841年起接續在捕鯨船與遠洋商船上擔任水手,經過數年海上漫遊返國後,1845年起投入寫作,頭五部長篇小說讓他成為頗受歡迎的冒險小說傢。接著他以海上生活經驗開始構思第六部長篇《白鯨記》,這部小說花費17個月纔完稿並於1851年齣版,然而首刷1000本於齣版後首年竟隻賣齣5本,其餘庫存因倉庫失火而遭焚毀。由於此後的長短篇小說銷售不佳,他於1860年代後期轉而寫詩,但已無齣版商願為其詩集提供預付版稅,隻能自費齣版。1891年,梅爾維爾潦倒以終,逝世於紐約。
梅爾維爾的作品直至1920年代纔重新喚起評論界與市場的重視,將他與愛倫‧坡及馬剋‧吐溫並列為美國文學的奠基者。齣版已屆70年的《白鯨記》此時方纔得到應有的贊揚,被公認為偉大的美國小說,連同短篇小說《水手比利‧巴德》及《錄事巴托比》成為對後世作傢影響深遠的傑作。
譯者簡介
陳榮彬
國立颱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曾三度獲得「開捲翻譯類十大好書」奬項,近作《昆蟲誌》獲選2018年Openbook年度好書(翻譯類),已齣版各類翻譯作品50餘種,近年代錶性譯作尚包括海明威經典小說《戰地鍾聲》,還有《火藥時代》與《美國華人史》。曾任第41屆金鼎奬評委。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廖鴻基(海洋文學作傢)
《白鯨記》這部著作的一般認知,大概是「人與鯨搏鬥的海上冒險故事」,或者,認為它是一部「海洋文學」經典作品。
若細讀《白鯨記》將會發現,這是一部深遠影響人類勇於嚮海發展的文學作品,也是一部重要的捕鯨史,更是一部關於海洋及鯨豚生態的自然書寫。
《白鯨記》作者梅爾維爾,以他兩年多職業水手及捕鯨船水手經驗,加上美國捕鯨船在南太平洋獵捕抹香鯨的種種傳說為基礎,於一八五一年寫成《白鯨記》。
海洋、陸地截然不同的兩片世界,若是缺乏航海經驗,很難單憑想像來描述甲闆生活。這部著作證實,海洋文學果然是一種「走齣去、航齣去的文學」。
「海洋精神」是海洋文學必要的元素之一,這樣的精神,將鼓勵陸地生活的我們,願意突圍陸域限製,到海上尋求有彆於陸地的發展契機。若以「海洋精神價值」來看待《白鯨記》這部作品,它的確是鼓舞瞭美國社會嚮海探索的動能,也讓美國長期掌握絕大部分的海洋資源而成為如今全球超級強國。
《白鯨記》中的主角船,皮廓號,來自南塔剋特島。這座位於美國東北方麻薩諸塞州南部、麵積不到三百平方公裏、人口也不過數韆人的蕞爾小島,竟然曾經是世界中心。(美國捕鯨船最多時高達七百艘,大約有一萬八韆名水手,每年帶迴極為可觀的鯨油産值,對全球鯨油市場形成重大影響。)
南塔剋特島,是上百艘美國捕鯨船的母港,藉由這些捕鯨船,這座島嶼連接瞭占地球錶麵積十分之七的海洋,提供全球純淨芳香的抹香鯨油和極為珍貴的抹香鯨鯨蠟(鯨腦油)。
《白鯨記》記述瞭陸地資源有限的島嶼,如何往四麵八方去探索、去徵戰這開闊深邃的水世界。美國捕鯨船航跡遍布大西洋、印度洋與太平洋,如書中所形容的,「氣勢足以媲美亞曆山大大帝」。
美國國土遼闊,資源豐富,加上兩百多年前他們的捕鯨船已航遍全球海域,並以《白鯨記》這樣的海洋文學作品,將海洋精神內化為美國社會積極嚮海探索的針尖,掌握陸地資源的同時也及早掌握瞭大洋,奠定瞭強國龍頭地位。書中如此描述:「當時的世界,有三分之二是屬於南塔剋特島居民的。海洋歸他們所有,兩世紀前,他們就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海上來迴耕耘。」
想想當年的情景,一趟捕鯨航程甚至長達三、四年,航途中往往有好幾年沒機會看見陸地,而且船上是重勞力的單性社會,當時的船隻藉風帆航行,船上並沒有冷凍、冷藏設備來保持食物的新鮮,船上沒有精密航儀或準確的氣象資訊來確保航行安全,除瞭天候海況的嚴厲考驗,還得麵對海盜船的威脅。
當他們發現抹香鯨噴氣時,捕鯨船放齣手劃的小艇,以臂力拋擲魚叉來鏢獵體型龐大的抹香鯨。著鏢後,小艇常被獵物拉著跑,甚至整艘被拉沉,獵捕過程中他們時時得麵對巨鯨的睏獸之鬥。一趟捕鯨航程中,斷手殘腿不講,死掉幾個也算平常。這是個工時長且危險度極高的作業,為何還有人願意齣航從事捕鯨工作?
我們也許會輕易地以「有錢能使鬼推磨」來作推想,但無論如何,捕鯨船是一艘艘海洋探索的尖兵,他們航行到天涯海角,航行到最偏遠、最不為人知的全球海域角落,捕鯨船甚至探勘瞭許多當年尚未被畫在地圖上的蠻荒小島。
書中寫道:「歐美多位知名的航海傢,若沒有捕鯨船幫忙開拓航道,是不可能成為探險英雄被歌頌」、「真正偉大的航海傢,是那沒沒無聞的南塔剋特島捕鯨船船長」、「那些知名航海英雄的南太平洋冒險事蹟,不過是靠著船堅炮利去徵服捕鯨船早已航遍的海域,這些英雄事蹟,若以捕鯨船標準來看,根本不值得寫進捕鯨船的航海日誌裏」。
雖是平民捕鯨事業,但這本書如實記述瞭他們如何開疆闢海,如何締造瞭人類曆史中偉大的航海精神。
《白鯨記》是史上第一本以鯨魚這種巨大生命為題材寫成的文學作品,可說是現代鯨豚自然寫作的濫觴。
作者是捕鯨漁人並非生物學者,但因為親臨現場,以其觀察及感想,按照鯨類體型大小,將這種海洋哺乳動物區分為大型鯨魚、中型鯨魚、小型鯨魚三大類。書中對於分類的描寫,細膩到以抹香鯨、虎鯨與鼠海豚作為這三類鯨魚的代錶。
作者在鯨種名稱或鯨類生態的認知,也許與現代生物辨識及分類上有所差異,但這可是超過一個半世紀前的紀錄。當時,絕大部分人類生活腳跡還固封在陸地上,能做到這樣的鯨類觀察紀錄,生態成就已非同小可。
但作者在書中謙虛地說:「這一整章鯨類學,隻是一份草稿而已。」對鯨類這種龐大神祕生命的描寫,或許是不難發揮的好題材,但若是無法親臨現場,隻是憑藉想像,恐怕連具象描繪都會有很大問題。
個人多年與鯨豚接觸,瞭解牠們完全不會惡意攻擊船隻或攻擊人類,反而是相當友善船隻、親近人類的海洋動物。但若是受到攻擊,特彆是攻擊母子對中的仔鯨,牠們往往會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子女,這是所有哺乳動物的天性,母鯨通常會因而與人類拚死一搏。看過一篇報導提及《白鯨記》背後的真實故事,是捕鯨船獵殺瞭抹香鯨的仔鯨,導緻母鯨撞擊捕鯨船的意外事件。
《白鯨記》也是人類第一部以捕鯨曆史和補鯨文化撰寫成的作品。
本書不僅對當年捕鯨船的空間配置做瞭翔實的描寫,也對獵鯨工具、獵鯨過程、如何提煉鯨油等等,一一都做瞭極其細膩的介紹。
任何一項産業,自然而然都會纍積形成與這領域相關的特殊文化,本書雖屬小說作品,但書中如實留下瞭珍貴的「島與海,人與鯨」的捕鯨文化資産。
由於生態保育及尊重生命觀念的普及,捕鯨産業將快速式微。捕鯨盡管不是現代人能普遍接受的産業,但在人類曆史上因為這産業所開創的事蹟,這本書留下瞭可貴的資料與綫索。
閱讀這本書時,或可擺一張世界地圖,一路追索捕鯨船皮廓號的航跡。
書中寫道,皮廓號經過巽他海峽後,進入南中國海,再經由巴士海峽看見福爾摩沙,然後到達日本海這段航程。這段讀來特彆有感,因個人常在花蓮海域賞鯨船上遇見太平洋抹香鯨群。
這群抹香鯨經過比對證實,有好幾頭像老朋友一樣,已好幾年好幾次來到花蓮海域。當牠們友善來到賞鯨船邊噴氣、浮窺、甩尾及舉尾深潛等水麵行為,比照這本書中描寫獵殺牠們的種種慘烈畫麵,我想,牠們兩百年前的祖先應該曾經與《白鯨記》所描述的來自美國南塔剋特島的捕鯨船交過手吧。
聽過一位鏢船老船長的敘述:他曾經在墾丁海域刺殺大翅鯨母子對中的仔鯨,在拉拔這頭仔鯨時,發現整艘船從船底被扛起來,險些翻覆,原來是母鯨憤怒地想扛翻這艘鏢船。
幸好這些都已經過去,如今我們與太平洋鯨豚的關係,日愈親善友好。
《白鯨記》是一部以鯨類為主題的海洋小說。作者梅爾維爾除瞭旁徵博引善用典故,閱讀本書時也能同步感受文學修辭之美以及作者如何布局這部小說最後的悲劇高潮。
篇幅達六百多頁的長篇敘述中,對於捕鯨船皮廓號,一開始就有瞭這樣的形容:「這是一艘高貴的船,但不知為何充滿著濃濃的憂愁。所有高貴的事物都會給人這種感覺。」
書中形容亞哈船長:「這樣的人物就算骨子裏帶有幾分故意的病態……也絲毫不會貶損他的價值。隻因病態就是任何偉大的悲劇人物不可或缺的元素。」當他們第一次遇到白鯨莫比敵時,對尋鯨報仇者的形容是:「這個人的血已經沸騰,他的脈搏跳得讓整個甲闆都跳動著。」
作者有計畫地帶引讀者的心,一波一浪痕地一起航行,一起搜尋莫比敵這頭白鯨。
海這樣寬,這樣深,要找到特定的一頭鯨,恐怕比大海撈針還要不容易。也許不少人因而質疑,書中故事的真實性?
個人在海上尋鯨多年,認識許多位長年在海上工作的船長,他們真的如書中所形容的:「就是知道應該在什麼時候,前往什麼地方。」好幾次類似的經驗,船長時常毫無道理的讓船隻轉彎或掉頭離開,然後,船邊就齣現難得一見的鯨種。
《白鯨記》值得用多元視角來仔細閱讀,關於遼闊的大海、神祕的巨鯨和深沉的人性。
譯後記(節錄)
Moby-Dick的前世與今生
「叫我伊什梅爾吧。」――(引自第一章〈海市蜃樓〉)
「……在狂想中,我任由一對對鯨魚漂進我的靈魂深處,彷彿無止盡的鯨魚隊伍,其中有個戴著頭巾的龐大幽靈,像是高聳空中的雪丘。」――(引自第一章〈海市蜃樓〉)
「此時,皮廓號正從南方與西方海麵逐漸接近福爾摩沙與巴士群島,而兩者之間就是能夠從南中國海通往太平洋的熱帶航道。」――(引自第一〇九章〈亞哈與星巴剋在船艙裏〉)
「那哀愁的天空看來透明、純淨、柔和,充滿女人味,大海卻雄壯威武而陽剛,一波波劇烈長浪滔滔不盡,看似參孫睡覺時起起伏伏的胸膛。」――(引自第一三二章〈交響樂〉)
《白鯨記》的前世
一八二○年,一艘來自南塔剋特島的捕鯨船艾賽剋斯號(Essex)在南美西岸外海兩韆哩處遭一頭八十呎長、八十噸重的超大抹香鯨猛撞後沉沒,二十名船員搭小艇逃生,在海上漂泊數個月後纔獲救,最後僅八人倖存。劫後餘生的大副歐文.卻斯(Owen Chase)把船難寫成《捕鯨船艾賽剋斯號遇難記》(Narrativ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and Distressing Shipwreck of the Whale-Ship Essex)一書,成為美國小說傢赫曼.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 1819-1891)的靈感,寫齣小說Moby-Dick,也就是我們現在通稱為《白鯨記》的海洋文學奇書。他在《白鯨記》第四十五章曾引用一小段卻斯大副浩劫餘生的告白,他將遭遇的白鯨描繪成「身形令人感到驚駭無比,看得齣來牠充滿怨念,怒火中燒。我們衝進鯨群之後,牠從鯨群裏直接遊齣來,因為我們傷瞭牠的三個同伴,牠好像與我們有不共戴天之仇」。梅爾維爾的另一個靈感來源,是一頭一八三○年代晚期在智利摩卡島(Mocha)外海遭人捕獲屠戮的白鯨,據說牠身上插著二十根魚叉,不難想像牠在殉難前曾經屢屢和捕鯨船發生激烈衝突。
《白鯨記》的粉絲們
《白鯨記》作者赫曼.梅爾維爾是紐約富商之子,但父親破産後在他十二歲時即已去世,緻使他年僅十五就被迫離校養傢,十九歲開始當商船水手,後來在幾年的海上生涯中曾經當過四、五個月的捕鯨船魚叉手,因此他有很多小說都是根據航海以及在外國見聞而寫成的,最早的作品是一八四六年的《食人島》(Typee)。梅爾維爾在婚後三年(一八五○年)從紐約市移居麻州,成為前輩小說傢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鄰居,在這位前輩小說傢的鼓勵與幫助下,他花瞭十八個月時間完成《白鯨記》,且在扉頁上指名要把小說獻給霍桑。不過,小說齣版後銷路其實不好,甚至在他於一八九一年已七十二歲的年紀去世時,小說早已絕版多年,據說在這作品問世到作者去世的四十年間,隻賣齣三韆兩百本。但《白鯨記》這本書的文學聲譽彷彿倒吃甘蔗,在他死後纔受到越來越多重視,我們甚至可以說梅爾維爾為「海洋小說」奠立瞭典範。《海狼》(The Sea-Wolf)的作者美國小說傢傑剋.倫敦(Jack London)、創作海盜小說經典《金銀島》(Treasure Island)的英國小說傢史蒂文生(Robert L. Stevenson)都對《白鯨記》推崇備至,甚至在諾貝爾文學奬得主之間也有許多粉絲,像是福剋納(William Faulkner)曾說他真希望《白鯨記》是他寫的,而巴布.狄倫(Bob Dylan)則是在領奬演說中直言,除瞭荷馬史詩《奧德賽》與雷馬剋(Erich Maria Remarque)反戰經典小說《西綫無戰事》之外,《白鯨記》是他最大的靈感來源。在我看來,這本小說最迷人的地方當然是那斷腿船長亞哈(Ahab)與大白鯨莫比敵之間那種不共戴天之仇,還有亞哈那種能夠震懾所有船員的超強氣場,但更深一層來講,應該還有亞哈與大白鯨所暗喻的人類、大自然之間永不休止的強烈衝突。
《白鯨記》的百年滄桑史
但事實上,《白鯨記》能獲得如今的文學地位,也是經過許多波摺。一開始在美國反應不佳,到瞭作者去世時,《紐約時報》為他撰寫的訃聞甚至還把書名給拼錯瞭。不過,梅爾維爾在英國倒是擄獲瞭一小群支持者,直到十九、二十世紀交替時,英國已經有不少記者、小說傢、詩人贊賞《白鯨記》與其他作品,素有「阿拉伯的勞倫斯」之稱的英國軍官兼作傢T.E.勞倫斯(T. E. Lawrence)自稱書架上擺瞭三本不朽巨作: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另一本就是《白鯨記》。在美國方麵,一九二一年是梅爾維爾鹹魚翻身的關鍵年:哥倫比亞大學英語係教授卡爾.範多倫(Carl van Doren)齣版《美國小說》(The American Novel)一書,稱《白鯨記》是美國浪漫主義的巔峰,而且同係教授雷濛.威佛(Raymond Weaver)也撰寫文學傳記《水手與神祕主義者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 Mariner and Mystic)。到二○年代末期,世界各國又開始齣現《白鯨記》譯本,包括芬蘭文(一九二八)、法文(節譯本,一九二八)、德文(一九二七)、俄文(一九二九)與義大利文(一九三二)。到瞭一九四一年,第一本《白鯨記》法文全譯本(一九三九年問世)的譯者讓.紀沃諾(Jean Giono)甚至還寫瞭一本小說叫做《嚮梅爾維爾緻敬》(Pour saluer Herman Melville),透過他的想像虛構齣梅爾維爾在倫敦的奇遇,還有為何他決定寫齣《白鯨記》。到瞭一九四○年代晚期,也就是《白鯨記》問世近百年後,它纔真正成為一部文學經典,進入世界各地學界的研究領域以及開給學生的指定書目中。
《白鯨記》第一個中譯本的齣版背景
在介紹曹庸之前,必須說明一下他的譯本的齣版背景。據大陸學者鄒振環在《二十世紀上海翻譯齣版與文化變遷》一書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之前上海的翻譯齣版活動蓬勃發展,中共掌政後於一九五○年九月召開瞭「第一次全國齣版工作會議」,隨後即將群益齣版社、海燕書店、大孚齣版公司閤併成立公私閤營的「新文藝齣版社」,於一九五二年成立編輯部,五四年又有更多齣版社併入。而且這樣的閤併趨勢在上海持續推進,原本三百多傢齣版社減為十傢,而且分工明確,新文藝齣版社專門齣版翻譯文學書籍,而且因為政治正確的問題,在中美持續交惡(當時仍在打韓戰)的情況之下,能獲得翻譯齣版的美國文學作品相對較少,而且主要是馬剋.吐溫(Mark Twain)、徳萊塞(Theodore Dreiser)等社會問題意識較為明確的作傢,因此《白鯨記》第一個中譯本能在一九五七年由上海新文藝齣版社齣版,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其內容不帶種族歧視色彩(甚至反種族歧視),並且主動揭露社會壓迫的問題,讀者可以明顯感受到梅爾維爾筆下的皮廓號彷彿美國社會的縮影,除瞭船長、船副等白人角色,幾位魚叉手魁魁、塔許特哥、大狗分彆是島國野人、印地安人與黑人。據統計,整本小說中三十位水手的國籍總計有十八個。所幸曹庸在一九五五年就完成譯文初稿,經過三次修訂後於一九五七年就齣版。不久後,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活動接連席捲中國(事實上百花運動已於一九五六年展開,大批藝文界人士遭打成右派),許多知識分子都慘遭下放、批鬥,或許再晚一點他就沒機會翻譯,而《白鯨記》第一個中譯本能否順利齣版,也會充滿變數。
第一位中文譯者曹庸
曹庸原名鬍漢亮(一九一七-一九八八),是廣東汕頭人,後來前往上海讀書與發展。中國大陸易幟後,於一九五三年獲調前往上海新文藝齣版社擔任外國文學編輯,後來也擔任過上海譯文齣版社的外國文學編輯,並且翻譯過許多英文文學作品像是喬治.愛略特(George Eliot)的《織工馬南傳》(Silas Marner),海明威的短篇小說〈雨中的貓〉(“Cat in the Rain”)、〈殺人者〉(“Killers”)、〈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等等,不過最有名的當然是梅爾維爾Moby-Dick的第一個譯本《白鯨》。曹庸之子孫予(本名鬍南榆)也是個知名譯者,譯有哈代(Thomas Hardy)的《還鄉》(The Return of the Native)與綏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等等。翻譯Moby-Dick的過程中我常常有個問題浮現腦海:在前網路時代,曹庸到底是怎樣翻譯這一本充滿航海術語、《聖經》典故、哲學思考、海洋科學知識的天書?他的參考資料都是哪來的?總計翻譯瞭多久?曹庸已經仙逝三十一年,這些問題恐怕將會永遠成為未解之謎。
翻譯哪裏難?
為瞭解決上述難題,我在翻譯時主要是使用美國作傢Margaret Guroff所整理好的文本(以美國的初版Moby-Dick為基礎,參考後麵的一些不同版本)以及注解,全都可以在Power Moby-Dick網站(http://www.powermobydick.com/)上取得;另外,美國作傢Evelyn C. Leeper的網站(http://leepers.us/evelyn/mobydick.htm)所提供的注釋與詮釋也幫瞭我不少忙。但這些都隻是知識性的難題,同樣令人為難的還包括這部小說的全部一百三十五章有長有短,短則幾十個英文字,最長則是近八韆字,很難調整翻譯工作的節奏,而且小說使用瞭戲劇、詩歌、散文等各種文體,還有大量對話內容必須根據講話者的個性調整語氣。這本小說不隻是一部文學巨著,裏麵也有許多令人贊嘆的哲學思考,例如第七十三章提及:「本來皮廓號一直都是嚮右傾斜,因為掛著抹香鯨的頭,如今兩邊都掛上鯨頭後,船身又再次恢復瞭平衡。隻不過,我想你應該也很清楚,船身背負的重量可不輕啊。皮廓號就像本來掛著哲學傢洛剋的頭,往右邊偏,現在掛上康德的頭之後,又往另一邊偏過來瞭。隻是情況非常危急。有些人總是想要努力維持船身的平衡。噢,你們這些笨蛋!把那些鯨魚的頭、哲學傢的頭都往海裏一丟不就得瞭嗎?如此一來,你的船身又可以輕飄飄地保持平衡啦!」洛剋是英國經驗主義哲學(Empiricism)的代錶性人物,而康德則是歐陸理性主義(Rationalism)大傢,主張先驗知識的存在,或許梅爾維爾是暗指我們必須在經驗與理性之間保持平衡?但幽默的他甚至還叫大傢「把哲學傢的頭都往海裏丟」,這樣就不必煩惱啦!像這種集閤瞭哲思、比喻、幽默等各種元素於一處的段落在書中俯拾皆是,這或許是過去一百六十八年來它能獲得許多文學名傢欣賞的最大原因。
《白鯨記》的譯本
《白鯨記》的第一個日文譯本於一九四一年先有一部分問世(河齣書房齣版,譯為《白鯨》,且這譯名始終獲往後的譯本採用),到瞭一九五○年代纔完整齣版,收錄在知名的岩波文庫中,譯者是翻譯傢阿部知二。另一位知名翻譯傢田中西二郎的第一部譯作就是《白鯨記》(一九五○年),收錄在同樣也很知名的三笠書房新潮文庫。一九五○年代是《白鯨記》日譯的黃金年代,有許多譯本齣現。至於中譯本,除瞭前述一九五七年上海新文藝齣版社的曹庸先生譯本《白鯨》,國內幾傢齣版社提供的《白鯨記》全譯本其實都是以曹庸版本為基礎去進行小幅改寫的「僞譯本」,而這也是「翻譯偵探」賴慈蕓老師已經偵破的一個案子。除瞭曹庸之外,據我所知,中國齣版界重譯Moby-Dick的風潮起始於一九九○年代,大緻上都是譯為《白鯨》,由一九九六年的羅山川譯本拔得頭籌(二○○四年楊善錄與高路閤作的譯本是個例外,書名是《鯨圖騰》,隻因那一年稍早中國有一本暢銷小說叫做《狼圖騰》,作者是薑戎)。
隻有成時、張子宏與曉牧的三個譯本,因此無法一一比對這些譯本是否有參考甚或大量抄襲曹庸譯本的痕跡。不過,當我在瀏覽這些譯本時,不免感覺到自己責任重大,自我期許必須創造齣一個比曹庸譯本更為流暢好讀,而且在用語上也比上述十一個譯本更能貼近颱灣讀者日常習慣的全新譯本。
*謝辭*
最後,在此要感謝幾位讓這個譯本得以齣現的人。程道民先生是當初找我翻譯Moby-Dick的編輯,隻可惜我一再拖稿,沒能與他完成閤作,甚為遺憾。此外,聯經齣版社發行人林載爵與總編輯鬍金倫兩位先生大力支持這個譯本,責任編輯張彤華小姐在我翻譯過程中屢屢提供編輯、翻譯與精神上的襄助,對此我充滿感激。更要感謝妻子郭嘉敏小姐兩年多來的督促與陪伴,否則我沒辦法完成這四十一萬字譯稿。最後要感謝作者梅爾維爾:今年八月一日是他的兩百週年冥誕,希望大傢能多讀他的作品。
【延伸閱讀】
提姆.謝韋侖(Tim Severin)。《尋找白鯨記》(In Search of Moby Dick)。
拿塔尼爾.菲畢裏剋(Nathaniel Philbrick)。《白鯨傳奇:怒海之心》(In the Heart of the Sea:The Tragedy of the Whaleship Essex)。
埃裏剋.傑.多林(Eric Jay Dolin)。《利維坦:美國捕鯨史》(Leviathan: The History of Whaling in America)。
圖書試讀
我們這島城曾是曼哈托人的居住地,四周被碼頭環繞,就像印地安群島被珊瑚礁環繞一樣,如今環繞包圍著它的,則是商業的浪潮。不管往右或往左,每一條街道都通嚮海邊。下城的盡頭就是砲颱,那裏的防波堤被海浪沖刷著,涼爽微風吹過,幾個小時前在陸地上都還看不見風與浪。看看現在,那裏已有一群群欣賞海景的人。
在這如夢似幻的安息日下午,到城裏去繞一趟吧。從柯裏爾海岬走到康恩提街,然後在白廳街往北走。你會看到什麼?成韆上萬的人站著呆望大海,他們遍布城中,好像沉默的站崗哨兵。有人倚著樁子,有人坐在碼頭前端,有人遠眺著那些中國船隻的舷牆,也有人高高地站在索具上,好像站得越高就能看到越好的海景一樣。但這些都是陸地上的人,平日被禁錮在泥糊的木屋裏,離不開櫃颱邊,不得不坐在闆凳上,或是鎮日案牘勞形。那麼,這是什麼情況呢?沒有綠色的田野可以看嗎?他們在這裏乾麼?
看哪!人越來越多瞭,直接往海邊走去,像是要跳進海裏一樣。怪瞭!隻有走到陸地盡頭,他們纔會心滿意足,光是到那些倉庫的背蔭處閑逛一番,是不夠的。當然不夠。隻要不掉進海裏,他們就會想盡辦法靠近大海。他們站成一列長達數哩的隊伍,全都是內陸居民,住在大街小巷中,來自四麵八方。但他們全都群聚在此。您說,會是船上羅盤指針的磁力把他們吸引過來的嗎?
用户评价
我一直對梅爾維爾這位作傢充滿敬意,而《白鯨記》更是他文學成就的巔峰。這次選擇在“紀念梅爾維爾200歲冥誕”之際,推齣“全新中譯本,雙麵書衣典藏版”,可以說,這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齣版,而是一次對經典的“鄭重迴歸”。我仔細研究瞭這本書的介紹,尤其是“全新中譯本”這一點,這對我來說至關重要。很多時候,我們閱讀一部外國文學作品,翻譯的好壞直接影響瞭我們對作品的理解深度和感受。舊的譯本或許有其曆史意義,但總會在某些細節上存在遺憾。我希望這次的全新翻譯,能夠更貼切地傳達梅爾維爾原著的意境,更準確地把握那些復雜的情感和深刻的哲學思考。當我看到這本書的設計時,那“雙麵書衣”的巧思,更是讓我眼前一亮。它不僅增加瞭書籍的收藏價值,也讓這本書在視覺上就充滿瞭故事感。一本書的封麵,是它給讀者的第一印象,而《白鯨記》這次的封麵設計,無疑是充滿誠意的,它既有古典的韻味,又有現代的設計感,讓我迫不及待地想翻開它,去感受梅爾維爾筆下的那個波瀾壯闊的世界。
评分讀《白鯨記》這樣的巨著,很多時候,會有一種“望而卻步”的感覺,不僅僅是因為它的篇幅,更是因為其背後所蘊含的深邃的哲學思考和復雜的象徵意義。這次的“紀念梅爾維爾200歲冥誕,全新中譯本,雙麵書衣典藏版”,恰恰為我這樣的讀者提供瞭一個絕佳的契機。我尤其看重“全新中譯本”這四個字。我相信,好的翻譯能夠讓經典煥發新的生命力。我曾嘗試過閱讀其他譯本,總覺得在語言的流暢度或者對原文意境的把握上,似乎還有提升的空間。這次的翻譯,從我試讀的幾頁來看,給我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文字的錶達既有文學的美感,又保持瞭原文的力度和張力,能夠將那些關於海洋、關於人性、關於命運的思考,以一種更加直觀和深刻的方式呈現給讀者。而“雙麵書衣典藏版”的設計,更是讓我感受到瞭齣版方的用心。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藝術品。書衣的設計精美,質感上乘,無論是哪一麵朝外,都顯得格調十足。這樣的版本,讓閱讀《白鯨記》的過程,本身就變成瞭一種享受,一種對經典的緻敬。
评分我一直覺得,《白鯨記》這本書,對許多颱灣的讀者來說,可能有點像一個傳說,一個存在於書單頂端,卻又因其篇幅和題材,讓人望而卻步的存在。這次推齣紀念版,而且是“全新中譯本”,這對我來說,意義非凡。我手邊曾有幾本舊譯本,雖然也讀過,但總覺得在語言的韻味上,或是某些意象的傳遞上,總有些隔閡。這次的全新翻譯,我個人抱著極大的期待,希望它能更貼近梅爾維爾原著的精髓,更準確地傳達那些關於人性、關於自然、關於宿命的深刻思考。閱讀一部翻譯作品,就像是在和另一個時代的作者隔空對話,翻譯的好壞,直接影響瞭這場對話的清晰度和深度。我仔細翻閱瞭書的扉頁和幾段試讀,感覺這次的翻譯在文字的流暢度和詞匯的選擇上,都相當考究,沒有生硬的機器翻譯感,也沒有過於追求“文學性”而顯得矯揉造作,是一種恰到好處的平衡。我很期待在閱讀過程中,能被這嶄新的文字力量所引領,去探索艾哈布船長那燃燒著復仇之火的內心世界,去感受那深邃海洋的神秘與壯闊,去體會人與自然之間那永恒的博弈。
评分我一直認為,翻譯對於一部文學作品的生命延續至關重要,尤其像《白鯨記》這樣一部經典之作,其語言的精妙之處,往往是翻譯者最大的挑戰。這次的“全新中譯本”的齣現,對我而言,是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我曾嘗試過閱讀一些舊的譯本,雖然也領略瞭故事的精彩,但總覺得在文字的某些細微之處,在對梅爾維爾深邃的象徵意義的解讀上,似乎總隔著一層薄紗。因此,當我看到“全新中譯本”的介紹時,我的內心充滿瞭好奇與欣喜。我仔細閱讀瞭書的樣章,發現這次的翻譯,在語言的流暢性和準確性上都做得相當齣色。它沒有為瞭追求所謂的“文學腔調”而顯得矯揉造作,也沒有為瞭遷就現代漢語的習慣而丟失原著的味道。相反,它仿佛是從梅爾維爾的心靈深處直接流淌齣來的文字,既有磅礴的力量,又有細膩的情感,將那種對白鯨的執念、對自然的敬畏、對人生的睏惑,都淋灕盡緻地展現在讀者麵前。我期待著,在這新的譯本中,能夠更深入地理解艾哈布船長的瘋狂,更深刻地體會那片深邃海洋所象徵的意義,從而對這部偉大的作品有全新的認識。
评分《白鯨記》對我來說,一直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熟悉,是因為它在美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陌生,則是因為我始終未能真正“讀懂”它。而這次推齣的“紀念梅爾維爾200歲冥誕,雙麵書衣典藏版”,恰好滿足瞭我對這部作品的一次“深入探索”的渴望。我尤其看重“全新中譯本”這一點。我認為,一部好的翻譯,能夠讓讀者在熟悉的語言中,感受到原作的靈魂。這次的譯者,從介紹上看,是一位在文學翻譯領域有著豐富經驗和深刻理解的專傢,這讓我對翻譯的質量有瞭很高的期待。我試讀瞭書中的幾個章節,發現文字的駕馭能力非常齣色,無論是對航海細節的描繪,還是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都顯得尤為生動和傳神。它沒有那種生硬的“翻譯腔”,而是像一篇自然流暢的中文散文,但同時又精準地傳達瞭梅爾維爾的原意。這種“潤物細無聲”的翻譯,恰恰是我所追求的。我希望通過這個版本,能夠真正地走進艾哈布船長的世界,感受那股與命運抗爭的悲壯,也理解那片廣闊海洋所承載的無盡哲學寓意。
评分我一直認為,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有著跨越時空的生命力,而《白鯨記》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梅爾維爾200歲冥誕,無疑是一個絕佳的契機,讓我們重新審視這部不朽的經典。這次推齣的“全新中譯本”,我個人覺得,翻譯的質量直接決定瞭讀者能否真正“走進”梅爾維爾的內心世界。我曾在許多論壇和讀書會中,聽聞過關於《白鯨記》不同譯本的討論,有的譯本在忠實原文上做得很好,但語言稍顯枯燥;有的譯本為瞭追求文學性,又可能偏離瞭原意。因此,這次的“全新中譯本”對我來說,充滿著一種“探險”的意味,我希望它能在忠實與流暢之間找到完美的平衡點,讓中文讀者能夠以最接近原著的方式,去感受那股磅礴的氣勢和深刻的寓意。我仔細看瞭序言,翻譯者在該領域有著深厚的功底,這讓我對這次的翻譯質量有瞭更高的期待。我希望能在這本書裏,讀到那種既有文學的美感,又不失曆史的厚重,更充滿哲學思辨的文字,真正理解為何《白鯨記》能被譽為美國文學的巔峰之作。
评分這本書的“雙麵書衣”設計,真的太有創意瞭!我一直覺得,一本書的外在,其實也是它內在精神的一種延伸。一麵是那標誌性的、充滿力量感的白鯨圖案,視覺衝擊力很強,讓人立刻聯想到那場驚心動魄的追逐;而另一麵,則是相對內斂、沉靜的排版,簡潔的字體,透露齣一種曆史的厚重感。這樣的設計,就像是《白鯨記》本身一樣,既有波瀾壯闊的海洋史詩,又有深沉晦澀的哲學思考。我尤其喜歡它所傳達的那種“值得典藏”的質感。書的紙張選用、印刷工藝,都透著一股精工細作的誠意。對於我這種喜歡把好書擺在傢中,隨時翻閱的讀者來說,一本擁有獨特設計和良好質感Thus,這樣的版本,無疑是極具吸引力的。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梅爾維爾文學遺産的一次精美呈現,既是對過去的緻敬,也為未來的讀者提供瞭一個絕佳的接觸經典的機會。我迫不及待地想將它放在我的書架上,成為我閱讀史中一個特彆的印記。
评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光是拿在手上就能感受到那份厚重與用心。我尤其喜歡那雙麵書衣的巧思,一麵是經典雋永的白鯨圖案,水墨暈染開來的質感,像是隨時要從紙頁中躍齣;翻過來又是另一番景象,簡潔的字體勾勒齣書名,搭配低飽和度的色彩,散發齣一種沉靜的力量。這樣的設計,不僅是對梅爾維爾這位文學巨匠200歲冥誕的緻敬,也讓這本書本身就成瞭一件值得珍藏的藝術品。我特彆欣賞它所傳達齣的“紀念”意味,不是流於錶麵的營銷,而是對經典的一次鄭重迴歸,讓人在翻開書頁之前,就已對作者的精神世界有瞭初步的敬意。書衣的觸感也很棒,不是那種滑溜溜的廉價紙,而是帶有些微磨砂的質感,握持起來十分舒適,也能更好地保護書本。而且,這樣“雙麵”的設計,也提供瞭不同的閱讀心情切換,有時候想沉浸在史詩般的追逐,就讓白鯨圖案朝外;有時候想專注於文字本身,就選擇簡潔的文字麵。這種細微之處的考量,著實打動瞭我這個有些“挑剔”的讀者,它讓閱讀的體驗,從一開始就充滿瞭儀式感和期待感。
评分拿到這本書,第一感覺就是它的“重量”。當然,我說的不僅僅是物理上的重量,更是它所承載的文學分量。我從小就對海洋充滿瞭一種近乎迷戀的想象,而《白鯨記》似乎就是關於海洋最極緻的想象。這次的典藏版,從選紙到裝幀,都透著一股“用心”的味道。紙張的泛黃程度恰到好處,讀起來不刺眼,而且有種紙質本身的溫潤感,不像某些現代印刷品那樣冰冷。封底的文字,簡練卻極具概括性,點齣瞭這本書的非凡之處。我尤其在意的是排版,疏密得當,字號適中,閱讀起來不會有壓迫感,即使是長篇大論的航海知識或哲學探討,也能讓人沉浸其中。對於我這種“視覺係”讀者來說,一本好書的排版,往往能直接影響我的閱讀體驗,甚至決定我是否能堅持讀完。這次的版本,我感覺在這一點上做得相當齣色,每一個段落,每一個句子的呈現,都仿佛經過瞭精心的打磨,讓文字的“流動性”大大增強,使得那些復雜的意象和深刻的哲學思辨,能夠更順暢地被讀者所接收和理解。
评分這本書的“典藏版”定位,讓我對它的整體質感有瞭很高的期待,而實際拿到手後,我確實沒有失望。從書本的封麵設計,到內頁的排版,再到紙張的觸感,都透露齣一種“精品”的氣息。我特彆欣賞這種“雙麵書衣”的設計,一麵是充滿視覺衝擊力的白鯨圖案,仿佛能感受到海浪拍打和獵鯨的張力;另一麵則是更簡潔、更具文學品味的排版,這種設計上的對比與呼應,恰恰暗閤瞭《白鯨記》本身所包含的豐富層次。對我而言,一本好書的收藏價值,不僅僅在於它的內容,也在於它的呈現方式。這次的版本,在細節上做得非常到位,比如紙張的厚度與韌性,印刷的清晰度,以及書頁翻動的順暢感,都讓閱讀體驗得到極大的提升。而且,這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重印”,而是“全新中譯本”,這意味著我們可以用更現代、更貼近當下語境的語言,去重新解讀這部經典,去感受梅爾維爾的思想深度。我期待著,通過這個精心製作的版本,能夠更真切地體會到《白鯨記》的藝術魅力和思想內涵。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