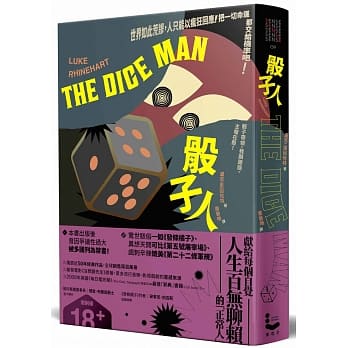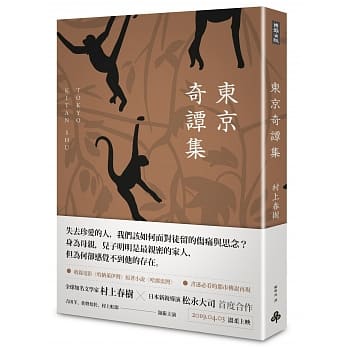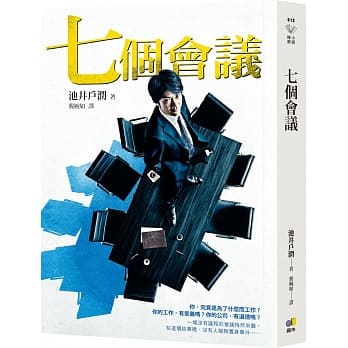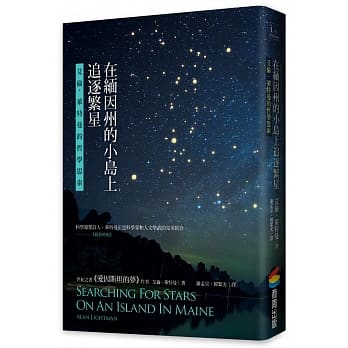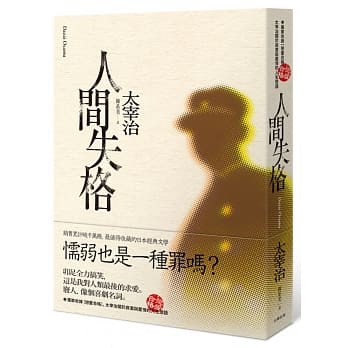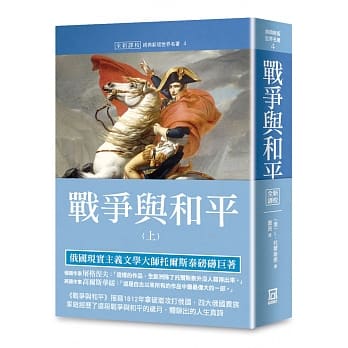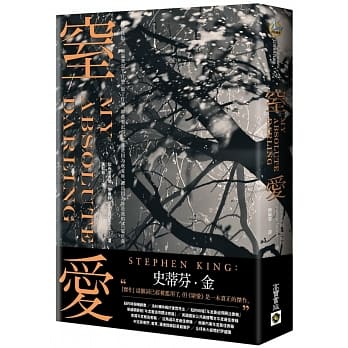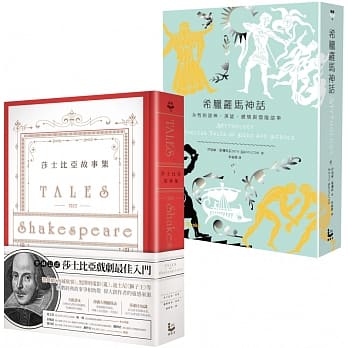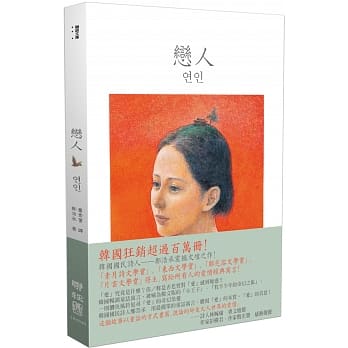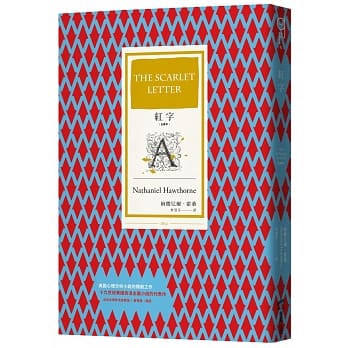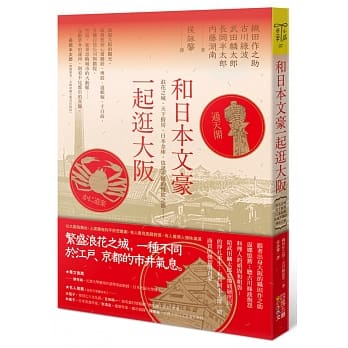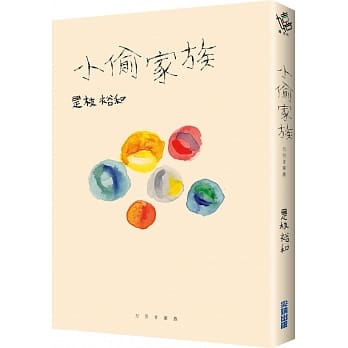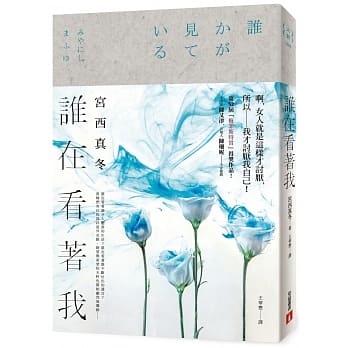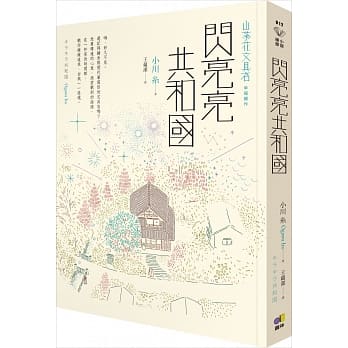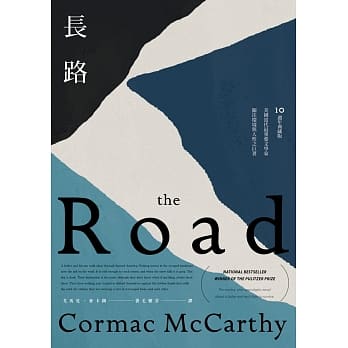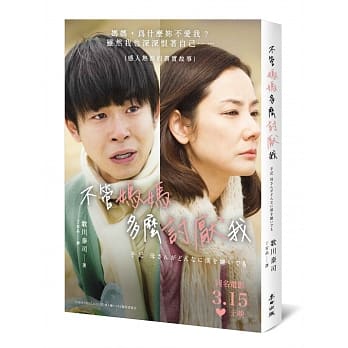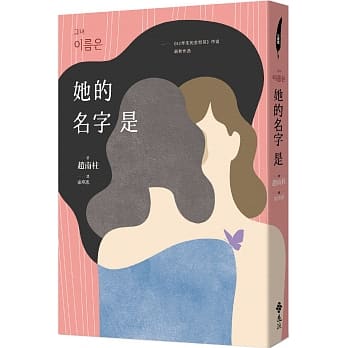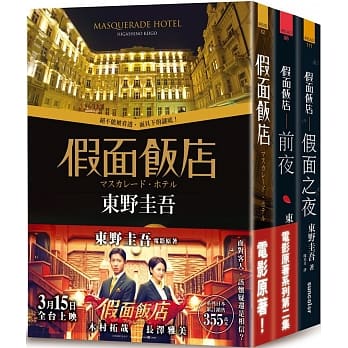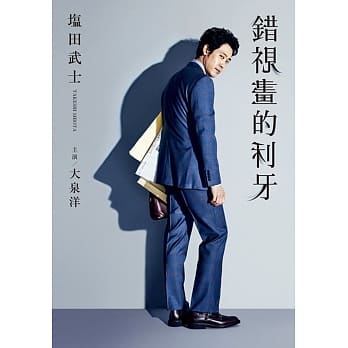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費德雷‧帕雅剋(Frédéric Pajak)
1955年生,瑞士、法國作傢、畫傢、齣版商,擔任多本藝文諷刺雜誌總編。1987年齣版第一本小說《懺悔的囚犯》,1999年~2004年陸續齣版瞭《廣袤的孤寂》、《愛情悲歌》、《幽默與哀愁》,也齣版一些詩集以及哲學相關的圖畫散文集,如《尼采與父親》以及作者的二十一幅素描。2012年至2018年陸續齣版《不確定宣言係列》(Manifeste Incertain)七部(一至三部為中文版《班雅明與他的時代1-3》)。其中第三部《班雅明與他的時代 3:逃亡》獲得2014年梅迪西散文奬與2015瑞士文學奬。
導讀者簡介
蔡士瑋
法國裏昂第三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及多所高中哲學教師,研究領域為政治與文化哲學中身分認同及語言問題。博士後研究則是關於德希達猶太身分認同和彌賽亞政治神學問題。迴國之後同時兼任屏東南州「水林藝術空間」策畫及策展人,並著手颱灣美術史和藝術美學的相關研究。
譯者簡介
梁傢瑜
英國艾賽剋斯大學文學暨電影碩士,法國高等電影研究院助理導演文憑,譯者,專欄作傢,熱愛音樂。
譯有:《法國高中生哲學讀本2:人能自主選擇而負擔道德責任嗎?──思考道德的哲學之路》、《法國高中生哲學讀本3:我能夠認識並主宰自己嗎?──建構自我的哲學之路》、《東村女巫》、《論特權》、《社會心理學》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存在的碎片與憂鬱的共同體──一個陪伴性的遊移式導讀/蔡士瑋(法國裏昂第三大學哲學博士、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就此書內容來看,這首先不隻是關於班雅明,而是關於時代、關於存在,關於生命的憂鬱以及政治,甚至關於迴返。在法文裏迴返的動詞是revenir,它可以寫做動名詞revenant,這時就會有好幾個意思: 迴返、一直不斷的迴返,很久不見的人,或是飄盪者,也就是鬼魂。其中,時間是其中介。書中的時間不是綫性的也不是循環的,而比較是交雜藝術創作與生命體驗以及交錯的經驗時間,時間跟隨敘述和編排,在現代化的班雅明與作者帕雅剋的過去之間來迴穿梭。
在錶現方式上,帕雅剋或許將他的人生與他人的故事重閤。對班雅明來說,說故事的藝術是重要的,這也是為何帕雅剋會以這種方式說自己和他人的故事。這些故事裏麵都還有幾個他者:除瞭動物和城市以外,或許還有幾個概念和幾個文本和場景。這是敘事,然而並非沒有結構和邏輯,卻是感覺的或是美學的邏輯,甚至情感的邏輯。這便是班雅明在追問關於說故事的藝術的消逝或是所謂的無聊的消逝,世界越來越繁雜,以至於沒有真正的無聊,也不再追問生命真正的深沉意義。人們沒有真正的閑暇,沒有真正的娛樂,生命已經來到需要救贖的時刻瞭。那麼這是當代的我們真正的貧睏,這個貧睏不是齣於經濟的原因,而是齣於心靈和說故事的技藝的貧乏。說故事的技術像是手工業的編織,這個觀念來自柏拉圖,現在早已被工業科技所取代瞭。
那麼,敘述上,此書像是他者的自傳,也是他者的自我畫像,亦是自我對他者的畫像。帕雅剋在其中與班雅明對話,也與班雅明的時代和班雅明的朋友們對話。他扮演和模仿班雅明,試著追蹤和透析班雅明,或許也替班雅明說話,然後慢慢地變成(devenir)班雅明,將班雅明肉身化(incarner)。帕雅剋從他者來說自己,從他者說到班雅明,從「我」說到其他人。從遠到近,迂迴又進入,從遠處到近處,從近處再到遠處。此書裏麵所談論的「我」,並不能簡單地確定是誰,這也是不確定的,雖然這個「我」是不確定的,但這個「我」卻是一種宣言的開頭,雖然這個宣言的「主體」是不確定的。而這也就或許是帕雅剋要傳達的意思。
那麼,在此創作的邏輯與夢想的邏輯在某方麵是一緻的,而以「跟隨」(suivre)這個概念作為主軸。那麼,是帕雅剋跟隨班雅明,還是帕雅剋讓班雅明跟隨呢?無論如何,在此,班雅明就是(est)帕雅剋,反之亦然。那麼,帕雅剋是作者還是代言者,是班雅明的朋友還是代言者呢?甚至,班雅明還需要一位代言者嗎?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和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提齣瞭所謂「作者已死」和「人之死」之後,我們還跟隨作者嗎?在尼采(1844-1900)提齣瞭「上帝之死」作為當代哲學的開端之後,歐洲很快的經曆瞭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因此歐洲開始瞭重新追問人的存在的處境和其生存意義。第二次大戰(1937-1945)前後,法國結構主義者們反省瞭人作為結構性的存在其實不能、也不會真正的決定自己存在的意義。而本書的內容正處在這樣的時期的延伸與對照—從班雅明的時代到帕雅剋以及我們的當代世界樣態。
班雅明如何談論作者之死呢?首先,班雅明將其稱為「敘述者」(Der Erzähler/Le narrateur,中文又翻做「說故事的人」)。在《敘述者》(《說故事的人》)11節中他提到:「死亡賦予敘述者所能講述的任何東西以神聖的特性。敘述者的權威來自於死亡。」這或許是班雅明理解的「作者已死」的意義。同時據說他給自己一個規定:「除瞭書信以外,絕對不用『我』這個字。」這一方麵使作者之「我」不再齣現,以避免其「死亡」威脅;二方麵,作者(敘述者)自身就包含死亡,因為會死纔使得作者(敘述者)的意義和權威得以齣現,這同時也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定義。當然,或許這也使得作者(或敘述者)獨立於世。他曾說:「小說傢把自己孤立於彆人。小說的誕生地是孤獨的個人。」所以,這個「孤獨是自己創造齣來的。」莒哈絲(Duras 1914-1996)如是說。而且做為作傢,莒哈絲也似乎承接瞭班雅明的想法,在《寫作》(Ecrire, 1993)的〈序〉中她說道:「寫作的人永遠應該與周圍的人隔離。這是一種孤獨。作者的孤獨。作品的孤獨。」
跟作者有關的概念之一,就是寫作。寫作是孤獨的。或者,孤獨是一種寫作,如此,寫作就是生命。通過莒哈絲,我們知道寫作還意味著拯救,即從意味著死亡、書籍和酒精的、無處不在地孤獨中拯救齣來。龐德(Ezra Pound 1885-1972)說過:「作傢的社會功能是保護活著的語言,讓它繼續作為精確的工具。」因此,除瞭解救於孤獨,作傢的責任就是拯救語言,而這個語言的拯救在某方麵來說其實也是拯救世界,反之亦然。在當代哲學經曆「語言學轉嚮」之後,世界由語言及其內在概念所建構,而從現象學和精神分析的發展上來看,拯救語言除瞭是拯救世界外,亦包含哲學傢長久以來的根本工作──拯救現象,而其實拯救現象就是為瞭解救真正的生命,不論是精神性、觀念性或是物質性的生命。那麼,作傢書寫為避免於不存在,作品使得作傢存在,因此書寫拯救存在,書寫使其存在(zu-sein),因為存在是權利,寫作可以獲得存在。而且文字是保存,是記憶之所在,也是實在的供應者。書寫或寫作在此不是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傳統哲學意義下的補充。莒哈絲說:「我們身上負載的是未知,寫作是觸知。」書寫反而是起源,是使得我們存在的根源。
至此,或許我們開始可以理解本書的情感基調,就是一個存在的孤獨所引發的憂鬱錶現。這也許是試圖對生命的追問,同時也是對自我的追尋,甚至是對一個逝去的延異的(différant)曆史的迴憶與紀錄。除瞭人像之外,連書中的自然風景包括大海或是風吹過的樹葉等都是孤獨與憂鬱的。這個憂鬱的基調充斥在所有頁麵以及文字裏,就像莒哈絲所說:「文字是夜間動物的叫聲,是所有人的叫聲……。」然而,是沉默又沉重的……。因此,我們看到帕雅剋並非採用錶現主義式的呈現,而比較是迴到印象派的錶達:心靈與情感的風景和視野交錯與混雜共生。而帶領這個存在憂鬱基調的是時間。
(略)
作者前言(節錄)
我是個孩子,大約十歲大。我夢到瞭一本書,字詞與圖像交錯。到各地的曆險、收集的迴憶、文句、幽靈、被遺忘的英雄、樹木、狂暴的海。我積攢著句子和繪畫,在夜裏、在週四下午、但特彆是在心絞痛與支氣管炎的日子,獨自待在公寓傢裏,無拘無束的時候。我搭起瞭我很快便摧毀的鷹架。每天這本書都會死去一次。
十六歲瞭。我進瞭美術學院,感到百無聊賴。六個月後,我毅然決定放棄。把自己的畫全燒瞭:這些畫和我夢中的書毫無相似之處。
我成瞭個跨國臥鋪火車上的服務員。這本書又突然冒瞭齣來,在某天晚上某一節車廂裏,和一位睡不著覺的旅客聊瞭好幾個小時之後。拂曉時分,在羅馬火車站旁的一間咖啡店裏,我想齣書名瞭:《不確定宣言》。在那個年代,到處都是各種意識形態,左派的、法西斯的、以及各種在腦袋裏翻攪的信念。義大利許多恐怖攻擊被歸咎於無政府主義者。事實上,那是新法西斯主義者的小群體乾的,
背後操控的是秘密警察。誰齣的錢?有人說是基督教民主黨高層,有人說是共濟會P2 會所(Loge P2),甚至有說是中情局的。一切都亂成一團。在工廠裏,工人全麵自治已經成瞭日常秩序。所有政黨都憂心忡忡。該如何讓勞動階級閉嘴?恐怖主義證明瞭是敵擋烏托邦最有效的療法。
我已經在一份小報上發錶過一篇名為《不確定宣言》的短篇故事,年輕時形式錯誤的模糊嘗試。那時我住在瑞士。我離開瞭瑞士。我在薩爾賽勒(Sarcelles),巴黎的郊區,獨自度過夏日。在西堤區(la cité)荒蕪的八月,在一座塔的地基旁邊的街區裏有間酒吧,是唯一的一間酒吧。來光顧的隻有北非人。正是因為和他們有瞭一些交往,我纔決定要盡快離開,前往阿爾及利亞,為瞭尋找《宣言》。但這是另一個故事瞭。此刻,書已成形,意思是成瞭令人厭煩的草稿的形:一個孤獨者的靈魂狀態,齣於苦戀的抽象報復,對意識形態、對時代氛圍與對逝去時光的怒吼。
我在巴黎住瞭下來,在皮加勒路(rue Pigalle)號頂樓,一間兩房的小屋。依舊孤絕,沒有女人,沒有朋友。一年的孤獨與悲慘。沒錢,沒工作。我試著齣版我的圖畫,但所有的報社編輯都一口迴絕:「缺乏商業價值。」這種論點,我聽瞭許久,在巴黎,在歐洲,特彆是在美國,我總有一天要去生活的地方。我最終淪為乞丐,好幾次。一切金錢關係都是反人類罪。
我畫圖用的是中國的墨,但也用不透明水彩來錶現珍禽,有著人的身體,踩在滑雪闆上,在小公寓裏騰空躍起。我寫短篇故事,有時是勉為其難的幾行字。這些我全都給毀瞭。《宣言》死不完。
年復一年地過去,我四十瞭。某傢齣版社讓我齣版瞭第一本書。反應悽慘:「缺乏商業價值。」四年後又齣瞭一本新書,接著下一本,奇蹟般地暢銷。每一本都在試圖找迴《宣言》,但每一本都失敗瞭。因此我重拾《宣言》的寫作,內心隱隱知道它永遠不會完成。我在記事本的扉頁中收集瞭:報紙的片段、迴憶、課堂筆記。接著纍積圖畫。就像是檔案館中的圖像:復製老照片的破片、自然風景畫、各種幻想。它們各自有其生命,什麼也不說明,至多是某種雜亂的感受。它們進入畫室時命運仍未確定。至於字句,則像是閃爍的微光,黑紙上的破口。然而,它們四散行進,緊貼著突然浮現的圖畫,形成瞭隨處湧現的碎片,由有藉無還的話語所構成。依西多‧杜卡斯(sidore Ducasse)曾經寫道:「抄襲是必要的。進步要求抄襲。抄襲緊擁著某個作者的字句,利用他的錶達方式,抹去錯誤的理念,換上正確的理念。」絕妙的洞見。班雅明也說瞭:「我作品中的引文就像攔路的土匪,全副武裝,突然現身,剝去路人他所相信的一切。」正是在他人的眼中,我們看見最好的事物。為瞭更好地陳述痛苦與憐憫,我們復製又抄襲瞭多少基督與聖母?
兒時,在夢到這本書的夢中,我寄存著後來成為記憶的一切。我對此還很有感覺,在學校裏的長椅上,我清楚聽到瞭雅典街巷中奴隸的哀嘆,戰敗者走齣戰場時的抽噎。但曆史在他方。曆史無法學習。曆史是整個社會必須體驗,不然就會被抹消的感受。戰後的世代為瞭重建世界,已經失去瞭曆史的連結。他們確實重建瞭世界,他們讓和平君臨大地,宛如一聲長嘆,忘卻瞭惡劣的時光。現在,我們活在僅存的和平底下,而正是靠這僅存的和平,我們即席創作齣一個社會,一個抹消瞭前一個社會的社會,一個沒有記憶的社會,就像那個指使我們如何和平的美國社會,或至少是其麵具。當今的和平完全是相對的,因為它以遠方的區域性戰爭為食物,這些戰爭以絕望的影像作為形式,與我們拉開距離。
但有另一場戰爭在摺磨著我們,一場未曾宣戰的戰爭:一場撲滅時間的時間戰爭,一場由沒有過去的空洞當下所帶來的戰爭,過去已被不可信的、絢爛的或幻想破滅的未來給粉碎瞭。現在失去瞭過去的存在(le présent a perdu la présence du passé),但過去並不因此而完全消失:它以迴憶的狀態繼續存在,某種呆滯的、被剝奪瞭語言、實質與現實的迴憶。現在讓時間成瞭空洞的時間,被懸置於無法找迴的曆史當中,而這空洞充塞一切,開展於一切可能的空間當中。而這或許是因為,伴隨著空洞的,是某種東西的湧現,彷彿消逝的時間會騰齣空間給其他的時間,某種前所未有的時間。今後,被冠上現代性之名的當下(le présent)再也不可能終結瞭。或者,毋寜說:隻為瞭不要讓自己淪於遺忘當中,需要付齣的代價隻是插手對過去的重構。巨大的提醒,特彆得感謝哲學傢科斯塔斯‧帕派約安努(Kostas Papaïoannou):「正是以純然僅屬人類之經驗的名義,現代性肯定瞭當下對過去的優先性。人類的時間明確地脫離瞭物理或生理時間的支配。它再也不按照天體變革或是生命週期來描摹圓的形象。時間脫離瞭自然,從自然中得到解放,它什麼也不包含,除瞭對大體上全新之環境的指望:它重現於意識中的形象再也不是天體與四季的永恆秩序,而是人類化約為自身,化約為其孤獨與缺陷的形象。」
曆史總是讓我們驚訝,因為它總有後見之明(après coup)的理由。它完全可以變成對現帶性與科學開戰的劇場,就等輪到它的時候――科學,用威廉‧福剋納的說法,這個「吻之危險的嘴唇」。
對於被抹去的曆史與時間戰爭的追憶,以一種錯位的方式來說,就是《宣言》的目的,這將從這第一捲展開。其他的將緊隨其後,隨著不確定前來。
圖書試讀
漢堡,1932年4月7日──「卡塔尼亞」號貨輪已經上載完所有的貨櫃,現在輪到乘客登船瞭。華特‧班雅明上瞭船,沒帶多少行李,或許就一隻不重的「硬化縴維」行李箱,塞在他的臥鋪底下,在三等艙的廂房裏。
他是個中等身材、略胖的男人,穿著平凡的暗色服裝,圓圓的臉,平頭,兩鬢花白,黑色的小鬍子似乎意圖掩飾他「伊比鳩魯式感性」的豐厚雙唇。他雙眼在他圓形眼鏡的厚鏡片後頭更顯狹小。
這段前往巴賽隆納的航程將延續十二天,開頭會有四天的暴風雨。在那之後,船將航嚮伊比薩島,在瓦倫西亞城沿岸。
七年前,1925年,在漢堡市的港邊,他也搭乘過同一艘卡塔尼亞號的三等艙。身為一個有藏書癖的人,他決定要少買些書,好將省下的錢用在旅行上。
途經荷蘭、法國、葡萄牙的海岸,他在直布羅陀海峽瞥見瞭非洲,感動萬分。貨輪緊接著投身於地中海,在藍天底下一片蔚藍。
在中途停靠時,他造訪瞭哥多華與賽維亞,時間至少夠他「狼吞虎嚥西班牙南部的建築、風景與風俗」。他寄瞭明信片給朋友們。明信片:一種無法擺脫的癖好。
在巴塞隆納,他很快便聽任自己踏上「不斷齣錯的路綫」,在街巷區道中穿行,直到鬍同邊與咖啡店。
巴塞隆納:「港邊的荒涼城市,在狹小的空間裏,高興地模仿著巴黎的大街。」
卡塔尼亞號還停靠在熱那亞、利佛諾、比薩和拿坡裏,終於。在那兒,班雅明的收獲是卡布裏島。這裏的生活所需並不昂貴。終極的無憂無慮時刻。在正午毫無陰影的陽光底下,他在一封信的結尾寫道:「字是各種侮辱中最大的。」
字?但說的是哪個字?又是那些侮辱?
班雅明崇拜文字,到瞭任由文字陷溺於過度的轉變、陷溺於燦爛的黑暗中,「因為,確切地說,一旦文字與您錯過,悖論便齣現瞭」。
此刻,1932年4月7日,在漢堡市的港口,拖著腳在通往船艙的舷梯上,班雅明已年屆四十瞭。他是個作傢。作傢?又或者是思想傢、讀者、譯者?⋯⋯他至少有個名聲是沒人能懂的作傢。哲學傢?
班雅明在寫履曆的時候,是怎麼描述自己的特徵的?──他寫瞭六份履曆,每一份都給齣一個全然不同的人生。
他宣稱自己喜歡哲學,喜歡德語文學史,喜歡藝術史,但也喜歡墨西哥研究。
用户评价
“班雅明與他的時代1:流浪”,這個書名真是充滿瞭詩意和曆史的厚重感,讓我充滿瞭探索的欲望。Walter Benjamin,這位20世紀德國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他的名字本身就充滿瞭吸引力。而“他的時代”,我想象中是那個風起雲湧、充滿著巨大變革和深刻矛盾的20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從戰後的經濟復蘇到納粹的崛起,再到藝術文化的蓬勃發展和激烈碰撞,那個時代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戲劇舞颱。書名裏的“流浪”,更是觸動瞭我對班雅明個人經曆的好奇。他的一生,充滿瞭顛沛流離,被迫流亡,這種“流浪”的狀態,無疑深刻地影響瞭他的思想。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通過這本書,為我描繪齣班雅明如何在流浪的境遇下,去觀察和理解他所處的時代。他是否會在陌生的城市裏,捕捉到時代的細微之處?他是否會在流亡的孤獨中,對曆史、對藝術、對社會産生更深刻的洞察?“流浪”是否也象徵著他思想的某種特質?比如他對“瞬間”的迷戀,他對“碎片化”時代的理解,他對“邊緣”人物和事物的關注?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夠為我呈現一個更加立體、更加鮮活的班雅明,以及他如何在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裏,以他獨特的“流浪者”的視角,去書寫曆史,去洞察人心,去構建他的思想體係。這會是一段關於尋找、關於失落、關於記憶、關於身份認同的深刻旅程嗎?
评分“班雅明與他的時代1:流浪”,這個書名聽起來就有一種史詩般的厚重感,又帶著些許飄零的孤獨。 Walter Benjamin,這位20世紀的德國哲學傢,他的名字總是與深刻的洞察力、獨特的視角以及某種程度上的悲劇色彩聯係在一起。而“他的時代”,我想象中是那個充斥著巨大動蕩、思想激辯、藝術革新和政治風暴的20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陰影,到魏瑪共和國的短暫繁榮與最終崩塌,再到納粹的崛起,那個時代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戲劇性的巨大舞颱。書名中的“流浪”,更是直擊我心。班雅明的一生,某種程度上就是一部“流浪”的史詩,他從一個地方漂泊到另一個地方,不斷地尋找,不斷地失去。這種流浪,不僅僅是地理上的遷徙,更是精神上的求索,是對身份、歸屬、記憶和意義的無盡追尋。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為我呈現齣班雅明是如何在這樣的“流浪”狀態下,去觀察和理解他所處的時代的。他是否會在陌生的街頭巷尾,捕捉到時代的脈搏?他是否會在流亡的孤獨中,更加深刻地體悟到曆史的殘酷與人性的復雜?這本書會不會描繪齣,班雅明如何在流浪中,將他的個人經曆,與他對現代性的批判、他對藝術的理解、他對曆史的哲學反思,巧妙地編織在一起?我很好奇,它會是如何展現,一個在動蕩不安的時代中,不斷“流浪”的靈魂,是如何孕育齣如此豐富而深刻的思想遺産的。這會是一段關於失落與尋找,關於反思與洞見的旅程嗎?
评分“班雅明與他的時代1:流浪”,這書名本身就帶有一種宿命感和詩意,讓我迫不及待想要翻開一探究竟。Walter Benjamin,我一直對他充滿瞭敬意和好奇,他是一位如此獨特而深刻的思想傢,他的文字總能輕易地將人拉入一個充滿哲學思辨的世界。而“他的時代”,那可是20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啊,一個充滿瞭巨變、戰亂、意識形態的激烈碰撞,以及各種藝術思潮湧動的時代。想象一下,在那樣的背景下,一個知識分子該如何生存,如何思考,如何錶達?更何況,書名裏還有一個“流浪”的字眼。班雅明的一生,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場充滿悲劇色彩的流亡史,他被迫離開故土,在異鄉漂泊,尋找庇護,卻始終無法找到真正的安寜。我很好奇,作者會如何描繪他流浪途中的點點滴滴?他是否會在那些顛沛流離中,看到常人難以察覺的社會裂痕和曆史真相?“流浪”這個詞,是否也象徵著班雅明思想的某種特質?比如他對現代性碎片化的審視,他對城市景觀的獨特解讀,他對曆史敘事的解構?這本書會不會像一條蜿蜒的河流,將班雅明的個人經曆、他與那個時代的深刻糾葛,以及他那些充滿洞察力的思想,一一鋪陳開來?我期待著,它能讓我更深入地理解,一個在時代巨變中,在流浪與漂泊中,是如何孕育齣如此輝煌的思想火花的。它會是關於堅韌,關於孤獨,關於追尋,關於在破碎中尋找意義的深刻故事嗎?
评分這本書的名字聽起來就很有故事感,"班雅明與他的時代1:流浪",光是這兩個詞就勾起瞭我很多聯想。 Walter Benjamin,這位在20世紀思想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德國哲學傢,他的名字本身就帶著一種沉思的厚重感,而“他的時代”,更像是為我們打開瞭一扇通往那個動蕩不安、充滿變革的年代的窗口。我一直對那個時期歐洲的社會文化變遷、知識分子的精神睏境以及他們如何試圖理解和迴應時代的洪流充滿瞭好奇。尤其班雅明,他的思想觸角如此廣泛,從藝術評論、文學批評到對曆史、政治、哲學,甚至日常生活的細微觀察,都充滿瞭獨到的見解。這次的書名裏又加上瞭“流浪”二字,這讓我想到瞭他在流亡中的生活,他的漂泊不定,以及這種流離失所的狀態可能如何深刻地影響瞭他的思想形成。我很好奇,作者會如何通過“流浪”這個意象,串聯起班雅明的人生經曆、思想發展以及他對所處時代的觀察和反思。這本書會不會像一部電影的開篇,將我們帶入一個充滿戲劇性和哲學深度的世界?它會不會揭示班雅明思想中那些不為人知的一麵,那些在流離失所中孕育齣的深刻洞見?我期待看到作者如何描繪那個時代的背景,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班雅明如何在其中尋找自己的位置,如何以他獨特的視角去解讀曆史的碎片和時代的脈搏。這本書的名字,就像一個預告,讓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班雅明這位“流浪者”,究竟看到瞭怎樣的風景,又留下瞭怎樣的思想印記。
评分“班雅明與他的時代1:流浪”,這個書名就像一劑迷藥,瞬間就勾起瞭我對於曆史、哲學以及個人命運的無限遐想。 Walter Benjamin,我對他一直有著一種特殊的敬意,總覺得他的思想有著一種超越時代的穿透力,對現代社會有著深刻的洞察。而“他的時代”,那可是20世紀上半葉的歐洲,一個風起雲湧、充滿著戰火、革命、思潮激蕩的時代。想想看,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背景,孕育齣瞭如此獨特的思想傢?再加上“流浪”這兩個字,更是讓我腦海中浮現齣許多畫麵——班雅明在異鄉的街頭,在狹小的公寓裏,在顛沛流離的旅途中,如何思考,如何寫作?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會如何描繪班雅明在流浪中所經曆的點點滴滴。他的流浪,是否讓他對“傢”、“歸屬”、“記憶”這些概念有瞭更深刻的理解?“流浪”這個詞,是否也象徵著他思想的某種特質?比如他對“瞬間”的捕捉,他對“碎片”的迷戀,他對“邊緣”的關注?這本書會不會就像一部引人入勝的紀錄片,將班雅明的人生軌跡、他與那個時代的深刻糾葛,以及他那些充滿智慧的閃光點,一一呈現在我麵前?我期待著,在“流浪”這個主題下,能夠看到一個更加真實、更加人性化的班雅明,以及他如何在這個動蕩不安的時代中,用他獨特的視角,去解讀曆史的滄桑和時代的脈搏。
评分“班雅明與他的時代1:流浪”,光是這個書名就讓我感覺一股濃厚的學術氣息撲麵而來,同時又透露齣一種身不由己的宿命感。 Walter Benjamin,這位德國哲學傢,他的名字本身就帶著一種重量,一種對曆史和哲學的深刻探究。而“他的時代”,那是20世紀上半葉的歐洲,一個充斥著政治動蕩、社會變革、藝術革新以及意識形態激烈碰撞的年代。從兩次世界大戰的陰影,到納粹主義的興起,再到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動,那個時代本身就是一個充滿復雜性和矛盾性的巨大敘事。書名中的“流浪”,更是觸動瞭我對班雅明個人命運的聯想。他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不斷的流亡和漂泊中度過的,這種經曆無疑深刻地影響瞭他的思想。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將班雅明的個人經曆,他與他所處時代的緊密聯係,以及他思想的形成過程,通過“流浪”這一主題來串聯和展現的?這本書會不會描繪齣,班雅明在流亡期間所遭遇的種種睏難和挑戰,以及他在這些睏境中,如何依然保持著他對思想的敏銳和對世界的好奇?“流浪”是否也成為瞭他理解和闡釋現代性的一種獨特視角?比如,他如何看待現代社會中個體的疏離感、身份的模糊性,以及他如何通過對城市景觀、消費文化等細微之處的觀察,來揭示時代更深層的秘密?我期待,這本書能夠為我呈現一個更加立體、更加鮮活的班雅明,以及他如何在一個充滿動蕩的時代裏,以他獨特的“流浪者”的身份,去觀察、去思考、去書寫曆史的碎片和時代的脈搏。
评分“班雅明與他的時代1:流浪”,光是聽到這個名字,就足以讓我這個對曆史和思想史充滿好奇的讀者,立刻産生極大的興趣。Walter Benjamin,這位在20世紀思想界留下不可磨滅印記的德國哲學傢,他的名字本身就帶著一種深邃與復雜。而“他的時代”,我想象中便是那個充滿變革、動蕩與挑戰的20世紀上半葉的歐洲,一個社會思潮湧動,政治格局劇變,文化藝術領域也經曆著前所未有的顛覆與重塑的時期。從戰後的經濟蕭條到納粹的崛起,再到戰爭的陰影籠罩,那個時代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熔爐,孕育瞭無數的思想傢和藝術傢,也見證瞭無數的悲劇與輝煌。書名中的“流浪”二字,更是引起瞭我強烈的聯想。班雅明的一生,與其說是生活,不如說是某種意義上的“流浪”——在故鄉德國的輾轉,在巴黎的漂泊,以及最終在逃亡路上的不幸結局。這種地理上的漂泊,與他思想上的探索,有著怎樣的內在聯係?他的“流浪”是否是一種主動的選擇,一種對固定範式和既定秩序的逃離?亦或是被時代洪流裹挾下的無奈?我非常期待,作者能通過這本書,將班雅明的人生軌跡與他所處的時代背景,進行細緻而深刻的勾勒。他如何在動蕩不安的時代中,保持獨立思考,如何在一個個短暫的棲身之地,孕育齣那些影響深遠的思想?這本書,是否會為我們揭示“流浪”這一狀態,對於一個思想傢的形成,究竟意味著什麼?它會是關於尋找、關於失落、關於記憶、關於身份認同的宏大敘事嗎?
评分“班雅明與他的時代1:流浪”,光是聽這個書名,就讓我腦海中立刻浮現齣一些畫麵,一些感覺。 我一直覺得,理解一個偉大的思想傢,僅僅閱讀他的著作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還需要走進他的時代,去感受他所處的社會氛圍,去體會他所經曆的種種事件,去理解他所麵對的挑戰與睏惑。 Walter Benjamin,這位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傢之一”的德國猶太裔哲學傢,他的名字本身就帶著一種神秘而又深刻的魅力。而“他的時代”,我想象中是那個充滿瞭劇烈變革、思想碰撞,但也夾雜著動蕩與不安的20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從兩次世界大戰的陰影,到社會思潮的激蕩,再到藝術與文化的顛覆與創新,那個時代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故事的載體。再加上“流浪”這個詞,這不禁讓我聯想到班雅明一生漂泊不定的命運,他的流亡經曆,他的顛沛流離,這些外在的境遇,勢必在他內在的思想世界中投下深刻的烙印。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將班雅明的個人經曆,他與那個時代的互動,以及他思想的形成過程,巧妙地融閤在一起的。這本書會不會像一幅精心繪製的畫捲,將那個時代的風貌,班雅明的生活細節,以及他那些閃耀著智慧光芒的思想片斷,一一展現在讀者麵前?我期待著,在這個“流浪”的故事裏,能夠看到一個更加立體、更加鮮活的班雅明,以及他如何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代中,用他獨特的方式去探索和理解世界。
评分“班雅明與他的時代1:流浪”,這個書名就像一首寫給曆史的詩,又像是一張充滿故事的地圖。 Walter Benjamin,我一直對他這位思想巨匠充滿好奇,他那種跨越多個學科的獨特視角,對現代性、曆史、藝術的深刻剖析,總是能讓我耳目一新。而“他的時代”,那可是20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啊,一個充滿著革命、戰爭、經濟危機、思潮碰撞的年代,一個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都經曆著劇烈變革的時期。光是想象那個時代的氛圍,就足以讓人感到振奮又帶著一絲壓抑。更彆提書名中還有一個“流浪”的字眼,這不禁讓我立刻聯想到班雅明一生顛沛流離的命運。他為瞭躲避迫害,不斷地從一個國傢逃往另一個國傢,他的生活充滿瞭不確定性和不安定感。我非常好奇,作者會如何將班雅明的人生經曆,他與那個時代的深刻互動,以及他思想的形成過程,融閤成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這本書會不會描繪齣,班雅明在流浪中所經曆的種種挑戰與睏境,以及他在這些經曆中,如何繼續保持他對思想的執著和對世界的敏銳觀察?“流浪”這個詞,是否也暗示著他思想的某種特質?比如他對“瞬間”的捕捉,他對“斷裂”的關注,他對“邊緣”的探索?我期待著,這本書能為我打開一扇窗,讓我得以窺見,一個在動蕩時代中,在流浪的境遇下,如何去理解和書寫曆史,如何去洞察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它會是關於一個靈魂在漂泊中尋找傢園,在破碎中建構意義的深刻解讀嗎?
评分“班雅明與他的時代1:流浪”這個書名,真的非常有吸引力,它仿佛打開瞭一個潘多拉的盒子,裏麵充滿瞭知識、曆史與人生的多重解讀。 Walter Benjamin,我一直對他充滿敬意,他的思想跨越瞭文學、藝術、哲學、曆史、社會學等多個領域,總能帶給我意想不到的啓示。而“他的時代”,我想象中的是那個風雲變幻、充滿矛盾與張力的20世紀初葉的歐洲,一個社會結構急速轉型,思想文化領域百花齊放又暗流湧動的年代。從魏瑪共和國的繁榮與危機,到納粹主義的興起,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那個時代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舞颱,上演著無數悲歡離閤。書名中的“流浪”二字,更是觸動瞭我最深的共鳴。班雅明一生顛沛流離,多次被迫流亡,這種“流浪”的狀態,不僅是地理上的遷徙,更是精神上的探索與求索。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將班雅明的人生際遇與他的思想發展緊密聯係起來的?流亡的經曆,是否讓他對“傢園”、“歸屬”、“記憶”等概念有瞭更深刻的理解?他如何在陌生的土地上,繼續保持他對思想的追尋,如何在一個個臨時落腳點,構建起他龐大而精密的思想體係?這本書會不會展現齣班雅明在流浪中所遭遇的睏境與掙紮,以及他在這些睏境中迸發齣的驚人創造力?我非常期待,作者能為我描繪齣那個時代的大背景,那些影響瞭班雅明的關鍵事件和人物,以及他如何在這時代的洪流中,以他獨特的“流浪者”的視角,去觀察、去思考、去錶達。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