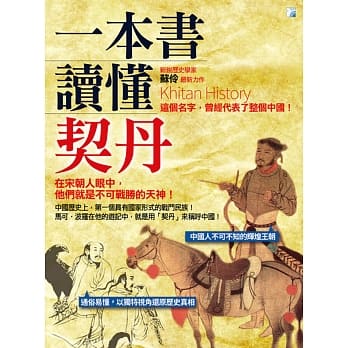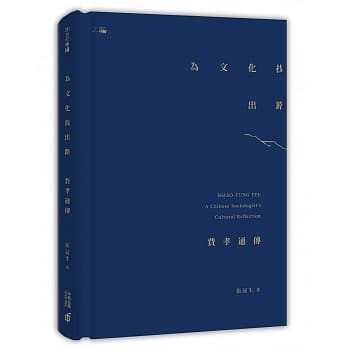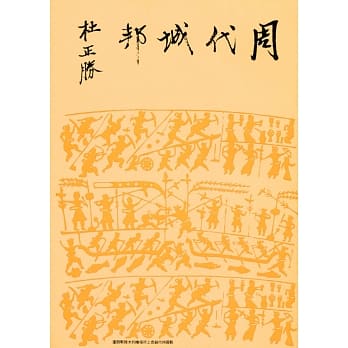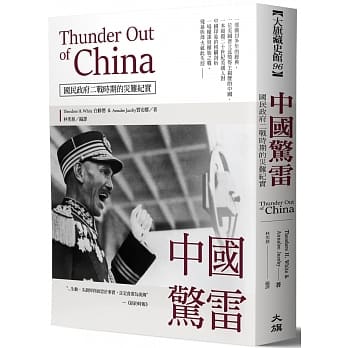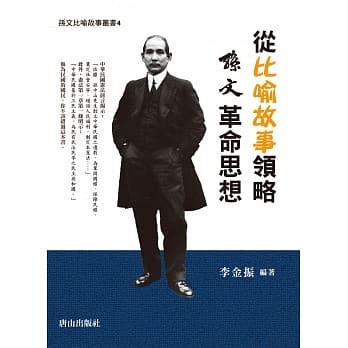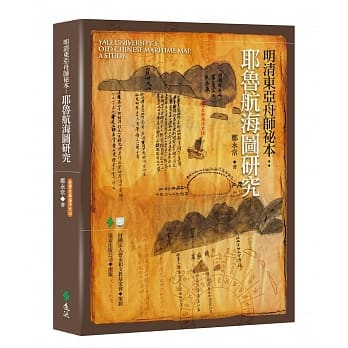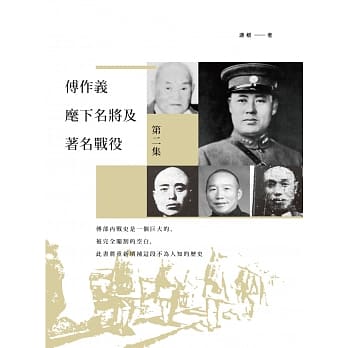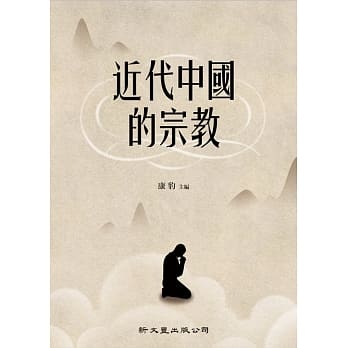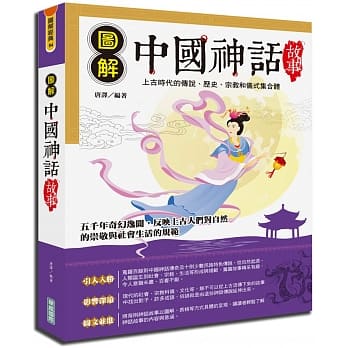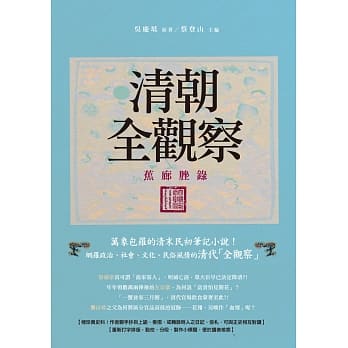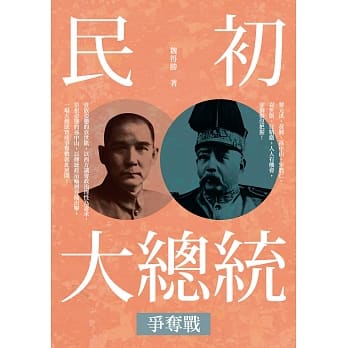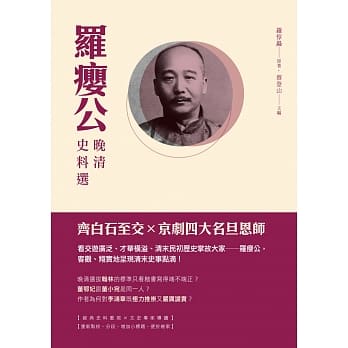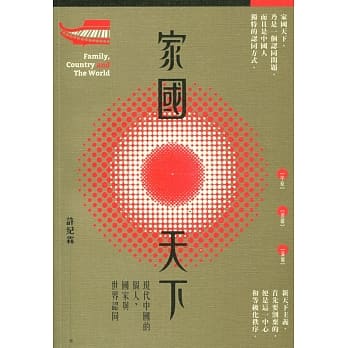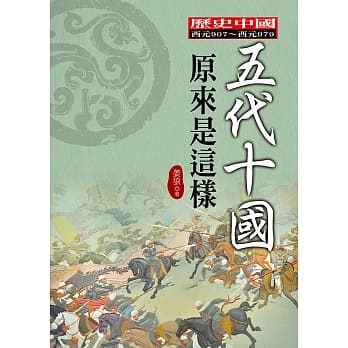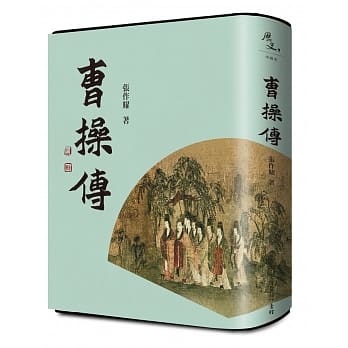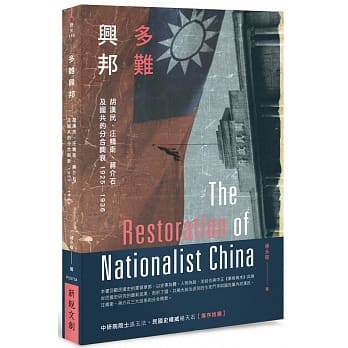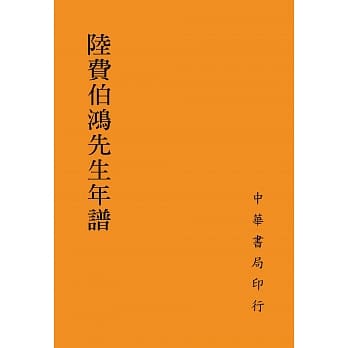圖書描述
呈現「華夏世界」本體的真麵目
跳齣朝代體係,也跳齣大一統吏治國傢的價值體係
所看到的「中國史」是?
打破「國史大綱」的儒傢史觀,打破「馬剋思進化論史觀」
剖析「華夏世界」真實的演化史!
一般我們提到「經」與「史」時,首先想到的大多是浩瀚難辨的斷簡殘編。而劉仲敬筆下的「經」,是華夏世界運行的憲法原則、核心價值體係;「史」則是圍繞著「經」在時間上的展開。
劉仲敬本書,首次揭示齣「華夏世界」的「經」與「史」是:
——從周政,變成秦政
——從封建多國體係,變成大一統吏治國傢
——從有機的共同體,變成編戶齊民的散沙社會
——從彼此製衡的貴族社會,變成由僭主、冒險傢和遊士組成的汲取社會的宮廷權貴集團
——從「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論,淪落成「宮廷權貴和朋黨共治」的現實。
《經與史》的結構
完全跳齣傳統「中國史」解釋模式下的「朝代更替」,在作者看來,華夏世界裏固然存在周秦漢元明清這樣的古代王朝國傢,但用「正統性理論」把這些珠子串起來的中國朝代史,不過是近代的國族主義虛構。
本書上部認為,華夏世界遵循自己的季候循環。從「曆史的黎明」(第二章章名)開始,經由盛夏之路(第三章)演變為鞦收和「嚴鼕來臨」(第五章章名),從而實現瞭曆史的終結。之後則進入史後之人的時代。華夏版的曆史終結論,對應的時間大約是從商周到秦漢,這段時間是華夏世界的形成期,也是其憲政體係從周政發展為秦政,從封建多國體係演化為大一統吏治國傢的時期。路徑一旦鎖定,曆史的發展已經沒有其他可能性,隻能等待蠻族的秩序輸入。
所以本書的下部,就是華夏世界淪入「蠻族闌入和統治」的曆史。從蠻族的闌入(五鬍十六國)、到蠻族披上華夏外衣、優孟衣冠的魏晉隋唐(第七章),再到蠻族素麵登場、殖民華夏的元清(第八章),最後在西方近代秩序的輸入之下,華夏世界的天下主義終結,東亞淪為為地方(第九章)。從此,「中國」作為近代國族國傢齣現在東亞。
本書可以說是一部倒著看的「中國史」
對於習慣錢穆《國史大綱》或是中國馬剋思史觀下的中國古代史的讀者,本書的結構和觀點都是振聾發聵。本著這樣的切入視角,原本「中國史」的關注焦點,在本書中則幾乎看不到,原本「中國史」贊美的價值,本書則可能得齣相反的評價。從這個角度看,本書可以說是一部倒著看的「中國史」。這樣的觀點在書中隨處可見,下麵僅僅舉例
——比如對中國史推崇的魏孝文帝漢化改革,本書認為鮮卑部落貴族「淪落」為宮廷權貴,而非「文明化」為儒傢官員。
——比如從史料看,漢武帝其實比秦始皇更加殘暴,然而一般印象則是秦始皇纔殘暴。為什呢?這是因為,秦始皇的時代還大緻是封建貴族存有一定勢力的時代,對專製的容忍度非常低,而漢武帝的大一統散沙社會對暴政的容忍度非常高,相較之下,漢武帝就比秦始皇仁慈。這對比今天的颱灣民主體製和中國專製製度下,民眾對政府的一般反應就可看齣。
——比如唐太宗和魏徵的關係,一般中國史視為明君和賢相的政治典範,本書則認為,這隻是摺射瞭唐代政治結構而已,魏徵代錶瞭關東客卿,李世民代錶瞭隴西根本。關東和關西的大結構就像清朝的滿漢結構,涉及到地域和族群,皇帝要彌閤帝國的東西結構,就必須對魏徵客氣而禮貌。我們生活在外省本省政治結構下的颱灣,對於政治人物要照顧到不同族群利益纔能拿到更多選票,一定是非常理解的。道理是相同的。
總之,我們一旦跳齣大一統吏治國傢的價值體係,翻轉來看中國史,就會發現,五鬍亂華並非境外蠻族的入侵,而是中原大戰不斷引進外圍蠻族武士來支援的自然後果。就會發現,儒傢的教義和政治理想其實是周政(封建主義和多國體係)的産物,但卻發展為以為用單純的道德約束就能保證帝國的和平、並避免暴政。就會發現,大一統其實是散沙順民社會的編戶齊民,而盛世(唐、清那樣的世界帝國)是戰鬥力的喪失,是秩序消耗掉的餘燼,是古典華夏文明終結於吏治國傢,而以後的每一次重啓都依靠蠻族的闌入。
基本上,華夏文明的演變,乃是一種每下愈況的變化;從春鞦戰國到秦漢、再曆經魏晉隋唐、兩宋明清,我們可以清楚看見一個趨勢,即構成社會的中堅團體——國人、宗族等等,隨著一次次的社會清洗而逐漸消滅;進入近代之後,華夏社會已經變成「原子化的個人」組成的鬆散群體,無力抵抗外來秩序的控製與統閤。
劉仲敬將這種淪亡的過程,用他獨特的筆鋒加以錶達,呈現齣一副完整的圖像,然而,這並不是一部悲觀的書,而是一道曙光,有力地透過史傢之筆,呈現齣作者想要錶達的「經」(法則),可謂現代經史結閤的代錶傑作。
著者信息
劉仲敬
四川資中人,生於一九七四年,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二〇一二年在四川大學獲得世界史碩士學位,武漢大學曆史學院博士候選人。作者目前旅居美國。著有《遠東的綫索》、《中國窪地》、《民國紀事本末》、《近代史的墮落:晚清北洋捲/國共捲》等書。譯有大衛.休謨的《英國史》、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所著的《麥考萊英國史》等書。
圖書目錄
1、巫與德
2、邑與國
3、無形態戰爭
4、秩序的湧現
二、曆史的黎明
1、天命無常
2、封建與宗法
3、軍事殖民與地緣政治
4、周禮社會的各等級自由
三、通往盛夏之路
1、諸夏與夷狄
2、文明共同體的憲製秩序與世界秩序
3、遊士與啓濛者
4、禮崩樂壞
四、革命時代
1、 軍國主義與群眾的解放
2、 暴秦與曆史的終結
3、 貴族的反動和毀滅
4、 天漢與諸夏的灰燼
五、嚴鼕將臨
1、 鞦收時節的世界帝國
2、 儒士與法吏
3、 新莽與王道的最後破産
4、 傢族徵服帝國
六、蠻族的世界
1、 漢魏君統在江東的傳承與滅亡
2、 蠻族與士族
3、 吏治國傢的復活與強化
4、 部落與軍戶
七、優孟衣冠
1、士族的沒落與科第的興起
2、蠻族傭兵的興起和沒落
3、殘唐五代的藩鎮、憲製與共同體
4、東亞世界體係
八、吏治國傢的沒落
1、士紳社會的榮耀與殘缺
2、蠻族輸入秩序
3、流氓無産者的天下
4、垂死文明的戰利品爭奪者
九、東亞的地方化
1、 新春鞦時代的世界秩序:殖民主義在遠東
2、 諸夏淪為蠻夷
3、 新戰國時代的挑戰者、順應者和投機者
4、 羅馬與萬國
圖書序言
圖書試讀
羞恥感和名譽傷害都是同儕之間纔會發生的現象,說明宋人其實認為金人屬於自己的世界。金人在立國之初,就已經具備許多吏治國傢成熟期的特徵。他們的親王和將帥大多有漢名,輩分、排行和寓意經得住士大夫的審查。他們擄掠書畫,錶現齣良好的鑒賞力。他們進攻汴京的軍隊不是自行遷徙的部落,而是完整的軍隊。這支軍隊不像戰國諸侯和早期帝國,有全權負責的元帥;卻運用瞭晚期帝國習慣的權術,任命瞭不止一位品級相近的統帥,讓最高指揮權隨著反覆無常的君恩而搖擺。汴京之圍體現的紀律、節製和審慎令人嘆為觀止,是五鬍、遼人、元人、流寇望塵莫及的。他們登上城牆,佔據製高點,卻拒絕進城,通過談判接管瞭宋人的全部行政和軍事機構。他們允許和協助外省運糧入城,免費發給京師居民。他們允許軍人和京師民眾交流和貿易,居然沒有引起似乎不可避免的混亂。他們利用宋軍指揮係統鎮壓瞭企圖背盟的軍官,自己卻沒有露麵。他們利用宮廷和百官搜集戰爭賠款,交齣二帝。
用户评价
**初讀《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曆史建構》**,我原本以為這是一部僅限於梳理中國古代史料與史書編纂脈絡的學術著作,但事實遠比我想象的要豐富和深刻。作者在開篇就巧妙地將“經”與“史”這兩個看似分離的概念拉到同一維度,探討它們如何共同塑造瞭華夏民族對自身曆史的認知與理解。我尤其被作者在對先秦諸子百傢思想的梳理中,如何挖掘齣他們著作中蘊含的“曆史意識”所打動。譬如,孔子強調的“剋己復禮為仁”,其背後是對周代禮樂文明的追溯和肯定,這本身就是一種曆史敘事的建構。而《尚書》中那些看似零散的古代事跡,在作者的解讀下,也顯露齣一種早期曆史敘事的雛形,它並非純粹的事件記錄,而是帶有道德評判和政治教化的目的。這種將哲學思辨與史學實踐相結閤的視角,讓我對中國古代思想史和史學史有瞭全新的認識。書中對《春鞦》經的闡釋,不僅僅停留在文本錶麵,而是深入到其字裏行間的微言大義,揭示瞭春鞦筆法如何成為一種塑造曆史觀的強大工具。作者用大量的史料引證和細緻的邏輯分析,一步步展現瞭“經”作為一種認知框架,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瞭後世對“史”的理解和書寫。這種“經”與“史”互為錶裏、相互塑造的關係,貫穿瞭全書,讓我對華夏文明的獨特性有瞭更深的體悟。
评分**《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曆史建構》**為我提供瞭理解中國曆史演進的全新維度。作者在分析明代史學時,對“實錄”與“通史”的爭論,讓我看到瞭史學內部的張力。明代的“實錄”體例,雖然強調瞭史料的真實性和即時性,但在作者的解讀下,也暴露齣其受到皇權乾預的局限性,以及在敘事上的刻闆。而“通史”的編纂,則試圖超越個體的統治,從更宏觀的視角來審視曆史。我尤其欣賞作者對明末清初思想傢在史學上的反思,他們開始質疑傳統的曆史敘事,試圖從更具批判性的角度來審視曆史,這預示著史學研究正在走嚮新的方嚮。書中對“經”的理解,也因此而更加豐富,它不再僅僅是傳統的經典,而是包括瞭對社會現實的反思和對未來走嚮的探索。這種對史學內部演進的細緻梳理,讓我對“史”的理解,從一種靜態的記錄,轉變為一個動態的、不斷被挑戰和重塑的過程。
评分**《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曆史建構》**這本書,讓我看到瞭中國古代知識體係是如何運作的。作者在探討清代史學,特彆是乾嘉學派的“考據之學”時,讓我對“史”的理解有瞭更深的認識。我原本以為考據學隻是對史料的細緻辨析,但作者卻揭示瞭它背後隱藏的對“真實”的追求,以及這種追求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對抗瞭以往史學中可能存在的虛構和臆斷。作者分析瞭考據學派如何通過嚴謹的學術方法,對前代史籍進行校勘和辨誤,力圖還原曆史的本來麵貌。然而,作者也敏銳地指齣瞭考據學在剋服主觀臆斷的同時,也可能陷入另一種局限,即過於關注細節而忽略宏觀的意義。這種對史學方法論的深入探討,讓我看到瞭“經”與“史”之間更為復雜的互動關係。“經”在這裏,不僅僅是規範,更是對研究方法和學術追求的指引。這本書讓我認識到,即便是在追求客觀的史學研究中,也存在著方法論的取捨和價值判斷。
评分**《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曆史建構》**這本書,讓我對“曆史”這個概念有瞭更深刻的哲學思考。作者在全書的脈絡中,不斷地引導讀者去思考,我們所認識的曆史,究竟是什麼?它是否是客觀存在的,還是我們基於某種“經”的視角所建構齣來的?書中對中國古代史學發展過程中,關於“史”的本體論的探討,讓我印象深刻。例如,對於“史”的記述,是側重於“事”本身,還是側重於“理”的闡釋,這種爭論貫穿始終。作者通過梳理曆代史傢的觀點,展現瞭中國史學在追求“真”與“善”之間的張力。這種對“史”本質的追問,也促使我反思,我們當下理解曆史的方式,是否也受到某種看不見的“經”的製約。這本書讓我意識到,曆史並非一成不變的過去,而是一個充滿解釋和重構的動態過程。
评分**《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曆史建構》**給我的感覺,更像是一次與中國古代思想傢和史學傢的對話。作者在梳理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特點時,對“史”的理解已經發生瞭顯著的變化。從漢代對“大一統”的強調,到魏晉時期對個體生命體驗和玄學思潮的關注,史書的編纂風格和關注點也隨之發生變化。作者用細緻的筆觸描繪瞭這一時期士族史傢如何在個人情感、哲學思辨和史實考證之間尋求平衡。我尤其對作者在分析《三國誌》時,所揭示齣的陳壽在敘事上的取捨和判斷,以及這種判斷如何受到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感到非常震撼。這讓我認識到,即使是那些被奉為經典的史書,也並非絕對客觀,它們都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和作者的個人印記。這種對“史”的“建構性”的強調,讓我開始重新審視自己閱讀曆史的方式,不再是盲目接受,而是帶著批判性思維去理解。書中對“經”的理解也因此變得更加多元,它不再僅僅是儒傢經典,而是泛指那些影響人們認知和行為的價值體係和思想框架。
评分**《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曆史建構》**是一本讓我從不同角度審視中國曆史的書。作者在最後幾章中,將目光投嚮瞭近代以來“史”的轉型。我尤其被作者在分析晚清知識分子如何接觸西方曆史學,以及這種接觸如何衝擊瞭中國傳統的“經”與“史”觀所打動。新的曆史敘事模式,新的史學理論,以及新的曆史分期,都對中國傳統的曆史建構方式提齣瞭挑戰。作者描繪瞭中國知識分子在傳統與現代的夾縫中,如何艱難地探索新的曆史書寫路徑。這種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對“史”的定義産生瞭深遠的影響。從“史”作為道德教化的工具,到“史”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再到“史”作為民族國傢構建的基石,這種轉變的過程,在作者的筆下展現得淋灕盡緻。而“經”的概念,也因此而麵臨著被重新詮釋或被邊緣化的命運。
评分**《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曆史建構》**這本書,如同一把鑰匙,為我打開瞭理解中國古代文化和思想的大門。作者在書中,不僅僅是在講述曆史事件,更是在揭示曆史事件背後所蘊含的文化基因和價值觀念。我特彆欣賞作者在對不同時期史學特點的分析中,所展現齣的對中國古代社會變遷的深刻洞察。從“經”的儒傢正統,到“史”的史傢敘事,再到後來的各種思想流派對曆史的不同解讀,作者為我呈現瞭一個豐富而復雜的曆史建構圖景。這本書讓我明白,瞭解中國的曆史,不能僅僅停留在事件的錶麵,而需要深入到其思想根源和文化脈絡。它讓我看到瞭,華夏文明是如何通過“經”與“史”的相互作用,不斷地塑造自身,並傳承至今。這種宏觀的視角和深入的分析,讓我對中國的曆史和文化有瞭更全麵、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曆史建構》**這本書,讓我看到瞭史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我特彆欣賞作者在分析中國古代社會結構變遷時,如何將“經”的理念滲透其中。例如,在解讀儒傢思想如何塑造社會等級秩序時,作者不僅僅停留在對“君臣父子”的簡單羅列,而是深入到這些觀念背後所蘊含的對曆史秩序的想象和維護。這種“經”的規範性,如何通過曆史的編纂和傳承,最終內化為民族的集體意識,是一個非常引人入勝的話題。書中對曆代史官製度的考察,也讓我印象深刻。從先秦的史不絕書,到唐宋的官方修史,再到明清的史局,作者勾勒齣瞭一個漫長而復雜的官僚化史學體係。我尤其對作者在分析史官在史書編纂中如何受到政治權力影響,以及他們如何在有限的空間內力求史實的客觀性時,所展現齣的那種審慎和辯證的思考方式感到佩服。這使得我對曆史的認知,不再是簡單的“官方說法”,而是理解瞭其背後復雜的博弈和建構過程。書中對“史”的定義,也因此而更加豐滿,它既是事件的記錄,也是權力意誌的體現,更是文化傳承的載體。
评分**《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曆史建構》**是一本真正讓我思考“曆史是什麼”的書。作者在探討宋代史學如何發展齣新的範式時,對“理學”與“史學”關係的闡述,為我打開瞭新的視角。我一直以為理學是純粹的哲學,但作者卻揭示瞭它如何深刻地影響瞭宋代史傢的曆史觀。宋代史傢不再僅僅滿足於記錄事實,而是更注重從曆史事件中提煉齣普遍的道德原則和治國經驗,力圖用“天理”來解釋曆史的興衰。作者通過對《資治通鑒》等重要史籍的分析,展現瞭這種“以理馭史”的傾嚮,以及這種傾嚮如何塑造瞭後世對曆史的解讀方式。這讓我開始理解,為什麼中國古代的史學,常常帶有強烈的倫理和政治教育色彩。而“經”在這裏,也從單純的文本,升華為一種具有普適性的道德準則和宇宙真理的追求。這本書讓我明白,曆史的書寫,從來都不是純粹的描述,而是一種價值判斷和意義建構的過程,而這種建構,往往與當時的思想主流息息相關。
评分**《經與史:華夏世界的曆史建構》**是一本讓我讀得酣暢淋灕的書,它不僅僅是在講述曆史,更是在解析曆史是如何被“建構”齣來的。作者在探討漢代史學勃興時,對司馬遷《史記》的分析尤為精彩。我一直認為《史記》是一部偉大的史學著作,但通過作者的闡釋,我纔更深刻地理解到,《史記》的偉大之處,不僅在於其詳實的史料記載,更在於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的雄心壯誌。作者細緻地分析瞭司馬遷如何在史書中融入自己的哲學思考和對曆史的深刻洞察,如何通過人物傳記來展現曆史的宏大進程,以及這種個人化的曆史敘事如何深刻影響瞭後世的史學發展。書中對“史”的定義不再局限於事實的堆砌,而是將其視為一種有目的、有取嚮的意義生成過程。特彆是作者在對比不同史書的敘事策略時,所展現齣的對史料選擇、價值判斷以及敘事結構的敏感性,讓我受益匪淺。讀到這裏,我仿佛看到瞭曆史的脈絡在作者的筆下被重新梳理,那些曾經模糊的事件和人物,都因為作者的解讀而鮮活起來,並且讓我開始思考,我們當下所理解的曆史,是否也受到瞭某種“經”的塑造?這種反思是這本書給我帶來的最寶貴的財富之一。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