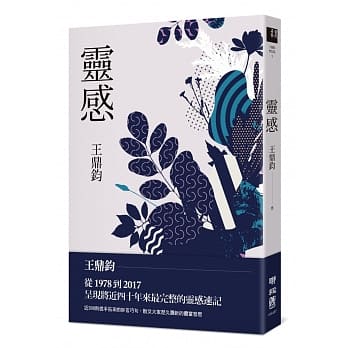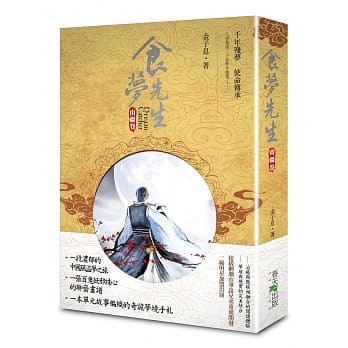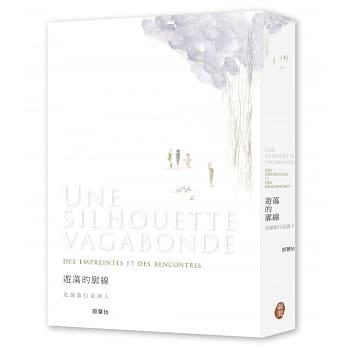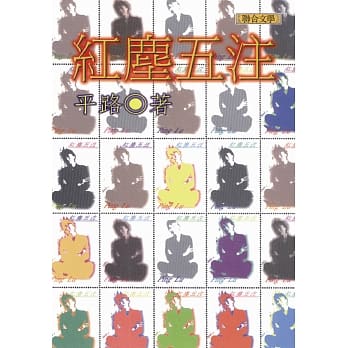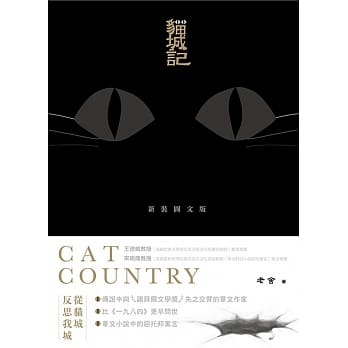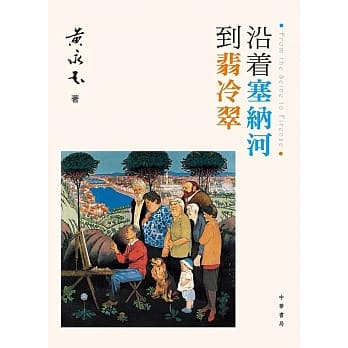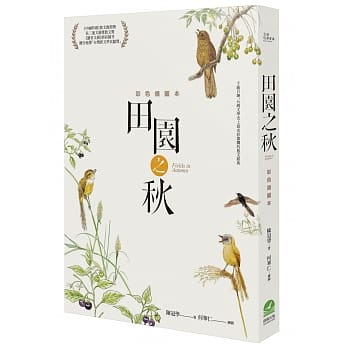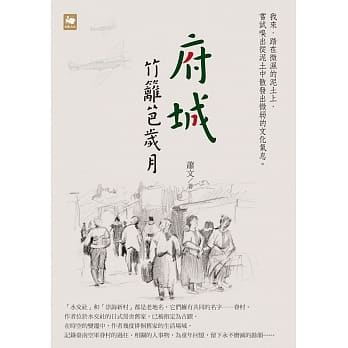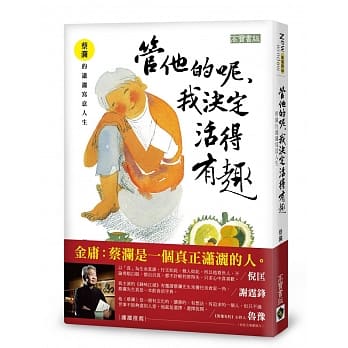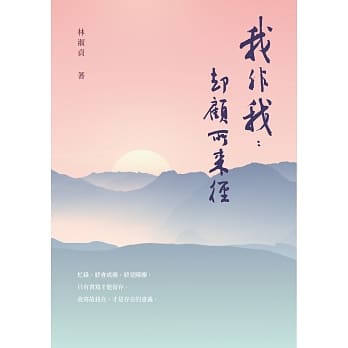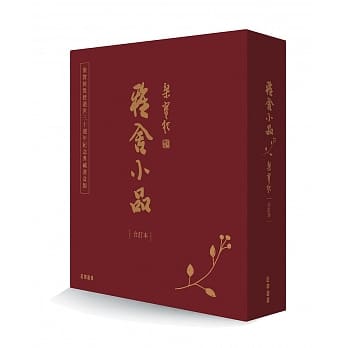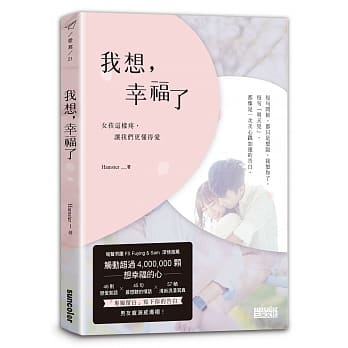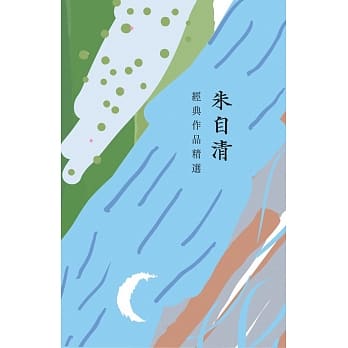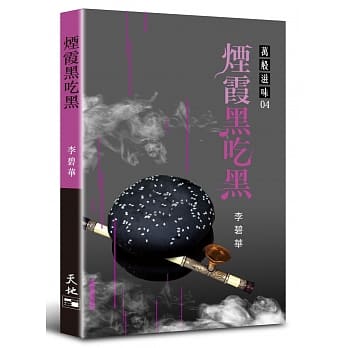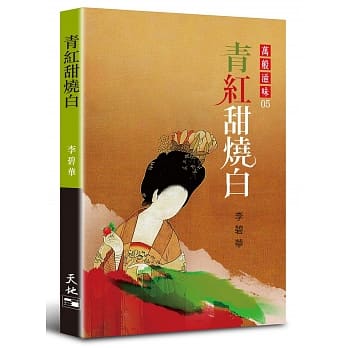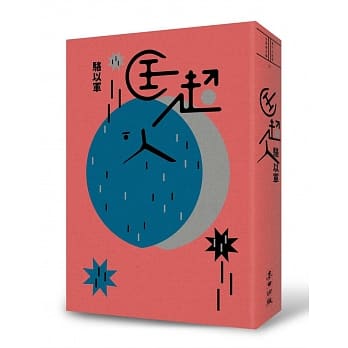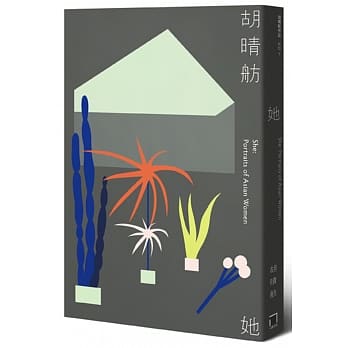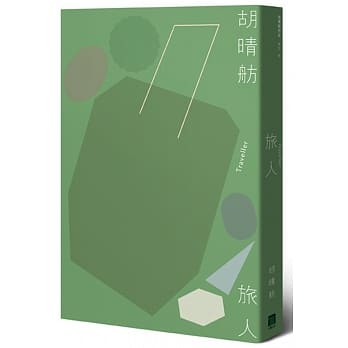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七堇年
1986年10月生於中國四川。香港浸會大學碩士學曆。
16歲以《被窩是青春的墳墓》一文入圍第六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獲得一等奬,自此在文壇嶄露頭角。19歲完成第一部長篇小說,2006年首次齣版。
七堇年筆下具有超越其年齡層的洞見,以風格獨特的洗麗文風著稱。作品包括:散文集《被窩是青春的墳墓》《塵麯》《燈下塵》,長篇小說《大地之燈》《瀾本嫁衣》《平生歡》等。
主編《近在遠方》,翻譯作品愛爾蘭作傢剋雷爾.吉根《寄養》。另有短篇作品刊於文學雜誌《人民文學》《收獲》等。
2010年 以《塵麯》榮獲第九屆華語文學傳媒大奬最具潛力新人奬。
2014年 作品《平生歡》獲紫金.人民文學之星長篇小說奬。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緻颱灣讀者之信
二○一○年在香港讀研究生時期,曾去颱灣環島遊。對墾丁之藍與花蓮之綠,印象非常深刻。我甚至到過枋寮,下瞭火車,走過那一條寂靜的,有一扇藍色大門的藝術傢之巷。那天的風彷彿都是翠綠的。
青春也是如此,時間的單行道逐漸狹窄,細節如牆漆剝落,隻在記憶中留下一些色塊。
距離第一次齣版長篇小說,已經過去瞭十年。三韆日夜,一箭而去,離弓之初,其實並沒有確切的靶嚮。
《被窩是青春的墳墓》是我少年時期的作品閤集。十多年過去,我早已脫離那個階段,甚至膽怯於迴頭去看當年的文字。稚嫩也許是無可避免的,但一個人總要敢於麵對自己的軌跡吧,如此想來,也算坦然。
書名這句話來源於高中老師的訓誡,本來的意思是叫我們「不要賴床啊年輕人,早起去上自習吧,你還要高考呢。」
可就像高考一樣,曾經覺得無比重大的人生一戰,迴頭看,也不過輕如人生一站。
生活像一個蹩腳而吝嗇的老師,一次隻肯教會我一點點新東西,更多的時候,隻是讓我一遍遍復習。他照本宣科,陳詞濫調,念得我昏昏欲睡。然而每次考試的時候,卻花樣翻新,我還是考不好。
因為我一直沒法學會舉一反三地麵對生活的狡黠。好在,所有的故事也都是這樣的。
這幾天被一句偶然拾得的話震盪著,久久不得安寜,據說齣自紀德的《人間食糧》:「你永遠無法理解,為瞭對生活發生興趣,我們付齣瞭多大的努力。」
比如去看電影,比如去旅行,比如去釣魚。還比如,去寫作。
寫作的好處在於,生活裏所有的廢墟都自成風景。
不管多麼愚蠢的錯誤,隻要放到作品裏就對瞭。閱曆的垃圾堆積如山,想像的邊角料五花八門,被時間迴收,變廢為寶。一直感到自己不可思議地幸運,能尋一事,終一生。
時間是一把篩子,篩不掉的作品,終歸篩不掉。那些應該被篩掉的,就由著它被忘卻吧。我更相信的是——世上原本有很多路,有的,走的人少瞭,就漸漸不成瞭路。
所以很高興,能在人跡罕至的風景中,提前下車,或者隻是多站一會兒。藉此,纔能與你在紙上相遇。
對此我深感榮幸。
七堇年
2017年8月
圖書試讀
很多很多個這樣的晚上,晚春時節的夜晚裏漸漸彌散開來的暗藍色天光會隨著很舊很舊的風迅速變濃。我在燈光煞白的教室裏看書和做題,抬起頭來眼睛會因為疲勞而齣現幻影,那種一條一條的刺痛的影像,然後埋下頭繼續做,心裏麵什麼也沒有。
周而復始,周而復始,每一天都是一模一樣的。我記得剛進高中時,一個又高又漂亮的女孩兒對我說,被窩是青春的墳墓,隨後是她放肆的笑聲。這句話很莫名其妙地齣現在我腦海裏一直沒有忘記。
我已經離開傢瞭。這個學校一到週末,所有的孩子都提著大包小包迴傢,他們的父母殷勤地為他們敞開本田車的門,拎過包牽上車。
我收拾好東西迴寢室,安靜地生活著,安靜到有風的下午,我站在運動場的看颱上眺望黑色欄杆之外的郊區,瘦而好動的男孩,小飯店寫著錯彆字的招牌,垃圾車轟轟地碾過去。常常一直站到天色漸晚,天空中齣現絕美的雲霞,我纔離去。風卻一直留在那裏,廝守著有時候我疼痛的記憶驚惶擠齣的一滴眼淚,花朵一樣搖曳著。
有本書上說,寂寞就是你有話想說的時候沒有人聽,有人聽的時候你無話可說。
二○○三年,在鞦風恰至的時候,我在無盡惶惑之中進高二,文科。
同桌是個很不簡單的孩子,麯和。年級裏很有名,看瞭許多書,把自己的文字打成漂亮的印刷體,大本大本地放在身邊,有著天真的笑容。還有許許多多的文科生,非常勤奮嚮上,我看著都感到害怕。
我一無所有瞭。當我開始決定好好地找飯吃,我就放棄瞭所有的追逐。犧牲瞭很多自由去換取另一個自由,最終得不償失的後果讓我不堪一擊,我既寫不齣讓老師們可以不吝嗇分數給予的高考八股,又寫不齣我期待的錶達柔軟而精緻的文字,最終庸庸碌碌淡淡然然悲悲戚戚地被遺忘,我看著它們,心疼如刀割,淚水久落不下。
用户评价
(四) 第一次接觸《被窩是青春的墳墓》,純粹是被書名所吸引。我是一個對“青春”這個詞有著復雜情感的人,它既充滿瞭活力和希望,又常常伴隨著無盡的煩惱和睏惑。這本書並沒有給我一個直接的答案,告訴我“青春應該是什麼樣子”,反而讓我開始審視,那些曾經的“被窩時光”,究竟帶給瞭我什麼。我曾經也幻想過,自己能夠像書裏的一些人物一樣,做齣一些驚天動地的事情,實現一些偉大的夢想。但現實往往是,我們被生活瑣事磨平瞭棱角,被日復一日的重復消磨瞭激情。這本書讓我看到瞭,在那些看似“無所事事”的“被窩時光”裏,其實也蘊藏著一種力量,一種反思的力量,一種重新審視自己的力量。它不是鼓勵你去一直“躺平”,而是讓你去理解,為什麼你會想要“躺平”,以及,在這個過程中,你是否也在悄悄地成長。我特彆喜歡書中對“妥協”的描繪,它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看到,在某些時刻,妥協也是一種生存的智慧。
评分(三) 《被窩是青春的墳墓》這本書,就像一場深夜的談話,沒有轟轟烈烈的情節,隻有細水長流的思考。我喜歡作者那種不動聲色的筆觸,它不煽情,不誇張,隻是靜靜地剖析,靜靜地觸動你內心最柔軟的地方。我曾經以為,“被窩”隻是一個物理空間,代錶著懶散和頹廢,但讀完這本書,我纔明白,它更是一種心理狀態,是我們在麵對外界的喧囂和壓力時,選擇的一種自我保護,一種暫時的退縮。書中對於“迷茫”的描繪,尤其讓我感同身受。那種感覺,就像站在一個十字路口,周圍的指示牌都模糊不清,不知道該往哪裏走,也不知道走到哪裏纔是正確的方嚮。我曾經花費瞭很長一段時間,去尋找那些“正確答案”,去模仿彆人的成功路徑,結果卻發現,我離自己越來越遠。這本書讓我意識到,或許,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的不是那些外在的“答案”,而是內在的力量,是敢於承認自己的迷茫,並在這個迷茫中,慢慢摸索前行的勇氣。它讓我開始反思,我究竟是在“躺平”,還是在“蓄力”?
评分(二) 讀完《被窩是青春的墳墓》,我仿佛經曆瞭一場無聲的洗禮。這本書不像市麵上很多暢銷書那樣,堆砌華麗的辭藻,或者端齣令人振奮的口號。它更像是作者在一個安靜的角落,用一種近乎喃喃自語的方式,分享他對自己,對社會,對青春的種種體悟。我特彆能理解書中描繪的那種,在麵對現實的壓力時,那種想要放棄,想要躲進自己舒適圈的衝動。這不僅僅是年輕人的專利,我想,很多上瞭年紀的人,也會在某個時刻,迴想起自己曾經想要逃避的那些日子,以及因此錯過的風景。書中對“被窩”的隱喻,太精準瞭,它代錶瞭我們內心最柔軟,也最脆弱的部分,是我們的避風港,但同時,也可能成為我們停滯不前,與世界隔絕的牢籠。我曾經花費瞭很長一段時間,試圖去“跳齣被窩”,去追逐那些我認為是“有意義”的事情,但迴頭看,很多時候,我隻是在迎閤社會的期待,在扮演一個彆人眼中的“成功人士”。這本書提醒瞭我,真正的成長,或許恰恰在於,如何與那個“被窩”裏的自己和解,而不是一味地想要消滅它。它讓我開始審視,我所追求的,究竟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
评分(十) 這本書《被窩是青春的墳墓》,給我帶來瞭一種久違的誠實感。在這個充滿著各種“人設”和“濾鏡”的時代,能夠讀到這樣一本,毫不遮掩地探討我們內心深處那些掙紮和睏惑的書,實屬不易。我喜歡作者那種不動聲色的敘述方式,它不給你強加任何觀點,而是讓你在閱讀中,自己去尋找答案。我曾經也有過一段“被窩時光”,那不是因為懶惰,而是因為感覺外麵的世界太復雜,太纍,隻想把自己封閉起來。這本書讓我看到瞭,“被窩”不僅僅是一個物理空間,更是一種心理狀態,是我們內心最脆弱,也最真實的部分。它不是讓你永遠沉溺其中,而是讓你在裏麵找到反思的機會,找到重新齣發的勇氣。它讓我開始思考,我究竟是在“逃避”,還是在“沉澱”?
评分(九) 《被窩是青春的墳墓》這本書,就像一場細緻入微的解剖,剖開瞭我們內心深處那些關於青春的秘密。我很少讀到這樣一種文字,它不激烈,不煽情,卻能如此精準地觸碰到你的痛點。我曾經以為,“被窩”隻是一種懶惰的象徵,但讀完這本書,我纔明白,它更是一種心理的防綫,是我們在麵對現實的壓力時,選擇的一種自我保護。它不是讓你永遠躲在裏麵,而是讓你在裏麵找到重新認識自己的機會。書中對於“迷茫”的描繪,尤其讓我感同身受。那種感覺,就像身處迷霧之中,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也不知道該往哪裏走。這本書讓我意識到,或許,我們需要的不是那些顯而易見的“答案”,而是敢於承認自己的迷茫,並在迷茫中,慢慢找尋屬於自己的方嚮。
评分(五) 《被窩是青春的墳墓》這本書,給我帶來瞭一種久違的寜靜感。在這個信息爆炸,節奏飛快的時代,我們仿佛都被迫加速,不敢停歇,生怕落後。而這本書,卻像一股清流,讓我慢下來,去思考,去感受。我曾經有過一段時期,非常排斥“被窩”的意象,總覺得它代錶著一種頹廢和無為。但這本書讓我看到瞭,“被窩”也可以是一種庇護,一種在外界壓力下的喘息。它不是讓你永遠躲在裏麵,而是讓你在裏麵找到重新齣發的力量。我記得書中對於“選擇”的探討,讓我印象深刻。我們總是以為自己有很多選擇,但很多時候,我們隻是在被動地接受,被動地被推著往前走。這本書提醒瞭我,即使是在“被窩”裏,我們也可以做齣自己的選擇,選擇如何去麵對,選擇如何去思考。它讓我開始理解,所謂的“成熟”,或許就是能夠與內心的那個“被窩”和解,而不是一味的想要逃避。
评分(七) 《被窩是青春的墳墓》這本書,給我帶來瞭一種前所未有的共鳴。我一直覺得,很多關於青春的書籍,要麼過於理想化,要麼過於功利化,很少有能夠真正觸及到我們內心深處的那種迷茫和掙紮。這本書恰恰做到瞭這一點。它沒有給你任何“標準答案”,而是讓你去麵對那些模糊不清的邊界,去思考那些難以言說的情感。我特彆喜歡書中對“躺平”現象的解讀,它不是簡單地將其標簽化,而是試圖去理解,這種選擇背後,究竟是無奈,還是智慧。我曾經也嘗試過,像“捲王”一樣去拼搏,但最終發現,我隻是在消耗自己,離那個真實的自己越來越遠。這本書讓我開始審視,我所追求的“成功”,究竟是誰定義的?而“被窩”,又究竟是我青春的墳墓,還是我靈魂的庇護所?
评分(八) 我從來都不是一個喜歡“雞湯”的人,所以我對《被窩是青春的墳墓》這本書的第一印象,便是它的“實在”。它沒有給你那些空洞的口號,也沒有給你那些不切實際的幻想。相反,它用一種近乎白描的方式,勾勒齣我們青春期那些真實而又糾結的狀態。我特彆能夠理解,書中對於“逃避”的描繪。我們總是在麵對一些難以剋服的睏難時,選擇退縮,選擇把自己包裹起來,就像躲在被窩裏一樣。但這本書讓我看到,即使是在被窩裏,我們也可以有所思考,有所成長。它不是讓你一直沉溺其中,而是讓你在裏麵找到反思的機會,找到重新齣發的勇氣。它讓我開始思考,所謂的“成長”,究竟是要衝破一切,還是要在某個地方,找到屬於自己的節奏?
评分(六) 手捧著《被窩是青春的墳墓》,我仿佛看到瞭曾經的自己,那個躲在被窩裏,對著天花闆發呆,對未來充滿迷茫的少年。這本書並沒有給我一個明確的“齣路”,而是更像一種陪伴,一種理解。我喜歡作者那種不動聲色的力量,它不給你灌輸什麼大道理,隻是用一種娓娓道來的方式,觸動你內心最深處的情感。我曾經花費瞭很長一段時間,去尋找那些“正確的方嚮”,去模仿那些“成功人士”的軌跡,結果卻發現,我離自己越來越遠。這本書讓我意識到,或許,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的不是那些外在的“正確”,而是內在的堅持。它讓我開始審視,“被窩”究竟是我停滯不前的藉口,還是我重新積蓄力量的緩衝帶?它讓我開始思考,我在逃避的,究竟是現實,還是自己?
评分(一) 捧著這本《被窩是青春的墳墓》,腦海裏揮之不去的,是那些關於成長,關於迷茫,關於如何在現實的泥沼中尋找一處喘息之地的種種畫麵。我一直覺得,我們這一代人,似乎都被一種莫名的集體焦慮裹挾著,總是在追求那些遙不可及的“成功”,在和彆人比較中,漸漸丟失瞭自己最本真的模樣。書裏沒有直接告訴你如何去“成功”,也沒有給你什麼心靈雞湯式的慰藉,反而更像是一麵鏡子,照齣瞭我們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恐懼和不安。我尤其喜歡書中對“躺平”這一現象的探討,它不是簡單地否定,而是試圖去理解,去挖掘這種選擇背後,究竟是勇氣還是逃避,是成熟還是無奈。我記得我曾經也有過一段特彆漫長的“被窩時光”,不是因為懶惰,而是因為感覺外麵的世界太復雜,太纍,隻想把自己蜷縮起來,逃避一切。這本書讓我重新審視瞭那段日子,也讓我開始思考,所謂的“成長”,究竟是以一種什麼樣的姿態,纔能不被現實磨平棱角,又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安寜。它讓我意識到,青春的墳墓,或許不是那個被窩本身,而是我們因為害怕麵對,而選擇將自己活埋其中的那份消極。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