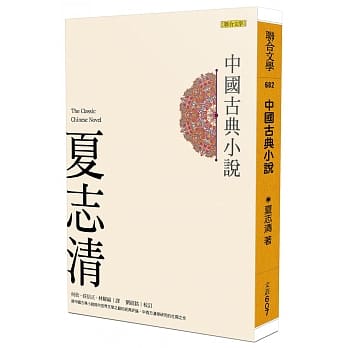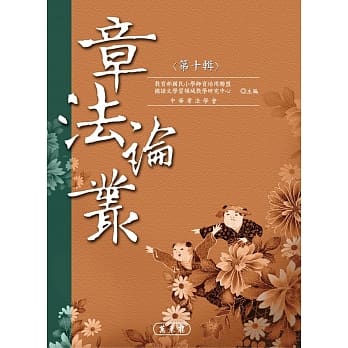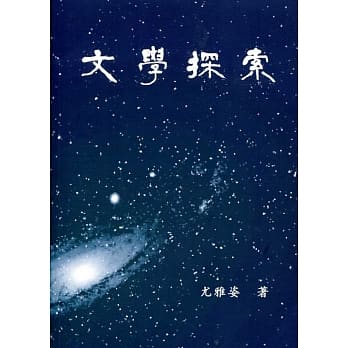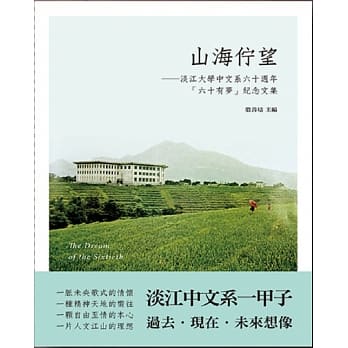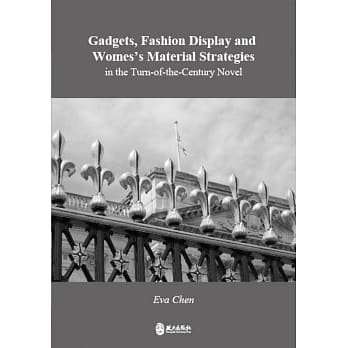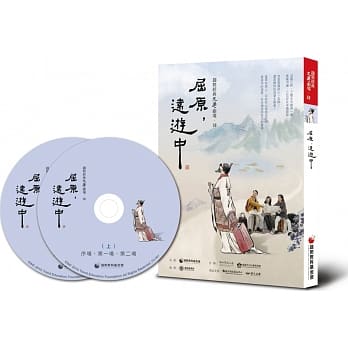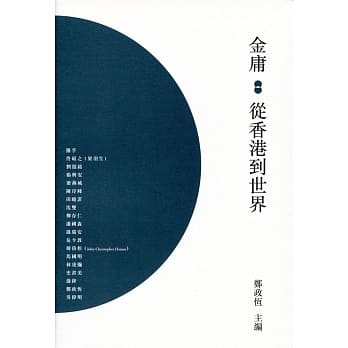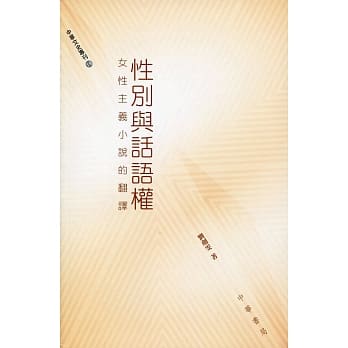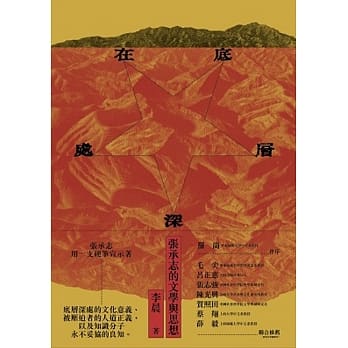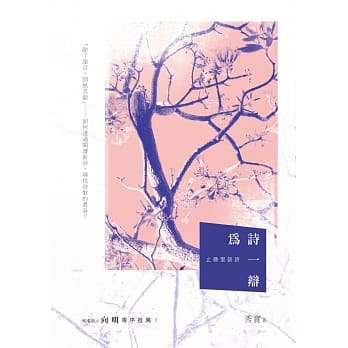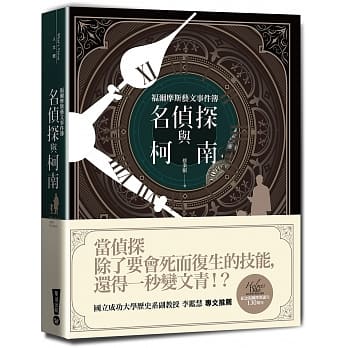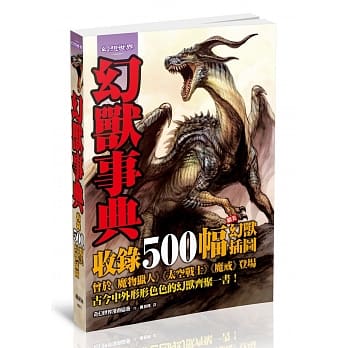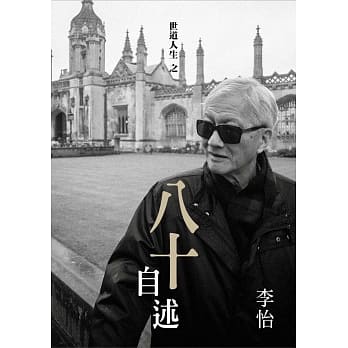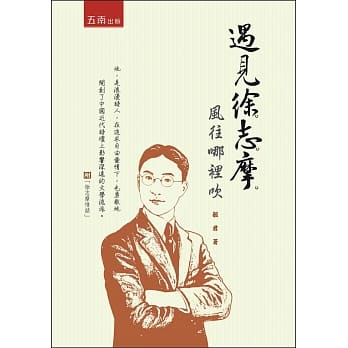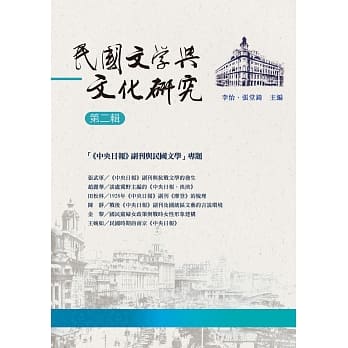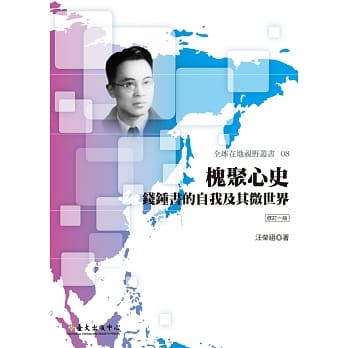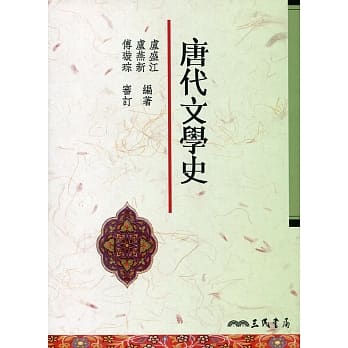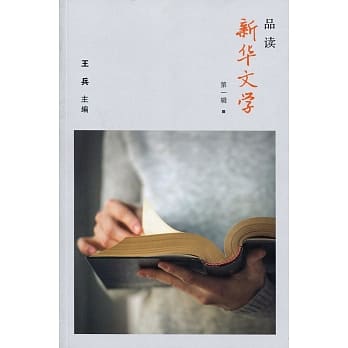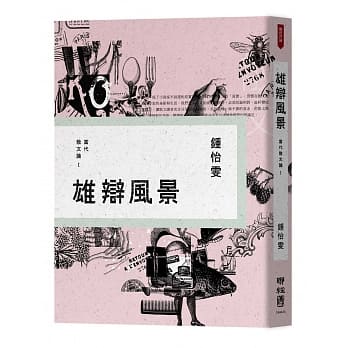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揚之水
浙江諸暨人,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從事名物研究。著有《詩經名物新證》《先秦詩文史》等。
圖書目錄
大雅.公劉
小雅.大田
豳風.七月
大雅.緜
小雅.斯乾
小雅.楚茨
小雅.賓之初筵
秦風.小戎
鄭風.清人
小雅.齣車
大雅.韓奕
小雅.鼓鍾
小雅.大東
小雅.都人士
鄘風.君子偕老
秦風.終南
附論
駟馬車中的詩思
詩之旗
詩之酒
引用文獻
後記
再版後記
詩中“物”與物中“詩”—關於名物研究(代新版後記)
《揚之水談名物》總目
圖書序言
春天還沒有到的時候,去瞭周原,沒能看見周原的美。而周原的春天是很美的 ── 曹瑋君一路都這麼說。他很長時間在周原從事發掘,現在作瞭省考古所的領導,說起周原,總還帶著感情。
但周原依然有風景。箭括嶺前,原地平衍開闊,青青淺淺一片新綠。太陽光淡淡的,岐山一道長長的影子勾畫齣周原的邊際。隻是“瞻彼中林”,“依彼平林”,漆水、沮水、西雍,詩中的河山,已不復舊日容顔。雖不至於“高岸為榖,深榖為陵”,但今天的周原,畢竟不是周人的周原。《河山集》中說,那時候的周原,包括現在陝西省的鳳翔、岐山、扶風、武功四個縣的大部分,兼有寶雞、眉縣、乾縣、永壽四個縣的少部分。而今,周原曆經河水侵蝕、切割,盡管名稱依舊,所指的範圍,卻已經很小很小瞭。
路經一道深深的原溝,這是扶風與岐山的縣界。過一個蘋果園,不多遠,便是岐山鳳雛村的西周建築遺址。遺址緊貼道邊,已經迴填,地麵上新草離離,看去像一塊撂荒的地。自文王時代、甚至更早,直到西周末年,這裏曾是一片由庭、堂、室、塾及兩廂與迴廊組成的四閤院式建築群 ── 根據建築遺跡勾畫齣來的一幅復原圖,足教人驚異。溥彼周原,曾經成熟瞭一個綿延數韆年的文明,腳踩在這樣一片沃土上,就不大有“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的曠達,也不大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悲慨,而是實實在在想尋找,尋找“天地之悠悠”的昨日之留,哪怕隻是星星點點。
扶風召陳的建築遺址比鳳雛要大,保護得也好。遺址周邊建瞭圍牆,原址同樣迴填 ── 迴填是保護,否則,經鼕曆春,冰封水潦,很快就會蕩然無存。原址的一部分地麵做瞭復原。遺址的前麵,塑瞭一個古公亶父的立像,膝前係芾,一手持龜甲,一手拄臿 ── 臿,好像是漢代的樣式。不很高的基座上,刻瞭《緜》中的幾句:“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古公亶父未必“築室於茲”,但他是在周原開拓基業的領袖人物,站在這兒,是一個很好的象徵。
一路經過齣土簋的齊傢陂塘,看見好大的一塘水。曹瑋君指點著遠遠近近的各個方嚮──美陽、劉傢、雲塘、京當,等等,都是齣土重要銅器的地方。不論周原怎樣變化,這沉埋地底的銅器,總還是依稀當年。扶風白傢村的一處青銅器窖藏,齣土微史傢族的銅器一百零三件,有銘文的,就有七十四件。著名的史牆盤,便是其中之一。盤有長銘二百八十四字,由頌揚曆代周王而說到輔佐諸臣,再說到君臣和諧纔可以得“天”佑助,最後歸結到史牆各代祖先如何臣事先王。頌揚之辭未免誇飾,但曆數文武成康昭各王業績,與《詩》《書》等先秦文獻相閤,可以互證、互補,它的重要,自不待言。
這一迴,臉對臉,看見瞭真的史牆盤。器身裏裏外外烏黑油亮,盤沿以下一圈長尾鳥紋規整秀麗,銘文字字清晰。它真真切切就在麵前,教人一時間無由馳想。而這人與物的相遇,雖近在咫尺,卻又分明橫亙著邈遠的時間和空間。隻覺得它竟接通瞭古與今的幽隔,雖然仍是幽隔,但歲月中失落掉的 ── 應該說,是氣象罷;史實,尚在其次 ── 究竟有瞭尋找、追問的一點憑藉。也許因為這相遇是在周原,是在周人的周原,所以這感覺,和在大都市博物館隔著玻璃展櫃的“參觀”,大不一樣。
同時看到的還有摺斝、師同鼎,又有黃堆齣土的一件陽燧。陽燧是祭祀的時候用來取火的銅鏡,這一件隻有手掌大的一點兒,上麵綠銹斑斑。曹瑋君說,因為銹得太厲害,沒法取火,但做瞭一件復製品作取火試驗,中心聚焦的地方不過黃豆大的一個亮點,聚光好極瞭。
還有幾塊銅餅,每塊差不多一斤重。曹瑋君說,這是製作青銅器的原料,在産地製成這種樣子,然後運瞭來,加工製作成銅器。那麼,詩中說到的“南金”,也會是這樣運來的吧。
又有一件四璜組玉佩,玉質細潤,閤瞭玉珠、瑪瑙珠、各樣玉飾,共六百件穿成長長的一串。它“消失”瞭多少代、多少世,偶然重返人間,竟然還是活生生的 ── 可以講述“佩玉將將”的故事,也可以令人想像齣“巧笑之瑳,佩玉之儺”的一點風緻 ── 因為它早把生命的因子灌注在詩裏,而詩是不曾消失的。
歸途,過渭河大橋。渭水河床不很寬,隻中心有一綫淺淺的水。
渭水和渭水的支流,是詩中最常提到的水。“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淠彼涇舟,烝徒楫之”,“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涇、渭、漆、沮豐沛的水量,曾為周原帶來一片溫潤、茂盛的綠。《河山集》中說,兩周時期的渭水,河床大約很淺,於是會有兩種景象:其一,若非河流流經峽榖之中或高峰之下,則在常水位時,河麵必然相當遼闊,水勢也必浩淼;其二,河床既淺,侵蝕的基準麵便相對抬高,河流兩側的侵蝕因此不至於十分嚴重,原麵因此能夠保持完整,因此而有麵積很大的周原、太原。
河山不總是依舊。比起來,文字的生命反倒最長久 ── 河山孕育齣來的詩,不是成為一個永遠的存在?
生命和它一樣永久的金石,可以作證。
很早就對文物有興趣,但很長時間僅僅是興趣而已。後來,承暢安先生之介,得與遇安先生識,於是可以常常請教考古學方麵的問題。先生五十年代初與瀋從文先生有過一段交往,有時會講起這一段交往中的故事。瀋先生很早便採用瞭“二重證據法”來作文獻與文物的考證,《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就是一個重要的成果。瀋先生還有一篇題作《“ 瓟斝”和“點犀䀉”》的妙文,專講《紅樓夢》“賈寶玉品茶櫳翠庵”一節中的兩件古器,卻因此揭齣文字的機鋒與文物的雙重奧義,由物的虛虛實實,而見齣人的真真假假。讀罷令人擊節。也就在這篇文章中,瀋先生希望有人結閤文獻和文物對古代名著進行研究,乃至直接提齣瞭撰寫《詩經名物新證》的課題。遇安先生說,作文獻考證和文物研究,能寫齣這樣的文章,纔是達到瞭一個高的境界,這樣的學問,纔不是死學問。瀋先生提齣來的“新證”係列,的確是一個新的角度,可是直到現在,還沒有人去做。
這“新的角度”,令人心動。從那以後,便有瞭“詩經名物新證”的醞釀與寫作,而遇安先生也因此付齣瞭大量的心血,直到付梓之前為它安排版式和賜序。
這是書稿得以完成的主要動力。而經常的談話(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授課)也總是充滿收獲的,許多想法,便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完成。
書稿涉及不止一個方麵,為瞭盡量求得準確,而拜請瞭幾方麵的專傢審閱。陳公柔、吳小如、黃永年、榖林、陳樂民、徐蘋芳、傅熹年、李學勤、王世民、陳美東諸位先生,都曾審閱瞭書稿中的若乾篇章,並且提齣瞭切實而中肯的意見。
需要查閱的資料很多,卻不是能夠容易找見,於是四處拜求師友。楊成凱、齊東方、李零、曹瑋、瀋昌文、俞曉群、王之江、陸灝、陳星燦、鍾曉青、辛德勇、姚敏蘇、蔣恆、孫歌、劉躍進、吳興文諸君,都曾給予熱情的幫助。
文學所提供瞭一方可以靜心讀書、寫作的樂土。文學所、語言所、曆史所資料室的師友,始終給予方便 ── 包括一再原諒我的“違章”,而這樣的方便,是完成這部書稿的基本條件。
寫齣第一篇《秦風.小戎》之後,便開始在《中國文化》連載 ── 劉夢溪先生始終的支持和鼓勵,是完成書稿的動力之一。
李航同誌幫助編製瞭附在書末的兩種索引 ── 在精疲力竭的最後階段,這樣的幫助,真是太需要瞭。
最後,是楊璐君的熱誠支持,書稿纔能夠以書的麵貌問世。
總之,友情是溫暖的,深厚的。而我更有一個始終可以獲得溫暖與支持的傢。我覺得,我是幸運的。
但仍然不免傷感:三年苦作,一“經”未窮,竟已皓首,沒有看見“燈火闌珊處”,卻已經“為伊消得人憔悴”瞭。
雖然近年的關注點不曾離開名物,但“走齣先秦”的確已經很久。打開電腦裏的“詩經名物新證”,其中每篇文字顯示齣來的最後修改日期都是一九九八年。因此聽到勃洋君關於重印此書的提議,不免既感且愧。感念這本小書竟然還被人記得,感念勃洋君竟不惜為此付齣寶貴的時間和精力,卻又分外慚愧對於這一課題的研究自己近年再無寸進。
這一版是否該稱作“修訂本”,是很有些猶豫的。正文的改動很少,算下來不過數十條腳註而已,卻也並沒有甚麼新的意見,多半是在寫《先秦詩文史》的時候讀《左傳》而隨手抄下來的文字,覺得有詩史互證的意趣,便夾在書頁中瞭,這一次的增補,即擇要補入瞭這一部分的內容。
近年的先秦考古頗有新材料的發現,上海博物館購藏的戰國楚竹書《詩論》更是在學界引起廣泛討論的重要文獻。然而我的精力已全部放在兩漢隋唐之後,對這一方麵的研究成果缺乏關注和思考,因此這一本再版的小書便更像是一份舊日的研究記錄而等待用新的標準來重新檢驗。這本來是最教人感覺不安的,卻又因為它是難得的求教機會而不能不特彆珍惜。
《詩經名物新證》一九九八年底交稿之後,我的讀《詩》並沒有就此結束。應友人之約,賈餘勇作瞭一本《詩經彆裁》,這本小冊子與名物研究無關,不過卻是在對《詩》之名物有瞭一定瞭解之後的貼近文學的讀《詩》,也因此更使我對《詩》懷有深厚的感情。之後一本讀書筆記式的《先秦詩文史》也是同樣的閱讀狀態。寫作這本書的時候讀《左傳》似乎讀得很認真,前幾天找齣當時讀的洪亮吉《春鞦左傳詁》,看見書的天頭地尾有不少從他書過錄來的或詮解或評述的文字,不覺又喚起昔日的一些閱讀印象,而依然能夠找迴感覺。在書中論及《左傳》的一節,我引述瞭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中的一段話:“要考察到中國古代人的傢族道德與傢族情感,最好亦最詳而最可信的史料,莫如一部《詩經》和一部《左傳》。《詩經》保留瞭當時人的內心情感,《左傳》則保留瞭當時人的具體生活。《詩經》三百首裏,極多關涉到傢族情感與傢族道德方麵的,無論父子、兄弟、夫婦,一切傢族哀、樂、變、常之情,莫不忠誠惻怛,溫柔敦厚。惟有此類內心情感與真實道德,始可以維係中國古代的傢族生命,乃至數百年以及一韆數百年之久。倘我們要懷疑到《詩經》裏的情感之真僞,則不妨以《左傳》裏所記載當時一般傢族生活之實際狀況做比較,做證驗。”“這便是中國民族人道觀念之胚胎,這便是中國現實人生和平文化之真源。倘不懂得這些,將永遠不會懂得中國文化。”我至今認為這是極好的意見。我從不以為傳統是沉重的負荷,而總覺得它是血脈,是根源,它可以予我以智慧,藉用《詩》之語,便是“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五百年間‘詩三百’,實在不能算多,但若看它是刪選之後的精華,卻也不算太少。五百年雲和月,塵與土,雖然世有盛衰治亂,但由《詩》中錶現齣來的精神則是一貫。其中有所悲有所喜,有所愛有所恨,也有所信有所望,不過可以說,健全的心智,健全的情感,是貫穿始終的脈搏和靈魂。孔子取《詩》中之句以評《詩》之精神曰‘思無邪’,真是最簡練也最準確。”“可以說,周人是開啓瞭一種智慧和開創瞭一種精神的,此中精華則大半保存在《詩》裏。源頭之水總是有著清澈的可喜和可愛,盡管這清澈未必全是曆史的真實,而也許隻是理想的真實。”──這是我寫在《詩經彆裁》中的兩段話,可以算作讀《詩》的一點點心得罷。
這本小書,我的老師和我後來都把它視作畢業論文,隻是我自己當時還沒有這樣明確的認識。在兩年前齣版的《古詩文名物新證》的《後序》中我寫道:“自一九九五年初夏從遇安師問學,至今已將近十個年頭。對老師的感激更不是幾句話可以說得盡,以《詩經名物新證》為基礎,遇安師引導我走嚮一條新的學問之路,從宏觀到微觀,無一不悉心指點。老師的學問如百科全書般淵博,我至今不敢說已經學到一枝一葉,但自信從學過程中總算逐步有瞭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這對於我來說該是最可寶貴的東西。用朋友的話說,遇到一位好老師,是求學途中最大的幸運,而我正好是一個幸運者。”時間過去瞭很久,迴首走過的路,纔更能理解老師當日指導我寫作這本書的良苦用心。
平日最喜歡引述的兩句詩,一是“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一是“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前者是對自己而言,後者是對朋友而言,今天再一次把它引在這裏,以用來寄託我的全部感念。
丙戌七月初五
代新版後記
詩中“物”與物中“詩”──關於名物研究
名物學是一門古老的傳統學科,先秦時代即已産生,此後依附於經學而綿延不絕,直到近世考古學的興起纔逐漸式微,乃至被人們淡忘。重新拾起這一名稱,是因為從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中發現,用他提齣的這一方法可以為傳統的名物學灌注新的生命。而在考古學逐步走嚮成熟的情況下,今天完全有條件使名物學成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而解決文學、曆史、考古等領域中遇到的問題。
我給自己設定的理想是:用名物學建構一個新的敘事係統,此中包含著文學、曆史、文物、考古等學科的打通,一麵是在社會生活史的背景下對“物”的推源溯流;一麵是抉發“物”中摺射齣來的文心文事。希望用這種方法使自己能夠在“詩”與“物”之間往來遊走,尋找它們原本就是相通的路徑。近年我曾在不同的場閤使用“詩中‘物’與物中‘詩’”這樣一對概念,我以為,二者原可相互置換,入手的角度不同,方法和目的卻是一樣的。
一詩中“物”:與文學的結閤
文學研究與文學史的寫作,通常是落墨於名傢和名篇(包括名傢之名篇和非名傢之名篇),亦即從藝術角度來看是屬於文學之精華的部分。但同時是否還可以有這樣一種角度,即它通過對詩(廣義的詩)中之物的解讀,而觸摸到詩人對生活細節的觀察與體驗,以揭齣物在其中所傳遞的情思與感悟,由此使得一些多半是在文學研究與文學史寫作視野之外,亦即藝術標準之外的作品(包括名傢之非名篇),彆現一種文心文事乃至彰顯齣詩意的豐沛。
相對於文學史寫作的主流,我所作的名物研究隻是旁枝細流中的一道小溪,是很邊緣化的。當然也可以說,它放在哪一個學科裏都是屬於邊緣,不論文學、史學、考古學,但它又有可能為每一個學科提供新的視角。名物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努力還原曆史細節和生活細節。或許在我們能夠洞悉古人生活細節的時候,對詩中最深刻的意蘊會理解得更加完全。
幾年前與友人閑談,說起我對“物”的關注,他說:“詠物詩的藝術性多半是不高的。”這句話使我想瞭很久,我不斷反問自己:我對“物”的關注,對於文學和文學史來說,意義何在?如果談不上藝術性,那麼作為詩,它是否還可以有另外的意義?
於是我想到應該先把我所關注的“物”與詠物詩稍作區分。詠物詩之物,是普遍之物,抽象之物,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說它通常是一個一個虛擬的話題。比如唐代李嶠、元代謝宗可、明代瞿佑等人的詠物詩。而我的研究物件,即詩文──或者更明確一點說是近年我主要關注的兩宋詩文──中的物,是個彆之物,具體之物,相對於前者,它是一個一個真實的話題。此所謂“物”,分散開來,是一個一個的點,把散落的點連接起來,便成一綫:它應該構成一部生活史細節的文學敘述史。套用一句成詞,即“詩人何為”,這裏的“為”,便是物在反覆不斷的吟詠中被賦予詩意,──在後來的明清詩文中它卻多半隻是典故辭藻和軀殼,血肉已不復存在。“物”因此以這樣一種方法被關注,被書寫,而成為文學史的一部分。詩的藝術性,固然文字、格律、節奏、意境、意象等是其要素,然而用“格物”之眼貼近文學,是否也可以成為一種研究方法呢。
二物中“詩”:與文物考古的結閤
“名物新證”的概念最早由瀋從文先生提齣。在《“瓟斝”和“點犀䀉”》一文中,他解釋瞭《紅樓夢》“賈寶玉品茶櫳翠庵”一節中兩件古器的名稱與內涵,因此揭齣其中文字的機鋒與文物之暗喻的雙重奧義。這裏的功力在於,一方麵有對文學作品的深透理解,一方麵有古器物方麵的豐富知識,以此方能夠參透文字中的虛與實,而虛實相間本來是古代詩歌小說一種重要的錶現方法。這篇文字實在應該推為名物考證的典範之作。也就是在這篇文章中,瀋從文希望有人結閤文獻和文物對古代名著進行研究,並且直接提齣瞭撰寫《詩經名物新證》的課題。而今距離這篇文章的寫作和課題的提齣,已經整整半個世紀。檢點我們這方麵的成績,不能不說是太少瞭。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我初從孫機遇安先生問學,遇安師命我把這篇文章好好讀幾遍,說此文本身便是“名物新證”的範本。同時又擬瞭兩個題目,即“詩經名物新證”與“楚辭名物新證”,要我選擇其一,我選擇瞭前者。《詩經名物新證》一書完成之後,我在後記裏曾寫下這一經過,不過當時還隻是剛剛入門,對“名物新證”的概念實在還沒有形成自己的認識,比如,為甚麼要重新起用“名物”一詞;“新證”之“新”究竟在何處;新的名物研究與古器物學又有哪些不同。
逐步有瞭一點想法,是在寫作《古詩文名物新證》的過程中。在此書的後序中我大緻總結瞭自己所作名物研究的基本方法,並且談到瞭研究中經常思索的幾個問題。
“名物”一詞最早齣現在《周禮》。《周禮》所作的工作便是用器物和器物名稱的意義構建禮製之網,它因此為後世的名物研究奠定瞭基礎,確立瞭基本概念,宋代金石學也正是在這一基礎上,以當代情懷追溯、復原乃至編織遠古曆史。
關於名物和名物研究的方法與曆史,日本學者青木正兒在《中華名物考》的《名物學序說》部分有一番簡明扼要的論述。即第一是作為訓詁學的名物學,它以《爾雅》、《小爾雅》、《廣雅》為主綫,此外又有性質相近的《方言》等,共同構成名物研究的訓詁學基礎。第二是名物學的獨立。以《釋名》開其端,以後又有從詩經的訓詁中獨立齣來的名物研究,再有從《爾雅》分齣來的一支,如《埤雅》、《爾雅翼》、《通雅》。第三是名物學的發展,它的研究範圍也在發展過程中逐漸確立,大緻說來有如下內容:甲,禮學;乙,格古(古器物);丙,本草;丁,藝植;戊,物産;己,類書(如《清異錄》《事物異名錄》《三纔圖會》)。第四,作為考證學的名物學。即特彆把經學中的名物部分提齣來,用考據的方法進行研究,並為之作圖解,如江永《鄉黨圖考》。若作分類,可彆為數項,如:甲,衣服考;乙,飲食考;丙,住居考;丁,工藝考。可以說,第四項主要是清代學者的貢獻。這裏列舉的四項基本概括瞭傳統名物學的主要內容,而古器物學也在其中構成瞭內容的一部分,其實它是可以獨立成軍的。
關於古器物學,李濟《中國古器物學的新基礎》一文所論甚詳,不僅分析得很透徹,而且給予瞭公允的評價。對於宋哲宗元祐七年完成的《考古圖》,他的意見是:“這部書的齣現,不但在中國曆史上,並且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件瞭不得的事件。在這部書內,我們可以看見,還在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史學傢就能用最準確的方法,最簡單的文字,以最客觀的態度,處理一批最容易動人感情的材料。他們開始,並且很成功地,用圖像摹繪代替文字描寫;所測量的,不但是每一器物的高度、寬度、長度,連容量與重量都紀錄下瞭;注意的範圍,已由器物本身擴大到它們的流傳經過及原在地位,考訂的方麵,除款識外,兼及器物的形製與文飾。”而古器物學八百年來在中國所以未能前進,“就是因為沒有走上純理智的這條路。隨著半藝術的治學態度,‘古器物’就化為‘古玩’,‘題跋’代替瞭‘考訂’,‘欣賞’掩蔽瞭‘瞭解’”。“這八百年的工作,好像在沒有填緊的泥塘上,建築瞭一所崇大的廟宇似的;設計、材料、人工,都是上選;不過,忘記瞭計算地基的負荷力,這座建築,在不久的時間,就顯著傾斜、捲摺、罅漏,不能持久地站住。”不過接下來作者乃把考古學作為古器物學的延續,這恐怕是當今考古學界所不能同意的。
三我所作的“名物新證”
(一)現在可以來討論名物研究的古今不同。關於“古”,即如前引青木正兒之說。而今天的所謂“名物研究”,就研究物件而言,與“古”原是一脈相承,我把它明確為:研究與典章製度風俗習慣有關的各種器物的名稱和用途。說得再直白一點,便是發現、尋找“物”裏邊的故事,──這裏用的是“故事”的本意。它所麵對的是文物:傳世的,齣土的。它所要解決的第一是定名。定名不是根據當代知識來命名,而是依據包括銘文等在內的各種古代文字材料和包括繪畫、雕刻等在內的各種古代圖像材料,來確定器物原有的名稱。這個名稱多半是當時的語言係統中一個穩定的最小單位,這裏正包含著一個曆史時段中的集體記憶。而由名稱的産生與變化便可以觸摸到日常生活史乃至社會生活史的若乾發展脈絡。第二是相知。即在定名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此物在當日的用途與功能。它要求我們有對藝術和藝術品的感受力,能夠從紋飾之細微去辨識氣韻和風格,把握名與實發生變化的因素,變化因素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不妨認為,文物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過程可分作兩部,其一是作為原初的“物”,即在被使用著的時代,它一麵以它的作為有用之物服務於時人,一麵也以裝飾、造型等愉悅時人的審美目光;其一是“文”物。即“物”本身承載著古人對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營造,亦即“文”。作為“名物新證”,它應以一種必須具有的曆史的眼光,辨明“文物”的用途、形製、文飾所包含的“古典”和它所屬時代的“今典”,認齣其底色與添加色,由此揭示“物”中或凝聚或覆蓋的層層之“文”。同樣是以訓詁與考據為基礎,新的名物研究與舊日不同者在於,它應該在文獻與實物的碰閤處,完成一種貼近曆史的敘述,而文獻與實物的契閤中應該顯示齣發展過程中各個時段的變化,此變化須有從考古學獲得的細節的真實與清晰。
迴過頭再來看古名物學和古器物學。如果為二者作一個並不完全準確的區分,那麼可以說,名物學是持“名”以找物,古器物學是持“物”以找名,名與物的疏離處是二者各自的起點,名與物的契閤處則是二者最有意義的殊途同歸。而新的名物研究便是從這兩個傳統學科中生長齣來,復由考古學中獲得新的認知與新的方法,──不僅僅是考古材料,而更在於考古學所包含的種種科學分析。
總之,“名物新證”所追求的“新”,第一是研究方法。融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於一身的考古學異軍突起,為名物學的方法革新賦予瞭最為重要的條件。第二是研究層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內涵的豐富。由單純對“物”的關注發展為“文”、“物”並重,即注重對“物”的人文意義的揭示與闡發。也就是說,與作為母體的傳統學科相比,今天的名物研究應有著古典趣味之外的對曆史事件和社會生活的關照。雖然它的視野裏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細節,因為弄清楚一器一物在曆史進程中名稱與形製與作用的演變,自然是關鍵,而若乾久被遮蔽的史之幽微,更應該是研究過程常有的發現。一葉障目不可取,一葉知鞦卻可以也應該作為“名物新證”的方嚮與目標。
(二)我本來研究的是文學,因此尚須迴過頭來,看一看名物研究究竟能夠為文學做些甚麼。
詩,當然也包括文,有各種各樣的讀法。賞其纔思,賞其韻緻,是一種;解讀與詩相關的故事,亦即求索其“本事”,也是一種。《唐子西文錄》:“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餘時年十八,謁之。問餘:‘觀甚書?’餘雲:‘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餘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蓋如此。”斷章取義藉用這裏的一點意思,則讀詩讀文隻留意於其中的“好亭子名”,也可以算作一種讀法。
我所涉及的古詩文,以宋詩佔得多數。討論宋詩的風格與特色,自是大題目,前修與時賢早作瞭很多工作,更有齣色的成就。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整理齣版的《全宋詩》,更為細緻的檢閱提供瞭極大的方便,其中雖有若乾疏失,但它畢竟提供瞭比較可靠的綫索與依據,而這樣一個詩的世界,也使人更有條件從廣闊的範圍,亦即宋人之詩,而不僅僅是詩人之詩的一個相對狹小的範圍,對兩宋詩重新審視。
以文為詩,為宋詩特點之一,詩因此變得輕易和平常。語言和風格的變化,使詩可以承載更多的平凡,它因此打破瞭詩歌成熟期所造就的精緻,而另外擴展瞭它的敘述功能。衣食住行,拈來即成詩材,以入世的精神求齣世的心態,以平等的心情與群物相“爾汝”,便可以在日用常行中體味生命。平易的敘述在日常生活的錶麵輕輕撫過,卻啓動瞭其中本來具有的詩性的品質,而詩意便多建立在對生活細節的關注和品味,對尋常事物的牽掛和愛惜。宋人對陶淵明的偏愛以及對他所作的種種當代詮釋,也可以從這一角度去理解。如果做一個並不全麵的概括,那麼大緻可以說,宋詞是以細膩柔軟的基調容納情的深婉,宋詩是以質實清勁的風格容納事的微至。文友止庵君寫過一篇文章,題為“體味不復存在的語境”。藉用這句話,我想說,理解宋詩,迴到“不復存在的語境”也是方式之一,即這裏不是從詩學角度探討詩人之詩,而是欲求解讀宋人之詩或曰士人之詩中所包含的生活之真實、生活狀態之真實,亦即藉助於名物研究,而復原“不復存在的語境”。如果稱之為“物質文化背景”,顯然太大,那麼以把它縮小為生活細節為宜。“風微僅足吹花片,雨細纔能見水痕”,一切都是微細的,但微細中原有它的深廣。在落花處駐足,也許可以捕捉到微風傳送來的一點消息。某一具體問題時首先要做的工作,然而它常常隻能是理想中的標準,我所讀到且可以方便利用的仍不過是一些最為常見的書。小中見大,本來是考證應該達到的境界,而在我,同樣也隻是成為嚮往。
四關於本書以及《揚之水談名物》
(一)《詩經名物新證》是我從遇安師問學邁齣的第一步,草就的第一則文字是《說〈秦風.小戎〉》。得到老師首肯之後,經李陀兄推薦,為劉夢溪先生所賞識,不僅很快刊發,而且竟在之後的同一期中破例刊發三篇。文章結集後初版於二〇〇〇年(北京古籍齣版社),再版於二〇〇七年(天津教育齣版社)。
本世紀初年以來,我的關注點就轉移到“三代”以下,因此至今仍如《再版後記》所說,數年來對詩經名物的研究成果缺乏關注和思考,這一本以不同形式兩番重版的小書,便總是如同一份舊日的研究記錄而等待用新的標準來重新檢驗。除瞭對我個人學術生涯的重要意義之外,也許它的價值僅在於,這是瀋從文先生“詩經名物新證”之倡議的第一個迴應者。
(二)一九九一年初夏,小書《棔柿樓讀書記》(署名宋遠)交稿之後,負翁先是提議,繼而相約,然後引領我同往啓功先生傢求題簽。那一日,啓功先生不僅題寫瞭書名,且又題瞭“棔柿樓”三個大字的橫匾,自己的第一本書,得有如此因緣,自是分外珍惜。
倏忽過去瞭二十多年,棔柿樓依舊,此中讀書依舊,讀書有得之“記”也是依舊的日課,於是成此一編,它是“全職”讀書十八年的一次自我總結,當然它也是“棔柿樓讀書記”的續集。而這六個字可以概括已經逝去的時光;未來的若乾年,這樣的讀書生活,又何嘗不是理想。
隻是以“揚之水談名物”為這一編命名,似乎太過自信,然而這樣的自信卻完全沒有驕人之意。如本書開捲之篇中所說,在我寫作《詩經名物新證》的時候,名物研究作為一個專題乃至一種研究方法,尚處在近世以來久被冷落的狀態,因此正是這種自信,使我始終覺得是選擇瞭一個很有意義並且很適閤自己興趣的研究方法,而能夠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治學途中行走二十年。時至今日,名物研究已經可以算是自己的一個標誌性的治學特色。不過,二十年的實踐,結果究竟如何?自我期許的對“物”的“定名”與“相知”,是否可以成立?實有待於讀者的檢驗。
《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喜歡此中的嚮學之意,也一嚮把它視作一種讀書狀態或曰境界。“慨我懷慕,君子所同”,誠願此生與書、與讀書、與讀書人結緣。
圖書試讀
一、關於詩經名物研究
二、詩與詩學的建立
三、從“西土”到“中國”
四、周之“南國”與“二南”
五、曆史中的細節
一、關於詩經名物研究
首先要說,這本書雖然以名物考證為題,其實並不僅僅局限在名物考證之內。這裏偏重的,是用考古材料 ── 主要是科學發掘而獲得的成果,證史、證詩。用瞭“名物”一詞,是錶明它仍從傳統中來;而所謂“新證”,則申言它與傳統的名物研究並不相同。
名物考證,自來是詩經研究中一個重要的方麵。所謂“六經名物之多,無逾於詩者,自天文地理,宮室器用,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靡一不具,學者非多識博聞,則無以通詩人之旨意,而得其比興之所在”(納蘭成德《毛詩名物解.序》)。而前人所說“詩經名物”,又多指草木鳥獸蟲魚而言。孔子最早提齣“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爾雅》之《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則為名物詮釋之宗。此後遂有詩經名物研究中的“博物學”一係,乃專以“多識”為務,考校詩中草木鳥獸蟲魚之名,記述異聞異稱,此中以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為最古,後世治名物者多從之。至清,此學乃成其大,著述更較曆代為多。該洽者,當推姚炳《詩識名解》和多隆阿《毛詩多識》,而圖文並茂的兩部名著,則是徐鼎《毛詩名物圖說》和日人岡元鳳的《毛詩品物圖考》。徐氏教學為業,而自幼用心詩經名物;岡元鳳則以醫為業,精於本草,但兩傢都很注重實踐,並且頗有實事求是的精神。比較而言,徐圖的文字說明更詳細一些,即所謂“博引經、傳、子、史外,有闡明經義者,悉捃拾其辭”(《發凡》)。而就圖的工緻與準確來說,則徐氏稍遜。總之,這兩本書可以說是這一類題目中總結性的著作瞭。
用户评价
**初探《詩經》的物質世界:一次令人驚喜的考古之旅** 作為一個從小就對中國古典文學懷有濃厚興趣的愛好者,我對《詩經》的嚮往由來已久。然而,長久以來,那些古老而優美的詩篇,對我而言,更多的是一種抽象的意境和文字的魅力,至於詩中描繪的物件、動植物、地理環境等等,總感覺隔著一層朦朧的麵紗,難以清晰地感知。《詩經名物新證》的齣現,恰恰彌補瞭這一遺憾。我一直很想知道,那些在詩歌中反復齣現的“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究竟是何種景象?“蒹葭蒼蒼,白露為霜”,鞦日蘆葦的真實形態又是如何?而“采薇采薇,薇亦柔止”,那古人眼中“柔止”的薇菜,究竟是何般模樣?這本書,沒有直接告訴我這些詩句的“意義”,而是通過一種更加具象、更加實證的方式,帶領我一步步走進《詩經》所處的那個物質世界。我尤其欣賞作者那種嚴謹而又不失趣味的考證方法,它不僅僅是簡單地列舉名物,而是將文獻記載、考古發現、植物學、民俗學等多方麵的證據巧妙地結閤在一起,構建齣一個立體而生動的圖景。讀著讀著,仿佛穿越時空,親眼目睹瞭先秦時期人們的生活場景,感受到瞭他們對自然萬物的細緻觀察和深情描繪。這種“眼見為實”的閱讀體驗,讓《詩經》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鮮活的生命,充滿瞭生機與活力。
评分**細節中見真章:撥開迷霧,重塑《詩經》的物質世界** 閱讀《詩經名物新證》的過程,對我來說,就像是在一片迷霧中跋涉,而這本書則是一盞明燈,不斷地為我撥開層層迷霧,讓我得以窺見《詩經》原本的物質世界。我一直覺得,《詩經》之所以能流傳韆古,不僅僅在於其優美的語言和深刻的思想,更在於它所描繪的那個生動、真實的生活場景。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古代的名物,在我們現代人的眼中,變得越來越模糊,甚至消失瞭。我們很難準確地知道,“伐柯如何?匪斧不剋”中的“柯”究竟是怎樣的木材,“坎坎伐輻,置轢於林”中的“輻”又是何物。這本書,就是一本“尋根問源”的百科全書。它沒有空談理論,而是從最具體的“物”入手,通過對文獻、考古、實物等各類證據的細緻分析,為我們一一揭示瞭這些“名物”的真實身份。讀這本書,我不再是站在岸邊遙望,而是仿佛置身於詩歌描繪的場景之中,與古人一同勞作,一同生活。這種“細節還原”,讓我對《詩經》的理解,不再是隔靴搔癢,而是觸手可及,充滿瞭畫麵感和生活氣息。
评分**穿越時空的感官體驗:沉浸式解讀《詩經》的田園牧歌** 在閱讀《詩經名物新證》之前,我對《詩經》的理解,大多停留在文本的字麵意義和後人的解讀之上。總覺得,詩歌所描繪的田園風光、生活習俗,離我太過遙遠,隻可意會,難以言傳。而這本書,卻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將這種“意會”轉化為一種“感官體驗”。它不是直接告訴我“這是什麼”,而是通過詳實的考證,讓我“看到”瞭它,甚至“聞到”瞭它。比如說,關於詩中描寫的“芣苢”,作者不僅僅給齣瞭植物學的鑒定,更通過對采摘工具、食用方法等細節的描述,讓我仿佛親手抓起一把芣苢,感受它在指尖的觸感,想象它被烹飪後的味道。又如,對詩中提及的各種禽鳥,不僅僅是簡單的辨識,而是結閤其鳴叫聲、棲息地、遷徙習性等,讓我能更具體地想象它們在詩歌中的“存在感”。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讓《詩經》中的一草一木、一蟲一鳥都變得鮮活起來,仿佛就在我眼前跳躍、歌唱。這種從微觀的物質細節齣發,最終勾勒齣宏大時代背景的敘事方式,令人耳目一新,也讓我對《詩經》的理解,上升到瞭一個全新的維度。
评分**超越文本的閱讀:《詩經》的“實感”重塑** 在我看來,《詩經》是一部充滿生活氣息的詩歌總集,但很多時候,我們對它的理解,都停留在文本層麵,缺乏一種“實感”。《詩經名物新證》這本書,恰恰給瞭我這種難得的“實感”。它沒有停留在對詩句的解讀和情感的抒發,而是將目光投嚮瞭詩歌背後那個物質化的世界。我一直很好奇,那些在詩中齣現的器物,比如“其器維何?有簋、有簠”,它們到底是什麼樣子?它們的功能是什麼?又比如,詩歌中描寫的各種服飾、工具、建築,在現實中又是如何運作的?這本書,就如同一本“考古日記”,將這些隱藏在文字背後的物質信息,一點一點地挖掘齣來。作者的考證過程,本身就是一場精彩的“探案”。他搜集各種古籍文獻,對照考古發掘的實物,甚至會結閤現代的民俗學知識,層層剝繭,最終為我們呈現齣一個個鮮活的名物形象。這種從“物”到“意”的迴歸,讓我感覺,《詩經》不再是遙遠的古籍,而是我生活中觸手可及的存在。這種“看得見、摸得著”的閱讀體驗,極大地增強瞭我對《詩經》的親近感和理解深度。
评分**跨學科的智慧碰撞:《詩經》研究的創新視角** 作為一個對學術研究略知一二的讀者,我一直關注著《詩經》研究的動態。《詩經名物新證》這本書,給我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其高度的跨學科性和研究的創新性。傳統上,對《詩經》的研究,往往側重於文學、曆史或語言學層麵。然而,這本書卻大膽地將考古學、植物學、動物學、民俗學,甚至地理學等領域的知識融會貫通,為《詩經》名物考證開闢瞭新的道路。我非常欣賞作者在處理那些古代文獻中模糊不清的名物時,所展現齣的那種“偵探式”的嚴謹和敏銳。他不會輕易下結論,而是窮盡各種可能的研究方法,細緻入微地搜集證據,層層推理,最終得齣令人信服的結論。例如,在考證某個植物的身份時,他可能要比對古籍的描述,查閱現存的植物誌,還要參考考古齣土的實物,甚至會去考察當地的生態環境。這種“庖丁解牛”式的精細研究,不僅讓“名物”本身得以“正名”,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們看到瞭一個更為真實、更為立體的先秦社會圖景。這種多角度、多維度的研究方式,不僅極大地豐富瞭我們對《詩經》的理解,也為其他領域的學術研究提供瞭寶貴的藉鑒。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