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書描述
這就是我遺書的全部。我想說,在你們的曆史上存在過這樣一個人。
再見。
在我心中,
一個人被殺是因為他值得被殺。
丁允恭(作傢,高雄市新聞局局長)◎專文撰序
我覺得有一把彈簧刀,事情就會有一種儀式感。
我將它藏在包裏,走過人群,不一會兒就忍受不住誘惑,將手塞進包裏,按起按鈕。
嗒,它彈齣去,嗒,它收迴來。
我感到眩暈,我是死神,可以隨時決定這些路人的生死,而他們隻能將之歸結為偶然。
大考前夕,十九歲的少年殺瞭一個美麗優秀的女同學,總共三十七刀。
不為錢財,不為性侵,沒有仇恨,理由僅因那份讓他再也無法呼吸的、生而為人的無聊。可怖的是,他連一點點歉意也沒有。
《下麵,我該乾些什麼》是根據2006年的一件「無理由殺人案」進行的一場文學演算,這也許我們看過最勇敢的小說。它與《麥田捕手》猶如一枚硬幣的兩麵:一麵犀利、深刻,直麵現實;一麵傷感、憂鬱,留有希望。比起沙林傑的感傷,阿乙顯然更加勇敢。
小說以第一人稱自述,從作案的籌畫、實施、逃亡、被捕、受審,一氣嗬成,教人屏息。活著的意義究竟何在?阿乙藉由此書對現代社會的人類生存本質拋齣瞭大哉問;他以一貫的犀利冰冷,逼迫眾人正視自身內在最難以自處的部分,令人如坐針氈,他更以此作嚮法國存在主義大師卡繆的《異鄉人》緻敬。
本書重點
◎繼《鳥看見我瞭》、《模範青年》等精彩短篇之後,阿乙首度推齣的長篇作品,在微博上引起眾多讀者討論,甚至與阿乙直接對談!
◎二十世紀中期,法國存在主義大師卡繆藉由《異鄉人》一書,探討瞭現代人在強大的現實威迫之下,生存意義和存在感都變得極端稀薄和虛無的狀態;而阿乙也因一起「無理由殺人案」的標題,引發瞭寫作《下麵,我該乾些什麼》的念頭。在當今二十一世紀,人心更加乾涸,人們皆受睏於巨大的疏離感與渺小的自我價值感,此書是阿乙嚮卡繆緻敬之作。
精彩摘錄:
我覺得有一把彈簧刀,事情就會有一種儀式感。我將它藏在包裏,走過人群,不一會兒就忍受不住誘惑,將手塞進包裏,按起按鈕。嗒,它彈齣去,嗒,它收迴來。我感到眩暈,我是死神,可以隨時決定這些路人的生死,而他們隻能將之歸結為偶然。但我得挑選。在我心中,一個人被殺是因為他值得被殺。我覺得這些人都不太閤適。
我們像兩棵樹、兩根木棍那樣擦肩而過,而我心知,我是殺過你的,隻是你不知道而已。
我捫心自問,在這世界與誰也沒有約定,如果非得算上一個,那就是自己。
我和他,我們都像是自己不得不承受的垃圾,我們沒有一天不渴望天空的飛機停下來,好甩齣繩梯,將我們撈走,帶我們去一個充實的地方。甚或那地方一點自由沒有也可以。但是什麼奇蹟也沒發生,我們不得不繼續忍受著時間。
有幾次我試圖問什麼時候可以開始,但這樣很操蛋。就像女人不能對罪犯說,你什麼時候可以強姦我啊。
此時讓我耿耿於懷的倒不是窗外自由的天空,而是在青山被捕的時刻。
那時我完全可以推倒刑警,奪路狂奔,撿起石頭或菜刀傷害行人,如此便可被當場擊斃。而現在我卻不得不獨自麵對龐大的時間。人世間所有的事情,行路、勞動、戰爭、求歡,都是阻擋肉身與時間直接接觸的屏障,但在我這裏,在這間無所事事即使有點事也會很快辦完的狹小牢房裏,我總是清晰地看著時間張大臂圍走過來。它孔武有力、無懈可擊、無所不在,沒有任何肉身都會有的情感,它既不會聽你的求饒,也不看你的哀傷,它就像是不停砸下的泥石、不停湧來的浪潮,塞滿整個房間,淹沒你,淩遲你,它淹沒你讓你感到全身被重量重壓時它是囫圇的,它割殺你它像竹簽一樣釘進你的指甲時它又是淩厲的。它讓你無法抵抗,讓你極緩慢地死亡。
著者信息
阿乙
本名艾國柱,一九七六年生於江西。擔任過警察、祕書及編輯。作品發錶於《今天》、《人民文學》、《收獲》及《GRANTA》雜誌。曾齣版短篇集《灰故事》、《鳥看見我瞭》、《春天在哪裏》,小說《下麵,我該乾些什麼》、《模範青年》,隨筆集《寡人》。
《模範青年》、《鳥看見我瞭》中文繁體版已由寶瓶文化齣版。
小說作品曾獲:
二○一二年,首屆林斤瀾短篇小說奬。
二○一二年,《人民文學》「未來大傢TOP20」。
二○一二年,颱灣《聯閤文學》「二十位四十歲以下最受期待的華文小說傢」。
二○一二年,華語文學傳媒大奬最具潛力新人奬。
二○一一年,《東方早報》文化中國年度人物。
二○一一年,《人民文學》年度青年作傢。
二○一一年,《南方人物周刊》中國青年領袖。
圖書目錄
開始
前奏
準備
行動
實施
逃亡Ⅰ
逃亡Ⅱ
逃亡Ⅲ
結束
審訊
遊戲
坐監
判決
上訴
庭辯
告白
【後記】一個作者,還是一個正義的作者
圖書序言
殺與逃的雙股螺鏇
丁允恭(高雄市新聞局局長、作傢)
關於這本書,首先,我們要談的,當然就是「殺人」。
阿乙問說:「下麵,我該乾些什麼?」於是,我們要問:那Meursault(編按)走瞭以後又怎樣?
那是《異鄉人》裏麵,在母親的喪禮之後、焦燥乾渴的刺眼日光之中,因為輕率的誤解而殺死瞭阿拉伯人的男子。後來我們都知道瞭,他百無聊賴,他麻木不仁,對一切都滿不在乎,連辯解都不屑為之,所以自構瞭荒謬的末路。存在主義的年代,不為瞭什麼而做些什麼,意義的一再削減,終至虛無;這虛無也成為一麵鏡子,反身看到無所依附的自己,成瞭一代文青的流行,這是大傢都知道的。
然而在開放槍枝持有的美國州份、一次次的校園槍擊事件後,在貼上禦宅標簽的鞦葉原隨機刺殺事件後,當然,也在颱北捷運令人悲傷的殺人事件之後,關於種種的「無意義殺人」,全都因為難以理解,而被反覆討論著。
異鄉人裏頭這樣高蹈的哲學,抽象的關於存在的反省,卻沒有辦法滿足我們對於每一個具體殺人案件裏麵,種種庸俗而真摯的好奇心。
Meursault縱然無賴,卻也稱不上可惡,關於那些真切地可惡著的人們,又或者所有那些擁有著「汪洋大的殺意、鼻屎大的動機」的人,他們到底在想些什麼呢?
對於這些無意義的殺人,我們還需要更現世的說法。
於是,我們有車載鬥量的通俗犯罪小說,也有像村上龍的《寂寞國的殺人》這樣的社會評論;也於是,阿乙在目睹瞭學生殺人的社會事件以後,寫齣瞭這本《下麵,我該乾些什麼?》。
就殺人者的主觀意誌而言,「殺人」常常是他們與世界對話的手段,可是在無意義殺人的情境下,殺人作為一種說話,通常是沒有對話基礎的對話。沒有對話基礎,我們又如何談論下去呢?
我們的社會,習慣於簡單的答案,與復雜的儀式,對於這些殺人事件,我們往往以死刑等手段作為迴應,然而對於並不畏懼死亡的人,這樣的迴話往往隻能讓他們冷笑,甚至對他們的惡我們也無從真正懲罰。這種無奈的情境,或許隻好交給小說傢以細緻的筆法來摸索,找齣真實對話的稀少可能齣來。
迥異於Meursault的漠然,阿乙的兇手充滿瞭獨白,然而這樣的獨白,雖然對於真實事件中那些謀殺者的模擬未必精準,卻是跟讀者最交心的對話。
在殺人以外,就是「逃亡」。
花瞭生平裏麵許多時間擔任犯罪追獵者 ── 警察的阿乙,決定採取被狩獵者的視角,展開一場逃亡之旅,也讓「逃亡」成為無意義殺人的意義所在,讓主角從殺人者的狩獵角色,轉置為被追捕的獵物角色。
逃亡本身就「不是」什麼,而並非「是」什麼。一場逃亡,就像是一隻不斷掙脫著自己舊皮的毒蛇一般,把過去所有拋諸腦後。「逃」也是常見的主動機,隨著情節的發展,它構成瞭一部公路電影,或甚至是一場RPG遊戲,不論基於道德感受使我們對逃亡者多麼厭惡,我們卻也不得不對他做齣投射與同情,也讓整個閱讀的過程成為兇手的從犯。在逃亡的過程中間,載荷瞭沿途的風景,也豐富化整個蒼白的犯罪故事,更因為拉長展延的時間軸,讓一切有機會在敘事中被反芻消化。
在阿乙的手下,逃亡本身也是匪徒對警察、對政府,乃至於整個體製的嘲笑方式,更與「殺人」所構成的挑戰互為呼應。逃亡的成功,讓體製自己所號稱的效能,因為本身的臃腫龐大,或是年久失修,而完全失靈故障。然而在這淺層的譬喻之下,更是挑戰一整個使我們感到安逸釋然的社會係統,原來所有那些我們以為足以保護我們的機製並不可靠,當然他們日常如同匪徒一般的行徑就更不在話下。
就在殺人與逃亡之間,交雜齣這部作品的雙股螺鏇,敘事在其中纏繞嚮前。我們小說的主人翁,透過冷血無恥的殺人,與大逃亡曆程的構思與實行,也幾幾乎就要反嚮地英雄化瞭起來。我們不禁也會猜測,或許這也是阿乙對自己未必情願的警察生涯,一種漫不在乎的嘲笑?
然而或許是對更多事物一種更為廣泛的巨大嘲笑。
後記
一個作者,還是一個正義的作者
阿乙
現在迴想這篇小說的寫作曆程,有如夢魘。它作為欲望的斑點,誕生於二○○六年夏,我看到一則簡短報導:一位年輕人殺死同學,沒人能找到他的殺人動機。當時我和文學的關係很簡單,隻是一個普通讀者。
我和很多事物擦肩而過,料想這報導也如此。但在幾個月之後,我發現它自行變大,成瞭一個可怖的世界。我每天都裝載著對它的龐大理解和無窮編造,就像背負重物。二○○七年春節,我沒有迴鄉過年,試圖將它産下來,但隻寫齣十五節。當年五一,續寫兩節,國慶時又加瞭一節,但被迫停手。因為寫作間隔時間太長,文本前後掣肘,互相矛盾,而詞句也因時間將盡而顯得倉促淩亂。當時它叫《殺人的人》,有八萬字左右,計畫總長度為二十四萬字。因為這個,後來我隻敢寫短篇。一些人還以為這是一種文學上的自覺選擇。
我差不多忘瞭它。直到二○一○年,在倒騰櫥櫃時看見材料,纔想起還有這一遭。我想到自己如何盡力搜集資料,如何曠日持久推算,如何試圖去法庭旁聽,如何鑽研卡繆、杜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的三部著作——我想到這些狂熱的準備,以及它的草草收場,便被一種恥辱感緊緊包圍,就像一個窮人生不起孩子。
我想從頭來過,而生活中彆的事情也按照它的軌道運行過來,擠成一團。在祖母下葬的同時,我按照父親要求,購買新房,準備結婚。而因為寫作所帶來的對生活的敵意,我與女友的關係其實已走到盡頭。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我看著世界盃報導的加班錶,哀楚欲死,感覺就像遊泳好手要將自己溺斃,「好,我陪你們去生活,陪你們買房、結婚、加班。」我像睏獸憤怒行走,最終做齣的卻是相反的選擇。今天看來,這個選擇沒有辜負我,但相比《月亮與六便士》裏的思特裏剋蘭德,以及不少狂熱的朋友,我還是缺少齣格的勇氣。他們都曾為創造的理想辭職,而我隻是命令自己無論如何也要開始。我容易在妥協狀態裏生存。我在開始時打上這天的記號,後來纔知在四年前,同樣是這一天,主人公的原型受激情驅使,舉起屠刀。這是一種可怕的巧閤。
最終因為我的專橫霸道,我和女友分手,每天早上六點多起床上班,傍晚八點多迴傢,我總是試圖在網站工作中保護住精力,但每次迴來都氣息奄奄,一個字也寫不動。然後我等週末。在週六,我會因為要找到續寫感覺而苦苦推敲,因此最終隻剩下周日能暢快地寫幾韆字。在這過程中,平均每三天,父親都打電話來,以商量的口吻問:「找女朋友沒有?」我每次都心藏怒火。我想說:「正因為你想讓我結婚,我有瞭一間房子;正因為要還月供,我不敢輕易辭職、跳槽;正因為這狗日的工作,我每天被消耗一空。」
有一天接過父親電話後,我翻開電話簿,找到一個自認妥當的人,發短信:我喜歡你。她和我進行瞭接觸,但是猶疑。對女人來說,這種緊迫的求愛不但值得懷疑,還值得鄙視。在見到她後我笨手笨腳地抱她,被掙脫開,這事情就完瞭。後來父親問我如何,我說高攀不起。聽得齣來他很悲哀。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這篇薄薄的小說終於修改完畢。當時是下午,窗外鋪陳死氣沉沉的建築物、冰塊、樹和時光,我一人呆坐,不知悲傷應該從哪裏來。我有一個朋友在寫完長篇後嚎啕大哭,我覺得我也應該這樣,但一直沒等來。我對自己很失望。當夜我失眠,恐懼像大風不停颳進空洞。我害怕這一切都是在做無用功。
後來我齣門去談戀愛,換瞭兩次工作,並還清欠義人的房款。
這篇小說標題(原名)為〈貓和老鼠〉,偏近於對故事的解釋,喻示的是互動關係中的位置與使命,一個窮凶極惡地追,一個沒日沒夜地逃。小說的主人公在被無聊完全侵蝕後,再也找不到自振的方法,因此殺人,試圖贏得被追捕所帶來的充實。想一想這場景:就是要睡瞭,也要在指間夾一根燃燒的香煙,好在煙頭燒到皮膚時醒來,繼續逃命。(而「該乾些什麼」偏近於對一種狀態的解釋,偏近於象徵)。小說可用一句話概括:因為太無聊,並無法依靠自己解決這種無聊,主人公決定犯罪,與員警玩你追我趕的遊戲。它取材於新世紀後發生的一起真實案件,在闡述犯罪動機時,當事人神神叨叨,看起來像是用瘋子的語言與外界交流。直到死刑執行,真相也沒齣來。但他成為一隻籮筐,將很多專傢、媒體、讀者的解釋都裝瞭進去,他們為著維護自己的利益、職責、良心還有可能是粗淺的見識,將他解釋成他們想像中的樣子,或者說是想要的樣子。我在其中之列。我想他就是因為無聊。
我想提醒一下,這裏所說的無聊是個重要問題,是每個人都可能遭遇的問題,而不是我們對彆人的街談巷議(不是一種吊兒郎當)。它甚至可以被解釋為無助。如果有上帝,那麼它也應該成為上帝同情的一種遭遇。
我將他設置為一個純粹的人。就像電影《計程車司機》裏的特拉維夫,他的子彈注定要射齣,至於射死的是總統候選人還是黑社會,他並未深究,他隻是需要子彈射齣。他並沒有先天的善惡動機,隻是在效果上,他不能殺死總統候選人而可以擊斃黑社會成員,因此被捧為城市英雄。
而我的主人公,他的行動為世人不齒,他們集體呼喊:
殺死他!
殺死他!殺死他!
殺死他!殺死他!殺死他!
在原初的動機上,我的主人公一心隻想著「如何充實」,殺人隻是這一動機的外延。我著重探究的是這一動機。從動機上看他和過去的我並無區彆,很多年我都渾渾噩噩,無所事事,每天盼望世界大戰。隻是我止於語言,而這個主人公卻付諸行動。他設想過頻繁地做好事,好讓受恩人去搜尋他,但他想這樣的搜尋注定鬆弛、鬆散,從技術上並不能使他充實。因此他去當瞭惡棍。在殺那個漂亮、善良、充滿纔藝的女孩時,他考慮的也是技術,因為殺掉一個完美的人,會激怒整個社會,進而使追捕力度增大。
寫作時我很平靜。我從來不贊美也不認同這種行為,但也沒有急不可耐或先入為主地對它進行審判。因為一個作者一旦將自己設置為正義的化身,他的立場便可能偏頗,思想便可能空洞,說教便可能膚淺,所揭示的也可能為人們所麻木。在這方麵,我遵循卡繆的原則,像冰塊一樣,忠實、誠懇地去反映上天的光芒,無論光芒來自上帝還是魔鬼。
但最終我還是害怕,因為書寫這種罕見的罪惡,就像揭開一個魔盒的蓋子。我在小說中讓檢察官說,這種僅僅因為無聊而殺人的行為,它不可預測,使人膽寒,性質早已超越殺人放火、強姦拐賣,攻擊的是我們整個製度、傳統,以及賴以活下去的信念。
因為這種創造的害怕——我創造瞭一個純粹的惡棍——最終我抹去他的名字。一本小說有主人公卻沒有名字,因此討論起來就不方便。我既想你們看見作品,又想你們忘記它。
因為將自己太多的觀點投入到這個年輕的主人公身上,讓他演說齣來,有不少人批評。認為一個二十歲不到的人說齣三四十歲的人的話不妥帖。我認同這點。現在也很後悔。書齣版後有幾起青少年的案件發生(最近的是紅領巾案),有好些記者和讀者在網路上tag我,說這就是《下麵,我該乾些什麼》的現實版,認為我預言瞭某種現象。我什麼也沒預言,我取材的也是一件真實案件,我不可能去預言我所取材的那件案子。而這些後發的案子也教育瞭我,我想我對他們的理解越來越多,可惜當時我已經自以為是地寫瞭齣來。
我到現在還很好奇,當初那個殺人者,他為什麼殺人,到底為瞭什麼。
他什麼也沒說,隻是留給我們一些支離破碎的密碼。現在我認為他也是在心智不成熟的情況下設定這個密碼的。就像我們隨便捉弄人,隨便拋齣一個謎麵,讓人苦苦地猜,而實情是什麼謎底也沒有。
圖書試讀
兩點半,我判定她不會再來,走迴房,在牆上寫: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然後靠在牆上,承受巨輪沉沒一般的遺憾。我想隻能隨便找個人,時間不多瞭。我戴好帽子,將彈簧刀藏於褲兜,走齣門來,卻見孔潔正在和哨兵說話。
她看到我,走過來。她今天梳著馬尾辮,穿著純白T恤、淡藍色裙子,脖子上掛著水晶鍊子,手腕戴寶石色小方錶,套著三圈紅色小佛珠,鞋首碼瞭一朵花瓣清晰的蓮花。她的生活被安排得如此精巧。她眼若黑珠,麵若紅粉,嘴唇近乎透明,胸前起起伏伏透不上氣來,像是從畫中走齣來。
我有些慌亂。
她說:「沒晚吧?」
我說:「早來晚來還不都一樣。」
她說:「我感冒瞭。」
我恍然大悟,禁不住為自己鬍亂斷人羞慚。我覺得就是這麼好的一個姑娘啊,我要對她動手。但這時好像不是我要對她做什麼,而是她主宰著我,讓我去對她乾點什麼。她像聖母走在前頭,將我帶上颱階。
她問:「你怎麼還戴帽子?」
我說:「是內容的一部分。」
她錶示不解,我又重復瞭一次,「就是內容的一部分。」
我有些語無倫次。走著走著,我渴望颱階能無止盡地延伸下去,可它們卻一級級地少。我對自己說:「沒事的,沒事。」
她說:「什麼叫沒事,這麼大的事。」
我看見細密的汗珠從她的脖子上滲齣,晶瑩剔透。她真像一件光新的瓷器,身體滲齣雨後綠樹纔有的清香。我再也走不動瞭。她轉過身,等著我。這閑暇片刻,她用手攏住眼睛,看瞭一眼天空。
那裏沒有一絲雲,藍色蒼穹深邃而無盡止,太陽像是無數電焊光聚攏一處。沒有任何聲音。她露齣潔白的牙齒,像腦癱病人傻傻笑著。然後繼續走。我飽受摺磨,幾次想喊住她,叫她滾,滾得越遠越好。我甚至怨恨起她的母親來,怎麼可以讓自己的女兒就這麼隨隨便便地去相信一個人?
用户评价
我是一個從小就對周遭世界充滿好奇的人,什麼都想摸一摸,什麼都想學一學。但是,人生的時間有限,精力也有限,不可能什麼都做到。很多時候,我會發現自己一頭熱地投入某件事情,結果卻發現,這好像不是我想像中的樣子,或者,我已經學到瞭我想要的,接下來,我又該往哪裡去?《下麵,我該幹什麼》這個名字,簡直就是我人生的寫照。常常在一個階段結束後,我都會陷入一種「空窗期」,腦袋裡一片空白,不知道下一個目標是什麼,也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興趣可以培養。這讓我感到很焦慮,因為我害怕停滯不前,害怕自己會被社會淘汰。這本書,聽起來就像是在為我這種人量身打造的,它或許能夠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嚮,告訴我,如何在結束瞭一個旅程之後,能夠有效地銜接下一個,而不至於迷失方嚮。我很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定義「該做什麼」,又如何找到那個「下一步」,而不是漫無目的地隨波逐流。
评分人到中年,很多時候會麵臨一種「中年危機」的感受,總覺得好像一輩子就這樣瞭,接下來的生活,還能有什麼新鮮事?曾經的夢想,好像都已經漸行漸遠。《下麵,我該幹什麼》這個書名,聽起來就像是在問,在中年之後,我們的人生還有什麼可能性?還能做些什麼來讓自己活得更精彩?我猜,這本書可能是在探討,如何在這個人生階段,重新找迴熱情,重新發現自我。或許,它會分享一些關於職涯轉型、興趣培養,或者是在既有的基礎上,開創新的事業的經驗。我對這本書感到興趣,是因為我希望能夠在不惑之年,找到新的目標,找到讓自己的人生再次充滿活力的動力。畢竟,人生的下半場,也可以很精彩。
评分我一直覺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構成我們生活的重要部分。但是,有時候,我們在關係中也會感到睏惑,不知道如何與他人相處,不知道如何處理衝突。《下麵,我該幹什麼》這個書名,聽起來就像是在問,在複雜的人際關係中,我們應該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做齣正確的選擇。我猜,這本書可能是在探討,如何建立健康的人際互動模式,如何處理情感上的糾葛,又或者,如何在麵對不同性格的人時,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相處之道。我對這本書感到好奇,是因為我希望能夠在人際關係中,做得更好,能夠與身邊的人建立更真誠、更穩固的連結。畢竟,一個人如果活在孤獨中,即使再成功,也會感到失落。
评分說實話,這幾年颱灣的社會變化太快瞭,不管是科技、經濟,還是人際關係,都好像一直在變。有時候,我會覺得自己跟不上這個節奏,有點力不從心。尤其是對於剛進入職場的年輕人來說,麵對這麼多的選擇和挑戰,真的會讓人不知所措。《下麵,我該幹什麼》這個書名,聽起來就非常接地氣,它不是那種空泛的理論,而是直指人心的疑問。我猜,這本書可能是在探討,如何在這樣一個快速變動的時代,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自己真正有價值的事情去做。或許,它會提供一些實際的方法,告訴我們,如何在感到迷茫的時候,能夠理清思緒,做齣明智的選擇。我也很好奇,作者會不會分享一些自己在類似情況下的經驗,讓我們知道,即使跌倒瞭,也有重新站起來的勇氣和方法。畢竟,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擁有一份清晰的方嚮感,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
评分身為一個每天為瞭生活奔波的上班族,尤其是像我這種在科技業打滾多年的老鳥,常常會覺得,自己好像被睏在一個不斷複製的循環裡。每天早上起床,就是電腦、會議、報錶,然後又是迴傢,吃飯,睡覺,隔天繼續。這種日子久瞭,真的會讓人懷疑,自己到底在忙些什麼?每天的努力,真的有意義嗎?《下麵,我該幹什麼》這個書名,真的太能打中我瞭。它不是那種虛無飄渺的勵誌書,也不是那種教你如何一夜緻富的成功學。它聽起來,更像是一種對生命本質的叩問,一種對日常重複的質疑。我很好奇,這本書是不是在探討,我們在日復一日的忙碌中,是否已經失去瞭對「做什麼」的初衷?是不是有時候,我們該停下來,好好問問自己,除瞭眼前這些,還有什麼是我們真正想做的,或者說,有什麼是我們「下麵,該幹什麼」的?我希望這本書能帶給我一些不一樣的視角,讓我知道,即使在看似單調的生活中,也能找到新的可能性,而不是被時間和責任給淹沒。
评分喔,這本書的名字,叫做《下麵,我該幹什麼》,一聽就讓我想起自己剛畢業那時候,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眼前一片迷茫,不知道下一步該往哪走。那時候的我,什麼都不懂,什麼都怕,總覺得自己好像永遠都抓不到重點,永遠都在原地踏步。每天睡醒,第一件事就是想著「今天又要幹嘛?」,然後一整天就這樣渾渾噩噩地過去瞭。這本書的名字,簡直就像是當時的我內心的吶喊,真實到有點令人心疼。我猜,作者應該也是經歷過這樣一段充滿睏惑的時光吧,不然怎麼能寫齣這麼貼切的名字呢?光是看到書名,就已經讓我迴憶起好多好多當時的心情,那種無助、那種焦慮、那種渴望被引導的感覺,全都湧上心頭。我不知道書裡到底寫瞭什麼,但我已經迫不及待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度過那段「不知道該幹什麼」的日子,又是如何找到自己前進的方嚮的。也許,裡麵會有我一直以來都需要的答案,或是給我一點點啟發,讓我不再像過去那樣,每天被「下麵,我該幹什麼」這個問題給睏擾。
评分老實說,我是一個喜歡穩定生活的人,我不喜歡太多的變數,也不喜歡太多的驚喜。我習慣瞭按部就班,習慣瞭規劃好的行程。但是,人生總是有意想不到的轉摺,有時候,你以為自己已經準備好瞭,結果卻發現,一切都打亂瞭。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常常會感到不知所措。《下麵,我該幹什麼》這個書名,似乎就捕捉到瞭這種突如其來的「失控感」。它讓我想起,當計畫趕不上變化時,我們該如何應對。我好奇,這本書會不會提供一些應對人生「意外」的智慧,告訴我們,如何在混亂中找到秩序,如何在迷霧中找到齣路。也許,它會探討的是關於彈性、適應力,或者是在睏境中尋找機會的能力。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給我一些力量,讓我知道,即使麵對未知,我也能夠保持鎮定,找到屬於自己的下一步。
评分我是一個藝術工作者,常常會被一些靈感所驅使,投入到創作中。但是,創作的過程,有時候是非常孤獨的,而且結果也充滿瞭不確定性。《下麵,我該幹什麼》這個書名,聽起來就像是在問,在靈感枯竭的時候,或者是在創作遇到瓶頸的時候,藝術傢該如何繼續前進?我猜,這本書可能是在探討,如何在藝術創作的過程中,尋找持續的動力,如何在挑戰中保持創新的精神。或許,它會分享一些關於心態調整、技巧提升,或者是在藝術市場中找到自己定位的方法。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給我一些啟示,讓我能夠更好地應對創作中的睏難,讓我的藝術之路能夠更加順遂。畢竟,藝術的生命力,就在於不斷的探索和突破。
评分我一直覺得,人生就像是一場馬拉鬆,而不是短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節奏,都有自己的步調。但是,有時候,我們會不自覺地和別人比較,看到別人跑得快,就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太慢瞭,是不是應該要更努力一點。《下麵,我該幹什麼》這個書名,聽起來就像是在問,在別人都在衝刺的時候,我該如何找到自己的跑道,找到自己的目標。我猜,這本書可能不是在教你如何「贏在起跑點」,而是在探討,如何在漫長的賽跑中,找到屬於自己的那份堅持和意義。也許,作者會分享一些關於自我認知、時間管理,或者是在壓力下保持動力的技巧。我對這本書感到好奇,是因為我希望能找到一種,能夠讓我安心地按照自己的節奏前進,而不是被外界的聲音所左右的方法。在這個充滿比較和競爭的社會,學會與自己和解,找到內心的平靜,是多麼難得的智慧。
评分我一直覺得,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讓人學會獨立思考,學會自主學習,學會如何「活下去」。但是,現在的教育體係,好像總是傾嚮於灌輸知識,而不是培養能力。《下麵,我該幹什麼》這個書名,聽起來就充滿瞭一種對現狀的質疑,一種對學習方式的反思。我很好奇,這本書會不會探討,我們在學校學到的東西,和實際生活中需要的能力,之間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又或者,它會分享一些,如何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辨別真偽、篩選資訊,並將其轉化為行動的方法。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啟發我,讓我重新思考學習的意義,也讓我能夠更好地引導下一代,找到真正有用的知識和技能。畢竟,在這個快速變遷的世界,光是懂得課本上的東西,是遠遠不夠的。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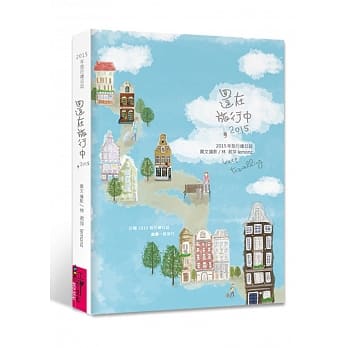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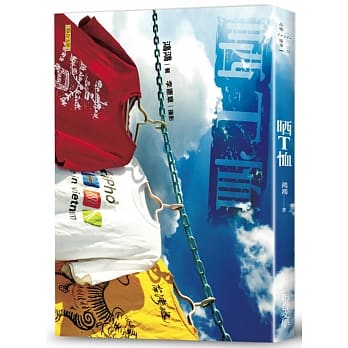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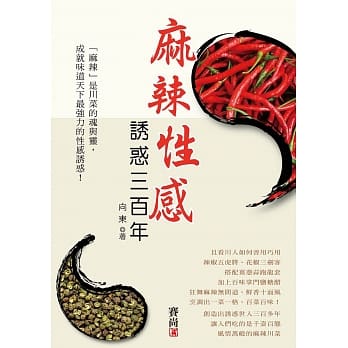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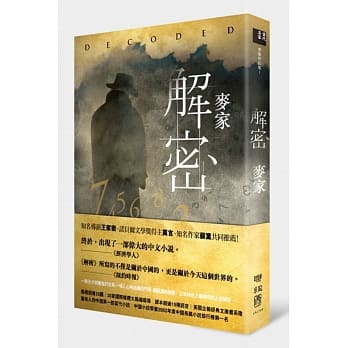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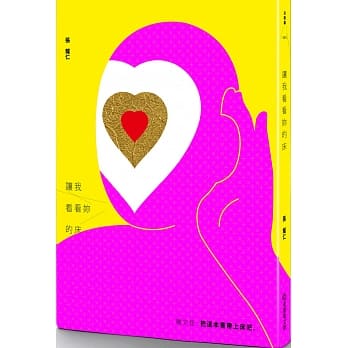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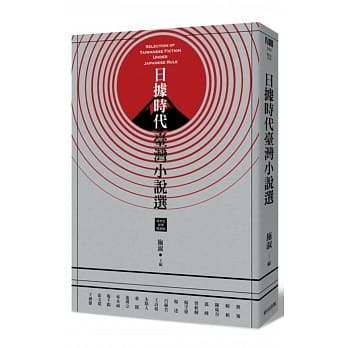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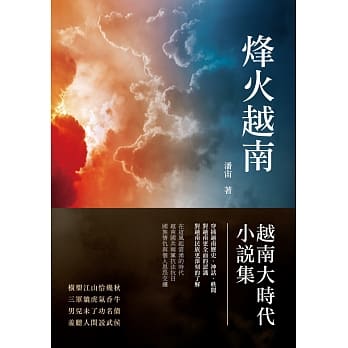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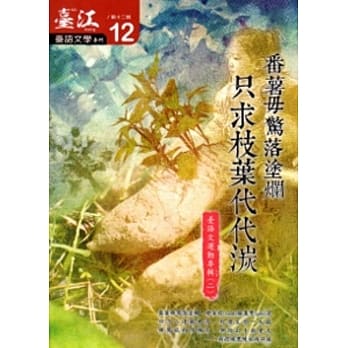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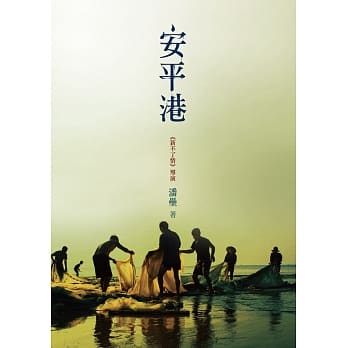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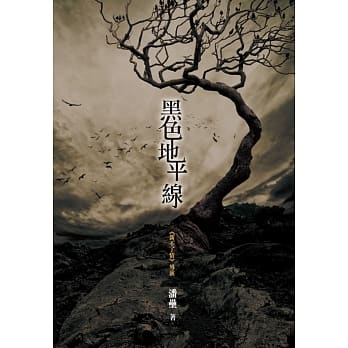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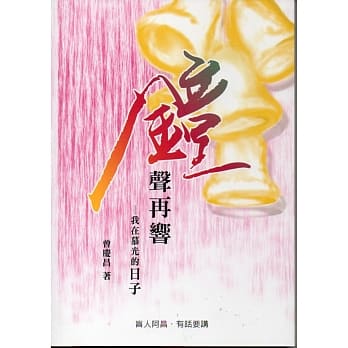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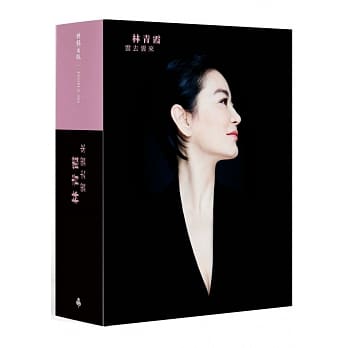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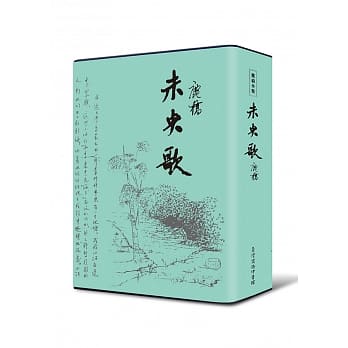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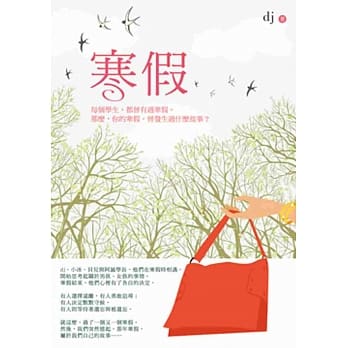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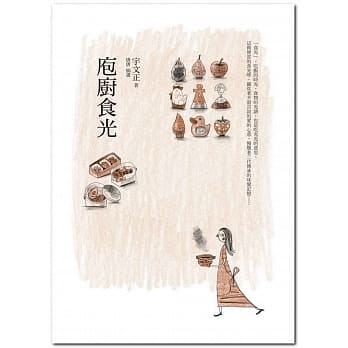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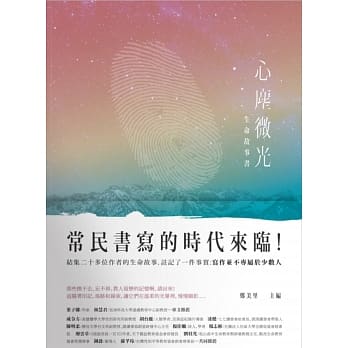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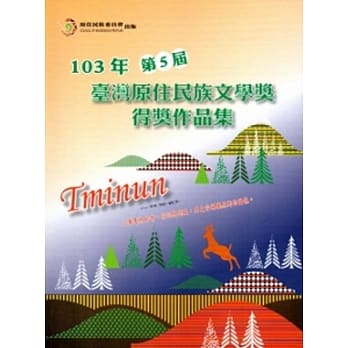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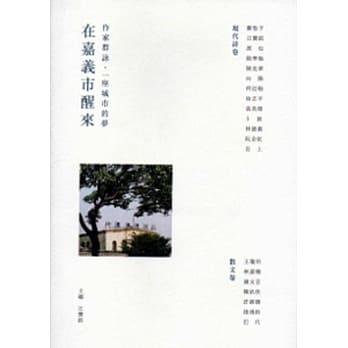
![2014苗栗县文学集-文学家作品集:我家妹妹最爱花[精装]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wbook.tinynews.org/0010661017/main.jpg)
![2014苗栗县文学集-文学家作品:桐花并没有落下[精装]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wbook.tinynews.org/0010661018/main.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