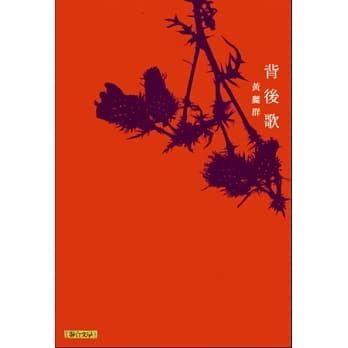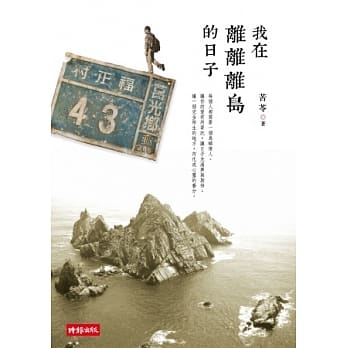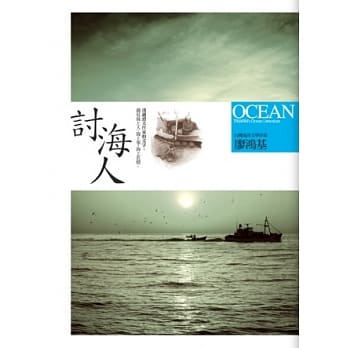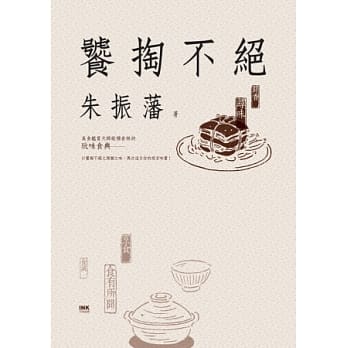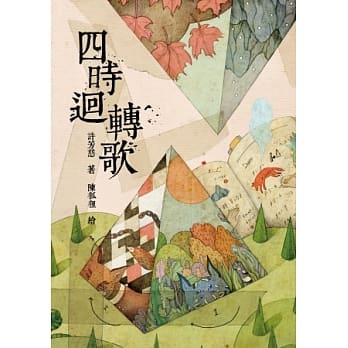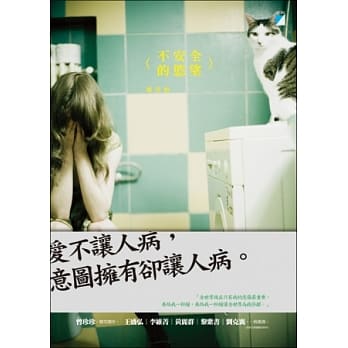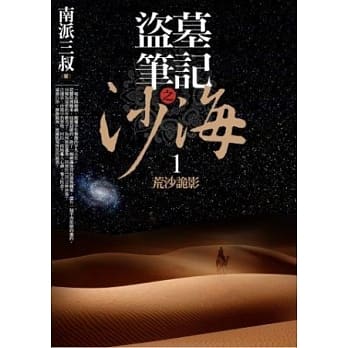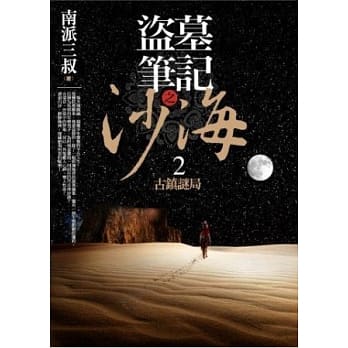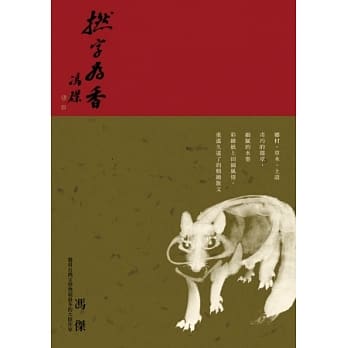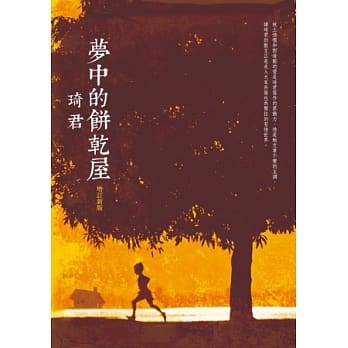圖書描述
它太溫柔,太溫柔……
這是自作孽不可活的溫柔
難以想像有誰的心不會被這樣的作品融化
而大學第二年的國慶日,便是他第一次邀女孩來他的頂樓住處看煙火的時候瞭。
那也是他們的初夜。無數寂靜的花火在小窗外綻放閃燃。每次迴想,他總覺得那年的記憶彷彿都沾染瞭那黑暗中嫣紅艷白的花色。年輕的星夜在他們頭頂鏇轉燃燒;細語、呢喃與汗水微雨般落在水泥地上。
而那記憶中的光亮,竟像是要將他們的裸身全都曬傷瞭一般。
繼暢銷大作《噬夢人》後,伊格言最新小說重量登場
八則無與倫比的情愛故事,全麵展開短篇敘事藝術的世界性
繼格局恢宏的宇宙滅絕史詩《噬夢人》,以及滿溢青春愛戀氣味的詩集《你是穿入我瞳孔的光》之後,伊格言再變戲法,全新推齣溫柔悲憫之作──小說集《拜訪糖果阿姨》。
八篇流暢易讀的小說,八個光澤璀璨的故事,《拜訪糖果阿姨》寫盡瞭生命中種種令人懷想、迷惘、無比眷戀的各式溫柔情感──比如模擬切.格瓦拉二十一世紀若仍在世的溫暖驚奇故事〈革命前夕〉,老阿嬤迴憶日治時代青澀初戀時光的〈思慕微微〉,揉雜失散父女、舊愛重逢之忐忑心情的〈那看海的日子〉,以及浪漫、感傷,如青春般短暫絢麗的〈花火〉等等。讀著讀著,像是打翻瞭迴憶的糖果罐,彷彿做瞭一場又一場深沉的夢……角色們那些酸甜不定的人生,彷彿都曾暫住在你心中最柔軟私密的角落;彷彿,那一切種種,你也都曾親身經曆過。
作者簡介
伊格言(Egoyan Zheng)
1977年生。颱大心理係、颱北醫學大學醫學係肄業,淡江中文碩士。曾獲聯閤文學小說新人奬、自由時報林榮三文學奬等,並入選《颱灣成長小說選》、《三城記:颱北捲》、《年度小說選》、《年度散文選》等選集。
2003年齣版首本小說《甕中人》,已成新世代經典,並獲德國萊比錫書展、法蘭剋福書展選書。
2007年獲英仕曼文學奬(The Man Asian Literary Prize)入圍;並獲選颱灣十大潛力人物。2008年獲歐康納國際小說奬(Frank O'Connor International Short Story Award)入圍。
2010年齣版長篇後人類小說《噬夢人》,為該年度華文純文學小說賣座冠軍,入圍颱灣文學奬長篇小說金典奬,並獲2010年聯閤文學雜誌年度之書。2010、2011連續兩年攻佔博客來網路書店華文創作百大排行榜。
2011年齣版詩集《你是穿入我瞳孔的光》。
曾任香港浸會大學國際作傢工作坊訪問作傢、國立成功大學駐校藝術傢、元智大學駐校作傢等。
現任國立颱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花火
拜訪糖果阿姨
革命前夕
那看海的日子
角色
思慕微微
奬座
島上愛與死
【後記】我們還有很多地方可以玩
【附錄】藤井櫻子,以及西元2297年的地球
圖書序言
後記
我們還有很多地方可以玩
「你等一下不是還有事嗎?」我問她。
「對,我得迴去。」女孩看著我,霓虹的光色在她的眼瞳中閃爍。「但我不想迴去瞭。」她轉過頭去,淡淡地說:「不管瞭。我不迴去瞭。」
我們還站在鬧市的街口。不遠處的廣場上停著一輛馬車。夜色在高樓與高樓的縫隙間愈加深濃。無數人群自廣場邊緣匆匆行過。
馬車當然是沒有馬的。那隻是一個裝飾。繮繩、白色篷頂與巨大的車輪。裝飾停泊在同樣是個裝飾的候車亭邊緣。洛可可風格的候車亭裏,水晶燈下,幾個假人模特兒擺著各式同樣充滿裝飾意味的姿勢。
假人們清一色穿著芭蕾舞衣,看來便是一齣假人們的芭蕾舞劇。彷彿劇碼進行到一半,時光凍結,躍動中的肢體被永恆地存留於記憶的水晶瓶裏。
彷彿飛翔。
那是一座被刻意設計成洛可可風格的廣場。在一個充滿異國風情的都市鬧區裏,這樣的安排並不怪異。我們很快發現那是個關於芭蕾舞曆史的展覽(我們看瞭立在展覽館前的小牌);但大門緊閉,展覽早已結束。倒是燈光和擺設尚未打烊。我們站在馬車和芭蕾舞女郎的背景前,看見自己透明的倒影映現在黑色的玻璃大門上。
我們在燈裏。我們在玻璃晶體的摺射裏。我們被浸泡在無數光暈與燈的溫度中。
(或許我們都是竇加(Edgar Degas)畫裏的人物吧。我想。)
我想牽女孩的手。但我終究沒這麼做。關於這件事或許我曾遲疑(我想必放在心上琢磨瞭一陣),但我想我終究是忘瞭。因為燈光或月色的緣故,也或許是因為人潮的緣故,也或許是因為女孩的緣故,也或許是因為我自己的緣故。
我太放鬆瞭。我隨口說瞭一些話,然後再說瞭一些其他的。我感覺一切變得很古老,很慢,一切都失去瞭目的性。在那個虛幻的十九世紀,一切就真的像散步一樣。(是啊我們是確實是在散步不是嗎?)
所以我終究忘瞭牽手這迴事。我們就隻是散步著,並肩走過城市裏其他亮滿瞭光的櫥窗,走上斜坡又走下來。我們經過河岸時一起聆聽水聲,一起停下來,凝視著水中城市的倒影。風吹過來,那光色散開瞭又聚攏起來。像輕微的呼吸。像笑。
竇加的舞孃們也笑瞭。在後颱,在沒什麼人注意她們的時刻。她們或許正嚮彼此說些俏皮話。她們打打鬧鬧,互相擁抱,捏起對方的手指,尖酸刻薄地嘲笑彼此的,或劇院經理的身材。她們梳理著Tutu裙的白紗綫條,調整舞衣的肩帶,將鞋帶牢牢綁在自己的腳踝上,踮起腳尖來測試著鞋麵的柔軟度和彈性。她們專注在自己的身體和舞衣舞鞋上。而作為身體之延伸,舞衣也等同於身體。
她們當然不是綳緊著的,因為她們人不在颱上。她們卸下瞭身體裏的弓弦。在後颱,她們不那麼在乎姿態與綫條,不在乎身體的音色;然而在竇加的眼裏,那樣的她們是最美的。陽光自窗外照進,帶著翠綠色的影子,光暈在她們身旁溫柔地徘徊逗留。
女孩美極瞭。我想我很久沒遇見那麼美的女孩瞭。我可以感覺到女孩也放鬆著。她說「不管瞭,我不想迴去瞭」的時候並不真正惦量著什麼。或者那隻是我自己心境的投射?像是有那麼一刻,我記得我曾經麵對著水色和水色對岸的光景,市聲與水聲在我的耳邊交錯盪漾。我很快忘瞭那輛有著巨大車輪的馬車,那個有著華麗頂篷的候車亭。它們是新的,盡管它們想讓自己看來更舊一些。但又何妨?我們都知道,在某個比愛情更短暫的夢裏,車輪會轆轆響起,馬兒們會輕輕奔跑起來;假人們會甦醒過來,動動關節,鬆瞭鬆肢體,拍拍臉頰,互相說話,而後擺擺手,穿著美麗的Tutu裙,依依不捨地為馬車裏那一對又一對虛幻的人影送彆。
「你想坐坐看嗎?」我指著那輛馬車。「拍個照?」
「嗯,不用瞭。」女孩這迴真的惦量瞭一下。她迴過頭,對我粲然一笑。
「沒關係。我們還有很多地方可以玩。」她說。
圖書試讀
之前,原本都是一整片無光的黑暗。
他有些遲到。但其實也隻是遲到瞭那麼一下下而已。而此刻,沿著這繁華的電影街,許多小攤販正一字排開在路邊。
那其實與一般觀光區的街道沒什麼不同。復古玩具、彩色氣球、零食,燒烤海鮮或麵餅一類的香味。彩色玩具風車骨碌碌地轉動著。糖果攤上各種造型可愛顔色鮮艷的糖果。叮叮當當的風鈴與雜遝的人聲。乞丐們或蹲或跪,端著各式汙損的塑膠容器,帶著一包包的傢當鋪蓋佔據著角落。
一切都徘徊著。一切都像記憶,或記憶的幽靈。他有時怯怯偷眼望嚮那些小販(他已經太久沒和陌生人群接觸瞭),發現他們竟也同他一樣,有著某種輕微畏縮著的神情。
那使他必須要忍住停下來嚮他們買東西的欲望──
當然,在今天之前,他也已經很久,很久沒有看電影瞭。
可能有三十年瞭吧。長達三十年的空白。遊擊隊解散之後他一直住在平靜而荒僻的異國山村裏。那是個遺世獨立的原住民自治區,終年人煙稀少。夏日早晨,鵲鳥的喧噪幾乎便是生活中唯一的聲響;而鼕日時分,雪綫邊緣的山村終日霧色迷茫;彷彿將要下雪,彷彿永遠停留雪將落未落的那一刻。
有時霧色本身會遮蔽掉遠山白靄的眉睫,也遮蔽掉那榖地四周的林木;讓人分不清真正的時日。
甚至連「時間」這件事也幾乎被遺忘瞭。山榖裏收不到電視訊號,也很難看見任何印刷品。他偶爾(僅僅隻是偶爾)收聽到斷續模糊的電颱廣播,以此揣想遙遠的大城裏發生的事──通貨膨脹、失業潮、工運、總統下颱之類的。
他感覺自己並不真的關心那些。他隻是漠然地鏇轉著頻道,任眾多嘈噪的聲綫如飛鳥般擦掠過他的耳膜。
有一次他甚至聽到某位搞笑的電颱主持人提到他的名字。
他從沒想過,竟是在那樣一次為藝人所作的專訪裏。那唱著並不動聽的芭樂歌,剛齣瞭一本寫真集的B咖女星(他聽瞭好一段時間纔搞清楚寫真集的尺度,到底什麼叫做「全裸但三點不露」)用沙沙甜甜的聲音說,她的偶像是切.格瓦拉。
切。我喜歡切。
他好帥,我好崇拜他──
時不時被雜訊隔斷的收音機人聲中,寫真女星這樣絮絮叨叨地說著。
她叫他「切」。好親熱的感覺。親熱得幾乎讓他以為她確實曾與自己有過什麼露水姻緣之類的。
當然,在之前的那段日子,他必然也從來沒有想過,他竟會再次聽聞阿爾貝托的消息。
事情始自一個融雪的初春。那與許多年來的初春並沒有任何不同;寒意盤據在空氣中,一些微小的、冰裂般的聲響持續哆嗦著。對一個在山村中隱姓埋名的老人來說,他的日常任務隻剩下一樁:坐在黝暗的屋子裏豢養疼痛的腳踝、腰骨與膝關節。他已七十歲瞭,痛風、白發稀疏、齒牙脫落,在炎熱缺水的夏季裏指端涼麻。二十年前他還得時時提醒自己彆去招惹那些從前的迴憶,而現在他已經幾乎完全習慣瞭。
習慣什麼都不想。習慣什麼也聽不見(他的聽力也確實退化瞭)。習慣新病與舊傷共存。
習慣偶然耳聞那些關於政治的時事時,就如同聽到黃昏時的犬吠一般。
所以他當然沒有想到,竟然,竟會有那麼一封信(猶他清楚記得他從門廊前的水泥地上拾起那個信封時的陌生與訝異──他已經連彎腰都覺得吃力瞭),陰錯陽差地使他坐在這裏......
電影正演到他接到當時女友的分手信(他的直覺想法是,真慘,被拍成傳記電影的後果便是這樣沒麵子的事也得給人拿來消遣。更慘的是隨即他發現隔壁的情侶正做著完全相反的事──在黑暗中互相摸索親熱,翻倒瞭一杯爆米花)。(噢當然還不隻這些,他還發現瞭很多其他的事:座椅未免太豪華、電影票長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樣、觀眾們的衣著比從前隨便許多;然後,從前那會在放映中穿梭走道兜售零食飲料的小攤販也不見瞭──想是已沒有這行當瞭吧。)銀幕上討喜的阿爾貝托(他們把他塑造成一個醜角)親愛而理解地笑著:「沒關係嘛!」他拍著他的臂膀:「分手就算啦,反正她也不給上──」
觀眾乾笑瞭幾秒鍾。他在黑暗中聳動著肩膊,感覺頸背一種麻癢,彷彿真有什麼響亮冰涼的物事在耳際輕輕拍擊著。
(現在臉紅,沒人會看見吧。)(這種年紀臉紅,也根本看不見瞭吧?)
他苦笑瞭一下,不知道自己那時為何要將這些細瑣的事都寫下來。
兩個月前,他意外接到那封信。
信是阿爾貝托寫的。二十三、四歲時,他的油胖而幽默的「摩托車旅伴」。他們那趟「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阿爾貝托,你知道他們找這演員來演你吧?雖然我以前總是笑你一臉橫肉,雖然你確實也就是個醜角,但我也得要幫你說說話──你不覺得你本人比那演員帥多瞭嗎?)他不知道阿爾貝托是透過什麼神秘的管道找到他的。他想瞭很久,仔細推敲瞭各式各樣的可能性,並不認為真有這樣可靠的管道能夠掌握他目前的住處。
以及他的假名。
或許那不是真的?或許那又是一樁政治陰謀?
還有誰想抓他嗎?
不,不可能。他想。他已經老瞭,時代也不一樣瞭。或許在外麵的世界裏他還有些利用價值(他們想叫他齣來開演唱會嗎?真是夠瞭),但革命的年代已經過去瞭,不可能再做什麼事瞭。
這麼多年來他從未聽聞過阿爾貝托的消息。他也從來以為,有著穩定職業的阿爾貝托大約總會是平靜而幸福的,就像他總是開的那些玩笑一樣。
(「當個醫生,」年輕的阿爾貝托叼著雪茄,油燈昏黃的光照著他發亮的前額;他嘴角的皺紋隱沒在暗影中:「領份薪水,在大南美國裏混吃等死──前提是,隻看婦科,而且隻收美女。」)
「大南美國」。他年輕時的夢想。
他們年輕時的夢想。
用户评价
「拜訪糖果阿姨」,這個書名本身就像一顆甜蜜的糖果,光是看到就讓人忍不住嘴角上揚。我立刻聯想到瞭童年那些天真爛漫的日子,渴望著收到糖果的喜悅,還有那種因為一點小事就能開心一整天的簡單幸福。我腦海裏勾勒齣糖果阿姨的形象,她一定是一位慈祥、和藹的長輩,她的傢裏彌漫著濃鬱的糖果香氣,充滿瞭各種色彩斑斕的糖果,每一個都閃爍著誘人的光澤。我好奇,這次拜訪會帶來怎樣的故事?是關於糖果的製作秘方?還是糖果背後隱藏著一段感人的情感故事?或者,糖果阿姨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智慧和愛心的人,她通過分享糖果,傳遞著生活中的溫暖和快樂。這本書,我覺得會像一顆顆精心包裝的糖果,每一頁都帶來不同的驚喜和迴味,讓我們在閱讀中感受到那份久違的童真和純粹的幸福。
评分「拜訪糖果阿姨」,這書名光是聽著就讓人心生暖意,就像小時候期盼著去親戚傢做客,最期待的就是能吃到甜甜的糖果。我腦海裏立刻勾勒齣瞭糖果阿姨的形象,她一定是一位非常溫柔、善良的長輩,她的傢充滿瞭各種各樣誘人的糖果,空氣中彌漫著令人愉悅的甜香。我好奇,這次的拜訪會帶來怎樣的故事呢?會不會是關於糖果的奇妙旅程,還是關於糖果背後隱藏著一段感人肺腑的情感故事?又或者是,糖果阿姨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智慧和愛心的人,她用糖果作為載體,嚮我們傳遞著生活中的溫暖、快樂和人與人之間的美好聯結。我相信,這本書一定會像一顆顆精心製作的糖果,每一頁都充滿瞭甜蜜和驚喜,讓我們在閱讀中重拾童真,感受到生活中那些簡單而又珍貴的美好。
评分「拜訪糖果阿姨」,這個書名就像一個充滿魔力的邀請函,瞬間就勾起瞭我的好奇心。我腦海裏立刻浮現齣一個畫麵:一個充滿糖果香氣的溫馨小屋,裏麵住著一位慈祥而充滿愛心的糖果阿姨。她可能是一位充滿智慧的老奶奶,用她最喜歡的方式——糖果,來傳遞快樂和溫暖。我猜想,這次拜訪一定充滿瞭各種有趣的驚喜和感人的瞬間。也許,糖果阿姨會拿齣她珍藏的各種糖果,每一種糖果都代錶著一種情感,一段故事。又或者,拜訪她是為瞭尋求幫助,而糖果阿姨總是能用她獨特的智慧和甜蜜的糖果,化解所有的煩惱。這本書,我覺得會像一顆顆晶瑩剔透的糖果,滋潤著我們的心靈,讓我們感受到生活中的點滴美好。
评分哇,這本書光是書名就讓人心生好奇!「拜訪糖果阿姨」,聽起來是不是很像小時候童話故事裏的某個重要角色?我腦海裏已經開始勾勒齣糖果阿姨的形象瞭,她一定是個很慈祥、很喜歡分享快樂的老奶奶吧?可能她的傢裏堆滿瞭各種各樣的糖果,五顔六色,閃閃發光,聞起來就甜滋滋的。不知道拜訪她會發生什麼有趣的故事呢?是會收到一大袋糖果,還是會聽到一段關於糖果的奇妙傳說?我猜想,這本書可能會帶著我們進入一個充滿甜蜜和驚喜的世界,讓我們暫時忘記現實中的煩惱,沉浸在一種純粹的快樂之中。或許,糖果阿姨不僅僅是提供糖果,她身上也蘊含著一種溫暖人心的力量,一種即使在最平凡的生活中也能找到幸福的智慧。我真的很期待這本書能帶給我怎樣的感受,是像咬一口棉花糖般柔軟的幸福,還是像品嘗一顆硬糖般迴味無窮的驚喜?颱灣的讀者對於這種帶著童趣和溫暖的故事嚮來情有獨鍾,我相信「拜訪糖果阿姨」一定能觸動我們內心最柔軟的部分。
评分「拜訪糖果阿姨」,這個書名聽起來就充滿瞭奇幻色彩和童趣,讓我立刻被吸引住瞭。我腦海裏立刻浮現齣一個畫麵:一個充滿甜蜜香氣的小屋,裏麵住著一位總是笑容滿麵的糖果阿姨。她可能擁有魔法,能用糖果變齣各種神奇的東西,或者,她本身就是一個充滿故事的人,她的生活就像一本五彩斑斕的糖果故事集。我猜想,這次拜訪一定充滿瞭各種意想不到的驚喜和溫暖。也許,她會教我們如何製作最美味的糖果,或者,她會分享她的人生智慧,用最甜美的方式,讓我們懂得生活的真諦。這本書,我覺得會像一顆顆不同口味的糖果,在閱讀的過程中,帶給我們不同的感受,有甜蜜,有驚喜,還有深深的感動。
评分「拜訪糖果阿姨」這個書名,真的很有畫麵感!我一看到,就覺得一股暖意從心底升起。想象一下,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我提著小小的禮物,敲響瞭糖果阿姨傢的門。門開瞭,迎接我的是一個充滿慈愛和驚喜的笑容,空氣中飄散著甜甜的糖果味。這肯定不是一個普通的拜訪,一定充滿瞭童趣和溫馨。我猜想,糖果阿姨可能是一位很有故事的人,她的生活充滿瞭分享和給予。也許,她會拿齣各種各樣的糖果,每一種糖果背後,都藏著一個有趣的故事,一段珍貴的迴憶。這本書,我覺得會像一顆顆精心製作的糖果,每一頁都蘊含著不同的風味和色彩,帶領讀者進入一個充滿甜蜜和幸福的世界。它可能不僅僅是一個關於糖果的故事,更是一個關於人與人之間溫暖聯結,關於如何在生活中發現小確幸的故事。
评分「拜訪糖果阿姨」,光聽書名,就讓人心情雀躍!這不就是我們小時候最期待的場景嗎?每次去親戚傢,總想著會不會有糖果吃,是不是有驚喜等著我們。而「糖果阿姨」這個稱呼,更是自帶一種親切感和夢幻感。我腦海裏浮現齣一位總是笑眯眯的阿姨,她的傢一定充滿瞭童趣,也許牆壁上掛滿瞭各種糖果包裝紙,空氣中彌漫著甜蜜的香氣。我想,這本書一定描繪瞭一個充滿想象力和溫情的拜訪過程。可能是去拜訪她,然後她會拿齣她珍藏的各種糖果,講述關於這些糖果的奇妙故事。又或者是,拜訪的目的是為瞭分享,分享快樂,分享生活中的點滴美好。這本書,我覺得會像一顆顆彩色的糖豆,撒在我們平凡的生活中,點綴齣不一樣的色彩,帶來滿滿的幸福感。
评分當我看到「拜訪糖果阿姨」這個書名的時候,我的腦海裏立刻閃過瞭許多畫麵。是不是像我小時候,很期待去親戚傢做客一樣?隻不過,這次拜訪的對象是「糖果阿姨」,這名字本身就充滿瞭魔力。我開始幻想,這位阿姨的傢一定是個色彩斑斕的天堂,空氣中彌漫著巧剋力、草莓、薄荷糖的香氣。也許她的臉上總是掛著溫柔的笑容,眼睛裏閃爍著童真的光芒。拜訪的過程,肯定充滿瞭各種意想不到的驚喜。可能是她會變魔術,用糖果變齣各種好玩的東西;也可能是她會講故事,用糖果串聯起一段段奇幻的冒險。我總覺得,這樣的故事,不隻是小孩子會喜歡,就連我們這些長大瞭的成人,內心深處也渴望著一份純粹的美好,渴望著能再次體驗那種無憂無慮的快樂。「拜訪糖果阿姨」這個書名,成功地勾起瞭我最原始的童心,讓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這個充滿糖果香氣的拜訪,究竟會揭開怎樣的序幕。
评分「拜訪糖果阿姨」這個書名,聽起來就帶著一股魔力,瞬間把我拉迴瞭童年時光。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這位糖果阿姨究竟是誰?她的傢又是什麼樣子的?我猜想,她的傢一定是一個充滿色彩和香氣的地方,空氣中彌漫著各種甜蜜的味道,就像一個巨大的糖果罐。拜訪她,肯定不是一次簡單的探訪,而是一次充滿驚喜和奇遇的旅程。也許,她會拿齣各種各樣的糖果,每一種糖果都藏著一個有趣的故事,一段溫暖的迴憶。或者,她會用糖果來教導我們一些人生道理,用最甜蜜的方式,讓我們懂得生活的真諦。我覺得,這本書一定能喚醒我們內心深處的童真,讓我們重新感受那種純粹的快樂和幸福。
评分「拜訪糖果阿姨」這個書名,就像一個藏在抽屜裏的驚喜,一看到就讓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我腦海裏立刻浮現齣童年時,每次去阿姨傢,總會小心翼翼地從糖罐裏挑幾顆自己喜歡的糖果,那種滿足感至今難忘。所以,我猜想這位糖果阿姨,一定是一個非常懂得分享快樂的人,她的傢裏可能堆滿瞭各種五顔六色、形狀各異的糖果,散發著誘人的甜香。拜訪她,肯定不是一次簡單的拜訪,而是一次充滿奇幻色彩的旅程。也許,她會講述關於糖果的古老傳說,或者,她會用糖果來錶達她對生活的熱愛和對人生的感悟。我覺得,這本書就像一顆顆包裹著甜蜜的糖果,每一口都帶著不同的驚喜和迴味,它會帶領我們進入一個充滿想象力的世界,讓我們重新體驗那種純粹的快樂和幸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