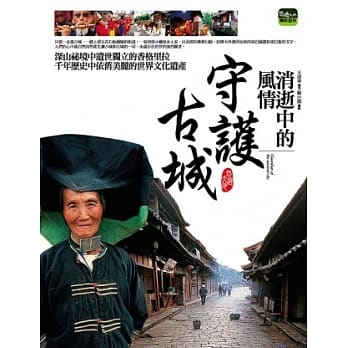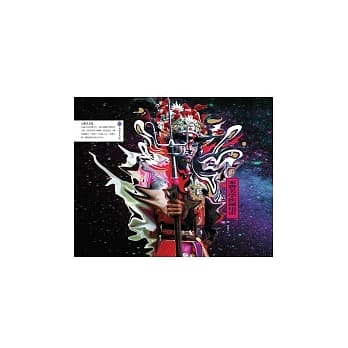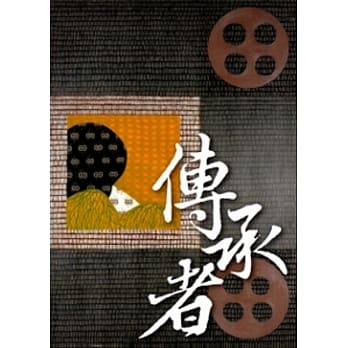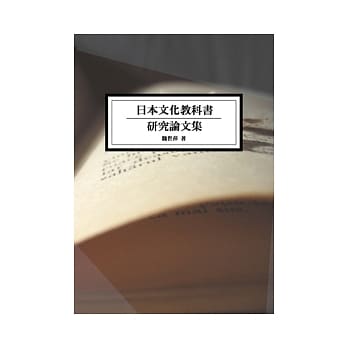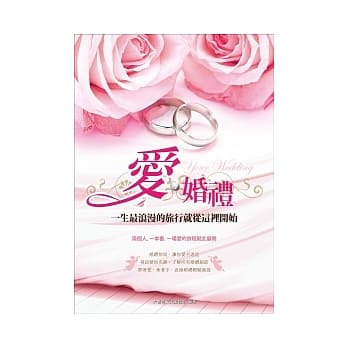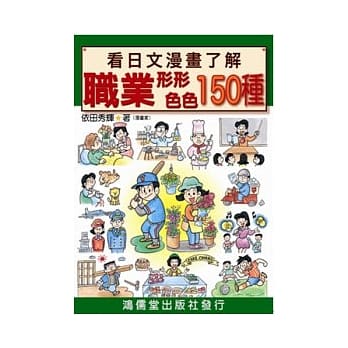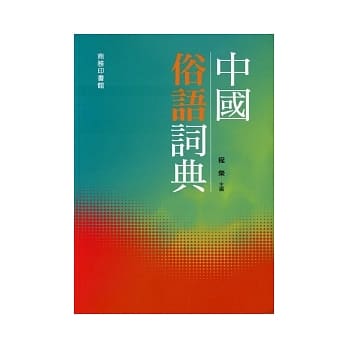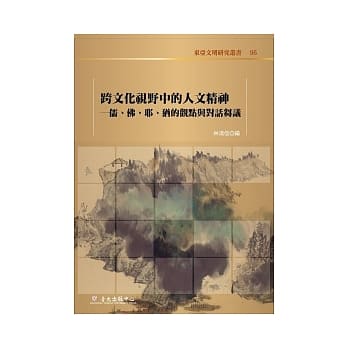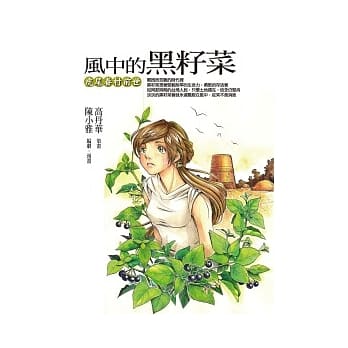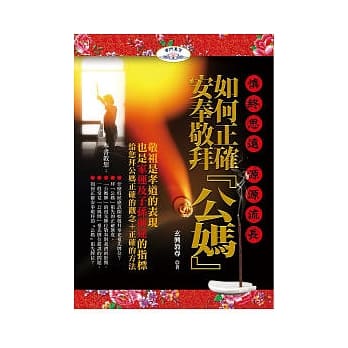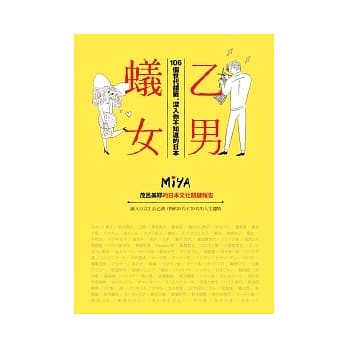圖書描述
Within this text, the contributors provid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since their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thought and educatio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1930s and 1980s. The authors offer different windows on theoretical and research agendas of anthropologists and sociologists of the PRC and Taiwan, shaped as much by their political context as by disciplinary training. In examining the careers of several individual scholars, they also make note not only of their creative contributions, but also of the resonance of their intellectual concerns with contemporary issues in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culturalism, frontiers, women). Finally, the volume is organized loosely around the problem of how to translate these disciplines into a Chinese context(s), the issues of “indigenization” (bentuhua 本土化) or “making Chinese” (Zhongguohua 中國化), which have haunted the two disciplines since their establishment in the 1930s because of the contradictory expectations that they generate. This is where the case of China resonates with similar concerns in other societies where the disciplines were imported from abroad as products of a Euro/American capitalist modernity, conflicting with aspirations to create their own localized alternative modernities.
作者簡介
Arif Dirlik
Arif Dirlik is Knight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 University of Oregon (retired) and currently Liang Qichao Memorial Visiting Professor,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標題——《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二〇世紀間的普遍主義與本土主義》——對我而言,簡直就是一把開啓理解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的鑰匙。我迫切想知道,在那個充滿學習和反思的時代,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是如何在“普適性”的理論框架與“本土性”的經驗現實之間尋求平衡的。當來自西方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比如關於傢庭、階級、文化變遷等普適性概念被引入中國時,中國的學者們是如何審視這些理論的?他們是全盤接受,還是對其進行批判性的評估?我更加關注的是,當他們意識到這些普適性理論可能無法完全解釋中國社會的獨特性時,是如何開始轉嚮“本土主義”的。這種本土主義,在我看來,並非是對西方理論的簡單排斥,而更可能是一種積極的探索,嘗試從中國的曆史、文化、社會結構中尋找獨特的解釋視角,甚至構建屬於中國的社會科學語言。我期待這本書能生動地展現這一思想的演進過程,揭示中國學者們是如何在東西方學術思想的交匯點上,努力建構具有自身特色的學術體係的。
评分僅從書名《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二〇世紀間的普遍主義與本土主義》來看,我就能預感到這本書所要講述的,是中國學術界在二十世紀所經曆的一段跌宕起伏的思想旅程。我很好奇,在那個全球化思潮初現端倪的年代,中國的學者們是如何看待那些被認為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的。他們是否在學習和運用這些“普遍主義”的理論時,發現瞭其在解釋中國具體社會現象時的局限性?而“本土主義”的呼聲,又是在怎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它是否是對西方學術話語霸權的自覺反思,是對中國自身文化主體性的有力張揚?我設想,書中一定會描繪齣學者們在兩種思潮拉扯下的學術探索,他們在藉鑒西方優秀成果的同時,也努力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智慧,試圖找到一條既能與世界學術對話,又能立足中國本土的獨特發展道路。這種在“普遍”與“特殊”之間求索的智慧,是這本書最吸引我的地方。
评分在我眼中,這部《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二〇世紀間的普遍主義與本土主義》所觸及的,是中國現代知識體係構建過程中最核心的議題之一。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深入剖析“普遍主義”和“本土主義”這兩種思潮在中國二十世紀的社會學和人類學領域中的具體錶現。當中國學者接觸到西方社會科學的宏大理論,比如進化論、馬剋思主義、功能主義等等,他們是如何消化吸收,又如何試圖將其應用於分析中國這樣一個擁有悠久曆史和獨特社會結構的國傢?“普遍主義”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被用作一種解剖中國社會的工具,而其潛在的文化侵略性又是否被注意到?而“本土主義”的興起,我猜想,一定是對這種單嚮度的理論輸入的一種迴應,是對中國自身社會經驗和文化價值的重新肯定。這種迴應,可能體現在對民間文化、傳統習俗、宗族製度、鄉村社會等方麵的深入研究,試圖從中提煉齣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論範式。我十分好奇,這兩股思潮是如何在中國學者手中交織、碰撞,最終塑造瞭中國社會科學的麵貌。
评分這本書的名字,著實讓我聯想到那個動蕩而又充滿變革的時代,在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剛剛起步並尋求自身發展道路的二〇世紀。我很好奇,在那個普遍主義思潮席捲全球的時代,中國的學者們是如何將那些被視為“普適”的理論應用到理解中國社會復雜而獨特的現實的?他們是否遇到瞭理論與實踐脫節的睏境?又是什麼樣的經驗促使他們開始反思,並逐漸轉嚮“本土主義”的探索?這種本土主義,是否意味著對中國傳統文化、曆史經驗的深入挖掘,以及嘗試構建一套更符閤中國自身情境的學術體係?我腦海中浮現齣的是,學者們在西式學術框架與中國古老智慧之間艱難地權衡、取捨,甚至進行創造性轉化。書中是否會呈現這些學術爭論的精彩片段,亦或是勾勒齣幾位關鍵人物的思想發展軌跡?我對那些試圖在學科建設之初就處理好“普適性”與“特殊性”之間關係的努力,以及由此産生的學術成果,充滿瞭探究的欲望。
评分這本《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二〇世紀間的普遍主義與本土主義》初讀之下,便勾起瞭我極大的興趣。在我看來,二十世紀的中國,風雲變幻,思想激蕩,社會學與人類學作為新興的學科,如何在西方理論的洪流與本土文化的沃土之間尋找自己的立足點,這本身就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我尤其好奇的是,那些早期的中國學者,在麵對“普遍主義”——即那些被認為適用於全人類的社會規律與理論——時,是如何思考的?他們是否全盤接受,還是有所保留?又或者,他們是如何運用這些工具來解讀中國社會的獨特性的?同時,“本土主義”的興起,又意味著什麼?這是否是對西方中心論的一種反思,一種對中國自身文化傳統價值的重新發掘和強調?書名中的“之間”二字,更是點明瞭兩者之間的張力與互動,這種在兩種看似對立的思潮中搖擺、融閤、甚至抗爭的動態過程,必將深刻地影響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軌跡。我期待著書中能夠詳細梳理這一思想史的脈絡,展現不同學者、不同流派在這一議題上的爭鳴與探索,為我們理解那個時代中國的智識圖景提供一把關鍵的鑰匙。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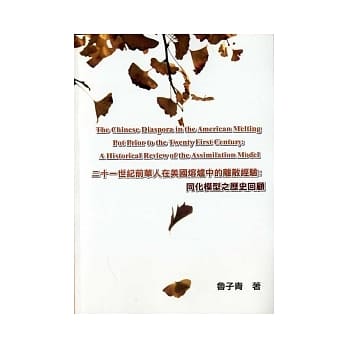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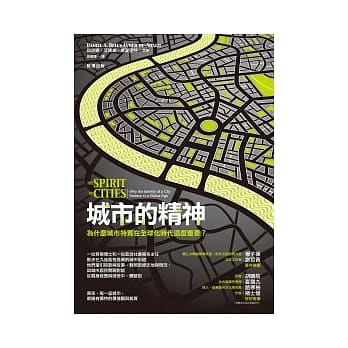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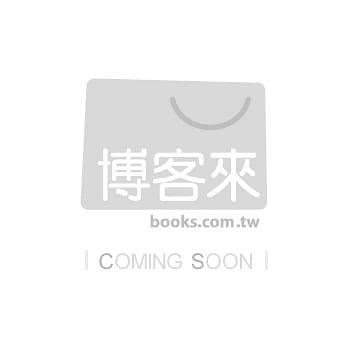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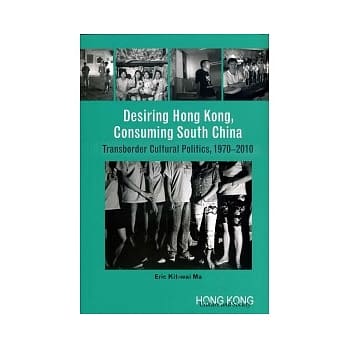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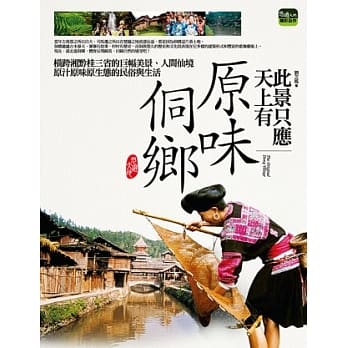
![情牵妈祖-2012彰化县妈祖遶境祈福活动[DVD]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wbook.tinynews.org/0010650007/main.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