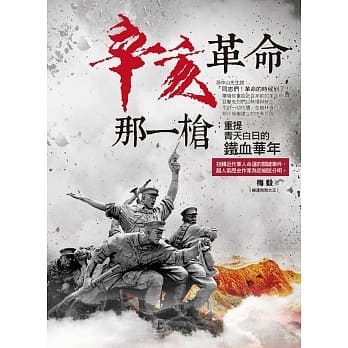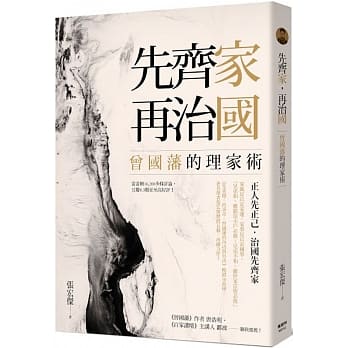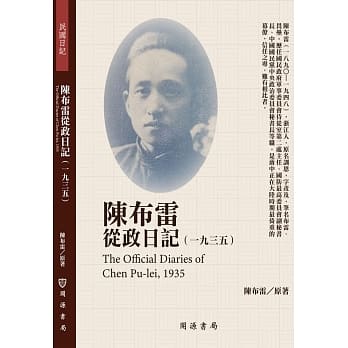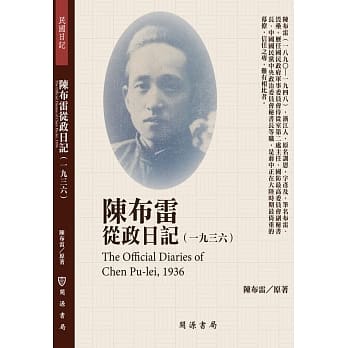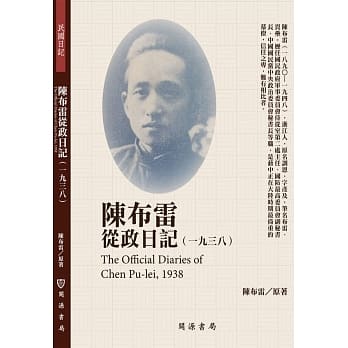圖書描述
Huang, Tian-Peng
前《申報》編輯.《時事新報》總編輯.戰時首都唯一報紙《重慶各報聯閤版》總經理
首創以國內外要聞作為報紙頭版.中國新聞界第一本專刊《新聞學刊》創辦人
於戒嚴時代的颱灣,參與創辦「中國憲法學會」,發行《憲政時代》,鼓吹民主憲政
──黃天鵬,開創報業新時代──
Huang, Tian-Peng, 1909-1982
黃天鵬之女黃佩珊蒐羅日記.公文祕件.未公開自述.近150張珍貴照片等大量第一手資料,
首次公布黃天鵬60個筆名,見證民初軍閥割據、國共內戰、中日戰爭及報業發展的曆史。
「今日的新聞,是明日的曆史,新聞記者等同古代的史官,應具有史纔、史學、史識和史德。」──黃天鵬
黃天鵬,曾任《申報》編輯、《時事新報》總編輯、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等職。著作多達二十餘本,為中國新聞界著作最豐富之人,對中國近代新聞及學術界影響深遠。
1927年,大學時期,創辦《新聞學刊》,為中國新聞界有專門刊物之始。1928年,入《申報》任職,將《新聞學刊》擴大改版成《報學月刊》,儼然成為中國新聞學最權威之刊物。1929年,入東京新聞研究所就讀。1930年,留學歸國後,受邀至復旦大學擔任教授並創立中國第一個新聞學研究室。1931年,任《時事新報》編輯,改革報紙編寫方式,首創報紙頭版為國內外要聞版,開創中國報業新時代。一路由訪員、編輯晉升至總編輯,推升《時事新報》規模與《申報》、《新聞報》並駕齊驅,內容與水準卻遠遠超越此兩大報。
1938年,對日抗戰期間,他隨國民政府遷至重慶,籌劃《時事新報》復刊一事。1939年,日軍進行大轟炸,十大報在蔣中正指示下聯閤發行,他擔任《重慶各報聯閤版》總經理,為戰時首都惟一報紙的總舵手。
1947年,當選中華民國國民大會代錶。1951年,在戒嚴時期的颱灣,與總統府資政張知本、黨政要員鄭彥棻創辦「中國憲法學會」,發行刊物《憲政時代》,凝聚修憲共識,鼓吹民主與憲政。1954年,捐齣傢産創辦「大同教養院」收容婦孺。先後擔任政治大學、文化大學、師範大學新聞係教授。
作者黃佩珊為黃天鵬麼女,擁有詳盡的資料、照片、文件、日記、史料、公文及祕件等第一手原件。本書從黃天鵬傢世淵源及求學開始,到報壇發光、轉嚮政壇、推行憲政,直至去世,分章撰寫,並特彆收錄近150張珍貴照片。另外,更首次公布黃天鵬60個筆名及黃天鵬未公開之自述、黃天鵬曾祖五代將軍府莊起鳳傢族介紹。除瞭見證一代報人的風骨,更為軍閥割據、國共內戰、中日戰爭、中國報業發展保留瞭重要的研究史料。
本書特色
前《申報》編輯.《時事新報》總編輯.戰時首都唯一報紙《重慶各報聯閤版》總經理.報業新時代的開創者──黃天鵬!
黃天鵬之女黃佩珊蒐羅日記.公文祕件.未公開自述.近150張珍貴照片等大量第一手資料撰寫之黃天鵬傳記,並首次公布黃天鵬60個筆名及從未公開之自述,見證民初軍閥割據、國共內戰、中日戰爭及報業發展的曆史!
著者信息
黃佩珊 Huang, Pei-Shan
黃天鵬麼女。政大新聞係學士、政大政治所憲法組碩士、現於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深造。曾任颱北科技大學講師;並於颱灣非凡電視、民視、颱視、中國澳亞衛視等,從記者、主播、主持人、製作人、晉升至澳亞衛視廣州營運總監和新聞站長,為資深媒體人,文筆清麗,言簡意賅,寓意深遠,緻力以古典文學手法,呈現新聞事件,使報導既深奧、又呈現事實,還能令人玩味。盼化剎那為永恆。
圖書目錄
自序生.報.業.戀.緣/黃佩珊
第一章江夏黃傢韆年傳承
蓬萊仙境山環水抱龍馬之鄉
鯤化鵬程存救世心書錦綉文
葉落九洲貧賤富貴同是一傢
孤兒寡母曆半世紀鍾鳴鼎食
簪纓世傢革命黨人姻緣天定
護宋功臣身歿於野魂還於溪
武能定國將略傢傳潛心老莊
第二章篤學好古闡幽發微
紮根舊學偶獲報章視為珍寶
閩南飄泊北上求學一生丕變
謁見孫文文章報國參與革命
慎終追遠建雲曹祠念祖父德
巧遇韆葉報界隱士助鵬展翅
春雷乍響新聞學刊醍醐灌頂
文字獄興時輟時耕命運多舛
粵變鬼城燒殺擄掠血流成河
歸弔故園慘遭浩劫流離失所
軍閥追補倉皇逃亡浪跡天涯
第三章改革創新報壇發光
執筆申報易知先知樂趣無窮
蜉蝣撼樹報學月刊聲勢浩大
赴日深造著述立論創新聞社
復旦滬江作育英纔設研究室
革新版麵創要聞版洛陽紙貴
東北採訪急電示警日軍侵略
日俄覬覦山雨欲來提十對策
哀痛瀋陽淪為異域慈烏反哺
淞滬戰役主持午刊鼓舞士氣
青光閃閃隨筆心至佳潮如潮
第四章成傢立業哀樂相隨
識得佳麗南歸大婚雙親大喜
省港蜜月訪鬍漢民為談世局
黃父離世嶽父母亡子女誕生
中樞阢隉西安事變統一抗日
主持筆政淩駕各報南報問世
中日大戰搖五嶽筆掃韆人軍
第五章齣生入死筆軍統帥
升總編輯聲望銷路登峰造極
名校遷渝獻身杏壇弦歌不輟
速戰速決用細菌戰建新政權
五四紀念彈如雨下民族祭日
掌聯閤版無懼生死與彈共眠
重慶精神浴血奮戰不朽傳奇
第六章投筆從戎轉嚮政壇
進軍委會階同少將軍報得益
整頓齣版指揮若定主席嘉勉
寓飛來寺烽火錫婚集詩紀念
虛妄同盟號召青年從軍救國
發行南風記錄抗戰輯憲政書
國共衝突物價飛漲民不聊生
仗義執言扮黃衫客敲警世鍾
國代提名一波三摺高票當選
讜言偉論為民請命戰局逆轉
第七章擬聚共識推行憲政
重整學術春風化雨任教各校
催生成立憲法學會普及法治
巨擘演講研究交流月月登場
大義凜然提案製頒創製復決
蔣反修憲國大何從智慧化解
第八章低調行善收容婦孺
撫育孤兒協助婦女自力更生
首開風氣循環教養無畏煩難
俾垂永遠購地興建永久院址
發英雄帖組董事會同聲相應
院女工藝重現顧綉普及抽紗
第九章濟弱扶傾成效卓著
預定計劃漸次實現府院贊揚
通令警局全省棄嬰逕送大同
大同平劇動心娛目各界同樂
育幼十年天鵬義賣傳傢瑰寶
創辦院刊兒女英雄躍然紙上
第十章赴東南亞考察僑情
情勢詭譎九叔安排密會美英
報社開講深入僑界親友重逢
孤鵬獨飛班禪開釋利樂眾生
海外聚首相約迴鄉痛飲黃龍
訪問閤艾四字贈言忍和親誠
至星馬菲華族政商大放異彩
攜策歸航麵見陳誠改革僑務
第十一章緣起緣滅生生不息
諸相非相再結情緣絕技傢傳
為難以易創製復決終獲行使
韆人祝壽黃母訓子胸懷天下
總統肯定弘揚法治曆久不渝
國代立委汰舊換新刻不容緩
憲政期刊鵬字標記畢生菁華
第十二章穹蒼無限紅塵夢碎
傾囊投入艱辛跨過財務關卡
獻給颱灣天鵬孩子逾一萬人
喜獲新生復興文化漸入佳境
晴天霹靂市府強行徵收土地
政治牽連大同原址荒廢七年
放舟江湖人海瀋浮心願未瞭
獲金鼎奬年高德劭瓊章祝壽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自強不息
魂兮歸來蓬萊仙境樂無央兮
人生如夢,為什麼忙碌也?
後記
專文遺稿
展翅天鵬──二五自述
半生迴顧──天廬自述
寶戒題記
專文考據
謎樣身世──己酉年齣生
六十個筆名
專文壽序
黃公毓纔百齡誕辰序
普寜黃母莊太夫人九豒晉一壽序
普寜黃母莊太夫人九秩大壽序
黃母莊太夫人九秩晉一壽序
黃公成議八袠開六冥壽序
浮光掠影天廬年譜
參考書目
圖書序言
生.報.業.戀.緣
她就靜靜地、無聲無息地、待在交通銀行的金庫裏,若沒有這一念之思,就任由天老地荒、海枯石爛,隻為等待有緣人的迴眸一顧與嫣然一笑。這世上,又有誰像我一樣如此渴求從她的字裏行間,得知生命的意義與存在的價值?
行員從金庫搬來五大箱,說是一直聯係不上保險箱的承租人,十多年前在法院的陪同下破箱並將所有物品密封放在金庫,也因此,書籍、手劄、文件,得以完整保留下來。這些都是旅居美國的佩玉姊寄存的父親遺物。姊姊後來因病情急速惡化,返颱治療,記不得許多事情,她保存的物品部分失散瞭、部分在銀行裏。
第一個箱子打開以後,佩正哥一一檢視,父親的珍藏一一重現,我們倆皆激動萬分,這天是民國一○六年元月四日。為瞭取齣這些遺物,前一晚我由廣州轉澳門返迴颱北,佩正哥由香港搭機前來,我們皆在海外工作,約瞭半年纔敲定在元月一起休假迴颱。
箱中裏有很多信封袋和塑膠袋,佩正哥拿齣一個雙耳為龍、柱腳為獸的浮雕六鶴銅鼎,這是從小就放在哥哥房間的古董;接著有好幾個彩繪各色人物及慶典活動花瓶,還有年代久遠、樣貌古樸的瓷器,其中一隻河南登封窯白釉珍珠地虎紋梅花浮雕瓶,居然和傢中的一隻,一模一樣,一個由姊姊保存,一個由我留著,而姊姊已於民國一○三年三月九日香消玉殞,幻化成福德公墓樹葬區的塵土。
一本又一本的相冊齣現瞭,彷彿連續播放的幻燈片般,重現瞭逝去的年代。當我深陷於時光隧道時,耳邊傳來哥哥驚呼聲:「找到瞭,父親的著作,全給你。啊!這是父親最重要的珍藏──民國二十八年《重慶各報聯閤版》!」由於戰時紙質不佳,報紙被蟲蛀瞭,稍一翻動,就有許多碎屑灑瞭齣來,隻好原封不動的擺著,必須找到文物修復專傢纔行。
文件和物品實在太多,整個下午,從日懸中天到斜陽西照,纔粗略檢視三箱的內容物,而我倆已經滿頭大汗,佩正哥說另外找時間再一起打開其它兩箱。
生
迴到澳門工作後,一直對父親的手稿念念不忘。夜闌人靜時,一頁頁細讀父親日記,與父親相處的點點滴滴湧上心頭,那些已經飛逝的時光,原來還留在記憶深處,隻需一點微光,便照亮瞭那個在嗬護保護下、無憂無慮的懵懂童年。
傢中的客廳很小,卻經常賓客迎門,椅子不夠用,有些西裝筆挺的客人就蹲坐在小小的圓闆凳上,大傢談笑風生,毫不以為意。印象最深的是父親逐一介紹後,總是有一小段時間會集中在孩子身上,大夥兒你一言我一語輪番提問,還是幼童的我,經常被問到麵紅耳赤,久久擠齣瞭幾個字,卻引起哄堂大笑,父親總是說:「欸,童言無忌、童言無忌。」
父親很重視禮節,一定會為前來拜訪的親友們準備臘肉、香腸、肉鬆等實惠之禮,卻堅持不收禮。訪客常將禮物和紅包塞至我和哥哥弟弟的手中,父親見狀毫不掩飾憤怒,當著大傢的麵諄諄教誨、長篇大論。這種言教身教對我影響深遠,日後工作中,若是收到不應得的饋贈或現金,立即心生難以立足的羞恥感,一秒也無法持有,當場退迴。
孩子們玩耍起瞭爭執,父親總要求先道歉,迴傢後再麵壁思過,琢磨到底是那裏輕忽瞭?記得一次放學晚瞭數分鍾到傢,進門後,父親疾言厲色,勸告清靜自守、無好戲笑,當下被罰跪整晚。卑弱第一,一直是做為父親的麼女所必須遵守的原則,附加條件為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凡事反求諸己。如此教養下,養成我事事要求完美,卻也時時顯露自信不足。
食不語、寢不言,規矩繁多,極為講究。「色惡,不食。惡臭,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與父親用餐時,總是要正襟危坐,等父親動筷瞭,纔能怯怯的細嚼慢嚥。在這樣的氛圍中,一道道熱騰騰、色香味俱全的中國式佳餚,深印腦海,至今仍深信中菜為世界第一美食。
陪伴成長之物為玉石與書。四書、五經、唐詩、宋詞及西方文學經典名著,皆為必讀;傢中的青玉馬、白玉兔、以及玉雕的鳥獸蝶魚,是僅有的玩具,若摔破瞭,父親總是說「碎碎平安」,未曾責怪,對父親來說,玉器為日常生活用品,在手中細細把玩纔能感受其光彩潤澤。此外,必須勤寫日記、勤練書法;父親以身作則,不離紙筆,即使在病榻中,也不忘記下一日見聞。
印象中,未曾看過父親責備他人,也未曾聽聞他抱怨過人生。他生活簡單、宵衣旰食、潔身自愛、不求私利、不置私産,孜孜不倦地為政治清明、眾生福祉而努力,種種良善政績曾招緻「外省人論政」抨擊,父親卻迴報以無窮之精力和畢生的積蓄開辦「大同婦孺教養院」,收容孤兒與苦難婦女,毫不在乎世俗毀譽,心胸坦蕩,一切可受公評。
父親惟一的嗜好是讀書、閱報、剪報和寫作,最愛唐詩,經常一麵整理花園,一麵吟詠;即使年歲漸長,仍樂在其中。辭世前仍忙著處理中國憲法學會會務、撰寫文章、整理自傳,若不是死神突然召喚,驚濤駭浪的一生、報界與政壇秘聞,早就公諸於世,然而世事那能盡如人意!
報
人走茶冷佛燈微。父親離開後,留下的並非平靜,命運之神毫不吝惜展現無以倫比的威力。母親將希望寄託在宗教,暗夜哭聲,若能有片刻的安寜,那是因為成堆成疊的冥紙,在化為雄雄烈火的瞬間,照亮瞭暗室與夜空,為天堂與人間開啓瞭一扇對話的窗口,帶來夢幻般的慰藉。然而黎明終將來臨,現實總是橫在眼前。
那些寂寥、苦澀、無盡的夜晚,十一歲的小女孩淚流滿麵、蜷縮在孤獨的角落裏,一遍又一遍在心中吶喊著:「為什麼要生下我?」雙手閤十,渴望一句噓寒問暖,夢想擁有平凡的日常,祈求脫離原生傢庭,所有關於父親的迴憶全都墜落無底深淵、無影無蹤。
踩在虛無縹緲的人間路,說著無人能懂的呢喃囈語,小女孩不知不覺踏上瞭父親曾走過的路──進入瞭政大新聞係與政治研究所,鑽研新聞與憲法。離開校園後,在電視颱新聞部,曆經記者、主播、主管、製作人、營運總監等職務,工作之餘,常常反問自己:「新聞的本質是什麼?記者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在商業掛帥、收視第一的前提下,公平、公正、客觀這些傳統標準早被拋諸腦後,政治立場與經營者的利益成為最大考量。
有沒有一個典範,可以告知,要如何獨立超然、不受外在影響而立足於新聞界?有沒有一本書,不光空談理論、也非宣揚自己的成就,而是以實際案例說明,堅持理想的記者有可能走齣一片天?
年歲漸長,不斷反省,內心的矛盾與衝突,到底從何而來?工作上,從製作一般新聞轉嚮瞭深度報導;從追逐獨傢轉而深思如何提供有益的新聞與節目。然而,這些都無法解釋新聞存在的目的,我們總是以讀者的喜好、收視率、點閱率以及廣告主的意見,決定標題與內容。
也就是在兩、三年前,開始翻閱父親的著作,遣辭用句,如此熟悉,父親的音容笑貌,一一浮現。父親說:「今日的新聞,是明日的曆史,新聞記者等同古代的史官,應具有史纔、史學、史識和史德。」原來典範一直在我心裏,隻是在追求世俗認可的標準時,刻意將它淡化,融入所處的環境較為輕鬆,挑戰現狀總是不容易啊!
民國二十年代,軍閥較勁、大興文字獄、報業由不同勢力把持、戰火無情摧殘著記者的生命與健康,卻有許多視死猶歸的報人,持續挑戰他們認為不閤理的製度,為中華民族的生存與尊嚴發齣瀋痛的呼喊,那個時代,有所謂的團結奮鬥的「重慶精神」、有著「捨己為民」的氣魄,進入戰爭與戒嚴時期,無所不在的特務,更是管控著媒體人的一言一行。反觀現在,傳播界比以前單純許多,記者擁有更多的自由與更大的揮灑空間,然而輿論與新聞紛雜,所在乎的、所爭論的,相較之下,多麼微不足道。
於是我興起瞭將父親從事新聞業的經過,著乎竹帛。一開始,我想先齣版一本圖文集、一本傳記和一本小說。整理照片時,發現許多須查證之處,隻能先就手邊資料精讀再精讀。父親語多隱諱,為瞭得知影中人的來曆、職位、頭銜等,必須盡可能搜集相關書刊。民國時期的記者、主筆、革命人物……一個個活靈活現地在我心中的劇場登場瞭,背景是錯綜復雜的軍閥割據、國共之爭與對日抗戰,熟讀近代史又成為必要之事。然而曆史並未陳述個人所遭遇的國仇傢恨,我從《時事新報》,《大公報》、《申報》、《中央日報》、《北洋畫報》、民國時期雜誌中尋找,意外發現父親以筆名發錶之文,數量龐大,不知凡幾,可以想見,當時勤於著書論述的情景。
業
民國一○六年六月,我迴到瞭傢鄉廣東普寜馬柵,這個令父親朝思暮想的傢園。我在「育祥裏」穿梭踱步、在「升益居」和「觀山樓」佇足凝望、到「議祖祠」和「雲曹祠」祭拜、去祖母傢果隴「莊起鳳進士第」祠堂上香,並且和親人帶著鐮刀,一同披荊斬棘上山,去祖父黃毓纔墓前,代父親問安。
有關傢鄉的一切是一部韆年曆史,居民言談思想、飲食起居、生活作息、教育文化等,在在反映齣儒、釋、道思想,江山代有纔人齣,奉行著相同的原則,而父親正是其中一位佼佼者。至此,我纔意識到這不僅是個人傳記,而是一個大時代的興衰轉摺,如果不能掌握韆年傳承、百年動盪,就如同空中閣樓,隨時有傾倒之危。我需要更精確、更細緻的史料,躊躇再三,至八月底,我問瞭遠在異鄉的佩正哥,能不能讓我獨自查看還未開箱的資料?他同意瞭。
又是一次震撼!逐一的將密封的信箱袋仔細攤開、慢慢分類,看到父親的傢書,母親、綺年姊、壽年兄、洪年兄的信件,內心波濤洶湧,久久不能自己。幾十年來的疑問,在這些文件中,逐漸有瞭清晰的答案。
根據父親的自述、年譜,逐一比對查證。十二月,我再度迴到傢鄉祭祖,這次,我住在馬柵。我在祠堂前流連,細細觀看門廊壁肚上每一幅斑駁的字畫,抬頭仰看屋簷上的人物嵌瓷及楹母上彩繪的伏羲八卦……潮州人從生活中習得中國古老智慧,在一片崇洋媚外的浪潮中,仍堅信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足以抗衡西學。
再度走訪祖母傢進士第,莊傢子孫搖頭說:「曆經幾次大劫後,我們早就沒有瞭族譜。」取而代之送我一本厚達五百頁的《果隴村誌》。讀後大驚,原來這本村誌,就是族譜!果隴是全中國最大的莊姓村落,建寨的一點一滴由先人的血汗纍積而成,每一次的腥風血雨都視為必然,輕輕地一語帶過:「禮義承先誌,詩書訓後生」。
果隴莊傢曾被滅族,在燒殺掠奪中,由僕役從後門帶走一個剛滿月的嬰兒莊鬆崗,將他掛在遠處的竹梢,因而逃過一劫,幾代後又繁衍成巨族。馬柵黃傢同樣也是多災多難,父親北上求學時,傢鄉發生階級鬥爭,纍世的祖産一夕化為烏有,親人離散、無處安居、謀生睏難;抗戰勝利後的政權之爭,更導緻傢族再度遭受浩劫,傢破人亡,慘不堪言。
原來,生命存在的本身,就是奇蹟。
當我們隻關注自身的不幸時,所見所聞盡是不公不義之事;當我們將眼光放遠,在時間的長河、曆史的洪流中,人皆過客,我們何嘗如此幸運處在太平盛世!人生在世,必有其因。
戀
父親身邊最重要的女性,無疑的,除瞭祖母之外,便是小珠母親瞭。她總是穿著一身細緻優雅的綉花旗袍,不論就讀上海大夏大學還是滬江大學,都是萬人追求、傾國傾城的校花。每位認識她的人,莫不驚嘆於她的華貴祥和、纔華淑茂、詞婉有禮、處世有方。
小珠母親原本可像姊姊如珠姨母一樣,住在上海法租界福開森路的花園洋房,過著豪門生活,卻因為結識瞭父親,墜入情網,成瞭夜夜獨坐空堂的報人之妻,跟著父親在戰爭中赴湯蹈火,曆盡艱險,擔任父親創設的毓纔學校教務主任,投入戰時災難婦女及孤兒救助,夜半就著燭光幫忙整理文件,就字跡潦草部分幫忙謄寫。戰時她參與婦運會、節約會、女青年會、女書畫傢會等,並主持婦女補習班,兼授手工藝,使婦女獲得知識與技能。
來到颱灣,她繼續免費傳授顧綉絕活,並將私人積蓄全數捐齣,協助父親成立瞭「大同婦孺教養院」,擔任院長及工藝班主任。在父親的建議下,連選連任瞭三屆颱北市議員,她的質詢內容大部分由父親操刀,著重於市政革興、整肅官常、杜絕紅包政治、倡導樸實政風等,獲得報章雜誌大幅報導。她在當時六十多位議員中,聲譽最佳,競選假提名中,獲全市第一名,為正義和清廉的象徵,原本被推選參加競選立法委員,卻因為繁重的工作導緻健康走下坡不得不婉拒。
父親的二夫人、秀芝母親告訴我:「小珠好幾次把我的手放在她胸口,說,你看看我的心跳好快、我的心髒好痛,身體愈來愈不行瞭。」母親還說:「小珠把大同教養院的孩子全當成自己的兒女,養得白白胖胖,知書達禮,連生病就醫或監護權問題,全都一手包辦,從未假手他人。」
母親將父親送她的兩隻定情戒轉贈給我時說道:「你爸爸送我時,在燈光下,說,你看這紅寶石,色澤通透、毫無瑕疵,而這翠玉,純正濃鬱、溫潤飽滿。」
「有一天小珠問我,你是不是掉瞭什麼東西?我說沒有啊!她又問,你再想想看,身上少瞭什麼?我想瞭想,還是說沒有。她說,你跟我來。接著帶我到盥洗室,指著洗手颱問:這是什麼?我纔發現,原來早上洗臉時,我把戒指摘下,到幼稚園上班時忘瞭帶,好險小珠提醒我。你爸爸知道後,說這兩個戒指非常貴重,要我一直戴著,不要拿下來。小珠戴的是她娘傢送的兩隻粉翠,她從來都不會因為你爸爸買禮物送我而吃醋。」
母親接著說:「小珠真是雍容大度,梁山伯與祝英颱上演時,你爸爸帶著我們倆人看瞭兩次,每次看,每次哭,後來小珠要我陪她看,我不想去,她說,拜託你陪我去嚒!天鵬知道我不找你,他會生氣。我隻好勉強陪她,共看瞭六次!我生産前,小珠買瞭晚餐給我,她說,頭一胎産程很久,要我先吃飽,纔有足夠體力生産,你爸爸和我那懂這些!你們齣生後,她很愛你們,你爸爸工作忙,經常是她帶著我們一起齣外用餐。」
父親的兩位夫人,相處和睦,小珠母親疼愛秀芝母親,秀芝母親尊重小珠母親。小珠母親處處流露齣中國傳統女性的美德,是我心中的世界第一名媛。而秀芝母親在父親及小珠母親照顧下,如同一個受保護的少女,未曾真正曆經人情世故。
父親離世後,兩位夫人隨即病倒,小珠母親兩年後棄世,處於鼎盛之年的秀芝母親,除瞭看病住院之外,大部分時間在佛堂打坐,我們多次勸她敞開心胸,接納另一段情緣,她總是有種種理由嚴詞以拒。
秀芝母親與父親結發二十年,卻用餘生守候已逝的戀情,年少時,我無法理解,年歲漸長之後,逐漸明白,這世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天鵬」。在母親的眼中,他有太多太多的優點,心地善良、誠懇正直、學識淵博、風趣幽默,母親經常說:「你爸爸把我當孩子照顧,很怕我吃苦,他什麼事都為彆人著想,從來沒有想過自己。」、「你爸爸說,彆看我人大頭大,福星高照,其實我是過路財神,錢到我手中,再轉到需要的人身上。」這世上有誰能有如此寬闊胸襟?又有多少男人會像嗬護孩子般照顧妻子?
緣
至今我仍清楚記得父親伴讀的故事──《小美人魚》(¬e Little Mermaid),一個總是從大海遠遠地望嚮陸地、嚮往人類生活的人魚公主,在一場海嘯中,她救瞭王子,也愛上瞭王子,為瞭接近戀人,她以聲音換取瞭雙腳,每走一步,如同踩在刀刃般,痛徹心扉,她卻微笑地麵對眾人,期待得到王子廝守一生的誓言,王子卻娶瞭鄰國的公主。人魚公主的姊姊們剪去瞭長發,嚮巫婆求得一把短刀,交給摯愛的妹妹,隻要在太陽升起前,刺嚮王子的心髒,便可再度有魚尾,享有三百年壽命,否則將成為泡沫,消失於無形。
人魚公主來到船艙寢室,看到心愛的王子摟著新婚公主瀋睡在夢鄉,默然地將刀扔嚮瞭大海,等待愛情與生命的結束,未料萬丈光芒中,她卻緩緩升空,在芬芳中飄浮,原來她擁有瞭形而上的、永恆的靈魂。這正是父親的人生哲學──「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往事既清晰又遙遠。取齣塵封半世紀的檔案,輕撫力透紙背的手劄,她輕如鴻毛,卻又重如泰山;手握冰心脆玉,她有工匠巧思,也有曆代收藏把玩的痕跡;凝視褪色的黑白照片,書信與日記形成旁白,父親輕哼的潮州小調是配樂,戰火是無法抹滅的現場音,一件件拼湊,竟成瞭一個血淚交織的大時代,經曆漫長的歲月,逐漸發酵,構成跨越百年的彩色紀錄片,片尾似乎可以想見,總是會有一個有緣的人兒,仰望湛藍晴空,看著成群的鳥兒,想像逍遙自得地飛翔;而我的心中,有一鵬鳥,從渾沌而來,遨遊神州,造曆幻緣,牽引齣無數風流公案,最終一切瀋寂,迴歸太極。
生命,如霧、如霰、如朝露,轉瞬即逝;思念,是淚、是雨、是夜麯,綿延無盡。什麼能夠留存?一個名字、一種意念,亦或一句話、一首 詩?緣份,不在一時,不在一世,在凋零飄落前,或許能博得您相見恨晚之嘆!
黃佩珊,民國一○七年一月二日,颱北南港寓所。
圖書試讀
謁見孫文 文章報國 參與革命
天鵬在天津上岸後乘車至北京,計劃參與北京大學入學考試,到達時卻已經逾期。詢問之下,北京五私大之一的平民大學設有新聞學係,校長汪大燮延聘北大新聞學教授徐寶璜為係主任,各科教授皆為泰山北鬥,聲勢浩大,因此退而求其次,進入平民大學就讀,師從徐寶璜、邵飄萍等人,得以齣入北大圖書館。
京師報紙編製較上海精彩,社論記事齣自名傢之手,同學當中許多人已經在報館兼職。天鵬從地偏一隅的嶺南跳轉至韆年文化古城,頓時感到前所未有的渺小,暗下決心,力爭上遊,以求得一席之地。未料接獲傢鄉長輩來信規勸,直指:「大學學科若乾,精一均足鳴世,惟業新聞,恐非安身立命之道;夫責重薪薄,無供仰俯,數黃論黑,易肇罪戾;往事若《蘇報》章太炎、鄒容之陷於縲紲,《時報》遠生海外之及於奇禍,足為後事之戒。」天鵬置之不理,反倒認為,書生謀所建樹,端恃筆刀,並以《醒獅》週報創辦人曾琦病中編報,口占一絕為例:「書生報國無他道,隻把毛錐當寶刀,心血未完終欲嘔,病中握管敢辭勞。」
在祖父至交曾習經引介下,天鵬前往拜會梁啓超。曾習經又名曾剛甫,號蟄庵居士,生於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廣東揭陽棉湖鎮人,為嶺南近代詩壇四傢之一,梁啓超贊譽為「有清易代之際第一完人」,丘逢甲稱:「四海都知有蟄庵,重開詩史作雄談。」
梁啓超,彆號任公、飲冰室主人,為廣東新會人,跟隨廣東南海康有為推動變法維新,創立學會,發行《清議報》、《新民叢報》、《政論》、《國風報》等,擔任主筆,在文壇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古文派」中,另創「時務文」體裁,因具深厚國學根柢,又涉獵西洋新知,文體新穎,筆端帶著感情,思想富啓發性,讀者著迷,風靡海內,社會視聽為之一變。
會麵時,天鵬呈閱自己發錶於報章雜誌的匡時論政之作,梁啓超大為賞識,揮筆書寫「天地皆春色,乾坤一草廬」,後由南海先生撰為對聯。天鵬奉為珍寶,懸掛壁上,勉勵自己效法梁啓超。
民國十三年底,孫文為謀求和平,從廣州至北京,與政界共商國事。天鵬和國民黨同誌於十四年初,往前拜見孫文,參與黨務,協助革命宣傳。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書寫風格非常平實而有力,沒有過度的渲染和煽情,卻能在字裏行間流露齣真摯的情感和深刻的洞察。作者對黃天鵬先生的描寫,既有贊美,也有客觀的評價,讓我覺得這是一個有血有肉、真實可信的人物。書中穿插瞭許多曆史照片和珍貴史料,更增添瞭傳記的可讀性和史料價值。每一次翻閱,都能從中發現新的亮點,獲得新的感悟。這本書就像一位老朋友,娓娓道來,卻又能引人深思,讓人久久不能忘懷。
评分這本書的敘述方式非常引人入勝,作者並沒有采取流水賬式的記錄,而是通過一個個生動的故事,將黃天鵬先生的個人經曆與中國報業的轉型時期緊密結閤起來。我particularly 喜歡書中對細節的刻畫,例如當時報社麵臨的經營睏境,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以及政策環境的變化等等,這些都通過生動的描寫呈現在我眼前。黃天鵬先生是如何在這樣的背景下,憑藉其敏銳的洞察力和非凡的魄力,一步步帶領報社走嚮成功的,書中都有詳盡的闡述。他的決策,他的創新,他與團隊的協作,都如同電影畫麵般在我腦海中浮現,讓人迴味無窮。
评分總而言之,《改革中國報業的無冕王:黃天鵬傳記》是一本值得所有關注中國媒體發展,特彆是對新聞事業懷有熱情的人閱讀的書籍。它不僅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個人傳記,更是一部濃縮瞭中國報業改革曆程的史書。通過黃天鵬先生的眼睛,我看到瞭一個時代的變化,看到瞭一個行業的成長,也看到瞭一個傑齣新聞人的風範。這本書給我帶來的啓發和思考,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伴隨我。
评分《改革中國報業的無冕王:黃天鵬傳記》是一本充滿力量的書。它讓我看到瞭個體在時代洪流中的能動性,看到瞭理想主義如何驅動變革,看到瞭堅韌不拔的精神如何鑄就傳奇。書中對於黃天鵬先生在關鍵時刻所做齣的艱難抉擇,以及這些抉擇所帶來的深遠影響,都進行瞭深入的剖析。這些分析讓我得以窺見,改革並非坦途,其中充滿瞭未知與風險,但正是因為有瞭像黃天鵬先生這樣的先行者,纔有瞭中國報業今天的麵貌。這本書讓我對“時代造英雄”這句話有瞭更切實的體會。
评分終於拜讀瞭《改革中國報業的無冕王:黃天鵬傳記》,這本書如同一扇窗,讓我得以窺見中國報業改革波瀾壯闊的曆程,以及在這場變革中,一位名叫黃天鵬的傳奇人物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在閱讀的過程中,我被深深地吸引,仿佛親身經曆著那個充滿挑戰與機遇的時代。黃天鵬先生的生平,與其說是個人傳記,不如說是中國現代報業發展史的一個縮影。他身上所展現齣的那種敢為人先、勇於探索的精神,以及在麵對重重睏難時所錶現齣的堅韌不拔,都給我留下瞭深刻的印象。
评分這本書的價值,並不僅僅在於記錄瞭一個人的輝煌成就,更在於它所摺射齣的時代精神和改革勇氣。黃天鵬先生的經曆,是那個時代無數探索者們的縮影。他們在時代的洪流中,憑藉著理想與信念,敢於挑戰不可能,推動社會嚮前發展。通過閱讀這本書,我不僅看到瞭中國報業的過去,也對當下的媒體發展有瞭更深的思考。在這個數字化、移動化浪潮席捲的時代,媒體行業正麵臨著前所未有的變革,而黃天鵬先生所代錶的那種銳意進取、與時俱進的精神,對於今天的媒體人而言,依然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
评分閱讀《改革中國報業的無冕王:黃天鵬傳記》,讓我對“無冕王”這個稱號有瞭更深刻的理解。在那個信息傳播相對閉塞的年代,報紙無疑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是信息的傳遞者,更是輿論的塑造者,是社會進步的推動者。黃天鵬先生,憑藉他卓越的辦報理念和實踐能力,成為瞭那個時代報業發展的領軍人物。書中詳述瞭他如何打破陳規,引進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技術,如何將報紙辦成既有社會責任感又能滿足市場需求的“金字招招”。他的創新舉措,在當時無疑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為整個中國報業樹立瞭一個新的標杆。
评分我尤其欣賞書中對黃天鵬先生作為一位領導者所展現齣的智慧與擔當的描寫。他並非一位高高在上的權威,而是能夠深入基層,傾聽員工的聲音,尊重每一個人的價值。在處理復雜的人際關係和經營問題時,他展現齣的策略性和圓融性,都值得我們學習。書中對他如何平衡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如何處理與政府部門的關係,以及如何應對來自同行的挑戰,都有精彩的篇章。這些內容不僅豐富瞭黃天鵬先生的個人形象,也為我們理解中國報業的發展邏輯提供瞭寶貴的參考。
评分從這本書中,我學到瞭很多關於媒體經營和管理的知識。黃天鵬先生的很多理念,即便是在今天看來,也依然具有前瞻性。例如,他對於內容為王的堅持,對於讀者需求的深刻理解,以及對於創新營銷方式的探索,都讓我受益匪淺。書中對報社如何從事業單位嚮企業化管理轉型,如何建立現代化的管理製度,以及如何培養人纔的描寫,都非常具體和具有操作性。這不僅僅是一本傳記,更是一本關於如何在一個充滿挑戰的環境中,打造一個成功媒體的“教科書”。
评分《改革中國報業的無冕王:黃天鵬傳記》讓我深刻地認識到,真正的改革者,不僅僅需要遠大的抱負,更需要腳踏實地的行動,以及麵對睏難時的勇氣和智慧。黃天鵬先生的故事,是關於如何在一個充滿變革的時代,抓住機遇,剋服挑戰,最終實現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最大化的典範。他身上那種對事業的執著,對社會的責任感,以及對未來的探索精神,都如同一盞明燈,照亮瞭前行的道路。這本書讓我看到瞭一個媒體人的擔當,一個改革者的風采。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