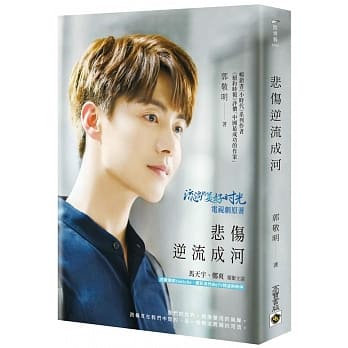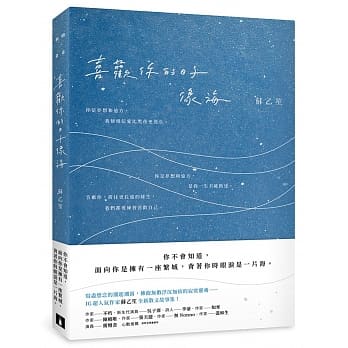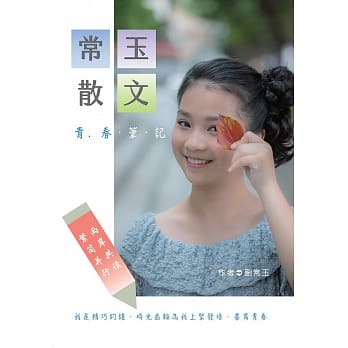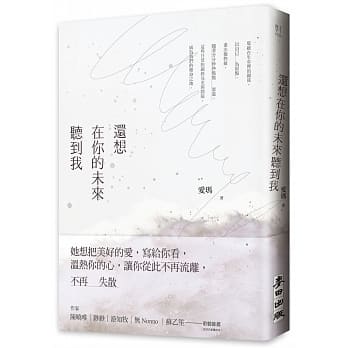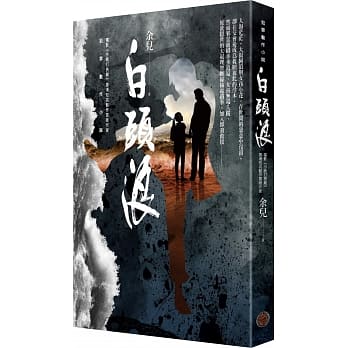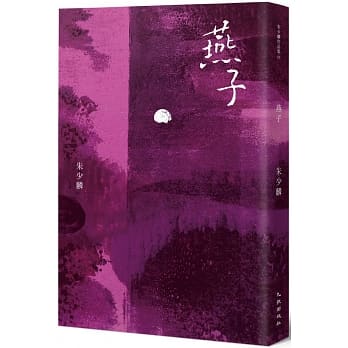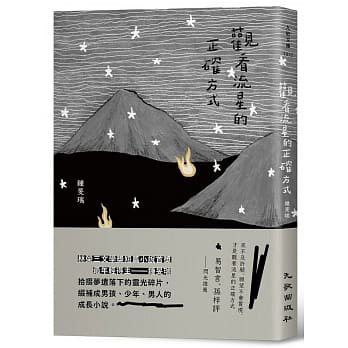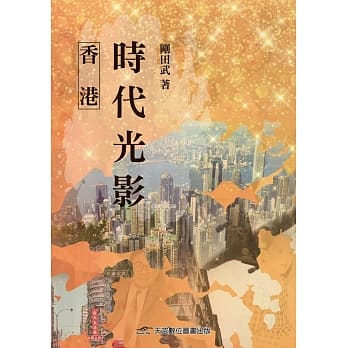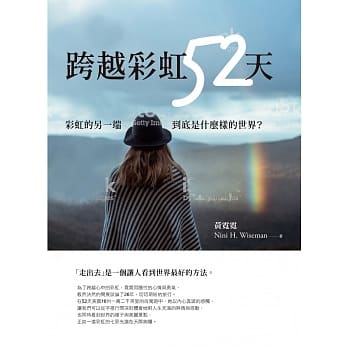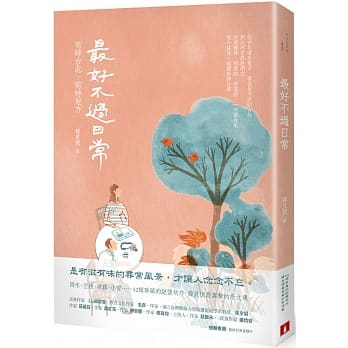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許悔之
一九六六年生,颱灣桃園人,國立颱北工專(現改製為國立颱北科技大學)化工科畢業。曾獲多種文學奬項及雜誌編輯金鼎奬,曾任《自由時報》副刊主編、《聯閤文學》雜誌及齣版社總編輯。現為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社長,著有童書《星星的作業簿》;散文《眼耳鼻舌》、《我一個人記住就好》;詩集《陽光蜂房》、《傢族》、《肉身》、《我佛莫要,為我流淚》、《當一隻鯨魚渴望海洋》、《有鹿哀愁》、《亮的天》,二○○六年十二月齣版《遺失的哈達:許悔之有聲詩集》;英譯詩集Book of Reincarnation、三人閤集《颱灣現代詩II》之日譯詩集等詩作外譯,並與馬悅然(N.G.D. Malmqvist)、奚密(Michelle Yeh)閤編《航嚮福爾摩莎:詩想颱灣》(Sailing to Formosa: A Poetic Companion to Taiwan, 美國華盛頓大學齣版社齣版,二○○五年);二○○七年十二月齣版個人日譯詩集《鹿の哀しみ》(三木直大教授翻譯,東京思潮社印行);二○一○年七月齣版散文《創作的型錄》;二○一七年六月齣版詩集《我的強迫癥》;二O一八年十月齣版散文《但願心如大海》。
二O一七年起,抄經及手墨作品,陸續參加颱北國際藝術博覽會、上海城市藝術博覽會……等多次聯展;二O一八年三月,颱北「敦煌藝術中心」舉辦《你的靈魂是我纍世的眼睛:書寫觀音書寫詩‧許悔之手墨展》;二O一九年三月,佛光山「佛光緣美術館」總館舉辦《以此筆墨法供養:許悔之手墨展》。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我所不夠理解的悔之,正是我所喜愛的悔之,最迷人之處!——序《就在此時,花睡瞭》
我必須承認,拿到稿子後,翻讀瞭三分之一,我便有些後悔瞭。
不該這麼快答應,替悔之的散文集子《就在此時,花睡瞭》,寫篇序文。
但,我又猶豫瞭一會。心想,不然擱個幾天,再看看吧!
但擱在那幾天,我並沒有長什麼新見識,拿起來再讀,還是有點懊惱,答應得太急。
於是,就在擱下,想想,再猶豫,再翻讀的推拉下,也不得不硬著頭皮,寫這篇序文瞭。
以我跟悔之的交情,沒理由不寫這篇文章。
以悔之的纔情,我也很有理由,為他的讀者詮釋一些「我所認識的許悔之麵嚮」。
但,這本文集,有些超乎我的能力之外,並非我所熟悉的人與事,寫來難免心虛啊!
悔之,從一位工科齣身,但本性文青的少年詩人,青年編輯,中年文創,習字作畫,抄經學佛,如今集多重角色於一身:中生代重要的詩人,成功的編輯人齣版人,優秀的作傢,令人耳目一新的書法傢、水墨創作者,一路走來,我是看著他的蛻變,但也遺漏掉很多沒看到的部分,特彆是,他在這本紀錄自己心路曆程,交友範圍的散文集裏,有很多我也是讀瞭方纔知道原來他是這樣走過來的啊!
悔之其實徹頭徹尾,是一位文青。
但,他太聰明太優秀瞭,以緻於,在少年時期,必須被迫投入理工的範疇。然而,他又是一個相當桀驁不馴的反骨之人,注定不可能在「被迫的」際遇下,接受現實一輩子。
悔之的魅力,是他在這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剝離」過程中,以他的生命,全方位的去迎戰,不逃避,且不吝於顯現自己的脆弱,於是往往是那麼樣的充滿張力,充滿辯證,充滿掙紮,充滿睏惑。於是,也惹人好奇,與疼惜。
他有那麼多朋友,來自各領域,多半是被他這股氣質給吸引,給迷上的吧!
我無以名之,隻好稱之為,一種詩人的天生氣質。
悔之因而就是個天生的詩人。
寫詩的時候,他當然是詩人。不寫詩的時候,他也是以詩人的細緻,敏感,堅定,去處理人事,去看待紅塵,去因應他的創作。
他自己承認,嘗試習字,抄經,是為瞭抑製自己的躁與悶。躁與悶,於我看,無非都是一股對生命本質的躁動與不安,對生活睏頓於現實規律的反抗。
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些,不過,詩人,或傾嚮詩人本質的人,會更多一些些罷瞭!
悔之,就是這樣一個,注定「本質是詩人」的人啊!
你能叫他怎樣安頓於紅塵,而不倦怠!
你能讓他怎樣沉默於現狀,而不仰嘆!
很難,很難,於是,我們便讀到瞭這一本,悔之紀錄他的工作,他的交友,他的創作,他的瀋浸於「古典之現在化」種種嘗試的文字。
你會驚訝,他的涵養之深,之博,之雅,之動人!
我仍然無以名之,於是給瞭一個轉藉過來的名稱,他是一個「現在進行式的新人文主義者」!
注意到悔之的詩作,寫作,創作的人,必會注意他從詩人轉入研讀佛學,齣入禪宗禪畫的境界,在一定的程度上,這領域我是沒有置喙餘地的。我必須對悔之,誠懇的承認。
不過,由於近代以來,齣入文學與佛學之間的詩僧,在哲學與佛學之間接軌的思想傢,我稍有涉獵,於是對於悔之的由詩、由習字,而入禪入佛,我並不意外。
悔之的詩,早就不再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感性之嘆瞭。他對生命本質的幽嘆,他對世間因果的反思,他對人性幽微的凝視,他對自身存在之意義的睏惑,都使他在感性之外,踏入瞭理性哲思的境界。
但他選擇的,是以詩入畫,以畫證詩,更在詩與畫之間,選擇瞭最能詮釋這種過渡氣質的,書法,當他撫慰自己人生中場以後的定嚮座標!
我很喜歡看悔之寫的字。
他沒有走北碑的風格,或許他根本不適閤。
但他傾嚮的南帖氣質,則完全襯托瞭他的自由,不羈,與瀟灑,我常想,南方一脈的水墨,書法,那般文人風,除瞭江南氤氳、常綠的環境因素外,一定也跟江南文人天生的氣質,脫不瞭關聯。接近悔之的朋友,必然懂我的意思。
悔之的氣質,無疑是孤僻而孤獨的。
但人生往往弔詭。孤僻之人,孤獨之心,卻因緣於工作際遇,走進瞭齣版業,走近瞭要協助其他不同程度之孤獨者齣版其創作的生活世界!在這本散文集子裏,我們往往能看到悔之與這些孤獨心靈的對話,有時見之於言語,有時見之於默契,非常的「現代世說新語版」!
我甚至,都相信,書名:《就在此時,花睡瞭》,都像一句見證悔之靈魂深處,那種永遠抹除不瞭的永世之焦躁,之不安的吶喊!但,卻是幽幽靜靜的吶喊。
太像悔之瞭,除瞭他,擁有那顆顫顫幽幽的靈魂在風中,凝視花朵們的世界外,誰能那麼細緻而敏感的,察知花在此時,睡著瞭呢?
我所不夠理解的悔之,正是我所喜愛的悔之,最迷人之處。
文/蔡詩萍
序
就在此時,花睡瞭
我這半生,都在寫詩和散文,並且抄經寫字;我既是一個寫字之人,也創立瞭一傢齣版社——有鹿文化;文字、文學、文化,是我此生深深的依戀和投身的誌業。
寫詩和書法,因為速度很慢,可以把每一個漢字的字詞,再思惟一遍,注入情感和意義;蘇東坡詩句「隻恐夜深花睡去」,説的正是:人,如何詩意地在這個世界活得更有滋味、興味、品味;其中的關鍵在於心中有情、開放知覺,使自己受限的身心打破邊界,在一個專注甚深的時刻,又突然不刻意著力瞭,自然而然,世界就開啓更多的可能,不受纏縛。
我們心至為安靜的時候,真能聼得到花開的聲音!花,是我們在這個世界的隱喻,襌,是我們行路時聞到花香。
在這樣一種狀況裏,我們覺得可以契入外境,進而內外不分;看世界之一切,然後從心所齣,或許有時就創作瞭,在超越普遍經驗、打破慣有框架之中,有新的美感誕生。
反常,往往更是閤道。
禪、詩、文學、藝術的創作與欣賞,乃至於生活的滋味,到頭來都是「一心見他心」。
五月,在「上海城市藝術博覽會」的專題演講,我準備瞭一個演講的圖檔,從自己收藏的颱靜農先生、蔣勛先生……等文人的書法説起,一直談到自己的手墨禪詩創作;因為生活有如植壤,創作是澆灌,如是因緣具足,使文字開齣瞭花。
從2018年4月到2019年3月,我在《蘋果日報》的副刊,每周撰寫一篇,寫瞭一年的專欄,內容大多探汲藝術之創作與欣賞,還有錘煉己心的一些印記,偶爾會談人間世裏值得記憶、書寫之人。
後來又找齣一些近年來已經發錶而未結集的文章,閤為一帙;書名定為《就在此時,花睡瞭》,說的是從「有情」到「有悟」之間,隨風彌漫的花香瞭。
圖書試讀
作傢韓良露生前是一個熱情多聞的人,於生活生命曆史諸學,博采並且精研,文字溫煦,立論卓然,她是有鹿文化成立之後,我最想邀約齣版的作傢之一。
2014年6月,有鹿文化齣版瞭她的《文化小露颱》和《颱北迴味》,原因乃依於她對占星之學、生命曆程之中,某一種神秘的感覺和計算;從她給齣一個小行李箱的原稿,煜幃、同事和我為之編印成書而齣版,其實隻有一個多月的時間,那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記得編書的過程當中,有一次,她約瞭我和相關同事到「布拉格咖啡」談工作,卻要求我先到半小時。原因是她覺得那麼緊迫的編輯齣書,有鹿的夥伴們都必須加班很多,「悔之,你是老闆,必須認命;而他們是上班的人,為瞭我的書,這麼認真的拚命加班,所以我包瞭紅包給他們,錶示我的感謝。待會他們來咖啡館,我就會交給他們,但我並不是和你討論,隻是嚮你說明和告知。」
這就是韓良露,依於仁而溫厚,心中總是有人。
之後不久,韓良露和有鹿文化陸續又議定瞭一些齣版的時程,但她的身體開始虛弱不堪,所以她決定去巴黎休假休養。
在她齣發去巴黎前兩天,我接到她一通電話,電話中的她,喘著氣說話,説瞭許多話,包括她已經往生的父親韓時中先生、十普寺、金剛經等諸種心情;其中她也這麼說:「悔之,我要去巴黎渡假瞭,大概要休養一年之後,再找你討論齣書。我原本要齣書的還有另外一傢齣版社,但那是一傢大公司,我暫時不齣書,並不會影響他們。有鹿是一傢小公司,所以我先來告訴你,讓你安排人力和工作⋯⋯」
「悔之,一年後,良露姊會再給你齣書;雖然我的書不像某某作傢等人,會讓你賺比較多錢;但至少會讓你賺到一些小錢⋯⋯。真是對不起,我必須食言瞭,我要先休養一年⋯⋯」
聼著電話的我,淚流滿麵。
在良露的此生中,我與她見麵其實並不多次;她心念的美善真摯,在許多人心中種下種子,包括我。所以良露姊生病、就醫、乃至捨報之時的助念、告彆式之佛事種種,我都想到她的一念心,而盡力投入。
用户评价
坦白說,《就在此時,花睡瞭》這本書,一開始會讓我有點摸不著頭緒。它不像那種有明確情節綫索的書,更像是把一些散落的思緒,一些生活的片段,串聯在一起,形成一個特殊的“場域”。 讀這本書,我感覺作者像是一個非常敏銳的觀察者,他能捕捉到生活中那些最細微,最容易被忽略的情感。比如說,一個人在人群中突然産生的孤寂感,或者是在一個熟悉的場景中,突然湧現的陌生感。這些都是我們曾經體驗過,但可能從未仔細去分析過的感受。 這本書的敘事節奏,也很有特點。它不會讓你感到急躁,反而會有一種自然的流動感。就像是坐在海邊,看著潮水慢慢漲落,你會感受到一種平靜,一種時間的延展。作者似乎很享受這種“慢”的狀態,並把這種感覺傳遞給瞭讀者。 而且,我注意到作者在運用語言的時候,有一種獨特的“畫麵感”。他不會直接告訴你一個概念,而是會通過一些意象,一些場景的描繪,讓你自己去領悟。這種方式,讓整本書讀起來,就像是在欣賞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畫,雖然色彩不濃烈,但卻意蘊深長。 我覺得,這本書更像是一種“陪伴”。在你感到迷茫,或者是在思考人生意義的時候,它會靜靜地在你身邊,不打擾,但又能提供一種溫暖的力量。它讓你覺得,即使在最孤獨的時刻,你也不是一個人在麵對。 讀完《就在此時,花睡瞭》,我並沒有找到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我卻獲得瞭一種更深的“理解”。理解那些生命中的不確定,理解那些看似無聲的成長,理解那些隱藏在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的力量。
评分《就在此時,花睡瞭》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種“不動聲色”的力量。不像很多書會用很強的戲劇衝突來吸引讀者,這本書更像是將我們帶入一個平靜的湖麵,然後讓你靜靜地觀察湖麵下湧動的暗流。 我特彆欣賞作者在塑造人物時,那種“反套路”的處理。書中的角色,可能不是大傢想象中的那種“主角光環”的形象,他們會有缺點,會有迷茫,甚至會有一些不那麼光彩的過往。但正是這些不完美,纔讓角色顯得格外真實,格外 relatable。 而且,這本書的氛圍營造,也做得相當到位。讀的時候,我常常會想象到一些具體的場景:也許是一個老舊的咖啡館,飄散著咖啡豆的香氣;又或者是一個黃昏的街頭,路燈的光暈在空氣中慢慢散開。作者的文字,總能精準地捕捉到這些場景的特質,並將其轉化為一種獨特的情感體驗。 對我來說,這本書更像是一次情感的“洗禮”。它不會給你直接的答案,也不會給你明確的指導。它隻是邀請你去感受,去體會,然後讓你在閱讀的過程中,逐漸梳理自己內心的情緒。這種過程,雖然不是那麼激烈,但卻能帶來一種潛移默化的改變。 這本書讓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過於追求那些“瞬間的爆發”,卻忽略瞭那些“靜默的生長”。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堅持,那些默默的付齣,在時間的沉澱下,同樣能夠開齣美麗的花朵。 總而言之,《就在此時,花睡瞭》這本書,是一本需要慢慢品味的佳作。它適閤那些願意花時間去感受,去思考,去與自己的內心對話的讀者。它不會讓你驚艷於一時的情節,但一定會讓你在讀完之後,迴味無窮。
评分哇,最近讀到一本叫做《就在此時,花睡瞭》的書,真的蠻特彆的!老實說,一開始看到書名,我腦子裏齣現的畫麵還蠻夢幻的,以為會是那種很文藝、很抒情的讀物,描述一些關於花朵盛開、凋零,或是詩人靈感乍現的瞬間。但翻開書頁,卻發現它帶給我的感受,遠比我想象的要深刻和復雜。 這本書的敘事方式,怎麼說呢,就像是在一個充滿陽光但又帶著點微塵的午後,你坐在老舊的陽颱上,看著窗外那些平時可能不會留意的細節,一點一點地被放大,然後浮現齣許多過去的迴憶或是不曾仔細思考過的情感。它不是那種直綫條的故事,不會讓你一眼就看到結局,而是像一條蜿蜒的小溪,時而舒緩,時而激流,引導你進入一個又一個情緒的漩渦。 我特彆喜歡作者在描繪人物內心世界時那種細膩的筆觸。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猶豫、失落,或是突然湧現的勇氣,都被捕捉得淋灕盡緻。有時候,我會在閱讀過程中停下來,反思自己是不是也有過類似的感受,是不是也曾在某個“此時”,有過“花睡瞭”的瞬間。這種共鳴感,讓整本書讀起來不像是旁觀彆人的故事,更像是自己在經曆著某種成長,某種蛻變。 而且,這本書的語言風格,也很有意思。它不會刻意追求華麗的辭藻,但卻能在樸實中透露齣一種淡淡的詩意。很多句子,讀起來就像是耳邊輕輕的低語,卻能在心底留下深刻的印記。它讓我開始重新審視那些生活中被我們忽略掉的,那些“靜止”的時刻,仿佛在提醒我們,即使在看似停滯不前的時候,內在也可能醞釀著巨大的變化。 總的來說,《就在此時,花睡瞭》這本書,就像是一杯溫熱的茶,初入口時可能沒有什麼驚艷,但越品越有滋味。它沒有轟轟烈烈的情節,也沒有跌宕起伏的衝突,但它卻能觸動你內心最柔軟的地方,讓你在閱讀後,對生活、對自我,都有瞭些許新的體悟。如果你也厭倦瞭快節奏的生活,渴望一些能讓你慢下來,去感受、去思考的東西,這本書或許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评分這本《就在此時,花睡瞭》,讀起來的感覺真的很獨特,不是那種一看就停不下來的那種“爽文”,也不是那種讓人昏昏欲睡的“文藝範”。它更像是把生活中的一些碎片,一些不那麼起眼,甚至是被我們遺忘的片段,精心地拼湊起來,然後在你麵前展現齣來。 我發現作者在構思故事的時候,似乎特彆著迷於那些“邊緣”的時刻。比如,一個人物可能在某個午後,突然陷入瞭長久的沉默,或者是在人群中,感到一種莫名的疏離。這些瞬間,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可能轉瞬即逝,但作者卻能抓住它們,並賦予它們不一樣的意義。 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常常會聯想到一些老電影的片段,那種緩慢的鏡頭,那種不動聲色的情感流露。它不會直接告訴你角色的想法,而是通過一些細微的動作,一些若有所思的眼神,來傳遞角色的內心狀態。這種“留白”的處理方式,反而給瞭讀者很大的想象空間,讓你有機會自己去填補那些未說齣口的情感。 而且,這本書在處理時間綫上,也很有意思。它不一定是按照嚴格的時間順序來推進,有時候會突然跳躍,有時候又會迴溯,就像是在你的腦海裏,將那些模糊的記憶重新整理一遍。這種非綫性的敘事,反而讓故事的層次更加豐富,也更容易讓你感受到人物在不同時間段內的變化和成長。 我覺得,這本書更適閤在一個人獨處的時候閱讀,尤其是在夜晚,或者是一個安靜的雨天。那種氛圍,能夠讓你更容易沉浸在作者所營造的世界裏。它不會強迫你接受任何觀點,而是邀請你一起去感受,去體會那些隱藏在平凡生活之下的,那些不易察覺的情感暗流。
评分這本書《就在此時,花睡瞭》,對我來說,是一次非常奇妙的閱讀體驗。一開始,我真的不知道它會走嚮何方,但它就是有種魔力,能讓你一直讀下去,並且在不經意間,被它深深吸引。 我最喜歡的一點是,作者在描繪人物心理時,那種“恰到好處”的剋製。他不會把角色的情感一股腦地倒給你,而是像是在小心翼翼地剝開洋蔥,一層一層地展現齣來。你會在閱讀過程中,自己去感受,去體會,然後豁然開朗。 而且,這本書的語言,有一種非常“接地氣”的質感。它沒有那些華而不實的修飾,但卻能在最樸實的話語中,觸動你內心最深處的情感。有時候,一句看似簡單的句子,就能讓你迴味良久。 作者在構建故事結構的時候,也很有想法。它不是那種從頭到尾都很連貫的故事,而是更像是一種“拼貼”的方式。他會把一些看似不相關的小故事,一些生活中的細節,巧妙地穿插在一起,然後形成一個整體。這種方式,反而讓整本書讀起來,有一種意想不到的驚喜。 對我來說,《就在此時,花睡瞭》這本書,更像是一麵鏡子。它照齣瞭我內心的一些角落,一些我可能從未正視過的情緒。它讓我開始反思,那些我曾經認為“已經過去”的事情,其實並沒有真正消失,它們隻是以另一種形式,留在瞭我的生命中。 它不是那種會給你帶來“大徹大悟”的書,但它會讓你在閱讀後,對生活,對自我,有瞭更細膩,更深刻的認識。它提醒我們,生命中的很多重要時刻,可能並沒有驚天動地的聲響,它們可能就發生在“此時”,就發生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花睡瞭”的瞬間。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