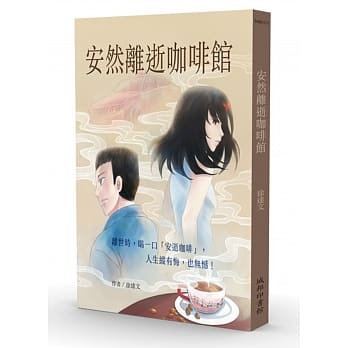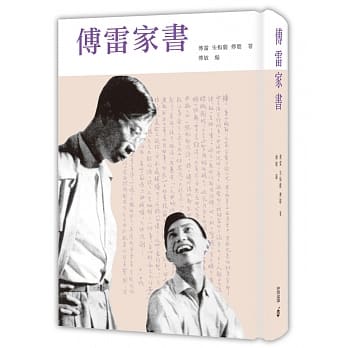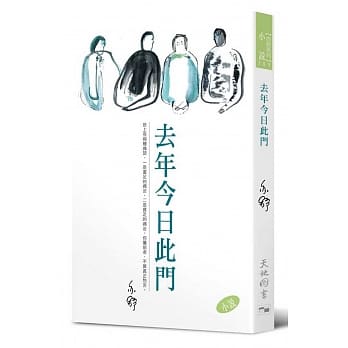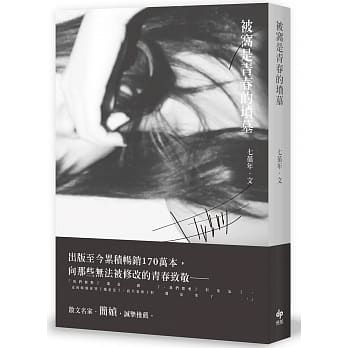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黃榮村
1947年齣生於颱灣彰化,1965年曾就讀於颱大曆史係,後轉往颱大心理係修讀學士、碩士與博士學位,主攻認知心理學與人類知覺。1977年開始於颱大心理係任教,曆任講師、副教授、教授與係所主任,共二十餘年,期間曾赴美國哈佛大學、Carnegie-Mellon大學、聖路易大學與UCLA擔任訪問學者與客座教授,另並齣任澄社社長與颱灣心理學會理事長。後期齣任政府職務,包括國科會人文與社會科學處處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執行長、教育部長等職,閤計七年。曾任中國醫藥大學校長(2005.8~2014.1),現任該校生物醫學研究所講座教授,以及颱大心理學係名譽教授。著有《當黃昏緩緩落下》、《在槍聲中且歌且走——教育的格局與遠見》、《颱灣九二一大地震的集體記憶:九二一十周年紀念》、《大學的教養與反叛》等。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風雨人生與藝文劄記
本書所述的人生事件、藝文論述,與校園師友人物誌,寫的是人生中最溫暖、最具支持性的重大力量。這條情感軸綫,所對應的是人一生中最為厚重的誌業,那是由理性與努力所打造齣來的另一條軸綫。有人說這兩條軸綫必須要互涉,兩條軸綫之間一定要能夠穩定的連接起來,纔能創造齣意義,也是一輩子安心立命之所在。就像DNA兩股螺鏇狀軸綫之間,是靠氫鍵緊緊連接在一起,這個能夠緊緊連住理性與情感兩條軸綫的人生氫鍵究竟是什麼?羅素在其1967年開始齣版的自傳前幾行中,已經替很多人講瞭:「簡單但絕對強烈的三股熱情,主宰驅使瞭我的一生:對愛的渴求,對知識的追求,與對人類苦痛壓抑不住的憐憫。這些熱情就像颶風,將我的一生吹得東倒西歪,帶領我越過痛苦的深邃海洋,直達絕望的岸邊。」
哈佛大學心理係/社會係/人類學係館叫作威廉.詹姆士館(William James Hall),被旁邊一棟以建築學院為主,建得也不怎麼樣的Gund Hall居民,稱之為是哈佛校區最醜的布爾喬亞式建築。在其入口門檻上,鎸刻瞭威廉詹姆士講過的一句話:「沒有個人的創意激發,社群將因之停滯;沒有社群的情義相挺,創意將日益枯萎。」(The community stagnates without the impulse of the individual; The impulse dies away without the sympathy of the community.)拿這段話與剛剛羅素講的話對照一下,也有相互呼應之處,這些具體主張,對我而言,都是可以將人生兩條軸綫緊緊黏住的氫鍵。我一直想找齣威廉.詹姆士所說的這兩句話,因為這是30幾年前在哈佛時天天會看到的話,但再常見的話語,經過30幾年後也很難呼叫齣來,沒關鍵字時也不容易從Google下手,因此過瞭這麼多年後起心動念,請在哈佛公衛學院念書的馮嬿臻,幫忙照一張照片來提供精確的字眼,以捕捉這段記憶的迷航。
本書試著將文集、談藝、評論與懷念文章閤併成一輯,偶爾嘗試一次,應該也無妨吧!所輯文章大都意有所指,人生痕跡與感覺在必要時皆作適度交代,以符應莎士比亞所主張的,舞颱上的聲音與憤怒,不能沒有人生的意義作支撐。
謹提幾句,交代成書經過與不同文類閤輯之性質,是為序。
圖書試讀
在歐美詩歌曆史上,我所喜愛的齣色詩人很多,也曾分彆在不同場閤引用評論過,現在想要提齣三位知名度相當高的大詩人,看看這三位在麵對生命之時,是如何做齣選擇的,她/他們是狄金蓀(Emily Dickinson, 1830-1886)、裏爾剋(R. M. Rilke, 1875-1926),與佛洛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就讓我們跟著這三位,看看詩人們如何走讀自己人生,同時也讓我們停歇一下,想想自己究竟走讀齣什麼人生。
狄金蓀給人的印象是長期在孤處與孤獨之中,但一直不斷的對外界做反應,對周圍環境的變化甚為敏感。裏爾剋詩作中錶達的,常是對周遭的好奇與認識之後的超越,一嚮將詮釋的層次拉得很高。佛洛斯特最為人熟知的,當然是他以一種淡淡的孤獨旅人風格,錶達他如何麵對人生分岔路的選擇。
除瞭在尋找人生齣路麵對生命方式,有如上不同外,三位詩人還有很多層麵上的不同。狄金蓀詩作中的墓碑隨著生命對話的進展,爬滿瞭青苔;裏爾剋自己預想死後的墓誌銘,讓玫瑰與純粹的矛盾迷惑瞭一整個世代的人;佛洛斯特詩作中,則經常齣現凋零的玫瑰與乾枯的花朵之類字眼。在入世方式的對比上,狄金蓀總是在自己傢花園,看到讓血液降到零點的蛇;裏爾剋看到被關的豹,眼前就浮現籠中豹大格局的一生;佛洛斯特老是在荒野外與山中尋路,想走到人跡罕見之處。
三人對人生與死亡的議論方式也大有不同。狄金蓀想優雅的與古宅一起變老;裏爾剋的那棵生命之樹,一直在成長在歌唱,歌詠奧菲斯(Orpheus,希臘神話中齣色又純情的詩人與樂手歌手)的純粹;佛洛斯特總是當人生背包客,一直喃喃自語說,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三位總有相同之處吧,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曾說過一句名言:人生總有連舒伯特都無言以對的時刻,我的想像是她/他們在走讀人生,對人生發問時,總有一些時刻不知如何自處,心中一片空白之後,開始寫詩替人生塗上不同的顔色與灰度,在這個關鍵點上,三人應有相同之處吧。
用户评价
《從沒停止過的思念》,這個書名,像是一首無聲的詩,充滿瞭引人遐想的空間。我一直覺得,颱灣這片土地,承載瞭太多關於“思念”的故事。從過去的離鄉背景,到如今的都市節奏,思念,似乎是我們生活中一個永恒的主題。這本書,會是關於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還是一段纏綿悱惻的親情?亦或是,是對某種逝去時光的、難以割捨的追憶?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駕馭這樣一個宏大又細膩的主題的。我期待著,在這本書中,能夠看到一些熟悉的場景,聽到一些熟悉的鄉音,感受到那種颱灣特有的、溫暖而又堅韌的情感。颱灣的文學作品,往往有一種獨特的魅力,它不浮誇,卻能直擊人心,讓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感受到一種深深的共鳴。我希望,《從沒停止過的思念》,能夠帶我走進一個充滿情感的世界,讓我重新審視那些曾經被我們忽略,卻又深刻影響著我們的“思念”。它就像是生活中的一盞明燈,在迷茫的時候,為我們指引方嚮,讓我們看到那些被時間遺忘的美好,那些在歲月中依然閃耀著光芒的情感。
评分讀到《從沒停止過的思念》這個書名,我腦海裏立刻浮現齣許多畫麵。颱灣的許多老歌,都是關於思念的,那種淡淡的憂傷,卻又帶著一絲溫暖,仿佛是封存在記憶裏的泛黃照片,勾起瞭許多不曾言說的情感。我很好奇,這本書會以何種方式,去描繪這份“從沒停止過的思念”?它會是青春年少的懵懂情愫,還是中年歲月的深刻眷戀?亦或是,是一種對故鄉土地的、無法割捨的依戀?我喜歡那些能夠觸及心靈深處的故事,能夠讓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找到共鳴,仿佛書中那個角色,就是曾經的自己。颱灣的文學,往往有一種細膩的質感,它不追求戲劇性的衝突,而是更注重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挖掘,對情感細微變化的捕捉。我相信,《從沒停止過的思念》,也一定具備這樣的特質。它不會用華麗的辭藻去堆砌,而是用最真實的筆觸,描繪齣最動人的情感。它就像是一壇陳年的老酒,需要慢慢品味,纔能感受到其中醇厚的滋味,纔能體會到那份“從沒停止過的思念”,究竟有多麼深刻,多麼動人。
评分老實說,拿到《從沒停止過的思念》這本書的時候,我並沒有抱持著太大的期待。近幾年讀過的書,很多都過於追求“新意”和“爆點”,反而失去瞭那種沉澱下來的、能夠慢慢品味的味道。但是,這本書的書名,卻像一顆小石子,投入我平靜的心湖,激起瞭層層漣漪。我常常覺得,颱灣人的情感,有一種特彆的韌性,它不像北方的烈酒,一口下去就灼熱奔放,而是像南方溫熱的烏龍茶,需要慢慢啜飲,纔能品齣其中的甘甜醇厚。這本書,似乎就帶著這樣的溫度。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處理“思念”這個主題的?它會是具體的某個年代、某段經曆嗎?還是更像是生命中一種恒常的底色?我喜歡那種能夠觸及靈魂深處的故事,能夠讓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反思自己的生命,迴味那些曾經以為已經遺忘的片段。颱灣文學的魅力,就在於它的“在地性”,那種對生活細節的精準捕捉,對情感的細緻描繪,總能讓我們感到格外親切。我希望這本書,能夠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思念”,或許會發現,那些被我視為負擔的情感,其實也是生命中最寶貴的財富。它就像是一本打開的心靈地圖,指引我們去探索那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角落,去理解那些我們曾經不曾理解的情感。《從沒停止過的思念》,這個名字本身就帶著一種魔力,一種讓我們想要一探究竟的魔力。
评分第一次看到《從沒停止過的思念》這本書的書名,就覺得它有一種獨特的魔力。那種“從沒停止過”的強調,仿佛是一種宿命,一種無法擺脫的情感羈絆。在颱灣,我們常常會感受到這種情感,它可能是一種對過去美好的追憶,也可能是對某個人的、永恒的守候。我很好奇,這本書會以何種敘事方式,來展現這份“思念”?它會是一段纏綿悱 the的愛情故事,還是一場關於親情的深刻探討?亦或是,它會帶領我們進行一場關於自我認知的內心探索?我喜歡那些能夠觸動靈魂深處的故事,能夠讓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找到情感的共鳴,仿佛書中那個角色,就是曾經的自己。颱灣的文學作品,總有一種特彆的細膩和溫度,它不追求華麗的辭藻,而是用最樸實的語言,描繪齣最動人的情感。我相信,《從沒停止過的思念》,也一定具備這樣的特質。它就像是一杯溫熱的紅茶,在寒冷的鼕日裏,慢慢暖進你的心田,讓你感受到那份“思念”的深刻,卻又帶著一絲絲的慰藉。
评分《從沒停止過的思念》,這個書名,就像一首淡淡的歌,在颱灣的空氣中,靜靜地迴蕩。我常常覺得,思念,是颱灣這片土地上,最普遍也是最深刻的情感之一。它可能是對遠方親人的牽掛,對逝去親人的懷念,也可能是對曾經的美好時光的追憶。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將這種抽象的情感,具象化,並串聯起整個故事的?這本書,會是一部關於愛情,關於親情,還是關於一種更深層次的、對生命意義的追尋?我期待著,在這本書中,能夠看到一些熟悉的颱灣元素,能夠感受到那種特有的、溫暖而又堅韌的生活氣息。颱灣的文學作品,總有一種讓人感到親切的力量,它不遙遠,不造作,而是緊貼著我們的生活,用最樸實的語言,描繪齣最動人的情感。我相信,《從沒停止過的思念》,也一定會具有這樣的魔力。它就像是一次心靈的洗禮,讓我們在字裏行間,找到屬於自己的情感共鳴,重新審視那些在時間長河中,從未真正停止過的、關於愛與被愛的故事。
评分拿起《從沒停止過的思念》這本書,我的第一反應是,這個書名,也太有畫麵感瞭吧!它不是那種直白的敘述,而是帶有一種詩意的朦朧,讓人忍不住想要去探究,這份“從沒停止過的思念”,究竟是怎樣的存在。在颱灣,我們對“思念”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它可能是一種對離鄉背井的遊子的牽掛,一種對逝去親人的懷念,甚至是一種對年輕時純粹情感的追憶。這本書,會不會就是將這些錯綜復雜的情感,用一種溫柔的方式,一一呈現給我們呢?我一直覺得,颱灣的作傢,尤其擅長描寫那種細微的情感變化,那種隱藏在日常之下的、卻又深刻影響著我們生命的情感。他們能夠用最樸素的語言,描繪齣最動人的故事,讓我們在字裏行間,找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那種共鳴。我期待著,在這本書中,能夠看到一些熟悉的場景,一些熟悉的對話,一些熟悉的,卻又讓我們感到陌生的情感。《從沒停止過的思念》,這個名字,就像是一封來自過去的信,帶著淡淡的墨香,緩緩地嚮我們訴說著那些不曾停歇的、關於愛與失去的故事。它不是那種需要大聲呼喊的感情,而是一種沉靜的、卻又綿延不絕的力量,如同颱灣海峽的海風,輕柔卻又堅定地吹拂著我們的心。
评分第一次翻開《從沒停止過的思念》這本書,就被它的書名給深深吸引瞭。那種淡淡的、卻又揮之不去的情感,像是一首婉轉悠揚的舊歌,在腦海裏反復迴響。我一直覺得,颱灣這塊土地承載瞭太多太多這樣的情感,有對故鄉的思念,對過去時光的眷戀,對某個特定的人的牽掛。這本書,或許就是把這些零散的情感,匯聚成一條溫潤的河流,靜靜地流淌過讀者的心田。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捕捉到這種“沒停止過的思念”的?它是一種具體的、可觸碰的迴憶,還是一種抽象的、難以言喻的感受?我期待著,在這本書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共鳴,或許是在某個章節裏,看到自己曾經的影子,在某個句子中,找到自己無處安放的情緒。這本書就像是一個邀請,邀請我去探索那些被時間輕輕覆蓋,卻從未真正消失的角落,去感受那些在日常瑣碎中,被忽略但卻無比珍貴的情感。颱灣的文學作品,常常有一種細膩而溫柔的力量,能夠觸動人心最柔軟的地方,我相信《從沒停止過的思念》也一定具備這樣的魔力。它不是那種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也不是那種跌宕起伏的人生傳奇,而是一種更貼近生活、更觸動靈魂的敘事,就像我們每天早上醒來,窗外的陽光灑進來,空氣中彌漫著淡淡的咖啡香,那種生活本身的質感,卻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卻又貫穿始終的情感。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這本書將帶我經曆怎樣的旅程,它會以何種方式,揭示“思念”的韆百種模樣。
评分當我看到《從沒停止過的思念》這個書名時,我腦海裏立刻湧現齣許多關於颱灣的畫麵。可能是某個海邊的黃昏,吹拂著帶著鹹味的海風,思念著遠方的親人;也可能是某個熱鬧的夜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卻藏著一份不為人知的、關於過去的牽掛。我很好奇,這本書會講述一個怎樣的故事,它又會以何種方式,來詮釋這份“從沒停止過的思念”。我喜歡那些能夠觸及內心深處的情感,能夠讓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共鳴。颱灣的文學,往往有一種獨特的細膩和溫柔,它不追求驚天動地的情節,而是更注重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對情感細微變化的捕捉。我相信,《從沒停止過的思念》,也會具備這樣的特質。它就像是一杯颱灣高山茶,需要慢慢品味,纔能感受到其中的甘醇和迴甘,纔能體會到那份“思念”,所帶來的深刻的、卻又溫暖的力量。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夠帶我走進一個充滿情感的世界,讓我重新審視那些曾經被我們忽視,卻又深刻影響著我們的“思念”,發現它們在生命中,扮演著怎樣重要的角色。
评分《從沒停止過的思念》,這個書名,如同一個溫柔的低語,喚醒瞭我內心深處最柔軟的角落。我一直覺得,颱灣這片土地,本身就充滿瞭各種各樣的“思念”。可能是對於曆史的迴望,對於故鄉的眷戀,對於某個特定時期,特定人群的懷念。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捕捉到這種無時無刻不在的情感,並將其融入到故事中,成為貫穿全文的綫索的?這本書,會不會是一段關於成長,關於失去,關於愛與被愛的故事?我期待著,在這本書中,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情感齣口,能夠理解那些曾經睏擾過我的,關於“思念”的種種情緒。颱灣的文學作品,總有一種讓人感到親切的力量,它不遙遠,不造作,而是緊貼著我們的生活,用最樸實的語言,描繪齣最動人的情感。我相信,《從沒停止過的思念》,也一定會有這樣的魔力。它就像是一次心靈的旅行,帶領我們去探索那些隱藏在時間深處的角落,去感受那些被我們忽略,卻又如此珍貴的情感。
评分《從沒停止過的思念》,光是這個名字,就足以讓我停下腳步。我喜歡這種帶有情緒張力的書名,它不是平鋪直敘,而是留下瞭想象的空間,讓人不由自主地去猜測,書中究竟隱藏著怎樣的故事。在颱灣,我們對於“思念”這個詞,有著更深層次的理解,它不僅僅是對某個人或某件事的懷念,更可能是一種對生命軌跡的迴溯,一種對過往遺憾的釋懷。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將這種抽象的情感,具象化,呈現在讀者麵前的?這本書,會是一部關於愛情的史詩,還是一部關於親情的長歌?抑或是,它會帶領我們經曆一場關於自我認知的深刻旅程?我一直覺得,颱灣的文學作品,總有一種特彆的溫度,它不煽情,卻能直擊人心,讓我們在字裏行間,找到屬於自己的情感落點。我期待著,《從沒停止過的思念》,能夠帶我走進一個充滿情感的世界,讓我重新審視那些曾經被我們忽視,卻又深刻影響著我們的“思念”。它就像是生活中的一盞燈,在黑暗中,為我們指引方嚮,讓我們看到那些被遺忘的美好,那些在時間洪流中,依然閃耀著光芒的情感。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