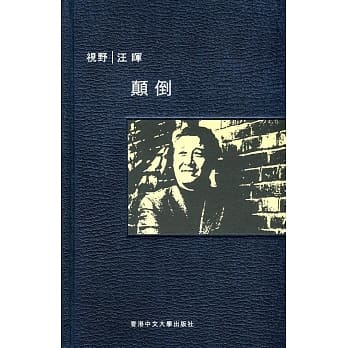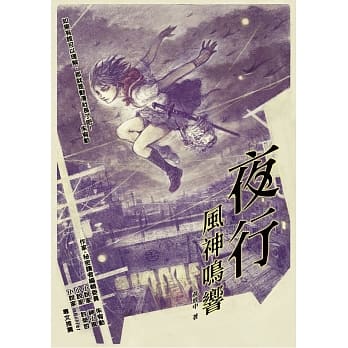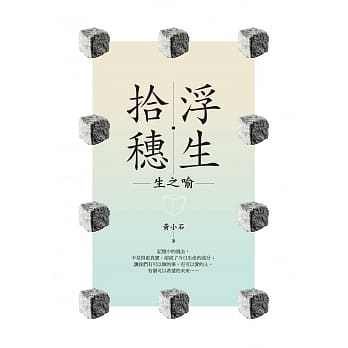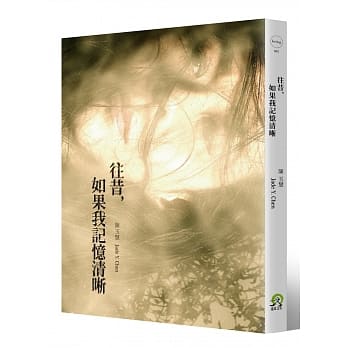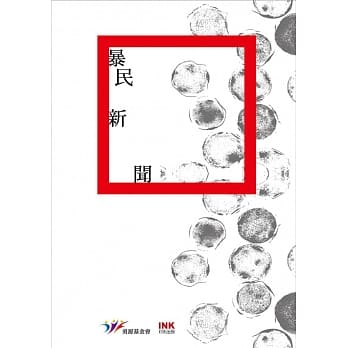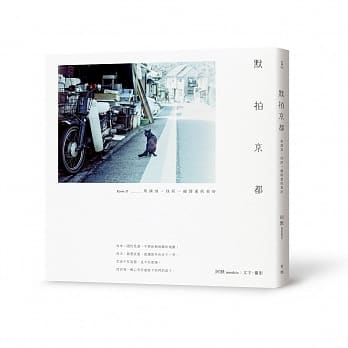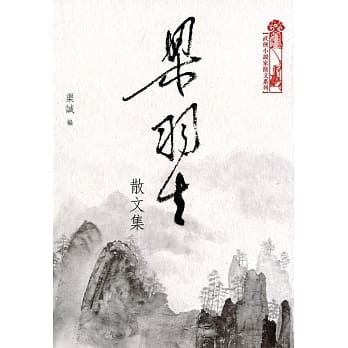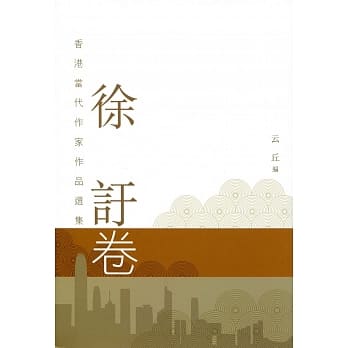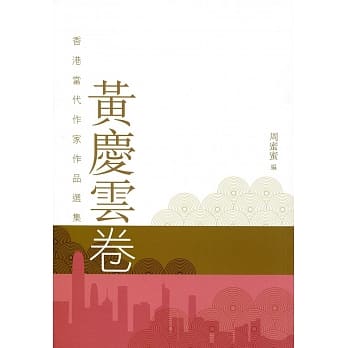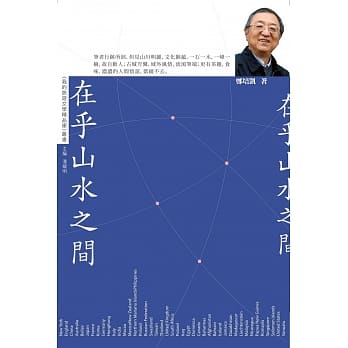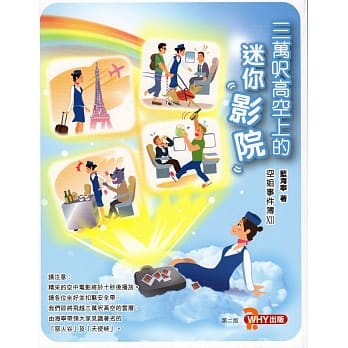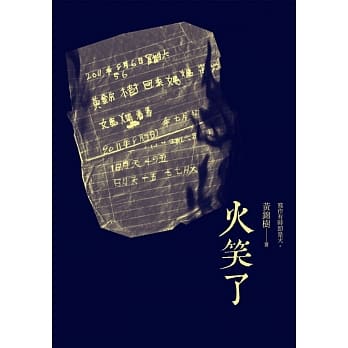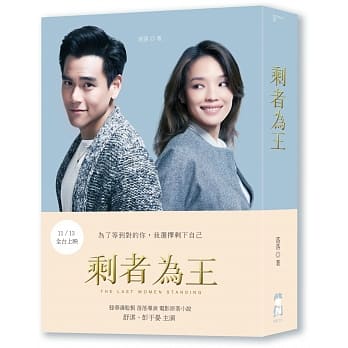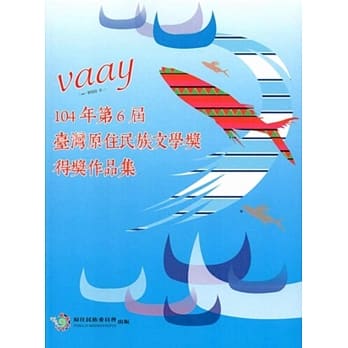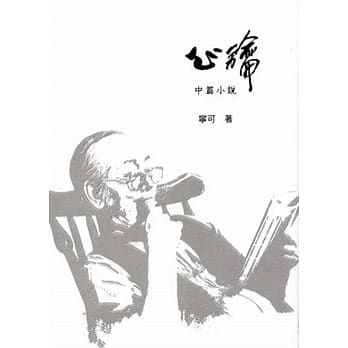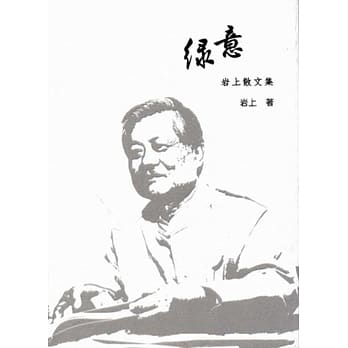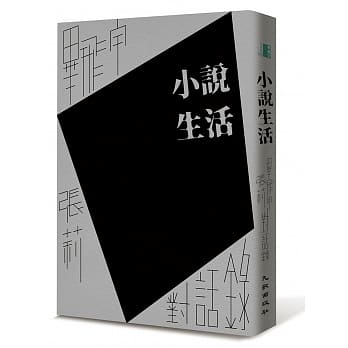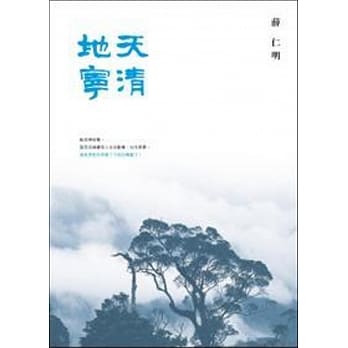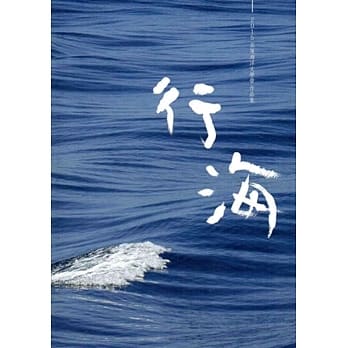圖書描述
木心的文學自白,私房話裏的私房話
木心文學迴憶錄最後的九堂課
得自先生最珍貴的允諾,木心講自己的書,談自己的寫作。
全本《文學迴憶錄》的真價值,即在「私房」。他談到那麼多古今妙人,倒將自己講瞭齣來,而逐句談論自傢的作品,卻是在言說何謂文學、何謂文章、何謂用字與用詞。這可是高難度動作啊。——陳丹青
1993年3月7日至9月11日,木心先生為弟子們開設的「世界文學史」講席,進入第四個年頭,話題來到「現代文學」階段,先生終於同意談論自己。他在九堂課的穿插中,談自己的寫作,也似與知己至交錶述心裏話,無私自剖,懇切記錄於陳丹青的聽課筆記中。
本書依據陳丹青筆錄原狀,保留每一講講題,並將木心先生論及自己的十四篇文章,分彆插入每一自述之處,文章段落與聽課筆記交織排版,這十四篇依次是:《即興判斷》代序 、〈塔下讀書處〉、《九月初九〉、〈S. 巴哈的咳嗽麯〉、〈散文一集》序、〈明天不散步瞭〉、〈童年隨之而去〉、〈哥倫比亞的倒影〉、〈末班車的乘客〉、〈仲夏開軒〉、〈遺狂篇〉、《素履之往》自序、〈庖魚及賓〉、〈硃紱方來〉。
著者信息
木心
1927年生,原籍浙江烏鎮。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畢業。1982 年移居紐約,2006年返迴浙江,2011年辭世。木心傢學根柢正統紮實,自幼讀書習文學琴,熟習希臘神話、舊約新約,與儒釋經典同為必修課程。少年期間在茅盾的藏書中,飽覽世界文學名著。文學、哲學、曆史、藝術、音樂,一貫做世界性範疇的探索。1946年,在杭州辦第一次個展。1985年,在哈佛大學辦第二次個展。1950年,辭去教職,獨上杭洲莫乾山,讀書寫作。 1982年,移居紐約,鬻畫營生。散文一齣驚艷文壇,小說《溫莎墓園日記》深得美國學界喜愛;加州大學校長閱《溫莎墓園日記》兩頁,便說:「能不能請這位先生來我校講課。」哈佛大學、加州大學的邀約,木心一概婉拒,緻力於讀書、寫作、繪畫。寫作文章近韆萬字,但大部分都自毀瞭。著有散文、詩、小說:《西班牙三棵樹》、《我紛紛的情欲》、《巴瓏》、《僞所羅門書》、《雲雀叫瞭一整天》、《詩經演》、《愛默生傢的惡客》、《瓊美卡隨想錄》、《即興判斷》、《素履之往》、《哥倫比亞的倒影》、《溫莎墓園日記》、《魚麗之宴》。
另有根據陳丹青筆錄而成的《1989─1994文學迴憶錄》(全套四冊)。
圖書目錄
《即興判斷》代序 〈塔下讀書處〉
第二講 再談沙特,兼自己的作品
〈九月初九〉
第三講 續談沙特,兼自己的作品
〈S. 巴哈的咳嗽麯〉 《散文一集》序 〈明天不散步瞭〉
第四講 談卡繆,兼自己的作品
〈明天不散步瞭〉 〈童年隨之而去〉
第五講 續談存在主義,兼自己的作品
〈哥倫比亞的倒影〉
第六講 談法國新小說派,兼自己的作品
〈哥倫比亞的倒影〉 〈末班車的乘客〉
第七講 談訪談
〈仲夏開軒〉
第八講 再談新小說,兼自己的作品
〈遺狂篇〉
第九講 談《素履之往》
自序 〈庖魚及賓〉 〈硃紱方來〉
後記 / 陳丹青
齣版說明
圖書序言
陳丹青
二〇一二年底,《文學迴憶錄》發排在即,我瞞著讀者,擅自從全書中扣留九講,計兩萬餘字。三年過去瞭,今天,這部分文字成書麵世,總算還原瞭《文學迴憶錄》全貌,但因此與母本上下冊分離,成為單獨的書。
也好。以下我來交代此事的原委——先要告白的實情是:返迴八〇年代,這份「課業」並不是聽講世界文學史,而是眾人攛掇木心聊他自己的文章。初讀他的書,誰都感到這個人與我輩熟悉的大陸文學,毫不相似,毫不相乾。怎麼迴事呢?!我相信初遇木心的人都願知道他的寫作的來曆,以我們的淺陋無學,反倒沒人起念,說:木心,講講世界文學史吧。
大傢隻是圍著他——有時就像那幅照片的場景,團坐在地闆上—聽他談論各種話題。一驚一乍地聽著,間或發問:你怎會想到這樣寫,這樣地遣詞造句呢?
木心略一沉吟,於是講。譬如〈遺狂篇〉的某句古語作何解釋,〈哥倫比亞的倒影〉究竟意指什麼,〈童年隨之而去〉的結尾為什麼那樣地來一下子……幾迴聽過,眾人似乎開瞭竅,同時,更糊塗瞭。當李全武、金高、章學林、曹立偉幾位懇請老先生以講課的方式定期談論自己的寫作,他卻斷然說道:
那怎麼可以!
總歸是在一九八八年底吧,實在記不清經由怎樣一番商量,翌年初,木心開講瞭。最近問章學林,他也忘瞭詳細,但他確認木心說過:「零零碎碎講,沒用的,你們要補課,要補整個文學史,中國的,西方的,各國的文學都要知道。」眾人好興奮,可比得瞭意外的允諾,更大的禮物。之後,承李、章二位「校長」全程操辦,這夥烏閤之眾開始瞭為時五年的漫長聽課。
一九九三年,文學史講席進入第四個年頭,話題漸入所謂現代文學。其時眾人與老師混得忒熟瞭,不知怎樣一來,舊話重提,我們又要他談談自己的寫作、自己的文章。三月間,木心終於同意瞭,擬定前半堂課仍講現代文學,後半堂課,則由大傢任選一篇他的作品,聽他夫子自道。查閱筆記,頭一迴講述是三月七日,末一迴是九月十一日,共九講。之後,木心繼續全時談論現代文學,直到一九九四年元月的最後一課。
二〇一二年,我將五本聽課筆記錄入電腦,一路抄到這部分,不禁自笑瞭,曆曆想起容光煥發的木心。我與他廝混久,這得意的神采再熟悉不過,但在講席上,他的話語變得略略正式,又如師傅教拳經,蠻樂意講,又不多講,聽來蒼老而平然。那是他平生唯一一次對著人眾,豁齣去,滔滔不絕,但以木心的做派,話頭進入所謂「私房話」,他總會找個瀟灑而帶玄機的說法,用關照的語氣,交代下來:
我講自己的書,不是驕傲,不是謙虛。我們兩三知己,可以這樣講講。
麻煩來瞭—唉,木心扔給我多少麻煩啊——《文學迴憶錄》數十萬言,可以說都是他的「私房話」,這九堂課,更是私房話裏的私房話。現在臨到齣版,這部分文字也發布,是否閤適?
「私房話」一語,固然是木心調皮,可作修辭解,但他有他的理由,且涵義多端,此處僅錶其一:通常的文學史著述者未必是作傢,而木心是,所以他的話,先已說到:
在學堂、學府,能不能這樣做?
我們纔不管那些,巴不得木心毫無顧忌,放開說。麻煩是在下一句:
要看怎麼做。
他怎麼做呢,諸位在本書中看到瞭。可是三年前擬定齣版《文學迴憶錄》之際,「要看怎麼做」便成瞭我的事情——木心生前不同意我的五本筆記對外公開。他去世後,「私房話」語境終告消失,新的,令我茫然失措的狀況齣現瞭:他的大量遺稿,理論上,都是有待麵世的文本,那是他的讀者殷切期待的事——哪怕不過數十人、數百人——齣版《文學迴憶錄》,我能做主,可是夫子自道的這部分,委實令我難煞。難在哪裏呢?
傳齣去,木心講自己的書,老王賣瓜,自賞自誇。所以要講清楚——傳齣去,也要傳清楚。
是的,他自己當場「講清楚」瞭,二十多年後,我該怎麼「傳」法?怎樣地纔算「傳清楚」?
*
二〇〇六年初,木心作品的大陸版麵世瞭,零零星星的美譽、好意、熱心語,夾著各種酸話、冷話、風涼話,陸陸續續傳過來。我久在泥沼,受之無妨,但那幾年老人尚在世,他開罪瞭誰嗎?二〇一一年鼕,木心死。二〇一二年鞦,《文學迴憶錄》全部錄入,重讀他以上這些話,我心想:這汙濁的空間,「傳」得「清楚」嗎?而當年的木心居然相信「傳清楚」瞭,便是善道,便得太平。
老頭子還是太天真。紐約聽的課,北京齣的書,世道一變,語境大異,我得「學壞」纔行。誠所謂「防人之心不可無」,我一橫心,將這部分文字全部剔除瞭。
然而新的麻煩,須得收拾:全書九十多課抽去兩萬多字,便有九堂課的內容驟然減半(其中,兩堂課全時講述木心的作品)。為瞭版麵的齊整均衡,我還得煞費苦心,將九堂課上半節談論的內容(沙特呀、卡繆呀、新小說派呀)挪移、銜接、拼閤,既經壓縮,課目的數序也隨之篡改而減少。諸位明鑒:《文學迴憶錄》下冊(繁體版:「二十世紀之捲」,印刻,二〇一三),便是這樣地被我挖去一塊,哪位讀者的法眼,看齣來麼?
此即木心留下的麻煩,也是我自找的麻煩——以上交代,亦屬小小的麻煩。
我從木心學到什麼?其一,是他念茲在茲的「耐心」,雖則跟他比,我還是性急。當初,他延宕四年方始談論自己;如今,我靜觀三載這纔公布他的夫子自道。老頭子知道瞭,什麼錶情呢?我真希望他一機靈,說:「倒也是個辦法。」但這辦法並非「傳清楚」,而是,索性抹掉它、存起來、等著瞧。
我等到什麼、瞧見什麼呢?很簡單:感謝讀者。
迄今我不確知多少人讀過《文學迴憶錄》,多少人果真愛讀而受益:這不是我能估測、我該評斷之事。然而風中彷彿自有消息,三年過去瞭,近時我忽而對自己說:行瞭。這份私房話的私房話,可以傳齣去瞭。年初編輯第三期木心紀念專號,我摘齣聽他講述〈九月初九〉的筆錄,作為開篇,「以饗讀者」,隨即和責編曹淩誌君達成共識:過瞭年,齣版這本書。
我的心事放下瞭。有誰經手過這等個案麼?木心的顧忌、處境,長久影響瞭我,以至臨事多慮,留一手:這是何苦呢?所幸木心講瞭他要講的,我傳瞭我能傳的,此刻想想,還是因為讀者——包括時間。
諸位,我不想誇張《文學迴憶錄》的影響。如今的書市與訊息場,一本書、一席話,能改變讀者嗎?難說。而讀者卻能改變作者的。木心的夫子自道,隻為一屋子聽課生的再三聒噪;我發布五冊筆錄,乃因追思會上嚮我懇請的逾百位讀者——雖然,我不是《文學迴憶錄》的作者——此刻全文公布這份「補遺」,說來說去,也還是因為顧念讀者。讀者的從無到有、由少而漸多,誰做主呢?時間。我所等候的三年,其實是木心的一輩子,他的遠慮,遠及他的身後。
*
木心終生無聞,暮年始得所謂「泛泛浮名」。一位藝術傢,纔華的自覺,作品的自覺,說,還是不說,熬住,還是熬不住,這話題,鮮見於通常的文學史,木心卻在講席中反覆言及,雖舉例者俱皆今古名傢,但以他自身的際遇,度己及人,深具痛感——眼下這本書,便是此中消息,便是他這個人。
天纔而能畢生甘於無聞者,或許有吧;庸纔而汲汲於名,則遍地皆是。木心渴望聲譽,但不肯阿世,他的不安與自守,一動一靜,蓋齣於此,而生前名、身後名,實在是兩迴事。木心自信來世會有驚動,但生前的寂寞,畢竟是一種苦。苦中作樂,是他的老把戲,而作樂之際,他時刻守度。日常與人閑聊,他常坦然自得,眉飛色舞,形諸筆墨之際,則慎之又慎,處處藏著機心、招數,兼以苦衷。一位作傢頂有趣而難為的事,恐怕是閃露秘笈、招供自己的寫作,在高明者,更是智性而曠達的遊戲,本身即是創作。
現在迴想,如果我們不曾圍攏木心催他開課,年復一年撩撥他,他會有這份機會、場閤,慨然自述嗎?我記得那幾堂課中的木心:懇切、平實,比他私下裏更謙抑,然而驚人地坦白——好像在座全是他最知心的朋友——同時,也如他儉省的用筆,點到即止,不使逾度。
木心寫作的快感,也是他長年纍月的自處之道,是與自己沒完沒瞭的對話、論辯、商量、反目,此書所錄,一變為亦莊亦諧、進退裕如的談吐。他的自賞與自嘲好比手心翻轉,他對自己的俯瞰與仲裁,接踵而至。日間校對這九堂課,我仍時時發笑。當他談罷〈S.巴哈的咳嗽麯〉的寫作,這樣說道:
好久不讀這篇。今天讀讀,這小子還可以。
如今「這小子」沒有瞭。下麵的話,好在他當年忍不住:
很委屈的。沒有人來評價注意這一篇。光憑這一篇,短短一篇,就比他們寫得好。五四時候也沒有人這樣寫的。
「他們」,指的誰呢?「五四時候」是也果然沒人這樣寫的:今時好像也沒有。就我所結識者,對木心再是深讀而賞的人,確也從未提及這一篇,而他話鋒一轉:
幸虧那時寫瞭。現在我是不肯瞭。何必。
這是真的。我總願木心繼續寫寫那類散文,九〇年代後期,他當真「不肯」瞭。此是木心的任性而有餘,也是他誠實。一九八五年寫成〈明天不散步瞭〉,他好開心,馬路上走著,孩子般著急錶功:「丹青啊,到目前為止,這是我寫得頂好的一篇散文!」可是八年後課中談起,卻又神色羞慚,涎著臉說道:
不過纔氣太華麗,不好意思。現在我來寫,不再這樣招搖瞭。
當時聽罷,眾人莞爾,此刻再讀,則我憮然有失:老頭子實在沒人可說,而稍起自得,便即自省,因他看待藝術的教養,高於自得。你看他分明當眾講述著,卻會臉色一正,好似針對我們,又如規勸自己,極鄭重地說:
當沒有人理解你時,你自己不要齣來講。
什麼叫做「私房話」呢,這就是私房話。全本《文學迴憶錄》的真價值,即在「私房」。他談到那麼多古今妙人,倒將自己講瞭齣來,而逐句談論自傢的作品,卻是在言說何謂文學、何謂文章、何謂用字與用詞。這可是高難度動作啊,愛書寫的人,哪裏找這等真貨?眼下,隱然而欠雛形的木心研究,似在萌動。此書麵世,應是大可尋味的文本,賞鑒木心而有待申說的作者,會留意他所謂「精靈」的自況,所謂「步虛」的自供嗎——承老頭子看得起我們,提前交瞭底,以世故論,誠哉所言非人:這是文學法庭再嚴厲的拷問也難求得的自白啊。
我知道,以上意思,不該我來說。但我也憋著私房話。那些年常與木心臨窗對坐,聽他笑嘆「不懂啊,不懂啊」,我好幾次急瞭,衝著他叫道:怕什麼啊,你就站齣來自己講!
這時,他總會移開視綫,啞著喉嚨,喃喃地說:不行的。那怎麼可以。
圖書試讀
(金高今天重返書院。)
今天,破例,講文學寫作——講我自己的作品。
三個比喻:畫傢,畫,你們看到的是最後的效果。有說是把畫傢畫畫全過程拍下來的,我就是說這寫作過程。其次,舞颱、後颱,我把我的後颱公開。再其次,過去的音樂傢,自己演奏自己的作品。蕭邦演奏自己的作品,最好。
今天算是木心文學作品演奏會。
不卑不亢地談。許多藝術上不允許講的話,我在課堂上講─我們相處十年瞭,開課四年瞭,其實很少有機會我來講自己寫作的過程。從來沒有深談過。
說得性感一點:這是不公開的。最殺手的拳,老師不教的─寫作的祕密。對你們寫作有好處。前幾年的課,是補藥,現在吃的,是特效藥。好處,是你們已經鋪瞭一些底。
是嘗試。可以鬆口氣。我每次要備課三天,兩萬字,有事忙不過來,這樣穿插可以調和。
眾人打開木心的書(颱灣版)。
今天講《即興判斷》裏的「代序」和〈塔下讀書處〉。
前一篇是答客問,後一篇是講彆人。諸位將來都會遇到這種事——講下去,你們會知道寫作有那麼一點奧妙。
「代序」,在音樂上類似序麯。有時可以取巧,用另一篇文章「代序」,很老練,用不到直接來寫序。
凡問答,採訪,不能太老實。要弄清對方意圖。這篇訪談,事先知道是對許多作傢的採訪,包括問哪些問題。我要知道說給誰聽─要刺誰。
發錶後,彆人的「答」也都發錶瞭,正好給我罵到。
我不願和他們混在一起,所以單獨取齣作代序。
《即興判斷》代序
丁卯春寒,雪夕遠客見訪,酬答問,不覺肆意妄言——謂我何求,謂我心憂,豈予好辯哉。鮮有良朋,貺也永嘆,悠悠繆斯,微神之躬,鬍為乎泥中。
——閱錄稿後識
先要來個「招式」,不宜用問答語,宜用文言(「閱錄稿後識」。「識」,音同「誌」。而且不能寫「木心閱稿後識」,要去名字。從前人傢多用自己名字,不必要)——「丁卯春寒,雪夕遠客見訪」,是文言的美。「不覺肆意妄言」,是退開,是謙虛。
「謂我何求,謂我心憂」,《詩經》的典故,簡化瞭。
「豈予好辯哉」是孟子的話,意思是我好辯嗎?不得已也。難道是我好辯嗎?這樣,就把「肆意妄言」解瞭。「鮮有良朋,貺也永嘆」(「貺」,音同「況」,賜的意思),取《詩經》,意思是少有朋友和我長嘆長談瞭。
用户评价
初次翻閱《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腦海中立即浮現的是木心先生那特有的、帶著疏離感卻又飽含深情的文字風格。在颱灣,木心先生早已是許多人心中的文學偶像,《文學迴憶錄》更是被奉為經典。因此,這本《補遺》的齣現,如同一份意料之外的驚喜,讓人迫不及待地想一窺究竟。 這本書並非對《文學迴憶錄》的簡單重復,更像是木心先生在多年後的又一次深刻的自我迴望。他以一種更為平和、更為個人化的姿態,與讀者進行著一場更為私密的對話。在《文學迴憶錄》中,我們更多的是驚嘆於他對西方文學史的宏大梳理,而在《補遺》中,他仿佛卸下瞭部分學者的光環,嚮我們展現瞭他內心更深處的風景。 我尤其欣賞木心先生對那些“遺珠”般的作傢和作品的獨特發掘。他並不局限於文學史上的“名傢名作”,而是善於在那些不那麼引人注目的角落裏,尋覓閃爍著藝術光芒的細節。他可能會花費相當多的篇幅,去解讀一位在文學史上並不那麼顯赫的作傢,或者分析一個在名作中看似微不足道的意象。這種“以小見大”的功力,不僅讓我驚嘆於他對文學藝術的深刻理解,也讓我看到瞭他那顆永不停止探索的赤誠之心。 從颱灣讀者的角度來看,木心先生的文字,總能以一種令人驚嘆的方式,將中西文化巧妙地融為一體。他在評論西方文學時,常常不自覺地引述中國古典詩詞的意境,或者用東方哲學的智慧來點亮西方文學的某些方麵。這種跨越文化的對話,在他筆下顯得如此自然流暢,又充滿東方特有的韻味。這讓我這些身處颱灣,既深受中華文化影響,又廣泛接觸西方思想的讀者,感到格外親切和認同。 更讓我著迷的是,書中那些“木心式”的、帶著智慧的幽默。他談論文學,談論人生,總能帶著一種清醒的旁觀,卻又充滿瞭溫情。他可能在評論某個觀點時,會突然冒齣一句讓人會心一笑的俏皮話,或者用一種看似玩笑的語氣,道齣人生的某種本質。這種在嚴肅與戲謔之間遊刃有餘的錶達方式,讓閱讀過程充滿樂趣,又在不知不覺中引發深刻的思考。 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知識的增長,更是一種精神上的滋養。在如今這個信息碎片化、節奏快速的時代,能夠靜下心來,閱讀木心先生這樣一位智者的文字,對我而言,是一種難得的寜靜。他引導我去思考,去感受,去發現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美好。他讓我明白,文學不僅僅是文字的組閤,更是對生命、對人性的深刻體悟。 我非常欣賞書中關於“孤獨”的深刻論述。木心先生對孤獨的理解,可謂入木三分。在《補遺》中,他對這個話題進行瞭更細緻的探討,他會通過具體的例子,來講述孤獨如何塑造一個藝術傢的靈魂,如何讓一個人的思想變得更加獨立和深刻。這讓我對孤獨有瞭新的認識,不再將其視為一種負麵的情緒,而是視為一種寶貴的創作源泉。 書中對一些“小眾”作傢的深入介紹,也讓我大開眼界。在《文學迴憶錄》裏,我們更多的是瞭解那些名垂青史的文學巨匠,而在《補遺》裏,木心先生則更像是“淘金者”,去發掘那些被埋沒的、卻同樣具有非凡纔華的作傢。這種對藝術的平等尊重,讓我覺得文學的世界是如此的廣闊,總有新的驚喜等待我們去發現。 這本書的裝幀設計,也透露著一種低調的精緻。沒有過多的華麗裝飾,卻恰到好處地襯托瞭木心先生文字的質感。翻閱時,仿佛能感受到他淡淡的煙草味,聽到他那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這種與作者精神上的連接,是我在許多齣版物中難以找到的。 總而言之,《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是一部充滿智慧、情感和獨特藝術風格的作品。它並非僅僅是《文學迴憶錄》的簡單延續,而更像是一次更為深入、更為個人化的精神探索。它讓我們有機會在木心先生的思想花園裏,發現更多未曾被注意過的珍寶。對於所有熱愛木心先生,熱愛文學,熱愛思考的人來說,這本書絕對是一份不容錯過的精神饋贈。
评分初翻《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一種久違的親切感油然而生。木心先生的名字,在颱灣文壇早就是傢喻戶曉的文化符號,《文學迴憶錄》更是激勵瞭無數求知若渴的心靈。而這本《補遺》,仿佛是老友間在多年後的一次閑談,又一次嚮我們揭示瞭他思想的深邃與廣闊。 這本書並非對《文學迴憶錄》的簡單羅列,而更像是在那些宏大的文學殿堂之外,為我們開闢瞭一個更加私密、更為細膩的觀察視角。木心先生似乎放下瞭部分學者的嚴謹,以一種更貼近生活、更富有人情味的方式,與我們分享他更深層的感悟。他談論的作傢、作品,可能在《文學迴憶錄》中隻是匆匆掠過,但在《補遺》中,卻被賦予瞭更為重要的地位,得以被他更為細緻地剖析和解讀。 我尤其欣賞木心先生對那些“遺珠”的獨特眼光。他並不拘泥於文學史上的“主流”,而是善於在那些不那麼引人注目的角落裏,尋覓閃爍著藝術光芒的細節。他可能會花費大量篇幅,去解讀一位在文學史上並不那麼齣名的作傢的某句話,或者分析一個在名作中看似微不足道的意象。這種“以小見大”的功力,不僅讓我驚嘆於他對文學藝術的深刻理解,也讓我看到瞭他那顆永不停止探索的赤誠之心。 從颱灣讀者的角度來說,木心先生的文字,總能以一種令人驚嘆的方式,將中西文化巧妙地融為一體。他在評論西方文學時,常常不自覺地引述中國古典詩詞的意境,或者用東方哲學的智慧來點亮西方文學的某些方麵。這種跨越文化的對話,在他筆下顯得如此自然流暢,又充滿東方特有的韻味。這讓我這些身處颱灣,既深受中華文化影響,又廣泛接觸西方思想的讀者,感到格外親切和認同。 更讓我著迷的是,書中那些“木心式”的、帶著智慧的幽默。他談論文學,談論人生,總能帶著一種清醒的旁觀,卻又充滿瞭溫情。他可能在評論某個觀點時,會突然冒齣一句讓人會心一笑的俏皮話,或者用一種看似玩笑的語氣,道齣人生的某種本質。這種在嚴肅與戲謔之間遊刃有餘的錶達方式,讓閱讀過程充滿樂趣,又在不知不覺中引發深刻的思考。 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知識的增長,更是一種精神上的滋養。在如今這個信息碎片化、節奏快速的時代,能夠靜下心來,閱讀木心先生這樣一位智者的文字,對我而言,是一種難得的寜靜。他引導我去思考,去感受,去發現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美好。他讓我明白,文學不僅僅是文字的組閤,更是對生命、對人性的深刻體悟。 我非常欣賞書中關於“孤獨”的深刻論述。木心先生對孤獨的理解,可謂入木三分。在《補遺》中,他對這個話題進行瞭更細緻的探討,他會通過具體的例子,來講述孤獨如何塑造一個藝術傢的靈魂,如何讓一個人的思想變得更加獨立和深刻。這讓我對孤獨有瞭新的認識,不再將其視為一種負麵的情緒,而是視為一種寶貴的創作源泉。 書中對一些“小眾”作傢的深入介紹,也讓我大開眼界。在《文學迴憶錄》裏,我們更多的是瞭解那些名垂青史的文學巨匠,而在《補遺》裏,木心先生則更像是“淘金者”,去發掘那些被埋沒的、卻同樣具有非凡纔華的作傢。這種對藝術的平等尊重,讓我覺得文學的世界是如此的廣闊,總有新的驚喜等待我們去發現。 這本書的裝幀設計,也透露著一種低調的精緻。沒有過多的華麗裝飾,卻恰到好處地襯托瞭木心先生文字的質感。翻閱時,仿佛能感受到他淡淡的煙草味,聽到他那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這種與作者精神上的連接,是我在許多齣版物中難以找到的。 總而言之,《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是一部充滿智慧、情感和獨特藝術風格的作品。它並非僅僅是《文學迴憶錄》的簡單延續,而更像是一次更為深入、更為個人化的精神探索。它讓我們有機會在木心先生的思想花園裏,發現更多未曾被注意過的珍寶。對於所有熱愛木心先生,熱愛文學,熱愛思考的人來說,這本書絕對是一份不容錯過的精神饋贈。
评分《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這本書,在我拿到手的那一刻,就有一種莫名的親切感。木心先生的名字,在颱灣的文化圈裏,早就不陌生瞭。他的《文學迴憶錄》更是像一本“聖經”一樣,影響瞭無數的年輕人,包括我。所以,當我知道有這本“補遺”的時候,心裏還是挺期待的,想知道在這個基礎上,他又會有什麼新的想法,新的分享。 翻開這本書,第一個感覺就是,他真的還是那個木心。那種既疏離又深刻的洞察力,那種對文學、對人性,有著不被世俗沾染的清醒。他談論文學,但他的話語,總能輕易地穿透文學的錶象,直抵生命的內核。在《文學迴憶錄》裏,我們更多的是看到他對西方文學的梳理和解讀,那些宏大的敘事,那些大師的群像。而在《補遺》裏,我感覺他更像是在和我們分享一些私人的感悟,一些更細微的情感。 就好像,你以為你已經把一個朋友的生活瞭解得七七八八瞭,結果他突然拿齣瞭一本日記,裏麵記錄著那些不為人知的喜怒哀樂。這本書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他會提到一些在《文學迴憶錄》裏可能隻是帶過的作傢、作品,但這一次,他會用更長的篇幅,更深入的視角去剖析。他會聊到某個作傢生命中的某個轉摺點,或者某個作品裏一個被忽略的細節,然後從中引申齣他對生活、對藝術的理解。這種感覺,就像是在跟著一位老朋友,在一傢安靜的咖啡館裏,慢慢地品味人生。 從颱灣的角度來看,我們一直以來都深受中西文化的影響。木心先生的作品,恰恰在這兩者之間找到瞭一個絕佳的平衡點。他談論西方文學,卻總能用東方人的視角去解讀;他談論中國傳統文化,卻又注入瞭現代的思辨。這本書更是如此,他可能在談到一段法國文學的評論時,突然蹦齣一句中國古詩,或者用一個中國式的比喻來形容一個西方藝術傢的情感。這種跨文化的融會貫通,讓我感到特彆的驚喜和受用。他仿佛在告訴我們,真正的藝術,是沒有國界的。 而且,這本書裏有很多木心先生式的“俏皮話”,那種帶著智慧的幽默感。他在談論一些嚴肅的文學理論時,偶爾會冒齣幾句讓人會心一笑的評論,或者用一種看似玩笑的口吻,揭示一些深刻的道理。這種在嚴肅與輕鬆之間切換自如的能力,真的是一種功力。它讓閱讀變得輕鬆有趣,又不失思想的深度。我覺得,這不僅僅是文學的魅力,更是人生的智慧。 對於我個人來說,在現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每天接收到的信息太多太雜瞭。能夠靜下心來,讀一本像《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這樣的書,對我來說,是一種精神上的洗禮。木心先生的文字,總是有一種安定人心的力量。他引導你去思考,去感受,去發現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美。他讓我們明白,文學不僅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情感的錶達,思想的碰撞,以及靈魂的共鳴。 我特彆喜歡書中關於“孤獨”的討論。木心先生對孤獨有著非常深刻的理解,他認為孤獨是藝術傢必備的品質。在《補遺》裏,他對這個話題有更深入的闡述,他會通過一些具體的例子,來講述孤獨如何塑造一個人的藝術視野,如何讓一個人的思想更加獨立和深刻。這讓我覺得,原來孤獨並不可怕,它反而是成長的催化劑,是創作的源泉。 還有,書中對一些“小眾”作傢的介紹和評價,也讓我耳目一新。在《文學迴憶錄》裏,他主要介紹的是那些赫赫有名的文學巨匠,而在《補遺》裏,他似乎更願意去發掘那些被埋沒的天纔,去和我們分享那些不為人知的藝術瑰寶。這種“淘金者”的精神,讓我覺得,文學的世界是如此的廣闊,還有太多的未知等待我們去探索。 這本書的排版和設計,也顯得十分用心。沒有花哨的裝飾,就是簡簡單單的文字,卻有一種沉甸甸的質感。翻閱的時候,仿佛能感受到木心先生的呼吸,聽到他低沉的聲音。這種與作者精神上的連接,是很多書都無法給予的。它讓我覺得,我不僅僅是在閱讀文字,更是在和一位老師,一位長者,進行一場靈魂的對話。 總的來說,《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這本書,對我而言,絕對是一份珍貴的精神食糧。它不隻是對《文學迴憶錄》的補充,更是一種升華。它讓我在理解木心先生的思想時,有瞭更深的層次,更廣的視野。對於每一個熱愛文學,熱愛思考的人來說,這本書,都值得你細細品味,慢慢領悟。
评分初捧《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心中湧起的,是熟悉又驚喜的情感。木心先生的名字,在颱灣文壇早已是文化界的傳奇,《文學迴憶錄》更是無數人心中的精神指南。這本《補遺》,恰似一位老友,又一次敞開心扉,與我們進行一場更為私密、更為深入的對話。 這本書並非對《文學迴憶錄》的簡單重復,而是更像木心先生在多年後,又一次對自己思想的深挖與延展。他在《文學迴憶錄》中為我們勾勒瞭宏大的文學版圖,而在《補遺》中,則更像是帶我們走進畫捲的某個角落,細細品味那些不曾被注意,卻同樣閃耀著藝術光芒的細節。他不再僅僅是那個站在高處的智者,而更像是那個在午後陽光下,與自己內心深處的某個片段進行纏鬥的思考者。 我尤為欣賞木心先生對那些“遺珠”般的作傢和作品的獨特發掘。他並不拘泥於文學史上的“名傢名作”,而是善於在那些不那麼引人注目的角落裏,尋覓閃爍著藝術光芒的細節。他可能會花費相當多的篇幅,去解讀一位在文學史上並不那麼顯赫的作傢,或者分析一個在名作中看似微不足道的意象。這種“以小見大”的功力,不僅讓我驚嘆於他對文學藝術的深刻理解,也讓我看到瞭他那顆永不停止探索的赤誠之心。 從颱灣讀者的角度來看,木心先生的文字,總能以一種令人驚嘆的方式,將中西文化巧妙地融為一體。他在評論西方文學時,常常不自覺地引述中國古典詩詞的意境,或者用東方哲學的智慧來點亮西方文學的某些方麵。這種跨越文化的對話,在他筆下顯得如此自然流暢,又充滿東方特有的韻味。這讓我這些身處颱灣,既深受中華文化影響,又廣泛接觸西方思想的讀者,感到格外親切和認同。 更讓我著迷的是,書中那些“木心式”的、帶著智慧的幽默。他談論文學,談論人生,總能帶著一種清醒的旁觀,卻又充滿瞭溫情。他可能在評論某個觀點時,會突然冒齣一句讓人會心一笑的俏皮話,或者用一種看似玩笑的語氣,道齣人生的某種本質。這種在嚴肅與戲謔之間遊刃有餘的錶達方式,讓閱讀過程充滿樂趣,又在不知不覺中引發深刻的思考。 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知識的增長,更是一種精神上的滋養。在如今這個信息碎片化、節奏快速的時代,能夠靜下心來,閱讀木心先生這樣一位智者的文字,對我而言,是一種難得的寜靜。他引導我去思考,去感受,去發現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美好。他讓我明白,文學不僅僅是文字的組閤,更是對生命、對人性的深刻體悟。 我非常欣賞書中關於“孤獨”的深刻論述。木心先生對孤獨的理解,可謂入木三分。在《補遺》中,他對這個話題進行瞭更細緻的探討,他會通過具體的例子,來講述孤獨如何塑造一個藝術傢的靈魂,如何讓一個人的思想變得更加獨立和深刻。這讓我對孤獨有瞭新的認識,不再將其視為一種負麵的情緒,而是視為一種寶貴的創作源泉。 書中對一些“小眾”作傢的深入介紹,也讓我大開眼界。在《文學迴憶錄》裏,我們更多的是瞭解那些名垂青史的文學巨匠,而在《補遺》裏,木心先生則更像是“淘金者”,去發掘那些被埋沒的、卻同樣具有非凡纔華的作傢。這種對藝術的平等尊重,讓我覺得文學的世界是如此的廣闊,總有新的驚喜等待我們去發現。 這本書的裝幀設計,也透露著一種低調的精緻。沒有過多的華麗裝飾,卻恰到好處地襯托瞭木心先生文字的質感。翻閱時,仿佛能感受到他淡淡的煙草味,聽到他那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這種與作者精神上的連接,是我在許多齣版物中難以找到的。 總而言之,《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是一部充滿智慧、情感和獨特藝術風格的作品。它並非僅僅是《文學迴憶錄》的簡單延續,而更像是一次更為深入、更為個人化的精神探索。它讓我們有機會在木心先生的思想花園裏,發現更多未曾被注意過的珍寶。對於所有熱愛木心先生,熱愛文學,熱愛思考的人來說,這本書絕對是一份不容錯過的精神饋贈。
评分初翻開《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腦海中浮現的,是那個在颱灣文壇依舊如雷貫耳的名字,木心。他的《文學迴憶錄》早已是無數求知若渴的靈魂的燈塔,指引我們在浩瀚的文學海洋中航行。而這本《補遺》,如同在熟悉的港灣中偶然拾獲的陳年信箋,帶著一種意想不到的親切與驚喜。它並非對既往的簡單重復,而是如同老友間的閑談,在那些已被奉為圭臬的論述之外,緩緩道齣更深層的感悟,更細微的洞見。 讀這本書,就像是透過一個更加私密、更加 unfiltered 的視角,重新審視木心先生那顆敏感而博大的心靈。我們熟悉的他對西方文學的宏大敘事,他對中國古典詩詞的精妙解讀,在這本“補遺”中,似乎被一層更加溫暖、更加個人化的濾鏡所籠罩。他不再僅僅是那個站在講壇上,運籌帷幄的文學大師,而是那個在午後陽光下,對著泛黃的書頁,與自己的內心對話的智者。他提到的那些被忽略的細節,那些在《文學迴憶錄》中可能一筆帶過的片段,在此刻卻被賦予瞭新的生命。仿佛他是在說:“你們以為你們已經看到瞭我所有的風景,但其實,我還有一片不為人知的花園。” 這種“補遺”的性質,本身就充滿瞭魅力。它不像是一部完整的續集,而更像是一種精神上的延續,一種思想上的延伸。那些曾經聽過、讀過木心先生言論的人,會立刻感受到一種熟悉的親切感,但同時,又會因為那些新鮮的、或是被進一步挖掘的觀點而感到耳目一新。他談到某個作傢時,可能不再是僅僅復述其生平與作品,而是會分享一個與之相關的、更具個人色彩的片段,或是對某個作品中的某個意象,給齣更為精煉、更為令人玩味的詮釋。這種細緻入微的補充,恰恰展現瞭木心先生思想的層次感和深度,也讓我們得以窺見他思考的更多維度。 從颱灣讀者的角度來看,木心先生的文字,總是帶著一種獨特的魅力,一種既有西方文明的理性光輝,又不失東方民族的情感底蘊的張力。這本《補遺》,更是將這種融閤發揮到瞭極緻。他在談論古希臘神話時,可能突然會聯想到《紅樓夢》中的某個人物,或是用一句中國古詩來比喻西方文學中的某個現象。這種跨越文化、跨越時空的連接,在他的筆下,顯得如此自然而然,又如此令人拍案叫絕。這讓我們這些身處東方,卻又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讀者,感到格外的親切和理解。仿佛他是在用一種我們都能懂的語言,講述著人類共同的文學記憶。 更讓我著迷的是,這本書中不乏那些充滿“木心式”幽默和智慧的段落。他對待文學,對待生活,始終保持著一種清醒的疏離和深刻的介入。他在“補遺”中,可能仍然會不經意間流露齣對當下某些文化現象的調侃,或是用一種看似輕鬆的口吻,道齣人生的本質。這種在嚴肅與戲謔之間遊刃有餘的錶達方式,是木心先生獨有的風格,也是吸引無數讀者,包括我,反復品讀他的作品的魅力所在。這本書,就像是他留給我們的一封封充滿哲思的便條,需要我們細細揣摩,纔能體會其中蘊含的深意。 這本書給予我的,不單是知識的增長,更是一種精神上的滋養。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我們常常被各種信息碎片所淹沒,而閱讀木心先生的作品,尤其是這本《補遺》,就像是在喧囂中尋得一片寜靜的角落,與一位智者進行一場深刻的對話。他談論文學,但他的話語早已超越瞭文學本身,觸及瞭生命、存在、孤獨、愛等種種人類永恒的主題。這本書,讓我重新審視瞭自己與文學的關係,也讓我更加深刻地理解瞭生命的意義。 我特彆欣賞書中那些關於“細節”的論述。木心先生總是能從宏大的文學史中,捕捉到那些微小卻至關重要的細節,並從中提煉齣深刻的見解。在《文學迴憶錄》中,這些細節可能隻是點綴,但在《補遺》中,它們被賦予瞭更重要的地位。他可能通過對某位作傢一句不起眼的話語的解讀,或是對某個作品中一個短暫場景的挖掘,來揭示作者更深層的情感和思想。這種“以小見大”的功力,正是木心先生過人之處,也讓我們這些讀者,在閱讀時,能夠更加細緻地體味文字的魅力,和作者的用心。 這本書的裝幀設計,也讓我感受到瞭一種特彆的誠意。不張揚,不媚俗,恰到好處的樸實,就像木心先生的為人一樣,內斂而有力量。翻開書頁,字裏行間,仿佛還能感受到他淡淡的煙草味,聽到他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是許多齣版物難以企及的。它讓我覺得,我不僅僅是在讀一本書,更是在與一位偉大的靈魂進行一次穿越時空的交流。 對於我們這些在颱灣生活,同時又深受中華文化熏陶的讀者來說,木心先生的作品,總是能夠引發我們內心深處最深刻的共鳴。他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理解,既有曆史的厚重感,又不乏現代的視角。在《補遺》中,他可能還會提到一些我們熟悉卻又容易被遺忘的典故,或是用一種全新的方式解讀我們耳熟能詳的詩句。這種“溫故而知新”的感覺,讓我倍感欣慰,也讓我覺得,自己的文化根基,在木心先生的引導下,得到瞭更加豐富和深刻的滋養。 總而言之,《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並非僅僅是《文學迴憶錄》的簡單延伸,而是一次更為深入、更為個人化、也更為溫暖的精神之旅。它讓我們有機會在木心先生的思想花園裏,發現更多未曾被注意過的珍寶。對於所有熱愛木心先生,熱愛文學的人來說,這本書絕對是一份不容錯過的饋贈。它將繼續點亮我們前行的道路,讓我們在文學的世界裏,找到更多的啓示和感動。
评分初翻《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便有一種久違的親切感撲麵而來。木心先生的名字,在颱灣的文化界早已如雷貫耳,他的《文學迴憶錄》更是影響瞭無數熱愛文學的靈魂。這本《補遺》,如同收到瞭一封遲到多年的、卻飽含深情的信件,讓人迫不及待地想要一探究竟。 這本書並非對《文學迴憶錄》的簡單復製或擴充,而更像是木心先生在多年後,又一次深入的自我剖析與生命迴望。他不再僅僅是那個站在講颱上,為我們梳理文學史的智者,而是更像一位在午後陽光下,與自己內心深處的某個角落進行對話的智者。他所提及的那些曾被忽略的細節,那些在《文學迴憶錄》中可能一筆帶過的作傢或作品,在此刻都仿佛被賦予瞭新的生命,成為瞭他思想另一重維度的呈現。 我尤為欣賞木心先生對那些“遺珠”般的作傢和作品的關注。他並非局限於文學史上的“名傢名作”,而是善於在那些不那麼引人注目的角落裏,尋覓閃爍著藝術光芒的細節。他可能會花費相當多的篇幅,去解讀一位在文學史上並不那麼顯赫的作傢,或者分析一個在名作中看似微不足道的意象。這種“以小見大”的功力,不僅讓我驚嘆於他對文學藝術的深刻理解,也讓我看到瞭他那顆永不停止探索的赤誠之心。 從颱灣讀者的角度來看,木心先生的文字,總能以一種令人驚嘆的方式,將中西文化巧妙地融為一體。他在評論西方文學時,常常不自覺地引述中國古典詩詞的意境,或者用東方哲學的智慧來點亮西方文學的某些方麵。這種跨越文化的對話,在他筆下顯得如此自然流暢,又充滿東方特有的韻味。這讓我這些身處颱灣,既深受中華文化影響,又廣泛接觸西方思想的讀者,感到格外親切和認同。 更讓我著迷的是,書中那些“木心式”的、帶著智慧的幽默。他談論文學,談論人生,總能帶著一種清醒的旁觀,卻又充滿瞭溫情。他可能在評論某個觀點時,會突然冒齣一句讓人會心一笑的俏皮話,或者用一種看似玩笑的語氣,道齣人生的某種本質。這種在嚴肅與戲謔之間遊刃有餘的錶達方式,讓閱讀過程充滿樂趣,又在不知不覺中引發深刻的思考。 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知識的增長,更是一種精神上的滋養。在如今這個信息碎片化、節奏快速的時代,能夠靜下心來,閱讀木心先生這樣一位智者的文字,對我而言,是一種難得的寜靜。他引導我去思考,去感受,去發現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美好。他讓我明白,文學不僅僅是文字的組閤,更是對生命、對人性的深刻體悟。 我非常欣賞書中關於“孤獨”的深刻論述。木心先生對孤獨的理解,可謂入木三分。在《補遺》中,他對這個話題進行瞭更細緻的探討,他會通過具體的例子,來講述孤獨如何塑造一個藝術傢的靈魂,如何讓一個人的思想變得更加獨立和深刻。這讓我對孤獨有瞭新的認識,不再將其視為一種負麵的情緒,而是視為一種寶貴的創作源泉。 書中對一些“小眾”作傢的深入介紹,也讓我大開眼界。在《文學迴憶錄》裏,我們更多的是瞭解那些名垂青史的文學巨匠,而在《補遺》裏,木心先生則更像是“淘金者”,去發掘那些被埋沒的、卻同樣具有非凡纔華的作傢。這種對藝術的平等尊重,讓我覺得文學的世界是如此的廣闊,總有新的驚喜等待我們去發現。 這本書的裝幀設計,也透露著一種低調的精緻。沒有過多的華麗裝飾,卻恰到好處地襯托瞭木心先生文字的質感。翻閱時,仿佛能感受到他淡淡的煙草味,聽到他那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這種與作者精神上的連接,是我在許多齣版物中難以找到的。 總而言之,《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是一部充滿智慧、情感和獨特藝術風格的作品。它並非僅僅是《文學迴憶錄》的簡單延續,而更像是一次更為深入、更為個人化的精神探索。它讓我們有機會在木心先生的思想花園裏,發現更多未曾被注意過的珍寶。對於所有熱愛木心先生,熱愛文學,熱愛思考的人來說,這本書絕對是一份不容錯過的精神饋贈。
评分初見《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書名,心中已然湧起一股期待與好奇。木心先生的名字,在颱灣文壇一直有著非同尋常的地位,《文學迴憶錄》更是許多人心中的經典之作。這本《補遺》的齣現,仿佛是收到瞭一位老友寄來的、充滿生活氣息的信件,讓人迫不及待想要一探究竟。 翻開書頁,那種熟悉的、帶著睿智和疏離的語調便撲麵而來。這本《補遺》並非對《文學迴憶錄》的簡單復述或擴充,而更像是在那些宏大的文學圖景之外,為我們勾勒齣更為私密、更為細膩的內心風景。木心先生不再僅僅是那個站在講颱上的學者,而更像是一位在靜謐的午後,與自己對話的智者。他所提及的那些曾被忽略的細節,那些在《文學迴憶錄》中可能隻是一筆帶過的作傢或作品,在此刻都仿佛被賦予瞭新的生命,成為瞭他思想的另一重維度。 我特彆欣賞書中對那些“遺珠”的關注。木心先生總是能在浩瀚的文學星空中,精準地捕捉到那些雖然不那麼耀眼,卻同樣閃爍著獨特光芒的星辰。他可能會花費相當多的篇幅,去解讀一位在文學史上並不那麼顯赫的作傢,或者分析一個在名作中看似不起眼的情節。這種“細節控”的特質,在《補遺》中得到瞭更為充分的體現。他並非簡單地羅列事實,而是通過對這些“小”的元素的深入剖析,來揭示更深層的藝術原理和人性洞察。 從颱灣讀者的角度來看,木心先生的文字,總是能輕易地跨越文化和時區的界限。他在評論西方文學作品時,常常會不自覺地援引中國古典的詩詞歌賦,或者用東方哲學中的概念來闡釋。這種看似跳躍的聯想,在他的筆下卻顯得如此自然流暢,又充滿東方特有的韻味。這讓我這些身處颱灣,既深受中華文化影響,又廣泛接觸西方思想的讀者,感到格外親切和認同。他仿佛在告訴我們,偉大的藝術,終究是相通的。 更讓我感到驚喜的是,書中不乏那些“木心式”的、帶著智慧的幽默。他談論文學,談論人生,總能用一種看似輕鬆的口吻,道齣深刻的哲理。他可能在評論某個作傢的某個觀點時,突然冒齣一句讓人會心一笑的俏皮話,或者用一種看似調侃的語氣,揭示某種普遍的人生睏境。這種將嚴肅與戲謔巧妙融閤的錶達方式,讓閱讀過程充滿樂趣,又在不知不覺中引發深刻的思考。 這本書給我的感覺,更像是一種精神上的陪伴。在如今這個信息碎片化、節奏快速的時代,能夠靜下心來,閱讀木心先生這樣一位智者的文字,對我而言,是一種難得的寜靜。他引導我去思考,去感受,去發現那些被忽略的美好。他讓我明白,文學不僅僅是文字的組閤,更是對生命、對人性的深刻體悟。 我尤為喜歡書中關於“孤獨”的論述。木心先生對孤獨的理解,可以說是深入骨髓。在《補遺》中,他對這個話題進行瞭更細緻的探討,他會通過具體的例子,來講述孤獨如何塑造一個藝術傢的靈魂,如何讓一個人的思想變得更加獨立和深刻。這讓我對孤獨有瞭新的認識,不再將其視為一種負麵的情緒,而是視為一種寶貴的創作源泉。 書中對一些“小眾”作傢的深入介紹,也讓我大開眼界。在《文學迴憶錄》裏,我們更多的是瞭解那些名垂青史的文學巨匠,而在《補遺》裏,木心先生則更像是“淘金者”,去發掘那些被埋沒的、卻同樣具有非凡纔華的作傢。這種對藝術的平等尊重,讓我覺得文學的世界是如此的廣闊,總有新的驚喜等待我們去發現。 這本書的裝幀設計,也透露著一種低調的精緻。沒有過多的華麗裝飾,卻恰到好處地襯托瞭木心先生文字的質感。翻閱時,仿佛能感受到他淡淡的煙草味,聽到他那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這種與作者精神上的連接,是我在許多齣版物中難以找到的。 總而言之,《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是一部充滿智慧、情感和獨特藝術風格的作品。它並非僅僅是《文學迴憶錄》的簡單延續,而更像是一次更為深入、更為個人化的精神探索。它讓我們有機會在木心先生的思想花園裏,發現更多未曾被注意過的珍寶。對於所有熱愛木心先生,熱愛文學,熱愛思考的人來說,這本書絕對是一份不容錯過的精神饋贈。
评分初捧《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心中湧起的,是一種久違的驚喜,以及對木心先生那永不褪色的文字魅力的再次確認。在颱灣,木心先生的名字早已是許多人心中的一座精神燈塔,《文學迴憶錄》更是無數求知者的案頭常備。而這本《補遺》,如同一封遲到的、卻又飽含深情的手劄,為我們打開瞭通往木心先生更深層思想世界的一扇窗。 它不像是一次簡單的“續集”,更像是在已經熟悉的畫捲上,又添上瞭幾筆更細膩、更動人的色彩。我們熟悉的木心,那個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的文學大師,在這個“補遺”中,似乎卸下瞭部分的光環,以一種更為平和、更為貼近的方式,與我們進行著一場更為私密的對話。他不再僅僅是那個站在高處俯瞰文學史的智者,而是那個在某個午後,對著窗外的陽光,與自己內心深處的某個片段進行纏鬥的凡人。 我尤其喜歡書中對那些“邊緣”的、或者說“被忽略”的文學細節的關注。在《文學迴憶錄》中,木心先生已然展現瞭他對西方文學史的宏大視野,而這本《補遺》,則更像是他帶著我們,在那些被大傢熟知的星辰之外,去探索那些閃爍著獨特光芒的黯淡星係。他可能會對某位二三流作傢筆下的某一個句子,或者某個作品中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意象,進行一番深入的挖掘和解讀。這種“以小見大”的功力,讓我驚嘆於他那顆敏銳而博大的心靈,以及他對文學藝術近乎偏執的探究精神。 從颱灣讀者的視角來看,木心先生的文字,總能巧妙地融匯中西文化的精髓。他在評價西方文學時,常常會引經據典,旁徵博引,但他的引用的“典”,卻常常是中國式的。這種跨越時空的對話,在他筆下顯得那麼自然而然,又那麼令人拍案叫絕。在《補遺》中,這種對話似乎更加頻繁和深入。他可能在講述一個古希臘神話的殘片時,會突然聯想到《莊子》中的某個寓言,或者用一句唐詩來形容某位現代派詩人的情感睏境。這種解讀,不僅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瞭西方文學,更讓我們重新審視瞭我們自身的文化傳統。 更讓我著迷的是,書中那些充滿瞭“木心式”黑色幽默和深刻哲思的段落。他對待文學,對待人生,始終保持著一種清醒的審視和超然的達觀。在《補遺》中,他可能仍然會不經意間流露齣對當下某些社會現象的調侃,或者用一種看似隨意的口吻,道齣人生的本質。這種在嚴肅與戲謔之間遊刃有餘的錶達方式,是木心先生獨有的藝術魅力,也是吸引無數讀者,包括我,反復品讀他的作品的根源。 讀這本書,就像是在與一位至交好友,進行一場深夜的促膝長談。他不再是那個遙不可及的文學巨匠,而是那個願意與你分享他最真實的感受、最深層的思考的知己。他提到的那些故事,那些感悟,雖然不是驚天動地的壯舉,卻往往能夠觸動我們內心最柔軟的地方。它讓我們反思,我們與文學的關係,我們與生活,與自己的關係。 我特彆欣賞書中關於“閱讀”本身的方法論。木心先生並非簡單地告訴你“讀什麼”,而是告訴你“如何讀”,以及“為什麼讀”。在《補遺》中,他或許會分享他自己早年閱讀的經曆,那些麯摺和迷茫,以及最終如何找到屬於自己的閱讀路徑。這種經驗的分享,對於正在文學道路上探索的年輕一代,具有極大的指導意義。它告訴我們,閱讀並非一項被動的接受過程,而是一場主動的探索和創造。 這本書的裝幀和排版,也讓我感受到瞭一種特彆的誠意。樸實無華,卻又不失品味,恰如其分地襯托瞭木心先生文字的風格。翻開書頁,字裏行間,仿佛還能感受到他那特有的、淡淡的煙草味道,聽到他那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是許多齣版物所難以企及的。它讓我覺得,我不僅僅是在讀一本書,更是在與一位偉大的靈魂進行一次穿越時空的交流。 對於我這樣身處颱灣的讀者來說,木心先生的作品,總是能夠激起一種強烈的文化認同感。他對於中國傳統文學的理解,既有曆史的厚重感,又不乏現代的批判性。在《補遺》中,他可能還會提到一些我們熟悉卻又容易被遺忘的典故,或是用一種全新的方式解讀我們耳熟能詳的詩句。這種“溫故而知新”的感覺,讓我倍感親切,也讓我覺得,自己的文化根基,在木心先生的引導下,得到瞭更加豐富和深刻的滋養。 總而言之,《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是一部充滿智慧、情感和獨特魅力的作品。它不僅僅是對《文學迴憶錄》的補充,更是一種精神的升華。它讓我們有機會在木心先生的思想花園裏,發現更多未曾被注意過的珍寶。對於所有熱愛木心先生,熱愛文學,熱愛思考的人來說,這本書絕對是一份不容錯過的精神饋贈。
评分初翻《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一股濃濃的木心式風格便撲麵而來,熟悉中又帶著新的驚喜。在颱灣,木心先生的名字早已深入人心,《文學迴憶錄》更是無數人心中的精神食糧。這本《補遺》,就像是老友再次為你打開心扉,娓娓道來的故事,讓人心生暖意。 這本書與《文學迴憶錄》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如果在《文學迴憶錄》中,木心先生是為我們勾勒齣一幅宏大的文學全景圖,那麼在這本《補遺》中,他則更像是帶著我們,深入到畫捲的某個角落,細細品味那些被忽視卻同樣動人的細節。他不再僅僅是那個站在講颱上,運籌帷幄的文學巨匠,而是更像一位在燈下,與自己曾經的思緒對話的智者。 我特彆欣賞書中對那些“被遺忘的角落”的關注。木心先生從不拘泥於文學史上的“顯赫人物”,他更喜歡在那些不為人知的地方,挖掘齣真正有價值的思想和藝術。他可能會花大量篇幅,去評論一位在文學史上並不那麼起眼的作傢,或者分析一部作品中一個看似微不足道的意象。這種“以小見大”的功力,讓我驚嘆於他對藝術的敏感度,以及他那顆永不停止探索的赤誠之心。 從颱灣讀者的角度來說,木心先生的文字,總能以一種令人驚嘆的方式,將中西文化巧妙地融為一體。他在評論西方文學時,常常不自覺地引述中國古典詩詞的意境,或者用東方哲學的智慧來點亮西方文學的某些方麵。這種跨越文化的對話,在他筆下顯得如此自然流暢,又充滿東方特有的韻味。這讓我這些身處颱灣,既深受中華文化影響,又廣泛接觸西方思想的讀者,感到格外親切和認同。 更讓我著迷的是,書中那些“木心式”的、帶著智慧的幽默。他談論文學,談論人生,總能帶著一種清醒的旁觀,卻又充滿瞭溫情。他可能在評論某個觀點時,會突然冒齣一句讓人會心一笑的俏皮話,或者用一種看似玩笑的語氣,道齣人生的某種本質。這種在嚴肅與戲謔之間遊刃有餘的錶達方式,讓閱讀過程充滿樂趣,又在不知不覺中引發深刻的思考。 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知識的增長,更是一種精神上的滋養。在如今這個信息碎片化、節奏快速的時代,能夠靜下心來,閱讀木心先生這樣一位智者的文字,對我而言,是一種難得的寜靜。他引導我去思考,去感受,去發現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美好。他讓我明白,文學不僅僅是文字的組閤,更是對生命、對人性的深刻體悟。 我非常欣賞書中關於“孤獨”的深刻論述。木心先生對孤獨的理解,可謂入木三分。在《補遺》中,他對這個話題進行瞭更細緻的探討,他會通過具體的例子,來講述孤獨如何塑造一個藝術傢的靈魂,如何讓一個人的思想變得更加獨立和深刻。這讓我對孤獨有瞭新的認識,不再將其視為一種負麵的情緒,而是視為一種寶貴的創作源泉。 書中對一些“小眾”作傢的深入介紹,也讓我大開眼界。在《文學迴憶錄》裏,我們更多的是瞭解那些名垂青史的文學巨匠,而在《補遺》裏,木心先生則更像是“淘金者”,去發掘那些被埋沒的、卻同樣具有非凡纔華的作傢。這種對藝術的平等尊重,讓我覺得文學的世界是如此的廣闊,總有新的驚喜等待我們去發現。 這本書的裝幀設計,也透露著一種低調的精緻。沒有過多的華麗裝飾,卻恰到好處地襯托瞭木心先生文字的質感。翻閱時,仿佛能感受到他淡淡的煙草味,聽到他那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這種與作者精神上的連接,是我在許多齣版物中難以找到的。 總而言之,《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是一部充滿智慧、情感和獨特藝術風格的作品。它並非僅僅是《文學迴憶錄》的簡單延續,而更像是一次更為深入、更為個人化的精神探索。它讓我們有機會在木心先生的思想花園裏,發現更多未曾被注意過的珍寶。對於所有熱愛木心先生,熱愛文學,熱愛思考的人來說,這本書絕對是一份不容錯過的精神饋贈。
评分初拿到《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這本書,內心泛起的是一種熟悉的溫暖與好奇。木心先生的名字,在颱灣文壇早已是大傢耳熟能詳的文化符號,他的《文學迴憶錄》更是許多人心中的文學啓濛。而這本《補遺》,就像是木心先生在多年後,又一次溫情地迴望,並嚮我們吐露更多心聲的誠意之作。 這本書並非是對《文學迴憶錄》的簡單照搬或復製,而是像一場更加私密的、深入的對話。在《文學迴憶錄》中,木心先生以他博大的學識,為我們梳理瞭西方文學的璀璨星河。而在《補遺》中,我感覺他更像是打開瞭自己更為私人的書房,與我們分享那些更加細微、更為觸動他心靈的片段。他談論的作傢、作品,可能在《文學迴憶錄》中隻是匆匆一瞥,但在《補遺》中,卻被賦予瞭更長的篇幅和更深的解讀。 我尤為驚嘆於木心先生對那些“遺珠”的獨特發掘。他並不局限於文學史上的“名傢名作”,而是善於從那些並不那麼光鮮亮麗的角落裏,找到閃耀著藝術光芒的細節。他可能會對某位不那麼齣名的作傢的某句話,或者某個作品中某個不起眼的意象,進行一番令人拍案叫絕的解讀。這種“以小見大”的功力,讓我在閱讀時,不僅感受到瞭他對文學藝術的深刻理解,也窺見瞭他人性中那種對美不懈追求的赤誠。 從颱灣讀者的角度來看,木心先生的文字,總能以一種令人驚嘆的方式,將中西文化融為一體。他在評論西方文學時,常常不經意間引齣中國古典詩詞的意境,或者用東方哲學的智慧來點亮西方文學的某些方麵。這種跨越文化的對話,在他筆下顯得如此自然而巧妙,如同渾然天成的藝術品。在《補遺》中,這種跨文化解讀更加深入,也更加貼近我們的生活經驗,讓我感到特彆的共鳴。 更讓我著迷的是,書中那些“木心式”的、帶著智慧的幽默。他談論文學,談論人生,總是帶著一種清醒的旁觀,卻又充滿瞭溫情。他可能在評論某個觀點時,會突然冒齣一句讓人會心一笑的俏皮話,或者用一種看似玩笑的口吻,道齣人生的某種本質。這種在嚴肅與戲謔之間遊刃有餘的錶達方式,讓閱讀變得輕鬆有趣,又在不知不覺中引發深刻的思考。 這本書帶給我的,不僅僅是知識的增長,更是一種精神上的滋養。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我們常常被各種信息碎片所淹沒,而閱讀木心先生的作品,尤其是這本《補遺》,就像是在喧囂中尋得一片寜靜的角落,與一位智者進行一場深刻的對話。他引導我去思考,去感受,去發現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美好。 我非常欣賞書中關於“孤獨”的深刻論述。木心先生對孤獨的理解,可謂入木三分。在《補遺》中,他對這個話題進行瞭更細緻的探討,他會通過具體的例子,來講述孤獨如何塑造一個藝術傢的靈魂,如何讓一個人的思想變得更加獨立和深刻。這讓我對孤獨有瞭新的認識,不再將其視為一種負麵的情緒,而是視為一種寶貴的創作源泉。 書中對一些“小眾”作傢的深入介紹,也讓我大開眼界。在《文學迴憶錄》裏,我們更多的是瞭解那些名垂青史的文學巨匠,而在《補遺》裏,木心先生則更像是“淘金者”,去發掘那些被埋沒的、卻同樣具有非凡纔華的作傢。這種對藝術的平等尊重,讓我覺得文學的世界是如此的廣闊,總有新的驚喜等待我們去發現。 這本書的裝幀設計,也透露著一種低調的精緻。沒有過多的華麗裝飾,卻恰到好處地襯托瞭木心先生文字的質感。翻閱時,仿佛能感受到他淡淡的煙草味,聽到他那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這種與作者精神上的連接,是我在許多齣版物中難以找到的。 總而言之,《木心談木心:《文學迴憶錄》補遺》是一部充滿智慧、情感和獨特藝術風格的作品。它並非僅僅是《文學迴憶錄》的簡單延續,而更像是一次更為深入、更為個人化的精神探索。它讓我們有機會在木心先生的思想花園裏,發現更多未曾被注意過的珍寶。對於所有熱愛木心先生,熱愛文學,熱愛思考的人來說,這本書絕對是一份不容錯過的精神饋贈。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