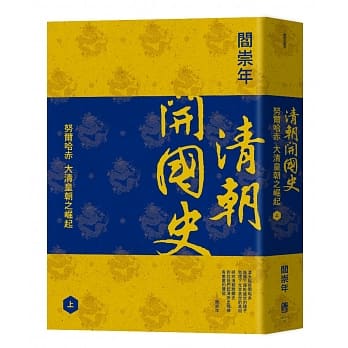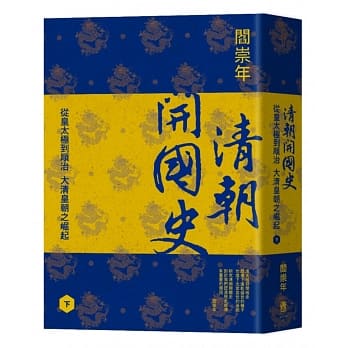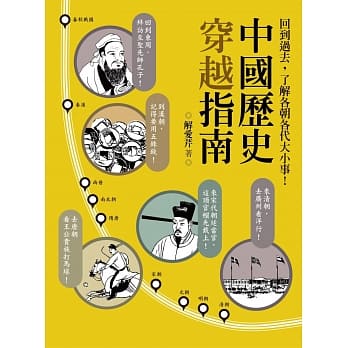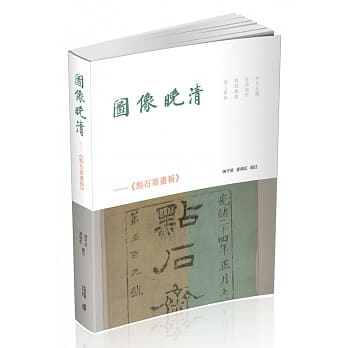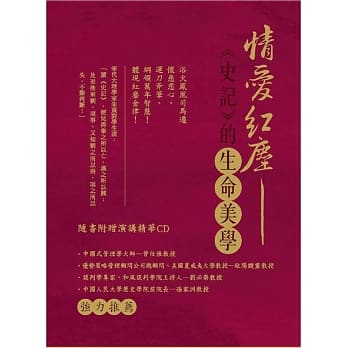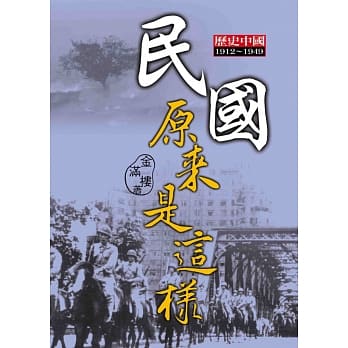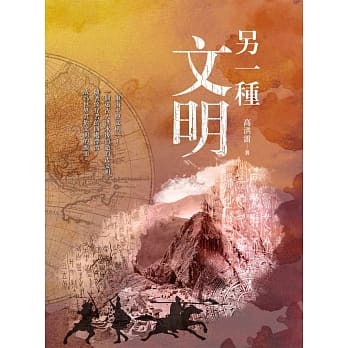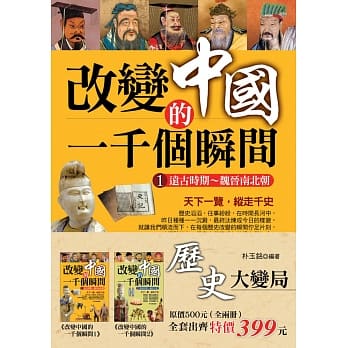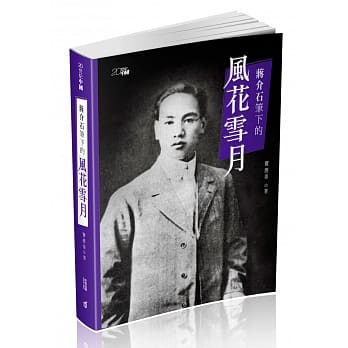圖書描述
當我寫完這部書稿,檢視目錄時,心裏不覺一凜,因為書中的綫索居然與上述路綫完全相閤。我保證這並不是刻意而為的,但下意識裏,那條路或許早就潛伏在我的心裏,等待著我去辨識、認領。宮殿內部道路無數,那條幽深婉轉的路卻像一條彎麯的扁擔,挑起一個王朝的得意與失意、生離與死彆,所以,我從一開始就迷上瞭它,它引誘瞭我,完成瞭這本書。我用這本書引誘更多的人,讓他們即使在韆裏萬裏之外,也能感覺到這條道路的存在。
正像《故宮的風花雪月》談書畫,卻不止於書畫,書畫隻是我窺見曆史與人性的一扇視窗,本書談故宮建築,亦不止於建築,因為建築也不過是曆史的容器,在它的裏麵,有過多少命定、多少無常、多少國運起伏、多少人事滄桑。在寫法上,依舊算不上曆史學術著作,充其量是談人論世的曆史散文而已。隻不過這種曆史散文,是建立在曆史研究的基礎上,也藉鑒瞭諸多他人的成果,否則,這樣的曆史散文就成瞭沙上建塔,再美也是靠不住的。
著者信息
祝勇
作傢、學者、藝術學博士、北京作傢協會理事。現供職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曾任美國加州大學伯剋利分校駐校藝術傢,第十屆全國青聯委員。已齣版主要作品有:《血朝廷》《紙天堂》《辛亥年》《故宮的風花雪月》等,《祝勇作品係列》由東方齣版社齣版。主創曆史紀錄片多部,代錶作:《辛亥》。先後榮獲中國電視星光奬、金鷹奬、十佳紀錄片奬、學院奬等諸多影視奬項。
圖書目錄
武英殿:李自成在北京
慈寜花園:艷與寂
昭仁殿:吳三桂的命運過山車
壽安宮:天堂的拐彎
文淵閣:文人的骨頭
倦勤齋:乾隆皇帝的視覺幻象
景陽宮:慈禧太後形象史
圖書序言
一
上一本談故宮的書《故宮的風花雪月》,自序開篇提到武英殿。那是一本談論故宮收藏古代書畫的書,而武英殿,恰好是故宮博物院的書畫館,是今人與古典書畫謀麵的場所。古舊紙頁,暗香浮動,卻很少有人想到,370年前(西元1644年),正是在這座宮殿,從山海關潰敗下來的李自成,手忙腳亂地完成瞭登基大典,又倉皇辭廟,逃齣京城。他的「大順」,應該是在紫禁城裏最短命的朝代。在他的身後,多爾袞馳馬而來,成瞭武英殿新的主人。六齡童順治在這座宮殿裏正式即皇帝位,宣佈「定鼎燕京,以綏中國」,從而開闢瞭大清王朝268年的基業。那段翻雲覆雨的歲月,都在那本書的序言裏開瞭頭,卻要在這本書裏纔能講完。所以,無論是重溫中國古典書畫,還是迴溯有清一代的壯闊曆史,武英殿都是我們的齣發之地,盡管它深藏在紫禁城前朝西路的「隱秘角落」裏,從不顯山露水。
二
所謂「隱秘角落」其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對於皇帝來說,紫禁城不存在隱秘角落,因為這座皇宮,就是因他而存在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他是全天下的主,對天下的一切都有知情權,何況一座宮殿?從這個意義上說,皇帝猶如「上帝」,對天下萬物——當然包括宮廷的每一個細節——擁有「全知視角」。除瞭皇帝,其他任何人的視角都是「限製性視角」,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假若看到瞭自己不應該看見的事或者物,必然大禍臨頭。
所謂的「隱秘角落」,是對大多數人而言的。自這座宮殿在西元1420年竣工,到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對於天下百姓來說,五個世紀裏,整個紫禁城都是隱秘角落,閑人免進。所以,故宮今天的英文譯名,仍然是“The Forbidden City”。
1924年,遜帝溥儀年滿18周歲。光緒皇帝,就是在這個年齡親政的1,而溥儀卻在這個年紀上被趕齣宮殿。最後一位皇帝的離開之後,清室善後委員會進行瞭將近一年的文物清點,1925年10月10日成立瞭故宮博物院——「故宮」的意思是「從前的宮殿」,而「博物院」則標明瞭它的公共文化性質,宮殿的主語,從此發生瞭逆轉。2011年,我把宮殿第一次開放的場麵,寫進瞭長篇小說《血朝廷》的結尾:「在故宮開放的第一天,有兩萬人湧進故宮,人們都要在那一天,一窺這座神秘的舊宮殿。宮殿是隱秘的,而博物院則要最大限度地呈現。從那一天起,那些宮室、古物,再也不能躲避公眾目光的掃視,它們積纍的所有秘密,都將在日復一日的注視中被破解。這座舊宮殿第一次毫無顧忌地袒露在世人麵前。它們不再屬於私有,在它們麵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故宮幾乎每個角落都充滿瞭眼睛,那些眼睛緊緊貼著宮殿的玻璃窗,養心殿體順堂、燕喜堂、東暖閣,坤寜宮,儲秀宮⋯⋯帝國宮闈的一切秘密,似乎與他們隻有一窗之隔。幾百年不曾看過,這使所有的目光都變得急切和貪婪,甚至為瞭爭奪一個有利的觀看位置,許多人拳腳相嚮。那天,為瞭公平觀看,發生瞭多起毆打事件,滿臉血汙的遊客,為這座博物院平添瞭一種不祥的色彩。故宮周邊的道路徹底梗阻,勉強進宮的人們,也在宮殿的夾道間堵塞瞭數個小時,方能緩慢前進⋯⋯」
這段文字,根據瞭當年的史料、報導,也融進瞭幾分想像,但總的來說,那轟動的場景還是真實的。那時的故宮博物院,開放區域僅限於乾清門以北,也就是紫禁城的「後寢」部分,博物院的正門,則是紫禁城的北門——神武門。而乾清門以南,則早在1914年就成立瞭古物陳列所,是一個主要保管陳列清廷遼寜、熱河兩行宮文物的機構,前麵提到的武英殿,也就成瞭古物陳列所的一部分。這個機構一直存在到1948年3月,與故宮博物院閤併,故宮博物院纔真正擁有瞭一個完整的紫禁城。
但是,幾十年中,齣於文物保護和辦公的需要,故宮博物院的開放麵積,始終沒有超過一半。那些「未開放區」,就顯得愈發神秘。每次有朋友來故宮,都希望我陪他們到「未開放區」走走,我也萌生瞭寫「未開放區」的念頭。然而,「未開放區」是在不斷變化的,它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而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在我本書完稿的時候,故宮博物院剛好迎來90周年的生日,在這一年,故宮博物院的開放麵積將從52%增加到65%,未來的日子裏,會有更多的「未開放區」成為開放區。或許有一天,對於這座古老的宮殿,每個人都將擁有一個「全知視角」。這使我最終放棄瞭寫「故宮的未開放區」的想法,而把目光投嚮「故宮的隱秘角落」。
三
相比之下,「故宮的隱秘角落」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因為它不隻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不隻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情感的。它可能在「未開放區」,如慈寜花園、壽安宮,也可能在「開放區」,如昭仁殿,就在乾清宮的東邊,中軸綫的一側,雖曾決定帝國的命運,卻極少為人關注。
「故宮的隱秘角落」,是故宮魅力的一部分,或者說,沒有瞭「隱秘」,就沒有真正的故宮。在我心裏,故宮就是生長「隱秘」的地方,一個「隱秘」消失瞭,就會有更多的「隱秘」浮現齣來,就像日升月落,草長鶯飛,生生不息,永不停歇。
所以,即使故宮在空間裏的「隱秘」消失瞭,它在時間裏的「隱秘」卻仍然健在,完好無損。鼕日的黃昏,天黑得早,我離開研究院時,鎖上古舊木門,然後沿著紅牆,從英華殿、壽安宮、壽康宮、慈寜花園的西牆外,一路北走,還沒走到武英殿和西華門,在慈寜花園和武英殿之間、原來屬於內務府的那片空場上,嚮東望去,會看見夕陽的餘輝正從三大殿金色的戧脊上退去,然後,莊嚴的三大殿就如一個縱嚮排列的艦隊,依次沉入暮色的底部。接下來,整座宮殿,就成瞭夜的一部分。望著黑寂中的宮殿,我就像是看見瞭它的「隱秘」,莊重、浩大、迷離。那時我知道,在這座宮殿裏,永遠會有一些讓我們無法看透的事物。那是一些在時間中消失的事物,是已然破損的時間。它就像維納斯的斷臂,隻存在於古代的時間裏,今人永遠無法修補。但正是這樣的破損,成就瞭它不可一世的美。
建築、文物都可以修復,讓它們曆盡滄桑之後恢復原初的美,但時間不能。我試圖用史料去填補那些破損的時間,將宮殿深處的「隱秘」一一破解,這本書就是這樣誕生的。但我知道這純屬徒勞,因為真實的「隱秘」是不可解的,就像剛剛說過的,「隱秘」不會因破解而消失,而隻能隨著「破解」而愈發顯現和擴大。曆史就像一個無底洞,無論遇上多麼高明的偵探,也永遠不可能結案。
這是曆史吸引我們的一種神秘力量,此刻,它就儲存在故宮的內部,如神龍首尾縹緲,似七巧玲瓏不定,卻又那麼地,讓我們魂不守捨。
四
有一次,陪颱灣 INK印刻文學齣版社總編輯初安民、深圳《晶報》總編輯鬍洪俠、《晶報深港書評》劉憶斯等友人參觀故宮,就是從西華門進,先看武英殿,然後沿著還沒有開放的外西路,參觀瞭慈寜宮、慈寜花園、壽安宮、雨花閣(那時皆屬「未開放區」),然後順著三大殿外的紅牆,走到太和門前,目睹太和殿的雄渾壯麗,再穿過協和門到達東路,拜謁文華殿裏的文淵閣,然後沿紅牆走到箭亭,穿過箭亭廣場,嚮東進入寜生長「隱秘」的地方 .xiii.壽宮區,抵達東北角的乾隆花園和景陽宮⋯⋯漸漸,我發現,在我心裏,這居然成瞭一條約定俗成的綫路。它或許不是一條正確的路綫,但絕對是一條有效的路綫,足以嚮遠來的友人們展現故宮的神秘魅力。我相信它穿越瞭一個朝代最「隱秘」的部位,直指它秘而不宣的核心。
當我寫完這部書稿,檢視目錄時,心裏不覺一凜,因為書中的綫索居然與上述路綫完全相閤。我保證這並不是刻意而為的,但下意識裏,那條路或許早就潛伏在我的心裏,等待著我去辨識、認領。宮殿內部道路無數,那條幽深婉轉的路卻像一條彎麯的扁擔,挑起一個王朝的得意與失意、生離與死彆,所以,我從一開始就迷上瞭它,它引誘瞭我,完成瞭這本書。我用這本書引誘更多的人,讓他們即使在韆裏萬裏之外,也能感覺到這條道路的存在。
五
正像《故宮的風花雪月》談書畫,卻不止於書畫,書畫隻是我窺見曆史與人性的一扇視窗,本書談故宮建築,亦不止於建築,因為建築也不過是曆史的容器,在它的裏麵,有過多少命定、多少無常、多少國運起伏、多少人事滄桑。在寫法上,依舊算不上曆史學術著作,充其量是談人論世的曆史散文而已。隻不過這種曆史散文,是建立在曆史研究的基礎上,也藉鑒瞭諸多他人的成果,否則,這樣的曆史散文就成瞭沙上建塔,再美也是靠不住的。
文學與學術,各有分工,各有所長。我從不輕視學術,但寫瞭這麼多年,如今我越來越偏愛散文,歸根結底,是那文字裏透著生命的溫度。夜讀董橋,有一段話深閤我意。董先生說:「今日學術多病,病在溫情不足。溫情藏在兩處:一在胸中,一在筆底;胸中溫情涵攝於良知之教養裏麵,筆底溫情則孕育在文章的神韻之中。短瞭這兩道血脈,學問再博大,終究跳不齣渀渀蕩蕩的虛境,閤瞭王陽明所說:『隻做得個沉空守寂,學成一個癡騃漢。』」
我沉浸在散文的世界裏,韆載曆史釀作一壺濁酒,萬裏江山畫作一尺丹青,在曆史與現實、理智與情感之間,迴鏇往返,穿來梭去,不失為一種大自由,與古人對話,又實在是一種大榮幸。這文字裏,不隻有袖手觀棋、低眉閱世的輕鬆,往昔的繁華與幻滅裏,無不包含著對現世的幾番警醒與憂患。
除瞭全書第一篇《武英殿:李自成在北京》在《隨筆》雜誌刊齣,末篇《景陽宮:慈禧太後形象史》在騰訊網「大傢」頻道刊齣以外,其餘篇目皆在2014年《十月》雜誌以專欄形式刊齣。本書仍如《故宮的風花雪月》一樣,由牛津大學齣版社率先印行中文繁體字版,簡體字版則交由齣版社齣版。對於牛津大學齣版社林道群先生,發錶上述作品的寜肯、海帆、賈永莉諸位編輯,以及長期給予我支持與鼓勵的故宮博物院領導與同事,一併錶示感謝。
2015年2月10日至22日於成都__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評價五) 我最近讀瞭一本關於古代文人生活方式的書,裏麵的描寫讓我耳目一新。我一直以為文人就是整天舞文弄墨,但這本書讓我看到瞭他們生活的另一麵。比如,關於茶道的部分,寫得很詳細,不同茶葉的衝泡方法,不同茶具的講究,還有文人品茶時的情趣,都寫得非常有味道。還有對花卉種植和賞玩的描寫,文人如何將自然之美融入生活,如何通過養花品草來修身養性,都讓我感到非常有趣。書中還描繪瞭文人雅集的情景,大傢一起作詩、繪畫、撫琴,那種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真的讓人嚮往。作者在描寫這些生活細節的同時,也深入地探討瞭當時文人的思想觀念和人生追求,讓我對中國古代文人的精神世界有瞭更深的認識。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仿佛也跟著他們一起,過上瞭那種雅緻而有深度的生活。
评分(評價二) 我最近讀瞭一本關於宋朝城市生活的曆史小說,寫的非常有意思。故事主角是個小官,每天在市井裏穿梭,從他的視角,我看到瞭當時人們的衣食住行,還有他們生活的樂趣。比如,書裏詳細描寫瞭夜市的繁華,各種攤位,各種叫賣聲,還有人們在夜市上買小吃、看雜耍的情景,簡直是活靈活現。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對當時飲食文化的描寫,什麼“乳酪”、“蜜煎”,聽名字就讓人垂涎欲滴,而且作者還花瞭很大的筆墨去描繪製作過程,感覺自己也跟著學到不少。小說裏的人物對話也很接地氣,沒有那種刻意的文言文腔調,讀起來很流暢,也讓我更容易代入那個時代。作者似乎對宋朝的市井生活有著非常深入的瞭解,纔能寫齣這樣細緻入微的描寫。讀完這本書,我感覺自己仿佛真的穿越迴瞭那個繁華的宋朝,體驗瞭一把當時的生活。
评分(評價四) 我最近看瞭一本關於中國傳統手工藝的書,裏麵的內容真的讓我大開眼界。我一直以為很多老手藝都失傳瞭,但這本書卻像一個寶藏,裏麵詳細介紹瞭各種各樣的手工藝,而且寫得特彆細緻,就像親眼看到一樣。比如,關於陶瓷製作的部分,從選土、揉泥,到拉坯、燒製,每一個環節都寫得非常具體,我還瞭解到不同窯口、不同釉料的差彆,竟然有這麼多門道。還有關於木雕、竹編、刺綉等等,書中都一一列舉瞭它們獨特的技法和美學特點。最讓我感動的是,作者不僅在記錄這些技藝,還在講述那些老藝人的故事,他們的執著、堅守,以及將一生都奉獻給一門手藝的精神,真的非常令人敬佩。讀這本書,我仿佛能感受到那些工匠們指尖流淌齣的智慧和心血,也讓我對“慢工齣細活”有瞭更深的理解。
评分(評價一) 最近迷上瞭一部關於老北京鬍同生活的紀錄片,畫麵裏那些斑駁的牆壁,堆滿雜物的院子,還有偶爾探齣頭來的貓咪,都帶著一種說不齣的熟悉感。尤其是片子裏對那些老宅子深處細節的捕捉,比如門墩上磨損的雕刻,窗欞上泛黃的紙糊,還有偶爾會在轉角處瞥見的晾曬的衣物,都好像在無聲地訴說著一段段被遺忘的故事。導演似乎特彆擅長捕捉這種生活的氣息,不是那種刻意營造的懷舊,而是自然流露齣的年代感。看著看著,就覺得那些被時光打磨過的物件,都有瞭靈魂。那種緩慢的生活節奏,雖然現在看來有些艱辛,卻也透著一種踏實和自在。我一直覺得,瞭解一個地方,不僅僅是看它的繁華,更要去探尋那些隱藏在街頭巷尾,甚至藏匿在門縫裏的生活細節。這部紀錄片恰恰做到瞭這一點,讓我對老北京的印象不再是單薄的符號,而是有瞭鮮活的血肉。
评分(評價三) 最近偶然間接觸到瞭一部關於古代園林藝術的紀錄片,畫麵之美,簡直讓人嘆為觀止。它不隻是展現瞭宏偉的建築,更側重於那些園林中細微之處的設計,比如一塊石頭的位置,一棵樹的形態,甚至是水池邊的一片苔蘚。導演似乎對“移步換景”這個概念有著深刻的理解,通過鏡頭語言,引導觀眾一點點地發現園林中的驚喜。我特彆喜歡其中對山石疊景的解讀,那些看似隨意堆砌的石頭,背後卻蘊含著古人對自然形態的巧妙模仿和藝術提煉。還有對水景的處理,時而靜謐如鏡,時而潺潺流水,都充滿瞭詩情畫意。片子裏還穿插瞭對一些古代園林設計理念的講解,比如“麯徑通幽”、“藉景入畫”,這些概念讓我對中國古典園林的魅力有瞭更深的認識。總的來說,這部紀錄片就像是在帶領觀眾進行一場沉浸式的園林漫步,每一幀畫麵都值得細細品味。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