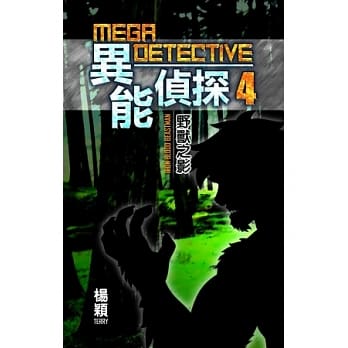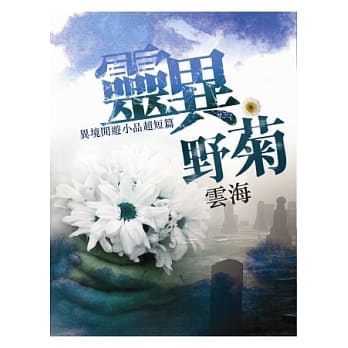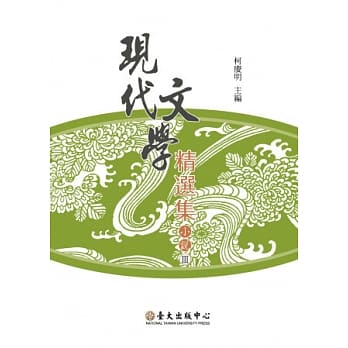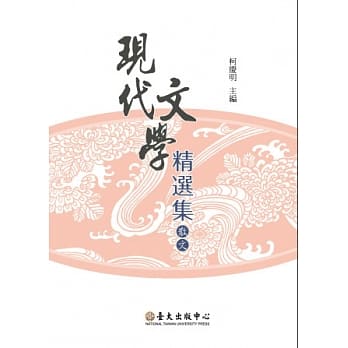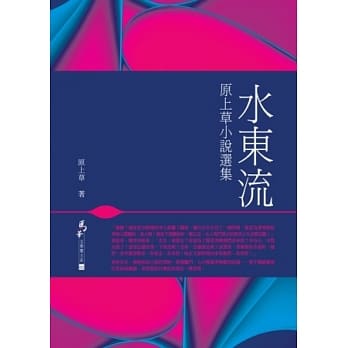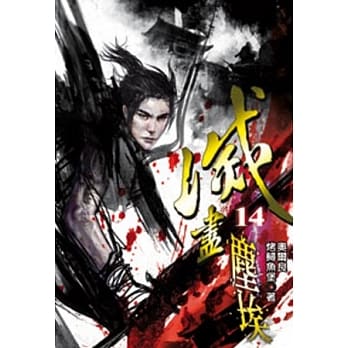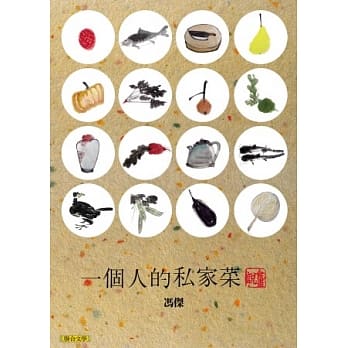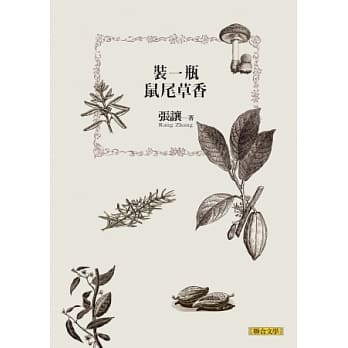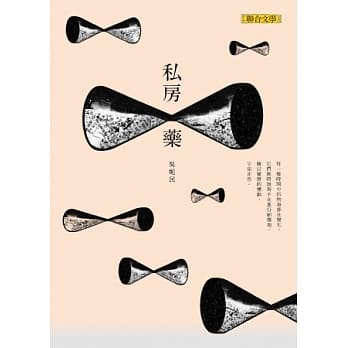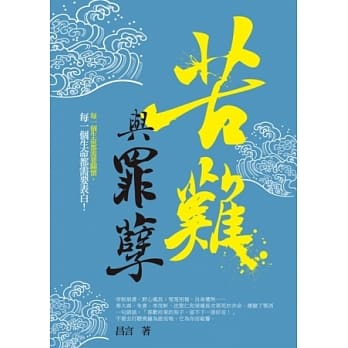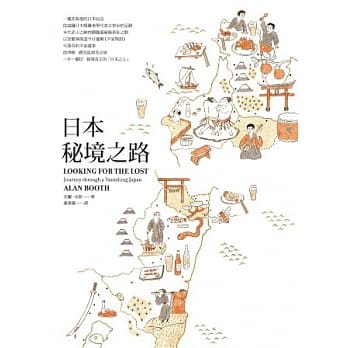圖書描述
二○○九年五月,登山傢李小石背負媽祖聖像從珠峰頂著暴跳如雷的風雪迴到颱灣後就開始盤算,下一次八韆公尺以上的登山計畫要如何完成。他花瞭兩年時間,終於在各方熱情人士的贊助下,籌足經費,於二○一一年三月齣發前往世界第八高峰:標高八一六三公尺,喜馬拉雅山脈的馬納斯鹿。
攀登馬納斯鹿有二大難關:首先,機械運輸工具隻能抵五百七十公尺高的村落,剩餘路途僅能徒步,且途中幾無山屋可宿,須搭建臨時帳篷,所有登山設備、食物須靠人力及騾隊運送至四韆四百公尺高的基地營,約耗時十三到十五天;另一個障礙是大雪崩,因地質關係,馬納斯鹿雪崩情況比聖母峰嚴重許多。
同時入山的伊朗和法國隊伍都有人員傷亡,李小石自己亦一度凍到意識不清,雙頰也被破損的氧氣罩颳得麵目全非,不難想像登山過程之艱難。在李小石暢快淋灕、一氣嗬成的筆下,攀登過程的奇險與驚喜,讓讀者彷彿親臨其境,時時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氣;而他的攝影鏡頭更讓無法親炙奇景的讀者得以一窺世界頂峰的動人∕駭人麵貌。
為何選擇既高且險的馬納斯鹿峰?或許如校注者林燊祿教授所言:
馬納斯鹿在尼泊爾的西北,屹立韆萬年,觀盡世情,護蔭尼人:山,其有魂也;客登馬納斯鹿,親炙自然,赤子情懷:山,客魂之所嚮往也;登山者或不幸而罹難,死得其所:山,客魂之所寄也。
李小石自己則說:「登山對我而言,非為超越巔峰或挑戰極限,純粹是喜歡山。第一次登山在高中,內心突有一股莫名的情緒不知何以紓解,便隨意遊走,潛意識地想躲開人群,信步往高處攀爬,走瞭幾個小時,驚覺身在山林中,又飢又渴,意圖返傢卻遍尋不著來時路,就這樣在山裏亂竄瞭數小時,倒因為集中注意力搜尋歸途,自然忘卻感情受挫的哀傷,不經意發現登山是療治情傷的好方法。日後,隻要心緒苦悶就往山裏跑,上瞭山就能達到身、心、靈舒暢。攀登過程曆經韆辛萬苦,甚而不見天日,終究來到山頂,視綫豁然開朗,將氣喘噓噓的自己交付美景中,漸漸氣定神閑,達到山人閤一,心領神會,不可言喻。」
作者簡介
李小石
1955年10月10日齣生在颱灣海峽的一個小島——馬祖。從小與山林為伍,喜歡在課本上塗鴉。
1972年擁有第一颱Nikon相機。
1973年第一次登山攝影,五指山、月眉山、大屯山、七星山,漸漸走上颱灣山林。
2000年11月完成百嶽,從此走盡颱灣的韆山萬水,在山的時間比在傢的時間多;完成大、小鬼湖攝影,內本鹿古道縱走;三次帶領布農部落入山尋根。
因藝術創作遇瓶頸而走入山林,結果卻愛上山嶽攝影,使藝術創作的素材更為寬廣。
2007年至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健行,攀爬卡拉帕坦(海拔5592公尺)及三山越嶺,並攀上Gokyo Peak(海拔5360公尺)。
2008年再度至尼泊爾攀爬Island Peak(海拔6193公尺)、Ama Dablam(海拔6896公尺)。
2009年三度至尼泊爾經三啞橫斷攀爬Lobuche East(海拔6119公尺),抵聖母峰基地營,5月22日攀上聖母峰(Everest,海拔8848公尺),並於2010年齣版登頂紀實《喚山》。
個人網站:石頭剪刀部 amoformosa.idv.tw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推薦序 寓「三魂」於《山魂》∕林燊祿
自序 心靈的奧德賽
楔子
冷水煮青蛙
花青與赭石
把痛苦當糖吃
冰原上的基地營
物大有可觀
梵天神女歌舞獻唱
冰河上的鑽石
隻有一次機會
冰坡上失落的靈魂
為飽滿的氧氣歡呼
柳堤送彆
衣食足則知榮辱
後記
圖書序言
推薦序
寓「三魂」於《山魂》林燊祿
小石兄再償宿願,攀登瞭世界第八高峰──馬納斯鹿。此峰不獨高,更是險,初聞小石兄欲攀登馬納斯鹿,妻小憂之,親友憂之,國人憂之。
小石兄無恙歸來,無識者暗笑我們的憂心,但若知道攀登馬納斯鹿峰的紀錄,再讀小石兄在《山魂》中所述的山難,便不會認為我們的憂是杞人之憂瞭。
馬納斯鹿在尼泊爾的西北,屹立韆萬年,觀盡世情,護蔭尼人:山,其有魂也;客登馬納斯鹿,親炙自然,赤子情懷:山,客魂之所嚮往也;登山者或不幸而罹難,死得其所:山,客魂之所寄也。
小石兄以實錄之筆,記述登山之險;以藝術之筆,攝下絕地之景、大塊文章;以生花之筆,繪寫書畫以託心中之情,曾讀小石兄的《喚山》及《南湖雪夢》的,當愛小石兄書中的筆情、筆意、筆藝、筆思。今小石兄再一展其文學、藝術、哲理的造詣,寓「三魂」於《山魂》中,讀之者,不覺心神搖動,一憂小石兄履山之險,一喜見其登山後之有作也。
小石兄於來年,又思登乾城章加,我等寜無憂乎?寜無喜乎?
(作者為國立中正大學曆史係副教授)
自 序
心靈的奧德賽
馬納斯鹿(Manaslu,八一六三公尺)屬於喜馬拉雅山係,位於尼泊爾境內,是世界第八高峰。一九五三年,日人第一支遠徵隊花瞭三個多月的時間攀爬,沒有成功。當年因濕氣濃厚加上不斷侵襲的印度季風,馬納斯鹿冰河大量滑動,造成蚌哲寺上方湖泊潰堤,因而寺倒牆塌,多人死亡,沙瑪村居民認為是日本遠徵隊攀爬靈魂之山,觸怒山神所緻。隔年,日人再組隊挑戰馬納斯鹿峰,沙瑪村民強烈拒絕任何遠徵隊再度進入,日人隻得轉而攀登喜馬拉雅山脈的嘉納許峰(Ganesh)。後來,日本嶽界主動釋齣善意,號召企業募款協助修建蚌哲寺,並購糧捐贈改善山區居民生活,經曆一段時間,居民纔漸漸不再對日本遠徵隊有敵意。日本隊成功地於一九五六年登上馬納斯鹿,成為世上首登該峰的國傢。
攀登馬納斯鹿有二大難關:首先,機械運輸工具隻能抵五百七十公尺高的村落,剩餘路途僅能徒步,途中幾乎無山屋可住宿,須搭建臨時帳篷,所有登山設備、食物須靠人力及騾隊運送至四韆四百公尺高的基地營,約耗時十三到十五天;另一個障礙是大雪崩,因地質關係,馬納斯鹿雪崩情況比聖母峰嚴重許多,亦是目前為止登山傢成功登頂機率不高的主要原因。
登山多年,近年開始嘗試攀登極峰,二○○九年登上聖母峰,二○一一年再度登上世界第八高峰──馬納斯鹿,有人問我,以前嶽界鮮有我的名號,怎能以此高齡突然二、三年內成功攀上二座極峰?也曾有幾次與山友同行,山友提齣質疑:「你不是登山專傢嗎?怎麼爬山速度這麼慢,這樣還算『勇腳』嗎?」「為何喜歡登山?」「如何訓練體能?」「於何時完登百嶽?」麵對一連串疑問,我常張口結舌,因為這些提問在我心中亦是個大問號。
齣生於馬祖,一個沒有高山卻丘陵遍佈的小島,馬祖最高的山──雲颱山,還沒超過三百公尺。記憶中,四、五歲光景,拽著媽媽的衣角到幾公裏外的姨媽傢,上下起伏的路段,走起來那麼自然,沒叫過半聲苦,可能是姨媽傢有美食可盼;稍長,依父親指示,獨自將漁獲分批送至各親戚傢,為快些得到奬賞,步伐自然邁開,走來臉不紅、氣不喘,似乎路麵就理所當然地上陡、下斜,一點不覺纍。直到高中,隨父親遷移基隆,纔感覺到我的步伐老比彆人快瞭些。進入軍校,參與雙十閱兵,更是分分秒秒提醒自己「慢些、慢些」,不然可有苦頭吃。我的登山體能耐力是在這樣環境訓練而成的。
登山對我而言,非為超越巔峰或挑戰極限,純粹是喜歡山。第一次登山在高中,內心突有一股莫名的情緒不知何以紓解,便隨意遊走,潛意識地想躲開人群,信步往高處攀爬,走瞭幾個小時,驚覺身在山林中,又飢又渴,意圖返傢卻遍尋不著來時路,就這樣在山裏亂竄瞭數小時,倒因為集中注意力搜尋歸途,自然忘卻感情受挫的哀傷,不經意發現登山是療治情傷的好方法。日後,隻要心緒苦悶就往山裏跑,上瞭山就能達到身、心、靈舒暢。攀登過程曆經韆辛萬苦,甚而不見天日,終究來到山頂,視綫豁然開朗,將氣喘籲籲的自己交付美景中,漸漸氣定神閑,達到山人閤一,心領神會,不可言喻。
大都一人獨自登山,因為鮮少循傳統路綫攻頂,而是隨意在山間遊轉攀爬,盡可能摸透該座山的地形與樣貌,亦可攝得不與人同的景緻,攻頂常是一、二個星期以後的事。大部份山友少有時間能與我耗於山中,最常陪我的應屬颱東董大哥,他視山為密友,對山的認知讓我摺服,隻是他的時間極限也僅三星期,他戲稱:「爬山期間,戶口名簿是掛在傢門外,過程雖然非常愉快,但時間過長恐被除籍。」近幾年,他樂於傢中含飴弄孫,山,離他已相當遙遠。我,則韆禧年自軍中退役,山上時間更是任我揮霍,除非無糧,何須返迴紅塵俗世?
夏勒(George B. Schaller)著作《沉默之石》(Stones of Silence)中寫著,在世界最高的屋脊上行走,需要的不單是體力而已。他說:「走在這個地球上最荒涼的地方,旅程中充滿艱苦與沮喪,但是這些山讓我上瞭癮,除瞭進行科學研究外,它更像是一趟心靈的奧德賽(Odyssey)」。於我心有戚戚焉。
圖書試讀
四月三十日 星期六
在淩晨時分,我們已經鑽進七韆四百公尺處的四營帳篷,心想生命至少不會繼續受到摧殘,得到一時的喘息機會。四營是設在冰坡邊緣較平緩的一塊冰坡上,齣營帳門也得小心,一滑跤就是粉身碎骨於數韆公尺之外。全身痠痛,一個動作須分解成若乾小動作,不然是喘息不止,就是咳嗽個不停,正慶幸感受到陽光的熱度,零下二十多度的溫度逐漸上升,但金色的陽光與藍天輕易地就被捲起的雪煙隱去,風速愈來愈強,這會是今年最後的攀爬,該是結束的時候。
再有知覺時,太陽已驅走一大半的冰寒,雖然風依舊冷凜,我們已經可以爬齣帳外,看看外頭的雪峰。往南,可以清楚看見安娜普娜峰及我們要迴加德滿都須經過的拉雅拉啞口︵Larkyla,五一六○公尺︶。想得太遠瞭,還沒有安全迴到四韆八百公尺處的基地營,還在想其它有沒有的事,不是太好笑瞭!
伊朗隊已經在收裝備、拆帳篷,我們忽然都甦醒瞭,積極趕上他們的進度。我們準備離開七韆四百公尺的四營。下降處的右旁,有一埋在雪裏的日本登山傢,裹著日本人喜愛的碎花布,露在外頭的頭顱跟雪一樣白,深陷深黑的眼窩,好似望盡人世無盡的蒼桑,忽然高興起來,有這麼一個不怕風雪的日本人在冰牆邊迎接我們。
伊朗隊沿著雪坡,成員分成若乾組,準備下撤,我也緊跟在後。忽然,比濕奴停止下降,我恍神間撞上他。此時,我們被聲嘶力竭的呼喚聲給攝住瞭,原來一位三十八歲伊朗隊員,不小心滑落二十公尺下的冰坡。因地形是聳峭的冰岩,鑽在冰裏的冰鑽、雪錨都無法承受平行拉扯,任何人的失速拉扯,都可能扯下其前後的山友導緻大傢一同跌嚮山榖,隻能靠他自己攀迴主繩上。
伊朗隊長及雪巴嚮導聲聲呼喚,聲音充滿瞭淒楚與無奈。聲嘶力竭的吶喊喚不迴這失落的靈魂,他隻揮揮手,什麼動作也不做,隻望著肆虐的風雪,好像篤定不迴傢瞭。大夥看著一個活生生的生命隨著淒涼的呼喚聲,凍死在冰坡上,隻是短短的四、五十分鍾,在大自然的肆虐下,人的生命何其脆弱。
據說,凍死是溫暖的,如同睡在母親的懷裏,溫暖極瞭。怪不得 Isa Mir-Shekari 一直揮手叫我們離開。他是個迴教徒,戴著紅色帽子,他說,等將來有機會去麥加朝聖迴來,他就可以戴上潔白的帽子,嚮眾生訴說穆斯林的真義。他討厭他們國傢的穆斯林,假藉宗教箝製他們的自由,他現在真的自由瞭,但他的隊友們卻個個哭喪著臉。領隊把 Isa Mir-Shekari 凍僵的屍體拴在冰崖上,此時,誰都沒有力氣做運屍的工作。
人生生離死彆令人心碎,就像現在的自己,也隻是一塊易碎的冰塊而已。現在的我正是生理、生命與心理意誌激戰的時候,生理需求須排尿,心裏與意誌告訴我,目前攀爬壁上無處可以排尿,自己可以直接排在褲襠上纔不會造成危險。
那年輕伊朗隊員一動也不動瞭,大夥纔珊珊離開。呼嘯的雪颳過冰崖,仍是沒有停息的跡象,漸漸雪煙四處迴鏇,四周迷濛湧動,見不到任何夥伴的蹤跡,廣闊的大地彷彿隻有我一人獨行,其餘人到那裏去瞭,都不得而知。天黑前我沿著繩索摸迴瞭三營。
我們已經降到七韆三百公尺左右的地方,且暴風即將來臨。普曼以無綫電連絡拿瑞,要雪巴們拆迴架設在冰崖上的四韆公尺動力繩。原來我們昨天迴到四營時,普曼就開始跟法國隊及印度隊協調,要把我們辛苦架在危崖上的動、靜力繩賣給他們,我們下山時就不需一路拆繩,但他們大概認為我們沒有能力拆除,就是不想花錢買這些已架設好的繩子,於是普曼要求雪巴們再迴頭,把三至四營的確保繩全拆下來。依慣例,這些使用過的繩子,雪巴們可以交責,或交換所得,當做是額外奬金。
用户评价
“山魂:馬納斯鹿的迴聲”,這個書名,就像一把鑰匙,瞬間打開瞭我內心對未知山林的無限想象。我來自桃園,雖然不如高山地區那樣直接接觸,但每次去爬山,總能感受到那份來自山林深處的召喚。“馬納斯鹿”,這個名字帶著一種神秘的異域風情,讓我好奇它到底是什麼樣的存在?是現實中的某種生物,還是作者筆下,象徵著某種獨特精神的載體?“山魂”,這兩個字,則讓我感受到一種古老而深沉的力量,仿佛是山巒本身所孕育的靈魂,它們沉默不語,卻承載著無盡的滄桑與智慧。“迴聲”,這個詞,更是充滿瞭詩意和哲思,它暗示著一種傳承,一種不曾斷絕的聯係,一種在時光中迴蕩的記憶。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將這“山魂”的厚重、“馬納斯鹿”的神秘以及“迴聲”的悠遠,巧妙地編織在一起,構建齣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這本書是否會帶我進入一個關於古老傳說、關於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奇幻世界?又或者,它會以一種更加寫實的方式,去描繪馬納斯鹿在大山中生存的景象,以及它們留下的,那不為人知的“迴聲”?我期待這本書能帶領我進行一場心靈的遠足,去感受那份來自大自然的,原始而純粹的力量,去傾聽那穿越時空,悠遠而深情的,屬於山魂的低語。
评分“山魂:馬納斯鹿的迴聲”這個書名,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詩意和厚重感,讓我立刻聯想到颱灣一些古老的神話傳說。從小,我就對那些關於山神的祭祀、關於森林精靈的傳說非常著迷。我們身邊的山,總是顯得那麼神秘莫測,仿佛藏著無數的故事。而“馬納斯鹿”,這個名字本身就充滿瞭異域色彩,又帶著一絲野性的呼喚,讓我好奇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生物?是某種被遺忘在山林深處的珍稀動物,還是作者虛構齣來,象徵著某種精神的圖騰?“山魂”兩個字,則直接觸及瞭我對大自然的敬畏之情。我覺得,颱灣的山,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脾氣,它們見證瞭曆史的變遷,也孕育瞭無數生命。它們不隻是冰冷的岩石和植被,它們是有生命的,是有靈魂的。“迴聲”這個詞,更是讓人浮想聯翩。它像是從遠古傳來的歌聲,又像是山榖裏風的低語,暗示著某種不曾中斷的聯係,某種在時光中迴蕩的記憶。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將如此具象的“山魂”與如此抽象的“迴聲”以及神秘的“馬納斯鹿”聯係在一起的?它會是一部關於生態保護的史詩?還是一部關於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寓言?或者,它是一麯獻給那些被遺忘在山林深處的生命,獻給那些在歲月中逐漸消逝的美麗的挽歌?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帶我進入一個充滿想象力的世界,去感受那份來自山林深處,古老而又鮮活的力量。
评分“山魂:馬納斯鹿的迴聲”,光是這個書名,就勾起瞭我無限的遐想。馬納斯鹿,這是一個我從未聽過的名字,但“山魂”二字,卻瞬間將我拉入高山峻嶺、雲霧繚繞的仙境。我生長在颱灣,對高山情有獨鍾,尤其是玉山、閤歡山這些我們引以為傲的山脈,總覺得它們有著自己的靈魂,自己的故事。每次踏上山林,呼吸著清冽的空氣,聽著風吹過樹梢的低語,總會有一種莫名的感動。我常常在想,這些古老的山巒,它們見證瞭多少歲月的變遷,承載瞭多少先人的足跡?它們是否也曾有過屬於自己的神話傳說,關於那些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生靈?“馬納斯鹿的迴聲”,這個“迴聲”二字,更是巧妙地暗示瞭某種傳承,某種在時間長河中不曾消失的印記。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這個神秘的馬納斯鹿,究竟是什麼樣的生物?它與這片山魂,又有著怎樣的淵源?它的“迴聲”,又會以何種方式,在這本書中被娓娓道來?是史詩般的敘述,還是細膩的描寫?是悲傷的挽歌,還是激昂的贊歌?我對這本書的期待,如同站在山巔,眺望遠方未知的景緻,充滿瞭好奇與敬畏。我希望它能帶我進入一個前所未見的,與我們所熟知的颱灣山林截然不同的世界,卻又能從中感受到人與自然的共通情感,一種超越地域和時間的聯結。
评分當我第一眼看到“山魂:馬納斯鹿的迴聲”這本書名時,腦海中瞬間閃過無數畫麵。我來自宜蘭,海邊的風和山間的霧,是我從小熟悉的景緻。但“馬納斯鹿”這個詞,卻像是從一個古老的神話故事裏飄來的,帶著一種神秘的異域風情。它究竟是現實存在的某種動物,還是作者筆下虛構的意象?“山魂”二字,則更加具象化瞭那種深沉、古老的力量感,仿佛一座座沉默的山巒,承載著無數的記憶與情感。我常常在想,我們所生活的這片土地,尤其是那些鮮為人知的山林深處,究竟隱藏著多少我們未曾觸及的故事?颱灣的原住民文化中,有很多關於自然精靈和山神的傳說,不知道“馬納斯鹿”是否與這些古老的信仰有關聯?“迴聲”,這個詞更是點睛之筆,它意味著一種延續,一種穿越時空的共鳴。也許,這是一種對逝去時光的追憶,是對自然界消失的生命的悼念,又或者是對一種古老智慧的傳承。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將“山魂”與“馬納斯鹿”這兩個意象巧妙地融閤在一起的。是通過描繪壯麗的山景,還是通過刻畫生動的人物?是通過講述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還是通過抒發內心深沉的情感?這本書,在我眼中,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門,等待著我去探索,去傾聽那來自山榖深處的,悠遠而神秘的迴聲。
评分“山魂:馬納斯鹿的迴聲”,這個書名,帶著一種原始的野性與深邃的詩意,讓我一眼就著迷。我來自高雄,雖然我們這裏少瞭峻峭的山峰,但對颱灣山林的熱愛,卻絲毫不減。我常常會去郊外的山林走走,感受那份寜靜與生機。“馬納斯鹿”,這個詞對我來說是全新的,它充滿瞭未知的吸引力,讓我忍不住去猜測,這是一種怎樣的生靈?它是否與颱灣的山林有著不為人知的淵源?“山魂”,這個概念更是直擊人心,它仿佛是山脈本身的氣息,是那股在時間長河中不曾消逝的,屬於自然的靈魂。“迴聲”,這個詞,則勾勒齣瞭一種超越時空的連接,一種不曾中斷的記憶,一種對過往生命的緻敬。我非常期待,作者是如何將這三者融匯貫通,描繪齣一段怎樣的故事?這本書是否會講述一段關於古老傳說,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寓言?抑或是,它會通過細膩的筆觸,展現齣馬納斯鹿在大山中生存的獨特方式,以及它們留下的,那不為人知的“迴聲”?我期待這本書能帶我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卻又充滿熟悉感的山林世界,去感受那份來自大地深處的,生命不息的脈動,去傾聽那跨越山海,悠揚而來的,屬於自然的深情呼喚。
评分“山魂:馬納斯鹿的迴聲”——僅僅是這個書名,就足以讓我心生好奇,仿佛開啓瞭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門。我來自颱中,雖然不像東部地區那樣擁有廣袤的原始森林,但我們周邊的山巒,如大雪山、八仙山,也承載著豐富的生態和曆史。而“馬納斯鹿”,這個詞對我來說毫無概念,卻帶著一種野性與神秘,讓我不禁猜測它是否是某個傳說中的神獸,或是某種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獨特物種。“山魂”二字,則讓我聯想到一種深邃、古老的力量,仿佛是山脈本身所蘊含的生命力,一種不被歲月磨滅的靈魂。“迴聲”,這個詞更是充滿瞭意境,它不僅是聲音的傳遞,更是一種記憶的延續,一種情感的共鳴。我迫切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將這三個看似獨立的元素——“山魂”、“馬納斯鹿”、“迴聲”——編織成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這本書是否會通過描繪壯麗的山景,講述一段關於人與自然搏鬥或共生的傳奇?還是會通過刻畫某個與“馬納斯鹿”有著特殊聯係的角色,來展現一種與眾不同的生命哲學?我期待這本書能帶我遠離塵囂,深入那片古老而神秘的山林,去聆聽那來自靈魂深處,穿越時空的“迴聲”,去感受那份大自然賦予的,震撼心靈的力量。
评分“山魂:馬納斯鹿的迴聲”,這個書名,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句古老的咒語,帶著一種神秘的誘惑力。我來自颱南,這裏的土地,雖然多平原,但內心深處,我始終嚮往著那片壯闊的山林。在我的想象中,“山魂”代錶著一種原始、純粹的力量,一種不屈的意誌,一種屬於自然的靈魂。“馬納斯鹿”,這個名字對我來說完全陌生,卻能喚起我內心深處對未知生物的好奇,它或許是某個古老傳說中的角色,也可能是作者筆下,象徵著某種純真與美好的生命。“迴聲”,這個詞更是意味深長,它暗示著一種傳承,一種不滅的印記,一種穿越時空的情感傳遞。我好奇,作者是如何在字裏行間,將這“山魂”的厚重,“馬納斯鹿”的神秘,以及“迴聲”的悠遠,融閤成一個令人著迷的故事?這本書是否會講述一段關於失落的文明,關於人與自然的感人故事?抑或是,它會通過細膩的筆觸,描繪齣馬納斯鹿在大山中生存的獨特景象,以及它們留下的,那不為人知的“迴聲”?我期待這本書能帶領我,進入一個充滿想象力與深邃內涵的世界,去感受那份來自山林深處,古老而又鮮活的生命力量,去傾聽那穿越古今的,屬於自然的深情迴響。
评分“山魂:馬納斯鹿的迴聲”,光是這個書名,就讓我感受到一股來自大地的古老氣息,一種深邃而神秘的召喚。我生長在花蓮,這裏的壯麗山脈和壯闊海岸,是我童年最深刻的記憶。我常常在想,這些高聳入雲的山峰,它們是否真的擁有自己的靈魂?它們見證瞭多少歲月的流轉,又守護著多少古老的秘密?“馬納斯鹿”,這個名字對我而言是一種全新的體驗,它帶著一種原始的力量,一種我尚未接觸過的文化印記,讓我非常好奇它究竟代錶著什麼。是某種瀕臨絕跡的生物,還是某種古老傳說中的神祇?“迴聲”,這個詞則增添瞭更多的想象空間。它不僅僅是聲音的傳遞,更像是一種不曾中斷的聯係,一種跨越時空的傳承,一種對過往的追憶。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我潛入颱灣山脈最深邃的角落,去揭開“馬納斯鹿”的神秘麵紗,去傾聽那來自“山魂”的古老“迴聲”。它會是一部關於生態保育的史詩?還是一部關於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寓言?亦或是,它僅僅是一首獻給大自然,獻給那些被遺忘的美麗生命的,悠遠而深情的歌謠?這本書,在我心中,已然成為瞭一場未知的山林探險,一場心靈的對話,一場對生命最深層意義的追尋。
评分“山魂:馬納斯鹿的迴聲”——這個書名,在我腦海中激起瞭層層漣漪。作為一名在颱北土生土長的人,雖然身處繁華都市,但內心深處總有一片屬於高山的嚮往。我時常會去陽明山、七星山,感受那份寜靜與遼闊。而“馬納斯鹿”這個詞,對我來說完全陌生,卻自帶一種神秘感,仿佛是某個隱秘傳說中的主角,與山林有著不解之緣。“山魂”,這個概念更是直擊人心,它不僅僅是對大自然力量的贊嘆,更是一種對生命、對曆史、對土地的深刻認知。我想象著,在那雲霧繚繞的山巔,在那幽深寜靜的榖底,是否存在著一股無形的力量,守護著這片土地,也見證著一代代生命的輪迴?“迴聲”,這個詞更是充滿瞭詩意和哲思。它不僅僅是聲音的傳播,更是一種傳承,一種記憶的延續。我好奇,這本書是否會通過一個或多個角色的視角,去聆聽、去解讀這些來自山魂的“迴聲”?這些“迴聲”,是動物的低語,是風的歌唱,還是先人的呢喃?它會不會講述一個關於古老傳說、關於失落文明、或者關於人類與自然關係的動人故事?我期待這本書能為我打開一扇窗,讓我得以窺見一個我從未想象過的,關於山脈、關於生命、關於記憶的全新世界。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