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圖書描述
童偉格 【2010. 2 INK印刻文學生活誌(78)期 封麵人物】最新長篇小說《西北雨》
一個關於離開或留下,逝去或復活,失落或尋找,溯想或遺忘…………微苦、無傷的「說不完的故事」。
「所以這是一個『自己』之書。所有死去亡靈的追憶、懷念、遺憾,全部進駐這個唯一活人(甚至他發現自己也早已死去)的意識。」「讓不知自己已死的親愛之人們重演活著的時光。」(駱以軍語)小說傢彷彿逞馭無窮盡騰挪變化的魔幻想像與詩意,煞停時間,將現實隔在一天光靜好的沉靜荒墟中,似一再重復的昨日,今日,明日,或一場永恆的睡眠,將那充滿颱灣當代偏鄉(孤島 / 山村)色彩的背景舞颱,捏塑成小說中漫行於離棄之途的一傢數代人(祖父祖母 / 父親母親 / 敘事者「我」)也是跨度相同歲月的我們讀者數代人無以名之卻也無傷的「鄉愁」---傢族中每個人如對鏡般成為彼此亟欲擺脫而不能的夢魘,也是最溫暖的贖救源頭。整部作品在宛如暴雨將至(或者,迴想著生命中曾經曆的雨水)的淡淡傷感氛圍中,人物雖生猶死、鬼魅行屍走肉般的活著;或者也同時是,跨越時空界綫,自死者國度被思念喚迴到敘事中的沉默亡靈們,雖死也猶生。
故事一開始(捲首),宛如一個將傢族亡靈---自過去自不復在的現實喚迴,或在一不思議彷彿沒有盡頭沒有因果邏輯的夢中重聚的盛筵,既熱鬧又寂寥。死者似乎不知自己已死,還過著日復一日的尋常的沒有齣口的時光,生者也不能確定自己的生活,是活在不斷遭到死者們(父祖母親們)離棄的現實或者是哪一個亡者無法醒來的夢中?
在童偉格那值得再三品味、充滿星團爆炸般龐巨詩意能量的小說中,不僅時空綫索、角色形象不停地變化傾斜;而情節或可視作是一連串的,召喚迴憶與傢族羈絆的過程---迴憶者召喚著迴憶,迴憶也召喚迴憶(總是無窮盡也無預兆的,擁有畸人特質的「我」〔許希逢 / 海王〕想起父親〔許豐年 / 士官〕,祖父,父親想起他的父親〔祖父 / 李先生 / 「詩人」〕,有時是母親,母親又想起她的母親,祖父則想起兒子與他的妻……故事碎片就在這層疊不息的思念中流轉,每個幾乎皆不習慣與人親近的人且都升起懸念,「為何那人總過著那樣寜靜透明、無傷且無望的生活?」卻也充滿依戀與感激。)---層層纏繞,過去的人(祖父 / 父親 / 母親 / 祖母……)活在將來的人的迴憶 / 夢中,將來的人竟也不時影影幢幢地在過去的人的迴憶甚至生活中走動:在傢族諸人輪流進齣摺磨彼此的安寜病房;在不斷想要逃離卻又由此生齣鄉愁耿耿的犬山村 / 海島的長街上;在祖父義肢的顛簸裏;在父親的狗籠故事或者在「另一個」父親魔術般開瞭鎖的門後;在肅殺壓抑的軍營;在一壁濕淋淋的海王神偶的諭示中;在其中一個母親總跟陌生男人訴苦的背影……也似反覆地徒勞印證,種種不堪的存在也是珍貴的存在。彷彿不停繞射的鏡影,真正的說故事者與他的故事逐漸閤為一體,與故事中的亡靈們真正的「團圓」,完成一趟趟死生、欲語或無言的無盡循環。
作者簡介
童偉格
1977年生,颱北縣人。颱大外文係畢業。颱北藝術大學戲劇碩士,現就讀颱北藝術大學戲劇學係博士班。作品〈王考〉獲2002年聯閤報文學奬短篇小說大奬,〈暗影〉獲2000年全國大專學生文學奬短篇小說參奬,〈躲〉獲2000年颱灣省文學奬短篇小說優選,〈我〉獲1999年颱北文學奬短篇小說評審奬。著有短篇小說集《王考》,長篇小說《無傷時代》,舞颱劇本《小事》。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捲首
捲上
捲下
贖迴最初依偎時光
代跋 / 駱以軍
圖書序言
贖迴最初依偎時光
駱以軍
剋蒂斯能描述各種自己從未見過的事物:世界是詞藻的海洋,是沼澤、是沙漠,瞬息萬變地環繞他所站立的方寸之地。魯恩總看著朋友,七手八腳為眼前所見的事實塗上一層又一層厚重的油彩,直到一切黝黑而可疑,不再是原來的樣子。……「朋友,」每一場戰役後,魯恩總對剋蒂斯說:「您知道的,我但求公平一戰。」
「我的朋友,」剋蒂斯總是聳聳肩,一手敲著拐杖,一手扶起魯恩,對魯恩說:「隻有讓他們在我的言語前,成為需要嚮導的盲人時,我們纔平等。對此,我深感抱歉。」我深感抱歉;幾乎每則曆險,都結束在這句話上頭。事後想起,這亦是整個童年時代,白紙黑字浮現在我腦中的最後一句話。」
我讀童偉格,視覺上那翻動著空曠的場景如此像年輕時看的塔可夫斯基。但流動的詩意卻讓我想到以色列小說傢奧茲,或較好時的石黑一雄。
等待,一個被遺棄的孩子。「時間本身,單純地讓每個人終成鰥寡。」一種時間的洞悉同時放棄。一種靜默的瘋狂,一種焦灼、緩阻,目視著學習老人們(後來你知道那其實是死人亡靈)如何無聲在這殘酷的荒原和時間中,慢速地活著,不,展演他們儀式般慎重以對,像某些要素被吃掉被隱蔽的記憶,「最好的時光」(但難以言喻的古怪)。
小說是這樣靜謐的獨自時光(也不是獨白或獨語),而是獨自感受著星光、流風、時間、大海、暴雨臨襲前的風雲變化,無害但存在於老屋或這座島各處的鬼魂。一個完滿的宇宙。
空間上它是一座島(或有兩個不同名字:狗山和光武島的不同兩座島)。這個島,也許譬似艾可的《昨日之島》,似乎泅泳過去便穿過換日綫到被時間沒收的另一端;但卻又曆曆如照明燈下近在眼前栩栩如生的遊樂場。「我好像必須花上淺薄生命裏的數十個年頭,纔敢嚮自己確認,也許,它將永遠如此靜靜的瘋癲,像宇宙中最稱職的療養院。」這個霧中小島有神話時期的父親,有史前時代的軍隊,有王爺府,有火車、鐵路,有校園、村落、傢庭、鄰裏親人……在這些地貌場所上活動並進行著什麼的人際關係。
小說的大半本以上這個小說像在翻印著一具你找不到邏輯的視窗,一種村上春樹的末日之街,石黑一雄《彆讓我走》那提供器官之復製人的寄宿學校,或瑪格麗特.愛特伍的《末世男女》、韋勒貝剋的《一座島嶼的可能》──是的,科幻小說,我們藉著小說傢的凝視,看著那一整片他描述齣來的畫麵風景,古怪又詩意,其實是童偉格將那「災難」的耳半規管從所有飛翔情節之鴿子的內裏摘除掉瞭,那變成一種「空望」。童偉格在晚近以單篇形式發錶的一篇題名為〈將來〉,奇怪的是,「將來」除瞭作為這整個小說接近結尾部位的一個時間邏輯的給予,恰像是童偉格自《無傷時代》即發展齣來的時光劇場,讓它們進入核爆過後的世界。
計時失去瞭任何藉以形成描述人類存在之意義,與迴憶相對應的是一個被永恆取消掉瞭的現在,那是一個死亡的時間,「已經」終結瞭,但無法在目蓮救母式的巨大悲願重建這一切枯荒無望之曠野的同時,「解決」那悖論的仍在前進的物理時間。
那讓人想起馬丁.艾米斯的《時間箭》。一部小說如錄影帶倒帶,時間是顛倒進行的,我們眼中所見,竟不止是動作的倒轉:抓姦的丈夫變成把妻子送給姘頭的皮條客,劊子手贈予死屍完整的身體和生命,惡心的糞便從馬桶的水喉上升吸入人的肛門,之後從他口中吐齣豪華豐盛的美筵……「當生命倒著走時,一切變得美好瞭。」
在童偉格的這個「將來」的世界發生著什麼事呢?一種保護著──甚至如在碎成破片的倒影世界裏傻笑著,如失聰者,如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白癡」──《無傷時代》的,以超荷於「小說所能贈與、贖償真實之空無」的願力──黏貼模型那樣「小小世界真奇妙」的一個空間化的「白銀時代」(藉王小波的書名)。那是我所能想像小說傢用不可能之死物與屍骸,用一「藉來的時間」讓它們活在宛然畫麵裏(一座被大海包圍的島)。
所以這個隻要用願力泅泳過換日綫的「昨日之島」,一切都變換成白銀熠熠的「將來」,在「我想起來瞭」的魔術啓動之前,它們恆隻是漂浮靜止於巨大標本皿內的死物(殘缺的曠野),一種內嚮封印於族類的環節們失落的「故事」。
這種刻意返祖,剝落掉寫實主義以降強大復刻「真實」的細節元素,使之類似神話(寓言)場景的「故事」,讓人想到巴加斯.略薩的《敘事人》:「因為在馬奇根卡斯人中間有一個擔負著十分特殊任務的人,他既不是巫師,也不是巫醫,而是主要擔負著講述曆史的任務。這個人是講述事情的、說話的。不久前,馬奇根卡斯人還是分散的,孤立成一個小小的公社,有時是人數很少的傢族團夥,因為他們居住的地區是非常貧瘠的……不能組成重要的社會集體。這樣他們便完全分散、孤立的生活。馬奇根卡斯人稱之為『敘事人』的人物是他們各團夥之間來往連係的一種形式,有些像中世紀的行吟詩人,也有些像巴西東北地區尚存的流浪歌手,彈著六弦琴,走村串鎮,邊走邊唱。至於『敘事人』並不是唱歌而是講故事──既講他們在彆的部落裏看到的事情,也講他們自己的經驗、公社裏過去的曆史故事、神話、傳說和個人編造的故事。」
這個在死者、祖先、昨日和將來間,傳遞故事(或夢境)的「我」,是一個退化癥的畸人(譬如《鐵皮鼓》的侏儒奧斯卡,《最後一個摩爾人》裏的早衰癥少年)。曆史在這個島因某種畫框外的重擊而擱淺瞭,所有人都停止在那故障的時刻裏,「一個人齣生的地方,終於成瞭他們所能抵達的,最遙遠的地方。」停格,曝光,永遠重覆。
「我」的父親是個外國人(飛行員。飛機被擊落而被島民俘虜關在大狗籠裏),像瘋瞭時的老邦迪亞那樣以原人形象成為猿猴般的展示物。真到父親的國傢戰勝,島民這一邊的國傢戰敗瞭。「但是,『恥辱』哪裏去瞭?『仇恨』哪裏去瞭?還有,『憐憫』哪裏去瞭?」「我」構造著父親的感受,凝視、獨白、頓悟。由這個退化癥的「我」,「無傷時代」的「我」,慢速,默片、黑白膠捲地投影那個父親孤自麵對一島之人的屈辱、仇恨和憐憫。這樣篩沙也似流光從眼前傾落,一種偏執的觀照,想看清楚無辜的每一個在場者是在哪個關鍵遭受侮辱和損害。其實其證物泯滅之哀慟一如舞鶴之〈拾骨〉。隻是童的「祖先遊戲」之抒情核心更在「寬諒」。寬諒什麼?「我」的罪如迷霧包裹,層層遮蔽。(他的祖先們並無罪啊,有的隻是被剝奪、被侵侮、被壓碎瞭)。
因為「我」無法修補父祖們的壞毀?「我」故障瞭,這個僅能用如此艱難晦澀故事重建殘酷時光劇場之「我」讓想像中的父祖失望瞭?「當簡潔與溫暖,終於也像餘燼那樣將要消亡,對他們的每次猜想,於我就像傾巢的話語,去抵禦那個終將沉默的自己。」
所以這是一個「自己」之書。但那又是一個魯佛的《佩德羅.巴拉莫》的世界,所有死去亡靈的追憶、懷念、遺憾,全部進駐這個唯一活人(甚至他發現自己也早已死去)的意識。「我」負載著這所有沉默無告的祖先們那麼巨大無垠的苦難,「自己」是遺忘的荒原最後一隻稻草人,最後一根鹽柱,但我難改自己血液基因裏那善於苦笑、沉默、原諒,和畏敬海天的天性,「我已經無話可說瞭」。
「我」,假定是復製自他人生命的膺品;但同時對抗這種復製,形成瞭楊照所說的「廢人存有論」:不給人帶來睏擾,不與這世界發生過多不可測的連係。
「我」養著一隻「穿透瞭老王的心」的那隻小象;「我」在父親麵前和看不見的貓玩把戲,這樣馬歇.馬叟式的和不存在,已離去的失落之物(親愛者)玩「他們仍在場」的默劇,「我」像捧著將要迸散碎落的水,那樣小心翼翼,那樣預示著「將要」,必然的失手。那個慢速連笑話都失去瞭該有的痙攣,「沒關係,笑話會等人。」或「好好想,你時間多。」「他」(在後來的章節證明是「我」的祖父)在「我」的夢裏,時光運鏡不斷往前推:包括「他」總是被陌生人騙走的母親;「他」在軍中承受那一次靜默荒謬的暴力,薛西佛斯式的浪費;「他」的父親為瞭兒子的命運去找神乩打架,想收迴海王之神諭,最後卻變成那麼悲哀、孤獨,那麼自由對羞辱的反轉冥想之死前時刻。
當「自己的故事」退無可退成為「箱裏的造景」──「『他的』山村如何被封固在一個更為繁復的人造童年裏,和時間兩相遺忘,在地理中消失。他帶動一整幢病院,發現世界並沒有瘋」,隻是變成一死者迴返的霧中風景。「我全部想起來瞭。」從無言、失語而至這整個小說最後滔滔不絕的描述,「我」成為那個之前因舌頭賈禍的海王,喚起所有人的記憶,「我深感抱歉」。「我」睡著瞭,在夢中造鎮,又用小圓鍬鑿毀整個島活人與鬼魂的阻礙;「我」,一種贖迴的意誌;「我深感抱歉」,為著同時祭起這驚擾亡魂而融化已凍結的時光,讓不知自己已死的親愛之人們重演活著的時光。但那正是「我」和所謂界綫外粗暴、快速、無感性的正常世界對決的「平等的話語幻術」。
倒帶、透明,揹著快樂無害的他們在這片夢中荒原跑,從葬禮齣逃,拉齣這樣一幅浩瀚如星河,讓我們喟嘆、悲不能抑、靈魂被塞滿巨大風景的「贖迴最初依偎時光」的夢的捲軸。
圖書試讀
無人知曉的是,每逢週四,我會和祖父陪她拖曳著房間齣門,搭公車,去港區的署立醫院和醫師諮談。那感覺挺愉快,因為往往一進醫院大廳,祖母就自在而活絡瞭。她會牽起我,和祖父領我乘老式電梯上樓,然後我們就一起坐在診間外的長廊上等候,大概從上午九點等到近中午十二點。等候之時,祖母會和長廊上的人攀談,理性而溫柔,用她自己最希望的方式說話。包括醫師,她總和在醫院遇到的人們聊得極好,總令在一旁聽看的我,彷彿身處她記憶中,過往的大港裏那些深藏在僻靜巷弄、騎樓之上的傢常小診所:醫生娘隨時就要提著菜籃進門,對候診室裏的人們和煦微笑;從窄仄的窗可望見海的剪影;孩子們將溫度計靜靜夾在腋下;醫生桌上,壓舌棒浸在半滿的燒杯裏。總之,事物都有一定的位置,來的人都會受到照料,離開的人都將康復。
那時,當我從她的腳踝迴望,後見之明一樣,我彷彿變得比較熟識他們瞭。我總猜想,在遠遠的那間房裏,也許,遠在青春期之前的孩提時代,她就開始準備著,要和一個什麼人白頭偕老。她夢想著這樣平和的幸福,盼望時間能允許她,任她就這樣老去,比記憶中的任何人都還要老。倘若真能和一個人長壽以終,她將不會懷疑那是命運的賜福,但她會謙卑地感傷,她會想:因為似乎,賜福總是交託給像她這般不適當的人,纔讓「命運」這樣的字眼,顯得永遠可疑。
可能,她會以為,命運交託我祖父,給在那間房裏的她。起先,他教養她,管訓她;最後,他成為她的病人,那惟一一個終生留在她身邊,不離開她的嬰孩。在那間房裏,像安寜病房裏的兩室友,她和他長久相處,和好而平靜地,讓彼此成為各自惟一一次生命的諧擬。當他在她身邊躺下,她會感覺多年來積存於心,無以對人說明的憂患,或身體裏剛剛壞死的細胞,已經正一點一點掏空他,於是他輕盈得多麼像是要被身上的薄被包裹,一把提走瞭似的。沒關係,她想,在床闆底下,有一口又一口沉重的甕,那是她為他們保存的食物:酒糟肉,鹹菜,醃漬蘿蔔。很適閤他遠行時攜帶,她寡居時獨食,或者,作他們在天荒地老長相廝守時的食糧。時間讓在不在一起失去分彆,或統攝瞭兩者:不是伴侶的逝去或走離,而是時間本身,單純地讓每個人終成鰥寡。
當她拉開窗簾,讓山村的太陽透進房裏,看微小的塵埃,彌漫在低抑的光綫裏,她可以木訥而無聲地與不在房裏的他對坐,而不會不時被時間龐大的頓挫給震顫。因為,就這麼單純:她嫁給瞭他,與他用彷彿藉來的衣物、鍋碗,身體,在那些櫥櫃的環伺下,演練著一種人稱婚姻生活的東西。也許,是在一切的細微與無足輕重裏,她放牧自己在他身邊,漸漸老成一位意料之中的慈藹婦人:那種自己的孩子最晚在青春期,就明白她的人生經驗對他全然無效;孩子的孩子最早從兒童期起,就自然疏遠瞭的慈藹婦人。即便是,或特彆是在可能曾有過的,愛情最濃烈的時日,她仍會幻想:她的配偶將早她三十年死去,而那大約就是他們婚姻的全長。她於是被應許,度過最與世無爭的人生,獨自在高壽中慢慢變得癡傻;對某些特定的往事,迴憶得愈來愈清晰,卻愈來愈靦腆地看待。看自己努力練就的溫婉言行,隨時間復返,變得像是自己天性的一部份。然後,她就要看穿自己在世間的最後一場睡眠,像看透一齣永遠排練不好的夜戲,預見自己的死亡。那時,她將仍平靜閉眼,彷彿隻是坐在澡盆裏,遊迴一麵過於深廣的海洋。
因此,每夜每夜,當他仍在她身邊,將他們的房間平躺得一如安寜病房,她感到驚訝,羞怯,快樂以及悲傷。彷彿牆麵都潔白瞭,而夜霧裏的空氣正一點一點過於清冷。彷彿門外,醫師與護士的便鞋,正敲在光滑的地闆上,一聲一聲過於規律而健忘。失眠的夜,當整個房間被細雨中的熹微給洗亮,婚姻裏一切器物的邊角,都彷彿發散虹霓,那總奇特地,給她一種溫暖的錯覺。當他們度過對彼此說的每句話,都不能免於訴說得太多的磨閤時日,她無言,傾聽熟睡的他,喃喃起偏遠的話語。那是夢囈,也是各處異鄉的混閤語。那像來自隔壁房間的聲音,即臨卻又帶有隔閡。
她傾聽,試圖捕捉一些耳熟的辭匯,想像過往如何存在對她而言,意義的空洞裏。她發現他正睏在一個人們稱作身體的軀殼裏,而這個軀殼正在床上持續萎縮,慢慢將他捆迴嬰兒般大小。她看望四周,想像年老就是這樣的:你的靈魂蝸居其中,格外容易知覺屋裏什麼是新修繕的,什麼是舊模樣的。你的靈魂有時快樂、有時沮喪,有時甚且迴到青春的激情與躁熱中,然而,這一切都不會被人瞧見。對路過的人而言,你始終就是間舊房子,靜靜覆蓋著時間的塵埃。有時,當你也像個路人那樣去迴看自己,你會發現,如果七十歲、八十歲,跟九十歲、一百歲沒有差彆,那麼,一個人若是老到某種程度,應該就永遠也不會死瞭吧。因為死亡是件極其年輕的事,而那個人,不小心錯過瞭。
祖母亦不知曉的是,那個夏末,一牆之隔,在遠遠的那間房外,孩提時代的我生平第一次,以為自己懂得瞭死亡原來該是什麼。我記得手心撫摩樹乾時的觸感;記得驟雨過後,枝葉閃閃的光澤。我記得當我醒來,我聽見橫溢的水聲,看見藻綠色的光所粉飾的櫥櫃,明白自己已經平安返迴瞭,在山村的夜,在祖母的房間裏。發現我醒瞭,祖母靠近我,觀察我,輕撫我的臉頰,在我額上輕輕敲敲叩叩。那連串無意義的動作,不知為何總能使我平靜下來。我不知道在那溫和的注視中,祖母究竟都從我臉上看見些什麼。隻是,我猜想,基於對孫輩的厚愛,我在祖母心中,大概總顯得比實際靈光許多。因為這樣的寬容,那一整個夏天,我得以安放自己在她身邊。在她的注視下,我身上換穿過一整代人兒時的衣物,那是她特地從衣櫃底翻撿齣來的。那些衣物初穿上身時,我鎮日聞到香茅油的強烈氣味,鼻子因此而搔癢,接觸袖口的皮膚,開始長齣細小的紅疹。但當我換下這些衣物,由她洗過、在風裏晾過,再穿迴我身上時,它們變得格外好聞,像藻綠色的陽光。像是我自己,也和祖母一樣,每日每日被靜靜淘洗瞭一遍。
用户评价
《西北雨》這個書名,瞬間就把我的思緒拉迴到那個充滿夏天迴憶的颱灣。我腦海裏立刻勾勒齣一幅畫麵:午後炎熱的天氣,悶得讓人喘不過氣,空氣中彌漫著一種特殊的味道,那是雨季將至的信號。緊接著,遠處傳來低沉的雷聲,天空的顔色也隨之變暗,樹葉開始瘋狂地搖擺,預示著一場傾盆大雨的到來。我猜想,作者筆下的“西北雨”絕不僅僅是關於天氣,它更可能是一種情感的載體,一種生活態度的象徵。它可能代錶著那些突然而至的挑戰,也可能象徵著那些滌蕩心靈的經曆。我甚至可以想象,書中會不會描繪齣,在雨中奔跑的孩子們,他們的臉上洋溢著純粹的快樂,又或者,是在雨中辛勤勞作的農夫們,他們臉上流露齣對自然的敬畏和期待。雨停之後,空氣中彌漫的泥土清香,以及天邊悄然掛起的彩虹,都可能成為書中重要的意象,它們代錶著希望,代錶著新生。因此,我非常期待,作者能通過《西北雨》這個書名所蘊含的獨特意境,為我講述一個充滿颱灣風情、觸動人心的故事,讓我仿佛親身經曆那一場場生命力頑強的西北雨。
评分《西北雨》這個書名,光是聽著就充滿瞭畫麵感和地域特色,讓人立刻聯想到颱灣夏季那種說來就來、轟轟烈烈的雷陣雨。我腦海裏立刻浮現齣,那種悶熱的午後,空氣中彌漫著潮濕和一種特殊的泥土芬芳,緊接著,遠處傳來隆隆的雷聲,天空迅速變暗,然後,豆大的雨點就如同斷瞭綫的珠子一樣,毫無預兆地砸下來。這種天氣,不僅僅是簡單的自然現象,它更像是一種颱灣人共同的生活記憶,一種季節的印記。我猜想,作者可能會用非常細膩的筆觸,描繪齣西北雨來臨前的種種跡象,以及雨水落下時,對周圍環境和人們生活帶來的影響。我甚至覺得,書名中的“西北雨”,可能也象徵著某種突如其來的變化,或者是一種滌蕩心靈、帶來新生的力量。因此,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將這種充滿生命力的自然現象,巧妙地融入到故事的情節和人物的情感之中,為我們呈現一個怎樣的、充滿颱灣風土人情的故事。
评分《西北雨》這個書名,自帶一種強烈的畫麵感和季節感,讓人立刻聯想到颱灣夏季那種說來就來、來勢洶洶的雷陣雨。我腦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現齣,當天空逐漸陰沉,空氣中彌漫著濕熱和泥土的味道時,那種即將到來的雨水的預兆。緊接著,一聲轟隆隆的雷鳴,預示著一場大雨即將傾瀉而下。我猜想,作者可能會用非常生動的筆觸,描繪齣西北雨的到來,以及它對周圍環境和人們生活所帶來的影響。這種天氣,在颱灣的記憶裏,總是伴隨著一種特殊的體驗:孩子們會在雨中奔跑嬉戲,大人則忙著收晾曬的衣物,空氣中彌漫著雨後特有的清新氣息。我甚至覺得,書中可能不僅僅是在寫天氣,而是在藉西北雨的意象,講述更深層次的故事。比如,它可能象徵著人生中的突如其來的變化,或者是一種滌蕩舊有事物、帶來新生的力量。所以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將這種充滿生命力的自然現象,巧妙地融入到故事的情節和人物的情感之中,為我們呈現一個怎樣的關於颱灣生活、人情風貌的故事。
评分《西北雨》這個書名,本身就有一種濃厚的畫麵感,讓人聯想到颱灣夏季那種說來就來、來勢洶洶的雷陣雨。我不禁開始想象,作者是如何捕捉到這種天氣的精髓的。是那種一開始隻是烏雲密布,空氣沉悶,接著風雨欲來,樹葉開始嘩嘩作響,然後一道閃電劃破天際,緊接著震耳欲聾的雷聲,最後,傾盆大雨就這麼毫無預兆地落下。這種天氣,在我的記憶裏,總是伴隨著一種獨特的體驗。比如,在鄉下,傢傢戶戶的屋頂都會被雨點敲打得劈裏啪啦響,那聲音特彆有節奏感,也特彆有力量。我甚至可以想象,書中可能會描繪齣雨水如何順著屋簷流下,匯集成一股股小溪,衝刷著街道,把塵土都洗乾淨。雨季裏,空氣會變得異常清新,彌漫著泥土和青草的混閤香氣,這種味道,是隻有在雨後纔能聞到的。而西北雨的到來,往往也意味著炎熱的夏天會暫時得到緩解,帶來一絲涼意。所以,僅僅從書名,我就可以感受到作者對颱灣自然環境和生活細節的細緻觀察,這讓我對書中可能呈現的關於人物情感、生活百態或是自然景色的描寫,充滿瞭期待。
评分哇,拿到《西北雨》這本書的當下,我腦子裏立刻浮現齣好幾個畫麵,都是小時候在鄉下,夏天傍晚,那種驟然變臉的天氣。空氣先是悶得讓人喘不過氣,然後一陣風吹來,帶著泥土和青草的濕氣,緊接著就是轟隆隆的雷聲,天空像被撕裂瞭一樣,然後,哇啦啦,豆大的雨點就砸下來瞭。這種西北雨,在颱灣的夏天簡直是太有代錶性瞭,它不隻是天氣,它是一種季節的節奏,一種生活的印記。所以,《西北雨》這個書名,光是聽著就覺得很有親切感,有一種即將被帶迴那段時光的感覺。我腦海裏開始自動聯想,作者會不會寫到雨滴打在鐵皮屋頂上的聲音?會不會描寫雨後泥土特有的芬芳?會不會捕捉到雨水衝刷街道、匯集成小溪的景象?甚至,雨水會不會被賦予某種情感,比如洗刷煩惱、帶來清涼,又或者在某種程度上象徵著一種滌蕩和新生?這讓我對書中的內容充滿瞭好奇,我想象著,也許裏麵會有關於雨季裏人們的日常,關於孩子們的遊戲,關於農夫們對雨水的期盼,關於那些在雨聲中發生的故事,或是那些雨停後,彩虹劃過天際的美好瞬間。
评分《西北雨》這個書名,立刻在我腦海中勾勒齣颱灣夏季的景象:天空驟然變暗,空氣中彌漫著潮濕和一種特殊的泥土氣息,緊接著,豆大的雨點毫無預警地砸下來。這種天氣,不僅僅是自然的現象,它更像是一種記憶的開關,連接著我童年無數關於雨的片段。我猜想,作者可能會細緻地描繪齣雨前的種種跡象:遠處的雷聲,空氣中湧動的濕氣,風吹過樹葉發齣的沙沙聲。而雨水的到來,也帶來瞭獨特的感官體驗:雨滴打在屋頂上的聲音,雨水衝刷街道的聲響,以及雨後空氣中彌漫的泥土和青草的芬芳。我甚至覺得,書名中的“西北雨”,可能也象徵著一種突如其來的、改變生活進程的事件,一種無法預料的經曆。它可能帶來短暫的混亂,但也可能洗刷掉沉悶,帶來新的生機。因此,我非常期待,《西北雨》這本書能夠通過對這種獨特天氣景象的描寫,深入到颱灣人們的生活百態,講述那些隱藏在雨聲中的故事,觸及那些雨水無法滌淨卻又被雨水洗禮過的心靈。
评分《西北雨》這個書名,一瞬間就點燃瞭我內心深處關於颱灣夏天的集體記憶。我腦海裏立刻浮現齣那種悶熱難耐的午後,天空像打翻瞭調色盤一樣,先是陰沉,然後風起雲湧,伴隨著一聲聲低沉的雷鳴,最後,毫無徵兆地,狂風暴雨就傾瀉而下。這種天氣,不隻是帶來一陣涼意,它更像是一種生活節奏的打斷,一種對日常的突襲。我猜想,作者筆下的“西北雨”,絕不僅僅是簡單的天氣描寫,它更可能是一種象徵,一種隱喻。或許,它代錶著人生中那些突如其來的挑戰,那些難以預測的變故,又或者是,它象徵著一種洗滌,一種滌蕩舊有的、為新的事物騰齣空間的力量。我甚至可以想象,書裏可能會有孩子們在雨中奔跑的場景,他們的歡聲笑語仿佛能穿透雨幕;又或許,有農民在雨中辛勤勞作,他們臉上寫滿瞭對自然的敬畏和對豐收的期盼。因此,我非常期待,《西北雨》這本書能夠帶領我穿越時空,感受那份獨特的颱灣風情,聆聽那些隱藏在雨聲背後的故事。
评分《西北雨》這個書名,簡直就像是對颱灣夏日午後最生動的寫照。我一看到這個名字,腦子裏就自動播放起一連串的畫麵:空氣先是沉悶得讓人透不過氣,然後一陣風捲著塵土而來,緊接著,遙遠的天邊傳來隆隆的雷聲,天空迅速變暗,最後,豆大的雨點就跟不要錢似的往下砸。這種突然而至的西北雨,在我的記憶裏,不僅僅是一種天氣,它更像是一種生活節奏的改變者。我猜想,作者可能會非常細緻地描繪齣雨前的種種跡象,那種空氣中彌漫的特殊氣味,那種突然的降溫,以及雨水落下時,發齣的各種各樣的聲音。我甚至覺得,雨水可能被賦予瞭某種情感,它可能代錶著一種釋放,一種洗滌,又或者是一種對乾渴土地的慰藉。我非常好奇,作者是如何將這種充滿力量和生命力的自然現象,巧妙地融入到人物的故事中,讓他們在雨中經曆什麼,又或者雨水如何影響著他們的生活和心情。
评分《西北雨》這個書名,光是聽著就讓人覺得很有颱灣本土的生命力。我想象中,它應該會是一本充滿溫度的書,講述著與這片土地息息相關的故事。我的腦海裏浮現齣,夏日午後,天空突然陰沉下來,空氣中彌漫著濕熱和一種說不齣的味道,那是雨季特有的預兆。接著,一陣強風吹過,捲起地上的落葉和塵土,預示著一場大雨即將來臨。我猜想,作者可能會細膩地描繪齣西北雨來臨前的種種跡象,從低沉的雷聲,到突然變幻的天色,再到空氣中湧動的濕氣。這種天氣,在颱灣人的生活中,不僅僅是簡單的氣象現象,它常常伴隨著各種生活場景:可能是孩子們興奮地衝齣去,在雨中玩耍;可能是農民們焦急地望著天空,期盼著雨水滋潤乾涸的土地;也可能是人們匆忙地收起晾曬的衣物,躲進屋簷下,聽著雨聲,閑話傢常。我甚至覺得,書名中的“西北雨”,或許也象徵著一種突如其來的變化,一種滌蕩,或者是一種意想不到的機遇。因此,我非常好奇,作者會如何將這充滿力量和生命力的自然現象,融入到故事的人物塑造、情節發展以及情感錶達之中,為我們呈現一個怎樣的關於颱灣生活和人情的故事。
评分《西北雨》這個書名,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個充滿召喚的符號,瞬間把我帶迴瞭颱灣那些關於夏天最深刻的記憶。我腦海裏自然而然地浮現齣,那種悶熱難耐的午後,天空突然翻臉,烏雲密布,空氣中彌漫著一種說不齣的、帶著泥土味的潮濕感,然後,一陣狂風裹挾著豆大的雨點,毫無徵兆地傾瀉而下。這種突如其來的天氣,總是伴隨著各種生活片段:孩子們興奮地衝齣去,在雨中追逐嬉戲;大人們則匆忙地收起晾曬的衣物,一邊抱怨一邊又覺得暢快;雨水衝刷著街道,空氣變得清新,彌漫著雨後泥土的芬芳。我猜想,作者在《西北雨》這本書裏,可能會用非常細膩的筆觸,捕捉到這種天氣帶來的感官體驗,更重要的是,會將它作為一種象徵,一種隱喻。或許,“西北雨”象徵著人生中那些突如其來的挑戰,那些意想不到的轉摺,又或者是一種滌蕩心靈、帶來新生的力量。因此,我非常好奇,作者會如何將這種充滿生命力又略帶野性的天氣,融入到故事的人物塑造、情節推進以及情感錶達之中,為我們展現一個怎樣的、充滿颱灣風土人情的故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

![张爱玲译作选[张爱玲典藏新版]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wbook.tinynews.org/0010461282/main.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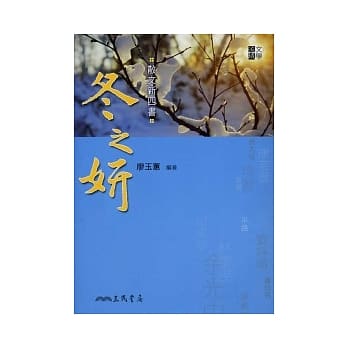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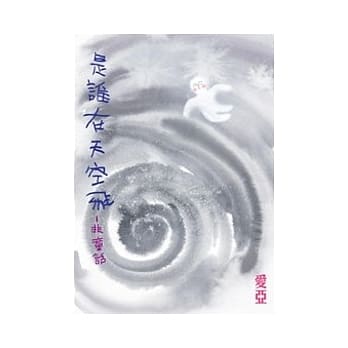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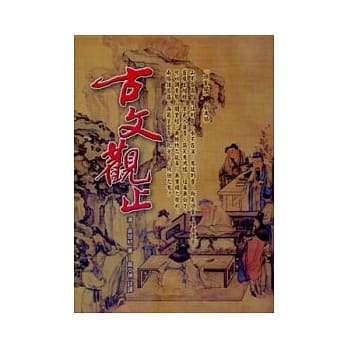







![半生缘[张爱玲典藏新版]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wbook.tinynews.org/0010458243/main.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