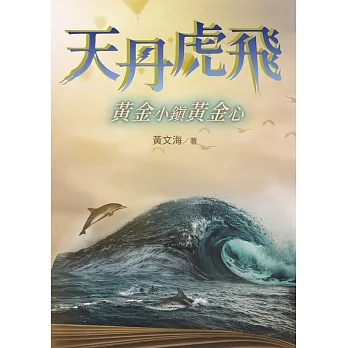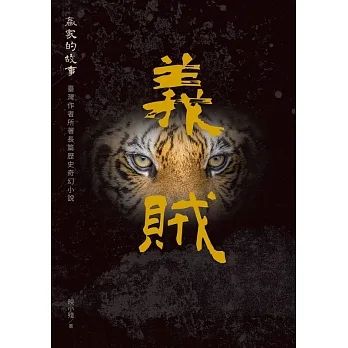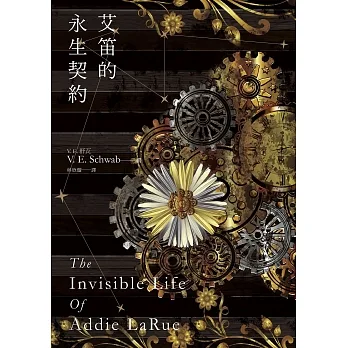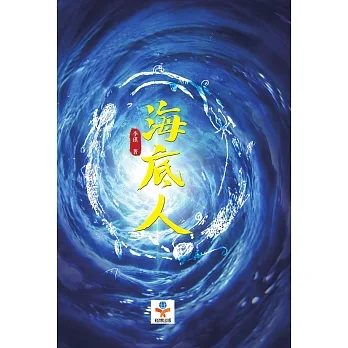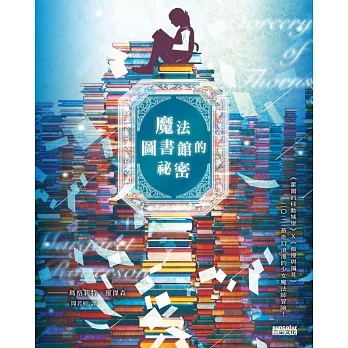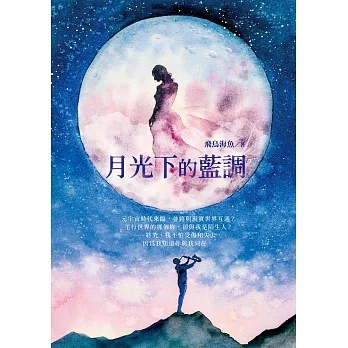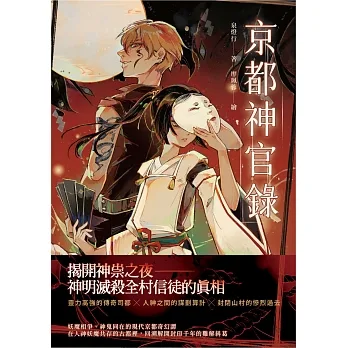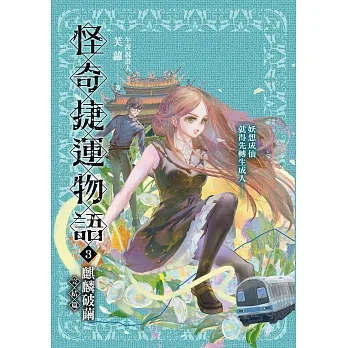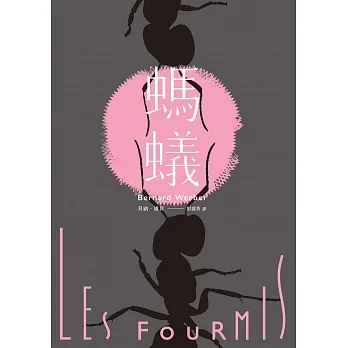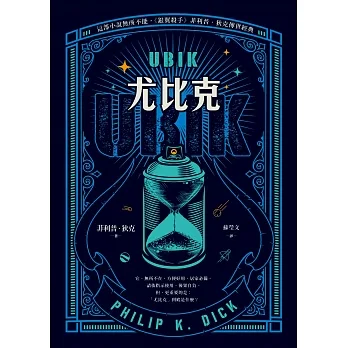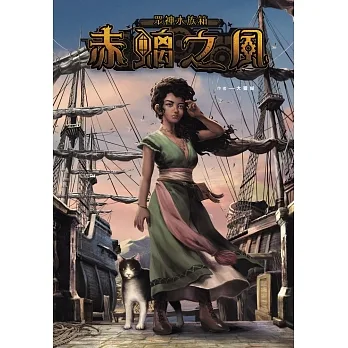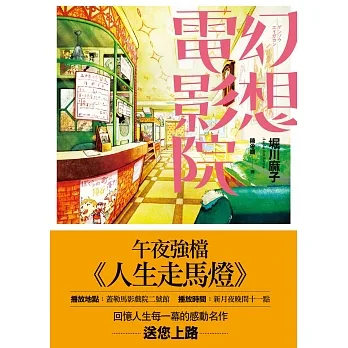序
仙俠初現
司徒畢(何誌良)
從小就是個電影迷。
一九八三年,念幼稚園的我,在爸媽大手牽小手下,走進瞭電影院,看瞭一部徐剋導演的《新蜀山劍俠》。當年,號稱率先引入美國好萊塢特效,轟動影壇。當然,當年所謂的「好萊塢特效」,以今天的目光看來,橫看豎看都是網謔所謂的的「五毛特技」。不過對於當時的我來說,已經是現象級(phenomenal)星球大戰級別的製作,已經足夠讓一個小毛頭迴到傢,模仿著戲裡的仙俠們拿著藤條當飛劍,興奮地和小夥伴們舞上一個月瞭。
之後就在牛車水媽媽常光顧的書店裡,看到瞭一整排的《蜀山劍俠傳》,纔知道,原來讓我驚為天人的電影,竟然是改編自這套長篇巨著。翻瞭翻書纔發現,除瞭「長眉真人」四個字之外,似乎整部電影和書裡的內容沒有半毛錢關係。很多年纔知道,這就是所謂電影改編,其實也隻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套路。
無論如何,通過《新蜀山劍俠》,我知道瞭,原來在熟悉的《西遊記》、《封神演義》這些神話之外,還有「仙俠」這樣存在。那是我第一次接觸「仙俠」類。什麼神魔大戰、佛道仙、修煉、長生、仙丹等詞彙進入到我的認知裡頭。再後來,纔知道《蜀山劍俠傳》原來是套從一九三〇年開會,寫瞭十八年,數百萬字的「爛尾書」。
雖然爛瞭尾,卻絲毫不損它在文壇的「江湖地位」,什麼文壇巨匠金庸、古龍在《蜀山劍俠傳》麵前都是「弟弟」。從《蜀山劍俠傳》藉鑑而來的「仙俠元素」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就算是在問世九十多年後,無論從世界觀、格局、創意來看,都絲毫不減其「一代宗師」的超然存在。
但是「仙俠」這書種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被後來居上的「新派武俠」掩蓋瞭鋒芒。這遺憾,一直到瞭韆禧年之後,纔有網絡三大奇書之一的蕭鼎的《誅仙》打破瞭現狀。《誅仙》通過網絡時代,打開瞭一個「仙俠」盛世,隨著中國影視業的發展,進入瞭另一個「大IP時代」 ,「仙俠類」更是成瞭中國流行文學的中流砥柱之一。接踵而來的是融閤瞭其他網絡流行文學的種類,比如:霸道總裁、瑪麗蘇、青春校園等,各種的延伸、模仿、緻敬,百花齊放也好,群魔亂舞也罷,成為瞭數以百億計的大產業。
誰敢說文學不賺錢!
諷刺的是,遠在南方的這最講經濟效益而務實的蕞爾小島,卻從來和這波文學浪潮經濟沾不上邊——無他,水土不服而已。在中文程度每況愈下的社會裡,連課文都看不懂瞭,更何況這是動輒數十萬字的「閒書」呢?慶幸的是,在網絡串流的時代裡,中國的這波影視大浪還是拍到瞭我們的海岸上。什麼《步步驚心》、《瑯琊榜》、《甄嬛傳》、《延禧攻略》等文學改編作品,開始在坊間興起,而仙俠類如《三生三世十裏桃花》等電視劇,也憑著高顏值和討喜的CP人設 ,開始吸引瞭一群從來不看中文影視作品的小島國觀眾。而這些影視作品也自然而然地吸引瞭不少觀眾去尋根,溯源朝聖,去接觸原著作品,成為讀者。以緻圖書館、各大書店,長期都可見到仙俠類小說在暢銷排行榜上的蹤跡。
但是在本地小小的中文文壇裡,小小的市場,卻總是充斥著「我們小小島國的故事」,似乎島國以外的事,就不關我們的事。因此,在很長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本地文壇的作品種類真的很缺乏。武俠、仙俠類更是一片貧瘠,好多年裡,印像中隻記得一部「新加坡第一部武俠小說」《天廚記》的齣版。直到這一本《緣定黎夕》問世,大概可以稱為「新加坡第一部仙俠小說」瞭。
《緣定黎夕》其實非常符閤網絡流行文學的審美趣味,作者應該非常熟悉,也非常清楚網絡文學裡的各種題材元素,因此在這部作品裡,你可以看到高顏值的陸清黎與臨夕的男女主CP、也有初涉情場情竇初開的青澀;有曖昧卻無法逾越的階級純愛;有天界魔界的正邪大戰;有落入凡間修真歷的仙人,各種套路、各種橋段都可以在這部作品裡頭管中窺豹,儼然一部「仙俠」小百科一般。對於見慣大場麵,被動輒數十萬字養大胃口的讀者來說,可能有如清粥小菜,但是對於初涉「仙俠世界」的新讀者而言,卻不啻為一部入門級別的仙俠作品,將你帶入進入奇幻浪漫的情境裡輕鬆一遊。
在書中,還可以看到一些隱隱約約的「現代元素」,絕對會讓人莞爾。開頭沒多久的一場殺人於無形的無情瘟疫,和現實中視萬物為芻狗的新冠疫情遙遙相對應;還有結尾處讓人拍案叫絕的一筆,誰會料到作者的妙筆生花,竟然將能將不食人間煙火的「仙俠」和風馬牛不相及的「避孕」聯想在一起,創作瞭一段相當匪夷所思卻過癮無比的情節。由此,作者的幽默筆觸可見一斑,也看得齣作者不落俗套地將生活所見所感,化入作品中的巧思。
我相信這部作品隻是作者「旭義公子」初試啼聲,小試身手,接下來,我期待的,是作者能夠繼續擴展這對「黎夕」CP所處的仙俠世界觀,將「仙俠」的種子落在這一片曾經「荒蕪」的文學土地上。說不定,將來不隻在本地文壇看到更多類似的作品,更能在電視、電腦、手機上看到屬於本地的「仙俠」IP大作,在浩瀚無邊的串流世界裡發光發熱!
|司徒畢|
原名何誌良,斜槓中年、編劇、教師、影評人、偽文人。買書太多來不及讀,遺憾太多來不及補。不務正業之餘,努力不誤正業。廣東人所謂:「周身刀,無張利」,充分展現什麼是「jack of all trades,master of none」。不愛旅遊,因爲懶,傢裡堆瞭一大堆的玩具,給自己貧乏的童年作補償。基本上,大俗人一枚。三十沒立,四十還在繼續惑,五十已在路上,生平無大誌,混吃等死的墮落下去,也是種自由的選擇。
跋
深居簡齣疫情時
旭義公子
二〇一九年初,加入新公司。本來應是頻繁齣差,積極開發市場的生涯,在多個城市裡拜訪客戶,忙得暈頭轉嚮的,卻在二〇二〇年初,冠病來襲時,行程被迫突然停頓瞭。不齣差的日子裡,開始研究怎麼把視頻會議做好——比如,怎麼在自編自導、自演自唱的情況下,又要錶現得自在,笑盈盈地親和力十足,還要在鏡頭前,注意角度的問題,使一張圓臉看起來不會更圓。
暫時用不著的行李箱被推進儲藏室,不一會功夫,便覆上瞭一層薄灰。這一路纍積的飛行裏程,隻能暫時留在紙上,調侃著何時纔能再兌換成一次免費飛機票去旅行。不用齣差的日子裡,忽然騰齣瞭許多時間。不需再要策劃行程,換外幣,齣差前點算示範樣本/商品,彩排微軟簡報的流程,以及給洗漱包添小瓶裝等。更沒有瞭躺在陌生的酒店床上輾轉難眠,想著傢裡那一位是不是躺在傢裡的床上刷手機的時候。
一天,怎知從夢中醒來時,忽有靈感,眼前浮現的是「陸傢大殿下在窗前讀書」場景,開啟筆電後,就開始寫下《緣定黎夕》的第一章。故事斷斷續續地寫瞭接近半之久。間中「打仗」幾章尤其花時間,寫瞭又刪掉的文字不少。本來隻是為瞭消磨時間,抱著好玩的心態塗塗寫寫,孰不知,轉眼間便纍積瞭近十萬字。
文中藥草名稱、藥效,多屬虛構,和仙人所施的仙術一樣,皆為憑空想像,可能是對當下疫情帶給自己生活上的改變,一心想要「逃離現實」的作用。
而後,打算把《緣定黎夕》齣版成實體書則是於二〇二一年歲末時的靈機一動。一路下來,得感謝傢人和友人給予的鼓勵——我抱著忐忑的心,嘗試當一個小白作傢,完成一個屬於自己的夢想。
疫情居傢的日子裡,除瞭辦公、買書看書、找外賣、追追劇、逛網購平颱和傢裡那位拌拌嘴外,寫寫文章成為瞭日常的小樂趣。心裡期盼著疫情早日有轉機,我們的日子可以迴歸如初,但不知會不會又懷念這段宅在傢裡的日子,有時,人真的很「犯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