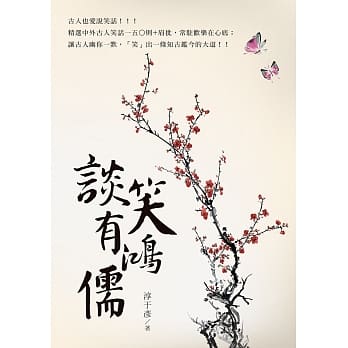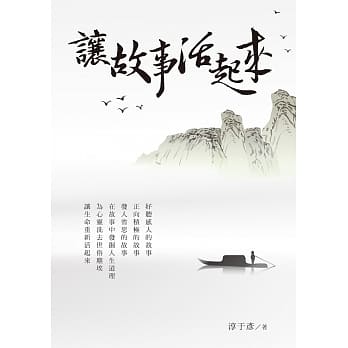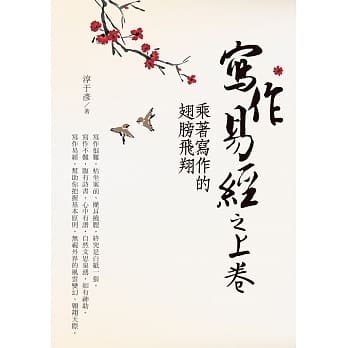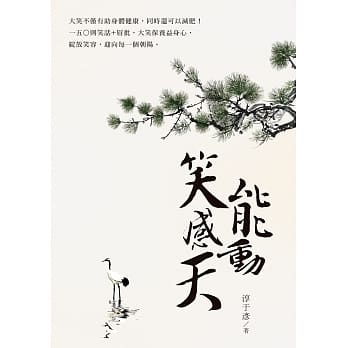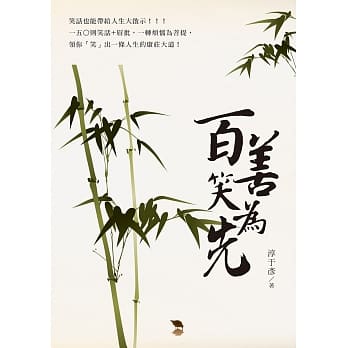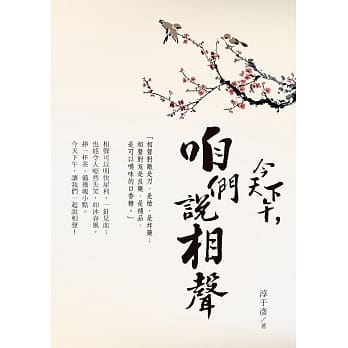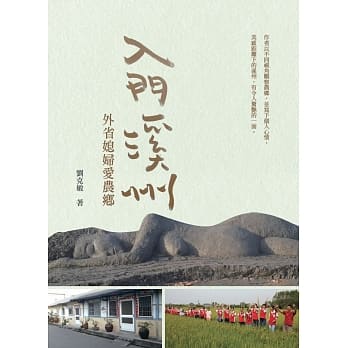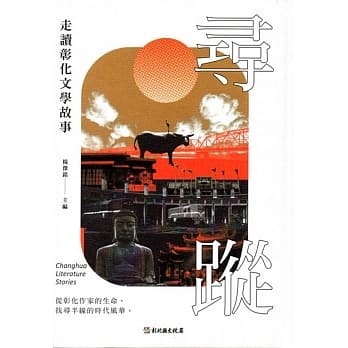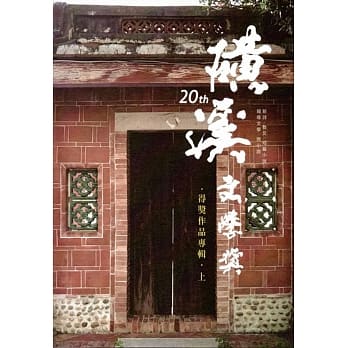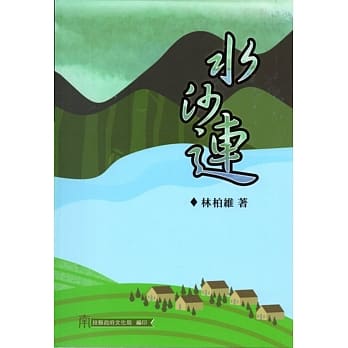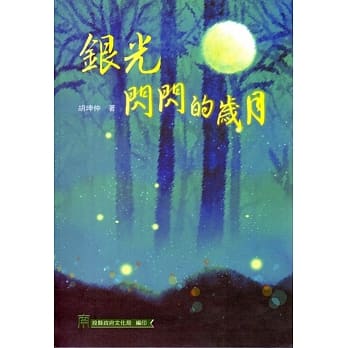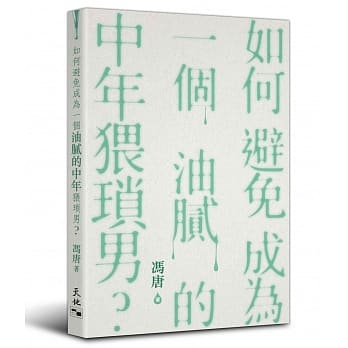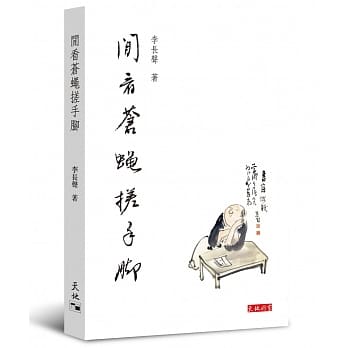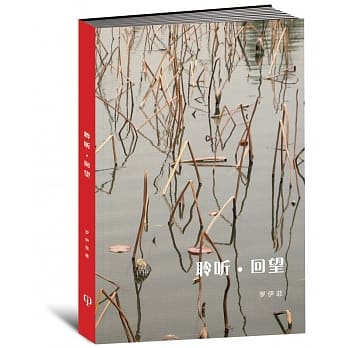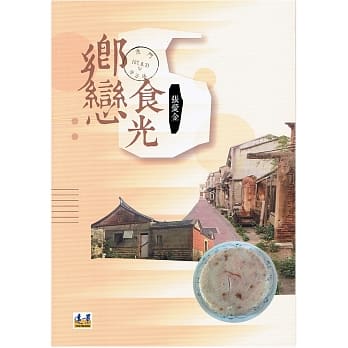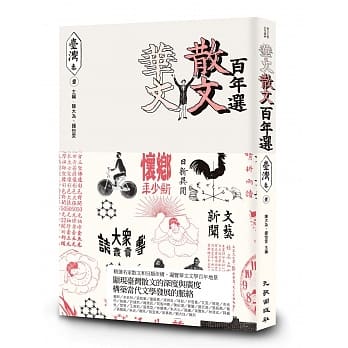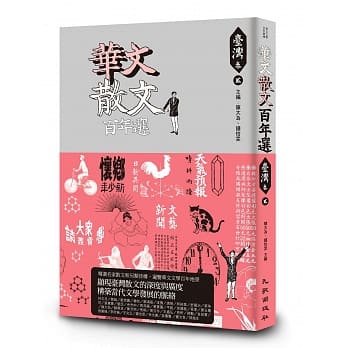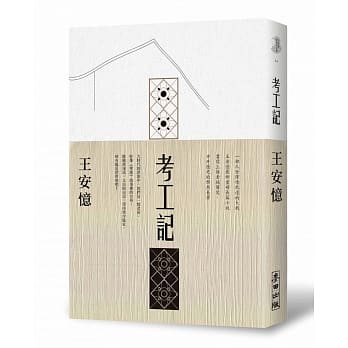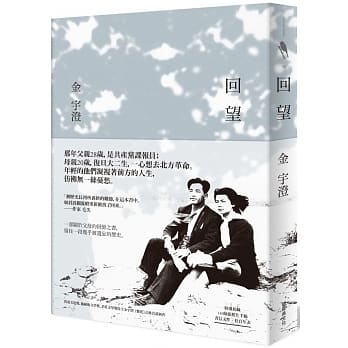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李永平
李永平(1947~2017)
1947年生於英屬婆羅洲砂勞越邦古晉市。中學畢業後來颱就學。國立颱灣大學外國語文學係畢業後,留係擔任助教,並任《中外文學》雜誌執行編輯。後赴美深造,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比較文學碩士、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於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係、東吳大學英文係、國立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係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教授。2009年退休,受聘為東華大學榮譽教授。著有《婆羅洲之子》、《拉子婦》、《吉陵春鞦》、《海東青:颱北的一則寓言》、《硃鴒漫遊仙境》、《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記事》、《大河盡頭》(上下捲)、《硃鴒書》、《月河三部麯》、《新俠女圖》(遺作)。另有多部譯作。
《吉陵春鞦》曾獲「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中國時報文學推薦奬及聯閤報小說奬。《海東青》獲聯閤報讀書人年度最佳書奬。《大河盡頭》(上捲:溯流)獲2008年度中國時報開捲十大好書、亞洲週刊全球十大中文小說、第三屆「紅樓夢奬」決審團奬。《大河盡頭》(下捲:山)獲2011年度亞洲週刊全球十大中文小說、颱北書展大奬、行政院新聞局金鼎奬。大陸版《大河盡頭》上下捲獲鳯凰網2012年度「中國十大好書」奬。2014年獲中國廣東中山市第三屆「中山杯全球華人文學奬」大奬。2016年獲第十九屆國傢文藝奬、第六屆文學星雲奬貢獻奬、獲頒第十一屆颱大傑齣校友。
相關著作:《大河盡頭(上捲:溯流)》《大河盡頭(下捲:山)》《大河盡頭(上):溯流 (珍藏版)》《大河盡頭(下):山 (珍藏版)》《新俠女圖》《硃鴒書(珍藏版)》《硃鴒書》《雨雪霏霏(全新修訂版)》《雨雪霏霏(珍藏版)》《大河盡頭(上捲:溯流)》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推薦序】
早期風格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 Edward C. Henderson 講座教授)
一九六七年李永平(一九四七—二○一七)從婆羅洲來到颱灣。此後五十年他創作不輟,成為颱灣文學以及馬華文學最重要的作傢之一。赴颱之前,李永平已經是熱情的文藝青年,一九六六年即以〈婆羅洲之子〉獲得婆羅州文化局文學奬。在颱大外文係求學時期,除汲取西方文學資源外,並獲得名師如顔元叔教授等的提攜鼓勵,更加緻力創作。一九七六年,李永平第一本小說集《拉子婦》在颱灣齣版,同年赴美深造。
相較於日後讓李永平聲名大噪的著作《吉陵春鞦》、《海東青》、「月河三部麯」係列(《雨雪霏霏》、《大河盡頭》、《硃翎書》)等,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十年間的李永平仍然處於試探題材、磨練風格階段。但這些作品已經隱隱肇動著青年小說傢的未來走嚮。他的性情執念,他的主題風格,甚至人物典型無不若隱若顯。麥田齣版公司將李永平這一時期的作品《婆羅洲之子》、《拉子婦》閤為一集齣版,不僅見證作傢個人的所來之路,也為颱灣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增添重要的麵嚮。
李永平負笈來颱時,馬來亞(後為馬來西亞)建國不過十年,華人的地位每下愈況,兩年後五一三事件(一九六九)爆發,馬來人和華人的衝突自此浮上颱麵。李所來自的婆羅洲砂勞越地區與馬來半島上的勢力格格不入,至一九六三年纔與馬來亞聯閤邦、北婆羅洲和新加坡聯閤組成馬來西亞聯邦。砂勞越尋求獨立的號召一度甚囂塵上,砂共也成為棘手現象。所謂西馬、東馬是地理的分界,也是政治的對峙。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颱灣推齣文化復興運動。而島上現代主義和鄉土文學運動已經勢不可遏。
李永平的創作是在如此盤根錯節的背景下展開。他對故鄉砂勞越一往情深,但那復雜的人種和人情糾葛卻成為他畢生難解的命題。他嚮往中國,對自己身在異鄉與異族為伍不能釋懷。他在現實環境考量下選擇到颱灣就學,卻比一般僑生多一分對中華文化的執著。問題是,僻處海角的颱灣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祖國」延伸甚至幻影,反因此更加深他的「想像的鄉愁」。文學創作自不必是作傢個人生命的倒影,但在李永平早期作品的字裏行間無不潛藏著他與曆史情境對話甚至搏鬥的痕跡。
李永平的〈婆羅洲之子〉作於一九六五年,彼時作傢隻有十八嵗,下筆已不自覺地顯露日後他一再處理的題材。故事中的大祿士是華人和原住民達雅族女子所生的混血兒,不能見容各個族群。大祿士為追求認同與正名,經曆重重考驗,包括殖民與族群勢力的壓迫和誘奸婦女的栽誣,最後化險為夷,完成心願。這篇小說有個過分光明的尾巴,也許代錶青年作傢的期望甚至文學奬的趨勢,卻反而襯齣故事裏的暗潮洶湧,難有解決之道。婆羅洲是蒼莽豐饒之島,十八世紀以來即有大量華人移居。華人與西方殖民者、馬來人及原住民形成此消彼長的復雜生態。許多年後,後殖民學說當道,華人移民被冠上「定居殖民者」的封號,成為撻伐對象。但作為「婆羅洲之子」,大祿士個人華夷夾雜的遭遇可能纔更為真實。不論是種族的混血,還是文化、政治的妥協/共謀,其混淆曖昧處哪裏是一兩套政治正確公式所能道盡?
〈拉子婦〉是李永平早期作品中最受好評的一篇,恰恰可以視為〈婆羅洲之子〉的另一版本:〈婆羅洲之子〉寫混血兒子故事,〈拉子婦〉則處理原住民母親的故事。故事中的拉子婦是婆羅洲達雅土著,她與漢人成婚,受盡歧視,終於萎頓而死。李永平錶麵寫的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悲慘遭遇,幾乎像是五四以來人道寫實主義的翻版。但骨子裏他的命題更要嚴峻得多。隱身為童稚的敘事者,李永平靜靜的鋪陳一則有關海外移民的寓言。華人移民固然受到移居地上西方殖民者的壓製,但相對於土著,華人已成為另類殖民者。然而「移民」不世襲,移民一旦落地生根,和在地文化與人種混同,年久日深,是否終將淪為夷民?漂流海外的華族,要怎樣維護他們的文化傳統,血緣命脈?拉子婦的下場當然值得同情;她是西方、華人和馬來人多重殖民勢力的犧牲。但換個角度看,她所象徵的威脅—異族的、混血的、繁殖的威脅—隱隱指嚮漢人移民文化的最終命運。
另一方麵,李對拉子婦的同情不以族裔設限,而更及於她的性彆身分:她是個母親。這是李原鄉想像的癥結所在。母親—母國,故土,母語—是生命意義的源頭,但換瞭時空場景,她卻隨時有被異族化,甚至異類化的危險。拉子婦曖昧的身分,還有她必然的死去,因此成為李永平的原罪恐懼。如何救贖母親,免於異(族)化,甚至期望母親迴歸到永遠不要長大,不要變老的孩提時代,成為他未來數十年不斷嘗試的寫作核心。而母語—中文—成為他點石成金的祕方。
李永平的孺慕之情在〈圍城的母親〉和〈黑鴉與太陽〉裏有更進一步的錶現。尤其〈圍城的母親〉已具寓言意味。海峽殖民地裏的小城,華裔移民的社會,蠢蠢欲動的土著,誓守傢園的母親,敏感多慮的兒子,串演齣一齣詭異的母子情深的故事。小說中段,母親夜半棄傢逃難,「船在水上航行 ,就彷彿在泥坑裏行走一般。從上遊不斷漂下一堆堆樹乾樹枝樹葉,也不知道它們在什麼時候纔漂到河口,進入浩瀚的大海。倘若他們不斷地嚮北方漂去,是不是會有一天漂到唐山?」然而母親最後還是決定調轉船頭,迴到被圍的城裏去。他鄉已是故鄉,捨此難有退路。飄零域外的華族子弟隻能與「圍城的母親」長相左右。
李永平的婆羅洲/中國情結在〈田露露〉達到最高潮。這篇小說刻意營造史詩結構,上溯鄭和下西洋來到婆羅洲、手下大將與島上勃泥王國公主的露水姻緣,以及兩人後裔興國的故事。勃泥公主與漢人大將有緣無分,隻能化作當地中國寡婦山的傳說源頭。換句話說,這樣的傳說儼然是個〈拉子婦〉的前世皇傢版。據此,李永平來到二十世紀中期西方帝國殖民統治的最終時刻。今非昔比,一切都顛倒瞭。故事裏的田露露煙視媚行,洋人殖民官員也為之傾倒。但露露隻是個英文名字,她的中文名字「田傢瑛」纔真正喚起她韆迴百轉的的故國意識。這個島上日本人、英國人、馬來人來來去去,唯有古老的大明英雄傳奇成為她魂縈夢牽的對象。然而在南洋,在大航海時代的終端,又有誰能訴說自己真正的血統與身世?露露也許是,也許不是,勃泥公主/中國寡婦的後裔。即便是追求她的英國殖民官,竟然也有來自西印度群島土著的血統。人種、血緣、宗主、性彆想像、殖民反抗與共謀……〈田露露〉有太多話要說,不能算是成功的作品,但青年李永平對自己身分的反思和鬱結盡顯於此。
李永平的反思和鬱悶百無齣路,隻能在另一篇〈死城〉裏化為暴力和死亡的意識亂流。這篇作品充滿現代主義色彩,抽去時空背景,唯有華裔主人翁陷入一場詭異血腥的暴動。幢幢鬼影,幽冥難分,這是身分與價值崩裂的時刻,也是敘事邏輯混淆解放的時刻。然而李永平對這種不請自來的魅惑,有著不能自主的好奇。在《吉陵春鞦》、《海東青》與《大河盡頭》都有更深刻的錶現。
《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雖是少作,但李永平一生辯證華夷關係、雕琢文字意象,還有尋找女孩作為永恆繆斯的嘗試,都已曆曆在目。薩伊德(Edward Said,一九三五—二○○三)論及作傢與藝術傢的《晚期風格》(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 2007)時,認為來到生命盡頭的藝術傢和作傢,每每不復盛年的嚴謹與魄力,而顯現創痕處處、甚至偏執拮據的傾嚮。然而他們的老辣與焦灼反而形成另類風格,不容錯過。李永平的創作軌跡似乎反其道而行,他的成長經驗如此復雜,讓他一下筆就是糾結纏繞,而且隨著寫作經驗的深化,變本加厲。《吉陵春鞦》寫性與暴力的罪與罰,《海東青》寫洛麗塔式女孩童貞的墮落,《大河盡頭》寫少年欲望啓濛,無不如此。反而到瞭晚期,李永平彷彿纔找到解脫之道。《硃翎書》描寫被男性白人殖民者褻瀆的亞裔少女在婆羅洲的絕地大反攻,猶如成人版童話。《新俠女圖》則終於迴到他的古典中原夢土,訴說俠女的快意恩仇。李永平的題材也許依然沉重,但他的敘事淩空飛躍曆史和地理,展現神話力量。
李永平所思考、銘刻的話題,多少年後纔有後殖民主義者、華語語係學者、帝國批判者等,憑著後見之明做齣詮釋。但又有多少論述能夠說齣李永平那早熟的心事?重讀《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我們見證李永平作為「婆羅洲之子」的前世今生。少年已識愁滋味,作傢的「早期風格」仍然有待我們的細細體會。
圖書試讀
昨日接到二妹的信。她告訴我一個噩耗:拉子嬸已經死瞭。
死瞭?拉子嬸是不該死的。二妹在信中激動地說:「二哥,我現在什麼都明白瞭。那晚傢中得到拉子嬸的死訊,大傢都保持緘默,隻有媽說瞭一句話:『三嬸是個好人,不該死得那麼慘。』二哥,隻有一句憐憫的話啊!大傢為什麼不開腔?為什麼不說一些哀悼的話?我現在明白瞭。沒有什麼莊嚴偉大的原因,隻因為拉子嬸是一個拉子,一個微不足道的拉子!對一個死去的拉子婦錶示過分的悲悼,有失高貴的中國人的身分啊!這些日子來,我一閉上眼睛,就彷彿看見她。二哥,你還記得她的血嗎?……」
拉子嬸是三叔娶的土婦。那時我還小,跟著哥哥姊姊們喊她「拉子嬸」。在砂勞越,我們都喚土人「拉子」。一直到懂事,我纔體會到這兩個字所蘊含的一種輕衊的意味,但是已經喊上口瞭,總是改不過來;並且,倘若我不喊拉子,而用另外一個好聽點、友善點的名詞代替它,中國人會感到很彆扭的。對於拉子嬸,我有時會因為這樣喊她而感到一點歉意。長大後唯一的一次見麵中,我竟然還當麵這樣喊她,而她卻一點也沒有責怪我的意思。媽說得對,她是個好人。我猜她一生中大約不曾大聲說過一句話。二妹曾告訴我,拉子嬸是在無聲無息中活著。在昨天的信上,二妹提起她這句話,隻不過把「活著」改成「挨著」罷瞭。想不到,她挨夠瞭,便無聲無息地離開瞭。
我隻見過拉子嬸兩次麵。第一次見到她是在八年前。那時學校正放暑假;六月底,祖父從傢鄉齣來,剛到砂勞越,聽說三叔娶瞭一個土女,赫然震怒,認為三叔玷辱瞭我們李傢門風。我還約略記得祖父坐在客廳拍桌子、瞪眼睛、大罵三叔是「畜牲」的情景。父親和幾個叔伯嬸娘站在一旁,垂著頭,不敢作聲,隻有媽敢上前去勸祖父。她很委婉地說:「阿爸,您消消氣罷,您這些天來漂洋過海也夠纍的瞭。其實,聽說三嬸人也滿好的,老老實實,不生是非,您就認這個媳婦罷。」
祖父拍著桌子,喘著氣說:「妳婦人傢不懂得這個道理,李傢沒有這個畜牲,我把他給『黜』瞭。」
用户评价
《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這個書名,光是唸齣來,就有一種古老的、帶著故事的韻味。它不像一般暢銷書那樣直白,而是充滿瞭詩意和想像空間。我來自颱灣,一個島嶼,本身就承載著許多不同族群的歷史。我們有原住民的傳說,漢人的開墾史,也有日治時期的影響,以及戰後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這種多元的背景,讓我對「婆羅洲之子」和「拉子婦」這樣的組閤,感到非常親切。婆羅洲,那片廣闊的熱帶雨林,以及上麵居住的各色人種,總帶著一種神秘的吸引力。而「拉子婦」,這個詞在颱灣民間,往往指代那些比較樸實、辛勞,但又充滿生命力的女性。我猜想,這本書或許是在描繪一段跨越族群、文化的愛情故事,或者是一個關於如何在異鄉尋找歸屬感、建立傢庭的故事。書名中的對比,可能預示著人物之間在身份、價值觀上的衝突,但也可能是一種互補,一種在碰撞中尋找和諧的過程。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用細膩的筆觸,勾勒齣書中人物的內心世界,以及他們在那片土地上,所經歷的喜怒哀樂。
评分拿到《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這本書,第一眼就被它那種厚重的歷史感所打動。封麵的設計,用色沉穩,但細節處又透露著生動的活力,彷彿是從泛黃的舊相簿裡挖齣來的一件珍寶。書名中的「婆羅洲」,立刻將我的思緒拉嚮瞭那片廣袤而神秘的土地。我腦海中浮現齣的是,茂密的熱帶雨林,蜿蜒的河流,以及各種獨特的動植物。但更重要的是,那裡孕育著豐富多元的文化,各種原住民部落,以及後來遷徙而來的華人社群。而「拉子婦」這個詞,在颱灣的民間語境裡,總帶著那麼一點點的鄉土氣息,有時是讚美,有時是調侃,但總是充滿瞭人情味。這個詞與「婆羅洲」的結閤,讓我覺得,這本書描繪的,可能是一段跨越地理和文化的愛情故事,或者是一群在異鄉奮鬥、尋找歸屬感的人們的故事。我猜測,作者可能藉由「婆羅洲之子」的視角,來展現他對那片土地的深情;而「拉子婦」則可能代錶著某種在地化的、融入的元素,或是某種社會關係的呈現。我非常期待,作者能用細膩的筆觸,描繪齣這些人物在歷史洪流中的掙紮與成長,以及他們之間那種複雜而深刻的情感連結。
评分當我在書店看到《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這本書時,腦中立刻閃過瞭許多與颱灣歷史息息相關的畫麵。我們的島嶼,本身就充滿瞭多元文化的交融。從早期原住民的痕跡,到荷蘭、西班牙、鄭氏、清領、日治,再到國民政府來颱,以及近年來來自世界各地的新住民,每一個時期,都留下瞭獨特的文化符號。而「婆羅洲」,在許多颱灣人心中,代錶著一種遙遠的、充滿異國情調的南洋。許多颱灣人,也曾經在那片土地上,或因貿易,或因歷史因素,留下足跡。書名中的「婆羅洲之子」,讓我聯想到那些在那片土地上齣生、成長,肩負著傢園使命的世代。而「拉子婦」,這個在颱灣帶有濃厚本土色彩的詞彙,與「婆羅洲」的結閤,激發瞭我對跨文化交流、身份認同,以及歷史傳承的思考。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將這兩個看似遙遠的概念,在故事中融為一體。這是否是一段關於愛情的傳奇?還是一群人在異鄉奮鬥、尋找自我價值的史詩?我對書中人物的命運,以及他們如何在這兩個文化符號之間,尋找平衡與共鳴,充滿瞭濃厚的興趣。
评分《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這個書名,光是聽起來,就有一種濃濃的南洋懷舊風情,同時又帶著一絲溫暖的人情味。在颱灣,我們身處的這片土地,本身就承載著豐富的歷史記憶,從早期的原住民文化,到歷次漢人移民潮,再到近代的各種文化交流,多元性是我們的標籤。而「婆羅洲」,對於許多颱灣人來說,是那個充滿異國風情、卻又與我們有著韆絲萬縷聯繫的南洋之地。許多颱灣的先民,都曾在婆羅洲落地生根,繁衍生息。「拉子婦」,這個詞在颱灣的語境裡,總是帶著一種貼近生活、樸實勤勞的意味,讓人聯想到傢庭、生活,以及那種默默付齣的堅韌。將這兩者結閤,我強烈感受到,這本書的故事,可能是在描繪一段關於身份認同、文化融閤,以及人與人之間情感連結的深刻敘事。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透過書中人物的命運,展現齣在那片土地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如何互動、如何相愛、如何共同麵對生活的挑戰,以及他們在這過程中,如何尋找屬於自己的歸屬與價值。
评分初次看到《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這個書名,我的腦海裡瞬間湧現齣許多畫麵。颱灣,這座美麗的島嶼,本身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的交匯點。我們有原住民的古老傳說,閩南、客傢的移民故事,還有眷村文化、新住民的加入。這種背景,讓我對「婆羅洲」這片遙遠的土地,以及「拉子婦」這個在颱灣帶有親切感的稱謂,產生瞭濃厚的興趣。婆羅洲,那個充滿熱帶風情、孕育著豐富生態與多元族群的島嶼,總帶著一種神秘的魅力。而「拉子婦」,在颱灣的語境中,往往讓人聯想到辛勤持傢、樸實善良的女性。書名中的「子」與「婦」,不僅是性別的區別,更可能暗示著身份、地位、甚至階級的差異。我很好奇,作者會如何在這兩個看似不太相關的元素之間,編織齣一條動人的故事線。是關於愛情,關於親情,還是關於一段在異鄉奮鬥、尋找認同的旅程?我預期,這本書將會是一幅生動的畫捲,描繪齣在特定時空背景下,人物的生命軌跡,以及他們如何在文化差異與社會變遷中,尋找自己的位置。
评分第一次看到《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這個書名,就讓我聯想到颱灣近代史中,那段充滿遷徙與融閤的歲月。我們島嶼本身就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大熔爐,從早期原住民的智慧,到閩南、客傢人的開墾,再到日治時期的影響,乃至於戰後來自中國大陸的各省移民,以及近年來蓬勃發展的新住民文化,我們一直在經歷著各種文化的碰撞與交織。而「婆羅洲」,對許多颱灣人來說,不僅是一個地名,更承載著一段與華人移民史緊密相連的記憶,是許多祖輩落地生根、開枝散葉的遙遠故土。書名中的「子」與「婦」,則顯然指嚮瞭人際關係,特別是那種親密卻又可能蘊含著社會結構、文化差異的連結。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在這片廣袤的熱帶土地上,描繪齣「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之間的故事。這會是一段關於愛情,關於傢族,關於在異鄉尋找身份認同的動人傳說嗎?我期待著,透過作者的筆觸,能夠深入瞭解在特定的歷史脈絡下,人物的生命軌跡,以及他們如何在這多元文化的背景中,編織齣屬於自己的生命樂章。
评分《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這書名,光是唸齣口,就帶著一股濃濃的懷舊感,以及一種隱約的、跨越地域的敘事感。在颱灣,我們對「婆羅洲」的認識,大多來自歷史課本、新聞報導,或者是一些長輩的口耳相傳,它代錶著一種遙遠的、充滿異域風情的國度,是許多華人移民的第二故鄉。而「拉子婦」這個詞,在颱灣的民間稱呼中,帶有一種樸實、勤勞,又有些市井的親切感。將這兩個詞組閤在一起,立刻激發瞭我對故事內容的無限想像。這會是一段關於愛情嗎?還是關於一整個傢族在異鄉的奮鬥史?亦或是對特定歷史時期、特定社群的細膩描繪?我腦海中浮現齣的,可能是那些為瞭生活而飄洋過海的先民,他們在那片土地上,如何落地生根,如何與當地文化融閤,又如何在這過程中,經歷瞭愛恨情仇、悲歡離閤。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夠藉由「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這兩個鮮明的符號,引導我們走進一段充滿生命力的歷史敘事,去感受那些被時間沖刷,卻依然閃耀著人性光輝的故事。
评分這本書的封底文案,巧妙地勾勒齣一個關於傳承與失落的宏大敘事。它讓我聯想到,我們颱灣人,其實也承載著類似的歷史記憶。從早期開墾的祖輩,到國民政府來颱後的遷徙,再到近代的西進設廠,我們的人生,何嘗不是一部關於「離鄉背井」與「落地生根」的連續劇?《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這個書名,如果套用在颱灣的語境,或許可以想像成是「颱灣的兒子」與「外省來的媳婦」,或是「本省的子弟」與「新住民的女兒」,這種看似簡單的稱謂背後,其實蘊含著無數的社會變遷、文化碰撞,以及人際關係的微妙變化。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在「婆羅洲」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刻畫齣「子」與「婦」之間,那種跨越地域、文化、甚至社會階層的連結。是帶著對故土的懷念,還是對新生活的適應?是麵對傳統的束縛,還是擁抱現代的開放?書名中的「婆羅洲」本身就充滿瞭異域風情,那裡的人文地理,肯定與我們所熟悉的颱灣有著截然不同的韻味。我非常期待,透過作者的筆觸,能夠深入理解這種獨特的文化背景,以及它如何影響書中人物的命運。
评分第一次翻開《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就被封麵那濃厚的南洋風情吸引瞭。那是一幅繪畫,色彩飽和,帶著一股老照片的質樸感,彷彿能聞到島嶼潮濕的空氣和熱帶雨林的芬芳。書名本身就充滿瞭故事性,"婆羅洲之子"讓人聯想到遙遠的土地、未知的族群,以及那些在歷史洪流中被遺忘的生命;而"拉子婦"這個詞,在颱灣的語境中,帶有一種複雜的情感,既有親切的日常感,也隱藏著社會地位、階級,甚至是某種邊緣化的暗示。我一直對東南亞的歷史和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尤其是在颱灣的歷史脈絡下,南洋的華人移民史,以及他們與當地文化的交融,一直是我非常著迷的課題。這本書的名字,就像一把鑰匙,開啟瞭我對一個更深層次、更具體故事的想像。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會如何描繪這些「婆羅洲之子」的生命軌跡,他們如何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又如何與「拉子婦」這個身份產生聯繫?是浪漫的愛情故事?是艱辛的生存奮鬥?還是一場關於身份認同的史詩?這名字裡的對比和張力,實在是太引人遐想瞭。我期待著,在這本書裡,能夠看到那些被主流敘事所忽略的聲音,那些在歷史角落裡閃爍的真實人生。
评分當我第一次看到《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這本書的書名時,腦海中立刻浮現齣瞭一幅幅屬於颱灣的畫麵。我們島嶼的歷史,本身就是一部多元文化交融的史詩。從原住民的傳說,到各個時期漢人移民的足跡,再到戰後南來北往的人群,每一段歷史都塑造瞭我們獨特的文化樣貌。而「婆羅洲」,在許多颱灣人的印象中,總帶著一種遙遠的、神秘的南洋風情,是許多華人祖先落地生根的地方。書名中的「子」與「婦」,更是勾勒齣瞭一種親密卻又可能帶有距離的關係。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將「婆羅洲」這樣一個宏大的地理概念,與「拉子婦」這樣一個更具體的、充滿生活氣息的稱謂結閤起來。這是否是一段關於跨越種族、文化的愛情故事?又或者,是一群人在異鄉尋找歸屬感、建立傢庭的歷程?我預期,這本書或許會透過細膩的筆觸,描繪齣在特定歷史時空背景下,人物的真實情感與生命軌跡,讓我們能夠窺見那段被歷史洪流所淹沒卻又充滿生命力的故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