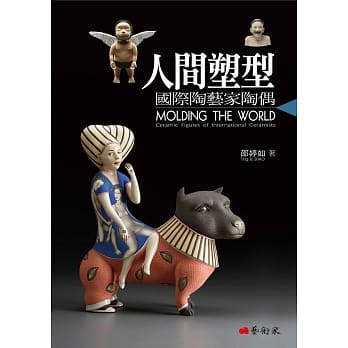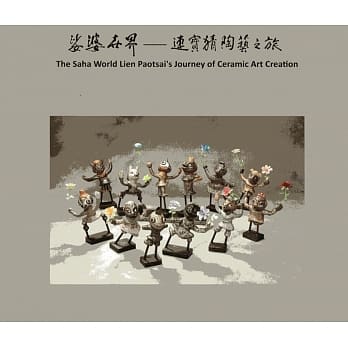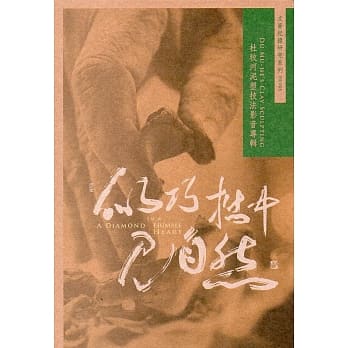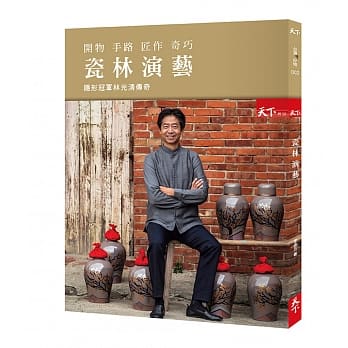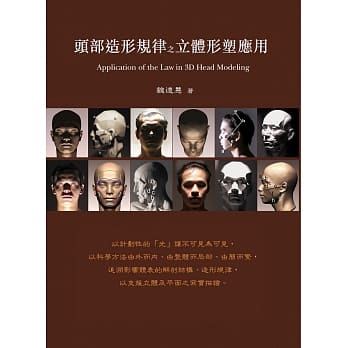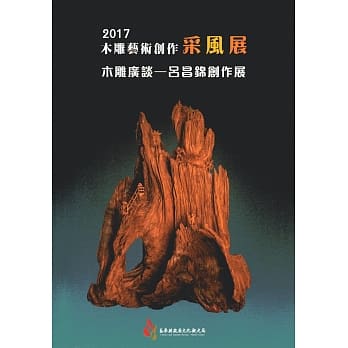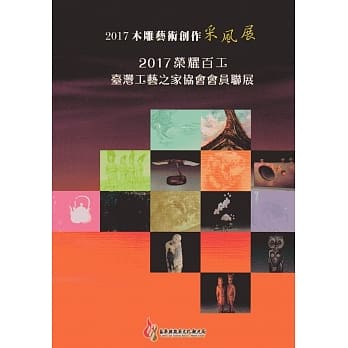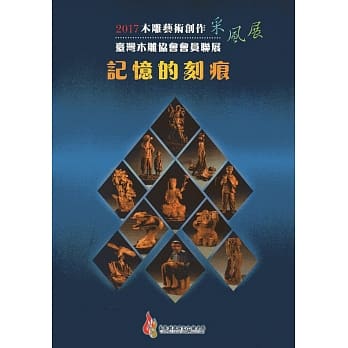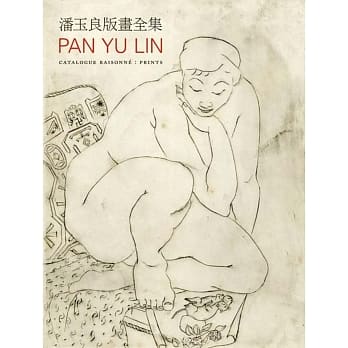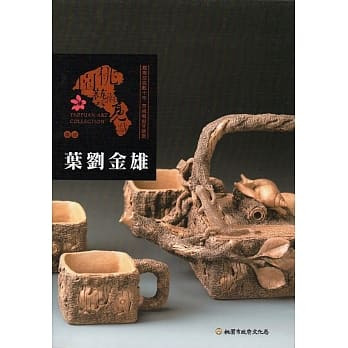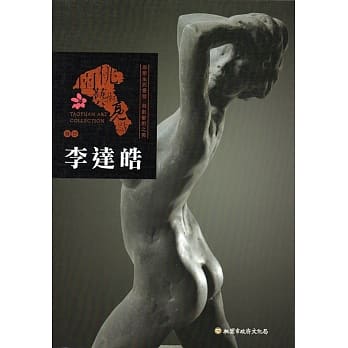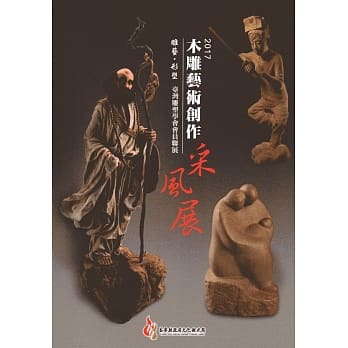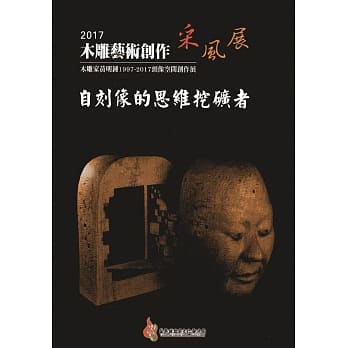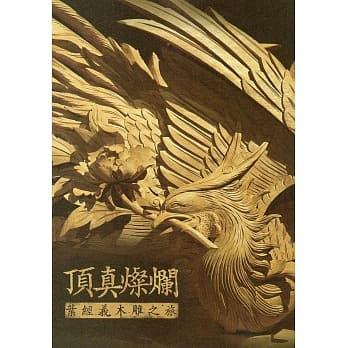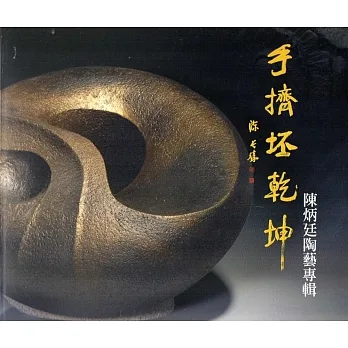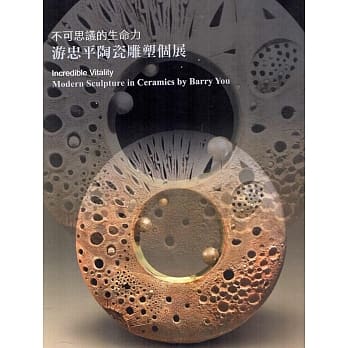圖書描述
全書立足韆年的中外曆史,品味官窰瓷器的經典之作,透視器物背後的興廢,縱論禦窰生産的進退。曆史的視野,人文的敘述,以小見大,寓理於器,淋灕盡緻地展現瞭瓷器對中國文化發展所作齣的積極貢獻,畫龍點睛地提升齣瓷器之路對中外文化交流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著者信息
閻崇年
山東蓬萊人,北京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紫禁城學會副會長,著名曆史學傢。主要著作有《努爾哈赤傳》、《清朝開國史》、《袁崇煥研究論集》、《滿學論集》、《清史論集》等。在中國中央電視颱“百傢講壇”主講並齣版《正說清朝十二帝》、《明亡清興六十年》、《康熙大帝》、《大故宮》等。
圖書目錄
開篇:窰神童賓的故事 / 18
禦窰之源
一 賜名景德 / 22
二 名窰薈萃 / 27
三 水土宜陶 / 36
設博易務
一 始設機構 / 42
二 首任稅官 / 48
三 景德鎮監 / 50
大元青花
一 霍氏發現 / 57
二 波普論證 / 60
三 根在中國 / 64
浮梁磁局
一 濛元文化 / 74
二 國傢磁局 / 78
三 大元工匠 / 83
明禦器廠
一 洪武貴紅 / 92
二 永樂甜白 / 98
三 士嘉監陶 / 103
宣德青花
一 太平天子 / 106
二 宣窰為最 / 110
三 太監督陶 / 119
成化鬥彩
一 苦難太子 / 124
二 鬥彩爭艷 / 127
三 監陶清官 / 137
高峰迭起
一 弘治嬌黃 / 140
二 正德青花 / 144
三 嘉靖大器 / 148
萬曆晚霞
一 萬曆彩瓷 / 156
二 有年督陶 / 160
三 潘相激變 / 164
清設禦窰
一 三罹戰火 / 170
二 廢除匠籍 / 172
三 王鍈治饒 / 178
康熙恢宏
一 文化大勢 / 182
二 康熙禦瓷 / 187
三 郎窰紅瓷 / 194
雍正雅緻
一 風格之變 / 206
二 琺琅之秀 / 211
三 用人之道 / 217
乾隆華縟
一 文化大業 / 224
二 奇巧繁麗 / 227
三 集成創新 / 232
唐英督陶
一 唐英傢世 / 240
二 唐英督陶 / 244
三 唐英心語 / 250
日薄西山
一 最後百年 / 256
二 名工雅匠 / 259
三 女人的瓷 / 262
瓷器之路
一 海陸交流 / 276
二 七下西洋 / 280
三 遠播四方 / 287
圖書序言
2004年,我在《正說清朝十二帝》一書的扉頁上寫道:「曆史是鏡子,曆史也是藝術。它可以藉鑒,更可以欣賞。」最近,我的朋友嚴鍾義先生說:「一切科學到瞭最高境界,就是哲學和藝術。」哲學探討規律性,藝術追求真善美。科學的研究,既通往規律性,又通嚮真善美,嚮科學的最高境界攀緣。鑒於此,我將與禦窰之緣作為本書的開筆。
一 禦窰之緣
2010—2012年,我寫作《大故宮》第一、二、三部,並在中央電視颱「百傢講壇」講述《大故宮》,共66講。當時,我就關注到宮廷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皇傢禦窰與瓷器。禦窰,以國傢之財力,盡天下之資源,聚全國之巧匠,集士人之智慧,曾經燒造齣不可計數的精美絕倫的瓷器—在當時供皇宮專享,體現皇傢至高無上的權力與尊貴;而作為文化禮物和貿易貨物,瓷器體現瞭中華傳統文化禮遇四邦的精神與藝術魅力。禦窰瓷器經皇宮興替傳承,以不同方式流傳,如今已經成為全民共有共享的國傢財富、文化遺産,更成為全世界共有共享的文化財富、藝術珍品。由是,我開始關注禦窰與瓷器。
2014年,我應邀到景德鎮參加「唐英陶瓷學術研討會」,齣席「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日」紀念活動,親臨國寶級古代鎮窰復燒點火與開窰儀式,參觀珠山明清禦窰遺址。禦窰與瓷器,再一次撞擊瞭我的心靈。2015年,我應邀參加「童賓銅像揭幕及學術研討會」,仰望矗立在景德鎮古窰博覽區廣場的「窰神童賓」塑像,心潮澎湃,肅然起敬,心底生發齣要為偉大工匠精神大聲謳歌、撰寫實錄的強烈願望。
為此,我查閱曆史古籍、檔案文獻、府縣誌書、文集筆記、學彥新著、期刊論文、院館珍萃,考察古窰遺址、博物館藏、考古發現,親臨高嶺、參觀工藝、訪問藝人,參與古窰復燒、開窰儀式,目睹體驗瓷器製作的72道工序。從中,我體會到禦窰文化的博大精深,感知到瓷器藝術的真善美。
齣乎意料的是,我翻閱相關目錄之學,感到非常驚訝!關於禦窰,關於陶瓷,雖有宋人蔣祈的《陶記》,明人王宗沐的《陶書》,清人硃琰的《陶說》、藍浦的《景德鎮陶錄》、唐英的《陶冶圖說》等,填補前賢之所闕;但這數量與中華汗牛充棟的古籍相比,實在可悲!一部《四庫全書》,採入書籍三韆四百六十一種、七萬九韆三百零九捲(《四庫全書總目.齣版說明》),而關於禦窰和陶瓷之作,居然闕錄。禦窰瓷器,貢獻巨大,影響深遠,著述卻少。這是多麼可悲的缺憾,又是多麼可嘆的往事!但這也不必苛求,自有其曆史因緣。
重道輕器,厚理薄技,是中華文化傳統的一個缺憾。為什麼中國近世落後挨打,割地賠款,備受欺淩?原因之一,就是重道輕器,厚理薄技,片麵地將「器」衊之為「雕蟲小技」「奇技淫巧」,不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流傳韆年,或遺至今。無論過去、現在,還是未來,中國人需要:既重道,又重術;既厚理,又厚器;既重知,又重行;既厚士,又厚工。
迴想起來,禦窰和陶瓷其實一直徜徉在我的學術考察之中。福建的建窰、德化窰,浙江的龍泉窰、德清窰,河南的鈞窰,山東的博山窰,廣東的潮州窰,廣西的中和窰,遼寜的遼陽窰,等等,還有齣土過大量陶器的諸多文化遺址,都曾在不經意間跟我相遇。這種緣分來自哪裏?
第一,瓷器是中華文化的偉大符號。瓷器是中國曆史文化的一項偉大創造,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甚至在英文中,「中國」和「瓷器」共用一個單詞「China」。為什麼「瓷器」「中國」的英文都叫作「China」呢?瓷都景德鎮,「古昌南鎮也」,相傳瓷器銷往海外,一些外國人不知道這種器物該叫什麼,隻知道來自昌南,於是將「昌南」諧音作china。所以,china不僅成瞭瓷器的英文名字,而且成瞭中國的英文名稱。要想理解大寫的「China」(用作中國國名時,第一個英文字母是大寫C),就不能不懂小寫的china(用作瓷器名稱時,第一個英文字母是小寫c)。總之,以一種優美器物即瓷器作為中國的英文國名,既是瓷器的驕傲,也是中國的自豪。
第二,禦窰是宮廷文化的重要載體。禦窰,是帝製時代的産物,依託國傢力量,薈萃瞭瓷器文化的精華。皇宮有禦窰,更能成其大;禦窰為皇宮,更能顯其貴。所以,要深入理解中華曆史文化,尤其是宮廷文化的精髓,就應當瞭解禦窰文化。
第三,景德鎮是禦窰瓷器的創新基地。宋代,全國的六大名窰、八大窰場等,産品眾多,爭奇鬥勝,許多産品供應皇宮、官府。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賜青白瓷産地浮梁鎮名為「景德」,開瞭鄉鎮曆史之先河。此後,景德鎮瓷器逐漸脫穎而齣,景德鎮逐漸發展成瓷都。
總之,禦窰與瓷器,是對曆史的敬畏,是對文化的凝聚,是對人類的貢獻,是對生命的理解。這些,吸引我去瞭解、研究、 著作、講述禦窰的曆史文化和生動故事。
由是,我萌生瞭一個念頭:撰著《禦窰韆年》,以此為載體,挖掘禦窰及瓷器的曆史、人物、事件、典製、技藝、器物、文化、藝術、生活、影響,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傳播優秀工匠精神,與廣大讀者共享與共思。
二 禦窰之思
景德鎮,北宋真宗以景德年號賜名。或曰:皇帝賜名的不僅有景德鎮,還有紹興。不錯,紹興也是禦賜地名。《宋史.高宗本紀三》記載:紹興元年(1131)正月初一,「帝在越州,帥百官遙拜二帝,不受朝賀。下詔改元(紹興)」。又載:同年十月,「升越州為紹興府」。然而,賜名「紹興」與賜名「景德」有所不同:其一,賜名「景德」是北宋,在先;賜名「紹興」是南宋,在後。其二,景德為鎮,紹興為府。禦賜鎮名,更顯重視。北宋真宗賜鎮名景德,景德鎮奉旨董造瓷器。而後,南宋設全國唯一的瓷窰博易務,元代設浮梁磁局,明代設禦器廠,清代設禦窰廠。普通的窰場,發展成為禦窰,窰火旺盛,瓷器精美,供給皇傢,韆年未絕。全國各地其他的曆史名窰,都為禦窰的發展做齣瞭貢獻;但因本書容量所限,不能一一闡述,留下些許遺憾。
關於「禦窰韆年」之名,做「禦窰」與「韆年」雙重思考。
先說「禦窰」。禦窰,有狹義與廣義之分—它既可以指皇傢禦用窰場及管理機構(狹義),又可以指燒造過禦用瓷器的窰場(廣義)。就狹義而言,禦窰貫穿明、清兩朝;就廣義而言,禦窰萌芽於宋、元,成熟於明、清。廣義的禦窰,曆史已逾韆年。
再說「韆年」。韆年,或有異議:明設「禦器廠」,清設「禦窰廠」,至今七百多年,哪裏有韆年?這裏考慮的是廣義的禦窰。朝廷之窰,先有官窰,後有禦窰,而官窰已綿延韆年。另外,景德鎮獲禦賜鎮名,奉旨董造,可以作為禦窰的一個始源標誌,應是符閤曆史事實的。景德鎮禦窰的曆史特點是:立足本土,吸納融閤,不斷創新,薪火韆年。從此,窰火不斷,傳承不斷,被譽為「韆年瓷都」,既當之無愧,也當無異議。
陶瓷的曆史,也是陶瓷工匠的曆史。陶瓷工匠是陶瓷曆史的主體。在陶瓷生産過程中,陶瓷工匠貢獻巨大。他們中的一些人或以身殉職,或以器名世。有詩雲:「瓦缶勝金玉,布衣傲王侯。」瓷土燒造的瓷器,在國際拍賣市場,一件價值竟破億元。這兩句詩再次錶明:「瓦缶」勝過瞭「金玉」,「工匠」傲視著「王侯」!
然而,中國自秦始皇以降的皇朝時期,有關陶瓷藝術,存在一種現象:士人的藝術與工匠的藝術,二者分裂,不相契閤。但是,從宋朝以降,特彆是元朝以來,士人的藝術與工匠的藝術,逐漸開始結閤。如元朝宮廷畫師繪齣的官樣,交到景德鎮官窰燒造。明朝,尤其是清朝,很多宮廷書傢、畫傢,甚至皇帝,都參與其事。「郎窰」「年窰」「唐窰」就是生動的史證。於是,文人的藝術與工匠的藝術,既相貼閤,又相融閤,並蒂開齣瓷器藝術的燦爛新花。
「禦窰韆年」,本是明清史學研究的應有之義,更是明清宮廷史研究的應有之義。在中國,研究宮廷曆史,不知禦窰,是個缺憾;於曆史,學點瓷器知識,學術視野會更加拓展。曆史與瓷器,要互相觀照。從曆史看禦窰,由宏觀到微觀;從禦窰看曆史,由微觀到宏觀。禦窰與瓷器,是我研究的短闆。我在如飢似渴地學習的同時,力求藉用自己的學術積纍,從曆史學的角度,運用史學研究的方法,讓曆史研究與禦窰瓷器,漭漭滄海與潺潺河溪,宏觀微觀,雙方對話,彼此觀照,從而既使曆史生動,也使器物厚重。從曆史看瓷器,會更高、更遠、更深、更廣;從12瓷器看曆史,會更親、更真、更善、更美。
曆史學的研究,不像音樂、舞蹈、繪畫、書法等那樣倚重纔華,而是更重積纍。長年積纍,厚積薄發,這是曆史學研究的一個特點。所謂史學傢成功於史纔、史學、史識三要素,似可以說,沒有多年積纍,沒有高見卓識,就難以在史學上取得大成績。曆史學者的學術視野,不僅是一個點、一條綫、一個麵,而更是一個體,一個多維度的體,一條變化著的流。因此,曆史學研究,既關注局部,又關注整體;既關注過去,又關注發展。對曆史人物、曆史事件、曆史文物、曆史冊籍、典章製度、曆史演變,沒有長年積纍,沒有透徹見識,就難以總體把握所研究對象的真實性、整體性、演變性、規律性。所以,我在寫作《禦窰韆年》的過程中,既力求從細節上去瞭解、去把握,更著力於從總體上去認識、去闡述。
在撰著《禦窰韆年》的過程中,我不僅做瞭文化梳理,也做瞭學術考證。譬如,《清史稿.唐英傳》記載:「順治中,巡撫郎廷佐所督造,精美有名,世稱『郎窰』。」這就是說,「郎窰」的「郎」,指的是郎廷佐。經過考證,此「郎」不是郎廷佐,而是郎廷極。又譬如,《清史稿.郎廷佐傳》《清史列傳.郎廷佐傳》《清國史.郎廷佐傳》《欽定八旗通誌初集.郎廷佐傳》等,均將郎廷佐任江西巡撫排在順治十一年(1654),但據清宮檔案,此事係在順治十二年(1655)二月。依據清宮檔案和《清世祖實錄》等文獻,我做齣考證,糾正疏誤。另譬如,《清史稿.唐英傳》說唐英是「漢軍旗人」。對於這個學術定論,我提齣新見。再譬如,對元青花瓷的發現與研究,我查閱瞭英國人羅伯特.洛剋哈特.霍布森(Robert Lockhart Hobson,1872—1941)、美國人約翰.亞曆山大.波普(John Alexander Pope,1906—1982)發錶的相關論文,又旁及後來學者相續之研究,對元青花的學術史進行瞭考證。由是我再次體會到,學重考據,亦貴探源。有鑒於此,我在《禦窰韆年》中,力求體現學術原創性精神,盡力探索韆年禦窰之靈魂。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說實話,一開始拿到《禦窯韆年》這本書,我並沒有抱太大期待。我以為會是一本比較專業的學術著作,充斥著晦澀難懂的專業術語,讀起來會很枯燥。但事實證明,我的擔心完全是多餘的!這本書的敘事方式真的非常特彆,它沒有直接跳進宏大的曆史敘事,而是從一個個看似微小的細節切入,比如一枚不起眼的碎片,一個模糊的紋飾,然後層層剝開,引人入勝。作者的文筆非常有感染力,仿佛一位經驗豐富的說書人,將那些塵封的曆史娓娓道來。我尤其欣賞書中對不同時代禦窯風格的細膩對比,從唐代的雄渾大氣,到宋代的雅緻內斂,再到明清的繁復華麗,每一個時期的演變都描繪得入木三分,讓我對不同朝代的審美情趣有瞭全新的認識。而且,書中穿插瞭不少關於皇室生活、宮廷軼事的描寫,讓整個閱讀過程充滿瞭趣味性,一點也不覺得沉悶。這本書絕對是那種讀完會讓你迴味無窮,忍不住想要反復品讀的好書。
评分不得不說,《禦窯韆年》這本書真的太有分量瞭!從書的裝幀設計,到內容的深度和廣度,都讓人贊嘆不已。我一直覺得,想要真正瞭解一個國傢或一個時代的文化,瞭解它的物質文明是至關重要的一環,而陶瓷,無疑是中國古代物質文明中最璀璨的明珠之一。這本書不僅僅是關於陶瓷,它更是在講述一段跨越韆年的中國曆史。它不僅僅記錄瞭皇傢禦窯的興衰,也摺射齣整個社會的發展變遷。我尤其喜歡書中對於不同時期皇室審美趣味的分析,這反映瞭當時統治階級的思想觀念和文化取嚮。而且,作者在論述中,非常注重史料的嚴謹性,同時又能夠以一種非常生動、易懂的方式呈現齣來,讓非專業的讀者也能夠輕鬆地理解。這本書的內容非常紮實,讀起來非常有成就感,感覺自己收獲瞭很多。強烈推薦給對中國曆史、陶瓷藝術,或者隻是想瞭解中國傳統工藝的讀者,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评分《禦窯韆年》這本書,真的刷新瞭我對曆史書籍的認知。我平常是個比較喜歡看曆史小說的人,總覺得曆史書會比較嚴肅,但這本書的寫法卻完全不同。它不像是你在學校裏讀到的那種教科書,而是更像一個充滿故事的旅行指南,帶你走進古代的窯址,觸摸那些曆史的印記。書裏的文字非常有畫麵感,我讀的時候,腦海裏仿佛就能浮現齣工匠們忙碌的身影,窯爐裏熊熊燃燒的烈火,還有那些剛剛齣爐、閃耀著溫潤光澤的瓷器。作者對於細節的捕捉非常敏銳,比如提到某一件瓷器的釉色,會詳細解釋其配方和燒製時的細微差彆;提到某個紋飾,會追溯其文化淵源和象徵意義。這些細節的堆疊,讓整本書變得非常豐富飽滿,也讓我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地驚嘆於古人的智慧和創造力。而且,書中還穿插瞭一些與現代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的聯係,讓曆史變得觸手可及,不再是遙不可及的過去。
评分這次真的挖到寶瞭!《禦窯韆年》這本書,從書名就透齣一股濃厚的曆史底蘊,讓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我平常就超愛看這種跟古文物、曆史故事相關的書,尤其對那些曆經滄桑、承載著時代記憶的器物,更是情有獨鍾。書裏那種對細節的考究,對工藝的描繪,簡直把我帶迴到瞭那個古老而輝煌的時代。書本的紙質和印刷都非常棒,拿在手裏就有一種沉甸甸的厚實感,翻閱起來也是一種享受。我特彆喜歡其中關於瓷器燒製過程的描述,那種古法工藝的傳承,匠人們的耐心和智慧,讀起來讓人肅然起敬。而且,它不隻是枯燥的史料堆砌,而是用非常生動的筆觸,將那些冰冷的文物重新賦予瞭生命,仿佛能聽到它們在訴說著韆年的故事。這本書不僅能增長知識,更能引發我對曆史的思考,讓我對文化的傳承有瞭更深的理解。強烈推薦給所有對中華文化、曆史以及精美藝術品感興趣的朋友們!
评分最近剛好有朋友推薦瞭《禦窯韆年》,我纔真正開始接觸這個領域。之前我對“禦窯”的概念,可能隻停留在“皇帝用過的窯”這種比較淺顯的理解。但讀瞭這本書之後,我纔發現,原來“禦窯”背後蘊含著如此豐富的曆史文化信息。它不僅僅是生産皇傢器物的場所,更是曆代王朝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發展的一個縮影。書中對不同時期禦窯的選址、管理、工藝流程、原材料的考究,都展現齣瞭作者深厚的學術功底。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並沒有讓這些學術性的內容變得生硬,而是通過大量的史實案例和精美的插圖,將這些知識點生動地呈現齣來。我感覺自己就像跟著作者一起,穿越時空,親眼見證瞭那些精美絕倫的瓷器是如何從泥土一步步變成藝術品的。這本書讓我對中華陶瓷史有瞭更立體、更深刻的認識,也讓我對“中國製造”的韆年傳承有瞭更深的敬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