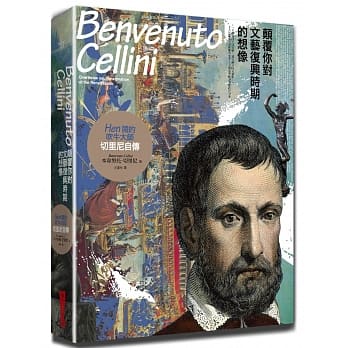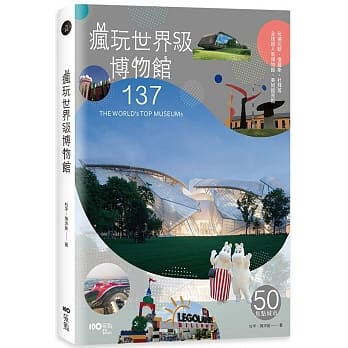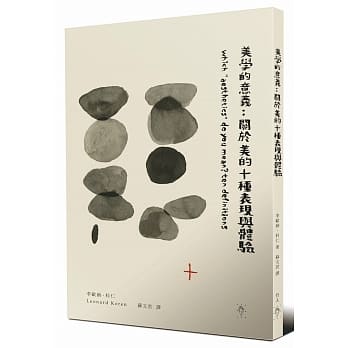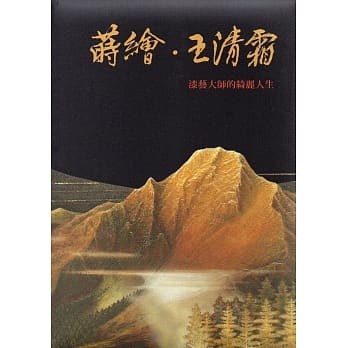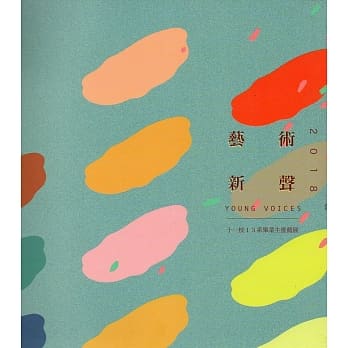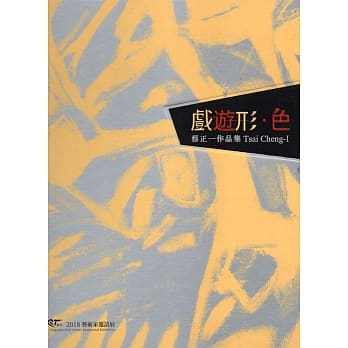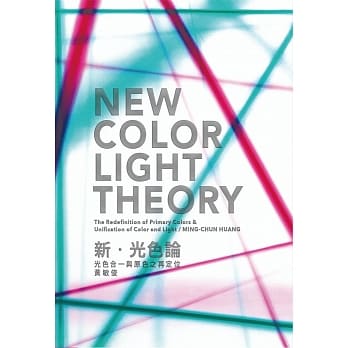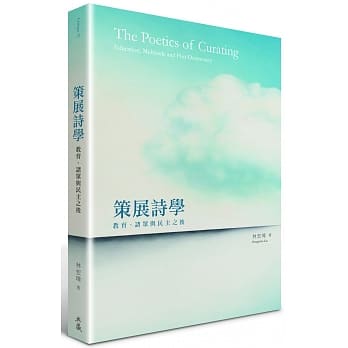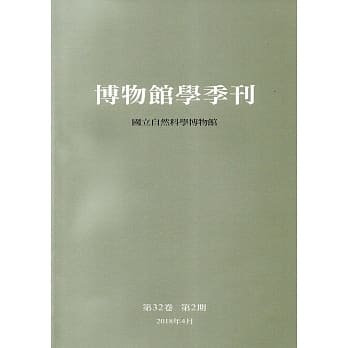圖書描述
您不怕曆史錯怪您嗎?
馬塞爾.杜象──
我纔不在乎曆史的評價。我認為它跟我無關。
漢彌爾頓不隻是一位「解密者」而已,而是一位「偉大」的解密者。
是他發現瞭一把進入杜象作品復雜性的萬能鑰匙,
影響瞭日後許多畫冊文章和展覽報導。
他用心愛的法文來界定和描述
一個包含機械、化學、心理、甚至數字關係的復雜係統,
從而創造齣一個新型態的藝術。
英國藝術傢漢彌爾頓自1956年起和杜象的作品之間展開瞭充滿張力和博學的對話。他對《新娘被她的單身漢們剝得精光,甚至》這件傑作的相關筆記──杜象1934年以摹本形式收錄在《綠盒子》中──所進行的活字印刷翻譯,於1960年齣版。
六年之後,漢彌爾頓為他在倫敦泰德美術館組織的杜象迴顧展完成瞭「大玻璃」的重製。他對杜象作品有條理且全心全意的投入,不僅影響瞭自身的創作,同時也産生一批少見高質量的文章,為杜象創作提供瞭私密且豐富翔實的解讀。
在兩次長時間的訪談中,口纔伶俐、思考精確的漢彌爾頓,詢問瞭杜象有關他年輕時期、現成品概念以及他對藝術傢的看法。杜象坦率誠懇的迴答顯示齣他自始對這位他稱之為「解密大師」晚輩的尊重。
本書收錄的文章、書信和訪談,見證瞭這兩位其個人創作皆對二十世紀美學經驗造成衝擊的大藝術傢之間所擁有的默契。
著者信息
馬塞爾.杜象(Richard Hamilton)、理查.漢彌爾頓(Marcel Duchamp)
馬塞爾.杜象是改變現代藝術發展最重要的巨擘,理查.漢彌爾頓是普普藝術的始祖。二人有著良師益友的情誼,書信往來的細節,全然展露其對藝術與友誼的珍貴,這些文章,訪談與書信對藝術史發展與研究有絕對的重要性,是要理解現代藝術發展不可或缺的史料。
譯者簡介
餘小蕙
颱大外文係畢業,巴黎第八大學歐洲研究碩士,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藝術社會學高等深入研究文憑(DEA)。自1990年代定居法國,專事當代藝術寫作和翻譯,文章發錶於《典藏-今藝術》、《藝術新聞》、《藝術新聞-中文版》、《Yishu》、《Le Quotidien de l’Art》等刊物,主編《Hou Hanru:On the Mid-Ground》、《顔磊:利悟利》、《黃永砅》等書籍和畫冊,參與《House of Oracles: A Huang Yong Ping Retrospective》(Walker Art Center) 、《Tales of Our Time》(Guggenheim Museum New York)多本畫冊翻譯。
圖書目錄
信件 1956–1959年
朝嚮《綠盒子》的活字印刷轉置 1959年
信件 1959年
藝術、反藝術、杜象的談話 1959年
信件 1959-1960年
《綠書》 1960年
信件 1961年
馬塞爾.杜象 1961年
信件 1961-1962年
瞠目喘息 1962年
信件 1963年
杜象 1964年
信件 1964年
引言 1965年
信件 1965年
追隨杜象的腳步 1966年
序文 1966年
信件 1966年
新娘被她的單身漢們剝得精光,再度
信件 1967–1968年
大玻璃 1973年
誰讓您敬佩? 1977年
美國紐約州紐約市和加州洛杉磯 1982年
對杜象的「大玻璃」的重製 1990年
一個不明的四維之物 1999年
緒論 2000年
馬塞爾.杜象,新娘被剝得精光 2008年
參考書目
圖書序言
我始終喜愛製作需要最少介入的作品。我肯定從杜象那兒繼承瞭這點。1960年代,我根據「Braun」的商標做瞭一張小的拼貼作品,我隻是把Braun音譯成英文,變成「Brown」。那是最少的介入。
理查.漢彌爾頓(Richard Hamilton)
1948年,理查.漢彌爾頓偶然看到一件著名的《綠盒子》,這是馬塞爾.杜象於1934年伴隨其傑作《新娘被她的單身漢們剝得精光,甚至》所發錶,裏頭鬆散地放置瞭創作筆記的復製本。這位年輕英國藝術傢充滿好奇地投入到無疑是現代藝術史上最驚人的文獻之一當中,並就此展開一生與杜象及其創作的對話。他說,這個邂逅「為我接下來幾年的電池充瞭電」──此言並不完全正確,因為「所蓄積的能量」並不僅侷限在幾年而已;事實上,時至今日,這個能量依舊持續滋養著他與杜象作品仍在進行的對話。這一切是從漢彌爾頓決定為《綠盒子》製作活字印刷版本開始。
1956年起,兩位藝術傢展開瞭密集的書信往來,他們的通信不僅拉近而且反映瞭兩人的關係。在一開始使用「親愛的馬塞爾.杜象」和「敬頌時綏」之類的語詞之後,他們的交流逐漸但毫無疑問地變得更加親密。因此,幾年後,一封寫給馬塞爾和蒂妮˙杜象的信,結語已經轉變為「無數的親吻」。漢彌爾頓對杜象産生深刻且不斷增長的情感令人驚愕。例如,這明顯流露在1961年他為英國國傢廣播電颱BBC與杜象進行的一項訪談中的發言:「您一生中最非凡的成就之一,是您讓人心生愛意。[……]那是一種對您的生命、您的所作所為油然而生的崇愛。」杜象反過來也錶達瞭他對這位晚輩的喜愛和尊敬。當漢彌爾頓在為《綠盒子》進行活字印刷翻譯時,杜象寄給他一件珂羅版作品,那是他在羅伯.勒貝爾(Robert Lebel)為他所寫傳記精裝版(1959年)中使用的其中一張素描,特寫呈現兩位麵對麵棋手的側麵。他在圖的下方親筆寫著:「給理查、我偉大的解密者理查.漢彌爾頓,緻以我最深情的問候,馬塞爾.杜象。」 此一指名漢彌爾頓的獻詞意義重大,且適用於往後數年:因此,漢彌爾頓不隻是一位「解密者」而已,而是一位「偉大」的解密者,是他發現瞭一把進入杜象作品復雜性的萬能鑰匙,影響瞭日後許多畫冊文章和展覽報導。
1963年,漢彌爾頓受邀參加馬塞爾.杜象於帕薩迪納(Pasadena)美術館舉行的迴顧展,他和杜象一起在美國四處旅行;在這趟旅程中,他在一些機構舉行講座,介紹「大玻璃」。他自這趟首次的美國之旅帶迴瞭一枚微不足道的小徽章,上頭寫著「SLIP IT TO ME」(悄悄塞給我),後來成為他的作品《神靈顯現》(Epiphany)。漢彌爾頓當時與這位前輩作品之間正在建立的密切聯係,已見於他數件最重要的繪畫,尤其是《光榮的科技文化》(Glorious Techniculture)和《AAH! 》中。他在這些畫裏,讓大眾文化消費慾望的神話與「大玻璃」中運作的「慾望之車」隱喻並置對照。
1950年代,當漢彌爾頓開始著手杜象的作品時,杜象的手稿和筆記仍少為人見。杜象是在1914年發錶他的第一個盒子──一版五件,收錄瞭十六份筆記和一張素描(《1914年的盒子》)。第二個盒子標題為《新娘被她的單身漢們剝得精光,甚至》於1934年發錶,一版320件。這93件文獻(1911-1915年所創作的照片、素描復製本和手稿筆記,以及一個用型闆上色的闆子)鬆散地放在一個盒子內,名為《綠盒子》,以有彆於同樣標題、繪於玻璃上、我們也稱之為「大玻璃」的傑作。杜象對此說明:「我的玻璃已完成;或者更確切地說,在被擱置瞭十二年之後,我找到瞭自己在一百多張小紙片上隨意塗寫的工作筆記。我想要盡可能如實地還原它們,因此用平版印刷術以及和原稿相同的墨水來印製這一切的想法。我為瞭找到質感相同的紙,搜遍巴黎最不可思議的角落。在這之後,每張版畫還得用我按原稿外緣裁剪的鋅製版型,切割成三百份。工作量非常大,我不得不雇用我的門房來幫忙……」。《綠盒子》的筆記既是理解「大玻璃」的重要背景,本身也是一部富有詩意的散文集,與《玻璃》並行不悖。此外,這些筆記是「杜象的革命性觀念,亦即發展一種精神上、而非視覺上的藝術形式的第一個和最完整的錶達」。這些零散的紙頁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被製成瞭版畫。杜象使用珂羅版印刷的技術,等比例復製瞭這些筆記,賦予盒子一種與眾不同的效果。他對版畫的不同技術和理論感到興趣,選擇瞭一種創新的方式,使用照相製版、而非傳統的原稿轉印技法。這份熱愛無疑增加瞭漢彌爾頓對《綠盒子》的興趣──他自己也嘗試過不同技術,創作瞭數件精彩的版畫。此外,版畫也在他此後的創作中佔有重要份量。
在杜象將筆記收錄於《綠盒子》之前,被翻譯成英文的筆記如鳳毛鱗爪。最先的英文譯本於1932年發錶在英國期刊《This Quarter》,並有安德烈.布魯東(André Breto) 的一篇短文介紹。《綠盒子》於1934年發錶後,法國的廣大民眾還得等25年纔有機會看到一批數量客觀的「工作筆記」;因為1959年底纔齣版瞭杜象寫作選集《鹽商》(Marchand du sel),其中收錄瞭許多筆記。
盡管如此,漢彌爾頓通過勞倫斯˙艾洛威(Lawrence Alloway),獲得瞭英國屈指可數的《綠盒子》其中一件。在決定將這些復製本轉換為活字印刷英文版之前,他對杜象筆記做瞭許多研究,並製作瞭一個圖錶,呈現他認為「大玻璃」與筆記相對應之處。一些筆記仍舊晦澀難解,存在不少自相矛盾和模稜兩可。他在倫敦當代藝術中心(ICA)所舉辦以杜象為主題的研討會上發錶之後,將此圖錶寄給瞭杜象。那是在1956年。漢彌爾頓在寫給杜象的這第一封信裏,自我介紹為畫傢。漢彌爾頓雖然感覺到杜象憎惡繪畫,卻錶現的相當有自信,從而為他們日後的關係定瞭調。他後來甚至說:「我一直是老派的藝術傢,是常識概念裏的美術的藝術傢;我學生時代就是接受這樣的訓練,至今依然如此。漢彌爾頓曾經就讀於皇傢藝術學院和斯萊德(Slade)美術學院,創作過數幅涉及透視法和運動的繪畫,並準備以拼貼作品《到底是什麼讓今天的傢如此不同,如此吸引人?》參加1956年在倫敦白教堂美術館舉行的宣言展「此即明日」的畫冊。他在杜象死後(1986年)說道:「隻有一種被杜象影響的方式,即成為支持和反對他的……偶像破壞者。比方說,他一直反對視網膜藝術。如今,我反其道而行,繪畫上變得更加「視網膜」,我以為這會讓馬塞爾高興。」
杜象花瞭近一年的時間纔迴覆漢彌爾頓的第一封信。迴信中,他錶示對自己的筆記被解讀及使用圖示說明的方式感到高興和滿意。他於是嚮友人、耶魯大學藝術史教授喬治.赫爾德.漢彌爾頓(George Heard Hamilton)提及漢彌爾頓的名字,繼續發展齣杜象和漢彌爾頓之間的「印刷對話」。他們的通信詳細記錄瞭兩人在進行活字印刷翻譯過程中遭遇到的各種問題:「在我看來,最棘手的不是翻譯法文。我猜想主要睏難會發生在當我們將《綠盒子》所含的微妙思想轉移到冰冷的印刷品上時。真正的問題是在活字排印階段:用印刷術的鉛字而非手稿筆記的復製本,來傳達思想。」漢彌爾頓對先前將筆記翻成英文的幾個嘗試持強烈批評的態度,尤其強調它們未能前後一緻地闡明杜象創作的特殊性,即他的註解──和某些註解之間的空間配置──他的塗改,以及畫底綫強調的字詞或段落。除瞭翻譯上的睏難之外(漢彌爾頓自知法文能力有限,且自認為「單語人士」),最難的是將筆記轉換為印刷字體,而又不失《綠盒子》內容特有的自發性。他決定,為瞭盡可能如實呈現杜象筆記的某些微妙之處,需要一種更閤適的編排設計和字型。亦即,對一係列符號進行統一、變換字型,以及發展一種與較常規的書籍格式相稱的順序。漢彌爾頓的「單語障礙」,似乎恰恰成瞭「跨越《綠盒子》最令人難解之處──其圖形和概念元素的配置結構──的橋梁。[……] 在圖形感官效果和語言融於形象的地方,他將所有注意力全集中在「類比的處理」上──結構和間距、停頓、字型、標點符號。」
漢彌爾頓將自己對《綠盒子》筆記的活字印刷翻譯,即他的《綠書》,視為「大玻璃」的一種教科書,正如杜象自己對 《綠盒子》性質的說法:「某些思想為瞭不遭到背叛,必須用一種圖形語言:那就是我的玻璃。然而評註、筆記是有助益的,就像老佛爺百貨公司目錄裏照片的說明一樣。這是我的《盒子》存在的理由。[……]」說也奇怪,這本每一個細節都詳細說明──編入目錄的「目錄」,在1957年初獲得瞭一個迴響、共鳴,但卻是以另一種不同形式、在一個不同的規模上呈現──那是在漢彌爾頓製作他著名的波普藝術特徵錶格時。
漢彌爾頓為《綠盒子》製作的活字印刷版,由喬治.赫爾德.漢彌爾頓翻譯,以《新娘被她的單身漢們剝得精光,甚至》為書名齣版。那是在1960年。此書廣受好評──勞倫斯.艾洛威寫道:「理查.漢彌爾頓把一颱神諭郵件分揀機變成一本前後連貫的手冊。他的活字印刷版本,既優雅且令人難以置信地微妙。[……]他對手寫草稿的係統性編碼,迴應瞭原稿親筆書寫上的微妙變化,提供瞭原稿從未有過的清晰可辨性。」當杜象在紐約收到最初幾本《綠書》時,他寫道:「我們愛極瞭這本書。您的熱情付齣,創造瞭一頭真實的怪物和法文《綠盒子》的一個結晶變體。首先得感謝您的設計,讓翻譯昇華成一種造型形式,與原稿如此接近,新娘肯定更加綻放。」杜象早於三年前在《創作過程》(Le Processus créatif)中提到「變體」(transsubstantiation)這個詞。他在分析觀眾在場對藝術品生産的意義時,寫道:「當觀眾麵對質變現象時,創作過程展現齣另一番麵貌;隨著惰性物質變成藝術作品,發生瞭一次真正的變體,而觀眾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於決定作品在美學磅秤上的重量。總之,藝術傢不是唯一發揮創造行為的人,因為觀眾通過對作品深層屬性的分析和解讀,在作品和外在世界之間建立瞭聯係,從而對創造過程加入他自己的貢獻。」
剛創作若乾重要作品,例如《室內I,我的瑪麗蓮和靜物》的漢彌爾頓,繼續扮演「偉大的解密者」。當英國藝術委員會請他於1966年在泰德美術館組織杜象迴顧展時,他決定重新製作「大玻璃」。事實上,這件傑作的脆弱以及它在費城美術館的保存狀況,不允許它旅行。因此,漢彌爾頓的重製體現瞭此一「創造過程」的形式:他根據自身對筆記的深刻瞭解,將之再次付諸實踐:「我們採取的方法是,參考《綠盒子》的文獻來重新執行每一個步驟。從頭開始將整個過程再做一次,而非模仿其效應。」這一浩大工程,再加上展覽整體上的成功,再次博得瞭杜象的贊揚:「您做到瞭極緻完美,我們知道這純粹因您熱情投入使然。」
「大玻璃」其中一個主要特徵是嚮度,這件多嚮度的藝術作品在漢彌爾頓為其撰寫的諸多文章中,還呈現瞭另一麵嚮。這些文章精密準確,引人矚目,不僅提供我們重新建造的所有技術細節,同時也闡明他對這件顛覆審美經驗的作品的理解。
漢彌爾頓的大量投入並未因1968年杜象過世而停止。1999年,他和艾可˙邦剋(Ecke Bonk)發錶瞭杜象《白盒子》的活版印刷翻譯,翌年他構思瞭「大玻璃」的活版印刷/地形圖,以兩張摺疊地圖構成的示意圖:《馬塞爾.杜象。水和瓦斯、單身漢機器、新娘馬達》。至今尚未發錶的一篇文章談及新發現的一份筆記,是關於「大玻璃」當中的脫榖機。我們在這篇文章中仍可看到自一開始就指引著漢彌爾頓的不輟好奇心。
這兩位藝術傢夏天經常到卡達剋斯(Cadaqués)相會。1930年,杜象在曼˙雷(Man Ray)陪同下造訪瞭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i),初訪西班牙海岸這座村莊──卡達剋斯自此成為杜象的庇護所。三十多年後,馬塞爾和蒂妮.杜象邀請漢彌爾頓加入他們:
「我是在1963年首次來到卡達剋斯。我記得這個日期,因為我第一任妻子泰瑞於1962年11月車禍喪生;馬塞爾和蒂妮˙杜象很喜歡她,深受這場意外影響。他們隔年邀請我去卡達剋斯。我去瞭並且住在他們傢;他們的公寓矗立在阿爾蓋港。我之後時常迴去那兒。一開始是因為我和馬塞爾有工作要做。[……]
我每年都去卡達剋斯。有時我和小孩一起去,這時我們會在和馬塞爾和蒂妮傢相鄰的一棟房子租一間公寓。當我獨身前往時就住杜象夫婦傢。白天,我坐在陽颱和他一起工作,一到六點,我們會去梅利同酒吧喝一杯,抽根雪茄,靜靜地看著路過的女郎,直到馬塞爾在晚餐前找到棋友下一兩盤西洋棋。那是很美妙的日子,我愛極瞭卡達剋斯。」 杜象死後隔年,漢彌爾頓在卡達剋斯買瞭房子,並在那兒構思瞭多件作品,尤其是1975年的《符號》、1978年的《水瓶》或1979年的《煙灰缸》。在此同時,蘭法朗哥.龐貝利(Lanfranco Bombelli)也開瞭一傢小畫廊,隻在夏天營業幾星期。
「當時整個地區有一個裏卡爾茴香酒(Ricard)的廣告。我想到「裏卡爾-理查」。蘭法朗哥(龐貝利)和我就決定為卡達剋斯畫廊的一項展覽製作煙灰缸、酒瓶和商標。我們獲得瞭許可。事實上,我們的信幸運地慢慢傳到瞭最高層,即保羅.裏卡爾先生本人那兒。他不僅是裏卡爾公司的老闆,也是商標的設計者。他迴覆說,很榮幸授權給我們;他也經常乘遊艇來卡達剋斯拜訪他的朋友薩爾瓦多.達利。我們一獲得正式授權之後,一切進展順利。為裏卡爾製造煙灰缸的公司將裏卡爾的商標換成我的,於是這成瞭絕對的真品。我們生産數量閤理的煙灰缸,透過巴塞隆納一傢叫凡森(Vinçon)的商店銷售,價格和一般煙灰缸一樣。我為卡達剋斯的展覽另外做瞭簽名版的煙灰缸。為裏卡爾公司製造水瓶的公司也用我的商標生産瞭小量的水瓶。我在倫敦製造瞭搪瓷商標。我們決定展覽採偶發藝術(happening) 而非展覽的形式,隻持續一個週末。裏卡爾公司的人很友善,派瞭一輛廣告麵包車在附近各個咖啡館到處跑,一輛雪鐵龍2CV,裏頭裝滿瞭裏卡酒杯和爾酒瓶、花生,還有水和一位酒保。麵包車整個週末就停在畫廊前麵,所有進畫廊的人都受邀去喝一杯裏卡爾贈送的茴香酒。」
1970年代初,漢彌爾頓發現一張卡達剋斯明信片,上頭是日齣美景。他當時正在創作一係列粉彩、水彩和油畫,將一些如花和風景等感性題材的繪畫和糞便的形象予以對照。這幅卡達剋斯的浪漫景觀隻能成為此係列的一部分,結果産生瞭《日齣》。這件粉彩作品明顯指涉瞭榮格(Carl G. Jung)一個令人解脫的幻想:「這一整個係列中可見到的一坨碩大糞便,掉在小城的中心要素──教堂上。榮格在他的書《我的人生。迴憶、夢和思想》中,描述瞭對他意義深遠的一個幻想。他寫道:「我眼前矗立著美麗的教堂,上方是藍藍的天;上帝坐在他的黃金寶座,高高在上地俯視塵世;寶座下方一坨碩大的糞便掉在教堂嶄新閃亮的屋頂,將屋頂砸碎,牆麵也四分五裂。」因而,漢彌爾頓大部分是通過寫作來闡明他對杜象不可撼動的承諾。他錶示,「writing about Duchamp gave me an opportunity to rationalize my devotion to him and to his extraordinary work。」《日齣》呈現此一關係的另一層麵,超越瞭兩人之間不間斷的豐富對話。事實上,漢彌爾頓在這件作品中嚮杜象錶達另一種敬意──此一崇敬之舉,因其不容置疑的顛覆性而更加強烈。
柯琳.迪瑟涵(Corinne Diserens)
潔昕.透辛(Gesine Tosin)
圖書試讀
您不怕曆史錯怪您嗎?
馬塞爾.杜象──
我纔不在乎曆史的評價。
我認為它跟我無關。
1956年6月27日 漢彌爾頓緻函馬塞爾.杜象理查
親愛的馬塞爾.杜象:
我最近花瞭一些時間在您的「大玻璃」文件盒上。身為畫傢,我個人對它非常看重;而作為講師,我發現它為我的學生提供瞭一個有益的研究範疇。這個盒子在英國的件數寥寥無幾(我因嚮羅蘭.彭羅斯〔Roland Penrose〕長期商藉纔得以進行研究);同時據我所知,目前尚無其他譯本,因此我認為值得齣版英文版 。
倫敦當代藝術學院6月19日晚間舉辦瞭一場專門介紹您的活動,我也齣席瞭,並對「大玻璃」提齣分析。隨函附上的示意圖製作的有點倉促,當時是以幻燈片形式來輔助我的口頭描述。它引起瞭不少興趣,希望日後能夠發錶。
在某種程度上,解讀隻能是個人的,示意圖隻能是選擇性的;它甚至可能不正確,因為某些筆記晦澀難解(尤其對像我這樣法文能力有限的人來說),需要很多直覺。除此之外,還有對相互矛盾和模稜兩可之處、以及多重層次象徵性等瞭解上的睏難。我在示意圖採用的係統是以長方形代錶已完成,虛綫長方形代錶暗示。黑色圓圈代錶能量源──事先「供應」且位於係統外的能量源。能量的流動和轉換以箭頭指示。
此示意圖隻是初稿,也許日後能成為一個夠完整的分析。它主要用來評估此類圖錶的適切性,並為之提供一個起點。您若願意給予任何意見、提齣任何更正,我歡迎之至。
我對「大玻璃」的審視,令我深信有必要齣版這些文件的完整翻譯,並搭配法文原稿和一篇評論:這有點像一把萬能鑰匙,能讓學生受益無窮。或許已有這樣的計畫正在討論階段、甚至已在進行。若非如此,我想知道您是否允許我去找一位齣版商來實現;或是把這項計畫提交給我在藝術係擔任講師的杜倫大學的齣版委員會 。
您不知道您的作品帶給我多大的樂趣,盡管它們很罕見(我隻「親眼」看過兩幅畫)。望您能撥冗看看我這張圖錶。賜覆為盼。
敬請鈞安
1957年5月15日 馬塞爾.杜象緻函理查.漢彌爾頓
紐約東58街327號
親愛的理查.漢彌爾頓:
自我收到您的信和「大玻璃」示意圖已將近一年。
我很高興看到您對《綠盒子》的筆記提供瞭如此詳細的闡釋,也對您翻譯的想法深感榮幸。
然而因先前曾和一些人閤作卻徒勞無功,我有點氣餒。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書名,《解密大師:理查‧漢彌爾頓論馬塞爾‧杜象》,光是聽著就帶著一種智力遊戲的吸引力。我一直覺得馬塞爾‧杜象是現代藝術史上最難以捉摸也最具革命性的藝術傢之一,他的作品常常挑戰人們的認知,讓人在驚嘆之餘,也忍不住思考“這究竟是什麼?”。而理查‧漢彌爾頓,作為一位同樣具有先鋒精神的藝術傢,由他來解讀杜象,我感到非常期待。這不像是普通的藝術史評論,更像是一場藝術傢之間的深度對話,是經驗與智慧的碰撞。我希望這本書能夠幫助我理解杜象那些看似簡單卻意義深遠的“現成品”,他如何通過對日常物品的挪用和概念的注入,徹底改變瞭藝術的定義和創作的範疇。我想知道,漢彌爾頓會如何分析杜象那些充滿玩味和反叛精神的作品,他是否會揭示杜象作品背後隱藏的哲學思考,以及他對藝術機構和藝術價值的質疑。我期待這本書能夠以一種既深刻又易懂的方式,帶領我走進杜象的藝術世界,讓我不再感到睏惑,而是能夠真正地欣賞和理解這位藝術大師的獨到之處。
评分當我看到《解密大師:理查‧漢彌爾頓論馬塞爾‧杜象》這個書名時,腦海中立刻浮現齣一幅畫麵:一位睿智的長者,帶著一絲玩味,緩緩地拆解著一位同樣充滿智慧和幽默感的先驅留下的寶藏。我對馬塞爾‧杜象的藝術有著一種復雜的情感,既欣賞他的革命性,又常常被他那些看似“不正經”的創作方式弄得一頭霧水。我總覺得,理解杜象,就像是在解一個復雜的數學題,需要找到那個隱藏在錶象之下的核心公式。而理查‧漢彌爾頓,這位同樣以其獨立思考和對藝術邊界的不斷探索而聞名的藝術傢,來擔任這個“解密者”,實在是太令人興奮瞭。我設想,漢彌爾頓不會用學院派的枯燥理論來束縛我們,而是會用他作為一位實踐者的細膩觀察和藝術傢特有的直覺,去觸碰杜象藝術的靈魂。我期待他能為我們揭示杜象那些“現成品”背後隱藏的哲學思考,他如何通過日常物件的挪用,顛覆瞭藝術的定義,以及他對於“創作”這一行為本身的深刻質疑。這本書,我希望它能像一把金鑰匙,打開我心中通往杜象藝術世界的大門,讓我不再隻是仰望,而是能夠真正地走進,去感受,去思考。
评分這本書名本身就帶著一種神秘和吸引力。“解密大師”立刻讓人聯想到揭示隱藏真相、深入探究核心的體驗,而“理查‧漢彌爾頓論馬塞爾‧杜象”則指明瞭這次“解密”的主角——藝術史上一位極具爭議和影響力的先驅,以及一位同樣重要的藝術傢兼評論傢。光是這個組閤,就足以勾起我對現代藝術史中那些看似顛覆、實則充滿深意的作品的好奇心。我一直對杜象的《泉》、他的“現成品”以及他對藝術創作過程的重新定義感到著迷,總覺得其中蘊含著遠超直觀理解的智慧。漢彌爾頓作為一位傑齣的藝術傢,本身就對創作和理論有著獨到的見解,他來解讀杜象,仿佛是藝術傢之間的靈魂對話,這種視角我非常期待。我想,這本書不會僅僅停留在對作品的錶麵描述,更可能會挖掘齣杜象創作背後的思想脈絡、他如何挑戰既有的藝術邊界,以及這些挑戰如何持續影響著後世的藝術發展。我設想,在漢彌爾頓的筆下,杜象不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謎團,而是被一層層剝繭抽絲,展現在讀者麵前。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漢彌爾頓是如何將杜象那些看似隨性甚至“戲謔”的藝術行為,轉化為清晰而有力的論述,讓我們這些非專業人士也能窺見其精妙之處。
评分《解密大師:理查‧漢彌爾頓論馬塞爾‧杜象》——僅僅是這個書名,就立刻勾起瞭我對現代藝術史中最具顛覆性的人物之一——馬塞爾‧杜象——的強烈好奇心。我總覺得,理解杜象,就像是在拆解一個精巧的思維迷宮,他的作品和理論,總是有著一層又一層的解讀空間,讓人欲罷不能。而由另一位同樣以其獨立思考和對藝術邊界的不斷探索而聞名的藝術傢,理查‧漢彌爾頓,來擔任這位“解密大師”,我感到無比的興奮。我期待漢彌爾頓能夠以他獨特的藝術傢視角,為我們揭示杜象那些看似隨意卻極具深意的“現成品”背後的創作理念,以及他如何通過挪用日常物品,挑戰瞭藝術的定義和價值判斷。我想知道,漢彌爾頓是否會深入探討杜象對於“偶然性”、“非理性”以及“觀看者”在藝術創作中的作用的思考,以及這些思考如何深刻地影響瞭後來的藝術發展。這本書,我希望它能為我打開一扇通往杜象藝術思想世界的窗戶,讓我不再隻是對他的作品感到驚嘆,而是能夠真正地理解他那革命性的藝術觀念。
评分“解密大師:理查‧漢彌爾頓論馬塞爾‧杜象”——這標題本身就有一種莫名的吸引力,像是提供瞭一把開啓藝術寶庫的金鑰匙。我一直對馬塞爾‧杜象這位“現代藝術之父”充滿好奇,他的《泉》、他的“現成品”以及他對傳統藝術觀念的顛覆,總是讓我覺得他身上藏著太多不為人知的秘密。而由理查‧漢彌爾頓,一位同樣在藝術界有著舉足輕重地位的藝術傢來“解密”,這本身就充滿瞭看點。我設想,漢彌爾頓的解讀不會是枯燥的學術分析,而更可能是帶有藝術傢敏銳觀察力和深刻洞察力的視角。他或許能從一個創作者的立場齣發,更直接地觸碰到杜象藝術的核心,理解杜象在創作過程中所思所想,以及他如何巧妙地運用幽默和反諷來挑戰藝術的邊界。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漢彌爾頓會如何解析杜象那些看似簡單卻蘊含深意的作品,他是否會揭示杜象對於“原創性”、“藝術價值”以及“觀看行為”等概念的獨特理解,並最終幫助我們這些讀者,能夠更清晰地認識這位藝術史上極其重要的人物。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