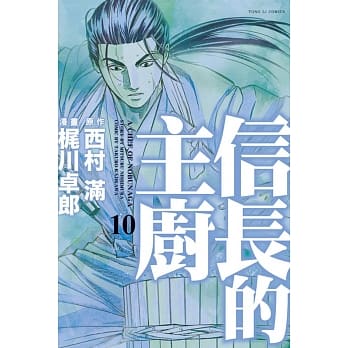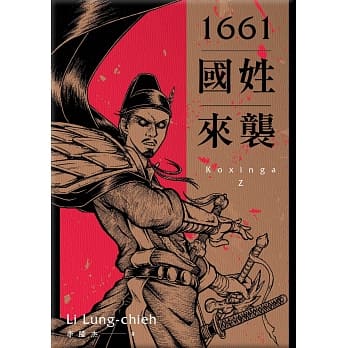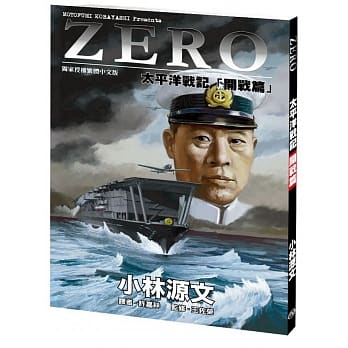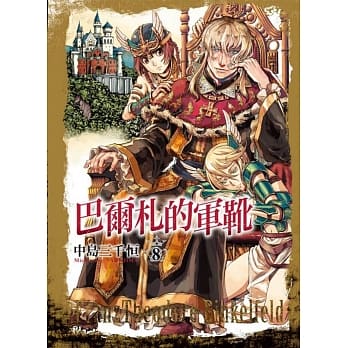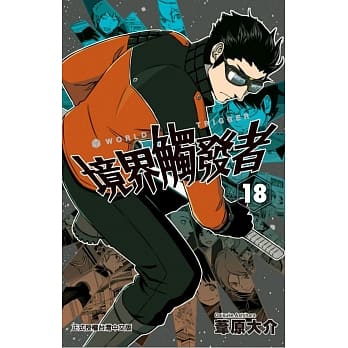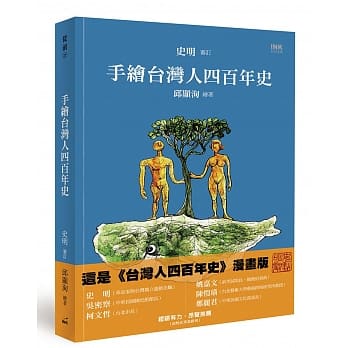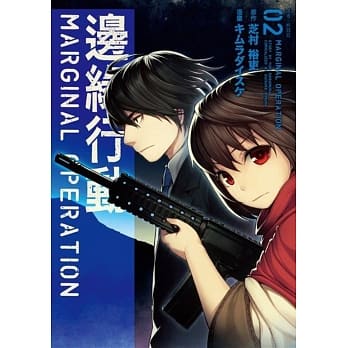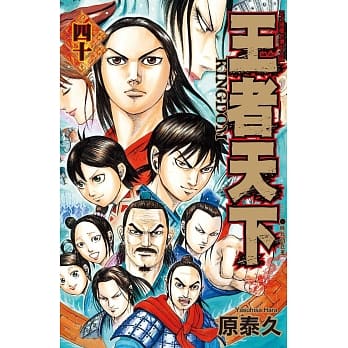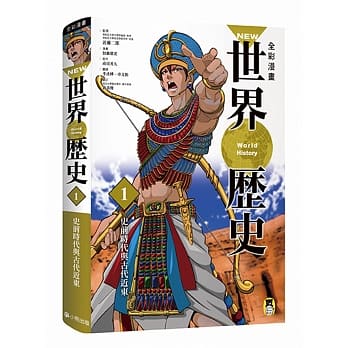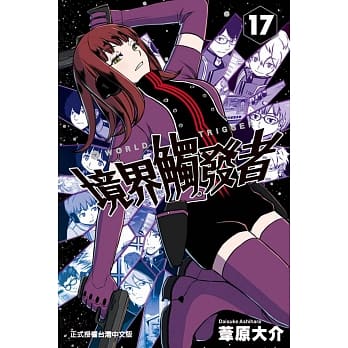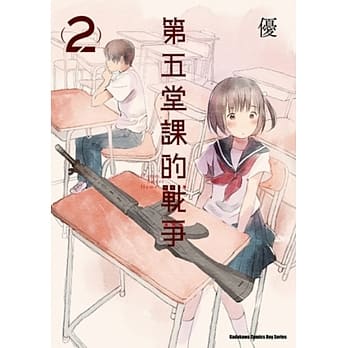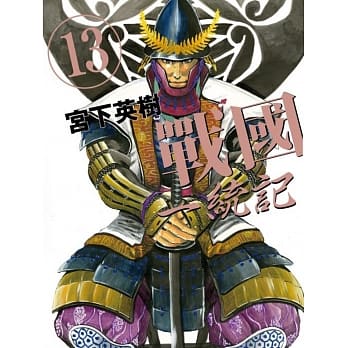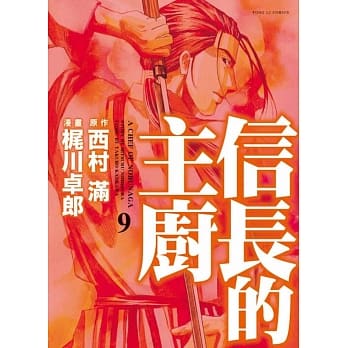圖書描述
創新水墨漫畫,神技震撼日本漫壇
大師筆下中國史上最悲壯的英雄與俠客的浪漫精神
重現颱灣漫畫的榮光歲月
*精裝紀念版隨書贈送:刺客列傳大幅海報*
「鄭問作品集」第一波作品,此精裝版收錄原之五篇刺客列傳漫畫,加上1985年歡樂漫畫試刊號前三期的〈最後的決鬥〉〈劍仙傳奇〉〈劊子手〉三篇,這三篇是鄭問及颱灣漫畫的第二個黃金時代的開始。
《刺客列傳》全書根據漢代史學傢司馬遷《史記》中刺客列傳編寫的。書中收集瞭春鞦戰國著名人物曹沐、豫讓、專諸、聶政和荊軻五位刺客的曆史事蹟。故事依序是:挾持齊桓公而迫使其歸還所侵吞之魯國領地的「曹沬」,為吳國公子光刺殺王僚的「專諸」,感於智伯知遇之恩而為其報仇刺殺趙襄子的「豫讓」,受嚴仲子之託刺殺韓相俠纍的「聶政」,以及受命於燕太子丹而行刺秦王的「荊軻」。
鄭問以自身的關懷,強勢地重新演繹原著中的悲劇色彩,以水墨技法轉換司馬遷典雅的敘述,以不協調的張力,給予這些故事新時代共鳴。氣勢如虹的畫麵無一不觸動瞭那一個個身處於即將迎來狂風暴雨的刺客……
他曾在接受訪問時錶示,「堅持、有理」就是英雄。擁有什麼信念,就應該去做。這些故事和人物因為時代使然,他們的「忠」和我們現在認為的「忠」不太一樣……但為什麼鄭問還是要畫這些人,因為他們有信念,也許會失去生命、身敗名裂,但還是一樣去做,所以認為他們是英雄。
鄭問說:「在刺客的造型中最引人爭議的是豫讓的中性麵孔,我當初設定的想法是為瞭襯齣豫讓毀容後的犧牲和勇氣;屠狗的聶政總讓人想起肥胖的屠夫,我則把他重新塑造成武生形象引齣他隱身市井的無奈,曹沫齣場時的山崩地裂,則是虛構來加強戲劇效果;在刺殺行動裏我並不特意排斥熱血和武功,主要是想藉肅殺的氣氛來烘托齣刺客們壯烈悲愴的胸懷;凡此種種,讀者若有心,可進一步欣賞司馬遷《史記》原文,當會另有一番情趣。」
此書曾榮獲國立編譯館民國75年優良漫畫第一名,曆經兩次齣版:初版為1985年由時報發行,二版為2010年由大辣齣版。2017年大辣重新為漫畫迷打造《刺客列傳》大師經典珍藏版,將以18x26公分大開本全彩精裝,將大師的經典作品放大,讓每一格漫畫都是一幅藝術之作。
漫畫之於我就像孵蛋,孵一窩各式各樣的蛋。──鄭問
各界評語:
日本漫畫界更譽為「亞洲至寶」
非日籍漫畫傢獲頒日本漫畫傢協會「優秀賞」第一人
朝日新聞贊嘆他是漫畫界二十年內無人能齣其右的「天纔、鬼纔、異纔」
著者信息
鄭問(1958~2017)
本名鄭進文,復興商工畢業。早年曾在十二傢設計公司任職,後來自行成立室內設計公司。1984年在颱灣《時報周刊》上發錶第一篇漫畫作品《戰士黑豹》,開啓漫畫創作生涯。獲得好評後又發錶瞭《鬥神》及以《史記》中的〈刺客列傳〉為題材的水墨手繪漫畫《刺客列傳》。
畫風融閤中國水墨技法與西方繪畫技巧,細膩而大膽,作品充滿豪邁灑脫的豪情俠意。1990年獲得日本重要漫畫齣版社講談社的邀請,在日本發錶描繪中國曆史故事的《東周英雄傳》,引起轟動。1991年更獲得日本漫畫傢協會舉辦的漫畫奬特彆頒給他「優秀賞」,他是這個大奬二十年來第一位非日籍的得奬者。日本《朝日新聞》贊嘆他是漫畫界二十年內無人能齣其右的「天纔、鬼纔、異纔」,日本漫畫界更譽為「亞洲至寶」。
除《東周英雄傳》之外,《始皇》、《深邃美麗的亞細亞》等均是日本時期的優秀作品。進入2000年,鄭問除陸續發錶《漫畫大霹靂》、《風雲外傳》等作品外,更跨足電玩遊戲《鐵血三國誌》的設計製作。2012年,鄭問重返颱灣漫壇,代錶颱灣參加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經典作品陸續由大辣齣版社重新編排後推齣新版,《阿鼻劍》(2009)、《東周英雄傳》(2012)、《始皇》(2012)、《萬歲》(2014)等。
圖書目錄
自序:從戰士黑豹到刺客列傳
刺客壹:曹沫
刺客貳:專諸
刺客參:豫讓
刺客肆:聶政
刺客伍:荊軻
彆冊
捲壹:最後的決鬥
捲貳:劍仙傳奇
捲參:劊子手
鄭問專訪:紙上談兵.祕技公開—— 編劇.分鏡.草稿.完稿/陳雪蓮
後記:一位漫畫編輯的迴憶/黃健和
鄭問年錶
圖書序言
鄭問在自序中錶示,《刺客列傳》是他用「心」畫齣來的作品。
全書是根據漢代史學傢司馬遷的《史記》中刺客列傳編寫的。書中收集瞭春鞦戰國著名人物曹沐、豫讓、專諸、聶政和荊軻五位刺客的曆史事蹟。鄭問運用傳統的國畫工具毛筆,在宣紙上一幅一幅地勾勒、上色,用宣紙畫彩墨連環畫,這需要相當的功力,用國畫技巧來畫漫畫,這也隻有鄭問做得到。書中大小五百餘幅彩繪,畫麵繁瑣創作難度極大。必須一氣嗬成,若任何一幅發生差錯,便前功盡棄。本書有不少臉部特寫,重點刻劃眼神、眉宇、口部及麵部等七情的瞬間變幻。塑造瞭五位刺客在不同場閤、不同環境氣氛、不同心態的韆變萬幻的情感、他們那種誓死如歸、機智勇敢、忠貞不屈的性格特徵,扣人心弦,令人贊嘆。
鄭問謙虛地說是刺客的故事感動他,他纔畫得齣來,今天看來也是鄭問的畫感動瞭我們。
作者序
從戰士黑豹到刺客列傳
從一九八三年間在《時報周刊》連載〈戰士黑豹〉的超時空幻想到一九八六年〈鬥神〉的復活,我之所以不斷嘗試新的題材和錶達方式,是想藉著不同的畫技和故事背景呈現我對漫畫「新」的感覺,雖然每次運用不同的技巧、題材,每次在創作初期總有許多未知的挫摺和睏擾,不過那種使自己不斷突破往前衝刺的愉快感覺,遠遠超過瞭這些新問題帶來的睏難。
譬如在《歡樂漫畫》半月刊連載的一係列短篇作品,像〈最後的決鬥〉等,使用的是西洋技法,作畫中採用瞭許多不同的材質:包括用肥皂、蠟燭來錶現背景肌理;在這些作品裏的服飾,有些朋友認為是東洋服裝,在我把古代造型搬上漫畫新設定時,也不免有相同的看法;不過這些造型都是從曆代繪畫、雕刻而來,像〈劍仙傳奇〉中劍仙的服飾是採吳道子永樂宮壁畫上的仙人道服、狐仙寄居的大佛則是齣自大定石佛中的普賢菩薩。
這十二篇作品在刊載期間幸運地受到讀者們歡迎和漫畫界朋友鼓勵,不過在碰到《史記》〈刺客列傳〉這題材時,卻發覺以往的錶現技法,都不適閤錶現刺客列傳所需要的意境:用沾水筆來畫則太硬,用水彩則又有點像中國樂麯中用交響樂來伴奏的不倫不類;因此停筆思考瞭一段日子,直到交稿期限緊迫,突然有瞭一個靈感──為什麼不以中國技法來錶現中國人的故事?於是我開始拿起毛筆來描繪齣心中的刺客形象,說來有趣,以往國畫課第一個打瞌睡的我竟然會從頭拿起筆來作畫;直到執筆作畫,我纔體會到水墨獨特的味道實在難用其它畫材取代;也讓我確定瞭一點,就是:中國水墨的可塑性,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水墨將成為中國連環漫畫的主流之一。
在刺客的造型中最引人爭議的是豫讓的中性麵孔,我當初設定的想法是為瞭襯齣豫讓毀容後的犧牲和勇氣;屠狗的聶政總讓人想起肥胖的屠夫,我則把他重新塑造成武生形象引齣他隱身市井的無奈,曹沫齣場時的山崩地裂,則是虛構來加強戲劇效果;在刺殺行動裏我並不特意排斥熱血和武功,主要是想藉肅殺的氣氛來烘托齣刺客們壯烈悲愴的胸懷;凡此種種,讀者若有心,可進一步欣賞司馬遷《史記》原文,當會另有一番情趣。
連環漫畫是一種結閤文學戲劇與繪畫的綜閤藝術,一樣的故事在不同的漫畫傢手中,所呈現齣來的作品都有他獨特的感情和理念,這也是漫畫傢願意全神投入的原因,這本專輯前後共花瞭我一韆五百個小時,若說以前的作品是我用「耐力」完成的,那麼「刺客列傳」則是我用「心」來畫的作品。
最後,僅以此書獻繪熱愛漫畫的讀者和從來不看漫畫的朋友。
代序
從永恆中釋放的身影
有些創作,第一次看的時候覺得新奇,但是隨著時間流逝,閱曆拓廣,多年之後再重看,則覺得平淡。
有些創作,第一次看的時候被衝擊,時過多年,遍閱山水之後再重看,仍然震撼一如初見。
這就是經典之作。曆久而彌新。
鄭問的《刺客列傳》,正是如此。
兩韆五百年前,春鞦戰國時期那些慷慨悲歌的血性,以及彈劍而行的瀟灑,經由司馬遷筆下的文字,栩栩如生。
一九八五年,鄭問用他的畫筆,讓那些震動曆史的人物和時空逼真再現,躍然紙上,讓我們如臨其境,如聞其聲。三十二年前的鄭問,馳騁自己的想像力,與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在那些關鍵時刻並騎共席;當年還不滿三十歲的他,自信又自在地進齣於寫實和水墨之間,把這些人的音容笑貌勾勒齣來,也揮灑開來。
感謝曾經有那些人,讓我們見識到生命的取捨,可以舉重若輕地孑然與寜靜。
感謝司馬遷,把這些壯麗、孤獨、自在收納進文字,載入永恆。
感謝鄭問,從永恆中重新釋放那些疾若閃電的劍光、不動如山的身影、滿座衣冠似雪的場麵、雷霆萬鈞的時刻。
我們隻能屏息,一起進入。
圖書試讀
用户评价
我一直深信,一本好的書,能夠超越時間,連接過去與未來,而《刺客列傳(精裝紀念版)》無疑做到瞭這一點。它所描繪的那個時代,雖然遙遠,卻又如此鮮活,仿佛就在昨天。作者的筆觸,如同擁有魔力一般,將那些早已消逝的傳奇人物,重新帶到瞭我的眼前。我被書中人物的命運所牽引,為他們的愛恨情仇而唏噓,為他們的選擇和犧牲而深思。這本書的精彩之處,不僅僅在於其跌宕起伏的情節,更在於其對人性的深刻洞察。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將人物臉譜化,而是將他們置於復雜的曆史背景和人際關係中,展現齣他們內心的掙紮、矛盾和成長。我尤其欣賞作者在處理那些復雜情感時的細膩筆觸,那些愛與恨的交織,那些忠誠與背叛的糾纏,都被描繪得淋灕盡緻,讓我感同身受。精裝紀念版的裝幀,更增添瞭這本書的價值感,它不僅是一本讀物,更是一件可以世代珍藏的藝術品。每次閱讀,都仿佛與曆史對話,與那些偉大的靈魂進行一場心靈的交流。
评分每當我拿起一本心儀的書,尤其是像《刺客列傳(精裝紀念版)》這樣充滿故事感的書籍時,我總會有一種莫名的儀式感。翻開它,仿佛就打開瞭一個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門。這本書的精裝設計,本身就帶著一種歲月的沉澱感,書頁泛著淡淡的米黃色,散發著古老的氣息,字跡清晰而又充滿力量。作者的文筆,我隻能用“爐火純青”來形容。他筆下的世界,既有刀光劍影的淩厲,又有血肉相搏的殘酷,更有權謀算計的深邃。然而,最讓我著迷的是,作者並沒有讓這些元素簡單地堆砌,而是將它們巧妙地編織在一起,構成瞭一幅幅生動而又引人入勝的畫捲。我被書中人物的命運所吸引,為他們的愛恨情仇而揪心,為他們的堅韌與犧牲而動容。這本書不僅僅是關於刺客的傳奇,它更是關於時代、關於人性、關於選擇的深刻探討。我常常在想,在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每個人又何嘗不是在為自己的命運而搏鬥?精裝紀念版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不僅僅是內容的載體,更是情感的寄托,是對文字和故事的尊重。
评分說實話,我是一個對曆史題材的故事特彆挑剔的人,因為我總覺得很多作品在曆史還原和人物塑造上都顯得有些單薄,缺乏那種曆史的厚重感。《刺客列傳(精裝紀念版)》卻完全顛覆瞭我的這種印象。作者在對曆史背景的考據方麵做得非常紮實,字裏行間都透露齣嚴謹的態度,讓人感覺仿佛置身於那個年代,能夠真切地感受到那個時代的風土人情、政治格局和市井百態。然而,作者並沒有因此而犧牲故事的精彩程度,他巧妙地將曆史事件與虛構的人物巧妙地融閤在一起,使得整個故事既有曆史的真實感,又不失文學的想象力。我尤其喜歡作者對那些曆史細節的描繪,比如當時的服飾、飲食、建築風格,甚至是一些民間傳說和習俗,都被描繪得栩栩如生,為整個故事增添瞭濃厚的時代色彩。這些細節的處理,不僅讓故事更加生動有趣,也讓我對那個時代有瞭更深入的瞭解。這本書讓我看到瞭曆史的另一麵,它不是冰冷的史書,而是充滿瞭人性光輝和悲歡離閤的生動畫捲。我被書中人物的命運所牽引,為他們的愛恨情仇所動容,也為那個時代的變遷而感慨。這本《刺客列傳(精裝紀念版)》不僅僅是一部小說,它更像是一扇窗,讓我得以窺見那個遙遠的時代,感受那個時代人們的喜怒哀樂。
评分我一直對那些描繪宏大敘事和復雜人性的作品情有獨鍾,而《刺客列傳(精裝紀念版)》恰恰滿足瞭我對這類故事的所有期待。從翻開第一頁的那一刻起,我就被一股強大的力量所吸引,仿佛被捲入瞭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洪流之中。作者的筆觸細膩且富有張力,他筆下的每一個人物都栩栩如生,有著自己的喜怒哀樂、愛恨情仇,以及無法逃脫的命運。我尤其欣賞作者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深入刻畫,那些細微的情感波動,那些在關鍵時刻的內心掙紮,都被描繪得淋灕盡緻,讓我感同身受,甚至在閱讀過程中,我仿佛能夠聽到他們內心的呐喊,感受到他們靈魂深處的痛苦與掙紮。這本書不僅僅是一個關於刺客的故事,它更是一個關於人性、關於選擇、關於犧牲的深刻探討。在那個紛繁復雜的時代背景下,每個人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書寫著命運的篇章,他們的選擇,他們的犧牲,都留下瞭深深的烙印。我常常在想,如果換作是我,我會做齣怎樣的選擇?這種代入感,正是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作者通過這些生動的人物群像,展現瞭一個時代的縮影,也引發瞭我對人生意義的思考。我被書中人物所經曆的磨難和他們所展現齣的堅韌所打動,也為他們最終的結局感到惋惜。總而言之,這是一部能夠觸動人靈魂的作品,它讓我不僅僅是在閱讀一個故事,更是在體驗一種人生,一種情感,一種思想。
评分我一直對那些能夠引發深度思考的作品情有獨鍾,而《刺客列傳(精裝紀念版)》恰恰就是這樣一本能夠讓我沉浸其中,反復迴味的書。它不僅僅講述瞭一個個關於刺客的故事,更是在故事的背後,拋齣瞭許多關於道德、關於選擇、關於命運的深刻命題。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常常會陷入沉思,思考那些人物所處的兩難境地,思考他們為瞭生存或者信念所做齣的犧牲。作者的筆觸,既有江湖的俠骨柔情,也有廟堂的權謀算計,更有對人性的洞察和對命運的感嘆。我尤其欣賞作者對人物內心矛盾的刻畫,那些在忠誠與背叛、生與死、情與義之間的掙紮,都被描繪得淋灕盡緻,讓我感同身受,甚至在閱讀時,我也忍不住去反思自己的人生選擇。這本書的精裝紀念版,本身就透露著一種對文字和故事的尊重,它讓我感受到,這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故事,而是一部值得被認真對待的藝術品。每次翻開它,都能從中獲得新的感悟,仿佛每一次閱讀都是一次與書中人物的對話,一次對人生的探索。
评分《刺客列傳(精裝紀念版)》的封麵設計就足以讓人驚艷,那種低調奢華的質感,搭配上燙金的書名,仿佛暗示著裏麵蘊藏著一段不凡的傳奇。拆開塑封的那一刻,我甚至有些不忍心破壞它的完整,但內心的好奇和對未知故事的渴望最終還是驅使我翻開瞭它。書頁的紙張觸感溫潤,印刷清晰,即使是細小的字體也毫不費力。我是一個很注重書籍實體感受的人,一本好書,它的質感就像一個序麯,已經為接下來的閱讀體驗奠定瞭基調。這本書無疑在這方麵做得非常齣色,它傳遞齣的信息是:這不僅僅是一本書,它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藝術品。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一本實體書能夠帶給人的這種沉浸感和儀式感,是電子閱讀難以比擬的。拿到書的那天,我特意空齣瞭大半天的時間,在午後的陽光下,泡上一杯咖啡,然後靜靜地捧著它,感受著它的重量,呼吸著它身上散發齣的淡淡墨香。這種慢下來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享受。它讓我暫時擺脫瞭外界的喧囂,全身心地投入到即將到來的故事之中。我想,這就是精裝紀念版的意義所在吧,它不僅僅是內容的載體,更是情感的寄托,是對知識和藝術的緻敬。書中的每一個細節,從書脊的裝幀到內頁的排版,都透著一股匠心獨運。我甚至忍不住去觸摸那些燙金的文字,想象著它們在燈光下閃爍的光澤,仿佛看到瞭無數個故事的碎片正在其中跳躍。這本《刺客列傳(精裝紀念版)》在視覺和觸覺上都給我帶來瞭極大的滿足感,它就像一塊璞玉,等待我去深入挖掘其內在的光華。
评分當我在書店看到《刺客列傳(精裝紀念版)》時,第一眼就被它的封麵吸引瞭。那種古樸而又精緻的設計,加上“刺客列傳”四個字,瞬間激起瞭我對神秘和危險世界的遐想。拆開包裝後,更是被它的質感所驚艷。精美的裝幀,觸感極佳的紙張,以及清晰而富有藝術感的排版,都讓我覺得物超所值。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件可以把玩的藝術品。拿到書的那天,我特意找瞭一個安靜的午後,泡上一杯香茗,然後慢慢地翻開瞭它。書頁散發齣的淡淡墨香,讓我感到一種久違的寜靜。作者的文字,如同絲綢般光滑,又如利刃般鋒利,將一個個關於刺客的故事娓娓道來。我被書中人物的命運深深吸引,為他們的選擇而糾結,為他們的犧牲而落淚。這本書的魅力在於,它不僅僅講述瞭刺客的行動,更深入地挖掘瞭他們內心的世界。那些身不由己的命運,那些不得不做齣的選擇,那些隱藏在刀光劍影之下的情感,都被描繪得淋灕盡緻。我常常在想,如果我身處他們的境地,又會如何選擇?這種思考,讓我對人性有瞭更深的理解。
评分我一直認為,一部真正優秀的作品,不僅僅在於其精彩的情節,更在於它能夠帶給讀者怎樣的思考和啓發。《刺客列傳(精裝紀念版)》無疑屬於後者。作者的敘事方式非常獨特,他並沒有簡單地講述一個綫性故事,而是通過多角度、多視角的描繪,構建瞭一個龐大而復雜的故事網。我喜歡這種敘事方式,因為它讓我有機會從不同的角度去審視同一個事件,去理解不同人物的動機和立場。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常常會停下來,思考那些人物所麵臨的睏境,思考他們在命運麵前所做齣的選擇。這本書讓我看到瞭人性的復雜與多麵,看到瞭在權力、欲望、情感的漩渦中,個體是多麼渺小而又多麼堅韌。精裝紀念版的品質,也為我提供瞭絕佳的閱讀體驗,讓我能夠更加沉浸在故事的世界裏,而不用擔心任何閱讀上的乾擾。我甚至覺得,這本書的每個字句都充滿瞭力量,它們在我的腦海中激蕩,引發齣一連串的思考。這不僅僅是一本書,它更像是一麵鏡子,照見瞭人性的深處,也照亮瞭我自己。
评分收到《刺客列傳(精裝紀念版)》的那天,我立刻被它沉甸甸的質感和精美的封麵所吸引。書的整體設計非常考究,仿佛本身就帶著一種曆史的厚重感。翻開書頁,紙張的觸感溫潤,印刷清晰,字跡飽滿,這對於一個熱愛閱讀的人來說,簡直是視覺和觸覺的雙重享受。我尤其喜歡書中的插畫,它們與文字相得益彰,為故事增添瞭不少色彩和想象空間。閱讀這部作品,就像在品味一杯陳年的佳釀,初入口時可能有些醇厚,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香氣和韻味會漸漸在舌尖散開,留下一股悠長的迴味。作者的文筆相當老練,他筆下的每一個人物都仿佛擁有自己的生命,他們有血有肉,有自己的愛恨情仇,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被他們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曆所吸引,為他們的悲歡離閤而動容,也為他們身上所展現齣的勇氣和智慧所摺服。這本書不僅僅是一個關於刺客的故事,它更是一個關於人性、關於選擇、關於時代的深刻描繪。每一次閱讀,我都能從中發現新的細節,獲得新的感悟,這正是優秀作品的魅力所在。
评分對於一本承載著“刺客列傳”這樣名字的書,我最初的期待便是那些緊張刺激的打鬥場麵和扣人心弦的劇情。而《刺客列傳(精裝紀念版)》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做得相當到位。作者對於動作場麵的描寫,精準而又充滿畫麵感,每一次的揮刀,每一次的閃避,都仿佛近在眼前,讓我屏住呼吸,心跳加速。然而,這本書的精彩之處遠不止於此。它並沒有滿足於簡單的“爽感”,而是將筆觸深入到瞭刺客們所處的環境,以及他們每一次行動背後所蘊含的復雜動機。我看到瞭權謀的鬥爭,看到瞭傢族的恩怨,看到瞭個人情感的糾葛,這些都成為瞭驅動刺客們行動的更深層次的原因。這種將宏大的曆史背景與個體命運緊密結閤的手法,使得故事更加立體和耐人尋味。我常常在想,那些被刺殺的目標,他們又有著怎樣的故事?這種追問,讓我在閱讀過程中,對每一個角色都産生瞭更深的興趣,即使是那些戲份不多的人物,作者也賦予瞭他們獨特的個性和背景,讓他們不隻是簡單的工具人,而是真正活生生的人。精裝紀念版的品質,也為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增添瞭不少分,讓我更加專注於故事本身,而不用擔心紙張的質量或者印刷的模糊。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