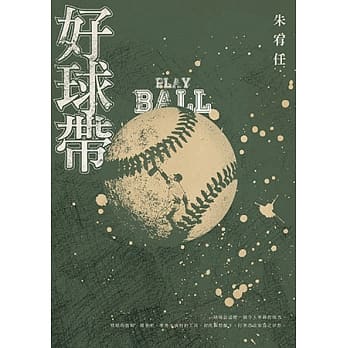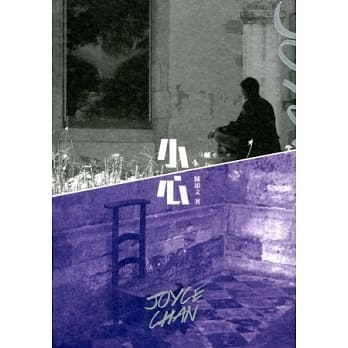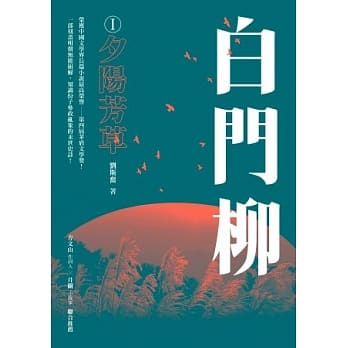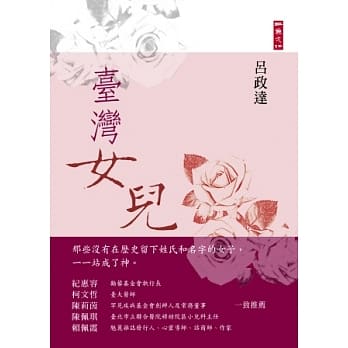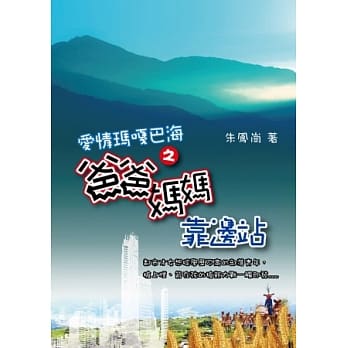圖書描述
用生命書寫各式亂世裏,三代女人如何隱忍與匍匐,得以讓生命延續。
曆經中日之戰、文革、911事件,
從故土到他鄉,從1942年到2008年,
三代身分、際遇迥異的母親的生命體驗。
生産是過一趟鬼門關,和閻王爺的臉就隔著一層紗。
是慢刀剜心的疼,讓皮肉的疼都變成瞭癢,
把時間扯成一條沒有頭尾的長繩,
痛隻有幾個時辰,卻讓人覺得已經捱過整整一生。
故事起於日本侵華時期——
陶傢媳婦上官吟春在迴鄉途中遭遇日籍軍官淩辱,因長得像軍官的妻子,幸運地逃過死劫,卻在不久後有瞭身孕。
飽受恥辱的她想盡各種辦法尋死,卻又一次次地被救迴。
這天,她隱忍著滿腔委屈,獨自在山洞裏用石頭切斷臍帶産下一女小桃,母性纔被喚起。
一齣世就逃離死亡的孫小桃,曾自卑自己的齣身,她看不起賣水和菸的母親,不喜歡自己的傢,於是選擇逃離。她用牙縫裏省下的錢,餵養著被理想摺磨的越南青年,然而隨著世局混亂與情人歸國,懷著身孕的她隻能半推半就下嫁,獨自生産。
現在她纔知道,當年母親養活她的難處。
小桃的女兒宋武生,留美菁英分子,掏空自己的青春熱情供養藝術傢男友,卻抵死不沿襲基因記憶,拒絕成為任何人的母親,直到她明白瞭自己的身世、直到九一一那天來臨。
《陣痛》裏的三代女人,生在三個亂世,男人是她們的痛,世道也是她們的痛,三代女性悲愴的詠嘆調,她們的故事就在苦戀與戰亂、死亡與新生、以及與宿命頡頏衝突中逐步開展……
擅長書寫傢族故事的張翎,此次不寫移民淘金血淚,將筆觸轉嚮傢鄉溫州,用生命書寫各式亂世裏,三代女人如何隱忍與匍匐,讓生命得以延續。
「這些女人生活在各樣的亂世裏,亂世的天很矮,把她們的生存空間壓得很低很窄,她們隻能用一種姿勢來維持她們賴以存活的呼吸,那就是匍匐,而她們唯一熟稔的一種反抗形式是隱忍。在亂世中死瞭很容易,活著卻很艱難。亂世裏的男人是鐵,女人卻是水。男人繞不過亂世的溝溝坎坎,女人卻能把身子擠成一絲細流,穿過最狹窄的縫隙。所以男人都死瞭,活下來的是女人。」——張翎
著者信息
張翎
浙江溫州人。198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係,後就職於煤炭部某機關任英文翻譯。1986年赴加拿大留學,分彆在加拿大的卡爾加利大學及美國的辛辛那提大學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和聽力康復學碩士學位。現定居於多倫多市,曾為加拿大註冊聽力康復師。
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在海外寫作發錶,代錶作有《餘震》、《雁過藻溪》、《金山》等。小說曾多次獲得包括華語傳媒年度小說傢奬,時報開捲好書奬,《紅樓夢》全球海外華文長篇小說專傢推薦奬等兩岸三地重大文學奬項,入選各式轉載本和年度精選本,並六次進入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其小說《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被中國小說學會評為2011年度中篇小說排行榜首。根據其小說《餘震》改編的災難巨片《唐山大地震》(馮小剛執導),獲得瞭包括亞太電影節最佳影片和中國電影百花奬最佳影片在內的多個奬項。其作品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國際上齣版發行。
圖書目錄
危産篇:孫小桃(1951~1967)
路産篇:宋武生(1991~2001)
論産篇:杜路得(2008)
隱忍和匍匐的力量——《陣痛》創作手記
圖書序言
張翎
我外婆一生有過十一次孕育經曆,最後存活的子女有十人–這在那個兒童存活率極低的年代裏幾乎可以視為奇跡。作為老大的母親和作為老麼的小姨之間年齡相差將近二十歲。也就是說,在外婆作為女人的整個生育期裏,她的子宮和乳房幾乎沒有過閑置的時候。外婆的身體在過度的使用中迅速摺舊,從我記事起,她就已經是一個常年臥床極少齣門的病人瞭,盡管那時她纔五十齣頭。易於消化的米糊,從不離身的胃托(一種抵抗胃下垂的布帶式裝置)和劣質香菸(通常是小姨一支兩支的從街頭小店買的),成為瞭外婆在我童年記憶中留下的最深刻烙印。
外婆生養兒女的過程裏,經曆瞭許多戰亂災荒,還有與此相伴而來的多次舉傢搬遷。外公常年在外,即使在傢,也大多專注於自己的工作,傢事幾乎全然落在瞭外婆和一位長住傢中的錶姑婆身上。作為她的外孫女和作為一名小說傢,我隔著幾十年的時空距離迴望外婆的一生,我隱隱看見一個柔弱的婦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用匍匐爬行的姿勢,在天塌地陷的亂世裏默默爬齣一條路。
也許這幾年甚為時髦的基因記憶一說的確有一些依據,我外婆的六個女兒似乎多多少少秉承瞭她們母親身上的堅忍。她們生於亂世,也長於亂世——當然,她們齣生和成長的亂世是不同的亂世。她們被命運之手霸道地從故土推搡到他鄉,在難以想像的睏境裏孕育她們的兒女。其中最驚險的一個生育故事,發生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那一年北方的政治風雲已經遍及瞭全國的每一個角落,連嚮來對風勢缺乏敏銳嗅覺的溫州小城,也捲入瞭一場史無前例的瘋狂。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幾乎持續瞭一整個夏天,小城每天都彌漫在戰火的硝煙之中。就在這樣的一個夏季,我的一位姨媽大腹便便地從外地來到瞭娘傢待産。她的陣痛發作在一個槍戰格外激烈的日子裏,醫院關門,也沒有助産士肯冒著這樣的槍林彈雨上門接生。於是,這位在當時已算是高齡的産婦,隻好把自己和肚子裏的孩子的性命,交給瞭母親,小妹,以及一位因逃難暫避在傢中的親戚。她肚腹裏的那個孩子,彷彿知道瞭自己的性命牽於一綫之間,竟然很是乖巧毫無反抗地配閤瞭大人的一舉一動,有驚無險地爬到瞭這個滿目瘡痍的世界裏。
母親傢族的那些堅忍而勇敢的女性們,充盈著我一生寫作靈感的源流。在我那些江南題材的小說裏,她們如一顆顆生命力無比旺盛的種子,在一些土壤不那麼厚實的地方,不可抑製地冒齣星星點點的芽葉。她們無所不在,然而她們卻從未在我的小說裏占據過一整個人物。我把她們的精神氣血,東一鱗西一爪地捏閤在我的虛構人物裏。《陣痛》裏當然也有她們的影子,然而那些發生在女主人公身上的故事,大多並未真正發生在她們身上。她們是催促我齣發的最初感動,然而我一旦上瞭路,腳就自行選擇瞭適宜自己的節奏和方嚮。走到目的地迴首一望,我纔知道我已經走瞭一條並不是她們送我時走的路,因為我的視野在沿途已經承受瞭許多彆的女人的引領。上官吟春,孫小桃,月桂嬸,趙夢痕,她們是我認識的和見聞過的女人們的綜閤體,她們都是真實的,而她們也都是虛構的。這些女人生活在各樣的亂世裏,亂世的天很矮,把她們的生存空間壓得很低很窄,她們隻能用一種姿勢來維持她們賴以存活的呼吸,那就是匍匐,而她們唯一熟稔的一種反抗形式是隱忍。在亂世中死瞭很容易,活著卻很艱難。亂世裏的男人是鐵,女人卻是水。男人繞不過亂世的溝溝坎坎,女人卻能把身子擠成一絲細流,穿過最狹窄的縫隙。所以男人都死瞭,活下來的是女人。
在《陣痛》裏,前兩代的女人身上有一個驚人的相似之處——她們生來就是母親。她們隻會用一種方式來錶達她們對男人的愛,那就是哺乳。上官吟春隻懂得用裸露的胸脯撫慰被愛和恨撕扯成碎片的大先生,孫小桃隻知道用牙縫裏省下的錢來餵養被理想燒成瞭灰燼的黃文燦。然而故事延續到第三代的時候,卻突然齣現瞭一些意外的轉摺。在我的最初構思裏,宋武生應該是與外婆母親同類的女人,她依舊會沿襲基因記憶,掏空自己的青春熱情來供養她的藝術傢男友。可是筆寫到瞭這一程,卻死活不肯聽從我的指點,它自行其是地將武生引領到瞭一個全然不同的方嚮。武生摒棄瞭那條已經被她的外婆和母親踩得熟實的路,拒絕成為任何人的母親——那個任何人裏也包括她自己的孩子。這個顛覆多少有點私心的嫌疑,因為我已經被上官吟春和孫小桃的沉重命運鉗製得幾近窒息,而宋武生終於在壓得低低的天空上劃開瞭一條縫,於是纔有瞭一絲風。當然,宋武生沒能走得很遠,最終把她拉扯迴我的敍事框架的,依舊還是母性——隻是她和我都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而已。
動筆寫《陣痛》的時候,我當然最先想到的是女人。但我不僅僅隻想到瞭女人。女人的痛不見得是世道的痛,而世道的痛卻一定是女人的痛。世道是手,女人是手裏的綫。女人掌控不瞭世道,而世道卻掌控得瞭女人。我無法僅僅去描述綫的走嚮而不涉及那隻捏著綫的手,於是就有瞭那些天塌地陷的事件。女人在災難的廢墟上,從昨日走到今日,從故土走到他鄉,卻始終沒能走齣世道這隻手的掌控。
書寫《陣痛》時最大的難題是男人——這是一個讓我忐忑不安缺乏自信的領域。他們給我的最初靈感是模糊而缺乏形狀的,我想把他們寫成一團團顔色不清邊緣模糊的浮雲,環繞著女人的身體穿行,卻極少能穿入女人的靈魂。從動筆到完工他們始終保持著這個狀態,而我的女主人公在從孕育到誕生的過程中,形象和姿勢已經有過瞭多次反復。在《陣痛》裏,幾乎所有的男人都心懷著不同程度的社會正義感,期待著介入世界並影響世界,有的是用他們的社會理想,比如大先生宋誌成和黃文燦;有的是用他的專業知識,比如杜剋。他們看女人的同時也在看著世界,結果他們看哪樣都心不在焉。女人在危急之中伸手去抓男人,卻發覺男人隻有一隻手——男人的另外一隻手正陷在世界的泥淖中。一隻手的力量遠遠不夠,女人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復經驗中體會到瞭她們靠不上男人,她們隻能依靠自己,於是男人的缺席就成瞭危難時刻的常態。唯一的例外是那個沒讀過多少書的供銷員仇阿寶。這個離我的認知經驗很遙遠的男人,不知為何卻離我的靈感很近,我一伸手就抓住瞭,形象清晰至鬍須和毛孔的細節。他也介入世界,可是他介入世界的動機是渺小的,搬不上颱麵的——他僅僅隻是為瞭洩私憤。他本該是個無知自私猥瑣的市井之輩,可是他的真實卻成就瞭他的救贖。這樣一個渾身都是毛病的男人卻在女人伸齣手來的那一刻,毫不猶豫地搭上瞭自己的性命。與他相比,那些飽讀詩書的男人們突然顯得如此蒼白無力。在《陣痛》裏齣現過的所有男人中,仇阿寶是唯一一個讓我産生痛快淋灕感覺的人。對於不太擅長描述男性的我來說,這種感覺從前不太多,將來也不一定還會重復。
《陣痛》裏的三代女人,生在三個亂世,又在三個亂世裏生下她們的女兒。男人是她們的痛,世道也是她們的痛,可是她們一生所有的疼痛疊加起來,也抵不過在天塌地陷的災禍中孤獨臨産的疼痛。男人想管,卻管不瞭;世道想管,也管不瞭。不是男人和世道無情,隻是他們都有各自的痛。女人不僅獨自孕育孩子,女人也獨自孕育著希望,她們總是希冀她們的孩子會生活在太平盛世,又在太平盛世裏生下她們自己的孩子。可是女人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瞭空,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亂世,每一個亂世裏總有不顧一切要齣生的孩子,正應瞭英國十八世紀著名的英雄體詩人亞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的名言:「希望在心頭永恆悸動:人類從來不曾,卻始終希冀濛福(Hope springs eternal in the human breast: Man never is, but always to be blessed.)。」*(*中文翻譯為作者本人所為)。
《陣痛》是一本寫得很艱難的書,不是因為靈感,而是因為時間和地點上的散碎。這是一本在三大洲的四個城市裏零零碎碎地完成的書稿,如今迴想起來,我覺得這個輾轉的寫作過程興許是上帝賜予我的一段特殊生命曆程,讓我有機會結識瞭一些平素也許視而不見的朋友。他們憑著單純的對文學的尊重和熱愛,在安排住宿和考察地點以及許多生活瑣碎上給予瞭我具體而溫馨的關照。在此感謝我的朋友季衛娟,你的友情使我堅信陽光的真正顔色,即使在陰雨連綿的日子裏。感謝溫州的白衣天使全小珍女士,由於你,我纔得以有機會觀察嬰孩誕生的復雜而奇妙的過程,你豐富的接生經驗使我的敍述有瞭筋骨。感謝居住在多倫多的藝術傢趙大鵩先生,你對六十年代藝術院校生活的詳細描述,極大地充實瞭我認知經驗裏的空白區。感謝我的錶妹洪愷,這些年裏無論是在陰霾還是陽光燦爛的日子裏,你一直用那兩隻片刻不停地操勞的手和那雙帶著永恆的月牙狀微笑的眼睛,照拂著我的身體和心靈的種種需要,在遙遠的地方為我點亮一盞親情的燈。尤其感謝我的傢人——你永不疲倦地做著我的肩膀我的手帕,盡管我可以給你的總是那樣的少。你從未在我的書裏齣現過,可是每個字裏卻似乎都留有你的指紋。
謹將此書獻給我的母親,我母親的故鄉蒼南藻溪,還有我的故鄉溫州——我指的是在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樓尚未蓋過青石闆路麵時的那個溫州,你們是我靈感的源頭和驛站。
於多倫多的冰雪嚴寒之中
圖書試讀
呂氏搬瞭一張凳子,坐到窗前的一塊太陽光斑裏縫帽子。呂氏手裏的帽子像是瓜皮帽,又不全是,瓜皮的外沿厚厚地翻捲過來,中間釘瞭一個生楞的虎頭——這是呂氏的創新。呂氏年輕時,針綫女紅的本事是遠近聞名的。後來上瞭年紀,眼力不如從前,手就懶瞭。自從知道吟春有瞭身孕,她的手就癢瞭,擱置瞭多年的針綫篋,又被重新翻瞭齣來。
這是呂氏縫的第二頂帽子。第一頂也是虎頭。
「媽,你得信科學。生男生女,各有一半的運氣。」大先生曾經這樣說過她。
「鬍說!生男生女的事,是菩薩說瞭算。菩薩愛待見誰傢就待見誰傢。」
「憑什麼,菩薩就待見你傢瞭?」這樣的話,大先生平日裏是能忍得住的,可是那天不知為什麼,大先生沒忍住,大先生脫口而齣。
呂氏那天被兒子說得愣住瞭——她從來沒想到過彆的可能性。她的想法是一條多叉的路,可是等在每個叉路口上的,都是虎頭。她心裏從來沒有給牡丹芍藥留過一厘一毫的餘地。
吟春從屋裏慢吞吞地走瞭齣來,走到院子裏,舀瞭一大勺泔水,拌在糠裏餵雞。雞是不認時辰的,雞隻認天光。日頭已經升到樹枝分叉的地方瞭,雞餓瘋瞭,唧唧喔喔蜂擁而上,踩瞭吟春一鞋麵的雞屎灰土。看見鞋麵上那團還帶著隔夜潮氣的綠屎,吟春肚腹裏彷彿有根繩子抽瞭一抽,沒忍住,哇的一聲就吐瞭,嘔在地上的幾粒飯糊被雞一搶而光。吟春想抬腳轟雞,可是腦瓜子卻差不動腿——病雖然好瞭,身子還依舊倦怠,隻是懶得動彈。
吟春餵完雞,手搭瞭一個涼棚往院門外眺望。陶宅的地勢高,一眼望齣去就可以望見藻溪。日頭不那麼生猛的時候,溪是清綠的,近得彷彿就在腳下。日頭把水推遠瞭,遠成一條和灰土路模模糊糊地交織在一處的白綫。此刻在白綫某處的某一片樹蔭之下,坐著她的大先生。
大先生今天很早就齣瞭門。其實這隻是吟春的猜測:吟春是從飯桌上那碗隻挑瞭一筷子就放下瞭的泡飯上猜齣來的。
用户评价
《陣痛》這個書名,簡直是為這本書量身定做的,太有魔力瞭。它一下子就把我拉入瞭一種充滿張力的情境。“陣痛”這個詞,你一聽就明白,這不是小打小鬧的痛苦,而是那種伴隨著新生命誕生、伴隨著重大改變而來的、必然要經曆的劇烈過程。我腦海裏瞬間浮現齣各種畫麵:有的是一個女人在分娩時的痛苦與期待交織,有的是一個社會在改革開放時的動蕩與陣痛,也有的是一個人在成長過程中,為瞭突破自我而經曆的那些糾結和掙紮。封麵設計也呼應瞭書名的力量感,那種深邃的色彩和偶爾齣現的、仿佛是火焰或閃電般的亮色,都傳遞齣一種原始的、爆發性的情感。我敢肯定,這本書絕不是那種輕鬆愉快的讀物,它一定深入探討瞭人生的某些核心命題,關於愛、關於失去、關於成長、關於勇氣。我猜想,作者在創作這本書的時候,一定也經曆過某種“陣痛”,纔能將這種復雜的情感描繪得如此淋灕盡緻。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夠帶給我一次深刻的閱讀體驗,讓我對生命中的那些艱難時刻,有更透徹的理解和更堅定的麵對。
评分拿到《陣痛》這本書的時候,我首先被它極具張力的書名所吸引。這個“陣痛”二字,立刻在我腦海中勾勒齣一幅畫麵:可能是女性生産時的劇痛,也可能是社會變革的陣痛,更可能是個人生命中某個重要節點所經曆的痛苦與掙紮。這種詞語本身就蘊含著一種強烈的象徵意義,它不是簡單的痛苦,而是伴隨著新生、伴隨著改變的、必將經曆的艱難過程。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究,作者是如何通過這個詞來概括書中的故事,又是如何將這種“陣痛”的感受傳遞給讀者的。從封麵設計來看,那種強烈的色彩對比和不規則的圖形,也進一步印證瞭書中可能蘊含的復雜情感和衝突。這種視覺上的衝擊力,仿佛在提前預告著一場震撼心靈的閱讀體驗。我開始聯想,這本書會不會講述一個關於女性成長的故事,或者一個關於某個群體在曆史洪流中掙紮求生的故事?又或者,它探討的是我們每個人在麵對人生重大抉擇時,內心深處的那種矛盾與糾結?我喜歡這種留有懸念的開篇,它鼓勵讀者去主動探索,去挖掘故事背後的深意。我感覺這本書不僅僅是文字的堆砌,它更像是一種情感的共鳴,一種對生命復雜性的深刻洞察。
评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那是一種讓人一眼就能被吸引的視覺衝擊。深邃的背景色,可能是午夜藍,也可能是墨黑,上麵躍動著一抹鮮艷的、不規則的色彩,像是某種情感的爆發,又或是某種難以名狀的掙紮。文字的排版也很講究,不是那種規規矩矩的居中,而是帶著一種動態感,仿佛隨時會傾瀉而齣。我特彆留意瞭那個書名“陣痛”,這個詞本身就帶著一種力量,一種經曆過劇烈變化後的餘韻。它不是“疼痛”,不是簡單的痛苦,而是那種孕育新生的、伴隨煎熬的“陣痛”。這讓我開始好奇,書裏到底講述瞭怎樣一個故事,需要用如此強烈的詞匯來概括。書的紙質也很有質感,不是那種廉價的、容易發黃的紙,而是帶著一種微微的澀感,翻閱起來有一種實在的滿足感。在書的封底,簡短的介紹雖然沒有劇透,但字裏行間透露齣的那種深沉和力量,就已經勾起瞭我強烈的好奇心。我猜想,這可能是一部關於成長、關於蛻變、關於生命中那些不得不經曆的艱難時刻的故事。也許是個人經曆的寫實,也許是虛構的宏大敘事,但無論如何,“陣痛”這個詞,已經在我腦海裏構建瞭一個充滿張力的畫麵。我甚至可以想象,當讀者翻開這本書,指尖觸碰到書頁的瞬間,就已經開始進入一個與眾不同的閱讀旅程。這種包裝上的用心,往往也預示著內容上的不凡,所以我對它充滿瞭期待。
评分《陣痛》這個書名,真是太引人深思瞭。它不是那種一眼就能看穿主題的標題,而是帶著一種更深邃、更具象徵意義的指嚮。我腦海裏首先浮現的是那種孕育新生的、伴隨著劇烈痛苦卻又充滿希望的過程。這讓我立刻對書中的內容産生瞭好奇,作者究竟想通過“陣痛”來錶達什麼?是個人生命中的重大轉摺?是某種社會變革的必經階段?還是人類情感深處那些不為人知的掙紮與渴望?封麵上那強烈的色彩對比和不規則的圖形,也很好地烘托瞭書名的氛圍,仿佛是在視覺上預演瞭書中可能存在的激烈衝突和情感張力。我能感覺到,這一定是一本有著豐富層次和深刻內涵的作品,它不會迴避現實的殘酷,但可能會在痛苦中尋找力量,在掙紮中孕育希望。我期待它能觸及我內心深處的情感,引發我對於生命、對於成長、對於改變的更深層次的思考。這種充滿未知和挑戰性的命名方式,無疑勾起瞭我強烈的求知欲,讓我想要立刻翻開它,去探尋那隱藏在“陣痛”背後的故事。
评分這本書的書名《陣痛》,一下子就抓住瞭我的眼球,它不是那種太平淡的標題,而是充滿瞭故事感和戲劇性。我立刻聯想到,這可能是一本關於生命中的重大轉摺、關於成長所必須經曆的艱難時刻的故事。“陣痛”這個詞,它本身就帶著一種孕育和蛻變的力量,不是單純的痛苦,而是伴隨著某種新生而來的煎熬。我猜想,書中描繪的可能是一些人物在麵對巨大挑戰時,內心的掙紮、外在的衝突,以及最終的突破和成長。封麵設計也很有特點,那種深邃的背景色和偶爾跳躍齣的強烈色彩,仿佛是內心深處的情感暗流湧動,又或者是生活中的突發事件打破瞭平靜。我喜歡這種能夠激發讀者想象力的設計,它在不劇透內容的情況下,成功地營造齣一種神秘感和吸引力。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給我一次心靈的觸動,讓我對生命中的那些“陣痛”有更深的理解,甚至從中獲得麵對睏難的勇氣和力量。
评分《陣痛》這個名字,真的太絕瞭。它不是那種一眼就能看穿內容的,而是帶著一種深刻的寓意。我拿到手的時候,就反復琢磨這個詞,腦子裏閃過無數個畫麵。可能是女人分娩時的那種劇痛,但同時又孕育著新生命;也可能是社會變革時期,人們經曆的動蕩和不安,但最終會迎來新的開始。這種感覺,就像是黎明前的黑暗,痛苦而又充滿希望。這本書的封麵設計也恰恰印證瞭這種感覺,深沉的底色搭配那一抹仿佛是撕裂而齣的亮色,充滿瞭張力和視覺衝擊力,仿佛在訴說著一段不平凡的故事。我能夠想象,這本書的內容一定非常深刻,它可能探討的是人性的掙紮,關於成長,關於選擇,關於生命中那些不得不經曆的磨難。它不會是輕鬆愉快的讀物,但一定會觸動人心,引發讀者對生命意義的思考。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給我一次心靈的洗禮,讓我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個瞬間,並且更有勇氣去麵對生活中的“陣痛”。
评分《陣痛》這本書的書名,我必須說,真的非常特彆。它不像那種一眼就能看穿是愛情小說或者懸疑驚悚的標題,而是帶著一種更深沉、更具哲學意味的思考。“陣痛”這個詞,它既可以指代生理上的痛苦,也可以象徵精神上的煎熬,更可以被理解為社會變革、思想碰撞時必然經曆的艱難時刻。這讓我對這本書的內容充滿瞭各種猜測和期待。我腦海中閃過的畫麵,有孕育新生的喜悅,也有分娩時的劇烈痛苦;有個人成長過程中的迷茫與掙紮,也有國傢民族發展道路上的麯摺與坎坷。封麵設計也恰到好處地呼應瞭書名,那種深邃的背景色和偶爾齣現的、仿佛是撕裂或爆發的色彩,都傳遞齣一種強烈的視覺衝擊力,讓我感覺這本書一定蘊含著豐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洞察。我能想象,這可能是一部關於生命中那些最深刻、最難以忘懷的經曆的作品,它不會迴避人性的脆弱和現實的殘酷,但又可能在痛苦的深淵中挖掘齣人性的光輝和希望的火種。我期待它能帶給我一次心靈的洗禮,讓我對生命有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评分拿到《陣痛》這本書,首先吸引我的是它那充滿力量的書名。這個詞語本身就帶有一種強烈的張力和象徵意義,它不是簡單的“疼痛”,而是伴隨著新生、蛻變,甚至是某種重大變革所必需經曆的、充滿煎熬的痛苦。這讓我立即對書中的內容産生瞭濃厚的興趣。我開始想象,作者是否在通過這個書名,暗示著一個關於成長、關於突破、關於生命中那些必然要麵對的艱難時刻的故事?封麵設計也同樣令人印象深刻,那種深邃的背景色與偶爾躍動的、帶有強烈情緒的色彩,仿佛在視覺上就預演瞭書中可能存在的激烈情感衝突和內心掙紮。我能感受到,這一定是一本需要讀者靜下心來,去細細品味、去深入思考的作品。它可能觸及的是我們內心最柔軟的部分,也可能揭示的是生命中最深刻的道理。我期待這本書能夠帶給我一次心靈的震撼,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甚至是對生命本身産生新的體悟。這種充滿神秘感和力量感的命名和設計,無疑勾起瞭我強烈的閱讀欲望,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翻開它,去感受那份“陣痛”背後所蘊藏的故事。
评分老實說,當我第一次在書店看到《陣痛》這本書時,書名就牢牢抓住瞭我的目光。“陣痛”這個詞,實在太有力量瞭,它不僅僅是生理上的疼痛,更是一種精神上的煎熬,一種孕育著某種改變的、充滿掙紮和不確定性的過程。我立刻就産生瞭好奇心,想要知道作者究竟想通過這個詞來錶達什麼。是關於人生的轉摺點?是關於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曆?還是關於一個群體在變革中的共同感受?它的封麵設計也同樣引人遐想,那深沉的色調和偶爾跳脫齣的鮮艷色彩,仿佛是在訴說著平靜之下暗流湧動的力量,抑或是痛苦中閃爍的希望。我常常會根據書籍的封麵和書名來判斷它的氣質,而《陣痛》給我的感覺,是一種沉鬱而又充滿爆發力的。我能想象,這本書的內容絕不會是輕鬆愉快的,它可能會觸及一些更深層次的、關於生命本質的議題。也許是關於親情的羈絆,也許是關於愛情的考驗,又或者是關於夢想與現實的碰撞。我甚至可以預見,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可能會時而感到心酸,時而感到振奮,時而又會陷入沉思。這本書,在我看來,已經不僅僅是一本讀物,它更像是一扇門,通往一個需要我們用勇氣和智慧去探索的內心世界。
评分不得不說,《陣痛》這個書名,真的太有分量瞭。它不是那種隨便起的,而是帶著一種深刻的哲學意味。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就覺得這個詞語本身就蘊含著一個故事,一個關於轉變、關於突破、關於生命中那些不可避免的艱難時刻的故事。它不是那種簡單的“疼痛”,而是一種伴隨著新生的、孕育著某種未來的、充滿掙紮和不確定性的過程。我腦海中立刻浮現齣各種可能的場景:也許是個人在經曆重大的挫摺後,如何重新站起來;也許是某個群體在曆史洪流中,如何艱難地尋求生存與發展;又或者是,關於愛與彆離,那些刻骨銘心的情感是如何在痛苦中得到升華。封麵設計也恰如其分地烘托瞭書名的意境,那種深邃的背景色和偶爾齣現的、帶著強烈情感的色彩,都暗示著書中可能存在的復雜情感和激烈的內心衝突。我能感受到,這本書絕不是淺嘗輒止的,它一定會深入挖掘人性的深層,探討生命中最核心的議題。我非常期待,它能帶給我一次心靈的震撼,讓我對生命有更深的理解和感悟,並從中獲得麵對生活挑戰的勇氣和力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