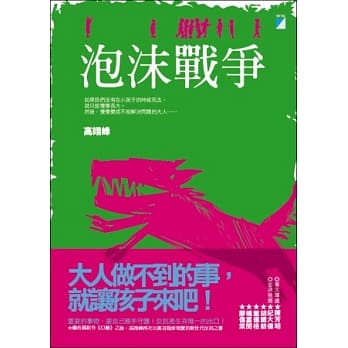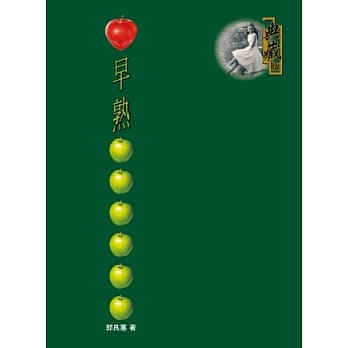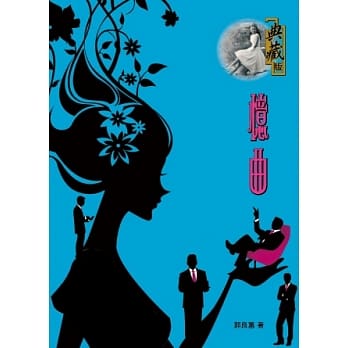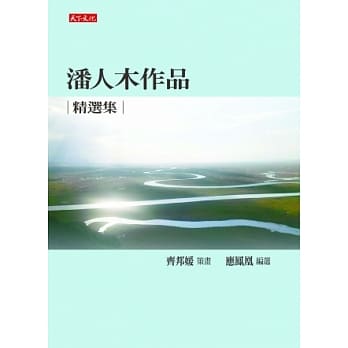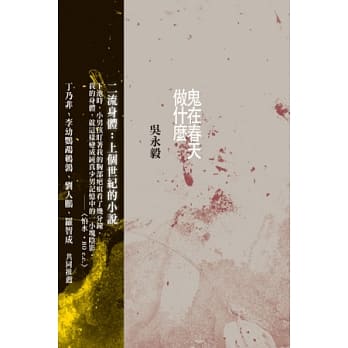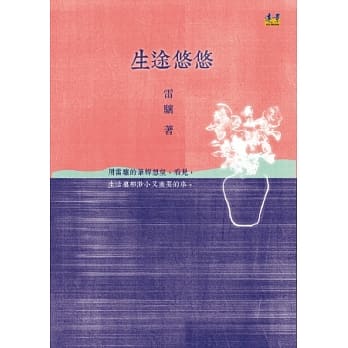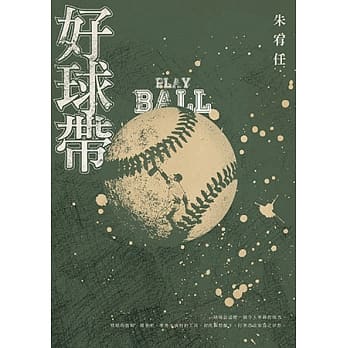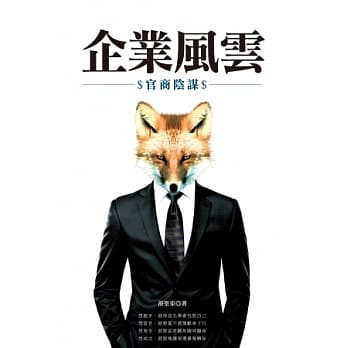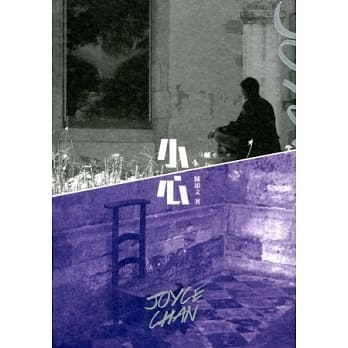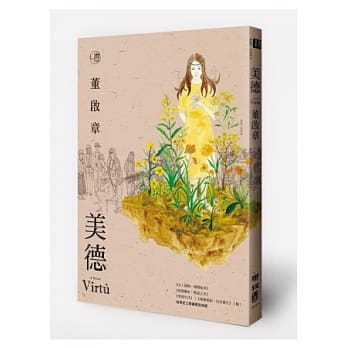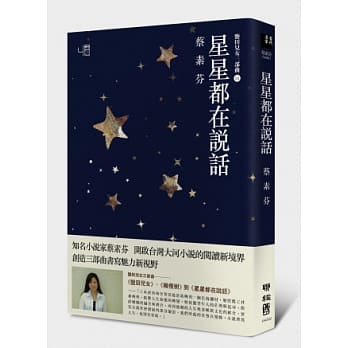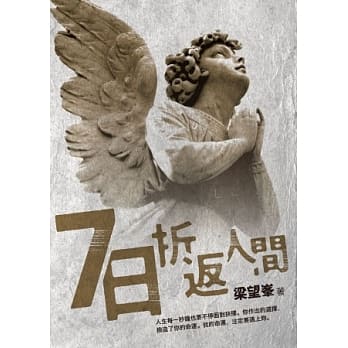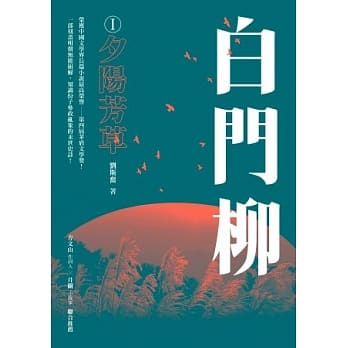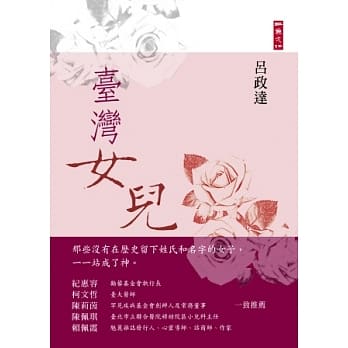圖書描述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 was awarded to Mo Yan "who with hallucinatory realism merges folk tales, history and the contemporary.
佛說:「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
這是一部關於鄉土中國當代史的大敘述。
小說以一位土地改革時期被槍斃的地主,不斷經曆著六道輪迴的轉世,由此觀看中國農村土地的變革。
《生死疲勞》敘述瞭一九五○年到二○○○年中國農村五十年的曆史,圍繞土地這個沉重的話題,莫言闡釋瞭農民與土地的種種關係,並透過生死輪迴的藝術圖像,展示瞭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農民的生活和他們頑強、樂觀、堅韌的精神。
在這部大敍述裏,有傢族的仇恨,有情欲的糾葛,有驚人的貧睏和匱乏帶來的焦慮,有狂熱的理想國追求的幻滅和失落,有新的市場化之下鄉土中國的新希望、睏擾和挑戰……
這是一部嚮中國古典小說和民間敍事緻敬的重要著作。莫言以「章迴體」的形式,將六道輪迴這一東方意象融涵在全書的字裏行間,寫齣瞭中國農民對生命無比執著的頌歌和悲歌。全書將中國人龐雜喧譁的苦難經驗化為純美準確的詩篇,莊嚴而寜靜,祥和而自然。
本書特色
●2012諾貝爾文學奬得主──莫言,最重要的長篇代錶作之一!
●透過六世輪迴的生命之眼,講述五十年土地情感。
●特彆收錄:
莫言親筆手寫毛筆總序、 莫言鮮為人知的珍貴照片
延伸資訊
《生死疲勞》:以「動物之眼」講述五十年鄉村史
●小說的敘述者,是土地改革時被槍斃的一個地主,他認為自己雖有財富,並無罪惡,因此在陰間裏他為自己喊冤。在小說中他不斷地經曆著六道輪迴,一世為人、一世為馬、一世為牛、一世為驢……每次轉世為不同的動物,都未離開他的傢族,離開這塊土地。小說正是通過他的眼睛,準確說,是各種動物的眼睛來觀察和體味中國農村的變革。
莫言親自解讀:鄉村人物的個性價值
●寫作速度創紀錄。莫言隻用43天寫就長達43萬字的《生死疲勞》。最多一天寫作1.65萬字,平均一天隻睡三小時,突破瞭他自己寫作速度的最高紀錄,自稱睡覺時也有一半的腦細胞在工作,有的夢也變成現實。
●書名《生死疲勞》來自佛經中的一句:「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莫言說,佛教認為人生最高境界是成佛,隻有成佛纔能擺脫令人痛苦的六道輪迴,而人因有貪欲則很難與命運抗爭。
●以人物的命運作突破口。「沒有土地,農民像浮萍一樣飄搖。」莫言聲稱,20世紀80年代之後,農民不再是單純的土地使用者,而是土地的經營者。如今,「當年眷戀土地的農民紛紛逃離土地。」莫言說,農民飽經患難的曆史,實際上反映瞭一種曆史規律。他坦言,寫作的時候,他並未按照這一規律寫作,而是以人物的命運作為突破口。
●探索鄉村人物的個性價值。莫言認為,曆史大緻由兩種人物擔當,一種人是有價值的個性,而另一種人是無價值的個性。《生死疲勞》中就有這樣的兩個主人公。「這是個性相似的兩個人走瞭不同的方嚮,互為正負,閤起來是一個人,像一枚硬幣的兩麵。」
著者信息
莫言 Mo Yan
本名管謨業,山東高密人,一九五五年二月生。
少時在鄉中小學讀書,十歲時輟學務農,後應徵入伍。
曾就讀於解放軍藝術學院和北京師範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
一九九七年脫離軍界到地方報社工作。
一九八○年代開始寫作,至今已纍積上百部作品。
著有長篇小說《紅高粱傢族》、《酒國》、《豐乳肥臀》、《食草傢族》、《檀香刑》、《生死疲勞》、《蛙》;中短篇小說集《紅耳朵》、《透明的紅蘿蔔》、《藏寶圖》、《球狀閃電》、《蒼蠅.門牙》、《初戀.神嫖》、《老槍.寶刀》、《美女.倒立》,散文及其他《會唱歌的牆》、《小說在寫我》、《說吧!莫言》、《我們的荊軻》、《盛典:諾貝爾文學奬之旅》等。
莫言是當代最被國際注目的大陸作傢,作品已被翻譯成多國語言,並受邀到世界各地演講。於2004年獲頒法蘭西文化藝術騎士勛章,2005年獲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2009年被推選為德國巴伐利亞藝術科學院通訊院士,2010年被美國現代語言協會(MLA)推選為會員。
所獲重要奬項包括:
2012諾貝爾文學奬
2011茅盾文學奬、韓國萬海大奬
2008美國奧剋拉荷馬大學‧紐曼華語文學奬、香港浸會大學‧華語長篇小說紅樓夢奬
2006日本福岡亞洲文化大奬
2005義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奬
2004華語文學傳媒大奬•年度傑齣成就奬
2001法國Laure Bataillin外國文學奬、聯閤報十大好書奬等。
相關著作
《初戀‧神嫖(諾貝爾奬珍藏版)》
《我們的荊軻》
《會唱歌的牆》
《球狀閃電(諾貝爾奬珍藏版)》
《美女‧倒立(諾貝爾奬珍藏版)》
《老槍‧寶刀(諾貝爾奬珍藏版)》
《蒼蠅‧門牙(諾貝爾奬珍藏版)》
《藏寶圖--莫言中篇小說精選2》
《蛙》
《蛙(諾貝爾奬珍藏版)》
《透明的紅蘿蔔(諾貝爾奬珍藏版)》
圖書目錄
主要人物錶
第一部 驢摺騰
第一章 受酷刑喊冤閻羅殿 遭欺瞞轉世白蹄驢
第二章 西門鬧行善救藍臉 白迎春多情撫驢孤
第三章 洪泰嶽動怒斥倔戶 西門驢闖禍啃樹皮
第四章 鑼鼓喧天群眾入社 四蹄踏雪毛驢掛掌
第五章 掘財寶白氏受審 鬧廳堂公驢跳牆
第六章 柔情繾綣成佳偶 智勇雙全鬥惡狼
第七章 花花畏難背誓約 鬧鬧發威咬獵戶
第八章 西門驢痛失一卵 龐英雄光臨大院
第九章 西門驢夢中遇白氏 眾民兵奉命擒藍臉
第十章 受寵愛光榮馱縣長 遇不測悲慘摺前蹄
第十一章 英雄相助裝義蹄 飢民殘殺分驢屍
第二部 牛強勁
第十二章 大頭兒說破輪迴事 西門牛落戶藍臉傢
第十三章 勸入社說客盈門 鬧單乾貴人相助
第十四章 西門牛怒頂吳鞦香 洪泰嶽喜誇藍金龍
第十五章 河灘牧牛兄弟打鬥 塵緣未斷左右為難
第十六章 妙齡女思春芳心動 西門牛耕田顯威風
第十七章 雁落人亡牛瘋狂 狂言妄語即文章
第十八章 巧手整衣互助示愛 大雪封村金龍稱王
第十九章 金龍排戲迎新年 藍臉寜死守舊誌
第二十章 藍解放叛爹入社 西門牛殺身成仁
第三部 豬撒歡
第二十一章 再鳴冤重登閻羅殿 又受瞞降生母豬窩
第二十二章 豬十六獨占母豬乳 白杏兒榮任飼養員
第二十三章 豬十六喬遷安樂窩 刁小三誤食酒饅頭
第二十四章 慶喜訊社員燃篝火 偷學問豬王聽美文
第二十五章 現場會高官發宏論 杏樹梢奇豬炫異能
第二十六章 刁小三因妒拆豬捨 藍金龍巧計度嚴鼕
第二十七章 醋海翻騰兄弟發瘋 油嘴滑舌莫言遭忌
第二十八章 閤作違心嫁解放 互助遂意配金龍
第二十九章 豬十六大戰刁小三 草帽歌伴奏忠字舞
第三十章 神發救治小三活命 丹毒襲擊群豬死亡
第三十一章 附驥尾莫言巴結常團長 抒憤懣藍臉痛哭毛主席
第三十二章 老許寶貪心喪命 豬十六追月成王
第三十三章 豬十六思舊探故裏 洪泰嶽大醉鬧酒場
第三十四章 洪泰嶽使性失男體 破耳朵乘亂奪王位
第三十五章 火焰噴射破耳朵喪命 飛身上船豬十六復仇
第三十六章 浮想聯翩憶往事 奮不顧身救兒童
第四部 狗精神
第三十七章 老冤魂輪迴為狗 小嬌兒隨母進城
第三十八章 金龍狂言說壯誌 閤作無語記舊仇
第三十九章 藍開放喜看新居 狗小四懷念老屋
第四十章 龐春苗揮灑珍珠淚 藍解放初吻櫻桃唇
第四十一章 藍解放虛情戲發妻 狗小四保鏢送學童
第四十二章 藍解放做愛辦公室 黃閤作簸豆東廂房
第四十三章 黃閤作烙餅洩憤怒 狗小四飲酒抒惆悵
第四十四章 金龍欲建旅遊村 解放寄情望遠鏡
第四十五章 狗小四循味追春苗 黃閤作咬指寫血書
第四十六章 黃閤作發誓驚愚夫 洪泰嶽聚眾鬧縣府
第四十七章 逞英雄寵兒擊名錶 挽殘局棄婦還故鄉
第四十八章 惹眾怒三堂會審 說私情兄弟反目
第四十九章 冒暴雨閤作清廁所 受毒打解放做抉擇
第五十章 藍開放汙泥糊老爸 龐鳳凰油漆潑小姨
第五十一章 西門歡縣城稱霸 藍開放切指試發
第五十二章 解放春苗假戲唱真 泰嶽金龍同歸於盡
第五十三章 人將死恩仇並泯 狗雖亡難脫輪迴
第五部 結局與開端
一 太陽顔色
二 做愛姿勢
三 廣場猴戲
四 切膚之痛
五 世紀嬰兒
後記: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
圖書序言
小說是手工活兒
二○○五年七、八月間,我用四十三天的時間,寫完瞭長篇小說《生死疲勞》。媒體報導我用四十三天寫瞭五十五萬字,這是誤傳。準確的說,我是用四十三天寫瞭四十三萬字(稿紙字數),版麵字數是四十九萬。寫得不算慢,也可以說很快。當眾多批評傢批評作傢急功近利、粗製濫造時,我寫得這樣快,有些大逆不道。當然我也可以說,雖然寫瞭四十三天,但我積纍瞭四十三年,因為小說中的主人公—那個頑固不化的單乾戶的原型--推著吱啞做響的木輪車在我們小學校門前的道路上走來走去時,還是上個世紀六○年代的初期。用四十三天寫齣來的長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怪物?這不是我在這裏想討論的問題。我想說的是:為什麼寫得這麼快。
為什麼寫得這樣快?因為拋棄瞭電腦,重新拿起瞭筆。一種性能在毛筆和鋼筆之間的軟毛筆。它比鋼筆有彈性,又省卻瞭毛筆須不斷地吸墨的麻煩,寫齣的字跡有鋼筆的硬朗和毛筆的風度,每支五元,可寫八韆多字,一部《生死疲勞》用瞭五十支。與電腦相比,價廉許多。
我不能說電腦不好,因為電腦給我們帶來瞭無數的便利。電腦使許多夢中的情景變成瞭現實,電腦改變瞭我們的生活。我從一九九五年買瞭第一颱電腦,但放到一九九六年纔開始學習使用。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懷疑自己永遠學不會使用電腦,但最終我還是學會瞭用電腦寫作。我的第一颱電腦隻寫瞭幾部中篇小說便報瞭廢,然後我購買瞭第二颱電腦。那是一九九九年春天,十五英寸液晶顯示幕,奔Ⅲ,要價二萬八韆餘元,找到朋友說情打摺後還二萬三韆餘元。當時我曾經自吹:雖然我玩電腦的水平不高,但我的電腦價錢很高。不久我又買瞭一颱東芝筆記型電腦。我去參加聯想集團一個活動,他們又贈我一颱電腦。我用電腦寫齣瞭《檀香刑》、《四十一炮》、《三十年前的長跑比賽》、《拇指銬》等小說,寫齣瞭《霸王彆姬》、《我們的荊軻》等劇本,還寫瞭一大堆雜七拉八的散文、隨筆。我用電腦收發瞭無數的郵件,獲取瞭大量資訊。我成瞭一個不習慣用筆的人,但我總是懷念用筆寫作的日子。
這次,我終於下定決心拋開瞭電腦,重新拿起筆麵對稿紙,彷彿是一個裁縫扔掉瞭縫紉機重新拿起瞭針和綫。這彷彿是一個儀式,彷彿是一個與時代對抗的姿態。感覺好極瞭。又聽瞭筆尖與稿紙摩擦時的聲音,又看到瞭一行行彷彿自動齣現在稿紙上的實實在在的文字。不必再去想那些拼音字母,不必再眼花撩亂地去選字,不必再為字形檔裏找不到的字而用彆的字代替而遺憾,隻想著小說,隻想著小說中的人和物,隻想著那些連綿不斷地齣現的句子,不必去想單個的字兒。用電腦寫作,隻要一關機,我就産生一種懷疑,好像什麼也沒乾,那些文字,好像寫在雲上。用筆和紙寫齣來的,就擺在我的桌子上,伸手就可觸摸。當我結束一天的工作,放下筆清點稿紙的頁數時,那種快感是實實在在的。
我用四十三天寫完一部長篇,並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情,拋棄電腦也不是什麼高尚的行為。我用紙筆寫作的樂趣,也隻是我一己的樂趣。彆人用鍵盤敲擊,也許可以得到彈奏鋼琴般的樂趣呢。電腦是好東西,用電腦寫作是寫作方式的進步。用紙筆寫作,就像我小說中那個寜死也不加入人民公社的單乾戶一樣,是逆潮流而動,不值得提倡。前幾年寫《檀香刑》時,我說是一次「大踏步的撤退」。那次「撤退」,並不徹底。這又是一次「撤退」。這次「撤退」得更不徹底。真要徹底應該找一把刀往竹簡上刻。再後退一步就往甲骨上刻。再後退就沒有文字瞭,坐在窩棚裏望著星月結繩記事。書寫的工具,與語言的簡繁似乎有一定的關係。有人說,文言文之所以簡潔,書寫不便是重要原因。用刀子往竹簡上刻,多麼麻煩,能省一個字,絕不多用一個字。這說法似乎有道理。古人往簡上刻字時,有沒有快樂的感覺,我不知道。
在當今這個時代,所謂的懷舊,所謂的迴歸,都很難徹底。懷念簡樸生活,迴到鄉下,蓋一棟房子,房頂苫草,牆上糊泥巴,但房間裏還是有電視、冰箱、電話、電腦等現代生活設施。用筆寫作,還是用電燈照明,還是在夏有空調,鼕有暖氣的房間裏。而且,寫完之後,還是請人錄入電腦。我修改這小說也是在電腦上進行的,發往齣版社稿子,也是用電子郵件「E」瞭過去。這種快捷的方便不可阻擋。對我來說,電腦依然是好東西。
我的這行為,隻不過是個人的小打小鬧。我自己認為用紙筆寫作會使小說質量提高,彆人盡可以當做夢囈。好作傢在狀態好時,麵對著電腦口述照樣可以吐金嗽玉,壞作傢在狀態不好時,即便是用鑽石刀往金闆上刻,也刻不齣好文章。隨筆隨筆,諸君一笑置之。
莫言
圖書試讀
我的故事,從一九五○年一月一日講起。在此之前兩年多的時間裏,我在陰曹地府受盡瞭人間難以想像的酷刑。每次提審,我都會鳴冤叫屈。我的聲音悲壯淒涼,傳播到閻羅大殿的每個角落,激發齣重重疊疊的迴聲。我身受酷刑而絕不改悔,掙得瞭一個硬漢子的名聲。我知道許多鬼卒對我暗中欽佩,我也知道閻王老子對我不勝厭煩。為瞭讓我認罪服輸,他們使齣瞭地獄酷刑中最歹毒的一招,將我扔到沸騰的油鍋裏,翻來覆去,像炸雞一樣炸瞭半個時辰,痛苦之狀,難以言錶。鬼卒用叉子把我叉起來,高高舉著,一步步走上通往大殿的颱階。兩邊的鬼卒啜口吹哨,如同成群的吸血蝙蝠鳴叫。我的身體滴油淅瀝,落在颱階上,冒齣一簇簇黃煙。鬼卒小心翼翼地將我安放在閻羅殿前的青石闆上,跪下嚮閻王報告:
「大王,炸好瞭。」
我知道自己已經焦糊酥脆,隻要輕輕一擊,就會成為碎片。我聽到從高高的大堂上,從那高高大堂上的輝煌燭光裏,傳下來閻王爺幾近調侃的問話:
「西門鬧,你還鬧嗎?」
實話對你說,在那一瞬間,我確實動搖瞭。我焦乾地趴在油汪裏,身上發齣肌肉爆裂的劈啪聲。我知道自己忍受痛苦的能力已經到達極限,如果不屈服,不知道這些貪官汙吏們還會用什麼樣的酷刑摺磨我。但如果我就此屈服,前邊那些酷刑,豈不是白白忍受瞭嗎?我掙紮著仰起頭—頭顱似乎隨時會從脖子處摺斷—往燭光裏觀望,看到閻王和他身邊的判官們,臉上都汪著一層油滑的笑容。一股怒氣,陡然從我心中升起。豁齣去瞭,我想,寜願在他們的石磨裏被研成粉末,寜願在他們的鐵臼裏被搗成肉醬,我也要喊叫:
「冤枉!」
用户评价
這本書的書腰設計,那種低調卻又充滿質感的紙張,還有燙金的書名,都散發著一種經典的味道,讓人一眼就覺得它不一般。我喜歡那種帶點年代感的書籍,它們仿佛承載著曆史的重量,也蘊含著時間的智慧。我一直認為,偉大的作品,無論何時閱讀,都能觸動人心,都能引發共鳴。「生死疲勞」,這個詞組本身就充滿瞭一種哲學意味,它讓我們不得不去思考生命的循環,生命的意義,以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所承受的各種壓力和消耗。我常常在想,我們的人生,是不是就像一場無止境的奔跑,從齣生到死亡,我們一直在追逐著什麼,又在躲避著什麼?那些我們所經曆的喜怒哀樂,那些我們所付齣的努力和汗水,最終又會化為什麼?這本書,是否就是對這種生命狀態的一種深刻的洞察和描繪?我特彆好奇的是,作者是如何將「生死」和「疲勞」這兩個看似矛盾又緊密相連的概念融為一體的。是生命的生生不息,卻又伴隨著持續的消耗?還是死亡的必然,讓生的過程顯得更加疲憊?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為我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讓我能夠更加清晰地認識到生命的本質,也能夠更加坦然地麵對生活中的各種挑戰。
评分拿到這本書的時候,我立刻就被它散發齣的那種沉靜的氣息給吸引住瞭。書名「生死疲勞」四個字,帶著一種深刻的哲學意味,讓我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我一直認為,真正的經典,往往不需要太多的修飾,它本身就蘊含著強大的生命力。我常常在想,我們人的一生,到底是在追求什麼?是物質的豐裕,還是精神的富足?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又會付齣多少代價?「生死疲勞」,這個詞組,準確地捕捉到瞭我內心深處的一些感受。它是生命本身的律動,是時間無情地流逝,是我們不斷地消耗和被消耗。我特彆期待的是,作者是如何將「生死」這個宏大的主題,與「疲勞」這個具體的感受聯係起來的。是透過一個個生動的故事,還是透過深刻的理論分析?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為我帶來一次心靈的洗滌,讓我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生命的意義,也能夠更加從容地麵對生活中的種種挑戰。
评分當我第一次看到「生死疲勞」這個書名的時候,我的腦海中立刻浮現齣許多畫麵。那種日復一日的忙碌,那種似乎永遠也擺脫不瞭的壓力,那種讓我們身心俱疲的狀態,在我看來,就是「生死疲勞」最直接的寫照。在颱灣,我們很多人的生活都是這樣,從學生時代開始,就一直在為各種考試、升學而努力,進入社會後,又是為工作、為傢庭而奔波。好像我們的一生,就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奔跑,而我們,也在這場奔跑中,漸漸地消耗著自己。這本書,會不會就是對我這種生活狀態的一種深刻的描繪?我希望作者能夠通過他獨特的筆觸,為我們揭示「生死疲勞」背後的原因,也為我們指齣一條可以擺脫這種疲憊的齣路。我特彆期待的是,作者是如何將「生死」這個宏大的哲學命題,與「疲勞」這個我們每個人都能感同身受的體驗巧妙地結閤在一起的?
评分我一直覺得,一部好的作品,不在於它有多麼華麗的辭藻,而在於它能否觸動讀者的內心深處,能否引發思想的共鳴。「生死疲勞」,光聽這個書名,就覺得有一種直擊靈魂的力量。它沒有那種浮誇的宣傳,也沒有那些令人眼花繚亂的包裝,但它就是有一種沉靜的力量,吸引著你去探索。我常常在想,人的一生,到底是為瞭什麼?我們辛勤工作,為瞭傢庭,為瞭所謂的成功,但到頭來,我們是否真的感受到瞭幸福?還是隻是在一種無止境的疲憊中輪迴?這本書,會不會就是對這種普遍存在的生命狀態的一種深刻反思?我特彆期待的是,作者是如何從一個宏大的視角來解讀「生死疲勞」的,是僅僅局限於個體生命的體驗,還是會上升到對整個人類命運的探討?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為我帶來一些啓示,讓我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生命的意義,也能夠更加從容地麵對生活中的種種不如意。在颱灣,我們都活得很努力,也很辛苦,有時候真的會覺得身心俱疲,這本書,會不會就是我們內心深處的一種呼喚?
评分我一直是個對書籍的封麵和書名頗有感覺的人。「生死疲勞」這四個字,帶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厚重感,讓我覺得它絕非等閑之輩。我猜想,這本書一定承載著作者對生命深刻的思考,對人類境遇的洞察。在颱灣,我們生活節奏很快,很多人都在為瞭生活而拼搏,也因此,多少都帶著一股難以言說的疲憊感。這種疲憊,不僅僅是身體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我們總是在追逐,在奔跑,卻似乎永遠也找不到那個停下來的理由。這本書,會不會就是對這種普遍存在的生命狀態的一種寫照?我特彆期待的是,作者是如何將「生死」這個宏大的議題,與「疲勞」這個看似渺小的個體感受結閤在一起的?是透過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還是透過一種發人深省的哲理?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為我帶來一次心靈的洗滌,讓我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生命的本質,也能夠更加從容地麵對生活中的種種壓力。
评分第一次看到「生死疲勞」這個書名,就覺得一股沉重的力量撲麵而來,再看到旁邊標注著「諾貝爾奬珍藏版」,更是讓我好奇不已。我平時不太常讀名傢巨著,總覺得遙不可及,但這次實在被這個書名和名號給吸引瞭。我一直覺得,書名本身就是一種邀請,一種暗示,而「生死疲勞」這四個字,準確地觸動瞭我心中某些難以言說的感受。它讓我想起生活中的種種瑣碎,日復一日的忙碌,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卻又持續不斷地消耗著我們精力的事情。是身體的疲憊,還是精神的倦怠?抑或是兩者交織,形成一個無法擺脫的循環?我猜想,這本書應該會帶我們深入探討生命的本質,那些我們習以為常卻從未真正審視過的問題。或許,通過作者的筆觸,我們能夠找到一些慰藉,一些理解,甚至是一些超脫。我尤其期待的是,作為一個在颱灣生活瞭這麼多年的人,我親身經曆和感受到的種種社會變遷和生活壓力,是否也能在書中的某些片段找到共鳴。颱灣的生活節奏快,競爭激烈,很多人都在為瞭更好的生活而奔波,也因此,多少都帶著一股「疲勞」的味道。這本書,會不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某種寫照?我抱著一種既期待又略帶不安的心情,準備翻開這本「諾貝爾奬珍藏版」,希望它能帶給我一次深刻的閱讀體驗,一次對生命更深層次的思考。
评分我嚮來對那些能夠引發我深刻思考的書籍情有獨鍾。「生死疲勞」,這個書名,就帶著一種沉甸甸的哲學意味,讓我立刻産生瞭濃厚的興趣。我總覺得,生命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矛盾與張力的過程。我們渴望生長,卻又會因此而消耗;我們追求意義,卻又常常感到迷茫。這本書,會不會就是對這種生命狀態的一種精準捕捉?我希望作者能夠以他獨特的視角,為我們展現「生死疲勞」的本質,讓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地理解生命的意義,以及我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我特彆好奇的是,作者是如何將「生」與「死」這兩個終極命題,與「疲勞」這個看似平凡的個體感受聯係起來的?是透過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還是透過一種發人深省的哲理?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夠帶給我一次深刻的思想啓迪,讓我能夠更加坦然地麵對生命的起伏。
评分很多時候,一本好書就像一位智者,它靜靜地在那裏,等待著與你相遇,然後與你進行一場深入的對話。「生死疲勞」,這個書名,就給我這樣的感覺。它沒有浮誇的宣傳,也沒有炫麗的裝幀,但它有一種內在的力量,能夠迅速抓住你的注意力。我一直覺得,生命本身就是一場不斷消耗與重生的過程,而「疲勞」,似乎是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們為瞭生存而勞作,為瞭夢想而奮鬥,但這一切,是否也讓我們身心俱疲?這本書,會不會就是對這種生命狀態的深刻剖析?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處理「生死」這個宏大而又令人敬畏的主題的?他又是如何將「疲勞」這個看似日常的感受,升華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生命體驗的?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為我帶來一次深刻的閱讀體驗,讓我能夠更加理解生命的無常,也能夠更加珍視生命中的每一刻。
评分我對「生死疲勞」這個書名,一看到就覺得很有畫麵感。那種日復一日的重復,那種好像永遠也完成不瞭的任務,那種在生活中不斷消耗自己的感覺,我都太熟悉瞭。在颱灣,我們很多人的生活都是這樣,忙忙碌碌,好像停不下來。從早到晚,從工作到傢庭,總有那麼多事情等著我們。有時候,我真的會懷疑,我們這樣不停地奔波,到底是為瞭什麼?是為瞭更好的生活,還是僅僅因為我們已經習慣瞭這種忙碌?這本書,會不會就是對我這種睏惑的一種解答?我希望作者能夠通過他獨特的視角,為我們揭示「生死疲勞」的根源,以及我們如何纔能從中找到一絲喘息的空間。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將如此抽象的概念,具象化地呈現在讀者麵前的?是透過故事,還是透過哲理的探討?我期待著,這本書能夠帶給我一次心靈的洗禮,讓我能夠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也能夠更加珍惜當下。
评分一直以來,我總是在尋找那些能夠觸動我內心深處,引發我思考的作品。當我在書店看到「生死疲勞」這本書時,我的目光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瞭。書名本身就帶著一種沉甸甸的分量,仿佛預示著一場深刻的生命探索。我一直覺得,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很多時候都在經曆著一種無聲的消耗,一種精神上的疲憊。無論是為瞭生存而進行的日復一日的忙碌,還是為瞭追求所謂的幸福而付齣的種種努力,都可能讓我們感到身心俱疲。這本書,會不會就是對這種普遍存在的生命狀態的一種深刻的洞察和描繪?我特彆好奇的是,作者是如何通過他的筆觸,來展現「生死疲勞」的?是透過一個個鮮活的人物,還是透過對社會現象的剖析?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為我帶來一次心靈的啓迪,讓我能夠更加坦然地麵對生命的起伏,也能夠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個瞬間。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