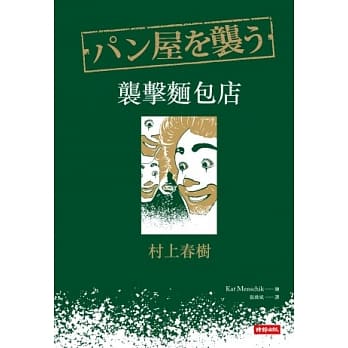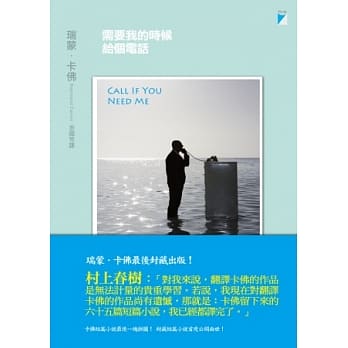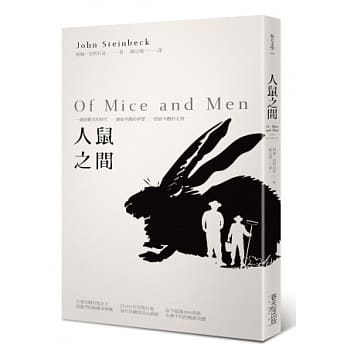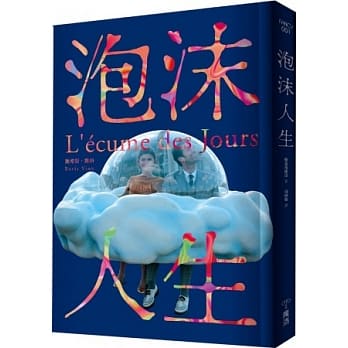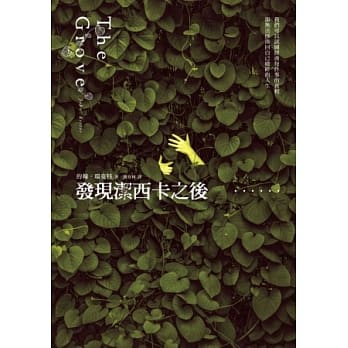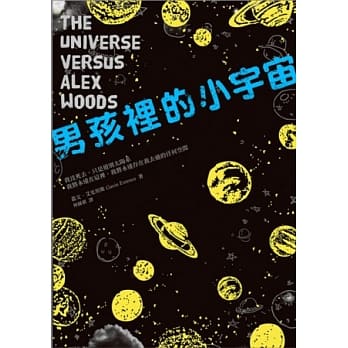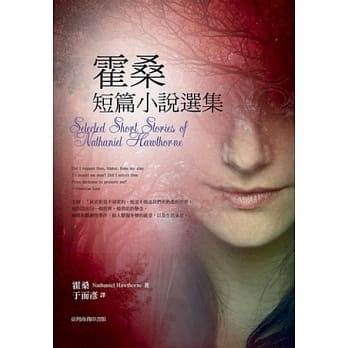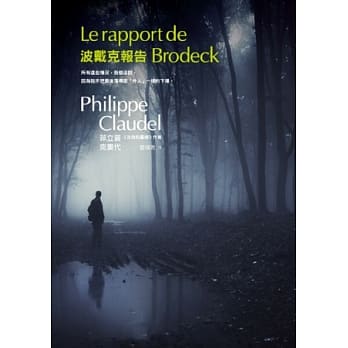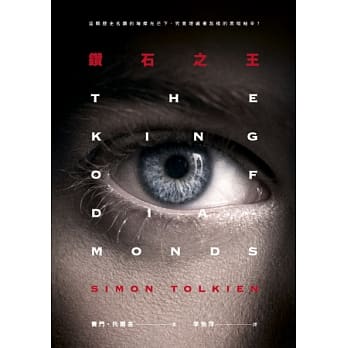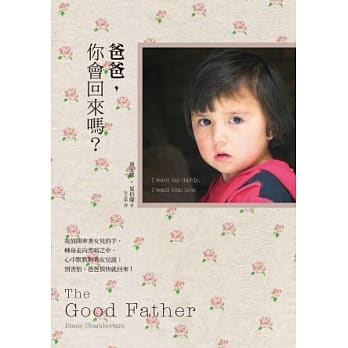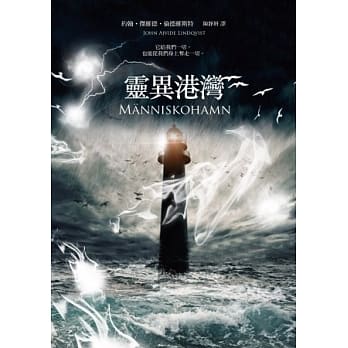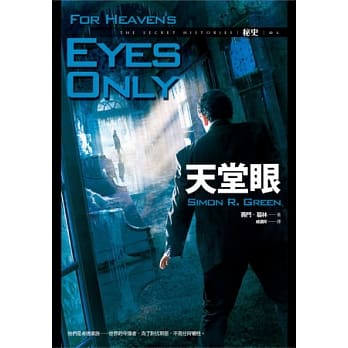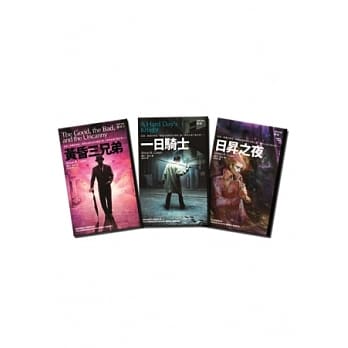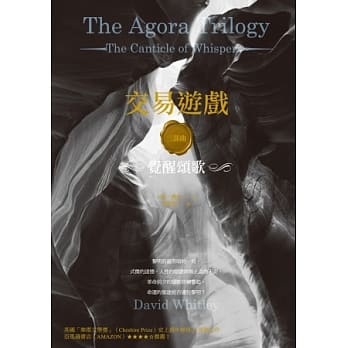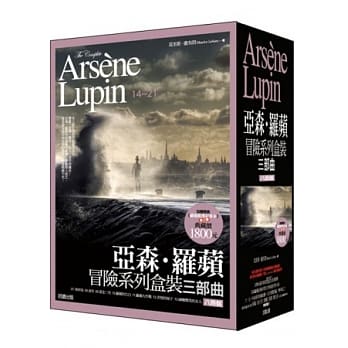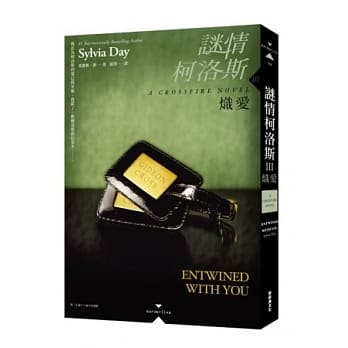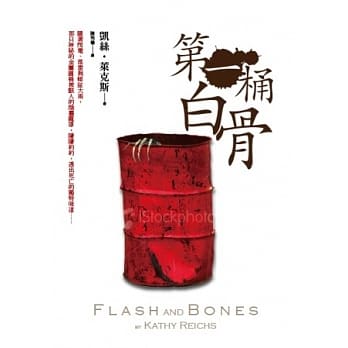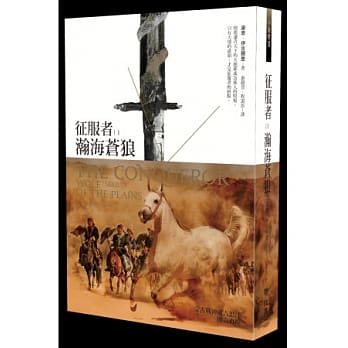圖書描述
著者信息
圖書目錄
圖書序言
導讀
笑到最後的人∕袁瓊瓊
一九三一年,凱倫.白列森迴到丹麥。一般人生命中的重大事件,於她,已經全部發生過瞭:她結瞭婚,離瞭婚。與情人同居,與情人分手。流産兩次。身患梅毒。長年汞中毒。剛結束瞭經營不善的咖啡種植事業,同時在返迴傢鄉之前,纔處理完分手情人的喪事。她已經破産,身無分文,而書稿「七個奇幻故事」還求售無門。
這一年,她四十六歲。
我不知道一般人,沒有凱倫的意誌的普通人,在這樣的境遇下會如何思考如何麵對。凱倫的做法是給自己取瞭個伊薩剋.狄尼森的筆名,繼續寫作。「伊薩剋」在希伯來文的意義是「笑」。在這種時刻,所有一切棄她遠去,前途茫茫未蔔,凱倫要自己大笑。這或許不單是嘲弄命運的意思,更多的,或者還有給自己打氣,不認輸,和某種殘酷的好奇:她觀看自己的生命,充滿興緻,好像在對上帝說:「已經到瞭這個地步,我看看你還能怎麼對付我!」
她的這種對生命的好奇,一切的生命,彆人的,自己的;是她所獨有的,一直延續到晚年。看她的老年照片,風華已逝,乾枯瘦弱,但是眼神慧黠靈動,甚至顯得淘氣。那個老人的身軀裏藏著個孩子。如果不是身體糟到極點,她想必還會「作」點什麼。
「作」這個字,是南方口語。有點「無事生非」,「故意」,「找麻煩」,甚至「損人不利己」的意味,類似目前常用語裏的「整」字。我母親是南方人,小時候挨罵,她總是說:你就是要「作」。凱倫這一生,至少前半生,她活生生就是個「作女」。
她齣生於一八八五年。傢中富裕。父親是「政治傢與作傢」,在她十歲的時候上吊自盡,之後她纔發現他患瞭梅毒。當年梅毒算是絕癥,無法可治,到末期病毒侵噬腦部,人會發瘋。凱倫的父親可能是懼怕這個結局,所以提前結束自己的生命。
她由母親撫養長大,環境優渥,所以小小年紀就周遊列國,在法國和瑞士念書,學的是藝術。在二十世紀初期,許多女性的婚姻還是由傢庭中的長輩決定的,中外皆然,而且成婚年齡極小,而凱倫二十八歲纔結婚。大概和她父親不在有關,這就缺乏一個有權勢的力量來主導她。凱倫一生,雖然一直被目為卓越的女性代錶,但是她沒有什麼叛逆性,很容易對權威臣服,甚至對於權威,某個強大的,完全掌控的力量,她不但仰慕,並且渴求。
她的婚姻可以說是建立在這種頭腦不清楚的渴求上。她愛上瞭她的遠房錶兄。這個感情的起點,據說跟他父親一段未完成的戀情有關。幾乎像少女漫畫。年輕的時候,她父親跟皇室的某位成員相戀,但是女方傢長不同意兩人結閤,之後各自婚嫁。這位錶兄就是那位公主的後代。凱倫跟父親命運一樣,但是這次拒絕她的不是對方傢長,而是錶兄本人。麵對拒絕,凱倫做瞭奇妙的選擇,她嫁給這位錶兄的雙胞胎兄弟--布魯.白列森。
沒有任何資料提到布魯跟他的雙胞胎兄弟是不是長相一模一樣,不過想必是肖似的。凱倫給自己找瞭個代替品。某方麵來說,甚至凱倫起初愛上的那位錶兄也是代替品,他是凱倫父親未完成戀情的象徵,而凱倫要承襲父親去「完成」它。
電影《遠離非洲》裏,梅莉史翠普飾演的凱倫對布魯說:「看在錢的份上,你可以娶我。」而布魯迴答:「你不過是想作男爵夫人。」我覺得他們的關係不會是電影裏演的那樣,那不是交換婚姻,交換太不浪漫瞭。除瞭奇妙的無限好奇心,凱倫另一個特點就是浪漫。
布魯.白列森其人,其實不像電影裏演的那樣無足輕重和無趣。他是瑞典籍,世襲男爵。為凱倫的作傳的多諾森說:「他人緣極佳,善良、風趣,精力充沛。」唯一的缺點大概就是多情。他沒法讓自己隻屬於一個女人。凱倫在寫給親友的信裏描述他,在自己生病或受傷的時候,他會照顧她,替她洗澡、按摩。而且在非洲,他是唯一帶著老婆去狩獵的獵人。他的帳棚裏有雙層床,總是和凱倫睡在一起。他和海明威也是朋友,據說海明威小說中某些人物的原型就是他。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攜帶大批精美瓷器與傢具的凱倫乘船從那不勒斯赴非洲的肯亞,她腦海中所編造的故事大概有點像中國曆史裏的「公主和蕃」;一個身份尊貴的女人(她事實上也是貴族)遠嫁到異鄉,之後改變瞭當地的風土和人民。
但是,事實和夢想,尤其是憑空編造的夢想,永遠是有距離的。
布魯.白列森要到非洲經營農場,凱倫於是跟著去瞭非洲,帶著娘傢支援的一大筆錢。但是抵達非洲後,發現布魯改變主意,決定種咖啡。這個不智的決定,導緻凱倫在十七年後破産。而這十七年中,咖啡園一直沒有收起來,像個無底坑一樣,不斷的吸取凱倫傢族的財富,直到把所有資源吃乾抹盡。
然而,上天對「財富」的定義和世間不一樣。凱倫散盡傢財之後,帶瞭另一筆更為豐厚的財富迴到丹麥,那就是她在非洲十七年的經曆。她的臣服,她的被傷害,她的榮耀,她的屈辱,她的病痛;以及她的擁有和她的失去。奇妙的是,當失去之後,她纔真正開始擁有。
漢娜.鄂蘭在《黑暗時代群像》一書中,有一章專談凱倫。依據鄂蘭的說法,凱倫原先並無意成為作傢。她二十齣頭發錶瞭處女作,「大傢鼓勵她繼續寫下去,但她立即決定不再寫瞭。」在二十世紀初,女性成為公眾人物並不適當,因為「公共領域的光綫過於刺眼」。但是迴到丹麥之後,這是她唯一的謀生技能,某種程度,凱倫沒有選擇。
她的《七個奇幻故事》後來在美國齣版,這是她使用伊薩剋.狄尼森這個筆名的第一本書。這時她已經快五十歲瞭。這本書廣受好評。之後她花三年時間完成《遠離非洲》,在五十二歲齣版。距她離開非洲已經六年。
狄尼森自述:「對於被固定在某個陷阱中有一種本能的恐懼。」稱之為陷阱,是因為「任何一種職業都會在生活中被指派為某個確定的角色,成為陷阱,遮蔽瞭生活本身的無限可能性。」雖然兩度得到諾貝爾奬提名,但是狄尼森顯然依舊不願意成為「確定的角色」,她總是稱自己為「說故事的人」,迴避作傢這個名銜。
她在《遠離非洲》書裏,也自比《一韆零一夜》裏的說故事的山魯佐德;那個聽故事的男人便是丹尼斯.芬奇—哈頓。這個人物,在影片中,由勞伯瑞福主演。
狄尼森自己在小說裏對芬奇—哈頓描寫的實在是太少太少,而且,實話說,不大看得齣兩人之間有親密關係。如果好萊塢沒拍成電影,至少我,可能會一直認為狄尼森對芬奇—哈頓隻是「非常欣賞」而已。書裏對他的描繪,或理解,甚至不如她寫她的非洲僕人法拉。
丹尼斯.芬奇—哈頓其人,白芮兒.瑪剋罕在《夜航西飛》裏寫過他,稱他為「非凡的驕傲的丹尼斯.芬奇—哈頓」。齣書的時候,芬奇—哈頓已經過世,她著墨不多,全是贊譽:
「丹尼斯是個從未有過豐功偉績的偉人。盡管他隻不過是斷續在非洲住瞭幾年,卻已贏得瞭最優秀白人獵手的盛名。他有一副為英國體育界稱羨的體格,也曾是名一流的闆球手。他是個學識淵博的學者,卻比沒受過教育的男孩更不懂賣弄。就像那些滿腦子想著人性弱點與韆帆過盡後産生厭世情緒的人,丹尼斯同樣會對人類深惡痛絕,卻在亂石間發現詩情畫意。丹尼斯是那道拱門上的拱心石,彆的石頭則隻是生命。」
感謝網路,什麼都找得到,所以也看到瞭芬奇—哈頓的照片。他人瘦長高大,有點禿頭。不過年輕時候是美男子。相貌很古典,容長臉,鼻梁細峭,薄嘴唇,典型撒剋遜種族的臉。他一手握拳頂住下巴,微微帶笑,在傾聽什麼。或許狄尼森講故事的時候,麵對的就是那樣的錶情。
迴到一九一四年。凱倫來到非洲,成為咖啡園的女主人。但是,立即,她發現自己從丈夫身上染到瞭梅毒。她迴丹麥治療。那年頭,青黴素還沒發明,治療梅毒主要靠水銀,不但外用而且內服。水銀就是汞。我們現在都知道汞是有毒性的。少量或許影響不大,不過凱倫晚年一直睏擾於汞中毒,看來她使用汞不但時間長,量大約也極大。
迴丹麥時,凱倫的病應當是治好瞭,但是猜想又染上瞭。因為她和丈夫並沒分開,如果依舊有床笫之事,被二度傳染是有可能的。六年後她纔與丈夫分居,又四年纔離婚。離婚主因可能是已經和芬奇—哈頓在一起,並且懷瞭他的孩子。
她為芬奇—哈頓兩度懷孕,孩子都沒留住。孕婦如果有梅毒,孩子很容易流産。事實上亦有捕風捉影的說法,認為丹尼森的奇幻想像力,多少跟後期梅毒有關。這個揣想至少錶明她為梅毒所苦的時間,延續瞭很久。
她與芬奇—哈頓的分手,或許也與無法生育有關。芬奇—哈頓是貴族,需要子嗣來繼承爵位。一般說法是芬奇—哈頓不要她生孩子。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之所以不要,或也是一種疼惜,總不能讓凱倫一直流産吧。總之,一九三一年,非洲的農場已經到瞭無可挽救的地步,必須變賣。凱倫要迴丹麥,而芬奇—哈頓不願意離開非洲。兩人協議分手。分手的過程非常平和,書裏寫得很清楚。並不像電影演的那樣「離情依依」,其實兩個人心裏大約都多少有數,日後可能也不大容易相見瞭。就在凱倫收好行囊準備離去之時,芬奇—哈頓墜機身亡。
這部分的描寫,如果完全屬實的話,給人感覺是芬奇—哈頓的選擇。不好說他是自殺,不過他知道這是適閤死亡的日子。他在一次大戰時就是飛行員,飛行技術高超。凱倫無數次坐他的飛機橫越非洲上空,而這次她要同行,芬奇—哈頓拒絕瞭,且也沒有理由。
他在草原上俯衝,之後墜毀。終年四十四歲。於死亡,這其實也是美好的年齡,衰敗尚未開始,而成熟已到瞭頂點。
凱倫把自己的情人葬在非洲。如果芬奇—哈頓不死,這個故事不可能完整。她帶著永遠不會再變化的記憶和情感寫下《遠離非洲》。
如果不是咖啡園破産,如果不是梅毒讓她流産,如果在非洲的生活無憂無慮,如果她和芬奇—哈頓生活美滿,白頭偕老,世界上可能不會有伊薩剋.狄尼森的存在。
一九五九年,凱倫七十三歲。她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來到美國。在全美藝術文學研究所年會上作瞭一次演講。她在演講上講瞭一個故事,關於一個中國皇帝。
這位皇帝年幼即位,但是一直由大臣攝政,當皇帝長大可以治理國事的時候,大臣把一個戒指交給他。大臣說:「我在這個戒指上刻瞭一句話,尊敬的陛下或許會覺得它有用。在勝利、凱鏇和獲得榮譽的時刻,您都應該讀一讀它。」
戒指上刻的話是:「此亦有盡頭。」
狄尼森說:「這句話不應該理解為:似乎淚水和歡笑、希望和失望,都消失在虛無的空間中。它告訴我們的是,一切在結束之時必然完整。」「即使我們說的是我們自己。我們中的每個人心中都一定能感覺到:我的生活,這獨特的東西,是多麼的豐富和奇妙。」
這是凱倫.白列森對世人最後的話語。兩年後她過世。從她的書籍,以及最後幾年的生活中,我們可以相信,她是笑到最後的人。
圖書試讀
縱使露露的行徑儼然就是個無理取鬧、放蕩不羈的女子,屋裏的人依然把她當寶一樣看待;隻是我們沒能使她快樂。有時她離開屋子好幾個鍾頭,甚至一整個下午都不見蹤影;有時她又像著瞭魔,對周遭的事物不滿到瞭極點,就在宅前草地上跳起一小段之字型的戰舞來,像是乞靈於撒旦似的,隻圖個心裏痛快。
「露露啊,」我心裏想,「我知道妳無比地強壯,妳能跳得比自己還要高。現在妳對大傢發怒,巴不得我們都死絕瞭,而說實在話,妳要是肯認真動武,我們死也甘願。但問題並不是像妳所以為的那樣。妳以為是大傢設瞭太高的障礙,妳纔跳不過去,可是妳想想,像妳這樣一個飛躍的能手,誰又礙得著妳呢?反之,大傢從來就沒有阻撓妳的意思啊。露露,偉大的力量在妳心中,障礙也在妳心中,問題的癥結,隻是時機尚未成熟罷瞭。」
露露有一晚沒有迴傢,我們四處尋找,之後整整一個禮拜都沒有消息。這對屋裏所有人都是沉重的打擊。清脆的鈴聲離開瞭這屋子,這屋子似乎也跟彆的屋子沒什麼兩樣。我想起瞭河邊的獵豹,有一晚就問卡曼提,露露要是遇到獵豹怎麼辦。
一如往常,他過瞭半晌纔答腔,好將我的無知咀嚼一番。過瞭幾天,他纔發錶看法。「嚜沙咘,您覺得露露已經死瞭。」他說。
我並不想把話說得那麼直截瞭當,隻說覺得納悶怎麼她沒迴傢。
「露露沒死。」卡曼提說,「她結婚瞭。」
這消息教人又驚又喜,我緊跟著問他怎麼知道的。
「真的,」他說,「她結婚瞭。跟她的『哇哪』住在森林裏。」哇哪是丈夫、主人的意思,「可是她沒把大傢忘瞭;大清早多半會迴來。我把碾碎的玉米放在廚房後方,快日齣的時候,她就從森林走來,把玉米吃瞭。她的『哇哪』也跟她在一塊兒,可是他怕生,總是站在草地另一頭那棵白色大樹下,不敢再往屋子靠近。」
我吩咐卡曼提,下次見到露露務必要叫我。幾天之後的一個早上,日齣前,他喚我到屋外去看。
那是個凈好的早晨。在等待露露齣現的時候,殘星隱沒瞭,天上一片清澈、安寜,而足下這塊土地仍然昏暗、靜止著,意味深長地沉默著。青草溼答答的,林中草坡泛著幽幽的螢光。清晨的空氣很冰涼,帶著一股紮人的寒意,這在北方的國度,就意味著再過不久,就是降霜的時節。晨間雖這麼寒冷、陰暗,可是不齣幾個鍾頭,太陽的酷熱與天空的光芒就會教人吃不消,無論在這裏住瞭多久,這落差總教人不可思議。灰濛濛的雲霧停在山上,山的輪廓變得模糊不清,給人一種異樣的感覺;像在雲端似的,如果在這時,水牛在山上吃草,那可是凍得刺骨呢。
用户评价
《遠離非洲》這個書名,在眾多書籍中,以一種沉靜卻不容忽視的姿態吸引瞭我。它不像某些書那樣直白地宣告內容,而是留下瞭大片的想象空間,像一幅未完成的畫,等待著讀者用自己的情感和理解去添上色彩。我常常會在書架前駐足,讓書名在腦海中迴蕩,試圖捕捉它傳遞的細微信息。《遠離非洲》,這兩個詞語組閤在一起,本身就帶著一種宿命感和故事性。它讓我想起那些宏大的敘事,那些關於探索、關於離散、關於情感糾葛的史詩。《遠離》二字,可能是一種主動的選擇,比如藝術傢為瞭尋找靈感而選擇的隱居,又或者是一種被動的遭遇,比如戰爭或變故迫使人們離開故土。《非洲》作為地點,更是充滿瞭無限的可能性,它既代錶著廣袤的土地和獨特的文化,也可能暗示著挑戰、艱辛,以及那些與現代文明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這本書的名字,在我心中已經形成瞭一個初步的印象:它可能講述的是一段關於放逐、關於尋找、關於在異域土地上發生的故事。
评分《遠離非洲》這個書名,如同一聲悠遠的號角,在我的腦海中激起瞭層層漣漪。它沒有直接點明故事的脈絡,而是提供瞭一個意象,一個充滿張力的場景。我第一反應是,這必定是一段關於告彆與追尋的故事。非洲,這個詞語本身就帶著一種原始的、充滿野性的力量,它召喚著冒險,也隱藏著未知。而“遠離”,則賦予瞭這個故事一種宿命感,一種不捨,或是一種主動的抽離。這“遠離”是地理上的距離,還是心靈的疏離?是被迫的離彆,還是主動的探索?我開始在腦海中勾勒齣一幅幅畫麵:或許是主人公身處廣袤的草原,告彆一段深刻的羈絆;又或者是在繁忙的都市中,對曾經在非洲度過的時光,生齣深深的眷戀與懷念。這本書的名字,像一個未解的謎,充滿瞭留白,激發著我的好奇心,讓我渴望去填補那些空白,去感受那段橫跨時空的,關於“遠離非洲”的獨特經曆。
评分當我第一眼看到《遠離非洲》這個書名的時候,我的腦海裏立即湧現齣一種淡淡的憂傷與無盡的遐想。它不像其他書那樣直接點明故事內容,而是像一幅寫意畫,留下瞭大片的留白,任由讀者去填補。非洲,這個名字本身就帶著一種神秘、廣袤、原始的色彩,它讓我聯想到壯麗的草原,奔騰的野性生命,以及那些古老而淳樸的文明。而“遠離”這兩個字,則像為這一切濛上瞭一層告彆的麵紗,讓故事瞬間充滿瞭情感的張力。是被迫的離開,還是主動的選擇?是充滿不捨的道彆,還是帶著某種釋懷的抽離?我開始在腦海中構思,或許是主人公在那裏度過瞭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時光,經曆瞭一段深刻的情感糾葛,最終卻不得不帶著這份復雜的情感,踏上遠離非洲的旅程。這本書的名字,本身就充滿瞭詩意和敘事感,它像一個未解之謎,激發瞭我強烈的好奇心,想要去探尋隱藏在“遠離”背後的,那段關於非洲的,獨一無二的故事。
评分在書店琳琅滿目的架子上,《遠離非洲》這個書名立刻勾起瞭我內心深處的某種共鳴。它似乎在訴說著一個關於告彆、關於追尋、關於一段不可復製的時光的故事。我並沒有立刻翻開書頁,而是讓它在手中沉甸甸地存在瞭幾秒,仿佛這樣就能抓住它所蘊含的重量和情感。我腦海中浮現齣各種關於“非洲”的想象:廣袤的草原,野性的生命,古老的文明,當然,也可能是人跡罕至的荒涼。而“遠離”則又給這一切增添瞭一層疏離感,一種不捨,或者是一種主動的抽離。我好奇,這“遠離”究竟是指空間的距離,還是心靈的隔閡?是主動的選擇,還是被動的命運?這本書的名字本身就像一首詩,充滿瞭留白,等待著我去填滿它的色彩和聲音。它激發瞭我對作者的創作意圖的猜想,也讓我開始思考,我自身生命中有哪些“遠離”的經曆,那些告彆是否也同樣充滿瞭復雜的情感。這本書,在還沒有讀過一字一句之前,已經在我心中種下瞭一顆期待的種子,我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它將如何在我腦海中綻放齣怎樣的畫麵與感受。
评分當我第一次在書店看到《遠離非洲》這個書名時,一種難以言喻的畫麵感便在我的腦海中油然而生。它沒有直接告訴我故事的內容,而是像一位藝術傢,用最簡潔的筆觸,勾勒齣瞭一個充滿想象空間的意境。非洲,這個詞匯本身就帶著一種原始、神秘、廣袤的色彩,它讓人聯想到無垠的草原、奔騰的野獸、古老的部落,以及那些與現代文明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遠離”這兩個字,則為這個意境增添瞭一種告彆的、略帶傷感的色彩。我開始在心中猜測,這“遠離”究竟是指什麼?是被迫離開,還是主動選擇?是告彆一段深刻的感情,一段難忘的經曆,還是僅僅是對一個地方的抽離?它可能是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一段艱難的探索,抑或是對人生某種答案的追尋。這本書的名字,就像一個精心設計的謎題,它沒有給齣答案,卻激發瞭我最強烈的好奇心,讓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翻開書頁,去探尋那個隱藏在“遠離非洲”背後的,屬於作者獨有的故事。
评分當我第一次看到《遠離非洲》這個書名時,我的腦海中瞬間閃過一幕幕畫麵,仿佛一部無聲的電影在眼前展開。它不像許多書名那樣直白地告訴你故事內容,而是提供瞭一個充滿詩意的意象,一個能夠引發無數聯想的起點。非洲,這個充滿神秘與原始魅力的大陸,本身就代錶著一種宏大的敘事,一種與我們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存在。而“遠離”二字,更是為這個故事增添瞭一層厚重的感情色彩。它可能意味著告彆,可能是對一段過往的釋懷,也可能是對某個地方、某個人、某種狀態的抽離。我開始思考,這“遠離”究竟是地理上的距離,還是心靈的疏隔?是充滿不捨的離開,還是帶著某種目的的主動選擇?這名字本身就像一個精心設計的懸念,讓我忍不住想要去探究,在那片土地上究竟發生瞭怎樣的事情,又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主人公不得不“遠離非洲”。
评分當我捧著《遠離非洲》這本書,指尖拂過封麵粗糲的質感,一種久違的、被故事召喚的感覺油然而生。這個書名,簡潔卻極具畫麵感,仿佛能瞬間將讀者帶入一個充滿神秘與未知的天地。我猜想,這本書所描繪的“非洲”絕非旅遊雜誌上那些經過濾鏡美化的風景,而是一種更為真實、更為深入的體驗。或許是熱帶雨林的濕熱,或許是沙漠的乾燥與寂寥,又或許是那片土地上人民淳樸卻又飽經滄桑的笑容。“遠離”這兩個字,更是讓人遐想聯翩。是遠離瞭文明的喧囂,去尋覓內心的寜靜?還是遠離瞭熟悉的環境,去探索人生的更多可能?或者,是一種告彆,告彆一段刻骨銘心的經曆,一段與非洲土地緊密相連的過往。我開始在腦海中勾勒齣故事的輪廓,是風沙吹拂下的孤寂旅程,還是熱情洋溢的異域風情?是關於成長,關於愛恨,還是關於那些難以言說的鄉愁?這本書就像一個未解之謎,它的名字本身就充滿瞭引力,讓我渴望去揭開它神秘的麵紗,去體驗那段“遠離非洲”的旅程。
评分《遠離非洲》——這個書名,像一首古老的歌謠,在我的心頭低語,喚醒瞭我對遠方和迴憶的渴望。它並沒有直接描述故事情節,而是用一種含蓄而充滿力量的方式,在我的腦海中勾勒齣一個個模糊卻引人入勝的畫麵。非洲,這片廣袤而神秘的土地,總是帶著一種原始的野性與深沉的魅力,而“遠離”二字,則在這片土地之上,增添瞭一層告彆、追尋,抑或是釋然的情感基調。我開始在心中猜測,這“遠離”究竟是身體上的漂泊,還是心靈上的覺醒?是與過往的決裂,還是對某種情感的放逐?它可能是一段在非洲經曆的風雨,一段刻骨銘心的遇見,然後,不得不帶著復雜的心情,踏上歸途,將那片土地,化作心中一份珍藏的記憶。這本書的名字,本身就充滿瞭故事的張力,讓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深入其中,去感受那份“遠離”背後,所蘊含的深邃情感與獨特經曆。
评分《遠離非洲》——這個書名,在眾多書名中,猶如一股清風拂過,帶著一種彆樣的意境。它沒有直接劇透,而是像拋齣瞭一顆石子,在我的思緒中激起層層漣漪。我開始在腦海中勾勒齣可能的場景:非洲,那片充滿野性與生命力的大陸,它的名字本身就帶著一種神秘的吸引力。而“遠離”二字,則在這片土地上,增添瞭一種告彆的意味,一種不捨,或者是一種主動的抽離。我猜想,這本書或許講述的是一段關於一段深刻經曆的告彆,關於在非洲那片土地上,所發生的一段刻骨銘心的故事。這“遠離”,究竟是地理上的距離,還是心靈上的距離?是無法忘懷的記憶,還是刻意淡忘的過往?它可能是一個人,一段情感,或者是一種生活方式,被留在瞭那片遙遠的土地上。這本書的名字,就像一個精心設計的引子,讓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翻開書頁,去探尋那份“遠離”背後,所隱藏的,關於非洲的,獨特而動人的故事。
评分當我的目光落在《遠離非洲》這個書名上時,一種莫名的畫麵感便在腦海中湧現。它不像許多書名那樣直接點明內容,而是提供瞭一個引子,一種意境,讓人忍不住想要深入探究。我試著去想象,這個“非洲”究竟是什麼樣的?是廣袤無垠的撒哈拉沙漠,還是生機勃勃的熱帶雨林?是古老神秘的金字塔,還是色彩斑斕的部落文化?而“遠離”這兩個字,則又增添瞭一層復雜的意味。它可能暗示著一種告彆,一段旅程的終點,或者是一種心靈上的隔閡。是被迫離開,還是主動選擇?是懷揣著不捨,還是帶著新的希望?我開始在腦海中構建故事的雛形,或許是主人公在非洲經曆瞭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卻不得不麵對分離;又或許是他在那裏找到瞭人生的真諦,卻最終選擇迴到熟悉的生活。這本書的名字,就像一個精心設計的謎語,它沒有直接給齣答案,卻能激發人無限的聯想,讓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翻開扉頁,去尋找那個隱藏在字裏行間的答案。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內容均為互聯網搜尋引擎提供的公開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儲任何數據與內容,任何內容與數據均與本站無關,如有需要請聯繫相關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於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tw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灣灣書站 版權所有